敘畫美學思想及藝術觀點研究
時間:2022-05-13 15:27:13
導語:敘畫美學思想及藝術觀點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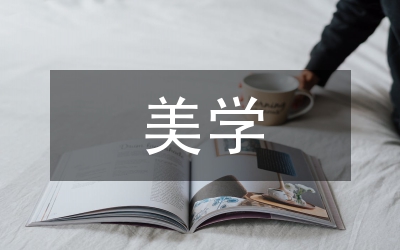
摘要:王微的繪畫思想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他在《敘畫》中提出了繪畫藝術的價值和地位,提出“明神降之”的創作方法,強調藝術創作過程中構思活動以及精神思考的重要性。王薇把繪畫與圣人經典放在同樣的位置,使山水畫擺脫了一直以來的人物畫角色附庸,強調了形神合一、身心結合,讓山水畫成為一門單獨的藝術畫科。
關鍵詞:敘畫;王微;山水畫;意義;思想
一個人的思想見地和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王微所處的時代,社會動蕩不安,獨尊儒術的局面被打破,各家思想蓬勃發展,使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影響。其突出表現則是玄學的興起、道教的勃興,思想界異常活躍,道教系統化,佛教和反佛斗爭激烈,佛儒道三教開始出現合流的跡象。這一時期還沒有系統的關于山水畫的論述,王微在繼宗炳之后,進一步發展了關于山水畫的美學理論,在宗炳山水畫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見解。王微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積極入世,積極進取的,但他又對做官沒有什么興趣,并長期獨處,不問世事,這又和道家出世的方面不謀而合,于是可以判定王微提出的繪畫功能實際上是儒道結合的思想,也從側面反映了晉時人們普遍的價值取向和精神狀態。在《敘畫》中王微提出“明神降之”的創作方法,強調藝術創作過程中構思活動以及精神思考的重要性。游歷山的“神飛揚,思浩蕩”的狀態,讓繪畫山水與用作實用功能的地圖在本質上劃清了界限。山水畫的創作方法,提出了筆勢筆法的變化和畫家的主觀構思,也體現了山水畫創作前與藝術鑒賞中的審美心理特征和由此帶來的審美效果,給創造繪畫的畫家們提出了精神上的要求。
一、主張“以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
文章一開始把繪畫的地位與圣賢的經典著作《易》做比較,認為繪畫可以和圣人的經典《周易》相媲美。這里的“藝”指一門技藝,屬于技術之列,不是我們現在所講的藝術。在當時技術并不被人們認可,并將技術看作低級的行業,難登大雅之堂;而很多人都會誤認為藝術就是技術,將畫畫之人稱為匠人,自然就將圖畫與技術劃為一類了,這在根本上是錯誤的。王微意識到這一問題,索性發出時代最強音,意圖糾正這個誤解,所以他明確提出繪畫不屬于技術的行列,而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通過繪畫完成的作品應該和《周易》是同等重要的地位。《周易》是儒家的經典著作,也是儒家思想本源的出處,《易》象就是指八卦,我們知道傳統八卦就是以圖形的變化來和天地陰陽相連,通過圖形本身的客觀存在和人的主觀理解,將圖形與天地萬物結合起來,做出合理想象,辨別事物兇吉,推測自然變化。《易經》中所提倡的是天道和人道,天地人本是一體,以模仿天地自然現象為主,主觀大于客觀。《易》象中的天地人的聯系,和圖畫的本源相契合,都是通過對主觀的創造,建立起人與自然天地的聯系。圖畫追求的不只是外在的形,還有內在的神。原文中“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者變心”,王微認為神形本就是一體,作畫中自然景色沒有變,變化的無非是人的心罷了。從這一點上也和《易》象有相似之處,所以可以看出作者對《易》推崇備至,而能夠將繪畫與它放在同一位置,也足見作者對繪畫的重視[1]。
二、明確區分繪畫山水景象與實用功能地圖的不同
對繪畫了解不多的人,只是一味追求客觀世界的外部印象,而且以為“案城域,辯方州,標鎮阜,劃浸流”,不按照藝術規律去創造,而是以實用為目的來編排,是繪制地圖的要領方法。[2]我們知道,地圖最主要的功能是實用,一張地圖若是能夠做到簡潔明晰,并且高度還原真實景物,要不得一點想象和猜測,給觀者一目了然之感,那肯定是一張實用性很強的地圖,而把這些標準用在圖畫上面的話,那就有一些格格不入了,這幅圖畫肯定是僵硬死板,毫無生氣而言,無法居于藝術行列,必定成為不了能讓人引起感官共鳴的藝術作品。畫家作畫并不是這樣機械地對現實景物照搬照抄,他們有自己的想法并加入主觀感受,讓畫面表達更多情緒。加入情感的繪畫作品與用作工具的地圖不同,因此才會說“效異《山海》”。繪畫是一門獨立的藝術畫科,它有自己的特點,不依賴模仿,與地圖的效果也是大相徑庭。《山海經》是一部古代式的百科全書,記載了方方面面的內容。其中一部分涉及地理,它不僅是繪制的地圖,而且詳盡標注著一些地理外貌和特點。而圖畫表現出來的雖和地圖類似,但它們本質上是不同的,帶給人的感受自然也不同。地圖是根據自然描繪自然,使其更接近自然,而山水畫則是以自然為參照,加入創作者的主觀構思,生活經驗等,避免太過自然。這就將圖畫和地圖明確分開,二者分屬不同領域,功能不同,切不可混淆聯系。
三、論述山水畫的創作方法
1.畫家創作中的主觀構思和審美特征作者指出,因“目有所及”“故所見不周”,眼睛能夠看到的景物畢竟是有限的,看不到的東西,眼光就被限制住了,但繪畫不會因為你目光的限制就使畫面內容匱乏,畫面題材也不會變得單調。一幅優秀的繪畫作品并不是對現實景物的照搬照抄,其中必定包含著畫家豐富的想象和精神聯想。繪畫作品是一種傳遞畫家情感,引起觀者和畫家強烈共鳴最有效的方式。[3]如果懂得欣賞,可以透過畫面內容把握到作者在畫面里要表達的深刻內涵和思想感情。我們知道很多文人寫詩都是信筆拈來,但實際上他們都是已經在腦海中或心里有了一個明確的構思,才能夠做到瀟灑自如,一氣呵成。畫家們并沒有因為目之所不及而安于現狀,而是“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發揮豐富的想象力,將理想中的景物以繪畫的形式表現出來,結合客觀存在,方能組成一幅生動自然的畫面。繪畫中的主觀聯想很重要,會給觀者帶來充分的空間想象,但畫家也需遵守原則,那就是不可隨意想象,在主觀繪畫的基礎上也要符合客觀實際,想象目之所不及,客觀描繪目之所及。要創作出好的山水畫,就不能局限于一人一陋室,眼睛能看到的已經很少了,而如果待在原地苦思冥想,便成為井底之蛙了。山水畫家的創作,必須積累素材,擴大眼界,應該去游歷山水,用眼睛看到更多更好地山川河景,看得越多,想象的元素也會更豐富,這樣可以有效地彌補目有所及的遺憾,變成眼見之明。通過畫家的全面構思,整幅畫就可大概確定,而山水之間并不全是山水和想象,還有和現實相聯系的人物車馬,畫面有了這些也就有了趣味性。王微提出“器以類聚”“物以狀分”,切不可隨意改變位置。因為這些東西是實際存在的,所以要將其安放在合理的地方。2.繪畫實踐中技法的運用,以書入畫素材的積累是準備的重要一步,在繪畫過程中畫家的技法和表現力也是畫面成功的關鍵。墨色、筆法的變化可以成就不同的畫面效果,要根據繪畫對象的特點施以不同的筆法。景物狀貌變化多姿,王微《敘畫》中提出:“曲以為嵩高,趣以為方丈”“以叐之畫,齊乎太華”,自然景物沒有完全相同的,繪畫技法也沒有固定程式,每個畫家也都有自己的風格,表現方法也有不同。歷朝歷代有不同畫家、畫派,這就是他們繪畫風格和表現方法的差異,如展子虔的《游春圖》,就想到以他為代表的青綠山水的自然風貌;談起王蒙就聯想到他濃密厚重的山水景色,畫家的風格差異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繪畫方法也會隨時代而變化,古人作畫以皴、擦、點、染為主,而現代畫家多形成個人風格,對古人雖有借鑒,但也有脫離趨勢。外出寫生,坐于山腳下,面對著同一景物,因個人理解不同,畫面效果也就不同了。用筆急促飛快,可表現高峻的山峰;用筆舒緩平和,可表現平靜自然的湖面;“枉之點,表夫隆準”,要表現山形的千變萬化就必須用不同的筆法。書畫本就是一家,《敘畫》中將書法用筆引入繪畫,根據書法的筆畫不同,勾提點筆勢就不同,運筆的速度和力度也隨之變化,寫出來的字的骨力也會各顯千秋。對山的刻畫亦是如此,是太行山那樣陡峭的石頭山,還是黃土高原的小土坯;是壺口那樣噴瀉而下的壯麗瀑布,還是江南烏鎮靜默流淌過的小橋人家,在山水畫面里,都是要依靠筆法的變化來表達的。書是將靈動之氣灌進筆尖,體現在字的筋骨氣里,畫也是將筆勢的靈動婉轉,變化多端來表現不同的山石狀貌。王微將山的態勢比作顧盼生姿的少女,將自然山水擬人化了,容顏姣好的少女本就很吸引人,山也是以這樣生動活潑的魅力吸引著畫家去表現[4]。王微所處的時代重書法而輕繪畫,甚至貶低繪畫的地位。王微主張將書法入畫,借鑒書法的長處提高繪畫技術。可見王微對事物的認識是很寬廣的,也具備精謹的學術眼光,他沒有局限于一個科目,而是懂得集眾家之長,思考如何吸收別家之長讓繪畫這一科有更長足的發展。3.山水畫家的精神追求繪畫本就是怡悅性情的東西,王微開始就提出繪畫不拘于技術行列,因為技術屬于謀生計的范疇,他是帶著目的去從事的,并且和社會人群緊密聯系,追求的是物質的滿足,這在繪畫者看來是不齒的,繪畫者更多追求的是精神的富足,對財富金錢視作糞土,“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仿佛之哉”,并且有遠離世俗的傾向,更多喜歡的是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從他們的繪畫作品中不難看出,以畫寄情,將所有的情緒都表現在繪畫作品中[5]。“望秋云,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這才是畫家們所追求的境界啊!繪畫得到的必須是精神上的滿足,能夠表達畫家的情感,使畫家的精神得到釋放,給觀者帶來精神上的滿足。
四、王微與宗炳思想之比較
宗炳與王微屬同一時代,因為宗炳的《畫山水序》寫于王微《敘畫》之前,人們更多的將注意力放在研究宗炳上而忽略王微。事實上,二人的觀點各有千秋,也有相似之處。王微的觀點是入世的,形神一體,沒有神必定沒有形,二者息息相關;宗炳的思想是儒道佛三家結合,但更多強調精神對人的作用。宗炳王微同屬魏晉,前面提到魏晉時期玄學思想興盛,老莊道家思想廣泛影響著當時的文人,玄學推動了文學藝術的發展,文藝思想的自覺自發性,使文人的思想更加活躍。宗炳和王微在山水畫方面提出的“傳神論”,是對山水畫的新發展,也是對美麗山水,自然之景新的認識[6]。宗炳和王微對于形與神的認識有所不同,宗炳是虔誠的佛教徒,認為形神可以分離,形神異體,他提出“精神不滅,諸法皆空”。他對佛的見解偏向于因果輪回,精神不滅方面,即便肉身離去,精神也是永存的。在他的《畫山水序》中提到山水畫創作的基本原則之一是“以形寫形,以色貌色”,講究真實再現自然山水的狀貌,看到什么就畫出什么,無須添加個人的感情,表現繪畫客體的真實性,強調繪畫的存在性,這是一種樸素唯物的繪畫方式,接近于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王微認為形若是不在了那神勢必也不存在,形神是一致的。在他的繪畫理論中強調抒發作者的感覺,表達內心的想法,把情緒帶入繪畫中,賦予繪畫作品以山水實感和作者強烈的感情色彩,以便觀者不只是欣賞山水之樂,更多是要體悟作者寄予山水畫的人文情懷。以“寫心論”為理論基礎,提出“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在欣賞山水時的方法二人也有所不同,宗炳晚年由于身體原因,沒有精力親身處于山水之中去體悟自然勝景,于是提出欣賞山水可以“澄懷觀道,臥以游之”,他認為真實存在的山水可以給人美的享受,依樣摹寫的山水畫同樣可以使人心馳神往,只不過是形式不同罷了。而王微指出,“望秋云,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加入了審美主體的情感,成為一種更積極主動的審美方式。他不僅提出創作要加入主觀情感,欣賞時同樣需要將審美主體的情感放在審美對象上,使審美過程更加豐富生動。宗、王二人都提出涉及“玄學”的思想,二人的思想不同,但都對山水畫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雖都有時代局限性,但對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具有不可忽略的積極意義。
五、《敘畫》對中國山水畫的影響
1.怡悅性情強調山水畫就是用來抒發感情的,如果沒有感情的投入,那與地圖無異。音樂令人心曠神怡,心馳神往,寶玉也是世上稀有之物,已經有這么珍貴難得的東西了,可還是覺得比不上圖畫帶來的精神享受。為了精神的怡悅,被世人奉為神圣的寶玉也就成了身外之物了,圖畫所抒發的性情更加重要。八大山人國破家亡,心中的憤憤不平郁結在心,只能通過繪畫來抒發心情,繪畫成了他宣泄情緒的出口,我們也能夠從他的畫中感受到作者的情緒變化。陶淵明與王微是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不問世事,淡泊名利,過著“悠然見南山”的舒適生活,寫詩作賦也是隨性而來,應是覺得怡悅性情更為重要[7]。2.擬人化的表現在文中作者將山水畫擬人化了,將自然山水比作是顧盼生姿的少女,“眉額頰輔,若晏兮”,將山水畫的景致和山勢的變化看作如同人的眉眼笑容。這一點王微是具有首創性的。將怡悅性情真正引入山水畫中,給繪畫的創作賦予了更多的含義。[8]啟發了更多的畫家在作品創作中增加了象征意義,將繪畫物象看作人的象征也好,還是將自己的感情抒發到畫里也罷,都是在王微引導的這條擬人化的道路上開始的。四王的畫作一味追求摹古,擬古不化,這也和他們所處的環境有關。3.“明神降之”觀點的提出在王微之前,眾人將山水畫看作是對自然景物的描繪,畫面感的好壞皆是取決于畫家技術的高低和手掌的功夫,然而“豈獨運諸指掌”?答案是否定的,應該是“亦以明神降之”。顧愷之在他的畫論中提出人物畫的“傳神論”,將傳神引入人物畫中,王微則提出山水畫也應該講究傳神,注重神韻的傳遞。[9]在以表現為主的中國畫上又有了全新的突破,讓我們認識到任何繪畫都不是呆板僵硬的,意在筆先。一幅作品的構成不單是表現技法,也凝聚著畫家的智慧和豐富的想象力,以及在作畫之前的構思。鄭板橋從“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創作過程,即是“明神降之”的體現。這一觀念的提出為中國古代畫家的成長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結語
仔細研讀《敘畫》一文,可隨王微先生進入他的世界。像是置身于高山云海之中,面對自然景色,高山仰止,“綠林揚風,白水激澗”,王微描繪的山水畫是一個神思飛揚,神形合一的理想境界,是他思想見解的直接再現。繪畫中若只是注重技巧,那繪畫也只是空有其外殼,稱不上是真正的繪畫,形與神應是內在的統一。繪畫也應講究藝術性,對圖畫懷崇高敬畏之心,充分構思后再下筆,也是對藝術的尊重。不管是作畫還是欣賞,都應該用心去感受和領悟。《敘畫》從人的審美角度出發,論述山水畫的最終意義,在山水畫中體現和傳達融于心的精神追求,將人文情懷納入繪畫創作中,為山水畫賦予了更廣闊的意義,體現了王微對于山水的理解和認識,身心結合才是山水畫傳遞出來的最高境界。
參考文獻:
[1]李修建.論六朝時期的繪畫觀[J].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2014年3期,第61頁.
[2]朱平.王微《敘畫》對中國山水畫創作的啟示[J].船山學刊,2009年1期,第186頁.
[3]秦菁怡.論王微《敘畫》中的美學思想及作用[J].南風,2014年24期,第14頁.
[4]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5]陳傳席.六朝畫論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第246頁.
[6]謝赫.古畫品錄[M].中華書局,1985年.
[7]田力.重讀王維敘畫的美學價值[J].廣西藝術學院校報,2004年12期.
[8]潘運告.漢魏六朝書畫論[M].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1997年.
[9]邵宏.衍義的“氣韻”——中國畫論的觀念史研究[M].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作者:馬曉芬 單位:西安思源學院
- 上一篇:大學英語翻譯教學模式構建路徑
- 下一篇:領導者提升領導效能轉型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