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農民解決三農問題
時間:2022-07-17 04:38:00
導語:如何讓農民解決三農問題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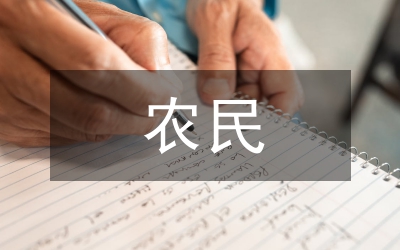
一、角色替代下的績效不足
在長達三十年的解決三農問題艱難歷程中,一直存在著一個角色錯位的奇怪現象:既然解決三農問題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農民,那么農民這一群體就應該最具有解決三農問題的積極意愿,并且,也會在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中發揮出主體作用,做出積極的有利于解決三農問題的行為選擇。然而,從歷年的中央支農一號文件,到免除涉農稅收,再到建設新農村,及號召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解決三農問題的舉措更多成了至上而下運作,農民反而成了配角,解決三農問題更多地成為了社會的,或者說是政府的事業。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一種市場經濟。在有市場的經濟中,農民,政府抑或其它群體,都是獨立的利益集團。各利益集團皆因自身利益訴求進行著利益博弈。因此,至上而下的,著重于從社會范圍來解決三農問題,或者由其它利益集團來替代解決,本身就有違于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因為,一個群體的利益訴求,是不可能由另外的對其有利益訴求的利益集團來代為實現的。
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具有著社會主義的性質,從而一個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就可以由社會或其它群體通過幫扶、反哺等行為來替代實現是極具理想色彩的。只要各群體有其自身的獨立利益,各群體之間的最基本的關系就是利益博弈。同樣,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具有社會資源的配置職能,但它仍然有其自身的利益,也是一個力圖實現自身收益最大化的集團,所以,由政府來替代農民解決三農問題,其行為也很難節制,它既可以采取一些扶農惠農措施,也可以為財政收入最大化圈占農地。因此,即使一個經濟具有著社會主義的性質,政府也具有社會資源配置的職能,但農民群體的利益訴求,或者說三農問題的解決,最終也只能通過農民主體作用的發揮來得到實現。
所謂農民的主體作用,其具體落實為農民為自身利益而與其它社會集團進行利益博弈的行為。各集團之間的利益博弈可以以各種方式進行,但只有交易這一種方式具有合作性,也即只有交易才能夠實現參與博弈各方的成本分擔和利益共贏,并同時實現資源的最有效配置。所以,所謂發揮農民在解決三農問題的主體作用,其準確含義就是農民這一群體能夠在市場上與其它利益集團進行機會均等的交易,并通過交易去解決三農問題。
如果農民的主體作用被抑制得不到實現,而由其它社會利益集團來替代農民去解決三農問題,預期目標就很難得到實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由于農民不能夠針對其它利益集團所采取的行動做出自己的對策選擇,所以,當這些措施即使具有扶農惠農愿望時,也可能并不符合農民的意愿,因此難以有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而當這些措施只是符合其它利益集團的利益而無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時,農民也只能消極接受,并不能對其進行矯正,反而可能加劇三農問題。總之,只要農民的主體作用得不到發揮,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不是經由農民和其它利益集團的市場交易,其結果都會是導致解決三農問題所做的努力歸于低效率或無效率。正由于此,三農問題迄今仍是中國社會發展難解的課題。
二、條件約束下的農民能力缺乏
但是,從中國三十年的實踐看,在現行條件約束下,農民又的確缺乏解決三農問題的能力。正如開啟農村改革,率先實行農地包干的安徽小崗村人所說,我們是“一步跨過貧困線,三十年沒進富裕門”。維護農民既得利益,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和減少農民,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三個關鍵環節,但現實表明,在這三個環節上,農民都難以勝任利益主體的角色,通過交易有所作為。
第一,失地直接導致農民既得利益受損,但農民卻不能通過交易方式或其它有效舉措抵制其它群體的掠地行為。農地實行家庭承包制后,農地不僅成為農民經營收入的基本可配置資源,也是農民生存的基本保障。但三十年來,社會其它群體以城市化,工業化等各種名目對農地進行著圈占。在圈占中,也會有對失地農民有所補償,但由于圈占農地不是農民與圈占方平等交易的結果,因此,補償既不是農民因舍棄農地而做出的選擇,經過層層拔毛也很難足額地讓農民獲得。農民失地導致了大量農民的返貧,形成數千萬三無流民。失地加劇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但在現有社會制度框架內,農民并無抵制其它社會利益集團圈征土地的合法措施,因此,農民群體就難以維護自身最基本的利益。
第二,農地的規模經營是實現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業經營效率,實現農民增收的基本途徑,但現存條件下的農民卻無法以交易實現農地經營的規模化。農業經營效率的提高是農民增收的基本途徑,但自家庭承包制實行后所造成的農地小規模的極度分散的農地經營卻從根本上制約了農業經營效率的提高。由于農地分散經營的無效率,在廣大地區可以看到的普遍現象是,即使中國的農地資源非常稀缺,但農民卻視土地如雞肋,不僅不愿意在土地上多做投入,且寧愿放棄經營,甚而拋荒,這就不僅使農地經營無助于農民增收,還使中國的農地總體利用效率低下,且直接誘發所謂糧食安全問題。在有市場交易的條件下,農民可以通過交易實現土地的集中并實現規模經營,但在現行農地制度下,農民并無農地交易權,因此,農民就失去了自主實現農地集中的途徑。
第三,減少農民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但農村居民卻無力通過交易行為遷居至城鎮。農村人口的數量偏大,是直接制約農村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農村居民世代以來也都向往著能到城鎮定居,以享受現代文明所帶來的更高質量的生活。但是,在長期的城鄉有差異發展之后,農村居民要遷居到城鎮就必須解決巨額的遷居費用問題。在現行狀態下,多數農民僅僅憑農地和進城打工收入,幾無能力支付遷居費用。因此,即使農民懷有遷居愿望,城鎮也存在就業機會,廣大農民也只能選擇在城鎮流動就業,而無力選擇遷居城鎮。這也是中國城市化進步始終落后于工業化進度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也正是因農民群體在解決三農問題上所表現出的無能為力,更強化了只有社會幫扶才能解決三農問題的意識。
三、讓農民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
農民的主體作用在解決三農問題中無力發揮,而其它社會群體替代農民解決三農問題又是低效率甚至是負效率的,這便是歷三十年而三農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的死結。不論是如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則所示,還是從三十年實踐經驗教訓來看,要破解三農問題所面臨的困境,出路并不是在于繼續強化社會資源以各種方式對三農的注入,而是在于讓農民的主體作用得到發揮。要讓農民發揮在解決三農問題中的主體作用,關鍵之舉是對現有農地產權安排進行重新界定。溯根求源,正是現有的農地產權制度安排,既造成了三農問題的積重難返,也導致了農民的作用無力發揮。
自上世紀70年代末至今,中國農村一直實行著家庭土地承包制。在家庭承包制這樣一種農地產權制度安排下,農民所擁有的只是農地的經營使用權和部份收益權,卻不擁有農地的所有權和處置權,農地的所有權及處置權歸于主體界定含混不清的集體。在現行的農地產權安排下,由于農民沒有得到農地的處置權,一方面,農地由農民經市場交易而可能形成的集中經營的過程被阻斷。即使小規模農地經營不經濟,農民也不能選擇轉讓土地,而且,由于農民不能夠選擇用農地這一稀缺度較高的資源來與社會其它群體進行交易,就只能以相對稀缺度較低的勞動力進行社會交易,因此也限制了向城鎮遷移費用的支付能力的提高,從而難以實現向城鎮的遷居;另一方面,農地所有權和處置權的集體所有,在現實中往往演變成少數人或地方政府所有,這就使得政府和其它利益集團可以堂而皇之地通過各種非交易手段得到農地,從中獲取利益,并危及農民的利益。所以,從深層次上說,中國的三農問題,其實就是現行農地制度運行的均衡實現方式,其社會收益表現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其它社會集團的收益,如開發商的利潤和地方政府的政績和財政收入的提高,其社會成本則是三農問題。
既然三農問題只是現有農地產權制度的社會成本,因此,根本解決三農問題的唯一途徑就只能是對現有農地制度進行重新界定,把農地處置權安排給已經擁有農地使用權的農民。
把農地處置權安排給農民,在中國一直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疑慮,其中,較為典型的兩種反對意見一是對糧食安全的擔憂,二是對產生城鎮貧民窟的恐懼。其實,就糧食安全問題而言,正是在農地集體所有的產權安排下,滋生了其它利益集團對農地的無節制圈占,導致農地規模的急劇下降,同樣,也正是由于農民沒有農地處置權,導致了農地經營的規模不經濟,效率低下,農業產業化無法進行,更有甚者,是出現了農民的對農地經營的輕視,直至大面積拋荒。所以,對中國的糧食安全的威脅,并不來自于農地處置權安排給農民,而恰恰來自于維持現有的農地產權制度。
認為讓農民擁有農地處置權即可能發生農民大規模向城鎮遷居,并因此而形成城鎮的貧民窟,加劇城市病,更是不切實際的危言聳聽。其一,農民群體的行為自有其利益選擇,如果遷居城鎮的機會成本偏大,農民就會合理地選擇留居在農村,而不會是盲目進入城鎮;其二,與巴西或印度貧民窟生成時的國情截然不同,由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提供了不斷增加的城鎮就業機會,這已由多年來農民大規模進城流動就業的實踐所證明。只要城鎮能夠提供就業機會,就可以避免因失業而造成的貧民窟現象;其三,反而正是由于農民不能通過交易農地獲得遷居費用的支付能力,導致了中國農民只能進城就業卻無能力定居,造成一些城鎮的流動人口規模急劇增加,并誘發城市病。因此,讓農民擁有農地處置權,并允許農民的農地交易,恰是中國治理城市病,推進城市化和城鎮化的重要環節。
一項制度安排有其歷史性,有其內在的生存規則。當一項制度社會成本大于其社會收益時,該項制度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變遷。家庭承包制這樣一項農地產權安排的制度,曾經為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帶來一片新氣象,但當三農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問題中的重中之重時,說明它已經到了與時俱進,必須變遷的關頭。讓農民擁有農地處置權,讓農民去選擇,這才是根治三農問題的唯一可行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