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利益統一才有國家競爭力最大發揮
時間:2022-03-17 02:03:00
導語:政企利益統一才有國家競爭力最大發揮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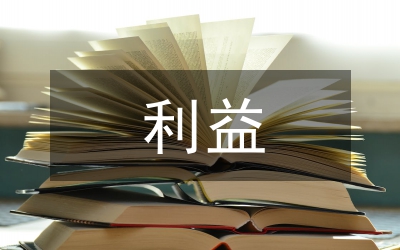
面對“后危機時代”美國拿出的“發展戰略”和“中美合作戰略”,中國該如何主動應對?筆者以為最核心的一條,盡快破解政企“利益沖突”的格局,扭轉產業結構調整和新的增長點探索行為上“主體缺失”的尷尬局面。中國政府多學點企業和市場相關的創造利潤的“戰術”,企業和機構則更要多學點宏觀和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對中國經濟生存環境產生影響的“戰略”知識
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和能源部長朱棣文這些天正在展開他們的訪華之旅。利用兩位華裔在中國會得到的天然“好感”,奧巴馬政府在謀求中國對美國未來新增長點的計劃和行動給予最大幫助。這是美國政府在“后危機時代”尋求政府和企業雙重利益的統一和利益最大化的戰略表現。
考察美國的金融危機歷史可知,他們解決危機的辦法不是在哪里跌倒從哪里爬起,而是摒棄在市場中已證明站不住腳的東西,并用最多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去探索和發現人類未來可以再次依托的嶄新的財富創造方式。所以,當IT泡沫破滅后,美國政府通過降息、廢除對金融活動的一些管制,住房政策的改革等措施,大膽扶持了本土金融體系的創新能力,以此來緩解IT泡沫破滅對美國所產生的巨大負面影響。事實上,在前幾年經濟繁榮時代最大的得益者還是美國的機構、企業和政府。而今天危機讓美國企業和美國政府付出的代價,就和以前歷次泡沫破滅一樣,是一次“正常”而又必不可少的“調整”,只不過如何將調整的成本和時間的代價控制在最小程度,確實需要美國市場和政府攜手的努力。
為什么這次美國“尋找新的增長點”要與中國聯手來做呢?這又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和啟迪呢?
眾所周知,在財富創造的“三大環節”過程中,美國向來重視跟“怎樣創造財富”有關的研發、設計和制定標準等所謂財富創造的第一環節。靠著第一環節的優勢,他們打造了大量的世界五百強企業,建立了種類繁多的世界品牌和專利,贏得了很多市場的“定價權”,從而,今天在全球市場運行機制和市場運行的物理平臺中,世人隨時都會看到“美國標準”。而從這次兩位部長帶來了新能源發展的合作戰略而論,顯然,美國已到了可將自身積累的成熟技術、研發成果甚至標準范式展現給合作伙伴。而不必擔心對方會有“高于一籌”的創新能力的“發展階段”。對他們來講,關鍵是如何充分發揮“規模經濟性”的優勢,將“思想”轉變為“現實”,將“無形資產”轉變成“有形資產”,而所形成的新產品價格要讓市場可以接受,讓市場感到物有所值!他們意識到了,當今世界只有中國才具有這樣的制造能力和成本優勢,而且甚至中國有可能成為消化這類新產品的市場主力。由此,筆者估計,環境和新能源領域的合作(美國研發新產品的核心內容)一定會成為將于本月27日至28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一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主要議題之一。
那么,中國的“比較優勢”究竟在哪里?在美國人看來,中國的“比較優勢”就在“形成實物”的第二環節上,且短時期內很難被取代和撼動。我們擁有龐大的勞動大軍,“敢闖敢干”的企業家精神,擁有沒有進入市場價值評估體系的落后地區(外資進入成本較低),擁有要素資源價格等相對穩定的政策環境,擁有勤奮努力好學向上的儒家文化傳統,擁有較為完善的市場運作的政策體系和制度機制,所以,能夠形成大規模生產和降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再加上中國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步入中產階層或形成中產階層意識,非常強烈向往能提高生活質量、改善生活內容的新產品。當然,從他們的視角來看,把新產品率先生產的“專利”交給中國,也給中國帶來了新的發展、新的就業和新的市場的絕好機會。
以筆者之見,這就是奧巴馬政府向中國謀求“雙贏”合作戰略的主要內容。
一旦美國新增長點通過與中國的合作形成了令人矚目的財富效應,那么,美國謀求的利益就不僅僅局限于技術、品牌和標準給他們帶來的豐厚碩果,而是會擴展到他們在服務行業(財富創造的第三環節)所具有的比較優勢——他們會充分挖掘市場潛力,將新產品真正轉變為夢寐以求的、更多的新財富。這樣一來,美國會再次推動圍繞新增長點的全球化進程,讓大家都參與到創造新財富和新生活的這一浪潮中,只要美國的金融體系仍然保持世界霸主地位,那么,新財富的管理依舊會仰仗美國的金融威力(當然世人對美國金融體系的監督要求也會不斷提高),美國還將可能成為下一輪新增長點的最大贏家。
針對“后危機時代”美國拿出的“發展戰略”和“中美合作戰略”,中國該如何主動應對?這是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程和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爭取“權力”和“義務”平等的關鍵所在。筆者以為,最核心的一條,就是社會上下都要充分意識到“政企利益的統一是國家競爭力發揮的核心”這個道理。今天,我們的問題是,政府看到了科學發展的重要性,并積極調整稅收制度和產業政策,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權機制,由于中國市場存在固有的壟斷勢力,出現了政企“利益沖突”的格局,中央政府的大國戰略中的“信號”引導不起作用,稅收成本和產業政策的約束力不但沒有讓企業放棄兩高一低的投資,反而把政策改變所帶來的成本提高因素,通過他們的市場壟斷力量轉嫁給了弱勢消費和生產群體,造成了產業結構調整和新的增長點探索行為上“主體缺失”的尷尬局面。
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中國政府應該多學一點企業和市場相關的創造利潤的“戰術”,而企業和機構則更要多學一點宏觀和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對中國經濟的生存環境產生影響的“戰略”知識。否則,缺乏“大氣”的中國企業和機構,無法意識到“無形資產”(創新的條件)在財富分配和風險轉嫁中的威力,而不了解“公平競爭”的政府,也無法體會在全球化環境中靠企業只身打拼的艱難和“安于現狀”的苦惱(在市場中,沖在第一線的國有企業也會感到“力不從心”,而民營企業則在渴求“政策的扶持”)。不管怎樣,今天我們在和美國新能源合作的談判中,中資企業和政府的“利益統一”,才是決定我們未來“利益分配”能力高低的最關鍵因素。
- 上一篇:問責規范化公權陽光化
- 下一篇:以黨政問責開辟公權制衡的制度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