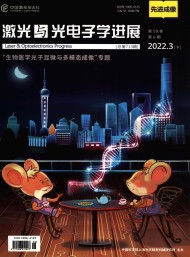申請檢察院抗訴申請書范文
時間:2023-03-18 11:45:46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申請檢察院抗訴申請書,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申請人:劉__,女,1958年10月1日生,漢族,個體醫師,住織__,系ss人民法院(1995)織民初字第899號民事判決中被告王正坤之妻。電話:180ssss5320.
被申請人(原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再審被申請人)張__,男,1959年2月17日生,漢族,農民,住__.
因申請人與被申請人房屋確權、房屋典當糾紛一案,不服織金縣人民法院(1995)織民初字第899號民事判決;不服織金縣人民法院(2002)織民初字第529號民事判決;不服畢節地區中級人民法院(2002)畢民終字第650號民事判決,于2002年12月18日向畢節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2003年12月5日,畢節地區中級人民法院(2003)黔畢民再終字第19號《民事判決書》駁回了申請人劉相英的再審請求。申請人不服該判決,于2004年3月向畢節地區檢察分院提起再審抗訴申請,畢節地區檢察分院交由織金縣人民檢察院辦理,織金縣人民檢察院于2004年3月30日作出了織檢民行立字(2004)第1號《民事行政檢察立案決定書》,至今未果。現依法向貴州省人民檢察院提起再審抗訴申請,請求事項如下:
一、請求貴州省人民檢察院依法對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抗訴。
二、此后,請求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撤銷畢節地區中級人民法院(2003)黔畢民再終字第19號民事判決;(2002)畢民終字第650號民事判決;織金縣人民法院(2002)織民初字第529號民事判決;(1995)織民初字第899號民事判決,提審或指定再審該案,支持申請人的申訴請求。
事實和理由:
____x
綜上所述,由于一、二審、再審判決不論在認定事實上還是審判程序上均存在錯誤,且拒不糾正,申請人深感不公,于2004年3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87條第二款、《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第33條的有關規定,向畢節地區檢察分院提出再審抗訴申請,畢節地區檢察分院將此案交由織金縣人民檢察院辦理,織金縣人民檢察院受理后決定立案審查,至今未果,故特請求貴院對本案予以抗訴。
此致貴州省人民檢察院
篇2
論文關鍵詞 刑事強制醫療 適用條件 救濟程序
刑事訴訟法修改設立了“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以下簡稱刑事強制醫療程序)作為四種特別程序之一,使強制醫療措施納入了法治軌道,對保護精神病人自身權益、社會其他正常公民合法權利、促進社會安定有序都具有重要意義。刑訴法第289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強制醫療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檢察機關,尤其是公訴部門,在刑事強制醫療的移送程序、申請程序、審理程序、法律援助等程序中,理所應當肩負起國家訴訟和法律監督職能。
一、適用條件及特點
根據刑訴法第284條規定,適用強制醫療,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幾個條件:一是犯罪行為的暴力性和后果的嚴重性;二是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鑒定的必經性;三是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人身危險性。條文規定這三個條件,表明了立法者對強制醫療程序適用的審慎態度。
作為特別程序之一的刑事強制醫療程序,概括起來具備以下特點:
第一,刑事強制醫療程序啟動的“三輪驅動”。即公安、檢察機關和法院。刑訴法第285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發現被告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可以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對于公安機關移送的或者在審查過程中發現的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人民檢察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申請。
第二,刑事強制醫療程序沒有程序意義上的救濟手段。根據刑訴法第287條規定,被決定強制醫療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親屬對強制醫療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法院申請復議。
第三,庭審方式特殊。控辯審三方的構造不同于普通程序,訴訟人(法律援助律師)或者法定人在場目的在于通過訴訟的參與權最終保障被申請人的權利。此外,刑事強制醫療程序并非必須開庭審理。
二、對檢察機關的影響
新刑訴法生效伊始,刑事強制醫療程序案件就正式進入檢察機關公訴部門的受案范圍,將會給公訴部門帶來不小的影響。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為例,我院公訴一處于2013年1月11日正式受理第一起刑事強制醫療案件,并于同年2月5日辦結。
第一,刑訴法正式實施后,公訴部門應當對符合強制醫療程序的案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根據刑訴法第285條的規定,對于公安機關移送的或者在審查過程中發現的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申請。刑訴法第289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強制醫療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
第二,刑事強制醫療程序作為全新的程序,公訴機關尚沒有辦理此類案件的經驗。從實體的角度來看,如何審查涉案精神病人是否實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為;如何判斷涉案精神病人是否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性等等。從程序的角度來看,案件的辦理期限,如遇有需補充證據的情況,應如何延展期限,公安機關補充證據的辦案期限是否也應該規定;鑒定程序是否適用刑訴法第二章第七節關于鑒定的相關規定等等。
第三,刑事強制醫療程序將會成為今后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新領域。如刑訴法第289條賦予檢察機關對強制醫療的決定和執行監督權;人民檢察規則第545條賦予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啟動強制醫療程序法律監督權。
三、應對措施
(一)指定辯護
從國家立法和司法解釋文件層面看,刑訴法第34條、286條規定指定辯護,主體是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
北京市三機關出臺的強制醫療實施辦法,是很好的貫徹落實法律、體現人權平等原則、保障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體現。該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強制醫療案件時,涉案精神病人、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沒有委托訴訟人的,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
(二)司法精神鑒定
法諺:無救濟則無權利。只有法律賦予公民更多救濟手段和途徑,才能使得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得到及時的治療,假冒精神病人逃避刑事處罰和“被精神病”的事件得到有效的遏制。
對犯罪的精神病人進行司法精神醫學鑒定,是正確適用強制醫療的前提。當前,刑事法(包括司法解釋)沒有對司法精神鑒定主體作專門規定,有的也只是概括式規定,如高院刑訴解釋第532條、人民檢察規則第543條第1款第4項、刑訴法第146條。簡言之,對于被申請人的司法精神鑒定作出主體是司法機關;如果被申請人及其法定監護人、訴訟人等對鑒定意見有異議的,那么需要檢察機關作出批準。
筆者以為這一做法需要完善,原因在于:《精神衛生法》(2012年10月26日通過,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的出臺,結束了之前混亂的司法精神醫學鑒定機構的局面,形成了明確的鑒定體系。根據該法第32條規定,精神障礙患者對于醫療機構鑒定有異議的,可以原醫療機構或者其他具有合法資質的醫療機構提出再次診斷;對再次診斷結論有異議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執業資質的鑒定機構進行精神障礙醫學鑒定。
因此,筆者贊同《精神衛生法》的規定,精神司法鑒定的主體是公安機關、人民法院、患者及其法定監護人,檢察機關扮演監督者的角色,對鑒定的程序合法與否進行監督。
(三)審查被申請人是否有繼續危害社會的可能
正如前文所述,啟動強制醫療程序條件有三,其中一條即: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采取了一種開放的表述,檢察機關在審查該強制醫療申請時有較寬自由裁量空間,但并不是無章可循。有無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重要前提是精神狀態,這涉及醫學專業領域,檢察機關的承辦人對于法律問題進行專業判斷,但是對于被申請人精神狀態的把握,筆者以為,主要還是需要憑借精神疾病方面的專家作出的鑒定意見或者其他材料,?這些材料均有助于判斷涉案精神病人的社會危害性,減少承辦人的個人主觀上的判斷。
(四)救濟程序
刑訴法第287條第2款規定,被決定強制醫療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親屬對強制醫療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這一規定區別于普通程序。在強制醫療程序中,考慮到時間緊迫以及案件非訟性質,實際是一審終審。啟動復議程序的主體既有被決定強制醫療的一方,也有因被申請人的暴力行為造成損害的被害人一方,法律如此規定較為全面的保護了被申請人一方。
(五)法律監督
第一,加強對公安機關的啟動監督。監督公安機關應當啟動而不啟動,類似于立案監督。人民檢察規則第54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公安機關應當啟動強制醫療程序而不啟動的,可以要求公安機關在七日以內書面說明不啟動的理由。經審查,認為公安機關不啟動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啟動程序。
第二,審查公安機關移送的強制醫療申請書是否符合要求。強制醫療申請書是公安機關移送檢察機關審查的書面文書,根據人民檢察規則第543條規定,需要對包括管轄在內的八項進行形式審查,進而提高辦案效率。
第三,監督公安機關采取臨時的保護性約束措施是否適當。根據人民檢察規則第546條之規定,對于采取臨時保護性約束措施不當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規定第332條,對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公安機關應當在七日以內寫出強制醫療意見書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可以看出,法律沒有對公安辦理是否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期限。因此,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對于臨時保護性約束措施進行監督就顯得十分重要。司法解釋規定的是在審查申請時對臨時保護性約束措施進行監督,筆者以為,檢察機關可以將啟動程序和臨時保護性約束措施一并進行監督。
第四,監督法院審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具體而言,包括是否通知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場,指定辯護,有無組成合議庭,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發現被告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擬作出強制醫療決定的,檢察院在庭審中發表意見等等。
篇3
關鍵詞:民事審判再審程序、民事審判再審程序的啟動、啟動再審程序的事由
依照通常的定義,再審程序(如無特別說明,本文以下所稱再審程序皆為民事審判再審程序)即審判監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依法對案件進行再審的程序⑴。在民事審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對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提高審判質量和法官素質等,起到突出的作用。現行民事訴訟法關于民事再審程序啟動的主體、事由、程序等規定缺乏科學性,或者規定的原則性較強,在操作上具有不規范性和隨意性,實踐中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當事人之間存在三方都不滿意的情況。所以,對再審程序及其實踐中具體做法做必要的研究,對今后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和完善,以及對民事審判實踐的指導等,都將大有裨益。而再審啟動程序的規范與完善是再審程序改革的關鍵,因此筆者根據民事訴訟法的原理、參照國外再審程序啟動的有關規定,擬就修正和完善我國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發表管見,以供商榷。
對再審程序啟動有關法律規定的分析
再審程序是為了糾正已發生法律效力判決、裁定中的錯誤而專門設置的一種程序。我國民訴法規定的再審程序盡管對糾正確有錯誤的判決、裁定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該程序在實踐中發揮的作用還遠未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一是盡管民訴法為發動再審程序設計了三種方式,即根據當事人的申請、由法院自行發動、通過檢察機關提出抗訴,但實際效果似乎不夠大,仍有不少明顯存在錯誤的裁判無法通過再審獲得糾正;二是裁判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因不斷再審而受到嚴重破壞⑵。正因為如此,一方面人民群眾對此深感不滿,以至于希望求助于訴訟制度以外的途徑來加強對審判活動的監督;另一方面,一些案件三番五次地進行再審,裁判不停地被更改,訴訟成了無底的黑洞,這種不斷改變的裁判給民事訴訟制度造成的損害不亞于不公正的裁判,它不僅鼓勵敗訴方通過纏訟來逃避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又嚴重損害了法院裁判乃至法律本身的權威。造成我國民事再審程序動作效果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設置程序的指導思想偏頗的問題,又有具體規定不盡合理或者不夠明確的問題,需要從各個方面進行分析,力求修正和完善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
再審程序立法思想的分析。我國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是建立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理論之上的,而并不重視終審判決的穩定性和終局性,尤其是忽略了程序的及時終結性,具體表現在:1、對再審的次數沒有限制,可以對生效判決,裁定進行無次數限制的再審;根據民訴法第179條規定,只要有新證據足以原判決、裁定的,或者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即可再審,從而使當事人只要發現了新的證據即可要求再審,甚至可以在一、二審中故意隱瞞證據,將之留待兩審終審后利用該證據啟動再審程序。由于“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的絕對化、擴大化、造成了一些案件出現多次數再審,根本不符合程序的及時終結性原則,一方面損害了司法的權威,造成了司法資源的嚴重浪費,違背效益原則,不利于裁判的既定力和穩定性;另一方面,這種拖延無法實現程序的正義和實體的正義,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法諺有云“法忌遲延”、“遲來的正義非正義”。這就說明了程序的遲延對當事人利益造成的重大損害。還要看到如果程序遲延將會使糾紛不能得到及時解決,可能釀成更大的糾紛和矛盾,影響社會的秩序與安定⑶。
再審程序啟動主體的分析。從現行法律規定來看,引起再審程序啟動的途徑主要有三種:
當事人申請再審。根據民訴法第178條規定,再審可以由當事人發動,一方面它充分尊重了當事人的處分權,另一方面允許當事人提起再審,使當事人的訴權獲得了充分的法律保障。但是關于當事人申請再審,目前仍缺乏明確的程序規定:1、關于法院對當事人申請后進行審查的期限沒有明確的規定;2、關于法院審查當事人的再審申請并做出答復的期限沒有明確的規定;3、當事人應當向哪一級法院申請再審不明確;4、法院針對當事人的再審申請如何進行審查沒有明確規定。由于沒有從程序上進行規范,不能引起人民法院的高度得視,使問題得到及時解決,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仍沒有得到有效保護。
人民法院依職權決定再審。根據民訴法第177條規定,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決定再審。在民事訴訟中由法院自己做出監督,是不符合民事關系的性質和審判規律的⑷。關于發動再審程序的主體和程序,兩大法系都規定必須由當事人來發動。民事關系本質上是當事人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由行使權利的領域,應當充分貫徹私法自治的原則,對當事人未提出再審申請的案件,法院原則上不應當進行干預。因為法院依職權決定再審存在以下問題:1、法院院長工作繁忙,無暇顧及所有案件,再則“尚未提起再審程序進行再審,何以知道原判決、裁定確有錯誤?怎么能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依據和理由‘審查屬實,’?顯然這是‘先定后審’的表現”⑸;2、如果當事人未申請再審而法院強行依職權再審,則是對當事人處分權的侵犯,因為存在“贏了官司更輸錢”的情況,這種損失由誰來承擔?3、法院依職權提起再審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因為當事人的反映,既然已經規定了當事申請再審救濟途徑,法院依職權再審就沒有必要了;最后,法院依職權決定再審也違背了訴審分離原則。所以,應當將法院依職權進行的再審歸入當事人申請再審。
人民檢察院依職權提起抗訴引起再審程序的啟動。根據民訴法第185條規定,檢察機關可以對法院已經生效的判決,裁定提出抗訴,從而啟動再審程序。筆者認為,既然在民事訴訟中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保障當事人的處分權,那么人民檢察院依自己的職權強行介入個人領域,有悖私權處分原則,不利于裁判的穩定性。甚至有學者提出“檢察機關民事抗訴權伊始,即暴露出許多無法解決的矛盾,所以廢除民事抗訴權是一種明智的選擇”⑹。當事人申訴的情況除外。
再審程序啟動事由的分析。對于我國現行法律對再審事由的規定,學者普遍認為存在缺陷,有必要進行重構。“改造再審制度的關鍵之所在是將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再審理由予以合理化和明細化。這也是完善再審制度的當務之急。”⑺筆者贊同此種意見。以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為例,其缺陷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1、規定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現行民訴法第179條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情形規定了五種事由,第185條對檢察院抗訴的情形規定了四種事由,兩條規定基本相同,均是原則性規定。至于第177條關于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的事由,則更籠統的只有“確有錯誤”四字。與之相比,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則要具體明確得多。如日本民訴法規定的再審事由有十種:(1)作出判決的法院沒有依據法律的規定組成審判組織;(2)依據法律不得參與裁判的審判官參與裁判;(3)對于法定權、訴訟權或對于人進行訴訟行為缺乏必要的授權;(4)參與裁判的審判官,犯有與案件有關職務上的罪行;(5)依據他人在刑事上應處罰的行為而自認或妨礙當事人提出可以影響判決的攻擊或防御方法;(6)作為判決證據的文書或其他物證,是出于偽造或變造;(7)以證人、鑒定人、翻譯或經宣誓的當事人或法定人的虛偽陳述作為證據;(8)作為判決基礎的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被以后的裁判或行政處分變更;(9)對判決有影響的重要事項在判決時被遺漏;(10)被申訴的判決與以前的確定判決有抵觸。通過比較不難發現,現行民訴法關于再審事由的規定過于籠統,勢必給適用帶來困惑。
2、表現出明顯的“重實體輕程序”傾向。人民法院違反法定程序的,只有“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才能申請再審。這里的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顯然是指影響案件實體上的判決、裁定。如果實體上的判決、裁定正確,即使案件嚴重違反法定程序也不能成為啟動再審程序的理由。這是典型的“重實體、輕程序”的表現,與現代法學理論公認的程序具有獨立價值的理念相悖。
3、現行規定多有遺漏。例如,無權審判的法官參與了審判;當事人在訴訟中被剝奪了辯論權;作為判決、裁定依據的主要證據是虛假的等等。對再審事由做完善的列舉是確保再審程序有效運行的前提,我國民訴法的現行規定離“完善”的標準尚有差距,再審實踐中當事人抱怨“申訴難”,與遺漏了應當作為再審事由的諸多事項不無關聯。
完善民事再審程序啟動的立法思考
立法指導思想的修正。有些學者認為,我國現行再審程序構筑的價值是基于“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應當說將實事求是作為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將實事求是這一哲學上的理性原則直接應用到某一學科領域,不過是一種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反映論的體現。尤其是將實事求是、有錯必糾聯系起來,作為再審程序的指導思想,而不考慮民事訴訟自身的特點,則必然會產生片面性⑻。筆者贊同上述觀點,現行民訴法的相關規定確實反映了這一指導思想,只要有新的證據、新的事實出現,已生效的裁判隨時都有可能被重新審理,甚至形成無限再審的局面。“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這一原則在民事訴訟領域中的適用,要受制于這樣幾個因素:1、民事糾紛解決的時限性。民事訴訟活動是對過去的事件進行證明并作出判斷的一個過程。嚴格依照法定程序徹底、完整地重現案件“原貌”雖然是一種最為理想的狀態,但是訴訟是要受到一定的時間、空間、證明方法、主體的認識能力、解決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不可能無休止地去苛求所謂“客觀真實”,而將民事權利義務關系長期處于不確定狀態,這將嚴重危及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2、民事判決是基于在一定時間內、一定的場合里所形成的訴訟資料的基礎上所作的判斷。這種訴訟資料是裁判賴以作出的基礎。應具有程序的約束力,無重大瑕疵不得隨意變更。3、對于訴訟成本的考慮。在訴訟中,變無限再審為有限再審,符合正義,效力和秩序的要求,樹立司法權威。
確定“再審之訴”的方向。再審程序的啟動,作為一項獨具特色的訴訟活動,需要程序保障,必須按照法定程序進行,以確保實體和程序正義。然而如前所述,我國法律目前對此缺乏規定,或者說規定缺乏科學性、原則性較強,可操作性較差,實務中問題較為突出。正如學者指出“我國再審程序反映出很大的內部運作特征,不規范的地方較多,特別是再審程序的立案審查階段,透明度、規范性都較差。”⑼其弊端主要反映在:1、法院對再審事由的審查不公開,不具有透明性,違背了程序公開的一般原則。由于審查的不公開,導致了審查程序的神秘和灰色,容易滋生司法腐敗。2、由于程序的非法定化,必然使審查程序不能統一和規范,給當事人的申訴造成困難,使錯誤的判決、裁定不能得到有效的糾正。3、既然民訴法給了當事人申訴權,就要求法院在審查申訴時有一個符合正義基本要求的程序。程序公開、充分陳述、程序法定等正義要求就應當在申訴審查中得到體現。如果沒有一整套完善和公開的“在陽光下”的申訴審查制度,一旦做出再審決定,并停止原判決的執行,也難以讓被申訴的當事人接受。4、民訴法規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作為再審程序啟動的主體,這違背了民訴法“不告不理”原則。鑒于此,學者們普遍認為,要改變這一狀況,有必要借鑒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建立再審之訴制度,取代現行審判實踐中的申訴復查制度,認為“將來再修訂民訴法時,有必要將申請再審改為再審之訴,并對再審之訴的與受理的程序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從而使當事人在再審程序中的訴權實在化,也使法院對再審之訴的受理規范化”⑽。
在大陸法系國家,再審程序是由再審之訴引起的,當事人提起再審之訴是發動再審的唯一途徑。有學者認為,“再審系指終局判決確定之后,發現具有訴訟程序方面的重大瑕疵,或者該判決的基礎材料中存在異常的不完善現象時,當事人以此為理由,例外地請求廢棄該確定判決重新審理該案的聲明不服方法。”⑾再審之訴具有雙重目的性,首先是要求撤銷原判決,其次請求法院按照人提出的實體方面的主張,做出有利于其的判決。由于再審之訴的主要目的是撤銷原判決,再審之訴的性質是變更之訴。相對于原來的訴訟程序而言,再審程序是一個新的訴訟程序,所以當事人要求再審須以提訟的方式進行,這就是稱之為“再審之訴”的原因所在。
對于申請再審,雖然我國民訴理論認為它已與申訴具有質的區別,它已不再是民利而是訴訟權利,是當事人的訴權在再審程序中的體現。但是由于民訴法對申請再審的規定過于簡單,很難說我國的申請再審就是再審之訴,至少不是規范意義上的再審之訴。由于當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只是“申請”而不是“訴”,并且是在訴訟程序已終結之后提出來的申請,客觀存在沒有具體的受理程序,沒有時限限制,不能引起法院足夠的重視,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權利就不可能象訴權那樣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由于傳統的“訴”的理論的規范性,將再審作為一個“訴”來規范,程序保障要完備得多。這樣既有利于當事人申請再審權利的訴權化,又便于法院啟動再審程序的規范化,從而為再審啟動提供有效的程序保障,解決當前再審啟動中的種種程序問題。這恐怕就是學者們主張以“再審之訴”取代“申訴或者申請再審”的原因所在。
將現行再審啟動中的申訴或者申請再審改造為再審之訴,借以規范再審程序,從長遠觀點看,不失為一個正確的選擇。但是此項改造,必須有賴于民訴法的大幅修改,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司法實踐中對再審啟動進行程序性規范的要求十分迫切。因此,從國情出發,本著充分利用本土資源的指導思想,對現行申請再審制度加以檢討,對其中實踐證明行之有效,且符合再審程序改革方向的做法,通過司法解釋等形式加以規范化、制度化,形成獨具特色中國式再審啟動程序。筆者認為,主要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明確其再審立案的性質。長期以來,再審程序處于立審不分的狀態,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不斷深化,立審分立作為法院內部分工制衡的一項基本原則確定下來,再審程序同樣面臨立審分立的問題。再審啟動程序是審查當事人的申請再審或申訴材料,決定是否受理的過程。從方法和手段來看,符合立案審查的特征。再審案件以此為起點進入實體審理,本文主要對再審案件的啟動進行闡述,對案件的實體審理不作贅述。現行申訴復查制度是作為啟動再審程序實際運作的,再審啟動、申訴復查與再審立案的過程是統一的,因此有必要盡快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進行明確,所謂“名正則言順”,明確申訴復查的再審立案性質后,可以適用法律對立案的程序規定來規范申訴復查的程序。2、推行審查聽證制度。申訴復查聽證制度是由合議庭成員共同組織案件各方當事人到場,用最簡便的形式聽取當事人申訴與抗辯的爭議焦點,以此來決定復查結果的迅捷復查方式⑿。3、對審查的程式做出規定。(1)形式審查,主要包括再審申請書或申訴狀、申訴時限、申訴主體資格等;(2)實質審查,即是否存在再審事由;(3)宣示審查結果,無論書面還是聽證審查,均應公開宣示審查結果,并說明理由。
受理事由規定的具體化。再審程序不同于一、二審程序,它既不是民事案件審理的一級程序,也不是審理裁決民事爭議的一種程序,而是一種特殊的救濟程序。一、二審的啟動是基于當事人行使其權和上訴權,權直接源于當事人的訴權,上訴權源于程序基本保障權。為了維護和保障當事人的訴權,保障和實現公民、法人受公正裁判的基本權利,一、二審程序的啟動都不要求有既存的事實理由。即使要求有理由,這種理由也是一種以當事人主觀判斷為轉移的理由,法院在啟動一、二審程序時,并不對這些理由進行實質性的審查。與此不同,再審程序作為一種特殊的糾錯和救濟程序。是在一般救濟手段即一審或者二審終結后,對已發生法律效力,但仍有錯誤的民事裁決加以糾正的程序,即可以通過撤銷已經生效裁決,以再次審理來保障民事爭議解決的公正性。由于對已生效裁決的否定,這就意味著將破壞已經穩定的法律關系,導致所謂通過裁決的訴訟終結實際上并不存在。因此,為了保持法律裁決的穩定性和權威性,作為一種事后的補救程序,就要求該程序的啟動應有嚴格的限制,這種限制就是法律規定的再審程序啟動的事由。再審事由是法院審查是否啟動再審程序的理由和根據,是打開再審程序之門的“鑰匙”⒀。再審事由在理論上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不以申訴人和法官的意志或主觀判斷為轉移,法院只有經過實質性審查,查明確有再審事由后,才能啟動再審程序。因此,從深層次原因上講,啟動再審程序以具備再審事由為前提,旨在限制再審程序的啟動,是為了在實現再審程序追求實體和程序正義的目的與保障生效裁決穩定性,以及爭議解決效率性之間求得一種平衡。
鑒于前面對我國民訴法關于再審程序啟動事由規定缺陷的分析,從再審程序的目的和有效運作制度的要求出發,借鑒國外立法先例,結合我國的司法實踐,筆者認為我國的民事再審程序啟動的事由可作如下規定:
篇4
關鍵詞:非法證據;被害人;申請排除;法理;程序;證明
中圖分類號:D91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4)05?0104?07
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56條第2款①賦予被害人及其訴訟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具有保護被害人權利的功能。這符合世界范圍內刑事司法加強被害人人權保障的趨勢,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中國特色之一。但立法僅僅作了原則性規定,缺乏操作細則,有關規范性文件也未見詳細解釋。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法理、程序與證明,仍是一個需要研究的課題。
一、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法理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早產生于美國。“作為對獲取證據過程中違反憲法行為的一種回應,排除似乎起源于對第四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保護的主旨的混同關注。”[1](319)“大多數排除規則只禁止在審判中使用不適當獲得的證據去證明被告有罪。”[1](353)因此,在刑事訴訟中,通過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來保護自己權利似乎成了被告人的一項專利。那么,我國《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害人及其訴訟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其正當性何在?筆者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
(一) 證據排除規則的理論基礎
證據排除規則作為世界各國(地區)普遍采用的憲法性權利救濟方式和程序性違法制裁措施之一,其理論基礎或正當性就在于,對于偵查人員通過侵犯公民
憲法權利的方法所獲取的證據,即使具有客觀性和關聯性,法庭也不應承認其證據資格而予以采納,從而抑制各種形式的違法取證行為,保護當事人的憲法權利,維護司法誠實性和社會公平正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Weeks 判決和Mapp判決中從三個方面論證了證據排除規則的正當性:一是憲法權利理論,認為排除規則是為了維護第四修正案所確立的憲法權利的唯一有效的救濟手段;二是抑制理論,認為排除規則是防止刑事執法官員繼續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有效制裁方式;三是司法誠實理論,認為如果法院要維護其作為司法裁判機構的榮譽,就不能對警察違反憲法的行為視而不見,甚至通過采納其以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方式所獲取的那些受到“污染”的證據,從而成為這種憲法權行為的“共犯”。[2](112?123)德國證據排除的理論基礎是“干凈的手”原理,法院排除非法證據的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懲戒違法的警察或警察機構,而是為了保護有關的利益和權利,尤其是保護由憲法保障的基本個人權利和利益。[3]立法賦予被害人及其訴訟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允許他們通過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來排除偵查機關通過不正當手段所獲得的證據,從而對偵查機關違法行為所導致的錯誤予以救濟,保護包括被害人在內的所有當事人的憲法權利,促進訴訟結果的準確性;另外,還可以懲戒或制裁偵查人員的違法取證行為,防止他們將來繼續違反法定程序,從而維護司法的誠實性和法律的尊嚴。這些都符合證據排除規則的理論基礎。
(二) 被害人的訴訟當事人地位
從域外立法規定看,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主要有證人、當事人和輔助人三種情況。[4]在大多數國家(地區),庭審由控訴、辯護和裁判三方組成,被害人作為證人參加訴訟,被認為與訴訟結果沒有直接利害關系,他們不是控訴方參加人,也無權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在中國、俄羅斯和我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等,被害人作為當事人或輔助人參加訴訟,立法承認他們與案件處理結果存在直接利害關系,能夠全程參與訴訟進程,并且是推動訴訟進行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們不僅有權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訴訟主張,而且有權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從而保護自己合法權利,維護訴訟程序的正當性。《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235條規定,被害人作為控方參加人之一,與國家公訴人一樣,有權參加庭審和提交證據,并且“申請從法庭出示的證據清單中排除任何證據”,包括非法證據。在德國附帶訴訟程序中,被害人作為公訴案件附帶訴訟的原告人,即當事人,有權參加庭審并且在審判中享有同檢察官幾乎相同的訴訟權利,包括申請查證權和排除非法證據。②我國《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58條規定,被害人作為檢察院的輔助人,雖然其參與訴訟程序從屬于檢察院的活動,但有權參與偵查或預審,并提供證據和申請采取視為必需之措施,包括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二)項賦予被害人訴訟當事人地位,第186~193條賦予被害人在庭審中自主陳述權、參加法庭調查與法庭辯論權等。被害人作為公訴案件中起輔助作用的控訴方當事人,有權提出不同于公訴的事實主張和法律適用要求,并提供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應當適度承擔證明責任”,立法當然應當賦予他們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因此,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是被害人訴訟當事人地位的重要體現之一。
(三) 刑事訴訟法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本任務
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2條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增加為刑事訴訟法的基本任務之一。有學者認為,刑事訴訟中人權保障問題的核心是,在公民的憲法權利遭受侵犯的具體場合,存在一種足以制裁侵權者和糾正程序法律錯誤的有效救濟手段。[2](86)世界刑法學協會《關于刑事訴訟中的人權問題的決議》第10條規定:“任何以侵犯基本權利的行為取得的證據,包括任何由此派生的間接證據,均屬無效,而且在訴訟程序的任何階段均不得采納。”我國憲法第二章規定公民享有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住宅、通訊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等一系列基本權利。刑法將侵犯這些基本權利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包括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等。學界和實務界主流觀點認為,被害人與被告人都是刑事訴訟人權保障的主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2010年聯合頒布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將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主體限定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忽視了“刑事上的對立者”――被害人及其訴訟人的同等需要,這顯然是不公正的。④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的通常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非法證據,而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非法證據,包括侵犯被害人基本權利的證據,以及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偽造的證據等,無法進入證據排除的視野。這不僅不利于保障被害人人權,而且可能嚴重損害司法權威,無法保證司法公正的全面實現。因此,《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害人及其訴訟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既是刑事訴訟法實現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本任務的具體措施之一,又是實現刑事訴訟中被害人與被告人人權保障平衡,讓被害人在個案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客觀需要。實務部門有學者反對賦予被害人該項程序性權利,理由是,如果這樣,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也將有可能被列入排除的范圍,這無疑是對疑罪從無、有利被告等刑事司法基本原則的違背。[5]該觀點明顯有失偏頗,片面強調被告人權利保護,不僅無法利用訴訟程序內機制解決非法取證這種程序性違法問題,而且司法實踐已經反復證明,對違法取證行為進行實體性制裁的效果并不理想。
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具有上述一系列正當性,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我國“四方組合”的“控辯式”庭審構造中,被害人作為“私原告”,與檢察機關(包括公安機關)共同組成控訴方。在司法實踐中,許多被害人擔心自己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申請后,可能失去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保護或降低他們追訴犯罪的熱情,因此不愿或不敢提出。從理論上說,被害人申請排除的證據既有言詞證據,也有實物證據;既包括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等私人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辯護證據,如辯護人或被告人近親屬采用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手段逼迫被害人做出的“虛假陳述”、辯護方偽造的證據等,也包括偵查人員以暴力取證等非法方法收集的控訴證據。這種控訴證據又可分為三類:一是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詞證據(包括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二是違反法定程序查封、搜查、扣押所取得的實物證據(包括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三是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的各種筆錄類證據(包括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筆錄等)。④如果這些控訴證據又屬于檢察機關指控犯罪的關鍵證據,就可能導致整個控訴失敗,使真正有罪的被告人逃脫法網,從而削弱社會公眾包括被害人對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此外,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第2款規定,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必須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這對那些“身臨其境”又“身受其害”的許多被害人來說,也是一個難題。這些局限性或難題就必須在健全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和完善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證明問題時予以兼顧。
二、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
“證據問題也是程序問題”,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必須遵循正當程序。根據《刑事訴訟法》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的規定,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一) 申請主體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4~56條規定,我國將取證手段的違法性作為判斷非法證據的標準,以遏制偵查人員非法取證行為作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理論基礎。我國非法證據排除包括依職權排除和依申請排除兩種,前者存在于偵查、審查和審判全過程,后者僅存在于審判階段。如果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人認為證據是以非法方法取得的,在偵查或審查階段只能向人民檢察院報案、控告或舉報,由人民檢察院調查核實并做出處理。在法庭審判階段,他們有權直接向法院申請排除,從而避免偵查人員從非法取證行為中獲得任何利益。這里的“被害人”是指其人身、財產、精神或其他合法權利遭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個人或實體,包括直接被害人中的個體被害人和單位被害人,但不包括間接被害人,和自身基本權利遭受非法取證行為侵害的“非法取證被害人”。訴訟人與被害人之間是一種委托關系,他們參加刑事訴訟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被害人的權利,其訴訟行為受被害人意志約束,因此,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也可以通過其訴訟人提出。為了充分保障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檢察機關、法院在告知被害人委托訴訟人、聽取被害人及其訴訟人意見時,應當明確告知被害人享有該項權利及其行使方式,并且記錄在案。
(二) 申請時間
各國有不同做法。美國、俄羅斯都允許庭前提出。在美國,被告人可以在專門的審前動議階段向法官提出有關排除非法證據的動議。⑤《俄羅斯刑事訴訟法典》第34章設立了專門的庭前聽證程序解決有關排除證據的申請。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82條增設了庭前會議制度,規定在開庭審判以前,審判人員可以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人就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筆者認為,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應在此時提出,由法院依法通知檢察機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后者同意排除的,法官應當在庭前會議上促成各方達成排除非法證據的共識,從而將該證據排除出法庭審判階段;如果各方意見不一致,由于我國庭前程序本質上是一個溝通協商程序,法官只能就審判有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不能獨立作出裁判,證據排除申請就要等到法庭調查過程中啟動專門的程序性審查程序先行處理。當然,如果非法證據是在法庭開庭后才知道的,被害人在法庭審判過程中直至一審宣判前都可以就全案或者部分證據提出排除申請,此時,法官既可以在法庭調查到某一個證據時進行,也可以待其他證據調查完畢后再對非法證據進行調查,決定是否排除。如果被害人在一審中沒有提出排除申請,在二審、再審中仍然可以提出,法院應當參照一審程序處理。
(三) 排除程序
各國做法也存在一定差異。美國、俄羅斯都設立了專門聽證程序解決。在美國,法官受理排除非法證據的動議后,會就有關證據的排除問題舉行專門的“證據禁止之聽證”。在這一聽證程序中,有關非法證據是否構成以及應否排除的問題,會成為控辯雙方辯論的核心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法官需要引導雙方提出證據和證人,被告人也有權出庭作證,控辯雙方就此進行交叉詢問,法官在聽取雙方證據、辯論和意見的基礎上,做出某一證據的取得是否違反憲法、應否禁止該證據在法庭上使用的裁決。[6]《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234條規定,庭前聽證由法官在不公開的審判庭獨任進行,控辯雙方包括被害人都有權參加。在一方申請排除證據時,法官應當向另一方查明該另一方是否對該申請有異議。在沒有異議時,如果不存在進行庭前聽證的其他理由,法官應同意申請并作出開庭的決定。根據該法第235條第3項規定,在排除證據的聽證程序中,法官有權詢問證人并將申請所要求的文件歸入案卷中。如果一方反對排除證據,法官有權宣讀偵查行為的筆錄和其他刑事案卷中現有的和(或)雙方提交的其他文件。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排除非法證據的具體程序。參照《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筆者認為,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和法院處理包括五個步驟。
1. 提出申請
被害人申請排除偵查人員或辯護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應當向法院提出申請,申請原則上采取書面形式,申請書副本由法院轉交給檢察機關及被告人、辯護人。申請書應當載明被害人申請排除的證據名稱,并說明申請排除該證據的理由,包括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從司法實踐看,這種“線索或者材料”主要包括被害人出示的遭受暴力取證留下的傷痕、照片、醫療證明、傷殘證明、詢問筆錄、知情人證明,以及偵查人員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取證留下的其他痕跡,或者可以顯示非法取證行為發生時間、地點、方式、內容及涉嫌非法取證人員等情節的線索或材料。特殊情況下,被害人也可以口頭申請,由法庭記錄并通知檢察機關及被告人、辯護人。
2. 法庭審查
無論庭前會議還是庭審過程中,法庭受理被害人申請后,應當進行審查并且聽取檢察機關和辯護方的意見,分三種情形分別做出處理:如果法庭認為明顯沒有根據或者不可能存在非法取證的,直接駁回申請,并書面通知申請人,說明理由。如果檢察機關和辯護方都對該排除申請沒有異議,法庭也認為不存在開庭聽證的其他理由,應當同意該申請并裁定排除非法證據;如果檢察機關或辯護方對該申請提出異議,并且法庭對該證據取得的合法性存在疑問,認為可能存在《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先行調查處理。
3. 證據收集合法性證明
如果審判人員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存在疑問,對于控訴證據,檢察機關應當對此加以證明;對于辯護證據,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應當對此加以證明。檢察機關的證明方法除了現有證據材料外,還包括詢問筆錄、原始的詢問過程錄音錄像或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詢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然不能排除非法取證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有關偵查人員作證。偵查人員應當出庭,而不能由偵查機關出具一份書面的“情況說明”來自證清白。有關偵查人員也可以主動要求出庭說明情況,洗脫自己非法取證的嫌疑。對于辯護證據,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必須舉證證明其取證行為符合法律規定。
4. 各方質證
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明屬于一種程序性證明。《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款規定,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可以排除非法證據。而第182條第2款規定的“了解情況,聽取意見”是否屬于庭前聽證程序,還有待相關司法解釋明確。筆者主張借鑒美國、俄羅斯等做法,將該款解釋為一種庭前聽證制度,以便法院能盡量在庭前解決非法證據排除問題,節約庭審時間,提高庭審效率。另一方面,這種庭前聽證程序與庭審調查程序應當統一規劃,構建一種專門的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性審查程序,由庭審法官以外的法官(或稱預審法官)主持,檢察機關、被害人及其訴訟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都有權參加,各方可以圍繞有關證據是否構成《刑事訴訟法》第54條所規定的非法證據,以及應否排除等出示證據,進行質證、辯論,被害人、被告人也可以陳述并作證。但這種審查聽證不應當涉及案件實體問題處理。
5. 法庭裁定
經過法庭審理后,如果法官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依法作出裁定,將被害人申請排除的證據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使其失去法律效力,禁止在庭審中使用或者作為法院裁判的依據。
(四) 救濟程序
如果法庭作出拒絕排除非法證據的裁定,被害人及其訴訟人是否可以就該問題再次提出申請或提起上訴等獲得救濟,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美國、俄羅斯都設立了專門的救濟程序。在美國,對于法官拒絕排除某一有爭議的證據的裁定,被告人除了可以在法庭審判階段重新提出排除的動議之外,還可以通過直接上訴和間接復審程序獲得救濟。[7]《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235條第7項規定,如果法院在庭前聽證中作出排除證據的裁決,“在刑事案件進行實質審理時,法院根據一方的申請有權再次審議認定被排除的證據可以采信的問題”。而根據該法第354條第4項規定,如果法院作出拒絕排除證據的裁決,被害人及其人都有權對此提出上訴尋求救濟。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6條規定,如果被害人在庭前會議階段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遭到拒絕,他在庭審中還有權再次提出。但《刑事訴訟法》第218條僅賦予被害人對一審法院判決不服的申請抗訴權,沒有賦予他們對判決或裁定(包括程序性裁判)不服的獨立上訴權。如果被害人認為存在《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情形而提出申請,一審法院裁定予以駁回,被害人此時顯然不能申請檢察機關抗訴,而刑事訴訟法又沒有為被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濟途徑,被害人及其家屬可能很難接受這種裁判結果,刑事糾紛并未得到最終解決。因此,筆者一直主張立法賦予被害人獨立的上訴權[8],包括借鑒美國、俄羅斯做法,設置專門的程序性救濟程序,允許被害人及其訴訟人對法院駁回其排除非法證據申請的裁定不服提出程序性上訴獲得救濟。
三、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證明問題
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作為一種程序性證明活動,證明對象是作為證據法事實的證據收集合法性問題,被害人及其訴訟人需要提供相應的材料或線索予以證明,這就涉及到證明責任、證明標準、證明方法、證據規則等證據法問題。證明方法以上已經談及,在此不再重復。
(一) 證明責任
在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分配上,各國(地區)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檢控方承擔,各國口供合法性的證明都采用該模式;二是申請方承擔,實行“誰主張、誰舉證”;三是申請方承擔初步證明責任,檢控方承擔最終證明責任。俄羅斯和英國采用前兩種模式。《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235條第7項規定,如果辯護方提出排除證據申請的理由是證據的取得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則在審議時,辯護方所提理由的證明責任由檢察長承擔。在其他情況下,證明申請理由的責任由申請提出方承擔。換言之,如果被害人申請排除證據,則由他自己承擔證明責任。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76條和第78條分別確立了兩種不同的證明責任分配規則。第76條規定,對于被告人口供是否屬于警察強迫所得以及口供是否可靠的問題,應當由檢控方承擔證明責任。第78條規定,如果被告人申請排除某一控方證據,他需要承擔相應的證明責任,證明該證據是警察非法所得,法庭采納該證據將對訴訟的公正性造成不利影響。美國和德國采用后兩種模式。美國證據禁止聽證程序的證明責任分配規則比較復雜。一般情況下,提出動議的被告人經常要承擔證明某一證據系屬非法證據的責任;但在很多情況下,這種證明責任也會轉移給檢控方。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判例確立了被告人申請排除不同種類證據的證明責任分擔和轉移規則。[9]而作為一項原則,被告人申請排除證據,必須首先證明其具有相應的法律資格,即其自身的憲法權利受到警察非法取證行為的侵犯。這也是一種初步證明責任。在德國,一般也是先由辯護方承擔使法官認為可能存在非法取證行為的初步證明責任,然后由控訴方對此可能的排除加以最終證明。[10]
我國《刑事訴訟法》采用第三種模式,無論被害人還是被告人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都由申請方承擔啟動證據收集合法性的初步證明責任,即提供相關線索或材料證明他具有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資格,這主要是為了防止該項權利被濫用,當事人無根據地行使訴訟申請權,以至于造成訴訟的不合理拖延。法庭經過審查,認為可能存在《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啟動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程序,由檢察機關或被告人、辯護人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承擔最終證明責任。
(二) 證明標準
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所承擔的初步證明責任作為一種程序性證明責任,既不同于被害人證明自己提出不同于公訴的訴訟主張而承擔的實體性證明責任,也不同于檢察機關為了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而承擔的程序性證明責任,更不同于檢察機關證明被告人有罪的實體性證明責任。它們之間的主要區別就在于證明標準的差異。由于這種初步證明責任主要用來解決被害人的申請資格問題,同時為了保障被害人人權,因此,其證明標準不能定得太高,否則,許多被害人遭受非法取證行為侵害后無法提供相應的證據予以證明而可能被排除出該項權利之外。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規定,只要被害人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或材料,能使法官產生疑問,認為可能存在《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情形,從而說服法官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即達到“表面上成立”即可,而非要求被害人必須提供某一具體種類的證據。否則,該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就可能成為公安司法機關剝奪被害人申請權的合法依據,甚至成為公、檢、法三機關相互庇護以阻礙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工具。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檢察機關證明證據收集合法性必須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與該法第195條規定檢察機關證明被告人有罪的實體性證明標準是一致的。如果他們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法官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該證據就應當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刑事訴訟法要求檢察機關承擔證據收集合法性的程序性證明標準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有利于加大對偵查人員非法取證行為的制裁,從而更加全面地保護被害人人權。該規定與英國做法一致。⑥但是,筆者認為,立法要求檢察機關對所有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明都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這與我國目前刑事法律規范尚不完善、全國各地偵查機關人員素質與偵查水平參差不齊等不協調,可能導致訴訟成本的提高和更多非法取證手段的使用,不利于實現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平衡。在美國,一般情況下,提出證據禁止動議的被告人如果需要承擔證明責任,這種證明最多只需要達到“優勢證據”的程度,而在檢控方承擔證明責任的場合下,其證明標準一般也是“優勢證據”,即使在特殊情況下也僅需要達到“清楚的和令人信服的證據”程度即可,無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有罪證明標準。⑦我國有學者認為,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明只要達到“較大證據優勢”即可,要求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程度要求過高,不太現實。[11] 筆者主張區別對待,對于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如果屬于偵查機關以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詞證據,即《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強制性排除”的情形,檢察機關對其收集程序合法性的證明應當達到“較大證據優勢”或“蓋然性優勢”的程度;而對于偵查機關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證、書證(嚴重影響司法公正且不能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即“自由裁量的排除”的情形,檢察機關證明只要達到“優勢證據”程度即可。因為“自由裁量的排除”規則所針對的違法取證行為并沒有侵犯重大的利益,一般也不會造成特別嚴重的后果,因此,在證明責任的確定上應當與“強制性的排除”有所區別。而如果被害人申請排除的是辯護證據,由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承擔證明責任,證明標準也僅需達到“優勢證據”程度即可,以區別于檢察機關承擔證明責任。
(三) 證據規則
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與被告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一樣,是一種特殊的程序性裁判,主要是為了解決證據收集合法性問題,而不是被告人定罪量刑問題,因此,通常具有較為簡易的程序模式,一般適用自由證明的理念,有自己獨立的證據規則,而不能適用實體性裁判的嚴格證明機制和證據規則。這種證據規則除了前面談到的特殊的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外,還包括有關證據的可采性規則等。對于后者,我國法律至今缺乏規范。有學者提出“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一體化”的觀點,認為對于程序性事實的證明,沒有必要嚴格區分證據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原則上,只要證據在真實性、可靠性或相關性上沒有異議,法庭就可以確認其證明力,也可以因此承認其證據能力。在程序性裁判的證據運用上,即使在取證手段、取證主體或者調查方式上存在一些程序上的瑕疵,只要不影響該證據的證明力,法庭都可以采納。[12]這種觀點總結了英美等國程序性裁判證明的共同做法,比較符合我國刑事司法現狀,便于當事人申請和法院更多地解決證據收集合法性爭議。《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第7條允許檢
察機關提交經有關訊問人員簽名或蓋章并且加蓋公章的說明材料作為證明取證程序合法性的證據,就是一個例證。但是,筆者認為,既然包括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在內的程序性裁判實行自由證明機制,立法就不應該對法官探知證據信息所使用的證明方法及其調查程序做出較多限制,也不應再援引嚴格證明機制中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概念來規范證據準入與采信,而應當賦予法官較為充分的自由裁量權。換言之,在程序性事實證明中,法官原則上可以使用所有可能取得的證據材料來探求證據信息,并且只要形成“很有可能”或“大致相信”,即“表面上成立”的心證即可,不受直接、言詞、公開審理等證據法原則和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等限制。對于特定訴訟要件是否存在,法官是否已有足夠的心證,也應當賦予他們合乎義務的自由裁量確定。在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性事實證明中,被害人、證人基于猜測、假設、傳聞所做的陳述、證人不能指出其信息來源的證言,以及被害人、被告人、證人的品格證據等任何形式的證據材料,只要法官認為真實、可靠,能幫助其形成正確心證,原則上也可以采納作為證據。
四、結語
被害人作為刑事案件當事人和刑事訴訟中起輔助作用的控訴方當事人,與訴訟結果有直接利害關系,其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具有正當性。但如果被害人申請排除的證據又屬于檢察機關指控犯罪的關鍵證據,就可能導致整個控訴失敗,使真正有罪的被告人逃脫法網,因而還存在一定局限性。筆者建議立法在庭前會議中增設專門的聽證程序,讓法庭通過公開聽證對被害人提出的排除申請作出裁定,同時,為被害人不服該裁定提供救濟。另外,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作為一種程序性證明活動,采用自由證明機制,證據收集合法性的最終證明責任由檢察機關或辯護方承擔,但只要達到“優勢證據”標準即可,并在證據規則上賦予法官更多的裁量權。這樣,既能充分保障被害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權利的實現和處理程序的正當性,又可以有效克服此類申請可能產生的局限性,實現被害人與被告人人權保障的動態平衡。
注釋:
① 該款規定:“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
② 參見《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95條第(四)項和第397條第(一)項。
③ 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定》起草過程中,理論界就被害人是否有權申請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存在爭議。起草者認為,被告人是整個刑事訴訟活動的中心,相對于被害人而言,被告人與審判結果有著最為直接的利害關系,為了避免司法機關的審查偏離重心,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審判效率,更為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暫時沒有賦予被害人申請證據收集合法性審查的權利。他們認為,如果在取證過程中,偵查機關的非法取證行為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被害人可以通過申訴、控告、檢舉等方式獲得救濟。參見張軍主編:《刑事證據規則理解與適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頁。
④ 從《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看,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不規范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等私人非法取證行為,也沒有明確派生證據,即“毒樹之果”問題。本文主要研究被害人申請排除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的控訴證據,包括《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以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和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證、書證(嚴重影響司法公正且不能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以及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等采取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逼迫被害人提供的“虛假陳述”等辯護證據。
⑤ 關于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詳細介紹,參見陳瑞華:《比較刑事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4-137頁。
⑥ 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76條規定,凡是對被告人采取“壓迫”的手段所取得的供述一律無效,除非檢察官能夠向法庭證明它不是以“壓迫”方式取得的,而這種證明的標準也是排除合理懷疑,與有罪證明標準一致。
⑦ See Lego v. Twomey, 404 U. S. 477(1972).
參考文獻:
[1] [美]約翰?W?斯特龍. 麥考密克論證據(第五版)[M]. 湯維建等, 譯.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
[2] 陳瑞華. 比較刑事訴訟法[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
[3] [德]托馬斯?魏根特. 德國刑事訴訟程序[M]. 岳禮玲, 溫小潔, 譯.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 187?200.
[4] 蘭躍軍. 刑事被害人作證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11: 64?66.
[5] 高林芳. 刑事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分析及改進[EB/OL]. 光明網, 2013-04-02.
[6] Stephen A. Saltzburg, Daniel J. Capra.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Cases and commentary Sixth edition [M]. Washington: West Publishing Co, 1997: 454?456.
[7] Stuntz. The Virtues and Vices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M]. Harv. J. L. and Pub. Pol. 1997(20): 443.
[8] 蘭躍軍. 刑事被害人人權保障機制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270?284.
[9] Joel Samaba. Criminal Procedure [M]. New York: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585?590.
[10] Mireille Delmas-Marty, Spencer J R. European Criminal Procedures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02?605.
篇5
[關鍵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量刑答辯
量刑答辯制是指刑事案件的控辯雙方,在對被告人的具體量刑的幅度上,控方享有量刑建議權,而辯方享有量刑答辯權。從這個定義看,量刑答辯制應包含兩個內容:一是量刑的建議權,也就是求刑權,指公訴人在指控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犯罪性質的同時,提出較為具體量刑意見的權力,系公訴人在量刑裁判以前的某個訴訟環節,在綜合考慮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的基礎上,依法就適用刑罰包括刑種、刑期、罰金數額和執行方式等提出建議。本質上,量刑建議權是公訴權的一部分。二是量刑的答辯權或異議權,由辯護人、被告人針對公訴人的量刑建議的內容進行答辯,也:可以提出自己關于量刑的建議。量刑建議權與量刑答辯權系公訴權與辯護權的必然延伸。
司法實踐中,對刑事案件被告人的量刑普遍存在不平衡性,原因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方面由于我國刑法在分則條文中對各罪分檔過粗,而造成法定刑幅度過大;刑罰標準過于寬泛,必然導致量刑的不穩定性和不一致性。且量刑彈性條款過多,使法官難以把握。另一方面,法官自由裁量具有不穩定性。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較大,法官自身的素質、個人經歷、專業素養、知識水平等方面的差異,對相同或相似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及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大小的理解、判斷存在較大的差異,使得量刑幅度、尺度不一的情況存在。
對于未成年被告人,由于我國立法的缺位,均是參照成年人的量刑標準在執行;未成年人又有著法定的從輕、減輕情節,量刑的彈性更大;在犯罪原因上,不僅有未成年被告人本身的原因,也有社會及家庭的原因;審理及處理宗旨是以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為主,懲罰僅僅是輔助手段,因此量刑時所考慮的因素就更多。
對未成年人犯的量刑,還有一種較特殊的狀況,就是判處非監禁刑的比例較大,量刑輕緩化夾出。據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審判庭在2003―2005年三年統計數據顯示,所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共計有347件856人,其中未成年人犯有464人;在這464人中,判處有期徒刑宣告緩刑、單處罰金、免于刑事處罰等非監禁刑的共計187人,占未成年人犯的40.3%。從這些數據看,當然體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輕緩化的特點,以及教育挽救為主,懲罰為輔的宗旨,但怎樣把握適用非監禁刑的標準,掌握好量刑的度,以更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仍然是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綜上所述,對未成年人刑事一審案件在庭審中適用量刑答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以下幾點思考意見。
一、對未成年刑事案件審理中適用量刑答辯的必要性
(一)意義。量刑答辯制是司法公正的體現,有利于完善和健全我國少年司法制度,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程序上,沒有經過辯論程序而直接予以判決是不合法的。量刑答辯作為對法官自由裁量制度的必要補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量刑答辯制度的實行是給控辯雙方發表量刑意見甚至進行辯論的機會,實際上增設了一個相對公開的量刑聽證環節,從而提高了量刑的透明度,把量刑置于一種無形的監督下,有助于未成年被告人對自己罪行危害性的認識,和對法院判決的理解與服從,有利于改造,也充分保障了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二)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因素具有特殊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在對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時,不但要根據犯罪事實、犯罪性質和社會危害程度,還要充分考慮未成年人犯罪的動機、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慣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節,以及犯罪后有無悔罪、個人一貫表現等情況,決定對其適用從輕還是減輕處罰,以及從輕或者減輕裁決的幅度,使判處的刑罰有利于未成年人罪犯的改過自新和健康成長。因此,全面調查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處罰影響很大。
在現代刑事司法制度中,法官對案件的處罰是中立而消極的,必須經控辯雙方充分陳述、辯論,在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綜合情況基礎上,才能做出對被告人恰當的判決,庭審中只有設立量刑答辯,才能促使控辯雙方對被告人進行全面調查,將社會調查報告中所涉及的內容作為對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理由來展開辯論,支撐自己的控、辯理由。法官就能從雙方的意見中獲取對未成年被告人全面和客觀的了解,既防止了對未成年被告人一味地懲罰,又防止了輕刑化的濫用所導致的量刑不當。
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被告人在量刑時,適用非監禁刑的情況較多,非監禁刑的適用對未成年被告人較為普遍。而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在適用緩刑條件上,它不僅僅需要被告人本人所具備法定的從輕、減輕情節,或者酌定從輕情節,比如偶犯、初犯、沒有惡習、受人邀約、引誘、案發后積極退贓、認罪、悔罪態度好、被害人予以諒解等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還必須要具備應有的管教監護條件,而且管教監護條件是否具備、條件好與不好,在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非監禁刑上有著關鍵性的作用。但就有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長,為了讓未成年被告人能夠適用非監禁刑,而提供不實的管教條件,甚至提供一些虛假的證明,以使法官相信該未成年被告人具備相應管教條件而判決適用非監禁刑。筆者不否認家長給法院提供這些管教條件是基于積極的態度以及其為幫助未成年被告人走上正道的動機,但不一定對被告人矯治有利,由于是法院單方進行審查,僅停留在書面上,缺乏一個相互辯論的程序,這也有悖于程序公正。
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非監禁刑,需要進行量刑答辯,這也是立法精神的體現。2002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二十二條規定:“對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悔罪態度較好,具備有效幫教條件、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未成年被告人,公訴人應當建議法院適用緩刑:(一)犯罪情節較輕,未造成嚴重后果的;(二)主觀惡性不深的初犯或者脅從犯、從犯;(三)被害人要求和解或者被害方有明顯過錯,并且請求對被告人免于刑事處罰的。”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二十九條的規定,法庭審理時,控辯雙方向法庭提出從輕判處未成年被告人管制、拘役宣告緩刑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緩刑、免于刑事處罰等適用刑罰建議的,應當提供有關未成年被告人能夠獲得監護、幫教的書面材料。上述規定明確了對未成年被告人在適用非監禁刑上實行刑罰建議。筆者認為,提出刑罰建議,并向法庭提供書面材料,其最終是要
法庭采納或確認其真實性,因此必然要適用量刑答辯。
(三)關于對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判處罰金刑的問題,一直以來對其如何體現平等性以及量刑幅度與經濟狀況的一致性,頗有爭議。依照刑法的規定,罰金刑并未將未成年人排除在外,但對于如何適用罰金刑、如何確定罰金刑數額等,立法沒有限制性規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只是將未成年人的罰金數額的起點與成年人相比,降低了500元(成年人是1000元)。但從被告人是未成年人這個角度講,在經濟上是沒有獨立的,沒有履行能力。無疑,繳納罰金的擔子就落在了其父母的身上。大多數未成年刑事案件是侵犯財產類的案件,搶劫案和盜竊案占了未成年犯罪80%以上的比例,故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罰金刑相當普遍。但審判實踐中卻很少考慮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經濟狀況、財產狀況,僅比照比成年被告人的罰金數額而主觀判決,隨意性相當大,難以體現刑罰與經濟狀況相統一。更嚴重的是,相同數額的罰金,對于經濟狀況不同的被告人具有不同的意義,這也就是罰金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適用的最大的弊端――不平等性。因為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家庭經濟狀況不盡相同,經濟承受能力可能相差很大。同樣是一萬元罰金,家庭經濟狀況好的,可能如九牛一毛,無關緊要,而對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的,則意味著要傾家蕩產或負債累累,事實上也出現了同樣犯罪情節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對同等額的罰金刑實際感受的痛苦出現極大懸殊,這樣也顯失公平的。
量刑答辯制度可以從程序上解決這個問題,能糾正控辯雙方只注重查清案件事實而不關心其家庭財產狀況,促使控辯雙方針對未成年被告人家庭經濟狀況收集證據,通過對罰金刑的量刑建議和辯論,讓法官做出公正而合理的判決。
二、量刑答辯在一審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適用也是可行的
(一)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刑事訴訟制度中都有關于量刑建議的內容。在英美法系國家中,對量刑建議的態度不一,如英國認為量刑權是法官的專有權力,對被告人處以何種刑罰,是法官和犯人之間的事,控方的任務只是協助法官確定量刑的事實基礎而無權建議處以何種刑罰。美國則不同,雖然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控方有量刑建議權,但量刑建議卻在實踐中被廣泛使用,尤其是在達成辯訴交易的情況下,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往往就是最后的宣告刑。
大陸法系國家,量刑建議制度比較普遍,如在日本,一般檢察官在論述指控時,對具體的量刑發表意見,這叫請求處理。“求刑”指請求量刑,一般要求有具體的刑名、刑期、金額、沒收物、價格等的明示,這是日本刑事訴訟審判實踐中早已被確定下來的訴訟慣例,既是檢察官的權利,又是檢察官的義務。而在德國,檢察官在審判中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驟是對刑罰的建議,尤其體現在其處罰令程序中。德國的處罰令程序是一種處理簡單、輕微案件的簡易審判程序。《德國刑事訴訟法》第407條規定了處罰令程序,即“在系屬刑事法官、陪審法庭可以不經審判以書面處罰令確定對詢問的法律處分。申請應當寫明要求判處的法律處分。提出了申請就是提出了公訴。”處罰令程序中的申請書要載明案件事實以及所請求裁定的刑罰種類及罰金數額。
縱觀各國對量刑建議的做法,雖各具特色,但也有一些共同之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量刑建議一般都在法庭上提出(德國的“處罰令申請”例外);(2)控方提出的量刑建議僅僅是一種建議,不對法官產生具有法律效力的約束;(3)在法官不采納檢察官的量刑建議時,檢察官不能以此為由提出上訴(我國為抗訴)。
(二)量刑建議權具有其法理依據。量刑建議權是公訴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訴機關在行使公訴權時,其內容實際上包括兩部分,一是請求法院對其的犯罪予以確認,行使的是定罪請求權;二是請求法院在確認犯罪成立的基礎上,請求予以刑罰處罰,即量刑建議權(求刑權)。長期以來,公訴人在行使公訴權時,只注重行使定罪請求權,對于量刑問題完全付諸法院,而沒有全面行使法律賦予的公訴權。沒有量刑建議權的公訴權,是一種有缺陷的公訴權。
從立法角度看,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這一條是關于決定提起公訴的案件的條件和如何提起公訴的規定,而其中就將“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作為提起公訴的條件。第160條規定:“經審判長許可,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人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并且可以互相辯論。審判長在宣布辯論終結后,被告人有最后陳述的權利”。本條規定的一個方面就是法庭辯論。根據這條規定法庭辯論是在法庭審理中,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人圍繞犯罪事實能否認定被告人是否實施了犯罪行為,是否應負刑事責任,應負什么樣的刑事責任等,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各自意見和進行互相辯論。這些法律條文為公訴人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議權、-辯護人享有量刑答辯權提供了法律依據。
(三)適用的有利條件。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在適用量刑答辯制上,有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理確立了強制辯護制度,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律師的出庭率高,為100%,這就為適用量刑答辯提供了程序和制度上的保障,讓被告人方有足夠的力量抗衡控訴方的指控。
未成年刑事案件在審判原則、程序和實體上,都具有其特殊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的規定,審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執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積極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因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重在教育挽救。教育挽救為主的宗旨貫穿未成年刑事案件審理的始終,故法庭辯論還應涉及到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什么樣的處罰對教育挽救更為有利,控辯雙方的對立性和抗爭性就沒有普通刑事案件那樣強烈,其對量刑進行答辯的目的容易得到統一,辯論的焦點也將會圍繞怎樣處罰對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最為有利,以及對被告人適用刑罰種類的理由等等,特別是在對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適用緩刑等非監禁刑的問題上,更能體現量刑答辯的優越性。故在“涉少”案件中,控辯雙方的對抗性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對抗,對抗性的強弱服從和服務于保護少年,教育、感化、挽救少年犯罪人的共同任務。法官的地位是主導性的,其行為是積極、主動,而非消極的。故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庭審中適用量刑答辯制是有必要且可行的。
三、司法實踐中量刑答辯所有在的問題以及尚需完善之處
(一)量刑答辯制度怎樣在未成年人刑事“暫緩判決”制度中得以體現
“暫緩判決”制度使刑事案件的審與判相分離。這種制度的特點在于經庭審以后只能確定案件的事實及性質,在判決之前對未成年被告人的考察對于法官量刑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力。那么庭審中的量刑答辯似乎顯得沒有必要。怎樣將兩者作有機的結合,是司法實踐面臨的一個新的問題。筆者個人認為,只要分清了法官自由裁量權與量刑建議權、量刑請求權之間的關系,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量刑答辯的意見是對法官的裁決提供一種參考意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是不受量
刑答辯意見的限制,量刑答辯的意見是控辯雙方對量刑的一種建議,并無法定的效力,也并不妨礙法官正確適用刑罰,對控辯雙方的量刑意見,法官既可以采納也可以拒絕。而“涉少”案件中的暫緩判決案件,由于其程序的特殊性,庭審中量刑答辯仍可進行,而且控辯雙方均可對該案件是否進行暫緩判決、暫緩判決考察期滿后的刑罰適用提出量刑的建議和量刑的辯論,法官可以將雙方的意見作為是否對該案適用暫緩判決的參考意見,在暫緩判決的考察期結束后,法官可在綜合控辯雙方的意見基礎上,結合暫緩判決考察期未成年被告人的具體表現作出量刑裁決。
(二)量刑的具體意見可否由辯護人在法庭上先于公訴人提出來,即量刑建議的主體是單一還是多元的問題
公訴意見中沒有具體的量刑意見,在司法實踐中是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擔心公訴人提出量刑建議后,如果法官不采納,會造成公訴人處于尷尬的處境;擔心由于推行量刑建議而加大工作量;擔心量刑建議會干涉審判權而引起法官的反感等等。是否公訴人沒有量刑建議,辯護人的量刑辯護就沒有針對性?就筆者所在法院少年庭對“涉少”案件適用量刑答辯的具體情況看,首先庭審活動是由審判長在駕馭,在公訴人沒有具體提出量刑建議的時候,審判長可以要求公訴人“就具體的量刑發表意見”;如果公訴人消極對待,法庭完全可以讓辯護人就具體量刑發表意見后,再征求公訴人對辯護人量刑的意見。司法實踐中這種情況較為常見。因此量刑建議的主體不應僅限于公訴人,在順序上由誰先提出都是可行的,不能因為公訴人不提量刑建議,辯護人就沒有量刑辯護的機會。公訴人不提量刑建議,那是公訴人自己放棄了其具體量刑建議的行使權。從總的程序來說,檢察機關在書中已載明適用的刑法條款,即使公訴人消極行使量刑建議權,辯護人的量刑意見仍然也具有針對性。
(三)控方量刑建議的具體時間
量刑建議的時間到底在何時較合理。司法實踐中,有的人認為公訴人提出量刑建議的訴訟時間越提前,辯護方量刑辯護的機會就越多,效果就越好,因此提議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就提出量刑建議,其具體的量刑意見既可以在書中進行具體表述,也可以以書面的形式在提起公訴時就隨卷移送到法院,辯護方就能盡早為被告人的量刑辯護做好充分的準備。筆者認為,量刑建議的具體時間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而靈活掌握。例如簡易程序的案件,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就可以在時以書面的形式提出,而對于普通程序的案件則完全可以在庭審辯論時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