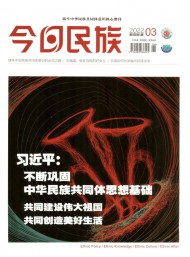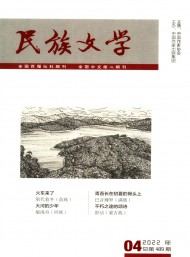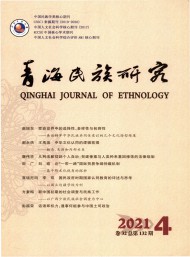民族政策論文范文
時間:2023-04-08 15:00:26
導(dǎo)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民族政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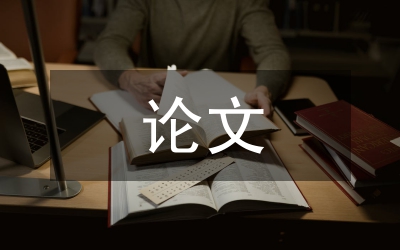
篇1
系統(tǒng)的外部條件:寧夏D鄉(xiāng)的基本狀況
(一)社會經(jīng)濟現(xiàn)狀
D鄉(xiāng)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qū)中部,曾處于沙漠地帶,飽受干旱和沙塵暴的侵擾,但地勢平坦且臨近黃河,因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成為自治區(qū)政府吊莊移民政策①的規(guī)劃地區(qū)。D鄉(xiāng)屬于回民區(qū),2008年總?cè)丝?2136人,回族占60%,計劃生育政策的松動和地區(qū)傳統(tǒng)重男輕女思想,導(dǎo)致單位家庭孩子數(shù)量相對較多。回族民眾篤信伊斯蘭教,全鄉(xiāng)各處佇立著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回漢文化多元并進。多年的經(jīng)濟整治使得砂質(zhì)土壤得到改良,再加上黃河灌溉和搬遷時統(tǒng)一規(guī)劃的水渠系統(tǒng)的使用,D鄉(xiāng)逐漸成為適宜種植和居住的地區(qū),以農(nóng)業(yè)為主,主要作物為玉米、小麥和經(jīng)濟作物枸杞,同時還有少量的畜牧與養(yǎng)殖。由于地理上的交通便利和臨近首府銀川、西安和蘭州等大城市,近年來進城務(wù)工的農(nóng)民越來越多,得益于現(xiàn)代化的趨勢和經(jīng)濟增長的拉動,D鄉(xiāng)近年經(jīng)濟進入快速發(fā)展時期,勞務(wù)需求和人工費的增加使得該地區(qū)農(nóng)民收入普遍增長。據(jù)當?shù)卣W(wǎng)站公布數(shù)據(jù)顯示,D鄉(xiāng)2009年有6000多人外出務(wù)工,勞務(wù)收入2800萬元,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的務(wù)工浪潮,給D鄉(xiāng)經(jīng)濟帶來了發(fā)展。
(二)義務(wù)教育政策的基本實施
在全國范圍內(nèi),《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wù)教育法》規(guī)定實行九年義務(wù)教育,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適齡兒童、少年,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家庭財產(chǎn)狀況、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義務(wù)教育的權(quán)利,并履行接受義務(wù)教育的義務(wù)。與此同時,D鄉(xiāng)作為少數(shù)民族自治地區(qū)的農(nóng)村教育,除法律規(guī)定的普遍性政策之外,還具有許多政策上的獨特之處。首先,致力于中西部地區(qū)的“兩基普九”。為貫徹推進西部大開發(fā),國家提出實現(xiàn)西部地區(qū)基本普及九年義務(wù)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目標的“兩基”計劃,少數(shù)民族教育成為“兩基”攻堅的難點。行走在D鄉(xiāng)的田間地頭,隨處可見基礎(chǔ)義務(wù)教育重點普及地區(qū)的標語,D鄉(xiāng)共有完小9所,遍布全鄉(xiāng)26個村莊,完中一所,基礎(chǔ)教育學(xué)校體系基本完善。其次,農(nóng)村義務(wù)教育的“兩免一補”。國家從2001年開始實施對農(nóng)村義務(wù)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xué)生就學(xué)實施兩免一補政策,即“免雜費、免書本費、逐步補助寄宿生生活費”,2006年又從西部地區(qū)開始全部免除農(nóng)村義務(wù)教育階段學(xué)生的學(xué)雜費。D鄉(xiāng)所有中小學(xué)生均享受了基本的兩免一補政策,學(xué)費書本費均由國家承擔,上學(xué)成本普遍不高,即便存在一定的日常開支,相對該地區(qū)近年來平均工資和人均收入而言也不算很多。再次,民族地區(qū)的教育政策傾斜。民族教育政策傾斜的支點則在民族基礎(chǔ)教育。[3]D鄉(xiāng)回族學(xué)生在入學(xué)升學(xué)方面均享有優(yōu)惠政策,以中考為例,回族學(xué)生可以有30分的加分政策,同時在入學(xué)和錄取上也享有優(yōu)先保障。日常生活中,政府的“雞蛋工程”讓所有學(xué)生每天可以得到一個雞蛋作為早餐。從2012年起,政府還啟動免費午餐的工程,而D鄉(xiāng)作為試點地區(qū)提前享受到這樣的補助機會。
系統(tǒng)的反常輸出:義務(wù)教育政策下D鄉(xiāng)的初中輟學(xué)現(xiàn)象
無論是國家整體推行的教育政策,還是落實到民族農(nóng)村地區(qū)的具體政策傾斜,其基本出發(fā)點都意在維持所有“適齡兒童接受教育”這一基本目標,而當既定政策目標群體的學(xué)生出現(xiàn)流失之時,政策本身也就出現(xiàn)了失靈。目前全國范圍內(nèi)普遍存在的農(nóng)村學(xué)生輟學(xué)現(xiàn)象就是這種教育政策失靈的體現(xiàn),而寧夏D鄉(xiāng)則尤為明顯。以全鄉(xiāng)唯一的D鄉(xiāng)中學(xué)為例,學(xué)校共設(shè)有七八九三個年級,2010年的在校學(xué)生人數(shù)為2400人,根據(jù)筆者對2010年新入學(xué)的七年級其中一個班級為期一年的跟蹤觀察顯示,從2010年9月入學(xué)時全班人數(shù)63人,到2011年6月學(xué)年結(jié)束之時全班人數(shù)51人,一年期間輟學(xué)人數(shù)達到12人,其中男生9人,女生3人,漢族2人,回族10人,男生占總輟學(xué)人數(shù)的比例為75%,回族占總輟學(xué)人數(shù)比例為83%。同樣的現(xiàn)象反映在學(xué)校2010年入學(xué)時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中,如表1所示:首先,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入學(xué)成本的降低,D鄉(xiāng)中學(xué)尚處在義務(wù)教育政策階段的初中生卻出現(xiàn)了輟學(xué)人數(shù)逐漸增多的反常趨勢,并且此增長一方面是輟學(xué)人數(shù)的絕對數(shù)字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從低年級到高年級,伴隨著年齡的增長輟學(xué)人數(shù)也增加。八年級和九年級的輟學(xué)率分別達到17.4%和25.5%,這一指標遠高于同期其他省份輟學(xué)率,也遠高于國家“兩基普九”規(guī)定的3%的輟學(xué)率警戒線。其次,盡管存有地區(qū)落后觀念和家長的影響,但多數(shù)學(xué)生輟學(xué)屬于主動輟學(xué)。輟學(xué)生離開學(xué)校,與家庭經(jīng)濟負擔沒有直接關(guān)系。[4]在同期進行的對家長和學(xué)生輟學(xué)的訪談記錄顯示,有73%的學(xué)生認為其輟學(xué)是自己的決定,且71%的家長對學(xué)生輟學(xué)持堅決反對態(tài)度,可見地區(qū)觀念和家長作用對學(xué)生輟學(xué)即使起到間接影響但也沒有決定作用。在經(jīng)濟困難時期,農(nóng)村青少年更多的是因為貧困而輟學(xué),是被迫輟學(xué);反之在經(jīng)濟發(fā)展時期,更多是因為眼前的社會經(jīng)濟利益而輟學(xué),是主動輟學(xué)。[5]調(diào)查中還發(fā)現(xiàn),民族基礎(chǔ)教育的政策傾斜并沒有減少回族學(xué)生輟學(xué)的可能,相反回族學(xué)生輟學(xué)率遠高于漢族,八年級輟學(xué)人數(shù)中回族135人,占88.2%,而在九年級輟學(xué)人數(shù)中回族占72%。在回族和漢族都具有的重男輕女思想的農(nóng)村地區(qū),以往女生為主的輟學(xué)現(xiàn)象被男生輟學(xué)人數(shù)遠多于女生的現(xiàn)象所取代,八年級輟學(xué)人數(shù)中女生只占36.6%,而相反男生輟學(xué)人數(shù)達到97人,占63.4%;九年級中輟學(xué)男生則占輟學(xué)總?cè)藬?shù)的52.7%。
系統(tǒng)輸入:對D鄉(xiāng)輟學(xué)學(xué)生和教育資源的考察
(一)要求輸入———學(xué)生的輟學(xué)邏輯
在嘗試辨析影響學(xué)生做出輟學(xué)決定的因素時,單靠分析訪談學(xué)生自身提出的輟學(xué)原因是不夠的,為減少這種主觀性的偏差,筆者通過學(xué)生提出的輟學(xué)原因和實際輟學(xué)去向兩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來分析,有33%的學(xué)生認為是學(xué)習(xí)困難導(dǎo)致信心喪失,無法繼續(xù)念書;30%的學(xué)生認為讀書無用是自己輟學(xué)的原因;26%的學(xué)生認為家庭困難是自己輟學(xué)原因;還有小部分因為身體等客觀原因而輟學(xué)。而輟學(xué)后去向,其中有56%的同學(xué)外出打工,22%的同學(xué)在家打工,6%的同學(xué)去清真寺念經(jīng),還有小部分同學(xué)結(jié)婚。在這兩組數(shù)據(jù)中可以看出學(xué)生輟學(xué)的隱性邏輯:學(xué)習(xí)困難容易導(dǎo)致普遍的厭學(xué)情緒,并且在朋輩交流和信息媒介的發(fā)展下得到傳播,而這種信息傳播和流動機會的增加助長了學(xué)生經(jīng)濟社會參與行為,在D鄉(xiāng)主要表現(xiàn)為學(xué)生周末常常跟隨父母進城打工,枸杞收獲的時節(jié),平均兩元錢一小時的人工費也使得大量的學(xué)生課余打工,更有甚者逃課曠課去打工掙錢,由于往來交通方便,許多學(xué)生出走銀川、蘭州等大城市,脫離校園走向社會。
(二)支持輸入———基層教育資源的缺乏
首先,經(jīng)費投入的不足。教育事業(yè)賴以發(fā)展的基礎(chǔ)是經(jīng)費投入,[6]經(jīng)費作為義務(wù)教育政策系統(tǒng)的支持性輸入,在我們這個窮國辦大教育,教育事業(yè)適度超前發(fā)展與教育投入不足的矛盾將長期存在,甘肅和江蘇的校車事件可見一斑。寧夏D鄉(xiāng)雖已基本建立遍布全鄉(xiāng)的小學(xué)體系,但在筆者走訪了解過程中,無論是學(xué)校建設(shè)還是教師工資都存在嚴重的資金缺乏,雖然國家普及的兩免一補和地方性的“雞蛋工程”和“免費午餐”體現(xiàn)出國家在教育經(jīng)費上的大力支持,但此種支持遠遠無法支撐完善農(nóng)村義務(wù)教育所需的開支,且還要考慮過程中可能有的教育腐敗和資源浪費現(xiàn)象,由中央層面下放的教育投入,經(jīng)由一級級政府機關(guān)的層次扣減,到最后留給基層部門可利用的資金非常有限,而作為這個體系當中最底層的學(xué)校和教師,可利用的資源更是少得可憐。其次,師資力量的缺乏。資金不足往往伴隨著師資缺乏,年輕教師流失的原因大多都是出于經(jīng)濟考慮,而這種師資不足又導(dǎo)致教師教學(xué)任務(wù)沉重。2010年D鄉(xiāng)中學(xué)有學(xué)生2400人,40多個教學(xué)班,并且這個數(shù)字會隨著吊莊移民地區(qū)搬遷人數(shù)的增加和人口出生率的居高不下而逐年遞增,而學(xué)校的教職工人數(shù)卻只有142人,除去后勤部門外,能擔任教學(xué)任務(wù)的教師不足百人,因而在教學(xué)任務(wù)上,平均每一專任教師負擔學(xué)生數(shù)為20~30人,遠遠高于2009年寧夏平均16人的水平。[7]此外教師流動和流失頻繁。一方面由于學(xué)校缺乏教師,因而許多從縣城和其他地區(qū)“借”來的支教老師和交流老師都擔任了主課教學(xué)任務(wù),這些臨時性老師經(jīng)常性的交換流動使得教學(xué)工作存在斷裂,對學(xué)生學(xué)習(xí)及心理成長產(chǎn)生消極作用。另一方面業(yè)已入職的年輕教師存在大量流失,無論是考取公務(wù)員還是研究生,抑或是到更好的縣城和市區(qū)求職,在導(dǎo)致師資力量不足現(xiàn)象更嚴峻的同時,也給學(xué)生們帶來不良的示范影響。
(三)隱性輸入———現(xiàn)代化與經(jīng)濟發(fā)展
從教育經(jīng)濟學(xué)角度分析,農(nóng)民將教育看作一種投資,這種投資可為接受教育的人帶來貨幣收益(如未來較高的工資),因而在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之間的權(quán)衡成為學(xué)生是否輟學(xué)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伴隨著經(jīng)濟發(fā)展和教育普及,教育的資本價值大大降低,讀書不再成為出人頭地前途似錦的唯一方式,世代經(jīng)學(xué)的傳統(tǒng)不再具有政治和經(jīng)濟的現(xiàn)實意義,如今人們更愿意認為“遺子一經(jīng),不如黃金滿籯”。現(xiàn)代化還打破了傳統(tǒng)的倫理格調(diào)和社會觀念,民眾對現(xiàn)實利益的追逐興趣遠勝于教育精神,當外出打工的流行和務(wù)工人員普遍收入增長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時,近在眼前的經(jīng)濟利益顯然比作為長期投資且存有風(fēng)險的教育更具有吸引力。此外農(nóng)村人口具有很強的同質(zhì)性,大家都沿著相同的軌跡生活,教育改變生活的示范和刺激效應(yīng)短期難以實現(xiàn),相反打工掙錢帶來的現(xiàn)實收益和示范刺激效應(yīng)卻很快對學(xué)生和家長產(chǎn)生影響。
政策執(zhí)行系統(tǒng):D鄉(xiāng)義務(wù)教育政策執(zhí)行分析
即使存在著學(xué)生厭學(xué)情緒和讀書無用論,以及教育資金和教師資源的不足和經(jīng)濟因素等影響因素,義務(wù)教育政策都有關(guān)于普及義務(wù)教育和抑制失學(xué)的預(yù)防措施,而原本可作為防止學(xué)生輟學(xué)的最后一道關(guān)卡的政策執(zhí)行在最后關(guān)頭失去作用,導(dǎo)致寧夏D鄉(xiāng)大量輟學(xué)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在實現(xiàn)政策目標的過程中,方案確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決于有效的執(zhí)行”。義務(wù)教育政策的形式內(nèi)容、適用狀況和社會理解程度,執(zhí)行機構(gòu)的具體執(zhí)行和目標群體的接受程度,以及文化社會環(huán)境等都是影響義務(wù)教育在D鄉(xiāng)成敗的考慮因素,如圖2。
(一)理想化政策:義務(wù)教育政策失靈
九年義務(wù)教育政策在國內(nèi)實施以來,曾經(jīng)取得了長期而廣泛的成就,建國初的1949年全國學(xué)齡人口入學(xué)率僅為20%,其中文盲達80%以上,到2000年,全國總?cè)丝诘?5%實現(xiàn)了義務(wù)教育,初中階段入學(xué)率達到85%,小學(xué)入學(xué)率達到99%。[8]然而任何政策,決不能有利而無弊,也不能歷久而不變。教育系統(tǒng)在D鄉(xiāng)的失靈源于理想化的政策與時代的脫節(jié),時代在變,相應(yīng)的政策和制度理應(yīng)隨之變化。
(二)目標群體:學(xué)生和家長教育認知
公共政策制定以后,如果政策目標群體不能正確理解公共政策的內(nèi)涵、基本原則及其制定政策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或者公共政策理解發(fā)生偏差,則可能使公共政策執(zhí)行行動發(fā)生偏差。[9]學(xué)生和高文盲率的家長對教育認知矛盾構(gòu)成了對政策理解的搖擺,在諸如D鄉(xiāng)這樣的偏遠的農(nóng)村地區(qū),一方面,厭學(xué)情緒的產(chǎn)生和“讀書無用論”在學(xué)生和家長中間的滋長流行導(dǎo)致對教育的質(zhì)疑進一步加深,另一方面,“教育”價值依然受到傳統(tǒng)的深刻影響,舊有的經(jīng)學(xué)致用風(fēng)氣的傳承導(dǎo)致學(xué)生和家長對教育的理解產(chǎn)生矛盾和沖突,而這種情況下,教育的功利性出路和國家的資金支持就成為影響的重要變量。義務(wù)教育政策的失靈伴隨的輟學(xué)現(xiàn)象客觀上是由于利益刺激下學(xué)生的經(jīng)濟參與行為,而這種利益刺激,一方面來源于輟學(xué)帶來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來源于教育資源不足帶來的間接損失。
(三)作為執(zhí)行機構(gòu)的政府部門和學(xué)校的偏差
一方面學(xué)校在政策執(zhí)行中出現(xiàn)問題和失范。九年義務(wù)教育鞏固率指標是國家“十二五”規(guī)劃新增的一項指標,即一個學(xué)校入學(xué)人數(shù)與畢業(yè)人數(shù)的百分比,這是義務(wù)教育政策中為了保障輟學(xué)控制而設(shè)置的一個特殊指標,而在D鄉(xiāng)中學(xué)它更多地成為一個象征性的指標,使得它在控制減少輟學(xué)的作用上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吊莊移民地區(qū)的特殊入學(xué)政策導(dǎo)致“高齡學(xué)生”眾多。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該地區(qū)學(xué)生相較于全國其他地區(qū)而言年齡普遍偏高,存在大量高年齡低年級的個體案例,有70%的學(xué)生在吊莊移民搬遷至大戰(zhàn)場后留級一到兩年,而這種留級不是根據(jù)其實際知識學(xué)習(xí)狀況,而是當?shù)匦W(xué)統(tǒng)一實行的留級政策,更有3%的學(xué)生從一年級重新讀起,這種入學(xué)方式使得后來升入中學(xué)的很多學(xué)生普遍年齡偏高,甚至已經(jīng)成年但仍未初中畢業(yè)的學(xué)生大量存在,這些“高齡”初中生成為輟學(xué)的主力軍。再者,當?shù)叵嚓P(guān)機構(gòu)在義務(wù)教育政策執(zhí)行中存在造假和腐敗行為。2005年中央黨校經(jīng)濟部的潘云良教授對全國十六個省市的義務(wù)教育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兩基”達標數(shù)據(jù)造假現(xiàn)象嚴重,地方政府通過編造假數(shù)據(jù)來蒙混過關(guān),由于“兩基”已成為政績考核的一個標準,與人事晉升直接相關(guān),甚至出現(xiàn)了“‘兩基’不過關(guān),鄉(xiāng)鎮(zhèn)干部一鍋端”的說法。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尚且如此,更何況社會經(jīng)濟尚在起步的D鄉(xiāng),“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用民族地區(qū)自主的“自由裁量權(quán)”解釋政策以為自己謀私利,背離了原有政策的精神。另一方面有關(guān)部門巧立名目,利用各種名義收取費用,給學(xué)生和家長帶來惡性印象。與此同時還缺乏獨立、多元和有效的監(jiān)督評估,都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D鄉(xiāng)的學(xué)生輟學(xué)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