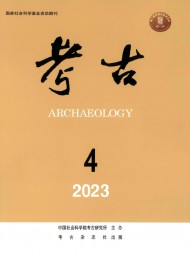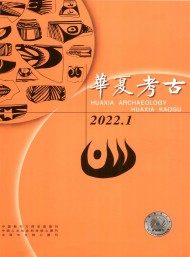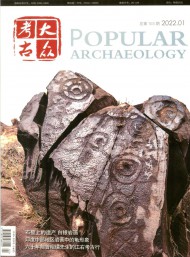考古學(xué)理論方法與實(shí)踐范文
時(shí)間:2023-10-18 17:38:19
導(dǎo)語(yǔ):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考古學(xué)理論方法與實(shí)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xiàn),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我國(guó)東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馬橋文化等,都是這一時(shí)期命名的,正是在這樣的形勢(shì)下,蘇秉琦先生根據(jù)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提出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系、類型”理論,對(duì)于我國(guó)考古學(xué)向縱深發(fā)展,無(wú)疑具有積極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和長(zhǎng)遠(yuǎn)的戰(zhàn)略意義;對(duì)于我國(guó)新石器時(shí)代的考古學(xué)研究,無(wú)疑發(fā)揮著重要的指導(dǎo)作用。“區(qū)、系、類型”理論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據(jù)“區(qū)、系、類型”理論,蘇秉琦先生將我國(guó)群星璀璨的考古學(xué)文化歸納為六大區(qū),“區(qū)、系、類型”中的“區(qū)”不僅空間大于考古學(xué)文化區(qū),而且“區(qū)、系、類型”中“區(qū)”的層次也高于考古學(xué)文化區(qū)。蘇秉琦先生從全新的高度將“考古學(xué)文化區(qū)”的概念上升為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系、類型”的“區(qū)”,不僅為考古學(xué)建立了更加廣闊的時(shí)空框架,也為宏觀地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進(jìn)行動(dòng)態(tài)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蘇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學(xué)文化的考古學(xué)“區(qū)、系、類型”理論的同時(shí),還提出中國(guó)文明起源的“多元一體”模式、從“古文化、古城、古國(guó)”的觀點(diǎn)到“古國(guó)、方國(guó)、帝國(guó)”的理論和“原生型、次生型、續(xù)生型”為國(guó)家形成的三種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論,因此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qū)、系、類型”理論實(shí)際上已成為通過(guò)考古學(xué)方法研究和探討中國(guó)文明起源的理論基礎(chǔ)③。考古學(xué)理論來(lái)源于考古學(xué)實(shí)踐,考古學(xué)理論應(yīng)對(duì)學(xué)科研究具有實(shí)際的指導(dǎo)意義。
三十年過(guò)去了,當(dāng)年蘇秉琦先生基于現(xiàn)有資料對(duì)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學(xué)文化區(qū)、系、類型理論的探索雖具有前瞻性,然這一理論在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學(xué)的實(shí)踐中也日漸顯現(xiàn)出理論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而出現(xiàn)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學(xué)文化“區(qū)、系、類型”理論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確。“區(qū)、系、類型”理論中出現(xiàn)了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考古學(xué)文化的“系”和考古學(xué)文化的“類型”,蘇秉琦先生對(duì)“區(qū)、系、類型”的定義如下:“在準(zhǔn)確劃分文化類型的基礎(chǔ)上,在較大的區(qū)域內(nèi)以其文化內(nèi)涵的異同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tǒng)。這里,區(qū)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系、類型”與原有的“考古學(xué)文化”、“考古學(xué)文化類型”等考古學(xué)專業(yè)名詞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義不同。根據(jù)蘇秉琦先生的定義,“區(qū)、系、類型”中的“區(qū)是塊塊”,屬于空間范疇;而考古學(xué)文化區(qū)也同樣屬于空間范疇。在蘇秉琦先生劃分的六大區(qū)系中,“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qū)”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qū),即海岱地區(qū);盡管蘇秉琦先生認(rèn)為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學(xué)文化屬另一個(gè)文化系統(tǒng),實(shí)際上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學(xué)文化可歸屬海岱地區(qū)的一個(gè)亞區(qū)。而“長(zhǎng)江下游地區(qū)”則包含了太湖地區(qū)的“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寧鎮(zhèn)地區(qū)的“北陰陽(yáng)營(yíng)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學(xué)文化。
根據(jù)蘇秉琦先生的劃分,“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qū)”大致相當(dāng)于“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qū);而長(zhǎng)江下游地區(qū)卻包含著“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陰陽(yáng)營(yíng)文化”和“薛家崗文化”的分布區(qū)。因此“區(qū)、系、類型”的“區(qū)”似乎既可等同于一個(gè)考古學(xué)文化區(qū),又可包含若干個(gè)考古學(xué)文化區(qū)。此外,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系、類型”的“區(qū)”,或以省命名,如“陜甘晉”“、山東”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長(zhǎng)江下游”“、南方地區(qū)”和“北方地區(qū)”等。考古學(xué)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學(xué)的基本標(biāo)準(zhǔn)④,而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系、類型”中“區(qū)”的命名,既無(wú)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又無(wú)規(guī)律可尋。“區(qū)、系、類型”中的“系是條條”,顯然屬于時(shí)間范疇;而考古學(xué)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發(fā)展演進(jìn)也同樣屬于時(shí)間范疇。根據(jù)蘇秉琦先生對(duì)大汶口文化發(fā)展演進(jìn)為龍山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發(fā)展演進(jìn)為良渚文化的論述,“區(qū)、系、類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發(fā)展演進(jìn)而不包括考古學(xué)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學(xué)文化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文化分期屬于量變,而文化的發(fā)展演進(jìn)則屬于質(zhì)變,質(zhì)變是由量變的積累而發(fā)生的突變。因此,“區(qū)、系、類型”中的“系”與文化分期、文化演進(jìn)的相互關(guān)系的區(qū)分,“系”的時(shí)間概念與文化分期和文化演進(jìn)的時(shí)間概念的區(qū)分,顯然存在著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在同一考古學(xué)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圍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異,往往又分為若干類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秦王寨類型”、“大司空村類型”和“西王村類型”等,而龍山文化則有“城子崖類型”和“兩城鎮(zhèn)類型”等。在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qū)、系、類型”中,“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區(qū)、系、類型”中的“類型”與考古學(xué)文化的類型有著不同的概念。
“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與分支也同樣存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綜上所述,“區(qū)、系、類型”的“區(qū)”不等同于考古學(xué)文化區(qū)的“區(qū)”“,區(qū)、系、類型”的“類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學(xué)文化類型”。考古學(xué)理論既須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為理論基礎(chǔ),又須符合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一個(gè)學(xué)科中用同樣文字的專業(yè)名詞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著不同的定義,似乎有悖于形式邏輯的基本規(guī)律———同一律。考古學(xué)理論應(yīng)具有普遍性,應(yīng)適用于不同時(shí)期的考古學(xué)研究。“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如僅適用于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學(xué),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區(qū)系的劃分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區(qū)。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蘇秉琦先生在“區(qū)、系、類型”中劃分的六大區(qū)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學(xué)文化空白區(qū)的情況下劃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區(qū)與下游地區(qū)。因此六大區(qū)系的劃分出現(xiàn)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東部和江淮中部地區(qū)在當(dāng)時(shí)還是考古學(xué)文化的空白區(qū),還沒(méi)有龍虬莊、侯家寨、凌家灘、雙墩等遺址的發(fā)掘,還沒(méi)有龍虬莊文化、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據(jù)對(duì)古史傳說(shuō)的研究,劃分了華夏、東夷和苗蠻民族集團(tuán)的空間分布范圍。其中將渤海灣以西到錢塘江以北劃為東夷民族的分布空間⑤(圖一)。而蘇秉琦先生將我國(guó)東部沿海劃分為“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qū)”和“長(zhǎng)江下游地區(qū)”,顯然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區(qū),顯然強(qiáng)調(diào)了我國(guó)東部沿海地區(qū)新石器時(shí)代考古學(xué)文化的考古學(xué)屬性而忽略了區(qū)系劃分的民族學(xué)屬性。“‘考古學(xué)文化’是代表同一時(shí)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內(nèi)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遺跡和遺物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應(yīng)該屬于某一特定的社會(huì)集團(tuán)的。由于這個(gè)社會(huì)集團(tuán)有著共同的傳統(tǒng),所以在它的遺跡和遺物上存在著這樣的共同性。
篇2
一、手工繪圖依舊是取得考古現(xiàn)場(chǎng)第一手資料的基本方法
我國(guó)20至21世紀(jì)的考古工作與考古學(xué)研究的結(jié)果表明,迄今為止,我國(guó)考古繪圖主要依賴手工完成。不僅貫穿于考古發(fā)掘的全過(guò)程,也是當(dāng)代考古學(xué)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依據(jù)。
從我國(guó)考古學(xué)建立之初,傳統(tǒng)手工繪圖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內(nèi)容,不僅在攝影技術(shù)不發(fā)達(dá)的時(shí)期,全部考古圖錄主要靠專業(yè)工作者手繪完成:“要親自動(dòng)手,文物一旦露頭,……必須完成當(dāng)天的考古記錄”,即使在考古學(xué)高度發(fā)展的今天,考古繪圖工作已經(jīng)加入了新的技術(shù)因素,大量在現(xiàn)場(chǎng)依照實(shí)況和器物實(shí)體手工繪出的圖紙,作為現(xiàn)場(chǎng)采集的第一手資料,其價(jià)值是臨摹、修改、復(fù)制、打印等后續(xù)而成的二手資料所不能比擬的。
在攝像與電子技術(shù)高度應(yīng)用于考古學(xué)領(lǐng)域的今天,人工對(duì)遺址現(xiàn)場(chǎng)的全景、地層、地形、遺跡及其分布的實(shí)測(cè)與繪圖,仍是保留現(xiàn)場(chǎng)信息的必要步驟,方格網(wǎng)等方法依舊被作為最基本的測(cè)量和繪圖方式在實(shí)際工作中使用,以保留考古遺址和器物的原貌。現(xiàn)場(chǎng)示意圖、剖面圖是考古遺址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驟。以河南焦作府城遺址發(fā)掘?yàn)槔龅拇罅繉?duì)遺跡的結(jié)構(gòu)、分布、地層堆積、坑底細(xì)部情況繪制的平剖面圖不僅是對(duì)現(xiàn)場(chǎng)的第一手記錄,也是后續(xù)分析研究工作的基礎(chǔ),特別是對(duì)結(jié)構(gòu)復(fù)雜的各墓葬、窯址等清晰的繪圖,是動(dòng)態(tài)發(fā)掘過(guò)程中不可遺漏的重要證據(jù)。對(duì)其深淺層位進(jìn)行精確的測(cè)繪,明確遺物的出土位置、疊壓關(guān)系,對(duì)后期墓葬主人身份的辨析考證,具有極重要的證明意義。
即使在一些特殊的考古場(chǎng)合,現(xiàn)場(chǎng)繪圖也是必不可少的,手工繪圖不斷運(yùn)用于考古新領(lǐng)域。2010年“南澳I號(hào)”的沉船船體和文物發(fā)掘中,繪圖工作是在水下數(shù)十米深處與現(xiàn)場(chǎng)發(fā)掘同步進(jìn)行,現(xiàn)場(chǎng)對(duì)考察“南澳I號(hào)”復(fù)雜的遺址堆積狀況的記錄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學(xué)界揭示南澳島水下的遺址群的概貌、探討南澳島作為海上古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地重要意義的關(guān)鍵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種原因,傳統(tǒng)考古繪圖方式被忽略、被扭曲的現(xiàn)象時(shí)有發(fā)生。隨著大規(guī)模建設(shè)的展開(kāi),少數(shù)匆忙開(kāi)發(fā)的遺址,由于缺乏專業(yè)繪圖理念,未能遵循正確的繪圖原則,往往造成第一手繪圖資料的缺失。如某些遺址的發(fā)掘,由于忽略了現(xiàn)場(chǎng)繪圖記錄,不僅缺乏寶貴的現(xiàn)場(chǎng)記錄資料,也為后續(xù)的疊壓關(guān)系研究、器物鑒定、排序與研究造成困難。
繪圖軟件的大量應(yīng)用,一方面帶來(lái)繪圖工作的便捷和細(xì)致,另一方面也使人產(chǎn)生誤解,認(rèn)為即便沒(méi)有繪畫能力,各種軟件也可以取代人工,完成繪圖工作。這導(dǎo)致傳統(tǒng)繪圖方法被忽略,手工繪圖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很多本應(yīng)由專門人員完成的原始資料圖由技術(shù)工人,將繪圖視為現(xiàn)場(chǎng)的簡(jiǎn)單記錄。
問(wèn)題的出現(xiàn)是考古工作中對(duì)繪圖工作的理解出現(xiàn)誤差。事實(shí)上,考古繪圖并不是單純圖錄備用,而是將現(xiàn)場(chǎng)復(fù)雜信息整理、篩選和保存的過(guò)程。特別是對(duì)地下遺物多、疊壓打破關(guān)系復(fù)雜的遺址,準(zhǔn)確保留第一現(xiàn)場(chǎng)的必要信息,將疊壓的復(fù)雜關(guān)系正確傳遞給后續(xù)研究,沒(méi)有相應(yīng)的專業(yè)知識(shí)是無(wú)法完成的。
我國(guó)長(zhǎng)期考古工作的經(jīng)驗(yàn)表明,傳統(tǒng)手工繪圖無(wú)法取代。它不僅貫穿于20世紀(jì)近百年的中國(guó)考古,并且會(huì)在21世紀(jì)的考古發(fā)掘中繼續(xù)發(fā)揮重要作用。
二、考古繪圖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國(guó)考古事業(yè)的不斷發(fā)展,使考古繪圖有著廣闊的發(fā)展領(lǐng)域。在承擔(dān)野外調(diào)查、現(xiàn)場(chǎng)發(fā)掘任務(wù)之外,考古繪圖貫穿于器物整理、考古報(bào)告、現(xiàn)場(chǎng)復(fù)原全過(guò)程,并且正在不斷深入影響考古學(xué)研究。
在后期的器物整理、遺址報(bào)告中,作為三大要素之一,繪圖也承擔(dān)著極其重要的任務(wù),是梳理和陳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段。幾乎所有的考古學(xué)報(bào)告,都要配以大量的圖錄,闡述考古過(guò)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發(fā)掘特征,提出新的觀點(diǎn)。武漢考古所等為盤龍城宋窯與商墓遺跡所做的大量清晰繪圖,清晰地表明了黃陂盤龍復(fù)雜的多層文化,為學(xué)界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最明了的答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石市博物館在《湖北大冶蟹子地遺址2009年發(fā)掘報(bào)告》的附圖包括遺址示意圖、探方圖、地層堆積剖面圖、各個(gè)時(shí)期的器物圖、紋飾圖等數(shù)百幅。而記錄600座楚墓,反映東周文化的考古報(bào)告《江陵九店?yáng)|周墓》,正是其圖繪工作的疏忽草率,而受到學(xué)界的批評(píng)。
器物的修復(fù)整理,往往需要對(duì)原物預(yù)先繪圖,特別是對(duì)彩繪器物的修復(fù),必須首先采集和保留原物信息。其中包括“詳細(xì)記錄描述器物各個(gè)部位的彩繪顏色、范圍和保存狀況”,“采用多種顏色進(jìn)行繪制,詳細(xì)記錄描述每層彩繪相互之間的關(guān)系”等。在對(duì)秦俑一號(hào)坑新發(fā)現(xiàn)的斷裂數(shù)塊的彩繪陶俑進(jìn)行搶救性處理前進(jìn)行的保存原樣的繪圖,就是修復(fù)器物的規(guī)范做法。
圖文并茂是考古學(xué)者深入研究的基本方法。蘇秉琦以北首嶺出土雙唇口、壺罐形口與姜寨壺罐形口的比較圖提出關(guān)于仰韶文化分期的重要論點(diǎn),劉慶柱《中國(guó)古代都城考古學(xué)述論》,以數(shù)十幅歷代城池遺址圖、地形圖論述中國(guó)都城考古的發(fā)展成就,都顯示了我國(guó)考古學(xué)家圖文并長(zhǎng)的研究功力。
篇3
山東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fā)現(xiàn),如今經(jīng)過(guò)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東地區(qū)的考古學(xué)文化譜系已經(jīng)基本建立,為深化這一區(qū)域的考古學(xué)研究創(chuàng)造了條件。伴隨著山東地區(qū)考古發(fā)掘工作的開(kāi)展,該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jìn)展。山東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統(tǒng)的研究則始于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吳詩(shī)池概述了山東新石器時(shí)代農(nóng)業(yè)考古發(fā)展情況(2),隨后又系統(tǒng)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區(qū)的史前農(nóng)業(yè)狀況(3)。隨著考古發(fā)掘資料的不斷增多,吳詩(shī)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對(duì)山東地區(qū)出土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資料進(jìn)行了綜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關(guān)于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在整體分析的基礎(chǔ)上,出現(xiàn)了一些區(qū)域性的系統(tǒng)研究,如石敬東利用出土文物資料研究了棗莊地區(qū)的史前農(nóng)業(yè)(5);房道國(guó)概述了濟(jì)南地區(qū)古代農(nóng)業(yè)考古發(fā)展情況(6)。同時(shí),這一時(shí)期的單個(gè)文化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的研究得到了發(fā)展,有學(xué)者在系統(tǒng)梳理海岱龍山文化生產(chǎn)工具資料的基礎(chǔ)上,對(duì)海岱地區(qū)龍山文化的生產(chǎn)工具進(jìn)行了類型學(xué)的考察,并進(jìn)而對(duì)區(qū)域間的生產(chǎn)方式的差異進(jìn)行了解釋(7)。另外,還有學(xué)者綜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農(nóng)具,認(rèn)為岳石文化的農(nóng)具較之龍山文化農(nóng)具有了很大的進(jìn)步,而不是像一些學(xué)者所認(rèn)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則散見(jiàn)于各類有關(guān)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進(jìn)入二十一世紀(jì),山東地區(qū)的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的文章鮮見(jiàn)于各類刊物之上,綜合系統(tǒng)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區(qū)域性的個(gè)案研究成果則未見(jiàn)發(fā)表。
從以上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研究的發(fā)展?fàn)顩r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綜合整體敘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個(gè)案研究,尤其是生產(chǎn)工具的個(gè)案研究。區(qū)域性的農(nóng)業(yè)研究雖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領(lǐng)域還有待擴(kuò)展。總之,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基礎(chǔ)比較薄弱,方法還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緊迫性較之其他領(lǐng)域更為突出。
二
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雖取得了一定的進(jìn)展,但是存在的幾個(gè)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這一研究領(lǐng)域的發(fā)展。這些問(wèn)題既有資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資料方面,目前山東地區(qū)史前考古發(fā)掘資料中,多數(shù)側(cè)重于陶器的統(tǒng)計(jì)分析,對(duì)石器基本上是粗線條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調(diào)查資料中,鮮有對(duì)石器的全面系統(tǒng)描述(指文字、線圖、尺寸描述齊全者)。資料的不足在發(fā)掘器物的數(shù)量上體現(xiàn)的十分明顯,例如山東龍山文化發(fā)表的資料中陶器數(shù)以萬(wàn)計(jì),而石器僅有幾千件,這種數(shù)量上的巨大差距說(shuō)明了學(xué)者們以往對(duì)石器的重視程度不夠。當(dāng)然,這可能是時(shí)代的原因造成的,因?yàn)檫^(guò)去學(xué)者們偏重于對(duì)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譜系的建立,而在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優(yōu)越性。另外,山東地區(qū)史前考古資料還缺少植物、動(dòng)物鑒定的資料,雖然發(fā)表的考古發(fā)掘報(bào)告和簡(jiǎn)報(bào)中有些這方面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綜合系統(tǒng)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東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過(guò)去多從生產(chǎn)工具入手來(lái)研究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fàn)顩r。這種方法上的單一化,不利于揭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發(fā)展的本質(zhì)。在一些具體的研究上則存在以下幾個(gè)主要問(wèn)題:偏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gè)案深入研究;側(cè)重農(nóng)業(yè)發(fā)展史的研究,缺乏農(nóng)業(yè)發(fā)展動(dòng)因的合理解釋;農(nóng)業(yè)起源研究略顯不足。
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存在上述問(wèn)題,資料豐富程度不足是一個(gè)原因,而要深入研究這些問(wèn)題,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關(guān)鍵。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是一項(xiàng)綜合的系統(tǒng)研究,多種方法的整體運(yùn)用是必然趨勢(shì)。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沒(méi)有文獻(xiàn)資料可供參考,只能采用考古學(xué)資料進(jìn)行分析。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以來(lái),新考古學(xué)的理論不斷傳入,為綜合系統(tǒng)分析提供了有利條件。如今,考古學(xué)研究領(lǐng)域中正呈現(xiàn)"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tǒng)化、技術(shù)國(guó)際化"的趨勢(shì),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國(guó)外一些先進(jìn)的技術(shù)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資料獲取程度,同時(shí)也相應(yīng)地?cái)U(kuò)展了研究的領(lǐng)域。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應(yīng)該以此為契機(jī),豐富自己的研究理論,改進(jìn)技術(shù)方法。這其中民族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數(shù)學(xué)統(tǒng)計(jì)分析的方法尤為重要、民族學(xué)中有關(guān)原始民族以及現(xiàn)代晚進(jìn)民族的資料是進(jìn)行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的"活化石",這些資料可以為史前農(nóng)業(yè)研究提供參考;經(jīng)濟(jì)學(xué)中有關(guān)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研究的原理,對(duì)史前農(nóng)業(yè)發(fā)展進(jìn)程的分析具有借鑒意義;數(shù)學(xué)中統(tǒng)計(jì)方法對(duì)史前農(nóng)業(yè)進(jìn)行量化研究可以發(fā)揮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講,過(guò)去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注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gè)案深入研究,而個(gè)案深入研究中一個(gè)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體敘述分析可以從整體上把握史前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進(jìn)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個(gè)時(shí)期的農(nóng)業(yè)狀況則必須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yàn)榱炕治瞿軌蚋宄亓私飧鞣N因素的比例關(guān)系,發(fā)現(xiàn)隱藏于實(shí)物資料背后的深層次動(dòng)因。例如,我們過(guò)去將目光過(guò)多地集中于生產(chǎn)工具的發(fā)展變化上,從生產(chǎn)工具的變化角度尋找社會(huì)變化發(fā)展的原因,但是近年來(lái)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屬生產(chǎn)工具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并未發(fā)揮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農(nóng)具不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從量化的角度來(lái)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一點(diǎn)。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不僅要復(fù)原古代農(nóng)業(yè)發(fā)展史,還要對(duì)此進(jìn)行解釋。既然農(nóng)具不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應(yīng)該找到另外的"指示器"。從山東地區(qū)史前遺址的發(fā)現(xiàn)情況能夠大致看出這方面的因素。山東地區(qū)史前文化譜系比較清楚,從早到晚依次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遺址數(shù)量中,后李文化為10余處,北辛文化100余處,大汶口文化500余處,龍山文化1300余處,岳石文化近300處。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還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shí)期磨制石器已占絕大多數(shù)。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沒(méi)有質(zhì)的變化的情況下,社會(huì)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東龍山文化時(shí)期遺址達(dá)1300余處,表明此時(shí)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釋這一現(xiàn)象還需聯(lián)系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發(fā)展情況。龍山文化時(shí)期社會(huì)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現(xiàn)、等級(jí)分化加劇,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從中國(guó)的歷史實(shí)際進(jìn)行分析。從綜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壇的建筑可以獲知社會(huì)組織管理職能的加強(qiáng)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種管理職能也會(huì)反映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分工協(xié)作上,從而提高了生產(chǎn)效率,擴(kuò)大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另外,農(nóng)作物栽培技術(shù)的改善也會(huì)相應(yīng)的增加產(chǎn)量,促進(jìn)農(nóng)業(yè)發(fā)展。因此可以說(shuō)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而非單一變量的原因。可見(jiàn),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礎(chǔ)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會(huì)發(fā)展的真正動(dòng)因。
總之,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無(wú)論是從整體敘述上還是從個(gè)案分析上,都要求我們必須采取多種方法并轉(zhuǎn)換傳統(tǒng)的研究視角,從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的實(shí)際出發(fā),在多種因素綜合量化分析的基礎(chǔ)上,揭示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規(guī)律,闡釋中國(guó)文明的本質(zhì)動(dòng)因。 三
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雖然存在資料不足的現(xiàn)實(shí)情況,但是這并不妨礙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的深化,而且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將來(lái)會(huì)逐步得到改善。現(xiàn)在重要的是能夠使廣大考古工作者特別是發(fā)掘者在意識(shí)上形成主動(dòng)收集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資料的觀念,帶著科研目標(biāo)去從事考古發(fā)掘工作。考古發(fā)掘是收集資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獲得科學(xué)資料的關(guān)鍵。近年來(lái),有關(guān)考古學(xué)分支學(xué)科的確立使得考古資料的信息量大增,這與發(fā)掘者的主觀意識(shí)是分不開(kāi)的。在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中植物考古學(xué)、動(dòng)物考古學(xué)等分支學(xué)科的確立,讓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識(shí)到了資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yàn)檠芯康纳钊雽?duì)考古資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在傳統(tǒng)考古學(xué)資料中有些是無(wú)法獲得的。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中植物硅酸體分析方法的應(yīng)用以及相關(guān)研究的開(kāi)展(12),為加強(qiáng)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資料的收集工作創(chuàng)造了條件。無(wú)疑新方法的應(yīng)用擴(kuò)大了研究的范圍,也提高了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資料收集的精細(xì)化程度。
在資料不斷豐富的條件下,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有望在以下幾個(gè)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礎(chǔ)上,能夠了解個(gè)別區(qū)域乃至整個(gè)山東地區(qū)生產(chǎn)工具的特點(diǎn)和具體的生產(chǎn)方式,不同地區(qū)、不同地域的生產(chǎn)工具是不同的,這與土質(zhì)以及環(huán)境有直接的關(guān)系,而只有深化個(gè)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區(qū)間的差異。其次是農(nóng)業(yè)起源的研究,多種理論與方法的綜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證。農(nóng)業(yè)是如何起源的問(wèn)題歷來(lái)為學(xué)術(shù)界所關(guān)注,山東地區(qū)地理環(huán)境較為封閉,其區(qū)域的系統(tǒng)研究必將對(duì)這一問(wèn)題的解決提供可資借鑒的經(jīng)驗(yàn)。這里民族學(xué)、人類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等的理論與方法在分析過(guò)程中的綜合應(yīng)用,有助于問(wèn)題的解決。最后是農(nóng)業(yè)與文明的關(guān)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斷深化的前題下,能夠取得長(zhǎng)足的進(jìn)展。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是社會(huì)發(fā)展的保證,但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不一定就能導(dǎo)致文明的產(chǎn)生。這里任何單一的因素都無(wú)法解釋文明的產(chǎn)生。因此,綜合分析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發(fā)展過(guò)程并結(jié)合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研究可以為文明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提供合理的解釋。
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研究的問(wèn)題還相當(dāng)多,這些問(wèn)題的解決還有賴于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理論、方法、技術(shù)的改進(jìn)。國(guó)外的一些研究理論、方法、技術(shù)是在總結(jié)西方實(shí)踐的基礎(chǔ)上提出的,對(duì)于中國(guó)的考古學(xué)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還需中國(guó)實(shí)踐的檢驗(yàn)。因此,山東地區(qū)史前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在應(yīng)用這些方法進(jìn)行研究的時(shí)候,對(duì)總結(jié)中國(guó)自己的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研究理論與方法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陳文華:《簡(jiǎn)論農(nóng)業(yè)考古》,《農(nóng)業(yè)考古》1984年第2期。
(2)吳詩(shī)池:《山東新石器時(shí)代農(nóng)業(yè)考古概述》,《農(nóng)業(yè)考古》1985年第1期。
(3)吳詩(shī)池:《海岱文化區(qū)的史前農(nóng)業(yè)》,《農(nóng)業(yè)考古》1985年第1期。
(4)吳詩(shī)池:《綜述山東出土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農(nóng)業(yè)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東:《從出土文物看棗莊地區(qū)的史前農(nóng)業(yè)》,《農(nóng)業(yè)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國(guó):《濟(jì)南地區(qū)古代農(nóng)業(yè)考古概述》,《農(nóng)業(yè)考古》1996年第1期。
(7)陳淑卿:《海岱地區(qū)龍山文化生產(chǎn)工具的類型學(xué)考察》,《遼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農(nóng)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這類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論山東地區(qū)新石器時(shí)代的養(yǎng)豬業(yè)》,《農(nóng)業(yè)考古》1986年第1期。
劉俊勇:《試論東夷史前經(jīng)濟(jì)》,《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東史前時(shí)期自然環(huán)境的考古學(xué)觀察》,《華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華:《海岱地區(qū)原始農(nóng)業(yè)初探》,《慶祝山東大學(xué)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何德亮:《試論山東地區(qū)的原始農(nóng)業(yè)》,《慶祝山東大學(xué)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國(guó)青銅時(shí)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及其考察》,《農(nóng)業(yè)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關(guān)山東地區(qū)史前植物硅酸體及其相關(guān)研究的論文主要有:
王克林、吳加安:《尉遲寺遺址硅酸體分析-兼論尉遲寺遺址史前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特點(diǎn)》,《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東臨淄田旺龍山文化遺址植物硅酸體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東滕州市莊里西遺址植物遺存及其在環(huán)境考古學(xué)上的意義》,《考古》1999年第7期。
篇4
關(guān)鍵詞:闡釋性呈現(xiàn);考古電視新聞報(bào)道;價(jià)值解析
作者簡(jiǎn)介:張殿元,男,新聞學(xué)博士,復(fù)旦大學(xué)新聞學(xué)院副教授,復(fù)旦大學(xué)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huì)研究國(guó)家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創(chuàng)新基地副研究員(上海 200433)
中圖分類號(hào):G229.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1-0169(2013)04-0073-05
人類社會(huì)的發(fā)展是建立在繼承和創(chuàng)新的基礎(chǔ)之上的,只有將前人的經(jīng)驗(yàn)、智慧、知識(shí)加以記錄、積累、保存并傳給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完善、發(fā)展和創(chuàng)造。我們的先祖?zhèn)冊(cè)?jīng)創(chuàng)造了璀璨的文明,它對(duì)于今天和未來(lái)中國(guó)的發(fā)展而言,意義重大。但正像培根所說(shuō),“知識(shí)的力量不僅取決于其本身價(jià)值的大小,更取決于它是否被傳播及傳播的深度和廣度”。
在考古知識(shí)的多種傳播途徑中,電視媒體成為最受公眾歡迎、接收考古知識(shí)和信息最多的渠道。近年來(lái),文物考古方面的新聞報(bào)道頗為引人關(guān)注,2000年至今,就有十多場(chǎng)考古類電視新聞直播和數(shù)百項(xiàng)考古新聞報(bào)道。然而在越來(lái)越熱的考古報(bào)道背后,考古工作者對(duì)電視媒介的認(rèn)識(shí)和電視工作者對(duì)考古項(xiàng)目的了解都還非常不足,一些好的考古項(xiàng)目苦于找不到出口,沒(méi)有好的宣傳和普及。一些被重點(diǎn)宣傳的考古項(xiàng)目,因受到報(bào)道者對(duì)考古項(xiàng)目了解的局限,沒(méi)有做到最充分的解讀和表達(dá)。如何借助電視媒體報(bào)道考古項(xiàng)目、傳播考古知識(shí),不僅是考古工作者也是電視新聞人迫切需要的,更是受眾所期待的。
早在20世紀(jì)60年代西方就已提出“公眾考古學(xué)”這一概念,旨在將考古學(xué)大眾化,使大眾理解、支持、參與考古和遺產(chǎn)保護(hù)活動(dòng),并做出了相應(yīng)的嘗試,比如建街邊博物館,文物修復(fù)透明化,創(chuàng)辦一些很有影響力的期刊等。我國(guó)在這方面起步較晚,尚處于萌芽階段,雖然也有如《故宮》、《中國(guó)博物館》等精品,但更多的是像《鑒寶》這樣的節(jié)目,娛樂(lè)性尚可,但嚴(yán)重缺乏內(nèi)涵。如何借助電視這樣一個(gè)獨(dú)特的視角,在廣播電視藝術(shù)學(xué)、傳播學(xué)和考古學(xué)的架構(gòu)中,思考考古學(xué)大眾化的問(wèn)題,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普及和提高:電視新聞報(bào)道對(duì)考古大眾化的價(jià)值呈現(xiàn)
電視出現(xiàn)之前人們對(duì)考古的了解主要通過(guò)對(duì)紙質(zhì)媒體的閱讀以及民間的口耳傳播獲得的,這種信息的傳達(dá)由于受到人們文化素養(yǎng)和媒介自身的局限,在考古大眾化的過(guò)程中影響僅限于少部分人當(dāng)中。電視的出現(xiàn)是傳媒史上的重大事件,多種傳播符號(hào)的聚合讓最大多數(shù)人卷入到了電視傳播構(gòu)成的世界里,即便是像考古這樣并非所有人都感興趣的節(jié)目也在電視的放大效應(yīng)下不斷走進(jìn)千家萬(wàn)戶。經(jīng)過(guò)多年的節(jié)目設(shè)計(jì),特別是隨著人們對(duì)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包括考古節(jié)目在內(nèi)的文化類傳媒產(chǎn)品成了各電視機(jī)構(gòu)開(kāi)發(fā)的熱點(diǎn)。
當(dāng)下電視對(duì)考古學(xué)及考古活動(dòng)的傳播從題材上看包括三種類型,一類是傳播國(guó)家有關(guān)考古方面的重大研究項(xiàng)目,如國(guó)家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在這些科學(xué)研究項(xiàng)目中考古發(fā)掘工作最為引人注目,因?yàn)橛^眾對(duì)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非常關(guān)心,這讓考古類節(jié)目在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中央電視臺(tái)第10套節(jié)目多次播放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片子,收視率很高;第二類是新聞媒體如中央電視臺(tái)和省市級(jí)電視臺(tái),經(jīng)常播發(fā)各地考古發(fā)掘的收獲,甚至搞考古工地現(xiàn)場(chǎng)直播。如北京老山漢墓的發(fā)掘,河南林州東周墓的發(fā)掘,湖北棗陽(yáng)戰(zhàn)國(guó)墓的發(fā)掘,江蘇泗陽(yáng)漢墓的發(fā)掘,還有水下考古的報(bào)道等等;第三類是配合基本建設(shè)的考古發(fā)掘的報(bào)道。大的諸如長(zhǎng)江三峽工地、黃河小浪底水庫(kù)工地、鐵路和高速公路建設(shè),小的如老城區(qū)改造等。由于這些工程建設(shè)過(guò)程中的古物發(fā)現(xiàn)和發(fā)掘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guān),有的就發(fā)生在現(xiàn)實(shí)生活里,因此在民間的影響也非常大。
近年來(lái)出現(xiàn)的比較多的有關(guān)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新聞報(bào)道和相關(guān)的專題節(jié)目,在不斷增強(qiáng)人們對(duì)中華古老文明的關(guān)注度的同時(shí),也對(duì)民眾的文物保護(hù)意識(shí)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動(dòng)作用。特別是與基本建設(shè)相關(guān)的考古發(fā)掘的報(bào)道,文物單位直接同基建部門、老百姓打交道,利用考古發(fā)掘現(xiàn)場(chǎng)講解文物知識(shí)和公民的行為規(guī)范,進(jìn)行文物保護(hù)宣傳,取得社會(huì)的理解和支持。此外,電視機(jī)構(gòu)的大量考古信息的傳播,也直接影響了老百姓對(duì)文物的價(jià)值判斷,并提高了文物保護(hù)的意識(shí),強(qiáng)化了文物是國(guó)家民族公共財(cái)產(chǎn)的心理,改變了處理文物的態(tài)度,最后讓大家共同行動(dòng)起來(lái)保護(hù)歷史文物。文物保護(hù)宣傳抑或電視新聞的考古報(bào)道,專業(yè)性強(qiáng),而我們面對(duì)的主要宣傳對(duì)象是基層的百姓,知識(shí)鴻溝以及興趣上的障礙很明顯。電視媒體應(yīng)該通過(guò)什么樣的傳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影響人、教育人,如何將文物保護(hù)的宣傳民生化,在貼近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上下功夫,是電視媒體在進(jìn)行考古報(bào)道的時(shí)候需要考慮的問(wèn)題。
二、好看和時(shí)效:電視新聞報(bào)道與考古大眾化的價(jià)值錯(cuò)位
考古報(bào)道熱產(chǎn)生的客觀效果是積極的,但考古學(xué)和電視新聞報(bào)道的特點(diǎn),也決定了電視新聞報(bào)道和考古工作之間存在一些較難處理的問(wèn)題:電視首先要好看,考古的判斷關(guān)鍵是價(jià)值,好看的未必有價(jià)值,而有價(jià)值的常常又不好看;新聞傳播要求快,再重大的考古項(xiàng)目錯(cuò)過(guò)了宣傳的時(shí)機(jī)就不再是新聞;考古研究要求嚴(yán)謹(jǐn),新發(fā)現(xiàn)之初,往往不希望新聞報(bào)道,因?yàn)樵诖蠖鄶?shù)考古學(xué)者的意識(shí)中,考古是個(gè)相對(duì)封閉的過(guò)程,完成這個(gè)過(guò)程需要學(xué)者潛心去努力,只有盡可能摒棄雜念,才會(huì)從考古第一手的資料中讀懂或者接受比較完整的古代信息,更何況輕易下結(jié)論有出錯(cuò)的風(fēng)險(xiǎn)。具體而言,目前中國(guó)電視考古報(bào)道中存在的問(wèn)題有以下幾個(gè)方面。
(一)電視作為一種理解模式無(wú)法深入解析考古活動(dòng)
考古學(xué)被認(rèn)為是一門典型的實(shí)證科學(xué),它的誕生是以實(shí)證科學(xué)的精神和方法對(duì)關(guān)于遠(yuǎn)古神話、傳說(shuō)的想象和思辨加以匡正的結(jié)果。相對(duì)于考古挖掘的器物而言,對(duì)考古器物的解析更重要。對(duì)考古發(fā)現(xiàn)的理解模式是多元的,相對(duì)的,可選擇的,但并非沒(méi)有優(yōu)劣高下之分。好的理解模式能夠把更多的考古證據(jù)聯(lián)系在一起,更深入、更廣泛地解釋人的社會(huì)活動(dòng)過(guò)程。考古學(xué)理論的進(jìn)步不僅表現(xiàn)在證據(jù)的積累,更重要的是選擇合適的理解模式,把盡可能多的已知證據(jù)聯(lián)系起來(lái),對(duì)已知的和未知的過(guò)去事件,提出更有說(shuō)服力、覆蓋范圍更為普遍的解釋。
理解模式有許多種,如考古學(xué)、新考古學(xué)和后過(guò)程考古學(xué)等等,新聞傳媒既可以再現(xiàn)這些理解模式,同時(shí)也是對(duì)考古的一種新的理解模式,但這種理解模式容易重蹈“鏡像論”的誤區(qū)。電視對(duì)考古的報(bào)道嚴(yán)格遵循真實(shí)性的原則,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現(xiàn)考古活動(dòng)的全過(guò)程,這種記錄性質(zhì)的報(bào)道體現(xiàn)出來(lái)的文化進(jìn)化的主要證據(jù),是考古器物及其制作工藝技術(shù)的改良和進(jìn)步,但這些證據(jù)充其量只是證明了物質(zhì)文化的進(jìn)步,在社會(huì)組織、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價(jià)值信仰體系等“觀念文化”的層面,史前時(shí)代是否比以后的時(shí)代更簡(jiǎn)單、更低級(jí)、更落后,對(duì)這一問(wèn)題的答案取決于解釋文化遺物的更科學(xué)的理解模式,而不是文化遺物本身。
考古報(bào)道的復(fù)雜性體現(xiàn)在通過(guò)器物思考史前人們的思維方式,而史前人的思維并不是簡(jiǎn)單地對(duì)包括器物在內(nèi)的物質(zhì)世界的反映,這是其一;其二是史學(xué)家對(duì)考古發(fā)現(xiàn)的思考,也是結(jié)合了自己的史學(xué)理論能動(dòng)化地解釋眼前的器物及其所代表的那個(gè)年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電視在報(bào)道考古發(fā)現(xiàn)的時(shí)候,往往找個(gè)別的專家和學(xué)者就自己的研究來(lái)向大眾講解發(fā)掘的器物所代表的古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有一定的片面性;其三,不管有多少機(jī)位,電視對(duì)考古挖掘的再現(xiàn)都是有選擇的,這種用鏡頭對(duì)考古事件所做的選擇性報(bào)道,無(wú)法還原考古事件的本來(lái)面目,演播室的專家更無(wú)法依次來(lái)完整解析古人的思想觀念等深層的內(nèi)容。
(二)考古電視新聞報(bào)道無(wú)法反映“過(guò)程考古學(xué)”的實(shí)質(zhì)
面對(duì)考古發(fā)掘出來(lái)的遺物,即使我們知道了它們的文化特征和類型,也常有“見(jiàn)物不見(jiàn)人”的感慨,要真正做到“透物見(jiàn)人”,就必須借助考古學(xué)以外的學(xué)科的知識(shí),賦予考古遺物一定的社會(huì)歷史意義,這樣它們就不再只是物質(zhì)文化的載體,而且與上古史記載的經(jīng)濟(jì)、政治、軍事和宗教等事件相對(duì)應(yīng),重現(xiàn)史前各部落集團(tuán)的生活和歷史。而電視的考古新聞報(bào)道多半都是以少于2分鐘的短消息的形式出現(xiàn)的,記者將復(fù)雜的考古活動(dòng)用10幾個(gè)鏡頭記錄并報(bào)道出來(lái),觀眾只是通過(guò)這些鏡頭了解了一個(gè)簡(jiǎn)單的新聞事件,那些硬邦邦的器物所代表的也只是一段已經(jīng)“死去”的歷史,有關(guān)那段歷史的豐富意義無(wú)法在大眾的眼中呈現(xiàn)。
“新考古學(xué)”強(qiáng)調(diào)研究人類活動(dòng)的過(guò)程,也被稱為“過(guò)程考古學(xué)”。它通過(guò)考察各地、各種族活動(dòng)的自然和社會(huì)過(guò)程,做出跨文化的概括。對(duì)考古證據(jù)的科學(xué)解釋更加重視文化遺物的社會(huì)意義,一件文化器物不是孤零零的客觀存在物,而是特定社會(huì)模式中的人的生活的一個(gè)片段,社會(huì)模式把一個(gè)個(gè)片段聯(lián)系在一起,使它們重現(xiàn)過(guò)去人類活動(dòng)的過(guò)程,使文化遺物所攜帶的信息得到完全的解讀。而串聯(lián)起一個(gè)個(gè)片段的社會(huì)模式無(wú)法從簡(jiǎn)單的一次考古活動(dòng)中概括出來(lái),需要一個(gè)超越時(shí)空的宏觀觀照,但考古新聞報(bào)道并不是基于考古學(xué)的原則生產(chǎn)出來(lái)的,它不會(huì)考慮不同時(shí)間和地點(diǎn)的考古發(fā)現(xiàn)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這種零碎的考古新聞報(bào)道事實(shí)上割斷了作為“過(guò)程的”考古學(xué)。
(三)考古電視新聞報(bào)道容易淪為利益集團(tuán)的工具
在普通大眾的眼里,考古挖掘的報(bào)道不過(guò)是一個(gè)新聞事件而已,但在當(dāng)?shù)卣难劾铮脊磐诰蛱貏e是可能與歷史名人扯上關(guān)系的考古挖掘就成了一件關(guān)涉到旅游和財(cái)政收入的大事件。這樣的考古新聞報(bào)道事實(shí)上就成了一個(gè)巨大的權(quán)力場(chǎng),相關(guān)的政府部門、有關(guān)的專家學(xué)者、科研機(jī)構(gòu)、社會(huì)輿論都牽涉其中,進(jìn)行有關(guān)歷史名人歸屬的大辯論。新聞媒體本來(lái)是這一事件的旁觀者和記錄者,應(yīng)該有自己對(duì)這一事件的價(jià)值判斷,但是當(dāng)事件本身成為一個(gè)社會(huì)議論的熱點(diǎn)話題時(shí),媒體也會(huì)不分青紅皂白大肆進(jìn)行報(bào)道炒作,以提高媒體的收視率,賺取廣告收益,這時(shí)候的電視機(jī)構(gòu)也便成了博弈的一方了。媒體的主動(dòng)介入讓更多的利益相關(guān)者出來(lái)發(fā)聲,以至于事件越鬧越大,作為事件的推波助瀾的媒體最終讓自己站在了事件的風(fēng)口浪尖上,成為被利益集團(tuán)利用的工具。2009年關(guān)于曹操墓的考古挖掘的新聞報(bào)道就是一個(gè)典型的案例。
2009年12月27日,中央電視臺(tái)《午間新聞聯(lián)播》報(bào)道了河南安陽(yáng)地區(qū)考古挖掘的“疑似曹操墓”。但當(dāng)晚《新聞聯(lián)播》與第二天CCTV-4的跟蹤報(bào)道稱,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開(kāi)新聞會(huì),專家宣布在河南安陽(yáng)發(fā)現(xiàn)的西高穴墓地,其墓主人已經(jīng)確認(rèn)為曹操。毗鄰安陽(yáng)的河北邯鄲,人所共知是曹操鄴城所在,曹魏文化源遠(yuǎn)流長(zhǎng).卻眼見(jiàn)著曹操墓現(xiàn)身河南,頗有些不平靜,除了質(zhì)疑河南方面外,也宣稱曹操墓可能在邯鄲一帶。而曹操老家、安徽亳州據(jù)說(shuō)也不排除開(kāi)挖疑似曹操墓的曹氏宗族墓群的可能。嚴(yán)肅的考古成果,不期引來(lái)大討論,掀起大波瀾,著實(shí)讓河南方面有些手忙腳亂。尤其糟糕的是,河南越強(qiáng)調(diào)此次考古的專業(yè)、科學(xué)和審慎,其遭遇的網(wǎng)絡(luò)阻擊就越強(qiáng)烈。2009年最后一天,河南方面組織文物專家集中答疑釋惑,試圖將口水仗平息在2009年。然而,事件的走向已不可控,網(wǎng)民乃至社會(huì)公眾的疑問(wèn),并沒(méi)有因?yàn)閷<掖朕o簡(jiǎn)練的幾條意見(jiàn)而消失。后來(lái),國(guó)內(nèi)某著名高校擬啟動(dòng)現(xiàn)代DNA基因調(diào)查技術(shù),專辟科研課題,尋曹氏后人比對(duì)遺傳信息,參與遺骨甄別,尋求新的信息支撐。在這場(chǎng)旋風(fēng)中,一些利益集團(tuán)包括少數(shù)專家學(xué)者不失時(shí)機(jī)地利用先驗(yàn)的“學(xué)養(yǎng)”信息優(yōu)勢(shì),利用手中控制的不對(duì)稱信息資源很“內(nèi)行”地炒作自我,操弄話語(yǔ)權(quán),成為眼球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的名利雙收者[1]。
此種情況下,受眾與電視傳媒或許反被輿論所牽引,成為睜眼瞎,不知不覺(jué)中為人作嫁而提供免費(fèi)論壇和廣告。事實(shí)上,面臨復(fù)雜的事件,電視媒體只是秉持客觀、公正的新聞報(bào)道原則還不夠,有時(shí)還需多一份審慎的保留,要關(guān)注事態(tài)的發(fā)展變化,使新聞報(bào)道更具可操作性、調(diào)控性和糾偏性,把握輿論導(dǎo)向的主導(dǎo)權(quán)。否則,盲目搶位,向受眾兜售本質(zhì)上并不客觀的新聞,必然損耗媒體的公信力。
三、闡釋和責(zé)任:電視新聞報(bào)道對(duì)考古大眾化的價(jià)值回歸
20世紀(jì)60年代以來(lái),公眾考古學(xué)開(kāi)始成為考古學(xué)中的一門重要分支學(xué)科。它的出現(xiàn)既是適應(yīng)考古學(xué)大眾化趨勢(shì)的一個(gè)必然結(jié)果,同時(shí)也反映了公眾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關(guān)注,對(duì)民族歷史文化的熱愛(ài)。進(jìn)入21世紀(jì),公眾考古學(xué)的發(fā)展更加迅猛,隨著現(xiàn)代傳媒技術(shù)的日益強(qiáng)大,我國(guó)考古學(xué)的大眾傳播近年來(lái)也呈現(xiàn)出不斷升溫的趨勢(shì)。現(xiàn)代傳媒在促進(jìn)考古學(xué)大眾化的過(guò)程中雖然起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著一些弊端,比如或多或少帶有金錢化、庸俗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誤導(dǎo)大眾,使大眾對(duì)考古學(xué)的認(rèn)識(shí)與獵奇、探險(xiǎn)等聯(lián)系起來(lái),而沒(méi)有真正認(rèn)識(shí)到考古學(xué)的社會(huì)作用等等。雖然有CCTV的“探索”、“走進(jìn)科學(xué)”、“國(guó)寶檔案”等專業(yè)考古欄目的設(shè)置,在大眾中享有較高的收視率,但作為普及范圍最大的電視傳媒領(lǐng)域,仍缺乏精品,大多數(shù)考古類的節(jié)目多流于形式而失去了節(jié)目的真正價(jià)值。要將公眾考古學(xué)的理論與中國(guó)的現(xiàn)實(shí)相結(jié)合仍需一段時(shí)間,但中國(guó)考古學(xué)家已開(kāi)始憑著與生俱來(lái)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邁出了公眾考古學(xué)社會(huì)實(shí)踐的步伐,相關(guān)科普類讀物相繼面世,考古學(xué)家也開(kāi)始與傳媒合作,而時(shí)下考古電視報(bào)道的策略應(yīng)該考慮的問(wèn)題是:
(一)超越電視考古報(bào)道的技術(shù)邏輯,解釋比描述更重要
我們可以通過(guò)發(fā)掘文化遺物,來(lái)認(rèn)識(shí)人類過(guò)去的歷史。在史前時(shí)代這段漫長(zhǎng)的歲月里,人類活動(dòng)遺留在地下或洞穴里的器具或痕跡是我們現(xiàn)在唯一可知的證據(jù)。考古學(xué)在創(chuàng)立時(shí)的主要任務(wù)是尋找這些證據(jù),重現(xiàn)史前時(shí)代的事件。通過(guò)考古證據(jù)的積累,可以對(duì)越來(lái)越大的范圍和越來(lái)越長(zhǎng)的時(shí)間中的原始文化做出越來(lái)越普遍的判斷。隨著技術(shù)的進(jìn)步,考古挖掘和考古發(fā)現(xiàn)面臨的障礙越來(lái)越少,現(xiàn)代的考古技術(shù)和儀器,讓被發(fā)掘的遺物的數(shù)量不斷增長(zhǎng)。
但是,考古學(xué)的目標(biāo)是對(duì)過(guò)去的事實(shí)和事件做出解釋,而不單純是對(duì)過(guò)去的描述。作為一門歷史科學(xué),考古學(xué)的研究不應(yīng)限于對(duì)古代遺跡、遺物的描述和分類,也不應(yīng)限于鑒定遺跡、遺物的年代和判明它們的用途與制造方法。考古學(xué)研究的最終目標(biāo)在于闡明存在于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規(guī)律,考古學(xué)家要論證人類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也要探求各個(gè)地區(qū)、各個(gè)民族在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差異點(diǎn)和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原始文化的要素,如語(yǔ)言和其他符號(hào)系統(tǒng)、儀式活動(dòng)、社會(huì)層次和價(jià)值系統(tǒng)等,需要通過(guò)對(duì)原始社會(huì)中的人的意識(shí)和行為模式的考察,才能被認(rèn)識(shí)或理解。考古學(xué)發(fā)掘的文化遺物所攜帶的信息主要與物質(zhì)文化相關(guān),但這些無(wú)生命的物件不足以揭示原始人群的意識(shí)和行為模式。
電視在進(jìn)行考古報(bào)道的時(shí)候,全方位記錄的現(xiàn)場(chǎng)感是任何其他媒體都無(wú)法比擬的,但與紙質(zhì)媒體相比,影像無(wú)法進(jìn)行思辨和邏輯演繹,電視代表的是肯定文化,而紙媒代表的否定文化。當(dāng)我們要對(duì)考古的過(guò)程做全面描述的時(shí)候,電視的優(yōu)點(diǎn)就可以發(fā)揮作用了,但我們要對(duì)考古發(fā)現(xiàn)做進(jìn)一步解釋的時(shí)候,電視的缺點(diǎn)就表現(xiàn)出來(lái)了。因此,我們要盡可能利用電視節(jié)目制作積累的經(jīng)驗(yàn)和提供的平臺(tái),盡可能超越電視的技術(shù)限制,通過(guò)專家解讀和電視深度報(bào)道的形式對(duì)考古發(fā)現(xiàn)做更精細(xì)深入的闡釋。
(二)避免零散報(bào)道造成的歷史隔斷,利用考古新聞宣揚(yáng)中華民族文化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多樣性和統(tǒng)一性的融合,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自上古時(shí)代起,就生活著眾多不同的部落,在千百年的歷史長(zhǎng)河中,經(jīng)過(guò)這些部落之間的征戰(zhàn)、聯(lián)姻、合作,慢慢形成了今天中華民族的完整格局。電視考古報(bào)道特別是那些篇幅較長(zhǎng)的考古電視直播報(bào)道,應(yīng)該在具體的某一地區(qū)的考古報(bào)道中,利用專家的講解將這一地區(qū)的文化和其他地區(qū)的關(guān)聯(lián)講清楚,讓廣大的電視觀眾科學(xué)地了解中華民族的形成歷史,不要讓觀眾看了這些報(bào)道后,產(chǎn)生“非我族類,與我無(wú)關(guān)”的想法。
能夠了解中華民族形成史的考古理論包括“上古三大集團(tuán)”理論和“文化區(qū)系類型”理論。學(xué)者徐旭生在分析先秦時(shí)期傳說(shuō)的史料基礎(chǔ)上,得出結(jié)論:“我國(guó)古代的部落分野,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集團(tuán)……。這三個(gè)集團(tuán)相遇以后,開(kāi)始互相爭(zhēng)斗,此后又和平共處,終結(jié)完全同化,才漸漸形成將來(lái)的漢族”[2](P3-4)。蘇秉琦根據(jù)中國(guó)各區(qū)域發(fā)現(xiàn)的史前遺址的器物的整理、分類和概括,把中國(guó)新石器時(shí)期的文化遺址分為六個(gè)區(qū)系:以燕山北為中心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陜西、晉南和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太湖地區(qū)為中心的東南部,以洞庭湖地區(qū)和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陽(yáng)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六大區(qū)系中的三個(gè)屬于歐亞大陸文化圈,三個(gè)屬于環(huán)太平洋文化圈[3](P120,69)。這兩個(gè)理論的結(jié)論是等值的,兩者相互對(duì)應(yīng),相互參證。“上古三大集團(tuán)”的理論使我們見(jiàn)到了不同類型文化遺物的屬主,他們是一些部落集團(tuán)。仰韶文化是華夏集團(tuán)的創(chuàng)造,山東的大汶口文化屬于東夷集團(tuán),而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長(zhǎng)江中游的屈家?guī)X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苗蠻集團(tuán)的勢(shì)力范圍,龍山文化和后來(lái)的中原龍山是混合華夏和東夷文化的文化類型。考古學(xué)家嚴(yán)文明說(shuō),這六個(gè)文化區(qū)的關(guān)系好似“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jié)構(gòu)”,“五個(gè)文化區(qū)都緊鄰和圍繞著中原文化區(qū),很像一個(gè)巨大的花朵,五個(gè)文化區(qū)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qū)是花心。各文化區(qū)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時(shí)又有不同程度的聯(lián)系,中原文化區(qū)更起著聯(lián)系各個(gè)文化區(qū)的核心作用。……它與古史傳說(shuō)中各個(gè)部落集團(tuán)經(jīng)常遷移、相互交往乃至發(fā)生戰(zhàn)爭(zhēng)的記述是相呼應(yīng)的。”[4](P258)
對(duì)考古發(fā)掘的器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模式,如果是專家學(xué)者私下的個(gè)人研究,很難分出這些模式的高下優(yōu)劣。但是,當(dāng)這些考古的研究通過(guò)電視媒體被放大到觀眾面前時(shí),就不一樣了。如果我們把傳媒呈現(xiàn)看成是精英考古學(xué)和大眾考古學(xué)區(qū)別的話,那大眾考古學(xué)理解模式的好壞就應(yīng)該在通俗之外秉承文化傳承和能否發(fā)揮教育功能的標(biāo)準(zhǔn),前面的兩大理論就是符合這種標(biāo)準(zhǔn)的理解模式。目前中國(guó)的電視考古報(bào)道還缺少這樣的大局觀,在以后的節(jié)目策劃特別是直播節(jié)目找嘉賓學(xué)者時(shí),應(yīng)該遵循這樣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
(三)強(qiáng)化電視考古報(bào)道節(jié)目的文本意識(shí),新聞生產(chǎn)要對(duì)歷史負(fù)責(zé)
新聞人都知道一個(gè)常識(shí),即今天的新聞將是50年后的歷史,因此,新聞人應(yīng)該具有一定的歷史使命感,當(dāng)新聞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記錄涉及考古之類的歷史命題時(shí),這種使命感就更強(qiáng)烈了。
我們知道,對(duì)于考古學(xué)而言,實(shí)物本身并不是經(jīng)驗(yàn),它們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能成為經(jīng)驗(yàn)證據(jù)。文字證據(jù)與實(shí)物證據(jù)對(duì)于我們的經(jīng)驗(yàn)有著同等重要性。但是,文字證據(jù)與實(shí)物證據(jù)這兩種經(jīng)驗(yàn)都不是獨(dú)立于命題的,在此意義上,兩者又都是“文本”。當(dāng)今的“解釋考古學(xué)”認(rèn)為,考古發(fā)現(xiàn)的遺物和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文本”。文本只有在一定的“語(yǔ)境”中才有意義,文本的語(yǔ)境是過(guò)去、現(xiàn)在和將來(lái)相互融合的“視域”。從“視域融合”的觀點(diǎn)看,史前的遺物不僅是那時(shí)候人的思想活動(dòng)的產(chǎn)物,而且反映了他們對(duì)社會(huì)、環(huán)境或“生活世界”的理解,他們的理解既是對(duì)過(guò)去的解釋,也被他們之后的人們所解釋。理解活動(dòng)代代相傳,每一時(shí)代的解釋都不能離開(kāi)相傳至今的過(guò)去的解釋,現(xiàn)在進(jìn)行的解釋也向未來(lái)開(kāi)放。
在這個(gè)意義上,新聞報(bào)道的考古也是一種可供考古研究的文本。一方面,電視考古報(bào)道對(duì)考古挖掘過(guò)程進(jìn)行全方位記錄,強(qiáng)烈的現(xiàn)場(chǎng)感真實(shí)完整地呈現(xiàn)古人的生活場(chǎng)景,這些影像資料就是將來(lái)考古學(xué)研究的重要文本。特別是那些超大型的古跡,無(wú)法挖掘出來(lái)在博物館保存,研究者不便于經(jīng)常光顧考古現(xiàn)場(chǎng),電視記錄的影像就成了重要的研究文本;另一方面,考古現(xiàn)場(chǎng)直播中專家的講解和電視人查閱大量資料編輯制作的節(jié)目都是對(duì)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一種理解,這種對(duì)器物和歷史的解讀也必將被后人所再次或多次解讀。同樣是文本,前者是對(duì)古人生活的記錄,要對(duì)歷史負(fù)責(zé);后者是今人對(duì)古人的理解,這種理解是對(duì)未來(lái)開(kāi)放的,要對(duì)后人負(fù)責(zé)。
參考文獻(xiàn):
[1] 張君安,汪開(kāi)海.論新聞傳播中的信息不對(duì)稱——曹墓考古引發(fā)眾聲喧嘩的啟示[J].新聞前哨,2010,(4).
[2] 徐旭生.中國(guó)上古史的傳說(shuō)時(shí)代[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60.
篇5
關(guān)鍵詞:福柯 理性 主體
在法國(guó)旺多佛爾小公墓里有一座樸實(shí)的墓碑,上面刻著“保羅-米歇兒?福柯,法蘭西學(xué)院教授,1926~1984”。保羅-米歇兒?福柯是誰(shuí)?仰望20世紀(jì)思想的星空,群星閃爍,燦爛奪目。但我們一眼就能發(fā)現(xiàn)一顆極其閃亮的星星,那就是米歇兒?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是當(dāng)代一位引人注目的思想家,被稱為是薩特之后法國(guó)最重要的哲學(xué)家。福柯這個(gè)名字已經(jīng)是我們?cè)谏婕?0世紀(jì)西方文明、思想、學(xué)術(shù)等方面時(shí)不能不提到的名字。他對(duì)于整個(gè)法國(guó)和當(dāng)代西方思想界的影響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當(dāng)代各種思想流派和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界的各門學(xué)科,幾乎沒(méi)有一個(gè)領(lǐng)域可以避開(kāi)他的思想光芒的照射。就像美國(guó)著名學(xué)者克利茲曼所說(shuō):“福柯之死在法國(guó)知識(shí)界造成了一個(gè)巨大的空白。在現(xiàn)代歷史上,沒(méi)有任何一個(gè)思想家像他那樣對(duì)歷史學(xué)、哲學(xué)、文學(xué)和文學(xué)理論、社會(huì)科學(xué)乃至醫(yī)學(xué)產(chǎn)生如此之大的影響。”①甚至法國(guó)著名哲學(xué)家德勒茲宣布:這個(gè)世紀(jì)將被稱作“福柯時(shí)代”。
福柯是一位反傳統(tǒng)和反西方正統(tǒng)文明的思想家,是當(dāng)代最偉大的哲學(xué)家之一。但他始終不愿意將自己的思想歸屬于任何一個(gè)流派,甚至拒絕給他的思想標(biāo)上一個(gè)特定的標(biāo)簽。然而,他畢竟深刻地影響了整個(gè)后現(xiàn)代主義的思想模式及其方法論,甚至影響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許多重要觀點(diǎn)。所以,人們往往將他列為后現(xiàn)代主義的代表人物,甚至被奉為后現(xiàn)代主義的啟蒙思想家。
福柯思想的基本出發(fā)點(diǎn)是批判現(xiàn)代性、人類中心主義和人本主義。與其他后現(xiàn)代主義者一樣,福柯反對(duì)啟蒙運(yùn)動(dòng)將理性、解放和進(jìn)步等同起來(lái),認(rèn)為現(xiàn)代性實(shí)質(zhì)上是一種控制和統(tǒng)治的形式,主體和知識(shí)等都是被它構(gòu)造出來(lái)的產(chǎn)物。另外,在他看來(lái),西方傳統(tǒng)思想體系致力于抹殺各種差異,建立一種整體歷史、統(tǒng)一的世界觀、統(tǒng)一的價(jià)值體系和統(tǒng)一的文明。這種思想體系在哲學(xué)上有兩種互補(bǔ)的方面:一方面把人的意識(shí)當(dāng)做一切歷史發(fā)展和一切行動(dòng)的原初主體,另一方面是把歷史說(shuō)成是連續(xù)性的進(jìn)步。因而,福柯的歷史哲學(xué)主要批判現(xiàn)代性和人類中心主義,包括對(duì)歷史理性、歷史主體、歷史總體化和連續(xù)性即線性進(jìn)步的否定。具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diǎn):
反對(duì)理性權(quán)威
福柯把現(xiàn)代性分成兩個(gè)時(shí)期:(1)古典時(shí)期(1660年~1800年);(2)現(xiàn)代時(shí)期(1800年~1950年)。在古典時(shí)期,一種強(qiáng)有力的控制人類的方式開(kāi)始形成,并且在現(xiàn)代時(shí)期達(dá)到高峰。恩格斯對(duì)這種現(xiàn)代性特征有過(guò)一段經(jīng)典式描述:“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辯護(hù)或者放棄自己存在的權(quán)利。思維著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理性主義作為啟蒙運(yùn)動(dòng)的標(biāo)志登上了歷史舞臺(tái)。至此,理性作為歷史隱蔽的“元力量”被一切文化學(xué)者所服從。
福柯認(rèn)為現(xiàn)性是一種強(qiáng)制力量。在古典時(shí)期,人的理性從神學(xué)束縛下被解放,它試圖在一片混亂和狼藉中重建社會(huì)秩序。18世紀(jì)以來(lái),人類的一切行為都被整合到現(xiàn)代話語(yǔ)實(shí)踐的帝國(guó)之中。啟蒙的任務(wù)就是伸展“理性的政治力量”,并且逐漸滲透到社會(huì)的各個(gè)角落,規(guī)范人們的日常生活。這樣,福柯揭開(kāi)了現(xiàn)代性的假面具。原來(lái),理性求真的精神將會(huì)帶來(lái)歷史進(jìn)步和人的解放的現(xiàn)代性信條,其實(shí)名不副實(shí),它不過(guò)是異于前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另一種傳統(tǒng)制度罷了。啟蒙的理性神話用“求全求同”的虛妄來(lái)掩飾和壓制多元性、差異性和增殖性。
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福柯通過(guò)對(duì)瘋癲現(xiàn)象進(jìn)行考古學(xué)研究,揭示了在西方社會(huì)中瘋癲是如何被歷史地構(gòu)成為理性的對(duì)立面,進(jìn)而被打入冷宮。他首先發(fā)現(xiàn)了從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到1656年之間的某種歷史中斷。在1656年之前,西方社會(huì)和文化尚能接受瘋癲現(xiàn)象,但是當(dāng)1656年巴黎“綜合醫(yī)院”誕生時(shí),瘋癲現(xiàn)象完全被作為異己和“非理性的危險(xiǎn)”而被排斥。由此,反對(duì)和壓抑癲狂現(xiàn)象的話語(yǔ)結(jié)構(gòu)和社會(huì)制度同時(shí)被建立起來(lái)。古典的和現(xiàn)代的話語(yǔ)實(shí)踐中,心智健全與精神病、正常與反常之間的界限首先被確立起來(lái)。理性通過(guò)排斥、拒絕、禁閉、阻礙、隱藏等非理性方式給理性與非理性劃界,從而樹立自己的權(quán)威。理性就是這樣通過(guò)這種否定性的機(jī)制成功地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非理性的控制。
否定歷史主體
主體和理性都是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一項(xiàng)發(fā)明,正如現(xiàn)代科學(xué)取代了宗教一樣,理性個(gè)體取代了上帝。現(xiàn)代概念無(wú)論是科學(xué)的、政治的還是歷史的都是隨著主體的定位而得到定位的。因此,消滅主體同時(shí)也是消滅了與它相聯(lián)系的所有現(xiàn)代觀念。可以說(shuō),主體成了對(duì)現(xiàn)代性進(jìn)行總批判的一個(gè)工具。福柯以現(xiàn)代性的反對(duì)者面目出現(xiàn),他繼尼采喊出“上帝之死”之后,宣布了“人之死”。
在《詞與物》中,福柯著手對(duì)現(xiàn)代人文科學(xué)進(jìn)行考古學(xué)分析。他研究了現(xiàn)代人文科學(xué)產(chǎn)生的歷史條件及其特定的話語(yǔ)結(jié)構(gòu)和規(guī)則,詳細(xì)分析了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古典時(shí)期和現(xiàn)代時(shí)期的內(nèi)在規(guī)則、前提和規(guī)范程序。特別是,他分析出“人”是隨著生命科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和語(yǔ)言學(xué)的興盛而誕生的。簡(jiǎn)言之,“人”是現(xiàn)代時(shí)期推論出來(lái)的產(chǎn)物。具體來(lái)說(shuō),隨著古典時(shí)期表現(xiàn)模式的解體,人類第一次不僅成為求知的主體,而且成為現(xiàn)代科學(xué)研究的對(duì)象。不過(guò)從一開(kāi)始,“人”這個(gè)概念就十分矛盾,它身兼兩職,既是認(rèn)識(shí)的主體,也是被經(jīng)驗(yàn)科學(xué)研究的對(duì)象,即它是“構(gòu)成者與被構(gòu)成者”的混合體。但是,隨著20世紀(jì)的到來(lái),各種新科學(xué)相繼問(wèn)世,諸如“精神分析理論”、“語(yǔ)言學(xué)”和“人種學(xué)”等,使得人作為認(rèn)識(shí)主體的地位岌岌可危,主體不再是認(rèn)識(shí)和主宰對(duì)象的出發(fā)點(diǎn),而是語(yǔ)言、欲望和無(wú)意識(shí)的結(jié)果和產(chǎn)物,因而“人”也就隨之死亡。
質(zhì)疑線性進(jìn)步觀
現(xiàn)代歷史觀把歷史看成是在時(shí)間緯度上逐漸積累式的進(jìn)步,它一勞永逸地拋棄了倒退的、停滯的觀念,樹立起樂(lè)觀主義。福柯對(duì)這種傳統(tǒng)的歷史線性進(jìn)步觀進(jìn)行了批判的質(zhì)疑。線性進(jìn)步觀是假定作為一個(gè)整體的人類是不斷進(jìn)步的,理性歷史的自我轉(zhuǎn)換就像生物學(xué)家構(gòu)想種類歷史的進(jìn)步一樣,是不斷進(jìn)步、不斷發(fā)展,是辯證地向前推動(dòng)的。福柯強(qiáng)調(diào)這種幻想“不是科學(xué)這樣說(shuō),而是科學(xué)史這樣說(shuō),此外,我并不是說(shuō)人性不進(jìn)步,我想說(shuō)的是,提出諸如‘我們是如何進(jìn)步的?’這類問(wèn)題是一種壞方法。問(wèn)題是‘事情如何發(fā)生?’而且現(xiàn)在所發(fā)生的并不比過(guò)去發(fā)生的更好、更先進(jìn)、更好理解”。③
福柯認(rèn)為歷史進(jìn)步是一種先驗(yàn)的目的論,它預(yù)設(shè)著一個(gè)人們持之以恒地向之運(yùn)動(dòng)的事先給定的目標(biāo)。這種目標(biāo)又是在線性的編年史時(shí)間中展開(kāi),因此編年史時(shí)間是對(duì)經(jīng)驗(yàn)作形式化處理的不加思考的一種背景或一套先驗(yàn)的框架。它具有魔法一樣的功能,一方面,僅僅由于時(shí)間的先后就有了新與舊、創(chuàng)新與模仿的區(qū)別和不同價(jià)值等級(jí)的區(qū)別;另一方面,無(wú)論是怎樣矛盾、不相容、斷裂、模糊、不可越的現(xiàn)象,一旦被納入這套框架中被重新組合和裝配后,歷史就變成了理想的、連續(xù)的,從而具有了生命。合理性變成人類的命運(yùn)或目的,并且運(yùn)用一些先驗(yàn)的話語(yǔ)單位維護(hù)這種目的。
福柯的系譜學(xué)和考古學(xué)方法中斷了思想史的先驗(yàn)?zāi)康恼摰倪B續(xù)過(guò)程,拋棄了樂(lè)觀主義的歷史發(fā)展論。它認(rèn)為,并不是任何事情都會(huì)一天天變得進(jìn)步起來(lái)。實(shí)際上,事情將更多地與其所處的具體的環(huán)境和形勢(shì)有關(guān),而不是被捆綁在一種必然性上面;事情將更具有一種隨意的性質(zhì),而非不言而喻的;事情將更為復(fù)雜,更有臨時(shí)性和歷史性,而不是由不可避免的人類學(xué)常數(shù)來(lái)決定。西方主流傳統(tǒng)中的理性、進(jìn)步觀念與瘋癲、犯罪一樣都是特定社會(huì)話語(yǔ)和非話語(yǔ)實(shí)踐建構(gòu)的,在不同時(shí)期會(huì)有不同的意義。歷史是知識(shí)――權(quán)力體系的轉(zhuǎn)換,它又會(huì)在一定條件下打破它,重建另一個(gè)知識(shí)――權(quán)力體系,我們不能抽象地說(shuō)這種轉(zhuǎn)換是否存在著由低向高的進(jìn)步。
拒絕歷史總體化
福柯反對(duì)理性、進(jìn)步的矛頭直指啟蒙以來(lái)現(xiàn)代性有關(guān)總體性、壓抑性的宏大話語(yǔ)霸權(quán)。理性的求真精神根本不是為了所謂的人類解放、進(jìn)步主題,只是另一種控制性力量而已。自啟蒙以來(lái),理性通過(guò)掩飾和壓制多元性、差異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強(qiáng)制性力量。福柯的一個(gè)重要任務(wù)就是要擾亂它,恢復(fù)話語(yǔ)的多元性、差異性和增殖性,給予被排斥、遺忘、邊緣化的主題如瘋癲話語(yǔ)、懲罰話語(yǔ)、性話語(yǔ)、街頭野史、不入流的作品足夠的關(guān)注。他用這些微觀話語(yǔ)對(duì)抗宏大話語(yǔ)的霸權(quán),取消整體歷史優(yōu)先權(quán)。如果說(shuō)在歷史元敘述中,抽象的宏大敘事占據(jù)了歷史敘述的講壇,歷史成了大寫的歷史的話,那么,福柯的學(xué)說(shuō)則是排除了傳統(tǒng)的歷史講壇的微觀敘事,把單數(shù)、大寫的歷史拆散成眾多的、復(fù)數(shù)的、小寫的歷史。
在《知識(shí)考古學(xué)》中,福柯堅(jiān)決反對(duì)總體化的觀念史,并描述了觀念史上發(fā)生的突變帶來(lái)的革命性后果:“它已分離了由意識(shí)的進(jìn)展、理性的目的論或人類思想的發(fā)展構(gòu)建的漫長(zhǎng)系列;它已質(zhì)疑了匯聚和完成這兩個(gè)論題;它已懷疑了總體化的可能性。它導(dǎo)致了不同系列之個(gè)體化……”④總體歷史觀念是一種目的論,即認(rèn)為人類是有目的地朝著某個(gè)預(yù)先決定的目標(biāo)從低到高前進(jìn)的,而福柯則要表明,由意識(shí)發(fā)展和理性目的論提出的總體化是不可能的。
福柯反對(duì)史學(xué)家和哲學(xué)家使用世界理想類型和時(shí)代精神這樣的文化總體性的范疇,他要用系列、界限、偶然來(lái)質(zhì)疑目的論和總體化。他主張用通史來(lái)取代總體史。因?yàn)榭傮w史“設(shè)法重構(gòu)一個(gè)文明的總體形式,一個(gè)社會(huì)的物質(zhì)或精神原則,一個(gè)時(shí)期的所有現(xiàn)象所共有的意蘊(yùn),說(shuō)明這些現(xiàn)象的連貫性規(guī)律,即人們用隱喻所說(shuō)的一個(gè)時(shí)期的‘面貌’”。⑤而通史則討論系列、區(qū)分、界限、斷裂、起伏、變化、轉(zhuǎn)換、差距、年代學(xué)特征等特殊形式、可能的關(guān)系類型。因?yàn)榭傮w史把所有的現(xiàn)象都?jí)嚎s在唯一的核心,即原則、意義、精神、世界觀、總體形式的周圍。而通史正好與此相反,通史將展現(xiàn)無(wú)主體的、分散的、非中心的、充塞著各種偶然性的多樣化空間。
總體歷史觀是把大寫的理性、大寫的主體確立為原則和核心,并進(jìn)而用這樣的抽象原則和核心來(lái)統(tǒng)領(lǐng)所有的文明現(xiàn)象。福柯對(duì)總體歷史觀的批判,是通過(guò)清算以往哲學(xué)中的總體化哲學(xué)理論來(lái)進(jìn)行的。福柯批判位于現(xiàn)代歷史意識(shí)和歷史核心處的康德的總體化的人類學(xué)中心主義,因?yàn)榭档掳沿毞Φ摹⒂邢薜闹黧w的構(gòu)造力轉(zhuǎn)變成了所有知識(shí)的先驗(yàn)條件,把歷史看做連續(xù)的進(jìn)步和久遠(yuǎn)的集體意識(shí);黑格爾歷史哲學(xué)是典型的總體化歷史主義。福柯不僅反對(duì)康德有限主體的總體化,而且也反對(duì)黑格爾絕對(duì)精神的總體化;福柯批判了馬克思那樣的總體化理論思考和總體化分析。福柯認(rèn)為理論是實(shí)踐,是局部的、地區(qū)性的和非總體化的實(shí)踐,是用來(lái)構(gòu)造適于讀者使用的工具的,而不是用來(lái)構(gòu)建具有永恒真理的體系的。
總之,福柯的研究成果對(duì)當(dāng)代西方歷史學(xué)和哲學(xué)的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福柯的哲學(xué)是一種獨(dú)特的哲學(xué),他不像其他哲學(xué)家那樣論述歷史上大哲學(xué)家的思想,也不討論傳統(tǒng)的哲學(xué)概念,而是通過(guò)一些從未被哲學(xué)家注意的邊緣領(lǐng)域如瘋癲、疾病、犯罪、性等的歷史考察來(lái)分析哲學(xué)問(wèn)題。福柯就是這樣將哲學(xué)主題引入歷史中,表層是歷史分析,深層是哲學(xué)思考,在歷史研究中包含著一套獨(dú)特的歷史哲學(xué)思想和方法論。福柯運(yùn)用考古學(xué)、系譜學(xué)方法嚴(yán)厲地批判了傳統(tǒng)的歷史主義,打破“歷史神話”,重塑“真實(shí)的歷史”,并對(duì)傳統(tǒng)的西方歷史理性、主體、進(jìn)步、總體化等問(wèn)題提出挑戰(zhàn),瓦解了傳統(tǒng)歷史觀念的根基,為我們研究歷史和哲學(xué)提供了一個(gè)全新的思路。從而也造就了福柯哲學(xué)無(wú)與倫比的魅力。
注釋:
①劉北成:《當(dāng)代法國(guó)思潮變遷與福柯》(前言),載劉北成編著:《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轉(zhuǎn)引自余章寶:《散亂的歷史――福柯后現(xiàn)代主義歷史觀》,《史學(xué)理論研究》,2001(1)。
③王利民:《解釋過(guò)去了解現(xiàn)在――從系譜學(xué)看福柯的歷史社會(huì)觀》,《社會(huì)》,2000(12)。
④⑤轉(zhuǎn)引自莫偉民:《論福柯非歷史主義的歷史觀》,載于《復(fù)旦學(xué)報(bào)(社科版)》,2001(3)。
篇6
關(guān)鍵詞:音樂(lè)藝術(shù);圖譜學(xué);圖像學(xué);書籍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相互補(bǔ)充;互為關(guān)聯(lián)
中圖分類號(hào):J0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近現(xiàn)代以來(lái),伴隨著歷史文化的轉(zhuǎn)型和學(xué)術(shù)思潮的風(fēng)起云涌,各種學(xué)術(shù)思想、方法和學(xué)科概念不斷翻新變化。如以科技文化為唯一標(biāo)準(zhǔn)發(fā)展階段,所有學(xué)科層層剝離,新學(xué)科概念汗牛充棟,而隨著“多元文化”理念的回歸,相近的學(xué)科嫁接交融、合而為一等,又成為一種全新的時(shí)代風(fēng)尚。擺在我們面前的有關(guān)圖譜圖像之學(xué)與書籍文獻(xiàn)之學(xué)的古今關(guān)系與現(xiàn)實(shí)意義問(wèn)題,就是這一時(shí)代文化背景下不得不重新提及和需要認(rèn)真探討的學(xué)術(shù)命題,要分辨二者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互為關(guān)系,及至和相關(guān)學(xué)科理論體系之間的關(guān)系,有必要從我國(guó)歷史文化、學(xué)術(shù)文化形成與發(fā)展的脈絡(luò)與接續(xù)關(guān)系等方面,進(jìn)行全面細(xì)致的梳理與分析。
一、歷史文明接續(xù)關(guān)系
在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歷史文明傳承發(fā)展的進(jìn)程中,圖像文化與文字文化的形式,相互接續(xù),相互映襯,形影相隨,不離不棄,在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又反映出不同的時(shí)代特征。筆者將其劃分為五個(gè)歷史階段,即圖像文明時(shí)代、圖文接續(xù)時(shí)代、圖文并存時(shí)代、文盛圖衰時(shí)代和圖像時(shí)代的回歸。
其一,圖像文明時(shí)代。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曾經(jīng)歷過(guò)圖像時(shí)代,即在我國(guó)語(yǔ)言文字尚未形成之前,先民們?cè)?jīng)有過(guò)一個(gè)漫長(zhǎng)的以圖記事、以圖說(shuō)事和以圖表情達(dá)意的時(shí)代,故圖像文化應(yīng)是早于語(yǔ)言文字而獨(dú)立存在的中華早期文明之一。而當(dāng)語(yǔ)言文字逐步取代了其功能和地位后,圖像則又轉(zhuǎn)化為一種藝術(shù)文化的形式,并在學(xué)術(shù)文化研究的平臺(tái)上得以綿延傳承。如《通志》說(shuō):“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xué)由此而生;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xué)由此而生。圖成經(jīng),文成緯;一經(jīng)一緯錯(cuò)綜成文。古之學(xué)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1]
伴隨著舊石器、新石器、青銅器時(shí)代等歷史期的變遷,圖像文化的形態(tài)也不斷地發(fā)生變化,如青海大通出土新石器時(shí)代彩陶盆上的舞蹈紋[2],江蘇省蘇州市中吳區(qū)江陵山出土新石器時(shí)代良渚文化墓葬的透雕冠狀舞蹈紋玉飾[3],包括分別見(jiàn)于甘肅大地灣、云南滄源、廣西花山、內(nèi)蒙古陰山、新疆昆侖山等地的巖畫、地畫圖像,以及全國(guó)各地出土后世各個(gè)時(shí)代的各種圖像,足以反映出這種圖像文明永恒的生命活力。
其二,圖文接續(xù)時(shí)代。據(jù)考證,作為具有中華文明象征意義的中國(guó)文字,是由先民們勾勒勾畫的表現(xiàn)世間萬(wàn)象的圖形圖畫漸漸地演化而成。如“象”字的產(chǎn)生,即緣于人和大象密切接觸的歷史基礎(chǔ)。上古時(shí)代,商人馴化大象,役象代勞,并根據(jù)象的形象創(chuàng)造了“象”字。“象”在漢語(yǔ)中最初是名詞,以后才引申和轉(zhuǎn)化出“現(xiàn)象”、“象征”、“想象”等意思。[4]安陽(yáng)殷墟遺址出土甲骨文中,可見(jiàn)“象”字的初始形態(tài)“”。
到了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由于氣候變化等多種原因,象在中原地區(qū)絕跡。如韓非子說(shuō):“人希見(jiàn)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5]也因于此種歷史的緣故,位居中原腹地的河南省簡(jiǎn)稱“豫”字,主體框架為“象”,其詳細(xì)字義為:形聲,從象,予聲。本義:大象。如《說(shuō)文》說(shuō):“豫,象之大者。”[6]中國(guó)字則被稱之為“象形”文字。關(guān)于中國(guó)文字(漢字)的起源,至今仍是一個(gè)未解之謎,考古發(fā)現(xiàn)最早的遺存,是安陽(yáng)殷墟出土商代后期(約公元前14世紀(jì))已初步定型的文字――甲骨文。這種“象形”的文字,應(yīng)是我國(guó)圖文接續(xù)時(shí)代的有效見(jiàn)證。
其三,圖文并存時(shí)代。世上任何一種人類文化形式的出現(xiàn),都要經(jīng)過(guò)人們長(zhǎng)期的生產(chǎn)生活實(shí)踐磨礪和體悟的過(guò)程,而一種文化形式取代另一種文化形式,也需要經(jīng)歷一個(gè)漫長(zhǎng)的過(guò)渡時(shí)期,包括一方的漸興、二者重疊和另一方減退等過(guò)程,圖像與文字兩種文化形式的交替,也存在著這樣一種漸進(jìn)的接續(xù)關(guān)系,而且二者之間肯定有著一個(gè)較長(zhǎng)時(shí)間的并存期。
關(guān)于我國(guó)古代的圖譜圖像與書籍文獻(xiàn)長(zhǎng)期并存與發(fā)展的歷史,在先秦時(shí)代的古文獻(xiàn)中也有相關(guān)記載。如《周易?系辭上》說(shuō):“天垂象,見(jiàn)吉兇,圣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7]這段在古人長(zhǎng)期的口頭文化傳播基礎(chǔ)上的文字記載,將圖像文化和書籍文化這兩種先后生成的文化形式并置為同一源頭,雖有一些夸飾、捏合的成分,但卻并非子虛烏有的憑空想象或神話傳說(shuō),而是以一種高度集中概括和精煉生動(dòng)的比擬手法,奇特傳神地把我國(guó)歷史文明形成與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一些不朽的歷史印跡連綴在了一起,簡(jiǎn)約而又翔實(shí)地記述了我國(guó)圖像文化與文字文化曾經(jīng)并存發(fā)展的歷史信息。
其四,文盛圖衰時(shí)代。隨著自漢以來(lái)我國(guó)古文字的逐步簡(jiǎn)化和定型,人們漸漸地用簡(jiǎn)約的文字文獻(xiàn)取代了圖譜圖像的實(shí)用功能,以至于逐步呈現(xiàn)出文字繁盛、圖像日衰的發(fā)展趨勢(shì)。如《通志》說(shuō):“……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qǐng)D;班固即其書為《藝文志》。自此以遠(yuǎn),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后學(xué)而墮良材者,皆由于此。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1]上文十分清晰地描述了“圖譜之學(xué)”和“書籍之學(xué)”之間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即“圖成經(jīng),文成緯,一經(jīng)一緯錯(cuò)綜成文”,及至漢代文字通行,著書立說(shuō)只用文字不用圖像,導(dǎo)致“圖譜日亡,書籍日冗”現(xiàn)象,預(yù)示著文盛圖衰時(shí)代的出現(xiàn)。
其五,圖像時(shí)代回歸。20世紀(jì)以來(lái),鑒于古文獻(xiàn)記載已不能滿足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研究之需的原因,圖像研究再度成為學(xué)界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并在世界范圍內(nèi)興盛蔓延,西方國(guó)家較前一步完成了作為現(xiàn)代學(xué)科屬性的圖像學(xué)學(xué)科理論與方法體系。作為一名哲學(xué)家的睿智與敏查,海德格爾于1938年就宣布到了“世界圖像時(shí)代”[8]的到來(lái)。
通過(guò)數(shù)十年來(lái)的發(fā)展蔓延,海氏預(yù)言已經(jīng)在學(xué)術(shù)實(shí)踐中得到了有效驗(yàn)證,世界各國(guó)、各民族及其諸多相關(guān)學(xué)科,都廣泛地運(yùn)用讀圖、說(shuō)圖和研圖的方法,從而全面呈現(xiàn)了圖像時(shí)代歷史性回歸的壯觀景象。當(dāng)然,圖像時(shí)代回歸的另一含義,是指以現(xiàn)當(dāng)代科技文化高度發(fā)達(dá)為標(biāo)志的視頻、視像,以其直觀、逼真和富有色彩的生動(dòng)畫面,再次撼動(dòng)了以文字為載體書籍文獻(xiàn)之學(xué)的一統(tǒng)地位。
二、史學(xué)研究互為關(guān)系
對(duì)于古代歷史學(xué)、文化學(xué)的研究,我國(guó)學(xué)人長(zhǎng)期以來(lái)探索實(shí)踐了多種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最具影響力的是自漢以來(lái)以書籍文獻(xiàn)為主體史學(xué)研究的方法,其次是以圖譜圖像和北宋時(shí)代肇始的“金石學(xué)”,以及近現(xiàn)代引入西方國(guó)家考古學(xué)、圖像學(xué)等以實(shí)物考據(jù)為主體的研究方法,它們之間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互為關(guān)聯(lián)。
1.書籍文獻(xiàn)史學(xué)研究
書籍文獻(xiàn)史學(xué)研究,在我國(guó)學(xué)界素有文獻(xiàn)考據(jù)之說(shuō),指對(duì)古代文字記述的史料進(jìn)行考證、辨析和闡釋解讀的一門學(xué)問(wèn)。由于文字記述有著比圖形圖像簡(jiǎn)便快捷的突出功效,自漢以來(lái)它逐步發(fā)展演變成為著史和進(jìn)行史學(xué)研究的主要方法。
“文獻(xiàn)”一詞,最早見(jiàn)于孔子《論語(y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證)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xiàn)不足之故也。”[9]在古代,文,指有關(guān)典章制度的文字記載;獻(xiàn),指見(jiàn)多識(shí)廣,熟悉歷史的賢人。
元代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中說(shuō):“文,典籍也;獻(xiàn),賢者也。”認(rèn)為“文”是經(jīng)史、會(huì)要、傳記等書本,可以互相參證史事;“獻(xiàn)”是學(xué)士名流的言論紀(jì)錄,可以用來(lái)考訂典故、史傳的是非。[10]簡(jiǎn)言之,文獻(xiàn)是指典籍記載與學(xué)士名流的言論。
我國(guó)古代將古文獻(xiàn)整理和研究工作叫做“校讎”,故有校讎學(xué)之稱謂。傳統(tǒng)文獻(xiàn)學(xué)正是在校讎、目錄、版本諸學(xué)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lái)的,即指研究古典文獻(xiàn)的源流、特點(diǎn)、處理原則、方法(如分類、目錄、版本、辨?zhèn)巍⑿?薄⒆⑨尅⒕幾搿⑤嬝龋┘袄玫囊婚T學(xué)問(wèn)。其宗旨為“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關(guān)于對(duì)待歷史的態(tài)度問(wèn)題,孔子說(shuō):“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11]這充分反映出,作為我國(guó)儒家學(xué)派創(chuàng)始人的孔子,尊重史實(shí)、重視傳統(tǒng)的優(yōu)秀品質(zhì),也為后世學(xué)人治史、證史和論史提供了有益的思想理論基礎(chǔ)。
總之,采用古文獻(xiàn)考據(jù)的方法,研究的對(duì)象主要是代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精髓的“經(jīng)”、“史”部分,它們構(gòu)成了歷代史料文獻(xiàn)的主干,“證經(jīng)補(bǔ)史”即成為中國(guó)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務(wù)。其優(yōu)長(zhǎng)和不足之處分述于下。
其一,書籍文獻(xiàn)史學(xué)研究的優(yōu)長(zhǎng)。
自《史記》作為中國(guó)封建王朝第一部國(guó)家史典問(wèn)世以來(lái),之后的每個(gè)朝代都有以此為例的官修史書,其中多有《禮樂(lè)志》《樂(lè)志》《藝文志》《音樂(lè)志》等記錄宮廷樂(lè)文化發(fā)展?fàn)顩r和具體活動(dòng)的部分。歷代官史文獻(xiàn)中的內(nèi)容,分別以記述帝王之事、王侯及特殊人物、年代世系和人物、典章制度、人物民族及國(guó)外諸事等為主體,是在所謂國(guó)之大事即時(shí)性在案記錄基礎(chǔ)上的編纂整合,故被尊為“國(guó)史”、“正史”,其余私人著述的此類書目則被稱作“野史”。后世學(xué)人一般認(rèn)為,“正史”中的內(nèi)容具有較高的可采信度,故歷代“正史”中關(guān)于音樂(lè)方面的記載,即成為古代音樂(lè)史學(xué)研究的主要對(duì)象。
其二,書籍文獻(xiàn)史學(xué)研究的不足。
在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學(xué)術(shù)研究實(shí)踐中,學(xué)人們不斷發(fā)現(xiàn)古代書籍文獻(xiàn)中存在著較多的遺漏、不實(shí)和自相矛盾等方面的諸多問(wèn)題,如著名音樂(lè)學(xué)家黃祥鵬先生所舉《樂(lè)問(wèn)》[12]百題,就是由于官史文獻(xiàn)的不詳或自相矛盾,造成后世學(xué)人的困惑和無(wú)所適從,以至于逐步形成了許多千年死結(jié)。“正史”文獻(xiàn)中的不足之處,大概有如以下幾個(gè)方面:一是古代文字記載的簡(jiǎn)約和多義性特征,致使后人無(wú)法讀懂其意;二是同一歷史事象,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會(huì)留下不同的信息;三是同一事象在口口相傳過(guò)程中,難免出現(xiàn)演繹夸飾成分,形成一些虛假信息;四是基于王權(quán)文化一統(tǒng)地位政治的訴求,有計(jì)劃和有目的地虛捧抬高或詆毀打壓某一歷史文化主體,造成蓋棺論定的虛假歷史信息;五是鑒于古代文字記述方式的單一,包括甲骨文、金文、木牘、竹簡(jiǎn)等文字載體,傳承和流通都存在著較大困難,極易丟失和損毀,造成史料文獻(xiàn)遺失現(xiàn)象嚴(yán)重;六是歷代官史中主要記述宮廷樂(lè)事,廣大社會(huì)的音樂(lè)生活則較少涉及,這對(duì)于中國(guó)音樂(lè)史的系統(tǒng)研究來(lái)說(shuō),無(wú)疑存在著較多的問(wèn)題。
2.圖譜圖像史學(xué)研究
所謂圖譜圖像,最初僅指人類文明肇始以來(lái)通過(guò)繪畫、雕塑等方式,記錄保存社會(huì)萬(wàn)象的圖形圖像和銘文等,近現(xiàn)代在西方國(guó)家興起的圖像學(xué),漸漸地把研究范圍擴(kuò)展至出土相關(guān)實(shí)物的照片等。
在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學(xué)術(shù)研究實(shí)踐中,由于史料文獻(xiàn)的不足、艱澀與語(yǔ)義不詳?shù)仍颍覈?guó)歷代學(xué)人一直十分看重圖像的史學(xué)研究?jī)r(jià)值。肇始于東漢時(shí)期的“古學(xué)”就包含有圖像研究的成分,魏晉以來(lái)金石圖像考據(jù)之風(fēng)漸盛,至北宋時(shí)期形成了以“證經(jīng)補(bǔ)史”為宗旨的“金石學(xué)”的學(xué)問(wèn),并在清朝成為顯學(xué)。關(guān)于金石學(xué),朱劍心認(rèn)為:“‘金’是以鐘鼎彝器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錢幣、鏡鑒等物,凡古銅器之有銘識(shí)或無(wú)銘識(shí)者皆屬之;‘石’是以碑碣墓志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經(jīng)幢、柱礎(chǔ)、石闕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圖像者皆屬之;那么,‘金石學(xué)’則是研究中國(guó)歷代金石之名義、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圖像之體例、作風(fēng);上自經(jīng)史考定、文章義例,下至藝術(shù)鑒賞之學(xué)也。”[13]可見(jiàn),金石學(xué)研究包含有音樂(lè)的器物和圖像;金石學(xué)的宗旨目的,除“補(bǔ)經(jīng)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以外,還有著辨章學(xué)術(shù)、藝術(shù)審美之學(xué)等十分寬泛的內(nèi)涵和外延。關(guān)于金石學(xué)的學(xué)術(shù)方法,“大約不出于著錄、摹寫、考釋、評(píng)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錄其文者,有圖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記載者,有分類編纂者。或考其時(shí)代,或述其制度,或釋其文字,或評(píng)其書跡,至為詳備。”[13](p.20)應(yīng)該說(shuō),這里面特別值得珍惜和弘揚(yáng)的是,我國(guó)一以貫之的綜合性、包容性學(xué)術(shù)文化理念。
其一,圖譜圖像史學(xué)研究的優(yōu)長(zhǎng)。
遺存不同時(shí)期豐富多彩的藝術(shù)圖像,有著直觀展現(xiàn)古代社會(huì)歷史文化基本形態(tài)與風(fēng)貌的突出功能,尤其是如和人類的生產(chǎn)生活密切相關(guān)并在上古時(shí)代建立起崇高地位的樂(lè)舞文化,本身具有瞬間即失的令人遺憾的屬性,歷史上所保留下來(lái)的只有文字的表象述說(shuō),而無(wú)樂(lè)舞藝術(shù)本體的東西留駐于世。在近現(xiàn)代以來(lái)考古發(fā)現(xiàn)的地下遺存中,見(jiàn)有大量以樂(lè)舞為主體的綜藝圖像和一些樂(lè)器實(shí)物,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再現(xiàn)了我國(guó)古代樂(lè)舞藝術(shù)包羅萬(wàn)有的形式形態(tài),以及一些樂(lè)器當(dāng)時(shí)的形制規(guī)格、放置與演奏方式、組合方式、藝術(shù)表現(xiàn)等鮮為人知的內(nèi)容,這些彌足珍貴的帶有直觀性的圖譜信息,相對(duì)于十分簡(jiǎn)約的古文字記載來(lái)說(shuō),具有更大的實(shí)用性參考價(jià)值,而且這種藝術(shù)的圖像既有著長(zhǎng)久持續(xù)傳播的縱向連續(xù)性,又有著廣布于社會(huì)的橫向普及性,形成了具有歷史文化價(jià)值和學(xué)術(shù)研究?jī)r(jià)值的宏大體系,從而受到眾多研究者的密切關(guān)注,成為古代藝術(shù)發(fā)展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其二,圖譜圖像史學(xué)研究的不足。
圖譜之學(xué)及現(xiàn)代的圖像學(xué)作為一種學(xué)術(shù)的方法并非完美無(wú)缺,它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有著許多明顯的不足之處。比如對(duì)于音樂(lè)形態(tài)的研究,它只能有效展示演奏、演唱與表演的形式形態(tài),卻無(wú)法準(zhǔn)確證明樂(lè)器的具體規(guī)格,不能還原音樂(lè)的樂(lè)調(diào)和聲響;另如自漢以前的藝術(shù)圖像,雖被學(xué)界譽(yù)為寫實(shí)性藝術(shù),但畢竟存在夸飾、想象的成分,需要通過(guò)其他資料予以互證;再如因當(dāng)時(shí)圖像載體材質(zhì)和表現(xiàn)手法等的局限,畫面細(xì)節(jié)漶漫不清,或由于畫工常識(shí)欠缺或技術(shù)失誤等原因,造成畫面上樂(lè)器形制的失真、變形或演奏形態(tài)的不一;特別是即便我們通過(guò)深入細(xì)致地考證研究,理清了其所有的環(huán)節(jié)之后,這種研究依然不能夠復(fù)原古代音樂(lè)的本體形象,故圖譜圖像的研究也和書籍文獻(xiàn)的研究一樣,存在著先天的局限和不足。
總而言之,在中國(guó)數(shù)千年歷史文明和文化發(fā)展衍變的過(guò)程中,圖文兩種文化現(xiàn)象從無(wú)到有,續(xù)斷蔓延,盛衰起伏,變幻無(wú)常,既分別從不同角度為后人勘驗(yàn)歷史提供了大量重要的佐證,又分別顯示出其難以逾越的不足之處。我們現(xiàn)在所要做的是,不要拘泥于某一局域或某種單一的學(xué)術(shù)方法,而應(yīng)放開(kāi)眼界,破除禁錮,從“多元文化”的宏觀視野入手,把所有的可資利用的學(xué)術(shù)資源匯集到一個(gè)平臺(tái)上,全面實(shí)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文化的接軌,方能在多種資料和成果的互證下,全面揭示古代藝術(shù)文化發(fā)展史的面貌。所以筆者認(rèn)為,圖譜圖像之學(xué)與書籍文獻(xiàn)之學(xué),在中國(guó)古代藝術(shù)史、文化史研究的平臺(tái)上是一種互為的關(guān)系。
3.學(xué)術(shù)網(wǎng)絡(luò)體系關(guān)系
如前所述,自漢以來(lái)我國(guó)進(jìn)入文盛圖衰和以文字著述為主體學(xué)術(shù)文化發(fā)展期,而由于歷代學(xué)人并未放棄“圖譜之學(xué)”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可視性作用,使得圖、文兩種學(xué)術(shù)方法得以并存互惠,相得益彰。面對(duì)全球性圖像文化回歸的歷史潮流,二者順其自然地復(fù)原其本元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學(xué)術(shù)網(wǎng)絡(luò)體系。
三、本源性學(xué)術(shù)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
鑒于我國(guó)古老悠久的“圖譜之學(xué)”與“書籍之學(xué)”,在歷經(jīng)數(shù)千年傳承接續(xù)的歷史文化發(fā)展軌跡中,呈現(xiàn)出如江河之水一脈流貫、混溶交互、永無(wú)止息的永恒性特征,在學(xué)術(shù)研究及學(xué)術(shù)文化發(fā)展衍進(jìn)的過(guò)程中,也必然地表現(xiàn)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元文化屬性。雖然說(shuō)自漢以來(lái)“書籍之學(xué)”漸居統(tǒng)領(lǐng)地位,但歷代學(xué)人沿襲保留下來(lái)的“左圖右書”和“上圖下文、下圖上文、前圖后文”等學(xué)術(shù)習(xí)性,足以證明遠(yuǎn)古先民們?cè)杏齽?chuàng)造的圖像文化非但沒(méi)有就此消失,而且還在學(xué)術(shù)研究活動(dòng)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如《通志?圖譜略》:“天下之事,不務(wù)行,而務(wù)說(shuō),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yè),未有無(wú)圖譜而可行于世者。……圖譜之學(xué)不傳,則實(shí)學(xué)盡化為虛文也。……圖譜之學(xué),學(xué)術(shù)之大者。”[14]這充分說(shuō)明,歷代學(xué)人在學(xué)術(shù)理論理念的天平上,從來(lái)沒(méi)有放棄“圖譜之學(xué)”的重要學(xué)術(shù)地位,在學(xué)術(shù)研究的實(shí)踐中,總會(huì)將“圖譜之學(xué)”與“書籍之學(xué)”進(jìn)行必要的比照研究,從而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二者之間牢不可破的本源性學(xué)術(shù)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
1.本元性學(xué)術(shù)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
在我國(guó)學(xué)術(shù)文化發(fā)展的歷程中,從北宋“金石學(xué)”的勃興,到具有現(xiàn)代學(xué)科定義的考古學(xué)、考據(jù)學(xué)、古器物學(xué)、圖像學(xué)等相關(guān)現(xiàn)代學(xué)科的確立,學(xué)術(shù)研究的視角得到了有效的拓展,學(xué)術(shù)的理論和方法也隨之得到升華。20世紀(jì)以來(lái),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理念不斷翻新。從對(duì)以科技文化為中心“一元論”文化發(fā)展理念的質(zhì)疑,到后現(xiàn)代諸多新理念的問(wèn)世,學(xué)科交叉理論成為一種新趨向,致使杜威的“多元文化論”形成一股強(qiáng)大的國(guó)際性浪潮,并成為國(guó)際學(xué)界教育與學(xué)術(shù)研究領(lǐng)域最具前沿性的新理論、新視點(diǎn)和共同的學(xué)術(shù)取向。
目前,多元文化理論及學(xué)科交叉的理論和方法在我國(guó)日漸盛行,如歷史學(xué)、文化學(xué)、人類學(xué)、民族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等領(lǐng)域,都和藝術(shù)學(xué)諸學(xué)科之間產(chǎn)生密切交融,生成了許多種交叉學(xué)科的研究體系和方法,展示著新時(shí)期多元學(xué)術(shù)文化的繁榮景象。誠(chéng)然,這種在學(xué)科切塊基礎(chǔ)上的學(xué)科交叉并非絕對(duì)完美,甚至于某種程度上仍存在著“遠(yuǎn)交近分”的特征,即僅在遠(yuǎn)距離間的學(xué)科之間尋求接合點(diǎn),而對(duì)于本來(lái)就有著密切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的各姊妹藝術(shù)之間的關(guān)系,尚缺乏應(yīng)有的眷顧。然而,具有特殊意義的是,多元糅雜、兼容并包是數(shù)千年中華文化一以貫之的精神傳統(tǒng),如上古至中古時(shí)期融歌、詩(shī)、樂(lè)、舞、雜技、武術(shù)、幻術(shù)、繪畫、田獵、宴饗等為一體的“樂(lè)”文化體系,近古時(shí)期以來(lái)包容更多文化形式的戲曲藝術(shù)的精神理念等,至今依然深深地影響著中國(guó)人的審美價(jià)值與取向。歷經(jīng)近百年來(lái)的學(xué)科切塊分割而理念尚存,足以反映出這種民族文化根脈深邃雋永的存在價(jià)值。隨著多元文化理念的回歸,必然形成多元交織的學(xué)術(shù)網(wǎng)絡(luò)體系,歷經(jīng)數(shù)千年文化積淀的中國(guó)音樂(lè)文獻(xiàn)學(xué),與在“古學(xué)”、“金石學(xué)”學(xué)術(shù)文化傳統(tǒng)基礎(chǔ)上吸納西方考古學(xué)精髓的中國(guó)音樂(lè)圖像學(xué),必將在這個(gè)網(wǎng)絡(luò)體系中起到骨架作用。
2.交融性學(xué)術(shù)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
如前所述,兼容并包是中華文化的悠久傳統(tǒng),它所呈現(xiàn)的是多元文化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狀態(tài),彰顯的是中華泱泱大國(guó)海納百川、吞吐四方的文化精神。在數(shù)十年來(lái)學(xué)科分割的狀態(tài)中,較多呈現(xiàn)的是各學(xué)科、各專業(yè)之間的奇風(fēng)異彩,甚至于在同一專業(yè)領(lǐng)域也會(huì)出現(xiàn)輕重量化的差異,比如音樂(lè)的史與論是一個(gè)問(wèn)題的兩個(gè)方面,而在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歷程中,卻曾出現(xiàn)“重史輕論”或“重論輕史”的選擇,提出過(guò)“以史代論”、“以論代史”或“論從史出”等不同主張。
故筆者認(rèn)為,學(xué)科交叉僅為表象上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學(xué)術(shù)交融才是實(shí)質(zhì)性的進(jìn)展,而有效地打破原有各相關(guān)學(xué)科(或曰專業(yè)方向)之間的森嚴(yán)壁壘,方是實(shí)施學(xué)術(shù)交融的基本要件。如音樂(lè)史與論的研究,本來(lái)同屬音樂(lè)學(xué)的范疇,一味地細(xì)分彼此,極易陷入你高我低的內(nèi)耗之中,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將受到影響。同時(shí),過(guò)多的強(qiáng)調(diào)特殊性,就等于陷入了局限性。從另一個(gè)角度來(lái)講,自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神壇破碎之后,世界各國(guó)、各民族的學(xué)術(shù)文化傳統(tǒng)均得到了應(yīng)有的尊重、保護(hù)與弘揚(yáng),人文社會(huì)學(xué)科再次受到應(yīng)有的重視等,均為全球性學(xué)術(shù)文化的實(shí)質(zhì)融營(yíng)造了相對(duì)平等與和諧的氛圍,在此種大文化背景之下,書籍文獻(xiàn)之學(xué)與圖譜圖像之學(xué)二者形成良好的交融性學(xué)術(shù)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勢(shì)所必然。
四、結(jié)語(yǔ)
在中華民族古老悠久的歷史文化與學(xué)術(shù)文化傳統(tǒng)中,“圖譜之學(xué)”與“書籍之學(xué)”一直成為著史與論史的兩大支柱,作為具有現(xiàn)代學(xué)科定義的圖像學(xué)與文獻(xiàn)學(xué),仍應(yīng)是史學(xué)研究多元學(xué)術(shù)體系的主干。而由于當(dāng)今的學(xué)術(shù)觀念異彩紛呈,許多時(shí)候會(huì)構(gòu)成學(xué)術(shù)角色的轉(zhuǎn)換與互融,許多新問(wèn)題、新關(guān)系都需要我們一一關(guān)注和妥善處理。
1.學(xué)科關(guān)系
現(xiàn)代意義上的所謂不同學(xué)科,實(shí)際上僅是殊途同歸的學(xué)術(shù)研究的不同方法,它們之間往往會(huì)形成較為復(fù)雜的關(guān)系。如傳統(tǒng)的音樂(lè)考古學(xué)將音樂(lè)文物的實(shí)物和圖像作為一體研究對(duì)象,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和側(cè)面構(gòu)成了其共同的研究目標(biāo),而由于這兩種材料的研究側(cè)重點(diǎn)有所不同,漸漸地又形成了兩類各有所偏的研究成果和學(xué)人群體。音樂(lè)圖像學(xué)在西方國(guó)家的異軍突起,等于從整體上打破了原有的學(xué)科結(jié)構(gòu)和形成了學(xué)理關(guān)系上的新矛盾,而音樂(lè)圖像學(xué)不斷地拓展其研究的范圍,如旅美學(xué)者韓國(guó)介紹說(shuō):“凡舉一切和音樂(lè)有關(guān), 可以用圖片呈現(xiàn)出來(lái)的都能作為研究對(duì)象, 這就包括了樂(lè)器、人像、手稿、文件、建筑(如音樂(lè)家的生活及表演場(chǎng)所)、風(fēng)景(和音樂(lè)家之創(chuàng)作和文化背景有關(guān)者)及一切含有音樂(lè)主題的美術(shù)作品等等的圖像或照片,可以說(shuō)是包羅萬(wàn)象。”[15]這又從另一個(gè)側(cè)面反映了現(xiàn)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肢體細(xì)化分解之后再度交融的新趨勢(shì)。
2.古今關(guān)系
從圖譜之學(xué)到古學(xué)、金石學(xué)、考古學(xué)、圖像學(xué),形成了中國(guó)學(xué)術(shù)文化發(fā)展的系統(tǒng)鏈條,具有上千年學(xué)術(shù)發(fā)展史的金石學(xué),應(yīng)該說(shuō)既是現(xiàn)代考古學(xué)、圖像學(xué)的前身,又是一個(gè)承上啟下的坐標(biāo)。然而,實(shí)際情況如有學(xué)者說(shuō):“由于西方新學(xué)科的引入與中國(guó)教育制度的變革――從科舉到辦學(xué)堂,金石學(xué)的發(fā)展反而越來(lái)越離開(kāi)主流學(xué)問(wèn)而日趨邊緣化……在這種學(xué)術(shù)分類的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綜合的金石學(xué)遇到了意外的窘境。原有的金石學(xué)所包含的學(xué)術(shù)的內(nèi)容,被分別歸入了現(xiàn)代學(xué)科分類意義上的考古學(xué)、古器物學(xué)、鑒定學(xué)、考據(jù)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等。它的分支越來(lái)越強(qiáng)大而自成體格;而它本來(lái)的母體‘金石學(xué)’,卻在被稀釋、被分化、被零散化細(xì)密化之后,反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了。”①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接軌的中國(guó)音樂(lè)圖像學(xué)研究,則必須在“金石學(xué)”中找到立身之本。
3.中外關(guān)系
1997年初,先生在北京大學(xué)的演講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覺(jué)”的學(xué)術(shù)命題,該主張啟發(fā)引導(dǎo)了我國(guó)學(xué)界開(kāi)始了尋找逝去的珍貴文化傳統(tǒng)的努力。如有學(xué)者將歐文?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xué)研究三層次”理論[16]與中國(guó)“金石學(xué)”傳統(tǒng)范式進(jìn)行比較研究認(rèn)為:“我們發(fā)現(xiàn),這三個(gè)層次與中國(guó)漢畫像研究的金石學(xué)的范式、考古學(xué)的范式與文化藝術(shù)學(xué)的范式,可以有一種內(nèi)在的類比的邏輯關(guān)系。”[17]另有學(xué)者針對(duì)音樂(lè)圖像學(xué)領(lǐng)域里的偏頗指出:“中國(guó)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所以我們?cè)谝魳?lè)圖像學(xué)研究方法方面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洋,更不能將西洋學(xué)者的說(shuō)法當(dāng)成標(biāo)準(zhǔn),否定自己的成績(jī)。”[16]同時(shí),許多學(xué)者極力倡導(dǎo)金石學(xué)的現(xiàn)代學(xué)科價(jià)值,認(rèn)為金石學(xué)與近代科學(xué)的考古學(xué)在研究目標(biāo)上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如果只強(qiáng)調(diào)西方考古學(xué)理論和方法的影響,而忽視傳統(tǒng)金石學(xué)的傳遞作用,中國(guó)考古學(xué)就成了無(wú)源之水、無(wú)本之木。另如有學(xué)者在美學(xué)領(lǐng)域提出顛覆性新主張認(rèn)為:“中國(guó)沒(méi)有西方式的美學(xué),只有心性文化體系中‘天人一體’、禮樂(lè)交融的樂(lè)學(xué)。”認(rèn)為“近百年來(lái)中國(guó)美學(xué)誤入歧途,忽視了中西美學(xué)在學(xué)科形態(tài)上的根本區(qū)別。所謂中國(guó)當(dāng)代美學(xué),應(yīng)稱為‘西方認(rèn)識(shí)論美學(xué)在中國(guó)’。”[18]此觀點(diǎn)雖有待于學(xué)界進(jìn)一步切磋認(rèn)定,但其歷史的、現(xiàn)實(shí)的和學(xué)術(shù)的價(jià)值已經(jīng)昭然彰顯,且對(duì)于中國(guó)藝術(shù)學(xué)諸學(xué)科建設(shè)與學(xué)術(shù)研究來(lái)說(shuō),亦不無(wú)啟示性、建設(shè)性意義。
4.圖文關(guān)系
《周易》關(guān)于“河圖”、“洛書”之說(shuō)看似荒誕,實(shí)則銘心刻骨地記錄了古代學(xué)人對(duì)待圖、文兩種華夏文明遺存的深厚情結(jié),從一個(gè)側(cè)面呈示展現(xiàn)了我國(guó)圖文并重的學(xué)術(shù)文化傳統(tǒng)。雖然從表象上自漢以來(lái)文字文獻(xiàn)漸成為著述主體范式,而圖像作為延綿古今的傳統(tǒng)文化形態(tài),足以彌補(bǔ)國(guó)史文獻(xiàn)特別是社會(huì)文化生活記錄的空白和不足,二者還可以起到互證與互補(bǔ)的作用。同時(shí),我國(guó)不同時(shí)期的圖像遺存,有著量大面廣、持續(xù)傳承的典型特征,形成了自成一體的獨(dú)立學(xué)術(shù)系統(tǒng)。如有學(xué)者說(shuō):“圖像決不是文獻(xiàn)的視覺(jué)化,圖像的象征內(nèi)涵和意義也不是文獻(xiàn)的意義可以包容的。圖像本身構(gòu)成一個(gè)完整的世界,確定圖像本身的意義就是圖像學(xué)要達(dá)到的目的。”[1]
總之,文化自覺(jué)、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qiáng)是一個(gè)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文化振興的系統(tǒng)工程,沒(méi)有文化的自覺(jué),就不可能產(chǎn)生文化自信,沒(méi)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出現(xiàn)文化自強(qiáng),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構(gòu)建和諧發(fā)展新理念是第一要?jiǎng)?wù)。故無(wú)論是在我國(guó)數(shù)千年歷史文明傳承接續(xù)的文化傳統(tǒng)中,還是在多元交織的現(xiàn)代學(xué)科與學(xué)術(shù)文化網(wǎng)絡(luò)體系中,各種不同的學(xué)術(shù)理論和方法,既有著各自的獨(dú)立性意義,又同時(shí)反映出本源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學(xué)術(shù)文化特征和密切關(guān)聯(lián),由來(lái)已久的圖譜圖像之學(xué)與書籍文獻(xiàn)之學(xué)將永遠(yuǎn)是一對(duì)相依并存、和諧發(fā)展的互為關(guān)系。(責(zé)任編輯:帥慧芳)
① [ZK(#]潘諾夫斯基《圖像學(xué)研究》(1939年)、《哥特式建筑與經(jīng)院哲學(xué)》(1951年)、《早期尼德蘭繪畫》(1953年)、《視覺(jué)藝術(shù)的含義》(1955年)等著作,奠定了圖像學(xué)方法的基礎(chǔ)。[ZK)]
參考文獻(xiàn):
[1]鄭樵.通志?總敘[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3、365.
[2]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duì).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出土的舞蹈紋彩陶盆[J].文物,1978,(03).
[3]董錫玖、劉峻驤主編.中國(guó)舞蹈藝術(shù)史圖鑒[M].長(zhǎng)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7.
[4]陳政.字源趣談[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40.
[5]梁?jiǎn)⑿?韓非子淺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5.158-159.
[6]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說(shuō)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74.
[7]孔穎達(dá)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70.
[8]海德格爾全集(上卷)[M].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1996.885-923.
[9]孔子著,孔穎達(dá)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論語(yǔ)?八佾[M].北京:中華書局,1980.2466.
[10] [元]馬端臨撰.文獻(xiàn)通考自序[M].北京:中華書局,1986.3.
[11]孔子著,孔穎達(dá)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論語(yǔ)?為政[M].北京:中華書局,1980.2463.
[12]黃祥鵬.樂(lè)問(wèn)[M].北京: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出版社,2000.
[13]朱劍心.金石學(xu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3.
[14]鄭樵.通志?圖譜略[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837.
[15]陳振濂.金石學(xué)研究的當(dāng)代意義與我們的作用[J].藝術(shù)百家,2008,(03).
[16]杜亞雄.應(yīng)該正確評(píng)價(jià)中國(guó)音樂(lè)圖像學(xué)的成就[J].藝術(shù)百家,2010,(01).
[17]朱存明.漢畫像研究的圖像學(xué)方法[A].中國(guó)漢畫學(xué)會(huì)第十屆年會(huì)論文集[C].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60.
[18]吳高泉.中國(guó)沒(méi)有“美學(xué)”只有“樂(lè)學(xué)”――評(píng)《中國(guó)古代美學(xué)(樂(lè)學(xué))形態(tài)論》[N].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11-11-03.
Illustrated Iconography and Literature Philology
LI Rong-you
(Department of Musicology, Zhejiang College of Music, Hangzhou, Zhejiang 310002)
篇7
現(xiàn)狀簡(jiǎn)析
關(guān)于藝術(shù)學(xué)門類下相關(guān)一級(jí)學(xué)科的設(shè)置,最初國(guó)務(wù)院學(xué)位辦采取較為審慎的態(tài)度,提出最好設(shè)置3個(gè)一級(jí)學(xué)科的意見(jiàn)。應(yīng)該說(shuō),從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文化循序漸進(jìn)發(fā)展的角度,此意見(jiàn)無(wú)疑有著深厚的學(xué)理意義和現(xiàn)實(shí)意義。然而,為了解決多種因素而形成的各種矛盾,經(jīng)不同層面的多番研討和論爭(zhēng),最終突破了這一限制,通過(guò)了藝術(shù)學(xué)科評(píng)議組提出的藝術(shù)學(xué)門類下設(shè)藝術(shù)學(xué)理論、音樂(lè)舞蹈學(xué)、戲劇影視藝術(shù)學(xué)、美術(shù)設(shè)計(jì)藝術(shù)學(xué)等四個(gè)一級(jí)學(xué)科的議案。之后,為了兼顧相關(guān)學(xué)科的需求和要求,經(jīng)國(guó)務(wù)院學(xué)位委員會(huì)討論,又將美術(shù)設(shè)計(jì)藝術(shù)學(xué)一分為二,成為美術(shù)學(xué)和設(shè)計(jì)學(xué)(可授藝術(shù)學(xué)、工學(xué)學(xué)位),共計(jì)五個(gè)一級(jí)學(xué)科。一級(jí)學(xué)科確定后,我們亟待解決的是藝術(shù)學(xué)理論相關(guān)二級(jí)學(xué)科的設(shè)置問(wèn)題。由于藝術(shù)學(xué)作為學(xué)科門類、藝術(shù)學(xué)理論作為一級(jí)學(xué)科的建設(shè),屬于史無(wú)前例、無(wú)從參照的新事物,這就只有依靠藝術(shù)學(xué)理論界集體的智慧,一方面是“摸著石頭過(guò)河”,審時(shí)度勢(shì),邁好關(guān)鍵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要遵循和秉承傳統(tǒng)學(xué)科發(fā)展完善的理論理念及其長(zhǎng)期實(shí)踐的經(jīng)驗(yàn),兼容并蓄、提煉升華,客觀科學(xué)、扎實(shí)有序地實(shí)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接軌這一時(shí)代賦予的重要?dú)v史命題。在此用“史無(wú)前例”一詞,可能會(huì)遭到質(zhì)疑,因?yàn)榘倌昵拔鞣絿?guó)家就有了藝術(shù)學(xué)的學(xué)科概念,中國(guó)的藝術(shù)學(xué)也是得益于西方藝術(shù)學(xué)理論理念的影響而出現(xiàn)的一個(gè)新學(xué)科。但若進(jìn)行系統(tǒng)地分析即可看到,處在不同地域和國(guó)度的中西方藝術(shù)學(xué)之間,確實(shí)存在著定義、對(duì)象、范圍及其精神實(shí)質(zhì)等方面的較大差異。如貢布里希所言:“不同的時(shí)期、不同的地方,藝術(shù)這個(gè)名稱所指的事物會(huì)大不相同。”[3]
比如說(shuō)西方人口中的“藝術(shù)”慣性指向于美術(shù),中國(guó)的“藝術(shù)”則包含所有的藝術(shù)門類;西方的藝術(shù)學(xué)僅僅作為造型藝術(shù)的一般性理論,中國(guó)的藝術(shù)學(xué)則包含著多個(gè)藝術(shù)門類一級(jí)學(xué)科與二級(jí)學(xué)科的實(shí)體運(yùn)作系統(tǒng)。故此“藝術(shù)學(xué)”與彼“藝術(shù)學(xué)”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當(dāng)屬于世界學(xué)術(shù)文化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正常現(xiàn)象。我們不僅要尊重二者之間永恒的共性特征,又要尊重其不同區(qū)域、不同民族長(zhǎng)期積累而形成的文化差異,只有這樣,起步之腳才能踏向?qū)嵦帯T谒囆g(shù)學(xué)理論二級(jí)學(xué)科設(shè)置的醞釀過(guò)程中,如凌繼堯先生所強(qiáng)調(diào),大約遵循了以下兩個(gè)原則:第一個(gè)是傳統(tǒng)的原則,第二個(gè)是現(xiàn)實(shí)的原則。所謂傳統(tǒng)的原則,即根據(jù)傳統(tǒng)學(xué)科發(fā)展過(guò)程中所形成的固定的學(xué)術(shù)名稱、研究對(duì)象、范疇、命題、概念、術(shù)語(yǔ)和問(wèn)題域等設(shè)置相關(guān)二級(jí)學(xué)科。現(xiàn)實(shí)的原則,即擬設(shè)置的二級(jí)學(xué)科,一是能適應(yīng)現(xiàn)實(shí)的迫切需要,能夠?yàn)閲?guó)家和區(qū)域的社會(huì)發(fā)展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服務(wù),并且確有很多理論問(wèn)題值得研究;二是在現(xiàn)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已經(jīng)存在,并且取得一定的業(yè)績(jī),我們應(yīng)該給予它合法的地位,從而促進(jìn)它更好地發(fā)展;三是這個(gè)學(xué)科涉及多種藝術(shù)門類,而不僅僅涉及某一種藝術(shù)門類。根據(jù)以上關(guān)系準(zhǔn)則,提出了藝術(shù)學(xué)理論一級(jí)學(xué)科下設(shè)藝術(shù)史論、藝術(shù)批評(píng)學(xué)兩個(gè)傳統(tǒng)意義的基礎(chǔ)理論二級(jí)學(xué)科,以及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的“藝術(shù)創(chuàng)意和藝術(shù)管理”應(yīng)用理論二級(jí)學(xué)科的主張。[4]目前統(tǒng)一的學(xué)科設(shè)置標(biāo)準(zhǔn)尚未出臺(tái),不過(guò)據(jù)了解,在各高校自主設(shè)置的藝術(shù)學(xué)理論二級(jí)學(xué)科中,已經(jīng)涉及了藝術(shù)史、藝術(shù)理論、藝術(shù)批評(píng)、藝術(shù)管理、藝術(shù)創(chuàng)意、藝術(shù)教育、數(shù)字媒體藝術(shù)、藝術(shù)與科學(xué)等多個(gè)相關(guān)二級(jí)學(xué)科。
些許思慮
負(fù)責(zé)任地說(shuō),藝術(shù)學(xué)獨(dú)立為學(xué)科門類,既是長(zhǎng)期以來(lái)被邊緣化的藝術(shù)學(xué)科確立自身價(jià)值的大好機(jī)遇,又是對(duì)中國(guó)藝術(shù)學(xué)人的智力、魄力與理智的嚴(yán)峻挑戰(zhàn)。因?yàn)閷W(xué)科建設(shè)是百年大計(jì),起始階段尤為重要,最要緊的是要選準(zhǔn)方向、定好目標(biāo),邁出關(guān)鍵的第一步。仲呈祥先生在2011年5月于杭州舉行的“2011藝術(shù)學(xué)學(xué)科發(fā)展的新向度暨對(duì)策研究高端國(guó)際論壇”主題發(fā)言中也再次強(qiáng)調(diào):“作為民族文化建設(shè)的一個(gè)重要方面,藝術(shù)學(xué)應(yīng)該為民族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營(yíng)造良好的氛圍,以體現(xiàn)中國(guó)社會(huì)、時(shí)代的文明水準(zhǔn),改變當(dāng)下令人堪憂的人文藝術(shù)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現(xiàn)實(shí)情狀。”[1]8并諄諄告誡老師們“千萬(wàn)不要去搶地盤”,不要“為了整合資源,把人家人文學(xué)院的、歷史學(xué)院的、哲學(xué)院的等其他學(xué)院的老師全部拉過(guò)來(lái)申報(bào)。本來(lái)就是獨(dú)立門戶了,要以我為主了,結(jié)果又反客為主,這不行”。“有的時(shí)候,本校校內(nèi)的資源的共用也是可行的,這得有個(gè)度,不要搞成了拼湊。”[1]14然而,由于歷史的、現(xiàn)實(shí)的、中國(guó)的、外國(guó)的等多種矛盾的存在,在截至目前的實(shí)際操作過(guò)程中,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如仲呈祥等學(xué)者擔(dān)憂的一些搶地盤、拼資源等現(xiàn)象。比如相關(guān)二級(jí)學(xué)科的設(shè)置問(wèn)題,由于在現(xiàn)行的普通高校辦學(xué)水平評(píng)價(jià)機(jī)制中,擁有碩士點(diǎn)、博士點(diǎn)的數(shù)量是一項(xiàng)重要的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故各高校無(wú)不希望借此機(jī)會(huì)擴(kuò)大自己學(xué)科點(diǎn)的數(shù)量,以致在學(xué)科設(shè)置過(guò)程中出現(xiàn)“化整為零”、東拼西湊現(xiàn)象。更加值得深刻思考和檢討的是,藝術(shù)學(xué)理論本是旨在將藝術(shù)作為一個(gè)整體,從宏觀角度進(jìn)行綜合研究,以此貫通各門類藝術(shù)的共性內(nèi)容與本質(zhì)特征,探索體現(xiàn)各門類藝術(shù)共同性發(fā)展規(guī)律的一門基礎(chǔ)學(xué)科和學(xué)問(wèn)。這一學(xué)科的突出特征是綜合性。
按照傳統(tǒng)的一般性學(xué)理結(jié)構(gòu)原則,人們常有“史、論、評(píng)不分家”的說(shuō)法,因?yàn)槿咧g有著割舍不斷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而在這個(gè)學(xué)科尚未擰成一股繩的初級(jí)階段,就簡(jiǎn)單化地將其拆解開(kāi)來(lái),或者更多地將一些本來(lái)的三級(jí)學(xué)科(專業(yè)方向)強(qiáng)化為所謂的“特色性”二級(jí)學(xué)科來(lái)建設(shè),極有可能是弊大于利。筆者認(rèn)為,在當(dāng)今世界學(xué)界都以崇尚學(xué)理規(guī)范、學(xué)術(shù)規(guī)范等為基本標(biāo)準(zhǔn)的時(shí)代,在作為“百年大計(jì)”的藝術(shù)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的起跑線上,中國(guó)藝術(shù)學(xué)界需要清醒頭腦,謹(jǐn)慎從事,不能夠讓暫時(shí)的利益沖破了理智的防線,因?yàn)檫@個(gè)天平一旦傾斜,矛盾和困難不但不會(huì)消減,而且會(huì)紛至沓來(lái)。目前值得思慮的核心問(wèn)題約有以下幾點(diǎn):顧名思義,藝術(shù)學(xué)理論是一門綜合性藝術(shù)理論,也是學(xué)術(shù)文化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規(guī)律支配下,經(jīng)我國(guó)許多代人共同努力而開(kāi)創(chuàng)的一個(gè)新局面,二、三級(jí)學(xué)科的設(shè)置更應(yīng)體現(xiàn)綜合性原則。然而,倘若我們?cè)谧龇ㄉ侠^續(xù)沿襲已經(jīng)過(guò)時(shí)了的“科技文化為中心”模式進(jìn)行切塊分割,則恰恰是違背了藝術(shù)學(xué)的基本理論理念和學(xué)科宗旨,形成了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走向。我們可以草草地算一筆賬,比如藝術(shù)學(xué)理論的二級(jí)學(xué)科可設(shè)置六到八個(gè),音樂(lè)舞蹈學(xué)等一級(jí)學(xué)科則可設(shè)置十四五個(gè),那么,同一所學(xué)校如若同時(shí)建設(shè)藝術(shù)學(xué)的五個(gè)一級(jí)學(xué)科,起碼要建50余個(gè)二級(jí)學(xué)科,按每一個(gè)二級(jí)學(xué)科設(shè)一個(gè)三級(jí)學(xué)科(專業(yè)方向)需3位教授計(jì),至少要有150余位教授,而在我國(guó)普通高校傳統(tǒng)建制的音樂(lè)、美術(shù)及至新建的設(shè)計(jì)院(系)中,能達(dá)此指標(biāo)者恐怕寥寥無(wú)幾,必然出現(xiàn)空巢現(xiàn)象,這就勢(shì)必要做那些拉郎配、拼資源等不應(yīng)該又不能不做的事情。《戰(zhàn)國(guó)策》說(shuō):“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5]歷史的教訓(xùn)必須記取。據(jù)悉,在關(guān)于學(xué)科設(shè)置問(wèn)題的醞釀過(guò)程中,藝術(shù)學(xué)差一點(diǎn)被取消了資格。除諸多客觀原因以外,本學(xué)科在十余年來(lái)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較多地關(guān)注表象上的繁榮,缺乏學(xué)科內(nèi)聚力的夯實(shí)打造應(yīng)是內(nèi)因所在。中國(guó)是個(gè)文明的國(guó)度,自古就有“禮樂(lè)之邦”“禮儀之邦”等美譽(yù),西周時(shí)期就制定了國(guó)之禮儀“五禮”,截至如今,許多傳統(tǒng)的倫理綱常,依然潛移默化地根植于人們的理念之中,成為約束個(gè)人的行為準(zhǔn)則和保持社會(huì)群體間井然有序的基本砝碼。藝術(shù)學(xué)理論一、二、三級(jí)學(xué)科的設(shè)置,理應(yīng)遵循一個(gè)基本的倫理關(guān)系準(zhǔn)則,不能夠成為無(wú)“禮”取鬧,如若倫理關(guān)系錯(cuò)位亦將貽害無(wú)窮。#p#分頁(yè)標(biāo)題#e#
薦言要議
在《國(guó)家中長(zhǎng)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中,制定了有關(guān)優(yōu)化學(xué)科結(jié)構(gòu)、加快創(chuàng)新型人才培養(yǎng)的重要舉措。藝術(shù)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與發(fā)展的首要步驟,就是要圍繞以上兩個(gè)方面開(kāi)展基礎(chǔ)性工作。有學(xué)者指出,“藝術(shù)學(xué)理論需要在面對(duì)質(zhì)疑和自身檢討中推進(jìn)學(xué)科的發(fā)展”,它“旨在打通各門藝術(shù)之間的壁壘,通過(guò)各門類藝術(shù)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構(gòu)建涵蓋各門藝術(shù)的普遍規(guī)律的宏觀理論體系”[6]23。仲呈祥先生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營(yíng)造氛圍說(shuō)”,警示老師們千萬(wàn)不要盲目地去“搶地盤”,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任何一門學(xué)科的建設(shè),均需要有長(zhǎng)期的學(xué)術(shù)積累、堅(jiān)實(shí)的學(xué)理基礎(chǔ)和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的科學(xué)性目標(biāo)定位,應(yīng)以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綜合吸納、兼容并包的傳統(tǒng)文化精髓為基本理念,以扎實(shí)穩(wěn)妥、循序漸進(jìn)、精益求精、質(zhì)量第一為立學(xué)準(zhǔn)則,必須恪守學(xué)術(shù)規(guī)律,講究學(xué)術(shù)規(guī)范,遵循學(xué)科形成與發(fā)展的基本路徑,讓其循序漸進(jìn)、天工雕琢,不能陷于盲目和盲動(dòng)。在這里需說(shuō)明的是,“搶地盤”等行為一般并非普通老師們樂(lè)行與可行之事,它往往會(huì)成為一種地方性行政指令讓你被動(dòng)地接受,別無(wú)選擇。當(dāng)然,學(xué)界同仁并不能因此而推脫或放棄應(yīng)盡的責(zé)任。受國(guó)務(wù)院學(xué)位委員會(huì)藝術(shù)學(xué)科專家組組長(zhǎng)仲呈祥先生的信任和重托,筆者有幸曾參與起草《藝術(shù)學(xué)學(xué)科簡(jiǎn)介與博士碩士培養(yǎng)要求》的工作,在此僅將自己通過(guò)初步調(diào)查研究、集思廣益基礎(chǔ)上提出的一些核心觀點(diǎn)和參考性意見(jiàn)作簡(jiǎn)要匯報(bào),敬希諸位方家批評(píng)指正。
百年前,先生主張“尚自然,展個(gè)性”,倡導(dǎo)美育教育,提出德、智、體、美相融并舉的育人方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xué)原則,推行溝通文理的學(xué)科設(shè)置,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等舉措。而今看來(lái),以上舉措仍可作為我們教學(xué)與治學(xué)的基本準(zhǔn)則。藝術(shù)學(xué)理論作為一門綜合性、高階性和理論性學(xué)科,其研究的對(duì)象包括各藝術(shù)門類的藝術(shù)實(shí)踐、藝術(shù)現(xiàn)象和藝術(shù)規(guī)律等,它體現(xiàn)了實(shí)踐性品格、理論性思維和精神性價(jià)值等多重特征,旨在以各門類藝術(shù)的實(shí)踐總結(jié)為基礎(chǔ),以各種藝術(shù)現(xiàn)象的宏觀梳理與綜合分析為鋪墊,最終形成用以表征人類藝術(shù)文化發(fā)展之普遍規(guī)律的科學(xué)理論、概念范疇、價(jià)值論和方法論等知識(shí)系統(tǒng)。具體而論,藝術(shù)學(xué)理論的學(xué)科研究對(duì)象既包括各門藝術(shù)(音樂(lè)、舞蹈、戲劇、影視、美術(shù)、設(shè)計(jì)等)共通性的主體創(chuàng)作、造型設(shè)計(jì)、表演展示、鑒賞評(píng)論、教育傳播等藝術(shù)文化實(shí)踐活動(dòng),也包括古今中外人類對(duì)藝術(shù)現(xiàn)象、藝術(shù)史、藝術(shù)價(jià)值、藝術(shù)精神和藝術(shù)思想的認(rèn)知經(jīng)驗(yàn)。進(jìn)而言之,各藝術(shù)門類之間必然存在著共通性的價(jià)值理念、思想坐標(biāo)、理論基礎(chǔ)、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和認(rèn)知路徑。藝術(shù)學(xué)理論屬于綜合性、交叉性人文藝術(shù)學(xué)科,其研究方法包括三大維度:一是用以分析并完善那些能夠涵蓋各門藝術(shù)基本概念的藝術(shù)知識(shí)學(xué)方法,涉及藝術(shù)史、藝術(shù)原理、藝術(shù)評(píng)論、審美范疇學(xué)、語(yǔ)義哲學(xué)等相關(guān)學(xué)科;二是用以解釋人類表達(dá)與感知各門藝術(shù)的形態(tài)特征,實(shí)現(xiàn)與體驗(yàn)它們的審美價(jià)值等藝術(shù)實(shí)踐規(guī)律的藝術(shù)現(xiàn)象學(xué)方法,涉及藝術(shù)學(xué)與相關(guān)學(xué)科交叉生成的藝術(shù)哲學(xué)、藝術(shù)美學(xué)、文藝學(xué)、藝術(shù)心理學(xué)、藝術(shù)民俗學(xué)、藝術(shù)社會(huì)學(xué)等相關(guān)領(lǐng)域;三是用以揭示并預(yù)見(jiàn)那些能夠整合各門藝術(shù)文化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用以建構(gòu)人類藝術(shù)創(chuàng)新精神的理性范疇,用以闡釋人類以藝術(shù)之道把握主客觀世界的價(jià)值真理的藝術(shù)之學(xué)的理論方法,涉及心理學(xué)、精神科學(xué)、美學(xué)、意識(shí)認(rèn)知科學(xué)、文化人類學(xué)、宗教學(xué)等相關(guān)學(xué)科。
二級(jí)學(xué)科是教育教學(xué)與學(xué)術(shù)研究的實(shí)體,一級(jí)學(xué)科的宗旨目的及其各項(xiàng)具體的指標(biāo)能否順利地實(shí)現(xiàn),關(guān)鍵在于二級(jí)學(xué)科設(shè)置的規(guī)范性和實(shí)施運(yùn)作過(guò)程中的合理性。審視任何一個(gè)傳統(tǒng)學(xué)科和現(xiàn)代學(xué)科的構(gòu)架體系,無(wú)不把學(xué)科的基礎(chǔ)理論和應(yīng)用理論作為不可或缺的兩大部分,故我國(guó)藝術(shù)學(xué)理論二級(jí)學(xué)科的設(shè)置,應(yīng)遵循繼承性、科學(xué)性兩個(gè)基本原則。繼承性原則。注重廣泛地繼承與借鑒世界各國(guó)藝術(shù)學(xué)優(yōu)秀學(xué)術(shù)理念、方法和成果,重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繼承與弘揚(yáng)中國(guó)藝術(shù)文化一以貫之的綜合性、包容性民族精神特質(zhì),以期在藝術(shù)學(xué)理論的學(xué)科建設(shè)進(jìn)程中強(qiáng)力凸顯文化自覺(jué)、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強(qiáng)的堅(jiān)定信念,在此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廣采博納、兼收并蓄的學(xué)科構(gòu)架體系的構(gòu)建與完善。科學(xué)性原則。倡導(dǎo)和尊重科學(xué)規(guī)律,堅(jiān)持以人為本,這是黨和國(guó)家及學(xué)術(shù)界、藝術(shù)界、教育界歷來(lái)秉持的發(fā)展觀。科學(xué)性是一種極具世界包容性、人類本體性和時(shí)代進(jìn)取性的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理念,處在重大轉(zhuǎn)型起始階段的藝術(shù)學(xué)理論二級(jí)學(xué)科的設(shè)置,如何更好地體現(xiàn)科學(xué)性原則,這是對(duì)藝術(shù)學(xué)理論界群體智慧的重大考驗(yàn)。具體來(lái)說(shuō),藝術(shù)學(xué)理論的學(xué)科建設(shè)與理論創(chuàng)新,首先需要基于人類據(jù)以內(nèi)化—轉(zhuǎn)化—外化藝術(shù)文化的審美價(jià)值規(guī)律,其次是需要基于人類用以認(rèn)知藝術(shù)文化和創(chuàng)造審美產(chǎn)物的心腦科學(xué)規(guī)律,再次是需要基于藝術(shù)家用以構(gòu)制藝術(shù)造型的形式法則、感性之道與技術(shù)規(guī)范。
根據(jù)上述基本原則,藝術(shù)學(xué)理論一級(jí)學(xué)科的學(xué)科范圍,可包含藝術(shù)基礎(chǔ)理論、藝術(shù)應(yīng)用理論兩個(gè)二級(jí)學(xué)科,下轄相關(guān)的若干研究方向(或三級(jí)學(xué)科)。藝術(shù)基礎(chǔ)理論。藝術(shù)基礎(chǔ)理論,主要涉及文化主體對(duì)藝術(shù)文化世界這個(gè)藝術(shù)本體系統(tǒng)的觀察、分析、判斷、評(píng)價(jià)等對(duì)象性的藝術(shù)認(rèn)知基礎(chǔ)理論。具體包括傳統(tǒng)學(xué)科的藝術(shù)史、藝術(shù)理論、藝術(shù)評(píng)論等三個(gè)主干研究方向。(1)藝術(shù)史:含中國(guó)藝術(shù)史,外國(guó)藝術(shù)史,以及藝術(shù)考古學(xué)、藝術(shù)圖像學(xué)、藝術(shù)人類學(xué)等交叉學(xué)科專業(yè)方向。(2)藝術(shù)理論:含藝術(shù)原理,藝術(shù)美學(xué),以及藝術(shù)文化學(xué),藝術(shù)社會(huì)學(xué),藝術(shù)教育學(xué),藝術(shù)宗教學(xué)等交叉學(xué)科專業(yè)方向。(3)藝術(shù)評(píng)論:含藝術(shù)鑒賞學(xué)(傳統(tǒng)藝術(shù)鑒賞、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鑒賞),藝術(shù)批評(píng)學(xué)(傳統(tǒng)藝術(shù)批評(píng)、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批評(píng))等。藝術(shù)應(yīng)用理論。在當(dāng)今時(shí)代,“全球?qū)徝阑?rdquo;“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審美化”“物質(zhì)審美化”“日常生活審美化”等學(xué)術(shù)理念不斷影響著藝術(shù)理論的更新。藝術(shù)和生活的關(guān)系再次產(chǎn)生巨大的變異,首先是徹底顛覆了傳統(tǒng)的審美價(jià)值觀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思維范式,倡導(dǎo)生活審美化的藝術(shù)理念,藝術(shù)已經(jīng)漸漸地遠(yuǎn)離神圣的象牙塔,回歸到人類生產(chǎn)、生活的本真的層面,也即實(shí)現(xiàn)了由人類的生活提煉升華成為以“美”為核心的藝術(shù),再由藝術(shù)的“美”熏染提升人類生活的一個(gè)博大的理論命題,“審美化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全球性的策略”。當(dāng)然,上述藝術(shù)理論的流派及其理論,并非構(gòu)成對(duì)傳統(tǒng)的和現(xiàn)當(dāng)代其他藝術(shù)理論流派的取代,而是形成了一種并存與互補(bǔ)的發(fā)展關(guān)系。從大局上看,上述變化有助于破除“藝術(shù)神圣”“至高無(wú)上”的象牙塔情結(jié),讓藝術(shù)回歸現(xiàn)實(shí),服務(wù)于社會(huì)生活,無(wú)疑是藝術(shù)理論研究造益人生的一大進(jìn)步。我們?cè)購(gòu)娜祟愃囆g(shù)文化演進(jìn)發(fā)展歷史的視角來(lái)看,從藝術(shù)與人類社會(huì)文明的共同源頭(源于生活),到藝術(shù)與生活的漸行漸離(高于生活),及至藝術(shù)再次回歸到生活中來(lái)(創(chuàng)意生活),總體上符合事物循序漸進(jìn)的基本輪回及普遍性發(fā)展規(guī)律。因此,設(shè)置藝術(shù)應(yīng)用理論二級(jí)學(xué)科既合乎規(guī)范又通于情理。藝術(shù)應(yīng)用理論,主要包括20世紀(jì)末以來(lái)在我國(guó)熱興的藝術(shù)管理研究和藝術(shù)創(chuàng)意研究?jī)纱笾鞲裳芯糠较颉?1)藝術(shù)管理學(xué):含藝術(shù)文化管理、藝術(shù)產(chǎn)業(yè)管理、藝術(shù)市場(chǎng)與營(yíng)銷管理、藝術(shù)展演與策劃管理、藝術(shù)產(chǎn)品與傳播管理,藝術(shù)品抵押與信托管理(藝術(shù)品抵押、藝術(shù)品按揭、藝術(shù)品信托、藝術(shù)品基金、藝術(shù)品“股票”)等方面的研究。(2)藝術(shù)創(chuàng)意學(xué):含藝術(shù)文化創(chuàng)意、藝術(shù)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意、藝術(shù)傳播創(chuàng)意、藝術(shù)經(jīng)濟(jì)創(chuàng)意、藝術(shù)科技創(chuàng)意等方面的研究。#p#分頁(yè)標(biāo)題#e#
篇8
袁從萬(wàn)(1988-),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師范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體育教育訓(xùn)練。
摘 要:本文通過(guò)文獻(xiàn)資料法對(duì)體育人類學(xué)的學(xué)科性質(zhì)和在體育學(xué)中的學(xué)科位置、研究的對(duì)象、方法以及體育人類學(xué)與人類未來(lái)的發(fā)展幾個(gè)方面闡述了體育人類學(xué)這門學(xué)科的重要性,并對(duì)體育人類學(xué)學(xué)術(shù)研究進(jìn)展進(jìn)行一定綜述。只有從人類持續(xù)發(fā)展角度把握體育未來(lái)的發(fā)展方向,體育與人類才能更好的互補(bǔ)發(fā)展,從而中國(guó)體育的發(fā)展也需要體育人類學(xué)提供新的認(rèn)識(shí)手段和方法和科學(xué)理論支撐。
關(guān)鍵詞:體育人類學(xué),學(xué)術(shù)進(jìn)展,綜述
體育人類學(xué)是在體育領(lǐng)域研究人類發(fā)展的一門學(xué)科,它揭示體育過(guò)程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在不同形式的體育過(guò)程和與之相似的社會(huì)現(xiàn)象中尋找共同的規(guī)律。因此,體育人類學(xué)是涉及體育與人類的各個(gè)方面,從人類起源、生存、發(fā)展的宏觀意義上去認(rèn)識(shí)體育,在探索體育的起源和發(fā)展方面,在挖掘和整理民族民間傳統(tǒng)體育方面,在研究人種差異與高水平競(jìng)技方面,在探索人類體質(zhì)狀態(tài)連續(xù)進(jìn)化方面,從而進(jìn)一步準(zhǔn)確地把握體育的本質(zhì),以便使體育這種社會(huì)實(shí)踐活動(dòng)朝著更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fā)展。體育將是人類生存和發(fā)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將成為各國(guó)經(jīng)濟(jì)文化領(lǐng)域的重要產(chǎn)業(yè)。[1]
1.體育人類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
體育人類學(xué)是運(yùn)用人類學(xué)的理論和方法,從人類進(jìn)化的角度,探討人類進(jìn)化過(guò)程中身體結(jié)構(gòu)和運(yùn)動(dòng)方式的變化,結(jié)合考古學(xué)和民族學(xué)來(lái)判斷處于不同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階段的體育狀況,居于更高層次,擁有更廣闊的視野,立足于體育對(duì)人類學(xué)的整體需要,體育人類學(xué)涉及到游戲、競(jìng)賽、鍛煉、舞蹈以及人類身體運(yùn)動(dòng)的許多方面。[2]
體育人類學(xué)對(duì)體育原理的研究,為體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研究民族體育,對(duì)民族體育進(jìn)行科學(xué)的挖掘、整理和改良,篩選出適應(yīng)現(xiàn)代社會(huì)需要的部分,不僅保護(hù)了民族文化,也為增強(qiáng)全民族的體質(zhì)健康提供最充分的理論依據(jù);競(jìng)技文化的研究,使人類從單純追求人體極限的誤區(qū)中解脫出來(lái),強(qiáng)調(diào)種族平等,競(jìng)技場(chǎng)上的成績(jī)高低,不應(yīng)該用以概括種族的優(yōu)劣;人類的發(fā)展,為體育的未來(lái)制訂了坐標(biāo),把握體育的未來(lái)發(fā)展軌跡,考慮到人類體質(zhì)和健康的終極效果,探討社會(huì)的異化導(dǎo)致的體育特殊需求,揭示體育與人類未來(lái)的發(fā)展。
2.體育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
體育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當(dāng)然要借鑒人類學(xué)的基本方法,根據(jù)體育領(lǐng)域的實(shí)際需要加以調(diào)整,主要有以下幾種:
2.1野外考察
“田野工作”的程序大致可分為四個(gè)方面:野外考察的準(zhǔn)備、野外資料收集技術(shù)、野外適應(yīng)、野外資料分析。田野工作—特別是參與觀察方法,重視人的行為,是人類學(xué)最基本的途徑,也是體育人類學(xué)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2.2人體測(cè)量
體育與文化人類學(xué)和體質(zhì)人類學(xué)都有密切關(guān)系,無(wú)論是檢驗(yàn)人體發(fā)育或健康水平,還是衡量運(yùn)動(dòng)鍛煉或訓(xùn)練效果,為開(kāi)展不同類型的體育活動(dòng)提供量化依據(jù),都離不開(kāi)人體測(cè)量方法。但應(yīng)該清楚體育人類學(xué)并不一味采用研究人體標(biāo)準(zhǔn)類型的測(cè)量法,也不主張靜止地去研究人體常態(tài)。
2.3其他
人類學(xué)家必須保持一個(gè)視野的寬度,也就是說(shuō)養(yǎng)成在寬廣的歷史和文化范圍內(nèi)來(lái)觀察事物的習(xí)慣,因?yàn)樗麄円袷厝祟悓W(xué)研究的兩大原則一一整體論和文化相對(duì)論。不僅如此,研究體育和競(jìng)技活動(dòng)的歷史需要考古學(xué),在對(duì)民族體育的比較和評(píng)價(jià)中,經(jīng)常也需要使用考古學(xué)的成果。
3.體育人類學(xué)與人類未來(lái)的發(fā)展
一般而言,人類學(xué)著眼于人類的過(guò)去和現(xiàn)在,但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未來(lái)。基于現(xiàn)實(shí):生存空間的異化、適應(yīng)的極限、腦體背離。體育人類學(xué)特別關(guān)注文明進(jìn)步給人類體質(zhì)帶來(lái)的負(fù)面后果,促進(jìn)人類的體質(zhì)健康與社會(huì)文化的同步發(fā)展,未來(lái)體育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需要借鑒生態(tài)人類學(xué)的理論,應(yīng)該是綠色的、生態(tài)的。
健康,體現(xiàn)著人類對(duì)自身前途和命運(yùn)的基本關(guān)懷;體育,是體現(xiàn)這種基本關(guān)懷的最佳執(zhí)行者。追尋健康,體育應(yīng)該是:最積極的休閑方式、最有益的健身方式、最有趣的娛樂(lè)方式。體育,和人的健康幸福更加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lái),站在全人類發(fā)展的高度,提供日益絢麗多彩的身體運(yùn)動(dòng)方式來(lái)源源不斷生產(chǎn)健康,未來(lái)的體育將是最積極、最有益和最愉快的途徑[3]。
4.我國(guó)體育人類學(xué)的學(xué)術(shù)進(jìn)展
4.1學(xué)科基礎(chǔ)理論研究
1999年,我國(guó)第一本“體育人類學(xué)”專著出版(胡小明,廣東人民出版社),對(duì)體育人類學(xué)的學(xué)科理論進(jìn)行了全面闡述。此后,北京體育大學(xué)出版社(席煥久等,2001)和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饒遠(yuǎn)、陳斌,2005)先后出版了“體育人類學(xué)”專著。
人類學(xué)研究更關(guān)注的是研究對(duì)象的多樣性及差異性,以及這一差異形成的原因及其發(fā)展演變。因此,田野調(diào)查是人類學(xué)研究最主要的方法,也成為理論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如楊世如對(duì)2009年由華南師范大學(xué)與貴州民族學(xué)院19位專家學(xué)者組成兩校聯(lián)合調(diào)查組以苗族獨(dú)木龍舟競(jìng)渡為調(diào)查對(duì)象的實(shí)踐活動(dòng)進(jìn)行闡述,從研究方法上釋義體育人類學(xué)為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研究開(kāi)拓了一個(gè)嶄新的理論空間[4]。楊海晨等在《論體育人類學(xué)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調(diào)查關(guān)系》一文中為田野調(diào)查法資料的客觀性提出一些建議[5]。
4.2民族體育的人類學(xué)視角
民族、民間傳統(tǒng)體育,是體育人類學(xué)研究的重要領(lǐng)域。當(dāng)前,有關(guān)民族體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武術(shù)研究;2、通過(guò)田野工作對(duì)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進(jìn)行考察;3、民族傳統(tǒng)體育多元文化研究;4、傳統(tǒng)體育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6]
胡小明、李吉遠(yuǎn)、鐘海明、萬(wàn)義、胡建文、楊世如等學(xué)者對(duì)民族體育的研究,有力的推進(jìn)了民族體育文化的保護(hù)與傳承。許多少數(shù)民族的體育活動(dòng)就是體育的原生態(tài),反映了體育的根,反映了體育最本質(zhì)的東西。斗牛、龍舟、摔跤、秋千、跳月、跳虎等在起源時(shí)都與自然力崇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體現(xiàn)著對(duì)自然的關(guān)懷、對(duì)生態(tài)的尊重;堆沙、打陀螺、跳竹桿、獨(dú)竹漂等則是粘著土、連著泥,沐浴在自然和風(fēng)里的。民族體育的發(fā)展趨勢(shì)主要與體育比賽、旅游產(chǎn)業(yè)、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等方面相結(jié)合,才能有更好的保護(hù)、傳承和發(fā)展。
結(jié)語(yǔ)
體育人類學(xué)是新時(shí)期我國(guó)體育意識(shí)重新構(gòu)建的關(guān)鍵學(xué)科,同時(shí)也是一門新興學(xué)科。新興學(xué)科的最顯著的特點(diǎn)是它具有開(kāi)拓性、創(chuàng)造性,研究新的對(duì)象,開(kāi)拓新的領(lǐng)域,發(fā)現(xiàn)新的規(guī)律,為人類認(rèn)識(shí)體育提供新知識(shí),為人類發(fā)展體育提供新的認(rèn)識(shí)工具。當(dāng)然,新興學(xué)科又大多是正在形成中的學(xué)科,這決定了它的不成熟性。因此,從學(xué)科的成長(zhǎng)期來(lái)看,體育人類學(xué)仍然處于童年,從人類發(fā)展的需要來(lái)看,體育人類學(xué)前景廣闊。(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xué)體育學(xué)院)
參考文獻(xiàn)
[1] 王洪.體育運(yùn)動(dòng)與人類發(fā)展的淵源[J].湖北體育科技,1999(4):45-47.
[2] 盧元鎮(zhèn)主編.體育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概論高級(jí)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5-151.
[3] 胡小明.體育人類學(xué)進(jìn)展[J].北京體育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4,27(3):289-293.
[4] 楊世如,韋佳.原始禮儀競(jìng)技的體育人類學(xué)研究——苗族獨(dú)木龍舟競(jìng)技文化調(diào)查[J].貴州民族研究,2010,31(5):64-68.
篇9
關(guān)鍵詞:比較史學(xué);價(jià)值;發(fā)展前景
中圖分類號(hào):K06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5-5312(2012)18-0077-02
一、淺析比較史學(xué)
史學(xué)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和重要領(lǐng)域之一就歷史的比較研究,它也是比較史學(xué)的基本特征和雛形。早在史學(xué)的萌芽階段,歷史的比較研究就開(kāi)始出現(xiàn),司馬遷曾在《史記》中指出,對(duì)歷史的研究如果想達(dá)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目的,應(yīng)必須通過(guò)比較研究,“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jì)”。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學(xué)家梁?jiǎn)⒊瑒t指出:“凡天下事比較然后見(jiàn)其真,無(wú)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長(zhǎng)。”
在西方,隨著歷史研究的領(lǐng)域更加廣泛,理論體系更加完善,史學(xué)家們逐漸在對(duì)歷史的比較研究之中總結(jié)出了比較史學(xué)(Comparative History)這一獨(dú)立的學(xué)科領(lǐng)域。西方公認(rèn)的比較史學(xué)之父,法國(guó)年鑒派史學(xué)家馬克·布洛赫在其1928 年發(fā)表的《論歐洲社會(huì)的歷史比較》一文中,提出了較系統(tǒng)的比較史學(xué)的理論。他認(rèn)為:“比較就是在一個(gè)或數(shù)個(gè)不同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選擇兩種或數(shù)種一眼就能看出它們之間的某些類似之處的現(xiàn)象,然后描繪出這些現(xiàn)象發(fā)展的曲線,提示它們的相似點(diǎn)和不同點(diǎn),并在可能的范圍內(nèi)對(duì)這些相似點(diǎn)和不同點(diǎn)做出解釋。”
使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并不等于就是比較史學(xué),比較史學(xué)有整套相對(duì)完善的理論和方法體系。所以說(shuō),在理解比較史學(xué)概念的基礎(chǔ)上,我們還必須要掌握比較研究的類型、程序、原則等基本理論問(wèn)題。比較史學(xué)遵循的最基本原則就是可比性原則,它是能否正確運(yùn)用比較研究方法的關(guān)鍵。可比性的判斷是基于對(duì)研究對(duì)象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而非表象的判斷。
二、比較史學(xué)在研究中的價(jià)值
比較史學(xué)對(duì)于進(jìn)行科學(xué)的歷史研究很大意義,“由于這類比較方法能夠更好地對(duì)近似點(diǎn)進(jìn)行嚴(yán)格的分類和論證,就有可能希望得到對(duì)事實(shí)做出假設(shè)少得多而精確程度卻高得多的結(jié)論。”
第一、有利于通過(guò)對(duì)各種歷史現(xiàn)象的比較研究,察其異同,揭示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
比較史學(xué)最主要的功用在于,通過(guò)比較考察,探求各種社會(huì)歷史現(xiàn)象發(fā)生、發(fā)展與消亡的共同之理,探求各種歷史現(xiàn)象發(fā)生與消亡的特殊規(guī)律,并進(jìn)而探求整個(gè)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的普遍規(guī)律。不同時(shí)期、不同地區(qū)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史實(shí)。差異性決定著歷史是豐富多彩的。但在具體研究中,我們往往把歷史進(jìn)程中某種制度、某種思想、某種社會(huì)現(xiàn)象等局限于一定時(shí)間和空間范圍內(nèi),片面地割裂了各種史實(shí)之間的客觀聯(lián)系,難以把握各種史實(shí)之間的同異關(guān)系。比較史學(xué)可以很好的揭示事物間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糾正歷史研究中的偏向。侯外廬學(xué)派認(rèn)為,對(duì)于思想史的研究應(yīng)當(dāng)將思想史與社會(huì)史的研究相結(jié)合。這啟發(fā)了我們應(yīng)當(dāng)從中國(guó)思想和社會(huì)這兩個(gè)維度進(jìn)行縱向比較,分析和比較不同歷史時(shí)期各種思想和制度方面的聯(lián)系及其特點(diǎn),從而提煉出值得繼承的精華部分。
第二、有利于深化對(duì)歷史的研究。
陳國(guó)慶教授在《史學(xué)與科學(xué)》一文中指出,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中,或許有若干種不同的觀點(diǎn), 但是, 研究者們最起碼在史實(shí)的判斷上不至于發(fā)生歧義。從另一個(gè)角度講, 歷史研究者不應(yīng)當(dāng)以單純的從事于史實(shí)的重建為滿足, 歷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史料學(xué)的階段, 而應(yīng)當(dāng)在充分掌握史實(shí)的基礎(chǔ)上, 采用當(dāng)代行為科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的力量與模式分析史料, 進(jìn)一步解釋史實(shí)。例如, 將許多同時(shí)代或不同時(shí)代的史實(shí)進(jìn)行縱向或橫向的比較研究, 以考察分析其異同和關(guān)聯(lián), 從而對(duì)史實(shí)作部分或全部的歸納與檢討, 進(jìn)而從更高層次上衡量該史實(shí)在整個(gè)歷史主流中所發(fā)生的意義, 將歷史、現(xiàn)實(shí)與未來(lái)聯(lián)系在一起。
當(dāng)代中國(guó)史學(xué)大體是在影響下的史學(xué)體系, 但前蘇聯(lián)的一套史學(xué)研究體系, 也給中國(guó)當(dāng)代史學(xué)的正常發(fā)展帶來(lái)過(guò)麻煩。通過(guò)中外近代史學(xué)的比較研究, 把中國(guó)近代史壇不時(shí)受西方諸種史學(xué)思潮撞擊情況及其引起這些撞擊的各種社會(huì)背景發(fā)掘出來(lái), 可以引起青年人作更深入的扣心反思, 通過(guò)中外當(dāng)代史學(xué)的比較研究, 把國(guó)門打開(kāi)后, 西方史學(xué)方法的大量引進(jìn)和對(duì)當(dāng)代中國(guó)史學(xué)變革的重要而深遠(yuǎn)的意義揭示出來(lái)。
第三、有利于開(kāi)闊研究者的視野,拓寬歷史研究的新領(lǐng)域。
根據(jù)人們獲得知識(shí)的來(lái)源,亞里士多德將知識(shí)劃分為三類,即理論、實(shí)踐和鑒別的知識(shí)。而鑒別的知識(shí)是靠比較獲得的,比較的長(zhǎng)處就在于能認(rèn)識(shí)事物的特殊性和多樣性。比較史學(xué)的興起,正是因?yàn)樗粌H可以推進(jìn)對(duì)事物的深層次的認(rèn)識(shí),而且還可促使新思想觀點(diǎn)的產(chǎn)生,從而擴(kuò)展研究的視野,甚至開(kāi)辟新的研究領(lǐng)域。
杜維運(yùn)認(rèn)為,只研究中國(guó)史學(xué),傾畢生之力寫成的中國(guó)史學(xué)史也只是地方史,不足以躋身世界史學(xué)之林。他 “居于世界漸幾于大同的今日,應(yīng)胸襟廣闊,眼光遠(yuǎn)大,以比較史學(xué)的觀點(diǎn),闡述中國(guó)史學(xué)的出現(xiàn),成立與發(fā)展,同時(shí)涉及世界其它地區(qū)出現(xiàn)的史學(xué),比較其異同,衡量其得失。如此則中國(guó)史學(xué)的世界性出現(xiàn),其價(jià)值將弘揚(yáng)于世界。”
陳國(guó)慶教授在《中國(guó)近代史研究需要?jiǎng)?chuàng)新》第二部分——近代專門史研究需要拓寬和深化中指出“對(duì)經(jīng)濟(jì)史的研究越深入, 人們感到需要進(jìn)一步研究的問(wèn)題就越多。從目前的學(xué)術(shù)進(jìn)展看, 有的學(xué)者從宏觀角度, 對(duì)中國(guó)工業(yè)化問(wèn)題提出了新的認(rèn)識(shí); 有的學(xué)者從中外歷史比較的視野, 對(duì)近代中外經(jīng)濟(jì)史進(jìn)行比較研究。”這啟發(fā)了我們,我們的視野不能僅僅局限于中國(guó)歷史的史事上,還應(yīng)將其投放到更廣闊的領(lǐng)域中去,與世界歷史的背景相結(jié)合、比較,這樣往往可以獲得更多更有價(jià)值的結(jié)論。
三、比較史學(xué)的發(fā)展前景
筆者認(rèn)為在當(dāng)前的史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中應(yīng)當(dāng)大大提升比較史學(xué)的地位。目前根據(jù)教育部的學(xué)科設(shè)置目錄,歷史學(xué)學(xué)科門類下設(shè)中國(guó)史、世界史、考古學(xué)三個(gè)一級(jí)學(xué)科。但縱觀這三個(gè)一級(jí)學(xué)科下屬的二級(jí)學(xué)科,都沒(méi)有比較史學(xué)的位置。對(duì)此,筆者認(rèn)為可以使用兩種方法解決:一是在中國(guó)史、世界史下分別設(shè)置中國(guó)比較史學(xué)、世界比較史學(xué);二是參考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學(xué)科設(shè)置,將歷史學(xué)分為史學(xué)理論、中外通史研究與考古學(xué)三個(gè)一級(jí)學(xué)科,并在史學(xué)理論下設(shè)比較史學(xué)二級(jí)學(xué)科。筆者更傾向于第二種設(shè)置,比較史學(xué)本來(lái)就是世界范圍的比較,如果按第一種方案,中國(guó)比較史學(xué)的存在意義就會(huì)大打折扣,但比較史學(xué)的研究方法,本來(lái)就不僅僅是世界史研究中所必須的,中國(guó)史的研究也應(yīng)當(dāng)采納。但鑒于第一種學(xué)科設(shè)置不至于對(duì)剛剛調(diào)整完畢的學(xué)科設(shè)置再做大的變動(dòng),也可以供決策者參考。無(wú)論怎樣,我們都應(yīng)當(dāng)重視比較史學(xué)在歷史學(xué)研究中的重大價(jià)值。
參考文獻(xiàn)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梁?jiǎn)⒊?論中國(guó)學(xué)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sh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楊豫, 胡成. 歷史學(xué)的思想和方法[M].南京: 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 1999.5.
篇10
[關(guān)鍵詞]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
圖書情報(bào)學(xué)認(rèn)識(shí)存在學(xué)科體系
[分類號(hào)]G250
1
引
言
用哲學(xué)化的視野觀察科學(xué)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揭示科學(xué)研究與知識(shí)、社會(huì)存在和人之間的關(guān)系,并最終促使我們用更為合理的方法得出更真實(shí)反映社會(huì)存在的理論…。圖書情報(bào)學(xué)理論和實(shí)踐中對(duì)自身理論基礎(chǔ)和身份的迷惑正是缺乏學(xué)科哲學(xué)觀照(philosophicalcounterpart)的反映。在此研究需求下,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開(kāi)始探索圖書情報(bào)學(xué)哲學(xué)層面的解釋和理論基礎(chǔ)”。],其中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解釋下的圖書情報(bào)學(xué)研究不乏深入見(jiàn)解。
本文在回顧圖書情報(bào)學(xué)哲學(xué)研究淵源的基礎(chǔ)上,對(duì)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也有“后現(xiàn)代哲學(xué)”的說(shuō)法,本文采納馮俊教授的說(shuō)法,即后現(xiàn)代主義的哲學(xué)轉(zhuǎn)向,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是后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社會(huì)特征、知識(shí)特征、文化特征、心態(tài)和思維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在理論上的反映)與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關(guān)聯(lián)研究進(jìn)行述評(píng),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對(duì)圖書情報(bào)學(xué)若干問(wèn)題的一種解釋。
2 國(guó)內(nèi)外研究現(xiàn)狀
“后現(xiàn)代主義”一詞最早被用來(lái)描述現(xiàn)代主義內(nèi)部發(fā)生的逆動(dòng),涵蓋哲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和社會(huì)文化,是一種思維方式和態(tài)度,以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統(tǒng)性、不確定性、非連續(xù)性以及多元化為特征。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的指導(dǎo)思想對(duì)圖書情報(bào)學(xué)現(xiàn)狀具有映射價(jià)值,并能夠?yàn)槠浒l(fā)展提供可能的方向和觀照。
2.1 國(guó)外研究現(xiàn)狀
國(guó)外圖書情報(bào)界的研究者基本認(rèn)同圖書情報(bào)學(xué)與哲學(xué)的天然內(nèi)在聯(lián)系。約赫蘭德(Birger Hjrland)曾總結(jié)出圖書情報(bào)學(xué)研究的如下哲學(xué)假設(shè),包括社會(huì)建構(gòu)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批判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經(jīng)驗(yàn)主義(empiricism)、女性主義認(rèn)識(shí)論(feministepistermology)、解釋學(xué)和現(xiàn)象主義(hermeneutics andphenomenology)、歷史主義(historicism)、哲學(xué)(marx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范式理論(paradigm―theory)、后現(xiàn)代主義和后建構(gòu)主義(postmodernism andpostconstmetural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現(xiàn)實(shí)主義和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realism and critical realism)、實(shí)用主義(pragmatism)和系統(tǒng)論(systems theory)。隨著哲學(xué)層面上圖書情報(bào)學(xué)研究的深入,科學(xué)哲學(xué)①、社會(huì)認(rèn)識(shí)論、信息哲學(xué)開(kāi)始進(jìn)入研究視野。
在此基礎(chǔ)上,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與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關(guān)系開(kāi)始引起關(guān)注。主要分為后代主義哲學(xué)與圖書情報(bào)學(xué)研究本身的關(guān)系以及對(duì)圖書情報(bào)學(xué)學(xué)科環(huán)境的觀照。
密蘇里大學(xué)圖書情報(bào)學(xué)院的巴德教授(John M,Budd)是較早開(kāi)展圖書情報(bào)學(xué)與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關(guān)聯(lián)研究的學(xué)者,認(rèn)為經(jīng)過(guò)修正的認(rèn)識(shí)論可以解釋圖書館的本質(zhì)和人在圖書情報(bào)學(xué)實(shí)踐中的認(rèn)識(shí)狀態(tài),并強(qiáng)調(diào)解決問(wèn)題可以有多種途徑和方法,即用后現(xiàn)代主義認(rèn)識(shí)論取代以理性和絕對(duì)正確為代表的現(xiàn)代性理論。1998年,萊德福德依據(jù)福柯的論文“The fantasia of li―brary”,運(yùn)用后現(xiàn)代認(rèn)識(shí)論的觀點(diǎn)對(duì)圖書館、圖書館實(shí)踐、圖書館員以及讀者的認(rèn)知和理解進(jìn)行重構(gòu),提出“圖書館的目標(biāo)是使讀者和作者自由建構(gòu)自己的知識(shí),而不是理解外界強(qiáng)加的知識(shí)排序”。此后,福柯的觀點(diǎn)開(kāi)始被越來(lái)越多的圖書情報(bào)學(xué)研究者關(guān)注。200B年,萊德福德運(yùn)用知識(shí)考古學(xué)的方法探討圖書情報(bào)學(xué)中的“管狀視野和盲點(diǎn)(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即圖書情報(bào)學(xué)中的話語(yǔ)成規(guī)何以成為問(wèn)題,這種話語(yǔ)成規(guī)如何阻礙圖書情報(bào)學(xué)研究多樣化以及如何利用福柯的知識(shí)考古學(xué)來(lái)促使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研究者進(jìn)行反思,并促使新的話語(yǔ)規(guī)范的形成。這種運(yùn)用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典型理論方法對(duì)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研究路徑和研究活動(dòng)本身進(jìn)行的思考,推動(dòng)了圖書情報(bào)學(xué)哲學(xué)研究的嚴(yán)謹(jǐn)化和深入化,并促使圖書情報(bào)學(xué)展開(kāi)跨學(xué)科思考。
與此同時(shí),美國(guó)情報(bào)學(xué)家維思格提出了后現(xiàn)代科學(xué)知識(shí)變遷的概念,包括知識(shí)的非個(gè)人化、可信度、零碎化和理性化,在這種情況下,情報(bào)學(xué)應(yīng)該成為一門后現(xiàn)代科學(xué),即不應(yīng)完全了解外在世界的運(yùn)作,而是以問(wèn)題為導(dǎo)向。英國(guó)情報(bào)學(xué)家穆迪曼提出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教育背景不再是informatin society能夠表述的,應(yīng)該用“復(fù)雜的、片段的和后現(xiàn)代”來(lái)表述,圖書情報(bào)學(xué)關(guān)注公共知識(shí)社會(huì)變遷的管理視角已不再適用。霍巴則把書目指導(dǎo)和學(xué)生教育聯(lián)系起來(lái),提出傳統(tǒng)的書目教育應(yīng)該汲取后現(xiàn)代教育理念,圖書館應(yīng)是一個(gè)在話語(yǔ)背景下的學(xué)習(xí)中心。
國(guó)外研究至少在三個(gè)方面為圖書情報(bào)學(xué)提供了研究幫助:①為關(guān)于圖書情報(bào)學(xué)本質(zhì)的思考提供新思路,比如福柯的觀點(diǎn)、后現(xiàn)代認(rèn)識(shí)論;②為圖書情報(bào)學(xué)研究提供了多種研究方法,比如解釋學(xué)的方法、話語(yǔ)分析的方法等;③為圖書情報(bào)學(xué)學(xué)科生存環(huán)境提供新的解釋,以此幫助研究者重新認(rèn)識(shí)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社會(huì)存在。
2.2 國(guó)內(nèi)研究現(xiàn)狀
國(guó)內(nèi)哲學(xué)層面的圖書情報(bào)學(xué)研究,一方面是引進(jìn)介紹西方哲學(xué)理論;另一方面也試圖用本土話語(yǔ)來(lái)解釋本土現(xiàn)象,或用西方話語(yǔ)來(lái)透視本土現(xiàn)象。傅榮賢認(rèn)為中國(guó)古代文獻(xiàn)收集、整理和利用的每一個(gè)環(huán)節(jié)都是向個(gè)體存在敞開(kāi)的,表現(xiàn)出與科技相對(duì)的哲學(xué)性。金勝勇等人提出用科學(xué)哲學(xué)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來(lái)對(duì)圖書館學(xué)的科學(xué)性進(jìn)行觀照性研究。王知津則對(duì)情報(bào)學(xué)中的哲學(xué)基礎(chǔ)理論、哲學(xué)方法應(yīng)用、哲學(xué)理論應(yīng)用進(jìn)行綜合分析。
其中,國(guó)內(nèi)學(xué)者運(yùn)用后現(xiàn)代主義觀點(diǎn)和方法對(duì)圖書情報(bào)學(xué)展開(kāi)研究較晚。蔣永福明確提出中國(guó)的圖書館學(xué)具有后現(xiàn)論特征:價(jià)值多元主義、權(quán)利話語(yǔ)取向、工具理性盛行。王建冬論述了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對(duì)情報(bào)學(xué)基礎(chǔ)理論的影響,包括波普爾現(xiàn)代本體論思想、庫(kù)恩科學(xué)歷史主義以及社會(huì)建構(gòu)主義的科學(xué)哲學(xué)在情報(bào)學(xué)理論中的顯性引入與啟發(fā)以及新解釋學(xué)和社會(huì)建構(gòu)主義兩種取向的作者、讀者與文本關(guān)系的后現(xiàn)代解讀方法對(duì)情報(bào)學(xué)認(rèn)知觀和領(lǐng)域分析等基礎(chǔ)理論的影響。王知津認(rèn)為情報(bào)學(xué)中表現(xiàn)出的非表達(dá)特質(zhì)、不確定性、多元性和去中心化等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典型特征,而情報(bào)學(xué)所面臨的主要問(wèn)題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情報(bào)學(xué)后現(xiàn)代主義趨勢(shì)的表現(xiàn)。俞傳正認(rèn)為后現(xiàn)代主義階段的科學(xué)哲學(xué)對(duì)“語(yǔ)境”的關(guān)注會(huì)對(duì)情報(bào)學(xué)的發(fā)展和走向產(chǎn)生重大影響。賴鼎銘分析了后現(xiàn)代社會(huì)對(duì)圖書資訊服務(wù)的沖擊,包括對(duì)經(jīng)典作
品的解構(gòu)、數(shù)字化技術(shù)對(duì)教育和學(xué)習(xí)體制的虛擬化沖擊以及數(shù)字化技術(shù)對(duì)圖書資訊服務(wù)的質(zhì)量、可得性和可用性的新要求。葉乃靜提出后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圖書館學(xué)要從傳統(tǒng)的精英視角為大眾服務(wù)。此外還有對(duì)后現(xiàn)代圖書館的描述。
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對(duì)圖書情報(bào)學(xué)與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的關(guān)注主要集中在對(duì)圖書情報(bào)學(xué)研究和實(shí)踐現(xiàn)狀的分析上,并沒(méi)有涉及研究所反映的社會(huì)存在以及對(duì)研究本身的歷史分析和邏輯分析,內(nèi)容較為淺層。值得注意的是,國(guó)內(nèi)學(xué)者開(kāi)始探索深層次運(yùn)用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的理論和方法關(guān)注國(guó)內(nèi)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研究與實(shí)踐,比如俞傳正在其博客中提到國(guó)內(nèi)圖書館事業(yè)的后現(xiàn)代轉(zhuǎn)型,即從事業(yè)轉(zhuǎn)向職業(yè),藉以改變國(guó)內(nèi)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的瓶頸,并提出如何借助話語(yǔ)分析方法對(duì)圖書館用戶進(jìn)行分析。
3 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對(duì)圖書情報(bào)學(xué)現(xiàn)狀的解釋
3.1 技術(shù)的地位
技術(shù)要素在圖書情報(bào)學(xué)發(fā)展中的地位不言自明。從討論芝加哥大學(xué)圖書館學(xué)研究生院對(duì)技術(shù)、方法和管理技能的忽視開(kāi)始,美國(guó)學(xué)者一直關(guān)注新技術(shù)的出現(xiàn)對(duì)圖書館學(xué)和圖書館事業(yè)以及情報(bào)學(xué)之間關(guān)系的影響。薩瑞塞維克認(rèn)為情報(bào)學(xué)與信息技術(shù)有密切的相關(guān)性,約赫蘭德認(rèn)為“一門學(xué)科必須由其研究對(duì)象而不是使用的工具來(lái)界定”。歐美研究者承認(rèn)信息技術(shù)在促進(jìn)情報(bào)學(xué)出現(xiàn)和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研究對(duì)象本身,連薩瑞塞維克也提出情報(bào)學(xué)面臨著最大的危險(xiǎn)――忽視用戶和人,只專注于技術(shù)。
如何看待技術(shù)在圖書情報(bào)學(xué)中的地位?一方面,生態(tài)后現(xiàn)代主義認(rèn)為技術(shù)既不是拖著我們尾巴隨它而走的獨(dú)立力量,也不僅僅是一種中立的、非價(jià)值的工具集合,每一種新技術(shù)的目標(biāo)和設(shè)計(jì)都反映了我們的文化。圖書情報(bào)學(xué)中的技術(shù)應(yīng)該成為學(xué)科價(jià)值和方向的體現(xiàn)和實(shí)現(xiàn)手段。另一方面,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中的非理性主義認(rèn)為技術(shù)是知識(shí)體系理性的表現(xiàn)形式,是現(xiàn)代社會(huì)最能展現(xiàn)理性實(shí)力的手段。現(xiàn)代性的圖書情報(bào)學(xué)研究正是用技術(shù)證明人對(duì)社會(huì)存在的掌控以及其在學(xué)術(shù)群體中的尊嚴(yán)地位。圖書情報(bào)學(xué)中普遍存在的工具理性被人們質(zhì)疑,其解決之路又在哪里?①在于對(duì)技術(shù)的重新定位,即技術(shù)為理論、實(shí)踐和價(jià)值服務(wù),而不是技術(shù)本身是理論、實(shí)踐和價(jià)值;②在于技術(shù)適用范圍的確定,并不是所有問(wèn)題都適合用技術(shù)解決以及在方法選擇表中的排序。非理性主義中對(duì)工具理性的發(fā)難、強(qiáng)調(diào)情感思維和感性方法可以作為突破口。傳統(tǒng)的社會(huì)學(xué)方法,扎根理論,也能促使圖書情報(bào)工作的改善并提供新的思路。
3.2 多種聲音的存在
圖書情報(bào)學(xué)研究的一大特點(diǎn)就是多種聲音同時(shí)存在。有人統(tǒng)計(jì)國(guó)內(nèi)關(guān)于圖書館學(xué)研究對(duì)象的觀點(diǎn),20世紀(jì)90年代末有五六十種之多。該特點(diǎn)一方面體現(xiàn)出研究者對(duì)研究對(duì)象、本質(zhì)和基點(diǎn)的固執(zhí)追求;另一方面又表明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研究正愈來(lái)愈顯現(xiàn)出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非中心化、非基礎(chǔ)主義、非理性主義和視角主義的特征。表現(xiàn)為:①拋棄“普遍性知識(shí)、總體化語(yǔ)言”,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總體總是不完全的,需要增補(bǔ),這種增補(bǔ)有賴于認(rèn)識(shí)的深入以及認(rèn)識(shí)對(duì)象本身的發(fā)展;②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客體和主體都是非中心的、非封閉的,只有正確認(rèn)識(shí)圖書情報(bào)學(xué)認(rèn)識(shí)對(duì)象和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的位置與空間,才不會(huì)局限于“機(jī)構(gòu)”與“非機(jī)構(gòu)”、“大圖書情報(bào)觀”與“小圖書情報(bào)觀”之爭(zhēng);③圖書情報(bào)學(xué)中不存在絕對(duì)的真理和永恒的框架,即不能對(duì)任何觀點(diǎn)抱以絕對(duì)化或力求學(xué)界統(tǒng)治地位的想法,也不能將追求真理與追求絕對(duì)等同;④對(duì)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研究應(yīng)脫離固定界限概念限制,傳統(tǒng)哲學(xué)和邏輯實(shí)證主義推崇的是概念分析,但其分析對(duì)象往往是抽象的和靜止的,忽略了對(duì)象本身的動(dòng)態(tài)發(fā)展和復(fù)雜性,圖書館學(xué)所關(guān)注的“圖書館”正是如此。國(guó)內(nèi)圖書館學(xué)研究?jī)A向于找到學(xué)科研究基點(diǎn),試圖通過(guò)明確學(xué)科基點(diǎn)和學(xué)科體系的建立來(lái)指導(dǎo)實(shí)踐并確立其科學(xué)地位的做法體現(xiàn)出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的碰撞與沖突、堅(jiān)持與突破。
3.3 身份危機(jī)
關(guān)于圖書情報(bào)學(xué)身份的迷惑以及由此帶來(lái)的危機(jī)感一直是研究者關(guān)注但又不愿直面的問(wèn)題。學(xué)科的地位以及由于現(xiàn)代性理論中對(duì)理性、地位的尊崇使得我們一直陷入“術(shù)”與“學(xué)(道)”爭(zhēng)論的怪圈中。從圖書館專業(yè)(1ibrarianship)、圖書館研究(1ibrary study)到圖書信息學(xué)(1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y),這些變化可以顯示此學(xué)科研究取向的范式遞變,圖書信息學(xué)的研究與學(xué)科本身也從錄音帶、影帶、光盤到網(wǎng)絡(luò),不斷學(xué)習(xí)調(diào)整,以求跟得上技術(shù)變遷的腳步,但卻面臨名稱的爭(zhēng)議、學(xué)院歸屬、失焦的教育目標(biāo)、核心課程的難產(chǎn)、學(xué)生來(lái)源狹隘、本土性教材、研究工作等方面的困境。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能夠?yàn)檫@種身份危機(jī)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困境帶來(lái)什么改變?首先是思想的轉(zhuǎn)變,圖書情報(bào)事業(yè)不再是最初現(xiàn)代性中維護(hù)自由與公平的宏大事業(yè),在其合法性危機(jī)、技術(shù)導(dǎo)致的生存危機(jī)的背景下,需要從現(xiàn)代性時(shí)期的一項(xiàng)事業(yè)轉(zhuǎn)而成為后現(xiàn)代時(shí)期一項(xiàng)普通的職業(yè);其次轉(zhuǎn)變方法,比如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的建構(gòu)主義,即關(guān)注用戶使用圖書館的目的及圖書館對(duì)他的幫助是什么。現(xiàn)代性指導(dǎo)下的用戶研究由常態(tài)模式看用戶,因此,在某一時(shí)空背景下,某一群人的行為是一樣的,和個(gè)人的信息需求情境沒(méi)有相關(guān)性。建構(gòu)主義認(rèn)為使用者是在建構(gòu)環(huán)境,而不是適應(yīng)環(huán)境。所以,預(yù)測(cè)及了解用戶如何使用信息,必須先了解其信息需求產(chǎn)生的情境,進(jìn)而了解用戶是在怎樣的情境下使用圖書館。圖書館若能由意義建構(gòu)理論來(lái)了解用戶信息需求產(chǎn)生的情境,并提供幫助,圖書館使用率必能提高,圖書館存在的意義得以體現(xiàn)。
4 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指引下的圖書情報(bào)學(xué)未來(lái)――一種可能
4.1
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存在環(huán)境
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誕生與知識(shí)和信息傳播及利用密切相關(guān)。利奧塔對(duì)后現(xiàn)代社會(huì)知識(shí)和科學(xué)狀況的考察展現(xiàn)出社會(huì)知識(shí)的深層特征。①知識(shí)的信息化(量化和可操作化),以計(jì)算機(jī)運(yùn)用為代表的信息技術(shù)正迅速改變知識(shí)的性質(zhì),只有將知識(shí)轉(zhuǎn)化為可操作的信息量,才能被生產(chǎn)者和使用者獲取和使用。②知識(shí)的商品化。知識(shí)和認(rèn)識(shí)者之間不再是單純的外在關(guān)系,而是為了價(jià)值的生產(chǎn)者和消費(fèi)者的供求關(guān)系。如此,知識(shí)的獲得(包括研究)和知識(shí)傳播(包括教學(xué))都發(fā)生了改變。圖書情報(bào)學(xué)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知識(shí)的信息化要求那些傳統(tǒng)載體形式的知識(shí)必須改變,否則將失去存在的價(jià)值和可能性;知識(shí)的商品化使得人們獲取知識(shí)的動(dòng)機(jī)、知識(shí)流動(dòng)的方式、知識(shí)的生產(chǎn)都將與利益、價(jià)值和金錢緊密相關(guān),那么純粹的閱讀、文化的教養(yǎng)與熏陶、知識(shí)的提供,乃至傳統(tǒng)的保存和繼承都將受到金錢的制約與改變,傳統(tǒng)的圖書館使命和情報(bào)機(jī)構(gòu)的工作該將何去何從?
4.2
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認(rèn)識(shí)與存在
對(duì)認(rèn)識(shí)和存在關(guān)系的重新解讀是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的重點(diǎn)。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影響和解釋下的圖書情報(bào)學(xué)認(rèn)識(shí)和存在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為:①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認(rèn)識(shí)對(duì)象(存在)處于不斷的變化中,即社會(huì)存在的變化。從最
初施萊廷格以圖書館整理作為圖書館學(xué)研究對(duì)象開(kāi)始,圖書情報(bào)學(xué)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認(rèn)識(shí)經(jīng)歷了所謂的由淺入深、由具體到抽象和由機(jī)構(gòu)到知識(shí)信息的過(guò)程。這一變化正是由認(rèn)識(shí)對(duì)象變化引起,即從最初的圖書整理、簡(jiǎn)單的圖書資料提供,到近現(xiàn)代的信息檢索和提供,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認(rèn)識(shí)對(duì)象在不斷擴(kuò)展、豐富。于良芝也認(rèn)為隨著信息職業(yè)的細(xì)化,圖書館職業(yè)和情報(bào)工作所要解決的問(wèn)題發(fā)生了巨大變化。②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認(rèn)識(shí)與存在之間并不是簡(jiǎn)單的對(duì)立關(guān)系,而是統(tǒng)一于科學(xué)知識(shí)對(duì)存在的解釋中。即研究者自身的立場(chǎng)、文化知識(shí)背景和社會(huì)背景決定著其對(duì)存在的解釋,正是這種理解的歷史性使得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知識(shí)必須建立在解釋的基礎(chǔ)上,并不存在絕對(duì)的客觀立場(chǎng)。因此,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研究必須出現(xiàn)多種聲音,即視角的多元化、解釋的多元化和意義的多重性。同時(shí),這種解釋性的認(rèn)識(shí)表示我們認(rèn)可的學(xué)說(shuō)和觀點(diǎn)也是建立在視域融合的基礎(chǔ)上,即研究群體的共識(shí)。③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認(rèn)識(shí)對(duì)象只有變化、復(fù)雜,沒(méi)有絕對(duì)的唯一和本質(zhì),試圖找到各種現(xiàn)象和存在簡(jiǎn)單化的努力都無(wú)助于問(wèn)題的解決。④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認(rèn)識(shí)本身是開(kāi)放的、多元的,且僅僅是對(duì)存在的一種解讀。⑤單純的概念不能解決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問(wèn)題,固定界限的圖書館概念不能把握龐大復(fù)雜且流動(dòng)著的圖書情報(bào)學(xué)認(rèn)識(shí)對(duì)象。
4.3
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學(xué)科體系
傳統(tǒng)的圖書情報(bào)學(xué)學(xué)科體系大多以線性的、單一的、封閉的模樣出現(xiàn),并試圖囊括所有認(rèn)識(shí)存在。在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解構(gòu)主義、利奧塔的知識(shí)合法性判斷等觀點(diǎn)指引下,圖書情報(bào)學(xué)的學(xué)科體系應(yīng)具備以下特征:①開(kāi)放性,即學(xué)科體系的邏輯解構(gòu)容許新內(nèi)容的加入;②非確定性,學(xué)科體系不能成為宏大的“元敘事”,即不能試圖成為解釋一切的標(biāo)準(zhǔn)統(tǒng)一語(yǔ)言,也不能試圖規(guī)定研究群體的話語(yǔ),話語(yǔ)的多樣性以及學(xué)科知識(shí)的話語(yǔ)敘述傾向才是學(xué)科的發(fā)展趨勢(shì);③非線性,即學(xué)科體系的各要素間充滿差異且彼此互補(bǔ),邏輯結(jié)構(gòu)體現(xiàn)的是多向性,而非直線單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