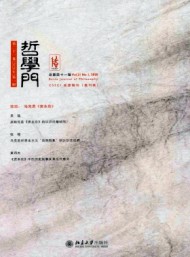哲學(xué)的起源與西學(xué)概論范文
時(shí)間:2023-10-19 16:05:27
導(dǎo)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哲學(xué)的起源與西學(xué)概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xiàn),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guān)鍵詞]中國文藝學(xué) 日本近代文藝思想 中間人
歷史上,日本一直是在學(xué)習(xí)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形成并發(fā)展著自己的文化。但近代以來,這種狀況卻發(fā)生了逆轉(zhuǎn)。近代日本在吸收和融會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為東西方思想的交匯點(diǎn)。在社會科學(xué)的各個(gè)領(lǐng)域――包括文藝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日本對于中國學(xué)術(shù)近代化的完成都起到了傳播西方思想和學(xué)說之“中間人”的重要作用。
“文藝學(xué)”作為一種現(xiàn)代形態(tài)的學(xué)科,在我國雖然是在20世紀(jì)中、后期才得以建立和發(fā)展,但20世紀(jì)初的“西學(xué)東漸”以及將西方一些近現(xiàn)代的學(xué)術(shù)思想、觀念、體系、方法譯介到中國,對中國文藝學(xué)科的創(chuàng)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文藝學(xué)西學(xué)東漸的途徑包括兩個(gè)方面:一是直接從西方輸入,一是間接從日本輸入。其中,近代日本作為輸入西方文藝觀念、文藝?yán)碚摗⑺囆g(shù)批評和藝術(shù)史學(xué)的“中間人”,對中國文藝學(xué)科由古典形態(tài)向近代形態(tài)的轉(zhuǎn)換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為現(xiàn)代形態(tài)的中國文藝學(xué)科的建立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16世紀(jì)末到18世紀(jì)中期西方耶穌會士東來及其“學(xué)術(shù)傳教”活動是歷史上東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學(xué)術(shù)界稱之為第一次西學(xué)東漸。這對中日兩國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接受西方先進(jìn)文化的契機(jī),但兩國的統(tǒng)治者和知識分子對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態(tài)度。導(dǎo)致了此后兩國文化發(fā)展的不同進(jìn)程。
在日本,西學(xué)的傳入可以分為兩個(gè)階段:1640年以前的南蠻文化和此后的“蘭學(xué)”。由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突出表現(xiàn)在、社會思想和倫理觀念方面。南蠻文化時(shí)期大量傳入的西方科學(xué)技術(shù)如天文歷法、地理學(xué)、航海術(shù)等經(jīng)過曲折的發(fā)展,為日本近代文化的產(chǎn)生作了準(zhǔn)備,并在此基礎(chǔ)上興起了“蘭學(xué)”。蘭學(xué)時(shí)期,大部分日本知識分子對西學(xué)基本持肯定、歡迎態(tài)度,而且不遺余力地進(jìn)行翻譯和宣傳,對蘭學(xué)在日本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xiàn)。而幕府統(tǒng)治者對西方文化在采取了長期的反對甚至鎮(zhèn)壓政策之后,也逐漸認(rèn)識到蘭學(xué)對于發(fā)展生產(chǎn)和鞏固統(tǒng)治的積極作用。因此,19世紀(jì)初,蘭學(xué)成為被統(tǒng)治階級所承認(rèn)、為政權(quán)服務(wù)的“公學(xué)”,得到幕府的保護(hù)和支持。這些積極的外部條件使得蘭學(xué)能夠在日本得以長期穩(wěn)步地發(fā)展并不斷得到普及。蘭學(xué)通過近百年的科學(xué)研究活動,加深了對西方科學(xué)內(nèi)涵以至社會原理的體系性理解,并形成了一個(gè)獨(dú)立從事西方科學(xué)研究的社會群體。由此,“蘭學(xué)”成為日本社會與西方先進(jìn)文化聯(lián)系的紐帶,為“明治維新”和日本近代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制度上、科學(xué)上以及思想上的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
而在一衣帶水的中國,十九世紀(jì)后半葉,中國社會延續(xù)兩千多年的封建統(tǒng)治日漸衰敗,長期處于封閉狀態(tài)下的中國人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然而事實(shí)上,不論是在科學(xué)技術(shù)層面、社會制度層面還是思想文化層面,中國都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西方國家。1840年的。西方列強(qiáng)用堅(jiān)船利炮強(qiáng)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在內(nèi)憂外患的情境之下,先進(jìn)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睜眼看世界”。他們不僅僅以科技層面的聲光電化之知識、堅(jiān)船利炮之技藝為滿足,還要求進(jìn)一步探究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以及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思想和學(xué)說。可以說直到這時(shí),中國人才開始真正認(rèn)識到西方文化的先進(jìn)性和全面學(xué)習(xí)西方文化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以各種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思想學(xué)說為中心的西方文化思想開始廣泛傳入中國,在中國知識界形成了第二次“西學(xué)東漸”的熱潮。
十九世紀(jì)末二十世紀(jì)初的西學(xué)東漸帶來了近代形態(tài)的西方文化,對于中國古典形態(tài)的文藝學(xué)來說,也同樣經(jīng)歷了一次近代化的啟蒙。西方近代美學(xué)和文藝思想的輸入推動了中國的文藝學(xué)從古典向現(xiàn)代的轉(zhuǎn)變。這一轉(zhuǎn)變涉及其性質(zhì)、內(nèi)容、形式、方法、體例及思維方式等各個(gè)方面,從而使中國文藝學(xué)的近代化成為可能。
文藝學(xué)西學(xué)東漸的途徑包括兩個(gè)方面:一是直接從西方輸入,一是間接從日本輸入。其中,近代日本作為輸入西方文藝觀念、文藝?yán)碚摗⑺囆g(shù)批評和藝術(shù)史學(xué)的“中間人”,對中國文藝學(xué)科由古典形態(tài)向近代形態(tài)的轉(zhuǎn)換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為現(xiàn)代形態(tài)的中國文藝學(xué)科的建立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近代以來,日本學(xué)習(xí)西方文化的狀況達(dá)到了空前的。明治維新之后的“文明開化”運(yùn)動使得日本僅用了短短幾十年的時(shí)間便取得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jīng)過一、二百年才取得的成就。日本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成功也刺激了中國人學(xué)習(xí)西方的愿望。但當(dāng)時(shí)從中國直接去歐美以及翻譯西文著作比去日本并翻譯日文書籍相對困難得多,而且日本已經(jīng)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并且經(jīng)過了篩選和消化。因此向去蕪存菁的臨國日本學(xué)習(xí),比直接向西方國家學(xué)習(xí)要簡便有利得多。當(dāng)時(shí)的一些開明知識分子已經(jīng)意識到了這一點(diǎn),如張之洞在《勸學(xué)篇》中說:“西書甚繁,凡西學(xué)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jié)而酌改之。”[1](《游學(xué)第二》)“我取徑東洋,力省效速”[1](《廣譯第五》)。可以說,中國人把通過中日文化交流的渠道來學(xué)習(xí)和吸收西方文化看作了一條可以事半功倍的捷徑。而向日本學(xué)習(xí)的主要途徑就是派遣留學(xué)生。從十九世紀(jì)末到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中國派往日本的留學(xué)生多達(dá)五萬余人。大批的留日學(xué)生為傳播西方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xiàn)。他們在日本接受了許多新思想、新知識。并通過翻譯日文書籍將這些新文化介紹到國內(nèi)。
西方近代美學(xué)和文藝思想同樣大多是由留日學(xué)生根據(jù)日文書籍或西方原著的日譯本翻譯介紹到中國的。十九世紀(jì)末二十世紀(jì)初,日本文藝學(xué)由古代到近代的轉(zhuǎn)型已經(jīng)基本完成,在學(xué)科體系、范疇、觀念、方法等方面都已充分吸收、融合了西方思想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可以說已經(jīng)基本具備了近代化學(xué)科的性質(zhì)。文藝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日文書籍的大量翻譯和廣泛傳播,對中國古典文藝學(xué)的各個(gè)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促使中國的文藝學(xué)開始向近代化學(xué)科轉(zhuǎn)變。從十九世紀(jì)末到二十世紀(jì)二、三十年代,中國翻譯日本文藝學(xué)著作的數(shù)量不斷增加,水平也不斷提高。因此,郭沫若在評論中日文藝學(xué)關(guān)系時(shí)認(rèn)為:“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xué)生建筑成的。……就因?yàn)檫@樣,中國的新文藝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禮的。”[2](P33)可以說,中國文藝學(xué)近代轉(zhuǎn)型的過程。主要是一個(gè)向日本學(xué)習(xí)的過程,中國近代文藝學(xué)的各個(gè)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日本的影響。
日本文藝思想對中國的影響首先表現(xiàn)在近代文藝學(xué)美學(xué)概念和范疇的引入。日本人在接受西方新思想、新學(xué)說時(shí),除了用日語直接音譯西方外來語之外。還利用漢語的意譯法創(chuàng)造了大量新詞匯。文藝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的許多重要概念 或范疇如“哲學(xué)”、“美學(xué)”、“文學(xué)”、“美術(shù)”等,最初都是日本學(xué)者借用漢語翻譯西方著作時(shí)確定下來的。由于這些用漢語表達(dá)的概念或范疇大都比較準(zhǔn)確地把握了西方文藝思想的內(nèi)容與特征,因此中國學(xué)者在翻譯日文書時(shí)也都普遍沿用了這些表達(dá)方式。關(guān)于這種情況,中國近代美學(xué)的開創(chuàng)者王國維曾在《論新學(xué)語之輸入》一文中作過較為公允的評價(jià)。他說:“數(shù)年以來,形上之學(xué)漸入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于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之文學(xué)界,……夫普通之文字中,固無事于新奇之語也,至于講一學(xué),治一藝,則非新增語不可。而日本之學(xué)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要之,處今日而講學(xué),已有不能不增新語之勢。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勢無便于此者矣。”[3](P387)這些新學(xué)語的普遍使用,表明了西方先進(jìn)的文藝思想已經(jīng)進(jìn)入中國文藝學(xué)的視野之中,成為近代文藝學(xué)所表達(dá)的內(nèi)容。
由日本傳入的新學(xué)語的接受和使用一方面使許多基本范疇和概念在中國文藝學(xué)中確定下來,為中國近代文藝學(xué)體系的形成做了必要的準(zhǔn)備: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美學(xué)和文藝觀念的更新,促進(jìn)了中國文藝學(xué)在表達(dá)方式上的變革。
表達(dá)方式的變革在話語特征上體現(xiàn)為對美學(xué)和文藝?yán)碚摰谋硎龈訙?zhǔn)確和規(guī)范。中國古典文藝學(xué)的話語表述特征是詩意化,思想家們慣于用名言雋語、比喻例證的形式來表述自己的思想。日本新學(xué)語的引入,使中國古典文藝學(xué)向近代形態(tài)的轉(zhuǎn)換有了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上的支持。這對于近代文藝學(xué)所要求的清晰、精確的邏輯分析話語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更為重要的是,表達(dá)方式的變革在外在形式上體現(xiàn)為文體表現(xiàn)形態(tài)的轉(zhuǎn)換。中國古典文藝學(xué)以“詩話”、“詞話”為主的文體形態(tài)受到?jīng)_擊,具有近代特征的“新文體”逐漸被接受和運(yùn)用。十九世紀(jì)末二十世紀(jì)初,一些留日學(xué)者借鑒日本經(jīng)驗(yàn),主張沖破中國傳統(tǒng)的文體規(guī)范,變革舊的文體形式,開展了一場具有近代意義的“文體解放”運(yùn)動。
由日本傳人的“新學(xué)語”帶來了大量的新知識和新見解。對于正處于啟蒙時(shí)期的中國文藝學(xué)來說,新知識意味著新的思想內(nèi)容,新見解則代表著新的文藝觀念,而這些都遠(yuǎn)非中國舊有的“詞章”、“典故”所能包容。因此。表達(dá)新的思想內(nèi)容和新的文藝觀念的需要帶來了文學(xué)體裁的變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梁啟超倡導(dǎo)的“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梁啟超“文體改革”的主張直接受到日本文學(xué)的影響。他在《夏威夷游記》一文中提出“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其靈感就是來自于對日本明治時(shí)期的政論家德富蘇峰作品的閱讀感覺。“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shí)為文界別開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dāng)亦不可不起點(diǎn)于是也。”[4](P191)所謂“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引進(jìn)“歐西文思”,即要在詩文中表現(xiàn)西方的新思想、新精神。要達(dá)到這一目的,新文體的語言就應(yīng)該力求通俗化,做到通俗易懂,平易暢達(dá),并“時(shí)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4](P191),以便徹底沖破古文規(guī)范的限制,更自由地表達(dá)作者的情感。作為文體改革的主要倡導(dǎo)者,梁啟超不僅提出理論上的主張,而且身體力行,廣泛借鑒并學(xué)習(xí)日本新文體的風(fēng)格。他在作文章時(shí)“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佛書的名詞,不避詩詞的典故,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5](P220),努力嘗試各種新的表達(dá)方式。這種日本化的新文體對二十世紀(jì)初中國文壇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幾使一時(shí)之學(xué)術(shù),浸成風(fēng)尚。而我國文體,亦遂因此稍稍變矣。”[6](P95)
日本近代文藝思想的大規(guī)模引進(jìn)與吸收,不僅使中國文藝學(xu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思想材料和新的表現(xiàn)方式: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文藝學(xué)具體的學(xué)術(shù)存在形態(tài)也在日本近代文藝學(xué)的強(qiáng)勁影響下自然而然地開始了由古典向近代的轉(zhuǎn)換。這種轉(zhuǎn)換以方法的更新為依據(jù),以體系的建構(gòu)為目標(biāo),以各種新的文藝思潮、流派的引介為具體內(nèi)容,在文藝學(xué)原理、藝術(shù)史學(xué)、文藝?yán)碚摵团u等方面都有所體現(xiàn)。
中國文藝學(xué)中關(guān)于美學(xué)和藝術(shù)原理的基本體系,主要是受到日本藝術(shù)理論家黑田鵬信的影響。他的《藝術(shù)概論》一書是一部系統(tǒng)講述藝術(shù)一般原理的著作。其內(nèi)容包括從藝術(shù)的本質(zhì)特征到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欣賞、從藝術(shù)分類、藝術(shù)起源到藝術(shù)內(nèi)容形式和風(fēng)格流派等,包含了藝術(shù)理論中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問題。這是最早被翻譯成中文的有關(guān)藝術(shù)理論的書籍,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問題不僅在當(dāng)時(shí)為中國藝術(shù)理論體系提供了范式,而且其中的主要部分至今仍沿用在中國藝術(shù)概論的教學(xué)過程中。此外,黑田鵬信的另外兩部著作《美學(xué)綱要》和《藝術(shù)學(xué)概論》也被譯成中文。這三本譯作對于中國美學(xué)和藝術(shù)基本原理體系的形成產(chǎn)生了深刻而又持久的影響。
在藝術(shù)史論方面,二十世紀(jì)二三十年代對日本美術(shù)史家木村莊八和板垣鷹穗等人的系列西洋美術(shù)史著作的譯介,是當(dāng)時(shí)重要的理論成果。其中魯迅翻譯的日本學(xué)者板垣鷹穗所著《近代美術(shù)史潮論》對中國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這本書將近代美術(shù)如何演進(jìn)到現(xiàn)代美術(shù)作了全面的闡述,揭示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美術(shù)思潮發(fā)生的根源和必然性。這本介紹西方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史的演變過程的著作,不僅為中國美術(shù)界提供了近代新的藝術(shù)及其思潮的信息,而且也為中國的美術(shù)史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方法,使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shù)思潮的產(chǎn)生有了必要的理論準(zhǔn)備。當(dāng)時(shí),學(xué)習(xí)和借鑒日本的成果成為開展近代意義上的藝術(shù)史論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許多后來很有成就的藝術(shù)史論家都曾翻譯過日本學(xué)者的著作,并借鑒其內(nèi)容、方法及體例等進(jìn)行近代藝術(shù)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成果。
在文藝?yán)碚摵臀乃嚺u方面,日本對中國的影響更為顯著。“五四”以后,中國文學(xué)界徹底擺脫了封建文化的制約。開始全面吸收近現(xiàn)代新的文藝思想并應(yīng)用到文藝創(chuàng)作和評論當(dāng)中去。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當(dāng)時(shí)中國新文學(xué)的主要人物幾乎全部都是留日學(xué)生,如魯迅、郭沫若、郁達(dá)夫、成仿吾等,他們在倡導(dǎo)新文學(xué)的同時(shí)還翻譯了很多日本書籍,其中以廚川白村的影響最大。他的代表作是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征》,在引言中,魯迅先生給予這部作品如下的評價(jià):“……作者自己就很有獨(dú)創(chuàng)力,于是此書也就成為一種創(chuàng)作,而對于文藝,即多有獨(dú)到的見地和深切的會心。”[7](P296)廚川白村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的達(dá)十四種之多,他的文藝思想一度成為中國文藝?yán)碚摰臏?zhǔn)繩,對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中國文藝學(xué)界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這一時(shí)期的許多藝術(shù)家、文藝?yán)碚摷摇⑽乃嚺u家也都是留日學(xué)生,他們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新的文學(xué)和藝術(shù)思潮,寫作了大量理論文章,內(nèi)容涉及藝術(shù)本體論、藝術(shù)創(chuàng)作欣賞及批評理論、藝術(shù)思潮與當(dāng)代藝術(shù)評論等諸多方面。他們對近代文藝?yán)碚撝幸恍┳罨镜膯栴}都作了深入的思考,使從國外學(xué)到的思想和理論真正融入到中國文藝學(xué)之中,為中國近代文藝學(xué)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xiàn)。
可以看出,中國文藝學(xué)由古典形態(tài)向近代形態(tài)的轉(zhuǎn)換是在日本這個(gè)“中間人”的作用下發(fā)端、開展并逐步完成的,這是一個(gè)不能忽視的歷史事實(shí)。因此,在繪制中國現(xiàn)代文藝學(xué)發(fā)展史的構(gòu)圖中。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添加“日本”這個(gè)板塊,對于更全面地認(rèn)識中國文藝學(xué)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以及更好地進(jìn)行東西方文藝學(xué)領(lǐng)域的交流,都具有相當(dāng)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張之洞,勸學(xué)篇?勸學(xué)篇書后,馮天瑜、尚川評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沫若文集》第10卷,桌子的跳舞,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論新學(xué)語之輸入,王國維論學(xué)集,傅杰編校,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7年版。
[4]梁啟超,夏威夷游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22,中華書局,1898年版。
[5],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xué),見《文集3》,歐理哲生編,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
[6]諸宗元,譯書經(jīng)眼錄序例,見《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張靜廬輯注,中華書局,1957年版。
[7]葉渭渠,日本文化史,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
篇2
【關(guān)鍵詞】梁啟超;目錄學(xué)思想;佛經(jīng)目錄
A Study of an Article by LIANG Qi-chao
the place of the Catalogue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Chinese Bibliography
WANG Li-ying SUN Xiao-mei YU Li-na CUI Jian-wei
(Liaocheng University Librar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China)
【Abstract】After reading the place of the Catalogue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Chinese Bibliography by LIANG Qi-chao, I was deeply moved by his spirit, attitude and courage when doing research. The article also makes an inquiry into LIANG Qi-chao’s bibliographical thoughts.
【Key words】LIANG Qi-chao; Bibliographical thoughts; Catalogue of Buddhist Scriptures
梁啟超先生的《佛家經(jīng)錄在中國目錄學(xué)之位置》(以下簡稱《位置》)一文,為中國古典目錄學(xué)的研究開啟了一個(gè)新的領(lǐng)域,為佛教目錄學(xué)研究的開山之作。梁啟超以其深厚的佛學(xué)功底,在中國目錄學(xué)史研究上,第一個(gè)較系統(tǒng)地探討了元以前的佛經(jīng)目錄。《位置》一文列出了元以前出現(xiàn)的49部經(jīng)錄,對其中的29部進(jìn)行了或祥或略的研究,對中國佛教目錄的重要之作一一提其旨要、評價(jià)得失。《位置》一文不僅體現(xiàn)出梁啟超先生深厚的目錄學(xué)功底,更讓人贊嘆的是其治學(xué)精神、態(tài)度和勇氣。
1 梁啟超先生之治學(xué)
1.1 治學(xué)之精神――妙手偶得之
梁啟超先生從前期主要從事西學(xué)新書目錄的編纂活動,轉(zhuǎn)而至后期從事中國傳統(tǒng)目錄的編纂和對佛經(jīng)目錄的整理研究上。梁啟超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集中研究了中國傳統(tǒng)目錄學(xué)和佛經(jīng)目錄。據(jù)余紹宋回憶:“六年前(1925年),予避亂居天津,與任公梁先生過從最密。時(shí)任公方撰諸家書目提要,陳數(shù)十種薄錄之書于案頭,朝夕討論。”[1]十年間他完成了中國目錄學(xué)史方面的研究。梁啟超先生對佛經(jīng)目錄的研究始于他對中國佛學(xué)史的研究,先生對于佛經(jīng)目錄學(xué)的研究并非刻意為之。
由此,筆者想到現(xiàn)如今學(xué)術(shù)研究中的功利性問題。中山大學(xué)古文獻(xiàn)研究所的許云和教授在其所著的《漢魏六朝文學(xué)考論》的前言中寫到:“本書不是對漢魏六朝文學(xué)的一個(gè)概論,也不是對漢魏六朝文學(xué)的某一個(gè)問題的專門研究,筆者只是就這一時(shí)期所感興趣的一些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2]感興趣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第一要件,感興趣才能有熱情,有熱情才會“享受”學(xué)術(shù)研究的寂寞,這大抵是許多有作為的文人學(xué)者最為珍貴的品質(zhì)。我們現(xiàn)在的學(xué)術(shù)研究卻頗多功利色彩,很多學(xué)者做研究的出發(fā)點(diǎn)并不在興趣,研究中的應(yīng)景之作不在少數(shù),可真正能夠啟迪后人學(xué)者的卻寥寥無幾。
1.2 治學(xué)之態(tài)度――不人云亦云
對于佛經(jīng)的起源問題,梁啟超并未采信眾人的說法,而是認(rèn)為“經(jīng)錄蓋起于道安”,“則安公之作前無所承可知”,[3]東晉道安的《綜理眾經(jīng)目錄》(簡稱《安錄》)乃是佛經(jīng)目錄的開山之作。而對《安錄》之前有記載的經(jīng)錄尚有七部:《古經(jīng)錄》、《舊錄》、《漢時(shí)佛經(jīng)目錄》、《漢錄》、《眾經(jīng)錄》(竺法護(hù))、《眾經(jīng)錄》(聶道真)、《趙錄》。先生經(jīng)過系統(tǒng)的考辨,認(rèn)為這些經(jīng)錄或是偽書,或是古人厚古薄今,將近書誤認(rèn)為是古書。
梁啟超在考辨《安錄》之前的幾部經(jīng)錄的真?zhèn)螘r(shí),不敢茍同世人已普遍認(rèn)同的觀點(diǎn),而是抱著懷疑的態(tài)度,將相關(guān)文獻(xiàn)中的信息聯(lián)系起來加以考量,在抽絲剝繭之后得出結(jié)論。先生未曾對任何已有結(jié)論妄下斷語,真或假、對或錯(cuò),自然需要有理有據(jù)的評辯,其間先生嚴(yán)肅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態(tài)度,可見一斑。
1.3 治學(xué)之勇氣――敢為人之先
佛教在漢代開始傳入中國,從東漢到隋唐的幾百年間,它在我國得到了廣泛而迅速的發(fā)展。佛經(jīng)是隨著佛教的盛行而日漸豐富起來的,眾多種類的佛經(jīng)目錄由此而自然而然的得到發(fā)展,歷代出現(xiàn)的佛經(jīng)專科目錄也至七十七部之多[4]。我國的佛經(jīng)目錄時(shí)代久遠(yuǎn),卷帙浩繁,體系完備,著錄精良,但長期以來,目錄學(xué)家深受“華夷之辨”思想的影響,對其的研究始終無人問津。在“華夷之辨”思想的影響下,儒家文化被無限放大,成為社會的正統(tǒng)文化,儒學(xué)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這使得佛教文獻(xiàn)盡管在東漢時(shí)期就已出現(xiàn),卻一直沒有受到應(yīng)有的重視,在整個(gè)歷史進(jìn)程中基本被排除在官方文獻(xiàn)之外。也正因?yàn)槿绱耍鸾?jīng)目錄一直被排斥在我國目錄學(xué)家的視野之外,對其在中國古典目錄學(xué)中的作用也多有忽略。
梁啟超先生于1920年歐洲游歷回國后,開始集中系統(tǒng)地研讀佛經(jīng),他對上起東晉道安的《綜理眾經(jīng)目錄》以來的各種重要經(jīng)錄作了較為系統(tǒng)的發(fā)微性質(zhì)研究。先生在學(xué)者恥于探討經(jīng)錄的風(fēng)氣之下,敢為天下人之前,以科學(xué)的精神,嚴(yán)謹(jǐn)?shù)膽B(tài)度研究佛經(jīng)目錄,實(shí)難不教人佩服其治學(xué)之勇氣。且對于佛經(jīng)目錄之研究,先生以前并無人涉及,因此先生的研究可說并無可參考之物。面對浩繁的佛經(jīng),要整理、辨?zhèn)巍⑻嵋瑢?shí)屬浩大的工程,但梁啟超先生并未產(chǎn)生半點(diǎn)推諉退縮之意,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佛經(jīng)目錄的整理當(dāng)中,這種如黑夜之中無指引地追尋光明的歷程,確是多數(shù)學(xué)者沒有勇氣開始的。
2 梁啟超先生之佛教目錄學(xué)思想
《位置》一文亦表達(dá)出梁啟超先生的目錄學(xué)主張,分類與提要是目錄學(xué)中兩件要緊事,故筆者僅就這兩個(gè)問題略表一點(diǎn)薄見。
2.1 分類
梁啟超歷來重視佛錄在圖書分類上的發(fā)展變化,《位置》一文中用大篇幅闡述了佛錄在分類上的獨(dú)到之處,特別是將一些在分類上做的比較優(yōu)秀的佛錄以圖表的形式將其分類情況詳細(xì)列出。通過對歷代佛錄分類方法進(jìn)行細(xì)致系統(tǒng)的梳理,梁啟超先生亦將佛錄分類方法的歷史變革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并得出結(jié)論:佛錄的分類“極復(fù)雜而周備”[3]。
梁啟超先生經(jīng)過系統(tǒng)的梳理,共總結(jié)出五種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佛錄分類方法。(1)收錄當(dāng)時(shí)所有佛經(jīng)的經(jīng)錄。“《安錄》(《綜理眾經(jīng)目錄》)是將當(dāng)時(shí)所有佛經(jīng)之全部加以整理有組織有主張的一部創(chuàng)作。”(2)“專記一人或一派之著述者”。[3]起于晉聶道真的《眾經(jīng)錄》,其后《菩提流支錄》和《靈裕法師譯經(jīng)錄》也屬于此類。(3)“專記一朝代或一地方之著述者。”[3]首開其緒的是十六國姚秦時(shí)釋僧鋇摹抖秦錄》,專記一朝譯經(jīng);又有無撰人姓名之《廬山錄》,專記一地方的譯著。(4)按經(jīng)錄是否按照大小乘進(jìn)行分類。(5)按經(jīng)錄是重分類及真?zhèn)芜€是重年代及譯人,可把經(jīng)錄劃為二大流派:“一專注重分類及真?zhèn)危涠W⒅啬甏白g人。
2.2 提要
所謂提要,就是用簡短的語言介紹文獻(xiàn)的內(nèi)容旨趣、學(xué)術(shù)價(jià)值、作者生平、學(xué)術(shù)沿革、校勘經(jīng)過、版本優(yōu)劣等內(nèi)容特征。提要融入了作者對文獻(xiàn)研究的心得體會,保存了大量珍貴資料,具有重要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歷來備受學(xué)者推崇。[6]但我國經(jīng)錄長期缺少提要而僅有小注。經(jīng)錄完全意義上的提要僅有元代王古《圣教法室標(biāo)目》。王古的解題深得梁啟超先生的好評,梁甚至認(rèn)為其是“極有價(jià)值之經(jīng)錄”。但此后的諸經(jīng)錄卻并未沿襲該傳統(tǒng),實(shí)乃經(jīng)錄史上的一大憾事。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其實(shí)經(jīng)錄大多不備提要是由佛教本身的特點(diǎn)決定的。作為一種宗教,佛學(xué)不是訴諸人的理智,而是要求盲從,佛經(jīng)更是被視為神物,只可意會,不可言教;而眾多教派存在的現(xiàn)實(shí)也不允許對佛經(jīng)內(nèi)容有某種定論,故經(jīng)錄多無提要是可以理解的。[7]
梁啟超先生之所以如此重視經(jīng)錄提要之價(jià)值,與其提出的另外一條重要的目錄學(xué)原則“著書足以備讀者之顧問,實(shí)目錄學(xué)家最重要之職務(wù)也”是不無關(guān)系的。梁啟超認(rèn)為題解是目錄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應(yīng)該以盡量少的筆墨勾畫出所錄書的主要內(nèi)容,使人不見書而知其大意費(fèi)時(shí)少而收益大,幫助學(xué)人進(jìn)行學(xué)術(shù)研究。
梁啟超的為讀者顧問是對目錄學(xué)職能的重新界定,表述了目錄學(xué)的最重要職能,具有創(chuàng)新價(jià)值。它突破了古典目錄學(xué)的理論體系,構(gòu)成了近代目錄學(xué)的理論內(nèi)核。它的提出,標(biāo)志著由以文獻(xiàn)整理為中心的古典目錄學(xué)開始向以讀者為中心的近代目錄學(xué)的轉(zhuǎn)變。[8]
3 小結(jié)
梁啟超先生以其深厚的佛學(xué)功底,堅(jiān)持不懈的學(xué)術(shù)精神,將一千多年的佛教目錄史進(jìn)行系統(tǒng)的梳理。梁啟超先生開我國佛教目錄學(xué)研究之先河,其后佛教目錄學(xué)才逐漸為學(xué)者們所關(guān)注,從而拓展了目錄學(xué)研究領(lǐng)域,豐富了目錄學(xué)研究內(nèi)容。
【參考文獻(xiàn)】
[1]余紹宋.飲冰室藏書目錄序[M].見:夏曉紅.追憶梁啟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許云和.漢魏六朝文學(xué)考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梁啟超.佛家經(jīng)錄在中國目錄學(xué)之位置[A].飲冰室合集.專集六十七[C].北京:中華書局,1989.
[4]李杰,梁啟超.佛家經(jīng)錄在中國目錄學(xué)之位置初探[J].江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85(3):86-91.
[5]轉(zhuǎn)引自:李杰,梁啟超.佛家經(jīng)錄在中國目錄學(xué)之位置初探[J].江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85(3):86-91.
[6]劉明鐺.讀佛家經(jīng)錄在中國目錄學(xué)之位置――淺析梁啟超目錄學(xué)思想[J].湖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版),2000,27(6):98-101.
篇3
關(guān)鍵詞: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xué)統(tǒng);嬗變;賡續(xù)傳統(tǒng)
中圖分類號:G80-051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6-2076(2017)02-0063-06
Abstract: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it expla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and its traditional way and regeneration of modern dualistic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 in ancient times, cultivated the spiritual power of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re-adoration in the cultural soil of pan-morality, and took both the unity of form and spirit and the concurrency of study-think as the learning way to inherit the academic tradition. For a wide range of mass founda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learning in the world between the two-way interactions, it promoted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ousands of years to show a strong vitality. In the modern times, under the tide of Western learning,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on the western academic ideas. In the face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hoices of the new era, we must adhere to the traditional sports ontology to promote the China traditional sports regeneration, so that we can make it more brillia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academic tradition; evolution; persisting in tradition
中傳統(tǒng)的思維模式注重統(tǒng)緒,學(xué)統(tǒng)指治學(xué)的傳統(tǒng),是一門學(xué)術(shù)體系及其傳統(tǒng)的傳承。方朝輝認(rèn)為,所謂“學(xué)統(tǒng)”,是一種獨(dú)立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包括一門學(xué)問所具有的獨(dú)特的運(yùn)作邏輯、意義世界和研究范式等[1]。學(xué)統(tǒng)是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生命”之系統(tǒng),民族傳統(tǒng)體育是具有豐富內(nèi)涵與民族性的傳統(tǒng)文化,它的塑造、傳承與發(fā)展與中國古代學(xué)統(tǒng)息息相關(guān)。近代以來民族傳統(tǒng)體育在經(jīng)受到西方體育系統(tǒng)的沖擊后發(fā)生嬗變,其傳統(tǒng)性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用西式的學(xué)術(shù)眼光解讀中國傳統(tǒng)體育,導(dǎo)致其內(nèi)外兼修、形神兼?zhèn)涞膫鹘y(tǒng)特色丟失,進(jìn)一步導(dǎo)致現(xiàn)代中國體育在精神上無家可歸。
成中英認(rèn)為:“傳統(tǒng)是歷史性的存在,尤其具有現(xiàn)實(shí)的影響力,構(gòu)成伽達(dá)瑪所謂的‘有效歷史’。因之,它不必只是歷史,而有或多或少的規(guī)范權(quán)威,但其規(guī)范力量不一定來之理性自身的說服力,而是來自人的群體情感與習(xí)慣[2]。”歷史之賡續(xù),興滅繼絕,慎終追遠(yuǎn),黨的十以來多次提出復(fù)興傳統(tǒng)文化。在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領(lǐng)域,大多數(shù)學(xué)者開始意識到立足于本民族體育文化的重要性。而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根本精神、最高理念與終極意義是什么,需要從古老的學(xué)統(tǒng)精神中去探尋,正如鄧曦澤所說,有效的學(xué)統(tǒng)不僅是賡續(xù)歷史的必要條件,也是開拓未來的必要條件――學(xué)統(tǒng)是學(xué)術(shù)積累與創(chuàng)新的自覺有效的組織形式。一個(gè)不能賡續(xù)歷史的文化是絕不可能創(chuàng)新而開拓未來的,在學(xué)術(shù)的歷史與未來之間,最有效的連接就是學(xué)統(tǒng)[3]。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界都在賡續(xù)舊有學(xué)統(tǒng),有關(guān)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理論與實(shí)踐均未涉及這一方面,追問學(xué)魂、重構(gòu)學(xué)統(tǒng),對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再生、守護(hù)民族體育的獨(dú)特性具有重要作用,促使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獲得技術(shù)進(jìn)步與精神旨趣的同步發(fā)展,找到安身立命的終極歸宿,更好地傳承和發(fā)揚(yáng)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讓國人感受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真正的意義之源,自覺承擔(dān)其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責(zé)任。
1 述古:古代民族傳統(tǒng)體育蘊(yùn)含的學(xué)統(tǒng)文化
傳統(tǒng)是圍繞人類的不同活動領(lǐng)域而形成的代代相傳的行為方式,是一種對社會行為具有規(guī)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4]。傳統(tǒng)使得不同歷史階段之間保持了連續(xù)性與統(tǒng)一性,是決定文化形成、延續(xù)、發(fā)展或停滯的相對穩(wěn)定的內(nèi)在要素。中國古代的“學(xué)統(tǒng)”以儒家為宗、以經(jīng)學(xué)為源、以子學(xué)為流,各個(gè)領(lǐng)域“同宗孔孟”,而民族傳統(tǒng)體育是通過身體活動展現(xiàn)出來的、對傳統(tǒng)文化本質(zhì)特征的高度概括和反映,在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治學(xué)方法、技藝傳承上也充分體現(xiàn)了蘊(yùn)含孔孟之道的治學(xué)傳統(tǒng),表現(xiàn)出豐富的人文情感性與社會價(jià)值觀。
1.1 文化土壤:情感連帶和重禮崇德是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精神力量
社會中的人設(shè)計(jì)出各種活動和動作形式,氏族公社成員在生產(chǎn)實(shí)踐、政治、宗教和藝術(shù)活動中受教育,利用游戲、競技、唱歌、跳舞、記事符號進(jìn)行教育,利用神話傳說作為材料和手段[5]。可見,民族傳統(tǒng)體育自古就是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和手段,孔子著書設(shè)教,提倡學(xué)習(xí)要務(wù)于下學(xué)上達(dá),通過學(xué)習(xí)人情事理,修養(yǎng)德行,以求通達(dá)于仁義,“君子六藝”中的射和御就是古代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代表內(nèi)容,“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其目的不在競技,而在修身知禮,強(qiáng)健體魄為修外,知仁義禮制為修內(nèi),以”仁“為核心的道德體系與”禮“為核心的教化體系貫穿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始終。同樣,產(chǎn)生于勞動生產(chǎn)、原始宗教的中國民族傳統(tǒng)體育多是集體性的活動,帶有明顯的社會倫理價(jià)值取向,參與者通過情感連帶獲得情感能量,因而其活動更注重表演、娛樂、養(yǎng)生,從而具有怡情養(yǎng)性的效果,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形成了以“天人合一”為哲學(xué)基礎(chǔ),堅(jiān)持和諧、寬厚、禮讓的價(jià)值取向的體育運(yùn)動。
民族傳統(tǒng)體育以肢體動作為載體,將形而上的倫理價(jià)值轉(zhuǎn)化成為實(shí)體動作與團(tuán)體活動。司馬光在《投壺新格》中寫道,“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抵地”,投壺的活動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中正觀,即不偏不倚恰到好處,即是“大中至正”的學(xué)問。在程陽侗族搶花炮項(xiàng)目中每年的勝者來年要進(jìn)行還炮儀式來酬謝神恩,整個(gè)儀式中體現(xiàn)了嚴(yán)謹(jǐn)?shù)纳鐣刃颍诨顒又幸笕藗冏裱赖乱?guī)范,尊重老人,遵從傳統(tǒng),自覺履行義務(wù),傾注了人們對搶花炮儀式的情感。厚德載物,內(nèi)外兼修的傳統(tǒng)觀念、對宗教神靈或是祖先的崇拜及信仰、深受儒家正統(tǒng)思想影響的思維意識在民族傳統(tǒng)體育中得以體現(xiàn)。
朱熹說:“《大學(xué)》之條目,圣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xué)之次第,至為纖悉。”(《朱子四書或問》,《大學(xué)或問》卷一)他強(qiáng)調(diào)做學(xué)問以《大學(xué)》為先,其三綱領(lǐng)八條目是修學(xué)明德的根本。文以彰德,武以顯德,在民族傳統(tǒng)體育中一門技藝的傳承,首先要考察徒弟的德行,少林《拳經(jīng)拳法備要》中就強(qiáng)調(diào)“道勿濫傳”,應(yīng)傳“賢良之人”。《峨眉槍法》也有:“不知者不與言,不仁者不與傳。談元授道,貴乎擇人。”弟子入師門,也先要遵守一系列戒規(guī),所謂“未曾學(xué)藝先學(xué)禮,未曾習(xí)武先習(xí)德”。道德的審查在整個(gè)傳承過程中不會中斷,許多門派在傳授拳術(shù)中講究“口德、手德、身德”[6],以此磨礪心性,正己修身。武德使人具有“內(nèi)圣外王”的俠義精神,在內(nèi)具有圣人的才德,對外實(shí)行王道仁義,這也是理學(xué)代表人物陸九淵提倡的教育目的。
1.2 學(xué)統(tǒng)傳承:形神兼?zhèn)浜蛯W(xué)思并行是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學(xué)習(xí)方式
古代學(xué)統(tǒng)的追求除了上文提到的主體精神的涵養(yǎng),更需要真才實(shí)能的精益求精。“一層功夫又一層,層層深進(jìn),層層入細(xì)。由顯至隱,由粗如微,徹頭徹尾,逐層向里”[7]。形而上者為體,形而下者為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即無形之道體,形而下哲即萬事萬物的象與形,道是所有器物運(yùn)動發(fā)展的規(guī)律,無形之道存在于有形之器。因而,熟練博學(xué)是治學(xué)的基本功,深造自得的境界來自爐火純青的功夫,“拳打千遍,身法自現(xiàn)”,只有通過長期反復(fù)的苦練,才能體會到傳統(tǒng)體育某項(xiàng)技術(shù)的精髓,感悟其內(nèi)涵。
孔子稱“學(xué)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xué)則殆”,是學(xué)思兼進(jìn)者為圣[8]。思想獨(dú)立為學(xué)統(tǒng)之本[9],中人向來強(qiáng)調(diào)以學(xué)養(yǎng)思、以學(xué)促思、思融于學(xué),學(xué)統(tǒng)也是思統(tǒng)[10]。學(xué)武的關(guān)鍵在于“悟”,所謂“師傅領(lǐng)進(jìn)門,修行在個(gè)人”,西方人擅長邏輯推理,而中國人則講究悟性高深,悟性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精髓之一,武學(xué)一途,勤學(xué)苦練固然重要,但不管是套路還是心法,都要在無數(shù)的體悟中,窺其精要。“道可受兮不可傳”(《楚辭?遠(yuǎn)游》),中國傳統(tǒng)的傳承方式不可以言語傳之,不可以照本宣科,而需要心領(lǐng)神悟,學(xué)與思并用,自思自得。
古代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傳習(xí)方式以經(jīng)驗(yàn)為主體,尤其注重心傳心悟的學(xué)統(tǒng)模式,以心傳和神傳為核心,師徒之間具有高度的同頻共振,這不僅是知識的延續(xù),更是生命的延續(xù),即是中國傳統(tǒng)的性命之學(xué),生命之間的學(xué)習(xí)傳遞才能保持知識技藝最鮮活最本真的狀態(tài),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項(xiàng)目的傳習(xí)講究神韻的模仿與體悟,這就是用一個(gè)生命去讀另一個(gè)生命,技術(shù)是一座橋梁用以搭載文化的傳承。
1.3 社會基礎(chǔ):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群眾需求與致用機(jī)制具有雙向互動性
文化活動具有其原本功能和自身的社會使命,儒家文化的致用傳統(tǒng),就是學(xué)問與社會關(guān)系緊密結(jié)合,梁啟超在《清代學(xué)術(shù)概論》中談到“蓋在有益于社會,有用于國計(jì)民生”,旨在提倡學(xué)術(shù)要有用于社會民生,在某個(gè)地域人民的社會實(shí)踐中,民族傳統(tǒng)體育成為教化當(dāng)?shù)孛耧L(fēng)、牽系民族情感的重要方式,與當(dāng)?shù)厝嗣竦娘L(fēng)俗習(xí)慣、生活方式密切相關(guān)。民族傳統(tǒng)體育因其具有廣泛的社會群眾基礎(chǔ)而有了經(jīng)世致用的原則與學(xué)習(xí)目的,也因?yàn)檫@種致用機(jī)制維系大眾情感而有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chǔ),這是一種良性的雙向互動,從而使民族傳統(tǒng)體育在幾千年的發(fā)展中展現(xiàn)出強(qiáng)大的生命力。
從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起源來看,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產(chǎn)生于其實(shí)用價(jià)值。其與勞動生產(chǎn)密不可分,如射箭發(fā)明于原始狩獵,“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后從撥殺,取以為弓,因名烏號耳。”(《四部備要》)原始戰(zhàn)爭促進(jìn)了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萌生,蹴鞠最早便是為了訓(xùn)練軍士,以提高軍隊(duì)?wèi)?zhàn)斗力創(chuàng)造出來的,“蹴鞠,黃帝所造,在練武士,本兵勢見。”(《四部備要》)與生產(chǎn)、抗災(zāi)等有關(guān)的活動,如由古代鮮卑等族射天儀發(fā)展而來的較射、瑤族的播公鼓舞、侗族的哆毽、高山族的竿球、黎族的跳竹竿等。原始部族通過這些儀式化的肢體運(yùn)動來實(shí)現(xiàn)自身與主宰自然的某種神秘力量之間的交流、互滲,從而獲得某種力量、結(jié)果或?qū)崿F(xiàn)某種角色認(rèn)同,這便是民族傳統(tǒng)體育最初的實(shí)用價(jià)值。
從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形式來看,民族傳統(tǒng)體育是一種身體活動行為,在動作技能的形成方面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教育的大眾化、社會化通過所在社區(qū)的各種民俗活動實(shí)現(xiàn),這就使得知識與技能相結(jié)合,我們往往能從一個(gè)地域民族的傳統(tǒng)體育活動中看到它的生活概貌、文化特征、民族性格等,這就是篤行與治學(xué)、踐履與修身相結(jié)合。朱熹說“學(xué)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shí)”[11]。民族傳統(tǒng)體育是技藝之學(xué),是一種強(qiáng)身健體、修身養(yǎng)性的行為方式,在肢體動作中展現(xiàn)出其特有的文化內(nèi)涵。
從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意義來看,人們有意無意創(chuàng)編的體育活動隨著歷史的發(fā)展進(jìn)入階級社會,逐漸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guān)系,帶上社會心理,越來越成為促進(jìn)民族認(rèn)同、增強(qiáng)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在儒家學(xué)統(tǒng)的影響下,古人不僅關(guān)注道德自律的內(nèi)在超越,而且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責(zé)任及使命感,這也是孔子所說的“內(nèi)修身克已,外齊家治國平天下”,把道德修養(yǎng)之事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司馬談?wù)f:“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wù)為治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將修身的成果貫徹到外在的治平實(shí)踐之中,這也是中國古代文臣武將的最高理想,文治與武功皆是治國安天下的必要手段,甲骨文中“武”的本意是一個(gè)人拿著兵器進(jìn)攻,通過軍事訓(xùn)練防身御敵,以此獲得“下武精技防侵害、中武入窗采硇摹⑸銜淶玫榔教煜隆鋇墓δ埽所以尚武精神與國家強(qiáng)盛關(guān)系密切。
2 嬗變: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xué)統(tǒng)的斷裂
19世紀(jì)中葉,西方的堅(jiān)船利炮使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文化也隨之滲透不止,而中國由于政治經(jīng)濟(jì)上的客觀狀況又必須要向西方學(xué)習(xí),一時(shí)“西學(xué)東漸”成為一種時(shí)代潮流,中國文化被迫走上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中國幾千年的統(tǒng)緒也就此打斷,傳統(tǒng)的學(xué)統(tǒng)無法擺脫對西方學(xué)術(shù)的依傍而自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治學(xué)的傳統(tǒng)被打破,民族傳統(tǒng)體育幾千年來的一些傳統(tǒng)特征也發(fā)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外源式的近代化進(jìn)程無疑是二元性的,即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轉(zhuǎn)型又要延續(xù)傳統(tǒng)的生命價(jià)值,又要在短期內(nèi)承受西方體育學(xué)術(shù)系統(tǒng)的影響。20世紀(jì)初,以““為背景的“土洋體育”之爭愈演愈烈,現(xiàn)代體育就是在這種從“抗?fàn)帯钡健叭诤稀钡那闆r下轉(zhuǎn)型。傳統(tǒng)體育中的學(xué)統(tǒng)裂變,西方的藝術(shù)體操與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技擊內(nèi)容相結(jié)合,其學(xué)習(xí)方式、教學(xué)方法以及競技思想也紛紛灌注于民族傳統(tǒng)體育之中。
2.1 傳統(tǒng)體育表現(xiàn)方式的轉(zhuǎn)變:性命之學(xué)走向外化之學(xué)
西方學(xué)術(shù)是建立在名詞、術(shù)語、邏輯、概念之上的文化系統(tǒng),受古希臘先哲和啟蒙運(yùn)動理性主義思想影響,做學(xué)問注重邏輯思辨,正如哈貝馬斯所言:“18世紀(jì)為啟蒙哲學(xué)家所系統(tǒng)闡述過的現(xiàn)代性設(shè)計(jì)含有他們按內(nèi)在的邏輯發(fā)展客觀科學(xué)、普遍化的道德與法律以及自律的藝術(shù)的努力。同時(shí),這項(xiàng)設(shè)計(jì)亦有意將上述每一領(lǐng)域的認(rèn)知潛力從其外在形式中釋放出來。[12]”由此,在理論研究方面,武術(shù)是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核心學(xué)科,在此領(lǐng)域過于側(cè)重競技、術(shù)法等方面研究,并且研究方法較為單一,由于西方現(xiàn)代體育思想的制約,大部分武術(shù)學(xué)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與現(xiàn)代奧林匹克運(yùn)動相關(guān)的技術(shù)、規(guī)則、競賽等技術(shù)方面的實(shí)用研究,忽視了對武術(shù)內(nèi)在理論價(jià)值的研究,忽視了武術(shù)蘊(yùn)含的極大的文化資源[13]。
在動作形態(tài)方面,民族傳統(tǒng)體育開始注重套路的嚴(yán)整性與技術(shù)的規(guī)范性,對動作技術(shù)的理解必須有高度的客觀性,同時(shí)追求高難新美的外在形態(tài),著力提升動作的難度與美觀等表演特色。舞獅原是在民間節(jié)慶時(shí)期開展的一種娛樂性體育活動,近年來隨著國家對許多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發(fā)掘和弘揚(yáng),舞龍舞獅項(xiàng)目也被總結(jié)和整理出來,賦予其規(guī)定的套路和難度,登上競技場,走向競技化,比賽的分值多偏向于技巧和難度動作,一味追求動作的高、難、險(xiǎn)而忽視了獅子應(yīng)有的獅型獅態(tài)。例如在以往的北獅項(xiàng)目上教條于比賽的人數(shù)和道具、音樂和套路等形式,這種帶有西方學(xué)術(shù)特點(diǎn)的概念化、知識化的學(xué)習(xí)是生命之外的傳承,與內(nèi)在的骨血生命很難融為一體,因而也就缺乏了真正的傳統(tǒng)韻味和藝術(shù)感染力,這是與中國傳統(tǒng)“性命之學(xué)”相對的“外化之學(xué)”。
2.2 傳統(tǒng)體育傳承方式的轉(zhuǎn)變:徹底的理性主義
西方學(xué)術(shù)以學(xué)制教育為載體,科目明確,條分縷析,正如錢穆所說“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他們崇尚“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信條,“把論證進(jìn)行到底”的思辨精神和徹底的理性主義。受西方分科教育的影響,將體育學(xué)列為一個(gè)單獨(dú)的學(xué)科,民族傳統(tǒng)體育學(xué)成為其下設(shè)的二級學(xué)科,傳統(tǒng)的師徒關(guān)系也轉(zhuǎn)為教練員與運(yùn)動員或者老師與學(xué)生的關(guān)系。
學(xué)術(shù)及其傳統(tǒng)的傳承是學(xué)統(tǒng)的重要方面,師承是古代文化延續(xù)的主要方式,在封建社會中,“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原則讓師父對弟子有著絕對的權(quán)威,拜師學(xué)藝的艱辛更是讓師道尊嚴(yán)不容侵犯,師父的言行對弟子有極大的影響,弟子也十分尊崇師父所傳授的“道”。而受到西方學(xué)制教育以及現(xiàn)代教育普及化、大眾化的影響,一門技藝的傳承不再因封閉而充滿神秘感,新建立的師生關(guān)系是民主平等的講究合作的人際關(guān)系,師生之間的內(nèi)在傳遞性消失,缺少了心傳心悟的呼應(yīng)與關(guān)聯(lián),不再傳承生命而是傳承知識,不再以心傳心而是傳承書本,教學(xué)上追求名詞、概念的傳遞,缺失了對傳統(tǒng)體育中神意氣韻的闡述,學(xué)生需要用邏輯去理解而不再用“道”的思維體悟。
2.3 傳統(tǒng)體育社會價(jià)值的轉(zhuǎn)變:民族認(rèn)同感缺失
在方法論上,西方的知識分子傾向于所謂的“價(jià)值中立”(valuefree)原則,也就是主張客觀知識與主觀價(jià)值的相對分立,面對自然、社會和人生保持“無動于衷”的價(jià)值判斷[14]。一些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項(xiàng)目的技術(shù)與內(nèi)涵逐漸分離,與人們的生活越來越遠(yuǎn),成為賽場所特有的競技項(xiàng)目或只有少數(shù)人參與的舞臺表演。
傳統(tǒng)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通過技藝切磋來健身強(qiáng)體,繼承弘揚(yáng)中華民族精神。中國龍舟運(yùn)動源于對原始圖騰龍文化的崇拜、先民的生產(chǎn)及軍事活動等,后來被賦予紀(jì)念屈原投江的含義,龍舟競渡始終具有對宗教情緒的虔誠、對祖先英烈的崇拜,人們通過這項(xiàng)團(tuán)體活動來抒發(fā)感情,它凝結(jié)了氏族部落群團(tuán)原始文化心態(tài)有的觀念意識與情感意志[15]。民族傳統(tǒng)體育注重情感的抒發(fā),以此來維系民族認(rèn)同感,增強(qiáng)民族凝聚力,它們源于社會、發(fā)展于人民群體中,因而總會表現(xiàn)出一定的社會意義。而西式思維打破了中國傳統(tǒng)修齊治平的學(xué)統(tǒng),民族傳統(tǒng)體育也不需要再有以武安天下的治世之用,其社會參與度逐漸降低,維系情感的功能減弱。以龍舟競渡為例,隨著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科技的發(fā)展,對宗教、祖先的崇拜情w逐漸低沉,其中很多傳統(tǒng)習(xí)俗也隨之減少或趨于商業(yè)化,因而民族認(rèn)同感較以往而言有所缺失。
3 賡續(xù):當(dāng)代人文教育與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傳統(tǒng)再生
民族傳統(tǒng)體育作為一門學(xué)科有其獨(dú)特的話語基礎(chǔ),用西方式知識眼光解讀傳統(tǒng)學(xué)問就失去了傳統(tǒng)體育安身立命的終極歸宿。在新的歷史發(fā)展條件下,民族傳統(tǒng)體育雖然由于各種歷史與社會原因發(fā)生嬗變,然而其深深植根于中華文化的土壤之中,一些根本原則不能廢棄,否則將不符合民族傳統(tǒng)體育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正如周積明所說,特定的價(jià)值傾向乃是從文化模式形成的進(jìn)程中積淀而生,是經(jīng)過人們尤其是文化精英反復(fù)感知和思考并用文化制度固定下來的集體意識,只要產(chǎn)生特定價(jià)值傾向性的文化土壤未發(fā)生根本性變化,特定的價(jià)值觀念也就必然具有強(qiáng)大的穩(wěn)定性、延續(xù)性與普遍性,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下衍生出不同形態(tài)而已[16]。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嬗變并不是危機(jī),這個(gè)階段正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文明交融的磨合期,代表著民族傳統(tǒng)體育在曲折中前進(jìn)的發(fā)展方向,當(dāng)代傳統(tǒng)文化復(fù)興的潮流也為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傳統(tǒng)再生帶來了新的契機(jī)。賡續(x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中的學(xué)統(tǒng),結(jié)合現(xiàn)代社會的客觀情況,就是重建民族傳統(tǒng)體育尊道求道、內(nèi)外兼修、求真務(wù)實(shí)的傳統(tǒng)特色。
3.1 “尊道求道”:回歸傳統(tǒng)體育的本體精神
中國的“士人”沒有西方的來安頓生命,而是在所謂的“道”的光輝之下安身立命,“道”與現(xiàn)實(shí)生活處在一種微妙的平衡狀態(tài)。堅(jiān)持道義、堅(jiān)持真理是中華文化的特征,而儒家傳統(tǒng)中的“道”與“學(xué)”本來就不能截然兩分,學(xué)統(tǒng)“是儒學(xué)在現(xiàn)時(shí)代得以存活與發(fā)展的基礎(chǔ)”[17],學(xué)統(tǒng)的主要任務(wù)就是解釋“道”,使“道”通過治學(xué)體現(xiàn)出來。隨著現(xiàn)代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競技性越來越突出,其內(nèi)意與外形逐漸分離,“道欲明者,當(dāng)先明學(xué)”,所以,重建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尊道求道的傳統(tǒng)是賡續(xù)學(xué)統(tǒng)的首要內(nèi)容,將技術(shù)文本轉(zhuǎn)化成文化文本,突破名詞概念的表象,尋找體育活動背后最鮮活的內(nèi)涵。對道的追求體現(xiàn)了一個(gè)人的價(jià)值觀,這是一個(gè)人生存處事的核心原則,是其內(nèi)心深處終其一生恪守的東西,這就是“道”作為中華文化代表的根本之處,也是民族傳統(tǒng)體育人文教育中的必要之處。
在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傳承上,尊道求道的傳統(tǒng)要求尊師重教,師者傳道授業(yè)解惑,是“道”的直接傳承者,而學(xué)生需要通過師承和心悟來體道,而不是拘泥于書本和固有技術(shù)套路。而古今兩種傳承方式各有長短,要有選擇地繼承傳統(tǒng),古為今用,同時(shí)也要看到西方民主教育的優(yōu)長,在兩種方式之間取得一個(gè)“中庸”的狀態(tài)。
在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形式上,不能盲目地追求難度、美觀的動作,而忽略了對內(nèi)在神韻的領(lǐng)悟與外在感情的抒發(fā),每一處細(xì)節(jié)都應(yīng)體現(xiàn)出它的傳統(tǒng)意義與社會價(jià)值,還原該運(yùn)動的本質(zhì)形態(tài)。民族傳統(tǒng)體育代表了人類的智慧與文明,傳統(tǒng)體育的魅力不在于“高難美新”的人為設(shè)計(jì),而在于簡單質(zhì)樸的動作中蘊(yùn)含的道理,大道至簡,無為無待,這是一種品心靜氣超凡脫俗的道德觀念,一種內(nèi)化的宗教關(guān)懷和人文精神。傳統(tǒng)體育秉承著中國學(xué)統(tǒng)的“內(nèi)明之智”,以肢體活體傳承著人類文明的靈魂,這也是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本體精神。
3.2 “內(nèi)外兼修”:繼承傳統(tǒng)體育踐行者的本質(zhì)素養(yǎng)
“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 述而》)是先秦儒家所倡導(dǎo)的進(jìn)德修業(yè)之法,其中的“藝”指陶冶性情是文藝活動,也指鍛煉身體的體育運(yùn)動,如御、射等等,然而身心皆娛的同時(shí)都不得游離于“道”“德”“仁”的大原則。武術(shù)精神是代表著中國人文精神,而武德武禮是武術(shù)精神的核心,也是一個(gè)武者素質(zhì)的集中體現(xiàn),拳諺有云“拳以德立,無德無拳,心正則拳正,心邪則拳邪”“拳品如人品”[18],武德教育是從古到今武者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學(xué)統(tǒng)文化在武術(shù)領(lǐng)域的重點(diǎn)要求。身修而根本立,大學(xué)強(qiáng)調(diào)“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學(xué)習(xí)如知識、器物、技術(shù)等形而下的領(lǐng)域,完成形而上的人格的塑造,把武德修養(yǎng)內(nèi)化為自己的自覺行為和價(jià)值認(rèn)同,從而實(shí)現(xiàn)自我完善,達(dá)到德才兼?zhèn)涞木辰纾瑢χR有清醒的認(rèn)識并且能夠去踐行,這就是習(xí)學(xué)成德。新時(shí)代的武德教育應(yīng)該結(jié)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并且貫徹到武術(shù)技術(shù)教學(xué)過程中,以培養(yǎng)社會需要的武術(shù)之才。
除了對武德武禮的重視,內(nèi)外兼修還包括民族傳統(tǒng)體育情感、氣韻的抒發(fā),比如太極拳富有極強(qiáng)的表意性和隱喻性,以神意為先帶動肢體行為,把自然現(xiàn)象、生活哲理灌注到拳勢中去,太極拳文化符號注重內(nèi)外的聯(lián)系,即思與身的協(xié)同,是融思想與身體為一體的整體行為[19],如果只學(xué)習(xí)其肢體動作將其體操化將失去太極拳的精髓。對民族體育傳統(tǒng)的復(fù)興即是回歸項(xiàng)目的本質(zhì),對身體活動內(nèi)在神意繼承發(fā)展,如北獅競賽從2015年起加入傳統(tǒng)項(xiàng)目,在保持公平與規(guī)范的同時(shí)突出“傳統(tǒng)”,從競技性過渡到藝術(shù)性,把人民群眾所熟知的傳統(tǒng)故事、民俗特色等編入其中,更加注重獅子的神韻形態(tài),使得北獅運(yùn)動大眾化、通俗化,主題鮮明新穎,不再拘泥于形式,不再僅僅是刻意的競技而是回歸舞獅的本質(zhì)內(nèi)涵,這也是傳統(tǒng)北獅發(fā)展的正確趨勢。
3.3 “求真務(wù)實(shí)”:重塑民族體育的民本價(jià)值
近代以來,在西方文化強(qiáng)勢入侵的背景下,中國的經(jīng)濟(jì)政治結(jié)構(gòu)、傳統(tǒng)思想文化改變,冷兵器時(shí)代湮沒在一次次工業(yè)革命的浪潮中,新技術(shù)不斷應(yīng)用,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實(shí)用價(jià)值面臨新的挑戰(zhàn)。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體育活動”是以軍事武藝為主干,以保健養(yǎng)生為經(jīng)絡(luò),進(jìn)而形成各地村落中漢族民間鄉(xiāng)土游戲與類似的“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兩大特色[20]。可見,傳統(tǒng)體育具有實(shí)用至上的觀念。發(fā)展到今天,武術(shù)、摔跤等活動由軍事技擊轉(zhuǎn)化為健身之技,古代的民俗藝術(shù)、宗教祭祀等活動多以娛樂、表演的形式展現(xiàn)出來,因而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實(shí)用價(jià)值已經(jīng)演變?yōu)閵蕵贰⒔∩怼⒔?jīng)濟(jì)、競技、表演等等。
然而,當(dāng)今操化的、用于比賽和表演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是遠(yuǎn)離人民群眾的,這種精英型的文化形態(tài)無異于孤芳自賞。發(fā)展競技體育的價(jià)值與意義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檢驗(yàn)一種活動發(fā)展優(yōu)劣的最主要標(biāo)準(zhǔn),是自愿自發(fā)參與其中的人口數(shù)量。民族傳統(tǒng)體育以其信仰向心力、情感傾訴性與經(jīng)世致用的普世價(jià)值成為雅俗共賞、老少皆宜的大眾化運(yùn)動項(xiàng)目,我們必須把傳統(tǒng)體育這種代代傳承的文化魅力繼承下來,扭轉(zhuǎn)傳統(tǒng)體育發(fā)展的形式化趨向,并與現(xiàn)代奧林匹克運(yùn)動的潮流結(jié)合,為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項(xiàng)目重新植入古老而又嶄新的文化內(nèi)涵。把人民群眾的文化財(cái)富還原到大眾生活中去,讓民族傳統(tǒng)體育成為一種實(shí)用性文化,逐步滲透到人民文化生活、社會生活、經(jīng)濟(jì)生活的各個(gè)領(lǐng)域,利用其實(shí)用價(jià)值使民族傳統(tǒng)體育更好地為大眾服務(wù),保持其具有的雅俗共p、老少皆宜、功能多樣、自娛自樂等文化特質(zhì),以功能復(fù)合與精神愉悅的結(jié)合來提升群眾參與度。
除了實(shí)用價(jià)值外,民族傳統(tǒng)體育得以安身立命的終極歸宿在于其精神價(jià)值。社會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傳統(tǒng)學(xué)統(tǒng)意識的弱化是毋庸置疑的,但那種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普世價(jià)值觀至今仍積淀于民族傳統(tǒng)體育人的心中,運(yùn)動員以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情感堅(jiān)守著這份精英型的文化形態(tài),秉承著為國爭光的態(tài)度走向競技場,傳承著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這不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訴求,也不是滿足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的功利性的需要,而是永恒的價(jià)值理想,民族傳統(tǒng)體育也應(yīng)在此基礎(chǔ)上繼承修齊治平、經(jīng)世致用的傳統(tǒng),由超越走向永恒,藉升華成為不朽。
4 結(jié)語
魯迅在《華蓋集》中寫到:“歷史上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yùn)。”“古為今用”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體育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古代學(xué)統(tǒng)下學(xué)上達(dá)、學(xué)思并行、經(jīng)世致用的特點(diǎn)使得民族傳統(tǒng)體育表現(xiàn)出重禮崇德、形神兼?zhèn)洹⒕S系情感的傳統(tǒng)特征,在文化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面對西方競技體育的壓力,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一些傳統(tǒng)與文化內(nèi)涵被逐漸邊緣化,民族傳統(tǒng)體育由傳統(tǒng)的“性命之學(xué)”走向“外化之學(xué)”,傳承方式具有了西方徹底理性主義的性質(zhì),社會價(jià)值轉(zhuǎn)變導(dǎo)致民族認(rèn)同感缺失。此時(shí),重視文化根源性、重視學(xué)統(tǒng)、重視傳承顯得尤為重要,傳承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以為時(shí)用對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繼承發(fā)展有重大意義。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價(jià)值理念與情感歸宿仍作用于中國人的內(nèi)心深處,即使在現(xiàn)代西方文化強(qiáng)勢入侵的狀況下也是如此,我們應(yīng)該深刻思考民族傳統(tǒng)體育在中國古代長期傳承經(jīng)久不衰的原因,賡續(xù)學(xué)統(tǒng),重建尊道求道的傳統(tǒng)以回歸傳統(tǒng)體育的本體精神,重建內(nèi)外兼修的傳統(tǒng)以繼承傳統(tǒng)體育踐行者的本質(zhì)素養(yǎng),重建求實(shí)務(wù)實(shí)的傳統(tǒng)以重塑民族體育的民本價(jià)值,發(fā)展多功能性的、形神兼?zhèn)涞摹⒀潘坠操p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追求歷史的延續(xù)性與非延續(xù)性的統(tǒng)一,以此守護(hù)中國傳統(tǒng)體育的根脈。
參考文獻(xiàn):
[1]方朝輝.學(xué)統(tǒng)的迷失與再造[N].中華讀書報(bào),2011-05-11(15).
[2]成中英.新論人文精神與科學(xué)理性:中西融合之道[J].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04(1):3-4.
[3]鄧曦澤.斷裂與傳承: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的學(xué)統(tǒng)問題――以馮友蘭、蒙培元、黃玉順為例[J].學(xué)術(shù)界,2009(6):214-225.
[4]希爾斯.論傳統(tǒng)[M].李家永,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6.
[5]毛禮銳.中國古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14.
[6]王培生.吳氏太極拳詮真[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3:15.
[7]錢穆.朱子新學(xué)案(上)[M].成都:巴蜀書社,1986:596.
[8]葉適.習(xí)學(xué)記言[M].北京:中華書局,2009:185-186.
[9]夏中義.九謁先哲書[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5.
[10]許紀(jì)霖,陳思和,蔡翔,等.人文精神尋思錄之三――道統(tǒng)學(xué)統(tǒng)與政統(tǒng)[J].讀書,1994(5):46-55.
[11]黎靖德.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86:86-89.
[12]王岳川.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與美學(xué)[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2:17.
[13]邱丕相,馬劍.武術(shù)學(xué)科的科學(xué)化歷程與面臨的挑戰(zhàn)[J].體育科學(xué),2004,24(4):62-64.
[14]劉悅笛.“政統(tǒng)”、“道統(tǒng)”與“學(xué)統(tǒng)”――中國社會轉(zhuǎn)型中“士人”向“知識分子”的身份轉(zhuǎn)變[J].中國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4):63-70.
[15]倪依克.當(dāng)代中華民族傳統(tǒng)體育發(fā)展的思考――論中國龍舟運(yùn)動的現(xiàn)代化[J].體育科學(xué),2004,24(4):73-76.
[16]周積明.乾嘉時(shí)期的學(xué)統(tǒng)重建[J].江漢論壇,2002(6):56-60.
[17]鄭家棟.斷裂中的傳統(tǒng):信念與理性之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1:194.
[18]張綽庵,韓紅雨.中華武術(shù)諺語文化特征管窺[J].上海體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8,32(6):67-69.
熱門標(biāo)簽
哲學(xué)論文 哲學(xué)理論論文 哲學(xué)科技論文 哲學(xué)思想論文 哲學(xué)研究論文 哲學(xué)畢業(yè)論文 哲學(xué)知識論文 哲學(xué)史論文 哲學(xué)觀論文 哲學(xué)小論文 心理培訓(xùn) 人文科學(xué)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