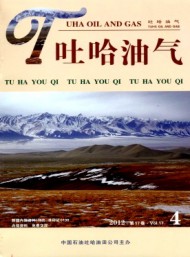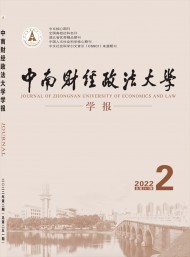簡述漢書的文學成就范文
時間:2023-10-26 17:55:30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簡述漢書的文學成就,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黃宗羲學術史研究的范式
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學術思想史專著,對二百余個明代學者的學術面貌按照年代順序與學派分屬進行了評述與介紹,其材料之廣富,內容之翔實,“可謂一代文章之淵藪”(《四庫全書在目提要》)。梁啟超曾指出:“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羲,所著《明儒學案》,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也”。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4頁。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黃宗羲是“中國學術史”的創始人。除《明儒學案》外,黃宗羲還始撰《宋元學案》,未成而卒,由其子黃百家和全祖望兩次補續而成。
從研究范式看,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首創了“學案體”的學術史研究范式, 應該說,這一觀點的提出者是原杭州大學的倉修良教授。參見:《國際黃宗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7-399頁。即按照學派特征,分析、概括一定時期學術發展歷史的寫作形式。在中國傳統學術史研究的發展進程中,雖然《禮記》中的《學記》、《儒行》、《檀弓》,《史記》中的《儒林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漢書》的《儒林傳》,《宋史》的《道學傳》,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周汝登的《圣學宗傳》、孫奇逢的《理學宗傳》等等,已經具有了中國學術史研究范式的雛形,但是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在收集資料的全面性、分類的系統性、編撰的獨特性等各個方面,均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即使比較晚出的唐鑒的《清學案小識》、尹會一的《北學編》,也不能與之相提并論。
具體而言,黃宗羲首創的學案體學術史研究范式的特征,主要體現于以下方面:
第一,資料豐富、全面。在中國學術史上,《明儒學案》以資料豐富、網羅詳備而著稱,其作為“一代文章之淵藪”的贊譽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于此。《明儒學案》成書于康熙十五年(1676),共分為六十二卷,記載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學術發展演變的概況。全書按照時代順序,將二百多名學者分作十九個學案組織起來,每個學案之前,均有一小序,簡述這個學派的源流和宗旨;隨后是學者的小傳,對各人的生平、學術源流、著作情況等作簡明扼要的述評;小傳之后,是學者本人的著作節錄或語錄,偶有作者的按語。全書上起明初方孝孺、曹端,下迄明亡劉宗周、孫奇逢,有明一學中人,大體網羅其中,實為一部明學史。由于陽明學為明代儒學中堅,故《明儒學案》述陽明學及其傳衍最詳。從卷十《姚江學案》起,至卷三十六《泰州學案》止,篇幅達二十六卷,入案學者計九十八人之多,亦足可謂是王學通史。
第二,分類系統、清晰。黃宗羲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基礎上,著重梳理各家學術的觀點,“為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明儒學案·自序》),這是《明儒學案》的重要創新。與同時代的周汝登《圣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相比較,黃宗羲《明儒學案》與這兩部學術著作的優劣十分明顯。周汝登的《圣學宗傳》的基調是弘揚禪學,見聞狹陋,“擾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孫奇逢《理學宗傳》的內容“雜收,不復甄別,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領”(《明儒學案·凡例》)。而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則“言行并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玄提要,一代學術源流,了如指掌。”(《莫晉序》)
《明儒學案》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對各個學者加以研究,然后分門別類地闡述各家學術觀點。黃宗羲在《自序》中表明自己研究學術史的觀念:“羲為《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后成家,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正是在深刻理解上下功夫,所以最終在系統性、條理性、明晰性方面,較之前的學術史著作更勝一籌,因而成為中國第一部最完整的學案體范式的學術史著作。
第三,體例獨特、新穎。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在體例上以“有所授受者分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學者,不甚著者,總列諸儒之案。”(《明儒學案·凡例》)這樣就形成一個個以學術創始人、繼承者為一體的完整、系統的學案。各學案又都冠以敘論,作簡括的介紹說明,隨后分列本案各學者,并依次敘述他們的傳略。在各個學者的敘傳中,除了介紹生平,還扼要介紹其主要學術觀點,并加以評析。隨后再接以案主言論的節錄和選輯,提供了解各家學術見解的具體資料。他選取的資料均取自原書,又經過精選,用黃宗羲自己的話說,就是“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明儒學案·凡例》)
黃宗羲《明儒學案》的體例結構,既汲取宋明以來《伊洛淵源錄》、《諸儒學案》、《圣學宗傳》、《理學宗傳》諸書所長,又自創新制,匠心獨運,使中國傳統學術史中“學案體”的研究范式臻于完善和定型。乾隆初,全祖望承黃宗羲、百家父子未竟之志,續成《宋元學案》一百卷;道光間,唐鑒著《國朝學案小識》;民國初徐世昌等編撰《清儒學案》二百零八卷,全氏學案以下的諸多“學案體”著作,卷帙雖多寡不一,但就體例格局而言,皆沒有逾越《明儒學案》的范圍。所以,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倘若沒有黃宗羲《明儒學案》的這一里程碑式的創制,在中國傳統學術史研究中,也就無從誕生“學案體”這一范式。
二、黃宗羲學術史研究的方法與學術使命
在哲學史的研究方法上,有兩種哲學史或學術史的寫作。一種是史學家的或偏重于歷史的哲學史,如梯利的《西方哲學史》;另外一種則是哲學家的或偏重于哲學的哲學史,如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等。以上兩種哲學史研究由于作者的出發點不同,又會產生不同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史學家的哲學史強調史料的真實、客觀,而哲學家的哲學史則往往注重獨立的見解和個性化的表達。但以上兩種哲學史的寫作,在黃宗羲身上得到可貴的統一,既是哲學家又是史學家的黃宗羲的學術史研究,具有在豐富、翔實的資料占有的基礎上貫穿自己獨立見解和深刻評價的特點。這些特點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首先,是客觀、公允的分析、評價。黃宗羲在編撰《明儒學案》時明確提出學術評價中何為“真”的原則,這就是:“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明儒學案·凡例》)“自用得著者”也即“自得”,自得就是功力深到、獨有見解,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產物。這就是說,學術評價當以“自用得著者”或“自得”為真,所謂“功力所至,竭其心力之萬殊者”,哪怕“一偏之見”、“相反之論”,也要加以重視;相反,若“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則無需認真對待。
縱觀《明儒學案》,黃宗羲基本貫徹了這一主張,因而也客觀、公允地反映了各家的學術觀點。正如莫晉在重刻《明儒學案》序中所論,黃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比如,在評價明初理學家吳與弼時,黃宗羲基本是以客觀、公允的態度闡述其學說宗旨,沒有因其遵循朱學路徑加以非議:“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為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后為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為轉手,終不敢離此矩鑊也。……椎輪為大輅之始,增冰為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后時之盛哉!”(《明儒學案·崇仁學案一》) 黃宗羲首先指出吳與弼對朱學的忠實繼承和遵循,在整體上突出了其關心踐履功夫及篤實的修心養性方面的學術特征,同時,客觀地指出了其對于明學的貢獻。這是黃宗羲的可貴之處。
黃宗羲的客觀、公允,還表現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學術態度。比如,黃宗羲在分析白沙學與陽明學的關系時,指出:“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陽明而后大。”又曰:“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明儒學案·白沙學案上》)從問題的一致性看,明代的心學思潮是由陳白沙開啟,由王陽明大成的,似乎非常清楚。但是,有一個問題黃宗羲想不清楚,即:“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不知陽明后來從不說起,其何故也。”(《明儒學案·白沙學案上》)對于王陽明不提起陳白沙,學者們雖然有一定的解釋,但總體上大家并不重視這一表面上看很偶然的現象,似乎認為這一問題并不值得深究,而黃宗羲顯然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由于自己沒有想清楚,所以在《明儒學案》中黃宗羲只是提出了問題而沒有冒然回答。這既顯示出他的敏銳性與洞察力,但同時又顯示出他的謹慎和小心,總體上這是一種客觀、公允的學術態度。
體現在《明儒學案》中的客觀、公允,還表現在對于學派劃分上面。比如,從師承和學派關系上講,陳白沙師從吳與弼,那么,陳白沙應歸于《崇仁學案》,但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的《崇仁學案》中,并沒有包括陳白沙,而是另起《白沙學案》,說明吳與弼與陳白沙其實學源不同。黃宗羲如此評價曰:“白沙出其門,然自敘所得,不關聘君,當為別派。”(《明儒學案·崇仁學案一》)依此亦可見其客觀、公允的態度。
其次,直指本質,關注理論實質。在關注“真”的同時,黃宗羲還貫穿自己的獨立見解,其《明儒學案》屬于哲學家的哲學史,因而具有自發的創造意識,而不是依傍某種“正確”、“權威”見解的歷史,這一點至今具有借鑒意義。
黃宗羲撰寫《明儒學案》,并不僅僅是為了闡述他人的學術觀點,而更為關注的是對哲學的基本問題進行的探討,如傳統哲學中關于理、氣、心的理論等。在《明儒學案》中,黃宗羲十分欣賞“盡橫渠之蘊”的明代哲學家羅欽順、王廷相等人的氣論,認為:“先生(羅欽順)之論理、氣,最為精確,……千條萬緒,紛紜膠葛,而率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以行也。”(《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中一》)又曰:“先生(王廷相)主張橫渠之論理氣,以為氣外無性,此定論也。”(《諸儒學案中四》)在這里,黃宗羲雖然主要是評價羅欽順、王廷相的氣論,但以評價為先導,借以詮釋自己的觀點,其實質是直指程朱理學“分理氣為二”的傾向,而提出“理氣為一”的觀點:“理即是氣之理,……理氣是一。”(《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中》)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到黃宗羲直指本質,關注理論實質的特點。
當然,黃宗羲所著《明儒學案》是以心學,尤其是以陽明心學為主線來代表明學的。《明儒學案》所收學者及他們的學術觀點和學術淵源,無論內容和分量,都以王陽明為中心,這顯示出黃宗羲的自己的學術立場。比如,對于王陽明與湛若水的“格物”之辯,黃宗羲主要是站在陽明學的立場上,對此做了總結:“先生(甘泉)與陽明分生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為之調人者,謂‘天理即良知也,體認即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為求之于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然天地萬物之理,實不外于腔子里,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為廣大,則先生仍是舊說所拘也。”(《明儒學案·甘泉學案一》)黃宗羲首先從王陽明、湛若水二人學說的分歧上,強調了“隨處體認天理”與“致良知”的不同,因而二者“終不可強之使合”。但是,在理論根基上,黃宗羲主要是以陽明學“天地萬物之理,實不外于腔子里”的觀點,批評湛若水“仍是舊說所拘”。從學術立場而言,黃宗羲維護陽明學、批評湛若水,主要原因還是與其關注“心學”的理論實質相關,即從“心之廣大”而言,并沒有門派的偏見。這一點,體現在黃宗羲描述當時王門的學生與湛門的學生相互出入方面:“當時學于湛者,或卒業于王,學于王者,或卒業于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明儒學案·甘泉學案一》)其并沒有顯示出談論門派高下的傾向。
應當指出,黃宗羲的學術史研究,除了具有哲學史與哲學研究相統一的研究方法之外,同時還表現出強烈的學術使命感。
一般而言,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學術使命有兩方面:一方面把以往的哲學成果作為建構自己哲學理論的出發點,即“接著講”;另一方面則真實地呈現以往哲學演變的歷史過程,即“如實講”。作為哲學家和學術史家的黃宗羲無疑同時具備以上兩個方面。從“接著講”方面看,黃宗羲在強烈的學術使命感的感召下,苦心孤詣地探求學術發展史,其實是從時代的學術發展脈搏中,尋找人類社會進一步完善的一般規律;而從“如實講”看,作為學術史家的黃宗羲,其學術史研究的目的是: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歷史文化的真實,期待啟蒙未來。
比如,黃宗羲編撰《明儒學案》,在資料的收集方面不遺余力。但他的根本目的并非出于“學案體”特征的網羅詳備,而是為了所肩負的學術使命。他曾指出《明儒學案》的缺憾:“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力聞見有限,尚容陸續訪求。即羲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采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明儒學案·發凡》)可見,在黃宗羲看來,學術史的編撰并非自己“一人之事”,而是事關天下,所以他號召“海內有斯文之責者”,要一起搜羅學術資料,共襄盛舉,這無疑表現出他強烈的學術使命感。這種學術使命感滲透在他的所有學術研究中,無論是探索理論實質、研究歷史事實、還是梳理學術史發展,無不體現出既是哲學家又是史學家的黃宗羲這一特點。
從總體上看,以上三個方面(“學案體”的研究范式、哲學史與哲學研究相統一的研究方法、“接著講”與“如實講”的學術使命感)在黃宗羲身上并不是沒有關聯的,而是形成一個整體,共同體現出黃宗羲學術史研究的特征。
三、黃宗羲學術史研究的意義
明清之際,黃宗羲編撰《明儒學案》的學術史成果對于中國哲學史研究具有歷史先導性的意義。其意義集中體現為:
1.突破霸權化的學術模式,形成對學術史本質的重新厘定。從歷史發展看,從南宋后期至明代,程朱理學占據了學術界乃至整個思想界的主位,成為霸權化學術的代表,學者們對程朱理學的崇拜幾乎到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地步。《明史·儒林傳序》指出:“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師承有自,矩鑊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這就是說,明初學術的基本路向表現為,僅僅是對程朱理學的講述和解釋,幾乎達到朱子學后再無學問、朱子學后再無真理的地步。三部《大全》即《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的纂修和頒布, 三部《大全》即《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書共260卷,成書于明永樂十三年(1415),由胡廣、楊榮等主編。編撰三部《大全》的目的和宗旨乃在于“興教化、正人心”,實現“家孔孟而戶程朱”的“思想大一統”。三部《大全》的編撰和頒布,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合眾途于一軌,會萬理于一原”的目的,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思想和文化的統一,而程朱理學亦由此確立了它在思想文化領域的“獨尊”地位,成為明代官方的正統思想,但《大全》的學術價值頗受非議,如顧炎武評論道:“《大全》出而經說亡”。( 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88頁。)朱子學被定于一尊,取得了其他學派無法抗衡的至高地位。
但是,唯權威是從顯然是學術的異化。其根本之處是喪失了學術的本質,追求現成說法,這是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的撰寫中主要針對的陋習:“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明儒學案·姚江學案》)黃宗羲認為,學術根源于心之本體,本體并非限于一種模式或途徑,所謂:“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所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靈根,化為焦芽絕巷。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明儒學案·自序》)黃宗羲在序文中批評了定程朱理學于一尊的政策,指出,學術“出于一途”,只能使盈天地之心的“美厥靈根”,化為焦芽;使“變化不測”的心之本體,變成絕巷。
正是在學術不能出于一途、定于一尊的指導思想下,黃宗羲《明儒學案》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學術觀念,形成“學不出于一途”、“論不主于一家”的學術史編撰,從而成為中國學術史的先導性著作,正如賈潤在《明儒學案》序中所言:“蓋明儒之學多門,有河東之派,有新會之派,有余姚之派,雖同師孔、孟,同談性命,而途轍不同,其末流益歧以異,自有是書(《明儒學案》),而支分派別,條理粲然。其于諸儒也,……論不主于一家,要使人人盡見其生平而后已。”學術總是哲學家的學術,從一定的哲學觀出發,哲學家們總是展開為個性化的研究(所謂“途轍不同”),那么,作為學術史研究就應該真實地匯集各家的成果,而不是學術“出于一途”。黃宗羲在《明儒學案·河東學案》記載,有人問呂柟:“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呂柟答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從《明儒學案》不難看到,明儒一家有一家之“宗旨”,不同講學者用各自所立的“宗旨”為標識,這些紛然各異的宗旨,實際上就是對于突破霸權化的學術模式、重建思想世界的不同取向。黃宗羲的這種對一家有一家之“宗旨”的認識,無疑形成了對學術史本質的重新厘定。
2.把握時代的脈搏,真實地呈現學術演變的歷史過程。從整體上看,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無疑主要是以王學為中心,除直接反映王學的《姚江學案》外,還有《浙中王門學案》、《江右王門學案》、《南中王門學案》、《王門學案楚中》、《北方王門學案》、《粵閩王門學案》,以及屬于王學稍有變化的《止修學案》、《泰州學案》等,占學案總數的一半以上。莫晉所說的“是非互見,得失兩存”,也是圍繞著“宗姚江與辟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晉又說:“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從《明儒學案》的布局,固然可以反映出黃宗羲本人的學術傾向,但也在客觀上把握了時代的脈搏,真實地呈現出明代學術演變的歷史過程。
從歷史發展看,明代近三百余年的學術,在王學興起之前,基本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也就是說,是一個朱學獨尊的格局。明弘治、正德間,王學崛起,學人翕然相從,而晚明的思想潮流,最為突出的是王陽明的心學大為流行:“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代表官方觀點的《明史·儒林傳序》中說,王守仁“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
然而入清之后,對陽明學“空談誤國”、“陽儒陰釋”的批評鋪天蓋地,如清初的儒學家王弘撰說:“大抵陽明之學,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格物》,《山志》卷五)呂留良則是近于謾罵:“王守仁,……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賊也。”(《答吳晴巖書》,《呂晚村文集》卷一)王夫之則云:“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圣之邪說,其究也為刑戮之民、為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序論》,《張子正蒙注》)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黃宗羲所選擇進行的明代學術史研究,其內在之義便是深入考察明代學術的發展,真實地呈現明代學術演變的歷史過程。當然,在這一過程中,王學淵源流變無疑是一個重點,不能不作為一個突出的內容加以對待。比如,對王學如何定位?其內在精神如何傳播、演變?回答以上問題實際上就是對明代學術演變過程的真實呈現。
對于王學的歷史功績,黃宗羲毫不諱言地予以肯定。他認為:“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圣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明儒學案·姚江學案》)應該說,黃宗羲的這一斷言并非完全出于其維護學派、光大師門影響的需要,而是在深入考察時代的發展、以及當時學術演變源流的基礎上所作出的客觀的結論。
那么,對于陽明后學的失誤,黃宗羲亦不袒護,所謂“宗姚江與辟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即圍繞著對王學宗旨的繼承和喪失,黃宗羲總體上否定失去了王學宗旨的學者和學派,如“越中”;而肯定繼承王學宗旨的學者和學派,如“江右”:“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郭、念菴、兩峰、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也。”《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一》
可見,判斷是否符合王學宗旨即成為關鍵。黃宗羲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辨析和分訣各家學說的宗旨。當然,以王學為宗旨分析各家學說,并非是要以“王學”去主導、規定各家,如此反而會形成一種新的“出于一途”的霸權學術模式,而這正是黃宗羲所要突破、擯棄的學術方法。因為王學本身的學術宗旨,是要求“人人反觀而自得”、“人人有個作圣之路”,所以,以王學為宗旨分析各家學說,反而是要求從各個學者自身出發,從其自得、“得力處”總結出其學說的宗旨,以此得到整體的學術面貌,所謂:“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茍非定以一兩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明儒學案·發凡》)可見,黃宗羲雖然圍繞“宗姚江與辟姚江者”,但其實是從各個學者自身出發,“分別宗旨,如燈取影”,充分地展示“其人一生之精神” (《明儒學案·發凡》)。
由此,黃宗羲之《明儒學案》才能夠真實地呈現學術演變的歷史過程,成為“一代文章之淵藪”,成為與時代變遷密不可分的學術史研究。其把握時展脈搏,客觀地呈現學術信史的研究特征,對于現代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發展、建構,無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三,《明儒學案》體現出學術史的獨立性,是現代意義上中國哲學史的先聲。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的編撰中,從根本上突破了傳統的學術觀,即不以君王將相為核心,不以政治題材為關鍵,而是真實、內在地考察明代學術的來龍去脈,這不僅是一個歷史觀的進步,而且還是中國傳統學術史上的一個突破。梁啟超對《明儒學案》的這一特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有之盛業也。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為學史之格,使后人能師其意,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史可作也,諸類此者,其數何限”。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學·中國之舊史》,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版。黃宗羲的學術史編撰,主要體現了學術史的獨立性,對中國哲學史的產生和學科的獨立性無疑具有積極影響。
從嚴格意義上看,中國傳統學術中并無哲學或哲學史學科,但正是由于黃宗羲《明儒學案》的歷史先導作用,不僅使中國哲學史,像中國政治史、中國種族史、中國財富史、中國宗教史一樣“可作”,成為獨立學科,而且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也為中國哲學史能夠保持自身的民族性,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