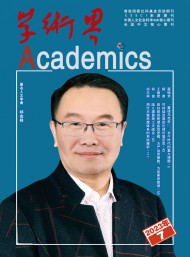論語的哲學思想范文
時間:2023-11-23 17:51:58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論語的哲學思想,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教育哲學;思想;《論語》
中圖分類號:G40-0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49X(2009)-12-0066-002
一、引言
《論語?述而》共包括38章,也是學者們在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時引述較多的篇章之一。前人多從語法或《論語》等先秦兩漢及以后的著作來判斷其涵義。但是,鑒于語言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著作年代影響語法的判斷。因此在本文采用結合語法判斷,主要依據《論語》本身中的互文關系的方式,對《論語?述而》中孔子關于教育對象的教育哲學思想進行研究。
二、孔子關于教育對象的論述
教育對象的問題,即什么人可以受教育和什么人應該受教育,是普通民眾和教育家們關注的問題。在當時的社會,孔子就主張擴大教育的對象。如在《論語?述而》第七中以下孔子對教育對象的選擇的看法的記述有以下兩條,將在下文分別論述:
1.子曰:“自行束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自行束以上”此句頗多爭議。大致有“年齡說”、“脯說”(肉干)和“修行說”三種解釋。持“年齡說”的如李澤厚先生。李澤厚先生認為:“束”一般都解作“十條肉脯”,本譯從漢代經師。而與孔子所講“十五而志于學”,書傳“十五入小學”相應。亦有以服飾、行為“束帶修飾”、“約束修飾”釋“束修”者。李澤厚先生將之譯為:“孔子說:凡十五歲以上,我沒有不收教的。” [1]。
持“脯說”(肉干)或類似的禮物說有楊伯峻先生等。楊伯峻先生在《論語譯注》中對“束”作了如下解釋:束--古代一種見面禮。“”是干肉,“束”即一束干肉,每束十條。楊伯峻先生將其釋義為“只要是主動地給我一點見面薄禮,我從沒有不教誨的。[2]”
另有一種解釋是“束”即“修行”,即吸收門徒以修行程度為依據。如高時良先生在其《中國古代教育理論體系》中提出:“如《鹽鐵論?貧富》:”余結發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3]但《鹽鐵論》成書日期為西漢,在孔子之后,故難以選擇此解釋。
根據互文關系的方法,結合《論語?鄉黨》來看孔子的飲食觀潔凈、新鮮、衛生,應該可排除“脯說”(肉干):“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殪而,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到孔子對食物潔凈的重視,其中蘊含了人生的智慧:病從口入,只有謹慎地選擇食物,才會避免因吃了不潔凈的食物而生病,不能保護好父母給的身體發膚,有損孝道;也不能盡忠竭力。具體到“沽酒市脯,不食”,即是說“從市上買來的肉干和酒,不吃”。更進一步地說明孔子的飲食觀。買來的肉干不食,是因為無法保證制作過程的潔凈,抑或是新鮮衛生。楊伯峻先生的解釋是:“參與國家祭祀典禮,不把祭肉留到第二天。別的祭肉留存不超過三天。若是存放過了三天,便不吃了。”古代大夫參加國君祭祀以后,可以得到國君賜的祭肉。但祭祀活動一般要持續二三天,所以這些肉就已經不新鮮,不能再過夜了。超過三天,就不能再過夜了。如果“束”做“肉干”解釋,拿孔子是否會拿學生送的肉干去交換或者贈人呢?從《論語?衛靈公》來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本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態度的孔子,應該不會把自己視作不衛生的“肉干”贈人。
另外,根據互文關系的方法,依據《論語?述而》中孔子寧取義而舍富貴的態度來判斷,也可排除“脯說”(肉干),如:“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同樣,在《論語?衛靈公》中記錄了孔子的主張:“子曰:有教無類。”(人人我都教育,沒有貧富、地域的區別 [4])加之,從孔子弟子的資料來看,有貧困如顏淵的學生,也可排除“脯說”(肉干)。如《論語?雍也》中記錄道: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
因此,根據互文關系的方法,看《論語》中的上下文中的相關主題的言論,無論是采用“年齡說”還是“修行說”,都可以看到在教育對象的選擇方面,孔子是持“有教無類”的態度。另外,從《論語?子罕》中可以看到孔子不厭其煩地盡力為“鄙夫”釋疑解難。如“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這一“有教無類”的關于教育對象的教育哲學思想,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不過時,對我們實現教育公平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2.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眾多學者對這一句話的義理的看法較為一致。如楊伯峻先生將其釋義為互鄉這地方的人難于交談,一個童子得到孔子的接見。弟子們疑惑。孔子道:“……別人把自己弄得干干凈凈而來,便應當贊成他的干凈,不要死記住他那過去。 [5]”徐前進先生認為《述而》“不保其往”的意思是:“不應該依據他往日(之表現)。”而應該依據他現在的(“潔己以進”)表現 [6]。
這句話也說明了孔子對受教育者的選擇是本著開放的、過往不究態度。根據互文關系的方法,可以在《論語?八佾》中看到孔子類似的言論:“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即是說已經做了的事不便再解釋了,已經完成的事不便再挽救了,已經過去的事不便再追究了 [7]。 高時良先生認為“不保其往”即對一個人的言行,應著重看他現在的表現。對教育改造人充滿信心。重視學生的學習自覺性和積極性,沒有理由挫傷學生的自尊心 [8]。這種理念不僅適用于今天的教育中的師生關系,也可以推廣到教育管理中的教職員工之間的關系中去。
另外,根據互文關系的方法,關于孔子對作為教育對象之一的少年或童子表示關懷、重視的言論可見《論語》中其他章節。如下列三例:(1)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論語?公冶長》)(2)子路曰:“愿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論語?公冶長》)(3)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論語?憲問》)
第一句中孔子說家鄉的學生志向高大,文采斐然,都不知道如何指導他們。第二句中說自己的志向是老者使他安逸,朋友使他信任我,年輕人使他懷念我 [9]。趙華倫先生認為“少者懷之”是“少年,要關心他們” [10]。第三句說闕黨的一個童子來向孔子傳達信息。孔子回答別人這個童子上進與否時說到,不是肯求上進的人,是一個急于求成的人 [11]。這些記載都說明了孔子的教育對象擴大到普通的民眾中去,乃至童子、小子,在那個時代具有積極的意義。
根據互文關系的方法,《論語》中孔子將教育對象擴大到士庶階層,以“民”為教育對象的教育哲學思想又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這句話斷句不同,意思不同。如:(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高時良先生贊許第一種斷句方法:如果不足以任使,便要教育他們 [12]。楊伯峻先生根據古人的慣用語法,提出如有第二種意思,則應為“民可,則使(之)由之;不可,則使(之)知之。”方不致晦澀而誤解。楊伯峻先生解釋道是“老百姓,可以使他們照著我們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們知道那是為什么 [13]。根據互文關系,在《論語?為政》中可以找到下例:“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德,民免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由此可以判斷,可以選擇高時良先生的解釋。
根據互文關系的方法,可以看到《論語》中孔子認為在教育過程中,教育對象的身份并非一成不變,在特定的情境下,可能會反過來對作為教育者的教師起著教育作用。如下例:《論語?陽貨第十七》: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開始說治理小地方的百姓,用不著教育。而子游申辯道教育總是有用的,此時,孔子承認了子游的觀點是正確的,自己不過是開玩笑的。孔子是否真的是開玩笑,已不可考。但孔子承認學生的正確觀點,也從一個側面驗證了“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
三、結語
根據互文關系的方法,可以看到《論語》中孔子關于教育對象的教育哲學思想在春秋末期的奴隸社會時代具有其積極意義,孔子促進了將“官學”下移到民間。這些對今天的教育,也具有啟示作用。然而,由于時代的限制,孔子關于教育對象的思想也并非完美無暇。根據互文關系的方法,可以看到《論語》中的以下例句: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這句話爭議頗多。這里選擇楊伯峻先生的解釋:“只有上等的智者與下等的愚人是不可改變的 [14]。”孔子由于時代、科技的限制,發出這樣的感慨。而如今的物質文明、科技發達,因此推行“全納教育”,擴大了教育對象,更大程度上實現了教育公平,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參考文獻:
[1]李澤厚.論語今讀[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2] [4] [5] [7] [9] [11] [13] [14]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3] [8] [12]高時良.中國古典教育理論體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篇2
一、對笛卡爾的總體性反思
勒內?笛卡爾,被譽為“近代哲學之父”,創立了“普遍數學”方法論 以分析和綜合的方法論原則為根據,并推導出超乎神創論的確定知識。在語言哲學的范疇中,笛卡爾將自身價值融入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笛卡爾對于基礎的人類知識的追問與鉆研迎合了整個西方哲學的研究主導方向,并對其做了合理的延伸。這種以人類為主題,通過揭示人和人的世界從而了解人性,探求人性,最終完善人性的理論主題,在某種程度上是超越了當代西方哲學家的語言現象的經驗分析。故,西方哲學家更是無法滿足于“瞎子摸象”的現狀。而另一方面,通過“我思故我在”及“我不懷疑我懷疑”這兩個話題,直擊人類世界,將人們的關注點聚焦于人的思想世界(精神世界)。[1]這一系列的哲學探求為歐洲大陸語言哲學的建立與發展建立及方法論創立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由于其語言的對象為語言,那么分析與解釋就是其必要的研究方法,而這種探索其目的就在于人。解釋和了解人與人的世界是諸多哲學家一生所追求的。
二、 探索笛卡爾哲學基礎
由于笛卡爾生于新舊知識新舊時代的交接時期,他接受的是舊時期的教育,提出的卻是引領時代的理論,他能直擊傳統經院哲學體系基礎的弱點,亦知道如何順應時代,證明新興科學的合理合法。笛卡爾的《方法談》和培根的《新工具》同樣是為理性時代而制定的,承認現代科學的全新的“游戲規則”。[2]
在一代哲學家笛卡爾的眼中,科學是靠綜合的方法考察得來的,在他認為,數學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物理學、醫學、力學、倫理學等其他的許多學科也都是服務于人的。這就好比哲學是一顆大樹的主干,而其他則是大樹的其他部分,我們想得到果實,光依靠樹干是行不通的。
笛卡爾引入普遍數學的概念,并將數學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如“度量”和“順序”應用到其他學科。他從哲學的角度看待并解釋這樣應用的合理性。這超越了舊時期孤立的哲學研究,將多種學科相互融合,從另一個側面來捕捉研究對象的同、異特點。這是哲學乃至科學的研究對象的概念的改革,這一點是史無前例的。
在完美的環境中,科學研究存在著這樣的順序,一個是由簡入繁的綜合性研究,另一個是由繁到簡的分析性研究。在數學中,以上的兩種方法是可逆的,但是哲學中不同,正如形而上學的因果關系研究,上帝創造的東西是有限的,而上帝卻是無限的,這樣,原因與結果并不同質。正因如此,哲學的范疇無法直接論述因果,而是從一個容易理解的點開始著手,構建有關原因,確定一個簡單明了的系統。由方法論看來,分析是形而上學的首要方法,通過分析尋找確定第一原則,然后利用科學的方法綜合理解,進而得出結論。
笛卡爾的方法論規則認為只要是沒有印證過的東西決不能當做真實的接受。簡單來說就是要避免先入為主的觀點影響,除了真實的放在面前的東西以外,不接受任何摻雜到里面的東西。化整為零,一一解決。按事情的次序進行思考,解決。理清事物的先后次序,逐次解決問題。全面考慮,避免遺漏。任何事情都要理清頭腦,全面考察,避免重復,確信做到毫無遺漏。有人曾分析以上幾點,確立了如下觀點:首先面對問題要先進行分析,找出真實可信的點。其次要說明分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應順應事物的發展方法,對問題進行分化,直到能解決的程度。再有就是綜合分析的過程,由簡單明了的道理一點點向前推進,最終收獲完全真理。最后說的是分析要徹底,不可半途而廢,執著追求才能達到真理。其實,笛卡爾對于思想的研究的切入并不是真正的證實,相反,是一種偽證,就是一種從反面考察人類思維方法的手段。其一是說笛卡爾的研究,其二就是其研究的落腳點――懷疑。
三、我不懷疑我懷疑
在笛卡爾的角度上,他懷疑一切的知識,并都將其放在不可靠的點上。想要重建知識,首先的切入點就是一個堅實可靠的結構基礎,一個哲學家,構建一個理論體系就像蓋樓一樣,堅實可靠的理論基礎是一切的前提,只有有了這個基礎,才能用自己的力量一磚一瓦的構建自己的價值體系。那么,為了打牢地基,修繕自己的基礎,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所有的“不可靠”,要注意的是不可靠和不真實還是有一定區別的,這里說的不可靠是因為有些東西并不能完全確定它是真實的,所以不能夠成為基礎。因為一旦基礎被毀,這個理論城池將不復存在,那么整個理論體系也將子虛烏有。所以,這里,我們用的是懷疑的方法,確保了理論體系基礎的堅實可靠。在笛卡爾的眼中,懷疑是具有普遍性的,這其中包括了一般人們認為的不可懷疑的確定性,這包括了周遭的世界,我們身邊常存的各種觀念。于是,笛卡爾會從另一個角度切入,用有條理的懷疑來驗證這些知識,從而建立自己的懷疑觀。
(一)懷疑哲學的過去
由于某種哲學提出的時間、背景不同,可能原則上的哲學家們說過的那些無可懷疑的事放在現今的情況下就有可能被懷疑了。既然過去的和現在的意見看法不同,那么在未來,這些看法和意見也會受到懷疑。這就說明我們完全可以懷疑現在的意見,也就是說任何哲學家的任何觀點都可以是懷疑的對象。
(二)懷疑周圍的世界
我們看到的、感受到的世界,都是我們感受到的意向。其實對于我們來說,造成欺騙的經歷不是周圍的世界,而是我們的感覺,我們應該去懷疑的是我們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周圍的世界。周圍的世界要首先成為知識。然后才能成為知識的基礎。只是,一旦世界成為了知識的基礎,那么它就不再是我們所認知的世界了,它,不過是一種形象。形象,不過是意向,是不同于原型的,而在這其中造成不同的就是人的感覺。這樣,感覺和感官依舊是懷疑和反思的對象。
(三)懷疑我們的感受
就像我們有時會陷入思維的圈子,如幻覺和錯覺。笛卡爾就以此為論證,提出我們的感受也是值得懷疑的觀念。就像海市蜃樓一樣,很多時候,騙你的就是你的感受。這也證明了,人的主觀意識有時是會出錯的。因此,我們的感覺依舊無法成為體系中的基礎,因為我們的感覺也是值得懷疑的。
(四)懷疑數學觀念
在笛卡爾的角度上來看,數學是簡單的,數學的觀念亦是明了的,看起來像1+1=2這樣的東西好像不會出錯,因為不管發生了什么樣的動蕩,1+1都不可能等于3這是死的,無法改變的。自然也是不值得懷疑的,然而,數學作為我們思想的對象而存在,那么我們思想的對象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每個人的心都不止一面,有可能一個本就不存在的東西卻被我們的內心封存,存在我們的心靈之中。但是這些都不是思維的產物,而是一個錯誤的根源,將自己放在了一個錯誤的點上。
(五)懷疑亞里士多德的中心邏輯論證
他的分析是關于這周遭的世界的,要證實一系列的論證,我們就要用可信的另一系列的論證去證實,此外,我們沒有其他的辦法。但是,我們要清楚,我們用來證明的論證也不一定是可信的。所以我們原則上依舊持懷疑態度。在方法論的高度上,我們可以將笛卡爾的普遍懷疑理論放在分析范疇,他的分析由繁入簡,由世界到個體,再到簡單的數學理念,最后才是論證方法。在他眼中,無論是哲學傳統,周圍世界,我們自己的感知力,還是數學觀念到邏輯論證都是可以被懷疑的,換個說法就是我們所能想到的一切都是可以被懷疑的。對于這個理論,笛卡爾也提出了實驗來論證。在試驗中,我們要探求的是我們是否存在懷疑的標準?分析一切可能的規則,他在最后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就是笛卡爾開始懷疑自己,從而找到他的第一原則,我不懷疑我懷疑。
四、我思故我在
根據笛卡爾的理念,懷疑的對象既可以是思想之外的也可以是思想之內的,甚至我們可以懷疑我們的思想,但是不能懷疑我們自身在懷疑。我們可以懷疑思想活動中的一切,但是不能去懷疑“我在懷疑”,否則,懷疑將無法進行。再者,懷疑活動一定要確立一個懷疑的主題,要知道作為懷疑的主題,“我”是存在的。
由此,“我思故我在”的理論被提出。有人將I think therefore I am中的I am譯為是,其實這種語言之間的轉換是很難通曉其中的真正韻味的。這也正是語言哲學研究的必要性所在。作為語言哲學的價值,我們可以將他看做是一種地方性的知識,他用地域性的民族編碼,要研究人及人類的世界,就要分析和解釋這種自然的編碼,因為這是最為直觀的表現方式。這個命題我們暫且分為“我思”與“我在”兩個部分。這其中,“我思”是指思想的東西,那么什么才是思想活動呢?用笛卡爾的話講,就是懷疑,在肯定與否定、愿意與不愿意之間感覺的東西。“我思”自然指我所思,就是我所想的一切,不管是理性還是感性,不管是聰明還是糊涂,不管是各種情緒,我思就是我思。更為要緊的是,“我思”作為一種純粹的活動,如果他有具體的內容和對象,那么他就是可以懷疑的了,或者更確切地說,“我思”不過是一種自我意識,既然已經表達出這樣的道理,那么這就是一個思考與反思考的活動。
笛卡爾認為,思想中的“自我”與“本我”都是獨立存在的個體,而“我思”與“我在”中的“我”也是同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故”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語言邏輯因果關系,而是闡述了“本我”與“自我”之間的必然聯系。“我思”說的是“本我”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進行思考,同時驗證了“我在”中“自我”的客觀存在性。我們思考問題時要從事物的本體出發,通過每一個個體的客觀獨立性與主觀能動性來思考研究,從中得出結論:“‘自我’是一個可以獨立思考的客觀存在的實體。”[3]
笛卡爾哲學思想的中心論點就是圍繞“我思故我在”進行的,其根本意義在于將“自我”這一概念歸結為一個可以獨立思考的客觀存在的個體,但是對于“自我”的獨立思考能力并沒有深入探究,下一步的研究就可以從這一方面出發,在確立了“我思故我在”這一命題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其他知識,我們必須明確的是,自我思考演繹出的本我存在這一客觀真理不僅存在于思辨范圍里,還適用在思辨范圍外。思辨與實質是兩種本質不同的研究對象,如果想將二者結合就需用到笛卡爾的“普遍數學”中的“度”。因為“普遍數學”中的“度”作為一個客觀標準在對比中才能體現其公正性。
笛卡爾在自己的研究體系中認為,“自我”這一概念由于其存在的客觀性本身就可以作為衡量研究對象的“度”,也就是說,“自我”本身就具備數學中“度”的客觀真理性。這也就證明了“只要是我們能深刻認識到的正確的觀點都是客觀存在的具有一定的真理性”這一觀點,而這一觀點的提出使笛卡爾在哲學上的研究由分析過渡到綜合,以“自我”作為“度”來衡量一切研究目標。按照這種觀念可以將以往很多混淆不清的觀念重新梳理,如數學中諸如1+1=2之類的問題,由于其淺顯明了不足以為真而缺乏依據,通過這種“度”就可以將這種簡單不足以為真的數學觀念定義為真實的。笛卡爾將哲學研究對象按觀念不同分為三類,即天賦,外來和虛構,虛構觀念就是由“本我”這一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根據其主觀能動性思考出的觀念,雖然“本我”是真實的,但“本我”思考的問題卻是不真實的,而天賦觀念和外來觀念卻是由外界事物產生的,一部分是真實的。
五、笛卡爾哲學思想的語言價值
笛卡爾作為唯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普遍懷疑出發,以“自我”與“本我”為核心構建的新的哲學思想,在方法論與意識形態上有著偉大的價值,語言研究大體崇尚思辨哲學的分析,而笛卡爾早在17世紀就將數學中的“度”這一概念引入到哲學研究中,使以往由于語言邏輯上的缺陷造成的混淆不清的概念有了新的度量。由此可見,實現科學研究的目標重點不在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而是在于方法論,“我懷疑我不懷疑”與“我思故我在”是將實踐方式與科學研究完美地運用到形而上學中,笛卡爾正是用這樣的方法找出一個清楚明白的道理作為認識論的出發點。
對于懷疑與懷疑對象,其實他們的本質都是同屬一個范疇的,就像希望,信任,是非,喜惡,等等,都是思想。或者更為確切地說是一種思想行為。并且我們要知道的是,思想的主題終歸是逃不開人的,思想行為的主題也必然是人。笛卡爾的思想就將人限制在了“我”之中,其哲學思想昭示了一個根本的道理,那就是一切可以用來認知的東西都是值得懷疑的,不能夠拿來作為認知的基礎,更不能成為第一原則。唯一的,不能夠被懷疑的就是“我在懷疑”,這個是不能改變的。也就是因為這一理論的提出,整個歐洲的哲學世界研究目標開始轉移,它開始注重人的思想行為,以及世界上的組織,而不再繼續周旋于漫無邊際的大千世界。
篇3
一語言為何能夠表達思想?弗雷格給出的解答是:“因為思想是由思想構筑材料構成的。這些思想構筑材料相應于構成表達思想的句子的語音組。因此,句子由句子部分構成,相應地,思想由思想的部分構成。人們可以稱思想部分為相應的句子部分的涵義,同樣,人們也可以將思想理解為句子的涵義。”[2]280在弗雷格看來,思想與句子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句子只是表達思想的一種方式,不同的句子可以表達相同的思想。思想與句子應該做出嚴格區別。“也許人們并不對語詞或符號表達式和被表達的思想進行嚴格區別。但是,為了清晰性,最好做出這種區別。”[2]180可以看出,弗雷格對語言為何能夠表達思想給出了一種結構性的解答,即思想語言具有相對應的結構。思想的部分與語言的部分又是如何相對應起來的,他沒有做出進一步的探究。維特根斯坦在TLP中提供的線索顯示與弗雷格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在他看來,語言是思想的可感表達方式(3.1),“在命題中,思想可以被如此表達而使命題指號的諸成分與思想的諸對象相對應。”(3.2)“以如此表達”是指命題指號的諸成分簡單指號或名字意謂對象,“簡單指號在命題中的配置,與對象在事況中的配置相對應”(3.21)。因為思想是事實的邏輯圖像,思想的諸對象對應于事實中的諸對象,所以命題的諸成分與思想的諸對象相對應。簡言之,命題與思想通過邏輯圖像論相互對應。但是繼之而起的問題是,命題—名字如何與世界—對象相互對應,思想—對象又如何與世界—對象相互對應?此外,由于維特根斯坦又講到“思想是有意義的命題”,那么,思想與語言是否可以如弗雷格所認為的那樣作出區分。
二在回答上述問題前,必須搞清楚思想的本質是什么?在維特根斯坦與羅素的通信中:羅素曾問:思想的構成成分是什么,并且與那些被摹繪的事實的關系是什么?維特根斯坦回復到:我不知道思想的構成元素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它必定含有與語言的詞語相對應的那種構成元素。另外,思想的構成元素與被摹繪的事實的那種關系是無關緊要的。那是心理學應該去尋求的東西。
關于羅素的問題,“思想是由詞語組成的嗎?”維特根斯坦回復到:不!而是像詞語一樣與實在具有同樣關系的精神元素(psychicalconstituents)。那些構成元素是什么,我不得而知[3]。據此,馬爾康姆認為,思想是由精神元素構成。
思想與語言是兩種不同的介質,但是可以表達相同的意義,也就是說,它們可以成為同樣的命題。因為思想與語言與實在具有相同的對應關系。思想可以用物質指號(physicalsigns)進行表達,但是無須非用物質指號表達。命題是對可能事態的摹繪,“我們利用可被感官感知的命題指號(語音的或文字的,等等)作為可能事況的投影。”因而事態是命題所具有的意義,而事態中的對象是命題指號或名字的意謂。在馬爾康姆看來,命題與事態之間的聯系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思想的意義被注入到了句子之中”[4]66,而這是由思維的精神活動(mentalactivi-ty)完成的。綜而論之,“思想比之詞語命題更為根本。”[4]66思想之所以能將世界—對象賦予命題—名字,是因為思想—元素與世界—對象之間的摹繪與被摹繪關系,后者是前者的意謂。那么思想又如何能夠摹繪世界呢?肯尼認為,思想的元素具有意義是由TLP中的“形而上學自我”(5.641)賦予的。肯尼說:在思想自身之中,也許,我們可以在具體的精神構造與那種構造的意義或意向之間作出區分。前者由心理學來研究,后者是由形而上學自我賦予的。思想……可能有恰當的數學復多性來描繪事實;但是它的復多性賦予它的只是描繪的可能性;事實上它描述的依賴于它的元素的意謂,二者是由超心理的意志賦予的,這種超心理的意志賦予這些元素一種用法,一種使用[4]78。
馬爾康姆對此持反對意見,在他看來沒有任何東西能將意謂賦予思想元素。它意謂一個特定的對象,是由它的內在本性決定的。思想是對與自身不同的某物的思考,它的意義是在其成為一個思想時已經具備,不可能先有思想后有一種意義,因此,思想—對象與世界—對象的聯系是由思想的本性所決定的,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給予幫助。
馬爾康姆的上述詮釋,并不能在TLP中找到充分的證據。他依賴上文所引的維特根斯坦回復給羅素的信箋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是對前期思想,特別是TLP的批判這種詮釋為其論證的主要文本依據和指路明燈。針對這兩點,溫奇一一作了批駁。上文所引材料所現,思想由對應于詞語的精神元素構成。溫奇認為,這封信“僅限于此,無法進一步得出,為了能夠把一串可感指號轉化為命題,諸如此般精神事態必不可缺。”[5]13其次,維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是不是對TLP中的思想的批判,這一點也很值得質疑。他確實在《哲學研究》的序言中說過:只有把他的新舊思想一起發表,新的思想“以舊的思想方式為背景,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6]。除此之外,還抨擊了這種說出一個句子的物理活動伴之以一種賦予它意義的內在活動的觀點,“思想并不是一種賦予言說以生命和意思的非實體的過程……”[7]。然而,這不意味著被批判的思想蘊含在TLP中。溫奇明確指出,與其說《哲學研究》所批判的關于意義、理解和思維的概念是針對于TLP,還不如說是針對于1914—1916年筆記。因為在他看來,筆記中有許多思想傾向如命題意義的精神性詮釋是維特根斯坦在經過深思熟慮后所拋棄并且在TLP中竭力批判的對象。
溫奇提出了一條不同的詮釋路徑。在他看來,命題中名字的意謂不是由思維賦予的,它之所以具有意義取決于它在句子中的“有意義的使用”。TLP中的命題3.326“為了就指號認出符號,我們必須觀察其有意義的使用”可以為此提供依據。除此之外,命題與思想的關系也不是截然分離的。維特根斯坦在序言3、4段中指出:因此本書是要為思維(Denken)劃一條界限,或者說得更確切些,不是為思維而是為思維(derGedanken)的表達式劃一條界限。因為要為思維劃一條界限,我們就必須能思及這個界限的兩邊(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能思不可思著)。
因此只能在語言中劃界限,而在界限那一邊的東西則根本是無意義的。
溫奇認為,為思想的表達式劃界不是指“我們必須使用語言來陳述界限的所在,而是界限自身在某種意義上必須被看做為語言的界限”[5]7,也就是說,思想的問題要通過語言的邏輯澄清來解決。在此,思維與語言是同一的。“說p是思考p可能采用的一種形式。所以:如果我斷定命題p,我也會有思想p,這兒的意思不是,除了斷定命題p外,我還在做其它某種事情,思考p,而是斷定命題p是思考p的(一種形式)。”[5]15然而,溫奇認為,思想除用這種可被感官感知的表達方式表達外,還可以以精神的元素來表達。這種由精神元素所構成的思想也是可能事態的投影,它與由物質元素構成的語言命題一樣可以表達同樣的意義,二者在邏輯上無先后之別。與之相反,馬爾康姆的觀點是,由精神元素構成的思想在邏輯上要優先于由物質指號構成的命題,命題只是思想表達的一種可感方式。然而,溫奇的詮釋同樣也面臨著思想的精神元素是如何與世界的對象相互聯系起來的的問題。
三馬爾康姆與溫奇的詮釋代表了對TLP思想、語言與世界三者之間關系思考的兩種路徑。二者都堅守自己的陣地,互不相讓,但又不能說服彼此。以筆者之見,二者的詮釋都有偏頗,都沒能真正將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完全地明示于眾。馬爾康姆的詮釋在TLP中能找到明顯的反駁例證。根據馬爾康姆的觀點,命題的意義來自思想的精神活動,那么,思想怎樣將意義賦予精神活動呢,這勢必要牽連出一個能操縱精神活動的主體。然而維特根斯坦明確表明“不存在能思維,能表象的主體”(5.631)。另外,思想的構成元素與被摹繪的事實之間的聯系,在維特根斯坦看來,是無關緊要的,屬于心理學研究的問題。以此看之,馬爾康姆將思想元素與被摹繪的事實之間的關系當作思想的本性使然,是一種心理學研究還是一種哲學的闡發?如果是一種哲學研究,那么必有違于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如果是對維特根斯坦思想的正確闡發,那么它必是一種心理學研究。
如果仔細察看TLP,我們可以發現,維特根斯坦多次闡釋了思想與語言的關系。命題4.112“……哲學應當把不加以澄清似乎就暗昧而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且給它們劃出明確的界限。”4.1121“我對指號語言的研究與哲學家們認為對邏輯哲學如此重要的那些思想過程的研究不是一致的嗎?”5.61“我們不能思我們不能思的東西;因此我們也不能說我們不能思的東西。”等等從中可以得出,維特根斯坦堅守的一個信條是:我們可以思的東西,就可以用語言來表達,或者說“思想是有意義的命題”(3.5)。我們可以在《哲學評論》中找到印證之處:……我認為,當他思維的時候,他也就創造了圖像,而這些圖像在一定意義上是任意的,因為其他的圖像也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另一方面,語言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也就是說,必須有一個始作俑者,他第一次用說出來的句子表達了一定的思想。
此外,整個過程都是無所謂的,因為每一個學習語言的孩子,都是通過開始用這種語言去思維來學的,是突然開始的。我認為,沒有什么準備階段,即孩子雖然已經使用語言,已經使用語言去所謂交流,但卻沒有用語言來思維這樣的階段。[8]
在此,維特根斯坦雖然認為在語言形成之前,思維已經存在,并且在時間上先于語言,但在他看來,這在邏輯上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用語言表達的思想在邏輯上不依賴于非語言的思想。后者雖然在時間上優于語言,但它屬于心理學關注的范疇。
篇4
【摘要】
伊安·巴伯認為科學和哲學為倫理學提供了重要基礎。一方面,雖然科學不能為推導出倫理原則提供一個自給自足的基礎,但科學對倫理學有著重要貢獻;另一方面,哲學中的功利主義原則及公正、自由等概念,使我們能夠澄清評價選擇的倫理原則。
關鍵詞
科學內在價值;進化論;功利主義;公正;自由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660(2015)03-0091-05
作者簡介:張漢靜,山西沁水人,(太原030006)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教授;
王江荔,河南林州人,(太原 030006)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博士生,(太原 030024)太原理工大學政法學院講師。
美國當代著名科學家、宗教學家、社會學家伊安·巴伯認為,所謂價值就是一個物體或一種事態具有如下特征:人們帶著喜好或偏見去看待它,相信它是有益的,并傾向于通過行動去發揚它。堅持一種價值,就是對它的實現持贊成態度,相信它的益處,并認為道德責任可以用來評價或者捍衛它。而當我們根據價值觀去捍衛一種選擇時,就援引出了人類行為的一般原則——人類行為對與錯的原則以及人類行為后果善與惡的原則,也就構建了倫理學的領域。在此構建過程中,科學和哲學則在評判人類行為后果的標準的選擇、各種相互沖突的價值觀的平衡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從而為倫理學提供了必要的基礎。
一、科學與倫理學并非彼此獨立
巴伯首先指出,關于科學和倫理學彼此完全獨立的假定是不能成立的。許多科學家斷言科學的中立性和客觀性,相信科學理論是完全價值自由的,以維護事實和價值之間的絕對區別。比如,實證主義者認為科學是理性的和客觀的,而價值判斷則是感性的和主觀的。他們在科學和價值之間劃了一條嚴格的界線,聲稱科學家對其科學發現的應用沒有任何責任,科學的應用是不可預測的,科學家也沒有資格在他們有限的技術專長領域之外做出判斷。科學史家羅蘭·雷格厄姆(Loren Graham)把這種觀點稱為“限制主義”(restrictionism):把科學限定在一個清楚劃分的領域內,并且拒絕了科學和價值之間的任何聯系,把科學從社會批判中隔離了。這種“隔離”阻止了“擴張主義者”(expansionists)對科學的誤用,即擴展科學理念去評價政治信念。但雷格厄姆反對這種絕對區別的觀點,認為不存在價值自由的科學,因為在科學中存在著這樣一個范圍:從物理學中價值的相對較小作用到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中“不可忽視的價值取向”的觀念。哲學家斯蒂芬·圖爾敏(Stephan Toulmin)也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判:其一,科學(尤其是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中的許多概念反映了價值判斷,比如生物學中的“功能”和“適應”概念、心理學中的“正常和不正常”概念;其二,科學和技術之間的界限并非涇渭分明,科學發現的可能應用是足以預見的,科學家有責任向公眾告知這些可能。圖爾敏認為,我們是世界的參與者而非旁觀者,因此科學客觀性的理念本身是有問題的。還有一些批評者指出,科學與政府機構、產業資金來源密切相關,當科學擁有了一個令人敬畏的自我調節系統(通過撥款、同伴審核、出版物和獎勵結構)時,它就決不可能從外在壓力下解放出來。
巴伯認為,以上解釋表明科學和倫理價值的相互影響,不能完全彼此孤立。那么,是否可以通過從科學中引申出倫理原則來支持科學與倫理的整合呢?他深入分析了把倫理學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內在價值基礎之上的嘗試,以及從進化論的生態學中推導出倫理原則的嘗試。
(一)科學的內在價值無法擴展為一般的社會倫理
有一種觀點認為,科學的內在價值可以擴展開來作為社會秩序的基本理念。比如雅各布·布朗勞斯基(Jacob Bronowski)提出,科學本身要求寬容、無私、理性、思想自由以及持不同意見的權利,科學知識是普遍的,追求科學需要合作、誠實、忠于真理。他鼓勵把這些“科學價值”擴展到社會秩序,其表現形式是政治自由、尊重他人和國際合作。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也聲稱,可以在制度化的科學倫理中發現最高社會價值,包括普遍性、非功利性和公共性等等。
在巴伯看來,這種對科學內在價值的描述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首先,科學家的真實動機比這種理想化描述所認知的更為復雜。事實上,科學家很少是大公無私的,也不僅僅為真理而獻身,他們也像其他人一樣追求專業認可、個人成功和較高酬薪。科學的激勵和獎賞機制更偏向于與主流認知體系相一致。優先權之爭表明影響科學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當“大科學”出現時,研究的目的就漸漸被工業或政府所決定,他們的目的不再是真理本身,而是作為權力工具的知識。其次,即使“科學的價值”作為一種理想的表達而非科學行為的實踐而被接受,它仍然是有問題的:一種合適的社會倫理能否從中推導出來?在科學中發現的價值作為人文的政治秩序的標準是不充分的。從歷史上來看,科學工作與更廣泛的政治、哲學觀念相一致。追求科學知識僅僅是人類無數努力中的一種,而且它也不可能為目標各異的行為提供統一的標準。神學家理查·尼布爾(Richard Niebuhr)曾經指出,在科學研究中有一種重要的倫理特征:毫無保留地獻身于真理以及科學共同體的信任和忠誠,但這種倫理特征僅僅表現了有限范圍的價值。巴伯強調,即使搶占他人功勞的欺騙事件屢有發生,誠實依然是科學家的本質特征;但誠實并不首先是科學家個人美德的結果,而是制度化的科學結構的結果。總之,“重要的倫理價值是內在于科學的,但是我們不能期望從中得到合適的社會倫理,或者為科學制度外的倫理選擇提供動機”。
(二)進化論引申出的倫理原則無效
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沃丁頓(C. H. Waddington)等生物學家曾假定:人類價值可以從進化趨勢的特點和方向中推論出來——進化論的歷史表現為一種向著理智、自我意識、合作與對組織的忠誠發展的趨勢,這些特征曾有助于我們的生存,因此在進化過程中被選擇出來。威爾遜(E. O. Wilson)也提倡從進化論科學中推導出倫理規范:“我們關于生物學特性的經驗知識將允許我們在競爭性的進步標準中做出最佳選擇。”比如,生物界的利他主義行為帶來了適應性的有利條件,因而被選擇過程所支持;鼓勵社會合作的倫理規范因增強了集體統一性而具有巨大的生存價值,文化體系則允許這種合作延伸出去超越親緣關系。
巴伯指出,此類建議的困難在于進化顯露出相互矛盾的特征:合作與互助存在,但競爭性的斗爭同樣激烈,因而可以從進化中推導出更為寬泛的倫理結論。例如,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把為生存而斗爭當作為資本主義競爭辯護的理由;托馬斯·赫胥黎相信與自然的殘酷斗爭恰好是人類應該追求的對立面;尼采則認為進化論支持“超人”理念。與此同時,許多生態學家則認為,由于忽視了人性與文化的特殊性,因而從進化論歷史推導出倫理原則的努力是無效的。辛普森(G. G. Simpson)和杜布贊斯基(Dobzhansky)就曾經提出,自我意識和反思性選擇能力是人類與其他生物之間的區別,即使過去的趨勢已然清晰可見,但我們依然擁有選擇權去發起與有意識的選擇目標一致的新趨向。而許多哲學家則指出,從描述性的前提推論出規范性的結果是不可能的。休謨曾討論過“應該”的陳述不能從“是”的陳述中推導出來,因為它們是邏輯上不同類型的表述。G.E.穆爾認為,任何試圖從事實中推導出價值的人都會犯“自然主義的謬誤”。安東尼·弗盧(Anthony Flew)和安東尼·奎因頓(Anthony Quinton)提出,進化的方向極其難以確定,即使它是一個清楚的方向,我們也不能不管其結果如何就預先贊成它。我們不得不通過獨立的標準去評價它,即無論我們在人類進化中發現的趨勢是什么,我們都可以自由地選擇是否要繼續堅持或者試圖改造它們。湯姆斯·內格爾(Thomas Nagel)主張,進化論可以解釋我們反思性能力的來源,但卻不能解釋憑借這些能力我們達到的結果是什么。邁克爾·魯斯(Michael Ruse)則認為倫理規范的具體內容不能從進化史中推斷出來,盡管支持社會合作的共有道德規則是適應性的,但它們是偶然的進化史的產物,不是永恒的原則。價值實際上是我們投射到世界的人類結構,但是為了嚴肅對待它們,我們不得不相信它們是客觀的。“進化論的理論表明:道德實際上是感覺的功能,但是它也表明我們必須有客觀性的錯覺……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道德是我們的基因強加于我們的集體錯覺。”巴伯認為,魯斯的觀點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一旦倫理規范是集體錯覺的秘密泄露出去,我們幾乎不能期望它們的社會效果能夠持續下去。“進化論生物學不能既建造又懷疑倫理原則。”因此,在巴伯看來,以上分析表明,從以進化論生態學為基礎的科學中引申出倫理原則的嘗試是無效的。
(三)科學以多種方式影響著倫理學
巴伯主張,雖然不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不能為推導出倫理原則提供一個自給自足的基礎,但是它們與倫理學存在著三個方面的聯系:
第一,生物學和社會學給我們指出了由我們的生理結構所引起的對人類行為的約束。人的選擇不能忽視界限,即由過去進化論所設置或由基因程序、生理過程以及心理活動、社會壓力所設置的界限。即使許多選擇對我們而言是開放的,我們依然依賴許多不受我們控制的條件。
第二,科學越來越能提供可信賴的對決策后果的評估。對后果的分析是倫理反思的重要組成部分。成本-效益分析、風險-效益分析、環境影響評估、技術評估和監管標準,都深深依賴于對可供選擇的政策決定的可能后果的科學判斷。由于對目標的選擇并非一個科學問題,因此,對達到目標的方式的選擇就要求技術可能性的相關知識,以及對直接和間接后果的估算。雖然科學知識幾乎不能完全擺脫價值判斷或個人與集團利益,但科學知識仍然是技術決策的基本組成部分。
第三,科學有助于世界觀的形成,而我們的決策則生成于世界觀之中。科學是關于世界和人類地位的不斷變化的看法的主要來源之一,也是解釋各方面經驗的哲學范疇的主要來源之一。我們對實在的統一觀點必須與科學發現和對人類潛能的理解一致。雖然我們不能從進化論中推導出一系列倫理原則,但是我們可以從中得到關于時間性、變化和所有生命形式的相互依賴性的新視角。總之,倫理學不能從科學本身推導出來,但科學知識以一種重要的方式影響了倫理學。
二、哲學有助于澄清倫理原則
在巴伯看來,哲學能幫助我們澄清評價技術選擇的倫理原則。他認真審視了作為技術政策選擇原則的功利主義的長處和弱點,提醒我們思考社會利益和個體權利的重要性;并深入分析了公正和自由的概念,主張最重要的自由形式就是參與影響我們生活的決策。
(一)義務論倫理學是功利主義的可替代性選擇
功利主義的核心原理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善”,即應該選擇導致以善勝惡后果的最大凈差額的行為。比如,杰瑞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認為善即等同于快樂,個人應該選擇能夠導致快樂與痛苦最大平衡的行為。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主張幸福是比快樂更為包容和持久的善。功利主義經濟學家們則尋求社會整體福利的最大化,或者是個體福利的總和,或者是主觀偏好與可感知的滿足的總和。
巴伯指出,對功利主義的批判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大多數功利主義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善”僅僅用來指人類,而且只適應于當前存在的人,通常很少考慮代際問題。一般來說,最大的整體福利可以通過擁有低水平福利的龐大人口而得到,因此,當后代被包括進來以后,就存在著困難。二、在功利主義中,與道德選擇有關聯的只是整體的幸福,而不是幸福在人們之間的分配。比如,一個很小的少數的消滅給大多數帶來幸福,以致整體幸福增加;部分社會階層異常貧困,而國家整體收入卻能夠增加。假如能夠證明行為的間接后果會傷害整體利益,功利主義就能夠反對這些行為,但功利主義并未找到不公正或不平等本身的內在錯誤。
因此,巴伯贊同許多哲學家的觀點:功利主義原則必須由正義原則來補充。如果整體利益是唯一標準,我們就能夠評價一個很小的社會利益的正當性——即使它需要巨大的不公平。但是,如果正義是唯一準則,我們將不得不糾正一個很小的社會不公——即使它是普遍的苦難或社會傷害的結果。我們既要考慮正義,又要考慮整體利益。同時,巴伯指出,當正義原則補充進來之后,如果是小數目選擇而且有一個較小范圍的具體目標的話,成本-效益和風險-效益分析將是有用的方法。但是,今天大多數政治決策包含大數目選擇和寬廣領域的影響,許多是難以甚至是不可能量化的。平衡協調是多方面的,而且不能以單一的單位來測量,或匯總起來作為數量總值,它們包括高度多樣的價值類型。因此,巴伯建議,環境作用評估與技術評估方法允許更寬范圍的價值思考,藉此擺脫功利主義思想的某些局限性。政策選擇一般需要在無法比較的東西中進行價值判斷,因此,必須通過政治程序而不是通過技術專家的形式化分析技術來做基本決定。
巴伯倡導一種替代性的倫理研究路徑即義務論倫理學——功利主義完全依據后果來做判斷,義務論除了計算后果之外,還強調義務和責任。歷史上,斯多葛派學者認為人們有責任去按照這個世界的結構所表達的自然秩序、理性和道德秩序去行動。猶太教和基督教要遵從圣經所揭示的神圣法則。對康德來說,對自由和正義的要求基于作為獨立自主的和理性道德主體的個人的平等,個體的人永遠不應該僅僅被看作達到社會目的的手段。因此,與功利主義強調社會利益相比,義務論倫理學通常維護個體權利。即使是為了有利的社會后果,基本權利也不應該被侵犯。權利與義務密切相關,我的生活權利同時意味著你有不侵犯我的生活的義務。而且,權利和義務不是絕對的,不同的義務有著份量上的輕重之分,當兩種權利相沖突時,其中一個可能被優先分配。在技術時代,政府掌握巨大權力(比如通過電子監控和控制信息),并且通常以對社會有利為理由為這種行為進行辯護。因此,捍衛個人權利事實上非常重要,可以保護少數人免于因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受到剝削。但是,在一個相互依賴的生態世界,人類行為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極為深遠,必須同時考慮保護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而且不存在二者結合的簡單公式。在某些情況下社會后果最重要(如核武器),而在某些情況下個人權利是主要問題(如電腦操作者的保密)。因此個人權利和未來社會利益很難協調一致,正如關于人口增長的辯論一樣。此外,巴伯還建議同時使用對后果的寬泛評估(通過包含非量化標準超越功利主義和成本—效益分析)和捍衛權利來避免絕對主義。
在巴伯看來,大多數關于正義的理念始于基本的人人平等的假設。人人平等或者基于一個宗教信念:在神的眼中每個人都是價值平等的;或者來自于人類權利生而平等的信條或和諧社會秩序的要求。那么,分配的公正則始于這一理念:因為人生而平等,所以人必須被平等對待。與此同時,不公正對待可以根據許多理由證明其正當性:為那些特殊的貧困者和殘疾者提供特殊供應本身是不平等的,但它的目的是人人有機會過上幸福生活;收入的差異可以作為生產效率的刺激來證明其正當性,但是當今工業社會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幾乎很難為這種目的進行辯護。簡言之,僅僅當不公正對待有助于糾正某些其它形式的不公正,或者它對于所有人的幸福而言必不可少時,不公正對待才可以證明其正當性。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權利不平等是必須的,但通向權利的路徑可以是平等的。但是,巴伯強調,我們為了其它社會利益而承受的不公平程度應該有一個限度。如果技術將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如果全球資源匱乏限制了用于分配的資源,那么,不公正問題就會承擔額外的緊急風險。因而他主張:“在資源分配中面對人類基本需求時(如食物、健康和避難所——馬斯洛需求理論的最低級),相比在其它商品和服務的分配中,公平更具有令人信服的價值。”因此,食物和醫療方面的公正應當具有最高的優先權。
(二)參與決策是最重要的自由形式
巴伯指出,在所有對技術政策的評估中都包含一種認知:它對自由的限制或擴展所達到的程度。自由有許多形式,它以各種方式被政策決定所影響。哲學家喬爾·費因伯格(Joel Feinberg)認為,自由可以表述為一個政府機構、一種約束和一種活動之間的關系,它有一個一般結構:x從y中釋放出來去做z。當人們去捍衛自由時,頭腦中就有了特定類型的約束和活動。
在巴伯看來,自由具有消極與積極兩個方面。自由的消極方面即外部約束的缺失:從被其他人或其他組織強加于身的壓力或直接干預中解放出來。洛克和英國早期自由政治哲學傳統曾把自由首先闡述為缺乏其他個體或政府的干預。自由的積極方面就是選擇機會的存在。個人的自由程度是自由的基本組成部分,許多選擇的條件是內在的,在替代選擇意識、進行慎重選擇的能力、個人主動性和自我導向方面,人們之間有很大不同。但是在對待公共政策時,我們需要關注外在條件即政府結構,在其中人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的未來。自由的消極方面和積極方面在任何社會秩序中都不可避免地相互關聯。政府是秩序和法律的根據,但是當政府限制某些行動而使得其他行動成為可能時,它也是自由的工具。政治自由的消極方面是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如審查制度和任意逮捕,而其積極方面則是自我決定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形式的政府,藉此,每位公民都能在做決定過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巴伯特別指出,在當代技術社會,為了保護人們的健康、安全和幸福,政府干預的權力已擴展到更加廣闊的領域,與技術政策有關的自由形式可以被積極地理解為參與技術決策的機會:第一,參與市場。在自由市場經濟中,達到市場效率和社會公平的協調一致并非易事。效率的缺乏在某種程度上伴隨著使用稅收來緩和貧富極端差距,以及支持健康和福利政策以確保無人缺乏生活必需品。政府行為在市場中比在其他地方需要承擔更多的干預。第二,參與政治程序。在現代民主國家,公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實現對政治的影響。但是,在面對復雜技術決策時,公民通常感到無能為力。比如,核反應堆和有毒物質對人類健康和安全的威脅就難以評估。這樣的決定不應該僅僅留給技術專家去解決,因為他們需要比較各種各樣的風險和收益以及對不同政策進行評價,這并不是純粹的科學問題。贊成技術發展的工業和政府機構通常比反對技術的機構擁有更廣泛的法律和科學資源。第三,參與關于工作的決定。開展此類工作的機構非常廣泛,它應該包括這樣的規定:使工人的聲音能被聽見,比如工會、勞動管理委員會、生產合作社等。巴伯指出,這三種參與形式在大型技術中比在中型技術中更為困難。比如,核能是復雜的集中的,需要巨額投資并承擔異常危險,這就需要特殊的政府監管和嚴格的安全評估。相反,許多形式的太陽能是疏散分布的,地方就可以安裝并管理,分散化抵制了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集中,并有助于多樣化和地方控制。不過,在許多情況下,權力集中是必須。比如,地方政府要依靠工業增長來增加稅收總額,而在控制污染方面收效甚微,因此國家對環境監管及能源保護的作用日益加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國家層面上公民參與將更為困難。
篇5
對祁克果來說,宗教B或基督教是與宗教A完全不同的途徑,是宗教階段中的最高境界或途徑,唯由此途徑才能最終成為單個的人。而這個途徑的起點就是罪,或個人自己對罪的意識。因此,祁克果希望在理論上再次喚起了人們對罪的問題的重視。可以說罪的問題在他的思想中占據著某種核心的地位。他自己認為所寫的最好的兩本書之一,《致死的疾病》,就專門討論了絕望與罪的問題。他的罪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他把罪與生存中的個體精神覺醒直接關聯起來,并且進而將其置于已被忽視的那個超越之維面前。在他看來,絕望證明了個體覺醒的精神具有非自立性,它依賴于一種更高的力量。而罪從根本上說就是對這種更高力量的拒絕。他對罪的討論開創了一種生存論的闡釋立場,因而成為現代思想試圖去理解罪的重要進路之一。盡管祁克果把自己對罪的闡釋方法歸之為一種“心理學”方法,但它實際上更近于一種生存“現象學”的方法,在這種方法中始終包含著這樣一種維度:生存的個人對自己罪的意識或覺醒。具體地說,從這種進路去理解罪, 即是將罪的問題置于人之成為單個的人(或一個基督徒)的生存過程中去理解它。
第一節 祁克果罪論的出發點
在上個世紀祁克果所處的時代, 自然神學和思辯哲學分別在神學和哲學領域占據了主流。受啟蒙運動以來人文精神的影響, 它們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把人的理性看作是終極性的,力求在理性中找到對于一切事物的最終說明。理性法庭成為人認識的終審法庭。當人們在這個原則下去認識罪的問題時,上帝這一超越的維度被取消了,罪(sin)的問題也就隨之變成了惡(evil)的問題。
在康德那里,這種惡的問題典型地表現為是一種道德論上的問題。于是罪的起源問題成為惡的來源問題,原罪似乎成為不可理解的。他認為:“最不適當的一種方式,就是把惡設想為是通過遺傳從我們的始祖傳給我們”。 他力求從理性上尋找惡的根源,將惡與人的理性和行為關聯起來, 從而使每個人要為這種由于自己的行為而出現的惡承擔責任。“每一種惡的行動, 如果我們要尋求它在理性上的起源,都必須這樣看待它,就好象人是直接從天真無邪的狀態陷入到它里面一樣”。 人是完全自由的,所以個人自己要為這種“陷入”負責。換句話說,如果人的理性認識到自己所應該做的,并按照那道德的律令去做,人就可以擺脫這種惡。 這其中就包含了康德倫理學的著名原則“我應該,我便能夠”。
黑格爾的思辯哲學在罪的問題上不僅取消了超越的維度,同時使其進一步越過了倫理的含義。惡成為具有邏輯意義的“否定”,即被看作是推動精神演進的一個促動因素或環節。具體地說,個人對自己有限的意識或反思本身就是惡,“人在他自在的即自然的狀態跟他在自身中的反思之間的聯接階段上是惡的”。 如果說人必然要從自然狀態邁向自我意識,那么,這種惡就是必然的;如果說有限的認識或反思相對于其最終要演進到的更為普遍的精神而言尚屬無知,那么惡就是一種無知。在這后一點上,黑格爾的思想與蘇格拉底對惡的看法有相似之外。
祁克果罪的學說與上述的觀點有根本的區別。祁克果認為:
正是罪的概念或關于罪的教誨最鮮明地將基督教與非基督教世界從質上區別開來,這也正是基督教從來就認為非基督教信仰和自然人都不知道罪是什么的理由。
可以說,就是在對上述觀點的批判中,在與整個西方哲學思想的區別中,祁克果的罪論方顯出它自己的特點。
首先, 祁克果從根本上批判了自蘇格拉底以來在西方哲學傳統中一直存在著的“罪即無知”的理性主義思想,這種思想總是想把罪或惡的根子歸在人的認知上。在祁克果看來,造成這種傾向的原因在于,這種思想把理性或理念的世界看的更加根本,而忽視了具體生存中個人的更為源始的意愿或情感。“按照基督教的解釋,罪的根子在意愿中,并非在認知中,并且,這種意愿的墮落影響到個人的意識。” 個人的意愿對于個人的生存來說,要較個人的認知具有更源始更直接的關系,而在蘇格拉底式的“罪即無知”的定義中,“缺少的就是這個意愿或這個違抗的意志了。” 因為理性主義思想“無法理解人竟然可以有意識地不去為善,明知何為正確,卻偏去做那錯的,” 以為人只要去“我思”,就會怎樣“我在”,只要知道了“應該”,就一定“能夠”實行。 但從個人生存的角度看,無疑在“思”與“在”之間,在應該與能夠之間, 以及在認識與實行之間無疑存在著一段距離,存在著一種決定性的轉換, 基督教所言的罪正是在這種轉換之中。 在現實的生存中,祁克果舉出常常有這樣富有笑劇性的事情:
當一個人站在那里說著正確的事情,因而表明他理解了它,可一旦行動起來卻做出錯誤的事情,并因此表明他并沒有理解它,就是極富于笑劇性的了。
這并不是說當事人在偽裝,或者他能夠意識到他在這兩方面之間表現出的差別。 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一個人可以在這樣說和那樣做上都表現的同樣真誠,人生存中這樣的笑劇性才是真實的。生存于現實世界中的具體人不僅有認知, 同時也受意愿(或本性)的支配,當兩者發生沖突時,人的選擇就會被延遲,只要時間長到一定程度, 認知總會被模糊或修正到與意愿相一致的地步。這期間某些理解便向當事人遮蔽起來, “這理解如不被遮蔽,就會引到他們的較低級本性所不喜歡的決定和結論上來”。 這其中所表現出的兩種角度的區別就在于:蘇格拉底把這種遮蔽看作是人尚未理解, 而基督教把它理解為是人不愿去理解。因此,祁克果的結論是,罪的根子是在具體生存者的意愿之中。
其次,針對黑格爾的思辯哲學, 祁克果特別批評了那種把人的罪只看作是其客觀和思辯的研究對象的那種方法。他明確地指出,罪不是任何科學(思辯哲學)的合適對象, 因此它不能被思辯地思考,罪一旦被思辯地思考,它就不能不成了抽象的“否定”。但罪并不只是一種自我的否定,相反卻是有所斷定或主張。 這種斷定之所以不被傳統的思辯哲學視域之外,乃是因為罪與生存中個人的緊密關系。在祁克果看來, “罪的范疇就是單個的人的范疇”, 而這個“個別的人類存在者位于這個范疇下面的更深處:他不能被這樣思考,只有‘人’這種概念才能被思考”。 換句話說,罪和單個的人作為罪者是不可分離的,罪即個別罪者,而這其中包括的含義就是,與罪相遇,首先是單個的人與有罪的自己相遇。在這個意義上,“罪是單個的人(the single inpidual)的資格”。 而單個的人在這里屬于對罪或精神有所覺醒的范疇。因此,盡管祁克果把自己對罪的闡釋方法稱之為一種心理學方法,但正如一些專家所指出的, 用現代的觀點看這種方法,實際它更近于一種“現象學”的方法, 在這種方法中包含著這樣一種維度:個體作為罪者對自身罪的意識或覺醒。
最后,祁克果在自己的罪論中恢復了上帝這個超越之維。 在托名于克里馬庫斯或其他作者的著作中,因為站在基督教外的存在論立場中,這種超越之維乃以悖謬(Paradox)的方式出現,這一點和罪的關系我們下面會談到。而在托名于安提-克里馬庫斯的《致死的疾病》中,因為是站在基督教內的立場,因而直接肯定了“罪就是在上帝面前”。 就是說,生存中的單個個人所以成為罪者,或對自身的罪有所覺醒,是因為“在上帝面前”,下面我們會看到,基督教中所言的罪(sin)由此和宗教A中所說的罪責(guilt)區別開來,并且,正如祁克果時常強調的,個體作為罪者的地位使人和上帝之間有那深不可測的深淵。
節二節 罪與人的不安和絕望
罪的本性是什么?它怎么源起的?對于罪的理解,自奧古斯丁以來, 在基督教內一直需要把它和原罪(祁克果將其稱之為遺傳之罪)聯系起來, 才有可能給出某種答案。人類始祖的犯罪,以及由此給人類帶來的影響,在教義學上是個即定的事實, 但在基督教外,它對人類的理性來說卻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以至在西方傳統思想中,尤其是在啟蒙之后,在對罪的理解上,基本上是停留在“無知”之說上。教內與教外的距離或隔閡幾乎是不可愈越的。祁克果在緩解這種隔閡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的復調式敘述方式同樣用在了罪的問題上,一方面是某種教內立場的論述; 而另一方面則是在生存論層面上的論述,即祁克果所說的“心理學”(現象學)方法的探索, 力求在啟蒙之后的人文語境中對于罪的問題給出某種理解, 其結果就是在這個維度上開創了理解罪的“生存論”進路。然而不管兩個維度的論述方式有怎樣的區別, 論述背景卻是一個:即把罪置于成為單個的人(或一個基督徒)的生存過程中。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祁克果把罪與單個的人遭遇自己時的不安和絕望關聯起來, 從而在存在論層面上把人對罪的理解向前大大地推進了一步。轉貼于
在《不安的概念》一書中,祁克果(或托名作者Vigilius Haufniensis )把基督教通常所說的原罪(original sin)稱之為遺傳之罪(hereditary sin),他認為傳統的神學家總想用這種遺傳之罪去說明罪本身或罪的來源其實是一種誤解, 人們并沒有把握住所謂遺傳之罪的主旨:“遺傳之罪的本性常被考察,但其基本范疇卻未被抓住---這就是不安,正是它真正決定了遺傳之罪......” 因此,他試圖從一種生存論的層面去理解這種遺傳之罪,將其解釋為人生存中“心理上”的不安狀態。 這里所謂不安實際是祁克果生存論中的一個重要范疇, 它指生存中的個人在獨自面對著自身充滿了各種可能性的未來,醒悟到自我的自由時,內心所經歷到的顫栗。
祁克果并沒有把不安本身看作是罪,它只是罪的機緣或誘因, 或者說是一種最趨近罪的生存狀態或條件。 正是這種生存論上的因素,而非生理意義上的遺傳,誘發了人的罪。因此,這里所謂的“遺傳”體現為,正是這種生存上的不安在一代一代地遺傳,并且不安在這種歷史的傳遞中表現出一種量上的遞增。 這種歷史地流傳到每一代人生存中的不安,對個人產生了這樣的影響:不安預先地使個人有向罪發生質躍的傾向。不過,這種不安只是使個人預先具有這種傾向而已,并不是強迫個人有這種質躍。這里我們注意到,祁克果十分強調,在不安到罪之間存在著一個不能被理論說明的質躍(qualitative leap),該質躍之所以不能被理論說明,乃是因為由不安到罪的過程所具有的個體性特征所決定的。在祁克果看來,人是由永恒或無限與有限或易逝構成的合成體。個人趨近精神覺醒即意味著精神(spirit)開始作為兩者的合成被意識到。不安就生發于這種精神覺醒的初始之際。從消極的意義上講,這時,每當精神想要抓住自己之際,它都失望地發現,本無任何“東西”可被抓住,所面對的只是“無”而已。 不安正是這種面對“無”的不安; 從積極的意義上講,精神的覺醒,初始是以“可能”的方式呈現,但這種可能卻不是關于任何“什么”的可能,只是可能之能,這種可能之能讓人看到自己控制力的有限。這時不安表現為是個人在自由面前的不安。 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講,個人精神覺醒之初的不安現象揭示出:個人不是所覺醒的自己的主人。 然而個人卻下意識地想要逃避不安給人帶來的這種無可奈何,或者想靠自己的方式去消除它。無論怎樣,這都會使個人與自己形成一種錯誤或扭曲的關系中, 其結果就是個人陷入絕望之中,這就是向著罪的質躍。
對于罪的本性的問題,祁克果主要在《致死的疾病》一書中, 將其與人生存中的絕望關聯起來,對其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在這本書中, 托名作者安提-克里馬庫斯在基督教立場上, 指出了他所理解的罪涉及到兩個重要因素或環節:“罪是絕望和處于上帝面前。”
首先,罪與個人生存中的絕望緊密相關。但什么是絕望呢? 《致死的疾病》一開篇就說到:“人是精神。但什么是精神?精神是自我。但什么是自我? 自我是一種自身與自身發生關聯的關系。” 簡言之,在存在論的意義上講,人在這里并非是傳統意義上的實體,而是一種關系, 精神不僅是有限與無限或永恒與易逝之間相互貫穿的關系,而且作為自我,則是這種關系的自身關聯關系(即反身作為第三者)。 絕望就是在這種關系的自身關聯中,形成的錯誤關系所致。這里, 構成自我的自身關聯關系之所以是錯誤的,在作為基督徒的安提-克里馬庫斯看來, 就在于當事人沒有意識到:這種自身關聯的關系只能為那更高者所建立。因此,絕望的出現,指明了兩件事。首先, 絕望意味著個人精神的覺醒。個人在成為單個人的過程中,作為其精神的覺醒, 精神的自我意識方有可能使之陷入絕望。在這個意義上,“絕望是精神的資格所在并與人里邊的永恒發生關聯”。 其次,絕望的出現說明精神下意識想要主宰自我,即與自己形成一種排他性的關系,但絕望總是對自己的絕望這個事實說明, 精神永遠無法獨自控制或主宰自己。
個人與自己的這種錯誤關系使絕望表現出兩種基本的形式。 1)在絕望中不要成為自身,這就是“軟弱”形式的絕望。這種形式的最初級樣式就是:在絕望 個人不認識或不愿意認識自己,一心尋求能崇拜的偶像來滿足自己的需求。而一般地說,如果個人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能夠把自我從周圍世界中區別出來,但卻由于種種原因不滿意于它,同時又不能擺脫它, 就會采取“外向”的解決方式:他把自我看作是他可以擁有的能力或天賦等, 一心想要得到別人的肯定:“他的言行舉止是基于人們的尊敬,基于別人對一個人的品評以及按人的社會地位所作的判斷。” 這種情況的可怕之處在于:在他看來是對絕望的征服,而他的狀況事實上仍是絕望。 這種情況發展到極端,便是個人將自己封閉起來。 封閉是這樣的一種矛盾反應:一方面是恨惡自己,一方面是憐惜自己。
2)在絕望中要成為自身,這乃是“違抗”形式的絕望。隨著自我意識的提高,絕望的形式和其深度也在發展, 這第二種形式就是對自身的絕望向前跨出的一大步:以違抗的心要成為自身。一方面,就行動的自我而言,絕望中的自我滿足于關注它自身, 并假定此自身將無限的興趣和意義給予了他的事業,但也正是這一點, 使得這些事業成為想象的,自我也日益成為假設的。另一方面,就被造成的自我而言, 盡管有面臨自我所遇到的種種困難與苦惱,但他“與其尋求幫助, 他寧可(如果必要的話)帶著全部地獄的痛苦成為自身”。 這里面包含著一種對更高者的怨恨。
就這兩種絕望的形式而言,前者可以歸于后者,或者說隨著自我意識的提高, 后者是前者的進一步發展。而且,就第二種形式, 可以證明它不過是對一種更高力量的消極見證:第一,個人想要成為自己或自己的主人, 但其絕望和怨恨的事實表明個人恰不是他自己的主人;第二,個人在怨恨中實際把痛苦看作是自己存在的一種證明, 證明自己能夠違抗一個無限的“救助者”。
絕望的這種發展形式,把人生存上的絕望與人的罪之間的緊密關聯顯明出來。 這也就是安提-克里馬庫斯進一步指出的罪的另一個重要環節:“罪是絕望的強化”, 這里所謂“強化”就是指“重點在于‘在上帝面前’,或具有上帝的觀念”。 他之所以將在上帝面前看作是一種強化, 乃是出于他的這樣一種思想:個人的自我認識在不同的標準下達到的深度不同。在人的標準下,個人對自我的有限認識使自我還是有限的自我,因而自我的絕望也只是有限程度的絕望。當上帝成為這個標準時, 情況就發生了質的變化。對上帝的觀念增一分,則自我也加強一分,反之,自我加強一分, 對上帝的觀念也增一分,“自我是在與這自我的標準的關聯中被強化,當上帝是這標準時, 則自我就被無限地強化了。” 隨著自我被無限地強化,其絕望便表明是基督教意義上的罪:
唯有自我作為一個特殊的單個個人意識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生存時,它才是一個無限的自我,這自我乃在上帝面前有罪。
因此,安提-克里馬庫斯表明,基督教意義上的罪, 乃是在個人于上帝面前的生存中顯明出來。如果說在宗教A的途徑中,個人的罪責感(guilt)是由于意識到自己的有限,不能實現絕對的倫理或永福的目標,但仍然對永恒有種向往的話, 那么在上帝面前的絕望表明,個人已經不再相信或者不再尋求這個“無限者”, 而愿意繼續沉浸于或者軟弱或者違抗的絕望中,這就是罪(sin)。在這個意義上,“正是在上帝面前生存的意識使得人的罪責變成為罪。”
總之,絕望證明了個人覺醒的精神具有非自立性,它依賴于一種更高的力量。在這個前提下,祁克果把罪定義為:“罪意味著:在上帝面前或懷著上帝的概念, 在絕望中不要是其自身,或在絕望中要是其自身”。
第三節 罪與個人的個體化生存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按照祁克果(或安提-克里馬庫斯)對罪理解的進路, 罪與個人成為單個的人的過程有著密切的關系。按照上述安提-克里馬庫斯的描述, 隨著個體精神的覺醒,意識越增強,自我越突出,人的絕望就越強烈,因而罪就越強烈。 我們從上面看到,不管個人愿意與否,消極還是被動,或者是否被意識到, 絕望總會把人帶到這個地步:這時個體象是和一個更高者單獨面對,或者更確切地說, 象是在和一個更高者暗自較量,因為受到冒犯或懷恨違抗是個體面對這個更高者的最初和自然的反應。這時處于絕望中的個體已經如此地軟弱,即使他意識到自己已經是一個錯誤, 他也會懷著對此更高者的不平,無論會有多少的痛苦,仍要固執下去。就象是說:即然已經如此,我也就不想免除。
這里所發生的不只是絕望,在安提-克里馬庫斯看來,如果此絕望是罪, 那么進而對罪絕望則是罪的強化。處于這種狀態的人不會相信自己的罪會被這更高者赦免, 就是說,去直接面對更高者,承認個人覺醒之精神的對他的依賴, 而從他那里得到一個全新的自我(精神)。相反,他則堅持自己的這種狀態,
它堅持只聽它自己的,堅持只與自己打交道;它將自己關閉于自身之中;將自己鎖入了更深一層的禁錮中,并且通過對罪的絕望而保護自己不受善的任何攻擊和追逐。
安提-克里馬庫斯認為,在越來越大的意識強度中, 罪的這種強化就是罪的狀態或罪的一致連續性。罪的狀態與罪的行為不同,罪的狀態從更根本的層面上揭示了罪本身。 而它的特點在冒犯中全然表現出來,“關于罪的寬恕的絕望乃是冒犯, 而冒犯就是罪的強化”。 冒犯作為人罪的狀態的情感性表露,它完全是個體性的,去設想一個冒犯而不想到一個被冒犯的人是不可能的。因而在這個意義上,罪正是單個的人的生存狀態。
冒犯之所以可能,在安提-克里馬庫斯看來, 是由于人與上帝之間存在的無限的本質區別造成的。這種無限的本質區別使那更高者成為人的理智所不能理解的。 即使是上帝親自道成肉身來到這個世上,也并沒有使這種理智上的不可理解減輕任何一點, 反倒是更加集中到了這位神-人身上。 這位神-人對于人的理智永遠是一個絕對的悖謬(Paradox),人在這位面前受到的冒犯是:什么?那個看上去與我同樣的人竟然自稱是神,而且自認為有權赦免我的罪?這就是基督同時代的猶太人所受到的冒犯。 也是今天人們在那更高者面前受到的最具體和最強烈的冒犯。從這一點看,造成個體受到這種冒犯的原因可以說有兩重:第一,不安或絕望已使覺醒的精神能夠如此地面對這個更高者, 以致他們就象是同時代人一樣。這個因素我們前面已經涉及到了。第二,這個更高者作為神人,對理智來說是一個絕對的悖謬。
這后一重因素更多地涉及到個體的理智因素。它表明在個人的理智被僵持之處, 冒犯就可能隨之被激起。 而這反過來意味著:當冒犯被激起時,正表明個人的理智也達到了他的界線。實際上,對一個生存于具體處境中的個人而言, 所謂個人的理智首要地體現為個人所生活之群體或社會的價值觀念、倫理規則、 以及各種的“合理說法”和習俗等, 這些都是個人之中屬于自然范疇的普遍性因素。 在個人成為覺醒的精神與那Paradox相遇之際,首先受到沖擊的正是這些普遍因素。它們在理解Paradox 時的無能為力,一方面讓個人親歷到冒犯,同時也把個人精神的個體化出來。
這也讓我們看到冒犯是個體性的。如果在生存論上說, 一個人所親歷的冒犯正是他自己的現身,而這冒犯同時又是其罪的狀態的顯露,那么, 這正說明了罪即個別罪人的結論。罪不是人抽象反思的對象,對罪的真正認識來自個體對自己的認識,或者說, 在那更高者面前,對自己不安和絕望的醒察。 實際上冒犯的顯露表明個體的精神已覺醒到這樣的地步,它已經被帶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或者懷疑,或者相信;或者違抗, 或者接受;或者封閉,或者開放。在這個意義上, “冒犯很可能是主體性和單個的人的最具決定性的資格”。 這意味著在單個的人的生成中,精神特有的內向維度(inwardness)已處在開啟的臨界點上。對于罪或他作為罪人,它所告訴這個人的, 遠較任何其他的知識途徑要更為具體真實。我們在第三章中已經看到,這個內向維度, 作為覺醒的精神的一種展開,是單個的人的主要標志。它的特點就是精神的熱誠關注(earnestness ), 這種熱誠關注構成了個人之為單個之人的人格性本身。 只有這種熱誠人格,才使之有可能性在做任何事情時都帶著自身特有的熱誠。對于罪也是如此, 當個體帶著這種熱誠關注自己的罪的時候,也正是自己作為一個罪人得到認識的時候。
在祁克果后期的著作《今日的時代》和《觀點》中, 祁克果多次激烈地批評這個時代, 指出這個時代是一個被反思敗壞因而缺少個性激情的時代, 它的特點概括起來就是人們毫無罪感和個人責任。而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即在于這個時代日益突出的群體( a crowd)及其所特有的幻象。祁克果罪論的宗旨就是要恢復個人的罪感及其責任。 為達到這個目的,他不僅批判了思辯哲學,同時也批判了這種群體的幻象。 在祁克果看來,群體不僅讓人感到確定和自在, 更重要的是,群體能讓人免除要承擔責任所給人帶來的不安。然而,如祁克果自己所說,不安是個體精神的資格, 因此群體中無不安的安全感就恰是以個人的無精神性(spiritlessness)為其特征的。
這里我們就遇到了祁克果罪論所遭遇的一個主要問題。 如果罪與個體精神覺醒的不安及絕望相關,成為單個人即意味著成為罪人,那么, 對在群體中處于無精神生存狀態的人,能否說他們就不是罪人,或者是處在了遠離罪的狀態中? 祁克果自己也意識到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對他之所以仍是一個問題, 是因為從他的罪論中確實難以對其給出一個十分完滿的回答。一方面當他從生存論層面力求通過不安和絕望去理解罪時, 他確實把個體的意識與罪緊密關聯起來, 他的罪論中始終有一個維度就是:當事者自己對自身罪的醒悟和認識。但是,祁克果并沒有直接把罪等同于意識, 而是把意識看作是趨近或認識罪的最切近的途徑。因此,盡管他說:“按照真正的基督徒的理解, 大多數人的生活變得太無精神性了,以致無法在嚴格的意義上稱之為有罪”, 然而這話聽上去卻象是反話。實際上,處于無精神狀態的人并非擺脫了不安或絕望,只是對其不意識而已,“但這不意識到自身的精神性的狀態恰恰就是絕望,或無精神性的絕望”。 對于罪來說也是如此, 這里他提醒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辯證的轉折:無精神性的狀態只是對罪沒有意識,而并不意味著其不在罪中。當人們想要在群體或理論或瑣事中忘卻自己的罪,想要由此擺脫潛在的不安和絕望之際,這種罪感的缺失所導致的只能是惡!
因此,祁克果的罪論乃至他整個的著述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這種群體的幻象和束縛,把個人從群體中分離出來,認識到自己是個罪人, 由此而成為一個有全新自我因而能夠承擔起個體責任的單個的人。但當祁克果視單個人高于人類, 并在此原則下討論罪的問題時,從基督教神學上看,就難免會有帕拉糾主義(Pelagianism)的傾向。 尤其是在他早期的《不安的概念》一書中,如果否定原罪或人類整體的罪, 單純從每個人精神的覺醒所導致的在自由面前的不安來理解趨向罪的途徑, 這在神學上就無疑會落入帕拉糾主義的窠臼。祁克果自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在其后來的著述中也力圖有所修正或為自己辯護。但無論如何,既然把罪與單個的人精神覺醒的過程關聯起來, 這個傾向就是難以完全消除的。這也反映出在祁克果思想中, 仍然保存有啟蒙運動以來人文主義影響的痕跡。
第六章 宗教B:單個的人與信仰
按照祁克果的思想,宗教B是個人成為單個的人的最高階段,嚴格地說, 只有達到這個階段,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單個的人,或者換句話說, 個人的自我才能得到最為真實和充分的實現。這里,宗教B實際就是指基督教。因此,對這個階段的分析, 實際就是圍繞著基督教信仰所作的分析。從個人向單個之人的實現而言, 基督教構成了與倫理-宗教A迥然有別的途徑。盡管基督教作為高一級階段要以倫理-宗教A的階段為前提, 但它所具有的獨特特征卻是一般宗教所不具有的。在托名作品中, 祁克果主要通過克里馬庫斯在生存論的層面上論述了基督教信仰的特征。限于本文主題的語境, 我們在將其看作一種實現單個之人的途徑時,基本上限在這種存在論的層面, 輔之以祁克果自己在其他(包括署名)作品中對信仰的看法。轉貼于
第一節 絕對的悖謬對于宗教B的意義
在托名于克里馬庫斯的作品中, 克里馬庫斯時常把宗教B稱之為關于悖謬的宗教(Religion of Paradox)。 可見悖謬是宗教B或基督教的主要特征。克里馬庫斯對基督教的分析就是圍繞著悖謬入手的。
悖謬對于克里馬庫斯來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存在論范疇, 有其比較獨特的含義。從生存論層面上一般地來看, 可以把它看作是對生存著的個體與永恒真理之相互關系的一種生存論表達。 因此, 它涉及到的是兩個方面的因素--個體與其所關切的永恒真理--之間的相互關系。 這種與永恒相關的真理或目標向生存著的單個的人所表現出的客觀不確定性、矛盾、沖突甚至荒謬,就是所謂的悖謬。
克里馬庫斯所說的悖謬范疇可以分為兩類:相對的悖謬與絕對的悖謬。 所謂相對的悖謬(relative paradox)是指, 單個的人所關切或追求的永恒真理或目標本身沒有矛盾或沖突,只是在具體的生存處境下,相對于生存個體表現為某種不確定性或沖突。 我們在倫理-宗教A中所看到的情況就是這種情況, 倫理的原則或目標不管以什么方式體現出來,其本身都是普遍和自洽的,但對生存中的個體實踐者則表現出不確定性。 另一種就是所謂絕對的悖謬(Absolute Paradox)。 它是指在單個的人所關切的永恒真理或目標本身就包含著人的理智永遠無法理解和解釋的沖突與矛盾。 這種絕對的悖謬只存在于基督教之中。在基督教中,如這個信仰所認定的,永恒真理已經進入到時間的生存中, 上帝已經道成肉身親自為人。作為道成肉身的耶穌既是上帝又是一個具體的人, 這對人構成了絕對的悖謬。需要注意的是,作為這種絕對悖謬的神-人(God-Man)是一個特定而又具體的人, 并非思辯哲學可以加以辯證的神性與普遍人性的某種“統一”:
神-人是上帝與一個個人的合一。那種人類是或應該是神親緣的觀念是古代異教學說,而某個個人同時是神卻是基督教的信仰,這個個人就是神-人。
所以在基督教的情況下,克里馬庫斯所說的悖謬,就其神學層面的含義來說, 實際就是指基督,或者說是對他在生存論語境中的一種表達。當人們去設想, 尤其是耶穌同時代的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發現所熟悉的某個人,看上去似乎和其他人沒什么區別,有父母和兄弟,也干過不少人干過的職業,這個人竟然是上帝,而且他自己竟也這么自稱, 那么人們,尤其是當時的猶太人,會感到多么的不可思議或荒謬。
這種悖謬的絕對性是以上帝和人之間所存在著的本質的區別為前提。 這種本質上的區別可以分別從存在論和認識論這兩個層面上來給予刻畫。首先, 祁克果十分強調上帝與人之間存在著存在論的鴻溝。上帝就是上帝,人就是人;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上。 兩者之間是沒有任何相通之處的。 這種存在論上的差別可以體現在多個方面:無限與有限的區別、永恒與流逝的區別、創造者與被造物的區別等。在克里馬庫斯的生存論語境中, 這種區別主要體現為時間之外的永恒與時間之中的流逝之間的存在論區別。 從生存論的層面看,永恒意昧著絕對與不變;而流逝則意味著相對和易逝。 這兩個方面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方面,現在卻通過一個歷史事件,完全地合在了一個具體的人身上, 由此而產生出人的理智所不能理解的荒謬:
什么是那荒謬?那荒謬就是永恒的真理已經進入到時間性的生存中,就是上帝已經進入生存,并且正是以與任何他人沒有區別的一個個人的身份進入到生存。
在西方哲學思想的發展中,自柏拉圖開始, 可知世界和可見世界的區別就以各種方式出現在人們的思想中。然而,時間中的個別與不變的永恒究竟如何關聯進來, 對人的理智始終是一個問題。就柏拉圖的思想來說, 他的“分有”說可以說一直是他思想中最有爭議的一個方面。從人的生存角度,絕對的悖謬給人理智提出的問題, 在克里馬庫斯的生存論語境看來,仍然是這一類的問題:永恒如何能夠進入生存(exist)?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沿倫理-宗教A的途徑,生存個體的這種實現基本上是失敗的。 個人的道德努力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一種努力而已。這里的悖論表現在:如果一種永恒的道德實在為其他的生存者提供了普遍的標準,那么個別、 易逝的個人永遠不會充分、完全地實現這種永恒的道德實在,。要是這種實現真的能夠達到如此完善的程度, 以至那實現了這種倫理標準的人與該標準本身再無區別,那么,這個人就成了標準。這在克里馬庫斯看來, 是“最為奇怪和不能理解的一種說法”。 因此,從人的普遍生存經驗, 人不能理解真會有這種悖謬的情況;然而,在基督教中, 人們卻不能不面對這種不可能的情況:永恒已經完美地實現在一個人的身上,并且因此成為人們所面對的一個標準或典范(Pattern)。轉貼于
從認識論的層面上, 絕對的悖謬同樣由于其間所具有的鴻溝而表現為是人的認識所不能調和的沖突。就上帝進入人類的歷史生存過程,成為一個歷史事件而言, 絕對的悖謬表現在,人們永遠無法從這個歷史事實出發,去認識、理解和說明基督的神性:
一個人能從歷史中認識到任何關于基督的事嗎?不會。為什么?因為一個人根本不可能‘認識’基督。他是一個悖謬,信仰的對象,只為信仰而存在。
這種認識論上的不可能性,可以從幾個方面體現出來。首先, 上帝道成肉身的歷史事件本身就具有特殊性,即從人類世界歷史的眼光看, 這個歷史事件不能用其他具體的歷史事件來給予解釋。相對前后的歷史事件而言,它是絕對新的事件。在這個意義上, 它是“永恒的事實”或“絕對的事實”。 它的意義只能從所謂圣史的角度去理解。其次,耶穌在世上生活的歷史過程,也不能為其同時代的人提供一個更優勢的地位, 讓他們能夠認識到他的神性:
如果我們所涉及到的事實是一個通常的歷史,那么同時代人就有其優勢。...
...但如果我們關注的是一個永恒的事實,那么,每個時代都與之同樣的近。
祁克果常用隱匿性(incognito)來描述耶穌神性的內向性。他常舉的例子就是微服出現的國王,或者穿便衣的警察。 這種內向性不能通過直接的方式被認識到:“如果他相信他的眼睛,他就會被蒙騙,因為上帝不被直接認識。于是,或許他會閉上他的眼睛,但是如果他這樣做,他所擁有的這種同代人的優勢又體現在那里呢?” 最后,基督教自身發展的歷史也不能給人在認識耶穌的神性方面提供更多的幫助。 如果說耶穌的同時代人在認識他的身份上不具優勢的話,同樣,1800 年后的人們也不具有任何的優勢。每一代的人所要面對的是同樣的悖謬。這里,祁克果區別了圣史與俗史:
人們已經完全忘記了基督在地上的生活是圣史(這正是基督教之所是,它完全不同于基督徒的歷史,基督徒的生活、他們的經歷和命運,以及所謂的異端和科學的歷史),它不能與人類的歷史相混淆。
因此,基督教自身發展的歷史,也不能成為人們認識耶穌神性優勢。總之, 如果在基督教的信仰中,關切絕對的悖謬與人對永福的追求相關的話,那么,在認識論的層面上, 克里馬庫斯的問題就如他在《哲學片斷》的扉頁上所發問的:“永恒幸福能夠依賴歷史知識嗎?” 這個問題從一個方面反映出近代以來的認識論所遇到的一個根本問題,這就是用萊布尼茲的話所表達出來的必然的真理與事實的真理之間所可能有的關系。 兩者間的鴻溝被萊辛進一步拉開了,并因此影響到祁克果,以至在《附言》中, 克里馬庫斯用了不少篇幅去談萊辛對兩者區別的強調及其意義。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看到,絕對的悖謬在存在論和認識論這兩個層面上均有其根源,悖謬的兩方之間所存在的鴻溝帶來了人的理智無法調和的矛盾與沖突。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這種矛盾不純粹是形式上的、邏輯上的或詞語上的自我矛盾, 象有些現代的分析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 如果絕對的悖謬僅僅是邏輯上的矛盾,人們就可能會由此推出某些誤解性的結論,例如理智和(對悖謬的)信仰的關系, 就成了一種直接對立的關系,似乎任何在邏輯上無意義的東西,就如個別分析哲學家所批評的, 都有可能成為人去信奉的對象。 實際上,克里馬庫斯在此之前就有針對性地指出:“我們所設定的這個事實[絕對悖謬]以及單個的人與上帝的關系不包含著自我矛盾(self-contradiction),思想是把它作為所有見解中最不能理解的東西來自由地占據自身。” 這里的一個區別就是:思想不能理解的并不等于就是邏輯上毫無意義的。
伊文斯更愿意把這種絕對悖謬所含的沖突稱之為是“顯明的矛盾”(Apparent Contradiction)。 他對這種矛盾的描述是:“顯明的矛盾是指某種有意昧的事實或事件的陳述,由于只能用邏輯上沖突的表述來描述,會以反直觀甚至不可能的方式出現。” 換句話說,這種矛盾本身是有意義的,其語言表述上的沖突反起到了吸引人的思想去關注它的作用,這也就是絕對的悖謬盡管為人所不理解,卻能占據人的心思的一個原因。在祁克果后期的著作中, 這種絕對的悖謬被表述成為“矛盾的標記”( sign of contradiction):轉貼于
矛盾的標記......是這樣一種標記:它在其構成中包含著矛盾,為使‘標記’之名合理,一定存在著能把人注意力吸引到它自身或其矛盾的東西。但矛盾的部分一定不能彼此取消對方,使得這個標記變得毫無意義,成為一個標記的反面,即無條件的遮蔽。
上述的分別或許只是在今天分析哲學的語境中才為人們所關注。實際上,克里馬庫斯提出絕對悖謬的用意,在黑格爾思辯哲學的背景下可能顯明的會更明確一些。一言以蔽之,絕對悖謬是不能為思辯哲學所說的那種辯證方法所“統一”或“綜合”掉的, 因為,正如克里馬庫斯所強調的,它根本就不是人的思想中那種一般與個別的沖突。 在基督教信仰中,這個絕對的悖謬,這個特定的被稱為基督的神-人, 是一個已經進入到歷史中的一個事實,而非理性達到一定階段思辯出來的結果。 克里馬庫斯把基督教所具有的這個絕對的悖謬作為一個重要的范疇,是因為在他看來, 它規定了基督教之為基督教的基本特征。伊文斯把這個絕對悖謬對于基督教的意義歸結為下述的四個方面。
首先,絕對的悖謬保證了基督教所具有的超越性品格(transcendent charac ter)。這種超越性體現在基督教信仰的啟示性。如果這種啟示都是人的理性可以通達的, 如自然神學或某些自由派神學所主張的,那么,這種啟示的源頭就可能被歸之于理性, 而使啟示失去自立性。以絕對悖謬(基督)的方式所傳達的啟示,是對人理性和經驗的中斷, 因此保證了基督教的超越性不至失去。
其次,絕對的悖謬肯定了基督教的生存性品格(existential character)。基督教在其自身的發展中總存在著這樣一種危險的傾向:即成為一種理性思辯的學說。 絕對的悖謬對人理性構成的絕對的挑戰,使得人不再能用理性去面對它, 而只能是一種生存的交往:
一個人無法真實地設定那本質永恒的真理來到這個世界只是因為它需要被一個思辯者所解釋;更好的設定是,由于人們的需要,那本質永恒的真理已經來到了這個世界。人們為什么需要它的原因肯定不能解釋它,因此人們還有事可做,
為的是能在其中生存。
再次,絕對的悖謬保留并強化了人的自我與自由。 對絕對悖謬的接受必須是一種“自己”的決定,并且是一種自由的接受,既不是出于他人,也不是基于證據, 而是在激情的主體性中作出的。我們下節會看到,正是絕對的悖謬保證了單個的人主體性的展開。
最后,絕對的悖謬減緩了人們在理智上的差距, 使得人們在接受信仰方面乃是平等的。如果基督教信仰是能夠完全被理智所解釋的學說,那么, 具有理智天賦的知識人就具有決定性的優勢。而絕對的悖謬使這一點成為不可能。
以上我們是從對一般人們的角度,來看絕對的悖謬對于基督教的意義。其實, 就從生存論上對悖謬的規定來說, 它的基本特點就是:它針對生存中的單個的人而言具有意義。這個特征與本文所討論的主題十分相關。如果換種方式來表達的話, 這個特征就是:絕對悖謬全部豐富的意義只對處于生存處境“局內”的個體顯明出來。 對于“局外”的旁觀者而言,或許它真就是“無意義的”。但對“局內”生存著的單個人而言, 它卻是其所不能擺脫的。在這個意義上,與悖謬的相遇,或者悖謬向個人的顯明, 正表明個人處于生存之中:“悖謬,在其嚴格意義上,就相對生存主體而言, 不是其宗教性關系的短暫形式,而是在其本質上以這樣的事實為前提:即人處于生存中。” 如果不從這種生存的“局內”關系出發,就無法理解絕對悖謬的意義。反之, 如果要去除掉這個悖謬的話,就會把人置于生存之外,使其沒有可能成為個體。
篇6
[關鍵詞]《論語》 理雅各 韋利 安樂哲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9-0053-01
就本文選取的《論語》的三個譯本,分別是英籍傳教士理雅格的譯本,漢學家亞瑟·韋利的譯本,哲學家安樂哲和羅思文的譯本。譯者盡量避免用西方哲學的超越的概念,二元論和中國基督教化與西方的翻譯方法及其目的論來代替中國哲學。時代的跨越,讓我們認識到了《論語》的英語譯本所發展的軌跡,這三個譯本是海外影響很大的經典之作。
一、譯本異化策略對比分析
三個譯本的共同點都是采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共同點中也存在著不同。傳教士的身份,讓理雅格在翻譯《論語》時主要的目的很直接,把中國的哲學思想傳給西方讀者,并且在《論語》的翻譯過程中保留了孔子的中心思想。在翻譯的過程當中,盡量保持作者的原文,保持語言的流暢性。韋利譯本的出現要在理雅格幾十年后,在這段時間,西方讀者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更加的深入,加上英語本身的發展,韋利通過用現代英語將《論語》再次展現在西方人的面前,他的譯本既能夠表達中心思想,又不失掉語言的流暢。安樂哲對于《論語》的英譯,主要是對其中哲學部分的詮釋,他主要提出了《論語》當中哲學思想的異化。
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及語言文化之間轉化的多樣化,包括譯者對原文、原語語法以及對作品當中的文學性的理解,所以譯本中不能避免出現誤讀誤譯。理雅格、韋利、安樂哲他們處于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背景,對《論語》都有著自己不同的闡釋,這當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對原著的誤讀。
(一)文化預設的引發
文化預設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明顯的。文化預設的出現是語言因素和非語言因素產生的。如不同的背景受到不同的文化熏染,這都是譯者很感興趣的。
(二)文化預設的復雜性
因為受到的文化熏染不同,文化的多樣,使其容易在交際中缺乏互相理解,產生文化交流的障礙。文化預設的復雜性的分析,有利于在譯者翻譯的過程中針對不同方面的文化預設,有更充分的文化交流和對原文的誤譯。
二、譯本誤譯的原因探析
在中國,傳統的理念和思想教會我們實踐經驗和整體思考的重要性,并且借助直覺與知覺在認識對方的過程當中從模糊到直接。讓我們能夠清晰地認識到對方內在的本質和規律,從而能夠直接快速地把握整體的感覺。《論語》則是靠直觀的自然知識證明道德規范。
語言是文化,翻譯是文化意義的傳遞。文化預設作為潛在的觀念選擇,影響著譯者對于翻譯文本的解讀。文化預設的不可避免、復雜性和歷史性,導致了翻譯過程中的文化譯讀。
在翻譯《論語》的過程中,相對復雜的是語言的轉換,這種復雜性是導致幾乎任何一個譯本都會出現誤讀和誤譯。處于不同時代、不同背景,譯者不能避免地會出現這些錯誤。
(一)理雅格譯本
1861年,香港出版了理雅格對《論語》的譯本,傳教士的動機和偏見導致了理雅格出現誤讀,誤譯,但他還是試圖努力地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達到客觀和公正。理雅格對《論語》的翻譯大多采用直譯的方法,幾乎是每個字每句話的英譯,努力把握《論語》的中心思想,對于思維形式和句法的結構他都盡量和原文一致。
(二)韋利譯本
韋利譯本,1938年在倫敦開始發行初版,1956年發行的新版。他的譯文當中并沒有附帶中文原有的文章,而是注明了解釋和序言。韋利是一個翻譯家,也是漢學家和文學家,他希望通過翻譯《論語》能夠超越理雅格對于漢宋注疏的依賴,并且他希望傳達《論語》表達的中心思想。韋利翻譯的文章充滿了文學的色彩和現代的氣息,有著英語的語言流暢和語言的優美,能夠做到把古代的漢語轉換到現代的英語。
(三)安哲樂
本著對《論語》哲學的詮釋精神,安樂哲和羅思文也翻譯了《論語》,并且做到了精準、精確,他們翻譯的《論語》對于《論語》本身的文本哲學有著巨大的影響,并且能夠反映出對于早期中國思想有了很深的解讀,包括語言的、動態和關聯上的解讀。這表現了中西方之間的差異、不同。
三、結語
綜上所訴,文化預設使翻譯當中的差異凸顯出來,并以文化預設的溝通互換結束。但是,在翻譯中,最敏感的話題就是以什么樣的文化為主體,翻譯當中的目的和譯者本身主體所存在的差異是受到不同時代和不同背景的影響,并且具有異化策略的特點。理雅格譯本出現的誤解,是因為他受到中西方的互相的交流不深入;韋利對于漢語的特殊句式和語法結構的曲解;安樂哲譯本相對的錯誤減少,基本的根源是中西方的語言文化的巨大差異。
【參考文獻】
[1]理雅格.漢英四書[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
[2]Waley,Arthur.The Analects[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
篇7
關鍵詞:古代典籍,英譯本,譯介學,古代文化
作者:劉石鈺
文學名著的譯介是民族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古代典籍在西方廣泛傳播,文學典籍如《論語》、《道德經》、《孫子兵法》、《史記》、《資治通鑒》、《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是中國文化的寶庫,建構并傳承了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精髓。本文擬以文化為主線,引導讀者深入了解中國的燦爛文化,體會中國文化傳播到英語世界的過程中體現的古代政治、思想、軍事和民俗文化等,同時分析其英譯過程中可能引起的失落和變形等譯介現象。
一、基于文學典籍英譯本的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譯介
《論語》、《史記》、《資治通鑒》等文學典籍中包含深奧的政治文化,但是典籍英譯中存在一些失落和變形。
首先,反映思想政治文化詞匯涵義的失落。比如,《道德經》中的“道”字是道家的哲學核心,其內涵博大精深。但在“道可道,非常道”、“天之道”與“大道”等詞語中,道字被韋利一律譯成“Way”(道路),這種翻譯和理解不僅使這個字所承載的深刻的哲學思想消失殆盡,還造成了語義的失真和讀者理解的誤差。
其次,只在表面含義上翻譯形象比喻詞。《道德經》中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當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韋利把這句話譯成“HeavenandEarthareruthless,TothemtheTenThousandThingsarebutasstrawdogs.Thesagetooisruthless,Tohimthepeoplearebutasstrawdogs.”。這里的“芻狗”本是指用草扎成狗,供祭祀時用。但是譯本中,老子通過“芻狗"所表達的哲學思想蕩然無存,“天地”和“圣人”也變成了殘酷的形象,會讓西方讀者誤以為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是多么的怪異和殘忍。
二、基于文學典籍英譯本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譯介研究
《論語》反映了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倡導的“仁”極富中國思想內涵,它是《論語》道德思想體系的核心。理雅各把“仁”翻譯為“truevirtue,benevolentactions,virtuousmanners,beneficence,perfectvirtue”等,韋利通篇把“仁”譯為“Goodness”或“Good”,辜鴻銘則選擇“beingmoral”、“moralcharacter”或“morallife”。各種翻譯方式各有利弊,但是,由于“仁”的詮釋意義豐富,單一的譯語詞很難真正傳達它的本意,削弱了原語的內涵。這些翻譯中精確的闡釋使“仁”字的不同含義得以呈現,但整體上卻給人一種散落的感覺。
三、基于文學典籍英譯本的中國古代軍事文化譯介研究
《三國演義》是一部和軍事有關的巨著,里面的很多戰役和軍事文化我們都耳熟能詳。第五回“破關兵三英戰呂布”大家都很熟悉,里面有個“英”字,字面意義是“英雄”,指劉、關、張三人,英文中與“英雄”字面意義相對應的詞是"hero",英語"hero"這個詞匯的內涵意義是不包括中國文化中“兄弟”這一層的。因此,羅慕士把“英雄”改譯成了“兄弟”,“三英”譯作“thethreebrothers”,突出表現了原文的內涵意義。
四、基于文學典籍英譯本的中國古代民俗譯介研究
中國古代文學典籍中英譯本中的民俗很多,其中包括物質、社會、精神和語言民俗等。
1.物質民俗。詩經的《七月》中有這樣的句子:“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此處的“三之日,四之日”等是指夏歷的正月和二月,如果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翻譯則不能表達原文要表達的含義,楊憲益,戴乃迭等將其意譯為thefirstmonth和thesecondmonth就比較貼切。
2.社會民俗。《紅樓夢》里元宵節有吃元宵的民俗,如直譯,讀者可能體會不出其深層意蘊。所以,楊氏譯本將“元宵”、“合歡湯”、“如意糕”分別譯為“NewYeardumplings”,而英國的大衛霍克斯將其譯為firstmoondumplings。兩者都兼顧了元宵節在中過民俗文化中的意義。
3.精神民俗。《詩經》中對于愛情、相思等精神民俗很多,比如,《關雎》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里的“窈窕淑女”指的是內心寂靜而善良的女子,楊憲益,戴乃迭等譯者用gentle和graceful比較恰當地表述了其端莊文雅又漂亮的意思。
4.語言民俗。《水滸》中的鄭屠笑道:“卻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說“灑家特的要消遣你!”。這兩句話賽珍珠的翻譯為:AtthisChengTheButcherlaughedandhesaid,"Areyounotmakingajokeofme?”“Ididindeedcometomakeajokeofyou!”ThenLuTayelledathim,"Ho,yourascal,”。譯成英文失去了原文的簡短和氣勢,無法淋漓盡致地表達出魯達的言語粗獷。
篇8
關鍵詞:《論語》 “仁” 三維轉換
中圖分類號:H31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7)12-0025-01
一、《論語》核心思想
《論語》作為儒家經典之作,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與思想,代表著中國古典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智慧的結晶。《論語》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在《論語》中具有靈魂性意義,使其成為儒家道德倫理的一個重要體系,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價值觀;這不僅是中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亦是炎黃子孫思想傳統的一扇窗。《論語》核心思想“仁”在英文三譯本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理雅各是系統研究中國古代經典的學者第一人,其分析了孔子《論語》的核心思想及其在中國的巨大影響,使西方世界了解了中華人民的傳統及思想核心價值觀。亞瑟?韋利是理雅各之后一位偉大的漢學家,其譯著多次再版,在國內外享有良好的聲譽,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哲學家安樂哲和羅思文掀起第三波譯儒家《論語》經典狂潮,其1998年出版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槲鞣降姆譯展現出新的維度,向讀者們展示《論語》核心思想體系及“兼容并蓄”的哲學思想。
二、生態翻譯學理論下《論語》核心思想“仁”的體現
生態翻譯學理論中指出翻譯是原文、讀者、作者、委托者、譯者背景等因素互聯互動的整體,是一種全新的翻譯理論。《論語》作為代表中國儒家學說典籍,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事跡和對話,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經濟、政治和道德倫理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三譯本《論語》核心思想“仁”得到了充分體現。例如:“ No sooner do I desire it than it is here”。其次,《論語》核心思想“仁”的情感基礎――“孝悌”和社會價值觀得以展現。例如:“the people will be fraternal to their brothers”。總之,生態翻譯理論視角下《論語》三譯本在多方面充分體現了“仁”的核心思想,為翻譯學及西方文化思想起到了積極促進的作用。
三、生態翻譯學視角下《論語》核心思想“三維”適應性轉換
(一)《論語》核心思想“仁”語言維的適應性轉換
《論語》乃儒家之經典,集孔子思想之大成。例如:《論語?雍也》中“觚不觚,觚哉!觚哉!”經典語句。譯文:Confucius was once heard to exclaim,“A goblet is no globular――why call it a goblet;why call it a goblet?”譯文中運用了兩個十分巧妙的詞匯globular和goblet,其中采用“頭韻”的修辭手法,譯者運用了疑問句語氣,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孔子的感慨與無奈。此例說明譯本對核心思想及文化底蘊在語言維轉換的完整性。例如: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論語?憲問》譯文:The Master say: “a superior man aims high,while an ordinary man directs downward”。此例中經典文言句的語言維的適應性轉換,完全能夠運用漢語語言表達習慣,深刻地解釋了漢語文言句的深刻內涵及其哲理性,不僅做到適應源語與目的語的特點及不同之處,更體現出《論語》中“仁”的核心思想。可以說:在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中不僅體現了《論語》核心思想,更以嶄新的視角賦予譯本語言的生命力。
(二)《論語》核心思想“仁”文化維的適應性轉換
《論語》是中國儒學經典代表,其大量詞匯覆蓋了豐富的中華文化,展現了中華民族文化內涵。例如: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譯文:The Master said: “The moral influence of the superior is like the wind while the moral inclination of the inferior is like grass. When the wind blows, the grass will bend”。此句在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運用上較為適當,不僅表現了儒家經典《論語》對“君子”道德和責任感的贊賞,也體現了中華文化意味深長的價值觀念。
(三)《論語》核心思想“仁”交際維的適應性轉換
《論語》三譯本在交際維適應的轉換中充分核心思想“仁”。例如: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論語?子路》 譯文:If he loves credibility, the people cannot but show sincerity.If he loves righteousness, the people cannot but show their submission. If the monarch loves the rules of propriety, the people cannot but show respect。可見,在交際維視角中,句子采用歸化性的翻譯方法,使西方讀者易于理解。
綜上所述:《論語》核心思想“仁”在生態翻譯視角下,三譯本通過“三維”理論轉換采取了不同翻譯策略對源語信息進行處理,使中華儒家文化的精髓被世界讀者深刻理解,并向世界傳遞中華民族儒家文化的哲理和寓意,對讀者了解、喜歡、傳遞中國文化具有深遠意義。
參考文獻:
[1]胡庚生.翻譯適應選擇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胡庚生.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J].中國翻譯,2011.
篇9
關鍵詞:孔子;音樂美學;想探究
音樂美學是以研究音樂藝術的美學規律為宗旨的基礎性理論學科。同時它也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學科,首先它是美學、藝術哲學的一個分支,又是音樂學的一個部門。孔子認為藝術在社會中產生積極作用,并提出一系列美學范疇和美學命題。
1 關于音樂美學的認識
如果把音樂美學看作一門對于音樂藝術的認識和思考的學問,亦即音樂思想,那么,它是自古就有的。它的歷史和音樂自身的歷史一樣久遠,因為人們在創造音樂的同時,也就開始了對它的思考。在我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但是,把它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看,并且稱之為音樂美學只不過近一、二百年的事情。音樂美學是美學――藝術哲學的一個分支,同時又是音樂學的一個部門,是以研究音樂藝術的美學規律為宗旨的一門基礎性理論學科。它特別把音樂的本質與特征、音樂的形式與內容、音樂的創作、表演與欣賞、音樂的功能、音樂的美與審美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
2 孔子對音樂的審美理想認同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禮樂教育家,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對音樂的審美理想的思想核心是“仁”。“仁”就是要把遵守奴隸制等級制度的“禮”作為內心自覺的要求,即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仁”在孔子那里,具有倫理學的意義。它首先體現在與“禮”、“樂”的關系中。“仁而不仁如禮何”,“ 仁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以“仁”的實現為“禮”、“樂”實現的前提,孔子說:“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就是說,君子中可以出現“不仁者”,而小人中決不會出現“仁者”。這樣說,“仁”也就成為一種天賦的道德屬性。孔子十分重視審美和藝術的“仁”用,孔子認為:審美和藝術對精神的影響深刻有力,所以審美和藝術在人們達到“仁”的精神境界而進行的主觀修養中就能起到一種特殊的作用。孔子又說:“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仁”或“不仁” 取決于個人的主觀愿望和自身的修養。
孔子是非常重視藝術和審美的作用。他認為:藝術和審美對于人的精神影響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在人們達到“仁”的境界里,藝術和審美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知者。”(《論語?雍也》)也就是說,僅僅認識到什么是“仁”愛好什么是“仁”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對“仁”產生情感和喜悅,從中得到一種審美的享受,要以審美的境界超越精神的境界。后來孟子也接受了這一思想。因此有了“仁言不如人聲之入之深也”的相同感慨。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與樂。”
孔子的審美態度“和”,“和”的這個概念其實在孔子之前就已經有了,孔子繼承了春秋時期“和”的思想并將其發揚。孔子在音樂審美中講的“和”一方面是對前人諧和的繼承和發展,另一方面也同他的哲學思想上的主張“和而不同”,倫理學思想上主張的“禮之用、和為貴、中和且平”。 以及品評人物時的“過猶不及”思想相一致。可見孔子的在藝術審美與人生實踐中講的“和”,是符合其“中庸”哲學思想和觀念的,具有“中和”的性質。這一思想在音樂審美上的主張就是要求音樂的表現,“樂而不,哀而不傷。”(《論語?八佾 》)他要求音樂的情感表現要有節制適度不過分,這是音樂的內在情感與外在的表現都保持在“中和”的狀態。他評價詩樂《關雎》“樂而不,哀而不傷”,與他對當時的新聲“鄭衛”之音的批評和強烈的指責(“鄭聲”“放鄭聲”)形成鮮明的對比。反映孔子音樂思想中,崇雅抑俗的審美態度。孔子的這種思想被荀子和《樂記》繼承和發展,對后世影響極大。很多藝術家、文學家的審美趣味、審美理想很多都是以“和”之為核心的。
“移風抑俗,莫善于民”。孔子之所以把“《韶》”樂、“《武》”樂提到“為邦”的高度,是由于充分并高度到認識音樂的社會功能。孔子聽了《韶》樂后,三月不知肉味。這說明藝術給予人的美感是一種精神愉悅,它不同于單純的生理。在音樂活動中,孔子也有“憤”的一面,如:“季氏八佾舞于庭”的音樂行為,孔子就表達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強烈的情感態度。
3 從孔子音樂美學思想看從事音樂教育的意義
孔子的樂教思想以及美育的實踐行為,都表現在《論語》、《史記》等相關篇章中。孔子辦私學,是以禮樂為教學內容的主要部分。孔子的教育內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與系統性。以人的全面發展和培養,構成其樂教的目標和任務。
孔子樂教的道德內容體現在對教育的對象上:“有教無類”,其本質是在教育的對象上,無有貴族與平民、華夏與華妻之分,在封建社會制度上的教育思想能與現代文明的教育思想相吻合,體現了孔子思想的進步性和超越性。“有教無類”的思想體現了孔子從事樂教的道德觀念,擴大了社會受教育面,變無教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孔子的樂教實踐中,他將“行”作為學習的延續,重視知的一致,這一思想在儒家以后得到繼承和發展《中庸》一書以孔子的名義,將孔子的“學”(“學而時習之”)、“思”(“學而不思則罔”)、“習”“行”(“子以四教:義、行、忠、信。”)發展為:“博學之、審向之、慎思之、明辨之、等行之”這五個階段。從孔子的樂教活動中看,他要求學生學習詩樂的目的,就是為了立人行事,能夠學有所用。據論語記載: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在孔子的樂教思想中,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無以對;不學《詩》,無以行。總之,不學《詩》,難以立人行事。春秋時期在社會交際場合中不會吟“詩”是難以進行交流的。孔子講的“興、觀、群、怨”中的群,就是立足于社會群體人際間的交流。當然,孔子最希望的,還是樂教在社會治理中的實現。
參考文獻:
[1] 張前,王次.音樂美學[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0.
[2] 羅小平,修海林.音樂美學通史[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0:59.
[3] 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M].上海:上海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388.
篇10
關鍵詞:儒學;社會思想:社會學
近年來社會各界普遍開始重新關注曾在中國占有顯學地位的儒家思想與學說。儒家學說代表人物眾多,內容紛繁蕪雜,很難用較為簡短的語言概括其全部內容及精神。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昭示著儒學有著其他學說難以企及的巨大彈性,因此今人對其的評價亦可有廣闊的操作空間。
儒學包含豐富的社會思想,大陸學界對儒學的認識中,亦有從構建中國學術譜系的企劃出發,將儒學中某些因素,作為西方社會科學中某些學科的中國樣本這一趨勢。例如,將儒學中的統治技術和國家治理思想視為中國古代的政治學,將儒學中的社會思想與社會學說視為中國古代的社會學(彭立榮,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看待東西方不同發展路徑條件下知識與學說的形成與性質。
一、關于社會學發生學意義的不同認識
社會學作為關于社會運行和發展的專門知識的理論體系出現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種種社會問題促使社會思想家和哲學家進行深入思考:同時,社會學的出現更是人類對社會及其本質的認識逐步深化的結果。在其正式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之前,它的許多思想觀點一直被包含在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等學說、理論之中,以社會哲學的形式存在(賈春增,2000)。
在西方,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出現的社會學經歷了從社會哲學到社會學的漫長轉變過程。古希臘哲學中的社會思想以及文藝復興以來的社會哲學思想,對社會學的逐漸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論積淀作用。特別是文藝復興以來自然科學的發展對社會學的產生同樣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學思想(從思辨的層次)上,通過哲學思想又直接影響到社會科學。因此社會學得以產生和發展,乃是長期存在的各種社會哲學思想演化的結果。
一些學者認為上述解釋固然合理,但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各種文化體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識與學科發展路徑。人類對自身群體進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種類型的社會思想與社會學說。就中國情況而言,由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包含著對人類社會和人際關系等內容的研究;這一類有關人類社會的理論與學說,不可否認其具有社會學性質。因此,儒家學說(或稱儒文化)就是一種以文化的形態出現,以規范人在社會中的行為為根本特征和對社會進行整合、治理為根本任務的關于社會的理論與學說,即為古代中國的社會學。
持有上述觀點的學者認為,古代中國無社會、社會學之名,且對社會事實的研究與討論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細致分工的學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及其繼承者使用今天的學術概念,更無法企望其思想與學說完全符合近代學術規范i今人對此類歷史上的思想、學說與理論的審視與界定,不應僅從其具有的概念與范疇出發,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對象、研究內容,檢討其理論體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論深度與社會功能處于何等程度。因此對儒家學說而言,審視其蘊含的具體內容,是對其進行定位與“正名”先決條件。
二、儒家學說的兩大主題
在上述觀點的支持下,不妨從儒家思想的主題入手,梳理其中蘊含的社會學意義。儒家學說的核心為兩大主題,即“禮”與“仁”,以此為核心儒家學說首先具有突出的倫理社會學性質與功能,同時兼具政治社會學意義。
作為一種規范系統,禮的形成適應了社會生活的客觀需要,孔子認為禮對維護傳統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起到正面的促進作用故對其極為重視(苗潤田,2002)。《廣雅》;“祉,髓也”,禮具有使人彼此結為一體的功能(王處輝,2002),成為維系社會的紐帶。與此相關,儒家學說對家庭的關注亦是由于對禮的維護,體現了其在家庭社會學范疇的理論已處于高度系統化程度,這種角色要求實際上同樣是一種具有強大約束力的社會規范。
推而廣之,家國同構。治家與治國被聯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認為在家庭倫理問題上持正確態度才具有參與政治的資格,主張從政者首先應當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榮,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對統治類型的期望和韋伯的“個人魅力統治”有著驚人相似。這種統治的基礎是統治者的個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現在倫理、英雄行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統治者所具有超凡的個人魅力與才能中,倫理道德標準是關鍵因素,“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篇)。
在闡發“禮”主題的同時孔子提出“仁”主題,為禮畫龍點睛。“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篇)。孔子認為仁是禮的內心,禮是仁的表達形式;仁是內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達,于是有禮樂(王處輝,2002)。在處理人際關系方面,仁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互敬的交往倫理;同時,仁應當成為為人處世的準則,是“君子”必須具備的品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論語》“里仁”篇)
推及政治領域,孔子的“仁”被發展為孟子的“仁政”,涉及統治者的政治合法性來源。先秦諸子學說中,儒家最關注政治合法性問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篇)。馮友蘭指出:“蓋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種不同的政治。中國后來之政治哲學,皆將政治分為此二種。王者之一切制作設施,均系為民,故民皆悅而從之:霸者則惟以武力征服人強使從己。”(馮友蘭,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上”篇)
綜上所述,儒家思想的兩大主題具有豐富的社會學思想,其中所闡發的一系列分析與解釋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路徑。
三、儒學社會思想、儒學社會學思想,古代中國社會學三者之間的關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會思想占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會學教學的主干課程——中國社會思想史中,這一部分會被著重討論。儒家思想存在著近代社會學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內容與理論假設,那么我們是否可以據此認為,儒家學說就是古代中國的社會學呢?筆者個人認為在西方學術規范主導的當代學術領域,我們不應該輕易下這樣的結論。近代科學起源于西方,包括社會學在內的一系列社會科學,在其漫長的學科發展歷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嚴謹的規范體系,這與東方學界長期以來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維、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學方式有著本質的不同,二者存在著體系的差異,因此用西方近代學術體系中的語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國的思想與學說,未嘗不具枘鑿之嫌。
在社會學中國化的過程中,汲取中國古代社會思想中的因素并賦予其社會學意義,是當代社會學工作者必須面對的課題;同時,在梳理中國古代社會思想時,采取科學、嚴謹的態度更不容忽視。正如馮友蘭先生認為,中國
古代有哲學思想而無哲學;我們或可認為,儒家學說中包含的社會思想,有些已具備近代學科意義上社會學思想的雛形,但我們不能武斷地承認儒家學說中的社會思想就是古代中國的社會學。
參考文獻:
[1]王處輝,《中國社會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彭立榮《儒文化社會學》,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潤田,《解構與傳承一一孔子、儒學及其現代價值研究》,齊魯書社,2002
[4]賈春增,《外國社會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5]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