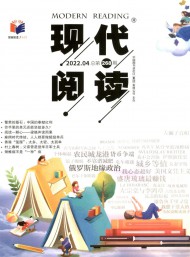對文化人類學的看法范文
時間:2023-12-18 17:41:15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文化人類學的看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薩摩亞人的成年》;青春期
一、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的緣起
20世紀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文化與人格學派的杰出代表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出生于中產階級家庭,父母均有良好的學術修養。1923年,米德畢業于巴納德學院,取得英語和哲學雙學士學位。隨后米德轉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心理學碩士學位,期間一次偶然的機會,她有幸結識了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被人類學研究深深吸引,并拜入博厄斯門下從事人類學研究。米德一生共千余篇,出版專著26本,堪稱著作等身。其中,通過數次對南部海岸七處地點的田野調查而寫成的《來自南海》三部曲,即《薩摩亞人的成年》、《新幾內亞兒童的成長》和《三個原始部落的性與氣質》更是聞名遐邇。1979年逝世的米德被追授總統自由勛章。
1910年前后,以高爾頓為代表的生物學家和以博厄斯為代表的人類學家之間,在西方科學界掀起了一場有關人類行為成因究竟是“先天”還是“后天”的激烈爭論。以高爾頓為首的遺傳派認為,“遺傳的力量在產生人的差異方面不僅遠比任何單個的環境因素強大的多,而且比全部環境因素加在一起還要強大”。以博厄斯為首的人類學家激烈地抨擊前者的主張過于極端,博厄斯明確提出了文化決定論,認為人類的行為模式,不是由其生物特征決定,他們所處的文化背景,所處社會的刺激比生物機制更為有效,人類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環境的產物。
當時美國青年騷動不安的狀況已經引起廣泛的關注,力求找到合理的解釋。遺傳派與人類學派對于青春期的問題各執己見。前者認為青春期是由生理變化造成的,兒童是遺傳傾向的嚴格綜合體;后者認為是后天的文化和教育形成了青春期的難題。為了證明本學派的觀點,1925年,24歲的米德前往薩摩亞群島對當地的土著部落進行了為期9個月的田野調查,旨在探尋存在于美國青少年之中的青春期危機在原始文化中是否也存在,為博厄斯的文化決定論提供實證依據。
二、《薩摩亞人的成年》的主要內容
《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是米德于1925年在美屬西薩摩亞進行為期九個月的田野調查后寫成的,米德通過對島上68位薩摩亞少女進行研究,意圖弄清青春期危機在原始文化中是否會呈現出與美國社會全然不同的景象。米德認為薩摩亞的少女在青春期并未表現出西方文明社會中的緊張與焦慮等不良情緒。
米德認為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如下幾點:
首先,米德將薩摩亞的生活描寫成具有“普遍的隨和性,在薩摩亞這塊土地上,沒有人孤注一擲,沒有人蒙受信仰的災難,也沒有人為了特別的目的而殊死拼搏。……任何人的生活的步履都不會被別人所催促不停,也沒有人因其身心發展緩慢而受到嚴厲的責罰。相反,那些富有天資、早熟早慧的人卻每每被扼止,以期他們當中最為遲鈍緩慢的人能夠趕上他們”。薩摩亞人的語言中,沒有固定的比較級,人們對于他人的評價非常小心謹慎,最令同齡人厭惡的特征反而是“自命不凡”。
其次,薩摩亞人缺乏專門化的感情。米德發現,薩摩亞的孩子們并不固定地居住于父母處,如果他們不愿意與父母同住,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選擇自己想要居住的地方。而那里的長輩也會照料他們,對所有孩子平等相待,同時需要他們幫助勞動。薩摩亞人尤其缺乏的是專門化的良性感情,這主要是由于薩摩亞的戶中成分復雜。“薩摩亞人的忠貞是以天計算的,最多按周計算,他們對終身相愛、堅貞不渝的愛情頗不以為然,甚至奚落嘲笑。”
再次,薩摩亞人對性以及生死知識的教育方式與我們截然不同。在薩摩亞,人們絲毫不會禁止孩子們接觸任何關于出生與死亡的知識。薩摩亞的孩子們見過出生和死亡,見過流產與尸體,生死之事在他們的早年生活中被剝奪了神秘性。薩摩亞的青年在性方面有比較大的自由,不禁止婚前。姑娘的第一個情人,多數情況下會是年紀較大的男性,比如鰥夫或離了婚的男性。“未婚男女之間的關系一般有三種類型:一種是‘相會在棕櫚樹下’的暗地交往,一種是‘阿瓦加’,即公開的私奔。還有一種儀式隆重的求婚。”女的住所僅以蚊帳遮擋,棕櫚叢的幽會等情形使孩子們很容易目睹與性有關的場景。如此他們對的認識比較成熟,不會有文明社會的青少年普遍有的騷動和壓力。
第四,在薩摩亞人的生活中,工作和娛樂并非完全獨立。在薩摩亞,舞蹈是男女老幼都能參加的活動。在舞會中,大人們鼓勵孩子參與,兒童從小型的、非正式的舞會中學會跳舞。大人對跳得好的孩子會給予肯定和鼓勵,長輩們的訓誡會由“坐好,別胡鬧!”變為“站起來,盡情地跳吧!”。因此,舞會對薩摩亞人來說是對壓力的一種調節方式。孩子們是舞會活動的中心,在其中他們得以充分展現自己的天賦和個性,而不再如日常生活中那樣受到長輩的支配。同時,這樣子的舞會也降低了青少年面對公眾的羞怯感。而且,村中有生理缺陷的孩子并不會在舞會中受到歧視,一個駝背的男孩子可以扮演海龜,一位患了白化病的小姑娘會因為舞跳得好而引來人們的陣陣喝彩。
三、國內外研究綜述
《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出版后受到了廣泛的關注,被譯成16種語言,發行量達數百萬冊,成為很多大學生學習人類學的必讀書目,是文化人類學文庫中的一顆明珠,對文化人類學與心理學的發展起到了深遠的影響。
對于《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人們對《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推進人類學發展的學術價值的評價。蔣強在《敢于挑戰權威的杰出女性――瑪格麗特?米德》一文中,認為米德對于薩摩亞少女的青春期研究證偽了生物決定論。由于米德認為在薩摩亞,處于青春期的少女并沒有經歷生物決定論者所認為的必然經歷的青春期的苦惱,因而將薩摩亞社會作為青春期危機的反例呈現給世人。徐黎麗,石在《論米德對文化人類學的貢獻》一文中,作者認為米德對文化人類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通過搜集大量不同文化背景下兒童生理、心理發展的資料,來研究文化和教育對兒童成年后人格形成的影響;證實了文化決定論;豐富發展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第二,對《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的質疑。雖然《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自出版以來一直被認為是一部人類學的經典著作,書中所認為的青春期的變化并非只受生物性控制,而且還受文化制約的觀點在很長時間受到人們的追捧。然而,澳大利亞學者弗里曼卻對這本書嚴厲批評,弗里曼在薩摩亞有著同樣豐富的田野工作經驗,對米德在薩摩亞所做的田野調查提出了質疑。莊孔韶《回訪的非人類學視角和人類學傳統――回訪和人類學再研究的意義之一》一文中提到,弗里曼認為米德的薩摩亞語言只學過一個半月,不足以完成與當地人流暢而深入的溝通,而米德女性的身份,也決定了她不可能參與薩摩亞社會的一些重要場合。米德的訪談對象更多的尚未度過青春期,不能當做從青春期向成年轉變的樣本。最重要的是,弗里曼對米德所做田野工作的結果也產生懷疑。弗里曼認為在薩摩亞盡管有私下的,但也存在公共道德的約束。烏熱爾圖在《不可剝奪的自我闡釋權》一文中著重對比了米德和弗里曼對于薩摩亞的研究。根據弗里曼的考證,米德前往薩摩亞前的準備工作比較倉促,在調查過程中米德沒有住在薩摩亞人的社區中而是選擇與島上的美國移民居住在一起。而弗里曼本人自稱深諳薩摩亞語言,并參與政治活動,因此田野調查工作深于米德。甚至一些知曉米德著作的薩摩亞人要求弗里曼對米德論證的不實之處予以更正。與米德不同的是,弗里曼認為薩摩亞人對童貞的崇拜到了嚴苛的地步,他們的社會充滿森嚴的等級制度,薩摩亞民族是一個剛毅且刻板的民族。作者認為薩摩亞社會處于早期的社會形態,是以“聽覺文化”為特征的民族,米德對薩摩亞人的理解是對他們自我闡釋權的壓抑。隨著薩摩亞社會的進步,自我闡釋的愿望將會一步步實現。
第三,米德對薩摩亞人的田野調查所引發的對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反思。20世紀世界急劇變化,時隔數十年后重訪田野點的情況是否大不相同,是人類學的興趣點之一,回訪也成為人類學的傳統。同樣是在《回訪的非人類學視角和人類學傳統――回訪和人類學再研究的意義之一》一文中,莊孔韶指出,后者的回訪是對前者研究中失誤的訂正,數十年后跨時空的回訪也可以形成歷時性的研究。徐杰舜《人類學洞察性簡論》一文,認為米德對不同于西方文明社會的調查是對于“他者”包括不同于自己的“異文化”的探尋,敢于跳出固有的文化的束縛,站在文化相對論的立場,用當地人的眼光體會他們的所做所想。另外,米德通過薩摩亞人青春期與美國青春期少年的對比,實質上是通過“異文化”來反思本土文化,將“他者”作為參照的鏡子。《人類學再研究及其方法論意義》一文中,作者蘭林友認為人類學再研究取向很有可能成為中國社會人類學研究的新范式。人類學的再研究取向具有多方面的學術意義,已有的民族志文本可以成為后續研究者的起點,成為可以借鑒的“巨人的肩膀”,民族志作為寶貴的學術遺產,可以讓我們跨越時空獲得新知,又有所啟迪增加研究視角。另外這種取向具有文化變遷研究的重要視角。
四、如何“選擇”――《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究竟留給我們什么
米德將全書的落腳點放在了為選擇而教育上,認為當代美國社會的少年在經歷青春期時之所以面臨緊張與焦慮是源于他們所處的文化給他們的壓力,他們面對宗教、信仰、價值觀等不同的選擇,因此作者指出“選擇”的重要作用,認為美國社會的青少年面臨來自眾多群體的不同準則,而不像薩摩亞人那樣生活環境單純而隨性。然而我認為,薩摩亞人隨性而溫和,并不代表他們不會面對選擇。比如書中提到,薩摩亞的青少年會自己選擇愿意居住的地方,可能是某個親戚家,每個家庭都像一個小型社會,有著不同的文化氛圍。孩子們面對不同的家庭環境也就面對著不同的選擇,但我們看到他們生活的很好。在我們的社會中,如果青少年更換居住家庭,會產生不適必然在情理之中。所以我認為重要的不是是否會面對選擇,而是如何處理選擇。
我們的社會發展到今天,代際之間已經無法保持這種單一性,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何況現在也有很多前輩人需要向后輩人學習的地方。因此我們無法選擇讓我們的社會回到生活單純的年代,我們所能做的是長輩在現存的傳承中引導青少年。就社會大環境來說,選擇多樣性是時代進步的標志,而為青少年確立準則卻并非不可為之。就我國來說,主流思想存在,大部分青少年需要接受學校教育,這就為傳播主流思想奠定了條件。因此,在合適的地點有選擇的宣揚青少年成長需要的準則,不懼怕選擇,而是引導青少年選擇,是幫助他們渡過青春期的有效途徑,也是《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帶給筆者的思考。
參考文獻
[1] 鄭琪.瑪格麗特?米德的文化與人格思想探析[D].黑龍江大學,2012.
[2] 德里克?弗里曼.李傳家等譯.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M].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3
[3] 瑪格麗特?米德,周曉紅等譯.薩摩亞人的成年[M].商務印書館出版社,2008:157.
[4] 蔣強.敢于挑戰權威的杰出女性――瑪格麗特?米德[J].大眾心理學,2014(1).
[5] 徐黎麗,石.論米德對文化人類學的貢獻[J].思想戰線,2005(3).
[6] 莊孔韶.回訪的非人類學視角和人類學傳統――回訪和人類學再研究的意義之一[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2004(1).
[7] 烏熱爾圖.不可剝奪的自我闡釋權[J].讀書,1997(2).
篇2
:哲學家黑格爾說:凡熟知的概念,往往是無知的。文化這個概念也一樣,東西方學者對文化的界定和看法各有側重,不同階層對文化的價值和把握也有差別。
顧久:確實是這樣。文化像一座大山,“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作為山中的人,無論是中西方,還是具體到我們的黨、政、士、民等各階層,對文化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把握。
我們從《現代漢語詞典》對文化的定義來看:“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這里強調是人而非上帝創造了文化。這個定義是西方人的視角。中國最早將“文”“化”兩個字連在一起的,是西漢的劉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 “文化”與“武力”相對,這里指用文明化育人。這是中國人的視角。
西方人強調“人類創造文化”,是因為他們有“人間”與“天國”兩個世界,該概念強調是人而非上帝創造了文化。中國人強調“用文明化育人”,是因為我們只有一個人間的世界,更關注人間的秩序是否和諧,如何和諧。其實,今天我們可以把西方“人創文”和中國“文化人”結合為一,像一個硬幣的兩個面,文化也有兩個面。
我們黨、政、士、民等各階層對文化的功能認識和看法也各有不同。黨關注的文化主要是主流意識形態的;政府(文化主管部門)看文化,主要體現在社會上那些既有教化功能又有娛樂功能的節點,比如戲劇、電影、圖書等。以前,把這些也看成意識形態,但改革開放后,發現娛樂功能的東西能賺錢,所以推向市場,叫“文化產業”,教化功能的東西要掌握好,叫“文化事業”;把產業和事業都做好,是政府關注的熱點。文化人(也就是士)對文化的看法和使命主要是文化藝術作品的創作和批評、學術的傳承和研究等等。老百姓說一個讀書人“有文化”,說自己“沒文化”,主要指通過文字吸取書本智慧的能力。總之,“文化”這個詞,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往往是多義的、復雜的、邊界不太清晰的。
:如何把西方視角的“人創文”和中國視角的“文化人”結合起來認識文化?
顧久:人是生物,要生存,就需要不斷地新陳代謝,還需要繁殖延續,所以有食、色的本能(中國古代稱“飲食男女”,馬克思、恩格斯叫“兩種生產”)。但人滿足食、色的方式,與一般動物大不一樣。這個“不一樣”不簡單,就是人類自己的“人文世界”(文化人類學家往往把“文化”解釋成“人文世界”)。
我認為,人類至少創造了四個大的子系統:上面提到的“謀生謀衍”的系統,以滿足生物性的需要。形成群體之后,更有意無意地創造了“人際秩序”的系統、“日常行為秩序”的系統和“心靈秩序”的系統,以滿足社會的、習俗的、精神的需要。這四個子系統相互聯結、影響、支撐著,共同形成一個更大的人文世界,更大的生存系統。
這四個子系統就像四根大繩,共同織出一張無所不及、堅韌異常又看不見摸不著的“大網”,使人們都成長在、生活在、痛苦在、陶醉在其中,并不知不覺、自然、文明地形成共同的思想行為。這個過程,并非武力強迫而就,而是文明化育而成,所以中國人稱它叫“文化”。
總之,人類為了生存,一方面,必須“創造”出可以生存的謀生手段、人際關系、行為方式、精神世界等東西(西方人的視角);另一方面,人類又被自己創造的謀生、人際、行為、精神等所“化育”(中國人的視角)。所以,文化是某人群的生存大系統、人文世界,其間包含著謀生謀衍、人際秩序、行為秩序和心靈秩序等子系統。
實現中國夢需要文化自覺
:人類創造了文化,文化又影響和改變著人類的生活。人們有時會困惑。比如,20世紀前半葉中國思想的主流圍繞著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而發展。面對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當時的思想界在思考現代中國人究竟是繼續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還是必須向西方文化轉向。針對這樣的問題,先生經過長期的思考,1997年提出“文化自覺”概念,他說這代表了當時中國思想界對經濟全球化的反應。“文化自覺”對于我們今天實現中國夢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顧久:先生在1997年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二屆社會學人類學高級研討班的閉幕式上說:“‘文化’在哪里?就在集體生活的人的行為和意識中。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就應當深入到中國的文化中和中國人的生活中去認識自己文化的歷史和現狀。人們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沒有用科學的態度去體會、去認識、去解釋,那是不自覺的文化。”
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進程中,步履維艱。怎樣才能使中國文化的發展擺脫困境,適應于時代潮流?費老有一種宏大的歷史感和憂患感,他感到我們正身處一個大時代,痛感我們卻看不透、跟不上、對不起它(他經常說我們“‘由之’而不‘知之’”)。當今國際、國內形勢都提出很多尖銳的生存問題,他提出認識自己,認清別人,看清自身過去、今天和未來,也看清別人的過去、今天和未來,取長補短,贊美別人、學習別人,但自主前行,乃至讓中華文化引領世界。所以他的理想是要培育“中國21世紀的孔夫子”來引領世界,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覺。文化自覺對人類認識各民族的文化從哪里來的、怎樣形成的、它的實質是什么、它將把人類帶到哪里去都具有指導意義。
中國人怎樣擁有自己的民族話語、自己的道路和自信?怎樣做到內振人心、外樹形象,明確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需要文化自覺。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覺才能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建立起中華文化的自信。認清自身文化的價值,才能找準自己的文化定位和出路,不斷提升我們的文化軟實力,從而進一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對貴州多彩文化的自覺認識
:您認為貴州文化自覺自信的出發點在哪里?
顧久:貴州人有足夠的理由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但首先要自覺認識到貴州文化多彩復雜的面貌,也正是這些多彩的文化面貌給我們打下文化自信的根基。
認識貴州人文地理多彩:貴州明代才建省,歷史上只有境內的、且蘭和夜郎等古國,或隸屬湖廣、云南、巴、蜀等省份,沒有一個長期、完整的歷史地域,也就沒有相對獨立完整的文化;認識自然地理多彩:貴州境內有丘陵、壩子、峒溪、山原,且處低緯山區,地勢高差懸殊,氣候垂直分布差異大,呈立體氣候;認識民族成分多彩:既有歷史相對悠久的百濮民族,也有稍后進入的苗蠻、氐羌、百越等民族,還有后來大量遷移而來的漢族;認識謀生方式多彩:游耕、定耕、畜牧、農業在這里并存;認識人間秩序制度多彩:既有早期父系血緣社會的“油鍋”制,也有階級社會性質的“則溪”制和漢族的封建制;認識日常生活習俗多彩:比如即便是同為苗族,也依習俗分為長裙苗、短裙苗、黑苗、白苗等等;認識精神生活多彩:既有人身居廟堂,影響中原,也有人耕作田野,足不出鄉。
:如何將貴州的文化建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和弘揚結合起來?
顧久:說:“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這就說清了培育核心價值觀與文化建設,特別是與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傳統根柢與現代花果的關系。他還說:中華文化的根在農耕文明,農耕文明中的精華不僅不能拋棄,而且要傳承與弘揚。
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們評價社會的標準是經濟至上論,視農耕文明為落后。貴州山隔水阻,是破碎的山地小農業,但保存了各種活態的農耕文明系統。
于丹老師曾感嘆,貴州應該打造農耕文明活態博物館,太美了!貴州人看到自己的大美,有自信。當然,我們更要創新性轉換、創新性發展傳統的農耕文明。怎樣創新?首先,要改善我們的謀生謀衍系統,向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城鎮化學習,這是省委、省政府正帶領全省人民致力的任務。其次,人際秩序要跟上中央提出的“治理體系”,變傳統農業的威權型家長制,為多元社會里各個成員共建、共享、共榮的公共生活。再次,要傳承并創新我們的日常行為系統(習俗文化)。以上三個子系統,共同支撐起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新心靈秩序。只有這樣,才能把多彩的貴州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起來。
:面對貴州豐富多彩的文化形態,我們怎樣去把握它的底色?
顧久:這就要抓住多彩中的兩大底色:
一類是代表著貴州的精英文化。他們類似于儒家,積極融入中原文化,走出大山,擔當天下。例如智殺安德海的丁葆楨,傳承中華文化的鄭珍、莫友芝和黎庶昌,挺身參與“公車上書”的貴州士子們,在抗日戰場上血戰淞滬、威鎮松山的貴州軍士群體等。其可貴處不僅在于展現了貴州人勇猛精進的一面,更在于他們使貴州人有了共同國家、共同民族的認同感,將貴州地域文化與中華大文化融為一體。
篇3
【關鍵詞】 互文性 跨文化
1. 文化、語言、翻譯和互文性
隨著社會和科學的發展,對于翻譯的研究無論是在橫向還是在縱向都進一步的擴大了。在這一領域里,逐漸有人借鑒了其他的學科,產生了多元化的局面和許多新的概念。而“互文性”就是在這多元化的局面中產生的一個新概念。“互文性”最初是由法國后結構主義文藝批評家茱莉亞·克里斯蒂瓦提出的,出自拉丁語“intertexto”,也有“文本互涉”或“文本互指性”等說法。克里斯蒂瓦認為,“作為一種源自其他文本的馬賽克圖案而建構,每個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加以吸收和轉換”。克里斯蒂瓦在提出這一概念后,打破借用、移植、拼湊等明確概念的狹義性,從而融合文章之間相互交叉、彼此依靠的不同表現形式。互文性可以使翻譯更加廣泛地涉及到社會文化和歷史中更深的層面,在了解文化和歷史因素的基礎上更深層的了解原文的意義并進行闡釋,使得譯文更加合理全面。
2. 文化、語言、翻譯和互文性的關系
正如我們所知,文化和語言是密不可分的。文化影響著人們使用語言的方式,左右著語言的發展方向;語言是文化進行發展和傳播的工具。翻譯不僅僅是將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行為,它是一種受文化背景因素制約的將歷史、宗教、傳說、習俗、傳統等因素的影響,有時又會與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而收到影響。因此,“互文性”就能進一步拓寬對翻譯工作的研究。語言順應論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它認為翻譯是語境與語言結構相互順應的動態過程。(田雨,2010)互文的驗證和支持是在翻譯的理解和表達中必不可少的。翻譯雖然是兩種不同語言間的相互轉換,但是時時刻刻受到歷史和文化等不同因素的影響,因此互文的驗證和支持是在翻譯的理解和表達中必不可少的。翻譯是一種具有互文性的將兩種不同語言相互轉化的行為,并從文化,思想,文章,語言等不同層面全面的展開。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行為,譯者在仔細體味蘊含在原文語言構架中的文化特征的同時,也應該周到。
3. 跨文化翻譯中的互文指涉
梅森和哈蒂姆的“互文指涉”:互文指涉的處理方法是跨文化翻譯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互文指涉這一概念最初由梅森和哈蒂姆于20世紀90年代在他們的作品《話語與譯者》中提出。他們并沒有給互文指涉定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只是將其稱作“暗示與指涉”。在進行翻譯工作時,譯者首先要進行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就是確立文章中的互文標志,然后再進入互文空間時就可以以此為標志追尋它的前文,再從信息、意向和符號三個層面評價這些符號在體裁、語言和文本方面的特色,互文指涉的成分之一,它也可以追尋到其他語篇中的所指。跨文化翻譯中的互文指涉:作者、譯者和讀者在跨文化翻譯的過程中進行的交流和對話時超越了時空限制的。對于跨文化翻譯來說,互文指涉是蘊含在語言構架中的文化特征和語言特征。而這兩種層面是密切相聯系的,它們的界限并不明確。互文指涉分為單詞短語和句法兩方面,簡單的說,就是單詞、短語、句子和語序。數個短句和四字成語組合成了一個長句,看似松散實際上語義十分緊湊。若譯者只是一字一句的按照原文直接翻譯,那么譯文會十分繁復且令人難以理解。而該譯者充分考慮到了英語和漢語不同的構句語法,準確把握到了原文的中心思想,按照英語的語言特色充分發揮,使得譯文的結構嚴謹、邏輯合理并且意義十分明確。從符號的方面出發,互文指涉分為體裁、語言和文本三個方面。在互文性的角度下,我們可以吧互文性的這三個結構符號和語域的三個變量:語場、語旨和語式相結合,考慮著單個變量在語境中的互動。在符號層面看語場,它就指向了體裁和它的傳統。翻譯十分惡毒,似是在詛咒奶媽,完全曲解了原文的意義,而第二個譯文則是溫婉且生動形象地描繪出了少女在等待情人消息時的焦急和忍不住抱怨的清純形象,生動地表達出了原文的寫作特點。翻譯與表現對于文化人類學翻譯的策略反思在隨著人類學研究中的語言和社會學轉向過程中也經歷了多次修正。翻譯作為一種文化轉換的方式,在一定時期內研究的側重由文化理解和文本闡釋轉化到表達正確與否的評判上來。民族志當中大量運用文學描述策略和會話策略,以及各種表達方法等,事實上,其描寫成為了具有獨立文本地位的闡釋性的翻譯。指望靠民族志的翻譯來傳遞全部正確的異域文化,這種期望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19世紀80年代的書寫文化爭論帶來了跨文化翻譯下文化差異表現問題。人類專著中的經驗翻譯自此之后正如文化翻譯過程中的文化虛構過程一樣成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從跨文本所應具備的前提條件,文化概念的轉化和表達的傳統方式上,還有對文化整體性的整合再造,人類學實踐均應涵蓋上述因素。因此,人類學實踐自身被視為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過程。翻譯理論的人類學構想是通過與原著民的對話進行表現,在所謂的獨白式表現中產生了對話人類學。人類學實踐的翻譯能夠弱化不同的、矛盾的聲音,它并沒有賦予內在文化整體以其他的文化意義,卻突出了翻譯的多元視角,展現了多元翻譯的必要性。即使是這樣,文化間的權利不平衡和民族志撰寫中的選擇壟斷用對話式的翻譯策略也無法消除。相反的是,民族志翻譯理論的構建收到了改變對于一種文化的理解的很大影響。后殖民理論是后殖民翻譯理論的理論基礎。譯文背后源語和目的語文化之間的權利斗爭和運作是由研究譯文與歷史條件之間的關系揭示的。因為在西方的翻譯史上,翻譯行為涉及權利、殖民主義和語言的不平等性,所以它始終具有政治和文化策略意義。文化人類學在經驗研究上和知識論層面上對翻譯進行了深入思考,殖民主義對民族志翻譯的制約,宗教翻譯特別是歐洲殖民地宗教翻譯在與民族志撰寫的相互借鑒和交流上,均體現出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行為,應被視為關乎種族和宗教的構建行為。交互翻譯的重要性也由知識論反思的切入點而更加突出強調,由此可以說,翻譯是各種文化相互影響的互動過程而不應該只是西方單方面學習異域文化的手段。新的民族學與以往傳統意義上理解的翻譯過程不同,并非只是作為兩種客觀語言環境之間相互有機轉化,而是要把不同的世界緊密聯系在一起,在文化人類學的發展中意會民族志文本,摒棄了傳統的二分法思維,主張話語平等性和互文性。
4. 跨文化翻譯中互文指涉的處理方法
注重互文指涉的符號層面:譯者首先要確立文章中的互文標志,語言和文本方面的特色,并在翻譯過程中適當的保留或舍棄這些特色,才能正確的表達跨文化翻譯中的互文指涉。互文標志的“形式”就是前文所指的信息層面,其“功能”是意向層面,而對于“形式”和“功能”的取舍就是符號層面關注的問題。處理跨文化翻譯中的三種互文指涉的譯法。但是由于文本的體裁和語言不同,即使互文指涉是在同一詞匯短語和句法層面上的,其文化內涵的保留程度也是會變化的。因此,這種分類方法是與語境密切聯系的。對于這一類型的互文指涉,我們可以采取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譯。由于人類生活所處的大環境是相同的,即使是不同的民族在生存上的劇本需求也是相同的,對于世界的認識和看法也有很多的共同之處。因為這些相同之處,使得互文指涉的移植有了可能。直譯能保留原文的風格和意義,有時可以將原文中的意象完全移植到譯文中。
結語
不同民族思想和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相互補充形成了世界的文化體系。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發展,不同國家的人們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頻繁,在仔細體味蘊含在原文語言構架中的文化特征的同時,也應該周到的考慮翻譯的互文性。以文本的體裁和語言為基礎,恰當的采用移植、補償或省略的方法,從而推進不同文化間的進一步交流融合。
參考文獻:
[1] 陳光祥.《可譯性與可譯度》.外語研究, 2003, (2): 58-60.
[2] 耿小超. 《從翻譯角度論中西文化差異》.山西大同大學學報, 2008, (2): 58.
[3] 胡文仲.《語習語與英美文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4] 金惠康. 《跨文化交際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
[5] 徐美珍.《試論英漢習語的文化差異及翻譯》.廣西民族大學學報, 2007, (12): 132.
篇4
【關鍵詞】后現代語境;民族志生產;地方性表述;反思
【作 者】龔德全,貴州民族學院民族文化學院2007級碩士研究生。貴陽, 550025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 號】1004-454X(2009)03-0032-008
Ethnography Production in Post modern Context:a Confused Pursuit
Gong Dequan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post-modern context, follow the diac hronic c ontext,Analysi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encountered confusion, controversy by an thropologists when doing ethnographic text. Its including traditional ethnograp hic “science” problems,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in the literatureToward i ssue, national historical texts in the mass media era, and this as the theoretical bas is and logical basis , thinking the “post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paradigms . For anthropologists, the ethnography of production is always a confused pursu it, perhaps, this is the continuing of ethnographic source of life.
Key words:post modern context; ethnographic production; loca l representation; reflection
一、傳統民族志:是真實還是詩意的真實?
在人類學史上,傳統民族志寫作范式的最終確立,是與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k. Malinowski)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在馬氏以前,古典人類學家受進化論的制約,傾向于借 用 世界各地的古代歷史文獻、神話傳說和旅行家們所提供的“第二手材料”,將不同時空里的 文化元素聚合在一起,來構造宏觀的人類文明史,無論是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澤的《 金枝》,還是韋斯特馬克的《人類婚姻史》,等等,皆屬此類,也正因此故,后世的人類學 者才笑稱這些前輩為“搖椅上的人類學家”(the armchair's anthropologist)。毫無疑 問,馬林諾夫斯基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所創立的田野工作方法與民族志描述體系是對古典人 類學的一種背叛,但是它卻對后來的民族志描寫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幾乎成了當時民族 志寫作范式的“正宗”。雖然在上世紀20―60年代,不乏有對其功能理論的批判,但是對其 所建立的民族志寫作范式的質疑卻實屬罕見。正如利奇所說,“馬氏的功能理論有很多漏洞 ,但他的民族志方法卻為現代社會人類學研究奠定了方法論基礎。”①
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然而,在上世紀70年代(或者更早一些),馬林諾夫斯基的整體民族志卻受到了質疑與批評 ,而且首當其沖的,就是他曾經一再宣稱的其民族志文本的“科學性”與“真實性”問題。 這一點,或許令馬氏及其追隨者們無法忍受,因為當年他們就是滿懷著建造“文化科學”的 壯志雄心來進行民族志描述的。雖然此種“崇高”的追求讓人心生敬意,但是,這種對于“ 文化科學”的虔誠,卻并不能證明他們的田野材料及其描述的“客觀性”,也不能證明他們 沒有受到其主觀傾向性的影響,已經抓住了文化的“真在”,因為“所謂真實,并不能夠與 對它的理解相分離”②。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就曾直白地指出,“原來人類學家 把民族志 視為‘文化科學’,這種看法值得商榷,因為在田野作業和民族志寫作的過程中,人類學者 所作的事實際上是通過描述表達自己對社會、文化、人生的闡釋。也就是說,雖然人類學者 研究的對象可以是同一個文化或同一種文化現象,他們可能對它產生不同的闡釋,從而使他 們提供的‘知識’具有相對性。”③關于這一點,我們很容易就想起了德雷克• 弗里曼( Derek Freeman)對米德(Margaret Mead)《薩摩亞人的成年》激烈而公開的批判;或者是 兩位著名的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與劉易斯同對墨西哥泰普茲特朗的村 莊進行研究,卻得出迥異結論的例證。
其實,對于傳統民族志描寫的“真實性”與“客觀性”的質疑,還與人類學家對西方世界與 非西方世界的文化權力或文化政治問題的反思密切相關。正如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 rdieu)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應該弄清楚:任一給定的作者是在何種權力場以及在該權力場 中的何種位置上進行寫作的④。不可否認,這樣的詢問有助于我們理解人類學與 它的“他 者”之間宏觀和微觀的權力話語關系。在梳理此種權力話語關系的過程中,傳統民族志所標 榜的“真實性”與“科學性”似乎更加不堪一擊。無論是阿薩德(Talal Asad)關于殖民主 義與人類學的論述,還是愛得華•薩伊德(Edward Said)關于西方話語與異文化的探究, 都曾尖銳地指出了所謂的“科學民族志”,其實無法掩蓋與殖民主義所具有的千絲萬縷的聯 系,更無法擺脫西方意識形態的價值傾向和西方文化的痕跡。于是,我們不得不略帶傷感地 承認:“恰當的人類學描述不可能脫離認識論和政治上的因素,這些決定了寫作的前提”。 ⑤
在這股對傳統民族志寫作范式進行反思的巨大浪潮中,一種較為激進的做法,是上世紀80年 代以來出現的運用文學批評的方法將“民族志作為文本”,并對其寫法和研究過程進行全面 的剖析。馬爾庫思和庫思曼(Marcus and Cushman)就曾做過此項努力。他們將馬林諾夫斯 基及其追隨者們的民族志視為一種現實主義作品,并從中歸納出了九個方面的特點⑥ ,試 圖從更深的層次揭示傳統民族志作品中所隱藏的矛盾和問題,以及他們是如何運用策略來努 力營造出一種所謂的“科學性”與“真實性”的。
伴隨著是真實還是詩意真實的困惑,人類學民族志描寫陷入了一場“表征危機”(crisis o f representation)。而“對民族志寫作中的表征危機的元反思(metareflections)表明 了人類學關注的重心已從對它與異文化之間的關系,開始轉向對我們文化中的表征傳統和元 表征的元傳統(metatraditions of metarepresentation)的一般性關注。”⑦ 作為此項 關注的一種表現,人類學家開始積極探索新的田野工作方法,試圖以此來修正民族志寫作中 “元表征的元傳統”,其最終目標為克服這場“表征危機”。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馬爾庫斯 和費徹爾(Marcus&Fischer)在《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中就 曾提出需要一種新穎的田野工作類型,他們稱之為“多元地點民族志研究”。即在研究的整 個時期里,田野工作者不應把自身固定在一、二個社區里;相反,田野工作者必須具有靈活 性,其工作場所應是一個包含多個地點的網絡⑧。在田野工作方法上,他們還提 倡“合作 型的人類學寫作規范”與“多視角的研究方式”,這樣就打破了人類學者對某一社區文化解 釋的“一家之言”,代之以各種不同解釋的并置。但是,無論如何都不可否認,這種并置依 然是各種主觀表述的聚合。
由此可見,人類學的民族志描寫其實根本無法達到超然的客觀性,因而至多只是一種“部分 真理”(partial truth),甚至是一種民族志故事(ethnographic fictions)。因為“無 論是人類學家還是普通人,都是在用自我去理解他者”⑨。換句話說,在所有的 文化研究 中――其實,在其他的人文科學研究中也是如此――都注定要浸染我們的主觀因素,而傳統 民族志的所謂“科學”面目也永遠只是一個“面具”(王銘銘語)。然而,盡管如此,我們 似乎也沒有必要感到沮喪,正如墨菲所言,帶有個人色彩這并不必然就是罪惡,只要我們時 時清醒地知道我們工作上存在著個人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立場觀點。至于貫穿于田野工 作中的理論信念,不僅不是累贅,而且是絕對必要的(10)。
二、“實驗民族志”中的文學轉向:是人類學寫作還是文學寫作?
擺脫了故作天真的價值無涉,告別了一廂情愿的“科學”追求,人類學者在對傳統民族志進 行深入反思與批判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民族志的實驗觀念,并出現了一股對民族志做出新 實驗的潮流,這一浪潮對民族志描寫所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深刻的影響就是:引發了民族志的文學轉向。特別是在以格爾茨為代表的闡釋主義人類學提出了人類學只是“ 一種創作”以后,民族志文本幾乎就成了“寫作產品”的代名詞,而人類學者則被認為是在 進行寫作形式的實驗。這不僅體現了闡釋主義在民族志生產中對人類學家“主觀性”的高揚 ,更是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對人類學的一種有力挑戰。
在被認為是人類學最早的后現代主義文本《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Writing Cu 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學人類學作品) 中,幾乎每一位作者都對民族志話語書寫方式的文學性給予了關注。例如,詹姆斯•克得福 德(James Clifford)在其論文《論民族志寓言》中,就提出要將民族志本身當成一種由有 影響力的故事設計出情節的表演。并且強調了這些故事在描繪真實文化事件的同時,進行了 附加的、道德的、意識形態的甚至是宇宙論的陳述。民族志寫作在其內容和形式兩個層面上 都是寓言性的(11)。這就肯定了民族志中的人物確實帶有文學性。馬爾庫斯(Marc us)在《 跋:民族志寫作與人類學職業》中很明確地指出,圣菲研討會(《寫文化》的各篇論文就是 在此研討會的基礎上誕生的)的任務就是通過展示解讀和寫作民族志的不同方法而引入一種 對民族志實踐的文學意識(literary consciousness)。而且他認為,當今的人類學家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自覺地認識到自己是作家,作為正在走向成熟的職業學者,按照常規,他 們已經超越了那些曾將他們引入人類學的民族志模式(12)。保羅•拉比諾在《表征 就是社會 事實:人類學中的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一文中,通過將克利福德•格爾茨(Geertz)的解釋 人類學與詹姆斯•克利福德(Clifford)的文本主義的元人類學并置比較,成功地讀解了克 里福德所提出的四種人類學寫作模式,即經驗的或現實性文本、解釋性文本、對話性文本以 及復調文本,并最終闡明了表征就是社會事實(13)。其他人類學家,如邁克爾•M .J.費希 爾、斯蒂芬•A.泰勒、溫明森特•克拉潘扎諾等,也對民族志文本的寫作模式、寫作策略 、修辭的使用(例如反諷、幽默的運用)以及語言技巧的展示等方面進行了文學意義上的探 索。
與《寫文化》同年出版的,還有另外一部重要的文學人類學作品《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這部著 述不僅對1980年代的批評浪潮之潛在意義進行了深刻的評述,而且還對民族志創作的主題、 風格以及“文學轉向”的實質給予了十分深刻的讀解。指出了現代主義民族志文本應該強調 民族志作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對話,或者力圖使讀者卷入分析的工作中去,并認為多樣化的 合理的聲音和觀念之間的對話將成為現代主義民族志文本書寫的新趨勢(14)。
自從《寫文化》與《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為民族志描寫的文學性正名以后,許多人類學 家都繼續著這種話語。格爾茨(Geertz)在他獲獎的《作品與生活》(Works and Lives:T 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一書中指出,人類學寫作應該包括講故事、制作圖片、構 思各種象征主義并進行描述和比擬:“半信半疑的作者試圖使半信半疑的讀者相信他們(作 者的)那一半的確信”(15)。很明顯,格爾茨已經十分確定地將人類學文本視為一 種文學 文本。美國人類學家諾曼•鄧金(Norman Denzin)認為田野民族志作者對各民族的描述應 該超越傳統的、客觀的寫作方式,寫作出更具實驗性、更具經驗性的文本,其中包括自傳和 基于表演的媒體;更多地表達情感;文本要小說化,借此表達詩意和敘述性的事實,而不是 科學事實;同時還要面向活生生的經歷、實踐、采用多視角進行寫作(16)。鄧金的 言論似乎 在告訴我們,田野民族志的本質就是它生而具有的文學性,人類學家對此應該毫無條件的承 認。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類學家都會對這種“文學轉向”表示認同,事實上,抵制性或拒絕性的 力量依然十分強大。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為人類學自身有著長久以來的學術傳統,存在 著某種具有排斥性和排他主義的寫作方式,而文學傳統對人類學寫作的深刻嵌入,在某些層 面上,則意味著人類學要向他的對手做出讓步。而此種讓步的直接后果便是,迫使人類學家 改變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實踐方式與寫作方式,這對某些人類學家而言,似乎已經超過了他們 的“底線”。他們擔心這種挖掘知識訴求如何具有修辭性的做法會降低人類學作為一門嚴肅 知識的可信度;并且強調人類學家創作文本并不是為了確立某種文學性的觀察:即既不是為 了形成某種獨特的風格,也不是為了融合入所謂的修辭上的“先鋒實踐”。所以,人類學家 如果反思這些文學性的問題而不是調查研究外部世界,這種做法會被認為是不恰當的(1 7)。
關于實驗民族志中的“文學轉向”問題,在我看來,我們應從不同的視點加以辯析。首先, 我們還是要強調文學與人類學兩個學科之間涇渭分明的界限,二者在寫作的基本旨趣、表述 基礎、表述方式以及對邏輯推理、藝術追求等方面都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相對于文學寫作 而言,人類學寫作要包含更多的現實主義精神,其寫作的第一要義就是忠于事實,而不是獲 得藝術上的滿足。相反,文學寫作對此方面的要求顯然要弱化許多,借用Erickson的話來說 ,即使文學把自己的目標定為現實主義,可是在描述的精確性上,兩者(文學與人類學)依 然是不同的。因為總是最先形成觀念,而后才是將現實與之匹配(18)。此外,人類 學寫作常 常注重前后關聯以及推理上的邏輯,而文學寫作常常是比較含蓄、抽象,比較自我的,并不 注重推理上的邏輯性,它所追求的往往是一種非邏輯的藝術上的美感。
然而,清楚地標示出人類學寫作與文學寫作的迥異特點,并不意味著我們就無法逾越二者所 具有的涇渭分明的界限,事實上,在人類學與文學各自對社會生活進行現實主義的表述過程 中,它們存在著許多交叉與重疊之處。而且,如果我們將文學與人類學聯立起來加以析解, 會很真切地看到二者之間所具有的內在邏輯關聯。在《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一版中對人類學 的定義是“人類學,是關于人類本性的話語”。同樣的,對于人類本性的話語敘述以及對人 類本性的思想關懷也是文學本質的應有之義。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人類學寫作還是文學 寫作,似乎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建立對人性更廣闊認識的手段。所以,我們完全可以將人類 學寫作的特有生產模式與文學傳統加以整合,創作出一個兼具文學和人類學意味的文本。因 此,我們并不同意Aunger將傳統民族志視為對“科學”的追求,而把實驗民族志看成是對“ 藝術”追求的截然分法(19)。
此外,每一個人類學家在民族志描寫中都具有極大的個體性,他們可以憑依自己的意愿,采 取多種形式來書寫其田野經驗。事實上,許多人類學家(包括傳統民族志學家)都是這樣操 演的,像馬林諾夫斯基、本尼迪克特、埃文思―普里查德、列維―斯特勞斯、利奇、格爾茨 ,等等人類學家,都曾使用過“田野日記”、“論文”、“專著”、“游記”等不同的方式 來進行寫作。以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為例,他在對南比克瓦拉(Nambi kwara)等幾個原始部落的田野經歷進行描述與分析時,既寫就了《結構人類學》這樣的理 論專著,也完成了類似于個人“游記”的《憂郁的熱帶》。此時,我們已不能嚴格地區分斯 特勞斯的民族志描寫究竟是人類學寫作還是文學寫作了,因為“民族志與文學作品一樣需要 詮釋” (20)。
綜上所述,我們既要對人類學寫作與文學寫作在寫作方式與風格等方面的一系列差異有一個 深刻的認知,但是又不能僅僅囿守于此,被自身所圍困,否則,人類學將無法界定自身。所 以,我們不應再規避民族志所具有的“文學品質”,而應努力在民族志描寫中樹立一種“文 學意識”(literary consciousness)。盡管對某些人類學家而言,這樣的言論會讓他們心 生不悅,但是民族志描寫的歷史與現實都已經證明:民族志的文學或修辭之維不應再與它的 事實部分如此輕易地被分割開來。這正如普拉特(pratt)所言,“沒有必要把特定的修辭 手段和風格流派與某一學科之間的關聯看成是自然的或者天生的,就如同人類學家過去曾經 采取某些手段,而如今他們可以發明出新的方法。人類學文本沒有必要遠遠地疏離于小說、 游記、回憶錄和新聞報道,或者前衛的文化評論,這些其實都可以被看成是某種對應的‘書 寫社會現實’的方式。”(21)也許我們應該承認:“民族志是混合的文本活動, 它跨越不 同的體裁與學科”(22)。在民族志文本的生產中,對風格、修辭和辯證的自我意識 將引導 我們發現其他更富想像力的寫作方式。但是,無論如何都不應忘記:我們堅持民族志是一種 寫作,但絕非是要聲稱民族志“只是文學”,甚至是借助文字上的游戲,來實現一種智巧的 策略。
三、傳媒時代的民族志書寫:何謂地方性表述?
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民族志生產所面對的時代背景始終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且這種變化的 速度與幅度往往超出我們的想像。如果說20多年以前,傳統民族志的“表征危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是人類學實驗性寫作的生命源泉,那么20多年以后,人類學所面臨的 “表征”困境卻依然沒有減緩。相反,隨著民族志生產全面遭遇傳媒時代的到來,一切都變 得更加撲朔迷離。
自從馬林諾夫斯基時代的社會人類學者不滿于古典人類學采取“切割文化”式的宏大理論敘 事模式,從而將相互連帶的文化特質置入一個整體內進行研究開始,以“全觀性”(totali ty)的方式對一個具體的族群(ethnic group)、社區(community)進行調查與描寫就已 經成了現代人類學的正統,同時這也是一種嚴格的學科要求。然而,對于已經習慣了在隔離 的時空座落中探求“文化本質”――在人類學的反思視閾中,所謂的“文化本質”,不過是 偏狹的、政治上受到摒棄的西方特質――的人類學者來說,傳媒時代的全面來臨,無論如何 都不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因為他們似乎無法預見:傳媒的力量究竟對人類學意味著什么 ?是被其消解嗎,還是誘發其重構?無論答案是什么,或許都不能令人類學者感到滿意。
之所以會產生如此令人驚恐的困惑,其深層次的原因就在于傳媒時代造成了人類學者從未預 料到的文化轉型,而且,此種文化轉型必然會導致民族志生產的內在結構與機制發生重大的 改變。如果我們把馬林諾夫斯基時代的社區/地方(community/place)描寫與傳媒時代的社 區/地方(community/place)描寫加以并置比較,將不難理解這一命題。前者所描寫的社區 通常被表述為:“是與西方社會相對立的、被理解為相對靜止的、保持文化‘原生形貌’的 類型,對象的形態被理解為一種固定的或變化緩慢的形式。”(23)其社區文化也 往往有著 自己的運行規則。而在傳媒語境中,傳統的小型、相對靜止的部落、社區已經被全球化、國 家化的巨大力量所滲透與連接,它們已不再是隔離于世界文化體系核心之外的一個區位,或 者僅僅是作為西方文化批評的一個十分有力的文化圖像,它們已經成為世界體系之內的邊陲 地帶,是“全球中的地方”(local in the global)。因此,今天的人類學家如果再次來 到努爾人的社會或者是特羅布里恩德社會去考察,所發現的將不再是埃文思―普里查德或馬 林諾夫斯基經典民族志中所描述的風俗,而很可能是一種被現代文化、西方文化浸染過的“ 變形文化”。他們或許也像西方人一樣用傳媒建構著民族國家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 ed communities)。實際上,即使是傳統社會的小型社區,也并非是一個完全封閉、自足的 空間座落,而所謂孤立的或永恒的社區不過是傳統民族志學家的一種想像而已,“只是因為 獨斷和政治排斥的意識才有了這種人類學建構空間和地域的方式;馬氏的特羅布里恩德島之 所以成為一個自在的部落,是以虛化他者為代價的。實際上無法劃分各個文化之間的邊界, 這些領域總是交叉的;空間從不與身份對應,地域也非均質的,任何文化群體都是暫時性的 。” (24)
毫無疑問,文化邊界的模糊性與“空間從不與身份對應”的特點在傳媒時代被無限地放大, 這就使得人類學家被推入了一種進退維谷的境地,陷入了如何“表述地方”的尷尬與困惑。 一方面,社會文化必須與一定范圍的地域緊密相連的人類學傳統,要求人類學家必須對“地 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給予觀照和表述;但是另一方面,所謂的“地方性知識” 又似乎無處可覓。因為在傳媒時代,“地方性知識”已經被越來越多地摻入了外來的、民族 國家的、現代的、西方的異質性文化元素,成為一種混合的、多質性存在。而當地人的觀點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也是在與外界不斷地對話與互動中逐漸建 構出來的,換言 之,他們是通過將“別人的”/“他者的”(與傳統民族志中的“他者”并非同一概念)觀 點加以內化與引申的方式來完成“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的。甚至有時候,他們 會刻意地按照“別人的”想像來建構自己。例如,在開發旅游的文化社區里,當地人會充分 考慮外地游客的觀點以及對于“異鄉情調”的想像,并以此來修正、構建自己的觀點,以便 吸引游客進行“文化消費”。在此情境下,人類學者所見更多的是一種“地方化策略”,卻 難以找到傳說中的地方性表述。
由此可見,傳媒時代的來臨使民族志書寫再一次陷入了更為嚴重的“表征危機”。“地方性 知識”被異質文化層層復加,其自身也在發生著異化,再加上持續社會變遷中文化群體間的 邊界越來越模糊,這一切過于復雜的情形,都讓人類學家猝不及防,他們已經隱約地感覺到 了對于傳媒時代民族志書寫的力不從心,甚至開始懷疑社會人類學方法是否依然足以表述文 化的形態。看來,人類學有必要利用本學科的元話語來對“何謂地方性表述”這一基本問題 做出新的評估與界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人類學目前還難以找到這樣一種具有足夠解釋 力的學科元話語。那么,這是否就意味著:在傳媒時代里,地方性表述已成為一個遠去的神 話,我們只能在誦讀《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經典民族志中才能尋找到呢?當然不會如此。 在我看來,最關鍵的問題并非要確證、抽取出“純而又純”的地方性表述,而是要對傳媒時 代里的人類學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實踐,以及文化格局的巨大變化有一個清醒而深刻的認 知。一如王銘銘所言,“如果說傳媒時代帶來了一個文化的世界格局的話,那么對文化進行 深究的社會人類學者便不應停留在‘土著文化’和‘遠方生活方式’的描寫之上。社會人類 學者的研究對象不應再是與世隔絕的‘村落’和‘文化的他人’,而應包容傳媒文化和流行 文化研究的對象,那就是來自現代社會的文化形態。”(25)人類學唯有做到如此的 轉向,將 來自現代社會的文化形態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才能真正克服傳媒時代的民族志生產所面臨 的社會現實生活的“表征”困境。
四、余論:關于“后實驗民族志”的想像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后實驗民族志”并非是在當下新出現的一種民族志描寫范式, 而是筆者基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后范式”(postparadigm)特征――如“后現代主義”、“ 后”、“后殖民主義”等――而冠以的名號(當然,它并沒有系統的理論體系作 為支撐,僅僅是筆者所想像的一個名稱)。既然1980年代出現了“實驗民族志”,那么在20 00年代及其以后,在共識的范式出現以前,人類學寫作的“后實驗民族志”這種稱呼還是可 以讓人接受的。
通過上述我們沿循歷時性脈絡,對人類學家在民族志文本制作過程中的困惑、論爭進行回溯 ,可以發現民族志范式走向中的一個基本規律,那就是:民族志對象始終與社會背景相依附 ,民族志的敘述主旨始終與同時代人類學關注的主題相對應;而且,民族志對象與敘述主旨 其實一直處于變化之中。無論是傳統民族志對于“民族與地方”(peoples and places)的 檔案的關懷;還是1980年代以來,人類學家在基本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實踐中所實際發生的 急劇變化,都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和人類學的研究取向相連接的。因此,我們要想對“后實 驗民族志”進行合理的想像,就要敏銳地觀察和深刻地把握出當下的社會背景與人類學研究 的重要趨勢。
毫無疑問,進入新世紀以來,人類學所面對的社會背景以及研究取向較之以往,已經發生了 巨大的變化,即使是與20年以前相比,這種變化也顯而易見的。正如《寫文化》編著之一馬 爾庫斯,在《寫文化》之后20年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說的那樣,變遷、政治、行為主義、后殖 民主義、全球化,今天構成了社會背景,大多數專業研究計劃在此背景中得以制定,并依據 在人類學之外的其他領域所生產出的社會與文化理論來界定。地區專門研究和田野工作的核 心特征仍然得到堅持,但是范疇的設置、具體研究參與的更廣泛課題的潛在意義以及核心方 法的實踐本身都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序言》中,馬爾庫斯還指出,在近年來,社會 文化人類學的多樣的求知欲和研究探索中具有一種現存的重要趨勢,那就是“公共人類學” (public anthropology),它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 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對公共導向 的、公民的人類學的期望日益高漲并在目前成為了主流。公共人類學將在它的研究努力中更 關注它的責任、它的倫理和它對各種他者的義務,而不是關注將它作為一門學科進行推動的 行會似封閉的,對辯論、模式和理論傳統的癡迷。這一趨勢在美國民族學協會于2003年度頒 發的“作品一等獎”的民族志中就有所體現,此獎勵是美國人類學中對年輕學者創作的民族 志的最重要的認可。這就是阿德里安娜•佩德里娜(Petryna)的作品《的生命》(關 于切爾諾貝利事件幸存者的斗爭)和金•福瓊(Fortun)的作品《博帕爾污染之后的倡議》 (關于跨國范圍的環境公正和激進主義,從1984年災難的數年之后在博帕爾的激進主義的田 野工作開始)。(26)這兩部作品可能暗示了今后民族志生產中的某些新方向和與之 相應的田 野工作的特殊模式;而且,需要強調的是,這兩部民族志作品中都包含了多元化的公眾,這 一點無疑也是“后實驗民族志”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生長點。
總之,當下的人類學面對的是變化多端的時代背景,其研究取向也趨向多元,這些復雜的情 勢都對“后實驗民族志”的生產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也是更高的要求。民族志研究中陳舊 的實證主義范式已經離我們遠去,而傳統的民族志可能將來會以新的方式重新出現(目前, 我們似乎無法預見此種方式的細節),但是卻沒有跡象表明它會出現在當下的歷史語境。那 么,“后實驗民族志”究竟會走向何方呢?雖然目前我們還無法做出精準的回答,但是,在 學術界似乎已經出現了一種共識的聲音,那就是:“人類學表現得越來越樂于采用綜合的方 法和其他理論傳統。”(27)“我們的研究必須是經驗性、解釋性、批評性和知識性 的綜合 ,從而必須在注重事實的同時,不以膚淺的觀察作為事實根據來反對學術解釋和學術批評。 ”(28)因此,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種兼容并蓄式的綜合方法可能代表著未來人類 學的研究趨向。在我看來,它同樣也代表著“后實驗民族志”生產的新趨向。
也許,我們應該承認,“后實驗民族志”生產同樣會遭遇到“表征危機”,而且和過去相比 ,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未來變化多端的社會情境,會時刻向民族志生產提出超乎人 類學家想像的苛刻要求。簡•科普詩中的“闡釋者的困境”到了今天依然存在,而且,可以 令人信服地說,未來也不會消逝。或許,對于人類學家而言,民族志生產本身――無論是過 去、現在或將來――就是一個困惑的追求。雖然我們并不知道這是否是人類學的宿命,但是 我們堅信:這一定是人類學不斷向前發展,民族志持續不衰的生命源泉。
參考文獻:
①轉引自王銘銘.西方人類學思潮十講[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 5.P147.原文見于Leach,Edmund.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 and New York:Fontana .1982.
②[美]喬治•瑞澤爾著,謝立中等譯.后現代社會理論[M] .北京:華夏出版社,20 03.P5.
③王銘銘.西方人類學思潮十講[ 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P150.
④轉引自[美]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高丙中等譯.寫文化 ――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C]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P305.原文見于Bordieu,P ierre.Distinc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⑤[英]奈杰爾•拉波特、喬安娜•奧弗林著,鮑雯妍、張亞輝譯.社會文化人 類學的關鍵概念[M]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P16.
⑥Marcus,George.and Cushman,Dick.Ethnographies as Texts[J].In A 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82,(11).P25-69.
⑦[美]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高丙中等譯.寫文化――民 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C]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P304.
⑧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徹爾著,王銘銘、藍達居譯.作為文 化批評的 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P135.
⑨[英]奈杰爾•拉波特、喬安娜•奧弗林著,鮑雯妍、張亞輝譯.社會文化人 類學的關鍵概念[M]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P22.
⑩[美]羅伯特•F•墨菲著,王卓君等譯.文化與社會人類學引論[M] .北京:商務 印書館,1991.P307.
(11)[美]詹姆斯•克利福德著,康敏譯.論民族志寓言[A].[美]詹姆 斯•克利福德、喬治•E. 馬庫斯編,高丙中等譯.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P136-162.
(12)[美]喬治•E•馬庫斯著,李霞譯.跋:民族志寫作與人類學職業[A]. [美]詹姆斯•克利 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高丙中等譯.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C]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6.P315-320.
(13)[美]保羅•拉比諾著,趙旭東譯.表征就是社會事實:人類學中的現代性 與后現代性[A].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高丙中等譯.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 政治學[C]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P285-314.
(14)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徹爾著,王銘銘、藍達居譯.作為 文化批評的人 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P101-112 .
(15)轉引自[英]奈杰爾•拉波特、喬安娜•奧弗林著,鮑雯妍、張亞輝譯.社 會文化人類學 的關鍵概念[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P205.原文見于Geertz,C.Works and Live 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Cambridge:polity.1988.
(16)[英]阿蘭•巴納德著,王建民等譯.人類學歷史與理論[M].北京:華夏 出版社,2006.P184.
(17)參閱[英]奈杰爾•拉波特、喬安娜•奧弗林著,鮑雯妍、張亞輝譯.社會 文化人類學的關鍵概念[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P205.
(18)轉引自[英]奈杰爾•拉波特、喬安娜•奧弗林著,鮑雯妍、張亞輝譯.社 會文化人類學的 關鍵概念[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P208.原文見于Erickson,V.‘Buddenbrooks ,Thomas M ann and North German Social Class:An Application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in F.Poyatos(ed) Literary Anthropology,Amsterdam:Benjamins.1988.
(19)Aunger,Robert.On Ethnography:Storytelling or Science?[J].In Current Anthropology,1995,(1).P97-131.
(20)泰特羅著,王宇根譯.文本人類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P47.
(21)[英]奈杰爾•拉波特、喬安娜•奧弗林著,鮑雯妍、張亞輝譯.社會文化 人類學的關鍵概念[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P206.
(22)[美]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高丙中等譯.寫文化―― 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P55.
(23)彭兆榮.旅游人類學[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P58.
(24)[英]奈杰爾•拉波特、喬安娜•奧弗林著,鮑雯妍、張亞輝譯.社會文化 人類學的關鍵概念[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P18.
(25)王銘銘.西方人類學思潮十講[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P166-167 .
(26)喬治•E.馬庫斯著,龔浩群譯.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后20年的美國人類 學.載[美]詹姆 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高丙中等譯.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C]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P1-23.
篇5
關鍵詞:組織研究 組織人類學 組織民族志
作者袁同凱,南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地址:天津市,郵編300071。陳石,南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天津市,郵編300071。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學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郵編102488。
民族志是文化人類學的標志。早期文化人類學的民族志,作為抓住“當地人觀點”的方法,主要是從前現代、異文化的初民社會——如薩摩亞、肯尼亞、巴厘島、巴西及澳大利亞的部落社會——的研究之中發展起來的。它們研究的是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家族、宗族等與現代社會組織形式有著顯著差異的社會組織。當時的人類學家試圖通過對非洲、北美、澳大利亞、太平洋島嶼等地區現存的原始或簡單社會的文化進行研究,探討人類社會初始階段的各種制度,重構人類過去的歷史,并試圖通過對上述地區的民族志研究,對有關的組織結構進行抽象的類型學分析。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持續發力,以芝加哥為代表的大批新興工業城市開始產生、擴張,人類學也逐漸將研究目光投向現代組織。
組織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家庭、宗族,到社團、企業、政黨乃至國家,任何組織都有自己的規則、行為標準,都有成員需要履行的責任,其發展構成了推動社會變遷的重要力量。組織研究幾乎從未作為獨立的學科體系而存在,而是活躍于多個不同學科的共同研究范疇之中,成為跨學科的研究領域,發展出眾多的研究視角與方向。經濟學和管理學以經濟理性和權力為出發點,建立了“經濟人”的組織研究模型;心理學從組織成員心理與行為的互動關系來探討這種互動關系如何影響人類行為;社會學關注組織現象,對于組織的功能、結構和機制加以研究;人類學在不同時期的組織研究,尤其在其研究方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國內學者對人類學組織研究的理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回顧與反思,并嘗試將理論與實踐結合開展組織中的田野工作。邱澤奇系統回顧了以工廠化為經典假設的(社會學)組織理論的發展,并分析了經典假設產生的社會經濟背景,認為在網絡化的社會發展趨勢下這種假設已面臨困境;莊孔韶、李飛、方靜文通過檢視人類學對現代企業組織的研究歷程,闡述了人類學組織研究的理論導向及研究特征,深入探討并反思了以“文化概念”為核心的組織研究的嬗變過程與變遷趨勢;②宋雷鳴、王寧、卓文、張華志、曹媞等學者,則通過各自的田野調查,運用“作為文化的組織”這一理論框架對中國本土企業、跨國公司及城市中的自發型組織進行解讀,從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的多樣性中展開理論詮釋和學理探究。
貫穿組織研究的人類學方法,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在與初民社會風格迥異的現代組織中從事人類學研究,傳統的田野調查方法是否適用?從20世紀20年代人類學將參與觀察方法引入福特現代管理制度研究,到60年代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而關注第三世界國家中族群與跨國企業的關系,再到80年代以來融人更多后現論觀念的多樣化組織研究的復興,人類學組織研究方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與管理學的組織民族志相比,人類學對現代組織的民族志研究有何獨特貢獻?本文通過梳理20世紀30年代以來人類學在現代組織領域的研究實踐與貢獻,嘗試厘清組織人類學的方法特征,以探究全球化情境下組織人類學的發展取向。
一、人類學與現代組織研究
喬丹(A.Jordan)認為,現代組織研究中人類學家所做的民族志研究及有關實踐大略可以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20至30年代,主要是工業組織的相關研究,涌現出人際關系(human relations)學派;20世紀60至80年代,關注全球化視野下的族群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表現為工商組織研究的復興及研究主題日益多樣化。人類學持有的歷史的、情境的、過程的、行動者為中心的特色方法,在每個階段都嘗試為組織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并持續促進組織研究對參與觀察、情境和意義的分析及有關分析概念的完善。
馬爾庫斯(G.Marcus)和費徹爾(M.Fischer)認為,人類學者承諾要從兩個方面給西方讀者以啟蒙,一是“拯救那些獨特的文化與生活方式,使之幸免于激烈的全球西方化之破壞”,二是“通過描寫異文化,我們可以反省自己的文化模式,并對西方自己的文化進行批評”。二人同時指出,相比第二個方面,人類學者在第一個方面的努力成效要好得多。但是越來越多的關于組織和制度的民族志研究,能夠證明這門學科能夠實現第二個承諾。
人類學在一段時間內曾處于現代組織研究的邊緣地位,直至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回歸這一領域。實際上,這已經是人類學第二次踏進這塊領地。早在20世紀20至30年代,人類學在霍桑實驗及之后的人際關系學派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正是霍桑實驗這項研究確立了組織行為研究的地位。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幾乎放棄了這塊領地。此后人類學者才將注意力重新投向復雜組織研究,復興了民族志傳統。一大批人類學者,如布萊迪奧(E.Briody)和巴達(M.Bada)、布萊頓(G.Britan)和科恩(R.Cohen)、杜賓斯卡斯(F.Dubinskas)、加姆斯特(F.Gamst)等,開始研究公共官僚機構、組織文化和職業文化。
這些研究逐漸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類學者的認可,同時來自社會的認可也日益激發了這類研究,就像羅斯(D.Rose)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日常生活都被裝入了公司的形式(corporate form)之中,盡管我們過去往往對其視而不見”。盡管人類學的“回歸”花費了一些時間,但是人類學者還是能夠迅速適應,開始研究人們非常熟悉卻似乎視而不見的組織生活和公司。越來越多的人類學者和其他學者開始認識到民族志方法的特殊價值,因為它能夠在日常互動的基礎上來審視個人和群體如何建構和解釋組織與社會。
二、霍桑實驗及其方法特征
回顧人類學組織研究時,霍桑實驗是不可忽略的標志性事件。迪克森(W.Dickson)甚至認為,即使在50年后,霍桑實驗仍然是最有影響力的商業企業行為科學研究。這項研究起初是為了檢驗泰勒(F.Taylor)的科學管理原則,但結果卻出現了令人驚訝的轉折,了科學管理的基本原則。在這一過程中,人類學家布朗(A.Radcliffe-Brown)的學生沃納(W.Warner)加入研究團隊并引入參與觀察方法,工人的非正式組織得以被發現,一個新的研究傳統——人際關系學派——由此誕生,并主導了接下來25年間的組織研究領域。但是,在這項有關美國組織的早期研究中,人類學者,特別是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作用,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被人類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者重新認識。
霍桑實驗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只是為了測試物理條件的改變對產量的影響,其成果就是后來最富有爭議的“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與物理條件相比,心理因素對于產量改變的影響更加重要。在第二階段,研究者們采用了大規模的個人訪談方法,目的在于探尋員工士氣(morale)與監管(supervision)之間的聯系。1928至1930年間共訪談了21,126名工人,直到大蕭條引起裁員才終止。研究發現,車問中的小團體對個人的工作行為能夠產生強烈控制。第三階段,直接觀察法(direct observation)成為主要研究方法,實驗人員選出14名工人在隔離的觀察室中進行電話交換機的接線器裝配工作,由三名研究者進行訪談、參與觀察,并對每日產量做詳細記錄。
在設計第三階段研究的過程中,新加入的成員沃納認為,工作組可以被視為一個小型社會,能夠應用田野調查中的觀察技術對其進行考察。他還試圖分離出正式組織的功能,分析其與正式組織之間的關系。人類學田野方法的引入,將這個經典實驗帶入另一個不同的層面,在組織研究中開創了“系統描述工業工作組這樣一個社會組織”的先河。羅斯里斯伯格(F.Roethlisberger)和迪克森(W.J.Dickson)肯定了沃納將人類學方法引入研究的貢獻,也指出了其局限:“本研究中使用的方法理念主要源自沃納。但是他沒有在工業背景下系統應用這些方法……他也建議研究者關注杜爾凱姆(E.Durkheim)、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布朗和齊美爾(G.Simmel)等人的研究,從他們的作品中獲得豐富的背景資料。”
盡管之后許多研究者指出,霍桑實驗在資料獲取、研究設計、實際結果及研究者對結果的分析中存在諸多問題,但必須承認這項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該項目最為重要的貢獻在于,研究的問題和方法隨著調查的不斷深入而變化,由此帶來了新的研究價值。研究項目最初是一個受控試驗,繼而轉為一個訪談研究,并最終發展成為一個定性的田野調查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研究中出現了新的問題,研究者不拘泥于最初的方法,不斷嘗試使用新的方法,而且提出了新的問題。迪克森總結了這一過程:“霍桑實驗開始是一個‘假設檢驗’,隨著研究的推進,逐漸變成‘提出假設’的研究。按照常規程序,這個過程看起來有些像倒退。我們則試圖為其做出一個符合邏輯的解釋。”換句話說,如果那些研究者不選擇“倒退”,那么就不能產生對工人群體詳細而系統的觀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霍桑實驗中積累的豐富的原始研究數據本身,為研究者提供了材料,才使當時及后來的學者重新審視這項研究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霍桑實驗是極力倡導在組織研究中使用民族志和定性研究方法,并且從中獲益的成功案例。
三、人際關系學派的民族志方法與模型
霍桑實驗的研究者將訪談技術和管理咨詢的模型作為主要的研究工具,因此忽略了在理解組織和組織行為中觀察技術和情境分析技術的發展。在霍桑實驗結束后的十年里,人類學的組織研究進展緩慢,其后大多數組織研究者走向了該研究方法的對立面,回歸使用實驗、定量研究方法或者訪談/調查的方法。至20世紀30-40年代,來自人類學和社會學的人際關系學派重新正視這一偏誤,通過各自的研究逐步深化了霍桑研究方法。1943年,沃納與加德納(B.Gardner)在芝加哥大學組織成立了工業人際關系委員會(Committee on Human Relations in Industry),人類學者的網絡不斷擴展。1946年,加德納成立了名為社會研究公司(Social Research Incorporated)的咨詢公司。最早的霍桑實驗研究者曾指出,該項目展示出工作場所中“人際關系因素”十分重要,但是在如何更好地研究這些因素的問題上,不同的研究者有著不同的看法。該領域的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發展出兩種人際關系研究傾向:一是查普爾(E.Chapple)的互動研究;二是沃納的社會分層研究。
查普爾使用“系統”這一分析框架,將組織視為個人關系組成的系統來研究,并試圖通過工業組織的研究實踐,發展出更廣泛的人類學和人類行為理論。他對記錄人們互動行為的系統研究方法有著特別的興趣,不僅通過發放交往問卷(contact questionnaire),甚至通過親自設計一種名叫“互動記錄器”的計算機來測量互動。理查德森(F.Richardson)和沃克(C.Walker)將查普爾發展出的互動研究方法用于研究一個小型制造工廠的雇傭關系。這個小工廠就是后來的IBM公司。研究主要圍繞工廠規模擴張與良性人際關系的關聯性展開,特別測量了規模擴張時期人際交往的橫向和縱向變化。研究發現,公司擴張推動了組織結構變遷,“整合員工、增加凝聚的人際交往增加了;而離問員工、削弱整合的交往減少了”,這也解釋了公司在規模擴張期內,內部人際關系不斷改善的原因。
沃納對待人際關系研究則持有另一種觀念,他將其視為一種路徑,并主張通過民族志方法來研究現代社會結構和變遷。在早期的澳大利亞田野時期,他已經產生出對現代社會開展人類學民族志研究的強烈愿望,認為對原始人的研究應該對現代人有所啟發,傳統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應被引入現代社會研究。他曾寫道:“我研究原始人是為了更好地了解現代人,希望能夠最終將研究置于更廣闊的比較之中。”沃納選擇了著名的揚基城(Yankee city)來研究現代人的社會生活方式。這個項目利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拋棄了對先賦社會階層因素的過分關注,轉而注重對社會行為的直接觀察及訪談,并強調將兩種方法相結合的重要性,要求研究者“詳細記錄細節,即使是最習以為常的細節”。這種詳盡的記錄文本,構成了美國現代社區研究的民族志腳本。源自此項研究的《現代工廠的社會體系》一書,具有鮮明的民族志研究風格。沃納在書中描繪了揚基城一個鞋廠的內部生活動態,并將該工廠置于社區的背景之中,追溯了曾引起罷工的勞資糾紛的歷史淵源。借助寬廣的分析框架,研究者將罷工與不斷改進的生產技術、勞資關系、生產過程的不斷機械化和日益弱化的員工監管聯系起來,由此使作者對研究現代社區的解釋更為可信,也展現了民族志作為文化書寫實踐的特性。布洛維(M.Burawoy)認為,這項研究不同于其他人際關系的研究,遠遠超越了僅僅對生產場所條件的研究,具體考量了“改變20世紀30年代勞動力和資本之間關系的社會、政治和社會力量”。
20世紀40-50年代,美國學術界涌現出了一批工業民族志,研究范圍包括技術革新、激勵機制和工廠生產力。在IBM公司進行技術變革和規模翻番的時候,人類學家理查德森和沃克分析了工廠生活的“社會結構”變化及其對產量的影響。有批評指出,人際關系學派的研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單向研究,有悖于傳統人類學“向下研究”(study down)的傳統取向,并沒有將工廠組織置于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過程進行對話或加以批評。布洛維等學者認為,人際關系學派的模型是勞資關系的管理模型,研究者關注工人之間和上下級之間的關系體系,是為了控制這個體系,與管理目標達成一致。不可否認的是,人際關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貢獻是顯著的,它將特定工作環境中的訪談和互動觀察結合起來,第一次將“文化”這一詞語帶人組織研究,形成了為數眾多的民族志式的研究成果,并孕育了20世紀80年代的組織文化研究。同時,人際關系學派也首次嘗試自上而下地開展人類學研究,關注現代工業社會,強調研究工作環境中交往模式和慣例的價值,引發了后來對于慣例和實踐的人類學理論轉型及對組織及社區研究的特別關注。
四、從工廠內部的參與觀察到更廣泛的情境分析
在人際關系學派受到種種批評和質疑之后,人類學者開始逐漸遠離工業和組織研究,此時工業社會學興起,開始廣泛運用人類學的田野方法。這些研究繼承了人際關系研究的傳統,通過發現工業和社會服務機構的“社會人”,來質疑“經濟人”、“理性人”等概念。由于大量田野方法的應用,這些研究在成果呈現時,或多或少帶有組織民族志的影子。默頓(R.Merton)和他的學生們的研究成為這一類組織研究的經典,如布勞(P.Blau)的《科層組織的動態》(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塞爾茲尼克(P.Selznick)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及其基層組織》(TVA and the Grass Roots)和葛德納(A.Gouldner)的《工業組織的科層類型》(Patterns of IndustrialBureaucracy)、《擅自罷工》(Wildcat Strike)等。
此后,只有少數人類學者研究現代社會的情況得以改觀,組織人類學的方法逐漸轉向情境研究。最為典型的范例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系勒普頓(T.Lupton)主持的工廠研究。人類學“整體參與觀察”方法在該項目中受到重視,研究者不僅把其作為一種民族志的描述方法,還將其作為一種研究社會情境細節的分析方法,借由界定社會情境及互動關系來增進對組織的理解,從更廣泛的角度理解社會組織。這種方法與之前的研究相比更具開放性,最終擺脫了工廠和社會是由結構組成的觀點,轉向分析人們在特定情境中制造意義的方式。人類學組織研究的方法也從初期的觀察參與,發展為“局內人”的參與、“局外人”的整體觀察。
1969年,納德(L.Nader)在名為“人類學家向上看”的文章中,向人類學者提出挑戰:“如果重新發明一種人類學,研究殖民者而非被殖民者,研究強勢群體(power)而非弱勢群體(the powerless)的文化,研究富人而非窮人的文化,那這種人類學會是什么樣的?”這一挑戰促使20世紀70-80年代的人類學者將注意力轉到現代社會的正式組織和工作場所之上,開始采用“向上研究”的路徑,使用“整體觀”研究權力機構和國家科層制度。例如,1980年納德通過觀察美國的兒童,發現了政府組織中隱藏的科層制度,認為是這些制度影響了他們的食物、健康和住房。這些嘗試和實踐對人類學方法和概念產生了重要影響。
如何將民族志擴展到更廣泛的情境中,有學者認為較為理想的做法是“既將更廣闊的秩序作為背景,同時又聚焦一個作為民族志的對象……完成對更廣闊的秩序的再現”,也有學者認為“探尋更大規模體系對日常生活的影響,進一步發現和解釋宏觀和微觀之間的聯動關系”。因此,這個時期的人類學組織研究強調從更廣泛的角度研究工作和工作場所,將正式組織置于現代階級社會更廣闊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之中來考察。這類研究應用民族志和民族史方法發展出新的分析框架,并將這一方法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框架中將工業企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維度納入分析范疇,審視了工廠和跨國公司等組織中的工作,強調工人和管理者之間的權力差異,并以此為中心試圖從公司生活的圖景中區分管理層的理性和管理理論的“迷霧”。
沙伐(H.Sara)使用這個方法,分析了美國服裝業的外逃工廠(runaway shops,指為了逃避賦稅或者法律監管而遷移到國外的工廠)在勞工招募過程中給美國和第三世界女工帶來的影響。納什(J.Nash)考察了跨國石油公司及其對美國和世界經濟體系的影響,撰寫了具有濃烈民族志色彩的《跨國公司人類學》一文,描繪了跨國公司擴張的近代史,將其同廣泛的政治經濟力量連接起來,解釋在這些背景情境中的個人和組織行為。此外,她還研究了美國工業從大規模生產向高科技軍工生產的轉型過程,以及這種轉型對家庭和社區的影響。加姆斯特(F.C.Gamst)提出人類學現代組織研究的另一條路徑,主張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志核心方法,強調“本土觀點”的表征,通過超越“主位”的方式滲透和考察社會現實。他對火車司機的研究展現了這一傳統。加姆斯特在鐵路引擎服務部門工作了6年半,同時開展田野和問卷調查,從機械師的視角發展出鐵路系統民族志。這一研究彰顯了“本土觀念”的特點,也印證了貝特(S.P.Bate)的“洞見總是來自內部”的觀點。
雖然此前定性的組織研究并不鮮見,但大多數采用哈佛式的案例研究法,很少使用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民族志方法的一個明顯優勢在于,降低了犯錯誤的可能性,能夠避免研究者用自己的意義取代實際參與者的意義。這些卓有成效的組織民族志研究,令更多的組織研究者意識到,應該給予當地人更多的表述機會。
五、組織民族志的特點
組織研究一直作為管理學的主陣地,吸收了管理學眾多優秀的理論和方法,也因此產生了某些局限性。佩蒂格魯(A.Pettigrew)在《覺醒的巨人》一書中,批評組織研究缺乏穩定且可行的方法論指導,缺乏歷史、情境和過程的觀點。人類學恰可以彌補其不足,為組織研究帶來不一樣的方法和理論視角。此外,作為對佩蒂格魯觀點的補充,貝特指出的“以行動者為中心”(actor-centered)亦是人類學的另一重要特性,這是一種局內人向外看(insider-out)的方法,而不是局外人向內看(outsider-in)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推進組織研究的發展進程”。綜合來看,人類學組織民族志具有如下四個特點。
第一是歷史的觀點。相較于管理學對前瞻性概念(如“愿景”、“預測”、“計劃”等)的偏愛,人類學顯然更重視歷史,注重從儀式、神話、傳說、民謠和軼事等日常生活中找尋過去,將過去帶到現在和未來,認為只有把現在和未來與過去聯系在一起才有意義。“每個人都是那個自己所處的并限定了自己的歷史傳統的產物”。組織民族志不是簡單地關注歷史,而是關注社會中保留至今,影響和形塑當下人們行為方式的文化慣習。典型案例是貝特(S.Bate)對英國鐵路系統文化圖式的研究。研究發現,蘊含其中的“思維習慣”大多形成于一個世紀以前,但在今天的組織中依然活躍,由此造成了現在日常管理中的混亂,并最終導致組織的衰敗。這樣的歷史觀對于解釋組織研究中發現的問題及其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是情境的觀點。貝特、派依(A.J.Pye)、珀塞爾(J.Purcell)和可汗(R.Khan)在對英國醫院及醫療體系的一項民族志研究中發現,英國醫院存在許多問題,包括高層團隊軟弱、董事會結構混亂、管理者和資深臨床醫生之間關系惡劣等。這些問題并非局限于醫院“自身范圍”(local)之內,而是源于其所嵌入的不同組織情境、行業情境、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情境和政治情境之間的一系列復雜互動。人類學的專長之一在于把個人置于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之中,置于行為發生的情境之中,觀察其日常活動。通過在“個人”和“社會”之間,在微觀和宏觀之間建立聯系,人類學能使研究者達到或更接近其他組織研究者無法達到的地方。“理論是我們的專長,我們可以在微觀的個體行為和宏觀的社會情境之間架起橋梁,找出隱藏于其中的模式,進而知道如何把個人行為作為整體行為模式的一部分進行理解”。同時,人類學也在不斷修正“整體”和“情境”概念,將更多后現代的觀點及參與全球化的后工業組織納入研究范圍。哈奇(M.J.Hatch)和舒茨(M.Schultz)對這一趨勢進行了解讀:“在后工業的情景下研究文化,要求我們拋棄單獨的、社會化的、組織的部落。在后工業時代,部落變得碎片化了,它們的連貫性破裂了,多樣性和解釋學取而代之。在這種文化的框架下,承載意義的是文本,而不是部落,這些文本在電子空間中傳播,無數不知姓名的人對其做出自己的解讀,這些解讀又會形成另外的文本,繼續被無窮無盡地解讀。”
第三是過程的觀點。組織需要其成員之間不斷協商和互動以完成目標工作,因此關注組織生活正式與非正式兩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變得尤為重要。人類學者更偏重組織生活中非正式的一面。霍桑實驗及布若威(M.Buroway)和羅伊(D.Roy)等人的成果都是對非正式過程研究的范例。道爾頓(M.Dalton)對美國四個公司中官方行為和非官方行為之間分裂和聯系的參與觀察屬于同一類研究。研究非正式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關注“競爭領域”(contested terrain),其中不同的亞文化或者觀點相互競爭,建立起脆弱的共存關系。古爾德納(A.W.Gouldner)提出了“縱容模式”(indulgency pattern)概念,用來描述管理者和員工之間非正式的,既緊張又互相妥協的動態系統。這一系統充當了二者關系之間的緩沖劑和劑,管理者放松對員工完全服從的要求,比如繞開正式規則,允許員工借用公家的工具和設備,甚至允許他們把甘油炸藥帶回家用來釣魚等,以此換取員工的合作。古爾德納和布若威的研究,首次引起人們關注員工和管理者共同參與的“游戲”。在“游戲”中,雙方并非針鋒相對,而是形成了共同利益。員工與管理者之間不是沖突關系,而是一種微妙的合作,是各方在非正式規則的基礎上形成的相互依存關系。當然,這種“游戲”通常不穩定,總有一方想要多占一些便宜。可見,“文化”不是管理學組織研究想象的那種靜止、固定的實體,而是一個過程,甚至本質上是一個政治過程,其中的意義在互動過程中被各方重新定義,而人類學的任務就是梳理、描述和解釋該過程。這就為研究組織提供了更加寬泛的新的視角,不僅關注組織生活中的工作本身,還關注其中社會的、非工作的部分。
第四是以“行動者為中心”。人類學的中心任務是“表述”(represent)他者的生活,特別是從“當地人的觀點”角度去理解當地人的感受,關注當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世界。這種方法是人類學的特色,在研究中不是問“我如何看待他們做的事情”,而是要問“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做的這些事情”。“人類學家的任務就是要發現,當地人是如何從人類學家認為一團亂麻的日常生活中創造秩序的”。有學者認為,“行動者為中心”的方法難以達到,因為人類學家只能接近當地人的觀點,最終還是通過自己的框架重構他人的世界。但不可否認的是,有些研究成功進入了“當地人”的世界。加姆斯特在鐵路引擎服務部門供職六年半,從機械師的角度寫成了關于鐵路系統的民族志;格里高利(Kathleen Gregory)研究了硅谷計算機公司中專業技術人員的“觀念世界”。這些民族志研究都體現了“豐富而真實”和“內部生活”這兩個特點。其中值得關注的并非上述正式系統和非正式系統之間的行為差別,而是所謂的文化“專家觀點”和當地人“普通觀點”之間的差異。關注這種差別的組織民族志能夠從新的視角研究思維、文化和行動之間的關系,最終構筑某種能夠解釋日常行為的、實用的理論。
六、結語
篇6
教育人類學認為,教育是人的身心發展的過程,包括個人在不同生命成長周期的發展。學術界通常將教育人類學細分為兒童人類學、青年人類學、成人人類學和老年人類學等研究領域。國外兒童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Children)研究已有許多重要成果。2001年,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批準成立了兒童、青少年與童年人類學委員會,表明了兒童人類學在國際人類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兒童人類學研究在我國尚屬起步階段,但已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隨著近年來國家對學前教育、小學教育的日益重視,我國兒童人類學研究的前景更為廣闊。
兒童人類學研究包括文化取向和哲學取向兩大視角。哲學取向的兒童人類學研究關注兒童的本質和發展,重視兒童的可塑性和可教育性,強調教育者(教師、家長等)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的作用。文化取向的兒童人類學研究認為,兒童是文化的構建,應將兒童視為童年的主體,在研究中應充分傾聽兒童的聲音,關注不同文化環境下兒童的文化習得差異,特別是性別、族群、階層等因素的影響。本期教育人類學專欄的4篇論文,分別從兒童人類學的兒童觀、教師的兒童觀、童年民族志書寫以及兒童與秘密的個案研究等不同角度切入,對“兒童與文化”等相關主題進行探討,以期引起國內教育學界和人類學界對兒童人類學這一研究領域更多的關注。(海 路)
摘 要:兒童人類學的兒童觀可以概括為如下3個主要方面:文化之網上的兒童、主位的兒童、具體的兒童。兒童人類學的兒童觀對分析教育問題很有價值,例如對當今貧困地區兒童教育、兒童個性發展、兒童自主發展這3個議題進行的分析。
關鍵詞:兒童人類學;兒童觀;兒童教育;教育人類學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124(2013)05-0027-05
兒童人類學①屬于人類學范疇,遵循人類學研究的準則,堅守人類學研究的學科立場,運用人類學研究的方法論和具體方法開展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兒童人類學的兒童觀體現了其在兒童研究方面的一些基本主張,對分析當今的兒童教育問題很有意義。
一、兒童人類學的兒童觀
兒童觀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界定兒童,這是所有有關兒童研究和兒童教育工作中最為基本的概念。人們心目中認為兒童是什么,就會怎么對待兒童;認為什么是好的兒童,就會把兒童的發展引導到什么方向。不過,由于人類學界在研究中關注于特定情況和背景,因而在關于不同年代和地方的兒童與童年的研究中反對對兒童和童年下一個統一的定義 [1 ]。但是,兒童人類學研究領域也形成了關于兒童的一些共同看法,可以回答兒童人類學視野里的兒童是什么樣子的。
1. 文化之網上的兒童
當今兒童人類學研究一個重要淵源是人類學的文化與人格學派,該學派的人類學家所用的比較研究的方法,使他們發現了不同文化中的價值觀和行為期望如何影響不同文化中的成員對他們的孩子進行教育或養育的方式,使得不同社會中培養出的兒童是不同的。例如,文化與人格學派的代表人物、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米德(M. Mead)在其享譽世界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中分析了薩摩亞兒童的成長歷程,其中涉及嬰兒的出生,薩摩亞人對兒童的哺乳、照管,兒童游戲與社交等方面,并發現薩摩亞青少年在青春期沒有美國青少年所經歷的各種情況,就源于他們在成長中的不同經歷,而兩種社會中青少年的不同經歷與社會文化是息息相關的。米德還在文化與兒童性別角色的形成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米德根據其在新幾內亞的三個原始部落中田野調查研究所寫成的《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一書中提出,男女兩性在人格特征上的許多差異與性別差異本身無關,而是與兩性受到教養的內容和方式方面的差異緊密相關的,而這種差異又是與該社會中的文化相聯系的 [2 ],這糾正了之前人們普遍認為的男女兩性不同的特征和社會行為方式是由兩性不同的生理結構決定的觀點。
關于兒童的其他大量人類學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社會中,塑造童年的社會文化基礎是不同的,其中包括對童年的形成有至關重要影響的方面。沒有對某一賦予童年以意義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充分的了解,關于童年的理解就是不可能的 [3 ]。例如,不同社會中人們養育子女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兒童習得文化、參與社會生活實踐的方式以及兒童的日常生活形態是不一樣的。不理解該社會的文化背景,就難以理解這一社會中的兒童。
對近些年人類學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人類學家格爾茲(C. Geertz)說:“馬克斯?韋伯提出,人是懸在由他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觀點。于是,我認為所謂文化就是這樣一些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 [4 ]任一兒童也是某一文化之網上的兒童。如果再細化的話,“文化之網上的兒童”,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文化層面的復數,即不同文化環境下的童年是不一樣的;二是個體層面的復數,即同一文化環境下的不同兒童也是各不一樣的。
正因為兒童是處于文化之網上,不同文化塑造了不同兒童,所以兒童人類學提出要關注把兒童的生活和經驗加以普遍化所帶來的問題。有關童年的研究者提出,既要關注有獨特和不同經驗的個體兒童,也要關注帶有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和政治特征的群體性兒童 [5 ]。簡而言之,任何兒童的文化背景都是各不相同的,任何兒童分別在不同的文化之網上度過了自己的童年。
2. 主位的兒童
所謂主位的兒童,通俗的理解即兒童自己視野里的兒童。根據格爾茲的觀點,在對文化的解釋中,不可能重鑄別人的精神世界或經歷別人的經歷,而只能通過別人在構筑其世界和闡釋現實時所用的概念和符號去理解他們 [6 ]。馬林諾斯基的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去描述闡釋的見解,在格爾茲的闡釋人類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一以貫之的指導意義的地位 [6 ]。正是因為人類學堅持的“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使得兒童人類學能夠從兒童主位的視野來分析問題。
拿在兒童生活中占較大比重的兒童游戲來說,兒童主位視角的分析特別有意義。在日常生活中,大人對兒童的游戲熟視無睹或在游戲引起“搗亂”情況下給予批評的情況很多,例如,大部分兒童喜歡并經常做的“假扮角色”的游戲,在很多成人看來只不過是“小孩子家”的玩耍罷了;再如,有些家長給兒童買槍炮之類玩具時,兒童或許并不將之當作槍炮來玩耍,而是將之拆卸下來,當作電話玩具等來使用。這時大人常會說:“我花那么多錢買給你的槍,你卻把它拆了!”更有甚者,斥責或打罵兒童。人類學關于兒童游戲的饒有興趣的研究,則肯定了兒童在所謂“假扮角色”游戲中呈現的是他們眼里的真實角色,人類學因而對之進行了細致的分析:游戲對兒童而言是一個有主體意義的事件;游戲是兒童以自己的方式闡釋對社會生活的理解;是兒童表達或處理其社會生活經驗的方式;兒童在游戲中主動學習有關社會文化習俗和生活技能②。
從關于游戲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兒童人類學的研究對成人有關兒童所做所想的假設提出了挑戰。因此,兒童人類學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分析當前有關兒童研究的理論,也有助于包括實踐工作者在內的所有與兒童發展相關的人員反思當下有關兒童日常生活和經驗的觀點。
正是諸如游戲方面的上述研究,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類學界人士呼吁,在研究中還要把兒童當作研究的參與者。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兒童、青少年與童年人類學委員會主席迪帕?庫瑪?比赫拉(Deepak Kuma Behera)提出:該委員會成立的初衷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目標和意圖,就是鼓勵那些把兒童本身作為主動參與者的研究,而不是像過去常常出現的那樣,僅僅把他們作為研究的對象 [7 ]。
3. 具體的兒童
如前所述,兒童人類學關于兒童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是文化。需要說明的是,文化視角的兒童研究并不是屬于兒童人類學所獨有的。但是,與其他方面文化視角的研究稍加比較不難發現,其他方面研究中的“文化”多是宏觀的、抽象的,很少涉及具體的文化;而人類學研究的獨特之處正在于,是對具體的文化進行研究,因而關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兒童的研究便能發現其他研究中難以發現的關于兒童的具體情況,所研究的兒童是具體的。對于兒童發展的各個方面,如認知、語言、游戲等方面的研究都是非常具體的,因而能夠詳細地描述出所研究兒童的具體情況。
例如,在認知方面,關于利比亞的佩里人計算能力的田野研究發現,雖然佩里地區的人們沒有現代社會所謂的數學方面的認知活動,因為他們不知道西方學校教育的課堂中所教授的基本的幾何概念,也不了解基本的計數或度量方面的知識,沒有西方課堂教學中專門性、程序化的數學認知活動,但是佩里人的數學認知活動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發生的,佩里兒童學習的數學知識是具體的和實踐性的。雖然佩里的兒童在做西方教育中用于測試數學能力的試卷時,成績通常是很差的,但是他們卻具有西方社會的學生所不具有的其他方面的數學認知能力。例如,估算大米的能力就是佩里人普遍具有的一種非常強的能力。一般地,佩里的兒童在只看一下一堆大米的情況下,就能精確地說出這堆大米能裝多少杯,而西方社會的兒童對此卻是望塵莫及。佩里兒童具有這種能力的主要原因是,大米是佩里重要的一種糧食,在市場上能夠精確地估計出所賣或所買的大米的數量是這個地區的人們必須掌握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能。這樣的研究就對佩里地區兒童的認知活動進行了非常具體的分析。
再如關于兒童游戲的研究。有關我國農村兒童游戲活動的研究發現,玩耍和游戲是兒童期的人生內容之一,是兒童“自己”的事情,因而成人很少給予干涉,成人也認為:“小娃娃不就是耍嘛!” [8 ]故盡可能讓兒童去玩耍和做游戲。農村地區兒童游戲有基于當地社會生活和生產的很多特點,有與當地社會生活和生產緊密相聯系的具體內容,這就很具體地揭示出所研究地區的兒童游戲情況。
正是關于具體的兒童的研究,能更有說服力地呈現出兒童生活形態的多樣性以及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兒童的獨特性,也清晰地呈現出兒童的日常生活結構及其它賴以形成的社會文化基礎,以及不同社會文化促成不同童年的過程,為其他相關學科及政治領域提出的保護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下兒童教育的不同資源與方式,提供了很好的佐證。
二、兒童人類學兒童觀的啟示:對當前三個兒童教育議題的分析
從兒童人類學的兒童觀來看,當前有關兒童教育中的很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
1. 貧困地區的兒童教育
當前,我國貧困地區的兒童教育得到了很多方面的關注,尤其是在促進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發展的背景下,政策領域給予貧困地區的兒童教育很多方面的扶持,有關社會人士和機構也給予援助。在各種援助中,所參考的標準多是發達地區兒童教育的標準。從兒童人類學的角度來說,這種做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例如,在師資建設方面的兩個做法就很值得反思,一是向貧困地區輸入師資,這些師資既包括發達地區的教育工作者,也包括發達地區的熱心于貧困地區教育發展并有一些文化水平的其他人士在貧困地區擔任教師;二是根據發達地區經驗給當地教師進行培訓,既包括在當地進行的培訓,也包括把當地教師送到發達地區進行的培訓。上述做法忽略了去了解當地作為教育中心的“兒童”的具體情況,如他們成長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對兒童認知、語言等方面的影響,而一味地給予“落后”的評價,然后把發達地區的一些價值觀或具體做法強加給當地。根據大量的人類學研究可以推測,長此以往,恐怕會出現學生在校內外經歷“非連續性”情況,也恐怕會帶來更多相關問題。
所謂“非連續性”是20世紀70年代一些西方人類學家在研究少數族群學生學業失敗問題時提出的。根據這一理論,教師和學生間在互動、語言和認知方式方面出現差異的話,則會導致學生在家庭和社區中所習得的被認為合適的行為與學校老師的期望之間的非連續性,而學生的互動、語言和認知方式與他們的家庭和社區背景是緊密相聯系的。這種非連續性導致一些學生在學校里出現學業失敗。例如,從互動規則方面來說,其社會與文化背景和學校的社會與文化背景相吻合的學生已經了解了與教師進行交流的一些隱性規則。相反,來自于其他文化與語言背景的學生則必須用寶貴的學習時間來學習這些規則,但是經常并不能學好。雖然這些學生在進入到學校中時具有多方面的交流能力,但是這些能力由于與學校所認可的能力不相吻合而被忽視了。近些年有人類學家在研究中也發現,所謂“主流”的兒童培養方式和邏輯背后其實帶著深刻的“階層烙印”。因為這種方式需要父母具備相應的物質基礎、教育文化水平以及“時間資源”,而這一切往往只是處于優勢地位的人群才擁有的 [9 ]。由于這種非連續性的存在,兒童在學業中很容易出現學業失敗的情況。
除了師資支持之外,在硬件建設、課程改革等方面也呈現很多類似的情況。從兒童人類學的角度來說,如果在幫助貧困地區兒童的過程中,用所謂發達地區的標準來發展貧困地區教育,把所謂“發達”地區群體的資源“資助”給貧困地區――人類學的諸多研究表明,貧困地區可能在經濟發展方面貧困,但是在文化發展方面并不缺乏“資源”――實是另一種“文化殖民”,則可能會帶來更大的不公平。
因此,貧困地區的兒童教育需要吸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實例證明,國外一些在基于人類學研究基礎上開發的教育援助項目是很成功的,值得當下我國借鑒。例如,為本土夏威夷兒童開發的“克姆哈馬哈早期教育項目”,為納瓦霍人設立的“拉夫洛克示范學校”,以及對墨西哥裔美籍孩子的介入研究。基于教育人類學的研究,另有研究者在維果斯基“最近發展區”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解決策略,認為由于在同一社會中不同文化群體之間智力活動發展的可能性不是完全一樣的,因而個體從智力活動中得到的抽象知識與在一定的文化中所具有的積極的日常知識之間存在著分歧,故最近發展區理論不但包括孩子如何通過教學獲得知識方面的觀點,還涉及社會文化方面的內容 [10 ]。
當然,完全根據貧困地區的情況,遵循當地人現有價值體系和認知方式等進行教育,是難以幫助這些地區發生實質性改進。但是,無論如何,貧困地區的兒童教育援助需要的是在充分了解當地社會文化情況、當地兒童發展的特征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進行。
2. 兒童個性發展
如前所述,任何兒童都是其所在文化之網上的兒童,每個兒童發展的情況肯定不是一樣的。因而,因材施教,針對不同兒童的具體情況進行教育是最基本的教育理念之一。但是,在教育實踐中,不因材施教的情況卻普遍存在,例如,有的教師看到有學生坐在椅子上不時動一下,就批評他們上課沒有認真聽講,“你看看人家都在認真聽課,為什么就你總搗亂?”有的家長看到其他家長給孩子報名去學鋼琴、奧數、英語等課外班后也給自己的孩子報名,并聲稱是為了孩子好。諸如上述的兒童培養目標和具體方法都沒有考慮到兒童的個性發展。這些問題的出現既源于當前我國教育研究中缺乏從文化的角度對兒童進行研究,也源于教師和家長們沒有深刻地理解個性發展的理念,源于他們沒有充分地了解兒童,缺少了解兒童的具體方法。一切教育行為如果沒有建立在對學生的充分了解之上,那么都是缺乏針對性的,其結局必然難以取得實效甚至是無效的,更為甚者,會阻礙學生的健康發展。
兒童人類學所分析的文化之網上的兒童,從兒童主位的角度來分析具體的兒童,都有助于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具體地了解所面對的每一位兒童。只有真正地從每一位兒童的角度來分析,才能真正地了解他,如他的認知特點、他的情感需求、他的人際交往特點等。例如,通過這樣的研究可以發現,有的兒童上課時一直一動不動坐著就難受,因而可能要不時動動身子,這并不能表明他們不認真,就如同有的兒童做作業時習慣聽音樂,或需要身邊有人陪著他,這些都是兒童個性的區別。再如,并不是所有的兒童都適合學習奧數或鋼琴,不同兒童在這些方面既有先天差別,更有后天家庭和社會文化背景方面的區別。
那么,教育工作者如何充分地了解兒童個性?兒童人類學視野下的兒童觀從宏觀上提供了方向;在具體做法上,則需要教育工作者關注每一位兒童日常生活和學習中點點滴滴的事例。格爾茲指出,典型的人類學家的方法是從以極其擴展的方式摸透極端細小的事情這樣一種角度出發,最后達到那種更為廣泛的解釋和更為抽象的分析 [4 ]。要細致地來了解和研究兒童的話,也需要細致地來研究兒童的諸多“雞毛蒜皮”的小事。
3. 兒童自主發展
幫助兒童自主發展是當今教育界特別強調的一個重要教育理念。兒童人類學的研究者也特別主張兒童自主發展的理念。哈德曼(C. Hardman)認為,應當把兒童作為有自己權利的人來研究,而非教育的容器。她指出,兒童人類學的研究“是為了發現兒童是否擁有一個自我調節和自主的世界,而不僅僅是早期發展中對化的反應” [11 ]。
但是,在教育實踐中,不難發現,兒童自主發展的情況卻不容樂觀。很多兒童仍然是在家長和教育工作者的指令和安排下學習,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在兒童與成人的溝通中,成人的有關要求沒有真正地讓兒童理解,兒童只是被動執行罷了。成人作為兒童發展的引導者,需要給兒童的發展提出方向和一些具體要求,兒童只有真正地理解了成人的要求,明確這些要求的意義,接下來的言行才是自主的,否則仍然是被動的。例如,很多家長和相關教育工作者要求兒童在學習時要“認真”,但是卻常常發現兒童沒有做到“認真”,如一會兒去喝水,一會兒東張西望,一會兒要看電視,等等。于是家長就說:“我已經告訴你要認真學習,你為什么不認真?”有些兒童則反駁說:“我已經很認真了!”聽到這句話,家長容易得出“學習不認真還嘴硬”之類的結論。實際上,在這一過程中,成人與兒童之間出現分歧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大人把自己的認真標準強加給兒童,如正襟危坐,而兒童處于兒童期的天性則讓他難以這樣做,所以是被動地“執行”成人要求;二是兒童并沒有真正地理解成人所謂的認真,或者說成人所提出的“認真”這一詞對兒童來說過于抽象。沒有讓兒童真正理解“認真”一詞而要求他們認真的話,他們是難以做到,更無法自主地做到,只不過是在成人的要求下“執行”認真罷了。但是,如果告訴兒童,所謂認真學習就是“10分鐘內專注于學習內容,沒有東張西望、看電視等與學習內容沒有關系的行為”,兒童就容易理解了。只有兒童真正地理解了成人的要求,才能主動用之來管理自己言行,才能做到真正自主地發展。
因此,成人只有在充分地關照并尊重兒童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經驗的情況下,兒童才能達到真正的自主發展。
需要提出的是,主張兒童自主發展,并不代表放任兒童發展。在兒童教育中,成人的主導地位是不可動搖的,成人的引導與兒童的自主發展是不相矛盾的。我們所反對的是,主要根據成人意志、不考慮兒童發展具體情況和兒童自主性的兒童教育。
以上只是分析了當前兒童教育中的三個議題。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一些議題也很值得從兒童人類學的視野進行分析。無論是教育理論工作者,還是教育實踐工作者,都可以汲取兒童人類學的成果,盡可能充分地了解兒童,用盡可能科學的方法改進兒童教育工作。
注 釋:
① 在國內,兒童人類學也被稱為童年人類學。盡管兒童與童年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學術界,關于兩者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主要觀點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本文也將二者視為同一。
② 相關內容請參見如下兩篇文獻的有關分析:吳航.美國兒童游戲研究的文化人類學傳統――海倫?斯瓦茨門理論述評[J].學前教育研究,2007,(6):12-15;涂元玲.村落中的本土教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59-73.
參考文獻:
[1]Myra Bluebond-Langner,Jill E. Korbi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Childhoods:An Introduction to“Children,Childhoods,and Childhood Studie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07,(2):241-246.
[2][美]米德. 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M].宋 踐,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3]Robert A. Levine. Ethnographic Studies of Childhood:A Historical Overview[J].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07,(2):247-260.
[4][美]格爾茲(Geertz,C.).文化的解釋 [M].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
[5]Myra Bluebond-Langner,Jill E. Korbin,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Childhoods:An Introduction to “Children,Childhoods,and Childhood Studie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07,(2):241-246.
[6]王海龍.導讀一:對闡釋人類學的闡釋[A].[美]吉爾茲(Geertz,C.).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7][印度]迪帕庫瑪?比赫拉.國際視野下的兒童權利――介紹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兒童、青少年與童年人類學委員會(楊春宇譯)[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1):5-10.
[8]涂元玲.村落中的本土教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9]肖索未.社會階層與童年的建構――從《不平等的童年》看民族志在兒童研究中的運用[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1,(1):36-38.
篇7
關鍵詞:跨文化理論 意識 文化
修訂后的大學英語教學大綱規定其教學目的是“培養學生具有較強的閱讀能力和一定的聽說寫譯能力,使他們能用英語交流信息。大學英語教學應幫助學生打下扎實的語言基礎,掌握良好的語言學習方法,提高文化素養,以適應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的需要”[1]1。現階段我國大學外語教學實現上述教學目的的主要途徑就是通稱的精讀課,但長期以來大學英語精讀課成了教師逐字逐句分析詞匯語法結構,學生課堂上記筆記,考試背筆記,局限于語言知識細節的滿堂灌。作為交際工具載體具有鮮活生命力的語言成了枯燥、毫無趣味的死板材料,學生為了考試而死記硬背這些語言材料。實際上,語言作為交際的工具、文化的載體,不應當僅作為抽象的語言材料來傳授學習,而應當結合與其相關的文化因素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傳授,語言的教學和學習必須聯系文化因素。
一、跨文化理論(Cross-Culturalism)與語言教學的基本理解
學界普遍把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1945年發表的《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視為跨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雖然跨文化研究的歷史不長,但其反映的社會現象卻可以追溯到原始部族間的通婚(intermarriage)。部族間的通婚不僅促進了部族人口素質的改善,也帶來了部族間的文化交流。現代跨文化交際是在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是研究世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并解決由此帶來的文化沖突為中心和目的,它綜合了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及心理學等各學科對文化沖突的見解,對語言交際、非語言交際、交際手段、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和認識行為等交際要素進行分析,闡釋跨文化交際的內涵,認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際過程中由于各交際要素上的差異可能造成交際障礙,合作受阻,交際失敗。在日常跨文化交際活動中,交際一方通常運用第二語言進行交際,因此交際成功與否不光受到第二語言的熟練程度、語境、交際策略的限制,還受交際雙方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語言心理、、習俗禮節等制約]2]68-72。
“文化”一詞源于拉丁語,意為土地的開墾、植物的栽培,后轉義為人的身體和精神培養,特別是藝術、道德、天賦的培養。人類學家和哲學家都給文化下過自己的定義。所謂文化,語言學家Douglas H. Brown說,“文化是信念、習慣、生活模式和行為的總和,這一切大致上為占據著特定地理區域的人們所共有。我們每行一事,無一不隱藏著文化的含義,留下文化的足跡,文化使一群人或一類人與另一群人或一類人區別開來。”[3]11美國文學家Kiluck John則認為“文化是歷史所創造的生存式樣的系統,既包括顯型式樣,又包括隱型式樣,它具有為整個群體共享的傾向,或在一定時期中為群體的特定部分所共享。”[4]327凡此種種理解和觀點都沒有超越杰出的文化人類學家泰勒(E. B. Taylor)1871年就給文化所下的明確而根本的定義,他認為:文化,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5]79。通而觀之,文化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文化是藝術、道德等社會意識形態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機構的總和,而廣義的文化則包括人們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作用于語言的文化因素應該是人們創造的一切的總和,是廣義上的文化,它涉及并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同時,文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還是個動態的、具有時空維度的概念。相同地區不同時代,相同時代不同地區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都存在著千差萬別,存在著主導“話語”,存在著主導的文化和主導的話語,要想進入其主導文化就必須了解并操縱其主導文化話語。
文化大系統的其他要素必須由語言來傳播,而語言本身是構成文化大系統的要素之一,這便是語言是作為文化的
一部分和作為文化傳播媒介的雙重性質。六十年代中期,人們開始意識到文化在語言教學中的作用。語言學家和外語教育理論家們開始擺脫索緒爾(Saussure)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喬姆斯基(Chomsky)的轉換生成語法及結構心理學的長期影響,意識到社會文化在語言教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語言學家拉多(R. Lado)在其《語言教學:科學的方法》(Language Teaching: A Specific Approach)中指出:“我們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語言。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準則,就不可能真正學到語言。”[6]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語言和文化的關系:文化包括語言,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同時,語言又是文化的載體,人類所有的文化現象都在語言中得到反映。文化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文化的民族和社會屬性同樣也體現在其載體――語言上,即所謂的語言鑲嵌在文化中。
因此,為了在不同語言之間進行交流為目的而學習掌握一門語言,除了掌握其聽說讀寫譯等技巧外,還要了解它所承載的文化要素。繼拉多之后,海姆斯(D. H. Hymes)1972年發表了著名的《論交際能力》(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指出“一個學語言的人,他的言語能力不僅包括他是否能造出合乎語法的句子,而且還包括他是否恰當地使用語言的能力”[7],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交際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這一概念,認為一種語言的習得不能脫離社會文化的客觀環境,提出了交際能力的四個要素,即語法性、可行性、得體性和現實性,后兩個因素和文化直接相關。但是語言學界對這一理論問題沒有一致的看法。學界普遍較為接受的是卡納爾和斯溫(Canale & Swain)提出的語言交際能力理論,認為語言交際能力至少應包括四個方面:語法能力(也稱語言能力,即linguistic competence,指掌握有關詞匯和語法規則的知識)、社會語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即關于語用方面的知識,使語言運用得體)、語篇能力(discoursal competence,即掌握和組織連貫的話語而不是孤立的句子的能力)和會話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即運用言語的和非言語的手段進行有效語言交際的能力);要進行有效的語言交際,僅僅掌握語言能力是不夠的。使用同樣的語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方式進行交際交流,其含義可能完全不同;而其中作為交際主體的人卻又是作為其文化的具體載體而出現,由他體現出來的文化上的千差萬將對交際的過程產生重要的影響。文秋芳教授1999年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模式。該模式包括了前人所講到的交際能力,還增加了跨文化能力(Cross-Cultural Competence);其中交際能力包括三部分:語言能力、語用能力和策略能力;跨文化能力也包括三部分: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對文化差異的寬容性和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而這三種跨文化能力都要求對兩種語言和文化相當熟悉,尤其是母語及其文化對于深刻理解外語文化極其重要,應該有它在外語教學中的地位[8]55-120。由于語言教育理論家的努力,文化背景對語言的影響日益為人們重視起來。
二、文化因素在精讀教與學中的重要性
我們的英語教學一直都比較注重語法,不重視英語語言文化的傳授和交際能力的培養,許多大學生雖然高考成績不錯,但對所學語言涉及和反映的文化所知甚少,這些都增加了大學英語教師在精讀課中傳授英語知識培養學生語言技能的同時,介紹英語國家社會文化的緊迫性。以現在幾乎每個非英語專業的大學生都要參加的四六級考試中的聽力測試為例,雖然聽力材料中明確地談到測試題目中的答案,但是學生由于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在聽的過程中不能形成聽力識別的興奮點,造成理解上的障礙。如1991年6月六級試題中的第16題:
What are you advised to do when you get a wrong number in making a long distance call?
A)Check your number and call again.
B)Tell the operator what has happened.
C)Ask the operator to put you through.
D)Ask the operator what has happened.
雖然聽力短文最后一段明確指出遇到這種情況該怎么辦“call the operator and explain what happened”, 卻有將近一半的考生未能選對正確答案B)。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也許是他們缺乏這一特定的背景知識,不知道在美國打長途電話遇到困難時可以向長途臺接線員(operator)求助而形成聽力理解上的障礙。有20%成績較好的考生誤選A),顯然是根據自己的經驗,想當然地回答問題[9]16。誠然,如果考生的聽力能足夠好,聽懂語言材料并答對問題也許根本不成問題。但是如果考生掌握了這一背景知識,即使聽的能力一般也能夠聽懂并完成試題。其實,老師如果在上課時(如外教社《大學英語聽力》第二冊第三課接打對方付費電話)稍微增加一些背景知識的介紹,學生遇到類似問題就可以自信地選出答案,不必瞎猜。
三、利用一切機會創設課堂語言環境,傳授社會文化知識
綜上所述,大學英語教師應該也可能利用一切機會融社會文化背景于教學之中,因為學生在中學時期打下的良好語言基礎可以幫助教師部分地從枯燥繁瑣的語法講解中解脫出來。教師可以利用具有豐富文化蘊含(culture-loaded)的詞語、句子和情景進行介紹,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詞語的構成和運用、句子的含義和課文語篇。
詞語是語言的構成要素。自從有文字以來,語言(表現為詞匯)成了記載人類生活、傳播人類智慧的載體。就以最常見的breakfast為例,恐怕大學生當中知道其構成及含義的并不多。breakfast是由break(打破)和fast(齋戒)構成的,因為每天的第一餐打破了前一天晚上至第二天早上就餐前不吃不喝的齋戒狀態,因此,這一頓就是breakfast(早餐)。了解了這些,這個單詞比乍學之時的一個個毫無意義的字母好記多了。在講到motel(汽車旅館),drive-in等詞的時候便可適當介紹美國的汽車文化。motel由motor(汽車)+hotel(旅館)構成,指設在公路兩旁不僅提供自己開車的旅客住宿,還提供汽車“住宿”的車庫或停車場的路邊旅店;而drive-in則指顧客無需下車即可得到服務,如drive-in restaurant或fast-food drive-in(“免下車”餐館或快餐店),drive-in movie/cinema(“免下車”電影/電影院),drive-in banks(“免下車”銀行)。這樣,讓學生既了解了文化,又了解了構詞法,增加了詞匯學習的樂趣。
當然,教師不僅能在詞匯上做文章,還可以利用課文來營造英語氛圍。教師在積極調動學生用英語介紹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鍛煉口語表達能力之后,對不足之處進行補充。外教社《大學英語》第一冊中Unit Five: A Miserable, Merry Christmas和Unit Seven: The Sampler都是從不同角度表現西方社會慶祝圣誕節的動人故事,教師可以請學生根據所知介紹西方國家慶祝這一傳統節日的來歷與習俗,補充疏漏之處,并有意識地引導學生注意課文的側重點。如果有了老師的周密指導和悉心介紹,學生得到的就不僅是全面的英語知識和技能,還有對英語國家社會、歷史、政治和文化的了解。
事實上,諸多大學英語教材在編寫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將文化視角作為其選材的原則之一。外研社的《新視野大學英語》就選編有不少異域文化氣息濃郁的課文,如第二冊第一單元的Time-Conscious Americans,第三單元的Marriage Across the Nations等;而外教社的《大學英語(全新版)》綜合教程每冊都包括有兩至三個單元英語國家社會生活的課文,如第三冊的Changes in the Way We Live,Civil-Rights Heroes,Security 等等。教師們完全可以在講解語言知識、培養交際技能的同時很方便有效地給學生傳授點點滴滴的文化背景信息。
四、運用各種媒介,加強課外學習,提高學習效率
為了有效地使社會文化因素最大限度地促進英語的教與學,教師和學生都必須培養在課內外都把語言放到文化整體當中來學習的意識。教師除了在課堂上將中西方人際交往中諸多方面的差異融合到教學中,還應該經常關注世界時事以及由此帶來的語言新變化;翻閱時代感強的有關英語國家社會、政治、經濟、科學、文學、藝術、風土人情、歷史和宗教等的書籍、報刊、雜志以便擴大知識面,更新知識,不斷了解其文化生活動態,向學生不斷介紹新知識,推薦新書目,充實課堂教學,提高教學質量。與此同時,教師還要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調動其主動性,引導他們重視對文化背景的了解。可以通過讓學生觀看英文電影、電視、幻燈、錄像,提高他們的鑒賞能力;向他們推薦易讀、易懂的西方國家文化背景的書報雜志,如《英美概況》、《英語國家背景文化知識》、《美國英語與美國文化》、Background to Britain, Background to the US, English Salon, English World等等,讓學生多看課外讀物,瀏覽英文網頁,訂閱英文報刊;組織中外文化差異專題講座、英語角、英語周或英語晚會等,采取多種形式和手段創設多樣的語言環境,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擴大視野,加強文化知識的理解和運用。通過激發學生的興趣,提高社會文化素養來促進英語的學習,而通過令廣大學生頭疼的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將成為語言學習過程中的副產品。
參考文獻:
[1]《大學英語教學大綱》修訂工作組.大學英語教學大綱[s].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2]金惠康.論跨文化交際翻譯[J].江蘇外語教學與研究,2/1999.
[3]鄢小鳳.論影響交際教學法推行的文化因素[J].國外外語教學,1/2000.
[4]張正東,杜培俸.外語立體化教學理論[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5.
[5]王福祥,吳漢櫻.文化與語言[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
[6] 省略/report/list.hcam.
[7] 省略/file_post/display/read.php
篇8
〔關鍵詞〕跨文化心理學;文化心理學;文化;心理
〔中圖分類號〕G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2684(2013)05-0004-03
心理學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心理學研究都是對特定歷史文化中的人類心理的研究。但主流心理學采納的是自然主義科學觀,其研究忽視心理以及心理學的文化特性。然而,在心理學研究中關注文化現象,以及在研究中采取文化視角,將日益成為心理學研究的趨勢。從跨文化心理學(cross-cultural psychology)到文化心理學(cultural psychology or trans-cultural psychology),其中的文化意識發生了重要衍變,表現為在不同階段,心理學對文化與心理的關系有完全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其中蘊涵著認識論、方法論的轉變。本文擬就跨文化心理學和文化心理學中文化意識的衍變作一探討。
一、文化觀上的差異
科學心理學采納的是自然主義科學觀。這種研究方式假定了人類統一的心理機制的存在,把人類心理理解為脫離歷史和文化的存在。這種無文化或超文化的研究,既忽視了研究的本土文化根基,也忽視了研究的跨文化差異。因此,這種脫離文化特征的研究既難以反映本土文化中真實的心理行為,也無法確切解釋和預測異質文化中的心理行為。心理科學對于人類統一心理機制的追求,是以犧牲人類的文化品性為代價的。心理學正是靠跨越文化和歷史來保證自己研究的合理性和普遍適用性的[1]。
人的心理是文化和環境共同塑造的結果,不同的文化和環境影響下的心理是不同的,要想對人的心理有完全、真實的認識就必須將人置于具體的文化和環境之下。文化進入心理學研究的視野之后,心理學家面臨的是如何處理文化的地位與角色的問題,而此問題實質是文化與心理的關系問題,必須在心理與文化關系的探討中得到說明。
在心理學的發展歷史中,文化與心理的關系曾經有過多種形式的體現。在主流心理學的研究中,人類心理被認為是超文化存在的,是普遍統一的心理機制,這使得文化與心理的關系是割裂的、分離的。20世紀中葉以后跨文化心理學興起,它試圖通過研究和比較不同文化群體的被試,找出一套全人類共有的心理機制和僅為某些群體所具有的心理機制。雖然它在研究中考慮到了文化、環境的差異,但由于其深厚的科學實證主義傾向,未在內容、方法、理論上有本質性的改變。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目的在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對既有的心理學理論進行檢驗,以及研究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人在心理結構、心理能力方面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其最終目的,仍是為了驗證人類共同心理機制的假設。文化在跨文化心理學中還不是研究的主要興趣,僅僅被視為需要祛除、剝離的因素。再如進化心理學的研究,它主要關注文化與生物因素的關聯,關心文化如何適應生理需要的進化與發展,試圖使文化研究融入生物學這個大科學(big science)中[2]。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文化作了生理、生物的還原處理。由此可見,心理學研究雖然對文化問題日益關注,但其對文化的角色的處理與認識并不一致,或者說當代心理學對于文化因素的采納與接受已經不是問題,而如何認識與處理文化在研究中的作用與角色才是更為根本的問題。
隨著心理學對文化因素的關注日益增強,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心理學產生了與跨文化心理學將文化視為心理過程發生的背景不同的觀點,而視心理為文化的投射物、對應物,認為人的任何內在的、深層的心理結構及其變化都不可能獨立于文化的背景和內容,心理和文化既是有著相互區分的各自不同的動態系統,又彼此貫穿、相互映射、相互滲透。在文化心理學家眼中,文化從根本上是一種價值和意義系統。文化不是作為環境和生態系統為人們提供客觀限制或給予便利,而是存在于實踐和建構活動中的意義系統。文化作為一種意義系統,主要具有以下功能:一是表象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即包括了人們共同持有的對經驗本質的理解;二是規范功能(prescriptive function),提供了人們行為的一般準則;三是創生功能(constitutive function),可以定義并創造生成某些事實[3]。當然,文化所具有的以上功能均是在視文化為一種意義系統的前提下進行的,對三者必須進行整體理解。真正文化取向的文化心理學不再以一種心理學理論為研究背景,去尋求理論在異域文化中的檢驗,而是從某種社會文化背景下特有的社會問題、心理問題入手,以社會化過程、人際互動過程為研究重點,以本土心理學代替普遍性心理學。
跨文化心理學假設超時空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心理規律的存在,它的學科任務就是要從不同文化背景的實例中抽象、概括出這些規律,以形成“超文化”的心理學理論。理論的抽象、概括程度越高,適用的范圍就越大。文化心理學家則認為,任何特定的心理過程都內在地蘊涵著文化因素,不僅如此,任何一種理論,包括它所使用的概念、命題、假設也都是特定文化的產物,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會使人對同一概念或理論產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如果離開特定的文化背景,將很難對觀察結果作出準確解釋。因而,文化心理學不再以一種心理學理論為研究背景,去尋求理論在異域文化中的檢驗,而是從某種社會文化背景下特有的社會問題、心理問題出發,以社會化過程、人際互動過程為研究重點,以“本土心理學”取代“普遍性心理學”。隨著文化心理學研究成果的不斷擴展,人們對心理學文化內涵(content)理解的不斷深化,“文化敏感”對于心理學研究的重要性也愈益凸顯。
二、方法論上的差異
在研究方法方面,跨文化心理學采用了科學主義的基本觀點,堅持二元論、基礎主義、本質主義和歸因主義,首先假設一種與現象世界相分離的“本質”,或者假設一種與現象世界相分離的存在方式,作為世界的本原或“真存在”;其次,假設人能夠認識這種“本原”或“真存在”,并以此為基礎,探究人“怎樣”實現這種可能的認識,即對那種設定的“本原”或“真存在”的重述和再現;再次,這種探究和認識通常具有一定邏輯,而這種邏輯與事物發展的邏輯一致或重合。換言之,跨文化心理學假設存在普適性知識,存在客觀真理,現象背后有本質,事物有其存在的普遍性基礎或規律,其基本目標是通過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去發現適合于各種社會、各種文化、通用的心理學理論和定律。它采用的基本上還是實證的方法,在具體研究策略和方法上,強調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異文化研究和控制研究,區分研究中的主體(研究者)和客體(被研究者或研究對象),堅持價值中立,強調量化方法,重視說明和預測,傾向于去情境化(decontextulized),尤其是沒有情境的問卷法、實驗室實驗法等。它通常把某種文化中生成的研究程序用于他種文化中加以檢驗,以確定其合理性與普遍性。
而文化心理學采用的是后現代主義和新解釋學的基本觀點,是以研究對象為中心的多元研究方法。文化心理學借鑒了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它是以特定文化中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生成研究程序,而跨文化的比較是次要的。在具體研究策略上,它強調主位研究(emic approach)、同文化研究和生態學研究,重視現實性研究而反對研究的“人為性”,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互為主體的關系,采用哲學解釋學方法,重視研究雙方的視域融合。
文化心理學認為,應對特定文化中的現象進行認真深入的密集性研究。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它認為人種學研究方法和質化方法是最為有用的,在研究任務上重視描述和理解,強調在“真實生活”情境中收集材料,研究許多變量和它們相互作用的情境,其基本研究是綜合的、整體的,而非決定論或確定性的[4]。
三、文化和心理關系
跨文化心理學把文化與心理的關系看作是影響與被影響的關系,認為人的行為是由外在客觀因素如自然環境因素、經濟發展水平、政治制度等決定的,文化是這些客觀因素中的一個方面。換言之,它把文化看作是與心理或行為不同的外部因素,強調對文化的控制、利用。由此它認為,心理學研究應通過對文化等因素的分析來描述和理解行為,考察文化對心理或行為有什么影響以及如何影響心理或行為,以達到用文化來解釋心理或行為之目的。
文化心理學則認為,文化與心理應該是一體之兩面,作為文化形態的歷史傳統、社會制度或社會結構等唯有放在人如何去知覺它、解釋它的前提下才取得其自身意義。也就是說文化既對心理活動有所界定,同時文化的意義又取決于心理活動過程,人的心理歷程是以文化為中介的歷史發展。這至少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文化與心理是同一整體,必須同時加以考慮,缺少任何一方則另一方也不存在;第二,文化與心理又是一體之兩面,存在一定的區別,不可以把一方還原為另一方,這也就是說文化與心理是保持著一定張力的整體存在,二者既不可以分割也不可以還原,這就是文化與心理的依存性。在文化與心理互相依存的條件下,二者又是相互建構、互為因果的關系[5]。文化是人用自己的心理構筑或規整的世界圖景,而心理在這種構筑和規整活動中被改造,從而得到發展,具有新的意義、結構和功能。文化與心理是一體兩面,文化是人的世界的基本特征,人及其世界就是文化性質本身。“人既是文化世界大廈的建筑師,同時又是這個大廈的磚瓦”[6]。
具體地說,人在實踐活動中,一方面依據自己的心理(意志、需要、認識等)來改造世界,賦予世界新的圖景(如梅花在我們中國人看來就不只是一種植物的花,它更意味著堅強),使它成為文化,適合于人;另一方面,人又運用心理來認識和體驗世界,獲得有關世界的知識。在這一過程中,世界和人本身都成為文化。世界轉化為主體化了的世界,成為文化的組成部分;而人的心理也在刺激活動的不斷作用下形成、發展和深化,具有文化特征,成為文化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又進一步轉化為文化創造活動。因此文化心理學認為,刺激的(文化)意義而不是客觀特性對人的行為具有決定作用。由于意義是主觀的,因此可以說人的行為是由主觀因素決定的。這些主觀因素有信仰、認知等,由此在理解人的行為時,應分析或了解刺激或事物對人的意義,以及人的其他主觀因素。
總之,文化心理學與跨文化心理學都在關注文化因素對心理和心理學的影響和作用,但它們對文化的看法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都存在較大差異。跨文化心理學主張進行多種文化條件下的比較研究,以把握更為普遍的心理規律。事實上,文化在跨文化心理學研究中仍處于邊緣角色,文化在研究中起到的只是標簽作用,其最終目的,仍是為了驗證人類共同心理機制的假設。文化心理學的基本主張在于:文化應該參與心理學基本理論的構建,成為心理學研究的基本視角;在文化與心理的關系上,文化心理學主張擺脫還原論和實體論,重視文化與心理相互構建的動態關系。
參考文獻:
[1]葛魯嘉,陳若莉.當代心理學發展的文化學轉向[J].吉林大學學報,1999(5).
[2]Plotkin H. Evolution in mind [M]. London: Penguin,1998(223).
[3]Miller J G. Cultural psychology: Implications for basic psychology theory[J]. Psychological Science,1999(2).
[4]李炳全. 論文化心理學在心理學方法論上的突破[J]. 自然辯證法通訊,2005,27(4):40-45.
[5]楊莉萍. 從跨文化心理學到文化建構主義心理學[J]. 心理科學進展,2003,11(2): 220-266.
[6]程. 當代文化哲學沉思[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
篇9
超越文化轉向
[美]理查德?比爾納其等著,方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繼西方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發生影響深遠的“文化轉向”之后,當代西方史學界也出現了重大轉折――新文化史興起并成為主流。〔1〕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是“文化轉向”的產物,它肇始于法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歐美史學界嶄露頭角并迅速發展。1989年,美國歷史學家林恩?亨特(Lynn Avery Hunt)主編了題為《新文化史》的論文集,首次明確地舉起了“新文化史”的大旗。
然而新文化史卻在20世紀末遭受廣泛的質疑。出人意料的是,主導質疑的并非受批判的社會史學者,而恰是深受新文化史影響的亨特本人及一批歷史社會學家。1999年,在《新文化史》發表10年之際,維多利亞?邦內爾(Victoria E.Bonnell)與林恩?亨同主編了論文集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中譯本《超越文化轉向》于2008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些曾經躬逢“文化轉向”盛會的學者,在書中試圖反思文化轉向所引發的問題,對其未來走向進行審視與預見;不僅如此,其討論不再局限于歷史學領域,而是擴大到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范疇。《超越文化轉向》反映了新文化史的最新學術走向,不僅走在史學研究的前沿,而且站在了西方歷史學、社會學諸學科新思潮的風口浪尖。
一、新文化史與歷史學的“文化轉向”
該書中,亨特對10年前“新文化史”的提法進行了反思,不再單純提“新文化史”,而代之以“文化轉向”。英國文化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亦言:“‘新文化史’或‘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它常被視為更廣義的‘文化轉向’的一部分。”〔2〕
戰后西方史學界盛行的社會史研究風氣主要受到史學和年鑒學派的影響,但在這兩種理論內部,也在逐漸發生重心的轉移,對文化史的興趣漸增,成為“文化轉向”的第一種理論基礎。此外,隨著分析的歷史哲學、敘述主義、后結構主義以及文化人類學理論的興起,法美兩國一批歷史學家不滿于傳統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他們在廣泛吸收上述諸種理論的基礎上,把重心放在對語言和文化的研究上,逐步發展成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以新文化史的興起為標志的歷史學的“文化轉向”。
正如該書引言中所說:“文化的研究方法十分成功地顛覆了經實踐證明可取的唯物主義的隱喻,這個隱喻是關于基礎與上層建筑(根據經典),或者一經濟、二社會、三政治文化層面(根據法國年鑒學派)。”〔3〕文化研究具有絕對的能動性,不僅不再依附于政治、經濟和社會,而且轉而塑造和生產它們,其地位也“由地窖升至閣樓”。正當新文化史逐漸取代社會史的主流地位,并以方興未艾之勢蔓延至歷史學的各個分支時,問題暴露了。事實上一些問題在新文化史興起之初就產生了。
二、《超越文化轉向》對新文化史的再審視
敏銳的新文化史家自己發現了陷阱,并進行了自我審視,焦點在于文化是否可以無限制地解釋一切,以及新文化史該向何處去的問題。該書重新審視了新文化史,并嘗試性地提出了要“超越”局限的概略前進方向。
第一,從“一切皆文化”到文化史與社會史的調和
彼得?伯克曾對新文化史近30年的發展情況作過總結,將其研究課題歸結為以下七類:物質文化史、身體史、表象史、歷史記憶、集中于政治態度和政治實踐的社會史、社會語言史和旅行史。〔4〕31,57―72從“文化轉向”之后,原本自成體系但采取新研究方法的諸如文化史、社會文化史、微觀史、心態史、歷史人類學等,都被評論家用“新文化史”一以概之。
新文化史以包羅一切之勢蓬勃發展,大大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幾乎任何東西都能落入文化研究的問題之下,因為文化在其概念化中扮演著一種無處不在的角色,幾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個方面屬于文化范疇,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3〕11那么繼柯林武德提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和克羅齊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之后,我們似乎可以大膽斷言:一切歷史都是文化史,一切皆文化。
然而,當文化的重要性被強調到極致時,也存在著危險。必須面對的問題是,文化的能動性究竟有多大?正如邦內爾和亨特提到的:“如果文化研究如同格爾茲堅持的那樣依賴于意義的闡釋而不是對社會科學解釋的科學發現,那么把什么用作判斷闡釋的標準呢?如果文化或語言完全彌漫意義的表達,那么個人或社會(social agency)如何能夠得到識別呢?”〔3〕10過于強調文化的重要性,會犯下把一切都囊括在文化之下,卻什么都解釋不清的通病。歷史學家如果只專注于提供“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5〕14,而不理會因果解釋,那么當一切都沉浸在文化中時,因果也無從區別。
事實上新文化史的這種困境與其和社會史的關系密切相關。新文化史取代社會史成為當代史學的一種主流,“社會”失去了原本被賦予的巨大解釋力量。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史本身的式微,更不能代表史學其他分支的消亡。社會史在“文化轉向”之后接受了來自新文化史的批評改造,并逐漸走向社會與文化并重的道路。
對于過分強調文化的作用引發的兩難,亨特等人開始認識到對社會因素的絕對排斥失之偏頗。他們拒絕激進的文化論與后結構主義將社會范疇完全排除在外,而認為:“社會作為一個范疇,其本身也需要加以研究”,并主張運用新的經驗主義的方法――從比較性分析方法的再生到在廣闊的不同背景下對微觀歷史事件的探索,來對“業已喪失用處的作為一種范疇的”社會進行再考察和重新配置。〔3〕11,27對于文化的定義也不應局限于符號或語言的解釋,而應放在更加具體、社會的語境中進行考察。他們回歸到歷史的文化分析當中,調和了社會史與文化史,提出了“文化的歷史社會學”(cultural historical sociology)〔3〕84―85的新界定。
第二,從舊范式的崩潰到新范式的超越
新文化史又與解釋范式的崩潰密切相關,文化轉向既是解釋范式崩潰的結果,又是原因。“文化轉向只是加強了崩潰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由實證主義和激發的研究是由于自身負擔過重而崩潰的:學到的東西越多,就越難以將那種知識整合到現存的范疇和理論中去。”〔3〕10
對于舊范式的崩潰,新文化史家用語言和文化代替社會和經濟范疇,用“符號”取代“階級”,試圖創立一種作為符號體系的文化模式或范式,并將其作為廣泛分析文化意義的工具。但這種范式無法解釋某些來自于社會實踐的執行,而非僅靠符號之間的對照“閱讀”就能理解的意義,此外也造成了語言、文本與具體實踐的脫離,較易陷入認為形而上的知識具體可觸,形而下的物質反而不可捉摸的誤區。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說,雖然學術界正是因為對既有社會科學解釋范式不滿而轉向“文化”的,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對文化轉向及其新的解釋范式產生新的不滿。當社會史學家和歷史社會學家共同面臨舊新范式先后帶來的問題時,完全可以在社會文化的重新界定中找到共同話題。他們認為對“文化轉向”的超越,并不意味著要重回以經濟或政治決定文化的舊模式,而是轉向對社會范疇的重新概念化。在對新范式的超越方面,書中也提到了最近許多年輕學者聚焦于文化與社會生活最明顯和有效交叉的場所――具體的物質文化生活領域,例如對家具、槍炮或服裝的研究,使文化成為日常社會經驗組成部分而獲得具體形態,并且這些形態使文化代碼變得清楚。〔3〕11―12
第三,對“文化”的重新界定
超越文化轉向提出的另一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對“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10年前的《新文化史》并未對文化作出明確的界定,招致了許多批評。在該書中,威廉?西維爾(William?H.Sevilla)和理查德?比爾納其都撰文闡明了新文化史家應有的文化概念和研究方法。提出“文化”的重新理解和界定問題,是超越文化轉向的好處之一。
西維爾認為文化最為有效的概念是作為系統與實踐之間的一種辯證法,它既可以作為一個有著特定一致性和定義的符號和意義的系統,又可以作為一整套的實踐。比爾納其認為文化研究者用文化和語言代替社會和經濟范疇,用“符號”取代“階級”,尋求到的完全是社會世界的不可歸約的依據,探究到的也只是與實際相差甚遠且不可復歸的社會。他堅持:“承認文化是一種用于分析的‘名義上的工具’將會把它解放出來,去從事社會學解釋的工作。”〔3〕13―14
三、反思與走向
綜合關于新文化史的論爭及其問題分析可知,要真正“超越文化轉向”,必須對以下問題進行反思。
其一,在敘述風格上,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預言的新的歷史敘述的復興和格爾茲 “深描”的理論對其影響巨大,但若一味強調敘事和“深描”而不辨因果,有可能從根本上陷入一種。例如敘事方法選擇的例子在哲學上缺乏說服力,僅是一種言辭而非科學的證據;敘事要求史家具備全面的分析經驗及技巧,要做到這些十分不易;一味追求敘事還可能回到純粹的“好古主義”,造成過分偏重聳人聽聞的一面,而忽視占生活大部分的枯燥與繁瑣。〔6〕19―46因而新文化史家必須反思敘述策略,要承認因果性敘事也要有堅實的客觀性史實為基礎,而不可對史實隨意地敘述、想象或解構。
其二,在歷史書寫的對象上,新文化史家不再只聚焦于精英的舞臺,而是轉向蕓蕓眾生的日常生活。在其視野中,小橋流水人家比瓊樓玉宇更值得關注,原為“舊時王謝堂前燕”的研究焦點,已悄然“飛入尋常百姓家”。但他們在“下探民隱”的嘗試中遇到的一大問題是,下層民眾能否“說話”?因為在古代,下層社會都是無話語權的群體,欠缺“發聲”途徑,我們今天所見關于下層民眾的描述,基本都依賴“精英”的記錄。那么這些側記的材料如何得以重建?如何聆聽下層民眾自己的聲音?〔7〕對于間接的材料,必須花費一番淘洗的工夫,才能較為真實地展現小人物的面貌,這也是新文化史家要突破的難題。
其三,在資料的斟選方面,必須對史料有起碼的尊重和敬畏,不能任意地當做文學作品來想象、批判和解構,也不能不加選擇地將任意文本納入研究分析范疇,仍需要對文本進行篩選和甄別。因為文學作品大多經過了想象和再創作,屬于虛構的領域,而歷史是事實的領域;世界可以作為文本來閱讀,但畢竟有別于文本。
其四,在注重微觀研究和進入社會底層的同時,也應該重視具有普遍意義的宏觀事件,傳統的宏大敘事的分析仍有其合理的方面。對于微觀和底層的研究有助于“發微”,探究具有獨特視角和意義的事件,而對宏觀歷史事件的考察,又有助于我們全面理解和把握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因為諸多問題的存在,該書出版后,曾在西方學界引發了一場關于新文化史未來走向的論戰,《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兩家雜志先后組織了對此問題的專題討論。對于作為歷史學殿堂中新潮流的新文化史,勞倫斯?斯通的一席話頗具啟示意義:“歷史學這門學問一直有很多華廈巨宅,而且若想在未來也能繼續繁榮昌盛的話,還必須維持如此的局面。任何一種‘文類’(genre)或學派占了主流都會導致狹隘的山頭主義、自戀狂、自我揄揚、輕視他人或對非我一派加以排斥攻擊,以及其他無法令人茍同的或是自我毀滅的情況。”〔6〕19―20正如20世紀60年代以來社會史在西方某些國家“當道”,造成不健康的狀況一樣,新文化史如果過于陶醉其在史學界主流地位的話,同樣既不利于其自身,也不利于整個歷史學界。
實際上新文化史自誕生之日起,一直處于積極的內省狀態中。新文化史并不是要去排擠或取代社會史、政治史或經濟史,而是去挑戰它們,并因此拓展視野,來刺激和檢醒整個歷史學,促進其繁榮。“文化”問題也不僅是歷史學的重要課題,而是一個具有廣泛性和普遍性的問題,新文化史也需要與其他相關學科攜手,致力于跨學科的研究。
該書在總結文化轉向得失的同時,并未能對“超越”之后的文化史應該如何書寫給出具體的答案,而是使用含糊其辭的闡述來提出大概模糊的方向。邦內爾和亨特說道:“該書不擬提出一種可供選擇的解釋范式,而且毫無疑問,作者們對這樣的范式可能會是什么樣子的看法存在矛盾。他們也許會滿足于某種不那么野心勃勃的東西,拋棄宣稱要么能解釋一切(如同實證主義和范式曾經希望做的那樣),要么什么也不能解釋(如同后現代主義有時用對解釋本身的拒絕似乎暗示的那樣)的主張。”〔3〕25那么,新文化史該向何處去?仍然有待思考和解答。
對新文化史的再審視,正如比爾納其的立場,“文化轉向”的代價固然很大,但不“文化轉向”的代價更大,目前必須要做的,應該是去“超越文化轉向”。如果說歷史的潮流如同鐘擺,在“超越文化轉向”之后,歷史的鐘擺應該不會從“文化轉向”的“頂點”蕩回“原點”,那么它將蕩向何處?我們拭目以待。
注釋
〔1〕20世紀歐美史學發展有兩次重大轉變,一是自60年代以來“社會史”挑戰了傳統史學,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主流;二是到了80年代,“新文化史”取代“社會史”成為史學界的寵兒。此處文中所指“重大轉折”即是指第二次轉變。
〔2〕[英]彼得?伯克:《西方新社會文化史》,劉華譯,載《歷史教學問題》2000年4期。
〔3〕[美]理查德?比爾納其等著:《超越文化轉向》,方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4〕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e History, Cambridge, U.K.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2004.
〔5〕克里福德?格爾茲認為文化是尋找意義的一種闡釋科學,文化語境中的事物可以得到“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論斷。參見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Selected Essays(New York,1973).
〔6〕[美]勞倫斯?斯通:《歷史敘述的復興:對一種新的老歷史的反省》,古偉瀛譯,載《歷史:理論與評論》2期,臺北人文書會,2001。
篇10
[關鍵詞]個體論;跨際文化觀;他律性比較;自律性比較
[中圖分類號]IO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12)07-0082-05
林瑋生(1966-),男,暨南大學文學院博士后,廣東外語藝術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廣東廣州 510632)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西文化范式發生的神話學研究”(項目批準號:12BZW12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中西‘神話形態’蘊含的‘文化范式’研究”(項目批準號:11YJA751045)、廣東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項目“中西‘神話形態’與‘文化范式’的全息性研究”(項目編號:11WYXM056)的階段性成果。
一、“比較”內涵界定的困惑及主要根源
作為一個學科,比較文學已歷經了一百多年。在這一百多年的歷程中,比較文學并沒有一帆風順,而是在曲折艱難的步履中走來。造成這一“曲折”境況的原因并不在于比較文學自身,而在于比較文學缺乏一套有機的、系統的學理支撐。其中一個表現是對“比較”含義界定的乏力與貧困,而“比較”含義的界定則關系到比較文學是否能在學科之林中安身立命。對“比較”闡釋的乏力,使比較文學遭受克羅齊們的不斷非難,盡管瑪利·伽列拋出“比較文學不等于文學比較”加以回擊,但至今仍然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比較”內涵的闡釋系統。
長期以來,為了解讀“比較”含義,不少比較學者從“比較”術語人手,去探求“比”/“比較”(包括“可比性”)的內涵。殊不知,這是一種本末顛倒的溯求。“比”/“比較”只不過是一種表面操作性的東西,而不是第一性、本質性、獨立性的東西。在“比較”的背后,還有更為本質、更為深層的主人,那就是“觀念”,“比較”受到了這個“觀念”的制約。離開了“觀念”的“比較”,就如一個斷了線的風箏,“比較”只能在空中無的放矢地飄游。“比較”只有與“觀念”建立關系,才能擁有定性的言說空間,而不再飄游不定。
長期以來,“比較”內涵一直沒有得到理想的揭示與界定,筆者認為:其中最主要根源是百年來“比較文學研究”所沿襲的“總體論”取向。所謂總體論,是指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把世界各國的比較文學視為一個大整體、統一體,從發生到發展對其進行總體敘述,希冀從中概括出一套共性話語的研究范式。
自從歷史上的第一部專著(1886年,波斯奈特的《比較文學》)問世至今,“比較文學研究”已走過了一百多年。百年來“比較文學研究”的主要特征是總體論取向。這一取向表現在理論(學科)專著的各項內容之中,其中,“定義”與“簡史”(“史”)是兩個重要的表現窗口。一個學科的定義即代表著對學科理論(簡稱為“理”)的基本理解,是“理”的出發點、歸宿點與聚縮點,是對“理”本質特征、內涵和外延的高度概括。“史”則是對“理”(定義)進行歷時性的演繹與展示。“理”(定義)與“史”是一種形異質同的關系。縱觀百年來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專著,例如,梵·第根的《比較文學論》、布呂奈爾等的《什么是比較文學》、韋斯坦因的《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盧康華、孫景堯的《比較文學導論》以及王向遠的《比較文學系譜論》,從“定義”與“簡史”兩個窗口可以發現,這些專著均不自覺地尋求著一個統一的定義,并根據定義的內涵,去編撰一部宏觀的世界比較文學發生史、發展史。這正是一種總體論取向,這一取向已經成了百年來“比較文學研究”不假思索的研究范式。
總體論雖是人類認識事物的一個重要途徑,但面對比較文學這一極為復雜的人文領域現象,總體論難以給個體提供釋放生動與活力的空間,難以彰顯比較文學中各種個體文化哲學觀的志趣,例如,在比較文學中,有兩大論者,即“平行論者”與“影響論者”,他們所把持的哲學文化觀不盡相同,有的持進化論、同源論等,有的持“單中心傳播論”、“多中心傳播論”等,這些迥異的哲學文化觀均是比較文學現象里更為深層、更為前提性的東西,這些因素使比較文學內部出現“欲合還分”的張力與斥力。而總體論以“一”述“多”的宏大共性研究,只能犧牲活生生的個性而求得抽象的共性,無法讓這些個體性得到充分的訴求,無法顧及到“比較”背后的各種“觀念”。而一旦“觀念”沒有自己的話語空間,“比較”的內涵便無從談起。
因此,在總體論的語境下去尋找“比較”的內涵,只能讓人走進一個黑暗的角落。
二、個體論視角下的“比較”二分
(一)個體論的研究取向
面對總體論取向在尋找“比較”內涵所遇的困境,本文另辟蹊徑,提出一種與總體論相反的路徑,即個體論取向,以求走出解讀“比較”含義的迷途。
個體論是以事物的個體為本位的一種研究模式,它一反總體論以“一”述“多”的取向,而是以“多”述“多”,使比較文學活生生的個體性得到充分的反映。個體論認為:比較文學的構成單位是個體比較文學,個體比較文學是比較文學自行說明問題的單位。個體比較文學構成的核心要素是“跨際文化哲學觀”(簡稱“跨際文化觀”)。跨際文化觀是指對世界文學文化的根本看法,也就是說,對世界文學文化是持進化論、傳播論,抑或是兩種理論的折中等等的一套先在的、隱在的系統文化哲學觀。它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對單數(某一)文學、文化的基本看法,二是對復數(多種)文學、文化之間關系的宏觀的、根本的看法。跨際文化觀是個體比較文學呈現“什么樣”的最深層的決定力量,是個體比較文學構成的核心要素。因此,個體論視野下的比較文學被描述為“以跨際文化觀為核心要素而構成的個體比較文學集合群”。總而言之,有多少跨際文化觀,就有多少個體比較文學。
例如,從“法國學派”背后的跨際文化觀可以窺視到這一個體比較文學建構深層決定力量。梵·第根在《比較文學論》中認為:比較文學是一種歷史科學,屬于國際文學關系史的研究,其研究方法是以史料為依據的歷史學的實證研究。這是“法國學派”所主張的比較文學的顯系統,其隱系統中的跨際文化觀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人文界產生重要影響的傳播論觀念。
傳播論學派是在與進化論派(同源論)的對話中形成的,主要起源于德國的民族學。傳播論者認為:進化論只注意到人類文化在時間上縱向的演變過程,忽視了文化在地理空間上橫向的分布,研究人類文化演進必須以文化的地理傳播(dffusion)為使命。傳播論者拉采爾(Ratzel)說:“因為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在空間中發生的,所以我們應該可以通過度量歷史事件發生的空間范圍來度量歷史事件的時間流變,或者說可以用地球的鐘來度量時間。”傳播論學派試圖把人類文化史歸結為文化移動、接觸、沖突和借用的歷史,認為人類的創造能力或獨立發明的能力是有限的;人類文化有共性,并不是因為進化論者所講的全人類的“心智的一致性”所致,而是文化傳播的結果。在傳播論派看來,全世界原來只有幾個地方或只有一個地方曾獨立發明各項事物,因而成為文化中心,各項文化特質均由這些中心向四面擴散、傳播,導致了文化的接觸、影響與變遷。
因此,傳播論者認為文化人類學的主要任務在于尋找歷史上各民族相互接觸、文化傳播與被傳播的關系和過程,主張通過探討不同文化之間的“親屬關系”。“法國學派”把傳播論者的觀點搬進了比較文學,所以,在比較文學研究中主張對文學之間“經過路線”的“實證研究”。可見,深藏于隱系統中的跨際文化觀,即“單中心傳播論”,是制約“法國學派”面貌最深層的決定力量。
個體論不僅認為“有多少跨際文化觀,就有多少個體比較文學”;同時也認為有多少個跨際文化觀,就有多少種相應的方法。也就是說,有多少個“觀念”(即跨際文化觀),就有多少種相應的“比較”。事實上,觀念與方法是一種相生關系,或者說,方法是觀念的次生之子。任何觀念總存在著與之匹配的方法,在方法的背后,總跳躍著一個支撐方法的觀念。沒有和觀念相脫離的方法,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觀念,方法與觀念互為相生、彼此彰顯。西文中的“方法”一詞,來源于希臘文,這個詞由“沿著”和“道路”兩個詞組合而成,意為沿著某條道路前行。這里,沿著某個目標(觀念)與道路(方法)合二為一,要到達一定的目標,必須通過一定的路徑,而在道路上行走,總通向一定的目標。從希臘文的“方法”一詞,可見古代哲人對觀念與方法關系的直觀理解。
在比較文學界,我們同樣可以見到觀念與方法的關系的精辟敘述。饒艽子認為:“方法又不僅僅是方法,一種新的方法論的出現,往往會導致一種新的研究觀念的誕生;反之,新的觀念、理論的提出,也總是伴隨著新的方法論的運用。”筆者認為:在個體論的視角下,在跨際文化觀(觀念)與“比較”(方法)的互動觀照下,“比較”一詞的歧義問題,可得到朗照與梳理。
(二)觀念與方法關系視角下的“兩個比較”:他律性比較與自律性比較
“比較”作為一種方法,自古以來便與思維聯系在一起。“用比較法來獲得知識或者交流知識,在某種意義上說和思維本身的歷史一樣悠久”。波斯奈特則將比較稱為支撐人類思維的“原始的腳手架”。因為“比較”的古老性與深廣性,常常使人“熟知無知”,把“比較”背后潛隨的“觀念”忽視了。
“比較”與觀念的關系就如上文所提到的希臘文中內含的道路(方法)與目標(觀念)的相生相隨關系。當我們將視點落在“比較”背后潛隱的觀念,并以觀念與“比較”的相生關系重新審視“比較”時,“比較”即可一分為二:與觀念關系密切的“比較”以及與觀念關系疏離的“比較”。這兩個“比較”移轉在比較文學領域里,便成了“兩個比較”——“他律性比較”與“自律性比較”。
個體論認為:不同的跨際文化觀,含有相應的方法論,作為方法論意義上的“比較”是跨際文化觀的另一個面相,一個屬性的延伸,本身無法成為一個封閉的自足體。本文將這一種“比較”稱為“他律性比較”。他律性比較是與跨際文化觀匹配的方法,它受律于跨際文化觀,與跨際文化觀相生相契,它是通達跨際文化觀的一種途徑。
與此同時,觀念與方法的關系還存在另一種相態:當觀念相對貧困而方法走向自足時,觀念與方法的關系發生一定的游離,在此語境下的“比較”不再忠心耿耿地承載著一個明確、統一的跨際文化觀,而只是作為單純的具體方法,自行奔走于文學比較活動的叢林中。本文將這種“比較”稱為“自律性比較”。
在學界,已有不少學者意識到“兩個比較”之間的異質性以及兩者之間混淆所帶來的紛爭,他們以不同的言辭,強調了他律性比較在比較文學中的重要性。
陳寅恪對此有一段精辟的言論,他說:“蓋此稱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不追詰,更無謂研究可言。”他這里強調的“比較研究方法”應與“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的結合,即是一個方法與觀念(跨際文化觀)的匹配問題,他的“比較研究方法”指的是他律性比較。
楊周翰提出:“比較是表述文學發展、評論作家作品不可避免的方法,我們在評論作家、敘述歷史時,總是有意無意地進行比較,我們應當提倡有意識的、系統的、科學的比較。”楊周翰在這里已經論及到兩個比較。“有意無意地進行比較”即為自律性比較,“有意識的、系統的、科學的比較”接近于他律性比較。
陳悖、劉象愚指出:“‘比較文學’中的所謂‘比較’,并不是一般方法論意義上的比較,而是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是一種觀念,一種強烈的自覺意識,一種研究工作中的基本立場:它是指超越各種界限,在不同的參照系中考察文學現象。所以,這種比較必須與跨民族界限、跨語言界限、跨學科界限等含義聯系在一起,離開了這些意義上的比較,就不再是比較文學的‘比較’了……我們不妨套用卡雷的一句話來說:沒有比較的觀念,沒有了比較的方法,比較文學也就終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文學研究領域的開始。”這里,陳悖與劉象愚用“一種觀念”去闡釋“比較”,并將“比較”與跨語言、跨民族等含義聯系,還借助了卡雷對比較與觀念關聯的論說,較為準確地闡釋了“比較”的內涵,該“比較”的內涵即是本文所提出的他律性比較。
本文認為:觀念對方法(比較)的統率力與作用力是巨大的,在一定情況下,他律性比較還可發生“形式融化”現象。所謂“形式融化”,即在形式上并不一定表現為顯態的比較,但在內在上仍然是比較,在功效上等同于比較。例如,當確立了一個跨際文化觀后,有時完全不用“比較”,在論述過程中,描繪、刻畫、闡釋、敘述、解說、評價等方法可等同于“比較”的功效。在影響研究中,主要是求證,當把一堆文學事實并列放在一起進行梳理、鑒別、比照時,你能說這些方法不是比較嗎?這時,“比較”已經融化在觀念的爐子里。“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此時,研究對象已自動進入比較的視閾或框架,即使在具體研究中,采用除比較以外的其他方法,比較仍隱性地作為研究的前提存在著。”他律性比較的“形式融化”現象同樣發生在翻譯活動中。Gadamer在《語言描寫思維的程度》中指出:“閱讀已經是翻譯,翻譯則是二度翻譯。”這句話敘說了同一個道理:當人們確立了一個翻譯觀念后,在該觀念驅動下的閱讀活動,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翻譯,這樣,閱讀活動與翻譯活動便融合了。
自律性比較是觀念貧困下的比較,即上文楊周翰所說的“有意無意地進行比較”,是一種隨意性的比較。在比較文學史上最著名的自律性比較例子,莫非來自克羅齊對比較文學中“比較方法”的非難。在他看來,比較文學與西方一般文學研究并沒有什么兩樣,“比較方法不過是一種研究的方法,無助于劃定一種研究領域的界限。對一切研究領域來說,比較方法是普遍的,但其本身并不表示什么意義。……這種方法的使用十分普遍(有時是大范圍,通常則是小范圍內),無論對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或對文學研究中任何一種可能的研究程序,這種方法并沒有它的獨到、特別之處”。在克羅齊心目中的“比較方法”,正是一個游離于觀念的方法,即是本文所指的自律性比較。
瑪利·伽列為基亞所寫序言中:“比較文學不等于文學比較……我們不喜歡不厭其煩地探討丁尼生與繆塞、狄更斯與都德等等之間有什么相似與相異之處。”其中所指的“比較”,是指觀念貧困下的自律性比較。不少學者對“缺乏觀念靈魂”的“比較”的作用紛紛表示質疑。梵·第根認為:如果“比較”只在于把那些從不同國家的文學中取得的書籍、典型人物、場面等羅列起來,從中證明它們之間的相同和相異,那么,這種“比較”除了得到一點好奇心、趣味上的滿足以及優劣高低的判斷之外,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因為這樣的“比較”沒有一點歷史的價值,對文學史的研究毫無助益。巴爾登斯伯格在創辦頗有影響的《比較文學評論》雜志時曾這樣說:“僅僅對兩個不同對象同時看上一眼就作比較,僅僅靠記憶和印象的拼湊,靠主觀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東西扯在一起來找類似點,這樣的比較決不可能產生論證的明晰性。”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后期,“x比Y”式泛行,并將之混同于平行研究,給比較文學的造成不良影響。季羨林等嚴厲批評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牽強附會:“‘x與Y這種模式’,在目前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中,頗為流行。原因顯而易見,這種模式非常容易下手……勉強去比,只能是海闊天空,不著邊際,說一些類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話。這樣能不產生‘危機’嗎?”錢鐘書也曾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我們必須把作為一門人文科學的比較文學與純屬臆斷、東拉西扯的牽強比附區別開來。”
上述梵·第根與巴爾登斯伯格所說的“比較”、季羨林所批的“x比Y”式、錢鐘書所點出的“牽強比附”,均是指本文所指的自律性比較。從這些比較學者的種種陳述中,可見他們對“兩個比較”混同的焦慮與痛恨。在比較文學領域,人們常因混淆了兩個“比較”,而造成諸多的紛爭。本文通過對“兩個比較”的區分,使長期以來的“比較”之爭得到有效的化解與梳理,同時也使比較文學的“比較”內涵得到一次學理性的朗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