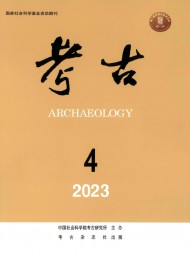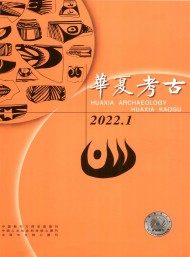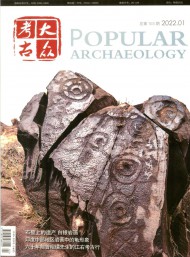考古學研究范文
時間:2023-12-19 18:03:57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考古學研究,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學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畢業(yè)于四川大學考古學專業(yè)的知名學者,對其著作進行研讀,對我們的學習、研究具有極強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領域有極高的造詣,對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獨到之處。故選擇論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三篇文章進行精讀。三篇文章分別從考古學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學文化之間的關系及考古學文化命名三個問題展開。這三個問題,無論是在考古學理論研究還是在田野考古實踐中都是時常碰到的核心問題。本文分別從文章的主要內容、觀點等方面做介紹。
一、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
《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一文曾發(fā)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該文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系統(tǒng)的介紹了學界對考古學文化命名這一問題所展開的討論。文章第一部分,詳細介紹夏鼐先生對考古學文化命名這一問題做出指導意見的具體論述及相關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舉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獨到見解,如:指出應在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中應強調陶器群的量化問題。文章第三部分,介紹各家對考古學文化“三要素” 的觀點,同時指出考古學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創(chuàng)新之處,提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確認要通過國家級的學術機構(如中國考古學會),并詳細闡述了“命名確認”的程序。
二、區(qū)系類型問題的研究―《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
《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一文曾發(fā)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該文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文章主要圍繞半坡與廟底溝類型確立及關系問題展開論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紹了1959年,類型劃分問題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廟底溝、后者早于前者、兩者同時并存這三種說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點介紹了廟底溝早于半坡這一最初的簡單論證,安志敏、馬承源學者的觀點。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紹了一個完全相反觀點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個簡要的地層關系報告,它對兩類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個新論證,即同時并存(犬牙交錯的兩個類型)。
三、對考古學文化淵源的解讀―《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
《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一文曾發(fā)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從文章題目可知該文重點探討仰韶文化“淵源”,即仰韶文化的“源頭”問題。該文主要從五個方面展開敘述。第一部分,80年代確定仰韶文化源頭的歷程。安特生將河南、甘肅發(fā)現(xiàn)的彩陶,同中亞土庫曼的安諾文化彩陶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梁思永先生發(fā)現(xiàn)了安陽后崗“三疊層”,尹達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來說”、“六期說”。但仰韶文化的來源問題并未得到解決。第二部分,從多源觀到一源觀。“分源”問題的提出,是一個重大突破。嚴文明、張忠培先生發(fā)表了相似的“分源”觀點,嚴文明先生建議將仰韶文化“一分為二”,將后崗―大司空和半坡―廟底溝作為兩個不同系統(tǒng)區(qū)分開來。第三部分,關于仰韶文化與仰韶體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來源,追本最為切要。目前學界構建的大仰韶文化體系內涵并不是單一的,內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將隴東―關中―陜南―豫西中心區(qū)的仰韶文化,分別命名為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嶺下層劃為前仰韶文化。周邊分布區(qū)分別命名后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來源問題。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灣、老官臺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來源。同時“北首嶺類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過渡的一個中間類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淵源,但北首嶺類型和仰韶文化半坡類型之間還有一段不小的缺環(huán)。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紀沒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幾點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確認”程序)中提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確認要通過國家級的學術機構(如中國考古學會),并詳細的闡述了“命名確認”的程序。這是他的創(chuàng)新之處。
2、通過這三篇文章的閱讀,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為出發(fā)點分別介紹了考古學文化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及它們之間的關系以及考古學文化淵源的探索問題。這三個問題在考古學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終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學文化研究的核心內容,也是我們在考古實踐中常常遇到的問題。那么,我們將運用什么樣的方法來進行考古學文化研究呢?
3、欲對一個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應當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間范圍和時間幅度。這項研究中通常要用到類型學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層學的運用。
4、同樣的地層,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王先生在《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一文中指出:爭辯的各方使用了地層學和類型學這樣的方法,路徑相同,證據(jù)確鑿,結論卻大相徑庭。為何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里,怎樣解決,現(xiàn)在似乎還沒有到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們依然可以總結出一些方法和經驗來。在考古學研究中,地層學和類型學是基本理論,關于這兩個理論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內容上文已做詳細闡述,但是如何正確熟練的運用這些理論卻是一個較難的問題。
5、通過閱讀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對考古學文化及考古學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們會發(fā)現(xiàn)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與不足,但是這也是我們不斷改進研究方法的動力,前人在探索過程中耗費的時間和精力,他們長時期的堅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
參考文獻
[1]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2]嚴文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的兩個問題》,《文物》1985年8期。
[3]張忠培:《研究考古學文化需要探索的幾個問題》,《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試論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馬承源:《略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問題》,《考古》1961年7期。
[6]楊建芳:《略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分期》,《考古學報》1962年1期。
[7]蘇秉琦:《地層學與器物形態(tài)學》,《文物》1982年4期。
[8]張忠培:《地層學與類型學的若干問題》,《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篇2
藝術遺物主要是指那些經過藝術加工創(chuàng)造的繪畫、雕塑、碑刻書法作品以及實用和審美相結合的工藝美術品,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實用與審美相結合的工藝美術品。
關鍵詞:藝術考古學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藝術品。古代藝術品的來源不外乎兩大類,一類是歷代流傳下來的傳世品;另一類是經過科學的田野考古調查和發(fā)掘得到的藝術品。傳世藝術品往往是中國古代藝術發(fā)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傳世藝術品有兩個致命的缺陷,一個是其確切的時代難以認證,給研究工作增加了難度;另一個更突出的問題是,對古代藝術品出于各種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偽。許多前代的青銅器、玉器、書畫等藝術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傳世藝術品不能成為藝術考古學的主要研究對象。
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植根于考古學,是運用科學的田野考古調查和發(fā)掘的手段得來的。它只是數(shù)量、品種眾多的考古學研究對象的一小部分。以此為前提,我們可以通過對已有定論的考古學研究對象的分析,逐漸剝離出非藝術性的物質產品,較為合理地勾畫出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面貌。作為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其首要條件必須是人類運用自己的雙手勞動創(chuàng)造的產物,這樣就從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中排除了與古代人類活動有關的“未經人類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種農作物、家畜、及漁獵或采集所獲得的動植物的遺存等”;同樣,從藝術品所具有的審美和情感性出發(fā),考古學研究對象中的灰坑、窖藏、礦井、水渠、壕溝等遺跡,雖然都是人工創(chuàng)造物,但僅具實用功能,或服務于生產生活,或用于戰(zhàn)爭的防御,很難激起人的審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為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至于古代人類以藝術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銅器、漆器、金銀器和各類裝飾品等工藝美術品,以及巖畫、壁畫、畫像石、畫像磚、雕塑等藝術作品,無疑是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然而,考古發(fā)掘出土的各種生產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買地券,甲骨、簡牘、紡織品、錢幣、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為藝術品的首要條件,即人工創(chuàng)造性的特征,但這些物品卻決非都是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
一、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分類
由于藝術考古學是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是一門在藝術學和考古學蓬勃發(fā)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交叉科學,其研究對象既是考古學研究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藝術學科研究古代藝術產生、發(fā)展、演變規(guī)律的重要資料,因此,對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分類,要以考古學的分類方法為主線,同時參照藝術分類法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資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類勞動創(chuàng)造的物質性遺存,一般分成遺物和遺跡兩大類。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則是考古學研究對象中人類精神文化創(chuàng)造的遺存,同樣也可以分為藝術遺跡和藝術遺物兩大類。
藝術遺跡是指經過古代勞動人民藝術性創(chuàng)造的歷史遺留,是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藝術遺跡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遺存,在中國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兩大類。中國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種木料,以斗拱、榫卯結構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為的種種因素的毀壞,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結構建筑物幾乎絕跡,僅存部分建筑物的殘缺構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遺跡也只有寺觀、塔、石闕、石窟寺、橋梁等幾類。中國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貴族建造的墳墓,以磚、石為材料,大多模擬當時地上建筑的風貌,但趨于簡率。相比較而言,考古調查和發(fā)掘出土的有關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實物資料并不豐富,但作為建筑附屬裝飾的壁畫和雕塑卻獨樹一幟,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藝術遺跡的分類便以壁畫和雕塑為主。
藝術遺物主要是指那些經過藝術加工創(chuàng)造的繪畫、雕塑、碑刻書法作品以及實用和審美相結合的工藝美術品,其中工藝美術品無論在數(shù)量、種類,還是在藝術題材和藝術成就上都遠遠超過前者。藝術遺物中的繪畫藝術品,主要有帛畫與絹畫、木版畫與木簡畫、卷軸畫等幾類。藝術遺物中的雕塑藝術品,主要有墓葬和遺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幾類。書法是文字的書寫藝術,從最初刻劃在陶器上的符號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戰(zhàn)國秦漢的貨幣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當文字、銅鏡文字、簡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書法藝術出現(xiàn)的基礎和源泉。中國古代的工藝美術品,按質地和裝飾手法可以細分為陶器藝術品、玉器藝術品、銅器藝術品、漆器藝術品、瓷器藝術品、絲織藝術品、金銀藝術品和骨雕、牙雕藝術品等。中國古代藝術品的種類紛繁復雜,除了上述繪畫、雕塑、碑刻書法和工藝美術品之外,還包括音樂、舞蹈、樂舞百戲、瓦當、剪紙、面塑等其它藝術品。
二、藝術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藝術考古學是一門建立在考古學和藝術學基礎上的新興的交叉或邊緣學科,因此,凡是考古學和藝術學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藝術考古學的研究中得到運用和借鑒。目前,對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學的方法論體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卻隨著考古發(fā)掘出土的古代藝術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漸露出端倪。一般來說,藝術考古學的研究方法主要來源于對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文化人類學、圖像學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鑒,以及對中國古代歷史文獻資料的運用。
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是研究資料重要的分類排比方法。正像歷史學家從一頁頁古代文獻記錄中尋找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軌跡一樣,考古學家也正是從這一層層的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文化堆積層中,艱難地復原古代社會的面貌,使它們成為科學的研究資料。考古地層學給古代藝術品貼上了時代的標簽,恢復了歷史的真實。考古類型學是考古學研究中整理分析資料的一個重要方法。考古類型學在藝術考古學上的應用,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通過對古代藝術品形態(tài)和裝飾題材的分析研究解決年代學的問題,從而使考古資料有更嚴密的科學性。另一方面,通過對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歸納出古代藝術品的內容題材和裝飾手法的種類,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統(tǒng)的研究資料。
文化人類學是解決原始藝術問題的一把鑰匙。如何盡可能準確地解釋史前藝術品,就需要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對史前原始藝術、有史時期野蠻民族和現(xiàn)存少數(shù)民族藝術創(chuàng)造的研究成果,又有與古代藝術創(chuàng)造有密切關系的人類生活狀況、倫理道德觀念、等物質文化和人類意識形態(tài)方面研究的成就。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菩薩灣;摩崖造像;唐末五代
中圖分類號:K87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6)03-0035-11
Abstract: There is a cliff sculpture of the Pusawan, or Bodhisattva Bay, in Yueyang Town, Anyue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consisting of nineteen niches filled with various Buddhist sculptures. Many motifs and classic Buddhist figures have been found, including the thousand-Buddha motif, Pure Land illustrations, thousand-armed and thousand-eyed Avalokitesvaras, Fifty-three Buddhas, Buddhas of the Ten Directions; even an inscription explaining why these sculptures were made is present in niche five.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s and styles of the sculpture as well as the inscription, the sculptures were mainly made during two periods, the first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second from the Qing dynasty till today. The work from the former period account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sculptures.
Keywords: Pusawan(Bodhisattva Bay); cliff sculpture; later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造像點概況
菩薩灣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安岳縣東北1.5公里的岳陽鎮(zhèn)新村一組菩薩灣東面山腰上,地理坐標為北緯30°06′39.0″,東經105°21′13.9″,海拔323.9米。現(xiàn)存摩崖造像19龕,2012年被公布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造像開鑿在3個呈“品”字形排列的石包上。1號石包位置略低,平面呈方形(圖1),東面開第6―8龕,南面開第3―5龕,西面開第1―2龕,北面開第10―12龕,東面與北面轉角處開第9龕。2號石包位于1號石包東南15米的現(xiàn)代寺院建筑內,位置略高(圖2),北側崖面由東向西依次開第13―16龕。3號石包位于2號石包東北側約10米,石包上部脫落不存,其上開第17―19龕(圖3)。
2008年7月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間,安岳縣文物局對該摩崖造像點進行了初步調查,并對1號石包的12龕造像進行編號(第1―12龕)。2014年7―9月,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縣文物局聯(lián)合組成調查隊,對該摩崖造像點進行了仔細調查和記錄,并首次對2、3號石包上的造像進行編號(第13―19龕)。
二 龕窟介紹
第1龕
該龕為單層方形龕,平面呈弧形,左壁及底部左側破壞、殘損嚴重,龕寬100厘米、高170厘米、深96厘米,龕向316度{1}。右壁下部有縱向裂隙,龕外頂部有圓形鑿孔,正壁前低臺左側現(xiàn)代水泥修補。正壁前起1厘米的低臺,臺上造一像,連座高102厘米,像高87厘米。頭頂有一個八角形華蓋,裝飾瓔珞,華蓋下方、造像頭頂有一個扁圓形物。造像頭戴風帽,面部方圓,有圓形頭光;頸部殘存兩道蠶紋,著交領袈裟;左手于腹前托一圓形物;右手于右胸前持禪杖;左腿下垂,跣足踩于蓮蓬上;右腿曲起,平放于身前;半跏趺坐于方形束腰臺座上。臺座上部覆帷幔,束腰裝飾立柱。座前中部有卷曲蓮莖,其中伸出蓮蕾、蓮葉、蓮蓬。低臺右側鑿一獸,頭部殘,面向龕外,四足趴跪。龕內左側下部似有一人輪廓,殘不可識。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造像均在現(xiàn)代被改刻、妝彩。
第2龕
該龕為單層方形龕,頂部左側左壁及右壁下部均殘損,龕內中上部有鑿孔,底部被水泥覆蓋。龕殘寬340厘米、殘高252厘米、深46厘米,龕向316度。正壁中央開單層圓拱形小龕,平面呈弧形。龕面呈尖桃形,裝飾火焰紋,左右壁及底部皆殘,寬35厘米、高37厘米、深5厘米。龕內正壁造三身像。中央主尊上身殘,風化嚴重,殘高25厘米,僅可見結跏趺坐于仰蓮臺座上。臺座底部呈四瓣形,裝飾四瓣形花紋。左右側各有一像,僅存殘跡。正壁及右壁均造千佛19排,大多風化嚴重。千佛頭上有肉髻,均結跏趺坐于上平下弧形臺座上,一般連座高14厘米、像高10厘米。袈裟有三種:一為通肩式袈裟;一為雙領下垂式袈裟,內著僧o支;還有偏衫式袈裟。姿勢有兩種:或雙手置于腹前,或雙手置于胸前(圖4)。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
第3龕
該龕為方形龕,平面呈橫長方形,現(xiàn)僅存中下部及左壁下部兩側,寬168厘米、殘高180厘米、殘深32厘米,龕向140度。
正壁中央雕一像,坐于高臺上,頭部、左右手均已無存,連座高120厘米,像高70厘米。雙層圓形頭光、身光,外飾一圈火焰紋。雕像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內著僧o支,其上束帶打結,胸前戴圓環(huán)狀項圈,項圈兩側及中部各有飾件垂下,中部飾件呈十字形;左手似托寶珠置于腹前,右手舉于右胸前,盤右腿,左腿垂下,踩于仰蓮圓臺上,跣足。臺座分兩層,上層為束腰方座,底部刻二蓮枝,分別自中央伸出,伸向左右,蓮枝下部飾卷云紋;下層為方形,方形臺上左右各置一蓮臺,蓮臺上各置一物,蓮臺中央似有一物突起。臺座底部雕一獅子,朝向右側,右前腿前伸,按寶珠,左前腿直立,左后腿前屈,作蹲坐狀,尾部翹起,似回首龕外(圖5)。
主尊頭頂上方及左側各雕祥云,僅存左側祥云的底部。左側祥云中有從像三身,高28厘米。左起第三身著袈裟,雙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于圓臺上。另兩身從像風化脫落較為嚴重,殘不可識。主尊左右各一立像,均高49厘米。左側為一菩薩像,頭挽髻,披巾自兩肩垂下,于腹前橫兩道后經小臂下垂及座,下著長裙,雙手執(zhí)禪杖。禪杖頂部裝飾復雜,風化不識。右側立像上半身及圓臺殘,著袈裟,下身著裙。
主尊左右各雕四排像,從上至下第一、二排各兩身,第三、四排各三身。第一至第三排像,均高35厘米。第四排像高49厘米。每身頭部內側均陰刻一豎長方形框,內磨平,字跡無存。左側從上至下第一排左起第一身殘;第二身雙手似置于胸前,倚坐于方臺上。第二排左起第一身頭挽髻,右手執(zhí)棍狀物置于胸前;第二身似著袈裟,雙手捧方形物置于胸前,倚坐于方臺上。第三排左起第一身頭戴冠,著交領廣袖大衣,足穿鞋立于圓臺上;第二身頭似戴冠,雙手捧物置于胸前,倚坐于方臺上;第三身左手在下,右手在上托物置于胸前,倚坐于方臺上。第四排左起第一身頭戴冠,面目猙獰,髭髯,著廣袖大衣,雙手抱棍狀物置于左胸前,倚坐于方臺上;第二身頭戴冠,頭微右偏,左手托物置于左腹前,右手舉于右胸前,倚坐于方臺上;第三身頭戴冠,雙手交疊,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托豎長方形物置于右胸前,倚坐于方臺上。右側自上而下第一排已不存。第二排右起第一身坐于方臺上;第二身頭似挽髻,發(fā)辮垂肩,著廣袖大衣,雙手捧一豎長方形物置于胸前,倚坐于方臺上。第三排右起第一身為立像,兩側披巾下垂及座,左手置于腹前;第二身頭戴冠,雙手置于腹前,倚坐于方臺上;第三身似頭戴盔,雙手置于腹前,身體微左轉,倚坐于方臺上。第四排右起第一身雙手捧物于腹前,倚坐于方臺上;第二身頭戴冠,髭髯,雙手執(zhí)豎長方形物置于左胸前,倚坐于方臺上;第三身頭似戴盔,上身著鎧甲,雙手托物置于左胸前,倚坐于方臺上。
另左壁底部雕一立像,光頭,著袈裟,雙手合十置于胸前,跣足。龕窟年代為唐宋時期。
第4龕
該龕為雙層方形龕,內、外龕平面皆呈橫長方形,內、外龕右壁被第3龕左壁破壞。外龕殘寬193厘米、高190厘米、殘深105厘米;內龕寬180厘米、高176厘米、深73厘米。龕向135度。
內龕正壁雕西方凈土,正壁中央高浮雕一佛二菩薩,均結跏趺坐于仰蓮臺座上(圖6)。佛像連座69厘米,像高48厘米。身后有舉身光,高肉髻,頸部有三道蠶紋,著通肩袈裟,衣紋于胸腹前呈淺U字形,雙手交疊,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掌心向上置于腹前,仰蓮座底部雕出三個橢圓狀物,其上各雕一壺門。
左側菩薩連座高67厘米,像高48厘米,頭后有尖桃形頭光,分為三層:內側一層飾花瓣,中層為連珠紋,外側一層為火焰紋。身后有內素面外火焰紋身光。菩薩戴高冠,發(fā)辮覆肩,繒帶自兩耳后下垂及肘,頸部有三道蠶紋,胸前戴圓形狀項圈,項圈上有掛飾及纓絡垂下,纓絡經腹前自兩膝折向身后,飾腕釧,上身斜披胳腋,兩側披帛自雙肩垂下搭小肩后下垂及座,雙手托圓柱裝物置于腹前。
右側菩薩連座高65厘米,像高47厘米,頭光、身光與左側菩薩同,頭戴高冠,發(fā)辮垂肩,頸部有三道蠶紋,繒帶自兩耳后下垂及肘,胸前所戴項圈及纓絡、腕釧、絡腋與左側菩薩同,雙手托蓮蕾置于胸腹前。
佛與兩側菩薩之間各有一弟子立像,頭后均有圓素頭光,著交領袈裟,雙手合十于胸前。右側弟子頸部三道蠶紋。佛與兩側菩薩座間各有一身菩薩坐像,均結跏趺坐于仰蓮臺座上,發(fā)辮垂肩,上身斜披絡腋,兩側披巾自兩肩垂下搭小臂后下垂及蓮座,雙手合十于胸前。
佛頭頂淺浮雕華蓋。華蓋兩端向內卷曲,頂端飾火焰紋,內置寶珠。華蓋底部有掛飾垂下,中間掛飾向左右分別伸出長飄帶。飄帶纏繞,各形成三圓圈,飄帶尾部飄向龕頂。左側左起第一圓圈內雕一佛二弟子。佛有高肉髻,雙耳碩大,雙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于覆蓮臺上。兩側弟子均為立像,身體微側向主尊。第二圓圈內雕一菩薩二弟子。菩薩頭頂向上突起,兩側繒帶下垂及肩,身著袈裟,雙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于覆蓮臺座上。兩側弟子均為立像。第三圓圈內雕一佛二弟子。佛頭頂向上高高突起呈三角狀,雙耳碩大,身著袈裟,雙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于覆蓮臺座上。兩側弟子均為立像。右側右起第一圓圈,雕一佛二弟子。佛頭頂向上突起,雙耳碩大,著通肩式袈裟,雙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于覆蓮臺座上。兩側弟子均為立像,微側向主尊。第二圓圈內雕一菩薩二弟子。菩薩頭頂向上突起,兩側繒帶下垂及肩,雙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于覆蓮臺座上。兩側弟子均為立像。第三圓圈內雕一佛二弟子。佛頭頂向上突起,雙耳碩大,著袈裟,雙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于覆蓮臺座上。兩側飄帶末端各雕一朵祥云。祥云內各雕五身像,分兩排。前排為三身佛像,著袈裟,雙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后排兩身菩薩立像,頭頂向上突起,兩側繒帶下垂及肩,似著袈裟,雙手置于胸前。
華蓋后雕一樓閣(圖7),可見圍欄、圓柱、屋頂,屋檐兩角向上翹起,鴟尾回首相向。圓柱將樓閣分為三開間,左右二開間前方各雕一立像,風化不可識。屋檐外側各有一飛天,朝向樓閣,回首看龕外,身后飄帶高高飄起。左側飛天雙手舉物于身體兩側,雙腿向后翹起;右側飛天雙手托物于胸前,雙腿向后翹起。
兩側菩薩外側各雕一經幢。幢座分五層:從下至上第一層為圓形覆蓮狀;第二層為圓球狀,上飾卷云紋;第三層為素面盤狀;第四層同第一層;第四、五層束腰;第五層為圓形仰蓮臺座。幢身為八棱柱狀。幢頂分七層:從下至上第一、三、五、六層為圓形仰蓮狀;第二層為圓球狀,上飾卷云紋;第四層為方形,中央開小龕,內一坐佛;第七層為尖桃形。經幢下方各雕一坐像,頭后均有圓形素面頭光、身光,挽高發(fā)髻,兩側繒帶下垂及肩,上身斜披絡腋,披帛自兩肩垂下,搭兩臂后下垂及座。左側菩薩盤左腿,右腿曲起;右側菩薩盤右腿,左腿曲起,身體微轉向主尊,坐于仰蓮方座上,臉朝向龕外。經幢外側各雕八邊形雙層樓閣,雕出圍欄、圓柱、屋檐。從下至上:第一層中央雕一佛二弟子,佛帳自頂部及兩側垂下。佛有高肉髻,雙耳碩大,著通肩式袈裟,雙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兩側弟子均立像,雙手置于胸前。第二層中央雕一佛二弟子,佛帳自頂部及兩側垂下。佛有高肉髻,雙耳碩大,著通肩式袈裟,雙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兩側弟子均立像,雙手置于胸前。第二層上為八角攢尖頂。雙層樓閣底部外側各雕一立像,頭后有內圓外尖桃形頭光,肉髻較高,雙耳碩大,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置于腹前。雙層樓閣底部內側各雕一菩薩立像,尖桃形頭光,挽高發(fā)髻,發(fā)辮垂肩,頸部有蠶紋,上身披絡腋,下著長裙,披巾自兩肩垂下,于腹前橫過一道后經兩臂下垂及底。左側菩薩雙手托圓盤,內盛火焰狀物置于胸前;右側菩薩雙手托物置于胸前。二者均微側身向主尊,回首龕外。
主尊及二菩薩底部雕通壁圍欄。圍欄上部中央雕二菩薩立于方形蓮臺上,均有圓形頭光,頭挽高髻,發(fā)辮垂肩,上身披絡腋,下著長裙,腰束帶,裙腰外翻,雙手執(zhí)飄帶,身體微內傾。二立菩薩左右各雕七身菩薩,結跏趺坐于覆蓮圓臺上,均有圓形頭光、身光,挽高髻,頸部有蠶紋,上身披絡腋,下著裙,腰束帶,裙腰外翻,披巾自兩肩垂下,搭小臂后下垂及座,雙手合十于胸前,身體微側向主尊,頭微偏,仰視主尊。
圍欄下部中央雕雙頭鳥,雙翅張開,尾部翹起,兩頭相背,踩于圓臺上。圓臺左右各雕一鳥相向而立。雙頭鳥兩側各雕人首鳥身形象,頭后有雙層圓形頭光,頭挽高發(fā)髻,尾部翹起,雙手執(zhí)物置于胸前。人首鳥身造像外側各雕四身伎樂,均朝向主尊而坐,回首向龕外,頭后有圓形頭光,挽高發(fā)髻。左側左起第一身似捧笙,第二身捧圓形物,第三身似撫五弦琴,第四身似執(zhí)橫笛。右側右起第一、二身僅存輪廓,第三身似執(zhí)橫笛,第四身捧柱狀物。樂器均置于頭前做吹奏狀,兩側伎樂外側各雕一菩薩立像,頭后有內圓外尖桃形頭光,挽高髻,發(fā)辮垂肩,上身披絡腋,下著長裙,披巾自兩肩垂下搭兩臂后下垂及底,雙手舉于胸前,身體微轉向內側,回首龕外。菩薩外側各雕一佛,均結跏趺坐于仰蓮臺座上,有內圓外尖桃形頭光,高肉髻,雙耳碩大,頸部有蠶紋,著通肩式袈裟。左側坐佛左手置于胸前,右手置于右膝處;右側坐佛右手置于胸前,左手置于左膝處。
雙頭鳥及伎樂下部又雕一重圍欄。圍欄中央雕水池。水池中伸出蓮葉及蓮蕾,其周圍雕有水波紋。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
第5龕
該龕為外方內圓拱形龕。外龕頂部及左右壁皆殘損,底部被鑿去,現(xiàn)為水泥地面,寬210厘米、殘高232厘米、殘深135厘米。內龕頂部及左右壁上方殘,平面呈長方形,寬187厘米、高230厘米、深87厘米,龕向135度。龕頂左部有巨大裂縫貫穿左壁與后壁交界處。龕外左右壁上部有方形鑿孔,左壁有圓形鑿孔。
龕內正壁底起低臺,正壁中央開圓拱形小龕,龕面呈尖拱形,平面呈長方形,寬81厘米、高62厘米、深10厘米。小龕正壁造三佛(圖8)。中間一佛頭部殘,連座高51厘米,像高31厘米,肉髻,雙耳碩大,有內圓外尖桃形頭光,頸部三道蠶紋,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內著僧o支;雙層橢圓形身光,雙手掌心向上置于腹前,上覆布帛,上有圓形物,結跏趺坐于方形束腰仰蓮臺座上。臺座上部覆帷幔,下部裝飾雙瓣蓮花。左側佛像頭部殘,連座高51厘米,像高32厘米,肉髻,雙耳碩大,有內圓外尖桃形頭光,頸部三道蠶紋,著通肩式袈裟,有雙層橢圓形身光,雙手于腹前結彌陀印,結跏趺坐于方形束腰臺座上。臺座上覆帷幔,束腰裝飾立柱。右側佛像頭部殘,連座高52厘米,像高32厘米,肉髻,雙耳碩大,有內圓外尖桃形頭光,頸部兩道蠶紋,著通肩式袈裟,有雙層橢圓形身光,左手于腰前托寶珠,上有火焰,右手撫右膝,結跏趺坐于方形束腰臺座上。臺座上覆帷幔,束腰裝飾立柱。
正壁除中央小龕三尊佛像外,另造五十佛,從上至下共分為六排,第一排造佛9身,第二排10身,第三排6身,第四排4身,第五排11身,第六排10身。佛像除兩身戴風帽者,均有肉髻,雙耳碩大。所有佛像均有尖桃形頭光、頸部三道蠶紋,結跏趺坐于方形仰蓮臺座上。蓮座下皆有蓮莖相接,蓮莖上伸出蓮蕾、蓮葉。佛像連座一般高28厘米,像高21厘米。
第一排左起第一身,殘不可識;第二身,雙手置于胸前;第三身,雙手于腹前托圓形物;第四身,雙手置于腹前;第五身,同第二身;第六身,著通肩式袈裟,掌心向上,持圓形物于腹前;第七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于腹前托圓球形物;第八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于胸前合十;第九身,雙手籠于袖中置于胸前。
第二排左起第一身殘不可識;第二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掌心向上托圓形物于腹前;第三身,戴風帽,雙手籠于袖中置于胸前;第四身,雙手置于腹前;第五身,殘不可識;第六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于腹前結彌陀印;第七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于腹前托圓球形物;第八身,著通肩式袈裟,左手撫左膝,右手置于胸前;第九身,同第六身;第十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置于腹前,上似搭布帛。布帛上有一圓形物,分兩層。
第三排佛像均著通肩式袈裟,左起第一身,雙手托寶珠于腹前;第二身,雙手托;第三身,雙手于胸前合十;第四身,同第三身;第五身,戴風帽,雙手籠于袖中置于腹前;第六身,雙手于腹前托寶珠。寶珠上有火焰。
第四排左起前三身均著通肩式袈裟。左起第一身,雙手置于腹前,掌上搭布帛,上有圓球形物;第二身,左手置于胸前,右手撫右膝;第三身,左手撫左膝,右手置于胸前;第四身,雙手置于腹前,掌上搭布帛,上有圓形物,分兩層。
第五排佛像均著通肩式袈裟。左起第一身,雙手籠于袖中置于胸前;第二身,雙手于腹前結彌陀印;第三身,雙手于腹前托;第四身,雙手于胸前合十;第五身,雙手掌心向上置于腹前;第六身,雙手于腹前托圓球形物;第七身,同第二身;第八身,雙手于胸前合十;第九身,同第三身;第十身,同第五身;第十一身,同第一身。
第六排左起第一身,著偏衫式袈裟,雙手置于袈裟之中;第二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籠于袖中置于腹前;第三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于腹前托圓球形物,分兩層;第四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于腹前結彌陀印;第五身,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內著僧o支,腹前束帶打結;第六身,同第二身;第七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于腹前托;第八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置于腹前;第九身,同第一身;第十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于腹前托圓球形物。
龕內右壁中部刻一碑,有碑首、碑身、碑座。碑首呈梯形,中部裝飾卷云紋;碑座呈梯形,裝飾覆蓮瓣;碑身呈長方形,寬51厘米、高110厘米,陰刻楷書題記12行,滿行18字,共存181字(圖9),全文如下:“敬造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并二菩薩一龕/敬造五十三佛一龕/右弟子白紹少在使劾職卅余年累主持/使錢投重務罷歸鄉(xiāng)久蒙差署勾覆官阻為征/討宦()人迫作十惡五逆無門懺悔今已年七/十有惡之身然遠遂發(fā)()心于此上代/內石上件功德今已成k伏/為白慕道見后發(fā)愿求來世中常于/十生誦持不退轉何多羅三藐/三菩眷屬往生凈土/……二果永為供養(yǎng)/……可……男兒使官可求。”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
第6龕
該龕為單層方形龕,平面近方形。龕頂右側表層脫落,龕口、四壁風化嚴重。寬226厘米、高170厘米、深55厘米,龕向120度。龕外右壁上部有兩圓形鑿孔,右上角坍塌處延伸一道裂縫,縱向貫穿右壁。龕內有大面積煙熏痕跡。
龕內正壁底部開高22厘米的低臺,臺上正壁造千手觀音及其眷屬、十坐佛(圖10)。千手觀音位于正壁中部,面部、手部、足部及臺座殘。連座高131厘米,像高124厘米。千手觀音戴鏤空卷草紋高冠,面部方圓,雙耳垂肩,頭兩側繒帶下垂,頸部有三道蠶紋。胸前戴寬帶圓形項圈,中部裝飾幾何形花紋,項圈下部裝飾卷草紋。胸前至膝前垂飾瓔珞。著雙領下垂式袈裟。披巾自左右肩垂下后,橫過身前,持于膝前兩手中,垂于座前。身后有尖桃形身光,邊緣裝飾一圈卷草紋。跣足,倚坐于方形臺座上,足下踏方形仰蓮臺。左右側各殘存20手,最上兩手捧化佛于頭頂;胸前兩手合十;腹前兩手拇指和食指相連,捧圓形物;膝前兩手掌心向上,執(zhí)帔帛。左側由上到下,可見一佛著通肩式袈裟,雙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于方形雙層臺座上,身后有尖桃形身光;其下一手持圓形銅鏡,中部有日形鈕,右側一手持蓮蕾;其下一手持盾牌,盾牌前雕出猙獰獸面,右側手持弓;其下數(shù)手持物皆殘;最下一手掌心向外,置于身左側。右側從上至下,一手持圓形物;其下一手持寶塔,寶塔為方形樓閣式,分兩層;再下一手持一環(huán)形物;再下一手持方形物,上有一“人”字形頂;再下一手持短棍形物;最下一手掌心向外,置于身右側。
臺座左右前方分別跪餓鬼貧兒。左側餓鬼頭部、左肩及雙手殘,殘高124厘米,雙手置于身前,上身,腰束帶,下著褲,面向右側而跪。右側貧兒面部風化,高37厘米,頭戴冠,冠帶垂于身后,著圓領長袍,腰束帶,雙手于身前持長條形口袋,面向左側而跪。餓鬼左側及貧兒右側分別跪一男一女。左側男子的頭冠、面部殘,高46厘米,面部豐圓,頸部殘存兩道蠶紋,帔帛自左右肩垂下,橫過腹前,繞左右臂后垂于身側,腰束帶,下著褲,跣足,雙手于胸前合十,面向右前方伏跪。右側女性左胸殘,全身風化嚴重,高40厘米,頭束高髻,面部豐圓,頸部殘存一道蠶紋,右側帔帛自右肩垂下,繞右臂后垂于身側,腰束帶,下著褲,跣足,雙手腕戴鐲,于胸前合十,面向左前方伏跪。
男子左側立一男子,面部、足部殘,高77厘米。頭上有小髻,雙目圓睜,面容猙獰,下頜存三角形胡須。衣服從左肩處垂下,經腹前于右腰側繞向身后,腰束帶,下著裙,足部著“T”字形履。左手握拳置于右胸前,右手持锏置于身側,微向右前方而立。
女子右側立一身像,頭部及雙手殘,高62厘米。著圓領廣袖大衣,腰束帶,下著裙,雙足著云頭鞋,雙手置于腹前,微面向左前方而立。
龕內后壁左右側上部各有五身坐佛,皆坐于方形臺上。臺座高8厘米。座前裝飾似花紋,外部為四花瓣形,內部裝飾卷云紋。臺座上左側五身佛像頭部殘,均高12厘米,結跏趺坐。左起第一身,雙手籠于袖中,置于腹前;第二身,著交領袈裟,雙手置于胸前,手上覆蓋布帛;第三身,著通肩袈裟,雙手籠于袖中置于腹前;第四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置于胸前,手上覆蓋布帛;第五身,著通肩式袈裟,雙手置于腹前。右側五身佛像均風化嚴重,均高12厘米,結跏趺坐。左起第一、三身雙手置于腹前;第二身雙手置于胸前;第四、五身姿勢殘不可識。
左右壁前各造一身天王像。左側一身,左手、足部殘,風化嚴重,高90厘米。戴冠,冠上部后側立呈拱形,冠前裝飾放射形紋飾,頭后垂發(fā)。雙耳下垂及肩。身著盔甲,飄帶繞過膝前飄于身側。右手腕戴手鐲,叉腰,呈立姿。足著履,足下有低臺,上部刻斜井字形凹槽,可能表現(xiàn)山形座。右側一身頭部、右臂及雙足殘,殘高97厘米。頭戴冠,頭后垂發(fā)。身著盔甲,腰束帶,飄帶繞過膝前飄于左右側。雙手掌心向下,于腹前持劍,呈立姿。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
第7龕
該龕為外方內圓的拱形雙層龕,內外龕除右上角外,四壁均殘損殆盡。外龕殘寬53厘米、殘高78厘米、殘深4厘米;內龕殘寬45厘米、殘高67厘米、殘深3厘米。龕向120度。內龕正壁中部造一像,全身及臺座均殘損嚴重,連座高84厘米,像高50厘米,僅存輪廓,可見一像坐于束腰臺座上。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
第8龕
該龕為單層圓拱形龕,平面呈弧形,四壁均殘損,左下角坍塌。龕殘寬60厘米、殘高98厘米、殘深5厘米,龕向90度。龕內正壁造一像,殘損嚴重,僅存輪廓,高90厘米。頭戴三尖冠,下著長裙,呈立姿。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
第9龕
該龕為圓拱形龕,平面呈長方形,僅存上壁及左右側壁上部。龕寬77厘米、高170厘米、深7厘米,龕向70度。龕內正壁磨光,無造像。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
第10龕
該龕為內方形雙層龕,內龕平面呈長方形,外龕頂部、右壁及左壁上部不存。外龕殘寬152厘米、殘高149厘米、深106厘米;內龕右壁中部殘損,寬145厘米、高149厘米、深52厘米。龕頂有數(shù)個鑿孔。龕向70度。
正壁近壁處造12厘米的低臺,臺上造一佛二菩薩。佛像頭部、雙臂殘,風化嚴重,連座殘高102厘米,像殘高96厘米。有尖桃形頭光,邊緣處裝飾火焰紋,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內著僧o支,左手抬起,跣足,立于圓形仰蓮臺座上。左側菩薩頭部殘,風化嚴重,連座殘高102厘米,像殘高85厘米。雙重頭光,繒帶自頭左右側垂下,帔帛自左右肩垂下,橫過身前,繞左右臂垂于身側。左手托凈瓶,右手持凈瓶頸部,置于腹前。腰束帶,下著裙,右膝微曲,微向左扭胯,跣足,立于圓形仰蓮臺座上。右側菩薩頭部、雙臂及臺座殘,連座殘高108厘米,像殘高90厘米。有雙重頭光,繒帶自頭兩側下垂及肘,雙手置于胸腹前,帔帛繞左右臂垂于身側,腰束帶,下著裙,左膝微曲,微向右扭胯,跣足,立于仰蓮臺座上。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
第11龕
該龕為方形雙重龕,外龕頂部及右壁不存,寬163厘米、高167厘米、深100厘米。內龕右壁部分殘損,平面略呈長方形,后壁略弧,寬147厘米、高147厘米、深86厘米。龕向37度。
正壁及左右壁的近壁處造15厘米的低臺,正壁臺上造一女性主尊及二侍女,中央主尊面部、雙手、雙腿及臺座殘。連座高110厘米,像高97厘米。主尊頭束高發(fā)髻,前戴鏤空卷草紋發(fā)冠,右后側插步搖,一端裝飾花朵,下垂珠飾;面部豐圓,頸部三道蠶紋,著雙領下垂式長袍;內著抹胸,胸前束帶打結;左手抬起,右手置于右腹前,垂足,坐于方形臺座上。臺座分兩層,由轉角處立一柱支撐。左側侍女足部殘,高100厘米;頭上雙丫髻,面部豐圓,頸部三道蠶紋;著雙領下垂式長袍,內著抹胸;雙手籠于袖中,置于胸前,懷抱扁圓形物,呈立姿。右側侍女全身風化嚴重,高93厘米;頭束高發(fā)髻,面部豐圓,雙手于右側抱小兒,頭部殘,面向內側,右手持蓮蕾狀物,呈立姿。
左壁臺上立二像。左起第一身,頭部、雙臂殘,全身風化嚴重,高55厘米;戴高冠,左手于右側抱物,右手置于身側,下著褲子,呈立姿。第二身全身風化嚴重,高53厘米;頭左右側束髻,左手置于腹前,右手曲于身側,手中持短桿,桿上有圓形物,呈立姿。左側臺前有一物,殘損嚴重,上圓,下似一臺。右壁臺上立二像。左起第一身,頭部殘,全身風化嚴重,高54厘米;頭似戴冠,左手置于左腰前,右手置于胸前,下著裙,呈立姿。第二身,頭部及雙臂殘,全身風化嚴重,高45厘米;頸部殘存兩道蠶紋,帔帛自左右肩垂下,飄于身右側;下著褲,左手置于腰側,右手置于腹前,呈立姿。臺前有一物,上部呈圓形,下似一圓臺。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
第12龕
該龕為雙重方形龕,龕底左部殘損,寬264厘米、高183厘米、深200厘米。內龕平面呈方形,龕口風化嚴重,右壁略有殘損,寬247厘米、高168厘米、深57厘米。龕向9度。
正壁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底部造8厘米高的低臺。臺上造五身坐佛,均連座殘高65厘米,像殘高45厘米。左起第一身頭部殘,內圓外尖桃形頭光,圓形頭光邊緣裝飾雙層花瓣,外層頭光邊緣裝飾火焰紋;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內著僧o支;雙層橢圓形身光,邊緣裝飾火焰紋;雙手掌心向上置于腹前,手上搭一布帛,上有圓盒形物;結跏趺坐于方形束腰仰蓮臺座上。臺座束腰和底部均裝飾卷云紋。第二身頭部及雙臂殘,頭光與第一身相似,著通肩式袈裟,身光與第一身相同,結跏趺坐于方形束腰臺座上。臺座上部覆帷幔,束腰處裝飾立柱,下部裝飾雙瓣仰蓮。第三身頭部殘,戴冠,繒帶自頭兩側垂下,頭光與第一身相同,著偏衫式袈裟,身光與第一身相同,內層身光邊緣裝飾蓮瓣,結跏趺坐于方形仰蓮束腰臺座上。上層蓮座覆帷幔,束腰處中部有一人頭,左右手向上撐起臺座;左右側各有一獸頭,雙手向上撐起臺座,下層裝飾卷云紋。第四身頭部、右手殘,頭光與第一身相同,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內著僧o支,腹前束帶打結,身光與第一身相同;左右手撫膝,結跏趺坐于方形束腰仰蓮臺座上。蓮座上部覆帷幔,束腰分上下兩層,平面呈八角形,上層凸出,每面均有方形框,下層轉角處裝飾立柱。臺座下部亦呈八角形,裝飾雙瓣蓮花。第五身頭、胸殘,頭光與第一身相同,著通肩袈裟,身光與第一身相同,雙手掌心向上,捧圓形物于腹前,結跏趺坐于方形束腰仰蓮臺座上。臺座束腰分為四瓣,每面裝飾四瓣形壺門。臺座下部裝飾卷云紋。
正壁下部近壁處起低臺,大部分殘損。臺上造五身坐佛,均連座殘高65厘米,像殘高45厘米。左起第一身頭、胸部及臺座下部殘,頭光與上層第一身相同,著通肩式袈裟,身光與上層第一身相同,雙手于胸前合十,結跏趺坐于方形束腰臺座上。臺座上部覆帷幔,束腰裝飾立柱。左側臺座前部有一小人,下身殘,僅存輪廓,面向右前方而立。第二身頭部、右手及臺座下部殘,頭光與第一身相同,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內著僧o支,腹前束帶打結,身光與第一身相同,左手掌心向上托圓形物于腹前,右手置于胸前,結跏趺坐于圓形仰蓮臺座上;左上方陰刻“東方阿”。第三身頭部及臺座殘,頭光與第一身相同,著偏衫式袈裟,內著僧o支,雙手掌心向上置于腹前,身光與上層第三身相同,結跏趺坐于方形束腰臺座上。臺座上覆帷幔,左上方陰刻“南方佛”。第四身頭部、右臂殘,腰部以下風化嚴重,頭光與第一身相同,胸部肌肉發(fā)達,著袒右袈裟,身光與第一身相同,左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于方形束腰臺座上。第五身頭部、雙臂、雙腿及臺座殘,頭光、身光與第一身相同,雙手置于腹前,結跏趺坐于臺座上(圖11)。
左壁下部造二像。左側一像僅存輪廓,殘高20厘米,呈立姿。右側一像頭部、左臂及腿部殘,殘高43厘米,著廣袖衣,雙手置于胸前,呈立姿。
上層低臺左側前部,第二身佛像臺座下,陰刻1行12字楷書題記“養(yǎng)佛志明僧金秋”。左壁上部中側有陰刻楷書題記“十方佛……”。左壁下部,陰刻楷書題記:“……永為供養(yǎng)”(圖12)。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
第13龕
該龕為外方內圓拱形龕。外龕右壁略存,寬190厘米、高180厘米、深134厘米。內龕呈圓拱形,平面呈豎長方形,寬140厘米、高156厘米、深77厘米。龕向45度。造像及臺座均有后代改刻痕跡,造像現(xiàn)代妝彩。正壁中央造一坐佛,有肉髻,內圓外尖桃形頭光,左手掌心向外,右手撫右膝,結跏趺坐于方形臺座上。左右壁內側前部各造二像,均立于方形臺座上。其身后各有四身立像。左右壁外側下部各造一力士,均有圓形頭光,面向中部而立。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造像均在現(xiàn)代被改刻、妝彩。
第14龕
該龕為圓拱形龕,平面呈拱形,龕頂部分殘損,寬205厘米、高155厘米、深84厘米,龕向32度。正壁及左右壁前起1厘米高的低臺,上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中央主尊有內圓外尖桃形頭光,頭部略大,面部方圓,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左手托圓形物置于左膝,右手垂于身側,結跏趺坐于方臺上。弟子位于主尊左右兩側,立于圓形臺座上。弟子外側各一菩薩立于圓形束腰臺座上。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造像均在現(xiàn)代被改刻、修補和妝彩。
第15龕
該龕為內圓拱形雙層龕。外龕除底部和左側下部外,均殘損,底部前有后代壘砌條石,寬170厘米、殘高134厘米、深125厘米。內龕平面呈橫長方形,龕頂及左右側壁均有殘損,寬100厘米、高116厘米、深55厘米。龕向45度。龕內正壁前造一佛,有尖桃形頭光,面部方圓,著雙領下垂式袈裟,內著僧o支,雙手于腹前托扁圓形物,結跏趺坐于方形束腰臺座上。左右壁內側前部各造兩立像,均立于臺座上。右壁前部兩立像身后又有兩身立像。左右壁外側下部有二力士。龕窟年代大致為唐宋時期。造像均在現(xiàn)代被改刻、妝彩。
第16龕
該龕為單層龕,龕及右壁皆殘損殆盡,形制不明,殘寬80厘米、殘高101厘米、殘深15厘米,龕向27度。正壁左側造一像,僅存輪廓。龕窟為現(xiàn)代所造。
第17龕
該龕位于3號石包西南側的一大龕內。大龕上部殘,僅存下部,殘寬270厘米、殘高125厘米、殘深35厘米,龕向315度。第17龕上部殘損,殘寬48厘米、殘高30厘米、深8厘米,龕向315度。龕內正壁前造一像,頭、胸殘,像殘高30厘米;雙手置于腹前,廣袖下垂于龕外,結跏趺坐于龕底。龕窟年代大致為清代。
第18龕
該龕頂部殘,寬51厘米、殘高22厘米、深10厘米,龕向315度。龕內造一像,結跏趺坐于臺座上,其余殘不可識。龕窟年代大致為清代。
第19龕
該龕頂部及右壁殘,殘寬98厘米、高66厘米、深9厘米,龕向315度。正壁前造四像,均坐于高21厘米的低臺上。左起第一身,高62厘米,戴冠,胡須下垂,身著鎧甲,左手置于腹前,右手托舉圓形物置于頭部右側,左腿下垂,右腿盤坐。第二身,高66厘米,戴三尖冠,披巾自雙肩垂于座前,左手置于胸前,右手托尖圓形物置于頭部右側。第三身,高63厘米,戴三尖冠,披巾自雙肩垂下于座前,雙手置于腹前。第四身,僅存殘跡,殘高18厘米。龕窟年代大致為清代。
三 年代及價值
菩薩灣是安岳一處保存較好的佛教摩崖造像。通過調查可知,第1龕左壁打破第2龕右壁,第3龕左壁打破第4龕外龕右壁、右側打破第2龕左壁,第9龕左壁打破第10龕右壁,第15龕右壁打破第14龕左壁,第16龕打破第15龕左壁。由此可知,第2龕早于第1龕,第2、第4龕早于第3龕,第10龕早于第9龕,第14龕早于第15龕,第15龕早于第16龕。
在此基礎上,通過觀察石包打破關系,結合現(xiàn)存造像的題材、風格和題記看,菩薩灣摩崖造像可分為兩組,一組為第1―15龕,另一組為第16―19龕。兩組龕窟的年代差異較大,第1―15龕為唐宋時期;第16―19龕為清代至現(xiàn)代,其中第17―19龕為清代龕,第16龕為現(xiàn)代龕。
第2龕的千佛,此種題材的造像主要出現(xiàn)在川西、川東地區(qū)及川北的巴中地區(qū),主要流行于8世紀末至9世紀[1],其題材與造型風格與四川蒲江石馬溝第3、第8龕以及蒲江花置寺的第3、第5、第6、第8龕極為相似,后者皆為晚唐時期的造像[2]。第4龕為西方凈土變,此類題材全川皆有分布,約從7世紀開始出現(xiàn),流行時間較長。像第4龕一樣的一佛二菩薩坐像、左右兩側雕刻天宮閣樓者主要集中出現(xiàn)在川西以及重慶的大足地區(qū),流行于8世紀至9世紀左右[1]194。第4龕與安岳靈游院第7龕年代大體一致[3],其年代亦應為晚唐、五代時期。據(jù)第5龕碑刻文字,五十三佛與西方凈土變俱為白氏發(fā)愿所造,二者為同一時期的造像,故第5龕的年代亦應為晚唐、五代時期。第3龕打破第2、第4龕,其年代比第2、第4龕略晚,從造像的風格看,其年代也應為五代時期。第6龕為千手觀音,類似的題材主要出現(xiàn)在安岳和大足地區(qū),多為五代時期的造像,其造像風格與造像內容與重慶佛灣第243、235、218、273龕以及四川安岳圓覺洞南崖第21龕相似,重慶佛灣第243龕的年代為唐天復元年(901),其余均屬前、后蜀時期{1},故可判斷第6龕的年代大致為五代時期。第12龕根據(jù)題記可知其造像為十方佛,此類題材目前發(fā)現(xiàn)不多,根據(jù)其造型風格,其年代應為晚唐時期。
菩薩灣摩崖造像的主體年代為唐宋時期,保存較好的6龕造像年代均為唐末、五代時期,造像題材豐富,雕刻精美,西方凈土變、千手觀音、五十三佛等都是當時社會流行的造像題材,反映了安岳地區(qū)佛教信仰及文化等情況,而西方凈土變底部雕刻的伎樂,為研究唐代生活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參考文獻:
[1]雷玉華.巴中石窟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09.
篇4
關鍵詞: 安陽地區(qū); 商周分界; 西周遺存; 分期
Abstract:Based on the criterion of boundary betwee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Anyang region, a pile of Western Zhou remains are distinguish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ttery patterns and combinations, Western Zhou remains are divided into 3 archaeological phases and the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y of Western Zhou in Anyang region is initially established.
Key words: Anyang region, boundary betwee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dynasty, Western Zhou remains, archaeological phases
位于河南省安陽市的殷墟遺址曾是商代晚期的都邑所在。根據(jù)文獻記載,周公二次東征后,“大邑商”遭廢棄,“殷遺多士”被強行遷往洛陽等地。然而,商王朝滅亡之后的殷墟遺址并未變成無人區(qū),殷墟遺址以外仍然存在眾多小型聚落。本文對安陽地區(qū)①的西周遺存進行全面系統(tǒng)梳理,提出安陽地區(qū)商周分界的全新判斷標準,新辨識出一批重要的西周遺存,在分析陶器形制與器類組合特征的基礎上,對安陽地區(qū)西周時期陶器進行系統(tǒng)分期研究,初步建立安陽地區(qū)西周時期的陶器分期年代框架。
一、 考古材料與以往研究
根據(jù)以往的考古調查與發(fā)掘,安陽地區(qū)發(fā)現(xiàn)西周遺存的地點有30處②(圖一),經過考古發(fā)掘并已公布材料的有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③、劉家莊北地(電業(yè)局)④、劉家莊南地⑤、孝民屯⑥、西北岡⑦、小屯東北地⑧、西高平⑨、黃張⑩和大寒南崗11等9處。此外,侯家莊南地亦發(fā)現(xiàn)有西周車馬坑和墓葬12。
發(fā)掘者曾將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清理的26座西周墓分為四期,推測“四期應是緊密相銜接的,墓地的總體時間跨度不長”,“與關中地區(qū)的西周墓葬進行比較,可以推測劉家莊西周墓的年代大體在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偏早階段”13。有學者將西高平遺址西周時期遺存的典型單位分為四組,認為“應該是從早到晚的四個發(fā)展階段”,年代相當于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晚期偏早14。迄今為止,尚未有學者對安陽地區(qū)的西周遺存進行過全面梳理,安陽地區(qū)尚未系統(tǒng)建立西周時期陶器分期年代框架。
二、 典型單位及層位關系
本文選取典型單位的原則:(1)所出陶器的時代特征較為一致,陶器的類型和數(shù)量較多;(2)盡管所出陶器的類型和數(shù)量較少,但時代特征較為一致,能夠填補分期上的缺環(huán)。依此選取的典型單位有西高平H18、H24、H88、H89、H90、H91、M1、M4,黃張H19、H64,孝民屯M742、M788、M843、M872、M882,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79、M81、M82、M85、M97、M104、M129,劉家莊北地(電業(yè)局)96T1⑧+96T2⑧15、M27,劉家莊南地M64,侯家莊南地M4、M13,大寒南崗M5、M7和小屯東北地M2。上述典型單位間可用的層位關系僅有“西高平H90H91”和“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82M81”兩組。
三、 陶器形制分析
安陽地區(qū)西周遺存所出陶器的常見器類有鬲、簋、豆、罐、盆、甑、甕等,以鬲、簋、豆、罐最為常見,且特征變化最為顯著,故選取為典型器類進行形制分析。
鬲
皆為夾砂陶,多為灰陶,頸部以下飾繩紋。根據(jù)足部特征可分為三型。
A型 肥袋足,無實足根。根據(jù)器體、頸部、口沿、腹部和袋足特征可分為五個亞型。
Aa型 扁方體,無頸,寬斜沿,斜腹微鼓,袋足外撇。根據(jù)沿面和腹部繩紋特征可分為三式。
I式 沿面無凹槽,腹部飾縱向繩紋。標本劉家莊南地M64:2(圖二,2)。
II式 沿面有粗細不均的凹槽,腹部飾縱向繩紋。標本西高平H18:25(圖二,3)。
III式 沿面有粗細均勻的凹槽,腹部飾縱向左曲繩紋。標本西高平H24:11(圖二,4)。
Ab型 扁方體,無頸,寬斜沿,鼓腹,袋足內收。根據(jù)沿面、腹部繩紋和襠部特征可分為三式。
I式 沿面有粗細不均的凹槽,腹部飾縱向繩紋,襠。標本西高平H18:27(圖二,6)。
II式 沿面有粗細均勻的凹槽,腹部飾縱向左曲繩紋,襠。標本西高平H88:10(圖二,7)。
III式 沿面有粗細均勻的凹槽,腹部飾縱向左曲繩紋,襠下鼓。標本小屯東北地M2:2(圖二,8)。
Ac型 扁體,無頸,寬斜沿,斜腹微鼓,袋足外撇。根據(jù)沿面特征可分為二式。
I式 沿面無凹槽。標本孝民屯M788:2(圖二,9)。
II式 沿面有粗細不均的凹槽。標本西高平M1:1(圖二,10)。
Ad型 扁方體,無頸,寬斜沿,微鼓腹近直,袋足內收。暫不分式,已有標本的式別特征為沿面有粗細均勻的凹槽。標本黃張H64:2(圖二,11)。
Ae型 扁方體,束頸,窄斜沿,鼓腹,袋足內收。暫不分式,已有標本的式別特征為沿面有粗細均勻的凹槽。標本侯家莊南地M4:1(圖二,12)。
B型 柱足。根據(jù)肩部和腹部特征可分為兩個亞型。
Ba型 肩部無戳印紋,腹部無扉棱。根據(jù)器體、沿面、頸部和襠部特征可分為五式。
I式 扁方體,沿面無凹槽,無領,低襠。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85:1(圖二,13)。
II式 扁方體,沿面無凹槽,矮領,低襠。標本孝民屯M872:2(圖二,14)。
III式 接近方體,沿面無凹槽,矮領,高襠。標本孝民屯M843:4(圖二,15)。
IV式 接近方體,沿面無凹槽,高領,高襠。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79:3(圖二,16)。
V式 接近方體,沿面有粗細均勻的凹槽,高領,高襠。標本侯家莊南地M13:1(圖二,17)。
Bb型 肩部通常飾一周戳印紋,腹部通常有扉棱。根據(jù)器體、頸部和襠部特征可分為三式。
I式 扁方體,肩部的戳印紋與折沿之間留白形成一道“假領”,低襠。標本西高平M4:2(圖二,18)。
II式 扁方體,矮領,低襠。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97:3(圖二,19)。
III式 接近方體,矮領,高襠。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104:2(圖二,20)。
C型 尖足。根據(jù)器體、肩部和襠部特征可分為二式。
I式 長方體,肩部無旋紋,高弧襠。標本劉家莊北地(電業(yè)局)96T2⑧:1(圖二,21)。
II式 扁方體,肩部飾旋紋,低弧襠。標本大寒南崗M7:4(圖二,22)。
簋
皆為泥質灰陶。根據(jù)口部和唇部特征分為二型。
A型 侈口,厚唇。根據(jù)口沿特征可分為兩個亞型。
Aa型 口沿外折。根據(jù)口部、腹部和圈足特征可分為四式。
I式 口部微侈,腹部微鼓,粗圈足。標本孝民屯M788:3(圖三,2)。
II式 口部外侈,腹部外鼓,粗圈足。標本孝民屯M882:2(圖三,3)。
III式 口部外侈,腹部外鼓,細圈足。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104:6(圖三,4)。
IV式 口部外侈更甚。標本西高平H89:44(圖三,5)。
Ab型 口沿內錯。根據(jù)口部可分為二式。
I式 口部外侈。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81:1(圖三,6)。
II式 口部外侈更甚。標本西高平H90:32(圖三,7)。
B型 敞口,薄唇。根據(jù)腹深、腹部紋飾和圈足特征可分為三式。
I式 深腹,腹部飾S形卷云紋,粗圈足較矮。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104:9(圖三,8)。
II式 淺腹,腹部飾S形卷云紋,粗圈足較高。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79:1(圖三,9)。
III式 淺腹,腹部素面,細圈足較高。標本侯家莊南地M13:2(圖三,10)。
豆
皆為泥質灰陶。根據(jù)腹深以及盤和柄外壁的紋飾特征可分為四型。
A型 深腹,盤和柄外壁素面。根據(jù)口部和唇部特征可分為二式。
I式 侈口,厚唇。標本西高平M4:1(圖三,11)。
II式 斂口,尖唇。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81:7(圖三,12)。
B型 深腹,盤和柄外壁飾旋紋。根據(jù)口部、唇部和柄的特征可分為二式。
I式 斂口,尖唇,粗柄。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104:4(圖三,13)。
II式 侈口,方唇,粗柄稍細。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79:5(圖三,14)。
C型 淺腹,盤外壁下部多飾旋紋。根據(jù)盤和柄的特征可分為四式。
I式 盤圓折,腹較淺,盤外壁下部飾數(shù)道旋紋。標本西高平H18:30(圖三,15)。
II式 盤方折,腹稍深,盤外壁下部飾數(shù)道旋紋。標本西高平H89:18(圖三,16)。
III式 盤方折,腹稍深,盤外壁下部飾少量旋紋,細柄,柄上有粗凸棱。標本大寒南崗M5:1(圖三,17)。
IV式 盤方折,腹稍深,盤外壁素面,柄更細,柄上有細凸棱。標本小屯東北地M2:3(圖三,18)。
D型 深腹,盤外壁有密集凸棱,柄素面。根據(jù)腹部和盤外壁凸棱特征可分為三式。
I式 鼓腹,盤外壁凸棱靠下。標本黃張H19:5(圖三,19)。
II式 直腹,盤外壁凸棱靠下。標本大寒南崗M5:3(圖三,20)。
III式 直腹,盤外壁凸棱靠上。標本小屯東北地M2:1(圖三,21)。
罐
皆為泥質灰陶。根據(jù)器表紋飾可分為四型。
A型 肩部飾旋紋。根據(jù)器體、口沿、肩部和底部特征可分為四個亞型。
Aa型 長方體,窄折沿,近折肩,小平底。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97:2(圖四,2)。
Ab型 長方體,寬卷沿,圓肩,平底。根據(jù)口部、頸部、肩部和底部特征可分為四式。
I式 大口,高領,高肩,小平底。標本孝民屯M788:1(圖四,4)。
II式 大口,領稍矮,肩稍低,小平底。標本孝民屯M882:3(圖四,5)。
II式 中口,領稍矮,肩稍低,小平底。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104:1(圖四,6)。
III式 中口,領稍矮,肩更低,小平底。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79:2(圖四,7)。
IV式 小口,矮領,肩部低至通高的一半,大平底。標本侯家莊南地M4:3(圖四,8)。
Ac型 方體,寬卷沿,折肩,平底。根據(jù)肩部旋紋特征可分為二式。
I式 肩部飾稀疏旋紋。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82:3(圖四,9)。
II式 肩部飾密集旋紋。標本小屯東北地M2:4(圖四,10)。
Ad型 扁方體,窄折沿,折肩,平底。暫不分式,已有標本的式別特征為肩部飾密集旋紋。標本大寒南崗M5:2(圖四,11)。
B型 素面。根據(jù)器體特征可分為兩個亞型。
Ba型 長方體。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129:2(圖四,12)。
Bb型 扁方體。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81:6(圖四,13)。
C型 肩部飾旋紋,腹部飾繩紋。根據(jù)口沿和肩部特征可分為兩個亞型。
Ca型 卷沿,圓肩。標本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27:1(圖四,14)。
Cb型 折沿,折肩。標本孝民屯M742:1(圖四,15)。
D型 肩部和腹部飾繩紋。標本侯家莊南地M13:3(圖四,16)。
四、 分組及相關問題
根據(jù)上述器物形制分析,可將典型器物中式別特征相同、文化面貌近似的典型單位歸為6組。
第1組:劉家莊南地M64,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85,西高平M4、孝民屯M788。
第2組: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97,劉家莊北地(電業(yè)局)M27,孝民屯M742、M872、M882。
第3組:西高平H18、H91,黃張H19,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81、M104,孝民屯M843。
第4組:西高平H89、H90,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79、M82、M129。
第5組:西高平H24、H88,大寒南崗M5,侯家莊南地M4、M13。
第6組:小屯東北地M2。
根據(jù)可用的兩組地層關系“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M82M81”和“西高平H90H91”可證第3組早于第4組。檢驗各典型器物的式別順序,應為由第1組依次發(fā)展至第6組,無顛倒現(xiàn)象。各典型器類及其型、式在典型單位中的分布情況見文后附統(tǒng)計表(表一、表二)。
五、 分期與年代
考慮到除第3組與第4組以外的其它組之間缺乏層位關系,典型器物的式別特征存在上下浮動的可能,另有部分典型單位暫無法細分入上述分組,因此有必要根據(jù)式別特征之間的差異大小進行并組。
第1組與第2組的B型鬲皆為扁方體,第3組與第4組的B型鬲均接近方體,第1組與第2組的A型簋為粗圈足,第3組的A型簋為細圈足,第1組與第2組的Ab型罐為大口,第3組與第4組的Ab型罐為中口,可見第2組與第3組之間的差異較大。第3組與第4組的Ba型鬲的沿面無凹槽,第5組的Ba型鬲的沿面有粗細均勻的凹槽,第3組與第4組的B型簋腹部飾S形卷云紋,第5組的B型簋腹部素面,第3組與第4組的豆為粗柄,第5組與第6組的豆為細柄,第3組與第4組的Ab型罐為中口,第5組的Ab型罐為小口,可見第4組與第5組之間的差異較大。盡管第3組與第4組之間有明確的層位關系,但這兩組的器物形制差異明顯小于第2組與第3組以及第4組與第5組之間的差異。據(jù)此可將第1組與第2組合并為第一期,第3組與第4組合并為第二期,第5組與第6組合并為第三期。
在對上述各期進行具體斷代之前,首先需要明確第一期的年代已進入西周,而非商代晚期或“商末周初”16。之所以判斷第一期的年代已進入西周,標準如下:
1. 西周早期周式聯(lián)襠鬲的出現(xiàn)表明年代進入西周
劉家莊北地(電業(yè)局)所出C型I式鬲96T2⑧:1(圖五,2)的長方體、高弧襠、飾細繩紋的特征與周原IVA1H4:217(圖五,3)相似,后者為周式聯(lián)襠鬲,年代為西周早期。96T2的地層堆積與鄰方96T1相同,96T1所出Aa型I式鬲96T1⑧:1(圖五,1)為商式分襠鬲,形制特征與殷墟四期相同,但年代已經進入西周早期。
2. 柱足鬲的出現(xiàn)表明年代進入西周
至殷墟四期,殷墟遺址普遍流行無實足根的A型鬲(圖二,1),少量鬲有小尖足(圖二,5),極罕見柱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劉家莊北地(抗震大樓)發(fā)現(xiàn)的西周墓葬隨葬陶鬲皆為B型鬲,最初形態(tài)的M85:1(圖二,13)是在典型商式鬲的基礎上增添柱足而成,屬于商式鬲的變體。相同形制的陶鬲亦發(fā)現(xiàn)于洛陽擺駕路口M167(陶鬲015號)(圖五,10),與之共出的有西周早期周式聯(lián)襠鬲(陶鬲016號)(圖五,11)18。
3. 扁體肥袋足無實足根鬲的出現(xiàn)表明年代進入西周
殷墟四期流行的肥袋足無實足根鬲多為扁方體,洛陽北窯鑄銅遺址在西周早期出現(xiàn)扁體肥袋足無實足根鬲H83:219(圖五,24),相比商末周初的陶鬲標本苗圃北地PNM238:120(圖二,1)器體更扁,邢臺南小汪遺址的西周早期遺存亦出有形制相同的陶鬲H89:3421(圖五,25)。孝民屯M78822的隨葬陶器組合為鬲、簋、罐,隨葬Ac型鬲M788:2為扁體肥袋足無實足根鬲(圖五,21),共出的陶簋M788:3(圖五,22)較商末周初的侈口厚唇簋標本后岡圓形祭祀坑H10:2623(圖三,1)圈足增高,但仍具備粗圈足特征,共出的圓肩旋紋罐M788:1(圖五,23)是西周早期新出現(xiàn)的器型,相比商末周初的圓肩素面罐標本GM233:624(圖四,3),在肩部新出現(xiàn)數(shù)道旋紋。
4. 高圈足侈口厚唇簋的復出表明年代進入西周
安陽地區(qū)在殷墟三、四期流行侈口厚唇簋(A型簋),腹部通常飾三角劃紋內填細繩紋,演變規(guī)律為由高圈足變?yōu)榘ψ悖棠┲艹醯某蘅诤翊襟吮竞髮鶊A形祭祀坑H10:2625(圖三,1)為粗矮圈足。進入西周,侈口厚唇簋的圈足重新由矮變高,同時也有由粗變細的趨勢(圖三,2、3、4)。另外,Aa型簋在商末周初為窄折沿,進入西周變?yōu)閷捳垩兀彝獬拗饾u明顯(圖三,1、2、3、4)。
5. 敞口薄唇簋的出現(xiàn)表明年代進入西周
商末周初墓葬小屯西地GM233出有仿銅陶簋GM233:4126(圖六,1);西周早期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27所出陶簋M1:397(圖六,2)的形制幾乎與之完全相同,惟腹部新出現(xiàn)S形卷云紋,長子口墓所出陶簋M1:395(圖六,3)已擺脫仿銅作風,腹部亦壓印有S形卷云紋;西周早期墓葬洛陽擺駕路口M16728和洛陽車站6:0129已出現(xiàn)典型形制特征的敞口薄唇簋(圖五,13、19)。可見,敞口薄唇簋脫胎于商末周初的仿銅陶簋,成型于西周早期。目前的材料顯示,腹部壓印S形卷云紋的敞口薄唇簋(圖六,4、5)在安陽地區(qū)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
6. 豆的復出表明年代進入西周
至殷墟四期時,居址中的豆已近絕跡,墓葬中的豆基本被盤取代30。西高平M4隨葬柱足鬲M4:2(圖五,5)和豆M4:1(圖五,6)各1件,柱足鬲的出現(xiàn)表明年代進入西周,豆的復出也表明年代進入西周。洛陽擺駕路口西周早期墓葬M16731亦有豆(014號)(圖五,12)復出的現(xiàn)象。
7. 圓肩旋紋罐的出現(xiàn)表明年代進入西周
商末周初墓葬小屯西地GM23332新出現(xiàn)圓肩素面罐GM233:6(圖四,3),由于該墓為仿銅陶禮器墓,其形制可能是由銅簡化而來。與殷墟文化流行圓肩繩紋罐的情況不同,圓肩旋紋罐(Ab型罐)常見于周原33、灃西34等地,亦見于西周早期墓葬洛陽擺駕路口M16735(01號)(圖五,14)和洛陽車站6:0136(圖五,20),為西周時期的常見器型。
8. 墓葬隨葬單鬲或鬲、罐組合的出現(xiàn)表明年代進入西周
殷墟商墓的隨葬陶器組合以明器化的陶觚、爵為核心37,也有部分墓葬隨葬陶鬲,甚至有以隨葬單鬲為主的墓群38,但這些墓葬通常隨葬典型商式鬲。安陽地區(qū)西周墓葬隨葬陶鬲多為柱足鬲,但也有西周早期墓葬隨葬肥袋足無實足根鬲,由于后者的器物形制與殷墟四期無明顯差異,故對其年代的判斷需要借助考古背景進行綜合考量。如,劉家莊南地M64出有肥袋足無實足根鬲M64:2(圖五,15)和柱足鬲M64:3(圖五,16)各1件,柱足鬲M64:3的折沿、微鼓腹、低襠、柱足的特征與洛陽車站西周早期墓葬6:0139所出陶鬲(圖五,18)相似,據(jù)此推知肥袋足無實足根鬲M64:2的年代為西周早期。劉家莊南地M64還出有陶罐殘片,表明該墓的隨葬陶器組合為鬲、罐組合。
鬲、罐組合應是受到了周人的影響40,鬲、罐組合出現(xiàn)在安陽地區(qū)表明年代已進入西周。如,劉家莊北地(電業(yè)局)M27為鬲、罐組合,隨葬陶鬲M27:3(圖五,26)的扁方體、低襠的特征與張家坡M175:5(圖五,28)相似,隨葬陶罐M27:1(圖五,27)的卷沿、圓肩、下腹斜收、平底、肩部飾旋紋的特征與張家坡M175:2相似(圖五,29),張家坡M175的年代被定為昭穆時期41,可知劉家莊北地(電業(yè)局)M27實為西周墓葬。
上述標準并非孤立,也并非絕對,必要時需要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判斷。由于陶鬲在安陽地區(qū)西周遺存的居址和墓葬中最為常見、數(shù)量最多,且為器物組合的核心,故將上述分期成果中陶鬲的典型形制與周原、洛陽、邢臺、琉璃河等地西周遺存已有的年代分期標準中陶鬲的典型形制進行比對,佐以上文的判斷標準,對上述分期成果的絕對年代進行推定。
第一期:上文已論證Aa型I式鬲、Ac型I式、Ba型I式鬲和C型I式鬲的年代為西周早期。Bb型II式鬲的扁方體、矮領、低襠的特征與洛陽北窯M93:442相似,后者的年代為西周早期。Bb型I式鬲、Bb型II式鬲與Ba型I式鬲、Ba型II式鬲除肩部飾戳印紋以及腹部有扉棱外,其余式別特征相同,故可將年代均定為西周早期。
第二期:A型鬲的沿面有粗細不均的凹槽、腹部飾縱向繩紋的特征與琉璃河97LG10H11:10相似,Ba型IV式鬲的接近方體、口沿無凹槽、高領、高襠的特征與洛陽北窯M186:143相似,Bb型III式鬲的接近方體、高領、高襠的特征與洛陽C3M198:144相同,后者的年代均為西周中期。Bb型III式鬲與Ba型III式鬲除腹部有扉棱外,其余式別特征相同,年代應為西周中期。
第三期:A型鬲與Ba型V式鬲的沿面上有粗細均勻凹槽的特征與琉璃河95LF10H106:245相似,Aa型III式與Ab型II式、III式鬲的腹部飾縱向左曲繩紋的特征與邢臺南小汪T13④:3446相似,C型II式鬲的扁方體、肩部飾旋紋、低弧襠的特征與周原H98:1847相似,后者的年代均為西周晚期,據(jù)此可將第三期的年代定為西周晚期。
六、 小 結
根據(jù)出土陶器及層位關系,本文對安陽地區(qū)西周時期陶器典型器類的演變規(guī)律進行了總結,將以陶器群為核心的安陽地區(qū)西周時期考古學文化分為三期,年代大體與西周早、中、晚期相當。通過對安陽地區(qū)西周遺存所出陶器的系統(tǒng)梳理,初步建立安陽地區(qū)西周時期的陶器分期年代框架。該年代框架的建立,為判斷安陽地區(qū)西周時期文化遺存的分期年代,以及進一步探索西周時期商人故地的文化、聚落與社會提供了一把比較詳細的年代標尺。
注釋:
① 本文所指的“安陽地區(qū)”包括今安陽市轄區(qū)和安陽縣在內的洹河中游地區(qū)。
② a.胡厚宣:《殷墟發(fā)掘》,學習生活出版社,1955年;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洹河流域的考古調查》,《考古學集刊》(第3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c.安陽市博物館:《豫北洹水兩岸古代遺址調查簡報》,《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d.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隊:《洹河流域區(qū)域考古研究初步報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殷墟劉家莊北地殷墓與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④ 安陽市文物工作隊:《1995~1996年安陽劉家莊殷代遺址發(fā)掘報告》,《華夏考古》1997年第2期。
⑤ 安陽市博物館:《安陽鐵西劉家莊南殷代墓葬發(fā)掘簡報》,《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行文簡潔起見,本文將“劉家莊南地85AQMM64”簡寫為“劉家莊南地M64”。
⑥ 殷墟孝民屯考古隊:《河南安陽市孝民屯遺址西周墓》,《考古》2014年第5期。
⑦ a.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二本?1001號大墓》上、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 b.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三本?1002號大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年; c.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四本?1003號大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年; d.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五本?1004號大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年; e.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八本?1550號大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6年。
⑧ a.鄒衡:《試論殷墟文化分期》,《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小屯建筑遺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市西高平遺址商周遺存發(fā)掘報告》,《華夏考古》2006年第4期。行文簡潔起見,本文將西高平遺址的器物單位編號進行了簡寫,如“04AXH41”簡寫為“H41”。
⑩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黃張發(fā)掘隊、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河南安陽市黃張遺址兩周時期文化遺存發(fā)掘簡報》,《考古》2009年第4期。
11 a.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fā)掘隊:《安陽洹河流域幾個遺址的試掘》,《考古》1965年第7期; 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隊:《安陽大寒村南崗遺址》,《考古學報》1990年第1期。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資料。
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殷墟劉家莊北地殷墓與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14 豆海鋒:《太行山東麓地區(qū)西周文化分期研究》,《華夏考古》2013年第2期。
15 劉家莊北地(電業(yè)局)96T2的地層堆積與鄰方96T1相同。
16 已有的研究認為:“殷墟第四期文化IV4段以前都屬晚商時期,而IV5段文化跨商末周初。”(唐際根、汪濤:《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33、47 黃曲:《周原遺址西周陶器譜系與編年研究》,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03年。
18 郭寶鈞、林壽晉:《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陽東郊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第9冊,1955年。
19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1975-1979年洛陽北窯西周鑄銅遺址的發(fā)掘》,《考古》1983年第5期。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21、4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臺商周遺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
22 殷墟孝民屯考古隊:《河南安陽市孝民屯遺址西周墓》,《考古》2014年第5期。
23、24、25、26、3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2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8、31、35 郭寶鈞、林壽晉:《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陽東郊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第9冊,1955年。
29、36、3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二隊:《洛陽的兩個西周墓》,《考古通訊》1956年第1期。
30 鄒衡:《試論殷墟文化分期》,《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4、4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家坡西周墓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
3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墟西區(qū)墓葬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1期。
38 安陽市文物工作隊:《安陽徐家橋村殷代遺址發(fā)掘報告》,《華夏考古》1997年第2期。
40 鄒衡:《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2、43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窯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
篇5
關鍵詞:語言學概論 教學研究 反思
一.與現(xiàn)代漢語課程關系的探討
“語言學概論”和“現(xiàn)代漢語”,作為專業(yè)基礎課程的性質已得到廣泛認同,它們之間有密切聯(lián)系,但也有明顯不同的目標。教育部在兩門課程的教學大綱里明確說明:現(xiàn)代漢語課程貫徹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原則,系統(tǒng)地講授現(xiàn)代漢語的基礎理論和基礎知識,加強基本技能的訓練,培養(yǎng)和提高學生理解、分析和運用現(xiàn)代漢語的能力;語言學概論課程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語言觀闡明人類語言的性質、結構、起源及發(fā)展等基本理論,通過教學,要求學生初步樹立科學的語言觀,掌握語言學的基礎理論和基礎知識,具備運用語言學的科學方法分析語言現(xiàn)象的能力。
“語言學概論”和“現(xiàn)代漢語”兩門課程的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存在著較大差異,但也存在密切聯(lián)系。具體教學活動中,兩門課都追求自身內容的完整性,很容易造成教學內容的重復。一些學者就此問題進行過探討,也提出了相應的具體措施。彭澤潤、陳長旭、吳葵(2007)提出“語言學概論”和“現(xiàn)代漢語”這兩門課程教學存在許多問題,認為進一步的改革措施有:把兩門課程結合起來協(xié)調改革、合理安排教學計劃、統(tǒng)一術語、適應現(xiàn)代生活、語料互補等。梁馳華(2008)就高等師范院校語言學概論教學改革提出了一些看法,認為語言學概論教學應當突出課程的普通語言學性質,提升課程的語言學習指導作用,聯(lián)系現(xiàn)實的語言生活,課程的語言教學指導作用和正確處理語言學概論與現(xiàn)代漢語的關系。蔡旭(2011)提出現(xiàn)代漢語課程與語言學概論課程在教學內容上存在很多重復,應當對現(xiàn)代漢語和語言學概論教學的銜接問題進行探索,從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等三方面提出改進的策略。甘智林(2008)、聶志平(2010)、張先亮(2010)也探討了這一問題,并提出了用普通語言學的眼光看待語言現(xiàn)象,對于兩門課程相重復的內容,要根據(jù)課程不同的性質與教學目標,有選擇、區(qū)分重點與非重點地安排授課內容,對重復的內容有所取舍,有所詳略地加以講授。
二.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的探討
彭澤潤(1998)提出,在語言學概論課程教學中,要結合國家語言建設中的政策,介紹和強調理論問題,更好地使理論聯(lián)系實際,結合國家語言政策,介紹與強調其理論問題:運用系統(tǒng)理論,幫助人們分析語言使用中的得失;運用符號編碼的原理,幫助人們理解不同文字的優(yōu)點;從共同語與非共同語的關系,幫助人們正確認識學習母語和學習外語的問題;運用抽象與具體、相對與絕對的哲學原理,解釋漢語拼音方案等的設計原理等。徐越(2000)結合多年的教學實際,就“語言學概論”這門課程該講什么,不該講什么,如何把語言學的一般理論和漢藏語系的語言特別是漢語的實際相結合,如何吸收國外語言學研究的新成果及如何安排和進行該課程的教學工作等問題作了一個初步的探討。李二占(2009)認為老師授課,不但要具有常規(guī)教學法的基本功,而且還要針對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知識,采取不同的靈活具體的教學方法,即“非常規(guī)教學法”:推導法、直感法、量化法、窮盡法、背景法、批評法等。謝奇勇(2010)就教學內容中的“語言學理論”與“語言理論經”、“語言學理論”與“語言學方法論”、“普通語言學”與“語用學”、“國外語言學理論”與“中國語言學理論經”等方面進行了探討。聶志平(2010)認為語言學概論的教法還應該是講授式,不是簡單的就書衍說,而是融入自己的理解和體會,多媒體課件不能取代教師教學,板書教學是課件的不可或缺的補充,強調每次課推薦閱讀書目的重要性。童湘屏(2011)提出“情景創(chuàng)設”在“語言學概論”課程實踐與教學設計方案中的應用及探索。根據(jù)實施情況,從課堂“情景創(chuàng)設”實踐教學和課外“情景創(chuàng)設”實踐教學兩個方面,闡述了其主要做法及實施效果。岑運強(1997)、李映忠(2008)、池昌海(2009)、趙宏(2004)就語言學概論教材進行了探討,許云(1996)、紀秀生(1997)、李樹新(2004)、郜峰(2006)、洪水英(2006)、羅耀華、柳春燕(2006)、郭新雨(2009)、劉云(2010)、趙賢德(2010)、徐紅梅(2011)、葉川(2011)等也分別對“語言學概論”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創(chuàng)新進行了探討。
三.基于課程建設的探討
學者們就“語言學概論”課程建設及教學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些相應的具體策略。曾毅平(2001)認為,教學內容調整要體現(xiàn)語言觀的進步,要處理好與其他語言學課程特別是“現(xiàn)代漢語”課的關系;要注意補充漢語方言和我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等方面的材料。彭澤潤、邱婧、方安琪(2010)必須加大語言學概論課程和教學隊伍的建設力度。聶志平(2010)從“課程地位與培養(yǎng)目標”、“師資”、“教法和教學手段”、“與現(xiàn)代漢語的區(qū)別與銜接”、“教材與課程體系”五個方面探討語言學概論課程建設的問題。紀秀生(1997)、杜道流(2004)、申小龍(2005)王健(2005)、楊宏(2008)、商艷霞(2009)、黃育紅(2010)、劉淑霞(2010)、劉麗麗(2010)、張麗(2011)、靳開宇(2011)也就“語言學概論”課程建設的問題及策略展開了探討。
篇6
【關鍵詞】初中科學;科學概念;能力考查;評估工具
【基金項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科學規(guī)劃課題“科學教科書習題質量評估工具的開發(fā)與應用”(批準號:2015SCG354);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課題“追求卓越:職前教師PCK的發(fā)展研究”(批準號:2016M592019)的系列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33.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6)31-0073-03
一、研究緣起
試題能力考查傾向不僅是其作為選拔性考試命題必須要考慮的因素,更是有效教學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國的義務教育階段各學科課程標準借助布魯姆――安德森的認知過程水平對各類教育目標進行相應的層次劃分,每一層次間缺少必要的說明而導致各層次間的界面不是特別清晰,從而在實際教學評價過程中出現(xiàn)操作性不強的現(xiàn)象。
以初中科學為例,我國各地的初中科學試題大多重在知識考查,而忽略了知識背后的能力要求,這不僅影響著人才選拔的質量,更對初中科學教學起著不良的導向作用。因此,本研究選取當前具有代表意義的初中科學試題為研究對象,在分析基礎上應用所開發(fā)的能力考查評估工具來分析試題的能力考查傾向,探查當前初中科學試題在能力考查傾向上存在的共性及差異,以期為由“知識考查”轉向“能力考查”提供有價值的啟示。
二、初中科學試題特點分析
本研究從全國不同地區(qū)選取了不同年份的初中科學試題,呈現(xiàn)出以下幾個特點:
1. 考查題型過于傳統(tǒng)
經研究發(fā)現(xiàn),當前初中科學試題題型種類豐富,有單選題、不定項選擇題、填空題、計算題、說明題、作圖題、推斷題、實驗開放題8種之多,但其中最主要的考查題型為單項選擇題與填空題,考查分值比例分別為34.75%、46.32%,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能力考查的靈活性。
2. 信息呈現(xiàn)方式單一
實驗圖、模型圖、數(shù)據(jù)圖、關系圖以及實物圖等解釋性工具必將是學生進行科學學習的輔助手段,也理應成為科學試題考查學生能力的重要載體。本研究所選樣本中絕大多數(shù)試題只使用語言文字表達信息,少部分試題采取了其他呈現(xiàn)方式和組合多種方式,這樣,就降低了由于信息識別、加工、運用所帶來的難度。
3. 試題結合生活情境
科學與學生的生活實際聯(lián)系緊密,科學試題需有目的地創(chuàng)設真實情境,讓考生在一種模擬的實際中分析、解決問題。所有樣本中,近40%的科學試題情境素材選自社會與生活,達到了“讓學生在考場感受考題生活化”的目的,只有2%左右的試題情境對學生而言有些陌生,這樣有助于減輕考生心理緊張而使得試題較為準確地測查學生的能力水平。
4. 重點考查科學概念
本研究根據(jù)相關參考文獻,將科學學習分為5個學習領域,分別是科學概念、科學符號、科學模型、科學實驗、科學計算,圖1是全部樣本中各學習領域考查分值比例的平均。由圖可看出,初中科學試題對各學習領域考查具有一定的差異性,科學概念學習領域的考查,分值比例最大,其次是科學實驗與科學計算學習領域的考查分值比例在19%左右,而科學符號與科學模型學習領域考查的分值比例僅為9%左右。
上述分析表明,初中科學試題題型、信息呈現(xiàn)、情境設置各有特點,但這些均屬于試題的外部特征,不能揭示試題的考查本質。因此,分析試題背后的能力考查要求就顯得十分必要,不僅可以把握試題考查的本質特點,還能為教學實際提供有意義的反饋指導。鑒于初中科學試題中考查科學概念的分值比例最大,本研究將以科學概念學習領域為例,構建能力評估工具并進行具體應用,為我國教學評價改革提供有意義的參考。
三、科學概念學習領域能力水平層次界定
概念在人們的認知發(fā)展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幫助人們將現(xiàn)實世界中紛繁復雜的現(xiàn)象、事物加以抽象、概括以及分類并建立起相互間的廣泛聯(lián)系,最終形成對世界整體化、結構化的認識,即概念幫助人們將其認識從簡單的知覺水平提升到思維水平,這樣可以更加全面地認識世界。
對于科學概念(Scientific concept)的理解有兩種:一是“科學”,指“正確、合理”的意思,科學概念就被理解成“科學的概念”;另一個比較廣泛的理解是“科學領域的概念”,而由于對“科學”所指范圍的界定不同,科學概念也有著不同的理解。本研究所指的“科學概念”是“科學領域的概念”,而且將科學領域限定為狹義的“科學”,僅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自然地理等自然科學領域,即本研究所指的“科學概念”是指“在科學研究中經過假設和檢驗逐漸形成的、反映事物本質屬性的概念”,“可用言語進行科學的解釋并可在教學條件下獲得”。科學概念作為科學理論體系的基石,必然也是科學學習的基礎內容,科學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學習者改變他們的已有概念,而不是僅僅增加記憶中的信息量。
由相關學習理論可知,概念學習(Concept learning)是一個復雜的認知過程,不同的學習理論從不同的角度解析了概念學習過程,但概念學習過程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心理過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具體的行為變化表現(xiàn)出來。Ebert等人設計了概念漸進發(fā)展的概括化模型(圖2),該模型的主要思想是認為“大多數(shù)概念都太復雜,不能讓人在一步之內對某個概念從不了解到了解,基于人們自己的建構,概念經常被再分解成漸進發(fā)展的幾步”。學生在概念發(fā)展過程中,必定還受到一定外界環(huán)境的影響,經過復雜的生理心理刺激、強化、轉換而習得。
由此,本研究根據(jù)學生學習科學概念的發(fā)展歷程將科學概念學習領域能力從低到高劃分為4個水平:識別(回憶和識別相關科學概念)理解(從多方面釋譯科學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區(qū)別(區(qū)別和聯(lián)系相似概念,建立概念間的聯(lián)系)應用(對科學事實進行原理闡述),具體規(guī)定如表1。
本研究為考察科學概念學習領域能力水平層次結構的合理性,通過專家咨詢對水平界定進行評估,并由兩位研究者選取特定樣本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本研究所提出的科學概念學習領域的能力、水平及層次、結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實際的試題分析中具有可操作性和穩(wěn)定性,可用于進一步的研究。
四、初中科學試題科學概念學習領域能力考查傾向分析
本研究按照既定水平界定結果,針對所有研究樣本中有關考查科學概念的試題進行分析,分別從考查水平、歷時變化、學段差異幾個方面來揭示我國當前初中科學試題科學概念學習領域能力的考查特點。
1. 考查水平特點分析
本研究對所用研究樣本進行綜合發(fā)現(xiàn),水平1考查的分值比例為27.4%,水平4考查的分值比例僅為5.7%。這一結果表明,我國初中的科學概念考查仍以基礎為主(水平2和水平3之和占據(jù)66.9%),也就是我們傳統(tǒng)意義上所說的“理解為主”,而且需要記憶的內容過多、高層次水平考查要求較低。本研究通過進一步分析考查知識點的選取狀況發(fā)現(xiàn),考查內容過分集中于物質科學中的部分內容,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當前初中科學試題偏重知識考查。
2. 歷時變化特點分析
本研究以課程改革的開始年份為節(jié)點,分別對課改前、課改初期、課改深化階段的初中科學試題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同樣不令人滿意:隨著課改的進行,科學概念的考查比例不斷增大;高層次考查要求在課改初期有所提高,但課改深化階段卻又減弱;“理解”層次要求考查比例始終高居不下。
3. 學段差異特點分析
本研究選取了某個初中為特定研究對象,對該校的月考、期中/末考、地區(qū)綜合考、最終的中考試題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月考試題中只涉及水平1、水平2、水平3的考查;到了期中/末考,仍然是加大水平2、水平3的考查要求,更加重視學生對科學概念的理解;綜合考對科學概念各水平的考查已經非常接近中考情況,這再一次體現(xiàn)了我國當下的終結性考試對整個教學評價體系的制約。
五、研究啟示
本研究聚焦科學概念學習領域,通過對能力評估工具的研究和具體應用,得到如下啟示:①我國當前的初中科學評價仍以知識評價為主,“能力立意”考查的傾向并不明顯、能力考查似乎還是一紙空文,這亟待統(tǒng)一的科學能力評估標準去指導評價工作的開展,本研究正是這一標準研究的嘗試;②本研究發(fā)現(xiàn)中考作為“指揮棒”現(xiàn)象依然十分嚴重,這樣勢必會阻礙初中科學教學的有效開展,教學仍然重視知識的識記與理解,本研究所建構的能力評估工具客觀上為初中科學教師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操作性框架;③本研究作為一種嘗試性探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仍有不足之處:能力水平是否可以進一步抽象?能力水平之間的邏輯關系究竟如何?能力水平是否存在下位水平?這些都需要進一步去探索。
參考文獻:
[1] 龔偉.義務教育階段(7~9年級)科學學科能力測評框架構建及應用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3.
[2] 林崇德,楊治良,黃希庭.心理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78.
[3] 理查德?邁耶.教育心理學的生機――學科學習與教學心理學[M].姚梅林,嚴文蕃等,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165.
篇7
關鍵詞: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實踐環(huán)節(jié);考試;學分制
作者簡介:邵艾群(1974-),女,四川南江人,四川師范大學繼續(xù)教育學院助理研究員,教育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成人教育與職業(yè)教育;邵曉楓(1967-),女,重慶永川人,四川師范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教育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成人高等教育及當代中國教育改革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是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劃基金項目“三十年來中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學術發(fā)展史(1978-2010)”(項目批準號:12YJA880095)的階段性成果,課題主持人:邵曉楓。
中圖分類號:G7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16-0026-06
教學是所有教育過程中最核心的環(huán)節(jié),由于自學考試是一種個人自學、社會助學和國家考試相結合的制度,特別強調考生的自學,這就決定了其教學具有與普通高校教學不同的特點。三十年來,人們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問題進行了研究,公開發(fā)表的期刊論文約有300多篇,另外,在一些著作中也有相關的一些論述,本文擬對這些研究作比較系統(tǒng)的回顧與反思。
一、三十年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研究回顧
三十年來,我國學術界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主要進行了以下幾方面的研究:
(一)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過程的研究
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作為一種現(xiàn)代教育形式,當然也就有教學過程,而自學考試的特殊性決定了其教學過程也具有特殊性。學術界普遍認為,自學考試中的教學過程和自學過程是同一過程,二者是統(tǒng)一的,缺一不可。任福昌把這兩個同一過程概括為自學助學教學過程,強調這一過程是一種特殊的認識過程,認為這種自學助學認識具有間接性、組織性、教育性三個基本特點。[1]自學考試中教學的基本形式,是個體自學者學習、認知指定教材的過程。[2]陳斌認為,自學考試中有兩種教學形式:一種是社會助學中的面授輔導形式,另一種是師生通過媒體進行間接交往的教學形式。[3]教師編寫教材,是教學雙邊活動中教這邊的活動,教的活動凝結在教材中了,個人自學者學習教材就是在接受教師教的活動,并轉化為自己的學習活動。[4]張世俊認為,自學考試教學過程是以教學內容、教學手段為中介,以教材為載體,由教師的教和學習者的學所組成的雙邊活動過程。他認為這一教學過程有以下特點:以學生為中心展開;沒有固定的教師隊伍,教師的指導作用主要通過教學媒體對學生學習的指導來體現(xiàn);教學過程中的教材及媒體起著比常規(guī)學校教育中的教材更突出的作用;是以統(tǒng)一考試科目安排為導向,學生按自身的選擇而進行的教學活動過程,學生是這一教學過程的選擇者、設計者,是教學過程的主體和主人;教學評價和考試,表現(xiàn)為平時的形成性評價和國家合格性考試兩種。[5]
(二)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實踐環(huán)節(jié)考核的研究
1.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內涵與目標的研究。有人認為,自學考試實踐環(huán)節(jié)的考核是指在對應考者課程理論知識進行考試外,對其運用理論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檢驗,考核其動手操作、解決工作和生產實踐技能的環(huán)節(jié)。[6]有人認為,高教自學考試實踐環(huán)節(jié)考核是要促進自考生以多種形式自主創(chuàng)新地學習實驗知識與技能,培養(yǎng)自身的創(chuàng)新能力和整體實驗能力,初步養(yǎng)成科學探究的習慣。他們認為實驗環(huán)節(jié)考核的目標體系由實驗知識和技能、實驗情感兩大部分組成。考核的形式有實驗筆試與實驗室操作測驗兩種。[7]
2.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意義的研究。首先,人們認為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是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教學環(huán)節(jié),是相關專業(yè)考試計劃中所規(guī)定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是主考學校的工作職責之一,[8]是實現(xiàn)考試專業(yè)或課程目標的重要步驟,是保證考試質量的重要方面,[9]是自學考試向科學評價制度發(fā)展的需要。[10]其次,人們認為搞好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有利于培養(yǎng)自考生的創(chuàng)新意識,促使自考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及主體性的建立,有利于促進學生全面發(fā)展。[11]此外,還有一些人指出,搞好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是經濟社會發(fā)展對實用性人才的需要。[12]
3.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的現(xiàn)狀與問題研究。人們認為,自學考試在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中,不斷增加了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的內容,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走向規(guī)范化。[13]但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同時也存在著不少問題:一些主考學校和考生對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重視程度不夠;難以確定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中的質量標準;難以解決考生的分散性與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方式的集中性矛盾;學校設備消耗大、考生管理難度大、理論教學和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難統(tǒng)一、基礎教學與技能訓練的關系難以處理等諸多問題還有待解決[14];國家對自學考試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概念、要求的規(guī)定普教化;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的質量兩極分化嚴重;考試大綱常跟不上趟[15];重考核輕培訓;考核模式單一;實習鑒定和畢業(yè)論文中誠信缺失問題嚴重[16]。
4.對如何加強自學考試中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的研究。人們對加強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提出了一些基本措施:以國家有關規(guī)定為指導,有一定實踐經驗的教師擔任指導教師;對自考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要有計劃;主考院校公布論文題目和考生的論文研究方向是多樣化、多向化的;不隨便變動主考院校對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的計劃和考生選擇的論文題目;處理好自考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與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實踐性環(huán)節(jié)及考生的共性與個性等問題;堅持教師是考核的主體,考生是實踐的主體原則;力爭做到以考養(yǎng)考;評分標準合理[17];結合自學考試具有的特點,做好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工作[18];考核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既要嚴密組織,又要方便考生[19];確定“以人為本”的教育觀,構建新的測試目標體系;努力開發(fā)實踐課程學習和課件[20];規(guī)范實踐環(huán)節(jié)考核大綱;加強實習基地的建設;提高實踐環(huán)節(jié)考核的輔導效果[21];開展實踐教學的教研活動[22];增加企事業(yè)單位對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支持的責任感和使命感。[23]有人從實驗室管理與建設、考核管理與科研工作三個方面構建了自學考試實踐性環(huán)節(jié)的評估指標體系。[24]
(三)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教學與考試關系的研究
在自學考試中,由于考試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這就使得自學考試中教學與考試的關系也具有了與普通高等教育中教學與考試關系不一樣的特點,學術界普遍認為,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教學與考試一方面是統(tǒng)一的關系,另一方面二者又是對立的,必須堅持教考職責分離的原則。
1.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教學與考試是統(tǒng)一的。人們普遍認為,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教學與考試的關系首先是統(tǒng)一的關系。兩者相對獨立地存在于實現(xiàn)總體目標的過程中,在形式上表現(xiàn)為分離,內容上表現(xiàn)為統(tǒng)一。人們認為使自學考試中的教、學、考三者統(tǒng)一的途徑有二條: 其一:統(tǒng)一于“考”,這有力地保證了自考質量,但容易導致“教”從屬于考,使自考成為應試教育,甚至難以以一種獨立、完整的教育形式存在;其二:統(tǒng)一于“教學”,這有利于充分發(fā)揮“教”的主體作用,其缺陷是自考不可能按每個自學者的學習計劃、辦學者的教學計劃進行,而且難以正確把握考試標準和確保考試質量。有人認為應該既堅持考試的獨立主導地位、又積極發(fā)揮教學的主體作用。[25]還有人指出,自學考試中的教學與考試均以考試大綱和教材的內容為依據(jù),教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教什么。考試與教學水平必須相當,教多難,考多難;考多難,教多難。[26]
2.對“教考職責分離”的研究。為保證自學考試的質量, 1995年11月,國家教委在《關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社會助學工作的意見》中作出明確規(guī)定:“‘教考職責分離’是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基本原則,‘辦考者不辦學,辦學者不辦考,命題者不輔導’”。[27]人們對教考職責分離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第一,對教考職責分離涵義的研究:有人認為,“教考職責分離”是辦考人員、辦考機構與辦學人員、辦學機構在工作職責上的分離,絕非教學與考試的目標和內容上的分離。[28]還有人認為,教考職責分離這項原則的真實含義是自學考試系統(tǒng)中的實施“國家考試”的職責與社會力量對部分考生實施“助學輔導”職責的分離。[29]第二,對教考職責分離原則作用的研究:人們認為,“教考職責分離”突破了舊的傳統(tǒng)教學論,把考試從常規(guī)的教學環(huán)節(jié)中分離出來,將考試制度和教育形式統(tǒng)一起來;促進了命題理論和題庫的建設;[30]既保持了辦學方式和經費來源的多樣性,又堅持了教學標準的統(tǒng)一性;保證了自學考試這種充分開放的教育的質量;保證了自學考試作為國家考試所特有的嚴肅性、公平性和權威性[31];第三,對貫徹教考職責分離提出了一些措施:制定自學考試法;加強教師隊伍精神文明建設;制定規(guī)章、明確職責、加強管理;加強對社會助學活動的指導和監(jiān)督;實行分卷考試;在經濟上給命題教師以補償;全面推進題庫建設;閱卷必須實行流水作業(yè);形成社會輿論監(jiān)督機制[32];堅決制止自學考試機構舉辦助學班;對違背“教考職責分離”原則的單位或個人要嚴肅處理。[33]
(四)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學分制的研究
自學考試制度試點伊始,教育部就在1981年頒布的關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試行辦法》中規(guī)定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采用學分制。人們對這一教學管理制度也進行了一些研究。
1.對自學考試學分制特點的研究。有人認為,自學考試制度與學分制在本質上是相通的:首先,自學考試考生對象的差異性與學分制管理制度上的靈活性相吻合。其次,自學考試制度和學分制在重視目標管理上相通。[34]還有人認為,自學考試學分制具有以下特點:考試計劃的“剛性”與修業(yè)、修讀時間的“無限度”、“彈性” 的統(tǒng)一;選修專業(yè)、修讀方式的“自主性”與修讀課程的“指令性” 的統(tǒng)一;取得學分依據(jù)的“單一性”與確定課程學分因素的“雙重性”的統(tǒng)一。[35]
康乃美等人還對自學考試學分制與普通高校學分制、成人高校學分制及與美、日、英等國的學分制進行了比較。[36]此外,他們還對自學考試學分制與專業(yè)考試計劃、課程設置、教材建設、考籍管理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37]
2.對自學考試學分制現(xiàn)狀、局限性的研究。康乃美等人認為,自學考試中已基本形成了“單科考試、學分累計、零存整取”的學分管理模式,這一管理模式側重于目標管理,具有開放性、靈活性等特點,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質量監(jiān)控體系。但在自學考試學分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專業(yè)學分數(shù)偏低;考試實踐環(huán)節(jié)考核占的學分比例較小;選考課總體上門數(shù)偏少;強化了考試結果,淡化了教學過程環(huán)節(jié)等。[38]還有一些人認為,自學考試考生必須嚴格按照考試計劃中所規(guī)定的課程進行學習,對發(fā)揮考生的情趣、愛好及自身特點起了一定的束縛作用[39];現(xiàn)行的學分制封閉性、單向性較強,不能更好地適應當今的社會對人才多層次、多方面的需求;不利于構建高等教育的立交橋;對建立結構合理、靈活開放、特色鮮明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教育考試新體系,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40];自考專業(yè)培養(yǎng)目標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使得各專業(yè)之間共有的部分較少,不具有學分制要求的靈活性;自學考試在培養(yǎng)目標、課程體系優(yōu)化組合、管理手段、方式方法及助學媒體建設等方面還不完善。[41]
3.對改革自學考試學分制的研究。康乃美等人提出改革自學考試學分制要以社會發(fā)展對人才需求的多樣化、受教育對象的個體差異、學科特性、自考獨特的教育考試特性、自考現(xiàn)行學分制的局限性、國內外學分制的成功經驗為依據(jù),他們認為改革學分制的總的指導思想是使自考更主動適應社會對人才多方面的需要和個體差異,促進個體充分發(fā)展和各學科的發(fā)展以及學分制自身的完善。為此,要進一步擴大自考學分制計劃的開放性、靈活性和自由度;建立靈活、科學的學分管理體系;促進個人自學和社會助學。他們認為自學考試學分制改革的目標與主要內容是:調整課程比例,構建彈性模式、中性模式和剛性模式三種學分制專業(yè)考試計劃模式;建立適合于學分制需要的課程體系;實行區(qū)間制,形成一套新的學分計算與評定體系;實行“單科考試、學分累積、零存整取、分等畢業(yè)”的管理模式;增加考試次數(shù),延長每次的考試天數(shù);改進考試手段;實行協(xié)作開考模式;開展技能考核;變專業(yè)管理為課程管理;改革準考證和報名程序及報名手續(xù);建立學習支持服務系統(tǒng)。[42]此外,還有一些人提出了改革自學考試學分制的措施。如有人提出要實行選考制、學分績點制和導師制。[43]有人主張建立自學考試“超市”,由以專業(yè)為核心轉變?yōu)橐哉n程為核心。[44]有人提出,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要將課程設置為專業(yè)核心課程和選考課程兩個部分,每個專業(yè)只規(guī)定選考課程的最低學分,考生可以任意選取考試課程。[45]
二、對三十年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研究的反思
三十年來,學術界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存在著不少的問題。
(一)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
1.學術界越來越關注自學考試教學的研究。由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首先是以一種考試制度的形式被大家所認識,而且如何完善這種考試制度,使其更加科學化也是自學考試制度建立之初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學術界在自學考試制度建立之后的十來年間把主要方向放在了如何完善考試各環(huán)節(jié)的研究上。這些研究固然是重要和必要的,但自學考試作為一種教育,只有對其教學進行認真深入的研究,才能提高自學考試的質量,也才能使自學考試實現(xiàn)內涵式發(fā)展。這一點正在為學術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從相關研究成果出現(xiàn)的時間就可以看出。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也即是最近十多年間,這是一個可喜的現(xiàn)象,表明人們對自學考試的研究正在從表面走向深入。
2.在研究中緊密結合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實際。由于研究者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工作的第一線,因此,在研究中體現(xiàn)了緊密結合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實際進行的特點:一是注意把自學考試教學的有關問題與其他教育形式,尤其是與普通教育中的相關方面相區(qū)分。二是注意從自學考試制度本身及考生實際出發(fā),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不少改革的建議與措施。這樣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充實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的相關理論,構建具有自學考試特色的理論研究體系;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在實踐中有的放矢,真正發(fā)揮指導自學考試教學工作的作用。
3.對自學考試教學的不少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觀點。人們對自學考試教學中的較多問題進行了研究,既有一般性的教學問題研究,又有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別突出的問題的研究,如人們不僅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的過程和基本特點等教學的一般問題進行了研究,而且還針對自學考試中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薄弱,難于進行考核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同時,還對自學考試中教學管理方面的問題,如教學與考試的關系、教考職責分離原則、學分制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后幾項是自學考試教學中最具特色,也是問題最多最突出的方面。在研究中,人們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觀點,如在對自學考試教學過程的特點進行了較好的探討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學考試中,教學過程和自學過程是同一過程的觀點,這就準確地揭示了自學考試教學的特殊性,也符合自學考試教學過程中師生既可以直接交流為主,也可以間接交流為主的實際。再如,人們提出了自學考試中,教學與考試是既統(tǒng)一又對立的觀點,盡管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還存在著一些值得商榷的觀點,但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很有價值的,因為自學考試制度兼具考試制度與教育制度的特殊性,使其教學與考試的關系與普通教育相比,既有共同處,又有不同點,只有弄清了這一問題,才能正確處理自學考試中教學與考試的關系。還有,人們對自學考試中實踐性環(huán)節(jié)的考核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建議,對改革自學考試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有著一定的指導作用,特別是其中提到的自學考試實踐性考核與普通高校實踐性考核是共性與個性的關系,要從自學考試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對普通高校實踐性學習內容進行必要的精簡與合并的觀點是非常正確的。還有人嘗試構建了自學考試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的評估指標體系,邁出了對自學考試實踐性考核評估系統(tǒng)化和量化的第一步,是非常可貴的。另外,學術界在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學分制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績,突出表現(xiàn)為對自學考試學分制與國內外高等教育的學分制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比較,較好地總結了自學考試學分制中存在的問題,并為解決這些問題提出了一些較好的建議。確實,在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學分制中,存在的一個最突出問題就是考生可選的課少,而學分制的核心就在于選課,其初衷在于使學生能在較大范圍內根據(jù)自己的興趣、特長等選擇不同的課程,并靈活地安排學習時間,最終達到促進學生個性和潛能健康發(fā)展的目的。但如果可供考生選擇的課程太少,上述目的也就難于達到。而如果多開課程,則難度很大,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這是一個長期以來在自學考試中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也是長期以來遭到人們詬病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學術界提出的諸如擴大免考頂替范圍,學分互通,打破課程在專業(yè)之間的界限,使其盡可能共享與組合,與普通高校溝通等對策,為解決現(xiàn)存問題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二)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的研究還存在著比較多的問題
1.對自學考試教學的研究總體較薄弱,特別是對教學具體實施的研究不多。要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質量,為社會培養(yǎng)更多高質量的人才,同時,也使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自身得到可持續(xù)發(fā)展,就必須對其教學的各個方面進行比較深入和系統(tǒng)的研究。較之把自學考試作為一種考試制度而對考試各環(huán)節(jié)的研究,對自學考試教學各個方面的研究總體比較薄弱,而且在某些方面還異常薄弱,存在著比較嚴重的研究不全面、不系統(tǒng)的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學術界的研究集中在教學管理方面(如實踐環(huán)節(jié)考核、教考職責分離、學分制等方面),對于教學的具體實施的研究較少,表明人們對于自學考試的研究重心還沒完全從辦學(辦考)體制轉向培養(yǎng)體制。如,自學考試是一種以學生自主學習為主的教育制度,其更需要發(fā)揮學生的主體性,那么,如何借鑒建構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主體性教育等相關理論來指導自學考試的教學,樹立更加科學的教學理念,是很重要、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但目前學術界對這方面的研究幾乎沒有。再如,自學考試的教學目標是什么?確定教學目標的依據(jù)有哪些?對教學中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如何針對自學考試的特點選取不同的教學內容,采用不同的教學模式、教學策略、教學手段與方法組織教學,實現(xiàn)有效教學,如何在教學中培養(yǎng)考生的自學能力和主體人格,如何在教學中建立更加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如何衡量自學考試教學質量的高低,其評價標準、評價對象、評價過程是什么?等等問題的研究很少,有的甚至沒有,對如何改進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提高教學質量雖然有人進行了一些探討,但一是數(shù)量少,二是只是提出了一些最粗略的觀點,談不上多少學理性,也沒有多少可操作性。另外,隨著互聯(lián)網的發(fā)達和現(xiàn)代遠程教育的興起,網絡教學越來越成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的重要教學形式,如何開發(fā)網絡教學資源、建立良好的互動平臺、創(chuàng)新網絡教學管理模式等問題本應成為學術界研究的重要課程,但現(xiàn)在人們對此的重視還很不夠,只是剛剛開始研究。
2.研究的深度不夠,學理性比較欠缺。在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的研究中,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就是研究停留在比較表淺的層面,有的甚至只是一些工作經驗的總結,還沒有把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也就是說,在整個研究中,都存在著學理性比較欠缺的問題,極少以相關的理論作指導,而教學論作為獨立的學科,國內外都有著比較成熟的、豐富而系統(tǒng)的理論研究,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從自學考試的實際出發(fā),在深入研究這些理論的基礎上,借鑒其中有益的觀點和思想,指導我們對自學考試教學的研究,但學術界顯然對此關注和研究不夠,致使研究的理論性不強,大多數(shù)研究缺乏理論依據(jù),不少研究還停留在工作總結的水平上。如人們提出在自學考試中,教學過程和自學過程是同一過程,師生以直接和間接交往兩種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觀點本來是很好很正確的,但在研究中明顯表現(xiàn)出深度不夠的缺陷,還可結合教學過程的相關理論和自學考試的特點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論述。再如,在研究自學考試教學過程時,現(xiàn)有的研究都只是泛泛地提出要提高自學考試教學質量的觀點,但卻沒有從相關的教學和學習理論去作比較深入的研究。
3.一些觀點值得商榷和思考。人們在研究中提出了較多有益觀點的同時,也有一些觀點值得商榷和思考。如有人認為所有學生都是教學過程的選擇者和設計者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在自學考試中,學生確實具有最大的自主性,但在全日制助學的教學中,學生不能被稱之為是教學過程的選擇者和設計者,因為要學習些什么內容,如何學,學到什么程度等都不再是學生自己決定的,此時,教師起著主導作用。再如,一些人提出了自學考試中教學與考試統(tǒng)一于考試,考什么學什么,考多難學多難的觀點,這個觀點帶著明顯的功利性和應試教育色彩,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現(xiàn)象。在自學考試中,教學固然不能決定考試,但考試本身也不應該決定教學。因為如果完全以考定學,則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應試教育。從教育的基本規(guī)律看,考試和教學都只是教育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都要統(tǒng)一和服從于培養(yǎng)目標。自學考試既然是一種教育形式,則必定要遵循教育的這一基本規(guī)律,雖然自學考試中考試的地位特別突出,起著導向的作用,似乎在指揮和決定著教學,但實際上一切的環(huán)節(jié),包括考試在內,都要服從于培養(yǎng)目標的要求。因此,應該說,在自學考試中,教學與考試不能統(tǒng)一于教學,也不能統(tǒng)一于考試,而只能統(tǒng)一于培養(yǎng)目標,即二者都要以共同的培養(yǎng)目標作為出發(fā)點和歸宿,是培養(yǎng)目標決定著考試與教學。
綜上所述,三十年來,學術界對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方面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同時也存在著不少的缺陷和問題,如何完善現(xiàn)有的研究,是我們今后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課題和內容。
參考文獻:
[1]任福昌.論自學考試教育系統(tǒng)社會助學的教學過程[J].中國高教研究,1995(1):89.
[2]任福昌.論自學考試教育教學過程[C]//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辦公室.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育規(guī)律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1996:147.
[3]陳斌.輔導材料常寫常新——兼談自學考試教育的教學問題[J].河北自學考試,1994(9):2-3.
[4]陳斌.自學考試是一種教育形式[J].中國考試,1996(3):17.
[5]張世俊.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育形式的研究[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113,25-26.
[6]羅志堅.淺談自學考試實踐環(huán)節(jié)的考核[C]/肖輝.江西省高教自考優(yōu)秀論文集.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18.
[7][11] [24]鄭深.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實驗環(huán)節(jié)考核的理論研究[D].福建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12-38,3-9,43-47.
[8][17]周濱.談高教自考實踐性環(huán)節(jié)的考核及原則[J].中國成人教育,1997(3):13,14.
[9][13][14][18]于健,劉曉敏,姜寶平.關于自學考試實踐環(huán)節(jié)考核如何適應自學考試教育特點的思考[J].遼寧教育研究,2001(4):22,22-23,23,23-24.
[10][12][23]柳博等.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命題特點研究——從考試比較研究的角度[C]//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自學考試分會.石頭集——自考繼續(xù)創(chuàng)新研究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40,138-139,152-153.
[15][20]周家連.自學考試實踐性環(huán)節(jié)考核的教育學研究[J].中國考試,2005(5)上:36-39,39.
[16]趙青文.自學考試類專業(yè)實踐環(huán)節(jié)課程設置的問題與對策[J],成人教育,2008(1):69-70.
[19]中國成人教育理論專著編纂委員會.中國自學考試[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4:204-205.
[21]應躍興.自學考試實踐環(huán)節(jié)考核管理研究[J].成人教育,2008(4):19-20.
[22]陳師正.加強自學考試實踐環(huán)節(jié)管理[J].繼續(xù)教育研究,2002(2):75.
[25]高迎春.淺議自考制度中教學與考試的統(tǒng)一[C]//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辦公室.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育規(guī)律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1996:47-51.
[26][30]廣崇武.淺談自學考試的“教考職責分離”[J].中國考試,1996(5):46,47.
[27]國家教委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辦公室.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文件選編(1993-1996)[C].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78.
[28]趙秉真.試論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教考關系[J].黑龍江高教研究,1997(1):83-84.
[29]于信鳳,劉鑄.關于自學考試幾個相關問題的認識[C]//王新民等.自學考試制度的改革與完善研究.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201.
[31]劉玉良.論自學考試教育中的“教考分離”[J].遼寧高等教育研究,1996(1):117-123.
[32]劉忠勇.對高教自學考試教考分離的再認識[J].中國成人教育,1996(10):20.
[33]莊燦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考職責分離”淺析[C]//教育部考試中心《中國考試》雜志社.1999年考試研究論文專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39-143.
[34]邊星燦.多維視野中的自學考試制度[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156-159.
[35][36][37][38][42] 康乃美等.中國自學考試學分制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07,123-196,206-246,86-100,248-277.
[39][43]何乃錦,宋榕.自學考試與學分制——關于改革自考管理辦法的思考[J].河北自學考試,1996(12):21,21-22.
[40][45]王繼榮.談高教自學考試學分制改革[J].中國成人教育,2003(5):51.
篇8
[關鍵詞] 民族考古法;學科獨立性;邏輯體系;專業(yè)語匯;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 K8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學是20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一種研究方法,主要通過利用現(xiàn)代民族志與考古學材料進行類比,再現(xiàn)古代人類社會文化面貌,從而進行考古學或民族學研究的方法。它“被視為新考古學的戰(zhàn)斗吶喊”,有學者將其理解為“民族學與考古學相結合而成為新的一門學科”。也有學者將其理解為是從“新考古學”發(fā)展來的一門分支學科。但筆者認為,把它定義為一門學科還是為時尚早,因其學科獨立性尚缺,使其難以突破依附性,而帶有明顯的學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學的學科獨立性
國際博物館學委員會前主席馬丁?施爾在對于博物館學的學科性時言“博物館學要成為一門學科,必須有專業(yè)的語匯體系,有自己的邏輯系統(tǒng),有明確的研究對象”。這對于任何科學的學科性考察明顯也是有借鑒意義,對于民族考古學的學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標準衡量。
從研究對象來看,有學者闡釋“民族考古學的學術領域是中國古代民族的考古學文化,它的研究資料,可分為氏族遺址、民族古遺物及與民族遺址、民族古遺物相關的古氣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環(huán)境等的遺跡或遺留”。但稍稍對比于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即“遺跡和遺物”,可發(fā)現(xiàn)兩者是有重疊的,民族考古學在研究對象上的獨立性很明顯的依附于考古學之上,也可以說只是考古學的小范圍研究對象,而不存在獨立研究對象。
二、邏輯體系
至于邏輯體系,側重是指用自己獨有的研究方法來解決屬于自身領域的問題,民族考古學的研究方法還是處于混沌狀態(tài)的。《民族考古學概論》提出的幾點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層學、器物形制學、文化區(qū)系類型理論,民族志與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層位學”、“類型學”及“文化區(qū)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則主要是用民族志類比法,而這恰是民族學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學概論》則認為主要應用的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這些包括有:進化論、文化的傳播、文化圈理論、文化輻合論等。
可見,民族考古學并未具有獨立的邏輯體系,而只是借鑒考古學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學的類比法,加以利用人類學的文化人類學理論。陳淳先生認為“民族考古學的分析一般有兩種模式,其一是直接歷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學研究對象與考古學遺存有歷史淵源關系的分析;而后者則是用民族學研究一些具有規(guī)律性的現(xiàn)象來分析并無淵源關系的考古發(fā)現(xiàn)”。
顯然,“民族考古學”缺乏自身的邏輯體系,卻帶有很強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將其定義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層位學”和“類型學”也同樣可以成為一門學科,這很明顯混淆了學科研究方法與獨立學科的范圍,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專業(yè)語匯體系
專業(yè)語匯體系的構建,前提是需要有專業(yè)研究隊伍的存在。筆者認為,就目前而言,研究隊伍是存在,因為對民族文物或是遺存進行研究的學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兩位先生的研究,但專業(yè)語匯體系卻還未形成,而只是借鑒了考古學的語匯體系對考古學文化進行闡述,如“城址”、“居址”、“窯藏”、“墓葬”之類術語。
專業(yè)語匯體系的建立,還需在大學中占有一席之地,作為一門學科建立起來。而實際卻是標榜為獨立學科的“民族考古學”,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學或民族學門類之下,而只作為一個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專業(yè)之中,這同“沙漠考古學”、“水文考古學”類似,如中山大學也只是將其列為考古學的一個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學的博士生導師許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學并不是考古學的分支學科,而是考古學的一種闡釋方法論。這種方法對于闡釋考古遺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遺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種方法,不可偏廢,實有完善、充實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將其作為獨立學科為立場而進行著作的撰寫,如《民族考古學概論》之類的出版,筆者認為,是帶有明顯的投機性,因其根本觀點即對民族考古學的定義、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闡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懸浮性,未能提出屬于學科的語匯體系,而完全依賴于考古學與民族學兩學科的支架之上。
四、結語
綜上所述,一個學科的建立就必須有自己獨立的學科體系、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專業(yè)的研究隊伍。顯然,民族考古學還是缺乏學科所需要的獨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與“類型學”、“層位學”的研究方法帶有明顯的類似性,因此,將其稱為“民族考古學”法而從屬于考古學研究方法之列顯得較為合適,而將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帶有牽強性。同時,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學與民族學的結合緊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學科互滲的結果,但我們不能阻止兩者互滲,我們要做的在認同考古學須和民族學結合下,讓兩者可以得到有進一步的發(fā)展,才會有更寬的拓展空間存在。
參考文獻:
[1]汪寧生.再談民族考古學[A].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C].1998,4.
[2]海.博物館理論研究的再出發(fā)[J].中國博物館,2001,(01).
[3]陳淳.談談民族考古學[N].中國文物報,1990-5-10.
篇9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葉以來,考古學的理論的形成與發(fā)展有了很大的飛躍,尤其是通過對中外考古學理論的對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學理論發(fā)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學理論在以后考古學的進一步發(fā)展道路上一定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某種角度來說,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們一定要對考古學理論的認識上升到一個高度,因為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我們進行考古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它決定著我們具體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響,而且也決定著考古學以后的發(fā)展道路和發(fā)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們對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種難以言明的情懷。其中有人們對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對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對古代事物的喜歡,等等。這也許是科學考古學形成的原因之一。科學考古學在形成之后就在技術和理論的影響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論的發(fā)展過程更是曲折,可以說考古學的理論是在不斷的否定基礎上前進的。下面就談一談關于考古學理論方面的認識。首先有這兩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我們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第二,考古學理論是什么?
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這個問題在現(xiàn)在看來猶如廢話,可是在中國考古學的早期它確實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那么無論我們在這上面花費多大的時間和精力,那都只會是徒勞。結合我國考古學的形成和早期的發(fā)展來看,考古學的理論在我國基本上沒有什么地位。張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時間與傳統(tǒng)》的中文譯本的序中提到,最近兩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年鑒》固然是對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很可靠的反映,而在這里面根本沒有“考古學理論”這個范疇。可見,“理論”這件東西在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中可以說沒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學理論在我國早期的考古學的研究中沒有被引起足夠的重視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現(xiàn)代考古學在我國的形成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當時受國內的“五四”運動和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對上古史提出了質疑,而且還對史籍中對早期國家的記載提出了質疑,于是這就遭到傳統(tǒng)史學派的反對,但是他們又沒有具體的實物證據(jù)。所以,雙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實物。其次,我國早期在國外留學的學生也陸續(xù)回國,他們大部分在國外學的是地質古生物學。李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人類學,并獲得了博士學位。回國以后由于各種原因他決定開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進行初步調查,并與1926年10月到12月開始了對夏縣西陰村的發(fā)掘。關于李濟先生發(fā)掘夏縣西陰村的動機我們可以在《李濟文集卷二》里找到,受當時安特生在對我國進行的一些考古發(fā)掘基礎上形成的對我國史前文化的認識和史前文化與歷史文化的關系問題的認識上,李濟先生想通過自己的實際調查與考古發(fā)掘找到關于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濟先生在山西夏縣進行的考古發(fā)掘為我國的田野考古發(fā)掘掀開了帷幕,也正是他的這一動機或發(fā)掘目的使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向了歷史學的范疇,其在發(fā)掘過程中對地層和出土物的觀察和分類的方法還難以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考古學和人類學,并受了現(xiàn)代考古學的專門訓練。1930年夏季畢業(yè)回國之后,便開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發(fā)掘,其主要貢獻之一是依據(jù)考古地層學的證據(jù),確定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間的關系,解決了中國考古學上的一個大問題。由于這些早期的學者將中國考古學堅定的放在了歷史學的范疇之內,將考古學引上了一條有別于西方考古學的發(fā)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學研究在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正統(tǒng)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學有著共同目標的證經補史的道路,也就是說考古學的發(fā)展是為歷史學提供服務的。它的目的只是通過考古發(fā)掘來填補歷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國考古學所運用的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都是用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考古學理論在我國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對于考古學的研究,筆者認為可以將其分為兩個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積累,這其中又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獲取考古材料的途徑,二是對獲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礎性的研究,為后面的進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礎。第二是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關于第一個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調查與發(fā)掘以及對發(fā)掘現(xiàn)場遺跡和遺物的基本信息的獲取,在發(fā)掘過程中對考古地層學的應用以及對出土遺物所進行的類型學的分析,而且從我國考古學發(fā)展的歷程來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發(fā)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的發(fā)掘和河北滿城漢墓的發(fā)掘都是在無意中發(fā)現(xiàn)的。所以在第一個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積累方面對考古學理論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對考古學的理論要求非常高。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如果沒有考古學具體理論的指導,那么對考古學的解釋可能就會停滯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學的發(fā)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對考古材料的解釋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積累的多少。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學科里一樣,如果我們只是積累現(xiàn)象而不去總結規(guī)律的話,那么就不會有那些對后來影響巨大的定理。考古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是一門學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學科一樣在于探索在某一領域的規(guī)律,而考古學要探索的規(guī)律不只是簡單的還原古代社會人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類在過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圖探索考古現(xiàn)象產生的原因,并解釋社會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換句話說,如果古代人們的生活是現(xiàn)象,那么我們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導致這些現(xiàn)象的發(fā)生。而我們現(xiàn)在的考古發(fā)掘所發(fā)現(xiàn)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生活的全部遺留。由于各種自然和人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質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導致了我們現(xiàn)在所發(fā)現(xiàn)的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的全部遺留物。所以我們要通過僅存的不完整的遺存去探索古代人們生活的規(guī)律,其難度無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沒有理論的指導,那么其結果就微乎其微。我們可以把考古發(fā)掘的遺留物劃分為物質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對于物質生活方面的遺留物,對精神方面的遺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論的指導,因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質生產對象,它反映的都是人們的日常精神生活。考古學探索的問題被西方考古學家用6個“W”來表達,它們是Who(誰)、What(什么)、When(何時)、Where(何處或從何而來)、How(怎么回事)和Why(為什么)。②隨著考古學的不斷發(fā)展,考古學家把他們研究的重點越來越放在了后兩個方面,也就是對產生事物內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產生的內在原因而不是對事物外在方面的觀察和總結,所以考古學的理論是在考古學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來越被重視的一部分。
篇10
關鍵詞:辯證唯物主義;高校;考古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2-0264-02
高校考古教學發(fā)展到今天,已經成為受到廣泛關注的熱門學科。但目前考古學專業(yè)教學存在很多弊端,影響了人才培養(yǎng)質量,如何改革高校考古教學以適應當今社會發(fā)展的需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任。本文認為高校考古教學改革要以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為指導,形成人才培養(yǎng)、學科建設、教學理論和方法三位一體的改革體系。
一、用“求是”的理論改革人才培養(yǎng)模式
高校考古專業(yè)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科學的人才培養(yǎng)制度。21世紀中國高等院校培養(yǎng)考古人才的標準是懂得文物考古法規(guī)、多學科基礎知識扎實、學術思想進步、具有嫻熟的田野技術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高素質綜合人才。然而,當代考古學人才的培養(yǎng)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一方面高校內部考古學科的資源仍相對匱乏。“考古學本身是一門基礎的人文學科,但其研究理念和方法技術卻具有文理交叉的性質,在對古代遺存進行分析研究的過程中,不但需要多種儀器設備,也需要具有多種知識背景的人員”[1]。如果高校過于看重招生數(shù)量和規(guī)模,依據(jù)招生盜顆渲醚Э譜試礎⑷范ㄊψ時嘀疲或者簡單地將考古學作為人文社會學科進行資源配置,就會嚴重地限制考古學科的進一步發(fā)展。另外,考古專業(yè)的課程設置也不甚合理,專業(yè)分割過細,知識結構單一,多學科融合層面相對薄弱。此外,在碩士研究生培養(yǎng)層面上,面臨著本科非考古專業(yè)的人數(shù)較多、生源基礎差的問題。很多考古專業(yè)本科生放棄了本專業(yè)的學習深造機會,改行從事其他專業(yè)的工作;大量的非本專業(yè)的本科畢業(yè)生卻帶著對考古學的誤解步入考古專業(yè)攻讀碩士學位。這些學生的考古學專業(yè)基礎相對較差,在碩士階段首先面臨的就是考古學專業(yè)基礎和專業(yè)實踐的補課問題,更高層次研究能力的培養(yǎng)無疑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博士研究生由于種種因素限制,與研究課題相結合的田野工作難以開展,因而導致依托田野發(fā)掘和第一手資料開展的博士學位學術成果數(shù)量不多。要改變這一現(xiàn)狀,關鍵是要實事求是,立足于人才培養(yǎng)現(xiàn)狀深化改革。總的說來有兩個原則:一是高校的改革與發(fā)展必須與現(xiàn)實社會的發(fā)展需要相適應,成為向社會培養(yǎng)輸出優(yōu)秀人才,促進社會發(fā)展進步;二是必須尊重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考古人才培養(yǎng)改革必須在保持專業(yè)特色的基礎上,實現(xiàn)專業(yè)培養(yǎng)目標、培養(yǎng)方式和課程體系改革的全面發(fā)展。總之,在考古學的人才培養(yǎng)方面要實事求是,該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該怎樣根據(jù)人才培養(yǎng)目標設置學科內容都要從實際出發(fā),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抄。
二、根據(jù)運動理論促進學科建設
學科建設要依托于人才培養(yǎng)目標,而人才培養(yǎng)目標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變化的,培養(yǎng)什么樣的考古學人才不同的歷史時期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學科建設也要不斷改革和完善,用運動的原理改革學科建設才是正確的方向。
首先,用運動的觀點構建史前史。史前史占據(jù)人類歷史的很大一部分,不能忽視,特別是人類、農業(yè)和文明三大起源問題。將這些考古學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及時補充到學科中,可以拓寬學生的視野,啟發(fā)他們從世界歷史體系角度來審視中國古史,彌補了文獻古史的不足和局限。
其次,用運動的原理建設考古學學科體系。“考古學的研究打破了中原中心論的錯誤與偏執(zhí),將中原之外的燦爛文化揭示出來。這一方面的內容在學科體系構建時需要重點關注,比如商時期的四川盆地出現(xiàn)了不低于中原文明的三星堆文明,北方草原也有極富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銅文明。通過與文獻的對比,有助于學生摒除中原文化優(yōu)于其他地區(qū)文化的錯誤史觀,對于學生樹立以考古學學科新知識體系為基礎的正確歷史觀有重要作用”[2]。
再次,用運動的原理豐富歷史學學科資料。教學中要適當增加史料比例,將不同歷史時期的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講授,引導學生對史料進行辨析、解讀,將歷史文化的背景與考古資料對照分析,增強學生的證據(jù)意識和邏輯思維能力。比如,禮制在中國古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思想和民俗上都有諸多表現(xiàn),文獻記載相當普遍,而其物化表現(xiàn)形式也在考古資料中大量存在,在教學內容設計中應將這些內容突出。
第四,地方史的研究往往是地方院校歷史專業(yè)的重要內容。我院考古專業(yè)根據(jù)考古新發(fā)現(xiàn)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增加紅山文化等特色考古學文化內容,使學科建設隨著考古發(fā)現(xiàn)不斷推進。這有助于增強學生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認識,并有助于學生地方文化情結和文化遺產保護觀念的形成。
總之,考古教學很多領域都有擴展的空間,考古學的學科建設要與時俱進,教學改革也應永遠處于運動中。
三、根據(jù)實踐理論更新教學理念
考古實踐既是培養(yǎng)考古專業(yè)研究生實踐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因此,考古教學改革一定要遵循實踐的原則。
首先,考古學是文理交叉學科,實踐環(huán)節(jié)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考古學專業(yè)應該加大考古學專業(yè)研究生實踐的力度,進一步完善教學體系。目前,學界以及教育界己經認識考古實踐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嘗試。比如,開創(chuàng)了田野學校這一培養(yǎng)考古學專業(yè)研究生創(chuàng)新能力的新途徑,期望能從根本上解決課堂講授與實踐相脫節(jié)的問題。
其次,考古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為了適應高等教育的發(fā)展以及國家各項事業(yè)對人才綜合素質和能力的要求,研究生階段的田野實踐應被納入考古學科研究生專業(yè)的培養(yǎng)計劃中,以便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理念,達到高校提高研究生綜合素質和能力之培養(yǎng)目標。
再次,考古學是一門綜合的學科,其發(fā)展既和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受到歷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又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科學發(fā)展的影響,田野調查雖然也受以上因素制約,但仍然不可或缺。同時,田野實踐在我國考古學專業(yè)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較為重要的作用,根據(jù)當前對考古學人才的要求:即著重培養(yǎng)具有扎實的理論基礎、過硬的基本技能和創(chuàng)新能力,我們認為田野實踐的開展和推行對我國高等院校考古學專業(yè)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養(yǎng)是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學的重要目標之一,也是落實科研、理論、實驗交叉融合的保障。基于這一指導思想,在注重考古學專業(yè)研究生基礎訓練的同時,應著重培養(yǎng)研究生的動手能力、學術創(chuàng)新能力”[3]。在教學改革中,除了要強調進行考古學的基礎訓練,即要求研究生熟練掌握國內外考古領域的基本理念、調查方法和資料分析方法,同時更要注重培養(yǎng)研究生的動手能力、發(fā)現(xiàn)問題的能力和進行學術創(chuàng)新的能力。
四、用發(fā)展的觀點促進教學方法改革
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古代的遺跡和遺物,考古專業(yè)的學生需要熟悉各時期遺跡、遺物的特征和演變規(guī)律,因此教學中直觀的內容占有較大比例。而傳統(tǒng)的考古教學一般是課堂灌輸,缺少考古調查、發(fā)掘和遺物等直觀、動態(tài)化演示,因此,必須用發(fā)展的觀點審視課堂傳統(tǒng)教學模式改革。在課堂教學中要采用大量r活的圖片和視頻資料來提高學生的學習和研討興趣,因為考古學本身就是直觀的、動態(tài)的,學生學習方法也在不斷在調整變化中,所以考古教學方法也要不斷變化。近年來,隨著計算機的普及,多媒體技術在考古學教學中的應用更加廣泛。在教學當中,多媒體教學法的高效、規(guī)范、聲像結合,大大優(yōu)化了考古學教學,并被學生所接受。在考古教學中采用這種教學手段,可將抽象內容具體化,將復雜事物簡單化,將微觀事物宏觀化,并能多角度地向學生傳遞教學信息,大大提高了課堂教學效果。“另外,通過多媒體教學,又可以節(jié)省時間,來進行其他的課堂教學,如組織和本節(jié)課相關的課堂討論、學生主題發(fā)言、讀書報告會等輔教學活動”[4]。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教學思想、教學方式、教學內容及課堂結構發(fā)生巨大的變化,而且,對于拓展學生的知識結構、開拓學生學術視野,激發(fā)學生的求知欲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運用多媒體教學可以給學生創(chuàng)造一個豐富、輕松的學習環(huán)境。多媒體技術,使教學內容形聲化、表現(xiàn)手法多樣化,對學生的感官進行多路刺激,使學生處于一種輕松愉快的環(huán)境中。這就從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學生聽課造成的疲勞和緊張,充分調動學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從而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除了采用多媒體技術外,還要綜合分析各個門類考古的學科特點,用“發(fā)展”的理論調整教學方法。因為考古學是一門涉及面很廣的學科,它和歷史學、古文字學、語言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宗教學、植物學、動物學、體質人類學、地理學、物理學、化學等都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這就要求教師在課堂上給學生提供各個門類相關的考古學信息,培養(yǎng)專業(yè)性強、學識精深的各門類考古學人才。時代在不斷發(fā)展進步,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斷提高,因此,教學方法的改革要根據(jù)教學內容的不斷更新而調整。
總之,高校考古教學改革要立足于時代需要,實事求是,要不斷完善學科建設,遵循考古學的實踐性原則,不斷改革創(chuàng)新,更新教學方法。用辯證唯物主義理論指導高校考古教學改革,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資源和人力資源,也必將取得很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1〕韓國河.關于考古學人才培養(yǎng)的思考[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06):137―138.
〔2〕彭長林.歷史專業(yè)考古學教學改革探討[J].凱里學院學報,2015,(01):164.
相關期刊
精品范文
10考古學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