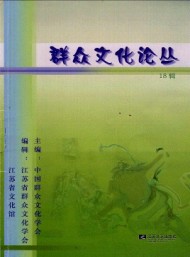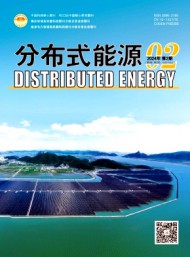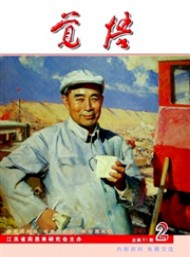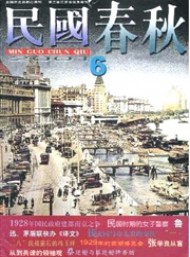表觀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時間:2023-12-28 17:50:3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表觀遺傳學的意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 成癮相關記憶的表觀遺傳學機制 愈肝顆粒對大鼠肝癌的抵制作用及其表觀遺傳學機制 自身免疫疾病的表觀遺傳學 表觀遺傳學的研究進展 表觀遺傳學與人類健康 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表觀遺傳學與食管癌相關性研究進展 表觀遺傳學調控的研究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表觀遺傳學在抗腫瘤領域的研究現狀及前景 研究生《表觀遺傳學》課程的教學改革與探索 表觀遺傳學在中醫藥研究中的應用 表觀遺傳學標記在急性白血病微小殘留病檢測中的臨床意義 急性髓細胞白血病表觀遺傳學的靶向性和個體化治療策略 淺析表觀遺傳學在高中生物課程中的教育價值及其實現 神奇的遺傳學 遺傳學的未來 表觀遺傳學有助解釋妊娠高血壓 關于遺傳學教學的思考 遺傳學中的數學思想 遺傳學的概率計算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有很多基于亞硫酸氫鹽(bisulfite)處理DNA的檢測啟動子甲基化的方法,其原理是亞硫酸氫鹽修飾將去甲基化的胞嘧啶轉化為尿嘧啶,但留下甲基化的胞嘧啶不變。在隨后通過聚合酶鏈反應(PCR)擴增CpG區域時,尿嘧啶被轉化到胸腺嘧啶,而從甲基化的胞嘧啶則在此過程之中保持不變。甲基化和去甲基化的胞嘧啶之間的區別可能是胞嘧啶和胸腺嘧啶之間的區別,最初甲基化的程度可以由Pyrosequencing TM技術計算。最近亞硫酸氫鹽測序、(定量)甲基化特異性PCR(MSP, methylation-specific PCR)、甲基化敏感單克隆核苷酸引物延伸(Ms-SNuPE,methylation-sensitive single nucleotide primer extension)等技術也普遍用于基因的甲基化測定。另有一些技術可以用于研究全基因組染色質結構的改變。例如利用特異性識別甲基化胞嘧啶的抗體進行免疫沉淀實驗,后進行質譜測定;另一方面也利用DNA結合蛋白抗體或組蛋白的特異性修飾抗體,進行染色質免疫沉淀(ChIP,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測定,后進行DNA測序。更新的技術可以結合芯片,進行高通量的實驗設定。
迄今為止,有關于神經性疼痛模型的表觀遺傳學研究數量并不是很多。從以往的研究報道來看,DNA甲基化、組蛋白乙酰化和非編碼RNA的調控模式在神經性疼痛的發生、發展及其維持的各個環節都有發生非常明顯的改變并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將進一步的探索表觀遺傳學參與神經性疼痛的調控的分子機制,研究相關的修飾程序是如何帶來了持久而長期的痛覺異常和痛覺過敏的,并為以后進一步的深入研究神經慢性病理性疼痛是如何發生、發展與維持打下基礎,并為其后續的控制、治療提供新的作用靶點。
*通訊作者:陳恒玲
參考文獻
[1] Doehring, A., G. Geisslinger, and J. Lotsch, Epigenetics in pain and analgesia: an imminent research field. Eur J Pain, 2011. 15(1): p.11-6.
[2] Chen, Y.C., et al., 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 PRDM12 is essential for human pain perception. Nat Genet, 2015. 47(7): p.803-8.
[3] Bell, J.T., et al., Differential methylation of the TRPA1 promoter in pain sensitivity. Nat Commun, 2014. 5: p.2978.
[4] Bai, G., K. Ren, and R. Dubner,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persistent pain. Transl Res, 2015. 165(1): p.177-99.
[5] Zhong, T., et al., Parental Neuropathic Pain Influences Emotion-Related Behavior in Offspring Through Maternal Feeding Associated with DNA Methylation of Amygdale in Rats. Neurochem Res, 2015. 40(6): p.1179-87.
[6] Li, K., et al., Epigenetic upregulation of Cdk5 in the dorsal horn contributes to neuropathic pain in rats. Neuroreport, 2014. 25(14): p.1116-21.
[7] Favereaux, A., et al., Bidirectional integrative regulation of Cav1.2 calcium channel by microRNA miR-103: role in pain. EMBO J, 2011. 30(18): p.3830-41.
[8] Sakai, A., et al., miR-7a alleviates the maintenance of neuropathic pain through regulation of neuronal excitability. Brain, 2013. 136(Pt 9): p.2738-50.
篇2
例如,Baylin實驗室早在1994年就觀察到約60%的腎癌起因于腫瘤抑制基因VHL的失活性突變,同時也觀察到在約20%的非VHL突變腎癌樣本中,VHL啟動子序列的高度甲基化導致該基因的表達被完全抑制。隨后,Baylin等又觀察到P16也可以由于其啟動子被高度甲基化而被抑制,從而導致很多種腫瘤的發生。近期人們還發現,表觀遺傳和遺傳也可以互相配合,抑制抑癌基因從而導致腫瘤的發生。例如,抑癌基因的一個等位基因因突變而失活,另一個等位基因則可能是因為啟動子甲基化而被抑制表達。其次,異常的DNA甲基化還會導致某些抑制細胞轉移的基因表達被抑制,進而促使腫瘤發生轉移。
這些轉移相關基因包括鈣粘附蛋白(E-cadherin)基因、乙酰肝素硫酸鹽合成途徑、蛋白酶類組織抑制劑、軸突生長導向分子、血小板反應蛋白(thrombospondins)和層粘連蛋白等。最明顯的是E-cadherin基因(CDH1):某些原發腫瘤呈現E-cadherin超甲基化,但相應轉移灶E-cadherin基因卻未發生甲基化。這些結果顯示,在原發腫瘤中E-cadherin表達缺失,但遠端轉移灶中E-cadherin表達可恢復。由此可見,轉移細胞要正確整合入一個新的正常細胞環境,E-cadherin去甲基化和再表達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基因內含子DNA,如LINE1和Alu重復序列被激活后,可轉錄或轉位至其他基因區域并擾亂基因組。LINE1和Alu元件內較高程度的低甲基化與神經內分泌腫瘤和淋巴結轉移相關。還有研究顯示,許多具有高侵襲性或具有轉移潛能的腫瘤中,某些基因呈現低甲基化,如SNCG和uPA/PLAU。
影響DNA甲基化水平的多種酶,包括DNMT3a、Tet蛋白的突變或失活也被證明與多種白血病有關。例如,急性髓細胞性白血病(acutemyeloidleukemia,AML)和其他幾種淋巴細胞白血病中發現MLL-TET1的異常融合。這些證據都提示了DNA甲基化在癌癥發生和發展中的關鍵作用。
組蛋白修飾與腫瘤
8個組蛋白(2XH2A、2XH2B、2XH3、2XH4)和約146bp的DNA組成染色質的最基本單位——核小體。組蛋白上面的很多氨基酸可以通過各種翻譯后的可逆的共價鍵修飾,包括甲基化、乙酰化、磷酸化、泛素化等,形成理論上數目繁多的特定的“組蛋白密碼”來形成“開放”或“關閉”的局部染色質結構,或是決定何種蛋白結合到特定DNA區域,從而調節多種DNA功能,包括轉錄、復制以及損傷修復。例如,組蛋白的H3K4、H3K36、H3K79三甲基化、H3K9和H3K14的乙酰化以及H4K20和H2BK5的單甲基化都導致基因激活,而H3K9的單/雙甲基化和H3K27的三甲基化會抑制基因表達。更有意思的是,在胚胎干細胞(可能也包括其他細胞)內,“預備狀態基因(poisedgenes)”有非常特異的“雙調節碼——H3K4和K3K27的三甲基化”,使得這些基因很容易被激活。迄今已發現數百種蛋白酶參與組蛋白共價修飾的精細調控。組蛋白修飾異常是腫瘤細胞的一個明顯標志,例如,腫瘤細胞有著非常顯著降低的H4K20的三甲基化和H4K16的乙酰化。而關于組蛋白修飾酶在腫瘤組織中的突變或表達異常的報道更是層出不窮,現在已知較多的是修飾組蛋白乙酰化和甲基化的酶在多種癌癥中的突變,而其他類的酶與癌癥的關系則還處于研究初期階段,例如最近發現癌基因JAK2其實是一個組蛋白激酶。
1組蛋白乙酰化酶和去乙酰化酶
數種組蛋白乙酰化酶基因的移位在許多種血液腫瘤中頻繁出現,這些酶包括EP300、CREBBP、NCOA2、MYST3、MYST4等,而腺病毒蛋白E1A和SV40T結合組蛋白乙酰化酶EP300和CREBBP后可異常激活許多基因,導致細胞增殖分裂加快從而在很多組織系統中引發癌變。有研究發現,EP300的突變和另一種組蛋白乙酰化酶KAT5的染色體移位可以大大增加結直腸癌、胃癌、乳腺癌以及胰腺癌的發病率。HDAC類和Sirtuins類兩個家族的組蛋白去乙酰化酶都在很多類型的癌癥中高表達,抑制他們的活性即可以抑制腫瘤生長。
2組蛋白甲基化酶和去甲基化酶
很多組蛋白甲基化酶和去甲基化酶也被發現與癌癥發生發展密切相關。在許多種癌癥中都有由于染色質移位、基因擴增或缺失、突變、融合、過表達或表達抑制等多種方式導致的酶表達水平或活性異常。例如,H3K4甲基化酶MLL在大于70%的新生兒白血病和5%~10%的成人AML和淋巴細胞性白血病中發生部分重疊性復制(partialtandemduplication,MLL-PTD)或者基因融合。和MLL異常有關的白血病往往對現有治療方法不敏感,從而預后很差。已發現的可以和MLL發生融合的基因有80多種,其中一個關鍵機制是MLL和其他蛋白融合后引起的DOT1L,即一種H3K79甲基化酶,其結合到更多的位點可以導致很多促癌基因異常激活。
另一個H3K4甲基化酶SMYD3高表達于結直腸癌和肝癌中,使細胞繁殖和惡變加強。NSD1是一個H3K36(還可能包括H4K20)甲基化酶,其與白血病、膠質瘤、神經母細胞瘤以及一種非常容易患癌癥的Sotos綜合征有關。但在這些組蛋白甲基化酶中,與癌癥關聯證據最多且最復雜的還是H3K27甲基化酶EZH2。EZH2是PRC2復合物的關鍵成分,通過影響基因表達而在干細胞自我復制、定向分化、器官形成等生命過程中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EZH2起初被發現高表達于前列腺癌、乳腺癌、結直腸癌、皮膚癌和肺癌,其誘發癌癥的機制為:EZH2對干細胞特異基因的激活以及對很多抑癌基因如P16、P27和BRCA1的調控等等。
已有研究發現,抑制EZH2活性的確能在小鼠模型中抑制甚至完全阻斷腫瘤的生長。在彌散性大B細胞癌中,EZH2的一個等位基因發生突變后和另一個等位基因表達正常的EZH2組合會出現更強的酶活性。而新近的研究卻發現EZH2在25%的T細胞白血病中發生失活性突變。因此,根據不同的細胞環境,EZH2既可以是癌基因,也可以是抑癌基因。一方面,關于組蛋白去甲基化酶在癌癥中的研究也越來越多。例如,催化雙甲基或三甲基化的H3K4去甲基化的JARID1家族的多個蛋白在多種癌癥中高表達且很可能是致癌原因。對EZH2起拮抗作用的H3K27去甲基化酶UTX在很多癌癥中發生突變。催化單甲基化或雙甲基化的H3K4去甲基化的LSD1在乳腺癌中的表達缺失,研究表明,LSD1的表達可以抑制乳腺癌細胞的侵襲和轉移,并且影響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growthfactor,TGF)信號傳導,這表明LSD1是一個強效的抑癌基因,可能是干預乳腺癌轉移的新的分子靶點。
染色質重塑與腫瘤
染色質重塑(chromatinRemodeling)指的是在沒有DNA和組蛋白共價修飾變化的情況下,染色質結構發生的變化,包括核小體的解體(DNA和組蛋白的分離)、移位、DNA-組蛋白之間親和力的變化以及染色質三維結構的變化。染色質重塑通常是由一些能水解ATP產生能量的較大的復合物催化的,這些復合物包括SWI/SNF、ISWI、INO80等,它們通過影響染色質結構而調控轉錄、復制、DNA損傷修復等等從而在干細胞自我復制、分化發育、器官形成等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近幾年研究發現,這些染色質重塑復合物,尤其是SWI/SNF復合物與多種癌癥相關。SWI/SNF復合物在從酵母到人的所有整合細胞中都保守存在,影響基因表達、復制等基本DNA功能。哺乳動物SWI/SNF復合物包含8~12個成分,其組成成分(和具體功能)呈組織特異性以及發育階段特異性。SWI/SNF復合物的ATP酶可以是BRG1或BRM其中之一,其他成分包括SNF5、BAF155、BAF170、ARID1a和BAF180等等。
編碼這些成分的基因在多種癌癥中發生突變,其中最早發現與癌癥有關且證據最多的成分是SNF5。早在1998年,Versteege等發現,突變基因SNF5反復出現在一種高死亡率的兒科惡性腫瘤——惡性柱狀細胞癌(malignantrhabdoidtumors,MRTs)中,而且SNF5突變和MRTs的關系還具有家族性:有單個等位基因SNF5突變的家族容易發生另一個SNF5等位基因失活,從而發生癌變。隨后,研究又發現神經鞘瘤(Schwannomatosis)等多種癌癥均存在SNF5突變。人為誘導SNF5在這些腫瘤細胞中表達,會導致這些細胞生長抑制。
為直接驗證SNF5的抑癌活性,我們構建了條件性SNF5缺失的轉基因小鼠,研究發現,SNF5失活會誘發全部小鼠出現惡性癌癥,包括與人MRTs組織學和全基因組表達模式非常相似的鼠MRTs以及來源于成熟記憶T細胞的淋巴瘤,且其癌變的潛伏期只有11周,遠遠快于任何其他抑癌基因失活的小鼠模型(P53失活致癌的潛伏期是20周,P16、P19、Rb等失活后癌變時間則更長)。這些實驗證據都表明SNF5是一個非常強的抑癌基因。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其他SWI/SNF成分也和癌癥強相關。例如BRG1在肺癌、乳腺癌、胰腺癌、前列腺癌等癌癥中缺失或突變;ARID1a在近50%的卵巢癌、胃癌、乳腺癌等多種癌癥中突變;BAF180在近半數腎癌中突變等等。
癌癥的本質:是遺傳病還是表觀遺傳疾病?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癌癥是一種“遺傳性”疾病,即主要是由若干(至少2~3個)基因突變累積導致靶細胞持續增殖、凋亡失控、侵襲能力增強等變化從而癌變。然而,最近幾年在以下幾方面的研究進展,尤其是癌癥基因組測序項目的實施,使得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這一理論。
首先,人們發現基因被激活或失活,并不一定要通過DNA序列改變,表觀遺傳調控失常也可和基因突變一樣造成致癌后果。例如基因突變可阻斷抑癌因子VHL的表達從而造成惡性腎癌,然而即使很多患者沒有VHL基因本身的突變,該基因啟動子高度甲基化也可以完全一致VHL基因的表達而致癌。又比如很多癌變細胞里P16基因雖然序列正常,但其表達卻受表觀遺傳抑制(例如其啟動子高度甲基化或SWI/SNF功能缺失)而不能發揮抑癌功能。此外,很多在發育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信號傳導通路,包括WNT、Hedgehog、TGF等的關鍵成分突變亦可導致癌變。最近幾年的研究表明這些信號傳導通路也可以通過表觀遺傳的方式調控,例如北京大學醫學部尚永豐實驗室發現LSD1可以調節TGF信號通路,我們實驗室也發現SNF5和Hedgehog信號通路關系密切。這些證據都表明遺傳(DNA序列改變)和表觀遺傳兩種方式可以導致同樣的結果。這些研究奠定了表觀遺傳調控失常致癌的理論基礎。
其次,最近幾年發展起來的測序技術使得人們有可能測定同一種癌癥的多個樣本的全外顯子序列甚至全基因組序列,從而比較全面徹底地發現致癌原因。這個項目除了發現人們熟知的癌基因或抑癌基因外,最令人吃驚的是發現了表觀遺傳調控基因的突變(包括DNA序列中堿基突變、缺失、移位、融合或多拷貝放大等)所導致的癌癥種類數量之多及發生率之高遠遠大于人們以前的理解。多個表觀遺傳調控因子被發現在血液系統惡性腫瘤(包括各種白血病)、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肝癌、結直腸癌、胃癌、卵巢癌、淋巴瘤等多種癌癥中以很高的比率出現。例如,SNF5基因在高達98%的MRTs中突變或缺失,而組蛋白甲基化酶MLL2的突變則在高達89%的濾泡性淋巴瘤和近30%的彌散性大B細胞淋巴瘤患者樣本中被檢測到。
再次,雖然很多癌癥患者的癌細胞中都有幾十、上百甚至更多的基因發生突變,然而重要的問題是:究竟哪些是真正的致癌因素(drivers),哪些是癌變過程中導致的或根本就是隨機的附帶突變(passengers),這個問題長久以來沒有得到解決。全基因組測序技術的快速進步為回答這個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方法——對同一種腫瘤的多個病例進行測序分析,如果有超過一定比例的患者都有某個基因的突變,則這個基因很可能就是這種癌癥的致癌基因,而且這種“重復突變(recurrentmutation)”的基因數目越少,這些突變的基因越有可能是真正的致癌因素。這兩種方法都為表觀遺傳在癌癥發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大量的實驗證據。
仍以MRTs為例,這種死亡率極高,發展極快(通常從發病到死亡不到1年)且對現有治療手段極不敏感的兒童腫瘤,其基因組卻很穩定,沒有任何染色質片段擴增或缺失,更沒有整條染色體的增多或減少。幾乎所有的MRTs都有SNF5基因的雙等位基因失活性突變或缺失。我們實驗室的一系列工作,尤其是近期對數十例MRTs樣本的深度測序,發現MRTs除SNF5本身外,只有很少幾個甚至沒有其他基因發生突變,因此,MRTs可以說是第一個被發現的“表觀遺傳性”腫瘤。這也說明癌癥可以是簡單的、純粹的表觀遺傳性疾病。又如在膀胱癌中,將近20%的“重復突變”基因的表達產物參與表觀遺傳調控。Nature雜志也曾報道,和以前的猜想完全相反,視網膜母細胞瘤也是一種“表觀遺傳腫瘤”:對該腫瘤的全基因組測序發現,除RB基因外,只有很少基因發生突變,但是很多基因卻通過表觀遺傳方式被異常激活,因此,其致癌機制很可能是RB通過和染色質重塑復合物相互作用及影響DNA甲基化而激活SYK等癌基因。此外,兒童成神經管細胞瘤和Wilms’瘤也都呈現較高程度的基因組穩定性而少有基因突變,很可能是“表觀遺傳腫瘤”。
另一個確定真正致癌因子的方法是在體外或模型動物(最常用的是小鼠)人工誘導同樣的基因異變,然后檢測是否誘發同樣的癌癥。最好的例子還是SNF5,SNF5基因突變在98%的兒童MRTs以及其他數種惡性腫瘤中被檢測到,而且還具有家族性:在丟失一個SNF5等位基因的家族中,其成員往往容易丟失另一個SNF5的等位基因從而導致MRTs。為了驗證SNF5的失活的確是這些惡性腫瘤的癌變原因,我們和其他實驗室制備了可誘導的SNF5條件性缺失小鼠。SNF5失活導致100%的小鼠在11周左右死于惡性腫瘤——主要是MRTs(和人的同類腫瘤在組織學和全基因組表達模式上都十分相似)和惡性的TCR依賴的成熟T細胞淋巴瘤。這些實驗數據證明,SNF5的確是一個活性非常強的抑癌基因,其活性喪失能直接導致癌變。值得一提的是,SNF5的抑癌活性比任何已知的抑癌基因都強:P53失活致小鼠癌變的時間是20周(是SNF5失活導致癌變時間的2倍),P16等其他抑癌基因缺失導致的癌變則需要更長的潛伏期,而且癌變率并不是100%。其他表觀遺傳調控因子,如MLL和AF9等基因融合,MOZ-TIF2基因融合的致癌性也在動物實驗中得到直接驗證。
最后,驗證表觀遺傳在癌癥發生發展中的作用還可以通過改變表觀遺傳調控活性能否阻斷或逆轉癌變過程。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FDA)批準的針對表觀遺傳的4個藥物都在臨床取得了很好的療效(詳述如下)。我們實驗室利用轉基因小鼠模型,發現了抑制Ezh2或Brg1的表達可以完全阻斷Snf5失活所致惡性腫瘤的發生,證實了表觀遺傳調控因子在惡性腫瘤發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也為這些分子作為潛在藥物靶分子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表觀遺傳致癌的可能機制
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表觀遺傳在癌癥發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然而其作用的分子機制還很不清楚,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第一,表觀遺傳通過影響基因表達,激活癌基因或抑制抑癌基因,例如表觀遺傳對VHL、P16、Myc等基因的調控。第二,表觀遺傳調控異常會導致染色質結構不穩定,從而引發染色體數目異常(aneuploidy)、大片段缺失或擴增以及DNA修復機制紊亂。第三,表觀遺傳可能影響細胞增殖或凋亡,例如Brg1/Brm缺失后,Rb不再誘導細胞凋亡,其他SWI/SNF也和P53有密切關系。第四,表觀遺傳可能影響重要信號傳導通路,如WNT、Hedgehog、TGF、細胞表面受體及許多激素受體等,這些信號通路在個體發育中具有關鍵作用,在癌變過程也扮演重要角色。盡管這些研究剛剛起步,但已經得出一些證據——SWI/SNF和Hedgehog密切相互作用、影響AR/ER信號、LSD1和TGF相互作用。我們還發現,SNF5缺失后會誘導非常惡性的依賴TCR信號的T細胞淋巴瘤發生。最后,表觀遺傳也能影響癌癥侵襲和轉移,例如LSD1可以顯著影響乳腺癌的侵襲和轉移能力,SWI/SNF也被證明與腫瘤轉移有關。
表觀遺傳在臨床中的應用
人們曾經認為癌癥是一種遺傳性疾病,并花了相當大的人力、物力和時間來尋找合適的基因治療方法,然而,實踐證明,試圖將一個突變的DNA序列變回正常是非常困難的,迄今為止尚無一例成功;而表觀遺傳的改變卻是可以調控、可以逆轉的,認識到表觀遺傳在癌癥發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將對癌癥的臨床預防、診斷及治療產生深遠影響。
1預防
很多證據表明在癌變過程中,表觀遺傳變化先于DNA序列變化,且表觀遺傳相對容易調控和逆轉,這為預防癌癥提供了新思路。例如,很多致癌因素,如吸煙、酗酒、高脂飲食都能導致DNA甲基化的變化;慢性炎癥和癌癥的關系,尤其是消化道慢性炎癥導致的食道癌、肝癌、結直腸癌等已為人們熟知,幽門螺桿菌或丙型肝炎病毒都能導致慢性炎癥繼而發展為癌癥,而表觀遺傳在此過程中就起著重要的作用,包括DNA甲基化異常、表觀遺傳性的基因表達異常,尤其是一些細胞因子或信號傳導蛋白(例如IL-B、TNF、IL-8、TGF等等)的異常。因此,目前研究者們都在思考如何調控DNA甲基化以預防癌癥。
2診斷
將表觀遺傳應用于癌癥診斷主要集中在以下4個方面。(1)檢測癌細胞,DNA甲基化異常和癌癥的相關性已為人們廣泛接受,隨著近幾年測序技術的驚人進步,全基因組的甲基化檢測變得容易,人們發現幾乎每一種癌癥都有其特有的“甲基化基因組模式”。目前的研究重點集中在發現這種癌癥特有而正常細胞沒有的全基因組水平DNA甲基化標記,并開發出簡單、快速、靈敏、可靠的檢測試劑盒。(2)針對高危人群(吸煙者、礦工、慢性炎癥患者、污染嚴重地區、有癌癥高發家族史等人群)的早期檢測,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GSTP1基因啟動子的甲基化發生在80%~90%的惡性前列腺癌患者血液中,但卻與良性前列腺癌無關。(3)對預后的預測,目前癌癥治療中最關鍵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對組織學相似的同型癌癥患者進行預后分析,以確定治療策略、選擇治療強度。目前已經發現多種表觀遺傳調控因子和多種癌癥預后相關,例如組蛋白甲基化酶NSD1的活性與神經母細胞瘤、DARK和肺癌、EMPS和腦癌、CDKN2A和直腸癌預后相關等等。(4)對化療效果的檢測和評估,目前也是一個熱門領域。
3治療
比起DNA序列的變化,表觀遺傳的變化更容易調控和逆轉,因此,近年來對表觀遺傳在癌癥發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的發現讓醫學界極為振奮,也為新藥研發提供了全新的、前景廣闊的一類抗癌靶分子,因而“幾乎每一個藥物公司都建立了研究開發針對表觀遺傳調控的抗癌藥的部門,或者建立了和表觀遺傳研究公司的緊密合作”(TheScientist雜志2010年4月刊)。迄今為止,美國FDA批準了4個針對表觀遺傳調控的藥物:其中兩個是針對DNA甲基化的DNMT抑制劑Vidaza和Decitabine,它們被用于Myolodysplastic綜合征及其并發的急性白血病;另外兩個是針對組蛋白去乙酰化HDAC酶的Vorinostat和Romidepsin,主要用于治療皮膚T細胞淋巴瘤;這4種藥物的不足之處是缺乏特異性,即對所有的DNA甲基化酶或組蛋白去乙酰化酶都有抑制作用,因而毒副作用較大。
目前正在研發其他針對某一個特定表觀遺傳調控因子,包括DNA甲基化酶、組蛋白修飾(乙酰化、去乙酰化、甲基化、去甲基化、磷酸化、去磷酸化等等)酶的特異性更強的藥物,其中,多集中在研發針對組蛋白甲基化酶和去甲基化酶的藥物。比起其他調控方式,組蛋白甲基化/去甲基化調控的特點有:(1)調控方式多樣而精確,可以發生在多個組蛋白的多個氨基酸位點,已經驗證的就有11個位點,而且甲基化狀態也有4種——無甲基、單甲基、雙甲基和三甲基。(2)特異性強:以上多位點的各種甲基化狀態理論上可以有上百萬種不同的組合,因而可以預見,在不同的細胞狀態、不同的基因位點可以有極其特異的甲基化編碼(code)。(3)可逆性:組蛋白甲基化可以通過各種甲基化酶和去甲基化酶來快速調控。(4)基于以上特點,調控組蛋白甲基化的酶種類繁多(目前已發現近百種甲基化酶和數十種去甲基化酶)且有很強的特異性,是非常適于做小分子藥物的靶分子(druggabletargets)。
因此,許多藥物公司正在積極研發特異性影響某個組蛋白甲基化酶和去甲基化酶(例如EZH2、MLL、DOT1)活性的新一代抗癌藥物。
總結與展望
篇3
【關鍵詞】新生兒遺傳代謝病;早期診斷和治療;血標本采集
新生兒遺傳病是指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低下癥和苯丙酮尿癥兩種疾病。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低下癥是導致兒童體格、智力發育障礙的常見內分泌疾病之一[1]苯丙酮尿癥是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由于苯丙氨酸羥代酶或其輔酶的缺陷,使苯丙氨酸及其代謝產物蓄積,影響中樞神經的發育,可引起嚴重的智力落后。我國新生兒發病率為1/11000[2]。新生兒遺傳代謝病是影響兒童智力和體格發育的嚴重疾病,若及早診斷和治療,患兒身心發育大多可達到正常同齡兒童水平。本篩查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實施辦法》、衛生部《新生兒疾病篩查管理辦法》在新生兒健康的先生性、遺傳性疾病實行的專項檢查,以達到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的目的。對防止殘病,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有著重大意義。我科是從2008年開展新生兒遺傳病篩查,2008年10月-2010年10月共篩查新生兒4808例,其中陽性2例,得到了早期診斷和治療,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2008年10月至2009年10月我院出生新生兒有2360例,而新生兒遺傳病篩查只有1680人,僅占出生率71%,采血標本合格率為95%。
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出生新生兒2448例,新生兒遺傳病篩查2260例,占出生率92%,采血合格率99%,出血率和感染率為0.
1.2方法:加強宣傳教育,做好采血的解釋工作。由于新生兒遺傳病是新開展的技術項目,家長認為這么小的孩子采血會很痛,心痛孩子而拒絕采血,且家長對先天性疾病的危害不了解,因此我們就要采取各種措施,取得家長的配合和理解。
1.2.1采用產前、產后發放資料,床旁介紹,入院介紹,指導母乳喂養過程中介紹,讓其頭腦中有個粗略概念。
1.2.2醫生查房或護士巡視病房時認真解釋篩查意義,并告訴他們這是一項操作簡單,痛苦很小的操作,不會有并發癥的,像平時打針或化驗室采指尖血一樣,我們在操作中一定會嚴格無菌操作規程的,會選擇采血技術特別好的護士為你的孩子采血,這樣才能取得家長配合同意。
1.3采血方法:
1.3.1采血護士必須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動作應輕柔,雙手應清潔溫暖。選擇出生3天并充分哺乳后新生兒,認真查對填好卡片,將采血濾紙訂于卡片上備用。
1.3.2首先用手觸摸孩子足部溫度,如不溫暖或呈紫斑色應先用熱水浸泡,熱敷或按摩,最好在沐浴或新生兒游泳后采血最佳。雙手握住膝關節以下輕按至足跟,再次按摩至足跟,使局部血液聚集充盈,用75%酒精消毒兩次足跟內,外側5cm以上待干。 1.3.3左手蹦緊采血部位皮膚,右手持一次性采血針快速拔斜刺約45度角,深度8mm,不可在同一部位的血斑上重復滴入血液,手持消毒棉球輕壓采血部位使其止血,將血片置于清潔空氣中,避免陽光直射,自然晾干,保存于密閉膠袋內,并放置在2-8℃冰箱內保存,在7天內將濾紙干血片選至新生兒疾病篩查中心,并登記新生兒相關信息。
2結果
篩查出陽性患兒2例,其中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低下癥及苯丙酮尿癥各1例。合格標本4760例,不合格標本48例,一次性采血標本合格率99%。采血過程中,護理人員嚴格無菌操作技術,出血和感染均為0。
3討論
3.1提高新生兒遺傳代謝病篩查,必須加強宣傳力度。通過各種形式加大宣傳力度,使全社會廣泛認識到疾病的危害性和新生兒遺傳代謝病篩查的重要性,及時召回陽性患兒,及時治療,預防殘疾兒的發生,從而提高我縣出生人口素質。
3.2 一次性成功采血。新生兒遺傳病人篩查血標本采集技術是產科及新生科護理人員應掌握的一項技術,要加強培訓,熟練掌握。要選擇最佳的穿刺部位,提高采血的成功率,根據解剖特點,針刺足跟內側的足底內例側靜脈及足跟外側的小隱靜脈分支處血流通暢,可提高一次性采血成功率,減少新生兒痛苦。
3.3 正確的采集血標本是新生兒遺傳代謝病篩查主要的環節,檢驗結果準確與否的關鍵,必須對采集血標本的護理人員進行嚴格的培訓考核,不斷提高相關知識和技術操作水平,增強工作責任感,確保參與血標本采集的護理人員在采血送檢等各環節中能嚴格遵守護理操作規程。
3.4 保證血標本的質量,必須嚴格血標本的收集管理。血標本的采集和血管理要求非常嚴格,任何一個環節出差錯,都將直接影響檢驗結果,科室要有嚴格的管理和質控制度,建立新生兒遺傳代謝病篩查信息登記本,由專人負責采血時,嚴格執行查對制度,防止差錯事故的發生。
參考文獻
篇4
在Watson和Crick發現DNA雙螺旋結構后的50多年里,基因工程藥物在治療人類疾病中逐漸占據一席之地,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完成為基因治療開辟了更廣闊的空間。近年來隨著遺傳學的新興學科——表觀遺傳學在人類疾病治療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證據[1]。它從分子水平上揭示復雜的臨床現象,為解開生命奧秘及征服疾病帶來新希望。
表觀遺傳學是研究沒有DNA序列變化的情況下,生物的表型發生了可遺傳改變的一門學科[2]。表觀遺傳學即可遺傳的基因組表觀修飾,表觀修飾包括: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染色質重塑、X染色體失活、基因組印記、非編碼RNA調控等[3],任何一方面的異常都可能導致疾病,包括癌癥、染色體不穩定綜合征和智力遲鈍[4]等。表觀遺傳的改變是可逆的,這就為治療人類疾病提供了樂觀的前景。本文從表觀遺傳學與人類疾病、環境與表觀遺傳學的關系以及表觀遺傳治療3個方面進行綜述。
1 表觀遺傳學修飾與人類疾病
1.1 DNA甲基化相關疾病
DNA甲基化是指在DNA甲基轉移酶(DNMTs)的催化下,將甲基基團轉移到胞嘧啶堿基上的一種修飾方式。它主要發生在富含雙核苷酸CpG島的區域,在人類基因組中有近5萬個CpG島[5]。正常情況下CpG島是以非甲基化形式(活躍形式)存在的,DNA甲基化可導致基因表達沉默。DNMTs的活性異常與疾病有密切的關系,例如位于染色體上的DNMT3B基因突變可導致ICF綜合征。有報道[6]表明,重度女襲性牙周炎的發生與2條X染色體上TMP1基因去甲基化比例增高有關。DNMT基因的過量表達與精神分裂癥和情緒障礙等精神疾病的發生也密切相關。風濕性疾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特別是系統性紅斑狼瘡(SLE)與DNA甲基化之間關系已經確定[7],在SLE病人的T細胞發現DNMTs活性降低導致的異常低甲基化。啟動子區的CpG島過度甲基化使抑癌基因沉默,基因組總體甲基化水平降低導致一些在正常情況下受到抑制的基因如癌基因被激活[8],都會導致細胞癌變。
1.2 組蛋白修飾相關疾病
組蛋白的修飾包括乙酰化、甲基化、磷酸化、泛素化、糖基化、ADP核糖基化、羰基化等,組成各種組蛋白密碼。其中,研究最多的是乙酰化、甲基化。一般來說,組蛋白乙酰化標志著其處于轉錄活性狀態;反之,組蛋白低乙酰化或去乙酰化表明處于非轉錄活性的常染色質區域或異染色質區域。乙酰化修飾需要乙酰化轉移酶(HATs)和去乙酰化酶(HDACs)參與。組蛋白修飾酶異常可導致包括癌癥在內的各種疾病,例如,H4K20的三甲基化是癌癥中的一個普遍現象。甲基化CpG2結合蛋白2(MeCP2)可使組蛋白去乙酰化導致染色質濃縮而失活,其中Rett綜合征就是MeCP2的突變所致。
1.3 染色質重塑相關疾病
染色質重塑是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染色質重塑復合物的共同作用。它通過影響核小體結構,為其他蛋白提供和DNA的結合位點[9]。其中染色質重塑因子復合物主要包括SWI/SNF復合物和ISW復合物。染色質重塑復合物如果發生突變,可導致染色質不能重塑,影響基因的正常表達,導致人類疾病。如果突變引起抑癌基因出現異常將導致癌癥,例如:小兒科癌癥中檢測到SNF5的丟失。編碼SWI/SNF復合物相關的ATP酶的基因ATRX、ERCC6、SMARCAL1的突變可導致B型Cockayne綜合征、Schimke綜合征甚至腫瘤。ATRX突變可引起DNA甲基化異常,從而導致數種遺傳性的智力遲鈍疾病如:X連鎖α2地中海貧血綜合征和SmithFinemanMyers綜合征,這些疾病與核小體重新定位的異常引起的基因表達抑制有關[10]。
1.4 X染色體失活相關疾病
哺乳動物雌性個體不論有多少條X染色體,最終只能隨機保留一條的活性。X染色體失活由X失活中心(Xic)調控,Xic調控X染色體失活特異性轉錄基因(Xist)的表達。X染色體的不對稱失活可導致多種疾病,例如男性發病率較高的WiskottAldrich綜合征是由于WASP基因突變所致。X染色體的PLP基因突變失活常導致PelizaeusMerzbacher病;X染色體的MeCP2基因突變失活導致Rett綜合征[11]。在失活的X染色體中,有一部分基因因逃避失活而存在2個有活性的等位基因,使一些抑癌基因喪失功能,這是引發女性癌癥的一個重要原因[12]。
1.5 基因組印記相關疾病
基因組印記是指二倍體細胞的一對等位基因(父本和母本)只有一個可以表達,另一個因表觀遺傳修飾而沉默。已知在人體中有80多種印記基因。印記丟失導致等位基因同時表達或有活性的等位基因突變,均可引起人類疾病。一些環境因素,如食物中的葉酸也會破壞印記。印記丟失不僅影響胚胎發育,并可誘發出生后的發育異常。如果抑癌基因中有活性的等位基因失活可導致癌癥的發生,如IGF2基因印記丟失導致的Wilms瘤[13]。15號染色體的表觀遺傳異常可導致PraderWilli綜合征(PWS)和Angelman綜合征(AS),PWS是由于突變導致父本表達的基因簇沉默,印記基因(如SNURF/SNRPN)在大腦中高表達所致;AS是由于母本表達的UBE3A或ATP10C基因的缺失或受到抑制所致。Beckwithweideman綜合征(BWS)是11號染色體表觀遺傳突變引起印跡控制區域甲基化的丟失,導致基因印記丟失引起[14]。
1.6 非編碼RNA介導相關疾病
功能性非編碼RNA分為長鏈非編碼RNA和短鏈非編碼RNA。長鏈RNA對染色質結構的改變起著重要的作用。短鏈RNA對外源的核酸序列有降解作用以保護自身的基因組。小干涉RNA(siRNA)和微小RNA(miRNA)都屬于短鏈RNA,在人類細胞中小片段的siRNA也可以誘導基因沉默。miRNA能夠促使與其序列同源的靶基因mRNA的降解或者抑制翻譯,在發育的過程中起著關鍵性作用。轉錄的反義RNA可以導致基因的沉寂,引起多種疾病,如使地中海貧血病人的正常球蛋白基因發生甲基化。由于miRNA在腫瘤細胞中的表達顯著下調,P53基因可通過調控miRNA34ac的表達治療腫瘤。在細胞分裂時,短鏈RNA異常將導致細胞分裂異常,如果干細胞發生這種情況也可能導致癌癥。
2 環境表觀遺傳學
對多基因復雜癥狀性疾病來說,單一的蛋白質編碼基因研究遠遠不能解釋疾病的發生機理,需要環境與外界因素的作用才會發病。疾病是外界因素與遺傳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流行病學研究已經證實,人類疾病與環境有明確的關系,高血壓、中風、2型糖尿病、骨質疏松癥等疾病的發病率與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15]。特別是在發育初期,不利的環境、 營養的缺乏都有可能導致出生低體重、早產、胎兒發育不成熟等[16]。環境與DNA甲基化的關系一旦建立,將為環境射線暴露與癌癥發生提供依據[17]。
環境污染等不利因素均有可能增加基因的不穩定性,每個人對環境和飲食的敏感性可因先天遺傳不同而不同,環境因素與個體遺傳共同作用,決定潛在表觀遺傳疾病的危險性。有人推測上述因素肯定會在我們基因組上遺留下微量的基因表遺傳學痕跡[1]。隨著年齡增長,DNA甲基化等化學修飾改變也在長時間中錯誤積累,這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很多疾病總是在人進入老年后才發生。由此可見,如果改變不良生活習慣、減少環境污染,都有可能降低表觀遺傳疾病的發病率。因此研究環境與表觀遺傳改變的關系對于預防和治療人類疾病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3 表觀遺傳學藥物
人類許多疾病都可能具有表觀遺傳學的改變,表觀遺傳學治療研究如火如荼。已經發現許多藥物可以通過改變DNA甲基化模式或進行組蛋白的修飾等來治療疾病。目前,很多藥物處于研制階段,盡管其有效性尚未得到充分證實,但給癌癥、精神疾病以及其他復雜的疾病的治療帶來了希望。
3.1 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
目前發現的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HDAC Inhibitor)有近百種。其中FK228主要作用機制是抑制腫瘤細胞內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活性,引起乙酰化組蛋白的積聚,從而發揮抑制腫瘤細胞增殖、誘導細胞周期阻滯、促進細胞凋亡或分化等作用[18]。FK228單獨用藥或與其他藥物或方法聯合應用表現出良好的抗腫瘤作用,同時還可阻礙血管生成,具有抑制腫瘤轉移、逆轉耐藥性、調節免疫力等作用。FK228還具有治療炎癥、免疫性疾病、視網膜新生血管疾病及神經系統等多種疾病的藥理學作用。
3.2 DNA甲基轉移酶抑制劑
核苷類DNA甲基轉移酶抑制劑作用機理是在體內通過代謝形成三磷酸脫氧核苷,在DNA復制過程中代替胞嘧啶,與DNMTs具有很強的結合力。核苷類似物5氮雜胞苷(5azacytidine)是第一個發現的甲基化抑制劑,最初被認為是細胞毒性物質,隨后發現它可抑制DNA甲基化和使沉默基因獲得轉錄性,用于治療高甲基化的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低劑量治療白血病。其他核苷類DNA甲基轉移酶抑制劑有5氮2脫氧核苷(5aza2′deoxycytidine),Zebularine(5azacytidine的衍生物)[19],5Fluoro2′deoxycytidine,RG108,Procainamide,Psammaplins(4aminobenzoic acid衍生物),MG98(寡聚核苷酸)等。DNA甲基化抑制劑Procainamide可用于抗心律失常。另外在茶葉和海藻中提取的EGCG也顯示具有體外活性。臨床中應用反義寡核苷酸對DNA甲基轉移酶進行抑制正在進行實驗。
3.3 聯合治療
DNA甲基化抑制劑與HDAC抑制劑聯合應用治療疾病可能具有協同作用。進行表觀修飾治療后的細胞可能對于化療、干擾素、免疫治療更具有敏感性。在癌癥的治療方面,應當包括遺傳治療和表觀遺傳治療兩個方面,同時運用兩種或兩種以上表觀修飾的方法對病人進行治療對人類疾病意義重大。
3.4 其他方法
人胚胎干細胞保留有正常基因印記,這些干細胞可能具有治療意義[20]。另外,在女性細胞中非活性的X染色體中存在正常的野生型基因,如果選擇正確的靶點,就有可能激活這個正常但是未被利用的野生型基因,從而對其進行基因治療。有報道[21]運用RNAi技術沉默胰島β細胞相關基因,抑制胰島淀粉樣形成可能用來治療糖尿病。短鏈脂肪酸(SCFAs)丙戊酸鈉用于抗癲癇,丁酸可用來治療結腸癌[22]等。siRNA可在外來核酸的誘導下產生,通過RNA干擾(RNAi)清除外來核酸,對預防傳染病有重要作用。目前,RNA干擾已大量應用于包括腫瘤在內的疾病研究,為一些重大疾病的治療帶來了新的希望。
4 結 語
從表觀遺傳學提出到現在,人們對表觀遺傳學與人類疾病的發生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人類表觀基因組計劃(human epigenome proiect,HEP)已經于2003年開始實施,其目的是要繪制出不同組織類型和疾病狀態下的人類基因組甲基化可變位點(methylation variable position ,MVP)圖譜。這項計劃可以進一步加深研究者對于人類基因組的認識,為表觀遺傳學方法治療人類復雜疾病提供藍圖[1]。但是,表觀遺傳學與人類生物學行為(臨床表型)有密切關系,人類對表觀遺傳學在疾病中的角色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應更進一步研究表觀遺傳學機制、基因表達以及與環境變化的關系,有效減少表觀遺傳疾病的發生風險,努力探索這片造福人類的前沿領域。
參考文獻
[1] DAVID R,MELLISSA M. Epigenetic and human disease:translating basic biology into clinical applications[J]. CMAJ, 2006,174(3):136-146.
[2] 董玉瑋,候進惠,朱必才,等.表觀遺傳學的相關概念和研究進展[J].生物學雜志,2005,22(1):1-3.
[3] 張永彪,褚嘉佑.表觀遺傳學與人類疾病的研究進展[J].遺傳,2005,27(3):466-472.
[4] GERDA E, GANGNING L, ANA A,et al. Epigenetics in human disease and prospects for epigenetic therapy[J].Nature,2004,429(27):457-462.
[5] 吳超群.表觀遺傳學和人類疾病[J].中國優生優育2007,13(3):112-119.
[6] 趙紅宇,李紅,張旭,等.侵襲性牙周炎的表觀遺傳學研究[J].醫藥論壇雜志,2006,27(21):29.
[7] MARTIN H,MARCO A.Epigenetics and human disease[J].Int J Biochem Cell Biol,2009,41:136-146.
[8]李莉,李真.表觀遺傳學在腫瘤診斷及治療中的研究進展[J].重慶醫學,2008,37(11):1250.
[9] LEWIN B.Gene Ⅷ[M]. New Jersey:Perarson Prenc Hall press, 2004:315-320.
[10] HUANG C, SLOAN E A, BOERKOEL C F. Chromatin remodeling and human disease[J].Curr Opin Genet Dev, 2003, 13 (3): 246-252.
[11] HEARD E.Recent advances in Xchromosome inactivation[J]. Curr Opin Cell Biol,2004,16:247-255.
[12] LIAO D J, DU Q Q, YU BW,et al. Novel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the X chromosome in rep roductive cancers[J].Cancer Invest,2003,21(4):641-658.
[13] FEINBERG A P,TYCKO B.The history of cancer epigenetic[J].Nat Rev Cancer,2004,4(2):143-153.
[14] ANDREW P.Phenotypic plasticity and the epigenetics of human disease[J].Nature,2007,447(24):433.
[15] GODRREY K M, LILLYCROP K A, BURDGE G C,et al. Epigenetic mechanismsand the mismatch concept of the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J].Pediatr Res, 2007,61:5R-10R.
[16] WAYNE S, CUTFIELD,PAUL L.et al. Could epigenetics play a role in the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J]. Pediatr Res,2007,61(5):68R.
[17] EDWARDS T M, MYERS J P. Environmental exposures and gene regulation in diseaseetiology[J]. Environ Health Perspect,2007;115:1264-1270.
[18] 南,徐克前.表觀遺傳學藥物FK228的藥理作用及機制[J].國際病理科學與臨床雜志,2008.28(4)297-300.
[19] CHENG J C,YOO C B,WEISENBERGER D J,et al.Preferential response of cancer cells to zebularine[J].Cancer Cell,2004,6(2):151.
篇5
HIC-1在腫瘤發生中的作用機制腫瘤的發生通常伴隨著表觀遺傳學的改變,包括基因甲基化、組蛋白修飾和非編碼小RNA干擾等,這些改變可使基因功能發生變化,從而導致細胞惡變。事實上,異常的表觀遺傳學修飾是腫瘤形成的必然要素,其已成共識。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HIC-1基因表觀遺傳學的改變,參與了多種腫瘤的發生。
啟動子的甲基化與腫瘤的發生
一般認為,HIC-1是一種腫瘤抑制基因,在多數實體瘤和白血病中表現為表觀遺傳學沉默,如前列腺癌、非小細胞肺癌、乳腺癌、胃癌和肝癌、食管癌、非精原生殖細胞癌、兒童髓母細胞瘤、神經膠質瘤和室管膜瘤。應用甲基化特異性PCR(MSP)和重亞硫酸鹽測序發現,人類許多實體瘤和白血病中HIC-1均表現出高甲基化。例如,Yamanaka等在研究前列腺癌的發生與7種基因甲基化的相關性時發現,HIC-1的甲基化率為99%;Eguchi等在非小細胞肺癌標本檢測出33%的腫瘤組織和31%非腫瘤組織中有HIC-1啟動子的甲基化,且基因的甲基化程度與腫瘤分化程度呈負相關;Fujii等對39例原發性乳腺癌組織研究發現,有26例腫瘤組織(67%)出現HIC-1基因的完全甲基化。一般認為HIC-1啟動子區域的高甲基化可抑制HIC-1表達,且整個HIC-1基因的表達水平隨腫瘤的發展不斷降低。
HIC-1的表觀遺傳學失活可能促使細胞在腫瘤形成早期調整生存模式和信號通路,或調整一系列特異性轉錄因子的表達。將HIC-1基因人為導入該基因失活的腫瘤細胞株可明顯降低腫瘤細胞的成活率。然而,HIC-1啟動子甲基化也被發現存在于兒童正常腦組織、成人腦和前列腺上皮組織中。此外,在已確診的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慢性期的病人中,僅有少數病人出現HIC-1甲基化。但在復發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和急轉的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病人中,HIC-1均表現出高甲基化。故HIC-1甲基化已被認為是造血系統腫瘤的晚期事件,提示降低HIC-1的表達可能存在其他機制。通過以上例證說明,HIC-1啟動子區域的甲基化程度與腫瘤的發生、發展有密切關系。干預腫瘤細胞HIC-1啟動子甲基化,有可能對抑制腫瘤的發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HIC-1與p53抑癌基因的協同作用
HIC-1識別的一個重要靶點是SIRT1(thesilentmatingtypeinformationregulationhomolog1),該基因編碼一種去乙酰酶。SIRT1可使p53去乙酰化,降低p53基因對細胞凋亡和(或)增殖的調節能力。據報道,在正常生理情況下,HIC-1能抑制SIRT1轉錄,進而抑制p53去乙酰化;但在腫瘤細胞中HIC-1表觀遺傳學的失活,導致SIRT1水平升高。p53因去乙酰化作用而失活,促使細胞抵抗凋亡而成活。另外,HIC-1的啟動子區域存在PRE,意味著HIC-1是p53的直接靶基因,p53能激活HIC-1的轉錄而不依賴于其甲基化狀態。因此,這個p53/HIC-1/SIRT1調節通路是HIC-1作為腫瘤抑制基因發揮作用及其與p53協同作用的重要途徑。
HIC-1與p53的雙雜合性缺失模型進一步證實了HIC-1以及HIC-1與p53協同作用在腫瘤發生、發展中的意義。Chen等研究發現,HIC-1+/-小鼠在老年時期發生一系列具有性別依賴性的惡性腫瘤,HIC-1+/-p53+/-小鼠骨肉瘤的發生率(35%)較p53+/-小鼠(20%)高,且具有年齡依賴性。在64只HIC-1+/-p53+/-小鼠中發現5例乳腺腫瘤(4例腺鱗癌,1例肌上皮瘤)及7例卵巢腫瘤,在p53+/-小鼠中僅發現1例卵巢血管肉瘤,而在HIC-1+/-小鼠中未發現上述腫瘤。
HIC-1在腫瘤發生中的其他作用機制
最近研究表明,腫瘤細胞中HIC-1的失活能使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結合蛋白1表達增加,從而導致血管形成或增生。Zhang等發現,HIC-1能調節ephrin-A1(EFNA1)基因的直接轉錄,從而抑制上皮腫瘤的形成。另外,實驗結果表明,HIC-1是一種新的細胞生長調控機制中的核心分子,這種HIC-1介導的信號通路的中斷將導致異常細胞增殖和腫瘤形成。Boulay等發現,腫瘤發生過程中HIC-1的缺失通過上調乳腺上皮細胞中β2腎上腺素能受體的表達促使腫瘤轉移。此外,HIC-1還是調節細胞生長及凋亡關鍵基因的中心轉錄調節因子,在髓母細胞瘤中HIC-1對Hedgehog信號通路具有抑制作用,在干細胞功能中HIC-1能調節Wnt信號通路。
HIC-1在腫瘤治療中的意義由于HIC-1基因受p53基因調控,而p53基因又是迄今報道人類腫瘤中突變頻率最高的基因之一,且目前報道的p53基因突變腫瘤中有75%以上為錯義突變,致使p53基因功能丟失,因此,通過活化其下游HIC-1作為靶點,是p53基因突變腫瘤治療的有效選擇;而對于野生型p53腫瘤,若聯合HIC-1靶點干預可能效果更佳。在許多實體瘤及白血病中,由于HIC-1啟動子甲基化導致HIC-1沉默或低表達,DNA甲基化狀態可用DNA甲基化酶抑制劑消除。因此,HIC-1成為DNA甲基化酶抑制劑5-氮雜-2-脫氧胞苷(5-Aza-2`-deoxycytidine,Decitabin,5-CdR)的治療新靶點。Nicoll等研究發現,通過5-CdR恢復HIC-1功能有可能改善乳腺癌病人的預后。另有研究表明,5-CdR的聯合應用可增強頭頸部鱗狀細胞癌的放射治療效果。另外,Eggers等通過臨床研究發現,HIC-1可作為預測腎癌病人無復發生存率的獨立因子。因此,深入研究HIC-1基因的功能與作用機制,將有助于應用靶向藥物治療腫瘤。
篇6
[關鍵詞] 胃癌;遺傳學;表觀遺傳學;非編碼RNA;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
[中圖分類號] R73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3)07(a)-0043-04
胃癌是消化道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在全球腫瘤死亡原因中排名第二,其5年生存率在10%左右[1]。胃癌的發生與發展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包括環境、飲食、遺傳、幽門螺桿菌感染、慢性炎癥浸潤、癌前病變等。隨著人們對胃癌研究的不斷加深,遺傳因素及表觀遺傳因素已經成為研究中的熱點,對于胃癌的發病機制、細胞免疫與防御、細胞分化及預防治療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就其研究進展做一綜述。
1 表觀遺傳學
表觀遺傳學是研究細胞分裂增殖過程中,不改變相關基因的DNA序列而影響相關基因的表達,這種改變能通過有絲分裂和減數分裂進行遺傳的一門學科[2-3]。表觀遺傳的變化在腫瘤的發生、發展、復發、預測預后的價值已經得到了證實[4-7]。表觀遺傳學的范疇包括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非編碼RNA的改變等。
1.1 DNA甲基化與胃癌
DNA甲基化是指在DNA甲基轉移酶(DNMT)的作用下,將甲基由S-腺苷甲硫氨酸轉移到胞嘧啶5位碳原子上,形成5-甲基胞嘧啶[8]。胃癌中存在很多癌相關基因的甲基化,在胃癌形成的各個階段都能檢測到DNA甲基化的存在[9]。Cooper等[5]對包括220份慢性萎縮性胃炎、196份腸上皮生化、134份胃腺瘤、102份不典型性增生和202份胃癌及其癌旁組織和相應血液標本,采用甲基化特異性聚合酶聯反應(methylation-specific PCR,MSP)檢測RUNT相關轉錄因子3(RUNX3)啟動子的甲基化狀態。結果發現RUNX3的甲基化水平與胃癌的發生發展有關,從萎縮性胃炎(15.9%)到腸上皮生化(36.7%)、胃腺瘤(41.8%)、不典型性增生(54.9%)、胃癌(75.2%),甲基化水平逐漸提高,RUNX3基因甲基化在血清中檢測到的水平與胃癌組織中的水平顯著一致,表示循環RUNX3基因甲基化可作為標志物檢測早期胃癌并有望用于胃癌的篩查。
既然檢測DNA甲基化可能用于胃癌的早期診斷,那么甲基化與胃癌的臨床病理特征、預后及治療是否存在某種聯系呢?賈安平等[10]應用甲基化特異性PCR(MSP)檢測74例胃癌組織p16基因的啟動子CpG島的甲基化狀態,發現胃癌組織中p16基因的甲基化陽性率為56.8%,腫瘤分期晚、有淋巴結轉移的陽性率更高。Guo等[11]使用MSP的方法檢測了92例胃賁門腺癌RASSF1A基因啟動子甲基化的情況,其中54例的出現異常甲基化,隨著胃癌的進展,其甲基化率也逐漸增高。表明p16基因及RASSF1A基因甲基化可能與胃癌的病期相關。姜蕊等[12]在54例胃癌組織中檢測鈣黏蛋白(E-cadherin)基因的異常甲基化,發現E-cadherin基因啟動子異常甲基化頻率為48.1%,顯著高于癌旁正常組織中的11.11%,并隨疾病進展而進一步提高。E-cadherin異常甲基化狀態與患者的性別及年齡均無關,而與胃癌的分化程度、病例類型、浸潤深度及淋巴結轉移、臨床分期有關。提示胃癌組織中E-cadherin基因甲基化狀態可幫助判斷胃癌分化程度、進展情況,及預測預后。Sugita等[13]又對轉移復發性胃癌異常甲基化與化療療效相關性進行了研究,分析80例手術治療后發生轉移或復發的患者,使用氟尿嘧啶為基礎的化療。發現存在BNIP3(Bcl-2/adenovirus E1B 19 kDa-interacting protein 3)和DAPK(death-associated protein kinase)基因甲基化的患者總生存期(OS)及無進展生存期(PFS)較短,且對化療的反應率較低。可見DNA甲基化與胃癌發生、發展和預后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進一步研究DNA甲基化的機制,全面繪制DNA甲基化譜,可能對于胃癌的篩查、早期診斷、療效預測及預后判斷有幫助。
1.2 胃癌與組蛋白修飾
組蛋白是存在于真核生物體細胞染色質中的一組進化上非常保守的堿性蛋白質,含精氨酸和賴氨酸等堿性氨基酸較多,是由德國科學家A.柯塞爾于1834年首先發現的。常見的組蛋白修飾方式有乙酰化、甲基化、磷酸化、泛素化等。研究發現組蛋白修飾與其他表觀遺傳學改變共存于胃癌中,現在以乙酰化、甲基化、磷酸化研究最多[14]。
組蛋白磷酸化 組蛋白磷酸化是在組蛋白尾區加入帶有負電荷的PO4基團,常發生于真白的絲氨酸、蘇氨酸和酪氨酸殘基上,并且是可逆性修飾。其在有絲分裂、細胞死亡、DNA損傷修復、DNA復制和重組過程中有著直接的作用[15]。Fehri等[16]發現幽門螺桿菌可以誘導組蛋白H3絲氨酸10(H3S10)磷酸化水平降低,從而調節細胞周期,與幽門螺桿菌誘導胃癌發生相關。
1.2.1 組蛋白甲基化 組蛋白甲基化的位點多位于組蛋白H3和H4的精氨酸及賴氨酸殘基上,其甲基化方式有單甲基化、雙甲基化、三甲基化。其中H3-K4三甲基化的缺失、H3-K9甲基化和H3-K27三甲基化,這些甲基化改變在腫瘤早期出現并隨腫瘤進展變化而改變[17]。這些都與胃癌的發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
1.2.2 組蛋白乙酰化 組蛋白乙酰化是組蛋白乙酰基轉移酶將乙酰輔酶A乙酰基部分轉移到核心組蛋白氨基末端特定賴氨酸殘基上。一般認為組蛋白乙酰化與基因激活相關,而組蛋白去乙酰化與基因沉默或抑制有關。Mitani等[18]通過對29例胃癌組織標本的分析,發現組蛋白H3去乙酰化可以抑制抑癌基因p21(WAF1/CIP1)的表達,而對乙酰化抑制劑處理后,胃癌細胞組蛋白乙酰化水平升高,從而誘導p21(WAF1/CIP1)的表達上調。
總之,特定的組蛋白修飾與特定的基因激活或抑制相關,組蛋白修飾在基因調控中起著重要作用。進一步研究組蛋白修飾及其與基因調控的關系,有利于腫瘤發病機制研究,開發新的抗腫瘤藥物,例如去乙酰化抑制劑等。
1.3 胃癌與非編碼RNA
非編碼RNA是指參與蛋白質翻譯過程,不被翻譯成蛋白質的RNA,如tRNA、rRNA、miRNA、snRNA等,而miRNA是目前研究的熱點。miRNA(microRNA)屬于非編碼RNA的一種,是內源性非編碼小RNA。miRNA是長約18-26nt的單鏈RNA分子,起始于pri-miRNA,pri-miRNA在核內被Drosha酶復合體切割為miRNA前體,經轉運蛋白expoin5的作用下,從核內運輸到胞質,再由Dicer酶進一步切割成miRNA[19]。Wu等[20]應用RT-PCR的方法檢測了30例胃癌組織和配對正常組織的60個候選miRNA,從中篩選出5個miRNA(miR-125a-3p, miR-133b, miR-143, miR-195,miR-212),經過ROC分析表明miR-195和miR-212對于預測是否發生淋巴結轉移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Brenner等[21]通過從45例胃癌患者手術標本中提取RNA,再通過QRT-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的方法檢測發現,miR-451、miR-199a-3p、miR-195在預后良好及預后不良的患者中,表達存在差異,表達高的患者復發率高、預后差。miR-451、miR-199a-3p、miR-195可以作為胃癌預后的預測因子。Konishi等[22]對胃癌患者的血漿檢測發現miR-451和miR-486的濃度在術后分別下降90%和93%,表明miR-451和miR-486可能作為血液學檢查的手段用以篩查胃癌。
miRNA的種類很多,對胃癌的作用途徑多種多樣,表1列舉了部分miRNA與胃癌的發生發展、治療及預后之間的關系。隨著對于miRNA作用機制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有望使miRNA成為胃癌診斷及預后預測的新的生物學標記,還可能使其成為藥物標靶或模擬其進行新藥研發,為胃癌治療提供一種新的手段。
2 遺傳學改變
遺傳學改變是指基于基因序列改變而導致的基因表達水平的變化,如基因突變、基因雜合丟失和微衛星不穩定等。其中尤其以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最為常見。SNP影響并改變了某些正常的炎癥過程、免疫調節、DNA合成及修復等病理生理過程,而這些變化最終導致胃癌的發生。
2.1細胞因子及酶的基因多態性與胃癌
細胞因子是免疫細胞產生的一大類能在細胞間傳遞信息、具有免疫調節和效應功能的蛋白質或小分子多肽。主要包括白介素(IL)、腫瘤壞死因子(TNF)、表皮生長因子(EGF)、轉化生長因子(TGF)、基質金屬蛋白酶(MMP)、環氧合酶(COX)等。Guo等[29]通過分析中國北方人群胃賁門腺癌患者的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1)基因多態性,發現患者中-509T和869C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較健康人群明顯升高,與非攜帶者相比,攜帶者發生Ⅲ期和Ⅳ期腫瘤的風險增加。有研究發現,IL-10的-1082G等位基因與胃癌高風險相關[30],Sun等[31]研究發現,IL-10的基因多態性分析中-1082G等位基因使胃癌患者發生惡液質的風險顯著增加。宋傳貴等[32]對福建地區102例完整隨訪的胃癌患者進行MMP-1基因多態性的基因型鑒定發現,2G/2G基因型可能是影響福建地區胃癌患者生存的不良預后因子之一,與含1G基因型相比,2G/2G等位基因攜帶者發生肝臟轉移的機會明顯增大。殷霞麗等[33]通過對118例胃癌患者的COX-2基因啟動子區-1195G>A的多態性研究發現-1195G>A基因型與腫瘤大小及浸潤深度明顯相關,其中-1195A提示存在腫瘤大、浸潤深度深的高風險,同時與COX-2免疫組化表達存在顯著相關性。
2.2 DNA修復基因多態性與胃癌
DNA損傷修復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維持基因穩定性和細胞正常功能的中心環節主要是DNA修復能力,如果相關修復基因發生突變,就會導致整個基因組DNA修復能力下降,從而引起細胞增殖和分化失控,導致腫瘤發生[34]。Yuan等[35]通過分析160例胃癌患者與其對照組的X射線損傷修復交叉互補基因1(XRCC1)的基因多態性分布,發現攜帶XRCC1 194Trp基因型的個體患胃癌風險增高,可能是由于該變異影響了XRCC1蛋白的修復功能。
2.3抑癌基因多態性與胃癌
抑癌基因是一類調控細胞生長、抑制腫瘤表型表達的基因,可通過純合缺失或失活而引起細胞惡性轉化。p53基因作為重要的腫瘤抑制基因,在腫瘤的發生、發展中都具有重要作用。Song等[36]通過大規模的病例對照研究發現p53-72Pro.Pro基因型的個體患胃癌的風險增加。而Shirai等[37]的研究也表明該基因型的胃癌化療效果及預后差、容易發生遠處轉移。
2.4其他基因多態性與胃癌
除了上述各種遺傳基因多態性與胃癌的發生發展及預后密切相關,還有多種胃癌易感基因。在中國人群中研究發現,前列腺干細胞抗原基因(PSCA)的rs2294008T等位基因能顯著提高非賁門胃癌的發病風險,并且rs2294008T等位基因和rs2976392A等位基因與非賁門胃癌低分化和高級別有關[38]。而最近的一項薈萃分析通過對9個病例對照研究的分析,表明PCSA的rs2294008T等位基因和rs2976392A等位基因與非賁門或彌漫性胃癌的易感性有關[39]。Xu等[40]通過對929例中國胃癌患者超氧化物歧化酶2(SOD2)和谷胱甘肽巰基轉移酶(GSTP1)基因多態性研究發現,SOD2的rs4880 CT+CC基因型與淋巴結轉移高度相關,GSTP1的rs1695 GA+GG基因型與腫瘤大小關系密切,表明SOD2的rs4880 CT+CC基因型與GSTP1的rs1695 GA+GG基因型與胃癌的進展及侵襲性相關,而活性氧(ROS)的代謝途徑可能成為潛在的治療靶點。
2.5遺傳學改變研究中的一些問題
以上論述只是目前已發現頗具規模的胃癌易感多態性基因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只有PSCA等少數幾個基因與胃癌易感性的關系較為明確。其主要原因可能為:①目前胃癌關聯研究樣本普遍都很小[41];②不同胃癌類型還受到表觀遺傳學的影響;③不良飲食、生活習慣和環境等外在因素促進甚至導致胃癌發生[42];④胃癌家系成員生活環境和遺傳背景較一致,基于家系的連鎖分析是鑒定胃癌相關基因的比較簡單的方法,但是胃癌家系樣本難以獲得,并且通過家系定位的致病基因往往是該家族特異的,應用到群體中具有一定局限性。
因此盡量使病例同質化,采用較大規模的研究樣本和不同群體的驗證,并在分析時注意不良飲食、生活習慣及環境等外在影響因素,將有利于明確胃癌的易感基因。
3 總結
胃癌的發生是多基因遺傳和表遺傳共同作用的結果,通過研究遺傳和表遺傳改變發現了很多與胃癌的發生、發展及預后密切相關的因素,它們對于胃癌的早期診斷及預后判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阻斷這些遺傳和表遺傳改變的發生為胃癌的治療提供了更廣闊的研究和發展空間。
近年來的遺傳學和表觀遺傳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胃癌的早期診斷及預后預測方面,但是其中大多數研究僅針對單個位點或者單個基因多態性的變化上,很少有研究其相互關聯的變化對胃癌的影響。而且這些檢測運用于臨床前,其敏感性及特異性也有待進一步明確。對于那些被發現可能成為潛在治療靶點的基因位點,需要更多更大的重復性研究來確定它的真實可靠性,而后才是更深入地去發現通過何種手段去阻斷及干預。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化,基因與基因、基因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將被更深入地解析,利用基因分析的方法來評估個體胃癌風險,制定更加個體化的治療方案是未來研究的方向。
[參考文獻]
[1] Nardone G. Review article:molecular basis of gastric carcinogenesis [J]. Aliment Pharmacol Ther,2003,17(2):75-81.
[2] Holliday R. The inheritance of epigenetic defects [J]. Science,1987,238(4824):163-170.
[3] Wolffe AP,Matzke MA. Epigenetics:regulation through repression [J]. Science,1999,286(5439):481-486.
[4] Lo PK,Sukumar S. Epigenomics and breast cancer [J]. Pharmacogenomics,2008,9(12):1879-1902.
[5] Cooper CS,Foster CS. Concepts of epigenetics in prostate cancer development [J]. Br J Cancer,2008,100(2):240-245.
[6] Nystrom M,Mutanen M. Diet and epigenetics in colon cancer [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09,15(3):257-263.
[7] Enokida H,Nakagawa M. Epigenetics in bladder cancer [J]. Int J Clin Oncol,2008,13(4):298-307.
[8] Cheng X,Blumenthal RM. Mammalian DNA methyltransferases: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J]. Structure,2008,16(3):341-350.
[9] Lu XX,Yu JL,Ying L S,et al. Stepwise cumulation of RUNX3 methylation mediated by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contributes to gastric carcinoma progression [J]. Cancer,2012,118(22):5507-5517.
[10] 賈安平,梁秀蘭,胡宏波.胃癌中p16基因甲基化及其與胃癌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J].華夏醫學,2011,(3):254-257.
[11] Guo W,Dong Z,Chen Z,et al. Aberrant CpG island hypermethylation of RASSF1A in gastric cardia adenocarcinoma [J]. Cancer Invest,2009,27(4):459-465.
[12] 姜蕊,趙春明,宋美娟,等.胃癌組織中E-cadherin基因啟動子異常甲基化狀態觀察[J].山東醫藥,2012,51(50):4-6.
[13] Sugita H,Iida S,Inokuchi M,et al. Methylation of BNIP3 and DAPK indicates lower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and poor prognosis in gastric cancer [J]. Oncol Rep,2011,25(2):513-518.
[14] Krause B,Sobrevia L,Casanello P. Epigenetics:new concepts of old phenomena in vascular physiology [J]. Curr Vasc Pharmacol,2009,7(4):513-520.
[15] Oki M,Aihara H,Ito T. Role of histone phosphorylation in chromatin dynam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disease [J]. Subcell Biochem,2007,41:319-336
[16] Fehri LF,Rechner C,Janen S,et al. Helicobacter pylori-induced modification of the histone H3 phosphorylation status i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reflects its impact on cell cycle regulation [J]. Epigenetics,2009,4(8):577-586.
[17] Esteller M. Epigenetics in cancer [J]. N Engl J Med,2008,358(11):1148-1159.
[18] Mitani Y,Oue N,Hamai Y,et al. Histone H3 acety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p21(WAF1/CIP1)expression by gastric carcinoma [J]. J Pathol,2005,205(1):65-73.
[19] Pillai RS. MicroRNA function:multiple mechanisms for a tiny RNA? [J]. RNA,2005,11(12):1753-1761.
[20] Wu WY,Xue XY,Chen ZJ,et al. Potentially predictive microRNAs of gastric cancer with metastasis to lymph node [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11,17(31):3645-3651.
[21] Brenner B,Hoshen MB,Purim O,et al. MicroRNAs as a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tor in gastric cancer [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11,17(35):3976-3985.
[22] Konishi H,Ichikawa D,Komatsu S,et al. Detection of gastric cancer-associated microRNAs on microRNA microarray comparing pre-and post-operative plasma [J]. Br J Cancer,2012,106(4):740-747.
[23] Hur K,Han TS,Jung EJ,et al. Up-regulated expression of sulfatases (SULF1 and SULF2) as prognostic and metastasis predictive markers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J]. J Pathol,2012,228(1):88-98.
[24] Hou Z,Yin H,Chen C,et al. microRNA-146a targets the L1 cell adhesion molecule and suppresses the metastatic potential of gastric cancer [J]. Mol Med Rep,2012,6(3):501-506.
[25] Su Y,Ni Z,Wang G,et al. Aberrant expression of microRNAs in gastric cancer and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iR-574-3p [J]. Int immunopharmacol,2012,13(4):468-475.
[26] Liu K,Li G,Fan C,et al.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MicroRNA-221 in gastric cancer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J]. J Int Med Res,2012,40(2):467-474.
[27] Tsai KW,Liao YL,Wu CW,et al. Aberrant expression of miR-196a in gastric cancers and correlation with recurrence [J]. Genes Chromosomes Cancer,2012,51(4):394-401.
[28] Hashiguchi Y,Nishida N,Mimori K,et al. Down-regulation of miR-125a-3p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and its clinicopathological significance [J]. Int J Oncol,2012,40(5):1477-1482.
[29] Guo W,Dong Z,Guo Y,et al. Polymorphisms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gastric cardia adenocarcinoma in north China [J]. Int J Immunogenet,2011,38(3):215-224.
[30] 白雪蕾,孫麗萍,劉瑾,等.白介素10-1082G/A位點單核苷酸多態性與中國北方人群胃癌發病風險的病例對照研究[J].癌癥,2008,27(1):35-40
[31] Sun F,Sun Y,Yu Z,et al. Interleukin-10 gene polymorphisms influence susceptibility to cachexia in patients with low-third gastric cancer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J]. Mol Diagn Ther,2010,14(2):95-100.
[32] 宋傳貴,劉星,黃昌明,等.MMP-1基因1G/2G多態性與胃癌預后相關性的探討[J].中華腫瘤防治雜志,2011,18(11):833-835.
[33] 殷霞麗,謝麗,魏嘉,等.COX-2單核苷酸多態性與胃癌生物學行為相關性研究[J].現代腫瘤醫學,2010,18(11):2192-2195.
[34] Berwick M,Vineis P. Markers of DNA repair and susceptibility to cancer in humans:an epidemiologic review [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2000,92(11):874-897.
[35] Yuan T,Deng S,Chen M,et al. Association of DNA repair gene XRCC1 and XPD polymorphisms with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gastric cancer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J]. Cancer Epidemiol,2011,35(2):170-174.
[36] Song HR,Kweon SS,Kim HN,et al. p53 codon 72 polymorphism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and colorectal cancer in a Korean population [J]. Gastric Cancer,2011,14(3):242-248.
[37] Shirai O,Ohmiya N,Taguchi A,et al. P53,p21,and p73 gene polymorphisms in gastric carcinoma [J]. Hepatogastroenterology,2010,57(104):1595-1601.
[38] Wu C,Wang G,Yang M,et al. Two genetic variants in prostate stem cell antigen and gastric cancer susceptibility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J]. Mol Carcinog,2009,48(12):1131-1138.
[39] Shi D,Wang S,Gu D,et al. The PSCA polymorphisms derived from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are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gastric cancer:a meta-analysis [J]. J Cancer Res Clin Oncol,2012,138(8):1339-1345.
[40] Xu Z,Zhu H,Luk JM,et al.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OD2 and GSTP1 gene polymorphism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J]. Cancer,2012,118(22):5489-5496.
[41] Chen B,Cao L,Zhou Y,et al.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T1(GSTT1)gene polymorphism and gastric cancer susceptibility:a meta-analysis of epidemiologic studies [J]. Dig Dis Sci,2010,55(7):1831-1838.
篇7
關鍵詞 行為遺傳學;數量遺傳學;分子遺傳學:基因:人格
分類號 B845
1 引言
人格是一個人獨特精神面貌的整體反映,是需要、動機、興趣、態度、價值觀、氣質、性格、能力等多個方面的整合。它的形成和發展與遺傳因素息息相關。然而,人格的遺傳性究竟如何?到底哪些基因在起作用?它們又是如何起作用的?針對諸如此類的問題,行為遺傳學家們試圖為我們提供有效的解答,并由此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即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
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就是運用行為遺傳學理論和方法來考察和揭示人格特征(包括人格障礙)和人格差異的遺傳基礎問題。它強調遺傳基因是塑造人格核心特征和造成人格個別差異的主要因素,但并不忽視環境的作用,甚至主張人格特征與人格差異是多種基因、多種環境以及基因與環境動態交互作用的結果。早在19世紀中后期,英國心理學家高爾頓(Galton,F.)就首先利用家譜法和雙生子法研究了人格差異的遺傳基礎。盡管他的研究因未將遺傳和環境區分開來而具有諸多局限,但它“為人類行為的變異范圍提供了檔案證明并且說明了行為變異存在遺傳基礎”(Plomin,DeFries,McClearn,& McGuffin,2008),是運用行為遺傳學方法研究人格差異的先驅性嘗試。高爾頓之后的20世紀,人格的行為遺傳學研究因行為主義主流范式的盛行而長期遭到“冷遇”。前者強調人格的遺傳性,而后者堅持環境論并認為人格由社會化的習慣決定,兩者的矛盾在這種勢力不均的情勢下曾一度不可調和。
但近幾十年來,行為主義的逐漸衰落和現代生物學特別是分子生物學的飛速發展分別為人格的行為遺傳學研究提供了巨大發展空間和發展動力,并使它由傳統的數量遺傳學取向發展到分子遺傳學取向。分子遺傳學取向是發端于20世紀初而到20世紀末才應用于人格研究的一種新取向,它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都較數量遺傳學取向具有革命性突破,目前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可以說,人格遺傳學研究進入到分子遺傳學時代(Johnson,Penke,& Spinath,2011)。不過,兩種研究取向在基本思路方面各有特色,在具體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有價值的成果,積極推動了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的復興和發展。
2 數量遺傳學取向
人格的數量遺傳學(quantitative genetics)研究取向主張運用雙生子研究、收養研究等設計來估計群體中遺傳因素對人格表現型方差的貢獻率,旨在用數量化的手段從宏觀上估計某種人格變異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遺傳效應引起的,并考察遺傳通過與環境交互作用或相關影響人格的方式以及這些效應發生的具體情境。
2.1 人格遺傳率
數量遺傳學衡量人格遺傳性大小的核心指標是遺傳率(heritability),即在某群體內觀測到的人格總變異中能被遺傳變異解釋的百分比,它既可以揭示遺傳是否影響某種人格特征又可以指明這種影響達到何種程度。人格遺傳率可以用公式h2=Vg/Vp(其中h2代表人格遺傳率,Vg代表遺傳導致的人格變異,V。代表觀測到的人格總變異)來表示,數值在0~1之間,越接近于0,說明變異越少源于遺傳;越接近于1,說明變異越多源于遺傳。需要指出的是,遺傳率估計具有如下三個特點:第一,它具有群體特異性,僅僅適用于解釋樣本或群體的人格差異,而不適用于描述個體人格的遺傳性;第二,它假定遺傳因子和環境因子之間不存在相關或交互作用;第三,它會因測量方法和計算方法不同而有細微差別(郭永玉,2005;Larsen & Buss,2009)。
2.2 數量遺傳學設計
為了把基因和環境對人格差異的貢獻分離開來,數量遺傳學家采用了家族研究、雙生子研究和收養研究等多種研究設計。家族研究是最早用于人格研究的行為遺傳學方法,但它不能將遺傳與共同環境的作用區分開來,因而不能得出準確的遺傳率;雙生子研究是現代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最常用的一種有效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家族研究的缺陷,但它的等環境假設和代表性也往往令人擔憂:收養研究作為一種強有力的自然實驗法,是“解開影響家族相似性的遺傳和環境源之結的最直接方法”,避免了雙生子研究中的等環境假設問題,提供了環境影響人格差異的最佳證據,但它也存在三個爭議,即代表性、生前環境影響和選擇性安置效應(Plomin et al.,2008)。
鑒于以上三種方法各有其長處和不足,在過去的20多年中,數量遺傳學家已經開始利用家族研究、雙生子研究和收養研究的組合設計來研究人格。例如,研究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就把雙生子研究和收養研究各自的優點進行了有效整合,并且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在某種人格特質上的相關系數可以直接解釋為遺傳率的一個指標(Larsen & Buss,2009)。另外,隨著離異和再婚現象增多而產生的繼親家庭研究,自然地綜合了家族研究與收養研究的優勢,也是一種有趣和有效的組合研究設計。對多組比較的組合設計,甚至簡單的收養和雙生子研究,現代行為遺傳學通常采用模型擬合(model fitting)的方法進行統計分析,即建立一個反映各種遺傳和環境因素對某種人格特質貢獻大小的結構方程模型,并將其與觀測到的相關進行比較,從而估計出遺傳和環境的影響程度(郭永玉,2005)。
2.3 具體研究與發現
數量遺傳學取向的人格研究者利用上述設計主要對人格特質、人格障礙以及態度與偏好的遺傳性問題進行了考察。
2.3.1 人格特質
數量遺傳學關于人格特質的研究主要涉及人格的五大特征,即外傾性、宜人性、責任心、神經質和經驗開放性,其中研究最充分的要數外傾性和神經質。多數數量遺傳學研究表明,“大五”人格模型中的所有因素都具有中等大小的遺傳率,并且此研究結果在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樣本群體中具有普遍一致性(saudino,1997;Loehlin,McCrae,Costa,& John,1998)。例如,兩項以雙生子為被試的研究表明,神經質和外傾性的遺傳率估計值分別為43%和52-54%(Wray,Birley,Sullivan,Visscher,& Martin,2007;Rettew,Rebollo-Mesa,Hudziak,Willemsen,& Boomsma,2008)。以往數量遺傳學對“大五”人格的研究通常都以正常人群為被試,最近許多研究開始關注異常人群“大五”人格的遺傳性問題。例如,Kendler,Myers和Reichborn-Kjennerud(2011)的研究表明,邊緣型人格障礙與“大五”人格中的神經質維度存在顯著的遺傳正相關,而與宜人性和責任心維度存在顯著的遺傳負相關。Hare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躁郁癥患者人群“大五”人格的遺傳率(23%~32%)某種程度上低于正常人群的研究結果(40%~60%)。我們固然可以推測是異常人格影響了“大五”人格遺傳率的變化,但要得出確切的因果結論還需依賴未來數量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更加細致的綜合研究。
除“大五”人格外,研究者還對活動水平(activity level)和“精神病”人格特質的個別差異進行了行為遺傳學分析。活動水平是氣質的一個組成元素,其個別差異出現于生命早期,并隨著時間推移在兒童身上表現出穩定性。Spinath,Wolf,Angleitner,Borkenau和Riemann(2002)對300對雙生子的研究表明,活動水平存在40%的遺傳率。“精神病”人格特質包括權術主義、鐵石心腸、沖動性不一致、無所畏懼、責備外化和壓力免疫等方面。Blonigen,Carlson,Krueger和Patrick(2003)對353名男性雙生子進行了研究,發現所有這些“精神病”人格特質都表現出中等或高等的遺傳率。
數量遺傳學研究發現,盡管不同研究設計所得出的具體數值會有所不同,但一般的人格特質都具有較高的遺傳率估計值(Krueger & Johnson,2008)。
2.3.2 人格障礙
數量遺傳學系統研究的人格障礙主要有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礙、強迫型人格障礙和邊緣型人格障礙。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礙具有輕微精神分裂樣癥狀,用個人訪談法和問卷法所做研究表明,它具有非常高的遺傳率(Kendler,Myers,Torgersen,Neale,& Reichbom-Kjennerud,2007)。強迫型人格障礙是一種神經精神病狀態,以思想、情感、觀念以及行為的反復為典型癥狀,它所包含的五個因素即禁忌、污馳/清潔、疑慮、迷信/儀式和對稱/囤積的遺傳率位于24%和44%之間(Katerberg etal.,2010)。上述兩種人格障礙可能是精神機能障礙遺傳連續體的一部分,因為它們分別與精神分裂癥和強迫焦慮癥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遺傳重疊(Plomin et al.,2008)。邊緣型人格障礙是一種以心境反復無常、自我認同感紊亂、情緒沖動以及行為不穩定等為主要表現的人格障礙,它很大程度上受遺傳基因影響。例如,對荷蘭、比利時和澳大利亞三個國家5000多名雙生子的數量遺傳學研究表明,加性遺傳效應(additive genetic effect)可以解釋42%的邊緣型人格障礙變異,而且這一結果具有跨性別和跨國別的一致性(Distel et al.,2008)。最近一項10年的雙生子縱向研究發現,邊緣型人格障礙特質在14~24歲的各個年齡段都具有中等的遺傳率,且遺傳率有隨年齡增長而輕微上升的趨勢,而這些特質的穩定性和變化受遺傳因素高度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受非共享環境的影響(Bornovalova,Hicks,Iacono,& McGue,2009)。
2.3.3 態度與偏好
穩定的態度和偏好通常被看作人格的一部分,并表現出廣泛的個體差異。數量遺傳學家對態度和偏好的遺傳性進行了饒有趣味的考察。綜觀多數研究可知,態度的核心特征傳統主義具有中等的遺傳率。例如,一項明尼蘇達的雙生子研究表明,傳統主義的遺傳率為63%;一項對654名收養和非收養兒童的縱向研究表明,遺傳對保守態度具有重要影響,并且顯著的遺傳影響早在12歲時就已產生(Larsen & Buss,2009)。然而,并不是所有態度和信仰都表現出中等水平的遺傳率,這要因所研究的態度類型而異。例如,一項對400對雙生子的研究表明,對上帝的信仰、對宗教事務的參與以及對種族一體化的態度的遺傳率為零(Larsen&Buss,2009)。基因似乎也影響職業興趣或偏好。一項用修訂版的杰克遜職業興趣量表(JVIS)做的研究表明,34種職業興趣中有30種的遺傳率在37%和61%之間(schermer & Vernon,2008)。這表明,我們絞盡腦汁作出的職業選擇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們從父母那里繼承的基因的影響。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為什么有些態度和興趣具有較高的遺傳性,而有些態度和信仰的遺傳性不明顯甚至為零?或許未來的行為遺傳學研究能夠給出答案。
3 分子遺傳學取向
人格的分子遺傳學(molecular genetics)研究取向主張在DNA水平上用基因測定方法研究特定基因對人格表現型的影響效應,旨在超越傳統人格數量遺傳學研究僅停留在統計學層面考察遺傳率的局限,而從微觀層面直接鑒別對人格產生重要遺傳影響的具體基因或基因組合,以精確揭示人格特征(包括人格障礙)或人格差異的根本遺傳機制。
3.1 人格候選基因
已知人類基因具有數萬種之多,要想從中找出對人格起作用的特定基因是件困難的事情。況且,復雜的人格或行為特質并不簡單地遵循孟德爾的單基因遺傳定律,而是同時受作用幅度不完全相同而又相互協同和相互作用的多個基因的影響,這就又大大增加了確定這些基因的難度。因此,研究者不可能對所有基因都進行考察,更多的是考察候選基因與人格的關系。人格候選基因(candidate gene)是被假定與某一人格特質有關的基因,通常人們已了解其生物學功能和序列,它們可能是結構基因、調節基因或在生化代謝途徑中影響性狀表達的基因。研究者一般通過了解相關生理機制來確定人格的候選基因。例如,用于治療活動過度的藥物常含有多巴胺,因而像多巴胺受體、多巴胺啟動子和多巴胺轉運體這樣與多巴胺有關的基因便成為候選基因研究的目標。我們通常缺乏哪些基因是人格候選基因的強假設,因此試圖將那些與具有生理作用的DNA標記有關的基因與人格聯系起來的做法是很有道理的(張麗華,宋芳,鄒群,2006)。
3.2 研究策略
人格分子遺傳學研究者主要采用連鎖策略和關聯策略來尋找和鑒別對特定人格或行為特質有廣泛遺傳影響的具體基因。連鎖策略(linkagestrategy)采取從行為水平到基因水平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它以攜帶某種人格特質或障礙的家系為研究對象,對連續幾代人的DNA樣本進行分析,以確定是否有對該人格特征影響較大的特定基因存在。由于研究者并無假定的候選基因,這種策略對定位單基因遺傳特質的強效基因十分有效,但當牽涉若干個作用較小的基因時它便不再那么有效。然而,大多數復雜的人格或行為特質往往牽涉多個微效基因,于是另一種較新的關聯策略(association strategy)便成為最常用的確定人格基因的策略。關聯策略采取由基因到行為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通過考察擁有某種特定基因(或等位基因)的個體比沒有該基因的個體在某種特定人格特質上的得分是高還是低,來確定候選基因與人格或行為特質之間的關聯情況,即一種可能的因果關系。關聯策略比連鎖策略更容易找到只有微弱效應的特定基因,但系統性不夠強。
隨著人類基因組多態性研究以及SNP分型技術的發展,全基因組掃描(genome-wide scanning)逐漸成為一種標志性的分子遺傳學人格研究策略(Strobel & Brocke,2011)。它主要包括對人格表現型的全基因組連鎖分析和全基因組關聯分析,先將人格表現型的相關位點定位于染色體某個區域,然后再進行候選基因研究或連鎖不平衡分析,確定其具體基因位點。例如,一項用全基因組掃描做的研究表明,傷害回避與8p21染色體區域存在顯著相關(zohar et al.,2003)。
3.3 具體研究與發現
基因主要是通過大腦中的神經遞質系統來影響人格的,因而參與調節神經遞質系統的基因便成為主要的候選基因。在Cloninger等人的人格心理生物模型中,新穎性尋求(novelty-seeking)、傷害回避(harm-avoidance)和獎賞依賴(reward-dependence)三種氣質維度被假定分別與大腦調節不同類型刺激反應的三種神經遞質系統即多巴胺(dopamine)系統、5-羥色胺(serotonin)系統和去甲。腎上腺素(noradrenaline)系統相聯系。此類理論假設促使人格分子遺傳學研究者們主要從這三種神經遞質路徑考察了基因多態性與人格之間的關系。
3.3.1 多巴胺系統
多巴胺是腦部負責快樂和興奮的一種積極化學物質,它的缺乏會促使個體積極尋求有效物質或新異經驗以增加多巴胺釋放。到目前為止,人格研究中最早且最多關注的DNA標記是位于第11號染色體短臂上的多巴胺D4受體基因(DRD4)。1996年,兩個獨立研究小組同時在《自然遺傳學》上報告了DRD4基因的3號外顯子中的48-bp VNTR多態性與新穎性尋求之間存在正相關,標志著人格分子遺傳學研究的初步登場(Ebstein & Israel,2009)。其中,Ebstein領導的小組運用三維人格問卷(TPQ)對124名猶太健康志愿者進行了測量,發現長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對新穎性尋求具有6%的解釋效應,而未發現它與另外三個TPQ指標(獎賞依賴、傷害回避和堅持性)有顯著關聯(Ebstein et al.,1996);Beniamin領導的小組運用大五人格量表修訂版(NEO-PI-R)對315名美國成人和兄弟姐妹進行了預測測量,也發現擁有長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的個體比擁有短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的個體新穎性尋求水平顯著高,并且發現長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與NEO-PI-R量表的外傾性和責任心兩個維度顯著相關,而在其他三個維度即神經質、開放性和宜人性上未見此結果(Benjamin et al.,1996)。對于這兩種研究的結果可能的解釋是,擁有長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的個體對多巴胺的相對缺乏反應敏感,需要尋求外界新異經驗來增加多巴胺釋放,而擁有短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的個體傾向于對腦中已經存在的多巴胺作出高度反應,無需尋求新異經驗便可使多巴胺含量達到適當水平。
此后,一系列研究對DRD4基因與新穎性尋求這種人格特質之間的關聯進行了重復驗證,但結果并不完全一致。兩項分別以德國人和日本人為被試的研究證實DRD4基因與新穎性尋求特質之間的確存在顯著關聯(strobel,Wehr,Michel,&Brocke,1999;Tomitaka et al.,1999);Burt等人對明尼蘇達137個雙生子家庭所做的研究發現,DRD4基因與新穎性尋求測量指標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Bun,McGue,Iacono,Comings,&MacMurray,2002);Ekelund等人則得出了與1996年研究相反方向的結果,即在新穎性尋求水平較高的群體中,2次和5次重復等位基因而非7次重復等位基因的頻率更高(Ekelund,Lichtermann,Jarvelin,& Pelmnen,1999)。除此之外,有些研究還發現DRD4基因與其他人格候選基因存在聯合效應。一項關于1歲新生兒對新異事物反應的研究發現,DRD4基因中的48-bp VNTR與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5-HTT)中的一種多態性存在聯合效應(Lakatos et al.,2003)。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多樣的研究結果,可能與樣本大小、被試特點(年齡、性別和種族文化等)、測量工具、研究設計等因素有關。例如,分組方法不同所得研究結果就會有很大差異(Tsuchimine et al.,2009)。不管怎樣,這都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證實。
除DRD4基因外,研究者還對多巴胺系統中的其他人格候選基因進行了考察,如多巴胺D2受體基因(DRD2)、多巴胺D3受體基因(DRD3)、多巴胺D5受體基因(DRD5)以及多巴胺轉運體基因(DATl)等。一項用多種人格測驗所做的研究表明,DRD2基因的-141C插入/缺失多態性與卡氏人格量表(KSP)測量的冷漠以及北歐大學人格量表(SSP)測量的自信缺乏之間存在關聯(JSnsson et al.,2003,),而利用氣質性格量表(TcI)對被試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141C插入/缺失多態性和DRD2/ANKK1基因的TaqlA多態性與人格特質之間可能并非存在直接強相關,而是在DRD2基因與ANKKl基因的交互作用條件下才對人格產生影響(Tsuchimine et al.,2012)。在一個由862名個體組成的樣本中發現DRD3基因與神經質和行為抑制存在關聯,而當該樣本擴大到1465人時這種關聯未得到驗證(Henderson et al.,2000)。有研究表明,DRD5基因可能與人格的持續性發展有關(Vanyukov,Moss,Kaplan,Kirillova,&Tarter,2000)。由于發現DAT1基因與具有某些新穎性尋求特征的注意缺陷多動癥(ADHD)存在關聯(Jorm et al.,2001,),有人用極端分數個體為被試考察了DATl基因與新穎性尋求之間的關聯,結果表明這種效應只在女性被試身上有所顯現(van Gestel et al.,2002)。
3.3.2 5-羥色胺系統
5-羥色胺作為一種生物胺,對于人類的攻擊性、抑郁、焦慮、沖動、幸福感等情緒情感具有重要調控作用。此系統中最經常被研究的人格候選基因是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5-HTT),該基因越長釋放和回收5-羥色胺的效率越高,已有許多研究考察了它與傷害回避等焦慮類人格特質之間的關聯。5-HTT基因具有兩種多態性:5-HTT基因連鎖的多態性區域(5-HTTLPR)和5-HTT基因2號內含子中的VNTR多態性,其中人格研究關注最多的是5-HTTLPR。
1996年的一項經典研究發現,短5-HTTLPR等位基因攜帶者較長5-HTTLPR等位基因攜帶者在神經質和傷害回避維度上的表現水平更高(Lesch et al.,1996)。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表明,攜帶一個或兩個短5-HTTLPR等位基因復本的個體在對恐怖刺激的反應中表現出更強的杏仁核神經元活動(Harid et al.,2002)。這種由遺傳導致的杏仁核對情緒刺激的興奮性差異支持了該結論。不過,也有一些其他研究并未發現此種關聯(Flory et al.,1999;Tsai,Hong,& Cheng,2002)。還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結果。例如,使用極端得分個體做的一項研究發現,短5-HTTLPR等位基因在低傷害回避群體中比在高傷害回避群體中出現的頻率更高(van Gestel et al.,2002)。2004年的一份元分析指出。這種可重復性的缺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樣本量過小以及所使用的量表不同而導致(Sen,Burmeister,& Ghosh,2004)。分析者發現,運用大五人格量表測量的神經質與5-HTTLPR有顯著關聯,而運用氣質性格量表測量的傷害回避與5-HTTLPR不存在任何顯著關聯。2008年的另一份元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結論(Munaf6 et al.,2008)。然而,使用NEO-PI-R量表對4000多名被試進行的一項大型研究發現,5-HTTLPR與神經質或其各維度(焦慮,抑郁,憤怒,敵意,自我意識,沖動。易受傷害性)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Terracciano etal.,2009)。近年來,有研究者發現,與其雜合子同伴或短等位基因的純合子同伴相比,具有長5-HTLPR等位基因的純合子個體通常更關注積極情感畫面,而選擇性地回避一同呈現的消極情感畫面(Fox,Ridgewell,& Ashwin,2009)。這表明他們通常更加樂觀。使用信息加工眼動跟蹤評估法進行的另一項研究發現,短5-HTLPR等位基因攜帶者在視覺上更加偏愛積極場景而回避消極場景,長5-HTLPR等位基因的純合子個體更加無偏地看待情緒場景(Beevers,Ellis,Wells,& McGeary,2009)。這表明,短5-HTLPR等位基因攜帶者可能比長等位基因純合子個體對環境中的情緒信息更加敏感。對于5-HTLPR與人格特質之間關系的這些看似不一致的結論,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確證。此外,一項最新研究顯示,5-HTLPR與Val66Met兩種多態性對傷害回避存在顯著交互作用(Ariaset al.,2012)。
除5-HTT基因外,研究者還對5-羥色胺系統中的另外兩個人格候選基因5-羥色胺2A受體基因(5-HT2A)和5-羥色胺2C受體基因(5-HT2C)進行了考察。有研究者在雙極性精神障礙患者和健康控制組群體中檢驗了5-HT2A的1號外顯子中的一種單核苷酸多態性與傷害回避維度之間的關聯,但是沒有發現任何關聯存在(Blairy et al.,2000)。還有研究者以健康日本人為樣本對5-HT2A的5種單核苷酸多態性進行了考察,沒有發現它們與氣質性格量表的任何維度存在關聯(Kusumi et al.,2002)。就5-HT2C與人格的關系而言,研究者發現5-HT2C中的一個點突變與三維人格問卷的獎賞依賴維度和堅持性維度存在關聯,并且DRD4與5-HT2C對獎賞依賴存在顯著交互效應(Ebstein et al.,1997)。然而,后來的一項重復性研究發現,5-HT2C對獎賞依賴不存在主效應,但DRD4與5-HT2C對獎賞依賴確實存在顯著交互效應(Kühn et al.,1999)。
3.3.3 去甲腎上腺素系統
在人格的分子遺傳學研究中,人們對去甲腎上腺素系統的關注遠不及對多巴胺系統和5-羥色胺系統的關注多,但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研究以健康被試為樣本,考察了去甲腎上腺素轉運體(NET)的一種外顯子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RFLP)與氣質性格量表中各維度之間的關系,但沒有發現任何關聯存在(Samochowiec et al.,2001)。不過,另一項以朝鮮人為被試的研究表明,去甲腎上腺素轉運體的T-182C基因多態性與氣質性格量表的獎賞依賴維度存在顯著關聯(Ham,Choi,Lee,Kang,& Lee,2005)。有研究表明,在中國人被試中,αla腎上腺素受體基因(ADRAlA)和0c2a腎上腺素受體基因(ADRA2A)的多態性與三維人格問卷各維度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Tsai,Wang,& Hong,2001)。而之前的另一項研究發現,ADRA2A的一種常見單核苷酸多態性與易怒性、敵對性和沖動性諸測量值之間的確存在某些關聯(comings et al.,2000)。關于去甲腎上腺素系統的諸候選基因與人格之間關系的研究,有待進一步加強。
4 總結與展望
行為遺傳學通過數量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兩條取徑對人格遺傳性問題進行了不同層次的詳細探索,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推進了我們對人格遺傳程度和遺傳機制的深刻認識,也有利于促進人格研究的科學化。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的兩類取向各具優勢和不足。數量遺傳學取向借助生態研究設計從宏觀上估計遺傳變異對人格差異的解釋程度,資料獲取經濟簡單、技術要求低,并且結果解釋相對容易,但它無法確切地告訴我們究竟哪些基因或多態性導致了人格差異以及具體作用過程如何(Parens,2004),對研究設計和被試取樣的依賴性較強,況且面對遺傳與環境實際存在相關或交互作用的不爭事實,遺傳率的解釋意義往往遭到質疑(Lerner,2011)。分子遺傳學取向擺脫了數量遺傳學取向存在的諸多不足,可以從DAN水平精確細微地探知造成人格障礙或差異的特定基因及其作用機制,但研究程序繁瑣復雜,對新興生物技術要求較高,在人格候選基因的選擇上帶有推測性,迄今為止尚未產生符合最初預期的可重復的實質性人格研究成果(McClellan & King,2010)。除此之外,兩類研究取向還存在諸多共同的問題:一是受測量手段限制,對被試自陳報告依賴性高,往往會造成某些人格特質在防衛或偽裝心理作用下被隱藏;二是由于研究設計和技術、被試取樣、人格和基因自身復雜性以及環境與基因的交互作用等原因,研究結果的可重復性不高(Kim & Kim,2011);三是受過去百余年消極心理學研究傳統的影響,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精神分裂癥、抑郁癥、多動癥等病理人群(張文新,王美萍,曹叢,2012),缺乏對健康人群積極人格品質的遺傳研究;四是研究成果的現實利用率低,未能把研究所得成果及時有效地轉化為現實效益。
鑒于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所存在的諸多問題,未來研究應特別注意以下五個方面:
(1)強調兩種研究取向的有機結合,在數量遺傳設計中加入對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測量。這兩種研究取向各有優缺,可以相互彌補,況且分子遺傳學的許多工作需用傳統數量遺傳學設計綜合考慮環境與遺傳因素來完成。未來研究可以在數量遺傳設計中加入對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測量,例如,可以先用數量遺傳學方法確定某種人格特征是否具有遺傳性以及遺傳到什么程度,然后再用分子遺傳學方法從根本上細微探究影響人格的具體基因及其作用方式。
(2)注重多學科和多范式的有效整合。人格的行為遺傳學研究是一項綜合性很高的困難工作,涉及遺傳學、心理學、生物學、神經科學、醫學和社會學等多門學科,因此需要在更廣泛的視野下進行多學科的整合研究。人格的遺傳機制相當復雜,靠單一研究工具(如自陳問卷)或研究范式很難獲得理想結果,今后應在傳統研究范式的基礎上綜合采用腦成像、誘發電位、前脈沖抑制和計算機博弈模型等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從多個角度綜合考察和相互印證人格與基因的關系,從而彌補由自陳報告帶來的弊端,同時克服可重復性低的問題。
(3)擴大對健康人群積極人格品質的研究。未來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不僅要研究病理人群的消極人格品質,而且更要研究正常人群甚至超常人群的積極人格品質,探究它們的遺傳性及分子作用機制,為積極人格品質的培養提供遺傳學依據。
篇8
【關鍵詞】 腫瘤抑制基因;DNA甲基化;胃癌
Abstract:Epigenetics is the study of genetic changes in gene expression without the sequence change of DNA, in which DNA methy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studied epigenetic mechanism. CpG island is the sequence of human genome, located mainly in the promoter as well as the first extron regions. The size of it is nearly 100~1 000 bp and it links with 60% of human coding genes. Methylation of CpG sites in the promoter regions of genes can lead to decreased expression and silence the tumor suppressor genes and contribute to oncogenesis.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DNA methylation in gastric carcinoma was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tumor suppressor genes; DNA methylation;gastric carcinoma
胃癌是人類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發病率高,據統計,其死亡率居全球惡性腫瘤死亡率的第二位,嚴重的危害著人類的健康和生命。胃癌發生的機制目前仍不是很清楚,研究表明,細胞無限增殖及分化受阻是腫瘤發生的基本過程,隨著分子生物學和基因工程技術的迅速發展,人們逐漸深化了對腫瘤發生學的認識。近年研究結果顯示腫瘤的發生是多基因異常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癌基因活化和腫瘤抑制基因失活,有關表遺傳學研究顯示[1],表遺傳學異常參與了腫瘤發生過程,而且在某種腫瘤的發生中起重要作用,其中DNA異常甲基化可致基因表達減弱或基因沉默,是導致腫瘤抑制基因失活的重要機制之一。本文就胃癌的發生發展過程中一些腫瘤抑制基因DNA異常甲基化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DNA甲基化及其作用
表遺傳學(epigenetics)是1939年由waddington首先提出的。表遺傳學是研究在DNA序列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所發生的可遺傳性基因表達的改變[1]168-174。其中包括DNA甲基化、基因組印記、染色體組蛋白修飾、隔離蛋白以及非編碼RNA調控等方式,這種模式傳遞給子代細胞是不依賴DNA序列的。其中DNA甲基化是研究最多、最深入的一種表遺傳學表達機制。
DNA甲基化是指在DNA甲基轉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 DNMTS)的介導下,二核苷酸中胞嘧啶(C)的第5位原子上的H被S—腺苷甲硫氨酸提供的甲基取代,使之變成5—甲基胞嘧啶(5-methy1cytosine,m5C)[2]的化學修飾過程。甲基化酶包括維持甲基化轉移酶(DNMT 1) 和重新甲基化酶(DNMT 3a,DNMT 3b)。維持甲基化酶的作用是識別子代DNA 雙鏈中親代單鏈上已甲基化的CpG 位點,催化互補單鏈的胞嘧啶(C) 發生甲基化;重新甲基化酶的作用是使非甲基化的雙鏈DNA 發生甲基化的過程[3] 。DNA的甲基化修飾反應主要發生在CpG二核苷酸的胞嘧啶,CpG 位點以兩種形式存在,一種為分散于DNA中,正常情況下這些 CpG二核苷酸甲基化可作為一種宿主基因的保護機制,它會抑制重復子轉錄以及重復子同源性重組,還可以抑制“寄生”DNA序列(如逆轉錄病毒片段)的侵入;另一種是CpG 結構高度聚集在一起,即CpG 島(CpG island)。CpG島在基因組內呈不連續分布,通常位于基因的啟動子區域(promoter region),也可位于第一外顯子區域, 故又稱5′-CpG 島[4]。在正常細胞中,CpG 島通常不發生甲基化修飾,而腫瘤組織常發生其相關基因啟動子區域的異常甲基化。DNA 甲基化異常可分為甲基化增強、甲基化減弱和甲基化轉移酶水平增高三種情況,其中抑癌基因甲基化增強在腫瘤中最常見。可通過改變基因的構型或與核內甲基化CG序列結合蛋白結合,阻止轉錄因子與基因形成轉錄復合物,從而導致其表達沉默,使腫瘤抑制活性喪失,被認為是腫瘤抑制基因失活的重要途徑。另外,DNA 的甲基化還可促進腫瘤相關基因突變,因5-甲基胞嘧啶可自發性或在SAM 作用下引起鄰位脫氨轉變為胸腺嘧啶,使甲基化的CpG 突變為TpG,因此其也是甲基化促進惡變的機制之一。
CpG島甲基化是一種基因外修飾,在正常細胞中基因的甲基化大多發生在其啟動子CpG 島之外,而在腫瘤細胞中某些抑癌基因的CpG島甲基化則導致該基因轉錄失活,故在腫瘤研究中檢測基因啟動子區CpG 島甲基化狀態,對于闡明腫瘤發生、發展的機制及建立早期診斷方法均具重要意義。目前DNA甲基化的檢測方法比較多,其中廣泛應用的技術是甲基化特異性的PCR技術(MSP)和甲基化敏感的單堿基延伸技術(Ms-SNuPE),這些技術的敏感性高,特異性強,適用于微量DNA或石蠟包埋DNA。在MSP技術的基礎上,又先后發展了基于熒光檢測方法的實時定量PCR(MethyLight)和依賴于限制性核酸內切酶的甲基化分析方法(COBRA),這些技術提高了檢測的敏感性,實現了高通量和高特異性。此外,有人將MSP技術與變性高效液相色譜法(DNPLC)相結合,來測定整個CpG位點的甲基化。近年,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與清華大學的研究人員合作,發展了基于水溶性陽離子型共軛聚合物的新DNA甲基化分析方法。通過熒光共振能量轉移技術(FRET)研究了質粒和人腫瘤細胞p16基因啟動子區特異CpG位點的甲基化狀態該技術具有較高的靈敏度和特異性。引物無需熒光標記,檢測在均相溶液中進行,無需分離、純化等手段,而且與高通量分析兼容,在癌癥臨床診斷上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5]。
2 胃癌相關基因的甲基化
近年研究結果顯示,多種基因的異常甲基化在胃癌發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有研究[6]表明,DNA的甲基化率在胃癌前病變轉化為癌的過程會發生改變。Kang等[7] 對非腫瘤胃黏膜和胃腫瘤進行p16、hMLH1、DAP—kmase、THBS1、及TIMP-3等5種基因檢測,發現除DAP—kmase甲基化的頻率相近之外,其他基因從慢性胃炎到腸化生及從腺瘤到腺癌甲基化頻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高。因此認為,這些基因的高甲基化在胃癌變發生過程中的較早階段就已出現,這為胃癌的早期診斷提供了新思路。
2.1 p16基因甲基化
p16基因又稱多腫瘤抑制基因(multiple tumor suppressor,MTS),定位于9p21 位點,由2個內含子和3 個外顯子組成。該基因編碼的蛋白是一種重要的細胞周期負調控蛋白,可與D型細胞周期蛋白(cyclinD)競爭性結合細胞周期蛋白依賴激酶CDK4 和CDK6而抑制蛋白激酶活性,使腫瘤細胞周期調節中抑癌基因Rb的表達產物(PRb)不能磷酸化而保持活化狀態,抑制轉錄因子EF解離,使細胞周期進展最關鍵的G 1/S轉換停滯,對細胞周期起負調控作用。因此,p16 基因的變異或其蛋白的失活會導致cyclinD-CDK4/6-pRb-E2F調節途徑的失控,而使細胞過度增殖,導致腫瘤發生。目前研究表明p16基因的純合缺失和點突變異常多種腫瘤的發生有關。在胃癌中p16基因異常甲基化主要發生在外顯子1和啟動子區域,且基因啟動子的高度甲基化更為常見。Lee等[8]最早報道了p16 甲基化與胃癌的關系,他們用甲基化敏感性限制性內切酶研究了9 個胃癌細胞株,發現2個細胞株有甲基化,而且不表達p16mRNA;體外以去甲基化劑5-deoxy-ezecytidine對胃癌細胞系處理后,因CpG島異常甲基化而封閉的基因又重新表達。Ficorella 等[9]發現原發性胃癌中p16 基因啟動子區域高甲基化是導致其轉錄失活的重要原因。Bai等[10]利用誘發Wistar 大鼠胃癌模型研究發現,在大鼠胃黏膜向胃癌演變過程中,p16 基因甲基化是在胃癌發生過程的較早階段出現,其甲基化的頻率在正常胃上皮中為2.7%, 在慢性萎縮性胃炎中為16.7%,在腸上皮化生中為37.5%,在胃腺瘤中為64.7%,在胃癌中則高達82.5%。Abbaszadegan 等[11]通過MSP 和免疫組化等方法同時對52 例胃癌患者組織和血清中p16基因甲基化及蛋白表達情況分析后,認為p16 啟動子區高甲基化在胃癌發生中起重要作用,并且與胃癌惡性程度相關。同時提出血清中DNA 甲基化水平的檢測可能是胃癌早期檢查的一個重要的生物學指標。
2.2 DNA錯配修復基因(MMR)、CpG甲基化表型(CIMP)與胃癌
研究發現,在胃癌的發生中存在微衛星不穩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和 CpG甲基化表型(CpG island methylator phenohype,CIMP)兩種分子途徑。在DNA MMR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基因hMLH1 和hMSH2。MMR通過修復DNA堿基錯配、降低自發性突變,而增強DNA的保真性和維持基因組的穩定性。Herman等[12]最早報告了在結直腸癌中MMR hMLH1失活與DNA甲基化有關,后來發現胃癌中同樣存在微衛星不穩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亞型,但還沒有胃癌中有關DNA MMR發生突變的報道。Fleisher 等[13]檢測了65 例胃癌組織的hMLH1甲基化情況發現,隨著胃癌中MSI頻率的降低hMLH1基因的甲基化率也隨之降低。由此推測,hMLH1基因啟動子區域甲基化與MSI有關,有可能是該基因失活的一種普遍機制。Poplawski等[14]通過甲基化敏感限制性內切酶PCR(MSRE-PCR)對比分析27例胃癌患者與25 例健康人后認為,hMLH1 甲基化對胃癌形成有促進作用。由此可見,hMLH1啟動子的甲基化與胃癌的發生有關,可能是胃癌發生機制中的早期分子事件。
CpG甲基化表型(CIMP)是指一些病例同時存在多個基因甲基化的現象。CIMP已在大腸癌、肝癌、肝內外膽管癌、胰腺癌、卵巢癌、急性髓性白血病、膀胱癌等惡性腫瘤中得到證實。由于胃癌的發生是一個多步驟、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涉及許多相關基因的異常表達,因此多基因的啟動子甲基化的研究也就自然得到了研究人員的青睞,而且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CIMP與胃癌有著密切的關系。Kim等[15] 通過檢測40例早期胃癌組織中hMLH1、TIMP3、THBS1、DAP—K、GSTP1、APC和MINT2的甲基化狀況發現,除了2 例基因甲基化陰性外,CIMP盡然高達40%。可見,啟動子甲基化在早期胃癌中是一種普遍現象。同時研究還發現,在腫瘤發生的不同階段、不同基因的啟動子甲基化表達狀況是不同的,有的基因隨胃癌的進展其甲基化發生率有不斷升高的趨勢,而在健康青年人標本及胎盤中未發DNA甲基化。可見CIMP在胃癌的發生中是一早發事件,可以利用此特征作為胃癌的早期診斷指標,同時對建立胃癌相關基因的甲基化譜也具有積極的作用。
APC 基因是一種抑癌基因,編碼的APC蛋白可以抑制上皮細胞增殖而抑制腫瘤的發生。早期研究證實該基因是結直腸癌的管家基因,近來研究發現該基因在胃癌的發生發展中也起重要作用。曾有學者用免疫組化方法分析了120 例胃癌病人的APC基因的表達情況,結果發現,APC缺失率為78%,因此認為APC 基因缺失可能與胃癌的發生有關。近年來大量的研究顯示APC基因啟動子1A部位甲基化與胃癌發生關系密切。Hosoya等[16]研究發現APC基因啟動子1A蛋白表達率與甲基化率在正常胃粘膜和非癌粘膜中保持一致,在癌粘膜中甲基化率增高。而1B均未發現有甲基化。由此可見,ACP啟動子甲基化主要發生在1A部位,且ACP啟動子1A部位的甲基化可能是胃癌發生的一個中間環節,而不是胃癌發生的始動因素。3 結 語
通過對胃癌相關基因甲基化分析發現,多種相關基因甲基化是胃癌形成的重要機制之一。DNA甲基化異常不僅可在手術標本中檢測到,還可從各種體液如外周血清中檢測到,為臨床應用帶來極大便利,因此腫瘤相關基因啟動子甲基化狀態是一種非常有前途的生物標記物,可作為腫瘤的敏感性生物標志物。檢測胃癌相關基因啟動子異常甲基化不僅可用于高危人群監測、腫瘤風險評估、胃癌早期診斷,還可用于判斷腫瘤遷移情況,預測胃癌手術、放化療療效等。由于DNA甲基化是一個可逆的過程,故通過恢復僅被抑制而未發生突變或丟失的生長調控基因表達.來恢復細胞正常生長調控功能,并且已有這方面的動物模型研究證實了這一想法。故DNA的去甲基化將為癌癥的治療提供新思路。由于一些病原體的感染可以誘發腫瘤相關基因甲基化從而導致胃癌的發生,故預防感染和及時的根除這些病原體會對預防胃癌的發生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Baylin SB,Herman JG.DNA hypermethylation in tumorigenesis:epigetics joins genetics[J].Trends Genet,2000,16(4):168-174.
[2] Jeltsch A,Beyond Watson and Crick . DNA methylation and molecular enzymology of DNA methyltransferases[J].Chem Biochem ,2002,3(4):274-293.
[3] 夏丹,范偉.DNA甲基化與腫瘤相關性研究進展[J].中國誤診學雜志,2009,9(6):1275-1276.
[4] Takai D,Jones PA. Comprehensive ana1ysis of CpG islands in human chromosomes 21 and 22[J]. Proc Natl Acad Sci USA,2002,99(6):3740-3745.
[5] Feng F,Wang H,Han Y,et al.Fluorescent conjugated polyelectrolyte as an indicator for convenient detection of DNA methylation[J].Am Chem Soc,2008,130:11338-11343.
[6] Kim TY,Jong HS,Jung Y,et a1.DNA hypermethylation in gastile cancer[J].Aliment Pharmacol Ther,2004,20(1):131-142.
[7] Kan g G H,Shim Y H,Jung H Y,et a1.CpG island methylatien in premalignant stages of gastric carcinoma[J].Cancer Res,2001,61(7):2847-2851.
[8] Lee Y Y,Kang S H,Seo J Y,et al. Alterations of p16 and p15 genes in gastric carcinomas[J].Cancer,1997,80:1889-1896.
[9] Ficorella C,Cannita K,Ricevuto E,et al. P16 hypermethyl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gene inactivation profiles in primary gastric cancer [J].Oncol Rep,2003,10(1):169-173.
[10] Bai H,Gu L K,Zhou J,et al. p16 hypermethylation during gastric carcinogenesis of Wistar rats by N-methyl-N'-nitro-N-nitrosoguanidine[J]. Mutat Res,2003,535(1):73-78.
[11] Abbaszadegan M R,Moaven O,Sima HR,et al. p16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a useful serum marker for early detection of gastric cancer[J].World J Gastroenterol,2008,14(13): 2055-2060.
[12] Herman J G,Umar A,Polyak K,et al. Incidence and 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hMLH1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in colorectal carcinoma[J].Proc Natl Acad Sci USA,1998,95(12):6870-6875.
[13] Fleisher A S,Esteller M,Wang S,et al. Hypermethylation of the hMLH1 gene promoter in human gastric cancers with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J].Cancer Res,1999,59(6):1090-1095.
[14] Poplawski T,Tomaszewska K,Galicki M,et al. Promoter methylation of cancer-related genes in gastric carcinoma[J].Exp Oncol,2008,30(2):112-116.
篇9
同時,學生難以通過自身的自主學習與實踐獲取知識,更難有機會對課程的內容和問題發表基于自己理解的看法與意見。教與學的雙方對這一現象都頗有微詞。教師覺得學生學得太被動,沒有主動思考; 而學生則抱怨老師教學不夠精彩,提不起興趣。為了改善這一狀況,提高教學效果,自2012 年始至2014 年的三個教學周期里,本教學團隊在原有教學體系的基礎上,嘗試進行了教學方法的改革,采用探究式教學模式,改變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學生的學習方式。強調教師的作用不單是傳道、授業和解惑,還要盡可能地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提高學習效率,同時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形成一定的創新意識品質和實踐能力,以期為農科其他專業課的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提供可借鑒的范例。
一、構建基于問題的探究式教學模式
通過設計問題情景,激發學生好奇心和求知欲是探究式教學模式的本質特征,其關鍵在于挑起學生在認識上的矛盾,形成認知沖突,并提出問題。怎樣才能在教學過程中制造出認知沖突呢?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創設懸念法。懸念是一種學習心理機制,是由學生對所學對象感到疑惑不解而又想解決時所產生的一種心理狀態。它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使思維活躍、想象豐富,在解決所提出問題的同時還培養了學生克服困難的意志力。探究式教學的基本框架與模式或步驟如下: ( 1) 設置情景。( 2) 提出問題( 包含問題) 。( 3) 提出猜想或假設。( 4) 搜集資料和事實。( 5) 驗證假設。( 6) 交流評價與得出結論。( 7) 整合、建構、遷移、應用。
( 一) 課堂理論教學方面
課堂理論教學是課程教學過程最重要的方式,在教學過程中,隨著生命科學、信息技術和工程技術的迅猛發展,我們一直不斷將新理論和新技術補充到園藝植物育種學課程的教學內容之中,如離體培養育種、分子育種等近年來取得的研究新成果都在課堂上余小林等基于問題的園藝植物育種學探究式教學模式研究得到了及時的反映。同時,在課程講授中,以育種途徑為主線,重點介紹園藝植物種質資源調查( 查) 、引種馴化( 引) 、選擇育種( 選) ,以及在現有資源基礎上,通過人工創造變異,選擇獲得新的品種類型的創造變異育種( 育) 途徑,以及采用這些途徑選育新品種的理論、方法、技術等內容。
根據探究式教學模式的要求,我們將部分章節的課程內容進行了問題化,把定論形式陳述的材料轉化成引導學生探究的問題形式。為此,本教學團隊經過多次討論,設計了10 個情景問題: ( 1) 如何協調栽培品種遺傳背景越來越窄與種質資源亟需保護間的矛盾? ( 2) 為什么在明末清初時我國的人口有個劇增的高峰( 主要得益于紅薯、玉米和馬鈴薯等重要農作物種質資源的引進) ? ( 3) 如何制定園藝植物的育種目標? ( 4)如何在育種過程中避免遺傳累贅,實現優良性狀的定向重組? ( 5) 航天育種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嗎? ( 6) 雜種優勢的分子遺傳機制是什么? ( 7) 芽變的遺傳機理及其在育種中的應用。( 8) 轉基因作物的是天使還是魔鬼? ( 9) 基因組測序及分子設計育種的現在與將來。( 10) 表觀遺傳在育種中的作用。在上述精心設計的情景問題中,有些是本學科相關研究領域的研究前沿問題,如雜種優勢的分子遺傳機制、表觀遺傳在育種中的作用和消除遺傳累贅實現定向重組是迄今為止植物育種領域的研究瓶頸和未解之謎; 有些是業內和社會當前的熱點關注問題,如分子設計育種、芽變的遺傳機理、航天育種和轉基因作物的取舍等; 有些則是影響社會發展進程的重大問題,如種質資源的保護和人口社會發展問題等。但所有情景問題都是動態和開放的,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需要學生通過查詢大量的文獻資料,進行認真分析和整理,才能形成自己的觀點或假設,并通過大量論證來支撐自己的觀點或假設。
具體做法為: 將全班同學分成67 個小組( 5 人/小組) ,每小組負責一個題目。當授課到相應章節,在講授完基本概念和理論知識以后,就由某一小組接受本章的探究式情景問題的任務,通過小組討論,一般在四周后選擇合適的時間,由本小組代表通過PPT 形式在全班進行交流,并由授課教師和各小組組長對其探究式教學成效進行考核,同時,各小組還要遞交以學術論文格式撰寫的總結報告。探究式教學討論部分占總成績的20%30%。為了促進小組之間的生生交流,防止產生能者多勞的現象,采用臨時抽簽的方式產生小組交流的代表,其他組員可以在后面的答疑階段進行必要的補充。
正是這一小小操作上的改進,大大增加了小組內學生的交流和討論時間。只有每個組員都熟悉本小組的探究問題和PPT 內容,才能在全班交流時取得好成績,因為上臺前誰也不知道誰會上臺主講,誰也不想因自己而拖全小組的后腿。
( 二) 實驗教學方面
實驗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一個重要教學環節,是進一步掌握和理解理論知識的鑰匙,也為學生后續實習及畢業后的工作提供專業基本操作技能的訓練。在傳統的實驗課教學中,大多偏重于對相關理論的驗證,且過于強調程序性,老師講得多,學生參與少。學生完全按照教師所講或教材所示的步驟,機械性地操作實驗,缺少對研究原理與方法、實驗過程和技巧的深入思考,甚至互相抄襲實驗報告,導致學生過分依賴教師及教材,缺乏學習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不利于創新性人才的培養。針
對這一現實問題,結合本課程實驗內容理論基礎要求高、操作性強和實驗周期長等特點,我們對部分自主設計性實驗開展了探究式教學方法的改革。在上一次實驗課結束的時候我們就布置下次實驗的任務,讓學生自主設計實驗,使其全程參與前期實驗方案的制定、實驗材料的準備和試劑的配制等各個環節。以園藝植物花粉生活力測定實驗為例,目前測定植物花粉生活力的方法主要有: 形態檢驗法、發芽法、授粉法和染色法,其中染色法有I - KI 法、氯化三笨四氮唑法( TTC) 、聯苯胺- 萘酚法和亞歷山大染色法等。
對此我們提出下面兩個問題: 這些方法對所有植物的花粉都適用嗎? 哪些方法適合哪些植物? 同時,老師在課前僅對各種檢測方法進行介紹和指導,具體實驗材料和方法均由每組自行選擇。在隨后制定實驗方案時,學生選擇最多的是形態檢驗法和染色法,發芽法和授粉法由于需要的時間太長而很少有人問津。
實驗的結果也同樣讓人感到欣喜,結果表明,上述四種染色法對十字花科植物( 白菜、油菜、蘿卜和二月蘭等) 的花粉均得到比較滿意的結果,TTC 法和聯苯胺- 萘酚法對桃花和梨花的花粉有較好的染色效果,而結香和白玉蘭的花粉僅對亞歷山大染色法較為敏感。在比較了多種植物的花粉和染色法以后,通過一系列的置疑、判斷、比較、選擇以及相應的分析、綜合、概括等過程,由發散到收斂,學生得到了不同植物的花粉對上述不同方法的檢測效果各異的結論。學生普遍反映,這樣得到的知識比老師在課堂上強調10 遍的效果還要好很多。通過自主設計實驗、自主完成實驗和自主管理實驗,大大激發了學生創新思維和創新意識,讓學生逐漸掌握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提高了學生創新實踐的能力。
隨后,我們對園藝植物開花習性調查和有性繁殖園藝植物的常規品種育種計劃制定等兩個設計性和綜合性的實驗也實行了類似的探究式教學改革,也同樣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二、探究式教學模式提高了教學效果
學生的學習效果是檢驗教師教學效果的標尺。探究式教學模式是對傳統的授予式教學模式的一種改革與補充,它以學生的自主探究為基礎,使學生掌握自主學習的基本方法,形成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并逐步廣泛的遷移到一切學習和生活領域之中,彌補知識轉化為能力的裂隙,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經過2012-2014 年三個學年度的教學改革實踐,園藝植物育種學課程教與學的方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教師的責任由教逐漸過渡到導,引導學生積極思考,拓寬了學生思維,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個人尋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團隊協作能力。學生的學也由主動代替了以往的被動,由以前的要我學變成我要學。真正體現了學生的主體地位老師和學生的平等關系,拉近了師生之間的距離。針對不同的情景問題,學生通過不同的途徑查詢文獻資料,通過小組討論和課堂討論,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總結歸納和口頭表達能力,整個教學過程培養和鍛煉了學生獲取知識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在近3 年的教學改革實踐中,我們還設計了一套問卷調查來檢測探究式教學模式的教學效果,
現將結果小結與分析如下。
( 一) 學生對探究式教學改革整體表示滿意根據對近3 年的調查問卷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2012 年非常滿意的比例是76%,基本滿意的比例是19%; 2013 非常滿意的比例是81%,基本滿意的比例是15%; 2014 年非常滿意的比例是82%,基本滿意的是比例14%。說明同學們對基于問題的探究式教學改革整體表示滿意,而且,隨著實施經驗的進一步豐富和對問題做相應的調整,非常滿意的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 二) 學生認可所凝練的十個情景問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對課程所提出的討論主題的平均滿意度高達92% 以上,說明學生對所凝練的十個情景問題表示相當的認可。出現這一結果的原因是上述情景問題都是據本課程的理論和實驗的教學內容,結合最新的研究熱點和前沿,以及身邊耳熟能詳的現象和事件而設計,因此,獲得高度認可也在情理之中。另外,學生普遍認為討論主題的意義是影響探究式教學成效的最關鍵環節,從重要性的排序為:討論主題的意義 文獻閱讀師生討論生生討論,說明我們在實施探究式教學方法的時候必須十分重視情景問題的凝練,同時,增加學生的文獻閱讀量,加強師生和生生之間的討論也是影響探究式教學的重要環節。鑒于此,我們擬建立一個情景問題庫,將根據學科發展的情況以及學生的實際情況實行動態篩選和匹配,挑選最適宜的討論主題供學生選擇。
( 三) 抽簽產生主講人的小改革極大地促進了學生小組內的討論
根據參加小組討論的情況,以及對近3 年的問卷調查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小組領到討論題目以后,一般由23 個骨干分子領銜查閱文獻和整理研討報告,學生小組討論的方式主要是QQ 群、課間和臥談會等時間開展交流,但面對面的長時間深入討論的機會較少。2012 年問卷調查中選擇交流很多和交流一般的有65%,而選擇交流很少和不交流的比例高達35%; 2013 年選擇交流很多和交流一般的有88%,而選擇交流很少和不交流的比例驟降到12%; 2014 年選擇交流很多和交流一般的有91%,而選擇交流很少和不交流的比例僅9%。2013 和2014 年小組討論時間大幅增加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小組主講代表由臨時抽簽產生而造成的,說明教學改革過程中適時適當地做些細小的程序改正也能顯著提高課程的教學效果,有著四兩撥千斤之功效。
( 四) 學生對探究式教學所需時間有所顧慮對調查問卷進行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有23%的同學認為探究式教學占用了太多的時間,認為占用時間有點多的比例是39%,選擇一般的有33%,僅有5%的人選擇根本不。上述結果顯示,認為需要較多時間的同學約占2 /3,說明我們所設計的情景問題的難易度稍偏難。如何把握設計情景問題的難易程度是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所討論的主題既要涉及學科的前沿,又要難易適中,其標準就是讓學生跳一跳能夠得著就好。通過對本課程的學習,學生全面、系統掌握園藝植物育種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并能應用于分析和解決生產中的有關問題。同時,學生在科學的態度、嚴謹的研究方法方面也得到了訓練,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學生對教師的教學評價連續3 年都在4. 5 分( 5 分制) 以上。
三、問題與展望
改變傳統的教學觀念和教學方法對教師和學生而言都是一個嚴重的挑戰,因為教學雙方都要花時間和精力進行磨合以適應新的教學模式。眾所周知,近年來,隨著寬口徑、厚基礎、重素質教改方向的確立,一些專業課程的課時縮減了很多,園藝植物育種學課程也由原來的84 課時縮減到現在的58 課時,要在有限的時間內把更多的知識教授給學生,必須改變原有的教學方式和教學觀念。通過20122014 三個年度的教學改革實踐,園藝植物育種學課程教學效果有了明顯的提高,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需要在今后的課程教學過程中加以不斷地改正和完善。
( 一) 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開展探究式教學改革
研究表明,不是所有的課程和教學內容都適合探究式教學模式。在本課程的教學過程中,一些基礎育種理論和育種方法還是采用授予式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先具備一定的專業理論知識和技能才能更好地開展探究式的學習和工作。雖然采用授予式教學,但在課上也要適當注意師生的互動,積極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
在理論學習方面,如緒論、育種途徑、引種馴化和選擇育種等內容是植物育種學的基本概念和基礎知識,這些內容適宜采用傳統的教學方式進行授課,重組育種和雜交優勢育種中的后部分內容可以開展探究式教學,而誘變育種、離體育種和分子育種則完全應用探究式教學模式開展教學。在實驗教學部分,基礎性實驗和驗證性實驗一般不適于探究式教學,而綜合性和自主設計性實驗是開展探究式教學模式的主要對象。在課時允許的前提下,今后我們將嘗試將更多的教學內容引入探究式教學模式,從而提高其教學效果。
( 二) 鼓勵學生在課堂上積極提問
和國外學生一有問題就舉手提問的習慣相比,我們的學生在課堂上提問的意愿非常低,不愿意在課堂上主動展示自己的觀點,只有在教師點名的情況下才會回答問題。對調查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產生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有: 學生認為打斷教師不禮貌( 22%) 、怕耽誤大家的時間( 20%) 、怕別人笑話自己問題太簡單( 12%) 、以上都是( 46%) 。因此,在課程教學開始,我們首先要培養學生的提問意識,不斷向他們灌輸上課打斷老師講課是認真聽課的體現的思想,打消他們不敢提問的顧慮,實現課堂上更好的師生互動,從而不斷提高課堂的教學效果。
( 三) 需更加合理地安排小組間的交流與班級研討時間
篇10
線粒體DNA非編碼區由兩個tRNA基因分離,D-loop區域就處在這個非編碼區中[2]。在線粒體DNA中,D-loop區是重鏈和輕鏈的復制起點,也稱之為“控制區ControlRegion”,其進化壓力較小,是線粒體DNA基因組序列和長度變異最大的區域,Horai等[3]發現該區域的基因變化速度比細胞核DNA和其他細胞器的基因快5倍,同時也是進化最快的部分。因此,選擇D-loop區作為鑒定種群遺傳狀況的分子標記直接有效。利用D-loop的序列在群體遺傳學上進行分析的工作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展開了,那時候僅僅用于分析區域內種間的親緣關系。現今,D-loop區已經廣泛被用作非常高效的工具來推斷不同區域內種間或種內的親緣關系和遺傳狀況。D-loop區中仍然細分為3個部分,中央保守區、終止序列區和保守序列區。其中終止序列區包含了線粒體DNA終止復制的相關序列,是變異最大的部分[4],最具研究和分析價值。在進行數據結果分析時,由D-loop序列分析得到的單倍型多樣性指數和核苷酸多樣性是兩個評價群體遺傳資源或者群遺傳多樣性的重要指標。
1.1野生群體遺傳多樣性分析
1.1.1D-loop部分序列分析D-loop序列分析中,由于并不是整個D-loop序列都發生堿基的插入或者替換,可以采取對保守序列區或者終止序列區的部分區域進行擴增。由于這兩個部分的進化比中央保守區迅速得多,只對這一區段的序列進行分析也能代表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和進化過程。張仁意等[5]對青海4個不同湖水采集的155尾裸鯉(Gymnocyprisprzewalskii)個體的線粒體DNA的D-loop區中部分序列進行擴增,得到754bp的序列長度,分析發現155個樣本中有34個單倍型,但4個群體中可魯克湖群體的單倍型多樣性和核苷酸多樣性遠低于其他種群;進一步的遺傳分化系數的分析表明,該地區已經產生一定的遺傳分化,但由于地理隔離的原因,系統發育樹結果還沒有發展出明顯的單枝,加之該區域群體的遺傳多樣性偏低,需要進行重點保護。
鄭真真等[6]對全球大青鯊(Prionaceglauca)進行了D-loop區中694bp擴增分析,采集了來自中東太平洋、中西太平洋、中東大西洋、西南大西洋和印度洋5個海域的165尾個體,分析發現145個單倍型,變異程度非常大。進一步分析后發現5個區域的大青鯊種群的單倍型和核苷酸都處于較高水平,種質資源較好;但是遺傳分化指數顯示5個區域存在強烈的基因交流,種群遺傳分化水平較低。鄒芝英等[7]采集了8尾長鰭鯉(Cyprinuscarpiovar.longfin),擴增得到600bp的部分序列,找到了與終止區域相關的6個特征序列;對這些特定的區域分析得到6個單倍型,13個變異位點,顯示了較好的種質資源狀況,核苷酸多樣性數值與其他魚類接近,遺傳狀況中等,由于該物種稀有且僅存在偏遠地區,保護珍惜水產動物資源已經迫在眉睫。向燕等[8]為了了解3種鱘魚:達氏鱘(Acipenserdabryanus)、中華鱘(A.sinensi)和史氏鱘(A.schrencki)親魚的遺傳狀況和遺傳背景,對線粒體D-loop區部分序列進行分析,擴增得到400bp的序列,49尾親魚個體一共得到僅18個單倍型,并且對于單倍型系統發育樹分析后,發現集中在6個單倍型中,說明這些群體很有可能來自同一母親;不過各單倍型遺傳距離較遠,說明父本來自不同的個體;其結果提示,在生產中仍要采用不同單倍型進行人工繁育,以避免近親而導致種質退化。
Kumazawa等[9]研究發現,D-loop的5'端和3'端有串聯重復序列,這段的變異速率較快。Abinash等[10]在北美不同區域采集淡水扁頭鯰(Pylodictisolivaris),對35bp的串聯重復區進行分析檢測,從美國35個水系采集了330尾樣本,分析結果發現,在東南墨西哥灣的70%樣本出現串聯重復的變異,而采自密西西比河95%的樣本和墨西哥灣西南沿岸的扁頭鯰沒有出現這個區域的變異;系統發育的計算結果表明,在70萬年和205萬年左右出現群體分流;從地理位置上看,密西西比河的支流進入墨西哥灣西南沿岸流域,而東南墨西哥灣為另一條流域;該結果表明種群的遺傳結構受到地域特殊性的影響。D-loop區部分序列的結果分析能滿足一定程度的遺傳多樣性和遺傳狀況分析,可以得到可靠的結果數據幫助人們進行資源保護和簡單的育種工作。隨著科技進步和測序水平的改善,進行全序列的測序漸漸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全長序列將獲得更加完整和正確的結果。
1.1.2D-loop全序列分析D-loop的多態性一種是來源于堿基的突變、插入和替換形成的不同單倍型,不僅種間有差異,種內個體間也存在差異,只是重復的差異小于種間的差異。而且在個體中D-loop一旦發生差異,線粒體DNA會穩定地將這種差異遺傳下去,這種差異在個體間表現為線粒體DNA分子的長度變異,因此對D-loop全長進行分析研究更能體現整體的變異程度。肖明松等[11]在淮河淮濱段、鳳臺段、蚌埠段、洪澤湖段采集84尾野生烏鱧(Ophicephalusargus)進行種群資源的研究,分析發現33個單倍型,檢測了單倍型多樣性(h)、核苷酸多樣性(Pi)、遺傳分化指數(Fst)、遺傳距離以及中性檢驗、錯配分析和NJ樹,發現其h和Pi較高,表明種群平均多態性相對較好;但在遺傳距離的分析中發現所有群體的差異都較小,這可能是由于在淮河流域中不同支流的種流程度較高造成的,所以變異發生在種內,而種群之間的分化較少。董志國等[12]對大連、東營、連云港、舟山、湛江和漳州6個地區的野生三疣梭子蟹(Portunustritubercatus)進行D-loop全基因組區的遺傳多樣性及群體遺傳結構的分析,選擇單倍型多樣性和核苷酸多樣性作為重要指標,并加入了群體遺傳分化指數的分析,進行Tajima’sD中性檢驗和單倍型間的分子變異分析,發現不同地區梭子蟹的遺傳多樣性很高,產生一定的遺傳分化;不過在系統發育關系分析中,地理距離對遺傳距離沒有顯著的關系,原因仍需要進一步研究。趙良杰等[13]在千島湖汾口、富文、臨岐3個大眼華鳊(Sinibramamacrops)主要繁殖區域采集了115尾個體,對樣品進行了形態學和D-loop序列測定后,分析形態主成分和各個基因遺傳學分析指標,發現千島湖各地的大眼華鳊之間有豐富的基因交流,并沒有形成容易滅絕的小種群,表明各個地理群體仍然有豐富的遺傳多樣性,面對一定的災害時有一定的彈性,不過這樣的良好狀況仍然需要政府和漁民對該區域的種質資源進行保護。高志遠等[14]對海南松濤水庫南豐鎮、番加鄉、白沙群體的長臀鮠(Cranoglanisbouderius)的D-loop序列全場進行分析,44尾個體中發現11個單倍型,但在分析中發現單倍型較高,而核苷酸多樣性較低,認為是由于海南島偏僻的地理位置難與大陸長臀鮠進行基因交流,推斷在歷史中可能出現過嚴重的瓶頸效應;中性檢測也表明沒有任何整體或局部的種群擴張,數據皆表明該地域長臀鮠正處在較危險的境地,需要進行種群的保護措施。
1.2養殖群體遺傳多樣性分析目前,國內對水產動物養殖過程中出現的生長不良與病害頻繁大多歸結于飼料與環境的問題。誠然,營養和免疫是養殖的關鍵,但是由于人工育種和繁育雜交造成的種質資源下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養殖戶往往在育種過程中,沒有考慮到育種群體的遺傳狀況,導致近親雜交,子代產生各種問題。徐鋼春等[15]對灌江納苗養殖刀鱭(Coilianasus)的子三代品種與在淡水生活環境下湖鱭(C.nasustaihuensis)兩個群體的遺傳多樣性進行了比較和分析,進行單倍型和核苷酸分析后,發現養殖刀鱭的遺傳多樣性要優于湖鱭,這可能是由于刀鱭僅是子三代,還未經歷大量的人工繁殖和育種,保留了較好的遺傳狀況;而湖鱭由于其陸封型的特點,導致其種質資源漸漸下降,需要進行放流等活動保證種質資源。姚茜等[16]對來自浙江湖州某公司的養殖群體、緬甸引進的群體和兩者雜交的“南太湖1號”群體的羅氏沼蝦(Macrobrachiumrosenbergii)的D-loop區進行分析,共16尾群體分析得到14個單倍型,結果表明緬甸引進的群體核苷酸多樣性最高,浙江湖州人工養殖群體的多樣性最低,說明人工育種對遺傳多樣性有較大的影響。通過遺傳距離和遺傳分化指數分析發現,雜交群體更加偏向本地種群。在今后的育種工作中,可在雜交代中選取優秀性狀的沼蝦,與緬甸種群雜交,以獲得更優秀的品種,為今后的人工繁育打下基礎。李勝杰等[17]將珠江水產研究所養殖品種大口黑鱸(Micropterussalmoides)與北方和佛羅里達兩個野生群體進行D-loop區的遺傳分析,在23尾采集的樣品中,5尾個體含有兩種單倍型,北方11尾個體發現9種單倍型,而佛羅里達僅有1種單倍型。在遺傳距離分析上發現,珠江水產研究所的養殖群體與北方群體更加接近。對于單倍型多樣性和核苷酸多樣性分析,結果表明養殖群體與國外種群相比,其遺傳多樣性處于較低水平,需要開展種質的保護工作,應引入國外品種進行雜交,改善國內養殖群體的遺傳結構,提高遺傳多樣性,豐富大口黑鱸的種質資源。
1.3親緣與起源分析D-loop區串聯重復的現象雖然豐富,但是不同動物的重復位置不一致,重復的序列和重復的單元也不一致,所以相近物種之間對比分析有助于明確不同物種的關系。郝君等[18]對烏克蘭鱗鯉(Cyprinuscarpio)、鯽(Carassisauratus)、鰱(Hypophthalmichthysmolitrix)、鳙(Aristichthysnobilis)、草魚(Ctenopharyngodonidellus)和烏蘇里擬鲿(Pseudobagrusussuriensis)6種不同魚的線粒體D-loop區進行測序,分析了種內、種間遺傳結構差異,發現作為分子標記對系統分化效果的差異,6種不同魚的堿基含量、堿基差異、遺傳距離和系統發育都有顯著的差異,構建的D-loop序列的NJ系統樹展示了6種魚的分類地位,肯定了D-loop區比鄰近區段的tRNA和12sRNA在魚類識別、分類、種類鑒定和遺傳多樣性分析上更加可靠。侯新遠等[19]對5種蝦虎魚類進行了系統進化關系的研究,分析了河川沙塘鱧(Odontobutispotamophila)、鴨綠沙塘鱧(O.yaluensis)、中華沙塘鱧(O.sinensis)、葛氏鱸塘鱧(Perccottusglenii)及尖頭塘鱧(Eleotrisoxycephala)這6種蝦虎魚類同源長度約為830bp的D-loop序列,通過系統發育樹和遺傳距離分析,得到6種魚類的親緣關系即河川沙塘鱧、鴨綠沙塘鱧、中華沙塘鱧、平頭沙塘鱧聚為一支,尖頭塘鱧、葛氏鱸塘鱧和褐塘鱧等聚為另一支,為魚類資源的分類和利用提供了基礎。馬波等[20]在額爾齊斯河采集了兩種類型的銀鯽(C.auratusgibelio),對幾種鯽魚的可量性狀和D-loop區進行分析,得到了優勢種群的生長性狀,確定了它們的遺傳學特征和分類學地位,同時通過D-loop區的單倍型共享率研究了兩種鯽的起源和遺傳特征,這些結果對我國將來進行銀鯽育種有很大幫助。Klaus等[21]利用D-loop序列對歐洲鯉魚(C.carpio)137的起源進行研究。在此之前對于歐洲鯉魚也有過很多關于起源的研究:Zhou等[22]發現一些歐洲養殖的鯉魚起源可能在德國和歐洲,而俄羅斯主要養殖的鯉魚起源在亞洲。Zhou等[23]在德國鏡鯉和伏爾加河的野生鯽魚利用D-loop區全序列獲得獨特的3種單倍型;而Mabuchi等[24]在日本鯉魚中發現有兩個D-loop區單倍型與Zhou等報道的歐洲發現的單倍型非常相似。Klaus等[21]的研究結果指出歐洲和中亞所有的鯉魚品種有一個共同的祖先,而且有可能是在后冰河時期傳播到中亞或者歐洲。對于這種現象,可能是由于在育種過程中,沒有進行規范的養殖記錄,導致各種群出現雜交現象。而且,養殖戶挑選具有優勢性狀的品種進行,容易導致其他稀有單倍型的消失,從而使得種質資源慢慢下降。
1.4個體內異質性分析同一個體內存在多種重復序列數目不同從而表現為異質。高祥剛等[25]采用克隆技術,在我國海域隨機采集了3頭斑海豹(Phocalargha),每尾個體任選14個克隆菌,對它們的線粒體DNAD-loop區的終止序列區進行擴增測序,發現其個體內存在多種不同的串聯重復單位,即存在異質現象,說明我國的斑海豹種質資源保護較好,進化狀態比較積極。張四明等[26]在野生的中華鱘種群種間和個體體內檢測線粒體DNA的長度變異情況,發現中華鱘有較多個體的異質性,表現出良好的遺傳多樣性。由此可見,個體的異質存在是導致線粒體DNA中控制區D-loop長度變化的主要原因,而個體的線粒體DNA長度異質性是直接推動動物物種遺傳多樣性的重要途徑。綜上所述,可以發現線粒體D-loop區的序列分析已經在水產行業取得大量進展,D-loop區基因的插入、突變和替換都是影響多樣性的關鍵,而個體內的異質和串聯重復的高頻率變化不僅存在于水產動物個體中,也存在于種群內,甚至在不同物種之間都對野生水產動物的起源、親緣關系、遺傳多樣性、遺傳結構和動物進化程度起著重要的作用。在養殖群體中,D-loop區的分析正在漸漸起到重要的作用,若結合微衛星、RFLP等其他分子標記技術,將來對人工育種和對親魚、親蝦的選育工作有重大意義。
2細胞色素b序列(cytb)
線粒體DNA中編碼蛋白質的基因有還原型輔酶I的亞基、ATP合成酶的亞基、細胞色素c氧化酶的3個亞基和細胞色素b[27]。Zardoya等[28]研究認為,cytb的進化速度適中,適合進行種內和種間的遺傳分析。現今利用cytb序列多數用于種內和種間的遺傳分化分析、遺傳圖譜建立和遺傳多樣性調查,并輔以其他標記技術進行組合分析。王曉梅等[29]獲取中華絨螯蟹(Eriocheirsinensis)cytb序列的PCR產物后,利用DGGE技術分析了溫州、儀征、江都、南京、盤錦和合浦地區的中華絨螯蟹的遺傳多樣性,并與合浦絨螯蟹(E.japonicahepuensis)對比,發現中華絨螯蟹與合浦絨螯蟹遺傳距離較大,在親緣關系上具有顯著的差異,但是仍有部分遺傳標記相同,說明存在一定的基因交流。
黃小彧等[30]利用cytb序列檢測了長江支流貴定與干流合江和宜都的中華倒刺鲃(Spinibarbussinensis)群體的遺傳多樣性,分析群體的遺傳距離,結合地理因素分析了該物種的種質資源現狀,發現合江的遺傳多樣性最好,而支流群體與干流群體的遺傳分化較大,地理隔離使同一物種的基因交流程度降低。夏月恒等[31]利用cytb序列對中國近海3個地區的鮸魚(Miichthysmiiuy)的遺傳多樣性進行分析,通過對地理環境和歷史因素的解釋,認為中國鮸魚基因型的單倍型多樣性高和核苷酸多樣性低可能是因為種群在某個時期突然擴張,使單倍型突變大量產生,但這段時間對于提高核苷酸多樣性時間不足,所以產生了如此差別;且Fst結果極低,說明該地區遺傳分化程度很低,加上不同地理的單倍型網絡圖交錯呈現,有可能是因為種群由于擴張之后還未達到平衡,需要對該地區進行保護。鐘立強等[32]調查了長江中下游5個湖泊的黃顙魚,利用cytb序列分析了不同地區遺傳多樣性和遺傳分化的程度,60尾個體檢測出37個單倍型,Fst分析顯示這5個種群的變異大部分都來自群體內,說明各個種群間有一定的基因交流,系統樹顯示它們沒有分化成譜系。司從利等[33]從長江貴定和樂山兩個群體的泉水魚cytb序列分析其遺傳狀況、結構和多樣性程度,發現這兩個群體由于三峽大壩的地理因素,已明顯受到嚴重的影響,出現高度的遺傳分化,建議對該物種進行分區保護,提高遺傳多樣性,豐富種質資源。
司從利等[34]在廣東、廣西等地基于cytb序列分析了華南居氏銀魚(Salanxcuvieri)的遺傳現狀,從鄰接樹上可發現有一定的分支,認為地理因素正在逐漸影響遺傳結構,推測瓊州海峽的地理位置可能影響廣東、廣西種群間的遺傳交流;中性檢測結果表明在更新世晚期發生擴增,地球當時的氣候影響了該種群的遺傳多樣性;根據現狀,建議分地區對該種群進行人為保護,避免出現種質退化。李偉文等[35]兩年中在7個遠洋捕撈點采集了黃鰭金槍魚(Thunnusalbacares),擴增了cytb部分序列得到663bp,108尾個體僅有24個單倍型,且單倍型多樣性和核苷酸多樣性都處于較低水平,群體的遺傳多樣性較差;Fst分析得到變異大多發生在群體內部,表明其遺傳分化程度較低,并且基因交流非常強烈,種質資源正在衰退,這與人類破壞環境和大面積捕殺有密切關系。謝楠等[36]利用cytb對魴屬(Megalobrama)4種魚類及長春鳊(Parabramispekinensis)進行了系統分類。但在結果分析過程中僅靠cytb的信息難以準確將不同品種進行區分,仍需要配合其他標記進一步研究。
3其他標記與組合分析
16SrRNA序列、12SrRNA序列和COI序列在線粒體基因組中變異速度較慢,保守性較高,因此很難由其單獨作為驗證工具來進行遺傳分析,往往需要結合其他的基因片段,才能同時作為鑒定種內親緣關系和物種遺傳多樣性程度的工具。劉萍等[37]選取了山東青島中華虎頭蟹(Orithyiasinica)野生群體的16SrRNA和COI基因片段研究其遺傳多樣性,但是發現16SrRNA變異程度較小,效果不佳;在遺傳距離和系統進化研究中,兩種技術檢測了不同蟹之間的親緣關系以及它們的進化分化時間,利用NJ系統進化樹發現中華虎頭蟹與梭子蟹類的親緣關系最近,并采用“分子鐘”對4個蟹類的分化時間進行計算。吳玲等[38]對沿海6個群體的白氏文昌魚(Branchiostomabelcheri)和日本文昌魚(B.japonicum)分別進行COI和16SrRNA序列的研究,發現兩種魚種內遺傳多樣性較高,但還沒有明顯的遺傳分化;其中茂名群體和威海群體具有最高的核苷酸多樣性,很有可能為這兩類魚的祖先。
翁朝紅等[39]對近江蟶(Sinonovacularivularis)、縊蟶(S.constricta)、小刀蟶(Cultellusattenuatus)、尖刀蟶(C.scalprum)和大竹蟶(Solengrandis)的COI和16SrRNA部分序列進行測序和分析,在進行遺傳距離和系統演化分析后,結果表明近江蟶已進化至獨立為一個種,并且通過聚類分析推斷近江蟶應歸屬于竹蟶超科,解決了這幾種蟶分類歸屬。郁建鋒等[40]結合12SrRNA和16SrRNA的序列為太湖流域河川沙塘鱧的分類提供了重要的幫助,發現了大量的變異位點和簡約位點,而且在兩種標記的驗證下,比較得出太湖流域河川沙塘鱧與福建流域河川沙塘鱧已經存在一定的遺傳差異。同時,系統發育樹分析表明,太湖流域河川沙塘鱧與其他鱧已存在遺傳分化差異。王慶容等[41]對長江中上游舞陽河、烏江、雅礱江、岷江和金沙江5個野生鲇(Silurusasotus)群體的親緣關系和遺傳差異進行了分析,對比了核苷酸和單倍型多樣性,發現舞陽群體與其他群體的親緣關系較遠。楊慧榮等[42]同時利用D-loop和cytb的序列對長江水系的赤眼鱒(Squoliobarbuscurriculus)進行了遺傳多樣性的分析,通過遺傳變異率、單倍型多樣性等指標發現長江赤眼鱒遺傳多樣性較高,種質狀況較好;同時,根據Fst和分子變異等級差異分析發現,不同水系的群體存在明顯的遺傳分化;系統發育樹證明了珠江水系赤眼鱒與長江水系赤眼鱒正在逐漸分化為兩類群體,并提出cytb序列在變異顯著的群體間更能發揮作用。
孫希福等[43]利用cytb序列和D-loop序列分析了江豚(Neophocaenaphocaenoides)在鼠豚類及一角鯨類的分類地位,系統發育樹表明,江豚的遺傳距離與一角鯨科較為接近,并確定棘鰭鼠海豚、太平洋鼠海豚及黑眶鼠海豚3種群有較近的親緣關系,否定了之前僅憑借形態學的分類方式。畢瀟瀟等[44]在某一水產品公司采集了來自美國與荷蘭的狹鱈(Theragrachalcogramma)、太平洋鱈(Gadusmacrocephalus)、藍鱈(Micromesistiuspoutassou)和遠東寬突鱈(Eleginusgracilis)4種不同屬的鱈魚,利用16SrRNA、cytb和COI序列比較了它們的序列結構,根據核苷酸分歧速率以及NJ系統發育樹,將太平洋鱈、狹鱈和寬突鱈歸為一支,也顯示了它們較接近的遺傳距離,給分類學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論基礎。
4展望
線粒體分子標記技術主要用于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分析、親緣、親權分析和物種進化程度分析。該基因組功能重要且能穩定遺傳,是物種個體基因組中變化速度較快且保留較好的部分。對D-loop區的序列進行測序、比對、計算和分析后能得到物種的種屬分類、遺傳結構、歷史發育情況和遺傳多樣性狀態。而且,D-loop區穩定的母系遺傳,使得分析起源有較好可靠性,聚類分析結果準確。同時,細胞色素b和16SrRNA等序列雖然進化速度較慢,但其穩定性的特征可以得到較好保留,獲得的插入、替換和缺失等突變可以持續遺傳,以作為數據分析的可靠依據。在進行不同情況的分析時,可以結合一到兩種分子標記技術,作為重要的輔助參考標記。
綜上,在水產行業的遺傳分析中,野生群體的遺傳多樣性是將來進行育種和引進的關鍵,通過線粒體分子標記技術對野生經濟水產動物的遺傳結構和遺傳多樣性分析是高效、準確和可靠的。其中單倍型多樣性和核苷酸多樣性表現了分子結構的變異程度,體現了野生群體種質資源的現狀;遺傳分化特征能表現群體的基因交流狀況,表明了群體間自由的自由度;分子變異等級分析可以讓我們了解不同地域群體突變的來源,表現了群體遺傳結構的差異;中性檢測等分析從分子層面揭示了魚類的系統發育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