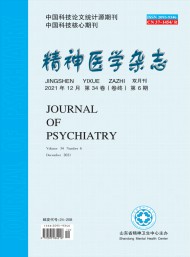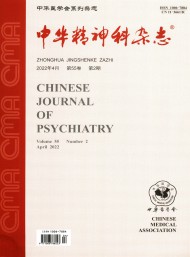精神科檢查報告范文
時間:2023-03-19 22:52:48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精神科檢查報告,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1.前言
精神科護理不安全事件難免發生,不僅給患者及其家屬造成痛苦,而且影響醫院的正常工作秩序,還給醫護人員的自信心帶來危機。針對精神科護理風險管理中的不安全事件開展品管圈活動,精神科護理部的醫護人員組成品管圈活動小組,以控制不安全事件發生率為目標開展品管圈活動。
2.資料與方法
2.1 一般資料
我院2016年間精神科共有86名病患,病區共有護士23名,其中主任護師1人,副主任護師2人,主管護師2名,護師5名,護士13名;年齡20~42歲,平均年齡(29.3±5.4)歲。
2.2 方法
2.2.1 組織團隊并選定主題。由精神科護理部的23名護理人員組織品管圈活動,圈長由主任護師擔任。針對2015年全年精神科護理質量報告中不安全事件發生率較高的結果,確定以“控制精神科護理風險管理中不安全事件發生率”為品管圈活動主題。
2.2.2 實施對策品管圈活動。每周由圈長安排進行1次,每次活動可由不同的品管圈成員主持,大家互相交流護理心得、工作過程中遇到難題,共同討論解決方法以及檢驗方法的實施效果、討論方法改善措施。對2015年全年護理質量檢查報告的總結中發現,精神科護理中精神衛生知識缺乏、安全防范工作不完善以及心理o理不到位這三個問題引起的不安全事件比較嚴重,特針對這三個方面制定改善措施。
2.2.2.1 加強學習,提高認知。雖然精神科護士都收到過專業知識、技術的教育與訓練,但由于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精神衛生知識的不足以及在精神病區工作的醫護人員得不到社會正確的理解與支持,部分精神科護理人員難免會認為精神科護理只不過是簡單的看管,沒有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品管圈小組在每次活動時,專門預留30min至1個小時的時間開展專業知識培訓,可由不同成員以PPT或書面報告的方式進行,講解精神科護理的技巧、案例或行業進展等,不僅提升護理人員自身的專業認知,而且使大家保持工作積極性。
2.2.2.2 安全管理,防范風險。通過制定相應的安全管理措施和培訓提高醫護人員的安全意識,具備意外事件的應急能力,降低不安全事件的發生率或嚴重后果。安全管理措施包括病房、病區內危險物品、各個病人精神狀況特點等,向病人及其家屬進行安全宣傳,讓家屬協助觀察、發現病人的不安全行為。對精神科護士進行自身安全防護培訓,對有攻擊或嚴重自殺危險的患者應掌握接觸技巧和防范技巧等。
2.2.2.3 重視心理護理,提高護理質量。護士在護理過程中使用文明禮貌的語言和關心的態度滿足病患希望受到尊重的心理,容易克服患者緊張、情緒不穩定的心理狀態。督促患者按時檢查,向患者家屬說明病情、疾病對身體的危害以及預防措施等,希望患者及其家屬對觀察治療和緊急處理能夠積極配合。在與患者交流過程中注意傾聽,學會有原則的妥協;保持溫和的態度,不要頻繁變動;注意溝通技巧,不要問敏感的話題。
2.3 效果評價
統計品管圈活動組織期間不安全事件的例數并計算發生率,與2015年護理質量報告中的不安全事件發生率進行比較。
2.4 統計學處理
以SPSS19.0軟件包進行數據分析,P
3.結果
開展品管圈活動后,由于護理人員、護理設施或病患引起的不安全事件發生率由2015年的30.59%降低到2016年的5.88%,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4.討論
近年來,精神疾病診療水平不斷提高,護理模式正朝著社會-醫學-心理模式轉變。品管圈即品質管理圈,成員可自發進行品質管理活動,從整體上提高工作質量。目前,品管圈活動已經在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的醫療機構廣泛開展,并收獲了滿意的效果。
品管圈活動在精神科護理工作中具有較高的應用價值,本研究結果顯示,我院精神科開展品管圈活動后,護士常規操作合格率、護士精神疾病知識考核優秀率、護患溝通合格率明顯上升(P
品管圈活動可提高基層護理人員參與管理的意識,激勵護理人員釋放潛能,提高集體凝聚力,也能提升護理人員解決問題的能力,最終提高精神科服務質量,減少護理風險。本研究品管圈活動中,應用人性化應用溝通技巧,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精神病患者對護士的抵觸感,降低護理難度;加強職業教育,強化查對制度可提高護士職業技能及應急能力;學習新知識、新技術可提高護理人員業務水平及綜合護理,幫助提升精神科護理質量,最終幫助醫院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
5.結束語
精神科護理是一項比較特殊的護理工作,精神病人,特別是重癥精神病患者由于其思維、情感、意志、行為常處于幻覺、妄想之中,加之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有明顯的藥物副作用和鎮靜作用,導致某些行為不能自控也不計后果或因患者感覺遲鈍,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安全事故。品管圈護理重在調動成員積極性,強化各級護理人員的管理意識,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提高護理質量,使護理工作更加完善。
參考文獻:
[1] 盛彩華.精神科護理安全論析[J].當代醫學.2016(10):60-62.
篇2
檢查結果大致正常,心電圖稍有異常,但屬于不能說明什么問題的那種。隨口問:“你哪里不舒服?”她答:“胸悶,老想嘆口氣才舒服。”問:“你什么情況下會悶?”她說不清。
我問她:“你工作壓力大嗎?”她愣了一下。一看就是典型勞動婦女,衣服都是打粗穿做粗工的。我耐著性子換個問法:“你干活嗎?”“干。”“什么活?”“我賣廢品,收鋼鐵。”我愣了一下,女人收鋼鐵?厲害。
她局促地坐在我面前,頭發濃黑,梳得整整齊齊,只是額頭有一縷突兀的白發,五官挺端正,也沒有什么皺紋,不大看得出年齡――我瞟一眼電腦,顯示54歲,只有一雙手是吃過許多苦的樣貌:粗大,滿布裂紋和傷疤,指甲沒有修剪,里面還有黑垢。
我本來是想問她干活時會不會胸悶,突然發現她在不斷抹淚,不像哭,只是眼淚一直涌出來。我以為她擔心病,寬她的心說:“怎么了,還沒得病呢,不用急。哭什么?是眼睛不好嗎?”她邊搖頭邊擦淚:“不知道,只是眼淚自己就流出來了,總是這樣。”
我正想再問點兒問題,進來一個男人,滿臉皺紋,個子矮矮的,站在她身邊。我第一反應是她父親,又覺得不像,問他:“你是……”她答:“我男人。”我語塞。也太不般配了,不管年齡還是相貌,我還是客氣地沖他點點頭,說:“你愛人可能心臟有點小問題。”他沒搭理我,也沒搭理她,自顧自走了出去。我同情地問她:“是你后老公嗎?”她搖頭。還在揩那止不住的淚。
我知道,她的胸悶多半不是心臟問題,只是心理問題。別的病人都已走光,還有時間,我把筆和檢查報告扔在一邊,看著她,試探地問:“干活累嗎?”她搖頭。“孩子好嗎?”她點頭。我索性不再問她,自己說:“我不是精神科醫生,但我覺得你的病是心病。你也許會承認,也許不愿意承認,但心結總在那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你自己應該知道,要么接受并忍受,要么試著去改變,要么……”我忽然說不下去了,心病就像生活中的其他疾病一樣,不會無中生有,一定有所緣由,可是,要用什么辦法才能解決掉那些緣由呢?
那男人晃進來,看看她,也不說話,又晃了出去。
她突然開了口,壓抑著,小小抽搐了一下:“我只是感覺不到愛,從來沒有人愛。”
我震了一下,這種文學腔的語言,我一直以為只有那些養尊處優、不識生活艱難的女人才說得出來。再一想:無論貧與富,貴與賤,女人都是女人呀。不是因為她底層勞動,她五十多,她就不應該有愛的渴望。
我心疼她。想問:難道你的孩子不愛你嗎?又想,她要的愛應該不是這個。想安慰她,覺得語言真是蒼白。
篇3
【關鍵詞】 軀體形式障礙;流行病學方法;患病率;人口學特征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in the People Aged 18 and Older in Hebei Province. Cui Lijun, Li Keqing, Jiang Qinpu, et al. HeBei Mental Health Center, Baoding 071000,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in Hebei Province. Methods From Oct.2004 to Mar.2005, Stratified multi-stage cluster randomization was used to identify 24,000 subjects who are 18 and older in Hebei Province. An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dentify subgroups of subjects at high, moderate and low risk of having a mental disorder, then psychiatrists determined their diagnoses by administering a structured psychiatric examination (SCID) that employs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Fourth edition. DSM-Ⅳ). Results 20,716 subjects completed the screening, prevalence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was 6.92‰ (95%CI=5.79‰~8.05‰). Somatization 0.48‰, pain disorder 3.86‰, unspecified somatoform disorders 1.57‰, hypochondriasis 1.02‰; The prevalence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in rural (7.55‰)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urban areas (2.62‰), the prevalence of somatoform in wome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men(1.87‰), P
【Key words】 Somatoform disorders; Epidemiologic; Prevalence; Demology characters
近年來,軀體形式障礙受到臨床醫學、精神病學及臨床心理學的普遍關注,國外已見有關軀體化障礙或疼痛障礙患病率的報道[1-4],國內有數個關于軀體形式障礙在綜合醫院的調查[5,6],但國內外有關此癥患病率的大樣本調查較少見,為此,我們于2004~2005年進行了河北省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現就有關軀體形式障礙的患病率及相關因素分析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樣本大小的確定 根據河北省經濟年鑒2003[7],將地級及以上城市確定為城市框架,共11個;縣或縣級市確定為農村框架,共137個。根據國外相關資料[8],估計我省精神疾病總時點患病率為15%左右,期望調查的精確率達到1%,由此所需樣本量約20000人。考慮到城市與農村、不同性別及不同年齡段需進行分層分析及個別精神疾病患病率低等因素,將樣本確定為24000人。
1.2 框架樣本的確定 按隨機原則抽取11個地級城市的4個框架區域,具有在地理、人口、經濟等方面的代表性。按照4個行政區劃的總人口比例分配24000樣本,共抽取城區12個;縣(縣級市2個)11個。其中居委會28個、鄉鎮40個、147個村,覆蓋框架人口915.55萬,占河北省總人口的13.59%。
1.3 抽樣方法 采用多階段、分層、整體隨機抽樣方法進行抽樣,年齡為18歲及其以上人群。根據樣本大小,按不同城區從公安分局中隨機抽取1~2個派出所,根據每個派出所所轄居委會,隨機抽取1~3個居委會。鄉鎮抽樣:本次調查將縣城作為1個鄉鎮計數,首先將該縣所有鄉鎮排列,采用隨機數碼表抽取該縣1/5所轄鄉鎮,再根據鄉鎮所轄人口,按人口比例確定該鄉樣本量,然后根據該鄉樣本量確定所抽行政村數,每村根據人口數量抽取樣本100~200人。
1.4 樣本個體的抽取 根據當地公安部門提供的人口學資料計算出該抽樣點(村、居委會)18歲以上成年人的總人口數,按出生日期排列,并按該抽樣點樣本數計算抽樣間隔,按抽樣間隔隨機抽樣。在全省范圍內共抽取樣本24000人,其中農村框架樣本20696人(86.23%),城市框架樣本3304人(13.77%)。其人口學特征與全省近似[7]。實際完成調查20716人,完成率86.32%,其中男10303人(49.9%),女10373人(50.1%)。共脫落3284人,脫落率13.68%。
1.5 替代樣本 由于各種原因,調查時的樣本連續3次無法找到定為樣本脫落,進行樣本的替代;替代方法:以性別一致,年齡±2歲為原則進行替代;最后主樣本完成14734人(61.39%),替代樣本完成5982人(24.93%)。
1.6 調查工具和診斷方法 調查工具采用改編后的一般健康問卷12項(GHQ-12)為本次調查的篩選工具[9],以《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Ⅳ)為診斷標準;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研究所翻譯、北京回龍觀醫院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室修訂的《DSM-Ⅳ-TR軸Ⅰ障礙定式臨床檢查》病人版(SCID-I/P)為本次調查的診斷工具[10]。根據被調查者GHQ總得分,把被調查者分為高危人群、中危人群、低危人群3類。根據2004年9月在保定市市區抽取600人樣本,農村抽取1000人樣本進行預試驗,按預試驗調查結果確定三段危險人群的分界分:GHQ≥4分者屬于高危人群,100%進行SCID-I/P檢查;2~3分屬中危人群,約40%需進行SCID-I/P檢查,0~1即屬低危人群,10%需進行SCID-I/P檢查。改編后的GHQ-12其分數及內容不變,另外增加8個問題均為高危因素,并進行SCID-I/P檢查。
1.7 調查人員 參加本次調查的調查人員均來源于現在河北省內市級以上精神病專科醫院工作的醫生和護士,在正式調查前于2004年9月在保定進行了為期1個月的培訓,共有27名護士、42名醫生參加,所有醫生SCID診斷取得了良好的一致性,Kappa=0.88。最后25名護士、34名醫生參加了本次流行病學的正式調查。河北省精神疾病流調組的有關人員作為領隊負責做好有關聯絡、協調、組織管理和總質量控制等工作。
1.8 統計分析 所獲資料在EPI Data下采用雙人雙重錄入計算機,轉入SPSS 11.0進行數據合并,合并為總數據庫后,進行邏輯糾錯,最后在SPSS 11.0下進行統計分析。
2 結 果
2.1 各種軀體形式障礙的患病率 在調查的20716人中,共發現各種軀體形式障礙患者111例,原始患病率為5.34‰,按高、中、低危險因素調整后患病率為6.92‰,95%可信限為5.79‰~8.0‰,見表1示,4種不同軀體形式障礙的患病率以疼痛障礙的患病率最高。
2.2 患病率的性別、城鄉、年齡比較 見表2、表3示總的軀體形式障礙的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農村高于城市,有顯著差異;各種類型女性均高于男性,男女比例為1:6.36;城鄉比較僅疼痛障礙的患病率農村高于城市,其他類型未見差異。從年齡的特點來看軀體形式障礙以40~60歲患病率最高,疼痛障礙以此特點為主,而疑病癥以40~49歲為常見。
2.3 軀體形式障礙患者的相關因素分析 見表4、表5示,軀體形式障礙患者女性多見,讀書年限較常人少,其他未見差異;通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影響患病的危險因素有:年齡30~39歲(OR=2.31;P<0.01),年齡40~49歲(OR=3.83;P<0.001),年齡50~59歲(OR=2.79;P<0.01);保護性因素有家庭年收入5001~10000元(OR=0.49;P<0.02),年收入10001~20000元(OR=0.49;P<0.02)。
3 討 論
軀體形式障礙主要特征是病人反復求醫,反復向醫生陳述軀體癥狀,不斷要給予醫學檢查,無視反復檢查的陰性結果,不管醫生關于其癥狀并無軀體基礎的再三保證,即使患者有時存在某種軀體疾病,但其所患軀體疾病并不能解釋其癥狀的性質和程度或病人的痛苦與先占觀念。軀體形式障礙按DSM-Ⅳ分為軀體化障礙、疼痛障礙、未分化的軀體形式障礙、疑病癥、軀體變形障礙。本次流調各種軀體形式障礙的總的患病率為6.92‰,其中軀體化障礙0.48‰、,未分化軀體形式障礙1.57‰,疑病癥1.02‰。與浙江省的調查比較,軀體化障礙患病率相似[5],但低于Karvonen1.1%報道[11];持續的軀體疼痛障礙,本次調查疼痛障礙患病率為3.86‰,明顯高于浙江省0.58‰的報道[5],而與美國社區調查顯示其終生患病率為6‰相近[12],而明顯低于Grabe等在一個4075名的普通人群樣本的調查的12.3%[4]。
本次調查女性軀體形式障礙患病率為11.89‰,男性為1.87‰,女性明顯高于男性,與Karvonen報道男女比為1:5相似[11],一般認為,軀體化障礙患者以女性多見,起病多在30歲之前,Eggor[2]認為女孩的軀體化癥狀與情感障礙有較強相關,男孩則與行為分裂相關,表明男性與女性的精神生物學過程可能不同。本位調查40~60歲患病率較高,而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30~60歲有較高的患病危險,反映出該病的年齡特點,提醒我們當患者進入中年后,更多的關注自己的軀體微小變化,對疾病的敏感性增加;邱亞峰等[13]研究軀體化障礙患者的心理防御機制發現患者較多的使用中間型和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機制如退縮、投射、軀體化、否認、同一化、防御機制。同時也發現家庭年收入5000~20000元者是相對的保護性因素,其原因還有待于進一步分析。
由于軀體形式障礙的表現涉及軀體各個系統,導致患者多在內外科就診,經過反復檢查未見相應器質性病變,且應用有關治療癥狀難以緩解,只有少數患者到精神科和心理科就診;孟凡強等[6]調查發現綜合醫院門診就診患者18.2%為軀體形式障礙,軀體化障礙占門診總就診數的7.4%。Fink在392名內科住院病人中,患軀體化障礙患病率為1.5%。未分化軀體形式障礙為10%[14],Portegijs對頻繁就醫的患者調查發現軀體化障礙占45%[1],Gureji報道的在基層醫療機構中16.7%[15],因此,應加強精神衛生的宣傳,加強對綜合醫院醫生就有關軀體形式障礙知識的培訓,提高對該疾病的識別能力,以便更好的提供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
4 參考文獻
[1]Portegijs PJM, Vander-Horst FG, Proot IM, et al. Somatization in frequent attender of general practice.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y Epidemiology,1996,31:29-37
[2]Egger, Helen link MD. Somatic complains and Psychopatholog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tomach Aches, Musculoskeletal Pains, and Headach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dolescent Psychiatry,1999,38:852
[3]Mde Waal MW, Arnold IA, Eekhof JA, et al. Somatoform disorders in general practice: prevalence, functional impairment and comorbidity anxiety and depressive disorders. Br J Psychiatry,2004,184:470
[4]Grabe HJ, Meyer C, Hapkeoll, et al. Somatoform pain disorder in general population. Psychother Psychosom,2003,72:88
[5]石其昌,章建民,徐方中,等.浙江省15歲以上人群各類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報告.中國預防醫學雜志,2005,39:229-236
[6]孟凡強,崔玉華,沈漁村,等.綜合醫院軀體形式障礙臨床特點的初步研究.中國心理衛生雜志,1999,13:67
[7]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河北省統計局,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河北省經濟年鑒2003.第1版.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458
[8]Regier DA, Boyd JH, Burke JD, et al. One-month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five 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site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1988,45:977-986
[9]Goldberg DP, Gater R, Sartorius N, et al. The validity of two version of the GHQ in the WHO study of mental illness in general health care. Psychol Med,1997,27:191-197
[10]李濤,周茹英,胡峻梅,等譯.DSM-Ⅳ-TR軸Ⅰ障礙定式臨床檢查病人版(SCID-I/P).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研究所,2004
[11]Karvonen JT, Veijola J, Jokelaimen J, et al. Somatization disorder in youngpopulation. Gen Hosp Psychiatry,2004,26:9
[12]駱艷麗,吳文源,李春波,等.持續的軀體形式的疼痛障礙的臨床特征及藥物療效.上海精神醫學,2003,15(增刊):42-44
[13]邱亞峰,馬麗霞.軀體化障礙患者防御方式與行為類型的相關研究.健康心理學雜志,2004,12:196-197
篇4
關鍵詞 腦卒中 失語癥 重復經顱磁刺激
中圖分類號:R743.3; R741.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33(2017)13-0027-04
Research progres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stroke aphasia*
SUN Changhui1**, BAI Yulong 1,2***(1.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Huashan Hospital North,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901; 2.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ABSTRACT Aphasia is one of the common functional disorders and sequelae of stroke patients, the incidence of stroke with aphasia is 21%-38%. Aphasia seriously hinders the normal communication and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brings in a heavy burden to the family and society. At present, the traditional speech language training is the main therapeutic method, but the treatment effect is not ideal.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has some effects on aphasia.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stroke aphasia.
KEY WORDS stroke; aphasia;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據2008年公布的我國居民第三次死因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腦卒中的發病率正以每年近9%的速度上升,隨著我國腦卒中患者日益增多,卒中后失語癥的發生也在逐年增加。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調查資料顯示,失語癥的恢復往往需要2年以上的時間,且僅有20%的患者可以完全恢復[1]。據《全國第三次死因回顧抽樣調查報告》顯示,腦血管疾病患者中,16.6%患有失語癥[2],國外報道為21%~38%[1]。有失語癥的患者通常比沒有失語癥的患者死亡率更高,參與的活動更少,生活質量更低。
失語癥是一種由于大腦局部神經受損導致患者后天習得的語言能力受損或喪失的一種獲得性語言綜合障礙。典型的失語癥包括Broca失語、Wernicke失語、傳導性失語、經皮質運動性失語、經皮質感覺性失語、經皮質混合型失語、完全性失語、命名性失語八類[3]。
目前,卒中后失語癥尚無公認有效的藥物治療。傳統的語言訓練仍是主要治療手段,但起效緩慢,效率偏低,難以達到滿意的治療效果。另外,缺乏一對一訓練模式的專業語言師等因素使得該治療難以廣泛實施[4-5]。
重復經顱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是1992年在TMS的基礎上新近發展的一種無痛、無創、簡單快捷的非侵入性神經電生理治療技術[6],在促進精神疾病[7]、癲癇[8]、\動障礙疾病[9]、脊髓損傷[10]等疾病的功能恢復方面取得了一定療效。近年來有小樣本研究報道表明rTMS治療對卒中后失語癥有一定成效[11]。本文就rTMS 治療腦卒中后失語癥進行綜述,以便為臨床研究提供參考。
1 rTMS治療失語癥的機制
生理狀態下雙側大腦半球存在交互抑制機制,其目的就是保持雙側腦功能的平衡。大腦左側半球損傷后,這種平衡被打破,左側大腦半球的抑制減弱,導致右側大腦半球興奮性相對增加,這不利于語言恢復。TMS是一種無創性的、在顱外對中樞神經進行干預的電生理調控技術,一般根據皮層刺激的頻率進行劃分。研究表明,高頻rTMS作用于患側腦區(左側大腦半球)及低頻rTMS作用于健側腦區(右側大腦半球)對腦卒中后語言功能的恢復是積極有利的[12-14]。因為高頻率rTMS有易化局部神經細胞的作用,使大腦皮質的興奮性增加;低頻率rTMS有抑制局部皮質神經細胞的作用,使皮質的興奮性下降,從而使大腦皮質發生可塑性改變,在神經系統具有可塑性的前提下,大腦言語代償區神經網絡能夠重建,進而恢復患者的言語功能[15]。
2 臨床應用
2.1 低頻rTMS對失語癥患者右側大腦半球作用
Martin等[16]對非流利失語患者(左側大腦半球卒中后5~6年)給予右側Broca區頻率為1 Hz的低頻刺激,治療后發現患者圖命名能力明顯改善。國內也有相關研究:陳芳等[5]對左半球腦梗死后運動性失語右利手患者的右側大腦半球Broca區給予1 Hz、80%運動閾值的rTMS治療,發現對患者的言語恢復有一定促進作用。樊影娜等[17]對急性腦梗死后運動性失語的患者予以右側Broca區,刺激頻率為1 Hz,磁刺激強度為健側肢體運動閾值的80%、每序列50次脈沖、每天10個序列、序列間隔120 s的治療,患者的語言功能有較明顯改善。Kakuda等[18]將rTMS與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術結合,對2例運動性失語患者的兩側額葉給予1 200個脈沖的低頻rTMS刺激,結果顯示,2例患者的語言功能都有所進步。同時,國內學者還將其他方法與rTMS結合,肖衛民等[19]將90例早期腦梗死后運動性失語癥患者隨機分為3組,在常規藥物治療及語言訓練的基礎上,對照1組再給予針灸治療,對照2組給予rTMS(1 Hz)治療,觀察組給予針灸加rTMS(1 Hz)治療。發現觀察組治療后的失語指數及自發言語、復述、命名等項目得分明顯優于對照組,提示將rTMS與其他治療相結合可提高治療效果。同樣的,Kakuda等[20]對4例運動性失語患者進行rTMS聯合每天60 min的強化言語訓練,具體方案是予以每個病人10 min 6 Hz的啟動刺激加20 min 1 Hz的低頻rTMS,刺激部位為右額葉,每位患者接受18次治療。發現治療后患者的表達和聽理解能力均得到有效提高。肖軍等[21]對Wernicke失語癥和傳導性失語癥者選取右側大腦半球相應語言區為刺激中心點,采用刺激頻率為1 Hz、80個序列、每個序列10次脈沖、間隔10 d、刺激強度40%~90%(具體根據患者年齡、病情、耐受程度調整),共10次治療。發現其中圖命名改善最明顯,自發性言語次之,聽理解和復述較差。
2.2 高頻rTMS對失語癥患者左側大腦半球作用
多數實驗結果支持高頻rTMS可易化興奮失語癥患者左側大腦半球,對語言功能的恢復有促進作用。王甜甜等[22]對24例腦卒中后非流利型失語癥患者進行分組治療,分為對照組,低頻組以及高頻組,對患者左側半球Broca 區進行高頻rTMS治療。采用運動閾值的80%為刺激強度、頻率為5 Hz,治療20 min,每周5次,共2周,對患者的視圖命名成績及反應時間均有明顯的改善。Szsflarski等[23]對8例中重度慢性失語癥患者的左半球Broca^給予80%運動閾值的刺激強度、為期2周、每周5 d的刺激,在左半球Broca區進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結果發現,有6例患者的語義流利度提高,提示左半球額顳頂葉語言相關功能區活動增強。陳芳等[24]對急性腦梗死后運動性失語患者采用高頻rTMS,刺激頻率為10 Hz、每序列50次脈沖、每天10個序列、序列間隔120 s,刺激部位為左側半球Broca區,連續治療10次,對患者的失語情況有一定的治療作用。Khedr等[25]應用3 Hz刺激左側大腦半球語言區,觀察到患者語言功能提高,但左側大腦中動脈供血區大面積腦梗死后患者語言功能沒有明顯提高。
2.3 高頻rTMS對失語癥患者右側大腦半球作用
胡雪艷等[26]對失語癥患者右側大腦半球Broca鏡像區進行10 Hz rTMS治療,發現對比在同一部位給予1 Hz刺激及無刺激對照組患者,高頻刺激對語言功能改善程度更好。可能是患者的Broca區損傷較嚴重,不能很好進行功能代償。由此可以表明對右側大腦半球進行高頻刺激可促進右側大腦皮層相應部位功能重組,從而促進語言功能恢復。Winhuisen等[27]對11例左側梗死后失語癥癥的患者(均為右利手)的右側額下回以4 Hz高頻刺激,采用正電子斷層顯像(PET)測得治療后右側額下回呈高代謝,但發現患者語言出錯率上升,流暢性下降,表明高頻rTMS刺激非優勢半球不利于言語恢復。
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研究都是針對非流利性失語癥患者,而對于流利性失語癥患者的研究非常少,同時主要集中于低頻rTMS刺激治療方面。
3 TMS治療副作用及的安全性
rTMS治療臨床比較安全,主要副作用是可以引發癲癇,但迄今為止未見明顯長期副作用的報道。Muller等[28]研究表明,大部份的影響是輕度不良反應,如頭痛、惡心,占16.7%;最嚴重的副作用是誘發癲癇,其中癲癇患者的陽性率是0.16%。Seniow等[29]和Kakuda等[20]的研究也均證實rTMS用于腦卒中后失語癥患者的治療是安全的。但至今尚無針對TMS操作安全系數及遠期安全情況等的完善報道。2009年Rossi等[30]針對TMS在臨床和科研中的刺激參數、使用倫理問題及癲癇、眩暈副作用的預防措施等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總結,但對失語癥尚無定論,隨著研究的逐漸增多將有更充分的數據提供最佳刺激參數以及安全指南。
4 TMS治療的局限性
Martin等[31]對5例慢性期失語患者進行右側三角部抑制性磁刺激治療,干預前后進行功能磁共振檢查,發現其中一名患者對rTMS治療效果較好,其他幾個失語較嚴重的患者TMS反應較差。作者認為,進行rTMS患者語言功能至少要達到波士頓命名測驗(Boston Naming Test, BNT)前20個平均正確命名3個,否則rTMs治療后不會觀察到患者命名能力的明顯提高。由此可見,損傷較嚴重的失語癥患者進行rTMS 沒有明顯效果。我們在臨床工作中也可見某些損傷較嚴重的患者進行治療后效果不明顯。
5 討論與總結
盡管目前的研究表明,rTMS可改善失語癥患者語言功能,促進大腦語言功能網絡重組,且rTMS副作用較少,但部分損傷較嚴重的患者對某些方案rTMS治療效果不佳。還有很多疑問等待研究和探索,如失語癥患者類型及刺激部位選擇問題;TMS治療腦卒中后失語癥的最佳介入時間;以及如何將目前研究結果更好地指導臨床實踐,取得更好的治療效果等。相信rTMS將有望成為失語癥患者的新福音。
參考文獻
[1] Berthier ML. Poststroke aphasia. epidemiology, pathophysiology and treatment[J]. Drugs Aging, 2005, 22(2): 163-182.
[2] 王新德, 陳海波. 急性腦血管疾病言語障礙的研究[J]. 中華神經精神科雜志, 1988, 21(4): 201-203.
[3] 李勝利. 失語癥康復[C]//中國康復醫學會第五屆全國康復治療學術會議論文集. 北京: 中國康復醫學會, 2006: 3.
[4] Weiduschat N, ThieI A, Rubi-Fessen I, et al. Effects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aphasic strok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pilot study[J]. Stroke. 2011, 42(2): 409-415.
[5] 陳芳, 王曉明, 孫祥榮, 等. 低頻重復經顱磁刺激對腦梗死失語的治療作用及其對腦電活動的影響[J]. 中華腦血管病雜志(電子版), 2011, 5(2): 7-10.
[6] Platz T, Rothwell JC. Brain stimulation and brain repairrTMS: from animal experiment to clinical trials ― what do we know?[J]. Restor Neural Neurosci, 2010, 28(4): 387-398.
[7] Schutter DJ.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s a treatment for depression[J]. Tijdschr Psychiatr, 2011, 53(6): 343-353.
[8] Sun W, Fu W, Mao W, et al. Low-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partial epilepsy[J]. Clin EEG Neurosci, 2011, 42(1): 40-44.
[9] Kodama M, Kasahara T, Hyodo M, et al. Effect of lowfrequenc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hysical therapy on L-dopa-induced painful off-period dystonia in Parkinson’s disease[J]. Am J Phys Med Rehabil, 2011, 90(2): 150-155.
[10] T新紅, 崔麗英. 經顱重復磁刺激的臨床應用研究進展[J]. 國際神經病學神經外科學雜志, 2010, 37(6): 535-538.
[11] 汪潔, 吳東宇, 袁英, 等. 應用在線經顱直流電刺激探查外側裂后部對失語癥恢復的作用[J]. 中國康復醫學雜志, 2011, 26(5): 406-410.
[12] Hamilton RH, Sanders L, Benson J, et al. Stimulating conversation: enhancement of elicited propositional speech in a patient with chronic non-fluent aphasia following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J]. Brain Lang, 2010, 113(1): 45-50.
[13] Murdoch BE, Barwood CH.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a new frontier in the treatment of neurogenic speech-language disorders[J]. Int J speech lang Patrol, 2013, 15(3): 234-244.
[14] Cotelli M, Fertonani A, Miozzo A, et al. Anomia training and brain stimulation in chronic aphasia[J]. Neuropsychol Rehabil, 2011, 21(5): 717-741.
[15] Málly J.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rTMS and tDCS) in patients with aphasia: mode of action at the cellular level[J]. Brain Res Bull, 2013, 98: 30-35.
[16] Martin PL, Nasser MA, Theoret H, et al.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s a complementary treatment for aphasia[J]. Semin Speech Lang, 2004, 25(2): 181-91.
[17] 樊影娜, 趙佳. 低頻rTMS對急性腦梗死后運動性失語的療效觀察[J]. 中國康復, 2016, 31(1): 28-30.
[18] Kakuda W, Abo M, Kaito N, et al. Functional MRI-based therapeutic rTMS strategy for aphasic stroke patients : a case series pilot study[J]. Int J Neurosci, 2010, 120, (1): 60-66.
[19] 肖l民, 李愛萍. 經顱磁刺激結合針灸與語言訓練對早期腦梗死后運動性失語癥患者的療效[J]. 廣東醫學, 2014, 18(7): 2132-2134.
[20] Kakuda W, Abo M, Momosaki R, et al. Therapeutic application of 6-Hz-primed low-frequency rTMS combined with intensive speech therapy for post-stroke aphasia[J]. Brain Inj, 2011, 25(12): 1242-1248.
[21] 肖軍, 馮園, 易剛, 等. 低頻重復經顱磁刺激治療腦卒中后外側裂周失語癥的療效觀察[J]. 實用醫院臨床雜志, 2014, 11(3): 119-120.
[22] 王甜甜, 陸芳, 李霖榮, 等. 不同頻率重復經顱磁刺激對腦卒中后非流利型失語癥患者視圖命名的影響[J]. 中國康復, 2016, 31(6): 412-413.
[23] Szsflarski JP, Vannest J, Wu SW, et al. Excitatory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duces improvements in chronic post-stroke aphasia[J/OL]. Med Sci Monit, 2011, 17(3): CR132-139. doi: 10.12659/MSM.881446.
[24] 陳芳, 詹成, 楊玲, 等. 低頻與高頻重復經顱磁刺激治療腦梗死失語的療效研究[J]. 世界臨床醫學, 2015, 9(11): 4.
[25] Khedr EM, Ahmed MA, Fathy N, et al. Therapeutic trial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J]. Neurology. 2005, 65(3): 466-468.
[26] 胡雪艷, 張通, 劉麗旭, 等. 高頻重復經顱磁刺激治療對左側大腦中動脈梗死后失語癥患者的影響[C]//中華醫學會, 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 中華醫學會第十七次全國神經病學學術會議論文匯編(下). 北京: 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 2014: 1.
[27] Winhuisen L, Thiel A, Schumacher B, et al. The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poststroke aphasia: a follow-up investigation[J]. Stroke, 2007, 38(4): 1286-1292.
[28] Muller PA, Pascual-Leone A, Rotenberg A.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 positive sensory phenomena: a review of literature[J]. Brain Stimul, 2012, 5(3): 320-329.
[29] Seniow J, Waldowski K, Lesniak M, et al.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speech and language training in early aphasia rehabilitation: a randomized double blind controlled pilot study[J]. Top Stroke Rehabil, 2013, 20(3): 250-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