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的天文學成就范文
時間:2024-03-22 18:03:0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古埃及的天文學成就,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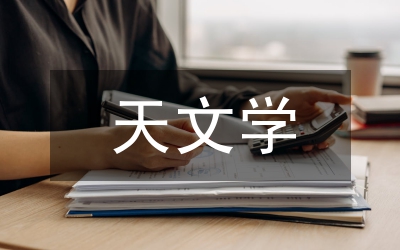
篇1
數學科學是以人們的社會生活需要及客觀現象為研究對象。它作為人類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和一定的社 會歷史發展水平相適應;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又受到整個文化結構的影響。東西方傳統文化的不同,對數學 的影響也存在著差異。
文化結構由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組成。由于一定的社會制度是一定的物質基礎上產生的,要受到一定的精 神文化制約,因而可將文化結構分成三個層面:“這就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①。數學在建立發 展過程中,受到了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影響及制約。
東方中國的古代文化的經濟基礎基本上是農業經濟。這種情況決定古代中國的物質文化是農業文化。中國 古代數學也與農業經濟有著密切的關系。《九章算術》是中國最古老的經典著作,書有九章,包含246個問題 。都和農業生產有關,九章分別是方田(土地測量)、粟米(百分法和比例)、衰分(比例分配)、少廣(減 少寬度)、商功(工程審議)、均輸(征稅)、盈不足(過剩與不足)、方程(列表計算的方法)、勾股(直 角三角形)。這些問題都是用來解決農田的測量、粟米的稱量,農業水利工程的測算等。《五曹算經》是一部 為地方行政人員所寫的應用算術,全書五卷,有田曹、兵曹、集曹、倉曹、金曹五個部分。田曹卷的主題是田 地面積的量法;兵曹算術大都是軍隊的給養問題;集曹問題和《九章算術》粟米章問題相仿;倉曹解決糧食的 征收、運輸和儲藏問題;金曹問題以絲絹、錢幣等物資為對象,是簡單的比例問題。我國古代大數學家劉徽到 祖沖之、祖沖之研究圓周率和圓面積的輝煌成就中,都深深地打著農業經濟的印記。農業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車 ,車輪是否圓,不僅和車輛行駛中的平穩狀況有關,而且還和省力有關,因而農業經濟的需要使得我國圓周率 的研究在世界數學中占有相當的地位。過去,農業的顯著特點是靠天吃飯,天文、節氣的測算是農業生產的需 要,在中國,古代天文測算的成果是相當輝煌的,“東漢末年天文學家劉洪造乾象歷法(公元206年),創立 了推算定朔、定望時刻的公式”。“隋朝天文學家劉焯在他的杰作《皇極歷》(公元600年)中創立了一個推 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比以前更加精密的公式”②。天文學的發展推動了數學的發展。解一次同余式就是由天 文測算開始的。天文數學的發展除了物質文化的需要,還受到制度文化的要求,中國數學的重要性在于它與歷 法有關,“在《疇人傳》中很難找到一個數學家不受詔參與或幫助他那個時代的歷法革新工作。”③除了中國 ,古代埃及數學的建立基礎也是農業的需要。埃及幾何學的起源被史學家們歸因于泥羅河泛濫后土地的重新測 量;巴比倫的數學起源也是如此,尤其是巴比倫數學的60進位制來自于天文學;印度數學和占星術有關,而占 星術又和農業及宗教有關。
東方數學的建立比西方要早,但東方的數學在理論化的道路上行動遲緩。原因何在呢?自給自足的自然經 濟的生產力狀況決定的生產力關系是以家族為中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等級關系,社會制度是宗法等級 制度。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分散的家族和農民需要有高高在上、君臨一切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統治 。在這種社會制度的影響和作用下,形成中國古代穩定的上下尊卑等級秩序的文化心理。主要特點是靜態的、 和解的、自然的、消極的心理特點。造成安于現狀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思想僵化、調和持中, 這種文化心理使得數學只停留在實用上。沒有就數學而數學,使數學自身的規律沒有得到完善。“在古代東方 的全部數學中甚至找不到一個我們今天稱之為‘證明’的例子,代替論證的只有程序的描述,所講授的內容只 是‘如此這般地做’,而且也不是以一般規則的形式提出來,只不過是在一系列特殊情況下的應用方法。”④ 這段話雖有失偏頗,但也道出中國古代數學的特征。在中國數學的發展史上曾出現了劉徽、墨子、惠施等天才 的數學家,但他們的數學研究和成就不能和西方的阿基米得、歐幾里德相比較。這主要是我國古代數學的理論 研究不受重視所致。漢王朝建立以后的“重農抑商”政策使數學研究受不到貿易的誘惑。農業經濟的財富有限 和填飽肚子的生活狀況,不允許人們的思想向實用以外的地方延伸;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也扼殺了大批在數學 研究上具有不凡才華的人。在科舉制度中數學不是要考的課程,為“學而優則仕”而奮斗的人們,自然不會將 數學當作主修課程來學習。另外,農業經濟的貧困使得沒有多少人來學文化,學數學的人自然更少。在這種情 況下,中國古代數學的許多成就只處在應用和描述過程階段,沒有提高到抽象的、系統的理論階段,從而使數 學的發展和升華受到限制,象“勾股定理”、“圓周率”這些值得中國人驕傲的數學成就,沒有造成相應的數 學的轟動效應。“勾股定理”在我國商高的時代就應用比西方的畢達哥拉斯發現早600年,但由于我們沒有給 出嚴格的數學證明,這個定理在現在還認為是畢氏的成果,稱為“畢氏定理”。墨子的極限理論也沒有引起足 夠的重視,后來西方數學傳入我國時才知西方極限思想和黑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重農抑商”的文化傳統的價 值觀具有明顯的倫理性。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的環境不需進行商品交換(至少不需要太多的貨幣介入)。生產 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價值,人們關心的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以不言利為榮,“重義輕利”的思想滲透到 人們的思想深處。數學的應用只局限于分配環節中。而在復雜的流通和交換領域中數學沒有機會“施展才華” 。多農少商沒有足夠的財富供人們享受,財產的有限性限制了人們的探險精神和“想入非非”,從而限制了數 學向理性的發展。
在西方,小亞西亞海岸新興的商業城市、希臘本土、西西里島和意大利海濱,由于海上貿易和戰爭的刺激 使得人們的思想活躍,商品貿易發達,對計算要求的提高,財富的增加使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從事“非實用”的 理論研究。古代東方靜態的觀點和西方動態的觀點不一樣,表現在數學上唯理論的氣氛濃厚起來。人們不但要 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但要問“什么”,而且要問“為什么”,要解決“所以然”和“為什 么”。古代東方的以實踐和經驗為根據的方法就顯得“無能為力”和“后勁不足”。為了知道“所以然”和“ 為什么”,就得在數學的證明方法上作一定的努力,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現代意義上的數學產生了。東方的幾 何學只為測量提供方法,而證明的幾何學是由公元6世紀前半期米利都的泰勒斯開創的。泰勒斯不是農業經濟 中的“耕夫”,而是一個商人,他在經商過程中積累了足夠的財富后,在后半生從事研究和旅行。他在幾何學 中的主要成果有“圓被任一直徑二等分”,“等腰三角形的兩底角相等”、“兩條直線相交對頂角相等”,“ 兩個三角形,有兩個角和一條邊對應相等,則全等”、“內接與半圓的角必為直角”等⑤。這些成果的意義不 在于斷言的本身,而是提供了一些邏輯推理(象他的第五個問題巴比倫比他早知道近1400年,但沒有形成嚴格 的證明)。使得數學被推向抽象、系統化軌道的還有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以及他們的繼承者形成的畢氏學派和 柏氏學派。由于商業的發達、財富的增長,使得人們旅行的欲望越來越高,而旅行和游動的生活方式給數學的 發展提供了機遇。前面提到的泰勒斯的后半生就是在旅行和數學研究中渡過的,“他有一段時間住在埃及”⑥ 。畢達哥拉斯也有旅行和流動生活的經歷。“他曾在埃及居住了22年,從埃及神廟的祭司那里了解了古埃及有 關數學、天文方面的知識……回國后,又前往希臘的移民地阿佩寧半島的克羅托納城定居”⑦。從這兩位數學 大師的經歷看,不能不說旅游這種文化活動給數學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商業貿易的發展,可誘導戰爭的爆發, 戰爭不僅給侵略者掠奪來物質財富,而且也帶來了許多精神財富,其中就有數學成就。公元前334年,馬其頓 國王亞歷山大領兵進入埃及,不久揮師東進,橫掃了波斯帝國的軍隊,到了印度河西岸,建立起龐大的亞歷山 大帝國和亞歷山大城,這個城市的建設主要著眼于文化科學設施的建設,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久就成為當時 世界科學文化的名城,歐幾里德就是在這個環境中熏陶和成熟起來的偉大的數學家。他對數學寶庫的貢獻是《 幾何原本》。他的幾何和東方幾何的不同之處是,不僅從應用的角度來談,而是就幾何而幾何的角度加以研究 ,運用邏輯推理來證明命題的真偽。而且用幾何的方法來解決代數方程。他的著作中的許多公理、定理和定義 除了適應當時的經驗外,還具有普遍的意義。阿基米得也是當時偉大的數學家,他采用窮竭法來求圓的周長和 直徑的比值,其指導思想和我國劉徽的計算圓周率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不同之點是“劉徽是從圓內接正多邊形 著手,而阿基米得不僅從圓內接正多邊形著手、還從外切正多邊形這個角度進行計算”⑧。這就體現出西方數 學家多方位的思維方式。另外,阿基米得在研究圓的同時,還研究了球和圓柱的問題,他在《論錐形體和球形 體》中使用了近似于現代數學的方法。他的工作不僅涉及到具有很大應用價值的數學問題,而且提出了許多明 確的數學概念,在這一點上要比東方數學先進。商業貿易具有一定的風險性、尤其是遠航貿易。這種背景下產 生了保除業。而保險的興起又促使了概率論的產生和發展。雖然刺激概率論的是賭博,但起源是商業文化。即 使是賭博也是產生于發達的商業文化城。可見,東西方傳統文化不僅影響到不同的數學分支和范圍,而且在同 一數學問題上所體現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同,表述的形式、研究的動機也存在差異。再來看一個事實,《周 易》及先天圖二分法與菜布尼茲的二進制,兩者一個講對分,一個講進位。但都“用兩個符號表示無限的事物 或數學其客觀存在的排列法則,決定了先天圖與二進制算術的一致”⑧。二進制和先天圖沒有關系,這是不同 時代的東西方數學家,在完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的產物,其一致性是令人吃驚的,但思想方法卻完全不同。二 進制是在西方傳統文化中歐洲科學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是有意識地運用十進制知識而創造的一種計數方法。 二分圖是《周易》眾多象數體系中的一個,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但其動機不免有些封建意識的糟粕,因為它不 是依靠科學的依據推出來的。
篇2
陸九淵不僅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王安石變法失敗是由于“凡事歸之法度”“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國不可得而治矣”。而且在與門人的講學中,也提到王安石變法的必要性,進而分析王安石變法失敗是由于“本原皆不能格物”,所以“學者先要窮理”: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卻是先定規模。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為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2]卷三十五《語錄下》442。”陸九淵此言不外乎說,變法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但是變法是有前提、有途徑、有先后順序的。“先要窮理”,這樣才算得上是“踏得實處”。另外,陸九淵在與門人問答時,談到所謂的事功問題時,認為事功的前提在于“正人心”:“學者問:‘荊門之政何先?’對曰:‘必也正人心乎[2]卷三十四《語錄上》425。’”“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2]卷三十五《語錄下》469。所以,在他看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由于本末不辨所致:“荊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為標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于其末,故至于敗[2]卷九《與錢伯同》121。”
陸九淵的《荊國王文公祠堂記》實質上反映了他的經世致用思想,即如果士大夫以實現外王,建立事功為己任,那么必須要先修內,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荊門之政以正人心為先”。否則便是本末倒置,所建立的事功也就必然不能夠長久。陸九淵把熙寧變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的緣由歸結為本末倒置。他認為,由“正人心”出發再到變法建立事功,才能夠真正達到建立事功的目的。其實,陸九淵更為關注的是建立長久的事功,而非短期的效用,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經世致用:“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后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卷二十二《雜說》274?”德,表面上看來,并不能夠為富為貴,但是這是為富為貴的根本。用我們的話來說,看似沒有實際用處的“德”,反倒是追求“富”與“貴”這般有用之物的根本,即虛無用實有用。這番道理在我們的基礎科學研究中何嘗不是如此呢?
二、基礎科學研究中的實用主義
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相對于科學創新而言,就類似于陸九淵在文中提到的內圣修心和外王事功的關系。世人往往通過科學研究的成果來認識科學,而社會往往也是通過對科學成果價值性的判斷從而賦予科學以一定的社會地位,從事研究的科學家在一定領域內才會被承認。這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思路:社會通過科學研究成果,也就是科學研究的有用性來判斷相關科學研究存在的價值;而相關領域的科學家也就為了獲得社會一定程度上的承認,去從事短期內能夠突顯實際效用的研究。由于基礎科學研究的基礎性作用決定了從事該領域的研究必將付出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而基礎性研究的成果又很難通過自身體現其社會價值,這種有用性難于為社會所承認,就像我們一般不會關注雕像的底座一樣,所以,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必然會被擱淺。這種評價的體系和思路會導致科學家只關注科學價值而忽略科學研究本身,更重要的是忽視基礎科學研究的奠基性作用。這種忽視,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都會在根本上延緩科學發展的進程。這也就是陳佳洱先生提到的“實用性”傾向阻礙科學創新的意思。這種阻礙,是指根本上的一種影響。缺乏底座的雕像如何能夠樹立起來呢?即便樹立起來了,能不能經受歲月的洗禮?古埃及有句諺語:萬物懼怕時間,時間懼怕金塔。金字塔距今約5000年,無論它的建造是如何符合工程力學原理,但如果沒有堅實的底座,還能夠成為人類文明的象征么?
科學,是以探究自然和人類社會的規律或規則為研究目的。只是在探究的過程中或者某一種科學理論建立之后的若干年,人類才發現其中的一部分可以有利于改善人類生活的環境或者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科學與科學價值應該區別對待。科學一定有其價值,并且也一定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類的需求,但是這種價值能否為當時的社會所發現或者承認是另外一個問題。以滿足人類需求為科學研究的惟一出發點,以是否有用的實用主義來衡量基礎科學研究,以科學價值來框定科學的發展空間,忽視科學內在的發展規律,這會在根本上窒息科學創新的思維,那么所謂科學研究的有用性又如何實現呢?科學史上著名的開普勒行星運動定律的提出就是基于丹麥科學家第谷•布拉赫長達20多年的天文觀測數據上提煉、分析而得出的,行星運動定律是改變西方天文學發展軌跡的重大理論,對牛頓建立經典物理學體系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們如何去衡量第谷天文觀測數據的實用性呢?但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第谷積累的觀測數據,起碼人類對宇宙產生革命性認識還不知道要推遲多少年。基礎科學研究的意義存在于整個科學研究、科學創新的過程中。或許它不一定“有用”,但每一項科學研究成果的獲得,科學創新思想的提出無不閃耀著基礎科學研究的金色光芒。
當前充斥于科學研究領域當中的實用之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體制的評價標準。相關的一系列條件要求科研人員必須在一定的時期內發表相當數量的論文,并且一定要有創新思想。另外,在一些研究生招生院校甚至要求碩士期間必須要發表文章,而且必須至少為省級級別的刊物。這種做法不禁令人啞然失笑。科學研究是積累的過程,這類似于文史哲及相關的社會學科的性質。研究者的成果是厚積而薄發的,尤其是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思想。以是否發文章和發了多少文章去衡量研究者的能力甚至與研究者的生活質量掛鉤,這能不促使研究者拋棄基礎科學研究,而選擇短時期內能夠出大量成果的熱門領域么?況且,上述情況中的碩士期間發論文的舉措,怎么可能培養研究生的“寧靜以致遠”的科研心態?快餐從根本上不利于人體健康,快餐文化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傳承,快餐科研更會動搖科學創新的根基。
三、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