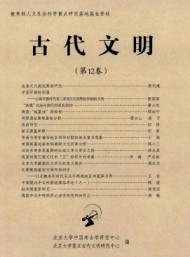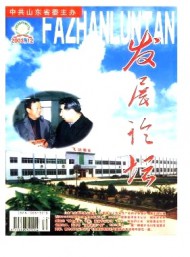對于校園欺凌的看法范文
時間:2024-04-18 17:59:4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于校園欺凌的看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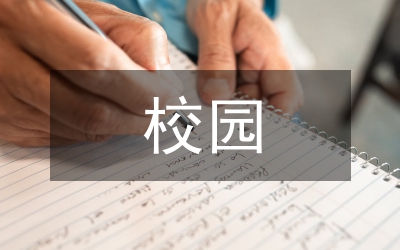
篇1
關鍵詞:校園;欺凌現象;欺凌行為;歸因分析
自20世紀90年代起,欺凌現象便進入學術研究的關注范疇。雖然至今對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可欺凌指的是“一種有意傷害別人的行為,不止一次發生,其實質是欺凌者和受害者之間力量的不平衡”。其中,校園欺凌作為一種發生在校園內外同學之間的特殊欺凌現象,值得引起全社會的格外重視。
一、關于校園欺凌現象(行為)的不同看法
1.學者眼中的欺凌現象(行為)
學者們認為欺凌行為指的是力量的不平衡,包括身體欺凌、語言欺凌以及會不斷引起恐懼的長期性的社交排斥。在他們看來,欺凌者和受害者對于力量的占有是不一樣的。這種力量既有可能來自體力優勢(相對健壯的身材,或者人數的眾多),也有可能來自腦力優勢,包括利用“正在發生的事情或將要發生的事情”來威脅和嚇唬別人從而讓別人感到壓力以做出和本意相反的
決定。
2.教師眼中的欺凌現象(行為)
Boulton的研究表明,大多數的老師認為欺凌行為包含身體和語言上的雙重欺凌,比如,強迫別人做他們本不想做的事情;25%的老師并不認可下列行為算是欺凌行為:比如,叫外號、散播謠言、目光恐嚇還有拿走別人的東西等。除此之外,超過50%的老師不認為社交孤立算是欺凌的一種形式。這個發現和Ramasut 和Papatheodorou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3.學生眼中的欺凌現象(行為)
學者和孩子之間關于欺凌行為的定義的不同之處主要集中在語言欺凌和身體欺凌、間接欺凌、欺凌行為的重復性和故意性方面。Guerin和Hennessey的研究證實,60%左右的受訪者認為“體力優勢在欺凌現象中非常重要”,并且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大
部分受訪者(63%)相信“在欺凌行為是否出自故意并不重要”,只有13%的人認為“欺凌行為絕對是出自故意的”。
4.父母眼中的欺凌現象(行為)
研究表明面,對校園中的欺凌現象,父母要么毫無覺察,要么感到非常無措,不知道該怎樣正確地處理相關問題。他們害怕被學校認為是自己太敏感或者過度操心了。除此之外,父母還擔心自己的不當處理會使孩子的處境“雪上加霜”。
小題大做或者大題小做,父母要么不能及時注意到孩子的遭遇并感同身受導致事情表面上不了了之,要么反應過度弄得局面無法收拾,很少有父母能夠恰到好處地處理類似情況。
二、關于校園欺凌的歸因研究
1.欺凌者歸因論
這種說法認為,之所以會發生欺凌現象責任在于欺凌者自身的原因。如果欺凌者感覺糟糕或者沒有安全感、自信心和自尊心低下,有心理問題或者愛慕虛榮等都有可能會導致他(她)去欺凌別人。
根據社會學解釋,當欺凌者想要展現、維持或者提高他們的權力、地位和受歡迎程度的時候,或者當他們試圖保護自己免于被孤立、被騷擾和被欺負的時候,都有可能對別人實施欺凌行為。這樣做能讓他們覺得感覺更好,自信心和自尊心似乎也能得到提高。如果欺凌者本身由于問題家庭,沒有得到父母的良好監管,家庭爭吵不斷、沖突不斷,家長總是在吵架、鬧離婚、感情不好,經常目睹家庭暴力,那么他(她)很難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這導致欺凌者本身可能并沒有道德概念和同情心,他(她)這么做或許僅僅是出于“好玩”或者“無聊”。
2.受害者歸因論
這種說法認為,受害者之所以受到欺凌是因為他們本身有問題。大概四分之一的受訪者都持有這樣的看法。其中,最大的問題在于受害者和別人不一樣,是與眾不同的或者奇怪的。除此之外,還包括受害者的言行讓人感到厭惡、做人卑鄙、自身看起來好欺負,以前被人欺負過因此容易繼續被人習慣性地欺負等情況。
3.同伴歸因論
這種說法認為欺凌現象產生的原因在于同伴群體。21%的受訪者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聯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同伴壓力,即如果“大家都這樣做或者希望你這樣做,那你就不得不做”。如果所在的小團體強化欺凌行為,認為是“勇氣”的象征,提倡并贊賞實施欺凌的人,為了不被排擠出去,那么欺凌行為的發生幾率就會非常高。
4.學校歸因論
這種說法認為欺凌現象之所以會發生是學校環境導致的。原因之一在于學校太無聊了,學生無事可做;原因之二則是學校的反欺凌措施極為薄弱,老師不關心這類事情或者即便看到了也僅僅是袖手旁觀,這些都在無意中助長了校園欺凌的不良風氣。
5.人性歸因論和社會歸因論
人性歸因論認為欺凌現象之所發生在于人性自身的問題(沖突、暴力等是不可避免的)和社會風氣。根據生物學解釋,人有排斥異己的本能,因此,針對和自己不一樣的人并不為奇。社會歸因論則說社會只重視那些身體好、長得好看的人,如果身體羸弱或長得不好看,那么自然容易被人欺負。
參考文獻:
篇2
這不禁讓我覺得難以置信,也許生活的不過是個并不發達的地方,所在的中學雖說不是很好,但是卻好像并沒有這種事情的發生,盡管打架斗毆的行為從不匱乏,但是校園霸凌現象似乎是沒有發生的。當然,這或許與我一向的性格有關,周圍的事情向來是沒有途徑傳遞到我的耳朵中的。所以,一直感覺,那種欺負侮辱別人,校園欺凌現象一向是發生在小說中或者日漫韓劇中人們想象出來的事情罷了。現實生活中怎么會發生這種事情的呢?
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情是,最后那三名下藥的男生,由于受害者并沒有出現任何不良反應,甚至不了解保存物證,結果在我國現行法的規定下,三名男生的行為因為沒有造成任何惡果,所以成功逃脫了法律的制裁,最后竟然得到了當地警方的祝福,祝這些涉事學生在高考中國取得優異的成績。看到這里,我不禁感到疑問不解,那三位學生的惡果真的沒有造成嚴重的惡果嗎?盡管,現實中,那名女生身體確實沒有受到損害,但是有時候精神上的傷害更加的讓人難以痊愈。更嚴重的精神創傷卻直接忽略,他們都沒有考慮到那位少女的心理。
但是終究還是以私了的結果結束了,若真就如此終結那頂多受到幾句吐槽,或許也就過去了,然而,大量的當地網友以及學校的學生卻對那一名女生進行了征討,怪她沒事找事,抹黑了學校,抹黑了那一個地方。明明是受害者卻受盡謾罵!只能感到無比的心寒與恐懼。他們的善惡觀人生觀價值觀呢?若是這樣,那受到欺負卻要忍氣吞聲,去告狀卻要被罵多事,這是什么道理?有一種“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若是自身或親人成為受害者,那恐怕就是與這截然不同的說法了吧。
篇3
[關鍵詞]庫切;《恥》;雙重意識
在2003年南非作家J.M.庫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中,評價“庫切作品的人物總是游移退縮、畏葸不前,無法率意而行。這種消極被動既是遮蔽個性的陰霾,卻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人們不妨以無法達到目的為由拒絕執行那些暴虐的命令。正是在對人的弱點與失敗的探索中,庫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小說《恥》中,以南非日益變化的新形式為時代背景,以白人的種族隔離政策土崩瓦解背景下的白人生活為主要線索,以及白人在種族認同和文化認同標準之間徘徊的兩難局面為主要矛盾,本文從溯源南非的歷史開始,在分析社會和作者背景中揭示《恥》中南非白人因其文化身份造成的雙重意識以及這種意識的堅守與疏離。
一、歷史的濫觴――雙重意識
雙重意識最早來源于美國的杜波依斯的評論,原指非洲裔美國黑人兩種種族和兩種文化身份。在后殖民的環境下,長期生活在南非土地上的白人從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一直受到黑人的影響,既要堅持自身的信念和自由,又屈服于當地黑人的管轄,在兩種種族和兩種文化身份的斗爭中徘徊,在心靈上留下雙重意識的深刻印記。生活在南非土地上的白人們不得不以“雙重自我”的身份獲得站起來的力量,這是庫切在有關后殖民主題的文學作品中突出反映的內容,也是他作品里潛藏在思想深處的雙重意識。
法農在其重要著作《黑皮膚,白面具》中認為,黑人靈魂深處有一種無可排解的自卑情結,他們被喻為沒有文化地位、沒有心性陶冶、也沒有自主的民族自尊的“原始野人”。經歷種族隔離而重獲和平寧靜的南非人對殖民留下的傷痕記憶猶新。這種歷史轉折蘊含著黑人的仇恨和對獲得身份認同無比堅定的決心。在南非社會角色的變換之中,黑人發泄般地對白人進行復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南非白人陷入了尷尬的兩難境地,他們意識中雖然還殘留著強勢文化的優越感,但已沒有那種如沐春風的,在黑人反撲勢力的席卷下,現實中“雙重意識”逐漸潛入他們內心深處。在南非的歲月里,庫切一直生活在這兩種種族和兩種文化的交融與斗爭中,形成南非黑人社會中的一個自我,和白人在黑人社會中的獨特體驗中的自我。在庫切的筆下,《恥》更多的是描述了在這種雙重意識下白人對現實所進行的反抗,合理的卻又充滿悲劇意味的情感糾纏。
二、夾在文化罅隙中的思想者――庫切
庫切的荷蘭血統標刻著殖民浪潮和帝國時代的遺跡,這種身份昭示著他和前殖民者千絲萬縷的聯系。繼承著殖民先輩們的遺風,他身上有著揮之不去的感情維系,但對哺育他成長的土地,他也始終懷著難以割舍的情愫。作為殖民后代,他在南非應該處于一種什么樣的地位?面對著一段早已完結的殖民恩怨,他還需要在白色的歐洲和黑色的非洲中做出選擇嗎?歷史遺留的問題一旦推移到后代的身上,它就顯得愈加敏感而凝重,庫切就是擔負著這種困惑和反思走上小說創作的旅途。在作品《恥》中,一如既往地凝聚著庫切對種族和文化身份的思考,沉重的歸屬感和雙重意識,交織出現于字里行間,客觀上也表明了庫切無法使自己的靈魂超脫于這種愁悶壓抑的禁錮。他的文字體現其關于特殊經歷的心聲,正是這么一種經歷和文化背景,使得他始終采取南非當代生活作為創作源泉,另外又客觀地審視剖析了南非生活的變遷和從容,更比同時代的其他作家多具備一份理智、融合與超越。
三、文化身份的烙印――南非白人的兩難境地
“《恥》這部作品通過各種細節的描寫,揭示了新舊交替時生在南非大地上,發生在南非各色人等之間的種種問題,對殖民主義在南非對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本人及其后代所造成的后果表現出深切的憂思和相當的無奈。”在開普大學里,盧里是位有思想、充滿自信的大學教授,但他同時也是個性風流、沒有道德判斷標準、放縱的中年人。面對著在殖民統治后復蘇的農村,他仍小心地保存著那份殖民文化上的優越感,他仍習慣過去的行為方式和準則,但這份優越感卻使他在鄉村處處碰壁。在鄉村,他的博學多才失去了用武之地,昔日的大學教授委身切狗食、給工人做下手,到動物福利會診所里幫忙。她的女兒露茜遭到黑人的欺凌時,他只能像個啞巴一樣。在他夢里和現實生活中,耳邊總縈繞著女兒無助的求救聲,可他卻無能為力。一個文學教授,在鄉村卻處于一種獨白狀態,這體現出一種文明的尷尬。他想聽佩特魯斯的故事,卻不期望用英語聽,“他越來越堅信,英語極不適合用做傳媒來表達南非的事。”盧里的無奈主要體現在前后身份的落差,在他意識當中,大學里是擁有著值得驕傲的身份認同感,也堅信自己的執著可以換來包括南非當地的所有人的認同。但在女兒遭受后,他逐漸平靜地接受了這么一個事實,并認識到要想繼續生存在后殖民語境下,所需付出的代價是重大的。每次盧里想起遭遇的事情,他心里就涌起一股悲慟,那種感覺如潮水般涌過,“倦怠,冷漠,還有無力。”黑格爾說:“沖突中對立的雙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辯護理由,而同時每一方拿來作為自己所堅持的那種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內容的卻只能是把同樣有辯護理由的對方否定掉和破壞掉。因此,雙方都在維護倫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過實現這種倫理理想而陷入罪過之中。”
相對于盧里從驕傲而自信走向無奈而失落,露茜則是一個在歷史和現實罅隙中逐步失去白人品格特征的形象。對露茜的描述主要聚集在父女間意見的分歧上。盧里稱其為“思想現代、充滿自信”比她母親“更銳利些”的女人。她遭到后,“溫和地,但卻堅決地甩開盧里的胳膊”,在警察面前只字不提受辱之事,當盧里百般奉勸她正視自己擁有的權利時,她卻說:“這跟你沒有關系”,“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屬于個人隱私。換個時代,換個地方,人們可能認為這是件與公眾有關的事。可眼下,在這里,這不是”,“這里就是南非”。在盧里勸露茜離開這個農場的時候,露茜堅決不從,露茜覺得在這片土地上的e人眼里,她“根本就一文不值”。她要求父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時候,她解釋道:“他們覺得我欠了他們什么東西。他們覺得自己是討債的,收稅的。如果我不付出,為什么要讓我在這里生活?”父女倆對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絕非完全歸咎于代溝,而是包蘊了更深刻的歷史內涵,也是“人能否回避歷史”的一種答案。在歷史變遷中,當年白人殖民者后裔正在以自己的名譽、身體、尊嚴的代價來贖罪。在盧里這么一個遠離殖民政策,在祥和平靜的大學校園中生活的人再也不能接受這一點,但 和他有著不同的成長背景的女兒卻早已被這種歷史耳濡目染,并敞開心胸去接受懲罰。
佩特魯斯出場時,作者僅用“線條分明,飽經風霜的臉,一雙透著機敏的眼睛”的描述似乎就是用來模糊我們對這位南非農民的印象的。佩特魯斯的身上飽含非洲原始的野性,又有長期磨煉出的對抗白人的野心和膽略。在一起相處的日子里,盧里分明地感覺到,在南非大地不明事理的犯罪的猖狂,執法部門的軟弱,白人生活、人身安全的窘迫境地,是千千萬萬如佩特魯斯一樣的人的反抗情緒造就的。露茜事件的肇事者正是佩特魯斯的親戚,在晚會上這根導火線被點燃后,盧里出于慣常的思維要求懲罰肇事者,到最后卻沒有人認為這事違反常規而不了了之。所有的這一切,都體現了新一代的黑人們對殖民主題正統合法性和文化優越感的藐視和顛覆。在這么一個白人和黑人的直接交鋒中,盧里最大的失敗顯然來源于他優越的文化認同感受到的挑戰,隨之而來的就是其主體身份的喪失。
作品主題“恥”的雙重含義也昭然若揭:一是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丑惡現象給后代白人所帶來的深刻恥辱感,二是黑人在南非獨立后對白人進行暴力報復所帶來的深刻恥辱。后者已經在歲月的前行中逐漸占了上風,并且正在使它的影響力不斷擴散。叔本華認為:“意識一般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意識主體對于主體自身的意識,二是對于作為意識主體的我們的身外之物的意識。我們自己愈是占據意識的中心,那么外部世界便愈是退居于意識的邊緣。相反,如果我們愈是較少地關注我們自身,那么我們就會愈多地意識到外在對象。”在小說中,庫切不僅譴責白人的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制度,也譴責后革命時代南非黑人對白人實施的暴力。在庫切的非暴力哲學中,暴力是無色的,是跨越種族和膚色界限的,暴力行為所帶來的“恥”不僅僅屬于南非白人,也同樣屬于南非黑人。
四、以文化追求永恒
露茜懷孕了,“就這樣,生命一直延續下去,這條存在線不斷發展,而他在其中的份額,他為此提供的奉獻將會越來越小,直到有一天被徹底遺忘。”這里的“份額”既指生命的血脈,也指文化的脈搏。一個混血兒的出生,讓盧里感覺不到生命延續的驕傲,而是對自我的影響力的不斷縮小,甚至消亡的感傷和無奈。征服和反征服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里或許還沒有完全顯露它的全部特征,但可能在下一代就被完全顛倒過來了,這對殖民統治者來說無異于是一個絕妙的諷刺。這還在母親肚中蠢蠢欲動的胎兒,身上流淌的是黑人和白人的血液,在黑人和白人彼此的仇恨澆灌下孕育出來的生命,哺育他的將還是這個因殖民而飽含仇恨的大地,等待他的又將是怎樣的一個命運呢?露茜對盧里說的“你對他的看法與事情根本沒有關系……他是生活中的事實。”
對于一個無法支配自己命運的個體來說,他可以在支配他者的生命中得到滿足,可這種支配是出于愛還是恨?如果不對,由他人來保護自己的命運,對弱者來說到底是不是另一種不幸?在這個自信的外表下,盧里也困惑、迷惘了。在舊有的黑人屈從白人的關系被交融的文化取代之后,如同盧里這樣的殖民后裔們正在失去其固有的身份標識,體現出后殖民文化下價值理念的無序、混亂。南非在經歷了漫長時間的白人絕對統治之后,多種彼此相異又相互交織的文化正試圖治愈種族隔離制度留下的創傷而作出最艱難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