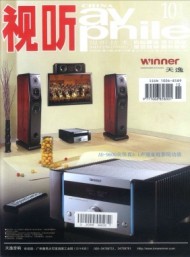張愛玲傳奇范文
時(shí)間:2023-03-25 03:21:28
導(dǎo)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張愛玲傳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xiàn),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擁有張愛玲所有作品版權(quán)的臺(tái)灣皇冠出版社近日宣布,作為對(duì)作家最好的紀(jì)念,又一本流落已久的張愛玲的首部電影劇本――《不了情》將結(jié)集出版。《不了情》是張愛玲的電影“處女作”,她在1946年末至1947年初的短短半個(gè)月時(shí)間里把這個(gè)劇本一揮而就,稍作修改即于1947年2月6日由桑弧執(zhí)導(dǎo)開拍,至3月殺青。同年4月初,《不了情》在上海公映,被譽(yù)為“抗戰(zhàn)勝利以后國(guó)產(chǎn)影片最適合觀眾理想之巨片”。但《不了情》劇本未能保存下來,連電影《不了情》膠片也一度下落不明。直到近年廣州俏佳人文化傳播公司出版“早期中國(guó)電影(1927-1949)經(jīng)典收藏”,電影《不了情》才奇跡般重見天日。劇本是根據(jù)修復(fù)的電影拷貝還原文字的對(duì)白。自然這樣的劇本與原稿還是有距離,有遺憾,但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2005中國(guó)電影產(chǎn)業(yè)投資高層論壇召開
由中國(guó)電影發(fā)行放映協(xié)會(huì)和《資本市場(chǎng)》雜志社共同舉辦的‘2005中國(guó)電影產(chǎn)業(yè)投資高層論壇不久前在北京召開。這是為紀(jì)念中國(guó)電影百年而舉辦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次盛會(huì),是國(guó)內(nèi)首次舉辦探討資本和電影產(chǎn)業(yè)互動(dòng)關(guān)系的高層論壇,也是業(yè)內(nèi)人士對(duì)一系列新問題進(jìn)行思索和探討的良好平臺(tái)。
在電影政策日漸開明、電影業(yè)投資環(huán)境日漸好轉(zhuǎn)的今天,面對(duì)改革的新形勢(shì),論壇主辦方邀請(qǐng)了國(guó)家廣電總局的高層官員、國(guó)內(nèi)外電影業(yè)精英、投融資機(jī)構(gòu)人士、電影創(chuàng)作人員、電影投資商、制片人、發(fā)行商、電影院線機(jī)構(gòu)經(jīng)理人以及電影產(chǎn)業(yè)相關(guān)人士近300人,就電影業(yè)面臨的發(fā)展機(jī)遇與挑戰(zhàn),電影和資本的高效連接,如何把握電影產(chǎn)業(yè)化商機(jī)等問題進(jìn)行研討。論壇致力于在電影和資本之間、在電影產(chǎn)業(yè)鏈各環(huán)節(jié)之間搭建一個(gè)高效交流的平臺(tái),讓大家了解各自在整個(gè)產(chǎn)業(yè)鏈上的價(jià)值,開展更多的競(jìng)爭(zhēng)與合作。
本次論壇還了由國(guó)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zhǎng)、金融學(xué)博士巴曙松牽頭調(diào)查、撰寫的《中國(guó)電影產(chǎn)業(yè)投資分析報(bào)告》。這是國(guó)內(nèi)第一份由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牽頭撰寫、得到電影業(yè)人士廣泛支持的權(quán)威的電影業(yè)投資報(bào)告。巴曙松博士認(rèn)為,在中國(guó)這個(gè)面臨資源短缺和環(huán)境的壓力,而又擁有五千年?duì)N爛文化的國(guó)度,大力發(fā)展對(duì)資源依存度低的傳媒文化產(chǎn)業(yè),將是中國(guó)進(jìn)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途徑之一。而“電影”這一集文化、藝術(shù)與娛樂于一身的產(chǎn)業(yè),市場(chǎng)前景巨大,可以說是文化產(chǎn)業(yè)中一顆璀璨的明珠、中國(guó)最具投資潛力的“鉆石礦”之一,未來很有可能成為中國(guó)內(nèi)需增長(zhǎng)動(dòng)力的新引擎之一。
(馮湄)
首部武俠動(dòng)漫電影上映在即
首部國(guó)產(chǎn)武俠動(dòng)漫電影《勇闖天下》預(yù)計(jì)將在11月初與全國(guó)觀眾見面。這部電影投資達(dá)1000多萬元,采用了目前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片中少見的三維電腦動(dòng)畫與二維電腦動(dòng)畫相結(jié)合的手法,由廣州統(tǒng)一影視數(shù)碼特技制作中心歷經(jīng)兩年多時(shí)間打造而成。據(jù)了解,房祖名有望演唱這部動(dòng)畫片的主題曲。
《勇闖天下》取材于黃飛鴻故事,講述了少年黃飛鴻以武懲惡的勵(lì)志故事。經(jīng)過演繹加工并賦予神話色彩,以適合觀眾的欣賞心理。片中三維的場(chǎng)景如神秘筍林、佛山城、活動(dòng)堡壘、飛弩箭雨等都刻畫得相當(dāng)逼真;而二維的人物則主要表現(xiàn)在武打設(shè)計(jì)上,據(jù)說片中每一個(gè)拳術(shù)腳法都參照真人動(dòng)作設(shè)計(jì)。武戲占到全片70%,復(fù)雜程度遠(yuǎn)超出一般以文戲?yàn)橹鞯膭?dòng)畫片。有專家介紹,這是繼《寶蓮燈》之后,有望再次引爆國(guó)產(chǎn)動(dòng)漫電影市場(chǎng)的大制作。
王義夫首度觸電出演公益電影
兒童賀歲公益電影《淺藍(lán)深藍(lán)》已于9月1日投拍。一批演藝明星、體育明星和社會(huì)名人傾情出演。
片中王義夫和陶虹出演小主人公凱文的父母。凱文是小區(qū)孩子們游戲當(dāng)中的小裁判,他出身體育世家。為了把真正的體育精神自然而然地帶入小凱文的家庭,劇組特意邀請(qǐng)了奧運(yùn)會(huì)六朝元老王義夫出演父親,邀請(qǐng)?jiān)莾?yōu)秀花樣游泳運(yùn)動(dòng)員的陶虹出演母親。
作為奧運(yùn)會(huì)六朝元老的王義夫這次是第一次“觸電”。奧運(yùn)會(huì)上,王義夫英勇拼搏,打完最后一槍后暈倒在地的悲壯情景讓人們記憶猶新,也成為他對(duì)體育精神的親身詮釋。這次,他熱情地接受了劇組的邀請(qǐng),他表示愿意為兒童做些事,為弘揚(yáng)體育精神做些事。劇組請(qǐng)他出演,以圖通過劇情和人物塑造,將他身上折射出來的體育精神給孩子的心靈以潛移默化的影響。
首部僧人抗日電影令人動(dòng)容
篇2
關(guān)鍵詞:王安憶 張愛玲 上海傳奇
上海是近代以來中國(guó)都市文化高度發(fā)達(dá)的大都會(huì),其豐富獨(dú)特的人文內(nèi)涵哺育了許許多多的作家。在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以上海為題材的都市文學(xué)描繪中,張愛玲和王安憶是非常突出的兩位。兩位作家同在上海長(zhǎng)大,熟悉上海生活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對(duì)上海市民,尤其是上海女性的生活習(xí)慣、心理狀態(tài)、審美趣味和價(jià)值觀念都非常了解。共同的地域文化,女性特有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使得二人在創(chuàng)作中有很多相似點(diǎn)。
1.上海―文學(xué)想象的共同空間
張愛玲出生于20世紀(jì)20年代,有一種“上海情結(jié)”。張愛玲文學(xué)寫作的經(jīng)驗(yàn)和想象來源于她所生活的上海,構(gòu)成張愛玲敘述底蘊(yùn)的是上海這個(gè)都市。上海之于張愛玲,其意義如同魯鎮(zhèn)之于魯迅、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從文。張愛玲欣賞上海人于傳統(tǒng)與新潮中那種不失開化的容忍、兼收態(tài)度,以及由此獲得的某種“智慧”。
王安憶也深深熱愛著自己生活著的上海。王安憶出生于20世紀(jì)50年代,、插隊(duì)、返城、改革,時(shí)代的烙印深深融入她的生命。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涉獵各種題材,其書寫狀態(tài)遠(yuǎn)比張愛玲復(fù)雜。王安憶文本中呈現(xiàn)的敘述空間很廣,包括鄉(xiāng)村、小城鎮(zhèn)及上海。然而,總體看來,她的絕大多數(shù)作品都是以上海為創(chuàng)作空間的。對(duì)于上海來講,王安憶雖是個(gè)“外來戶”,但她早已把上海作為自己深愛著的第二故鄉(xiāng)。
兩位生活在不同時(shí)代的作家,以敏感而深刻的眼光,深深眷戀和關(guān)注著上海這個(gè)或許是近代以來中國(guó)最具魅力的都市,把它作為各自的書寫空間。上海給她們提供了施展才華的舞臺(tái),她們也在自己植根于上海的書寫中呈現(xiàn)和延展著上海的景觀,并以各自的文字賦予上海以獨(dú)特的魅力。
2.舊式傳奇的貼膚書寫
1944年,小說集《傳奇》出版后,光艷奪目的張愛玲便一下子躍上了文學(xué)的舞臺(tái)。張愛玲生活在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與香港,帶有濃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上海租界是張愛玲主要的書寫空間。當(dāng)時(shí)的上海是有著特殊的地域色彩的:作為商業(yè)中心,世界性都會(huì),上海承受了江南幾百年累積的富庶和文化,同時(shí),歐美帝國(guó)主義把它作為最后的盤踞地,革命黨人將其視為散播新思想的中心,日寇的侵略又造成上海孤島畸形的繁榮與混亂。
懷著深厚的“上海情節(jié)”,張愛玲取材上海普通小市民生活,以人生的安穩(wěn)作底子,新舊意境雜糅,新舊場(chǎng)景交替,以小觀大,準(zhǔn)確描摹了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與精神狀態(tài)。張愛玲生來就有一個(gè)天才女子的聰慧與高傲,有一種都市人的優(yōu)越感,對(duì)上海都市生活的熟稔、深刻的觀察與領(lǐng)悟、天才的表現(xiàn)與想象,使她用生花妙筆把衰敗的舊家庭、沒落的貴族女人、都市男女的日常生活及對(duì)人性的關(guān)注與時(shí)代變動(dòng)中的道德精神狀態(tài)的把握成功結(jié)合起來,書寫著上海生活與殖民地文化,呈現(xiàn)出舊派小說不可比擬的精神內(nèi)涵與審美情趣。張愛玲和上海是渾然一體的,對(duì)城市的天然親和力與認(rèn)同感使她的敘述高度市井化,成為上海都市的貼膚書寫者。張愛玲的都市小說堪稱中國(guó)現(xiàn)代都市文學(xué)的標(biāo)高。
3.新式傳奇的歷史建構(gòu)
王安憶的都市小說也大都取材于上海,也在續(xù)寫著上海生活的“傳奇”。王安憶認(rèn)為:“其實(shí),每一日都是柴米油鹽,勤勤懇懇地過著,沒一點(diǎn)非分之想,猛然間一回頭,卻成了傳奇。上海的傳奇均是這樣的。傳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還必須格外地將這日月夯得結(jié)實(shí),才可有心力體力演繹變故。別的地方的歷史都是循序漸進(jìn)的,上海城市的歷史卻好像三級(jí)跳那么過來的,所以必須牢牢地抓住做人的最實(shí)處,才不至恍惚若夢(mèng)。”
作為都市上海的闡釋者,王安憶熱切地想擁抱這個(gè)城市,想融入這個(gè)城市,想發(fā)表自己對(duì)這個(gè)城市的想法與看法,這使得她常常自覺地直接跳進(jìn)文本的敘述中,表達(dá)自己的理性思考。在《長(zhǎng)恨歌》的開頭王安憶一往情深地描寫“弄堂”、“閨閣”、“流言”這些具有都市特質(zhì)的對(duì)象,并進(jìn)行理性的概述。王安憶對(duì)上海生活的理性審視使得上海沒有完全融入王安憶的敘述中去,但卻比張愛玲的敘述視角要更開放些、寬廣些,也更具有歷史的意味。王安憶深入都市生活,在對(duì)都市上海進(jìn)行歷史建構(gòu)時(shí),在理性思考中探尋出比張愛玲更廣闊和豐富些的都市生活的“芯子”。
綜上所述,張愛玲與王安憶都以上海作為自己的書寫空間。比較而言,張愛玲用高度市井化的敘述,在相對(duì)靜止的敘述時(shí)間和相對(duì)封閉的敘述空間內(nèi),以人生的安穩(wěn)作底子,書寫著上海三四十年代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因素疊加下的日常生活的舊式“傳奇”。應(yīng)該說,王安憶的敘述視點(diǎn),既有其個(gè)人的文學(xué)取向,更有歷史發(fā)展所提供的契機(jī)。張愛玲和王安憶的都市小說文本,從不同維度為讀者構(gòu)建了一道豐富多彩、意蘊(yùn)深厚的上海景觀,我們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到上海這個(gè)都市在文學(xué)文本中的闡釋的巨大變遷。
篇3
三毛把自己無私的奉獻(xiàn)給了無垠的撒哈拉沙漠。她用筆書寫了自己的生活,平樸的文字、真實(shí)的感情。她用一個(gè)小女子的心態(tài)活著、愛著、寫著。那么多的文字里是同一個(gè)三毛,我在讀那些恍如隔世的故事時(shí),甚至可以看到寫字的三毛、流浪的三毛、快樂抑或悲傷的三毛。她是這樣真,真到了純。我愿意相信那些剖析自我的人,那些人寫出的文字是真正屬于自己的傳奇。有時(shí)去讀那些泛濫在市面上的小說,我總是覺得,沒有經(jīng)歷過的人,寫下的文字,不過是一堆沒有骨架的腐肉。
荷西死了,三毛的筆終于不再屬于自己,寫下的文字也不再是自己的傳奇。她寂寞地獨(dú)自生活,碰上了另一個(gè)男子——王洛賓。她以為她依舊可以如曾經(jīng)那般放下一切不顧一切的去愛,然而她錯(cuò)了,在她來說無所謂的年齡差距卻沒有讓王洛賓勇敢愛她。荷西走了,王洛賓走了,文字也走了,三毛終于決定做自己的終結(jié)者,用一只絲襪來結(jié)束自己飄忽的生命。
對(duì),飄忽的生命。靈魂太過輕靈就無法依賴重心穩(wěn)穩(wěn)站著,或許最后終結(jié)是最好的結(jié)局。
另一個(gè)傳奇女子的生命卻太過厚重,如同大上海里妖嬈的胭脂,暈開來,是濃重的猩紅,不停的蔓延,無法停息。
她叫張愛玲。她筆下的愛情總有著太多的無奈,有好的結(jié)尾如《傾城之戀》,也有始終的無奈像《半生緣》。張愛玲的才氣是時(shí)代給予的。在那個(gè)奢靡的城市里,我想象著她燃著的煙夾在手指上,絲絲苦澀纏卷著她的心扉。我似乎能看到她深冷如幽潭的目光俯瞰著這大上海繁華背后的頹萎。那姿態(tài)何等冰冷寂寞,‘眾人醉唯我獨(dú)行’是境界,更是痛苦。
她寫了那么多的愛情,寫的都是別人的,她可以看透別人的心,我無話可說。這世上聰明如三毛可以剖析自己的人極少,如張愛玲可以剖析別人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若荷西是三毛愛和魂的終結(jié)者,那張愛玲的命運(yùn)更是慘淡許多。張愛玲最終選擇離開賣國(guó)賊胡蘭成——選擇離開了她唯一的愛。現(xiàn)實(shí)和她的小說何其相似,最終總是無奈的結(jié)局。張愛玲再也寫不出什么好的東西了,再也無法愛上別的什么人了,而這,是她選擇離開時(shí)她就知道的。看——她是如此聰明。
篇4
另一則是張愛玲,這個(gè)“民國(guó)臨水照花人”,她用自己傳奇的人生點(diǎn)燃了無數(shù)美麗的煙花,瞬間璀璨,而后,彈指湮滅。
傳奇的張愛玲,寫過一本《傳奇》的集子,她筆下的女人們,曼楨、七巧、白流蘇,將傳奇的一生寄附于傳奇的時(shí)代。是的,張愛玲的誕生,那些如花似玉的音容、如夢(mèng)似幻的人生能夠存在不是歷史的偶然。她們必然也只能存在于民國(guó)。
亂世出英雄,悲痛出詩人,正所謂國(guó)家不幸詩家幸。唐傳奇的傳世是由于傳奇的唐代,僅那公公搭上兒媳的皇家愛情就足夠令人嘆為觀止。
正因?yàn)槊駠?guó),因?yàn)槟莻€(gè)戰(zhàn)火連天中反現(xiàn)妖異美的亂世,才容得下這么瑰麗的傳奇。張愛玲讓一座城的淪陷成全了一個(gè)女人的愛情,那么民國(guó)就是用整個(gè)世道的混沌成全了無數(shù)女人的傳奇。
《傾城之戀》改編成電視,女主角由陳數(shù)出演,我本來不甚以為然。看過幾集后卻覺得,雖然并不那么驚艷稱心,卻也有演出了幾分張愛玲骨子里的清冷凄楚之意。張愛玲,她以一種獨(dú)特的色調(diào)孤存,那種色由朱紅襯以暗紫,亮藍(lán)揉進(jìn)墨綠,那是熱鬧之后的荒涼,是繁華過后的悲哀。她用涼薄的笑掩飾自己的孤獨(dú),用莫大的熱情來面對(duì)人世的失望。這樣矛盾的一個(gè)人真真有顆七竅玲瓏心,她的靈魂活在筆下的每個(gè)人物身上,身世如她的白流蘇也分得了一魂一魄。
這樣的女子,若要尋個(gè)得當(dāng)?shù)娜税缪荩蚁肟傇撚袔讉€(gè)基本條件。一自然是要貌美,美麗的女子才有創(chuàng)造傳奇的資本。然則,美固然重要,卻不是絕對(duì)條件,潘玉良容貌說不上國(guó)色,卻耽不了她演繹一場(chǎng)驚天動(dòng)地可歌可泣的傳世大戲。張柏芝美得毫無爭(zhēng)議,卻讓周璇在她現(xiàn)代容貌的演繹下黯然失色。所以更重要的是那骨子里的清冷,這要靠眉目間那點(diǎn)清朗之氣來把握。清朗之氣,一是清明二是硬朗,所以選的女演員在柔媚中總該帶點(diǎn)丈夫氣。
眉目清朗的陳數(shù)“發(fā)跡”于《暗算》黃依依,那也是個(gè)民國(guó)女子。民國(guó)因?yàn)檎值膭?dòng)蕩混亂,反而給了文化更多的自由和可能。五四之后舊的已破新的還未建立,一方面封建遺老遺少們固守自己浸染鴉片氣味的長(zhǎng)袍馬褂繡花鞋,而留洋少爺小姐們狂熱的追求法蘭西英吉利風(fēng)的禮帽西裝緊身衣。
黃依依就是“海龜”先驅(qū)的一員,由千年禁錮到徹底自由,猛然勃發(fā)的生命意識(shí)讓愛之火熊熊燃燒。她就像一頭剛出籠的懵懂小獸,這頭小獸知道要去愛卻還不懂該怎樣去愛,怎樣讓愛之火在一個(gè)安全的范圍內(nèi)燃燒,既獲得溫暖,又不會(huì)灼傷彼此。她對(duì)愛的執(zhí)著熱烈奔放實(shí)在令人嘆為觀止。安在天的靜水深流沒能澆熄這捧躍動(dòng)的火焰。愛之火給了她溫暖,卻也最終焚毀了肉身。
白流蘇不是黃依依,她更像張愛玲自己。沒落的遺老家族出身,放不下尊貴的身份,卻不得不接受現(xiàn)實(shí)的窘迫。想保留自己的自尊,卻不得不拿自尊換取體面生存的權(quán)利。就像晴雯嘆詞中唱的“心比天高,身為下賤”。在這樣的夾縫中,想追求幸福都要小心翼翼,時(shí)不時(shí)問自己?jiǎn)杽e人“可不可以”。 這樣的環(huán)境使白流蘇形成“賭徒”的性格,她唯一的賭注是自己的青春和美貌,為了掙脫命運(yùn)的悖論庸俗的賭一把。當(dāng)愛來到身邊,她不敢相信,因?yàn)檫@種不信,也因?yàn)橄嗨瞥錾矸读牟恍拧K麄儌z就像兩只蝸牛,玩起了愛的游戲。躲在厚重的殼里,不斷伸出觸須想探知對(duì)方心意,一旦觸須落空,就趕緊縮回,用冷漠來掩飾自己的失望和受傷。愛情,平白多了許多挫折。直到香港城的淪陷,在非常時(shí)刻,他們才勇敢的擁抱在一起,忘記身上的負(fù)累,忘記身后的刺芒,忘記所有責(zé)任義務(wù)虛榮世俗,大膽擁抱自己的愛自己的幸福。
但是,時(shí)局安定之后,他們又會(huì)縮回自己的殼中,開始反復(fù)的試探吧。張愛玲說“他們開始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cè)谝黄鸷椭C地活個(gè)十年八年。”如此通透的諒解,也不過維持十年八年,比起人類不算長(zhǎng)的壽命,這也算不上長(zhǎng)吧。這是人性的劣根,是人生的宿命,天長(zhǎng)地久只是童話。小說的結(jié)尾,不像電視那么光明。電視要給太太小姐們看,結(jié)尾太悲了是沒人高興的。就像前些日子的《宮鎖心玉》,聽說芒果臺(tái)要播一個(gè)悲劇結(jié)局,聽說而已,就險(xiǎn)些被四爺黨八爺黨峰冪粉的口水淹死。
張愛玲可怕不著這個(gè)。戰(zhàn)火暫時(shí)平息了,一切如常,白流蘇和范柳原的婚姻終成美滿,但白流蘇最后笑吟吟的將蚊香盤踢到桌下,那一腳不免又讓人心灰起來。張愛玲,她是不肯讓你痛快笑一場(chǎng)的。就算已經(jīng)王子公主從此生活在一起,她也得給你留個(gè)巫女在窗外冷笑的楔子,讓你心里咯噔一下,惴惴一時(shí)。
篇5
【關(guān)鍵詞】變態(tài)母性;情緒記憶
一、張愛玲出生在一個(gè)沒落的官宦家庭
母親黃逸梵是清末南京水師提督黃軍門黃翼升的孫女。黃逸梵出生之前即喪父,出生后不久,母親也染病去世。因此,她從未享受過親情的溫暖,致使她對(duì)親情相當(dāng)?shù)氐钡阶约撼蔀槟赣H,她的這種心理也未曾改變過。
四歲那一年,張愛玲經(jīng)歷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分離:時(shí)年二十六歲的黃逸梵拋夫別子,與小姑子遠(yuǎn)赴法國(guó)留學(xué),直到張愛玲八歲才回國(guó)。然而不久,張父又故態(tài)復(fù)萌,黃氏忍無可忍,終于再次離家,不長(zhǎng)時(shí)間之后就與張廷重離婚,從此再?zèng)]有踏入張家半步。她解脫了,年幼的張愛玲卻從此少了更多的被愛的希望,這給她幼小的心靈帶來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她感覺自己是被徹底拋棄了。這種心理,使她對(duì)愛抱有最初的懷疑態(tài)度。
在《私語》中,張愛玲曾說道:“最初的家里沒有我母親這個(gè)人,也不感覺到任何缺陷,因?yàn)樗茉缇筒辉倌抢锪恕!雹偻昴笎鄣娜笔В瑢?duì)張愛玲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母親只是一個(gè)名詞,存在在她的頭腦中。這也反映出,張愛玲與母親在一起的快樂時(shí)光是少之又少的。唯其因?yàn)樯伲瑥垚哿岵艑⒁稽c(diǎn)一滴都印在腦海中。對(duì)于這少得可憐的時(shí)光,張是很珍視的。
二、作品中不健全,甚至變態(tài)母性形象的來由
“如果說,四歲那年與母親分離時(shí),張愛玲因?yàn)槟挲g的關(guān)系,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種物理空間意義上的分離,那么十余年后她與母親的再次分離則是張愛玲清醒認(rèn)識(shí)到的心理空間意義上的分離。
……如果說四歲那年母親的遠(yuǎn)去,并未讓年幼的張愛玲覺得有‘任何缺陷’,那么這一次母女間的分歧卻讓她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嚴(yán)重的心理危機(jī)。”[1]母女兩人自有不同的思想,并且互相不理解對(duì)方。她雖然在母親身邊,但是,她的世界里還是無愛的。她是裸的一個(gè)人。而在《童言無忌》中,張愛玲寫她當(dāng)時(shí)對(duì)母親的感覺:“在孩子的眼里,她是遼遠(yuǎn)而神秘的。”[2]感覺母愛遼遠(yuǎn)而神秘,是因?yàn)殚L(zhǎng)期的分離,造成了張愛玲與母親的隔膜。它在張愛玲的心上造成了難堪與折磨,愛只能一點(diǎn)點(diǎn)被吞噬掉。很難想像這樣的母親,究竟能給女兒多少真正的關(guān)懷?張愛玲用這一系列語言來描述對(duì)母親產(chǎn)生懷疑后的無依與絕望。這種無依與絕望感在張愛玲的身上來得分外強(qiáng)烈,敏感內(nèi)省的氣質(zhì)使她對(duì)外在傷害的感覺纖細(xì)而深刻。
暴虐的遺少父親,極少相處而又冷淡的母親,這就是張愛玲全部的來自家庭生活的感情體驗(yàn)。沒有體味過深厚的父母之愛的人,又怎能寫出充滿溫情的作品?因此,她筆下才出現(xiàn)了不健全、甚至變態(tài)的母性形象。
三、在《傳奇》中,最具體典型性、最復(fù)雜也最為變態(tài)的是曹七巧
曹七巧出身寒門小戶,原本是一個(gè)青春潑辣、生活無憂無慮的美麗姑娘。三十年前,她由兄嫂安排嫁給了患骨癆的姜家二少爺。在姜家,她雖是主人,但她貧寒的出身、粗淺的見識(shí)與言語,使她經(jīng)常受到妯娌們的鄙夷,甚至丫頭們都看不起她。在這冷酷的世界,她沒有做人的尊嚴(yán),沒有人關(guān)心她、理解她、在乎她,她體會(huì)不到人生的樂趣,人間的溫情,時(shí)刻伴隨著她的是孤獨(dú)與空虛,因此,她便將所有的心思都傾注在金錢上。為了錢,她在分家產(chǎn)時(shí)大鬧,她罵走了年幼的侄兒,罵走了她唯一愛過的男人姜季澤。她緊緊地抓住了錢,她的生命中只剩下了錢。對(duì)她來說,錢是最可靠的。對(duì)金錢的極端占有欲,使她的性格變得狂躁、尖刻,她漸漸失去了溫厚的本性。她對(duì)誰都不信任,包括自己的兒女。
如果說,之前的曹七巧是金錢異化的結(jié)果,那么她對(duì)兒女的態(tài)度則體現(xiàn)了性壓抑對(duì)人性的戕害。曹七巧渴望正常的性生活,可是她的丈夫根本就不能滿足她。她愛上了三少爺姜季澤,幾次勾引,都沒有成功。性的壓抑,使七巧變得暴躁變態(tài)、喜怒無常。不知不覺中,她將自己郁積多年的怒氣瘋狂地發(fā)泄在自己的一雙兒女身上。她為兒子長(zhǎng)白娶了一房媳婦,卻又時(shí)時(shí)刻地霸占著兒子,讓兒子一夜夜地?zé)裏熍荩T使兒子說與媳婦的閨房私事,然后再添油加醋地在牌桌上告訴眾人,羞走了親家母,媳婦不敢反抗,不敢表示不滿,在變態(tài)婆婆的之下,最終積郁成疾而死。另一個(gè)丫頭絹姑娘在扶正后不久就吞食鴉片自殺了,這自然又是七巧變態(tài)行為下的犧牲品。兒子從此不敢再娶親,只往窯子里鉆。七巧終于達(dá)到了霸占兒子的目的。
女兒長(zhǎng)安也并未逃出母親的魔掌。女兒因?yàn)閼賽鄱皶r(shí)時(shí)微笑著”,也不再反抗她,并且努力戒煙,她心里不由得就有氣。她以女兒的名義邀請(qǐng)女兒唯一可能的結(jié)婚對(duì)象吃飯,卻又故意在童世舫面前詆毀女兒,徹底破壞了女兒的婚事,將女兒一步步逼入“沒有光的所在”。七巧變成了一個(gè)極端變態(tài)與瘋狂的母親,其行為讓人不寒而栗。
七巧的變態(tài)除了自身的性格缺陷之外,主要是外部環(huán)境造成了她人性的毀滅。
張愛玲筆下的變態(tài)女性形象的獨(dú)特性在于:“她們是中西文化混雜的現(xiàn)代城市北京中為金錢名利異化、物化,為感情壓抑折磨的變態(tài)典型,這些生活在十里洋場(chǎng)的變態(tài)女性顯得更寫實(shí)、更世俗化。”這些都與張愛玲早年對(duì)女性的情緒記憶密切相關(guān)。也許,我們還應(yīng)該感謝她這段不幸的經(jīng)歷,使她創(chuàng)造除了如此獨(dú)特的母性形象,成就了她對(duì)女性生存狀況與心理的深入挖掘與思考,有了她作品與人生的“傳奇”。
注釋:
篇6
關(guān)鍵詞:張愛玲小說;浪漫主義;個(gè)人身世;安穩(wěn)情懷
張愛玲作為上個(gè)世紀(jì)四十年代有過重要影響的上海女作家,其蒼涼與華麗的文學(xué)風(fēng)格帶有強(qiáng)烈的浪漫主義特征。當(dāng)然除了浪漫主義理論影響,張愛玲的生活經(jīng)歷、社會(huì)姿態(tài)乃至氣質(zhì)秉性都影響了她的創(chuàng)作,所以對(duì)于張愛玲小說的浪漫主義問題,不能將作品與浪漫主義理論逐一對(duì)應(yīng),要充分考慮到時(shí)代精神、人文環(huán)境和個(gè)人生活際遇的變遷,對(duì)其小說的浪漫主義問題進(jìn)行個(gè)性化的梳理。
張愛玲的小說從不塑造時(shí)代英雄的傳奇,她塑造的是可憐可恨的平凡男女,在參差對(duì)照中追求真實(shí)和素樸的美,通過小說的敘述中表達(dá)郁郁蒼蒼的身世之感,既是自己生活際遇和女性命運(yùn)的感傷,又蘊(yùn)藏著對(duì)人世命運(yùn)的悲觀和通達(dá)。對(duì)于張愛玲小說的浪漫主義風(fēng)格,我認(rèn)為主要有以下兩點(diǎn):
一、個(gè)人身世的感傷
張愛玲承自清末名臣李鴻章,如此傳奇的身世,影響了張愛玲一生的創(chuàng)作。張愛玲小說的主觀性強(qiáng),大膽表現(xiàn)人性和欲望,流動(dòng)著強(qiáng)烈的個(gè)人情緒。早期的小說,《心經(jīng)》的小寒,《沉香屑 第一爐香》的葛薇龍都帶有張愛玲生活經(jīng)歷的影子,一直到移居美國(guó)后創(chuàng)作的《小團(tuán)圓》,個(gè)人身世的感傷風(fēng)格更加強(qiáng)烈。徐子?xùn)|認(rèn)為“自傳體文學(xué)”出現(xiàn)在四十年代后,有一個(gè)由社會(huì)轉(zhuǎn)向私人的傾向,《小團(tuán)圓》沿著這一方向繼續(xù)往極端發(fā)展。作家在她中年至晚期的“美國(guó)階段”痛下決心,只寫自己,撕肝裂肺,不厭其煩,而且基本上,只寫男女關(guān)系與母女關(guān)系。”①與同時(shí)代成長(zhǎng)起來的知識(shí)女性相比,張愛玲的經(jīng)歷又顯得更為復(fù)雜。
張愛玲的英文自傳體小說《雷峰塔》和《易經(jīng)》取材于張愛玲的生活經(jīng)歷,小說中琵琶與露的母女關(guān)系是小說中刻畫得細(xì)致入微、撼人心魄的一筆,與以往文學(xué)作品中慈愛寬容的母親相比,露可以說是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獨(dú)特深刻的母親形象之一。“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diǎn),看完《雷峰塔》和《易經(jīng)》,你才發(fā)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shí)是母親”,②在張愛玲的一生中母親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她對(duì)母親的情感也是矛盾復(fù)雜的,既想在她面前有所成就又不免自慚形穢,既想與她保持距離心里又藏著敬愛。這樣愛恨交織、層次豐富的情感成為她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要參照。
“浪漫的靈魂是一種分裂的靈魂,沖突只在內(nèi)心,在靈與肉,情與理之間,而不在(至少不直接在)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人與人之間”。③在《雷峰塔》中,一段婢女葵花與保姆何干的對(duì)話耐人尋味:“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道世界都變了。”禁錮女性的雷峰塔是倒了,但女性自身內(nèi)心的禁錮卻沒有倒塌。在新舊文化的激烈交鋒中,露和琵琶都是傳統(tǒng)家庭走出的新女性,她們受到西方的新式教育,但她們走出家門走向社會(huì)后,又發(fā)現(xiàn)社會(huì)對(duì)女性的包容和女性的生存空間都是有限的,因此她們?cè)诰褚庾R(shí)上依然帶有傳統(tǒng)的枷鎖,礙于自身的倫理責(zé)任與性別角色,又無法掙脫內(nèi)心欲望的呼喊,在過去與現(xiàn)在,情理與欲望之間徘徊無助。
張愛玲的小說刻畫了眾多畸形病態(tài)的母女關(guān)系,如《金鎖記》中的七巧,《花凋》中的鄭太太,張愛玲無意描述這種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倫理道德與責(zé)任,而是在母女關(guān)系中表達(dá)個(gè)人身世的感傷,是對(duì)于傳統(tǒng)道德與個(gè)人自由,性別責(zé)任與內(nèi)心欲望的掙扎與矛盾。她的小說一再解構(gòu)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母親形象,她用深刻細(xì)膩的筆觸批判著母親,也鞭笞著個(gè)人的自私無情。對(duì)母親的復(fù)雜情感,想要走出而不得,成為禁錮一生的陰影,這樣復(fù)雜的情感一直影響著張愛玲的創(chuàng)作,乃至人生。
二、亂世中的安穩(wěn)情懷
在張愛玲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很少談及政治,她書寫的是宅門弄堂里小兒女的愛恨情仇和現(xiàn)代都市的摩登生活,對(duì)于張愛玲來說,時(shí)代歷史只是一個(gè)華麗的場(chǎng)景和促使小說發(fā)展的契機(jī),無論時(shí)代如何變幻,對(duì)于安穩(wěn)情懷的追求始終沒有改變。面對(duì)新舊文化參差、戰(zhàn)火紛飛的時(shí)代,張愛玲企圖從過去尋找詩性的記憶,可是文明的腳步已經(jīng)讓現(xiàn)代人無法回到獸性的時(shí)代,當(dāng)戰(zhàn)火摧毀了文明與過去,張愛玲的精神家園也坍塌了,她極力想抓住當(dāng)下真實(shí)瑣屑的生活,它是短暫的安穩(wěn),但仍然是永恒的。在張愛玲的藝術(shù)世界里,真實(shí)瑣屑生活是順應(yīng)人性的、自然的追求,是逃避過去與未來的人生形式,在這樣的人生形式里,安穩(wěn)是對(duì)時(shí)代宿命的悲觀,是悲觀后的通達(dá)。
張愛玲寫的是亂世中的普通市民,她無意渲染人世的苦難,而是以現(xiàn)代女性的視角刻畫古老與現(xiàn)代交匯下,戰(zhàn)爭(zhēng)烽煙中最普通真實(shí)的人性。 《傾城之戀》是張愛玲小說中刻畫戰(zhàn)爭(zhēng)背景下平凡男女的經(jīng)典之作,寫的是小兒女的日常生活與情感算計(jì),身處亂世,她在這樣的背景下借主角命運(yùn)表達(dá)了孤獨(dú)蒼白的人生無常,幻滅之后對(duì)人世生存的安穩(wěn)情懷。當(dāng)城市文明的腳步越來越近時(shí),都市人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對(duì)人生和生命普遍的懷疑和悲哀,文明的進(jìn)步使人類追求生活的歡愉,當(dāng)文明倒塌,活著的意義又是什么? 張愛玲的筆觸是真實(shí)殘酷的,這是張愛玲獨(dú)特的人生體驗(yàn)和歷史視野。
不同于我們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慣性想象,戰(zhàn)爭(zhēng)最大的劫難,是人世普遍的蒼涼。戰(zhàn)爭(zhēng)摧毀了文明,人無法從現(xiàn)在和過去的記憶中尋找依靠,在生死劫難中只有繼續(xù)生存下去,尋找自私平凡的生活。白流蘇和范柳原是戰(zhàn)爭(zhēng)背景下的凡人,張愛玲無意塑造戰(zhàn)爭(zhēng)影響下頓悟的英雄,她刻畫的是自私和軟弱的普通人,在過去與現(xiàn)在的矛盾中,張愛玲的小說選擇了安穩(wěn)情懷,時(shí)間和變化都是如此倉促,人只有緊跟文明的節(jié)拍,抓住當(dāng)下的物質(zhì)生活,但是在時(shí)代的變遷中,安穩(wěn)和文明只是暫時(shí)的,生活充滿了破壞的威脅,這是張愛玲對(duì)人生的感懷和疑惑。她不推崇完美的人性,她喜歡的是真實(shí)、瑣屑的人性,正是這些短暫的安穩(wěn)構(gòu)成了時(shí)代的永恒。她無意去創(chuàng)造英雄美人的神話,她忠于人性的真實(shí)和復(fù)雜,對(duì)世情保持自己冷靜的思考與嘲諷,在平凡瑣屑的世俗生活中去收獲千帆過盡后的平靜和寒涼。張愛玲的安穩(wěn)情懷是一種帶有嘲諷的安穩(wěn),是在亂世中尋求精神的慰藉,是充滿懷疑蒼涼想象,在自己建構(gòu)的小說圖景中尋找短暫的心靈歸宿。
三、結(jié)語
張愛玲的小說帶有強(qiáng)烈的主觀色彩,她從不隱藏個(gè)人的自私和欲望,她表達(dá)著最真實(shí)細(xì)膩的生活體察和生命經(jīng)驗(yàn)。張愛玲的浪漫主義帶有悲觀蒼涼的性質(zhì),是對(duì)過去的失落和對(duì)未來的懷疑。在新舊交替、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參差碰撞的時(shí)代,張愛玲選擇了安穩(wěn)情懷作為精神的家園,孤獨(dú)蒼白的家園圖景是真實(shí)基本的存在,在那些平凡瑣屑的存在中收獲短暫的慰藉。現(xiàn)在是悲觀的,卻無法從過去中尋找歸屬,在更大的破壞中抓住那一點(diǎn)安穩(wěn)的情懷,蘊(yùn)藏著對(duì)時(shí)代和人生失落與幻滅后的通達(dá)理解。(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
注釋
① 許子?xùn)|:《張愛玲晚期小說中的男女關(guān)系》,見《許子?xùn)|講稿.第2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② 張瑞芬:《童女的路途: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jīng)〉》,見張愛玲《易經(jīng)》,北京出版集團(tuán)公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
③ 許子?xùn)|:《郁達(dá)夫風(fēng)格與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的浪漫主義》,《許子?xùn)|講稿.第2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86-87頁。
參考文獻(xiàn)
篇7
知道胡蘭成,自然是因?yàn)閺垚哿帷_@個(gè)仿佛一直生活在舊上海灘的女子一直是我眼中的傳奇,透過她的文字,在那滿目繁華抑或蒼涼和世俗背后,分明是個(gè)翩翩濁世佳人,宛如邈姑射仙人的出塵與蹁躚。然而,卻有個(gè)叫胡蘭成的男子讓她落了紅塵,結(jié)了緣復(fù)又?jǐn)嗔司墸瑥拇死纤啦幌嗤鶃怼K裕诳赐辍督裆袷馈业那楦袣v程》時(shí),我覺得,他的不守節(jié),在私人生活上也暴露無疑。《今生今世》的胡蘭成,是中國(guó)文學(xué)中難得一見的唐璜式人物。他對(duì)女性,情雖不偽,卻也不專,他要的是“此時(shí)語笑得人意,此時(shí)歌舞動(dòng)人情”,而他的情意會(huì)隨其行蹤的轉(zhuǎn)移而改變,焉能系于一身!他自認(rèn)為是“永結(jié)無情契”的高人,旁人看來,到底只是個(gè)朝秦暮楚的蕩子。對(duì)胡蘭成,是可以罵一句“負(fù)心薄幸”!而《今生今世》便也通篇都成了一句推辭和借口。
全書中胡蘭成回憶了一生中六個(gè)重要女子:婚后七年病歿的發(fā)妻玉鳳,“民國(guó)女子”張愛玲,武漢護(hù)士周訓(xùn)德,溫州范秀美,日本女子一枝,還有老來相伴的奇女子佘愛珍。胡蘭成一路走來,人生竟有如此多的偏離與轉(zhuǎn)折!他總是自稱“天涯蕩子”,他說,“回到天地之初。像個(gè)無事人。且是個(gè)最最無情的人。”多情與無情,對(duì)于這么一個(gè)天涯蕩子,原本就不是那么分明的。
才子散文,胡蘭成堪稱個(gè)中翹楚,巨奸可為憂國(guó)語,熱中人可作冰雪文,評(píng)諸胡蘭成,倒也貼切。然而,他的多情節(jié)虧使文品也變得面目可憎,但他卻不自知,他逃離武漢后曾寫就《武漢記》一書,內(nèi)中大量并詳細(xì)地寫了他與武漢護(hù)士,文中稱為小周的周訓(xùn)德的相識(shí)相處,并寄往上海一心向張愛玲賣好,張回信一句“看了開頭,實(shí)在看不下去”打發(fā)了他,此時(shí)的胡蘭成竟又驚異:“愛玲也會(huì)吃醋的么?”他復(fù)又解釋說“自覺與愛玲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這紅塵的糾纏又怎能煩擾她的心?”乍聽之下倒真該笑罵這個(gè)文人一聲“憨厚爽直不解機(jī)心”了,可這又怎么可能?!胡蘭成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當(dāng)年的紅人,汪偽南京政府宣傳部政務(wù)副部長(zhǎng),《中華日?qǐng)?bào)》社論委員會(huì)主筆,在政治上實(shí)是慣于官宦沉浮、長(zhǎng)袖善舞又游刃有余,后一路逃命到日本,處處留情又怎會(huì)是個(gè)不解風(fēng)情的榆木疙瘩?張愛玲說:“你何必在我面前遮掩?”胡蘭成的借口由此可見一斑。
“女人矜持,恍若高花,但其實(shí)亦是可以被攀折的,惟也有拆穿了即不值錢的,也有是折來了在手中,反復(fù)看愈好的。”胡蘭成深明男女關(guān)系的個(gè)中三昧,“今生無理的情緣,只可說是前世一劫,而將來聚散,又人世的事如天道幽微難言。”在與張愛玲分手的許多年后,仍說“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guān)于張愛玲的,便皆成為好”,然后一邊說一邊又走到新的情感中去,這些話,自然又成了蒼白的借口,他背叛的遮羞布!
不過還好,張愛玲及時(shí)解放了自己。在那封著名的絕交信中,她說:“我已經(jīng)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的。這次的決心,我是經(jīng)過一年半的長(zhǎng)時(shí)間考慮的,……你不要來尋我,即或?qū)懶艁恚乙嗍遣豢吹牧恕!彼憩F(xiàn)出了高妙和收斂的姿勢(shì),盡管她仍然傷心,在信中附了三十萬元。
篇8
張愛玲(1920-1995)近百年中國(guó)最知名女作家,出身名門,一生特立獨(dú)行。代表作《傳奇》《流言》等。
作者手記 民國(guó)女子里,張愛玲是最有現(xiàn)代感的一位,這種現(xiàn)代感,包括她對(duì)于愛情和故鄉(xiāng)的理解。她原本對(duì)愛情并不執(zhí)著,對(duì)故鄉(xiāng)也無概念,她的小說縱然多言及情事,也寫得理性冷冽,但真正進(jìn)入愛情的實(shí)戰(zhàn)中,才發(fā)現(xiàn),她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個(gè)人,但最終她還是走出了愛情也遠(yuǎn)離了家園。下文圍繞“愛情”與? 故鄉(xiāng) ?兩概念,展現(xiàn)張愛玲生命里的? 重 ?與? 輕 ?。
《異鄉(xiāng)記》
1946年,火車上,穿著藍(lán)棉袍的張愛玲安靜地坐著,旁邊是一個(gè)鄉(xiāng)紳模樣的男子。周圍人聲喧囂,張愛玲從早晨坐到黃昏,到站了,前面的站牌上,寫著“杭州”。
男子帶張愛玲到親戚家投宿,張愛玲艱難地跟人打著招呼,被安排到一個(gè)房間,和一個(gè)女人擠住在一起。她不知怎么跟對(duì)方搭訕,只有把自己壓縮再壓縮。深夜,她捂嘴流淚,心里問:“蘭成,我離你很近了嗎?”轉(zhuǎn)汽車,到溫州。胡蘭成正在生爐子,抬頭看見她,一驚。他又警覺地看了眼四周,低聲喝道:“你來做什么?”屋里,一個(gè)女人問:“誰來了?”胡蘭成回頭答:“我妹妹。”三人在燈下坐著。胡蘭成說,我現(xiàn)在還是不安全,只說你是我妹妹吧。指著那個(gè)女人說,這位是范秀美,這次多虧了她護(hù)我一路到這里。張愛玲想問什么,還是沒有說。
張跟胡街上散步,竭力快樂地談文學(xué),胡蘭成只是漫不經(jīng)心,又說肚子疼。兩人回到旅館,范秀美來了,胡蘭成馬上像個(gè)孩子一樣向她訴說起自己的痛苦來。張望著兩人,不覺愕然。
閃回到1943年,上海。胡蘭成敲響一家公寓的門,一個(gè)女聲說:愛玲小姐不在。胡蘭成留下個(gè)字條離去。到家接到電話,說,愛玲小姐明天來訪。次日,張愛玲坐在他的房間,安靜、蒼白、寡言。胡蘭成滔滔不絕說起自己的經(jīng)歷,張聽得興味盎然,她很少這樣。出門時(shí),胡蘭成做了個(gè)的姿勢(shì),在她頭上一比,說:你這么高,怎么可以?張愛玲瞬間驚詫,但也是笑了下。
胡蘭成帶了詩集到張愛玲家看,張愛玲邊看邊評(píng)論,隨口一說,便舌燦蓮花,讓胡蘭成傾倒不已。
又閃回至張愛玲的上海公寓房間,胡蘭成說:“我不喜歡戀愛,我要和你結(jié)婚。”張愛玲微笑:“我想好了,將來你在我這里來來去去亦可,你知道,我不在乎形式,連鄉(xiāng)愁這種東西都沒有。”胡蘭成說:“那怎么行,你是一個(gè)女人。”張愛玲說:“我只想將來去找你,我們?cè)谶叧腔椟S的油燈下重逢。”閃回胡蘭成家中,他的妻子歇斯底里地扇了他一耳光,痛哭著去收拾箱子。
鏡頭切換:胡蘭成和張愛玲共同打開一張大紅婚書,張愛玲寫道:“胡蘭成先生和張愛玲小姐,結(jié)為夫妻。”胡蘭成添上:“愿歲月靜好,現(xiàn)世安穩(wěn)。”張不以為意地一笑,胡蘭成正巧看見,不由得驚異了,對(duì)這個(gè)女子,他其實(shí)并不真的懂得。
胡蘭成逃亡去武漢,認(rèn)識(shí)了護(hù)士小周,迅速墜入愛河,和她的戀愛是輕松的,追逐打鬧,或去江邊散步,非常快樂。他把這些寫進(jìn)文章,給張愛玲看。張很不愉快,兩人有點(diǎn)冷戰(zhàn)。
抗戰(zhàn)勝利了,胡蘭成被通緝,張愛玲送他,說天涯海角都會(huì)去找他。他們終于在昏黃的油燈下重逢了,卻是三個(gè)人而不是兩個(gè)人。張愛玲驚覺,那愛情不過是一場(chǎng)想象,這世上,又有多少真正的懂得,都不過是誤解碰撞上誤解。
不得已張愛玲坐船離去,在船上淚落如雨,到這時(shí),她才真正感到是在異鄉(xiāng),相愛如在故鄉(xiāng),不再愛,便瞬間變成異鄉(xiāng)。
篇9
張愛玲,那個(gè)有著“惡俗不堪”的中國(guó)名字的女人,那個(gè)被無數(shù)文人墨客描了又描寫了又寫的癡情女子。她在自己編織的文字與夢(mèng)魘里從容穿梭,可一到自己的感情生活,卻即可變得手足無措。在那楨黑白照片里,她有著凜冽的眼神,仿佛她所要的一切早已被她的纖纖素手緊握。只是當(dāng)她看向掌心時(shí),卻分不清那糾纏著的生命線的走向。她也只是個(gè)被命運(yùn)拽著走的可憐女人,無論頭上罩著多少天才的光環(huán),此刻也黯然無光。
記得有人曾說過,如果把蘇青比作春天,把炎櫻比作夏天,那張愛玲就是比秋天還要蕭索的冬。就是在這樣一個(gè)冬夜里,寒風(fēng)凜冽著,冰冷著張愛玲的心。
作為一個(gè)執(zhí)筆者,張愛玲把自己的感情構(gòu)筑的太過于美好。她曾在《傾城之戀》中借范柳原的口說過: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我想,這可能是最悲哀不過的詩句了,因?yàn)闋渴种蟊闶欠攀帧垚哿崤c胡蘭成,兩人若是平行線,那么他們便永遠(yuǎn)不會(huì)有交點(diǎn),在相同的方向上不斷延伸,卻只能彼此遙望;兩人如果是交線,那么就只能在相遇后說再見,然后奔向各自的遠(yuǎn)方。只因?yàn)樗菑垚哿幔呛m成。他們只是直線,不是曲線。不肯彎曲,亦不肯回首。
張愛玲的生命是一個(gè)多風(fēng)的夜,幸福于她總是那般吝嗇。
篇10
1984年香港著名導(dǎo)演許鞍華以忠實(shí)原著的態(tài)度對(duì)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進(jìn)行改編,但只在人物設(shè)置和情節(jié)安排上遵循了原著,卻沒能抓住原著的精髓,在對(duì)原著故事表達(dá)的精神領(lǐng)略上發(fā)生了錯(cuò)位,導(dǎo)致電影失去了原著的風(fēng)格神韻。
一
作為張愛玲小說改編的最早嘗試,許鞍華的電影《傾城之戀》推出后,引來學(xué)者與“張迷”的很多不滿,其中顯而易見的原因就是,許致力于在形式上與張愛玲的小說達(dá)到契合,演員的說辭對(duì)白守于小說原著的窠臼,對(duì)原著的字句過于遵循,使得整部電影成為小說《傾城之戀》的“影像志”,并沒有導(dǎo)演再創(chuàng)造的意義所在,只是單純的記錄小說。電影是一門繪聲繪色的藝術(shù),其獨(dú)特的語言是鏡頭的記錄,電影《傾城之戀》的內(nèi)容卻是由張愛玲精彩的文學(xué)性對(duì)白來支撐,這就使電影《傾城之戀》喪失了作為一部電影本初的魅力。又由于張愛玲的小說語言精致而富有張力,給讀者留下韻味無窮的想象空間、思考。《傾》電影微弱的鏡頭表現(xiàn)力與精彩的哲理化的臺(tái)詞相結(jié)合,使觀眾沉浸于回味咀嚼人物對(duì)話的思考之中,同時(shí),電影因遵循原著頻繁的鏡頭切換與冗長(zhǎng)的人物對(duì)話,使整個(gè)觀賞影片的過程節(jié)奏都非常緊張,影片安排沒有張力,致使觀眾對(duì)于電影更多是“審視”,少有“審美”之感。《傾城之戀》電影多處用情節(jié)演繹旁白顯得蒼白無力,不合常理。如“白流蘇送徐太太在下樓后,“徐太太道:‘……明兒吃飯的時(shí)候免不了要見面的,反而僵的慌。’流蘇聽不得‘吃飯’這兩個(gè)字,心里一陣刺痛,硬著嗓子,強(qiáng)笑道……”[2]電影在演繹這段文字的時(shí)候不能夠表現(xiàn)人物的心理活動(dòng),但導(dǎo)演同時(shí)放棄了外在的鏡頭表現(xiàn)形式,比如對(duì)演員表情的刻畫,電影中只有僵硬的說一句“吃飯?!”代替上述的心理描寫,喪失了原著的生動(dòng)。再如白流蘇從香港回家以后,白家認(rèn)為流蘇有辱家門,大逆不道,大家先議定“家丑不可外揚(yáng)” 這對(duì)于封建保守的白家是合乎情理的,而在電影中白家人心里刻薄流蘇的話借四少奶奶之口展現(xiàn)了出來,這就改變了張小說中為白家營(yíng)造的偽善,中庸的氛圍。
二
小說《傾城之戀》披著才子佳人故事外殼出場(chǎng),但張愛玲實(shí)質(zhì)表達(dá)對(duì)傳統(tǒng)才子佳人小說的顛覆。正如小說所說“他不過是一個(gè)自私的男人,她不過是一個(gè)自私的女人”,“他們把彼此看得透亮。因而雖然最后作者以香港的淪陷成全了他們,讓他們成為一對(duì)平凡的夫妻,但他們的結(jié)婚,交易的成分多于愛情的成分。這樣的故事情節(jié)與小說標(biāo)題“傾城”構(gòu)成反諷的意味,張愛玲不過想描寫庸庸碌碌的眾生之相,對(duì)于讀者閱讀標(biāo)題的期待形成審美距離,但是,許鞍華卻將一個(gè)顛覆才子佳人的故事拍成了才子佳人的套路。
首先,導(dǎo)演對(duì)小說的精神內(nèi)質(zhì)沒有很好的把握。電影的序幕是于昆曲《牡丹亭》“驚夢(mèng)”一出拉開,雖然沒有唱出戲文,卻可以想得出柳夢(mèng)梅那句:“恰好花園內(nèi),折取垂柳半枝。姐姐,你既淹通書史,可作詩以賞此柳枝乎?”許鞍華正想就此死亦可以生的古典轟烈,與白流蘇廢墟之中建立的愛情構(gòu)成一個(gè)互文的效應(yīng)。電影為我們塑造了一個(gè)大義凜然的范柳原和一個(gè)木訥溫婉的白流蘇,小說中二人機(jī)關(guān)算盡,斗智斗勇的主題全然不見,張愛玲在小說開頭的結(jié)尾反復(fù)詠唱“胡琴依依呀呀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拉過去,說不盡的滄桑故事――不問也罷!”[3]這句話奠定了小說蒼涼基調(diào)和小市民百無聊賴的一種感情狀態(tài),電影的改編把小說這一層的精神內(nèi)蘊(yùn)解構(gòu)殆盡。
其次,是電影這種藝術(shù)形式鉗制了張愛玲小說精神內(nèi)蘊(yùn)的表達(dá),《電影的本性》中論述道“小說也常常熱衷于描繪實(shí)體―――臉、物體、風(fēng)景,等等。但這只是小說所掌握的世界的一部分而已。作為一種文字的作品,它能夠直接提出和深入揮究?jī)?nèi)心生活的事件―――從情緒到觀念、從心理沖突到思想爭(zhēng)論。小說的世界主要是一種精神的連續(xù),這種連續(xù)現(xiàn)在常常含有某些非電影所能掌握的元素,因?yàn)檫@些元素并不具有可資表現(xiàn)的客觀形態(tài)……在攝影機(jī)所能再現(xiàn)的現(xiàn)實(shí)范圍內(nèi)不存在任何可以依附的東西。”[4]
三
電影《傾城之戀》對(duì)于小說形式上細(xì)節(jié)的遵循和精神內(nèi)質(zhì)的誤讀,造成了電影自身出現(xiàn)矛盾的狀況,電影主題游離于“夢(mèng)幻愛情”與諷刺批判之間。
張愛玲的的小說往往被認(rèn)為關(guān)注私人生活而缺少時(shí)代意識(shí)。實(shí)際上,張愛玲的創(chuàng)作依然曲折地回應(yīng)了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問題,白流蘇的生存狀況是關(guān)于女性啟蒙狀況的隱喻,反映了20世紀(jì)前期普通女性生存與啟蒙之間的對(duì)立沖突,間接傳達(dá)了五四啟蒙范圍。白流蘇去香港,與范柳原談戀愛,建立自己想要的婚姻,是流蘇第二次主動(dòng)追求自己的人生、開創(chuàng)自我生命的勇敢、驚人之舉,白家是一個(gè)在幾千年儒家思想熏陶下大家庭,白流蘇的舉動(dòng)是違反封建綱常的,小說語言把白的舉動(dòng)戲謔為“一些遼遠(yuǎn)的忠孝節(jié)義的故事,不與她相干了”,白流蘇在鏡子前的對(duì)照,實(shí)質(zhì)上是一種自我生命的審視與重估,生命軌跡和態(tài)度的再選擇從這一刻改編,電影中對(duì)于流蘇鏡前自照的一段演繹的十分生動(dòng),但是后來演員對(duì)于流蘇形象的塑造又回到軟弱,沒有生氣,等待他人救贖的狀態(tài),歸根結(jié)蒂,還是導(dǎo)演對(duì)于小說精神的誤讀造成的。
許鞍華的《傾城之戀》一改張愛玲《傾城之戀》給讀者的華麗印象,拍出普通男女平實(shí)戀愛的感覺,這是導(dǎo)演再創(chuàng)造的顯現(xiàn)。其他的情節(jié)實(shí)際上就是一種失卻了原著神韻的機(jī)械復(fù)制,因而一個(gè)在才子佳人故事外殼下顛覆才子佳人傳奇的作品,只剩下了一個(gè)才子佳人故事的外殼,其失敗也就是必然的了。
注釋:
[1]夏志清:《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再讀張愛玲》,劉紹銘等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