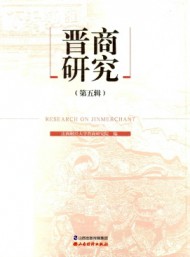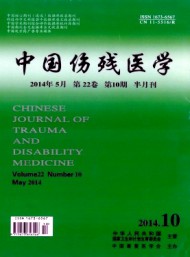晉明帝數歲范文
時間:2023-03-23 11:41:07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晉明帝數歲,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比司馬睿更為可憐可嘆的,是他的兒媳婦,明帝的皇后庾文君。《晉書列傳》顯示,此女也有陛下之尊稱,咸和年間,“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以女性被稱陛下者,前無古人,后來者武則天,比她晚了370年。
庾文君,河南鄢陵人,十余歲時,隨父親庾琛南渡,居會稽。一說其成長于江南,恐怕有誤,永嘉五年,她已然年方二八。當然,庾文君也確實有江南女子的風韻,《晉書》贊她“性仁慈,美姿儀”,《太平御覽》贊她“令儀淑美”。就是說,她不但容顏嬌美,性格賢淑,坐臥行止,亦無一處不優雅。
當時皇室最佳的聯姻方案,應是“王與馬,共枕席”。然則庾文君太出類拔萃了,盡管她比太子司馬紹(晉明帝)大三歲,元帝仍然聘她做了太子妃。永昌元年(322),王敦以“清君側”為由發動兵變,與江南大族沈充組成聯軍,很快攻下建康。司馬睿無力翻盤,只好媾和,委屈加窩火,一命嗚呼。明帝即位后,被迫給予王敦“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覆上殿”的待遇,政局稍稍穩定,便冊封庾文君為皇后,“以后兄中領軍(庾)亮為中書監”。
晉明帝與王敦,屬于冤家對頭。王敦有大功于朝廷,但是其人“心懷剛忍”、“敢肆狂逆”,仗著手中握有槍桿子,從來不把皇帝當回事兒;晉明帝頗有勇略,王敦忌憚,曾要挾元帝廢太子,未能得逞。君臣彼此不待見,明帝尚能隱忍,王敦先坐不住了,豎起大旗造反;明帝也不是吃素的,微服察看軍情,親自指揮戰斗,結果,王敦病死軍中,叛軍也被擊敗。
斯役,“流民帥”蘇峻因功崛起。
南宋的趙構曾譏笑東晉的幾個皇帝茍安江南,不思進取,他固然缺乏資格,但也不無道理。東晉君臣之間常常窩里斗,從晉元帝到晉成帝,歷三代僅區區八年,流民問題尚未解決,王敦又鬧過兩次,哪有工夫恢復中原!晉明帝倒也想勵精圖治,可惜身體不幫忙,在位三載,即英年病逝。
成帝司馬衍即位時才五歲。按慣例,要么母親以皇太后身份出來幫襯,要么托孤。知妻莫如夫,明帝大概其了解庾文君無心政治,也就選擇了托孤,臨死前任命的顧命大臣依次是:太宰司馬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壺,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丹楊尹溫嶠等。明帝不愧謚號為“明”,確實很精明,以同族的司馬羕為首輔,與大舅子庾亮一起護航幼帝,王氏家族的勢力勢必得到抑制。但是,他千算萬算,卻始終沒有算到問題會出在大舅子庾亮身上。
庾亮極不安分,他覬覦司馬羕的首輔地位,私下里聯合同樣不甘心的王導,二人一拍即合,劍指司馬羕。由于其時政出尚書,印把子在司馬羕手里,負責朝廷宿衛的左、右衛將軍分別是司馬宗和虞胤,這兩位也都是司馬羕的人。庾亮沒轍,遂與王導商量,將皇太后庾文君推上前臺。
《資治通鑒》載曰:“群臣以帝幼沖,奏請太后依漢和熹皇后故事;太后辭讓數四,乃從之。”那么多顧命大臣都健在,有必要效法鄧綏嗎?庾文君絲毫沒有權力欲,只想安安靜靜的過日子,拗不過大家的“好意”,勉為其難,臨朝稱制,的第一道詔書:王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共同輔政。誰在背后搞鬼,不言而喻。事已至此,司馬羕只能下野,其馬仔也相繼換了崗位。
篇2
[關鍵詞] 溫州 古代 海外貿易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人以敢于闖天下聞名于世,形成了特有的溫州人現象。如今,溫州商人不僅分布在全國各地,還遠渡重洋,將足跡踏遍世界各地。今天溫州的外向型經濟,可上溯至溫州海外貿易的悠久傳統,也與溫州獨特的地理、歷史、文化傳統密切相關。
地處浙江南部的溫州在春秋戰國時“并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初為東甌王國,后為會稽郡回浦縣地”,“三國吳屬臨海郡”。東晉明帝太寧元年(323年),析臨海郡始置永嘉郡,郡治設在甌江下游南岸(今溫州市鹿城區),是為溫州建郡之始。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置溫州,自此以后,歷1300余年至今,州名無改,州境亦無大變。
雖然溫州歷史源遠流長,在戰國時期溫州的海外交通也有一定的發展。然而偏居浙南一隅的溫州,在東漢以前,一直地廣人稀,戶不足萬。與當時其他的通衢大邑相比,地位自然微不足道。東晉南朝時期,溫州相對安定,中原名門土族、達官貴人,紛至沓來,中原文化、移民文化與本土文化交融,促進了溫州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唐初,溫州的海外貿易逐步興起。唐中晚期溫州海外貿易漸趨興盛。唐代溫州的主要貿易國是日本,以民間貿易為主。唐武宗會昌二年(842年),中國商人李處人在日本造海船一艘,由日本值嘉島啟航,直達溫州,是為有記載以來日本與溫州的首次直航。由于當時溫州與日本之間商船往來頻繁,一些日本高僧前來中國時,也由溫州入境再轉赴各地。但綜觀整個唐代,溫州的遠洋貿易仍然以轉口到明州、泉州再行出口為主。
五代時,中原戰亂紛擾,而吳越錢氏實行“保境安民”政策,境內“休兵樂業二十余年”。溫州成為吳越國重要港口之一,設有博易務,“航海收入,歲貢百萬”。瓷器、茶葉等仍是溫州出口的主要物資。溫州的主要貿易國仍然是日本。兩地交通不絕,商船往來分外頻繁。北宋時期,隨著造船業的興盛和航海技術的提高,溫州的海外貿易繼續有所發展。北宋淪亡,宋室南遷,溫州接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其中不乏世家大族,更曾一度成為宋高宗避難的駐蹕之所,以往的“僻遠下州”,一躍而成為“十萬人家城里住,少聞人有對門山”的繁華都市。
宋室南渡后,由于陸上絲綢之路的阻絕,南宋統治者愈加重視海上貿易,這也是溫州海外貿易繁榮的重要因素。加上南宋時羅盤針得到廣泛使用,并應用于航海事業等,使溫州的海外貿易在南宋時達到鼎盛。
南宋初年,溫州設立市舶務,管理海外貿易。溫州市舶務設立后,溫州海外貿易日益興盛,海內外的友好往來也非常頻繁。除了國內東南沿海各港口之間的貿易往來之外,日本、朝鮮的商人亦來溫州經商。除此之外,溫州還與大食、印度、交趾、占城、渤泥、三佛齊、真臘等國有貿易往來。朝廷還專門設立來遠驛,作為各國客商居留之所。同時,市舶務還對外國商人和商船采取了保護措施,“番舶為風飄著沿海州界,若損敗及舶主不在,官為拯救,錄貨物,許其親屬召保認還”。如遇風水不便,船破桅壞者,即可免稅。
南宋從溫州輸出的產品主要是青瓷、漆器、書籍、文具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瓷和漆器。甌江上游處州的龍泉窯在當時是全國最大的窯場,所產的青瓷,“胎薄如紙、光潤如玉”。這些產品大部分沿甌江經溫州出口,遠銷東亞、南洋和非洲諸國,再到歐洲,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組成內容。溫州的漆器在宋代號稱第一,工藝精美絕倫。由于當時海外貿易的發達,也有許多外籍人士在溫州經商或駐足,南宋永嘉著名詩人徐照在他所寫的《移家雁池》詩中就有“夜來游岳夢,重見日東人”之句。所謂日東人,即是指日本人。慶元元年(1195年),溫州市舶務撤銷,并“禁賈舶泊江陰及溫、秀州,則三郡之務又廢”,溫州的海外貿易一度陷于停頓。
元初,由于戰爭的原因,溫州人口劇減,商業一時蕭條。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在溫州設立市舶轉運司后,溫州成為元朝對外開放的七大港口之一,溫州的海外貿易恢復了往日的繁盛景象,“百貨所萃,廛氓賈豎咸附趨之”。至元三十年(1293年)溫州市舶司雖并入慶元市舶司,但溫州的海外貿易并未完全斷絕。
明朝建立后,為防止沿海居民與反明勢力的聯系和抗擊倭寇進擾,實行了與宋元時期完全不同的“海禁”政策,三令五申“申禁人民,無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溫州的海外貿易幾乎處于停頓或半停頓狀態。溫州沿海居民只好冒禁出洋市販,以走私形式維持宋元以來形成的海上私商貿易。嘉靖年間,溫州沿海倭患猖獗,百姓深受其害,人口流散甚眾,資財耗竭,四業委頓,海外貿易又陷于低谷。隆慶元年(1567年),朝廷面臨財政危機,為開辟財源,宣布部分開放“海禁”,默許私人進行海外貿易,但仍加以諸多限制條件,尤其是以往的主要貿易對象日本,更嚴厲禁止,“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濟之例”,因之溫州的海外貿易并沒有多大的起色。
清王朝建立后,以鄭成功為首的抗清力量在溫、臺沿海活動。清政府為隔絕溫州沿海人民和鄭成功聯系,于順治十三年(1656年)宣布“海禁”,嚴禁商民下海交易,“片版不準入海”,犯禁者治以重罪。順治十八年(1661年)又下“遷界”令,強迫沿海10里居民內遷,“三遷而界始定”,溫州所屬瀕海居民被迫內徙。遷界后,溫州沿海為之一空,魚鹽之利盡失,海外貿易處于完全停頓狀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平定臺灣后,廢“遷界”令,開“海禁”,許百姓往海上貿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置浙海關于寧波,下轄溫州、瑞安、平陽等15個海關分口。溫州海關分口的設立,標志著溫州海外貿易的復蘇。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一艘溫州商船滿載貨物前往日本長崎銷售,溫州與日本的海上交通恢復。但清政府又規定,溫州海關只準出口貿易,進口須經寧波等地轉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又頒布禁令,僅限廣州粵海關一口對外貿易,封閉江、浙、閩海關,溫州、瑞安、平陽三個分口亦隨之關閉。同時又設置種種禁令,使溫州民間海外貿易陷入困境。三年后,又禁外國商船來浙。為謀生計,溫州沿海居民不得已只有鋌而走險,以武裝走私對抗朝廷的禁令,并不時與清軍在溫州海域發生沖突。
明清兩朝長期實行的海禁政策,使得溫州傳統的輸出商品,如漆器、青瓷等由于出口不暢,從數量到質量上都日趨衰落,造船業也因之一落千丈,從而嚴重抑制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道光年間,鴉片走私開始盛行,溫州也不免波及。英國更覬覦東南沿海,英軍戰艦不時侵擾溫州沿海。爆發后,中國進入近代社會。溫州的海外貿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溫州古代的海外貿易,雖幾經沉浮,卻始終維持著頑強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優越的地理條件。位于甌江口的溫州港是天然良港,歷經各代不斷修繕,至元代,沿江“大石堤延袤數千尺”,且建造有燈塔以作航標。沿江而上連綿800里的甌江,流經處州、溫州兩地,流域面積達1.8萬平方公里。甌江及其支流沿岸各地借舟楫之利,和溫州交通往來,并經此進行海外貿易活動。“江城如在水晶宮,百粵三吳一葦通”,地處中國海岸線中端的溫州,同鄰近的閩浙各港口也交往密切,海外貿易由彼處轉運亦極為便利。
第二,發達的造船業。溫州造船業歷史悠久,早在三國時期,就是中國沿海主要造船地區,其附近的平陽就有“橫嶼船屯”。降及唐代,溫州的造船技術進一步提高,已能建造遠洋海船,成為中國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北宋初,溫州年造船125艘,為全國11個造船中心之一。到哲宗年間,“歲造船以六百只為額”,居全國各船場之首。南宋以后,除官營造船廠外,私營造船業也十分興旺。
第三,海納百川的移民社會。溫州偏處東南一隅,不太容易受到中原戰亂的波及,再加上適于人居的氣候,因此西晉末年以來,為躲避戰亂南來的中原移民駱繹不絕,周邊地區也有大量移民涌入,這就造成了溫州民間社會少有根深蒂固的鄉土觀念,有著四海為家的勇氣和魄力。再加上從自然環境來看,溫州處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山區地理,耕地匱乏。為了求生存,面對貧乏的土地,歷代溫州人更多地選擇了發展手工業和商業。“其貨纖靡,其人多賈”,是其最好的評價。
第四,工商皆本的價值觀。一面向海的溫州,卻又是三面環山。由于高山阻隔,交通不便,與中原文明的交流相對閉塞。因此溫州本土文化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響就來得不那么深厚,溫州人也就少了些正統觀念、規范意識,少了些拘束,行為也有敢闖之精神。南宋的永嘉學派就是順應并反映了當時宋代溫州這種普遍的自發的市民意識,經過自覺的理性加工,指出“抑末厚本非正論”,提出了“以利和義”、“工商皆本”的新價值觀。這些新思想對宋代溫州商品經濟和海外貿易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2](清)徐松:宋會要輯稿[M].北京:中華書局,1958
[3](明)胡廣等:明實錄[M].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4](明)張孚敬:嘉靖溫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M].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1
[5](明)姜 準:歧海瑣談[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6](明)張燮. 東西洋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