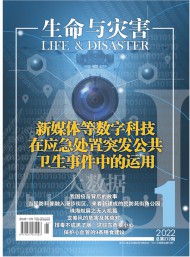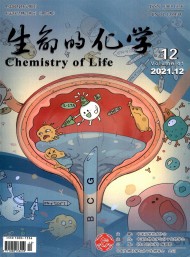生命哲學范文
時間:2023-04-12 09:10:13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生命哲學,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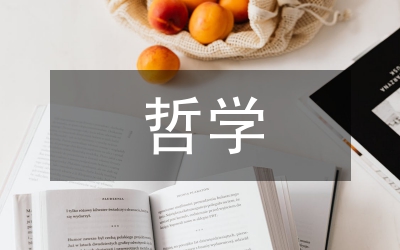
篇1
莊子在《列御寇》篇中講了這么一個小故事:
莊子快死了的時候,他的很多學生就商量,老師如果真的死了,我們一定要厚葬他。就是要好好安葬他,禮儀用品一定要奢華。
莊子聽了,跟他的學生們說,我死了以后,要“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赍送”。這廣大天地就是我的棺材,日月星辰就是我陪葬的珠寶,天下萬物就是送給我的禮物。
形體歸于天地,生死歸于自然。這就是莊子對自己的形體和生死的看法。
其實莊子從來就是一個不畏懼死亡的人。他不懼怕的方式就是“樂生”這兩個字,也就是說,活得好比怕死要強的多。
這個觀點跟儒家的思想不謀而合。孔夫子回答他學生關于死亡的問題時,回答了六個字:“未知生,焉知死?”人活還沒有活明白呢,干嘛去想死亡的事呢?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儒道相通。
孔子給我們揭示的都是一種溫暖的情懷和一種樸素的價值,就是“活在當下”。人活在當下,在當下看破了名,穿透了利,不畏懼生死,那么,我們的心靈將擁有一個多大的空間,一分多大的境界啊!
轉貼于
可以說,莊子在他的這本書里,留下了很多隱約的生活的影子。這里面有很多判斷跟儒家彼此呼應。只不過儒家所看重的永遠是大地圣賢的道德,永遠是人在此生中建功立業的信念;而道家看重的永遠是更高曠的蒼天之上的自由,永遠是人在最終成全以后的超越。
中國的儒家思想在社會這個尺度上,要求人擔當;但道家思想在生命層面上,要求人超越。擔當是我們的一份責任,超越是我們的一個生命境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看過《莊子》中的很多故事,會通達他的一套生命哲學,這不是簡單地積極或消極,而是在我們生命的不同體系上給我們建立起來的一套參照系統。
以莊子的話說,人生至高的境界就是完成天地之間一番逍遙游,也就是看破內心重重的樊籬障礙,得到靜觀天地遼闊之中人生的定位。
篇2
The man stroked the Cat on his lap and sighed. The Cat opened his eyes, purred and looked up at the Man. A tear rolled down the Man’s cheek and landed on the Cat’s forehead.The Cat gave him a slightly annoyed look.
“Why do you cry, Man?”the Cat asded.“Because you can’t bear the thought of losing me? Because you think you can never replace me?”The Man nodded “yes.”
“And where do you think I’ll be when I leave you?”the Cat asked. The Man shrugged helplessly. “Close your eyes, Man,” the Cat said. The Man gave him a questioning look, but did as he was told.
“What color are my eyes and fur?” the Cat asked. “Your eyes are gold and your fur is a rich, warm brown,” the Man replied.
“And where is it that you most often see me?”asked the Cat. “I see you…on the kitchen windowsill watching the birds…on my favorite chair…on my desk lying on the papers I need…on the pillow next to my head at night.” “Then, whenever you wish to see me, all you must do is close your eyes,” said the Cat.
“Pick up that piece of string from the floor――there, my ‘toy.’” The Man opened his eyes, then reached over and picked up the string. It was about two feet long and the Cat had been able to entertain himself for hours with it. “Now take each end of the string in one hand,” the Cat ordered. The Man did so.
“The end in your left hand is my birth and the end in your right hand is my death. Now bring the two ends together,” the Cat said. The Man complied.
“You have made a continuous circle,” said the cat.“Does any point along the string appear to be different, worse or better than any other part of the string?” The Man inspected the string and then shook his head “no.”
“Close your eyes again,” the Cat said.“Now lick your hand.” The Man widened his eyes in surprise.
“Just do it,” the Cat said.“Lick your hand,think of me in all my familiar places, think about all the pieces of string.”
The Man felt foolish, licking his hand, but he did as he was told. He discovered what a cat must know, that licking a paw is very calming and allows one to think more clearly. He continued licking and the corners of his mouth turned upward into the first smile he had shown in days. He waited for the Cat to tell him to stop,and when he didn’t, he opened his eyes. The Cat’s eyes were closed.The Man stroked the warm, brown fur, but the Cat was gone.
The Man shut his eyes hard as the tears poured down his face. He saw the Cat on the windowsill, then in his bed, then lying across his important papers. He saw him on the pillow next to his head, saw his bright gold eyes and darkest brown on his nose and ears. He opened his eyes and through his tears looked over at the circle of string he still held clutched in his hand.
One day, not long after, there was a new Cat on his lap. She was a lovely calico and white…very different from his earlier beloved Cat and very much the same.
男人非常傷心。他知道貓余下的日子不多了。醫生說已經沒得治了,他只能把貓帶回家,并盡可能地讓他在剩下的時間里過得舒服些。
男人把貓放在腿上,嘆了口氣。貓睜開眼睛,呼嚕呼嚕地叫著,抬眼看了看男人。一滴眼淚從男人的臉頰邊滑落,落在了貓的額頭上。貓有點不高興地看了他一眼。
“你哭個什么啊,伙計?”貓問道,“因為你無法承受將要失去我的念頭?因為你認為永遠都沒有什么能代替我?”男人點了點頭。“是啊。”
“那么你認為我離開你以后,會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貓問道。男人無望地聳了聳肩。“閉上眼睛吧,伙計,”貓說。男人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但還是聽話地閉上了眼睛。
“我的眼睛和毛皮是什么顏色的?”貓問。“你的眼睛是金色的,你的毛皮是濃郁而溫暖的褐色的。”男人回答道。
“那你最常在什么地方見到我呢?”貓問。“我經常見到你……在廚房地窗臺上看鳥……在我最喜歡的椅子上……躺在桌子上我需要用的文件上……晚上睡在我腦袋邊的枕頭上。”“那么,無論什么時候你想見我,你只要閉上你的眼睛就可以了。”貓說。
“把地上的那段繩子撿起來――那里,我的‘玩具’。”男人睜開眼睛,伸手撿起了繩子。繩子大約有兩英尺(約0.6米)長,貓曾經能夠玩著繩子自娛自樂一玩就是幾個小時。“現在用兩只手捏住繩子的兩端。”貓命令道。男人照做了。
“你左手捏著的那端就是我的出生,而右手的那端就是我的死亡。現在把兩端連在一起。”貓說道。男人又照做了。
“你做出了一個連貫的圓圈,”貓說,“這個繩子上的任意一點同其他點有什么不同嗎?比繩子的其他部分更好或者更差嗎?”男人審視著那根繩子,然后搖了搖頭。“沒有。”
“再次閉上你的眼睛,”貓說,“現在舔舔你的手。”男人驚訝地睜大了眼睛。
“照我說的做吧,”貓說。“舔舔你的手,想想我在所有我熟悉的地方,想想所有的繩子。”
要舔自己的手,男人覺得很蠢,不過他還是照做了。他發現了貓所知道的秘密――舔爪子能讓你平靜下來,并讓你能夠思考得更加清楚。他繼續舔著,他的嘴角開始上翹,好多天來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他等待著貓叫停,可是沒等到,于是他睜開了眼睛。貓的眼睛已經閉上了。他摸了摸貓溫暖的褐色皮毛,可是貓已經去了。
篇3
【關鍵字】生命哲學 冬天 孤獨 春天
作為西部的散文作家,劉亮程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揭開遮蔽生命存在的文明面紗,逼近西部生命乃至所有生命的本真狀態。在返身自然、復歸生命本體的精神追求中,表現出了直面生活、敬畏生命、珍愛生命的仁慈態度和莫大的悲憫情懷。在《寒風吹徹》中,本著對其創作特色的堅持,我們亦可以看見濃濃的生命哲學意識。
一、無法規避的冬天
《寒風吹徹》中的文字是寒冷的,它的每一個字好像都曾被寒風撫摸過、被大雪包裹過。然而真正吹徹人心的并非文字本身,而是作者在其背后所注入的生命感悟。四季輪回,冬天終究會降臨到我們的生活中。劉亮程筆下的冬天是寒冷無比的,寒風和大雪作為冬天的兩個分意向出現,作為冬天的使者,忠實地傳遞著冬天的消息――寒冷。寒風,其力量在于無法防備的穿透力,不論我是怎樣地糊好窗戶,掛上棉門窗,寒風還是進來了,它比我們更熟悉墻上的每一道細微裂痕;大雪,并非只出現在我們生命中的某個特定時刻,它將覆蓋我們的一生。經過許多個冬天之后,我才漸漸明白自己再躲不過雪。它無邊無際,不放棄一切在外的生命;
作者筆下的寒風和大雪是具有象征意義的:不管我們怎么將自己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寒風還是會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吹涼我們的背脊。這不正如生活中那些無可防備的意外嗎?紛紛揚揚的大雪,也都將會落在我們正經歷的每一段歲月里。大雪象征著生活中的苦難,在寒風和大雪充斥的世界中,我們日漸發現,不論我們怎么抵抗,那些出現在具體生活中的風霜最終還是會在看不見的角落給我們帶來意外,會在每個人的生命荒野中植入苦難并一點點凍結我們的生活。
《寒風吹徹》中的冬天同樣具有雙層指向性,當我們經歷過一個個自然之冬,伴著陣陣寒風和大雪,走過生活中的意外和苦難后,我們終將走入生命中的另一個冬天――生命的終極。生命的冬天也是寒冷的,那里依舊寒風習習。可那份來自內心的寒冷,我們卻永遠只有自己能夠感知。在生命本身的冬天里,衰老與疾病詮釋著它的內涵,冷漠行走的時間將它一步步地引向終極。因為衰老,“我親眼看見老人凍死在那個冬天,我的爺爺奶奶也在多年前的冬天走了”。因為疾病,“盡管姑媽一到冬天就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從來不敢邁出半步,可她還是在一個冬天走了”。每個人都會迎來自己的冬天,在這個冬天里,我們所能等到除了無法抗拒的衰老,還有無力擺脫的疾病。我們都在掙扎著,想要等著春天的到來,可在生命之冬里,我們永遠也等不來另一個春天。生命之冬帶來的絕望和終結,我們無法避免。
二、必須承受的孤獨
在《寒風吹徹》中,我們可以看見個體生命存在的本質孤獨感是出現在每個人的生命中的。并不是每一段路都會有跟你走向相同方向的人,十四那年我只身一人外出拉柴禾時,卻把自己的一根骨頭永遠地凍壞在那段天亮前的雪路上了。其實那個夜晚并不比其他夜晚更冷,但孤身一人的我卻感覺那夜的寒風似乎全部地對付我。只有陷入如此的孤獨之境,對于寒冷我們才有更為深刻的感知。在這份寒冷中,那根被凍壞的骨頭再也無法解凍,這也是每個人對于孤獨的堅守,那些在孤獨中的感悟,無法溝通也無法表達,只能深深淤積在人們的心中。
孤獨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十四歲的我會經歷,年邁的姑母也得面對。每年冬天,她都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孤獨過冬,很多年后,姑母走了,母親的孩子長大了,孤獨又開始在母親的生命中出現了。不論曾經多么繁華熱鬧,終有一天,這些都會在我們的個人世界中退去,只剩孤獨循環。
身體的孤獨迫使我們如履薄冰地迎接著人世的風雨,盡管這份孤獨會把我們弄得滿目蒼夷。雪夜中獨自行走的老人最終在孤獨中去世了,在這里,身體的孤獨已經上升到精神的孤獨。這位風燭殘年的老人究竟孤獨地在這人生道路上行走了多久,我們無法得知,但從他那比多少個冬天加起來還要寒冷的心境來看,這種孤獨的存在絕非一天兩天。初涉孤獨的我很快就懂得了將身體那點溫暖一步步退守到連自己都難以找到的深遠處,不僅是我,每個人都會在孤獨中隱藏溫暖。可這位老人內心的溫暖顯然快被人生的孤獨磨盡了,孤獨往他內心逼進的寒冷太過強大,以致于當他坐在我的火爐旁時,爐火須臾間變得蒼白。這是一顆凍結的心,一個人孤獨久了,心便會麻木難以復蘇,甚至會拒絕溫暖。因為孤獨,寒冷已從身體侵入到老人的靈魂。這份精神上的寒冷和孤獨已經使他不再愿意過多地接受人世間的溫存,孤獨就像一把鎖,老人用它將自己封鎖起來,自己走不出,別人進不去。這也許就是孤獨的本質,它會無限地擴大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我們必須承受卻又帶著溫暖越逃越遠。
三、依然期待的春天
當陣陣寒風和漫天的大雪向整個世界侵襲時,我“還是會拉緊門簾,燃起早早就準備了的柴禾。我知道,這輪爐火只能烤熱漫長生命的一個時刻,但依然會堅持走下去”,這是因為春天是我們永遠的企盼。只有洞悉了人的生命中也有一個冬天的人,才會早早地準備下一爐度過生命的冬天的火,而這輪火,終將帶我們進入下一個春天。
“終將帶我們進入下一個春天”,這雖然是我們的對不可輪回的生命之冬的美好愿景,但它卻始終鼓舞著我們向著溫暖靠攏。有些人可能永遠也等不到自己生命中的春天,可是看到它出現在別人的生命里,依然那么明媚,那么溫暖。姑媽雖然已經邁入生命之冬,但我們看到她對于春天還有那么多的渴望,盡管春天來了她沒有一片要抽芽的葉子,沒有半瓣要開放的花朵。但是春天能給她帶來溫暖,溫暖,對于一個飽受苦寒折磨的老人來說何其重要。
也許出現在我們生命中的寒風和大雪有時候卻也并非刻意存在,寒冷雖然會驅趕溫暖,但它無法將其凍結。因為溫暖不管怎么藏匿,它始終還在我們的心里;因為孤獨,老人最終被那個冬天留下了,但我相信他心中一定是有一絲溫暖存在的。因為在那個冬天,我曾給他提供過一份溫暖,盡管杯水車薪,但畢竟“我”曾經做過努力,努力讓這位老人溫暖。
每個人都得穿梭在一個又一個寒冬之際,雖然最后終究走不出生命之冬,但我們卻始終相信溫暖,相信春天。因此,不論是怎樣的寒風大雪,我們都不應讓它奪取了內心的溫暖。面對孤獨,我們應多一份悲憫、理解與珍愛。有些溫暖也許永遠沒有機會送出,但在你升出橄欖枝那一刻,春天也許已經出現,在他或她的生命里,在跟我們沒有任何關系的陌生人的生命里。
【參考文獻】
[1]萬月玲,《的人文關懷之解讀》,[A]經濟與社會發展,2005年6月3日期。
篇4
一、將文本中的“象”與生命哲學做一次聯想
“一切景語皆情語”,景與情之間具有一種互通的關系。我們運用聯想將萬物與自身的情感并聯成為一條通往真理的路徑。可以說,文本之中“象”生成的初衷就是要與這條真理之路相契合,指引讀者通向生命哲學的領域。教師在講解文本中作者所設置的這一個個“象”時,不要就“象”論“象”,而要將所涉及的“象”代入生活,讓學生發揮想象,將種種原本沒有語言和感情思想的“象”與生命哲學做一次聯想。這對語文教學來說百益而無一害,它培養了學生的洞察能力和抽象思維,讓他們能夠從身邊的一事一物中體察到生命的意義,這就是語文教學的最高理想和旨意。
美籍華裔學者王浩稱“魯迅是一個廣義的哲學家”。這一評價有的放矢。對于魯迅的散文詩《雪》來說,其最閃光的地方也是其哲學價值。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將文本中的“象”與生命哲學做一次聯想。《雪》主要敘述了兩個“象”:江南滋潤美艷的雪、朔方如包藏火焰升騰太空的雪。這兩種雪并不是單純的雪,教師要引導學生,讓他們透過雪的形以及諸多特點,看到由其引申出來的東西。學生就會有意識地進行深層次的分析:我看到了人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性格;看到了柔軟和堅韌的兩種靈魂;看到了兩種生活境遇、兩種生活狀態;等等。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做了一次“象”與生命哲學之間的聯想,總結出不同的思想意味。這有力地證明了語文內容的豐富性與不確定性。
二、將文本中的“境”與生命哲學做一次溝通
文本就是由語言文字構建起的一個空間,這個空間由無數個“象”相互聯系構成一個“境”。這個“境”可以是生活的環境,也可以是人生的境遇,或者是生命的遭遇。但無論是哪種“境”,都是一個生命空間,我們存在其中總會獲得許多感觸和啟示。但從語文課堂教學層面來說,我們不能喧賓奪主。生命哲學是一種智慧和態度,是作為文本敘述指導人生的一個過渡。這個過渡點類似于水泥漿,覆蓋住文本的“虛”與人生的“實”之間的縫隙,讓它們之間不會形成一個斷層。可以說,文本當中作者所創造的“境”都是指涉現實的一個案例,就如小說中的人生是對現實人生的描摹一樣,兩者之所以能夠相互聯系起來,就是因為兩個“境”中有生命哲學的溝通。
詩人常常喜歡以月亮來構境,而對月獲得樂觀、豁達的生命思考的還要屬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為最。詞中作者借助天馬行空的想象將自己置于一個虛境中,又聯想到自己不如意的仕途宦境,而得出具有哲學意味的思考:“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從“境”到人生哲理,文本中作者的情感形成一次升華和飛躍。在這一環節中,教師要讓學生了解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要用豁達的態度對待生活,也就是作者所說的“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通過對這一生命哲學的闡述,文本之虛境與現實人生完美地聯系起來,文本作為一個指向生活的案例成了對人們生活的概括、總結。
三、將文本中的“意”與生命哲學做一次締結
文本中的表層意蘊只屬于作者本人,只具有作者本人的色彩,是一種個性的流露,但是若將其延展開來,就顯示出人類普遍的某種共性。就如我們在寫母愛的時候,通常是以自己的母親為出發點去寫,在一位母親身上,我們看到無數位母親的影子,然后總結出母愛的無私和偉大。這種敘述方式類似剝玉米葉一樣,一層一層具有層次締結感。從文本所述的事情,我們看到文本中所表達的情,又從其流露出來的情感,我們洞察到作者要表明的“意”。但“意”并不是文本的終結點,我們再由“意”延伸開去,又會得到更多的生命旨趣、生命體會,文本中的“意”與生命哲學做了一次遠程的締結。
篇5
關鍵詞: 生命哲學特殊教育生命本源性
人類對生命的關注,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人們對心身問題和心物問題的探討,而生命哲學作為一個哲學流派則是19世紀反對實證主義和理性主義思潮的產物。生命哲學將哲學關注的主題由外轉向內,其核心是人的生命以及與之不可分割的人的生活、心理狀態和歷史文化等[1]。用“生命”解釋人類的一切活動則是生命哲學的基本內涵。其代表人物柏格森、狄爾泰等人認為,生命是世界的本源,是一種絕對自由的、不受任何客觀條件和客觀規律制約的創造力量,是最真實、最直接的實在[2]。這一觀點揭示了一條重要的生命法則――“生命的流動性”,即生命本身不是實體,而是活力,這種非實體的活力源自精神層面,有著不可遏止的永恒動力。在確定了恪守生命的研究本體之后,生命哲學進而用生命的發生、演變來解釋世界、文化及歷史,認為古代人留下的古籍、文獻、民俗等是他們的生命,同時也是文化,能夠書寫歷史。
在認識論上,生命哲學認為直覺高于理性,情意又高于認知。這使得生命哲學具有非理性的傾向,因此它也因具有“破壞理性”的一面而一直遭到許多人的批判。甚至有人因其強調意志、意識對于生命的意義而將之歸為唯心主義。然而,隨著其外延的不斷擴大,生命哲學對人類反思生存的價值和意義,以及提升和完善人類的生活具有重大深遠的影響。
一、生命哲學內涵對教育本質取向的影響
“科學性導向”是近現代教育發展的重要法則,然而它在發揮作用的同時,也造成了深重的負面影響,不僅造成了教育對象的工具化和教育目的的功利性,而且導致“關注人性”被擠出了教育的視野,教育生命發展的本質受到了挑戰。雖然在生命哲學的影響下,以人為對象的教育活動亦將“生命”引入自身的范疇,但是,應在何種意義上理解“生命”在教育學中的使命和旨歸,又如何判斷它的是與非,仍然是教育工作者需要進一步深思的問題。
生命哲學的科學觀把“科學”的概念由自然領域擴大到人文社會領域,認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不再是自然界的事物,而是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包括社會和人的精神現象。根據這個命題,狄爾泰作了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分,并強調研究人的生活的精神科學比自然科學更為根本、更為重要[3]。生命哲學的這種科學觀啟示教育應首先關懷人的生命,關注人的價值,關心人性完善。在本質取向上,教育應以“培養人”作為自己質的規定,關注“人”及其本質性要素――人的生命及生命意義的提升[4]。
事實上,教育確是直面生命、提升生命的社會活動,是以人為本的社會中最能體現生命關懷的神圣事業。某種意義上講,教育承載著喚醒人性、洞悉人生、徹悟人生,使混沌的人生變得清澈,使沉睡的生命得到喚醒的巨大使命。生命哲學呼喚對生命的尊重,以生命的視角來關注人、發展人、完善人,這本身就是教育的追求。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以“生命”為內核的生命哲學,因其對生命超乎尋常的關注及其獨特的詮釋對整個教育生命價值的回歸都大有裨益。“生命”的介入使教育接近本真,并折射出教育與生命之本源性、本體性的關系,即生命是教育發生的原點,教育是生命的存在形式;教育是一個內在的、灌注著其個人感受和體驗的生命活動過程,而不是外在于其生命本體的異己力量。
二、生命哲學視野下特殊教育的發展趨勢
關注生命是時代的強音,特殊教育需要兒童作為生命多樣性的一種重要體現,同樣需要給予充分的關注和尊重。因此,生命哲學視野下的特殊教育,要求教育直面特殊需要兒童作為人的本質,更要求整個社會提升對他們的生命關懷和價值肯定。
(一)特殊教育理念的提升
柏格森認為,智力在生命面前無能為力,因此教育教學千萬不能用狹隘的智力觀以偏概全地對待一切教育對象和學習內容[5]。這一觀點對特殊教育理念的提升有著重大啟示,同時也與我國和諧社會建設下“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具有同位性質。如果學生首先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不是一個鮮活的生命,那么他生命價值的實現是極其有限的。因此,新的特殊教育理念首先要求摒棄將特殊需要兒童當作成人依附者的觀念,而把他們視為獨立的“個體”。在教育目的上提出開發所有學生的潛能,使特殊需要兒童成為他們自己的旨歸。在教育方法上,要求不再針對個體之不足進行“補償性”、“糾正性”教育,而是依據個體優勢進行“發展性”、“建設性”的積極教育[6]。
(二)對特殊教育成果本位的強調
隨著特殊教育理念的提升,特殊教育領域出現了有關教育實效性的探究。所謂特殊教育的實效性,即學校所提供的教育和服務,對特殊需要兒童今后融入社會、獨立生活、獲得平等機會及培養其創造性一定是有益的。這一主題涉及在特殊教育過程中如何實施適當的教育。所謂適當的教育是指學生能夠從中受益的教育,即特殊需要兒童在享有平等教育機會后,要從特殊教育中獲益,做到生活獨立、經濟自主,并能充分參與社會生活;特殊教育要對他們未來的生活品質擔負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殊教育成果也是衡量“真正的”教育的一個標準,而要想達到理想中的特殊教育的成果,辦學者所持的特殊教育理念十分重要。
(三)特殊教育教師的角色轉變
教育與生命的本源性關聯表明,教師工作的對象不是知識,而是一個個充滿靈性、千姿百態的生命[7]。這就要求特殊教育教師必須跳出和超越傳統的訓練者角色,認識到教師的職責不在于“教書”和“訓練”,而在于喚醒和開啟新的精神生命。教師必須從“專業的教書者”轉變為“生命型的教師”,像生命哲學所提倡的那樣,用生命去理解生命,以自己的心靈喚醒學生的心靈,從而在教學生涯中構建新的共同特質,即堅持一種“以人為本”的理念,“視兒童自身為目的,而不是手段”。
(四)特殊教育課程改革
特殊教育的成果導向要求培養特殊需要兒童的生活適應能力。按照柏格森的觀點,直覺與體驗是生命中普遍存在的力量,真正符合生命的做法則是引導學生學會將自己置于認識的對象之內,使學習者與認識對象達到物我同一,從而實現自我體驗。這也啟迪特殊教育在課程改革中要以真實生活情境為核心組織教學與活動,并在其中充分考慮學生的體驗。此外,特殊教育課程改革并非只是教學設計的轉變,還應隨之配套完善相應的課程標準、評價體系等。
參考文獻:
[1]方明軍.生命哲學視野下的教育反思[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5,4,(5):31-33.
[2]娜仁高娃.生命哲學視野下的主體性教育[D].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3]劉琦艷.生命哲學對基礎教育的幾點啟迪[J].當代教育論壇.2008,2:29-30.
[4]石蘭月.生命視角中的教育[J].平頂山工學院學報,2003,12,(4):82-84.
[5]燕良軾.生命哲學中的教學理念蘊含[J].高等教育研究,2004,25,(4):12-16.
篇6
(關鍵詞) 自我批判,哲學創新,生命力
張揚哲學的社會批判功能,重建人的生活世界和生存價值,是現代哲學之思的一種路徑。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不是簡單地、刻板地描述現時代及現實問題,而是通過反思性的批判,對時代內容作出評價,進而明確時代進步的動力和發展趨勢,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也促使哲學自身的發展。
哲學從來沒有以提供知識為己任,哲學的本質在于提供思想。哲學本質上不是一種知識體系,而是系統的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維活動,它不是記住自己“是什么”的知識,而是思考“為什么不是這樣”和“應該是那樣”的一種追問活動,哲學不側重于學問,而更多是一種思考的狀態。正如哲學的本意在于“愛智慧”,即在于追求,而不在于終結;在于通過對現有現存的批判,為人們指出更新更合理的生存方式,以解答人們對生命的疑惑和意義,幫助人們更有價值地生存。之所以能做到這些,在于哲學與其他具體科學不同,它看起來不具體,不在某些確定的領域,不能解決具體的生活問題,但它能立足于整體和全局,在現實的運動中思考人與世界的關系,它幫助人們從身邊的瑣事中超脫出來,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人生和世界的根本問題,使人能活的明白,努力地去做一個有靈魂人。從事哲學研究而不批判現實,或者只知道為當下社會結構提供知識辯護,這有背哲學精神。
批判并不是對原有的全部否定,不是全盤拋棄,對現有的進行反思和批判,是為了以此為基礎探索新的發展道路,不是也不能是對過去的全盤否定,也可以說是對原有的進行適度調整,批判的基礎首先在于對現存進行合理的理解。正如馬克思對待黑格爾那樣,切莫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哲學的本質在于追求智慧的過程,但這個過程要立足于現實,以現實為根基,是在繼承中的發展和創新。哲學要幫助人們理解和認可現在的生活,為現實作論證;永不滿足是人的本性,但這是基于已經有所滿足這個前提的,不安于現狀的人類,是在已有現狀的基礎上的不滿足。如是,原有的哲學對現存的哲學思維活動,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可以說它是現有哲學思維活動的前提,沒有這樣一個前提作為批判的靶子,批判的血脈就無法繼承和延續,現有的批判者也就得不到足夠的精神食糧,就無法為人類的進一步發展作出奉獻。以實踐為基礎的人類認知活動,具有不同于一般生物的特點,人們以語言符號系統作為媒介和社會傳遞物,不但能夠掌握前人獲得的知識和經驗,實現以前人為基礎,同時也能夠把自己所取得的知識和經驗傳遞下去,為后人的認知和創新活動奠定堅實的基礎。這種社會傳遞方式使人類發展更快,同時要求人類對前人的東西進行鑒別,不能一味地全盤接受,否則就體現不出發展和創新了,所以批判是人類發展和創新的需要。哲學就是在西方哲學傳統的基礎上產生的,沒有對這個傳統的繼承,就不可能有哲學;當然,哲學對人類的作用,更在于對傳統的革新,在批判中實現對傳統的變革。對現實的論證,也是哲學批判得以進行的條件,在論證中才能深刻理解現實生活,才能發現其中的不足,才能知道批什么以及應該怎樣去批判,通過批判要么修補了原有的觀點,從而實現超越,或者摧毀了原有的體系,實現自我揚棄,開拓出新天地。
批判精神是與時俱進的要求,與時俱進是的品質。哲學的產生,絕不意味著人類哲學思想發展的結束,而是在更高的階段繼續向前推進的開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沒有把自己的哲學自封為終極的思想體系,認為理論必須隨著生活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它自身的定位就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堅持理論與實踐能動統一的原則,就要把理論理解為一種歷史現象,它既是歷史環境的產物,又是變化著的歷史環境的創造者。經濟全球化和飛速發展的社會,使人們更容易看到現代性的東西,同時人們反叛與遺忘歷史的心理日益加重。人們在親近新東西的同時,將過去的一切幾乎都要廢棄掉了。這種貌似徹底批判實是的躁動,不僅是膚淺和浮躁的表現,而且會帶來難以想象的危害。只有堅持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才能克服短視、淺薄和狂妄。理論之花的繁榮,是人類能力和品格提升的體現和表達。
哲學之思是反思性的思維方式,在追根究底的過程中,對構成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因素不斷進行追問、檢討和批判。這種反思,既體現了人與世界關系的“為我性質”,也體現了關于人類的活動狀況和歷史發展階段的“從后思索”的特性。哲學反思在其合理形態上,是一種辯證思維,其本質是批判性思維。哲學批判不是單純的消極的否定、破壞和全盤拋棄,它是積極的培育、建設和創造,是破與立的統一。哲學批判是自我批判,其批判更為自覺和徹底,批判使理性的人成為了能動的自我超越的主體,批判是人類精神生活中的必要的基本素質。哲學之思反對人們對現行的生活態度、道德習俗、審美情趣、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采取無批判的全面接受態度,反對人們躺在因循守舊、循規蹈矩的溫床上睡大覺。哲學是深沉的反思,是厚重的批判,它有別于那些不斷制造“轟動效應”的行當。解決哲學關注的困惑、時代命題,需要靜下心來認真思考,需要以海納百川的寬容來對待,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態來追求和探索,任何浮躁的作風不僅于事無補,而且會引人誤入歧途。
在哲學批判中,通過對時代的存在和意義的理解或自我意識,科學地把握實踐中的矛盾,正確地提出問題,以及對事物特別是慣常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理論前提的勇敢懷疑,是兩個至關重要的環節。不能正確地提出問題,批判就會失去對象,“胡批”、“亂批”不是哲學的功能;沒有勇于懷疑的精神和態度,迷信權威,唯書唯上,做習慣思維、習慣勢力的奴隸,也就不可能有批判的要求。
哲學批判是徹底的批判,這種批判貫穿著對批判者及其哲學本身的自我批判,它所批判的不僅是作為思想對象的現實,更是哲學理論或哲學思維方式自身。哲學的自我批判內在要求批判者敢于正視并勇于承認時代、環境、傳統給自己造成的局限性。無人能超越自己的時代,制造永恒者恰恰不能永恒。真正有生命力的哲學,在于它自覺地意識到這種局限,并將對這種局限的反思、批判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前提。只有不斷地進行自我批判,才能不斷深化對人的現實存在的歷史性的理解,從而才能確保哲學的價值性原則不會因僵化自封而死亡。通過不斷地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修正、自我超越,才能使現代哲學的價值立場更為合理,才能為人類更合理地生存和發展提出更優的方案。
哲學通過冷靜無私地反思和批判,通過對時代的自覺把握,逐步認清人類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狀況,進一步明確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使命,從而增強人自身發展的方向感,增強實踐的自覺性、預見性和有效性。哲學之不可替代,在于人類不能沒有關于自身存在和發展意義的理解或自我意識。哲學以自己提出的新問題、新的提問方式,以及對問題的新探索,批判性地反思人類生活的時代意義,理性地揭示人類生活的矛盾與困惑、理想與選擇,從而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到來。
哲學的創新是必須的,但創新不是隨意進行的。只有當能夠進行自我批判和系統反思的時候,才能實現自我完善,才能向前發展,才能既肯定自己又超越自己,不僅實現哲學創新,而且能夠推動社會現實的改變。
哲學必須創新的根據,在于實踐沒有止境,新的實踐要求有新的哲學指引,因此創新也就沒有止境。一定社會歷史階段上的實踐,由于受到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等因素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局限性;不同歷史時代的社會實踐具有不同的時代特征,具體實踐活動的對象、內容和水平也都各不相同。實踐是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是在限定和超越限定、制約和打破制約的矛盾斗爭中不斷前進的。只有在實踐中勇于創新,不斷求得新的真知,才能永葆哲學的生機和活力。不同時代不同時期的哲學創新,從來都是以當時實踐突出的問題作為自己的立足點和著眼點,并存在著自己特有的歷史局限性,不斷克服這種局限性就構成了歷史的連續和理論的發展。哲學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實踐中能夠不斷創新,每一次理論上的重大突破,都是對于現實實踐的徹底反思和深刻批判的結果,不僅為人們解決現實問題指明了途徑,更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指出了方向,并描繪出了具體的藍圖。哲學批判不是隨意進行的,不是感情用事的發泄,更不是故弄玄虛的炫耀,而是以社會實踐為出發點,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目的,冷靜理性地導引人們讓生命存在更合理,讓人與世界的關系更和諧。
在哲學創新過程中,必須以社會實踐的發展為依據,根據實踐的歷史任務和所提出的問題,結合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才能夠進行。理論源于實踐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但不能以為,在實踐基礎上會自然而然地形成新的理論,也不能認為實踐活動越多的人,理論水平就越高。哲學的創新要掌握前人傳下來的思想資料,要提高自己的理論修養,要開闊眼界、勤于實踐,善于接受同時代人的新見解,敢于提出解決問題的新思路,不為世俗所羈絆,要以海闊天空的胸襟和卓越超凡的智慧,才可能進行艱難的創新。創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切不可把創新簡單化、庸俗化。所謂表述、術語、概念的變換,或者陳詞濫調的翻新,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創新。
對社會實踐的反思和批判,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是為了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在批判中,才能培養人的獨立意志和懷疑精神,才能因此逐步走向公平公正的新境界。當代中國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步伐較快,在這只爭朝夕的節奏中,有時來不及對當下所發生的進行反思,更不用說批判地評價了。這不利于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現代化是人類的必由之路,在現代化過程中,可能產生正負兩種效應,我們應努力避免負效應的出現,即使出現也要想方設法使負面效應降到最低限度。加入Wm后,我國在經濟領域日益與國際標準接軌。同時我們又有著自己光輝燦爛的文明傳統,我們應在深刻領悟中華文化根本精神的基礎上,容納西方文化精要,以文化的自覺和實踐,再興中華文明。
篇7
生命的哲學定義:生命是生物的組成部分,是生物具有的生存發展性質和能力,是生物的生長、繁殖、代謝、應激、進化、運動、行為表現出來的生存發展意識,是人類通過認識實踐活動從生物中發現、界定、彰顯、抽取出來的具體事物和抽象事物。
生命的本質:生命是條件產物,從出生到成長,到衰老,死亡, 整個過程的完成都時時伴隨著各種條件,有些條件具備延續生命則為福,有些條件具備結束生命則為禍。生命于自然,社會中就處于自我選擇,自然選擇,社會選擇。生物是具有生命、生存意識、生存性能的自然物體。生命和生物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生命、生存發展性能、生存發展意識是生物具有的本質、屬性、規定和規律,是生物的組成部分和組成元素。
(來源:文章屋網 )
篇8
關鍵詞:天;命;性;生命;《中庸》
中圖分類號:G40-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124(2016)01-0024-08
“天命之謂性”是《中庸》開篇提出的第一個基本命題,是對《中庸》生命思想的集中表達和總體概括,揭示了生命的本源性、普遍性、目的性。“天命之謂性”所表達的生命思想具有深刻的教育哲學意蘊。
一、“天”、“命”與“性”的本質內涵
1. 天:生生不息、創生萬物的本源存在
《中庸》中的“天”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天”①一樣,具有多重含義:
其一,自然之天。“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中庸》第二十六章)這里所言的天是對地而言,自然之天的色彩非常濃厚。
其二,人格意義上的天。“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朱子注解為:“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中庸章句集注》)“誠”即是真實無妄。“天”的本性真實無妄,其運行也真實無妄。由“誠”到“誠之”,由“天之道”下貫成“人之道”,讓人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中庸》之“天”具有的某種人格上的意義。
其三,主宰之天。《中庸》還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中庸》第二十六章)。天地是“至誠無息”的,所以才能具有博大、厚重、高遠、光明、長久、永恒的德性;才能“為物不貳”,“生物不測”,使萬物得以生成滋養。
最能體現《中庸》“天命之謂性”之“天”的思想內涵的是作為名詞的“自然”和作為形容詞的“自然的”,分別對應英語的“nature”和“natural”,是一種本源性的自然存在,即“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莊子?逍遙游注》),“天,則就自然者言之”(《朱子語類》卷五)。《中庸》第二十六章言:“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萬物載焉。”這里的天是對地而言,與“天命之謂性”的“天”一樣,自然之天的色彩非常濃厚。《說文》:“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說文解字注》),“至高無上,是其大無有二也”(《說文解字?一部》)。這些注釋說明了漢語語境中的“天”傳遞給人的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基本意象,體現了其對于萬物生命(當然也包括人)的凌駕。伍曉明先生也指出:“‘天’――本來意義上的天,或所謂‘自然’之天――的自然特征首先就正是高和明” [1 ],即《中庸》第二十六章所言的“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本《中庸》以‘高’和‘明’來形容天,其實正是對天的最普通、最真切而又是最為意味深長的描述” [1 ]。天本質上是一種無限性和超越性的精神性存在,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中庸》第二十六章)的形上存在,是一個生生不息、創生萬物的生命之流。此“天”正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中的“天”。“天”是乾,是生命的起源,呈現蓬勃向上之勢,自然地蘊涵和承載著生命。在《中庸》看來,“就人而言,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之性,乃天之所命,與天有內在的關聯;天的無限價值,即具備于自己的性之中,從而成為自己生命的根源” [2 ]。
2. 命:貫通“天”與“性”的中介
“命”在古漢語中有名詞、動詞、形容詞三種詞義類別。名詞和動詞詞義的“命”是基本詞義,形容詞詞義的“命”是由名詞和動詞詞義的“命”衍生而來,其意相當于現代漢語詞義的“……的”。作為名詞的“命”有生命、性命、命運之意;作為動詞的“命”具有命令、使派、賦予、給予之意。從文字學上看,最早見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命”和“令”兩字往往是可以互解的。傅斯年先生的考證表明:“‘命’字作始于西周中葉,盛用于西周晚期,與‘令’字僅為一文之異形。” [3 ]《說文》曰:“命,使也。從口從令。”(《說文解字》)段玉裁注曰:“命也,天之令也。”(《說文解字注》)后來的阮元在《經籍纂詁》中則以“令也”、“教也”、“使也”等來解說“命”字。這里的命蘊含一種不可違抗的意思。《左傳?成公十三年》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孔穎達在《易?乾卦?疏》曰:“命者,人所稟受。”應當說,最初由“命”合成的“性命”、“生命”與天有著緊密的聯系,由天命下貫而成。“性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 [4 ],人之“性命”、“生命”由上天給予,領受于天命,并要理解和遵行天命。
“天命之謂性”之“命”是在由動詞轉化而來的形容詞詞義上來使用“命”的,“天命之”即“天命的”。我們在上文對“天”作了“自然”或“自然的”理解。循此,“天命之謂性”可以解釋為:自然萬物生來所稟賦的根本的內在的東西就是生命的本質。意思是說,“性”本于自然,成于自然,“命”上顯于天,下化成性,是貫通“天”與“性”的中介。在這里“命”作為謂語動詞使用,從天(發號主體)的角度來說是“賦予”、“委任”、“委托”,從性(受令主體)的角度來說是“稟受”、“接受”,理解和遵守天的指令而完成自己的生命活動,即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所言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二程也說:“天所付為命,人所受為性。” [4 ]在這里,“命”實際上就在命者(天)與受命者(生命)之間建立了一種委托性的契約關系,“命”使“天”得以發揮其決定性的支配作用,“性”則使“天”賦予“命”的內容得以表達。朱熹在《中庸章句》中也把“命”釋義為“命,由令也”,正是“命”的存在才使得天的博厚、深邃、高明得以下貫于萬物的生命之中,即“天之賦予萬物者,謂之命”(《朱子文集》卷六十七)。正如國學大師唐君毅先生所言:“‘命’這個字代表了天和人的相互關系……‘命’存在于天人之間相互的影響和回應以及相互的取予之中。” [5 ]“命”即是上天生生之道的過程表述,是天地自然界具有神圣意義的目的性活動和轉化機制,“不僅僅存在于外在的‘天’之中,也不僅僅存在于內在的‘人’之中” [5 ],“命”承接的是“天”,指向的是“性”,孕育在生命的生長、發育、流行之中。
3. 性:上天所賦予的自然生命
《中庸》開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在《中庸》里被看做是修道立教的基礎。古往今來,關于“性”的闡釋很多,除《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認為“性一般指人性,亦有天性、本性等涵義” [6 ]之外,人們還從天、理學、心學、生等不同的角度闡釋了“性”②。在先秦哲人對生命的追問中,性字與生字往往直接相關。大約晚周時期,人們開始將目光由上天轉向人自身,積極探索人自身生命的內在主宰力量和生命形成與發展的依據,并有意識地把“生”字與“心”字結合,由此產生了“性”字。據徐灝《說文解字箋》中的研究:“生,古性字,書傳往往互用。《周禮》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為性。”生字像草木從土中生長出來,由其象形義可進一步引申出生命的意思,五代時期的徐鍇在《說文系傳通論》也言:“故曰;性者,生也。既生有稟,曰性”。
《中庸》里對性的論述并沒有具體展開,借助同為性命之學的《性自命出》中“性或生之”的命題或許有助于我們窺見《中庸》之性的真義。“性”與“生”均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范疇。“性或生之”的意思是說生是性的本義,其理論價值在于正式提出了性的最基本的內涵就是生命本身。“性或生之”蘊含著生命自身的創造,生成和目的等諸多方面的內容。《中庸》里的“天命之謂性”的性亦含有生命之義。“天命之謂性”是說生命是上天所賦予的,這實際上是從本源上定義了“性”,由于天是宇宙生命的本源,性(生命)即是由天所賦予人的本質性的東西。“性”從天(宇宙自然)而來,是一種“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就是《中庸》談到的“誠”。“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中庸》第二十章),所以在徐復觀先生眼中“誠即是性” [7 ],“誠”作為天道的本體,是“性”之實現和完成的根源,即“凡天下之物,誠之則有,不誠則無,故物之始終,全系于誠也” [4 ]。錢穆先生也認為:“性則賦于天,此乃宇宙之至誠。” [8 ]《中庸》里的“性”(如率性之謂道,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盡性等)均可理解為上天所賦予的天然的、自然的、固有的資質,即是指生命。“故誠乃自成,而其道乃自道也,非有假于外也,我固有之也” [4 ],“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所有固有也” [9 ]。告子、莊子、荀子都有過與之相類似的精辟論述,如告子的“生之謂性”(《孟子?告子上》),莊子的“性者,生之質也”(《莊子?庚桑楚》),荀子的“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不事而自然謂之性”(《荀子?正名》),以及后來韓愈的“性也者,與生俱生也”(《原性》)。
二、《中庸》“天命之謂性”所闡發的生命思想
“‘生’的問題是中國哲學的核心問題,體現了中國哲學的根本精神。” [10 ]《中庸》正是緊緊圍繞“生”(性)、生命(性命)等問題與現象展開論述的,是典型的儒家性命之學,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精神。《中庸》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寬裕雍容的生命哲學,它并不是純粹地以科學的理性分析手段來對待、處置和研究生命,而是在“天―地―人”三位一體的天道與人道相統一的結構中,在“人―物―我”的相互關照下審視生命這種宇宙中存在的獨特現象,此種生命意識恰恰是西方生命哲學所欠缺的。
《中庸》認為,“天”的內涵需要通過“天道”體現出來,“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中庸》第二十六章)。“博”、“厚”、“高”、“明”、“悠”、“久”實際上表明了天的生生不息以及化育萬物生命的功效,生命即是在上天自然悠久無疆的不斷創生過程中存在并生成的,“天”是被體現的對象,“性”是體現的一種結果。“天命之謂性”實際上構建了由“天”而“命”至“性”的生命創生模式,亦即天命下貫模式,蘊含了《中庸》對生命本體及其生成展開的認識以及儒家天人關系的基本觀念,類似于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中“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所體現的生命生成模式,這也體現了商周到春秋時期一直嘗試由外在的天轉向人的思想主流。“天命之謂性”是說個體自然稟受的本然的東西就叫做“性”,生命的發展是在對“天之性”的體悟和踐行中自然而然的過程。盡管從現代生命哲學的角度來看,《中庸》所言的“天命之謂性”似乎并不能如具有科學化傾向的西方生命哲學一樣為生命的具體形態找到確定的位階與秩序,但“天命之謂性”卻體現著極為博大寬廣的宇宙生命觀,主要包括生命的本源性、生命的普遍性、生命的目的性三層意思。
1. 生命的本源性:生命源于自然,本于自然
所謂“生命的本源性”是說生命的根源、淵源、源頭在哪里,也就是關于生命從何來的問題。錢穆先生用《中庸》釋《中庸》:“性則賦于天,此乃宇宙之至誠。” [8 ]正是天賦予了人之“性”,才使“性”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自然特質,“性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 [4 ]。人的生命正是從天那里獲得自身的本質性內在規定(或“質”或“理”)。“天命之謂性”實際上就回答了幾千年前先哲們一直苦苦思索的生命本源問題。《中庸》理解的生命是從“天”而得,由“命”進行轉化,“天”作為一個宇宙本體,規定著生命的本性和價值之源。鄭玄用漢代五行思想對“天命之謂性”進行解釋:“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 [4 ],朱熹用理說性:“命,尤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11 ]。二人的立足點不同,但都把握住了“天命之謂性”這一命題所傳遞的基本信息:天作為宇宙的本體性存在,是萬物衍生的根源;人的生命源于自然,本于自然。徐復觀先生也認為:“性乃由天所命而來,一切人物之性,皆由天所命而來。至誠,盡性,即是性與命的合一。” [12 ]如果說迄今為止所見到的關于先秦心性論的最早、最完整的文獻――《性自命出》是從現實的人性向天命追溯,出發點是人,方式是追根溯源式的話,那么《中庸》直接以天命來規定人性,出發點則是天,方式則是本體貫注式的 [13 ]。
《中庸》把天“當做指述‘形上意義之本體’的詞語看” [14 ],“天”是宇宙萬物的價值本原,本質上是一種無限性和超越性的超驗性存在,是一個生生不息、創生萬物的生命之流,并賦予萬物以生命和意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中庸》第三十三章),天的生生之道雖是無聲無臭的,但卻是客觀的普遍的而無所不在的,即“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中庸》第二十七章)。正如蒙培元先生所言:“天地‘生物’,亦可以說是天地之道‘生物’,自然界作為生命整體,其本性就是‘生物’,就是‘化育’萬物,天地之高明博厚,就是一切生命的根源” [15 ],在《中庸》看來,作為自然意義的天是一個生命整體,具有覆載生養宇宙萬物生命之功效。“生物”和“化育萬物”是天的大德,即“本性”,“生物”是“載物”、“覆物”而又“成物”的前提,而一切生命的根源在于高明博厚之天,即“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中庸》第二十七章)在《中庸》第二十六章的描繪中,日月星辰、江河山川、禽獸寶藏、草木山石、魚鱉蛟龍等萬物生命經過不斷地生殖繁衍,體現出一派生機盎然欣欣向榮的景象,而這正是“天”之生生創造功能的體現。“為物不二”與“生物不測”也是用來形容天的創生功能。《中庸》第二十六章還引用詩經的話,“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這與《易傳》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及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思想基本一致,也從本體論上精辟地闡明了生命產生與發展的本源,體現了《中庸》的生命本源觀。
2. 生命的普遍性:由“天”而“命”至“性”的生命生成與展開模式
所謂普遍性,是指對于一切人乃至一切生命都是適用的、有效的。“天命之謂性”除了回答生命的本源和目的問題之外,還構建了一種由“天”而“命”至“性”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命生成與展開模式。牟宗三先生就認為,《中庸》“天命之謂性”代表著中國生命哲學里從天命,天道下貫而為性的老傳統。由天這一創生實體賦予個體生命性體的事實是一種典型的宇宙創生論式的說法,將生命的根據直接與宇宙(天道)論掛鉤,亦是《中庸》的一大特色。而“誠”則是《中庸》用來溝通天人、物我的橋梁和中介,是天道性命貫通的根本,即“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二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中庸》第二十五章),“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中庸》第二十六章)。“至誠不息”之道即是其永不停息的生命生成與運行之道,誠從生命的意義上確立了天“生物”、“化育”萬物的真實性。
天賦予(“命”)人和萬物以“性”,人和萬物又通過“盡己之性”、“盡物之性”始終保持與天地自然的和諧一致。由于人與萬物同稟天命之性,稟賦著同質的價值,也就是張載所說的“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正蒙?誠明篇》)。“‘天命之謂性’更重要的是:使人感覺到,自己的性,是由天所命,與天有內在的關聯;因而人與天,乃至萬物與天,是同質的” [12 ],因而,宇宙間的不同生命從根本上來講也是平等的,生命與天具有著同等的性質,即“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第三十章)。萬物在生命的意義上是相同的,人之生命與物之生命均從天而來,不存在什么特殊,都有著各自存在的權利和價值,人不能高居物之上,不能主宰其他生命,這就與西方的“人類中心論”有著實質的不同。荀子對其思想作了更進一步的發揮:“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惡》)也就是,同為上天所賦予的生命在本質上一般是沒有什么區別的,這與《中庸》要表達的意思是一致的。
在“天命之謂性”中,“性”從天(宇宙自然)而來,就使得生命與天具有同等的性質,肯定了生命的本然獨立地位,讓生命越發地自尊、自信。在《中庸》看來,天賦予(“命”)人和萬物以“性”,人和萬物能通過“盡己之性”、“盡物之性”始終保持與天地自然的和諧一致,在這種共同本質的相互溝通中,在“天命之性”的內在基礎上通過“誠”實現了天地萬物宇宙人生“化生化育”的目的。
3. 生命的目的性:自我生命與他者生命的雙向互動
“天命流行”就是自然界的發育流行,人之生命是天命的賦予和實現,自然界的發育流行與人的生命存在之間實際上就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目的性關系。天命既不是完全自在的,人性也不是完全自為的,而是成己與成物的結合。在《中庸》看來,一方面,生命是上天的賦予,與天有著內在的關聯,人后天的發展不過是這種本質性內在規定的合規律合邏輯地自然展開罷了,人后天的各種努力都不過是實現或達成這種本質性內在規定而已。生命過程在本質上是一個自然天性自由展現的過程,即“盡人之性”和“成己”的過程。正如徐復觀先生所說:“只有在‘天命之謂性’的這一觀念之下,人的精神才能在現實中生穩根,而不會成為向上飄浮,或向下沉淪的‘無常’之物。” [12 ]
另一方面,宇宙自我生命和他者生命(人與物)都是自然界生命整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萬物生命存在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實現自身的發展(《中庸》言:“成己”),其存在也離不開他物、他者生命的作用,還要以他物、他者生命的存在而存在(《中庸》還言:“成物”),于是,他們之間就建立一種目的關系。這正是《中庸》“盡物之性”和“成物”想要闡明的目的意蘊。“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第二十二章)“誠者,非自成而已矣,所以成物也……成物,知也。”(《中庸》第二十五章)主體生命實現自身價值意義的同時,還要賦予自我生命的外部世界以價值意義,他者生命的完善又能為成就自我提供動力與支撐,自我生命與他者生命的完善就構成了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
三、《中庸》“天命之謂性”生命思想的教育哲學意蘊
正如葉瀾先生認為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過人的生命,為了人的生命質量的提高而進行的社會活動,是以人為本的社會中最體現生命關懷的一種事業” [16 ]一樣,《中庸》“天命之謂性”的生命思想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教育哲學意蘊:教育緊緊圍繞“性”(生命)展開,在起點上基于生命(“天命之謂性”);在過程中循于生命(“率性之謂道”);在目的上又歸于生命(“盡性”、“成己”、“成物”)。生命是《中庸》修道立教的阿基米德原點及最終歸宿,也就是說,《中庸》理解的教育本質將教育看做是屬于生命的和為了生命的活動,“教育必須立足于人的生命存在這一向度,尊重人和人的生命存在是教育價值合理性的基本要求” [17 ]。不關注人之生命的教育必然導致教育的失真與變質,是一種非教育、假教育、偽教育。離開生命、剝奪生命成長主動性和自由的教育亦不是真正的教育。
1. “率性”:自然本真的生命是教育的阿基米德原點
“《中庸》運用獨特的概念、范疇、命題和思維方式全面闡述了生命及其教育問題。” [18 ]王陽明在釋《中庸》時,認為“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傳習錄?薛侃錄》)。“天命之謂性”實際上就從“性”(生命)的角度回答了教育的本原問題。“性”作為上天賜予萬物生命的自然秉性,是一種“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 [11 ]。“誠者,天之道。”誠是自然的普遍法則,也是生命內在的客觀準繩。實質上是說,“誠”即“性”,是一種根植于人的內在生命的自然天性。所以鄭玄注曰:“言‘誠者’,天性。” [19 ]誠如王夫之所說:“性、教原自一貫;才言性則固有其教” [20 ],教因性而立,性因教而成,“誠明皆性,亦皆教也”(《讀四書大全說?中庸》)。性是教育活動賴以產生與形成的基礎,任何趨向的教育活動都必須矗立在生命這塊基石之上。“性”的存在為《中庸》“率性”、“尊德性”與“盡性”等修道活動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自性而道,自道而教,性道教一體連貫。
荀子言:“性者,本始材樸也。”(《荀子?禮論》)本始材樸的生命給教育提供了“可學、可事”的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實際上就為教育活動的順利展開提供了可能性。傳統經典之一的《淮南子》則把性與教育有機統一起來:“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淮南子?泰族訓》)。這表明了“教訓”之類的教育活動里離不開“性”,“性”的發展也離不開教育的觀點。“性”的存在是教育產生的前提條件,只有通過教育才能發展“性”。梁啟超先生曾對“性”與“教”之間的關系有過精辟的論述:“為什么要教育,為的是人性可以受教育……無論教人或教自己,非先把人性問題解決……一個人意志自由的有無,以及為善為惡的責任,是否自己承擔,都與性有關系。性的問題解決了,旁的就好辦了。” [21 ]在梁先生眼里,性就是教育的基礎,非要把性的問題解決了,才能更好地開展教育。“性無不善,循而行之,是之謂道。道有品節,修而全之,是之為教。” [4 ]其實,《中庸》里并沒有直接對性之善惡進行詳細闡釋,但既然講要“率性”、“尊德性”和“盡性”,且《中庸》又十分推崇象征美好的“誠”,將其視為人之生命的內在本質(“誠之者,人之道”),實際上就表明了《中庸》的觀點:人之自然本性中含有某種良好的向上的潛質。也就是孟子眼中的善端③、夸美紐斯所言的“種子”④、康德所指的“胚芽”⑤。教育的本質就在于激發和喚醒這種內植于生命之中的天性與潛質,發現和發揚自己內在的先驗的本性,孟子認為這需要“存心養性”⑥、“擴而充之”⑦、《中庸》則認為這需要“率性”和“盡性”,即“修道之謂教”:一方面可通過自我教育(“誠明”)的方式激活生命的內在本質(“誠”);另一方面可通過外在教育的方式(“明誠”)因勢利導地把生命的天賦發揮出來,具體的實踐途徑則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第二十章)。“率性”、“盡性”和“至誠”是一種生命自由自然發展并使生命得到最大綻放的歷程,也是一種基于生命而展開的教育過程,其立教的本原在于“天命之性”。
“天命之謂性”開宗明義:“性”秉承了“命”的至誠,為順利展開《中庸》遵循生命規律(“率性”―“道”)的人生修煉(“修道”―“教”)提供了可能,也是由“命”至“教”再達“性”的重要基礎。因此,《中庸》“天命之謂性”實際上在闡明生命本源問題的同時,也從生命自然觀的角度回答了教育緣以發生如何發生以及實際發生的基礎等問題,為教育活動的展開進行提供了價值基礎和理論來源,即形成了“天―命―性―道―教”上下相互通達的生命實現模式,從而回答了人類教育發生的本原問題――教育源于生命自身發展的需要⑧。“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中庸》首章),這里的“道”亦表達了教育時刻也不能離開生命原點的道理,“率性”的教育必然是屬于人的生命的、基于人的生命的、為著人的生命的,“必須立足于人的生命存在這一向度,尊重人和人的生命存在是教育價值合理性的基本要求” [17 ]。人的生命的存在與延續、維持與提升、發揮與實現一刻也離不開教育,“人是教育的、受教育的和需要教育的生物” [22 ],任何偏離生命原點的教育、偏離生命目標的教育,都不是真正的教育或只是被異化的教育,也就是杜威先生所說的:“沒有考慮教育的本質” [23 ]。《中庸》“天命之謂性”實際上就啟示我們不能游離于生命之外去考量教育,教育要以自然本真的生命(“性”)為阿基米德原點來展開。
2. “盡性”:最大限度地激活生命是教育的最終目的
“天命之謂性”洋溢的是強烈的生命主體意識,視生命為教育的原點和最終歸宿,這與當下諸多偏離生命原點違逆生命規律的教育形成鮮明的反差。《中庸》理解的教育本真是要從內植于生命之中的“性”出發,以達成“性”的整全為目的,即“使教育回到人、人的生活中來,把促進人的發展和生活的完善作為教育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教育要以‘育人為本’” [24 ]。“生命承載了教育的全部目的,生命是教育永恒的和基本的工作場,生命中發生了教育的最終動力,生命作為億萬年發展的成果,擁有教育最寶貴和巨大的資源。” [25 ]但《中庸》“天命之謂性”并未僅僅停留在教育發生的基礎等問題的認識上,還從目的論的角度揭示了教育即促進人的生命生長的觀點,教育面對的是活生生的生命存在,教育目的需著眼于個體生命的生長,而不能使個體生命的生長屈從于外在于人的生命的事物,即“人是目的,人在任何時候要被看成是目的,永遠不能只看成手段” [26 ]。
《中庸》言“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中庸》第二十二章),這本身是對“天命之謂性”的回應與拓展。在徐復觀先生看來,“‘至誠’即是‘盡其性’。此性乃由天所命而來,一切人物之性,皆由天所命而來。至誠,盡性,即是性與命的合一。” [12 ]《周易?說卦傳》則有“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說,北宋理學大師張載的“盡其性然后能至于命”(《正蒙?誠明》)也是由此繼承演化而來。《周易?說卦傳》與張載之說把“盡性”與“天命”聯系起來,表明了人必須先盡其性,之后才能達成命。《中庸》之“盡性”其實也是對天命的落實,是根據天命之性而引導自己完成和實現人之天命的過程,亦是去實現人之生命或人之為人,是一種生命的“修道”。錢穆先生在他的《人生三步驟》一文中將“性命合一”作為人生命的最高層次。《中庸》里“盡性”與“至誠”即是對“天命之謂性”的呼應,要表達的也是要充分地展現和發揮生命的自然天性,徹底地激活生命的內在潛能并使生命得到最大程度綻放的意思,從而實現“性命合一”,達成“至誠”、“盡性”的生命最高境界。“盡”有最、極、充分、完全、最大限度等意思,按《中庸》的邏輯,“盡性”就是要充分徹底地發現生命、發掘生命、發揮生命、發展生命,將上天賦予的生命天性發揮到極致,“盡性”的落腳點在生命,是為了最終實現生命的自由成長和全面綻放。唯有盡此,宇宙才能生生不息,最終達成人之生命與天地萬物生命和諧統一的《中庸》至誠境界。即《中庸》第二十二章所言的:“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因此,“天命之謂性”不僅回答了《中庸》立教的本原問題,還回答了其最終歸宿的問題。同出《禮記》的《大學》中有類似的觀點,即通過“教育”與“養性”使人能夠經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性命合一”以及“性”與“天”的統一。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則知天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盡心上》)只要個人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⑨,最大限度地發掘生命的善端與潛能,就能認識生命本身固有的本性,從而達到生命的整全,這個時候也就懂得天道了。后世宋明理學的“學達性天”亦充分繼承和發揮了這種“盡性成物知天”的思想。按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理解,這種“盡性”的教育活動“關注的是,人的潛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并加以實現,以及人的內部靈性與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 [27 ]。若用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話語來表達,那就是:“教育將更強調人的潛力之發展……強調向自我實現的發展。這種教育將幫助‘人盡所能成為最好的人’” [28 ]。
注 釋:
①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將其概括為“五義”:“所謂天有五義:曰物質之天,曰主宰之天,曰運命之天,曰自然之天,曰義理之天。”物質之天即與地相對之天;主宰之天即所謂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如《論語》中孔子所說之天;運命之天即孟子所言“若夫成功則天也”之天,指人生中吾人所無奈何者;自然之天指自然運行之天;義理之天,如《中庸》“天命之謂性”之天,乃謂宇宙之最高原理。此五種天可分別對應:“天”、“上帝”、“命運”、“自然”、“先驗道德法則”。
② 從天的角度而言,性是天命下貫而成的產物,是上天所賦予的,是與生俱有、不可學不可事的先天遺傳素質。如孟子所言“性”是“天之所與我者”,荀子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等;從理學的角度而言,程朱學派把理看做是世界的本源,即所謂“權本窮源之性”,典型代表如朱熹就認為“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等;從心學的角度而言,王陽明把性與心看做是同一種東西,即“心之體,性也”,“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賦予人也謂之性,主于身也謂之心”;從生的角度而言,“性”實際上蘊含生的意蘊,具有“生命”、“性命”之意。如《禮記?樂記鄭注》中直言:“性之言生也”,“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荀子的“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中的“性”均具有此意。
③ 《孟子?盡心上》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善端”就是教育發生作用的基礎。
④ 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在《大教學論》中高喊:“種子自然存在我們身上。”
⑤ 德國教育家康德曾言:“人生來具有許多未發展的胚芽。”
⑥ 《孟子?盡心上》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⑦ 《孟子?公孫丑》言:“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⑧ 在人類教育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由于人們對人性本原的不同理解,曾經形成了知識論、道德論以及力量論等不同的教育起點觀。知識論的教育起點觀以“知識人”的培養為目標,圍繞知識的傳遞來搭建整個教育的邏輯體系;道德論的教育起點觀以“道德人”或“善人”的培養為目標,把德性看做是人的本質規定性;力量論的教育起點觀視非理性為人的生命本質,過于鼓吹生命本能的沖動力量。三種教育起點觀其實都只是側重人的生命的某一方面,片面地放大某一維度的價值,并以此為基點來構建教育體系,導致培養的人只可能是不完整的人。《中庸》則從“性”(上天賦予的完整生命)出發,表達了健全和諧的生命、身心和諧統一的生命始終是教育的原點的觀點,這比知識論、道德論以及力量論等教育起點觀要全面深刻的多!
⑨ 《中庸》第二十章:“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其非常形象地闡釋了如何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問題。
參考文獻:
[1]伍曉明.天命之謂性――片讀《中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74,74.
[2]馬育良.重讀《中庸》――關于性情道誠和中節諸問題的若干思考[J].倫理學研究,2005(5):91-95.
[3]傅斯年.性命古訓辨正[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0.
[4][宋]衛 .中庸集說[M].楊少涵,校理.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14,14,270,272,14,6,19.
[5]唐君毅.先秦中國的天命[J].東西方哲學,1962(2):195- 198.
[6]馮 契.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K].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485-486.
[7]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411.
[8]錢 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M].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295.
[9][宋]程 顥,程 頤.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4:50.
[10]蒙培元.為什么說中國哲學是深層生態學新視野[J].新視野,2002(6):42-46.
[11][宋]朱 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北京:中華書局,2001:50.
[12]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50.
[13]丁為樣.從《性自命出》看儒家性善論的形成理路[J].孔子研究,2001(3):36-37.
[14]勞思光.大學中庸譯注新編[M].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41.
[15]蒙培元.《中庸》的“參贊化育說”[J].泉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5):14-24.
[16]葉 瀾.教育理論與學校實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36.
[17]樊 浩,等.教育倫理[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50.
[18]李 卯.《中庸》尊德性與道問學:本土生命教學思想初探[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4(1):52-56.
[19][漢]鄭 玄.禮記正義?中庸?十三經注疏之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0,40.
[20]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六冊[M].長沙:岳麓書社,1996:892.
[21]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538.
[22][德]O.F.博爾諾夫.教育人類學[M].李其龍,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188.
[23][美]杜 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6.
[24]魯 潔.教育的原點:育人[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科版),2008(4):15-22.
[25]郭思樂.教育激揚生命――再論教育走向生本[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6.
[26][德]康 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苗力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81.
篇9
的“生命”是由“身體”和“心”組成的,但莊子主要強調通過《養心》來提升“生命”。莊子認為,心靈的修煉決定了生命的存在狀態,因此他強調,我們必須堅持“乘物以游心,不情愿地環游太平洋”的修煉原則,使人們能夠在心中培養一種空虛和沉默的狀態,即,實現“游心乎德之和”的修煉目標,回歸本真狀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莊子提出了《心齋》、《坐忘》、《攖寧》和《自得》的繁殖方法。莊子培育“生命”的智慧對現代人培育自己的“生命”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莊子。but的《莊子》關注身體和心靈的生命,認為人需要精神文化來滋養生命。在莊子看來,, 這個 耕種 屬于 介意 決定 這個 現有的 狀態 屬于 《莊子》內篇提出,人們應該充分遵循“隨遇而安,放飛心靈,回歸the inevitable”的原則 所以 像 到 收到 人 進入 這個 狀態 屬于 寧靜 屬于 介意 即 到 實現 這個 目標 屬于 返回 到 這個 自然的 狀態 屬于 “讓 他的 介意 漫步 在里面 這個 領域 屬于 自然的 和諧”。 莊子 提議 這樣的 混凝土 方法 像 “禁食 屬于 這個 “注意” “坐忘”、“土默爾中的寧靜”、and的“naturally acquired”,Zhuangzi關于滋養生命的智慧,對當代人滋養自己的生命仍有重要啟示。莊子。提高“生命”與“生命”相關。安的“生命”一般指安頓的不幸和迷茫的生活,以消除世界生活的困難,而提升“生命”則指提升生命,使生命的本質達到和諧的狀態。兩者的共同目的是提高生活質量和價值。因此,從廣義上講,這里的“生命”和“生命”屬于莊子所謂的“養生”實踐。當然,在嚴格的意義上,提出“生命”無疑不同于于安的“生命”。“生活”關注的是安頓下來放下生命,避免生命受損,這是養生實踐的基本課題。而“生命”則著眼于提升生命,使生命達到和諧狀態,這是養生實踐的高級階段。兩者明顯不同。本研究主要探討生命和諧的孕育路徑。根據莊子的內章,提高“生命”主要是通過《養心》實現的,《養心》的主要機制在于“蒂凡尼早餐”,也就是說,在寧靜、道德和生活的真實性之間徘徊。首先,人們普遍認為莊子的“緣督以為經”這是養生的基本原則。廣義上,這無疑是正確的,但狹義上,最好直接認為這是莊子“生命”養生的基本原則。從以下原文可以看出:“雪王國相信坐忘可以保護身體、一生、養育親人并持續一年。”[1]115很明顯,只要《緣督以為經》能夠達到“保身”和“全生”的目的“是為了達到保存生命的目的。毫無疑問,保存生命是養生實踐的主要內容和目的,也是安頓“生命”的主要實現途徑。當然,莊子認為,完全的養生顯然不僅僅是保存“生命”,因為莊子主張維護“生命”《乘物以游心》不能不看看養中的基本原則“[1]160。它還必須提高內心靈魂的培養,即培養內心空虛、沉默與和諧的境界。其中《乘物以游心》“意指心靈可以自由游動并適應外來事物的變化,其直接目的是“養中”。陳鼓應認為,所謂的“養中”意指“主體通過自我修養達到空虛和精神意識的境界,除了等級和地位的限制”[2]許建良指出,這里的“中間”就是中虛也就是說,內心的空虛與沉默2。當然,這里的“中”也包含了中和的含義,因為心是一個空寂的虛無狀態,它實際上是一個中和的狀態。因此,成玄英將養中解釋為“養中心”[1]160和書15并非不合理。簡而言之,莊子專注于用一顆空靈而沉默的中和之心來培養“生命”,而不是專注于維持身體意義上的“生命”。從狹義上講,身體的保存并不是莊子強“生命”恢復的主要內容,但莊子強調如何確保“生命”的實現路徑。只有內心的空虛和寧靜才是莊子想要發展的目標。簡而言之,它是通過修心而不是修身來達到空虛寧靜的人生境界。當然,
認為,莊子有理由通過培養心靈而不是身體或形體來培養一種“生活”,一顆空寂的中和之心。首先,既然我們想要培養這樣一種精神和諧的狀態,那么通過最直接的方式來培養心靈是一種自然的選擇。第二,莊子認為心遠對“生命”比形式更重要:“有一種可怕的形式而不會傷害心臟,有一種旦宅而不會無情地死亡。”[1]275也就是說,人的生命應該有沒有精神損害的身體變化,沒有精神死亡的身體轉變。如果形式改變了,思想和精神也會改變,這對生活來說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因此,莊子說:“與它在一起對它的形態和心臟來說不是一件很悲傷的事嗎?”[1]56可以看出,心臟的培養對于維持生命的存在狀態是非常重要的,但形態并不是那么重要。正如莊子所說,小豬們發現死母豬后,他們“在太平洋周圍”因為小豬們“看不見焉爾和類焉爾。愛他們母親的人不愛他們的外形,而愛他們外形的人”[1]209。這意味著,小豬們發現,盡管死母豬的身體似乎沒有變化,但母豬的生活狀態不同,因此小豬們“在周圍”根據郭象的注釋,“使其形者”指的是“才德”。成玄英解釋說,“天賦和美德,精神”[1]160,稀疏3,所以“使其形者”“是支配身體的精神。然而,修行顯然必須通過修行心靈來實現。莊子認為,心的修養決定了生命的存在狀態,因此他強調要加強心的修養,使個體養成一種空寂的心的狀態和境界,即強調要堅持心的修養原則乘物以游心,養中[1]160.
總之,內心的空虛和沉默應該是一種中和的狀態和境界。對此,莊子有著特殊的思考和探討。在他看來,最高的心態是“和諧”和“心莫若和”使個體達到精神空虛的和諧狀態。這就是莊子提出“生命”的目標,正如一些學者所說:“莊子真正關心的是人的自我和心靈的總和,在他看來,‘和諧’是生命的自然,應該成為我們的終極理想和不懈追求。”〔3〕莊子說:
·
·顏闔問余蘧伯玉,傅衛靈公的長子:“如果有人在這里,德天會殺了他。如果他有錯,危吾國就會被摧毀。如果他是對的,就會危及我。他的知識足以知道人們的錯誤,但他不知道為什么。如果是這樣,我的奈是什么?”蘧伯玉說:“善哉問乎!戒掉它并保持謹慎是個好主意。形莫若有一顆莫若的心。雖然兩人都有問題,但他不想進去也不想出去。他進入狀態,它顛簸,它被摧毀,它倒塌,它破碎。他帶著一顆和諧的心出來,這是一個名字,一個惡魔,一個罪惡。他也是個嬰兒,他也是個嬰兒。他是無町畦人,他是無町畦人。他是沒有懸崖,對于“生命”他是邪惡的,莊子認為“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必須實現,“形就”必須是“不欲入”。如果“形就而入”,則會導致“崩潰和崩潰”,根據郭象的注釋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1]160,注4,形就和不欲入的意思不同,“形就而入”的意思相同。而心和一定是不欲出,也就是說,光突出自己的能力是不夠的,因為如果你表現得太多,往往是一個“為聲”“名字,為妖為孽”,這也會把自己置于危險境地。
,如上所述,與形式相比,莊子當然更注重重心的培養,因為心臟能更好地決定生命的存在狀態,所以“心和”是莊子內在生命培養的目標,莊子的“心和”之和也是“德之和”,這是道德的總和,因此莊子強調游心乎德之和應該是道德的。莊子說:
·
仲尼說過:“死亡和生命是偉大的,不能隨它們而改變。雖然天地都在倒下,但它們不會被拋在后面。不動就判斷事物,命令事物改變并保留它們的祖先,這是真的。”常季曰:“這也是什么?”仲尼說:“那些從不同角度看待它的人越來越真誠。從同一角度看問題的人都是一樣的。如果一個人是這樣的,他不知道什么適合他的耳朵和眼睛,但徘徊在美德的和諧。事物看自己是什么,看不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失去了雙腳仍然是一種遺產。”[1]189
的精髓是在命物之化的基礎上實現“游心乎德之和”“也就是說,心靈處于道德和諧的狀態,這實際上要求心靈走在生命本質的和諧軌道上。其中,“命物之化”的意思是服從萬物的變化3,即“順物自然”[1]294。其實質是要求“守其宗”,即遵守“道”,而“游心”的樞機主教則遵循“道”4。如果人們按照“道”讓自己的心在“德”中徘徊"在和諧的情況下,自然會從同一個側面看待和包容萬物,即"物視其所一"。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忽略該機構的存在和保存,即“不知耳目之所宜”和“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海盜”。莊子認為,這種“游心乎德之和”的生活方式是精神和諧的最佳狀態和生命修養的最高狀態。事實上,這種狀態或境界是人們對生活真理的回歸和呈現。
《德之和》?這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論思維,在這方面,莊子內部主張將《心齋》、《蒂芙尼早餐》、《攖寧》和《自得》等修煉方法作為《德之和》生命境界的實現路徑”
主要通過堅持“游心”和“養中”的原則來提升他的“生命”,即主要通過《養心》來實現生命的修煉。因此,《心齋》自然是《養心》的具體操作方法之一。易言說,莊子的《心齋》的上升方式是一種自然選擇,因為莊子的《養中》意味著上升時的內心空虛,“心齋”也是實現精神空虛的途徑。莊子說過:
、
、仲尼說過,“禁食,如果我有一顆心,很容易作惡?這不適合皞天去改變。”顏回說:“回之家貧,只有那些幾個月不喝酒不吃肉的人。這樣,他們才能禁食嗎?”他說:“禁食是為了犧牲,不是為了心。”回族說:“敢問心齋。”仲尼說,“在雪域中,如果你不聽,你會聽心。如果你不聽,你會聽心。如果你聽,你會聽氣!如果你聽,你會停在福島上。如果你也是氣,你會空著去對待事物。唯道集虛。如果你是空的,你會禁食。”顏回說,,“如果你回來,你就會回來。如果你能回來,就不會有回報。它可以說是空的?”大師說:“盡矣。我的話是如果!如果你能用它的扇子旅行而不感覺它的名字,當你進入時發出聲音,當你不進入時停止。沒有門,沒有毒藥,你不能生活在沒有選擇的房子里。[1]146-148
顯然,莊子認為,如果你對有心(即有意的)做一些事情,那將不是“容易的”,否則它將與自然的理性(即“皞天不宜”)不一致。因此,莊子建議我們必須先通過“心齋”。當然,“心齋”不是《祭祀之齋》,因為《祭祀之齋》只需要“不飲酒不茹葷”。心齋指的是精神禁食,即培養一種純凈而空虛的心境,這是借助于“氣”來達到心境的,因為“氣”具有“虛而待物”的功能,即空性,可以容納外來的東西,只有“道”可以“收集”這種空虛。這種空虛實際上是指心靈通過修煉而達到的空虛狀態或境界,即形成一種心靈的空虛狀態5,即“心齋”。易言和如許建良認為,“心齋”是“由心靈的氣化驅動,其特點是空虛和靜止,這是“道”精神的具體體現[4]246.客觀地說,《心齋》的修煉方法并不能直接解決世界上人們遇到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它的主要功能是培養一種純凈而空虛的心態,即讓心靈達進入空虛和精神覺悟的狀態,使一切活動都能得到滿足心靈的聯系可以按照自然的原則來進行,也就是說,它可以自然地在心靈之外無意識地進行一切精神活動。由此可見,《心齋》的實用方法將有助于完成“游心乎德之和”,即精神和諧的目標和境界。
應該說,“蒂芙尼早餐”的養育方式與“心齋”的養育方式相似。兩者都強調通過精神修養來提高生命的共同目的,但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實際操作方法。《心齋》的佛法意義是指精神禁食的方法,其功能是修煉一種純凈的心境,即通過修煉使心靈達到空虛和精神覺悟。“蒂凡尼早餐”的佛法意義是指忘記形式和精神的方法,其功能是忘記對自己的所有約束,達到心靈的“大通”境界。莊子說:
、
、顏回說:“回益矣。”仲尼說:“它是什么?”他說:“忘記仁義。”他說:“可矣還不在那里。有一天我再次見到你時,他說:“回益矣。”他說:“它是什么?”他說,“回忘禮樂矣。”他說,“可矣還不在那里。”。“第二天,我會再見到你的。他說,“回益矣!”他說,“也是什么?”他說:“回坐忘矣。”仲尼說,“何謂坐忘?”顏回說:“四肢下垂,智力消失,形同虛設,就像大通一樣,這叫做坐忘。”仲尼說,“同樣的不好,變化是無常的。而其賢乎!邱,請跟隨。”282-285
由此知道,莊子所謂的“蒂凡尼早餐”不僅僅是“忘仁義”和“忘禮樂”,而是“形式”和“知識”必須被遺忘,也就是說,形式和精神都應該被遺忘。“墮肢體”是“離形”,它實際上是忘記了形式,也就是忘記了形式的局限性,這是為了消除人們從生理學中衍生出來的貪婪,屬于忘記形式的領域。而"黜聰明"是"去知",它實際上是忘記了智慧,也就是忘記了心靈的運用,它是為了拋棄人們從智慧中衍生出來的虛偽,這就屬于忘記上帝的范疇。毫無疑問,肉體上的貪婪和精神上的欺騙足以擾亂本應空虛、寧靜、和諧的靈魂,因此我們必須堅決揚棄它,以解除靈魂的枷鎖。只有這樣,人們才能到達“同于大通”王國,“大通”是指第六大道,“大通”王國實際上是指第六大道王國。現在人到了與大道一樣的狀態,自然就沒有對錯的好惡,可以毫無偏執地關注大華的演變,即"一樣不好",化學是無常也。這樣,精神和諧的目標才能實現。事實上,
的“遺忘”提高生命的方法是莊子一直非常關注的一種方法。莊子的內心反復強調,“遺忘”是一個明確的證據:“忘年忘義是受無竟啟發的,所以沒有什么可做的。”[1]108“當他們在太平洋周圍時,忘記他們的身體,何暇討厭悅生。”[1]155“美德有力量,但忘記形式,人們不會忘記他們忘記的,而是忘記他們不忘記的,這叫做真誠的忘記。”[1]216“在泉涸上,魚在陸地上,互相打濕,互相滋潤。在江湖上忘記總比譽堯而非桀好。”[1]242“它就像一個異物,把它抱在同一個身體里,忘記了它的肝膽,留下了它的耳朵和眼睛。它一直在重復,沒有任何線索。芒然在塵土飛揚的外面游蕩,逍遙乎沒有生意可做。他也可能是邪惡的。這是一種世俗儀式,讓觀眾耳目一新。”[1]268“魚相忘乎江湖,人們互相忘記,這是道教。”[1]272。這些“忘記”“這里所列的一種修身方法,與生命本身有著直接的關系。
。顯然,《攖寧》不僅可以看作是一種生活教養的境界,而且可以看作是一種生活教養的方法。當然,這里只是作為一種教養方式來分析。莊子說:
·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很古老,它的顏色像個孩子,何也?”說:“吾聞道矣。”南伯子葵說,“你能學會邪惡嗎?”“邪惡!邪惡可以!兒子不是一個人。夫卜梁靠的是圣人的才能,而不是圣人的方式。我有圣徒的道路,但沒有圣徒的才能。我要教導他們,普通人就會成為圣人。否則,通過圣人的方式很容易看出圣人的才能。我仍然保留著它并告訴它,我可以在三天內走出世界。我已經走出了這個世界,我保留著它,我可以在七天內走出這個世界天。我已經走出了這個世界,我可以再去保存它九天,然后它將是外生的。在它被外生之后,它將能夠穿透。穿透后,你可以看到獨立。看到獨立后,你就不會有古今之分了。沒有古代和現代,你可以進入不朽而沒有生命。殺人的不會死,活著的不會活。這是一件既能滿足也不能滿足的事情。一切都將被毀滅,不會成為現實。它的名字是《攖寧》。攖寧是一樣的,后者也是一樣的。“[1]251-253
由此知道,女偊雖然年紀大了,但他仍然有一個色若孺子。原因在于他的“聞道”,因為在“聞道”之后,他可以“孤獨一百年”(忘記世界的復雜)三天,然后“外物”(不是為了物質服務)7.只要“外生”能“朝徹”(心情像朝陽的升起一樣清澈透徹)8.只要“朝徹”能“見獨”(見《道的勝利》)9.只要“見獨”能“無古今”(突破時間限制),只要“無古今”就可以“不死不生”(“生”不受生與死的約束)10.作為《殺生者》和《生生者》,道本身就是不死不生的起源。道是一種東西。一方面,它有“一般”和“歡迎”,另一方面,它有“毀滅”和“成功”“這意味著,就整個宇宙而言,萬物始終處于生與死的變化運動中。莊子認為,這就是所謂的“攖寧”。所謂的“攖寧”,簡而言之,就是從“道”走向“寧靜”通過修行持道,即在紛擾中維持和平。其中,萬物的“意志”、“歡迎”、“破壞”和“成功”都屬于“成功”的范疇,它們的演繹節奏自然生成并自我形成。而“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徹”則,《見獨》、《無古今》和《不死不生》屬于“寧靜”的范疇,需要通過人們的修煉才能獲得,因此,《攖寧》的修煉方法要求人們面對運動的變化“歡迎”、“毀滅”、“成為”,即通過道家修煉,逐步實現寧定安然從“外天下”到“不死不生”的內在自我。
可以看出,莊子認為,如果你能保持《色若孺子》中的樣態,即使你已經老了,關鍵是不要動你的心,那就是保持內心的平靜。也就是說,攖寧就像《心齋》和《坐忘》一樣,可以使精神世界達到一種沉默與和諧的狀態,從而達到提升生命的目的。顯然,這本《攖寧》“提升“生命”的方法”無疑啟發了當今世界,為了提高“生命”的內涵和質量,回歸生命的真理,我們應該安全地面對塵土飛揚、勞碌和欲望的社會環境,始終保持一個平和冷漠的內心世界。
如上所述,一切事物的“意志”、“歡迎”、“破壞”和“成為”都是自然生成的,因為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斷變化的運動中生成和交換的,它們的生命詮釋的節奏是自我形成的。事實上,這意味著世界也需要磨練和使用“自得”方法來實現“養活生命”的目標,而不僅僅是通過對上述方法的內在修煉。莊子說:
的古代真人。。。我們不應自滿。如果是這樣的話,爬得高而不長栗子,入水而不受潮,入火而不發熱。對于那些知道自己可以在道中記錄虛假的人來說也是一樣的,“明朝的統治:如果你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你似乎不相信自己,如果你把一切都借給民弗恃。如果你有一個名字,你可以讓事情變得快樂。如果你站在事故中,你可以在沒有事故的情況下游泳。”〔1〕296
的真人“當而不自得”,雖然他行為得體,但他也“不自得”,即他不擁有自己行為的成就。在歷史上“明王之治”,甚至“功蓋天下”也是“不自己”也就是說,它沒有顯示出自己的優點,也沒有占據實際成果,即“游于無有者”。可以看出,他們并不認為他們的行動所取得的成果是他們自己取得的,即“不自得”,而是認為這些成果是自然取得的,即“自得”。顯然,“自得”是正如許建良所說,“自得是根據‘道’自然獲得的,而不是根據自己的主觀意愿,而這種獲得的追求是基于對其他事物價值的實現。”[4]250不難理解,這本《自得》修煉法主要強調生命修煉的自然無為。從人際關系的角度來看,自然無為的《自得》自然可以達到為演員自己培養的目的,也是行為關系中他人最大的收獲,因為他們以自己為榮“充分給予他人自然行為的條件和機會,從而創造條件最佳海盜,實現最大價值”[3]250.易言說,《自得》的栽培方法不僅可以自然提高自己的生活修養,而且不會阻礙甚至有利于他人在其行為關系中實現“生活”的目標。綜上所述,在具體的修煉方法上,一方面,莊子選擇了“心齋”、“最后一頓飯”和“攖寧”等注重內在修煉的運作方式,使人們的精神世界充滿空虛與和諧,從而提高了人們的生命保守性。另一方面,莊子采用《自得》即自然行為法來提升自己的生命,這也為他人在行為關系中提升“生命”提供了條件和機會,最終讓自己和他人充分實現提升“生命”的目標。簡言之,上述兩個方面的四種操作方法是莊子所強調的通往《德之和》所支持的“生命”境界的實現路徑。
[1]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老莊新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235.
夏洛克·
[3]李延倉。莊子哲學思想論綱[M]。濟南:齊魯書社,2012:244。
夏洛克·
[4]許建良·蒂凡尼早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1“養生”是莊子(本研究引文采用郭慶藩版本: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最初的概念可以從“善哉!我聽了庖丁的話,得到了百年的孤獨”中看出(莊子·健康大師[M]//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4:124),“擅長醫療保健的人,如果他們是牧羊人,看看后者而鞭之。”(莊子達生/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645),“皇帝和其他圣人的功績并不是《養生也》的終點”(莊子·讓·王[m)/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971)。事實上,莊子的“養生”被廣泛使用,包括“生活”和“生活”的內容也就是說,只要在《養生》的視野中,有益于“生命”的實踐是以“道”為基礎的,莊子就不會嚴格地將“生命”和“生命”分開。
2(1)許建良認為,莊子所謂的“養中”的“中間”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的“中間”具有相同的含義在《老子》中,“守中”的“中間”指的是中間的空虛,即心的空虛和沉默(見許建良·先秦道家的道德世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243)。
3(2)“命物之化”指的是對萬物變化的服從。參考郭象注:“以變化為生命,不服從。”(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4:190)
4(3)指的是孫以楷和甄長松所說的:從自然哲學的角度來看,“隨物”和“游心”的主體是道,人的“隨物”和“游心”是天道,只是人有意志,天道是自然的,沒有意志。”(孫以楷,甄長松)可汗。莊子的一般理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130)
夏洛克·
5(4)陳鼓應認為“虛而待物”的氣指的是精神狀態。通過修行活動達到空虛和精神覺悟的精神狀態稱為氣(見:陳鼓應。老莊新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234)。
6(5)成玄英解釋道:“大通,猶大道也是。”(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4:285)
7(6)“外天下,外物和外生,從易到難。參考陸長庚和宣穎的解釋。陸長庚:“外面的世界不同于外面的世界。世界遠而事物近。世界稀而事物近。因此,外面的世界容易而事物難。外面的事物容易而事物難。”(崔大華·莊子·歧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2:295)宣穎:“從外部世界看,事情是天生的,越是接近,越是困難。”(宣穎。南華經解[M]。曹礎基,學校點。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53)
8(7)指成玄英書:當你看死生的時候,我忘記了這兩件事和我自己。惠照突然開始像朝陽一樣,所以它被稱為朝車。”(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4:254)
夏洛克·
9(8)杜福舒:夫至道凝然,美妙的文字和圖像,非物質和不存在,古代和現代,獨特和絕對。睹斯的勝利被稱為“看到獨立”。(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4:254)看到道的勝利實際上意味著認識和回歸自己的本性。因此,阮毓崧認為“見獨”等同于“見性”:“獨立沒有權利,也就是說,看到獨立是它的本性。”(崔大華·莊子,歧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2:238)
篇10
【關鍵詞】 ;對比研究;學生
【中圖分類號】 R 161.5 G 47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7)03-0205-02
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指兩性性器官的接觸行為。廣義的指以生育或性滿足為基本目的的一切行為,依據有無性對象可分為:(1)自身,如、夢遺、等;(2)社會,凡是以人為對象的,因牽涉到系列社會倫理問題,故屬于社會的,異性戀、同性戀、群集雜交等行為都在此列[1]。
大學生性機能已經成熟,性意識已經基本健全,與異往增加。這一時期心理特征表現為對性知識的尋求、對異性的向往追求和非理性的性沖動。為了解大學生的現狀,為健康教育提供參考,筆者于2005年10月對浙江省751名大學生進行了調查。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在金華市、杭州市的10所高校中,用抽簽法隨機抽取1個文科班、2個理科班或2個文科班、1個理科班,對抽取的文科班與理科班數量的分配,再采用抽簽法。由于專科院校每個班級人數一般較多,從每所調查的專科院校中,用抽簽法隨機抽取1個文科班和1個理科班。共抽取1 000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回收問卷978份,回收率為97.8%,其中有效問卷751份,有效率為76.8%。問卷有效率較低可能與一部分學生對“性”非常隱晦從而不做答或僅做答一小部分問題有關,在數據分析時研究者剔除了這部分問卷。有效被試中,男生361名,女生390名;文科生340名,理科生411名;城市學生288名,農村學生463名。平均年齡為(19.89±1.37)歲。
1.2 方法 采用自編問卷。該問卷包括7個題目,涉及、性幻想、性夢、接吻、撫、等。在問題后,對幾種進行了界定,定義主要依據《性學辭典》[1]。對所抽取班級的全體學生進行施測,采取現場答卷方式,無記名填寫,統一回收。所有統計分析使用SPSS 10.0軟件,主要采用χ2檢驗。2 結果
2.1 不同性別大學生發生情況 被試學生行為報告率為53.9%,性夢為77.0%,性幻想為74.3%,接吻為45.5%,撫為27.4%,為16.6%;初次年齡為(18.48±2.71)歲。3.0%的學生曾與同性發生過接吻行為,男生為4.7%,女生為1.5%。同性撫的發生率為2.3%,男生為3.6%,女生為1.0%。同性發生率為1.9%,男生為3.3%,女生為0.5%。見表1。
2.2 不同學科大學生發生情況 由表2可見,文科生和理科生、性夢和性幻想發生率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1),理科生高于文科生;理科生在接吻、撫、方面也高于文科生,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
2.3 不同生源地大學生發生情況 由表3可見,城市學生、性幻想、接吻、撫和發生率高于農村學生,農村學生在性夢上略高于城市學生,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
3 討論
調查顯示,在本次調查的幾項上,男生的發生率均高于女生,可能與男生的性開放意識強于女生[2-3]有關;男生性知識水平高于女生[4],可能與女生更多地把、性夢、性幻想等視作不健康或不應該有的行為有關。理科生、性夢、性幻想發生率顯著高于文科生,可能與理科生中男生較多且平時課業負擔比文科生重有關。在高校中,文科生一般比理科生更活躍地組織、參與豐富多彩的社團和社會實踐活動,更可能通過這些活動得到轉移、釋放。
調查還顯示,部分大學生曾有過同性。有研究指出,許多人在早年會參與同性戀游戲,在青春期之后則停止這種游戲[5],但并不意味他們都是同性戀患者。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有同性戀傾向,那么其應該在社會認可的范圍內。所以,幫助同性戀者平衡性渴望與社會環境的壓力,對他們進行積極的引導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