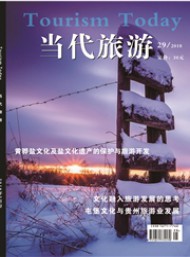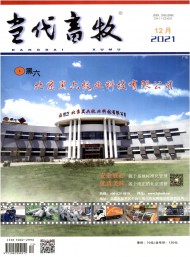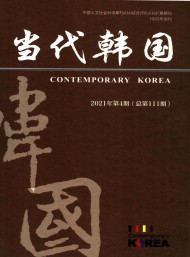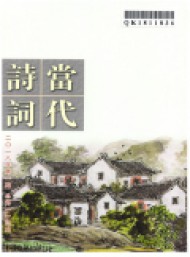當(dāng)代文學(xué)范文10篇
時(shí)間:2024-01-16 06:28:57
導(dǎo)語(yǔ):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yàn),為你推薦的十篇當(dāng)代文學(xué)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審視當(dāng)代文學(xué)策略
陳曉明先生在《有一點(diǎn)中國(guó)立場(chǎng)如何?》[1](以下所引陳曉明說法皆出自此文,不另注明)一文中以及在接受媒體訪問[2]時(shí),提出了評(píng)價(jià)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應(yīng)該有中國(guó)自己的立場(chǎng)的主張。此說針對(duì)國(guó)內(nèi)外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有太多的貶損和否定性評(píng)價(jià)而發(fā)。德國(guó)漢學(xué)家顧彬的部分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是垃圾的說法,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加上其異邦學(xué)者身份,成了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最富代表性的批判。若干年前,有人已為20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寫了“一份悼詞”[3],送進(jìn)了墳?zāi)梗F(xiàn)在,當(dāng)代文學(xué)除了少數(shù)之外,大部分又要被扔進(jìn)“垃圾場(chǎng)”了。筆者并不試圖為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號(hào)脈,只是分析一下陳曉明可疑的“中國(guó)立場(chǎng)”說,談一下為什么這種說法似是而非,為什么以“文學(xué)立場(chǎng)”取代之會(huì)更好。
陳曉明的“中國(guó)立場(chǎng)”說,是對(duì)其“前所未有的高度”說[4]的學(xué)理性補(bǔ)充,是為這一論斷尋找到了更高的正當(dāng)性依據(jù)。陳曉明先生的論說邏輯可以這樣概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是中國(guó)獨(dú)特的現(xiàn)代性進(jìn)程中的一部分,加之漢語(yǔ)寫作“總有超出西方的文學(xué)價(jià)值尺度的例外”,是“永遠(yuǎn)無(wú)法為西方文學(xué)規(guī)訓(xùn)”的,也就是說,中國(guó)當(dāng)代的歷史和文學(xué)都異于西方,而以西方的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yàn)和西方的文學(xué)價(jià)值尺度來評(píng)判之,則“中國(guó)的文學(xué)永遠(yuǎn)只是二流貨色”,所以,我們應(yīng)有自己的價(jià)值準(zhǔn)則,中國(guó)臣服于西方的“規(guī)訓(xùn)和尺度”夠久了,是到了要有中國(guó)立場(chǎng)的時(shí)候了,要“對(duì)由漢語(yǔ)這種極富有民族特性的語(yǔ)言寫就的文學(xué),它的歷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國(guó)的闡釋。這與其說是高調(diào)捍衛(wèi)中國(guó)立場(chǎng),不如說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異性的維度上,給出不同于西方現(xiàn)代普遍美學(xué)的中國(guó)美學(xué)的異質(zhì)性價(jià)值”。如果再加以概括就是這樣一個(gè)三段論述:中國(guó)歷史和文學(xué)具有獨(dú)特性———西方文學(xué)標(biāo)準(zhǔn)和價(jià)值尺度不適用(如用,就會(huì)造成過低和不合理的評(píng)價(jià))———應(yīng)有中國(guó)自己的價(jià)值立場(chǎng)和美學(xué)尺度(有了自己的尺度就會(huì)對(duì)中國(guó)歷史和文學(xué)做出合理解釋,就會(huì)發(fā)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達(dá)到了60年來“前所未有的高度”)。細(xì)究起來,這看似很有邏輯的論說實(shí)際上存在諸多學(xué)理上的疑點(diǎn)。中國(guó)歷史和文學(xué)具有獨(dú)特性,這毫無(wú)疑問。但中國(guó)近現(xiàn)代歷史也是整個(gè)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國(guó)的民族獨(dú)立、反法西斯戰(zhàn)爭(zhēng)以及社會(huì)主義的實(shí)踐和現(xiàn)代化道路,無(wú)不處在世界歷史的總體格局中,社會(huì)前行和變革的思想資源也主要來自西方,從“德先生”、“賽先生”到“馬克思主義”都是如此。身處其中的中國(guó)文學(xué)也的確有其獨(dú)特性,最顯著的就是,中國(guó)文學(xué)有更多族群承續(xù)、家國(guó)存亡的宏大關(guān)懷與焦慮,承擔(dān)起了更多“救亡”的責(zé)任和塑造新的社會(huì)和國(guó)家意識(shí)形態(tài)的功能,它一度成為宣傳抗戰(zhàn)的工具,服務(wù)于革命及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甚至成了階級(jí)斗爭(zhēng)的工具。但中國(guó)文學(xué)在艱難的歷史進(jìn)程中也還有更多、更高的企望,尤其是從“五四”舉步啟程的新的白話文學(xué),在眾多優(yōu)秀的世界文學(xué)那里尋找到了范例和標(biāo)準(zhǔn)。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的那種自足和封閉狀態(tài)隨著中國(guó)歷史“被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開啟,也永遠(yuǎn)不可逆轉(zhuǎn)地被打破了。強(qiáng)調(diào)中國(guó)歷史和文學(xué)的獨(dú)特性,不能抹煞了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世界視角和文學(xué)尺度。
對(duì)于中國(guó)文學(xué)與政治及國(guó)家意識(shí)形態(tài)的過多糾結(jié),尤其是“社會(huì)主義主流革命文學(xué)”、“走向共產(chǎn)革命的文學(xué)”,陳曉明認(rèn)為中國(guó)現(xiàn)有的文學(xué)史寫作觀念無(wú)法闡釋其“合理性和正當(dāng)性”,對(duì)這些文學(xué),無(wú)論是“左”的贊頌還是“右”的貶抑(在夏志清和顧彬那里成了“中國(guó)作家受政治壓迫的歷史的佐證”),都不適切,應(yīng)有一種更中性化的“中國(guó)的闡釋方式”。陳曉明沒有具體說,這是一種什么方式。但他是預(yù)定了其“合理性和正當(dāng)性”的,是傾向于要有“對(duì)自身歷史的認(rèn)識(shí)”,而且是“肯定性的認(rèn)識(shí)”的。不贊美,不貶損,但肯定。陳曉明也許是想走一種相對(duì)客觀化的道路吧,對(duì)歷史先要同情地理解,而不是急于進(jìn)行價(jià)值上的評(píng)判。他所說的“合理性和正當(dāng)性”僅是指這種歷史的“合理性和正當(dāng)性”吧,抗戰(zhàn)爆發(fā)了,民族面臨生死與存亡,文學(xué)還是一派“后庭花”肯定是不行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才具有喚起民眾救亡的力量,才更具歷史的“合理性與正當(dāng)性”。陳曉明在這里過分地強(qiáng)調(diào)這種獨(dú)特情形下歷史的“合理性與正當(dāng)性”,而忽略了正常歷史條件下的普遍的常態(tài)的文學(xué)標(biāo)準(zhǔn)。我們肯定《放下你的鞭子》的歷史功績(jī)和作用,這并不妨礙我們也用相對(duì)純文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來看待它。文學(xué)史的“實(shí)然”(實(shí)際如何)并不總是符合文學(xué)的“應(yīng)然”(應(yīng)當(dāng)如何)。簡(jiǎn)單說,歷史合理性并不等于文學(xué)合理性。就前者而言,黑格爾式的命題是對(duì)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現(xiàn)實(shí)的就是合理的,一個(gè)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總有它的成因和理由。但從后者看,則“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比如說,文學(xué)從其根本性價(jià)值來說,不應(yīng)被主要當(dāng)成是一種政治宣傳的工具,這是文學(xué)的應(yīng)然,但歷史的實(shí)然是文學(xué)有時(shí)就被當(dāng)成了這樣的工具。以歷史的實(shí)然的合理性拒絕普遍的應(yīng)然,顯然是一種價(jià)值判斷的缺失。夸大中國(guó)現(xiàn)代性歷史進(jìn)程和文學(xué)的獨(dú)特性還不要緊,如果認(rèn)為獨(dú)特性本身就可以拒絕應(yīng)然的普遍正當(dāng)性的裁決,則有害而無(wú)益了。政治對(duì)文學(xué)過多地介入,文學(xué)過多地依賴和受制于外在規(guī)律,而不是其內(nèi)在規(guī)律,那么,不管如何具有歷史的正當(dāng)性,都不是文學(xué)的應(yīng)然狀態(tài)和理想狀態(tài),更不能作為我們給予其正面價(jià)值肯定的依據(jù)。浩然就曾以歷史的正當(dāng)性來為自己文學(xué)的正當(dāng)性辯護(hù),尤其是他的《金光大道》,簡(jiǎn)言之,他認(rèn)為自己的作品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產(chǎn)物,“真實(shí)”反映了那個(gè)時(shí)代,所以他有價(jià)值。[5]是啊,有歷史價(jià)值和文獻(xiàn)價(jià)值(不管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但有文學(xué)價(jià)值嗎?
陳曉明先生還一再?gòu)?qiáng)調(diào)漢語(yǔ)及漢語(yǔ)寫作的“獨(dú)異性”,存在著同樣的對(duì)普遍性文學(xué)標(biāo)準(zhǔn)的拒絕與盲視。漢語(yǔ)及漢語(yǔ)文學(xué)的確具有其語(yǔ)言上的特殊性,但這種獨(dú)異性是否發(fā)展到了可以棄普世的文學(xué)價(jià)值尺度于不顧的程度了呢?按陳曉明先生的邏輯,你不能拿西方文學(xué)標(biāo)準(zhǔn)來看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也不能拿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來看當(dāng)代白話文學(xué),于是乎只能以當(dāng)代文學(xué)為參照來看當(dāng)代文學(xué),因?yàn)樗仟?dú)異的現(xiàn)代白話文,它自己就是標(biāo)準(zhǔn)。也難怪,他要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代文學(xué)達(dá)到了60年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不又成了“夜郎自大”了嗎?陳曉明先生說:“我們?yōu)槭裁粗挥羞@一種尺度(指的是西方文學(xué)尺度)呢?是否有可能,有意外,漢語(yǔ)言文學(xué)的尺度會(huì)有一點(diǎn)例外呢??jī)H就這一點(diǎn)例外,它永遠(yuǎn)無(wú)法為西方文學(xué)規(guī)訓(xùn)呢?”漢語(yǔ)肯定有其獨(dú)特性,誰(shuí)也不會(huì)拿十四行詩(shī)的標(biāo)準(zhǔn)來要求中國(guó)的格律詩(shī),但它們追求的語(yǔ)言的美、詩(shī)意的美、情感的美是一樣的啊。中國(guó)古琴樂曲很美,沒有誰(shuí)會(huì)因?yàn)槲鞣降匿撉俣穸ü徘伲餮髽菲鳌耙?guī)訓(xùn)”不了中國(guó)樂器,但講求節(jié)奏、曲調(diào)等樂理是相通的吧,追求音樂的美是一樣的啊。漢語(yǔ)寫作是獨(dú)特的,但漢語(yǔ)就沒有美丑之別嗎?講求語(yǔ)言精美是中國(guó)的呢,還是西方的呢?怎么是一個(gè)規(guī)訓(xùn)另一個(gè)呢?讀讀當(dāng)代文學(xué)中某些粗糙的似糞土一樣的語(yǔ)言吧,讓人懷疑這是生活于屈原、李白的國(guó)度的人寫出來的。這就是中國(guó)文學(xué)的尺度?這就是不受西方文學(xué)規(guī)訓(xùn)?說“漢語(yǔ)文學(xué)”與其他的非漢語(yǔ)文學(xué)有差異是對(duì)的,但這種差異不能強(qiáng)調(diào)到不恰當(dāng)?shù)牡夭剑吘故澜绺鲊?guó)文學(xué)的相通性要遠(yuǎn)大于這種阻隔性。不能以“漢語(yǔ)”的獨(dú)特性消泯文學(xué)的相通性,文學(xué)的相通基于人性的相通、情感的相通、真善美等價(jià)值的相通、人類歷史命運(yùn)的相通。惠子的“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陷在了邏輯主義的深淵中不能自拔了。如果說,所謂的“中國(guó)立場(chǎng)”只是為了抵擋和拒絕到目前為止人類文學(xué)所達(dá)到的高度和標(biāo)準(zhǔn),只是以貌似中性的態(tài)度,以尊重差異為口實(shí),實(shí)現(xiàn)精神上的自足和自慰,那么,這顯然不過是作繭自縛,是自我麻醉和精神封閉,顯現(xiàn)出的是深層潛藏的無(wú)數(shù)心虛和怯懦,如同走夜路,大喊幾聲以壯膽一樣。
陳曉明先生讓我們牢牢記住中國(guó)的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并且認(rèn)為“依憑西方的文學(xué)價(jià)值尺度,中國(guó)的文學(xué)永遠(yuǎn)只是二流貨色”,他這里說的“中國(guó)的文學(xué)”,僅指當(dāng)代文學(xué)而言。為什么永遠(yuǎn)是二流貨色?夏志清如果是按西方標(biāo)準(zhǔn),也沒有把所有現(xiàn)代文學(xué)都看做是二流貨色,顧彬也很肯定中國(guó)當(dāng)代的詩(shī)歌。而且“,西方的文學(xué)價(jià)值尺度”是個(gè)包含了太多差異的集合名詞,如果是指所有出自西方的理論觀點(diǎn)與批評(píng)方法,那么,用這些西方的觀點(diǎn)和方法來評(píng)價(jià)中國(guó)文學(xué),并不總是發(fā)現(xiàn)它們是所謂的“二流貨色”,反而更加發(fā)現(xiàn)了它們的獨(dú)特價(jià)值。王國(guó)維評(píng)《紅樓夢(mèng)》用的是叔本華的悲劇理論,得出的結(jié)論是《紅樓夢(mèng)》是“悲劇中的悲劇”,放在世界各大悲劇中亦無(wú)愧色。國(guó)外漢學(xué)家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研究,多為肯定性的研究,并沒有研究一番,得出“不過二流貨色”的結(jié)論了事。中國(guó)文學(xué)的許多特性和價(jià)值倒是在西方視野之下才越發(fā)清晰起來的。為什么偏偏當(dāng)代文學(xué)一放在“西方的文學(xué)價(jià)值尺度”下,就成了“二流貨色”呢?無(wú)非有這樣幾種可能:一,當(dāng)代文學(xué)本來一流,被忽視或扭曲成了二流的,甚或不入流的;二,當(dāng)代文學(xué)本來就是二流的,所以放在中國(guó)古典的視野下,或西方理論的視野下,就不可能是一流的;三,當(dāng)代文學(xué)本無(wú)所謂一流或二流,它豐富復(fù)雜,現(xiàn)有一切標(biāo)準(zhǔn)都難以對(duì)其進(jìn)行衡量和評(píng)價(jià),文學(xué)的妙與不妙,是不可言傳的,只能意會(huì)心知,批評(píng)就是妄言,如果非要評(píng)價(jià),也要拉開極大的時(shí)空距離而后可,當(dāng)代無(wú)法評(píng)價(jià)當(dāng)代,所以,放在任何尺度下都是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的侮辱和歪曲。
一些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者或們就持這種看法,他們仇視和排斥文學(xué)批評(píng),認(rèn)為文學(xué)批評(píng)與真正的文學(xué)無(wú)關(guān)。肖鷹、張檸、孫郁等人顯然持第二種看法。而第一種看法顯然符合陳曉明先生的邏輯,這種看法包含著一個(gè)更深層的問題:“西方的文學(xué)價(jià)值尺度”到底有沒有普世性?西方的思想體系,有一些確實(shí)帶有西方中心論的偏見,對(duì)異己的文化和價(jià)值選擇充滿了蔑視。我們知道黑格爾等人就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有很多不公正的否定,一些國(guó)家至今并不承認(rèn)中醫(yī)是科學(xué)等。但西方思想中的普世性內(nèi)容的確又是豐富和廣大的,要不然,“五四”一代乃至中國(guó)的現(xiàn)代性實(shí)踐,就不會(huì)如此熱烈地去擁抱那些誕生于西方的價(jià)值、精神和主義。在文學(xué)方面同樣如此,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受國(guó)外文學(xué)的影響是巨大的,歐洲文學(xué)、俄蘇文學(xué)、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xué)都在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中留下了清晰的烙印,這也說明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至少是部分地在向異域的文學(xué)張望和看齊。如果沒有對(duì)其價(jià)值普遍性的認(rèn)同,就不會(huì)有這樣主動(dòng)的創(chuàng)作上的借鑒和模仿。作家們,如果不是全部,也有很多,已接納了西方文學(xué)的滋養(yǎng),這就說明“漢語(yǔ)寫作”的獨(dú)異性是有限度的,其體現(xiàn)出來的文學(xué)普遍性反而是無(wú)限的。“西方的文學(xué)價(jià)值尺度”并不只適用于西方文學(xué),同樣也適用于作為普遍文學(xué)和世界文學(xué)一部分的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因?yàn)椤拔鞣降奈膶W(xué)價(jià)值尺度”必然包含著對(duì)人類文學(xué)高度及人類文學(xué)所能達(dá)到的高度的理解,這種理解是普世性的。筆者并不贊同所有的“西方文學(xué)的價(jià)值尺度”就是好的,任何一種尺度可能都有其相對(duì)性,但這種相對(duì)性不能成為我們拒絕其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理由。
當(dāng)代文學(xué)探討論文
內(nèi)容提要本文認(rèn)為,當(dāng)代文學(xu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名實(shí)相分,概念所指不一。當(dāng)代文學(xué)有時(shí)間和意義兩個(gè)維度,人們僅僅在時(shí)間維度上認(rèn)同和使用這個(gè)概念,而在意義維度上則各有其所指,各說各的。“當(dāng)代文學(xué)”因原有性質(zhì)被“新時(shí)期文學(xué)”脹破而發(fā)生意義破裂,給修史者造成難以擺脫的困境,已經(jīng)是一個(gè)不合時(shí)宜的概念。本文具案分析這個(gè)概念意義破裂的狀況,認(rèn)為這是在社會(huì)文化急劇轉(zhuǎn)型的過程中必然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
關(guān)鍵詞當(dāng)代文學(xué)文學(xué)史概念意義破裂
洪子誠(chéng)曾經(jīng)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這個(gè)概念進(jìn)行過有點(diǎn)類似于“譜系分析”方法的扼要辨析。他“所要討論的,主要不是被我們稱為‘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性質(zhì)或特征的問題,而是想看看‘當(dāng)代文學(xué)’是如何被‘構(gòu)造’出來和如何被描述的”①。他注意到當(dāng)代文學(xué)與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共生性,發(fā)現(xiàn)這兩個(gè)概念都不是客觀的,而是“人為”的產(chǎn)物,認(rèn)為當(dāng)代文學(xué)是在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合歷史、合邏輯地延伸中生成,并在社會(huì)主義的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被描述定型,在“”結(jié)束以后社會(huì)的變遷和文學(xué)標(biāo)準(zhǔn)的變化中發(fā)生“概念的分裂”的。洪子誠(chéng)所關(guān)注的是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構(gòu)造過程即其生成、衍化的史跡,自然無(wú)法顧及或者根本就不在意“必也正名乎”的概念清理,以及當(dāng)代文學(xué)這個(gè)概念是否還有足夠的理由存在下去的問題,因而給我們留下了再辨析的空間。
我覺得,當(dāng)代文學(xué)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名實(shí)相分、概念所指不一。因?yàn)槊麑?shí)相分,所以用起來相當(dāng)混亂;因?yàn)楦拍钏覆灰唬杂幸粋€(gè)“誰(shuí)的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問題。
一
一個(gè)不可否認(rèn)的事實(shí)是:至遲從上世紀(jì)80年代中期“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命題提出開始,學(xué)術(shù)界就不再存在一個(gè)人皆認(rèn)可的當(dāng)代文學(xué)。
當(dāng)代文學(xué)言語(yǔ)粗狂敘事
人是言說的動(dòng)物,也是社會(huì)生活文化圈的理性動(dòng)物。語(yǔ)言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可以說主宰了整個(gè)人類社會(huì)漫長(zhǎng)的文明發(fā)展史。古往今來有多少哲人和思想家對(duì)語(yǔ)言和人的關(guān)系問題進(jìn)行了長(zhǎng)篇累牘的探討。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人們對(duì)于語(yǔ)言的認(rèn)識(shí)都有一些驚人的相似性。人們已經(jīng)意識(shí)到語(yǔ)言是人認(rèn)識(shí)、掌握、理解這個(gè)世界的一個(gè)有效的武器。正是有了語(yǔ)言,人類把自我與動(dòng)物區(qū)別開來,能夠運(yùn)用語(yǔ)言將實(shí)踐中習(xí)得的經(jīng)驗(yàn)代代相傳下去。英國(guó)語(yǔ)言學(xué)家羅杰•富勒在《語(yǔ)言學(xué)與小說》中還寫到:“語(yǔ)言是社會(huì)共同體的特性,共同體的價(jià)值和思想模式都隱寓在語(yǔ)言之中。”①可以想見,語(yǔ)言不單純只是人言說的工具,它更是承載著一個(gè)時(shí)代、一個(gè)社會(huì)、一個(gè)民族的思想價(jià)值觀念、文化知識(shí)、情感心理。語(yǔ)言的功效如此之大,這就如同一個(gè)硬幣的兩面,既有正面的效應(yīng),也有負(fù)面的結(jié)果。
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歷史,其實(shí)也是重新認(rèn)識(shí)語(yǔ)言與人的關(guān)系,認(rèn)識(shí)語(yǔ)言的正反兩面效應(yīng)問題的歷史。在這一問題上,也使得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具有了鮮明的現(xiàn)代性的質(zhì)素,并從整體上與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之間有了很大的區(qū)別。從清末民初梁?jiǎn)⒊母牧贾髁x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開始,途徑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延安解放區(qū)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新中國(guó)成立以后的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中國(guó)歷次的這些大的文學(xué)變革運(yùn)動(dòng),無(wú)一次不是與語(yǔ)言的改造、文字的改造息息相關(guān)。但是,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作家在思考語(yǔ)言與人的關(guān)系問題時(shí),往往還是停留在工具性、政治性、思想性的層面上。這與中國(guó)特定時(shí)代的思想主題即“啟蒙與救亡”兩個(gè)主題有關(guān)。五四一代的作家,以魯迅為代表,他們?cè)谛≌f中反映語(yǔ)言的暴力特征,向人們展現(xiàn)過日常的生活語(yǔ)言由于集結(jié)了大量的陳腐的封建思想意識(shí),是如何以無(wú)意識(shí)的殺人團(tuán)對(duì)無(wú)辜的群眾進(jìn)行精神的殺戮。這種精英主義的啟蒙立場(chǎng),是把語(yǔ)言作為一種可以改善人心、改變中國(guó)國(guó)民性的工具,希圖能夠在黑暗無(wú)望的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有所獲救。這一種精英主義啟蒙立場(chǎng),一直延續(xù)到了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的筆下。例如余華作為深受魯迅思想影響的作家,他在短篇小說《我沒有自己的名字》中寫到了一個(gè)不知道自己姓名的傻子,任由鎮(zhèn)上的人們欺壓和凌辱。這個(gè)人物讓人想到了魯迅筆下的阿Q。作者寫這樣的一個(gè)傻子,其實(shí)是要指出語(yǔ)言的無(wú)名化對(duì)于人的精神戕害。無(wú)獨(dú)有偶,在韓少功的《馬橋詞典》里,也同樣探討了有關(guān)人的命名權(quán)問題。三十年代后,一系列精神家族相似的革命政治話語(yǔ)把中國(guó)的語(yǔ)言帶向了另一種暴力敘事的路徑。這種話語(yǔ)的暴力敘事路徑,就是用階級(jí)的劃分來涵蓋人性的劃分,用階級(jí)的矛盾斗爭(zhēng)來總結(jié)中國(guó)的歷史發(fā)展本質(zhì)和規(guī)律,用群體的宏大敘事來泯滅個(gè)體的小我敘事。也正是這種話語(yǔ)暴力敘事特征,為整個(gè)當(dāng)代文學(xué)劃下了一道難以磨滅的精神創(chuàng)痕。在莫言的《豐乳肥臀》這部小說中,有一段描寫可以說是中國(guó)革命政治話語(yǔ)對(duì)中國(guó)國(guó)民內(nèi)心深處無(wú)意識(shí)情結(jié)進(jìn)行控制和戕害的最好注解文本。小說寫到上官金童身處中國(guó)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后,因?yàn)楹推拮油翥y枝的關(guān)系日漸惡化,他把幾十年動(dòng)蕩不安的生活中學(xué)到的罵人的政治術(shù)語(yǔ)說出來,罵他的妻子汪銀枝:“汪銀枝,你這個(gè)反革命,人民的敵人,吸血鬼,害人蟲,四不清分子,極右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dāng)權(quán)派,資產(chǎn)階級(jí)反動(dòng)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腐化變質(zhì)分子,階級(jí)異己分子,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蟲、被綁在歷史恥辱柱上的跳梁小丑,土匪,漢奸,流氓,無(wú)賴,暗藏的階級(jí)敵人,保皇派,孔老二的孝子賢孫,封建主義的衛(wèi)道士,奴隸主義制度的復(fù)辟狂,沒落的地主階級(jí)的代言人……”。②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其實(shí)是飽受歷史創(chuàng)傷和語(yǔ)言侵害的一代人。僅從莫言小說人物的這段語(yǔ)言中,就可以看到那些以階級(jí)成分劃分人類社會(huì)、以階級(jí)斗爭(zhēng)為綱領(lǐng)的政治術(shù)語(yǔ)是如何進(jìn)入了中國(guó)國(guó)民的集體無(wú)意識(shí)心理層面,并如何影響了他們對(duì)于語(yǔ)言的認(rèn)知能力和對(duì)于世界的理解能力。
八十年代中后期,昆德拉的兩本小說在中國(guó)大行其道,一本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一本是《玩笑》。《玩笑》這本小說帶給中國(guó)知識(shí)文化界的震撼是相當(dāng)大的,因?yàn)樾≌f中所展現(xiàn)的因言獲罪的故事,在當(dāng)代中國(guó)特定的極左歷史階段可以說是一個(gè)司空見慣的社會(huì)現(xiàn)象。每一個(gè)人都會(huì)因?yàn)檠哉Z(yǔ)的不慎,或者言語(yǔ)染上的政治色彩,而遭到無(wú)妄之災(zāi)。這種話語(yǔ)暴力在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的敘事中是處處可見的。正如劉小楓所言:“話語(yǔ)對(duì)人的行為和社會(huì)的確具有一種無(wú)法否認(rèn)的統(tǒng)治力量,眾多社會(huì)悲劇不過是靠幾個(gè)語(yǔ)詞來導(dǎo)演的。重審人的話語(yǔ)性質(zhì),尤其是知識(shí)者的話語(yǔ)性質(zhì),成為知識(shí)學(xué)本身的一項(xiàng)課題。”③話語(yǔ)既然具有如此可怕的魔力,那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在重審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近現(xiàn)代歷史時(shí),究竟是從哪幾個(gè)方面來思考言語(yǔ)的暴力特征呢?在他們的筆下,這些言語(yǔ)暴力敘事又呈現(xiàn)出怎樣的不同的形態(tài)呢?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言語(yǔ)暴力敘事,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gè)方面:第一,共名詞語(yǔ)的話語(yǔ)暴力。劉小楓指出:“漢語(yǔ)思想應(yīng)警惕“大眾”或“人民”之類的總體概念,小心“人民利益”的話語(yǔ)對(duì)個(gè)人權(quán)利的無(wú)化。“人民”是不在的,只有每一個(gè)個(gè)人在。“人民的意愿”經(jīng)常身著中山服,而自由從不穿國(guó)服。”
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確定了從個(gè)體走向集體的革命政治路線,也加強(qiáng)了對(duì)中國(guó)小資產(chǎn)階級(jí)知識(shí)分子的思想改造。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提倡的個(gè)性解放、獨(dú)立自由的精神,被宏大崇高的民族國(guó)家敘事所掩蓋,被至高無(wú)上的“人民利益”所遮蔽。在中國(guó)歷次的政治文化運(yùn)動(dòng)之中,有多少的冤假錯(cuò)案都是假借“人民”這一共名詞語(yǔ),假借組織的力量來執(zhí)行的。這種共名詞語(yǔ)的話語(yǔ)暴力,至今都讓中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心有余悸。王小波的《黃金時(shí)代》、韓少功的《馬橋詞典》中都寫到了這種共名詞語(yǔ)的話語(yǔ)暴力帶給生命個(gè)體的精神傷害。第二,階級(jí)性大于人性的話語(yǔ)暴力。語(yǔ)言一旦與政治之間結(jié)下了依附關(guān)系,失去了它本身的獨(dú)立性和純粹性以后,就好像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以后就具有難以控制的精神魔力,能夠剔除環(huán)繞在一個(gè)人身上所有的個(gè)性色彩,只剩下冷冰冰的、枯燥無(wú)味的階級(jí)和政治定性。這種用階級(jí)性來消解人性,泯滅個(gè)性的話語(yǔ)暴力方式,在余華、莫言、蘇童、韓少功的筆下也多有涉及。以莫言的《豐乳肥臀》為例,瞎子徐仙兒因?yàn)橥春拮约旱睦掀藕退抉R庫(kù)私通,于是在農(nóng)民訴苦大會(huì)上歪曲事實(shí)控訴司馬庫(kù),并且要求政府把司馬庫(kù)的兒子和女兒也槍斃掉。作為解放區(qū)代表的魯立人最終同意了瞎子的無(wú)理要求。魯立人對(duì)自己的這一行為決定進(jìn)行了一番話語(yǔ)解釋,他的話語(yǔ)邏輯是:“我們槍斃的看起來是兩個(gè)孩子,其實(shí)不是孩子,我們槍斃的是一種反動(dòng)落后的社會(huì)制度,槍斃的是兩個(gè)符號(hào)!老少爺們,起來吧,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沒有中間道路可走!”在魯立人的話語(yǔ)體系中,階級(jí)性是遠(yuǎn)遠(yuǎn)大于人性的。孩子的生命與政治身份緊密相關(guān),而與它所應(yīng)該獲得的、本該獲得的生命權(quán)利沒有絲毫聯(lián)系。這不能不說是中國(guó)革命歷史敘述中對(duì)于極權(quán)和左傾路線的一個(gè)深刻的反思。第三,表述與命名權(quán)的話語(yǔ)暴力。在韓少功的《馬橋詞典》里,有一個(gè)詞條是“話份”。韓少功對(duì)話份的解釋,實(shí)際上就揭示了漫長(zhǎng)的人類歷史文化發(fā)展過程之中語(yǔ)言與政治、與權(quán)力、與個(gè)體存在之間的關(guān)系。語(yǔ)言實(shí)際上并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思想交流的工具,它具有一種強(qiáng)大的權(quán)力效用,誰(shuí)掌握了語(yǔ)言,控制了語(yǔ)言的表達(dá),掌握了命名的權(quán)利,誰(shuí)就是政治的掌權(quán)者,誰(shuí)就是歷史的主人。這種“話份”的背后,其實(shí)表現(xiàn)的是一種政治的專制主義和思想的權(quán)威主義。它強(qiáng)迫生存和呼吸在語(yǔ)言之圈的人們,服從這種“話份”的等級(jí)制度,遵守著“話份”所圈定的人的生存位置,同時(shí)也強(qiáng)烈地排斥一切與“話份”之外的語(yǔ)言表達(dá)。第四,人言當(dāng)成圣言的語(yǔ)言暴力。這一語(yǔ)言暴力與中國(guó)幾千年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有著根深蒂固的聯(lián)系。中國(guó)的封建社會(huì)體系之所以能夠延續(xù)幾千年的時(shí)間,這其中也取決于封建大一統(tǒng)的思想體系對(duì)于中國(guó)民眾的控制和戕害。正如劉小楓所指出的:“關(guān)于“天人合一”論和“人人可以成圣”論的義理困難以及其蘊(yùn)含著的據(jù)人性之自信和危險(xiǎn)的人本中心主義,……“中國(guó)”人的體知功夫固然宏富深厚,但把人言當(dāng)天言不正是無(wú)數(shù)謬誤和災(zāi)難之源嗎?”⑤韓少功在《馬橋詞典》中就不無(wú)沉重地寫到:“如果說語(yǔ)言曾經(jīng)是推動(dòng)文化演進(jìn)以及積累的工具,那么正是神圣的光環(huán)使語(yǔ)言失重和蛻變,成為對(duì)人的傷害。”⑥韓少功指出語(yǔ)言一旦進(jìn)入不可冒犯的神位以后,就會(huì)失去各自與事實(shí)原有的聯(lián)系,而成為了戰(zhàn)爭(zhēng)主導(dǎo)者們權(quán)勢(shì)、榮耀、財(cái)產(chǎn)、王國(guó)版圖的無(wú)謂包裝,也就是引發(fā)從爭(zhēng)辯直至戰(zhàn)爭(zhēng)的人際沖突,造成各種各樣的語(yǔ)言的血案。
從以上的歸納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在理性層面上對(duì)語(yǔ)言暴力問題有著清醒的認(rèn)知,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面對(duì)語(yǔ)言,往往呈現(xiàn)出了一種復(fù)雜矛盾的情感狀態(tài)。一方面,他們?cè)噲D沖破語(yǔ)言帶給他們的歷史記憶創(chuàng)痛,在作品中書寫語(yǔ)言暴力帶給人的命運(yùn)悲劇,以此反思中國(guó)的具體歷史情境。另一方面,他們?cè)谧约旱膭?chuàng)作中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深受語(yǔ)言暴力記憶影響的痕跡,這使得他們?cè)谧髌分兴\(yùn)用的敘述者的語(yǔ)言對(duì)于閱讀者來說也產(chǎn)生一種難以抗拒的精神暴力。他們?cè)诰唧w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往往會(huì)不自覺地受到這種語(yǔ)言暴力記憶的牽制,在他們的具體語(yǔ)言表達(dá)中成為這種語(yǔ)言暴力的復(fù)制者和摹寫者。這也是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語(yǔ)言暴力的一個(gè)比較突出的現(xiàn)象。與魯迅、茅盾等現(xiàn)代作家相比較,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一直都缺乏一種大的精神氣象,他們是在坍塌的精神世界體系下重建自我的一代人。要想在這個(gè)坍塌的精神廢墟中重新創(chuàng)建自由的精神王國(guó),這是一件相當(dāng)艱巨而又漫長(zhǎng)的工程。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無(wú)法忘記歷史帶給他們的噩夢(mèng),也無(wú)法逃離先于他們而存在的語(yǔ)言之場(chǎng)。他們只能暫時(shí)棲息于這個(gè)命定的文化語(yǔ)言圈之中,做著暫時(shí)逃離和掙扎的夢(mèng)境。也正是這個(gè)先天的文化缺陷,使得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在使用語(yǔ)言、調(diào)遣語(yǔ)言上經(jīng)常為人所詬病。近年來在中國(guó)知識(shí)文化界引起了廣泛熱議的“顧彬談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事件,就一再地暴露了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中作家的語(yǔ)言使用問題。王彬彬在《漫談?lì)櫛颉芬晃闹芯鸵会樢娧刂赋觯櫛蛑砸l(fā)驚人之語(yǔ),說“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是垃圾”,其批判的靶子和重心就在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語(yǔ)言的貧乏和干枯。王彬彬還進(jìn)一步地指出:“‘’時(shí)期,是漢語(yǔ)遭破壞最嚴(yán)重的時(shí)期。在漢語(yǔ)發(fā)展史上,‘語(yǔ)言’絕對(duì)是一個(gè)飽含毒液的怪胎。幾代中國(guó)人其實(shí)一開始就是通過這種有毒的語(yǔ)言思考人生、認(rèn)識(shí)世界的。更糟糕的是,‘’式話語(yǔ)方式,并未在我們的生活中絕跡。在我們的政治生活、經(jīng)濟(jì)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式話語(yǔ)方式,還時(shí)時(shí)可見。”⑦楊小濱也指出,研究20世紀(jì)80年代中后期出現(xiàn)的“先鋒小說”不能忽略的話語(yǔ)體系,“因?yàn)檎窃捳Z(yǔ)暴力對(duì)心靈的震撼最強(qiáng)烈的時(shí)期。……話語(yǔ)于是留下了精神創(chuàng)傷的記憶痕跡,但不是一般的記憶,因?yàn)樗冀K保持在無(wú)意識(shí)中。”⑧所謂“式話語(yǔ)方式”,應(yīng)該從這種話語(yǔ)的內(nèi)容和表達(dá)形式兩方面來談。從內(nèi)容上來看,這種話語(yǔ)與時(shí)期以階級(jí)斗爭(zhēng)為綱的武裝革命斗爭(zhēng)精神息息相關(guān)。這種話語(yǔ)的內(nèi)容里面也明顯地具有種種革命政治話語(yǔ)暴力的色彩,往往是以革命的一方來壓倒不革命的一方,以占據(jù)精神的優(yōu)勢(shì)地位的一方來藐視處于精神劣勢(shì)地位的另一方。這種話語(yǔ)內(nèi)容上有著明顯的主客體二分的狀態(tài),帶有鮮明的權(quán)力色彩和膨脹的意識(shí)形態(tài)特征。這在王蒙、王朔、以及九十年代的先鋒作家群的筆下都時(shí)有顯現(xiàn)。從話語(yǔ)的表達(dá)形式來看,這種“語(yǔ)言”又存在著一種過分的語(yǔ)義重復(fù)、排比、夸張、變形、缺乏語(yǔ)言修辭本身的邏輯性、嚴(yán)密性、真實(shí)性、準(zhǔn)確性的特征。這種句式表達(dá)是運(yùn)用了無(wú)數(shù)的排比句造成一種排山倒海式的革命激情,使得言說者似乎擁有無(wú)窮無(wú)盡的話語(yǔ)權(quán)力和言說的正義性,但實(shí)際上又經(jīng)不起從思想到情感多方面的推敲和琢磨,而處于一種假、大、空的語(yǔ)義缺失狀態(tài)。
漢語(yǔ)本來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語(yǔ)種之一,幾千年的文化積淀和知識(shí)傳統(tǒng)更是讓漢語(yǔ)在世界語(yǔ)言之林中大放光彩。但是,“語(yǔ)言”存在的嚴(yán)重的政治權(quán)力化現(xiàn)象,致使語(yǔ)言失去了豐富生動(dòng)的能指特征。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對(duì)于語(yǔ)言的操持和使用大多停留在對(duì)事物的簡(jiǎn)單模仿和描摹狀態(tài),往往都是同一個(gè)模式,同一個(gè)程序,語(yǔ)句簡(jiǎn)單、俗套、缺乏任何的想象力和詩(shī)意。實(shí)際上,無(wú)論是語(yǔ)言本身帶有的“”痕跡也好,還是語(yǔ)言存在的陰柔化、復(fù)制性也好,它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一種變相的語(yǔ)言暴力敘事。文學(xué)本來就是語(yǔ)言的藝術(shù),是憑借語(yǔ)言來建構(gòu)一個(gè)詩(shī)性的審美王國(guó)的藝術(shù)。一旦作家所使用的語(yǔ)言無(wú)法呈現(xiàn)出世界的豐富圖景,無(wú)法把握住跳動(dòng)的生命之律動(dòng),神秘的人生底奧秘,那這種貧乏失血的語(yǔ)言本身也是對(duì)讀者精神的一種僭越,也是剝奪了讀者閱讀樂趣和審美興趣的精神暴動(dòng)。
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分段研討
一、現(xiàn)代文學(xué)時(shí)期
首先,白話文的現(xiàn)代文學(xué)。1917年初發(fā)生的文學(xué)革命,為中國(guó)文學(xué)史樹立了一個(gè)鮮明的界碑,標(biāo)志著以文言文表現(xiàn)形式的古典文學(xué)結(jié)束、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開始。“五四”后,各地愛國(guó)學(xué)生團(tuán)體紛紛效仿《新青年》、《每周評(píng)論》,創(chuàng)辦白話報(bào)刊,僅1919年就出版400多種。由陳衡哲1917年創(chuàng)作了白話短篇小說《一日》,以“莎菲”的筆名發(fā)表于《留美學(xué)生季報(bào)》,這是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只不過影響較小。中國(guó)大多以魯迅《狂人日記》為第一篇白話文,《狂人日記》也是魯迅的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它發(fā)表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雜志四卷五號(hào)上,后收入《吶喊》中,其內(nèi)容與形式的現(xiàn)代化特征成為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的大開端,開辟了我國(guó)文學(xué)(小說)發(fā)展的一個(gè)新的時(shí)代。而在之后,中國(guó)短篇小說大抵是新的智識(shí)者登了場(chǎng)。白話文的出現(xiàn)改變了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形式,為今后中國(guó)文學(xué)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gè)全新的表現(xiàn)手法。其次,各種體裁、題材類型爭(zhēng)相涌出。隨著清末廢科舉、興學(xué)堂,新式文化教育得以發(fā)展,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現(xiàn)代科學(xué)文化知識(shí)的生力軍,為了適應(yīng)文化思潮運(yùn)動(dòng),思想進(jìn)步的有識(shí)之士對(duì)舊有的文學(xué)體裁進(jìn)行大膽的創(chuàng)新寫作,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都發(fā)表自己的文學(xué)作品。其中代表有,郭沫若的戲劇《三個(gè)叛逆的女性》(其中包含《卓文君》、《王昭君》、《聶嫈》三個(gè)劇本),在歷史人物的“骸骨”里吹進(jìn)了“五四”時(shí)代精神;五四新詩(shī)運(yùn)動(dòng),胡適提出了“詩(shī)體的解放”、“詩(shī)體的經(jīng)驗(yàn)主義”,他的《嘗試集》,顯示出從傳統(tǒng)詩(shī)詞中脫胎、銳變,逐漸尋找、試驗(yàn)新詩(shī)形態(tài)的艱難過程;第一批白話文詩(shī)人如胡適、劉半農(nóng)、周作人、沈隱默、俞平伯、康白情都是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骨干;以為代表的作品《青春》、《今》、《新的!舊的!》、《新紀(jì)元》等開創(chuàng)了散文流派,以及大量的白話文小說出世。
各種體裁也在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中深深扎根,中國(guó)在現(xiàn)代文學(xué)時(shí)期也正是在這樣的探索嘗試過程中,產(chǎn)生了一批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學(xué)大師。各具特色的著名小說家、散文家、戲劇家、詩(shī)人、文藝?yán)碚摷遗c批評(píng)家,為中國(guó)與世界文學(xué)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為文學(xué)寶庫(kù)增添了新的內(nèi)容。第三,受外國(guó)文學(xué)的影響,現(xiàn)實(shí)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代主義并重。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是文學(xué)自身發(fā)展孕育的結(jié)果,但外面文藝思潮的影響則是不可忽視的外因。胡適在美國(guó)留學(xué)時(shí),曾非常注意歐洲詩(shī)壇的意象主義運(yùn)動(dòng),中國(guó)的“五四”運(yùn)動(dòng)也是深受俄國(guó)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改革初期,發(fā)動(dòng)者們不斷翻譯介紹外國(guó)的文藝作品,向閉塞的中國(guó)文壇吹進(jìn)新鮮的現(xiàn)代氣息,在《新青年》的帶動(dòng)下,《新潮》、《少年中國(guó)》等許多刊物都翻譯過大量外國(guó)作品,現(xiàn)實(shí)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一時(shí)在中國(guó)文壇盛行。郭沫若的杰出作品《女神》也是受泰戈?duì)枴⒏璧隆⑷A格納等外國(guó)作家多元的影響;郁達(dá)夫的抒情小說《沉淪》,則是19世紀(jì)歐洲浪漫主義以及近代日本“私小說”影響下的產(chǎn)物。受不同文藝思潮和藝術(shù)方法影響的不同作品,浪漫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現(xiàn)代主義并重。第四,臺(tái)灣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臺(tái)灣現(xiàn)代文學(xué)是在大陸的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直接影響和推動(dòng)下發(fā)展的,1920年,當(dāng)時(shí)一些留日的臺(tái)灣學(xué)生仿效大陸的《新青年》在東京創(chuàng)辦了《臺(tái)灣青年》,旨在“研究臺(tái)灣革新,謀求文化向上”,并由此引發(fā)臺(tái)灣的新文化運(yùn)動(dòng)。1923年4月,《臺(tái)灣民報(bào)》在東京創(chuàng)辦,全部采用白話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25年張我軍發(fā)表的《至臺(tái)灣青年的一封信》和同年出版的《亂都之戀》,之后又有賴和的《斗鬧熱》、楊云萍的《光臨》。1925年至1937年,臺(tái)灣的進(jìn)步青年相繼發(fā)表一些具有藝術(shù)水準(zhǔn)的作品。由于當(dāng)時(shí)的臺(tái)灣處于日本的控制下,所以這一時(shí)期的作品多以憂郁的目光凝視災(zāi)難的臺(tái)灣,批判舊社會(huì)習(xí)俗,揭示在日本統(tǒng)治下的這塊土地的流血與傷痛、呻吟與呼喚,展示了頑強(qiáng)不屈的民族精神。從上看來,現(xiàn)代文學(xué)時(shí)期多以結(jié)束封建的思想、宣傳新社會(huì)的文化思想為主流。思想向傳統(tǒng)文學(xué)觀念與手法挑戰(zhàn)的激進(jìn)的精神為主導(dǎo)。開展告白舊文化、提倡中國(guó)國(guó)民思想走向另一個(gè)文學(xué)時(shí)代。
二、當(dāng)代文學(xué)時(shí)期
第一階段:1949-1978年。“”前的文學(xué)。1949年7月,中華全國(guó)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者代表大會(huì)召開,正式確立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所規(guī)定的中國(guó)文藝新方向?yàn)槿玌IWENXUE國(guó)文藝工作的方向。其中民間故事文學(xué)在發(fā)展,例如,1958年,田漢改編的最成功的話劇《關(guān)漢卿》,塑造了知識(shí)分子英雄形象。但在這一時(shí)期,只有工農(nóng)兵才能居于中心地位的“理想英雄”。從中國(guó)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語(yǔ)言來觀察,充斥了戰(zhàn)爭(zhēng)心態(tài)的詞匯幾乎俯首可視,在戰(zhàn)爭(zhēng)文化心理的支配下,給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批評(píng)的主流帶來深刻的影響。“”開始至1978年的文學(xué)。“”使文學(xué)遭受空前的災(zāi)難,它是以文學(xué)藝術(shù)作為其主要批判領(lǐng)域,各界的學(xué)者大多被作為左翼分子被關(guān)進(jìn)“牛棚”接受批斗,從事強(qiáng)制性勞動(dòng)。對(duì)胡適等文人批判否定了“五四”一代知識(shí)分子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浩三的《艷陽(yáng)天》是“”時(shí)期唯一可以公開出售的“”前的作品,那時(shí)主要是為闡釋和捍衛(wèi)文藝的紅色思想。在舉國(guó)狂亂的大浩劫時(shí)代,也有學(xué)者在壓抑的逆境中寫出自己的文章,如牛漢的《半棵樹》與《神的變形》。但由于“”時(shí)期由于長(zhǎng)時(shí)間的文學(xué)打壓,讓大多數(shù)學(xué)者在“”時(shí)期的創(chuàng)作都被淹沒。第二階段:1978-1989年。在這段時(shí)期,中國(guó)社會(huì)發(fā)生急劇的轉(zhuǎn)型,國(guó)家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改革步伐正在加快,商品經(jīng)濟(jì)意識(shí)不斷滲透到各個(gè)社會(huì)文化領(lǐng)域,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多種因素構(gòu)成了對(duì)知識(shí)分子的嚴(yán)峻考驗(yàn),許多作家的作品呈現(xiàn)出心態(tài)浮躁和價(jià)值虛妄的缺陷。但同時(shí),由于改革開放,作家的寫作環(huán)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五四”文化的新文學(xué)傳統(tǒng)又漸漸恢復(fù)了活力。1980年,中央正式提出了含義比較寬泛的“文藝為人民服務(wù),為社會(huì)主義服務(wù)”的總方針。其中的代表有以巴金率先反思“”和總結(jié)自我的《隨想錄》,以及改革開放政策下1979年夏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zhǎng)上任記》脫穎而出,“改革文學(xué)”開始了它的發(fā)軔期。民間風(fēng)土的精神文化融入到文學(xué)作品中,開始有了鄉(xiāng)土小說和市井小說,其中出現(xiàn)了《小巷深處》、《美食家》等膾炙人口的經(jīng)典小說。1985年,以汪曾祺為代表的作家開辟了民間世界的空間,宣揚(yáng)與民族文化的國(guó)家意志和引進(jìn)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xué)思潮結(jié)合在一起,開始了“文化尋根”寫作的文學(xué)藝術(shù)熱潮,許多知青作家參與到寫作中,知青作家成為一時(shí)的文學(xué)潮流作品的創(chuàng)作主體。例如韓少功在《文學(xué)的“根”》一文中,第一次明確闡述了文學(xué)的根應(yīng)該深植于民主文化的土壤里的文化立場(chǎng)。第三階段:20世紀(jì)90年代后。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信息的不斷傳播,20世紀(jì)90年代仿佛是一個(gè)碎片中的世界,作家在不同的立場(chǎng)上寫,逐漸擺脫了帶來了影響。作家們?cè)谳p松自由的環(huán)境中創(chuàng)作屬于自己的文體風(fēng)格,寫出了許多優(yōu)秀作品。如朱蘇進(jìn)強(qiáng)調(diào)人物本身個(gè)人欲望的長(zhǎng)篇小說《醉太平》、瞿永明宣傳女性的《女人組詩(shī)》、民間宗教與理想的《殘?jiān)隆贰€(gè)人對(duì)時(shí)代的反省《叔叔的故事》等。21世紀(jì)的到來,中國(guó)出現(xiàn)了許多不同的文學(xué)形式,如瓊瑤的愛情小說、韓寒的現(xiàn)實(shí)小說、網(wǎng)絡(luò)小說等,現(xiàn)在正在被廣大的文學(xué)愛好者所接受。各種文學(xué)傳播形式也日益更新,如網(wǎng)站、報(bào)紙、電視臺(tái)、廣播、雜志等媒介傳播形式。
三、結(jié)語(yǔ)
當(dāng)代文學(xué)研討與空間
當(dāng)代空間認(rèn)識(shí)論發(fā)生了結(jié)構(gòu)性轉(zhuǎn)移,它強(qiáng)調(diào)空間的能動(dòng)性、自我生成性、異質(zhì)性,由此深刻地影響著文學(xué)研究和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后者將話語(yǔ)重心轉(zhuǎn)向忽視已久的“文學(xué)空間”問題,以期在對(duì)文學(xué)空間的重新審視中,建構(gòu)適應(yīng)于當(dāng)代空間認(rèn)識(shí)論的文學(xué)理論和批評(píng)話語(yǔ)。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對(duì)文學(xué)空間的研究分為兩個(gè)階段,它們也表征著20世紀(jì)隨著歷史語(yǔ)境的變化,文學(xué)研究從關(guān)注文本形式的內(nèi)部研究走向側(cè)重社會(huì)文化的外部研究的歷程和重心變換。文學(xué)文本學(xué)空間研究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中,巴赫金最早真正注意到了文學(xué)空間問題,他在20世紀(jì)初就提出小說的時(shí)空體概念。巴赫金吸收了新康德主義和愛因斯坦相對(duì)論,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中“空間和時(shí)間不可分割”,文學(xué)時(shí)空體是“形式兼內(nèi)容的一個(gè)文學(xué)范疇……空間和時(shí)間標(biāo)示融合在一起被認(rèn)識(shí)了的具體整體中”[1],他以時(shí)空體為基點(diǎn)分析了從古希臘到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指出時(shí)空體是區(qū)分?jǐn)⑹骂愋吞卣鞯幕A(chǔ),它經(jīng)歷了從公共空間(狂歡廣場(chǎng))到私人空間領(lǐng)域的演變。巴赫金站在歷史詩(shī)學(xué)的角度,于社會(huì)歷史語(yǔ)境和文學(xué)審美緯度中洞察文學(xué)空間問題,提出文學(xué)的空間和時(shí)間不可分割辯證統(tǒng)一的觀點(diǎn),為文學(xué)空間研究提供了有意義的研究框架。同時(shí),弗蘭克在對(duì)喬伊斯、龐德等現(xiàn)代小說的分析基礎(chǔ)上,提出“空間形式”概念,它是現(xiàn)代小說中使用并置、主題重復(fù)、多重故事、夸大反諷等的藝術(shù)手段,用以說明現(xiàn)代小說文本中出現(xiàn)的空間化傾向。弗蘭克繼承了西方詩(shī)畫對(duì)比說的古老傳統(tǒng),在形式美學(xué)角度考慮文學(xué)空間問題,把現(xiàn)代小說中出現(xiàn)的碎片化、拼貼等形式美學(xué)技巧視為現(xiàn)代小說的新趨向,使文本形式呈現(xiàn)出繪畫一樣的空間效果。巴什拉獨(dú)樹一幟,他運(yùn)用現(xiàn)象學(xué)和精神分析法專門研究文學(xué)文本中具有詩(shī)意的空間意象和其間蘊(yùn)涵的存在論哲理意蘊(yùn)。對(duì)于巴什拉而言,文學(xué)文本中的詩(shī)意空間“并非物理空間和抽象邏輯空間圖示,它是想象的,體驗(yàn)的,印證人此在的內(nèi)部空間……”[2]以上論述可以看出人們對(duì)文學(xué)空間的探討角度多樣,既有形式緯度也有社會(huì)文化和生存哲理緯度,文學(xué)空間含義不斷擴(kuò)大,從背景的、想象的、形式的、情感的、時(shí)空一體的到隱喻的、詩(shī)意的、哲理的,但對(duì)文學(xué)空間注意還只限于文本某個(gè)層面范圍。
70年代以后,古倫、米切爾、佐倫等人對(duì)文學(xué)空間研究進(jìn)一步深化,直接談?wù)摗拔膶W(xué)空間”概念和整體構(gòu)成上。古倫提出文學(xué)空間是文本的空間,認(rèn)為在文本中具有操縱力量是創(chuàng)作,它產(chǎn)生了文學(xué)藝術(shù)品這一文學(xué)空間,它是文字語(yǔ)言的,具有時(shí)間緯度,又是精神的、情感的、心理的、人格化的、認(rèn)知的,總之要將文學(xué)空間作為整體的一部分,要和時(shí)間、人物、敘述者和讀者聯(lián)系起來而非分割開來理解。古倫首次正面論述了“文學(xué)空間”概念,他要求將作者、讀者和文本空間聯(lián)系起來考察,這一認(rèn)識(shí)對(duì)于目前當(dāng)代文學(xué)空間研究仍有啟迪。W.T.J.米切爾將重點(diǎn)放在文本空間的整體構(gòu)成上,他以“空間形式”指代文本整體空間,認(rèn)為文本本身極為復(fù)雜,它是多層的,有多重的空間維度,為此,他將文本空間分為字面層、描述層、結(jié)構(gòu)形式層、意蘊(yùn)層來考察文本整體空間。加百列•佐倫在《朝向空間的敘事理論》一文意在闡明文本空間結(jié)構(gòu)一般模型,他將文學(xué)空間嚴(yán)格限定在“模仿真實(shí)空間存在于作品中重塑的空間維度”[3],進(jìn)一步細(xì)化文本空間整體構(gòu)成,在垂直和水平維度上分析空間整體結(jié)構(gòu)模式。相比前人,佐倫對(duì)文本空間結(jié)構(gòu)分析最為嚴(yán)謹(jǐn)和細(xì)致,但是佐倫科學(xué)理性地建構(gòu)他的文本空間模型,基本排斥了文學(xué)空間的想象性、情感性、隱喻性、動(dòng)態(tài)性等多元內(nèi)涵。
21世紀(jì)初,文學(xué)研究和理論出現(xiàn)文化轉(zhuǎn)向浪潮,對(duì)文學(xué)的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強(qiáng)調(diào)影響到文學(xué)空間研究,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敘事學(xué)家試圖突破敘事理論封閉自足、過多強(qiáng)調(diào)時(shí)間忽視空間的缺陷,試圖將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與文本空間結(jié)合起來。弗里德曼重點(diǎn)放在文本再現(xiàn)空間(敘事)層面,為凸顯文本再現(xiàn)空間的動(dòng)態(tài)性和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引入作者和讀者兩極,格外強(qiáng)調(diào)讀者閱讀的心理建構(gòu),認(rèn)為敘事文本空間結(jié)構(gòu)是在閱讀中逐漸建構(gòu)起的,提出敘述橫縱軸空間化閱讀和闡釋策略,水平軸是虛構(gòu)人物在文本時(shí)空體的運(yùn)動(dòng),縱軸是作者書寫讀者闡釋,如此,文本與文學(xué)、社會(huì)與歷史形成互文對(duì)話。弗里德曼引入作者、讀者、社會(huì)歷史語(yǔ)境等因素將文本空間構(gòu)成指向一個(gè)動(dòng)態(tài)形態(tài),突破了前人將文學(xué)文本空間視為靜態(tài)、同質(zhì)、被動(dòng)的狹隘觀點(diǎn),但是他立足于文本再現(xiàn)世界而懸置了文本空間其他層面,忽視了文本本身復(fù)雜性、多重的空間層面,且將文本敘事空間構(gòu)成完全轉(zhuǎn)移到讀者心理建構(gòu)上的做法也未必完全妥當(dāng)。隨后,瑪麗•拉熱瑞爾在弗里德曼的基礎(chǔ)上指出敘事學(xué)的空間概念不應(yīng)僅局限于承載事件和場(chǎng)所容器樣的再現(xiàn)世界中,應(yīng)包括文本各個(gè)層面。他將敘事文本空間劃分為敘述空間、文本的空間延伸、文本載體的空間,文本的空間形式,提出要結(jié)合敘述視角對(duì)文本再現(xiàn)空間的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進(jìn)行分析,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bǔ)了弗里德曼的疏漏。文化學(xué)文學(xué)空間理論的建構(gòu)與此同時(shí),當(dāng)代另有一條從社會(huì)文化路徑通往文學(xué)再現(xiàn)世界中的地理、場(chǎng)所,它以跨學(xué)科的視域,融合后現(xiàn)代地理學(xué)、社會(huì)批判理論洞悉文本再現(xiàn)空間中意識(shí)形態(tài)元語(yǔ)言,形成目前極為熱門的當(dāng)代文學(xué)空間理論。文學(xué)空間理論深受當(dāng)代社會(huì)學(xué)理論中空間認(rèn)識(shí)論轉(zhuǎn)型的影響。列斐伏爾、福柯為代表的社會(huì)理論思想家對(duì)傳統(tǒng)的空間觀發(fā)起挑戰(zhàn),賦予空間和時(shí)間一樣的本體論地位,強(qiáng)調(diào)空間的社會(huì)生成力量和異質(zhì)性、多元性、能動(dòng)性提出空間的社會(huì)屬性和空間的生產(chǎn),將空間視為他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判的基石。90年代以來,后現(xiàn)代地理學(xué)進(jìn)一步推波助瀾,在對(duì)傳統(tǒng)歷史決定論的清算時(shí),意欲建構(gòu)歷史—空間—社會(huì)的三維辯證法,以形成充滿政治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人文地理批判話語(yǔ),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批判功能。在社會(huì)理論和后現(xiàn)代地理學(xué)重申空間的推動(dòng)下,人文知識(shí)領(lǐng)域各學(xué)科(包括文學(xué))紛紛參與空間問題的探討上,共同積極建構(gòu)空間理論,探討空間問題,完成從時(shí)間意識(shí)向空間意識(shí)的轉(zhuǎn)向。跨學(xué)科的空間理論與文學(xué)理論和研究形成互動(dòng)策應(yīng)關(guān)系:各學(xué)科從不同角度切入文學(xué)領(lǐng)域,對(duì)空間的分析多少涉及文學(xué)藝術(shù),文學(xué)理論和研究也積極參與空間理論的建構(gòu),成為其中重要組成部分。文學(xué)理論在吸收跨學(xué)科空間研究豐富的理論資源基礎(chǔ)上,積極構(gòu)筑出文學(xué)空間理論和批評(píng)話語(yǔ)。它以文學(xué)文本再現(xiàn)世界中的地理、場(chǎng)景、地點(diǎn)等再現(xiàn)空間為主要對(duì)象,從文化、社會(huì)角度切入,關(guān)注文本再現(xiàn)空間的指涉系統(tǒng),挖掘其間隱藏的文化、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等因素,意旨在實(shí)現(xiàn)其社會(huì)批判功能,并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批評(píng)成果。文學(xué)空間理論和批評(píng)的興趣并不在于追尋“文學(xué)空間”概念和“文學(xué)”本身,對(duì)它們而言,文學(xué)空間便是“文學(xué)景觀”,是文學(xué)表述層面中的地理、地點(diǎn)、場(chǎng)景等再現(xiàn)空間和其背后的文化、社會(huì)等指涉,“文學(xué)景觀最好看做文學(xué)和景觀的兩相結(jié)合,而不是視文學(xué)為孤立的鏡子……文學(xué)提供觀照世界的方式,顯示一系列趣味的經(jīng)驗(yàn)和知識(shí)的景觀。”
文學(xué)空間理論和批評(píng)之所以聚焦于文本再現(xiàn)空間,重要原因在于它非但是跨學(xué)科空間理論的組成部分和產(chǎn)物,還源自目前身處的文學(xué)文化轉(zhuǎn)向語(yǔ)境。文學(xué)空間理論批評(píng)與其他文學(xué)文化、意識(shí)形態(tài)批評(píng)一樣,不再糾纏于文本審美性、文學(xué)性等問題,而將它們視為是特定社會(huì)、歷史、文化的關(guān)系性構(gòu)成的產(chǎn)物,是漂浮的能指和社會(huì)實(shí)踐的話語(yǔ)結(jié)果,不再具有終極的意義價(jià)值。為此,文學(xué)空間理論和批評(píng)與后現(xiàn)代人文學(xué)科一道,將文學(xué)再現(xiàn)空間置于前臺(tái),將之視為濃縮著當(dāng)代社會(huì)文化問題的一個(gè)文化表征和符碼,對(duì)它進(jìn)行社會(huì)文化意識(shí)形態(tài)分析,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批判功能。文學(xué)再現(xiàn)空間和文學(xué)一樣成為文化研究的實(shí)踐,益處在于“文化研究,因?yàn)閳?jiān)持把文學(xué)研究作為一項(xiàng)重要的研究實(shí)踐,堅(jiān)持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是如何影響并覆蓋文學(xué)作品的,所以它能夠把文學(xué)研究作為一種復(fù)雜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現(xiàn)象加以強(qiáng)化。”
文學(xué)空間理論和批評(píng)以外部研究方法積極探索文學(xué)空間的社會(huì)文化歷史因素,體現(xiàn)出文學(xué)與文化間復(fù)雜的關(guān)聯(lián),尤其將文學(xué)空間拓展到能動(dòng)、異質(zhì)和社會(huì)生成力層面上,進(jìn)一步深化了文學(xué)空間研究。如果說世界是符號(hào)系統(tǒng)的差異性關(guān)系的話語(yǔ)建構(gòu),那么文學(xué)則是關(guān)于這個(gè)話語(yǔ)的話語(yǔ),文學(xué)有相對(duì)獨(dú)立的自主性和邏輯,文學(xué)空間并不等于現(xiàn)實(shí)空間和地理。但文學(xué)空間理論卻將“文學(xué)空間”縮減為“文本再現(xiàn)空間”一個(gè)層面,完全忽視文本審美維度和自主性,一味趨向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方法,必然引起喪失文學(xué)本體論的身份定位的危險(xiǎn)。尤其重要的是,新的空間認(rèn)識(shí)論堅(jiān)持空間的多元性、開放性、異質(zhì)性,文學(xué)空間理論和批評(píng)也必須以此為依據(jù),在文學(xué)學(xué)科視野中,重新界定“文學(xué)空間”,建構(gòu)出相應(yīng)的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方法策略。在這點(diǎn)上,文學(xué)空間理論還有待繼續(xù)深化和亟待自我理論建構(gòu)的完善。
當(dāng)代文學(xué)營(yíng)銷行為
自從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文學(xué)傳播的一個(gè)突出現(xiàn)象便是文學(xué)營(yíng)銷日益成為自覺自主的行為,以吸引社會(huì)注意力為主要目標(biāo)的各種文學(xué)炒作行為成為文學(xué)營(yíng)銷的集中表現(xiàn)。文學(xué)營(yíng)銷與炒作是在新的社會(huì)條件尤其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條件下,文學(xué)傳播方式具有重要意義的變革。對(duì)文學(xué)營(yíng)銷進(jìn)行深入探析,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其具有復(fù)雜的內(nèi)在機(jī)理和多樣的客觀效應(yīng)。
一、何為“文學(xué)營(yíng)銷”
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之前的傳統(tǒng)社會(huì)中,文學(xué)傳播目的并不具有十分強(qiáng)烈的經(jīng)濟(jì)利益色彩,創(chuàng)作者經(jīng)常無(wú)償?shù)胤瞰I(xiàn)自己的才智。在商品社會(huì)中,文學(xué)活動(dòng)以一種特殊方式在運(yùn)作:文學(xué)生產(chǎn)—文學(xué)產(chǎn)品—文學(xué)市場(chǎng)。文學(xué)產(chǎn)品可以被視為“藝術(shù)價(jià)值”與“經(jīng)濟(jì)價(jià)值”的統(tǒng)一體,“藝術(shù)價(jià)值”要在接受活動(dòng)中由接受者的鑒賞活動(dòng)來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要在文學(xué)市場(chǎng)中由讀者的文學(xué)消費(fèi)活動(dòng)來實(shí)現(xiàn)。正如其他商品走向市場(chǎng)要經(jīng)過推廣一樣,文學(xué)產(chǎn)品也需要宣傳推介活動(dòng),即文學(xué)營(yíng)銷。文學(xué)營(yíng)銷是整個(gè)文學(xué)生產(chǎn)活動(dòng)系統(tǒng)中文學(xué)產(chǎn)品走向文學(xué)市場(chǎng)、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價(jià)值的必要環(huán)節(jié)。文學(xué)營(yíng)銷中所流動(dòng)的文學(xué)信息將三個(gè)行為主體,即作者、營(yíng)銷者和讀者(受眾)聯(lián)系在一起。三個(gè)主體中的任何一方都無(wú)法獨(dú)立主導(dǎo)整個(gè)文學(xué)營(yíng)銷,文學(xué)信息并非單向地流動(dòng),而是在三個(gè)主體間雙向或多向傳輸,表現(xiàn)出明顯的互動(dòng)效應(yīng)。通過以上簡(jiǎn)要的分析可知,文學(xué)營(yíng)銷是借助于大眾媒體進(jìn)行的宣傳活動(dòng),在作品、作者、營(yíng)銷者和文學(xué)受眾之間形成了多向互動(dòng)的信息流動(dòng),其主要目的是實(shí)現(xiàn)文學(xué)作品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如果在文學(xué)營(yíng)銷過程中超出了必要的限度,過分關(guān)注與文學(xué)聯(lián)系并不密切的外圍信息,如個(gè)人隱私、司法糾紛等,那么就可以將這種行為視為“文學(xué)炒作”,是文學(xué)營(yíng)銷中消極行為的集中展現(xiàn)。需要說明的是,在市場(chǎng)營(yíng)銷理論中,“文學(xué)營(yíng)銷”是一個(gè)專門術(shù)語(yǔ),指借助于以文學(xué)為代表的文化資源開展?fàn)I銷活動(dòng)的一種策略和方式,營(yíng)銷的對(duì)象主要是物質(zhì)產(chǎn)品和服務(wù)體驗(yàn),因此其確切的名稱宜為“文化營(yíng)銷”。本文所論“文學(xué)營(yíng)銷”的對(duì)象是文學(xué)作品這種精神產(chǎn)品,即對(duì)文學(xué)作品的營(yíng)銷。
二、文學(xué)營(yíng)銷產(chǎn)生的動(dòng)因與條件
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社會(huì)中,人們對(duì)物質(zhì)的欲望較之以往更加惡性膨脹,文學(xué)藝術(shù)要想使人們聽到自己的聲音,要獲得并鞏固加強(qiáng)對(duì)生活的干預(yù)作用,實(shí)現(xiàn)對(duì)人的終極關(guān)懷,單單依靠傳統(tǒng)的“田園吟詠”式的傳播方式已無(wú)以為繼。因此文學(xué)就要借助市場(chǎng)化機(jī)制,在一片喧囂中為自己爭(zhēng)得注意力。只有被關(guān)注、被傾聽、被思索、被接受,文學(xué)的終極關(guān)懷精神才能得到昭彰。文學(xué)營(yíng)銷在這種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上應(yīng)運(yùn)而生,文學(xué)借助于各種營(yíng)銷策略與手段激越地吶喊,其內(nèi)驅(qū)力正是文學(xué)對(duì)自我價(jià)值復(fù)歸的渴望。在中外文學(xué)史上,每當(dāng)社會(huì)處于轉(zhuǎn)型期往往會(huì)有極具思想深度與藝術(shù)影響力的作品出現(xiàn)。但遺憾的是,這條規(guī)律在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界卻遲遲難以復(fù)現(xiàn)。文學(xué)努力證明自身價(jià)值但又不能以有力的創(chuàng)作實(shí)績(jī)來達(dá)到這一目的,于是采取了營(yíng)銷這種表面化的策略來獲得關(guān)注。文壇雖然熱鬧,你方唱罷我登場(chǎng),但終究只是各領(lǐng)風(fēng)騷三五年,有的甚至更短。即使是獲得過文學(xué)大獎(jiǎng)的作品,也只是在當(dāng)時(shí)紅極一時(shí),時(shí)過境遷后幾乎無(wú)人再次提起。文壇的“藝術(shù)泡沫”不斷產(chǎn)生崩裂。文學(xué)泡沫便是文學(xué)營(yíng)銷的直接結(jié)果,從這個(gè)角度來看,對(duì)營(yíng)銷的過分重視正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衰弱的表現(xiàn)。文學(xué)營(yíng)銷所需要的條件首先是以?shī)蕵窞槟康牡淖x者群日益壯大。文學(xué)讀者獲取知識(shí)、接受教育以及獲得審美享受的接受意圖轉(zhuǎn)變?yōu)閵蕵废采踔磷汾s時(shí)尚的接受意圖。讀者平和沉穩(wěn)的閱讀心境已為外界紛繁豐富的生活欲望大大削弱。讀者成為文學(xué)產(chǎn)品的消費(fèi)者,閱讀不再是思想歷險(xiǎn)而變成了尋求刺激的途徑。文學(xué)營(yíng)銷恰恰最善于提供快餐式作品,適應(yīng)了淺閱讀成為文學(xué)主要接受方式的趨勢(shì)。文學(xué)營(yíng)銷借助于技術(shù)發(fā)達(dá)且類型豐富的大眾傳播媒體獲得了更快、更廣、更專的效果。文學(xué)營(yíng)銷的重要陣地是解釋型媒介———報(bào)刊。詳細(xì)的介紹與評(píng)說對(duì)于文學(xué)營(yíng)銷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讀者的接受過程帶有反復(fù)性,報(bào)刊的深度特點(diǎn)與可保存性正與此相適合。廣播與電視具有圖文并茂、時(shí)效性強(qiáng)等特點(diǎn),為文學(xué)營(yíng)銷炒作提供了巨大機(jī)會(huì),在效果上具有紙媒難以比擬的優(yōu)越性。網(wǎng)絡(luò)的迅猛發(fā)展使文學(xué)營(yíng)銷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媒介條件。文學(xué)信息在網(wǎng)上傳播不僅兼具其他各種媒體的優(yōu)點(diǎn),而且三要素之間的互動(dòng)性大大增強(qiáng)了,網(wǎng)絡(luò)受眾的反饋信息可以及時(shí)傳遞給作者與營(yíng)銷者,進(jìn)而影響整個(gè)創(chuàng)造與營(yíng)銷過程。
三、文學(xué)營(yíng)銷的主要策略
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理念研究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到如今已有六載,莫言本身作為一種傳播媒介的符號(hào)不斷地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教學(xué)建構(gòu)中,莫言的獲獎(jiǎng)使整個(gè)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的理念發(fā)生深刻的變化。
一、“媒介訊息論”與莫言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理念的影響
“媒介即訊息”[1]33是麥克盧漢提出的重要觀點(diǎn)。媒介不僅是信息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還作為傳播的渠道用于擴(kuò)大信息的通道。作為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莫言,媒介宣傳與傳播“莫言”這個(gè)信息,使莫言成為當(dāng)下最為著名的作家。傳媒傳播莫言時(shí),同時(shí)又把“莫言”作為一種符號(hào)媒介影響著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發(fā)展的走向,進(jìn)而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理念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美國(guó)文藝學(xué)家M.H.艾布拉姆斯于1953年出版了《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píng)傳統(tǒng)》,提出了著名的藝術(shù)活動(dòng)四要素理論:世界、作家、作品、讀者。這個(gè)四要素理論“幾乎可以包括西方文論史上各種理論學(xué)派的批評(píng)特征,可以使初步涉獵西方文論領(lǐng)域者對(duì)這一領(lǐng)域內(nèi)的歷史演變、流派紛爭(zhēng)以及當(dāng)今狀況很快就有一個(gè)大致的了解。”[2]但是,理論發(fā)展無(wú)止境,它也會(huì)隨著社會(huì)的進(jìn)步,新事物與新的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調(diào)整自己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現(xiàn)代傳媒技術(shù)的興起,不僅影響著社會(huì)生活的各個(gè)方面,它的介入已經(jīng)影響到文學(xué)理論建構(gòu)的新發(fā)展。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文學(xué)理論家開始關(guān)注世界、作家、作品、讀者之外的另一個(gè)重要因素(媒介),如學(xué)者單小曦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出版了《媒介與文學(xué):媒介文藝學(xué)引論》一書,從理論上探討媒介在文學(xué)活動(dòng)中存在的重要方式,把媒介提升到文學(xué)存在論的角度,認(rèn)為媒介是文學(xué)中除四要素之外的一個(gè)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文學(xué)的組成部分。文學(xué)作為一種語(yǔ)言的藝術(shù),語(yǔ)言符號(hào)本身就是文學(xué)的成分。然而,若只是將文學(xué)理解為一種簡(jiǎn)單邏輯的語(yǔ)言符號(hào),遠(yuǎn)沒有將文學(xué)的媒介作用挖掘出來。單小曦正是從該論點(diǎn)出發(fā),更感性、直接、精細(xì)地捕捉到媒介的意義與存在的價(jià)值,將文學(xué)媒介分為專門性和功能性兩種媒介進(jìn)行論述。什么是文學(xué)媒介呢?他說:“文學(xué)媒介指?jìng)鬟f文學(xué)信息的專門性媒介,在這個(gè)意義上主要包括四個(gè)層面的四種類型:(1)符號(hào)媒介,它是承載文學(xué)信息的符號(hào)形式,與文學(xué)語(yǔ)義內(nèi)容一起構(gòu)成了文學(xué)信息;(2)載體媒介,它是書面文學(xué)語(yǔ)言、字的承載物,包括石頭、泥板、象牙、甲骨、竹簡(jiǎn)、布帛、膠片、光盤、電子屏幕等;(3)制品媒介,指的是符號(hào)媒介與載體媒介的結(jié)合物被進(jìn)一步加工成產(chǎn)品,包括冊(cè)頁(yè)、扇面、手抄本、印刷書刊、電子出版物、互聯(lián)網(wǎng)網(wǎng)頁(yè)等;(4)傳播媒體,它是對(duì)文學(xué)的文本進(jìn)行選擇加工、集體生產(chǎn)或再生產(chǎn),然后向讀者傳播的傳媒機(jī)構(gòu),包括出版印刷、期刊、電影、電視、網(wǎng)絡(luò)公司等。這些傳媒機(jī)構(gòu)集生產(chǎn)職能與傳播職能為一身,從傳播學(xué)的角度來說,就是傳播媒介。”[3]46單小曦給予文學(xué)媒介以清晰的理論價(jià)值定位,他對(duì)媒介的劃分標(biāo)準(zhǔn)有利于具體操作世界、作家、作品、讀者與媒介五個(gè)要素之間錯(cuò)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這不僅便于深入整個(gè)文學(xué)活動(dòng)內(nèi)部的創(chuàng)作過程,還可以動(dòng)態(tài)地探究文學(xué)內(nèi)部與外部之間的相互作用與意義。介于媒介與文學(xué)的不可分性,不妨以此作為一個(gè)角度,分析莫言獲諾貝爾獎(jiǎng)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理念改變的作用。在媒介的視角下,莫言不只作為作家,他還作為一種信息媒介貫穿于整個(gè)文學(xué)活動(dòng)與傳播過程。如在莫言剛剛獲得諾貝爾獎(jiǎng)的初期,各位專家學(xué)者、作家把莫言作為主題,紛紛以各種方式傳遞他們的心聲,無(wú)論是恭賀還是嫉妒,莫言成為專家學(xué)者心目中走出國(guó)門、走入世界的中國(guó)文學(xué)的象征。莫言是中國(guó)文學(xué)的,也是世界文學(xué)的符號(hào)。處在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群中的佼佼者或者奮進(jìn)者,無(wú)不以莫言為楷模照亮自己創(chuàng)作的道路。莫言獲諾貝爾獎(jiǎng)的消息不脛而走,各高校,尤其是具有中文專業(yè)的高校、研究機(jī)構(gòu),歡聚一堂,談?wù)撃浴⒄務(wù)撝袊?guó)文學(xué)、談?wù)撝袊?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價(jià)值與意義,為廣大師生了解、接近、研究莫言提供了契機(jī),同時(shí)也為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堂增加了活力。作為從事專業(yè)研究領(lǐng)域機(jī)構(gòu)的高校,紛紛舉辦莫言研究講座積累研究成果,成立研究莫言文學(xué)、挖掘探索莫言文學(xué)的深層次意義,出版莫言研究專著。高校教師作為文學(xué)批評(píng)界的主力,在不斷擴(kuò)大莫言研究的范圍與影響中,以點(diǎn)帶面地提升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作用,進(jìn)一步影響到高校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理念變化。莫言的存在,是以作品的敘述風(fēng)格,小說獨(dú)有的特色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影響,使讀者不得不以莫言為首,成為劃分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家流派的標(biāo)桿,使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潮重起。媒介,不只是作為符號(hào)存在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它還作為一種文學(xué)傳播流通的渠道貫穿于文學(xué)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過程中,這在傳播學(xué)中稱之為傳播媒介。文史學(xué)家“嗅著”莫言的名聲,再度重新審視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書寫。雖然文學(xué)史的更新還跟不上時(shí)代的步伐,但是這種新因子的“發(fā)現(xiàn)與提倡”,高校教師在私下里進(jìn)行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教學(xué)時(shí),未免借由莫言的名頭,不假思索地加進(jìn)了相關(guān)莫言的課時(shí),并對(duì)他及相關(guān)信息多做一些“評(píng)頭論足”之論,這樣勢(shì)必帶動(dòng)整個(gè)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內(nèi)容的變化。莫言作為語(yǔ)言符號(hào)媒介的新時(shí)代因子影響著整個(gè)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理念,而以當(dāng)代文學(xué)為研究與傳播對(duì)象的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必然受到這個(gè)語(yǔ)言符號(hào)建構(gòu)的影響。莫言不僅作為一種語(yǔ)言符號(hào)構(gòu)建著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的教學(xué)理念,同時(shí),莫言還作為一種制品媒介影響著受眾的心理,以莫言為圓心擴(kuò)大了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影響,進(jìn)而使更多的人關(guān)注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
二、符號(hào)媒介:莫言與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內(nèi)容的改變
符號(hào)媒介,是指任何表達(dá)與運(yùn)動(dòng)所運(yùn)用的形式。沒有無(wú)內(nèi)容的形式,也沒有無(wú)形式的內(nèi)容,二者如同硬幣的兩面不可或缺。而符號(hào)是“被認(rèn)為攜帶意義的感知”[4]1。符號(hào)所說的感知部分,指的就是媒介———“符號(hào)即媒介”[5]139-154。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作為一門課程,它是由不同的符號(hào)媒介構(gòu)成,從文學(xué)的整體框架而言,包括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方面。他們都只是作為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因子通過各自的組合方式,以不同的形態(tài)影響著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走向。此處主要把莫言作為一個(gè)符號(hào)媒介,分析其如何建構(gòu)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內(nèi)里,影響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內(nèi)容。莫言出生于山東高密鄉(xiāng),他的出生經(jīng)歷沉淀著山東鄉(xiāng)民民間生活的意義。莫言以中西結(jié)合的方式講述著山東鄉(xiāng)民的點(diǎn)滴生活,影響著莫言文學(xué)的風(fēng)格。這一點(diǎn)以莫言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lì)C獎(jiǎng)詞為證,“莫言作品將一個(gè)被遺忘的農(nóng)民世界生動(dòng)展現(xiàn)人前,他比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以及當(dāng)代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以來多數(shù)作家更滑稽和震撼人心。”陳思和作為當(dāng)代文學(xué)建構(gòu)的權(quán)威,他在評(píng)論這一評(píng)價(jià)時(shí)說:“我感到他們真的看懂莫言了,這不僅僅是語(yǔ)言問題。莫言的民間立場(chǎng)和民間寫作與拉伯雷所代表的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民間狂歡傳統(tǒng)有相似之處。”同時(shí),陳思和從民間文化這個(gè)角度指出了莫言小說的獨(dú)特性,“在文學(xué)史上,不僅在中國(guó),西方國(guó)家也有這樣一種悠久的民間傳統(tǒng)。而這種傳統(tǒng)就是寫底層,體現(xiàn)了下層人民的一種美學(xué),一種力量,強(qiáng)調(diào)了生命力,莫言恰恰是在這樣的領(lǐng)域里做出了貢獻(xiàn)。當(dāng)我們用一種高雅文化的態(tài)度去談莫言是很難的,莫言的語(yǔ)言不美;莫言所塑造的形象很粗糙,可是他那種人物的生命力量,那種對(duì)生命的謳歌和贊美,在中國(guó)和歐洲都很缺乏。”莫言以這樣一種填補(bǔ)當(dāng)代文學(xué)空白的創(chuàng)作力作,充分證明了文學(xué),尤其是世界文學(xué)的方向。“莫言所代表的民間文化立場(chǎng),不僅僅是中國(guó)獨(dú)有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因素。”[6]656-700雖然與莫言同時(shí)出現(xiàn)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作家,如王安憶、賈平凹、余華、閻連科、張煒等(許多評(píng)論家都預(yù)言若中國(guó)再出現(xiàn)一位諾貝爾獎(jiǎng)獲得者,就是他們中的某一位),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確實(shí)會(huì)落于這些作家中的任何一位。諾獎(jiǎng)卻選擇了莫言,無(wú)樹不成林,無(wú)川不成海,莫言的拔尖顯示了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實(shí)力。而此時(shí)獲諾獎(jiǎng)的“莫言”這個(gè)符號(hào)不僅從他的作品風(fēng)格,莫言以自己所習(xí)慣的語(yǔ)言符號(hào)媒介表達(dá)著自己的思想。從莫言的一系列作品,《透明的經(jīng)蘿卜》《紅高粱》《肥乳豐臀》《蛙》《生死疲勞》《檀香刑》《酒國(guó)》等作品,看出莫言在語(yǔ)言方面經(jīng)歷的變化:由感覺化的西方傳統(tǒng)文化的滲透,到粗鄙的先鋒姿態(tài)語(yǔ)言運(yùn)用,再到白描式書寫。語(yǔ)言作為一個(gè)符號(hào)反映出了中國(guó)當(dāng)代小說的文學(xué)潛在的變化。從文學(xué)語(yǔ)言這個(gè)典型的文學(xué)符號(hào)媒介所表達(dá)的文學(xué)內(nèi)容意義來看,語(yǔ)言是文學(xué)的一個(gè)外在表現(xiàn),而作為文學(xué)的內(nèi)容是通過文學(xué)語(yǔ)言媒介所表現(xiàn)出來的。莫言創(chuàng)作的作品作為文學(xué)符號(hào)成為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一個(gè)主要流變的方標(biāo)。以“莫言”這個(gè)符號(hào)為坐標(biāo),梳理當(dāng)代文學(xué)的作家流派,以他們同時(shí)代的一個(gè)大團(tuán)體作為一個(gè)大的文學(xué)環(huán)境,又以年齡特征與他們下一代的韓寒、張悅?cè)坏刃碌淖骷冶容^,同時(shí)還有畢飛宇等下下一代這批作家,他們雖然各自為政,成其一方“諸侯”,而他們卻共同構(gòu)成了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文學(xué)環(huán)境,成其為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講授的主要內(nèi)容。教材內(nèi)容比例的偏重傾斜變更,與教材理念的變化有莫大的關(guān)系。曾經(jīng)的當(dāng)代文學(xué)內(nèi)容相較現(xiàn)代文學(xué)總是不夠自信。20世紀(jì)80年代興起重寫文學(xué)史的潮流,使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編排方式打破舊格局,走向新天地,洪子誠(chéng)的《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就是代表之一。教材本身也是一個(gè)傳播媒介的信號(hào),而傳播媒介受到“把關(guān)人”價(jià)值觀念的影響就有被選擇與不選擇的權(quán)力。寫于教材里的作家作品往往被認(rèn)為是重要的作家作品,排斥于教材之外的作家作品,也許相對(duì)編于權(quán)威教材里的內(nèi)容來說就顯得名不正言不順了。由于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主要是大學(xué)階段漢語(yǔ)言文學(xué)專業(yè)的主要教學(xué)課程,同時(shí)也涉及對(duì)外漢語(yǔ)或文秘教育專業(yè)的學(xué)生。他們作為大學(xué)生,理應(yīng)以自由思考為主。所以,大學(xué)所教課程內(nèi)容,似乎教師的自主性會(huì)更強(qiáng)些,并非所有教學(xué)內(nèi)容都必須與教材吻合。在教學(xué)中教師完全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判斷,結(jié)合文學(xué)發(fā)展的前沿,展開他們認(rèn)為更有意義和價(jià)值的作家作品傾斜的課程。而且教材的更替遠(yuǎn)沒有文學(xué)自身發(fā)展之快,例如,莫言獲諾獎(jiǎng)這個(gè)對(duì)于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大事件,在現(xiàn)有的教材中還沒有及時(shí)地把這一事件編入教材,但是作為高校的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專業(yè)教師就不能以教材為牢,不顧莫言的存在,或以簡(jiǎn)介的方式簡(jiǎn)單地對(duì)莫言作一評(píng)價(jià)。莫言在高校的課程中成為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八九十年代文學(xué)的主角,并且以他為主軸形成一個(gè)文學(xué)圓心,來梳理莫言同時(shí)代作家作品的信息,及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的歷史文學(xué)語(yǔ)境,和當(dāng)時(shí)的文學(xué)思潮的影響。但以當(dāng)今高校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使用頻率最高的洪子誠(chéng)的《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教材看,莫言只是在這本文學(xué)史中略有半頁(yè)之多的介紹,至于他那些重要的長(zhǎng)篇小說以注釋的方式出現(xiàn)。當(dāng)然,作家作品的介紹還需與文學(xué)史體例本身的結(jié)構(gòu)勻稱相關(guān),若莫言一個(gè)人占的篇幅過多,有失于教材的結(jié)構(gòu),但是莫言的介紹從內(nèi)容上說只是王安憶的一半。此處并非說王安憶不重要,以此為例說明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的內(nèi)容結(jié)構(gòu)。而對(duì)莫言民間文化體現(xiàn)的高度評(píng)價(jià)者陳思和,在他以作家作品為體例來結(jié)構(gòu)當(dāng)代文學(xué)教材的著名的《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教程》中,莫言也沒有專章的內(nèi)容出現(xiàn)。《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教程》編寫前后,陳思和對(duì)作家的理解理念已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若這本教材重新編例排版的話,大膽地猜想,也許陳思和將會(huì)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新的看法有所體現(xiàn)。由此可以看出當(dāng)代文學(xué)教材內(nèi)容的變化。莫言,不僅是名作者,還包含他的作品,還作為一個(gè)符號(hào)媒介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內(nèi)容建構(gòu)的波動(dòng),從而引起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內(nèi)容的變化。
三、傳播媒介:莫言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受眾范圍變化的影響
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教學(xué)改革論文
摘要:簡(jiǎn)要分析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存在的問題,側(cè)重介紹實(shí)施教學(xué)過程中所作的教改探索——注意授之以法、把握學(xué)科動(dòng)態(tài)、完善教學(xué)手段、加強(qiáng)課外閱讀,以期為高校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課及相關(guān)課程的教學(xué)改革提供借鑒。
關(guān)鍵詞: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教學(xué)現(xiàn)狀課程改革
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是高校中文專業(yè)的一門專業(yè)基礎(chǔ)課,學(xué)好這門課程對(duì)學(xué)生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思維方式乃至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幫助。然而,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價(jià)值觀念的變化,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和古代文學(xué)、外國(guó)文學(xué)等不能產(chǎn)生即時(shí)效應(yīng)的基礎(chǔ)學(xué)科一樣,日益受到冷落。較之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學(xué)生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學(xué)習(xí)積極性普遍降低,身為中文系學(xué)生不明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現(xiàn)代名家名作的大有人在,不了解當(dāng)代尤其是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的作家作品現(xiàn)象也屢見不鮮。為數(shù)不少的學(xué)生并不通過閱讀體味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深厚意蘊(yùn),當(dāng)然也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學(xué)作品中所蘊(yùn)涵的人文精神。這種現(xiàn)象不能不令人擔(dān)憂,針對(duì)這種狀況,我們?cè)谥v授《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課程時(shí)也動(dòng)了些腦筋,作了些嘗試性的教改探索,以提高課堂教學(xué)效果。
一、注意授之以法,提升學(xué)生理論素養(yǎng)
學(xué)習(xí)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不單是讓學(xué)生了解一些文學(xué)現(xiàn)象、文學(xué)知識(shí),更重要的是透過現(xiàn)象、知識(shí)把握其內(nèi)在聯(lián)系,即把握文學(xué)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從現(xiàn)象、知識(shí)上升到理論的概括和思辨,給學(xué)生以理論武器,使之學(xué)會(huì)用以觀照、解讀文學(xué)現(xiàn)象、作家作品。在教學(xué)中凡能聯(lián)系上升到理論的地方我們盡量突出理論色彩,講出理論高度,力求以文學(xué)藝術(shù)規(guī)律來貫穿史的脈絡(luò),按規(guī)律來整合文學(xué)史的建構(gòu)。如講朦朧詩(shī),不重于詳盡解析某幾位詩(shī)人及其詩(shī)作,而重在對(duì)朦朧詩(shī)整體性的理論闡釋上,重心放在講授朦朧詩(shī)的產(chǎn)生原因、概念界定,特別是審美藝術(shù)特征上。詩(shī)人詩(shī)作只在講審美藝術(shù)特征時(shí)作為例子舉出,與理論觀點(diǎn)相印證。最后再講朦朧詩(shī)何以為美-模糊認(rèn)知、模糊美、美與模糊的“血緣”關(guān)系問題。這樣,學(xué)生就會(huì)對(duì)這個(gè)新崛起的詩(shī)群有個(gè)宏觀上的理論的認(rèn)知。再如講新時(shí)期探索戲劇時(shí),先講探索戲劇的概念、類型、審美藝術(shù)特征、價(jià)值評(píng)估,然后再講代表作《屋外有熱流》、《野人》、《狗兒爺涅梁》、《桑樹坪紀(jì)事》,學(xué)生就可以對(duì)戲劇探索潮流態(tài)勢(shì)、成就有較為完整全面的了解。再如講王蒙小說,如果用較多篇幅分析他的作品,介紹他的“敏銳感知、發(fā)現(xiàn)問題”、“既有傳統(tǒng)手法,又有現(xiàn)代手法的文體革新實(shí)驗(yàn)”、“價(jià)值判斷的矛盾性與多向性”,如此論述固然面面俱到、全面完整,但點(diǎn)到為止,理論穿透力不夠,王蒙最突出的特點(diǎn)還是沒能揭示出來。我講此專題時(shí)把王蒙作為“東方意識(shí)流小說”的代表,突出他“第一個(gè)吃螃蟹”借鑒外國(guó)現(xiàn)代派手法寫作意識(shí)流小說的開創(chuàng)之功,著重介紹其意識(shí)流小說三種主要技法,即追求感覺印象、內(nèi)心獨(dú)白以及自由聯(lián)想的基本手段、夢(mèng)幻描寫、時(shí)空交叉的放射型心理結(jié)構(gòu)形態(tài)。
講這些觀點(diǎn)時(shí)把王蒙的諸多作品作為例子穿插結(jié)合進(jìn)去,這樣既評(píng)介了王蒙作品,也顯示了意識(shí)流小說的基本理論,使學(xué)生不獨(dú)了解一位作家、幾部作品,而且懂得意識(shí)流小說的精義,以后再讀此類作品就可以舉一反三了。再譬如講一部作品的主題,倘若就題論題,單講該作品主題必顯單薄,如果探源索流,挖掘一下文學(xué)史母題,從主題學(xué)的視點(diǎn)審視該作品的主題,就深刻豐贍得多。如講《紅高粱》以“童年視角”為本體,從父母——當(dāng)時(shí)13歲的豆官的感覺記憶中來寫抗日斗爭(zhēng),從孫子“我”的追憶中回?cái)敔敗⒛棠痰睦寺松⒃谂で信畈L(zhǎng)的人性。由此引申出文學(xué)史上的父親主題。從最早的原型、荷馬史詩(shī)奧德修紀(jì)海上漂流年后回鄉(xiāng)與妻兒團(tuán)聚的父親講起,講到近現(xiàn)代流浪漢小說的尋找父親——斯丁小說的恭維父親——司湯達(dá)小說的敵視父親——巴爾扎克小說的嘲笑父親——卡夫卡小說的順從父親——喬伊斯小說的呼喚父親,聯(lián)系到中國(guó)文學(xué)的孝父主題,最后串連起當(dāng)代文學(xué)王愿堅(jiān)小說《親人》的將錯(cuò)就錯(cuò)假認(rèn)父親、張承志小說《北方的河》渴望父親、主人公在黃河找到了父親周克芹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的關(guān)愛父親、洪峰小說《奔喪》的冷漠父親,這樣便把作為父權(quán)文化產(chǎn)物的父親主題的發(fā)展線索梳理出來,使學(xué)生從中了解文學(xué)主題自身的演變進(jìn)化規(guī)律。
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德育教學(xué)實(shí)踐探索
一、挖掘德育資源,打造立德樹人新課堂
指出:“文藝是時(shí)代前進(jìn)的號(hào)角,最能代表一個(gè)時(shí)代的風(fēng)貌,最能引領(lǐng)一個(gè)時(shí)代的風(fēng)氣。實(shí)現(xiàn)‘兩個(gè)一百年’奮斗目標(biāo),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作為高校漢語(yǔ)言文學(xué)專業(yè)的基礎(chǔ)課程,講述的是以來,我國(guó)一百多年的文學(xué)發(fā)展史。文學(xué)歷史與社會(huì)歷史密切相關(guān),具有極強(qiáng)的時(shí)代性。從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huì)主義革命與建設(shè),百年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走向強(qiáng)起來的奮斗歷程和不斷實(shí)現(xiàn)的民族愿景,在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中都有著濃墨重彩的記錄。中國(guó)人民自強(qiáng)不息、救亡圖存、為民族解放和復(fù)興不懈奮斗的精神,化為一幅幅真實(shí)、形象、生動(dòng)、感人的文學(xué)圖景,升騰為最深沉、真摯的家國(guó)情懷,積淀在一代代學(xué)子心中,最終匯成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生生不息。五四文學(xué)濫觴于蒿目時(shí)艱的社會(huì),傳播于長(zhǎng)歌當(dāng)哭的時(shí)代。個(gè)人自立、民族自強(qiáng)的歷史必然要求敲響了時(shí)代的大門,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的左翼文學(xué)、抗戰(zhàn)文學(xué)、解放區(qū)文學(xué),當(dāng)代文學(xué)中的革命歷史題材文學(xué)都真實(shí)地記錄了中國(guó)革命艱難的奮斗歷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當(dāng)代社會(huì)生活成為作家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源泉。這些植根于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偉大實(shí)踐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所體現(xiàn)出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黨領(lǐng)導(dǎo)人民在革命、建設(shè)、改革中創(chuàng)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huì)主義先進(jìn)文化,必將更加堅(jiān)定學(xué)生的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在無(wú)數(shù)藍(lán)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著一雙寶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驕傲,我是中國(guó)人!在無(wú)數(shù)白色的皮膚和黑色的皮膚之中,我有著大地般黃色的皮膚,我驕傲,我是中國(guó)人!”回響在詩(shī)人王懷讓詩(shī)作中響徹云霄的吶喊,從歷史中走來,又奔向未來。它必將在青年人心中激起最澎湃的浪花,同黃土高原、黃河長(zhǎng)江、長(zhǎng)城泰山一樣,挺起胸膛、沸騰熱血、揚(yáng)起手臂,永遠(yuǎn)堅(jiān)實(shí)地站立在中華沃土上。不僅如此,“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還在回答和呼應(yīng)青年人的困惑中,啟發(fā)他們思索,引起其情感認(rèn)同和價(jià)值認(rèn)同。比如,青春應(yīng)該怎樣度過?怎樣的青春才是最有意義和價(jià)值的?對(duì)于這些問題,楊沫的《青春之歌》、王蒙的《青春萬(wàn)歲》給出了最生動(dòng)的回答。舒婷也在《致橡樹》中對(duì)木棉致橡樹的意象化書寫中,詮釋了對(duì)愛情真諦的理解。這些必將對(duì)青年人樹立正確的戀愛觀、價(jià)值觀起到潛移默化的引導(dǎo)作用。
二、創(chuàng)新教育理念,筑牢德育新高地
2018年5月,在與北京大學(xué)師生座談時(shí)指出:“要把立德樹人的成效作為檢驗(yàn)學(xué)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標(biāo)準(zhǔn),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斷提高學(xué)生思想水平、政治覺悟、道德品質(zhì)、文化素養(yǎng),做到明大德、守公德、嚴(yán)私德。”這是新時(shí)期對(duì)高校教育提出的新任務(wù)。泰山學(xué)院一直把德育工作放在學(xué)校教育的中心位置,早在2012年就啟動(dòng)了“德育系統(tǒng)工程”,將立德樹人貫穿到教育教學(xué)全過程。文學(xué)與傳媒學(xué)院最先響應(yīng),在全院建立起了覆蓋各門課程、各個(gè)教育環(huán)節(jié)的課程德育體系,制定了詳盡的課程德育大綱,打造了課程德育的經(jīng)典案例和課堂。“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具有豐富的德育資源,但將散落的德育珍珠挖掘和培育出來,就需要在教學(xué)思路和理念上多下功夫。(一)德育與文本解讀相結(jié)合。“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有自身的特點(diǎn),文學(xué)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因此,對(duì)德育資源的挖掘,不能脫離文學(xué)作品本身,不能生硬拔高文學(xué)作品的主題。必須在細(xì)致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主題內(nèi)容、時(shí)代背景、作家經(jīng)歷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引發(fā)思考、加以引導(dǎo)。比如,在講授現(xiàn)代作家作品時(shí),通過剖析“棄醫(yī)從文”這一普遍現(xiàn)象,幫助學(xué)生理解作家的文學(xué)道路選擇問題。為什么一大批作家諸如魯迅、郭沫若等,要走上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道路?文學(xué)對(duì)于作家自身乃至對(duì)于中國(guó)社會(huì)起到什么作用?一個(gè)個(gè)問題的拋出,必將引導(dǎo)學(xué)生深入思考。一個(gè)個(gè)進(jìn)步作家“拍案而起”,弘揚(yáng)正義、為國(guó)為民吶喊的身影,也必將更進(jìn)一步激發(fā)學(xué)生的愛國(guó)情懷。(二)將德育融入情感共鳴。文學(xué)是人學(xué),人類共同的情感是理解文學(xué)作品的關(guān)鍵。“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中的經(jīng)典作品無(wú)一不能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這種共鳴建立在共同的價(jià)值認(rèn)同基礎(chǔ)上,可以感染,可以傳遞,在給予人類普世性情感的同時(shí),也起到陶冶情操、塑造人格的德育作用。教師在講授《紅巖》中江姐的形象時(shí),不僅把她當(dāng)作一位革命戰(zhàn)士,還可以啟發(fā)學(xué)生從母親、妻子、女兒的角度來理解主人公犧牲的精神,并以“你能做到嗎”這樣的啟發(fā)式提問,讓學(xué)生反躬自省,感同身受。(三)德育與美育相互滲透。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一生身體力行提倡美育,他說:“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由于感情推動(dòng)力的薄弱。要轉(zhuǎn)弱而為強(qiáng)、轉(zhuǎn)薄而為厚,有待于陶養(yǎng)。陶養(yǎng)的工具,為美的對(duì)象,陶養(yǎng)的作用,叫作美育。”艾青也曾說:“我們的詩(shī)神是駕著純金的三輪馬車,在生活的曠野上馳騁的。那三個(gè)輪子,就是真、善、美。”在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純金的“三輪馬車”比比皆是,必將深深感染學(xué)生,成為他們向真、向善、向美的力量和榜樣!
三、教學(xué)與德育相融合,探索德育滲透新路徑
為更好地讓“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中的德育元素產(chǎn)生更好的教育效力,還需要繼續(xù)深化教學(xué)改革,創(chuàng)新教學(xué)方法。(一)將文學(xué)課程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相結(jié)合。2020年的肺炎疫情,打亂了很多人的生活。在線上教學(xué)實(shí)踐中,教師結(jié)合戰(zhàn)“疫”實(shí)際,堅(jiān)持思想引導(dǎo)與課程德育相結(jié)合,助力戰(zhàn)“疫”宣傳,鼓勵(lì)學(xué)生與國(guó)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yùn),增強(qiáng)師生戰(zhàn)勝疫情的信心。一是在課程開始前錄制了防疫溫馨小提示,呼吁學(xué)生做好自身防護(hù),配合國(guó)家防疫工作。二是帶領(lǐng)學(xué)生重溫食指的《相信》,用詩(shī)歌凝聚師生戰(zhàn)“疫”必勝的信念。讓學(xué)生在課程學(xué)習(xí)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個(gè)人命運(yùn)與國(guó)家命運(yùn)相連,14億中華兒女在行動(dòng),海外無(wú)數(shù)的華人華僑也在行動(dòng),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學(xué)生的民族自豪感。三是鼓勵(lì)學(xué)生撰寫聯(lián)播報(bào)道《一線抗疫群英譜》,激勵(lì)學(xué)生用自己的方式謳歌抗疫英雄,讓線上教學(xué)成為愛國(guó)主義教育的新陣地、疫情防控的主戰(zhàn)場(chǎng)。(二)搭建德育教學(xué)的廣闊平臺(tái)。廣闊的社會(huì)生活、豐富的社會(huì)實(shí)踐,也是課程德育的重要陣地。在講述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英雄譜時(shí),教師將身邊的英雄與之融合。泰山消防中隊(duì)在2010年被國(guó)務(wù)院、中央軍委授予“泰山衛(wèi)士”榮譽(yù)稱號(hào)。2019年12月,以“泰山衛(wèi)士”消防英雄們的故事為藍(lán)本,教師帶領(lǐng)學(xué)生自編、自導(dǎo)、自演了一場(chǎng)以紀(jì)念授稱九周年為主題的大型情景劇《讓紅旗高高飄揚(yáng)》,將英雄的故事穿越到了今天,將德育課堂搬到了舞臺(tái),使其成為新型思政課堂的范例,實(shí)現(xiàn)了讓學(xué)生排演一場(chǎng),接受一次思想教育的目標(biāo)。在劇本創(chuàng)作階段,教師還多次組織學(xué)生赴泰山中隊(duì)采風(fēng),通過實(shí)地走訪、體驗(yàn)生活,讓學(xué)生更加真實(shí)地感受“泰山衛(wèi)士”精神,更加懂得什么是使命擔(dān)當(dāng),什么是舍己為人。“消防救援”“泰山衛(wèi)士”成了學(xué)生熱議的焦點(diǎn)與話題,“火焰藍(lán)”“藍(lán)朋友”成為學(xué)生心中的顏值擔(dān)當(dāng)。
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教學(xué)改革分析論文
摘要:“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是高校漢語(yǔ)言文學(xué)專業(yè)的一門專業(yè)基礎(chǔ)課程,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審美性特征。然而該課程在現(xiàn)行的教學(xué)中存在著諸多問題,教學(xué)改革勢(shì)在必行。作為教師,首先要從改革課程教學(xué)內(nèi)容入手,做到經(jīng)典性與人文性、審美性相結(jié)合,力求使學(xué)生的審美能力和人文素質(zhì)有所提高;其次要嘗試多種教學(xué)方法與現(xiàn)代化教學(xué)手段。
關(guān)鍵詞:課程體系;教學(xué)方法;教學(xué)手段;教學(xué)改革
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是高校中文系一門重要的專業(yè)基礎(chǔ)課,同時(shí)由于它與現(xiàn)實(shí)聯(lián)系緊密,對(duì)學(xué)生的人文素質(zhì)提高有較大影響。筆者在從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教學(xué)十多年的實(shí)踐中,力求把教書育人的宗旨貫徹其中,通過本課程的教學(xué),提高學(xué)生的審美能力,增強(qiáng)學(xué)生的文素質(zhì),為培養(yǎng)高素質(zhì)的人才搭建一個(gè)教學(xué)的平臺(tái)。近幾年來,為了適應(yīng)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新形勢(shì),尤其在深化教學(xué)改革、推進(jìn)素質(zhì)教育、實(shí)施教育創(chuàng)新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嘗試,取得了良好的教學(xué)效果。
一是改革課程教學(xué)內(nèi)容,力求使學(xué)生的審美能力和人文素質(zhì)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教學(xué),是一種典型的知識(shí)型教學(xué),主要是從歷時(shí)的角度梳理文學(xué)史的線索,在此基礎(chǔ)上,評(píng)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學(xué)現(xiàn)象和文學(xué)潮流,目的是使學(xué)生獲得應(yīng)有的文學(xué)史知識(shí)。而作為文學(xué)史最基本的構(gòu)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審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紛繁的文學(xué)史知識(shí)和抽象的理論分析所遮蔽和掩蓋,并沒有充分發(fā)揮它在培養(yǎng)學(xué)生審美能力、提高學(xué)生人文素質(zhì)方面的潛在功能。從教學(xué)實(shí)踐看,許多同學(xué)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名作的理解,過于依賴文學(xué)史教材中的學(xué)術(shù)定論,而忽略了個(gè)體在閱讀文學(xué)作品的過程中對(duì)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將自身的情感體驗(yàn)、生命意識(shí)融入對(duì)作品的審美體驗(yàn),因而雖然獲得了知識(shí),但對(duì)自身的人格養(yǎng)成和素質(zhì)培養(yǎng)并未產(chǎn)生太大的影響。加之課時(shí)的限制,如當(dāng)代文學(xué)部分在我校是開設(shè)一個(gè)學(xué)期,每周3個(gè)課時(shí),卻要講授從1949年到1997年近50年的內(nèi)容,更使得這種講授淺嘗輒止。為使這種知識(shí)型的教學(xué)模式向素質(zhì)型的教學(xué)發(fā)生轉(zhuǎn)變,筆者在教學(xué)改革中,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選》教學(xué)大綱做了較大調(diào)整,在宏觀把握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發(fā)展脈絡(luò)的前提下,把教學(xué)的重心傾斜到了作品方面。緒論部分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概念、分期、發(fā)展概況、重要的文學(xué)史事件進(jìn)行介紹,通過這部分內(nèi)容,學(xué)生對(duì)50年的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就有了一個(gè)整體的輪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選能夠覆蓋當(dāng)代文學(xué)三個(gè)發(fā)展階段的十幾部作品進(jìn)行精講,作品的選擇原則是既要考慮審美性,又要兼顧文學(xué)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時(shí)在文體方面兼顧小說、詩(shī)歌、散文、戲劇多種體裁。
與所講篇目有關(guān)的文學(xué)史知識(shí)會(huì)在篇目講授時(shí)再次強(qiáng)化,以區(qū)別于一般的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鑒賞,這樣在講授過程中就能進(jìn)一步把文學(xué)史教學(xué)具體深入到作品的閱讀和解析中去,雖然講授篇目不多,卻能通過引導(dǎo)學(xué)生細(xì)致深入的閱讀和體驗(yàn)作品的思想與藝術(shù)特質(zhì),把獲取文學(xué)知識(shí)、提高審美能力、增強(qiáng)人文素質(zhì)結(jié)合起來,在學(xué)習(xí)本課程的同時(shí),不知不覺地接受藝術(shù)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潤(rùn)。內(nèi)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傳統(tǒng)表述主題思想、人物形象、藝術(shù)特色等幾個(gè)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詩(shī)意或哲理的小標(biāo)題,如“人———詩(shī)意的棲居”、“了悟死亡”、“活著,永遠(yuǎn)的追問”等,給學(xué)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觀上也給予了學(xué)生美的感受。
為了彌補(bǔ)講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節(jié)課就擬定了一份本課程的必讀書目,讓學(xué)生課下閱讀,并要求他們制作索引卡片,寫出評(píng)論摘要和自己的閱讀感悟,期末檢查評(píng)分,作為平時(shí)成績(jī)的一部分計(jì)入期末總成績(jī)。每堂課后再為他們提供與本節(jié)課有關(guān)的閱讀文獻(xiàn)與參考資料,使學(xué)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資訊,拓寬了學(xué)生的學(xué)術(shù)視野。同時(shí)我還要要求他們充分利用教材。本課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棟霖等主編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該書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jì)教學(xué)內(nèi)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jì)劃”的研究成果,被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公認(rèn)為本專業(yè)和本課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著重從“文本”的角度出發(fā),在編寫方法上,注重宏觀考察與微觀分析相結(jié)合;在編寫內(nèi)容上,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經(jīng)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講述和評(píng)析。配套作品選(四卷)更保證了學(xué)生的一定閱讀量。與學(xué)界其他《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相比,它有著突出的優(yōu)勢(shì),即所觸及的內(nèi)容相當(dāng)扎實(shí)、條理清晰、詳略得當(dāng)。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結(jié)合,力爭(zhēng)多角度、多維度、多側(cè)面地向讀者展示現(xiàn)代文學(xué)史豐富的內(nèi)蘊(yùn)。教材編寫重點(diǎn)旨在培養(yǎng)學(xué)生獨(dú)立思考、閱讀、寫作和批判、審美能力。正因?yàn)榻滩木哂邢冗M(jìn)性,因此對(duì)教材的研讀成為學(xué)生必做的功課。這樣,課內(nèi)與課外結(jié)合,點(diǎn)與面結(jié)合,經(jīng)典性、人文性與審美性結(jié)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熱門標(biāo)簽
當(dāng)代藝術(shù) 當(dāng)代文化論文 當(dāng)代文學(xué) 當(dāng)代文學(xué)論文 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發(fā)展 當(dāng)代學(xué)生論文 當(dāng)代社會(huì) 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 當(dāng)代青年 當(dāng)代價(jià)值
相關(guān)文章
3戲曲音樂元素在當(dāng)代音樂創(chuàng)作的應(yīng)用
4當(dāng)代手工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批評(píng)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