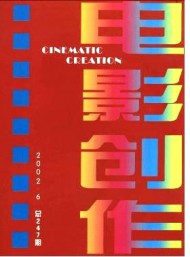電影敘事范文10篇
時間:2024-01-19 15:26:42
導(dǎo)語: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yàn),為你推薦的十篇電影敘事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文人電影改編敘事研究
摘要: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和商業(yè)電影大肆興起,傳統(tǒng)“人”的文學(xué)和文人電影似乎正在失去一隅領(lǐng)地。一方面現(xiàn)代知識分子能夠在“超然”于自己的專業(yè)領(lǐng)域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的同時,力爭追求難能可貴的“介入”,懷有嚴(yán)肅的社會使命感,是其突圍的主觀前提。另一方面,如何通過探究兩種不同媒介的敘事規(guī)律以完成二者之間成功的敘事轉(zhuǎn)換,是其突圍的根本條件。小說《推拿》和電影《推拿》在敘事視角、敘事時空、情節(jié)結(jié)構(gòu)方面都完成了較為出色的轉(zhuǎn)化,靈魂相通而不失個性,具有范式意義。
關(guān)鍵詞:文人電影;《推拿》;敘述視角;敘事時空;情節(jié)結(jié)構(gòu)
一、前言:“人”的文學(xué)與“文人電影”的發(fā)展瓶頸
自電影濫觴以來,電影對文學(xué)作品的改編一直長盛未衰,并成為文學(xué)和電影融合的最直接最普遍方式。究其原因,這兩個藝術(shù)門類創(chuàng)作方式的互通性和兼容性是最主要的原因。除了將文學(xué)改編成電影,柴春芽在其電影處女座《我故鄉(xiāng)的四種死亡方式》上映先后,出版了同名“電影小說”;程耳在《羅曼蒂克消亡史》上映的同時,出版了同名小說,但兩者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文學(xué)改編,故事上相對獨(dú)立。近年來又出現(xiàn)了影視劇為先,小說創(chuàng)作為后的方式,被稱為Biop-ic。電影和文學(xué)正在形成更多樣化的互動模式。然而,站在當(dāng)代知識分子的角度,應(yīng)該認(rèn)識到:如果將文學(xué)改編電影作為傳統(tǒng)“人”的文學(xué)發(fā)展的一個有效新方向,其中依然存在著嚴(yán)峻挑戰(zhàn)。(一)文人電影在這里,筆者首先想厘清“文人電影”的概念。“文人電影”最早是中國香港學(xué)者對上世紀(jì)30年代的大陸電影進(jìn)行研究時,廣泛運(yùn)用的一個稱謂,是一個表現(xiàn)文人文化,有著相對獨(dú)立審美內(nèi)涵和文化特征的電影形態(tài),富于人文關(guān)懷[1]10-11。孟憲勵受“戲人電影”與“文人電影”兩個概念的啟發(fā),從中國兩大文化傳統(tǒng)對中國電影史進(jìn)行了整體性的高度概括。以敘事為主的史傳文學(xué)成為粗俗清新、長于敘事的“民間文學(xué)”的藍(lán)本,直接投射在電影中則形成了主題鮮明、矛盾沖突明顯、敘事結(jié)構(gòu)完整、人物性格鮮明的“戲人電影”。詩歌或具有詩歌精神的文學(xué)成為高雅精致、注重抒情的“文人文學(xué)”的源頭,被電影吸收后演變?yōu)榍楣?jié)弱化或退隱、抒情性文藝精神作為主導(dǎo)、運(yùn)用頗具特色的鏡頭語言的“文人電影”[2]37-43。吳琦定義“文人電影”為“在市場日益繁榮的環(huán)境之下,潛心建構(gòu)屬于中華文化基因譜系的電影類型。”綜上所述,把握文人電影需要抓住兩個關(guān)鍵點(diǎn):一是創(chuàng)作手法重抒情和詩意,一是作品精神上注重文化內(nèi)涵和人文關(guān)懷。(二)外部:文化工業(yè)時代神圣性的缺失在西方啟蒙思潮發(fā)展進(jìn)程中,隨著工具理性與政治權(quán)威合流,啟蒙之光竟成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后現(xiàn)代文化工業(yè)的重要推手,這導(dǎo)致了反啟蒙思潮的興起。后知后覺的中國社會,厚積薄發(fā)的啟蒙根系天生缺乏,平穩(wěn)漸進(jìn)的啟蒙之路難以維系,救亡讓啟蒙幾乎流產(chǎn)。隨著90年代的經(jīng)濟(jì)大發(fā)展,中國啟蒙又遇到另一個重要敵人———世俗文化。文化工業(yè)時代[3]、“娛樂至死”[4]、世俗社會神圣化的消亡,成為我們所處時代的關(guān)鍵特征。尤其到了新世紀(jì)以后,商業(yè)消費(fèi)的利益原則滲透到文化的各個角落。“新世紀(jì)文學(xué)的空前變化,從表面看似乎源自于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蓬勃興起,本質(zhì)上卻是信息革命引發(fā)的文化價值系統(tǒng)的轉(zhuǎn)化與重組。”[5]繁而不榮、多而不精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攜手影視產(chǎn)業(yè),更多以文化商品的屬性定義自己,對傳統(tǒng)意義上“人”的文學(xué)的發(fā)展提出了嚴(yán)峻的挑戰(zhàn)。就本文討論的主體對象———由畢飛宇長篇小說《推拿》改編的同名電影而言,上映5天僅200萬票房,院線排片不到0.3%,卻奪得柏林電影節(jié)、金馬、金像、金雞等多項(xiàng)大獎[6],這些數(shù)據(jù)將該片置于叫好不叫座的尷尬境地。相反,網(wǎng)絡(luò)大IP生動的收視和票房紀(jì)錄①對文人電影所造成的失衡的、扭曲的壓倒性排擠。“文學(xué)改編不僅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在文化工業(yè)體系中,它還是文化商品的生產(chǎn)方式”[7]62,這一點(diǎn)是文化工業(yè)時代不得不承認(rèn)并面對的現(xiàn)實(shí)。在世俗文化和“戲人電影”的壓迫之下,“人”的文學(xué)和文人電影的突圍是悲壯的、孤獨(dú)的、痛苦的。即便如此,現(xiàn)代知識分子仍應(yīng)認(rèn)清并堅守自我本位,即“在‘超然’于自己的專業(yè)領(lǐng)域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的同時,追求難能可貴的‘介入’,懷有嚴(yán)肅的社會使命感”[8]103-104。(三)內(nèi)部:文學(xué)改編規(guī)范性和創(chuàng)造性缺失在厘清了“文人電影”的概念之后,梳理中國當(dāng)代電影文學(xué)改編史,導(dǎo)演們?nèi)〔挠谖膶W(xué),尤其是中國大陸第五代導(dǎo)演和中國香港新浪潮導(dǎo)演,致力于探索文學(xué)改編成文人電影的內(nèi)部規(guī)律,但其電影作品藝術(shù)高度的不穩(wěn)定性,是文學(xué)改編理論不完善現(xiàn)狀的直接表征。例如:張賢亮的短篇小說《浪漫的黑炮》在作家的所有作品中名不見經(jīng)傳,但由黃建新執(zhí)導(dǎo)的改編電影《黑炮事件》卻因精巧的視聽設(shè)計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了光輝一筆。電影中藝術(shù)化的開會場面成為經(jīng)典一幕。在蒙太奇的完美剪接中,電影將小題大做、形式化、古板的中國式辦事風(fēng)格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而這強(qiáng)烈的觀感背后,是80年代維護(hù)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時代隱意。反之,王安憶的《長恨歌》算得上作家的出色代表作,但由關(guān)錦鵬執(zhí)導(dǎo)的同名電影卻反響平平,甚至被學(xué)者評價為“失去靈魂的改編”。與關(guān)錦鵬的其他影片相比,這部影片更像是一部簡略而生硬的小說介紹,片中的上海灘被桎梏在導(dǎo)演故作小資的視聽世界中,將城市變遷的大情懷僅僅講成了一段女人的愛恨浮沉。從文學(xué)到電影,如何從“研究不同媒介的敘事作品的性質(zhì)、形式和運(yùn)作規(guī)律,以及敘事作品的生產(chǎn)者和接受者的敘事能力”[9]110的角度,在把握原作靈魂的基礎(chǔ)上探究兩種不同媒介之間的敘事轉(zhuǎn)換是本文的核心。
二、《推拿》的兩種敘事視角
“當(dāng)我的目光再也不能聚焦、再也沒法造型的時候,我知道,我的瞳孔只剩下了光感,我的面部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盲態(tài),我的臉上布滿了華而不實(shí)的表情。”畢飛宇在《推拿》的《序》中如是說。當(dāng)作家失去“聚焦”和“造型”的本領(lǐng),便呈現(xiàn)出一種盲態(tài)“聚焦”和“造型”,構(gòu)成了作家寫作的基本過程。明晰了“看”和“說”的分野,熱奈特提出三種聚焦———“零聚焦”“內(nèi)聚焦”和“外聚焦”。“零聚焦”是無所不知的上帝視角;“內(nèi)聚焦”是彰顯人物個體讓人物來看來感知的視角;“外聚焦”是旁觀的客觀記錄視角。在這里,筆者欲將小說和電影的敘事視角進(jìn)行特征化的提煉并加以區(qū)別分析。(一)小說熱表達(dá):人性平等的內(nèi)聚焦視角+邏輯嚴(yán)密的全知視角畢飛宇在《推拿》中將視角聚焦到“主流社會”意義上的邊緣人物———盲人群體。《推拿》末章《夜宴》中的一段話對理解“聚焦”起到了啟示作用:“都說盲人的生活單調(diào),這就要看怎么說了。這就要看盲人們愿意不愿意把心掏出來看看了。不掏,挺好的,每一天都平平整整,每一個日子都像是從前的日子拷貝出來的,一樣長,一樣寬,一樣高。可是,掏出來一摸,嚇人了,盲人的日子都是一副離奇古怪的模樣。”[10]233首先,聚焦的核心是讓盲人“掏心”;其次,是盲人“愿意不愿意”;最后,畢飛宇用“一樣長,一樣寬,一樣高”三個盲人詞匯來代替一切感知。誠如以上所說,對健全人擁有生理優(yōu)勢之后隨之膨脹的心理優(yōu)勢進(jìn)行了深刻反思,敘述者并沒有將自己置于盲人所敬畏的“神靈”位置。筆者認(rèn)為,這是該小說的敘事前提和心理基礎(chǔ)。盲人心中有眼睛的主流社會具有神靈的意味,而大多數(shù)健全人對盲人的精神世界缺乏揣摩知之甚少。這從根本上就造成了兩個世界之間不對等的隔閡。敘述者用自由間接引語的敘述語言和盲人內(nèi)聚焦的敘述視角,構(gòu)成了隱身敘述者+人物視角的敘述方位②。諸如此例:正常人對殘疾人“自食其力”的夸贊,在盲人心里的潛臺詞也許是“這是多么荒謬、傲慢、自以為是的說法。就好像殘疾只要沒餓死,沒凍死,很了不起了”;泰來在形容金嫣的好看時,用了“和紅燒肉一樣好看”這樣生動的只屬于盲人審美系統(tǒng)的詞匯。在這個過程中,作者讓盲人給常人的“掃盲”,并成功將邊緣化的盲人中心化。小說敘述者更多地站在全知的角度,即“零聚焦”視角,將“沙宗琪推拿中心”作為中心,從這個地理中心輻射出沙復(fù)明、張宗琪、小馬、都紅、金嫣等盲人作為故事主角,再以人物為發(fā)散點(diǎn),突破時空界限,插敘了每個人來到推拿中心之前的故事,在間斷的散文式結(jié)構(gòu)之下,鋪就了一張完整的邏輯網(wǎng)。都紅的鋼琴事件彰顯了她超強(qiáng)的自尊心,這與她最終受傷后無法接受大家的救濟(jì)而出走,具有本質(zhì)上的精神共通;張宗琪的防毒事件對他和沙復(fù)明的“對陣”和“分家”之必要性做出了合理的解釋;沙復(fù)明的兩小時戀愛讓他產(chǎn)生了通過與正常人談戀愛進(jìn)入“主流社會”的信仰,這襯托出他后來為了追求都紅的“看不見的美”而放棄信仰是多么真誠。作者將“內(nèi)聚焦”視角運(yùn)用在盲人的平等表達(dá)中,將全知視角運(yùn)用在邏輯的鋪陳和建構(gòu)中,而非鞏固由高高在上的上帝視角帶來的心理優(yōu)勢。剝開盲人看似無趣的日子,作者用開闊,深邃,從頭至尾洋溢著令人沉醉的體溫的言辭和語匯,現(xiàn)出一個逐漸升溫的過程,“一小部分蕩漾起來,蕩漾連成了片,波浪千軍萬馬……”。運(yùn)用皮爾斯的符號三分法進(jìn)行分析,雖然中國文字來源于象形文字,在本源與肖似符號性質(zhì)相通。但漢字演化到今天,大多以冷靜客觀的象征符號形態(tài)出現(xiàn),與它所表征的對象之間沒有直接必然的聯(lián)系,它的意義的產(chǎn)生更多需要人運(yùn)用想象力或約定俗成的意義系統(tǒng)。正因如此,文字之“冷”需靠作家的情感之“熱”來調(diào)動觀眾的情感想象,以達(dá)到移情效果。(二)電影冷處理:紀(jì)錄片的“超然”+藝術(shù)片的“介入”按藝術(shù)形態(tài)的感知方式為標(biāo)準(zhǔn)來區(qū)分,文學(xué)屬于想象藝術(shù)而電影屬于視聽藝術(shù)。婁燁導(dǎo)演深知用鏡頭難以描摹的,正是天馬行空的想象語言。然而,跳脫文學(xué)的敘事框架,婁燁認(rèn)為“電影的沖擊力恐怕還在于那種身體感受”[11]。而這種沖擊力,即指畫面和聲音先作用于受眾生理而后滲透到心理的直觀感染力。關(guān)于電影敘事視角,若斯特將熱奈特的敘事角度一分為三,包括所知角度、視覺角度和聽覺角度[12]93。與傳統(tǒng)全知視角的小說相對應(yīng),電影所知角度中的“觀眾所知角度”,即為觀眾比劇中人物知道得早或者多的情況。顯然,在影片《推拿》中,導(dǎo)演承襲了畢飛宇出于人性關(guān)照的平視心態(tài),只是保留了觀眾在視覺上的生理優(yōu)勢,而不是通過有意的視角設(shè)計來突出觀眾的心理優(yōu)勢,導(dǎo)演更多地使用了人物所知角度(影片中人物的行為動作出乎觀眾意料)和內(nèi)知角度(觀眾既看得到人物經(jīng)歷的事又知道人物腦中所想)。針對這兩種情況,筆者將做詳細(xì)論述。1.人物所知角度:以“冷”載“熱”的紀(jì)錄片。一直以來,《推拿》因?yàn)槠浯竽懚址诺募o(jì)錄式美學(xué)而被認(rèn)為是具有革新性的美學(xué)實(shí)驗(yàn)。推拿中心雜亂平常的背景、本色出鏡的非專業(yè)演員、虛焦搖晃的紀(jì)錄式鏡頭……日常化、生活化、真實(shí)化的敘述對象和敘述手段,正是導(dǎo)演所要呈現(xiàn)的“沖擊力”的源頭。對于這種有悖于正常敘事美學(xué)的“錯誤”,導(dǎo)演有意為之,旨在呈現(xiàn)一種原始而震撼的盲人美學(xué)系統(tǒng)。導(dǎo)演打破偶像劇中郎才女貌的慣例,觀眾看到帥氣的郭曉冬(飾演王大夫)真的與張磊(飾演小孔)在一起親昵、形影不離。演員外貌不匹配給觀眾造成一定的感官震撼。與沒有以貌取人的盲人世界相比,健全人的世界可能存在更多虛假和看不到的陰暗。真正的愛情也許根本就不需要眼睛,也許我們正處在“主流社會”的盲態(tài)中失去辨別真心的能力。與以上這種“自然”流露的沖擊力相比,事件高潮的沖擊力,是直觀強(qiáng)烈的。在小孔去男生宿舍串門的橋段中小孔和小馬滿是肌膚之親的打鬧、沙復(fù)明試圖從都紅臉上模出“美”來、王大夫拿菜刀瘋狂地割傷自己、小馬因內(nèi)疚對著嫂子扇自己耳光……當(dāng)盲人用心地表達(dá)自己的情感時,無論是歡騰、焦急、悲憤、愧疚,演員的表演都近乎扭曲甚至變態(tài),直勾勾的眼神有強(qiáng)大的穿透力。這些段落,畫面和音樂卻出奇地平淡,毫無介入感。用客觀記錄的方式記錄主觀情感流露,以“冷”載“熱”,導(dǎo)演在這中間找到了平衡。2.內(nèi)知角度:主觀窺探的藝術(shù)片。小說中,小馬在時間感知中自我塑造、小馬對于嫂子的向往、金嫣關(guān)于婚禮的崇拜等段落,作者的描寫天馬行空,構(gòu)成了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中最為羅曼蒂克的段落,讓人久久回味。然而,把這些精彩的心理描寫移植到電影中,卻是難上加難。對此,導(dǎo)演在表現(xiàn)人物內(nèi)心活動時多選用內(nèi)知角度,用藝術(shù)片式的“介入”,即通過主觀鏡頭和主觀聲音絲絲入扣地表現(xiàn)出人物的心理變化。在視覺方面,內(nèi)知角度主要通過鏡頭的內(nèi)視覺角度,即主觀鏡頭實(shí)現(xiàn)的。例如,當(dāng)小孔第一次來到推拿中心迎面遇到小馬時,小馬也許是被一陣女人的氣息所吸引,立刻對小孔產(chǎn)生了獨(dú)特的關(guān)注。鏡頭隨之變成了小馬的主觀鏡頭———遠(yuǎn)遠(yuǎn)窺視小孔。雖然盲人無法真正“看”到,但視覺方向也是其心理狀態(tài)的直觀體現(xiàn)。片中用到極致的主觀鏡頭,是表現(xiàn)小馬失明前的恐慌迷離和被打后恢復(fù)模糊視力的狂喜的主觀鏡頭,極度搖晃、模糊、暗沉。江逐浪提出了影像轉(zhuǎn)化內(nèi)聚焦敘事的一個悖論:“影像不善于表達(dá)人物內(nèi)心,現(xiàn)代科技運(yùn)用地越來越繁復(fù),越能表達(dá)人物內(nèi)心,但也使影像創(chuàng)作者對內(nèi)聚焦的主觀控制程度越大。”[13]85出于這一點(diǎn),她認(rèn)為很多電影對于文學(xué)作品中讓人物自己敘述的“內(nèi)聚焦”轉(zhuǎn)化并沒有真正徹底地完成。筆者認(rèn)為,充分利用鏡頭內(nèi)外視角的切換以表達(dá)豐富的畫面意義,比一味地為了追求人物“內(nèi)聚焦”而純粹追求用客觀表達(dá)主觀的處理方式更加合理。正如婁燁自己所說:“一個專門為象征或隱喻工作的作品是沒什么價值的。”[11]3在聽覺方面,婁燁說“這是一部聲音為先的電影”,主要通過旁白、主觀音樂和主觀音響的介入方式來完成內(nèi)知視角。首先,片頭業(yè)余女聲的旁白配以白底黑字的畫面,向觀眾交代了片名、主創(chuàng)名單等重要信息,對盲人光感感知和聲音感知的方式給予了十分的關(guān)懷。其次,將幾乎原封不動摘抄自原文的大段旁白穿插在故事當(dāng)中,是原文思想最為直接的體現(xiàn),也是一種最原始的主觀介入。這樣的處理方式,讓這部充滿了文學(xué)性的人文電影擁有了些許的文學(xué)厚重感。在小說中,聲音對小馬心理變化的描寫起到關(guān)鍵作用。小說中,小馬從極度狂躁企圖輕生,到安寧沉默;到“嫂子”出現(xiàn)之后一潭靜水被撩撥起漣漪,再到最后小蠻出現(xiàn)后終于重歸寧靜。小說中小馬這段精彩的心理變遷移植到影片中,被聲音完美翻譯:他用瓷器碎片割破自己脖頸的一刻,類似耳鳴的聲音出現(xiàn),鏡頭緊接著進(jìn)入到他在盲校的生活,不安、焦躁、壓抑的耳鳴聲和學(xué)校的客觀聲音相互交疊,逐漸后者變強(qiáng)前者消逝。音樂變化的過程,也是小馬從起初的狂暴到慢慢接受現(xiàn)實(shí)的變化過程。諸如此類,主觀音樂的介入,是心理暗示的重要信號。不得不說,導(dǎo)演即使在使用主觀介入的視角時,仍然保持著與客觀表達(dá)一樣的低明度、冷色調(diào),音樂也以“安于幕后”的配角姿態(tài)出現(xiàn)。導(dǎo)演用禁欲式的視聽展現(xiàn)人的原始欲望,用非理性敘事去揭示現(xiàn)實(shí)中缺失的理性。
電影敘事分析論文
中國早期電影:民族民間故事的引入
中國電影產(chǎn)生于一種異常錯雜的語境,正是這種特殊的語境制約著中國早期電影的敘事格局。在《現(xiàn)代中國電影史略》(1936)中,鄭君里相當(dāng)深入地分析和闡發(fā)了“推動并約制”中國影業(yè)前程進(jìn)而顯現(xiàn)中國電影發(fā)展“規(guī)律性”的各種“矛盾的總和”①。實(shí)際上,無論是“藝術(shù)性”與“民族文化”之間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還是“帝國主義國家”與“半殖民地”的文化事業(yè)在“投資”方面的矛盾;無論是中國電影的“企業(yè)性質(zhì)”與“文化運(yùn)動”之間的關(guān)系,還是電影的“藝術(shù)性”與“商業(yè)性”之間很難調(diào)和的矛盾;甚至半殖民地的“電影技術(shù)條件的落后”等許多問題,都是中國早期電影不可回避也無法克服的癥結(jié)之所在。在這里,中外文化相互交織,新舊思想彼此對話,而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在政治、經(jīng)濟(jì)與文化方面的強(qiáng)勢地位,跟半殖民地的弱勢中國形成鮮明的反差;“中學(xué)”與“西學(xué)”、“舊學(xué)”與“新學(xué)”之間的不期而遇和劇烈沖突,也將中國早期電影置于一種前所未有的復(fù)雜境地。
這種令人迷惑的錯雜語境,制約著中國早期電影的敘事格局。毫無疑問,歐美電影的輸入激發(fā)了中國電影的創(chuàng)業(yè)熱情,而中國電影也確實(shí)需要向歐美電影學(xué)習(xí)許多基本的表達(dá)技藝,包括“故事”的選擇及其講述方式。頗有意味的是,在20世紀(jì)20年代前后進(jìn)入中國的歐美電影中,一度非常盛行的瘋狂鬧劇和偵探長片,并沒有引發(fā)中國電影的跟風(fēng)潮流;此后美國的各種類型影片和歐洲的藝術(shù)電影,盡管在中國的普通觀眾和電影輿論中享有不錯的口碑,也沒有真正促動中國電影的模仿心理。誠然,包括卓別林(CharlieChaplin)、羅克(HaroldLioyd)、格里菲斯(D.W.Griffith)、朗(F.Lang)、西席·地密爾(CecilB.Demille)與恩斯特·劉別謙(ErnstLubitsch)等在內(nèi)的歐美電影人,幾乎已成中國觀眾耳熟能詳?shù)拿帧5?dāng)中國民族電影艱難探索之初,仍然稟賦相對清晰的本土意識,不僅注重民族民間故事的選擇,而且致力于講述這些民族民間故事。
對于中國早期電影而言,盡管民族民間故事是一種不可多得的題材資源,但并非別無選擇的選擇。實(shí)際上,明星影片公司的《空谷蘭》(1925)、長城畫片公司的《一串珍珠》(1925)與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的《殖邊外史》(1926)等影片,也采用外國“故事”為藍(lán)本,或在“歐化”浪潮中編織缺乏根據(jù)的新“故事”;另外,格里菲斯的《賴婚》(WayDownEast,1920)和《亂世孤雛》(OrphansoftheStorm,1922)等影片及其“最后一分鐘營救”,都對中國早期電影敘事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據(jù)當(dāng)時的評論,明星影片公司的《盲孤女》(1925),其“格調(diào)劇情與導(dǎo)演方法”,“似脫胎于葛雷菲斯之《亂世孤雛》一片”②;細(xì)讀華劇影片公司出品、目前仍能獲得膠片的《雪中孤雛》(1929),也能體會到格里菲斯《賴婚》的深重痕跡。
中國早期電影對民族民間故事的選擇,是通過電影的生產(chǎn)和消費(fèi),在錯雜的語境中堅守民族意識和個體身份的有效手段,也是這一時期中國民眾維護(hù)民族自尊、反思文化傳統(tǒng)和尋求精神寄托的重要舉措。為了拓展本土電影的生存空間,一大批存留在戲曲、鼓詞、話本、小說以至流傳在民間的諺語、傳說等民族民間故事,均被搬上銀幕,力圖作為歐美電影的替代品,迎合或滿足中國觀眾的欣賞趣味;更有許多“民間生活倫理”,被處理成新的“故事”提供給觀眾。正因?yàn)槿绱耍谥袊缙陔娪笆飞希餍怯捌疽云涮鼐叩膼矍椤⒒橐龊图彝惱砉适拢删蜑椤百Y格最老”、“出品最多”、“人才最眾”、“銷行最廣”的制片機(jī)構(gòu)。③另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從1905年開始到1949年為止,僅僅出自《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聊齋志異》的“故事”影片,應(yīng)該不下200部(集);根據(jù)《西廂記》、《桃花扇》、《琵琶記》等著名戲曲改編的“故事”影片,也不會少于50部;至于“唐伯虎點(diǎn)秋香”、“梁山伯與祝英臺”以及“孟姜女”、“白蛇傳”等膾炙人口的民間故事,更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翻拍。而天一影片公司,則不僅以一大批取材于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和歷史演義的“稗史片”成功地開辟國產(chǎn)影片的南洋市場,而且在20世紀(jì)2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影壇引發(fā)了一場聲勢不小的“古裝片”熱潮。更加值得反思的地方在于,這種古裝片(或民間故事片)熱潮,不僅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泯,反而會在特定的時空中反復(fù)出現(xiàn)。20世紀(jì)20年代中后期之后,在1940年前后的“孤島”,古裝/歷史片再度繁盛。木蘭從軍、費(fèi)貞娥刺虎、紅線盜盒的事跡與岳飛精忠報國、林沖雪夜殲仇、關(guān)云長忠義千秋的壯舉,成為“孤島”影人以古喻今、宣傳抗敵的武器。1940年還被稱為中國電影史上的“民間故事年”,主要原因是“什九的女明星,都扮過私訂終身的小姐,什九的名小生,都扮過落難公子”④。為了競爭拍攝民間故事片,“孤島”影壇還破天荒地鬧過三件“雙包案”,第一件是國華公司和藝華公司的兩部《三笑》,第二件是國華公司和新華公司的兩部《碧玉簪》,第三件是國華公司和合眾公司的兩部《孟麗君》。可見中國電影史上民間故事的生產(chǎn)與消費(fèi),已達(dá)相當(dāng)驚人的規(guī)模。
而從根本上說,只要是聚焦于中國民眾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電影故事,都是民族民間故事。民族民間故事進(jìn)入電影并引發(fā)一次又一次的熱潮,形成中國早期電影不同于歐美電影的獨(dú)特的敘事格局。當(dāng)民族民間故事以曲折的情節(jié)設(shè)置和動人的情感訴求搬上銀幕,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電影敘事研究論文
說起來,黑幫片的定義是明確的。“‘黑幫’是廣義地包括一切不法之徒和犯罪分子。與描寫破案過程的偵破片不同,黑幫片不聚焦在某樁罪案上,不以執(zhí)法人員為中心人物,也不一定非以犯罪分子落網(wǎng)為結(jié)局。黑幫片以黑幫頭目或黑幫分子為中心人物,以黑幫人物的犯罪活動或興衰歷史為中心內(nèi)容。”①可以看出,黑幫片拒絕現(xiàn)實(shí)社會的理性“執(zhí)法人員”,將黑幫虛構(gòu)為一個獨(dú)立的社會空間,描述黑幫興衰歷史的同時也潛在地詮釋了存在的合理性。從敘事結(jié)果來看,雖然黑幫分子“命歸西天”,但由于并不表達(dá)正義的介入,善惡的混淆形成了價值判斷的含混。因此,在國家電影政策干預(yù)下,黑幫片在國內(nèi)的電影市場上被禁,甚至涉黑內(nèi)容都在禁止傳播之列。
事實(shí)上,時下流行的武俠大片與黑幫片頗有相似之處。區(qū)別僅在于武俠大片借用歷史的朦朧把暴力、等多種元素包裹起來,用遙遠(yuǎn)幽深的時間長廊成功地遮蔽了特殊題材對當(dāng)下現(xiàn)狀的影射;而黑幫片是以邊緣空間(一個與主流社會相對立的空間)來容納這種具有現(xiàn)實(shí)觀感的暴力與血腥,很難驅(qū)除現(xiàn)實(shí)狀態(tài)的隱喻與聯(lián)想。這就造成了兩種類型在國內(nèi)截然不同的命運(yùn)。但另一方面,黑幫片在合拍片、引進(jìn)片以及影碟音像市場上的熱鬧,吸引了許多觀眾的注意。近年來,黑幫電影在類型元素不斷裂變與重組中,已逐漸走出了表現(xiàn)黑幫斗爭的淺表層次,挾帶著政治批判、唯美追求、人生哲理等紛繁多義的主題,進(jìn)入了描摹復(fù)雜人性的深度。這從威尼斯電影節(jié)對杜琪峰執(zhí)導(dǎo)的黑幫類型片《放逐》的接納②,就可以明確體察到黑幫與文藝片的融合跡象,杜琪峰的系列作品就被稱為“黑幫文藝片”。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說,從政策的角度限制黑幫片的發(fā)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從藝術(shù)上否認(rèn)黑幫片的價值就有些不合時宜了。
一、思想資源:提升黑幫類型的精神
眾所周知,黑幫片在國內(nèi)電影市場上的缺席由來已久。賈磊磊僅用幾部電影就概括了黑幫電影在新時期20年的發(fā)展:“在1977-1997年,中國的幫派電影的出現(xiàn)無疑是受到港臺黑社會動作片的影響,《一無所有》(1989)、《外灘龍蛇》(1990)、《京城劫盜》(1992)、《綁架在午夜》(1993),這些影片雖然沒有形成經(jīng)典化的制作風(fēng)格,沒有大師巨作,但也出現(xiàn)了《搖啊搖,搖到外婆橋》(1995)這樣的同類影片中的重要作品。”③除了張藝謀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具有一定的影響,其余幾部均是默默無聞。而與之相映的是,黑幫類型電視劇卻曾在國內(nèi)熒屏上大行其道,《黑冰》、《黑洞》、《黑霧》等大量黑字當(dāng)頭的涉案劇吸引了觀眾眼球,陳道明、王志文、孫紅雷演繹的黑幫人物超過了正面人物的魅力,掀起了一股富有中年男人魅力的黑幫老大的浪潮。此后雖被廣電總局管制,但無論怎樣,電視劇對黑幫類型的實(shí)踐大大超出了電影。因此,大陸黑幫片在創(chuàng)作思路上受到嚴(yán)格的限制,數(shù)量偏少,不可能形成嚴(yán)密的敘事邏輯與相對成熟的敘事套路,沒有用大陸題材的內(nèi)容培育起欣賞黑幫片的觀眾。
我們知道,任何類型片背后都存在著某種思想資源的支撐。黑幫片也不例外,與武俠古裝片一樣,只要不滿足槍戰(zhàn)打斗的黑幫片都要尋找提升題材的精神資源。大陸黑幫電影在類型整體上的缺席,其實(shí)折射出支持黑幫的思想資源在主流文化中的式微。我們只要考察一下香港黑幫電影就可以知道,其精神狀態(tài)無外有如下幾類:
1.極端的個人主義。它既有自主獨(dú)立的積極一面,又存在著自私自利的消極一面,給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物系列提供了行為的依據(jù)與真實(shí)的心理動機(jī),均能喚起觀眾真實(shí)的心靈感應(yīng)。就黑幫電影的嬗變來看,積極意義所張揚(yáng)個人風(fēng)格的英雄系列呈現(xiàn)出逐漸淡化的軌跡。個人英雄主義在“吳宇森系列”、“林嶺東系列”,如《英雄本色》、《喋血雙雄》等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但近年來,如杜琪峰的《槍火》、《放逐》、《黑社會1》、《黑社會2》、黃精甫的《江湖》等等,人物完全取消了正、反的對立,黑社會中核心事件刺激了黑幫頭目自私的本能,展示出人性極端惡的一面,應(yīng)該說《黑社會》系列電影推翻了觀賞的慣例。一般說來,即便在黑幫電影中,大都也以相對的善惡,來區(qū)分正反人物類型,如《江湖》中下手狠毒的左手與相對寬容的就哥,雙方都有機(jī)會面對鏡頭闡述自身的人生哲學(xué),但到了給黑社會寫史的杜琪峰這里,黑幫頭目均以極端狠毒的手段牟取權(quán)勢,我們很難判斷人物的善惡,也就很難產(chǎn)生必要的情感認(rèn)同。在這里,極端個人主義為反面人物提供了思想的資源,僅以真實(shí)的本能欲望促使對現(xiàn)實(shí)生存的殘酷性的隱射與聯(lián)想,贏得觀眾潛意識的支持。然而這恰恰是大陸主流文化所反對的。
電影《兔子洞》敘事藝術(shù)分析
【摘要】電影《兔子洞》改編自大衛(wèi)•林賽—阿貝爾的普利策戲劇獎同名作品,于2010年12月在全球上映。電影講述了一對普通夫婦痛失4歲愛子后,如何在以后的生活中尋求內(nèi)心的慰藉。作品通過雙重的敘事形態(tài)、巧妙的敘事結(jié)構(gòu)、豐富的敘事情感和幽默的敘事話語,誘導(dǎo)觀眾對內(nèi)心困惑和生活壓抑作出反思,表達(dá)了人類認(rèn)識生命價值、實(shí)現(xiàn)生活目的和追求活著的意義的深刻內(nèi)涵。
【關(guān)鍵詞】《兔子洞》;敘事形態(tài);敘事結(jié)構(gòu);敘事情感;敘事話語
現(xiàn)代傳播學(xué)是一門由多個領(lǐng)域相互交叉和相互滲透的綜合學(xué)科,其傳播核心是人們對信息的傳遞和交流。傳播學(xué)是研究社會信息系統(tǒng)及其運(yùn)行規(guī)律的科學(xué),因此,它可以作為我們認(rèn)識了解各種文化現(xiàn)象的理論工具。[1]從傳播學(xué)視角來看,電影文本以電影為媒介來傳遞信息,電影傳播過程也是一個信息傳遞和交流的過程。電影文本是通過文字、聲音、影像、色彩等符號,傳遞給觀眾一些連貫系統(tǒng)的、邏輯嚴(yán)密的、生動形象的信息。一部電影作品是否得到成功傳播,從傳播學(xué)視角探究附著在文本載體上的信息,可以最大限度地擴(kuò)大意義空間,電影傳播過程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制約、多個元素緊密結(jié)合的有機(jī)整體。電影是一門藝術(shù),電影敘事也充滿了藝術(shù)特色。本文試圖通過分析電影《兔子洞》的敘事形態(tài)、敘事主題、敘事結(jié)構(gòu)、敘事情感、敘事話語和敘事美學(xué),解讀對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情感問題思考的深度和廣度,解碼這部電影的藝術(shù)特色。20世紀(jì)90年代,隨著異域文化差異的各類戲劇風(fēng)起云涌,美國戲劇繼續(xù)呈現(xiàn)多元化的發(fā)展趨勢。美國電影《兔子洞》(RabbitHole)于2010年12月上映,再次將大衛(wèi)•林賽—阿貝爾(DavidLindsay—Abaire)的戲劇作品《兔子洞》搬上銀幕,不斷掀起觀影風(fēng)潮,引發(fā)觀眾及其讀者對作品非常之多的評論,反映出人們對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感困境的思考。電影《兔子洞》由林賽擔(dān)任編劇、約翰•卡梅隆•米切爾擔(dān)任導(dǎo)演,在保留劇本大部分對白的風(fēng)格中,取得了令人滿意的影片效果。影片的主線是著名女演員妮可•基德曼飾演的妻子貝卡和艾倫•艾克哈特飾演的丈夫霍伊,他們心愛的兒子遭遇一場意外車禍而身亡,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通過悲傷的音樂和特設(shè)的布景以及獨(dú)特的語言渲染了作品敘事轉(zhuǎn)變的發(fā)展方向。人物刻畫出面對意外和死亡的種種矛盾和傷痛,一次又一次無奈地接受著保守的心理治療。一個中產(chǎn)家庭遭遇外來的不測,加快了原本滿足或平衡的生活狀態(tài)逐步惡化為滿足遭到破壞或失去平衡的發(fā)展進(jìn)程,起到了核心和催化的關(guān)鍵性作用。
一、敘事形態(tài)
隨著20世紀(jì)中后期結(jié)構(gòu)主義文論研究的進(jìn)程,由法國著名文學(xué)理論家、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學(xué)家茨維坦•托多洛夫提出的“敘事學(xué)”逐漸完善起來,已發(fā)展成為一門獨(dú)立的學(xué)科。敘事理論體系深受以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xué)為基礎(chǔ)的符號學(xué)理論及以結(jié)構(gòu)主義詩學(xué)為基礎(chǔ)的神話學(xué)理論的影響,過度重視研究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各要素之間的規(guī)律和聯(lián)系。解構(gòu)主義、女性主義以及新文學(xué)理論思潮的出現(xiàn),打破了以文本內(nèi)部關(guān)聯(lián)研究為主的經(jīng)典敘事學(xué)的封閉局面。現(xiàn)代敘事學(xué)沖出文本內(nèi)部的固有模式,緊密聯(lián)系人文、歷史及社會背景,拓展了敘事理論及研究對象,成為一門一脈相承的、動態(tài)發(fā)展的文學(xué)理論體系。隨著時間的推進(jìn),敘事學(xué)向其他媒介滲透,架構(gòu)起跨學(xué)科研究的橋梁,具備了跨媒介的特性,不僅僅應(yīng)用于文學(xué)領(lǐng)域,在繪畫、影視劇等文化領(lǐng)域的研究也越來越廣泛,形成了敘事學(xué)的諸多分支。20世紀(jì)80年代,安德烈•戈德羅和弗朗索瓦•若斯特合著的《什么是電影敘事學(xué)》問世,電影敘事學(xué)作為一門藝術(shù)學(xué)科正式誕生。集文學(xué)敘事和電影敘事于一體的表現(xiàn)形態(tài)為敘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維角度。電影敘事形態(tài)既有敘事內(nèi)在實(shí)體的規(guī)律分析,也有敘事文本的個性研究;既探討文本角色的功能,也研究故事架構(gòu)中受眾群的作用。觀眾的參與使電影敘事形態(tài)呈現(xiàn)多樣性和靈活性,結(jié)合高科技的拍攝手段和剪輯方式等,大大提升了電影作品的銀幕魅力。為迎合現(xiàn)代人豐富紛繁、錯綜復(fù)雜的生活,電影敘事的形式與內(nèi)容在民族傳統(tǒng)文化和大眾流行文化的相互制約和影響下,其敘事形態(tài)沿襲影視藝術(shù)的獨(dú)特機(jī)制,淋漓盡致地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在文學(xué)與電影的藝術(shù)形式轉(zhuǎn)換中,實(shí)現(xiàn)二者敘事形態(tài)的契合和交融,并試圖將電影精神和思想內(nèi)涵超越文本本身。林賽的原著劇本《兔子洞》曾先后兩次被搬上舞臺,首先在2006年百老匯上演話劇版,而后在2010年林賽親自操刀以編劇的身份推出電影版。電影的特點(diǎn)突出了心理活動,由一對夫妻近乎怪誕的語言及其心理獨(dú)白等信息編碼,傳遞給觀眾細(xì)膩的情感變化,從而洞察其復(fù)雜的內(nèi)心世界。劇本敘事形態(tài)在轉(zhuǎn)換成電影的過程中更為單純,而忠于劇本的簡單故事情節(jié)則無法達(dá)到理想的效果。語言作為人類靈魂表達(dá)的重要形式,是電影文本與觀眾之間最為重要的情感交流的途徑,是電影藝術(shù)思想表達(dá)的敘事形態(tài)。電影的敘事,有別于文學(xué)語言的敘事,是依賴電影作品的情節(jié)發(fā)展,剖析角色的性格特征,來領(lǐng)悟電影藝術(shù)的內(nèi)在獨(dú)特性。這部家庭悲劇作品是人物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承受痛苦的隱喻,是快樂人生與悲苦現(xiàn)實(shí)縱橫交錯的寫照,反映了人物在孤獨(dú)和絕望中痛苦掙扎的無奈。一個平鋪直敘的表層故事并不足以觸動讀者和觀眾的心靈,改編后的電影由于媒介表現(xiàn)手段的不同,不只是停留在劇本的原有結(jié)構(gòu)和語言層面上,還有鏡頭中的影像、語言和聲音所呈現(xiàn)出來的敘述,表現(xiàn)出獨(dú)特的雙重敘事形態(tài)。
二、敘事結(jié)構(gòu)
微電影廣告敘事策略探析
摘要:微電影廣告作為一種反映當(dāng)代社會現(xiàn)狀以及社會文化的重要形式,通過屏幕媒介與觀眾交流。傳媒性、互動性、較強(qiáng)的指向性及豐富的信息量是微電影廣告的重要屬性,短小的篇幅要容下巨大的信息量,決定了微電影廣告在敘事的把握、情節(jié)的設(shè)定、語言的提煉和細(xì)節(jié)的掌控上要考慮更多的因素。
關(guān)鍵詞:微電影廣告;敘事策略;情節(jié);結(jié)構(gòu);主線
一、線性敘事為“慣用手段”
(一)主線清晰。微電影從網(wǎng)絡(luò)短視頻逐步發(fā)展而來,敘事上以線性敘事為主、非線性敘事為輔。首先,單線敘事貫穿影片。克里斯蒂安•麥茨曾在對第二電影符號學(xué)的研究中指出:“經(jīng)典電影是作為歷史故事而不是話語來呈現(xiàn)的”“它的確切性質(zhì)以及它作為一種話語的效力之秘密在于,它抹去了話語陳述的一切標(biāo)記,并偽裝為一種故事形式”,電影的敘事在于將敘事所產(chǎn)生的記號給消除,讓人覺得是原有故事的發(fā)展態(tài)勢,而不是故意在講述。電影依靠畫面敘事,以屏幕作為載體,從而訴諸于觀眾的無限遐想、不切實(shí)際的夢想乃至塑造一個全新的世界。線性敘事作為一種經(jīng)典的敘事方式,在敘事時注重故事的完整性、時間的連貫性、情節(jié)的因果性。微電影廣告多采用傳統(tǒng)的線性敘事方式,從事件的發(fā)生到故事的結(jié)束,影片架構(gòu)清晰。然而,非線性敘事打破了原有時間以及空間的順序,是一種反傳統(tǒng)、多樣化的敘事手段,甚至可以說是電影敘事發(fā)展過程中創(chuàng)新出來的附屬品。其次,主線簡單清晰能夠在有限時間里將故事敘述清楚。微電影廣告由于在互聯(lián)網(wǎng)新媒體平臺播出,大多屬性表現(xiàn)為短小精悍、互動性強(qiáng)、易于傳播。與傳統(tǒng)的直白式廣告相比,微電影廣告更加具有話題性、吸引力和想象力。微電影廣告有屬于自身的優(yōu)勢,但是也存在著內(nèi)容受到時間限制的問題。主線清晰成為了短時間內(nèi)將故事講清楚的重要條件。(二)結(jié)構(gòu)明確。結(jié)構(gòu),是對段落、情節(jié)、畫面等組成部分的組織和安排。經(jīng)典敘事的線性結(jié)構(gòu)除單一時間向度的線性原則以及因果邏輯之外,還包括打亂了原有時空的線性原則,以交錯的方式所呈現(xiàn)出來的內(nèi)容。首先,微電影廣告的敘事結(jié)構(gòu)以線性順序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北大宣傳片《星空日記》中,講述了生活在普通家庭、擁有普通的長相的主人公,從擁有夢想、為夢想而奮斗到遭遇挫折,最終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摘星夢。他經(jīng)歷了同學(xué)老師的不理解、同伴的嘲笑、家人的不支持、摘星星夢想的實(shí)現(xiàn),這一系列框架性的構(gòu)造清晰明確。其次,非線性的敘事結(jié)構(gòu)為輔。非線性敘事打破了原有的時空概念,時空成為不連貫的部分片段的組接,主觀性、片段性以及非理性都是非線性敘事的重要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同時,主觀性以及非理性的特點(diǎn)被無限放大。心理敘事線索的介入使得現(xiàn)代電影更加注重非理性的本能和直覺,邏輯性、戲劇性被淡化消解,偶然性得到增強(qiáng)。非線性敘事甚至可以說是更加具有創(chuàng)意性的敘事表現(xiàn)手段,為微電影的敘事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巧妙的敘事結(jié)構(gòu)可以讓原有的劇作內(nèi)容更加具有表現(xiàn)力,更好地渲染氣氛、塑造環(huán)境。非線性的敘事結(jié)構(gòu)對于原有故事的架構(gòu)要求很高,在打亂了時間以及空間的情況下將事件敘述清楚,一方面有利于建構(gòu)故事,故事的內(nèi)容更豐富。另一方面則增加了敘事的難度。微電影廣告短小,信息量足,線性敘事原有的簡單易懂的邏輯性特點(diǎn)則成為了微電影廣告主導(dǎo)敘事結(jié)構(gòu)的不二法則。
二、情節(jié)構(gòu)建的“簡單化”
(一)藝術(shù)與細(xì)節(jié)的真實(shí)。情節(jié)設(shè)計必須符合真實(shí)性原則,即藝術(shù)與細(xì)節(jié)的真實(shí),其中的設(shè)計不僅僅包括情節(jié)內(nèi)容的設(shè)計,還包括情節(jié)與情節(jié)之間內(nèi)容的銜接以及編排。并不是說照搬生活中所發(fā)生的瑣事,而是將生活的部分戲劇性成分進(jìn)行提煉,從而創(chuàng)作出合乎情理、合乎生活邏輯的故事情節(jié),即情景再現(xiàn)。情節(jié)的創(chuàng)作還要遵循事件與事件之間的聯(lián)系,所描述的創(chuàng)作目標(biāo)是一系列彼此相連的事件。人物、事件、環(huán)境環(huán)環(huán)相扣,情節(jié)逐步推動事件的發(fā)展。微電影廣告作為大眾消費(fèi)語境之下衍生出來的產(chǎn)品,傳播媒介的特性起到主導(dǎo)性的作用,是傳播信息、交流思想、表達(dá)情感、獲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微電影廣告《三分鐘》由陳可幸導(dǎo)演,描述火車列車員與家人相約站臺見面的故事。車間內(nèi)嘈雜的環(huán)境、站臺上焦急等待候車的人群、大大小小的包裹行李、寫著福字的大紅色的窗花,短片用許多細(xì)節(jié),營造出整個大的氛圍,細(xì)節(jié)與藝術(shù)的真實(shí)給觀眾帶來了的親切感,拉近了影片與觀眾之間的距離,觀眾與影片之間更容易產(chǎn)生互動。微電影廣告《過年回家》《筷子》《爸爸是個騙子》等,運(yùn)用小物件作為切入點(diǎn),大量細(xì)節(jié)的陳列參與敘事,影片生動且富有感染力,從而在視覺與聽覺上打動觀眾。(二)淡化情節(jié)。電影的語言常被稱為“視聽語言”,這就意味著電影運(yùn)用的物質(zhì)元素包括活動的影像和與之相匹配的聲音。首先,情節(jié)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片段式的組接,形式感增強(qiáng),對畫面與聲音的要求提升。情節(jié)弱化,臺詞、獨(dú)白以及旁白參與敘事的功能增強(qiáng)。人的聲音具有很強(qiáng)的造型功能,聲音通過語言、力度、音色等表達(dá)出許多微妙的信息,包括人物的精神面貌、身體狀況、身份地位、性格等。短小的微電影廣告惜字如金,由語言承擔(dān)起大部分的抒情、表意以及敘事的功能。其次,缺乏情節(jié)的空泛化敘事造成形式大大超過了內(nèi)容。敘事上的空洞,使得影片只能在視覺上以奇觀印象示人卻不能真正從故事上打動觀眾。開端高潮到結(jié)尾摒棄模式化、程序化、簡單化的故事情節(jié)以及敘事手段,反之以炫酷的鏡頭運(yùn)動、特效制作、絢麗夢幻的造夢手段吸引觀眾。這正是因?yàn)樵诖蟊娤M(fèi)的時代背景下,快節(jié)奏的生活方式讓人們偏愛觀看視覺沖擊力強(qiáng),帶有消遣性、娛樂性的短片。(三)互動性增強(qiáng)。互動是一種最基本、最普遍的日常生活現(xiàn)象。影視在不斷發(fā)展,觀眾隨著觀影量的不斷提升,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銀幕之外,而是想要參與其中。電影與觀眾的親近性,要求影片情節(jié)的設(shè)計、細(xì)節(jié)內(nèi)容的含括、場景的構(gòu)思要符合人們當(dāng)下所處的環(huán)境,所發(fā)生的事件要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從而形成互動性。從某種程度上講,“賀歲片”的出現(xiàn)是電影站在受眾的視角以及心理上全方位考慮的結(jié)果,也是電影市場化發(fā)展過程中衍生的附屬品,受眾的感受以及票房的高低成為影片創(chuàng)作、發(fā)行、放映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微電影廣告本身具有很強(qiáng)的功能性、寓意性、指向性和目的性,也可以說是為觀眾而生的產(chǎn)品,受眾接收所傳遞的信息才能完成短片最終的使命,因此,觀眾的觀影感受以及影片的吸引力成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電影戰(zhàn)狼2國家敘事研究
講好中國故事是2013年習(xí)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來的,他指出“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chuàng)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1]。由此可見,講好中國故事,樹立好、傳播好中國國家形象成為新時代國家對文藝作品的新要求。電影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載體之一,電影要講好中國故事,包含如何講述和講述什么兩方面內(nèi)容。目前,中國電影在如何講述方面取得很大的進(jìn)步,但在講述什么方面進(jìn)展不太理想。如我國21世紀(jì)興起的景觀電影就是典型范例。“景觀電影是相對敘事電影提出的一個概念,是指在當(dāng)前圖像化的時代語境中,電影對畫面和視聽效果的重視,傳統(tǒng)的單純靠講故事取勝的電影觀念在新近國產(chǎn)電影中發(fā)生了重要轉(zhuǎn)變,圖像的作用發(fā)揮到令人眩目的程度,而敘事則不見起色甚至漸趨空洞”[2]。以2002年的電影《英雄》為例,這種重視觀眾視覺享受、場面宏大、形式華美的影片掀起國產(chǎn)景觀電影的創(chuàng)作熱潮,一度成為中國電影的主流創(chuàng)作形式。此類電影還有《無極》《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夜宴》等。這些電影在如何講述方面取得巨大成功,通過華美的講述形式贏得市場。但電影在完成如何講述(電影形式)后,沒有進(jìn)一步琢磨講述什么(敘事內(nèi)容),這使得這些景觀大片在內(nèi)容上缺乏深刻的思想內(nèi)涵和時代精神,無法激起觀眾的共鳴更無法贏得觀眾的認(rèn)同。2017年電影《戰(zhàn)狼2》完成對景觀電影的超越,影片既講究如何講述,具有好萊塢大片的視覺效果,更重視講述什么,尤其國家敘事法則的運(yùn)用使影片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一次成功的文藝實(shí)踐,點(diǎn)燃了觀眾的中國夢激情,產(chǎn)生轟動效應(yīng),創(chuàng)造了國產(chǎn)電影的奇跡,獲得了票房與口碑雙豐收,成為2017年夏天最燃情的電影。國家敘事是指敘事學(xué)視野下以國家為主體的政治傳播,其目的是對內(nèi)凝聚共識、引導(dǎo)認(rèn)知,對外展現(xiàn)國家形象,以此獲得國際認(rèn)可[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治化文藝觀念被成功運(yùn)用到很多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創(chuàng)作中。“作為最大眾化、最具影響力的藝術(shù)載體,電影除了體現(xiàn)藝術(shù)審美價值,還在政治與藝術(shù)的結(jié)合上創(chuàng)立了一套充滿政治激情的電影語言體系。”[4]電影《戰(zhàn)狼2》對國家敘事的成功運(yùn)用,使得影片成為新時代的紅色經(jīng)典影片,影片無論在主題、人物塑造還是事件安排上都極具主流意識形態(tài),時代精神指向鮮明,國家敘事特征明顯。
一、英雄主義敘事
英雄主義是國家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英雄主義是人類社會由野蠻向文明演進(jìn)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具有集體意識的精神價值觀,它具有鮮明的民族和國家特色,有強(qiáng)烈的歷史感、時代感和人格的震撼力”[5]。英雄主義具有集體主義特征,代表國家的理想,承載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英雄具有榜樣的力量,是民族理想的表征,是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符號代碼,能喚起整個社會對其奮斗目標(biāo)的認(rèn)同,社會群體通過對英雄的認(rèn)同進(jìn)而認(rèn)同英雄身上承載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1.新英雄形象的塑造。電影《戰(zhàn)狼2》的英雄主義敘寫特征,首先體現(xiàn)在對英雄人物冷鋒的塑造上。影片開場,冷鋒在回國的輪船上遭遇海盜襲擊。面對海盜入侵,曾是軍人的冷鋒挺身而出,從游輪的甲板跳入海中,在水下赤手空拳與海盜展開殊死搏斗,打敗海盜,解救了整船人的生命。這凸顯了冷鋒作為超級英雄的能力,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氣概。之后,由于要為女友復(fù)仇,冷鋒踏上非洲的土地,卷入非洲國家叛亂之中。冷鋒原本可以安全撤離,但曾經(jīng)身為軍人的經(jīng)歷使他產(chǎn)生保護(hù)受難同胞的使命感。他孤身一人勇闖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到戰(zhàn)亂區(qū)解救即將被屠殺的同胞和難民,與雇傭軍和叛軍展開生死大戰(zhàn),從而樹立了孤膽英雄的形象。由個人復(fù)仇到拯救同胞,冷鋒完成了個人英雄主義的升華。為正義而戰(zhàn)、為民族而戰(zhàn)、為國家而戰(zhàn)這些英雄主義的特征在冷鋒身上得以彰顯。驚險的打斗場面、重型武器的熟練使用、堅韌的意志力等淋漓盡致地刻畫了冷鋒作為新時代英雄的智勇雙全和堅韌不拔。新英雄冷鋒,喚起大眾深藏于心的英雄情結(jié),引發(fā)大眾對具有正義、勇敢、犧牲等特質(zhì)的英雄代表人物的呼喚,喚醒人們對具有社會責(zé)任感、國家使命感的英雄思想的認(rèn)同。值得一提的是,電影對新時代新英雄的塑造是以強(qiáng)大的祖國為后盾的,冷鋒的義無反顧、奮勇前行是在祖國的支持下實(shí)施的。當(dāng)英雄冷鋒面對蜂擁的敵軍、呼嘯的子彈、死亡的威脅時,來自祖國軍隊(duì)的炮彈呼嘯而至,準(zhǔn)確地?fù)糁袛耻姡瑖业膹?qiáng)大讓英雄具有了時代自信與民族豪情等新英雄特質(zhì)。2.對傳統(tǒng)英雄敘事視點(diǎn)的突破。電影的英雄主義敘事還體現(xiàn)在對傳統(tǒng)英雄敘事視點(diǎn)的突破上。《戰(zhàn)狼2》突破了傳統(tǒng)華語電影中民族悲情英雄的敘事視點(diǎn),構(gòu)建了新時代背景下能引發(fā)民族自豪感的新英雄敘事視點(diǎn)。在傳統(tǒng)的功夫電影中,電影中的英雄往往在近代中國的失敗和屈辱中奮起,飽含民族悲情。20世紀(jì)50年代,中國功夫電影迅速崛起。傳統(tǒng)功夫電影《精武門》《霍元甲》《黃飛鴻》等塑造了一批強(qiáng)身救國的英雄形象,這些傳統(tǒng)英雄背負(fù)著沉重的包袱,往往身處困境,通過武術(shù)較量獲得象征性的勝利,成為具有時代特征的悲情英雄。比如李小龍、李連杰、甄子丹等演員在電影領(lǐng)域的成功都離不開悲情英雄的塑造。他們演繹的英雄在國家積貧積弱的時代背景下,即使在武術(shù)上取勝也大多難逃死亡或隱姓埋名的命運(yùn),電影充滿了悲情與傷感。《戰(zhàn)狼2》中的英雄冷鋒則不需要背負(fù)傳統(tǒng)英雄的沉重包袱,他背靠世界新格局下日益強(qiáng)大的中國,擺脫了傳統(tǒng)功夫電影的悲情與傷感,展現(xiàn)了充滿民族自豪感的新英雄形象。其中“一朝是戰(zhàn)狼,終身是戰(zhàn)狼”的戰(zhàn)狼精神是新時代英雄的特質(zhì),面對受難的同胞與非洲難民,冷鋒義無反顧地伸出援手。與傳統(tǒng)悲情英雄的被動反抗不同,冷鋒更多是主動選擇保護(hù)。比如他所說的“我就是為他們而生的”,充分體現(xiàn)了時代英雄的豪情與自信。《戰(zhàn)狼2》新英雄敘事還體現(xiàn)在對新時代英雄群像的塑造上。當(dāng)國家和同胞有需要時,我國的軍人總是義無反顧地站出來,牢記軍人的職責(zé)與使命,就如同電影里所說的“一朝是軍人,終身是軍人”。軍人的職責(zé)和使命在退役軍人冷鋒、何建國和海軍艦長身上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延續(xù)了革命英雄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他們以生命為人民保駕護(hù)航,體現(xiàn)了新時代新英雄群體的特質(zhì)。
二、民族主義敘事
民族主義敘事是電影敘事的重要方式之一,“羅蘭•巴特在其名著《神話學(xué)》中對《巴黎競賽》雜志(ParisMatch)所做的分析或可作為一個例子,他為我們解讀民族主義敘事提供了一個有趣且重要的視角——視覺文化”[6]。民族主義研究學(xué)者安東尼•史密斯提出:“影視成為一種有效的工具,用于表現(xiàn)國家的文化政策以及那種影響千百萬人的民族理想……通過攝像機(jī)對獨(dú)特的民族風(fēng)景、傳說與環(huán)境、歷史與現(xiàn)實(shí)重新創(chuàng)作,傳達(dá)一種民族個性意識。”[7]可見,民族主義敘事與電影的有效結(jié)合,使得民族想象共同體——國家形象變得鮮明直觀,成為國家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主義是強(qiáng)調(diào)民族獨(dú)特的歷史、文化、語言、價值、制度,維護(hù)民族的自治、統(tǒng)一和認(rèn)同的情緒、學(xué)說、意識形態(tài)、政治原則或運(yùn)動”[8]。民族主義是電影《戰(zhàn)狼2》的重要敘事元素,但電影中的民族主義與傳統(tǒng)近代民族主義的悲情不同,更多是對新時代背景下引發(fā)民族自豪感的新民族主義的敘寫。其主要體現(xiàn)在愛國主義精神與國際人道主義精神的敘寫與展現(xiàn)上。1.愛國主義精神的彰顯。愛國主義是電影《戰(zhàn)狼2》的主基調(diào),列寧說愛國主義是個人對祖國最深厚的感情,“中國的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現(xiàn)實(shí)意味著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本質(zhì)上就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最高表現(xiàn)形式”[9]。《戰(zhàn)狼2》中的愛國主義敘寫主要表現(xiàn)在冷鋒的愛國形象刻畫與中國國旗和中國護(hù)照的特寫上。首先,對男主人公冷鋒的愛國形象刻畫。冷鋒是新時代中國國民形象的代表,他展現(xiàn)了強(qiáng)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為了祖國和人民,冷鋒不惜一切代價甚至生命,去救助受困的華僑和中國工人,這種無畏犧牲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延續(xù)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當(dāng)冷鋒和雇傭兵頭子“老爹”決戰(zhàn),“老爹”使用卑鄙的手段將冷鋒壓制在身下。冷鋒命懸一線時,“老爹”以侮辱的言語“你們這些民族就是懦弱膽小,就該一輩子被欺壓”挑釁冷鋒。此時民族曾經(jīng)的苦難、國家榮譽(yù)感激發(fā)了冷鋒的潛能,他奮起反抗,壓制“老爹”并給他重重一拳。這一拳打消中國百年的屈辱,打出國人的自信,也打出國人的赤誠愛國之心。其次,對國家象征符號——國旗和護(hù)照的特寫。冷鋒帶領(lǐng)國人在途經(jīng)非洲硝煙彌漫、槍聲密集的交戰(zhàn)區(qū)無法通過時,他爬上車頭,丟掉槍支,化右臂為旗桿,充滿自信地高高舉起鮮艷的五星紅旗。交戰(zhàn)區(qū)的政府軍與反叛軍因此暫停交火,讓冷鋒帶領(lǐng)的中國車隊(duì)順利通過。國旗是國家的象征,隨著國家和民族的崛起,國旗成為新時代祖國強(qiáng)大的代名詞。中國國旗凝聚著中華民族的力量,當(dāng)國旗護(hù)佑人們走過炮火紛飛的交戰(zhàn)區(qū)的那一刻,觀眾們深刻體會到祖國強(qiáng)大給自己帶來的尊嚴(yán)、安全與自豪感。因此,當(dāng)電影最后給出中國護(hù)照的特寫時,每一個中國觀眾火熱的愛國激情被激發(fā)了,這時的劇情凸顯了愛國主義精神,有些影院甚至出現(xiàn)觀眾全體站立一起唱國歌的感人場面。《戰(zhàn)狼2》通過國旗、護(hù)照等象征物激發(fā)民眾強(qiáng)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可以說,這是電影通過愛國主義敘事,激發(fā)民眾對國家強(qiáng)烈的認(rèn)同感與歸屬感。2.國際人道主義精神的體現(xiàn)。國際人道主義精神是《戰(zhàn)狼2》彰顯的主題之一,主要表現(xiàn)在國際人道主義援助與以人為本的精神上。國際人道主義援助是新民族主義內(nèi)涵之一,《戰(zhàn)狼2》通過對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的敘寫,完成了新時代下國家新形象的塑造,從而激發(fā)民眾對國家的認(rèn)同感。電影中中國派出以陳博士為首的醫(yī)療隊(duì)對非洲進(jìn)行人道主義援助,對抗瘟疫。在戰(zhàn)亂與瘟疫蔓延的非洲,為了幫助非洲人民,以陳博士為首的醫(yī)療隊(duì)不僅以醫(yī)療技術(shù)提供幫助,甚至獻(xiàn)出生命,以生命譜寫了一曲國際人道主義的贊歌。自中非建交,中國給非洲提供了多方面的人道主義援助。電影中,非洲土地上有許多中國烈士的墓碑,這些烈士是中國派到非洲開展醫(yī)療、建筑等人道主義援助而不幸犧牲的英雄。電影通過墓志銘的方式傳達(dá)了中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同時讓觀眾在滿懷對中國烈士的尊敬和感動的同時,涌現(xiàn)滿滿的愛國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獲得了非洲國家人民的認(rèn)可與尊重。當(dāng)冷鋒手舉五星紅旗通過非洲交戰(zhàn)區(qū)時,無論政府軍還是反叛軍都停止戰(zhàn)爭,讓中國車隊(duì)安全通過,這是中國推行國際人道主義援助在國際上特別是在非洲獲得尊重的體現(xiàn)。電影中國際人道主義精神還體現(xiàn)在影片打破國界,弘揚(yáng)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上。主人公冷鋒在非洲淪陷區(qū)救助中國同胞時不忘救助非洲平民,這種不分國界、不分種族、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向觀眾傳達(dá)了一種超越民族與國家的大愛,這也是人類和平共處的大愛的體現(xiàn)。影片通過男主人公的價值取向進(jìn)一步向觀眾傳遞了中國堅守的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體現(xiàn)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在維護(hù)世界和平、促進(jìn)世界發(fā)展中承擔(dān)的責(zé)任與義務(wù),還體現(xiàn)了中國在人類發(fā)展史上做出的努力與貢獻(xiàn),進(jìn)而樹立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國際新形象。電影《戰(zhàn)狼2》通過英雄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國家敘事,完成了影片講好中國故事中的講述什么的環(huán)節(jié),是弘揚(yáng)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的新時代中國具有代表性的文藝作品,它點(diǎn)燃了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觀眾在享受視覺盛宴的同時,精神也得到洗禮與升華,可以說,《戰(zhàn)狼2》激發(fā)了觀眾強(qiáng)烈的愛國精神與民族自豪感。綜上所述,國家敘事法則的運(yùn)用不僅為影視文藝作品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可供借鑒的視角與經(jīng)驗(yàn),同時對新時代下國家形象的構(gòu)建具有積極意義。
作者:趙銳 單位:凱里學(xué)院人文學(xué)院
微電影廣告敘事特征
【摘要】廣告的故事化敘事傾向和人類對故事的需求使電影媒介成為一種理想的廣告載體,加之新技術(shù)變革下的“碎片化”時代特征與商品化邏輯促使微電影廣告的生成。后現(xiàn)代文化同樣也是技術(shù)變革的產(chǎn)物,深深地打上了商品化邏輯的烙印。微電影廣告敘事承載著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傾向和精神內(nèi)涵,呈現(xiàn)出意義淺表化、情節(jié)拼貼化、話語多元化特征。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感性需求,但對感性需求的過度滿足則會導(dǎo)致人的社會批判意識的喪失。
【關(guān)鍵詞】微電影廣告;敘事;后現(xiàn)代語境
美國著名媒介學(xué)者保羅•萊文森提出的“補(bǔ)償性媒介”理論認(rèn)為:“任何一種后繼的媒介,都是一種補(bǔ)救措施,都是對過去的某一種媒介或某一種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補(bǔ)救和補(bǔ)償。”[1]就傳播媒介形態(tài)來看,微電影廣告作為“一種后繼的媒介”勢必是對傳統(tǒng)媒介的一種“補(bǔ)救和補(bǔ)償”,與傳統(tǒng)媒介形態(tài)相比,有其獨(dú)特性。而這種獨(dú)特性的生成更與其所處時代特定的語境是分不開的。我國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由物質(zhì)產(chǎn)品的極度匱乏到物質(zhì)產(chǎn)品的極度豐富、由以實(shí)物消費(fèi)為主的消費(fèi)方式到以符號消費(fèi)為主的生活方式的演變。我國現(xiàn)代商業(yè)廣告的興起和繁榮得益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也經(jīng)歷了一個發(fā)展、演變的過程,即由以產(chǎn)品信息為主的叫賣式廣告,到以宣傳、論證為主的實(shí)證式廣告,再到以感性、敘事為主的故事化廣告的過程。當(dāng)傳統(tǒng)的叫賣式廣告、實(shí)證式廣告無法引起人們觀看興趣時,以情感敘事為主的故事化廣告自然大受青睞。美國廣告大師托尼•施瓦茨的理念是:“相對于觸動了觀眾心弦的廣告,那些試圖向觀眾傳遞信息的廣告怎么都要遜色一些。”[2]施瓦茨所言的“觸動了觀眾心弦的廣告”就是那些側(cè)重情感敘事的故事化廣告。高小康斷言:“人是講故事的動物。”[3](22)即人在“講故事”中延續(xù)著人類的生命與意義。“故事的插入使直接的生存活動被延宕的同時得到了意義,這是人之所以要講故事的根本原因。”[3](21)因此,講故事、聽故事成了人類一種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不論是作為現(xiàn)代社會的一種經(jīng)濟(jì)活動,還是文化現(xiàn)象,廣告的故事化敘事傾向都是現(xiàn)代廣告發(fā)展的趨勢之一。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電影,具備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扣人心弦的懸念設(shè)置、豐富的人物形象、立體的時空環(huán)境和較高的藝術(shù)審美品質(zhì),是一種理想的廣告載體。同時,進(jìn)入21世紀(jì)以來,新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變革使電影作為廣告的載體成為可能。隨著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各種移動終端與網(wǎng)絡(luò)的普及,人們的媒介接觸行為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不再像以前,花上整段時間完整地觀看電視節(jié)目或閱讀報刊;而是在工作與生活的空隙時間,利用“碎片化”的時間即時觀看或閱讀。因此,人們的媒介接觸習(xí)慣乃至生活方式完全碎片化、快餐化。為了適應(yīng)新技術(shù)變革帶來的受眾媒介接觸習(xí)慣的改變,“微”時代應(yīng)運(yùn)而生,微博、微信、微電影等新媒體相繼出現(xiàn)并得到迅猛發(fā)展。而微電影以“微時長、微制作、微投資”為特征,短則三五分鐘,最長也不過二十分鐘左右,加之其所具備的電影敘事優(yōu)勢,受到廣告主們的青睞,有了資本的投入,微電影廣告作為一種新的廣告形態(tài)的產(chǎn)生便水到渠成。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新技術(shù)變革下的“碎片化”時代特征與商品化邏輯構(gòu)成了微電影廣告的生成語境。后現(xiàn)代主義作為當(dāng)今世界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流行的理論話語,肇始于對理性主義、主體性等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范疇的批判,是伴隨著后工業(yè)社會(或信息社會、消費(fèi)社會)的到來而興起的,其影響力已滲透到人文社會科學(xué)的各個領(lǐng)域,尤其是已滲透并深刻影響了大眾文化的各個行業(yè),諸如電影、電視、流行音樂、廣告、游戲等,使大眾文化呈現(xiàn)出明顯的后現(xiàn)代特征。“后現(xiàn)代主義是信息時代的產(chǎn)物……后現(xiàn)代文化與美學(xué)浸漬了無所不在的商品意識,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對立在此歸于失效,商品稟有一種‘新型’審美特征,而文化則貼上了商品的標(biāo)簽。”[4]后現(xiàn)代文化同樣也是技術(shù)變革的產(chǎn)物,深深地打上了商品化邏輯的烙印。它不再追求文化背后的深層邏輯與意義,只注重文化的表層形式;不在乎人的主體性意識,只關(guān)注人的現(xiàn)實(shí)處境;不再倡導(dǎo)絕對性、超越性、恒定性的單一話語,而要建構(gòu)異質(zhì)性的多元話語。后現(xiàn)代文化的這些特質(zhì),要求新的媒介形態(tài)、新的文化實(shí)踐活動來滿足后現(xiàn)代語境下人們的需求。因此,我們說以微博、微信、微電影為代表的微媒介不僅是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與資本合謀的產(chǎn)物,更是后現(xiàn)代語境催生出的大眾文化現(xiàn)象。換言之,作為當(dāng)今世界一種普遍流行的社會思潮的“后現(xiàn)代主義首先是一種文化傾向,是一個文化哲學(xué)和精神價值取向的問題”。[4]這種文化傾向必然反映在當(dāng)下的文化實(shí)踐活動之中,因而微電影敘事必然承載著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傾向和精神內(nèi)涵。由這種語境看來,微電影從產(chǎn)生之初就與廣告天然地結(jié)合在一起,才有了微電影廣告形態(tài)。因此,后現(xiàn)代語境下的微電影敘事特征必然體現(xiàn)在微電影廣告之中。同時,微電影廣告直接受資本邏輯的控制,其本質(zhì)在于功利性地傳遞產(chǎn)品、服務(wù)或品牌的信息,這種后現(xiàn)代敘事特征也便自然有著屬于廣告的特殊屬性。如此,將微電影廣告置于上述后現(xiàn)代語境下對其敘事進(jìn)行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意義的淺表化、情節(jié)的拼貼化、話語的多元化等諸多特征。
一、深度消失:敘事意義淺表化
任何敘事都必定存在于特定的時空之中,不存在超越時空的敘事現(xiàn)象。只是“傳播媒介的性質(zhì)往往在文明中產(chǎn)生一種偏向,這種偏向或有利于時間觀念,或有利于空間觀念”。[5]自結(jié)構(gòu)主義敘事學(xué)興起,敘事理論便一直以文學(xué)文本、又主要是以小說文本為研究對象,側(cè)重對敘事與時間之間關(guān)系的研究,印刷媒介的性質(zhì)對文明產(chǎn)生了有利于時間觀念的偏向。隨著電影、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以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為基礎(chǔ)的新媒體的發(fā)展和普及,敘事學(xué)理論便逐漸將電影、電視、廣告、MTV等大眾文化文本納入自己的研究范疇。由此,敘事理論研究出現(xiàn)了向空間維度的轉(zhuǎn)向,電子傳播媒介的性質(zhì)對文明產(chǎn)生了有利于空間觀念的偏向。換言之,敘事理論經(jīng)歷了由“時間中心觀”向“空間中心觀”的轉(zhuǎn)向。而這種向“空間中心觀”的敘事轉(zhuǎn)向,具體到后現(xiàn)代語境之中,則表征為一種視覺化、景觀化敘事。傳統(tǒng)的電影敘事,以故事的因果邏輯為主線,注重敘事的情節(jié)性、時間性,是一種線性敘事。將人物置于特定的時間線索和歷史意識之中,通過人物對過去的回憶和當(dāng)下的處境來反思未來的走向,建構(gòu)電影主題的深度意義,發(fā)揮電影敘事對受眾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而當(dāng)代電影敘事深受后現(xiàn)代思潮影響,呈現(xiàn)出一種由傳統(tǒng)的“敘事電影”向后現(xiàn)代語境下的“奇觀電影”的敘事轉(zhuǎn)向。[6]在這一轉(zhuǎn)向進(jìn)程之中,“奇觀電影”敘事中的歷史意識斷裂,呈現(xiàn)出一種“非連續(xù)性”的時間敘事,無法將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進(jìn)行聯(lián)系,敘事的深度意義也就被消解,呈現(xiàn)出一種平面化、淺表化的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唯美的畫面、刺激的場景、美化的人物以及蒙太奇手法所拼貼出的視覺多維景觀。微電影廣告以電影為載體,呈現(xiàn)出明顯的電影敘事特征。可以說,微電影廣告敘事正是當(dāng)代電影視覺化、景觀化敘事的表征。微電影廣告是“碎片化”時代的產(chǎn)物,以“微時長、微制作、微投資”為特征,短則三五分鐘,最長也不過20分鐘,受制于時長,不能像商業(yè)電影那樣注重故事情節(jié)的跌宕鋪陳,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nèi),通過緊湊的故事情節(jié),巧用敘事手法,而刺激、直觀、唯美的視覺敘事則是吸引受眾眼球的常用策略。因此,多數(shù)品牌都會利用視覺、景觀敘事來表達(dá)品牌訴求。康師傅茉莉清茶微電影廣告《總會遇見你》,以“男女主角的三次偶遇”為故事主題,情節(jié)簡單:男女主角第一次因一束茉莉花在商場扶梯偶遇,第二次因一只玩偶在女主角的花店相遇,第三次經(jīng)歷了多次擦肩而過后再次因茉莉花而相遇。廣告全程男女主人公“茉莉清茶”飲料不離手,并且多次出現(xiàn)以茉莉花海為背景的畫面,最后出現(xiàn)廣告文案:“遇見茉莉,浪漫一世。”廣告之中的“清新美麗的女主角”“帥氣暖心的男主角”“時尚清新的創(chuàng)意花店”“唯美浪漫的茉莉花海”等敘事元素構(gòu)建了一幀幀極具視覺享受的唯美景觀。如此費(fèi)盡心思塑造的視覺景觀,只為吸引產(chǎn)品的目標(biāo)受眾——年輕消費(fèi)群體的關(guān)注,終極目的在于表達(dá)茉莉清茶能帶給消費(fèi)者一種時尚清新的享受和對美好愛情的期待。這一敘事過程并沒有揭示有關(guān)愛情乃至社會倫理道德等的深度意義,而受眾在這種視覺享受與滿足之中也無意去探求故事背后是否存在某種深刻意義。意義正是在這種視覺享受與滿足之中被消解。英特爾微電影廣告《超極本來了》亦是如此。王珞丹主演的美女特工在一酒店房間竊取了“超極本”電腦后,經(jīng)歷緊張、刺激的追逐,沖破重重阻撓而逃出,最后顯示文案:“超極本來了!”廣告運(yùn)用性感的美女特工、緊張而刺激的追逐場面等淺層的表象,只是為了吸引受眾注意從而達(dá)到傳遞“超極本來了”這一信息的目的,根本無意表達(dá)某種深度意義。微電影廣告的“微”,原本就是后現(xiàn)代語境下的碎片化特征所致。與此同時,當(dāng)人們長期浸染于“微”媒介所建構(gòu)的碎片化、快餐式的生活方式之中,人們的媒介接觸習(xí)慣、閱讀習(xí)慣乃至思維方式也都逐漸碎片化了。因此,如何在有限的碎片化的閱讀或觀看時間里引起受眾注意,發(fā)揮廣告最大的傳播效果就成了微電影廣告的主要任務(wù)。很顯然,傳統(tǒng)的以因果邏輯為主線的、體現(xiàn)深度意義的線性敘事已經(jīng)不合時宜,只需讓人們在作品的直觀呈現(xiàn)中體驗(yàn)、感受作品。
二、主體喪失:故事情節(jié)拼貼化
電影《小偷家族》重復(fù)敘事探析
【摘要】是枝裕和電影《小偷家族》的藝術(shù)特質(zhì)不僅體現(xiàn)在人文主義色彩上,還體現(xiàn)在重復(fù)敘事手法的運(yùn)用上。其重復(fù)敘事呈現(xiàn)出多種藝術(shù)形式,對深化電影主題有重大意義。是枝裕和在《小偷家族》中一方面以人物回憶、宿命輪回、生命反復(fù)、細(xì)節(jié)復(fù)制等變形手段豐富了重復(fù)敘事策略;另一方面,這些多元的重復(fù)敘事策略強(qiáng)化了人物的生存境遇與環(huán)境,解構(gòu)了傳統(tǒng)的基于血緣的家庭觀念。
【關(guān)鍵詞】重復(fù)敘事;小偷家族;是枝裕和;家庭電影
以家庭題材享譽(yù)世界的日本導(dǎo)演是枝裕和,是日本新電影運(yùn)動的代表人物。從目前對其的研究來看,大部分都聚焦于對其電影主題的研究或者對其紀(jì)實(shí)手法的分析。早期研究者一致認(rèn)為,是枝裕和電影中對家庭問題的描摹與思考、家庭關(guān)系、家庭觀,是其最擅長的母題。一些研究開始將視角轉(zhuǎn)向其電影中的父親形象、母親形象、父子關(guān)系等,豐富了是枝裕和電影主題的研究。紀(jì)實(shí)手法的主要特征在于視聽影像風(fēng)格極具東方婉約、含蓄的美學(xué)色彩,以淡淡的“物哀美”平衡了電影敘事與角色情感;在看似平淡散漫的平鋪直敘中,蘊(yùn)含著雋永、溫暖的物哀情感;長鏡頭語言保持著克制與疏離感。[1]對于紀(jì)實(shí)手法的研究是以服務(wù)主題研究為目的的。誠然,學(xué)術(shù)界熱衷于是枝裕和電影主題的研究,與其電影主題的鮮明性不無關(guān)系。那么,是枝裕和電影的主題何以如此鮮明?電影何以呈現(xiàn)出對于“家庭”的理解、解構(gòu)與重建,筆者認(rèn)為,這與電影的重復(fù)敘事是分不開的。重復(fù)敘事最早出現(xiàn)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重復(fù)理論研究的集大成者希利斯•米勒在《小說與重復(fù):七部英國小說》中提出了“異質(zhì)性假說”的重要概念。[2]他認(rèn)為,任何小說都存在著兩種互相矛盾且相互交織的重復(fù)類型,而這種異質(zhì)性形式在其他體裁的作品中都有所體現(xiàn)。他將重復(fù)劃分為“一種事物對另一種事物的復(fù)制的‘柏拉圖式’”和“一種事物對另一種事物的變異的‘尼采式’”兩種樣式。“柏拉圖式”重復(fù)建立在固定的原型基礎(chǔ)之上,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對這個自我同一的原型世界的模仿,因此彼此之間具有相似性;“尼采式”重復(fù)主張絕對差異,萬事萬物所呈現(xiàn)的相似性只不過是這種無法還原的差異所產(chǎn)生的幻象與魅影。影視中重復(fù)敘事是指相同(或相似)的鏡頭(或畫面、聲音、道具、環(huán)境等)在影視作品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組合方式,它能夠起到提醒、強(qiáng)調(diào)、回憶、對比的作用。關(guān)于是枝裕和電影的重復(fù)敘事,學(xué)界至今沒有專門論及。國內(nèi)已有一些研究對重復(fù)問題有所涉及,如李龍蓮指出,“是枝裕和作品總常常能看到某一意象的重復(fù)。”[3]獲得戛納電影節(jié)金棕櫚獎的電影《小偷家族》,講述了一個沒有血緣關(guān)系的家庭最終破碎的故事。本文基于米勒的兩種重復(fù)觀,從人物回憶、宿命輪回、生命反復(fù)、細(xì)節(jié)復(fù)制四個方面分析《小偷家族》重復(fù)敘事的多元變形,進(jìn)而進(jìn)一步討論重復(fù)敘事在深化主題、人物塑造等方面的意義與價值。
一、回憶
《小偷家族》中重復(fù)敘事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是“回憶”。回憶是對過去的重現(xiàn),對刻骨銘心的經(jīng)歷、難以釋懷的舊事重提,回憶是話語重復(fù)的變形。也就是熱奈特所指的“重復(fù)性敘述”。熱奈特認(rèn)為,“‘重復(fù)’事實(shí)上是思想的構(gòu)筑,它去除每次出現(xiàn)的特點(diǎn),保留它與同類別其他次出現(xiàn)的共同點(diǎn),是一種抽象。”“一系列相似的、僅考慮其相似點(diǎn)的事件在這里將被稱為‘相同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復(fù)現(xiàn)’。”[4]熱奈特根據(jù)故事和敘事文各自提供的兩種可能(事件有無重復(fù),語句有無重復(fù))先驗(yàn)地推論出四個潛在的類型,即講述一次發(fā)生過一次的事(單一性敘述);講述若干次發(fā)生過若干次的事(仍然屬于單一性敘述);講述若干次發(fā)生過一次的事(重復(fù)性敘述);講述一次發(fā)生過若干次的事(綜合性敘述)。在熱奈特看來,只有第三種類型才是重復(fù)性敘述。在《小偷家族》中,是枝裕和善于通過對往事、場景等的不斷再現(xiàn),喚起主人公的情感共鳴,從而消解原生家庭的意義,為營造家庭烏托邦尋求合理性支持。影片中的第一個重復(fù)是尤里在吃面筋時,和大家說自己的奶奶也曾經(jīng)喂她吃過面筋。這和此時初枝奶奶喂她吃面筋的場景相呼應(yīng),仿佛時光倒流。值得注意的是,尤里手臂上的傷疤在全片中重復(fù)出現(xiàn)了3次,第一次是初枝奶奶問尤里是怎么回事,尤里撒謊說是摔倒的。第二次是翔太在車?yán)锝衣队壤锏膫淌潜粻C的,并問是不是媽媽干的,尤里再一次撒謊說媽媽很好。第三次則是信代和尤里洗澡時,信代的手臂上有一個一模一樣的傷疤,通過信代的敘述,觀眾才知道,二人在之前都受到過家庭暴力。相同的事件發(fā)生在兩個年齡相差很大的人身上,可以說是一種宿命的輪回。包括后來亞紀(jì)在援交店交往男友后,和信代的對話中也透露出,信代和柴田治也是在援交店認(rèn)識的,柴田治曾經(jīng)也是信代的客人,兩人的經(jīng)歷再一次重復(fù)。日本經(jīng)濟(jì)在高速增長的同時,家庭帶來的約束力變得孱弱,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家庭集體的約束關(guān)系逐漸變?nèi)酢6S著現(xiàn)代社會的不斷進(jìn)步,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變得脆弱,處在隨時都會割裂的狀態(tài)。近年來的日本電影也凸顯出人們對于家庭集體關(guān)系的渴望,或是一種對于歸屬感的渴望。而導(dǎo)演是枝裕和在家庭電影中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他嘗試建立一種新的集體。在電影《小偷家族》中,沒有血緣關(guān)系的眾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yàn)橹貜?fù)的經(jīng)歷而加重了雙方之間情感的羈絆,進(jìn)而能夠同在一個屋檐下生活。這種非鏡頭蒙太奇式的重復(fù)是十分值得探究的,這類重復(fù)更像是一種懸念的設(shè)置,導(dǎo)演在之前的敘述中就放出線索,比如傷疤,以及四號先生在影片前段反復(fù)出現(xiàn)等。電影中最常見的是單數(shù)性敘事的懸念,這是最普通的線性故事所具有的特點(diǎn),在電影敘事中,也有著對某些細(xì)節(jié)的重復(fù)化敘事,由此形成“伏筆”和“暗示”[5]。然后通過一段對話對這一懸念進(jìn)行解答。電影《小偷家族》用的是順敘的敘事手法,并沒有運(yùn)用閃回、倒敘、插敘等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導(dǎo)演盡可能讓鏡頭遠(yuǎn)離人物內(nèi)心世界,為的就是能讓觀眾對電影有一個客觀的認(rèn)識,觀眾只能從敘事者的敘述中找到線索。同時本片中關(guān)于重復(fù)經(jīng)歷的臺詞都呈現(xiàn)出回憶性的特點(diǎn)。在不知不覺中拉長了在此時此刻空間中彼時彼刻的時間長度,也就是說,觀眾通過敘事者的敘述,從而展開對另一時空的豐富聯(lián)想,電影的時空維度變得豐滿,同時經(jīng)歷的重復(fù)也會讓觀眾產(chǎn)生一種原來如此的感覺,滿足了觀眾的期待感。
二、輪回
古裝電影敘事策略分析
[摘要]中國古裝類型電影誕生于20世紀(jì)20年代上海的城市文化中,是最具中國傳統(tǒng)文化韻味的電影類型范式。新世紀(jì)以來,古裝電影在中國乃至世界商業(yè)電影市場所爆發(fā)出的巨大能量使中國導(dǎo)演陸續(xù)投身于古裝電影的制作,引發(fā)了內(nèi)地古裝電影的創(chuàng)作熱潮。盡管古裝電影不斷創(chuàng)造票房奇跡,但其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表述卻飽受觀眾的詬病。本文力圖從電影敘事的角度入手,以新世紀(jì)以來的熱映古裝電影為研究范本,探究其遭遇惡評的根源,進(jìn)一步研究古裝類型電影所面臨的困境以及應(yīng)對策略。
[關(guān)鍵詞]古裝電影;敘事;想象;文化;娛樂至死
新世紀(jì)以來,華語電影乘著中國國家實(shí)力崛起的東風(fēng),疾步跨入巨制大片時代,以2001年的古裝武俠電影《英雄》為起點(diǎn),《無極》《夜宴》《十面埋伏》《畫皮》系列、《西游•降魔篇》《四大名捕》系列、《三打白骨精》《捉妖記》等古裝類型電影紛至沓來。在中國電影市場極速發(fā)展的十余年間,古裝電影已然成為商業(yè)電影的中堅力量,華語電影導(dǎo)演不約而同地嘗試通過古裝片這一具有特定歷史與文化內(nèi)容的電影類型,來尋求觀眾對民族文化的認(rèn)同,同時希冀以此為支點(diǎn),再次觸發(fā)類型電影在中國乃至世界電影市場的全面突圍。然而,在古裝電影屢屢締造票房奇跡的同時,卻很難得到觀眾的普遍認(rèn)可。近幾年來,隨著網(wǎng)絡(luò)新媒體侵入生活的每個角落,古裝類型電影亦經(jīng)歷著從經(jīng)典到拼貼的轉(zhuǎn)身,其內(nèi)置的精神內(nèi)核正無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一、古裝電影的敘事機(jī)制
古裝電影最早誕生于上海這一中國近代城市文化的中心,是在城市文化的孕育中產(chǎn)生的大眾文化娛樂產(chǎn)品。誕生伊始,古裝電影便受到了城市市民階層的追捧,不僅為片商攫取了巨大的商業(yè)利潤,還在短時期內(nèi)衍生出了武俠、神怪等全新的電影類型,樹立了中國電影的類型范式。20世紀(jì)20年代,中國商業(yè)電影熱潮中出現(xiàn)的這一獨(dú)特的文化現(xiàn)象,是由于古裝這一極具民族代表性的銀幕符號,其背后所指征的文化內(nèi)涵滿足了影院觀眾對于古老中國文化的想象。自古以來,服裝始終是人類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人類著裝的顯性目的首先要滿足諸如驅(qū)寒保暖的原始本能,其次才是為了彰顯其所指的性別、品牌、格調(diào)等隱性的附加含義。如果將服飾置于人類文明的宏觀命題下,在東西方文明的發(fā)展進(jìn)程中,由民族文化差異造就的著裝樣式的演變,則是承載民族歷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原始符號,尤其是當(dāng)中華民族處于農(nóng)耕文明時期,外來統(tǒng)治者對于占領(lǐng)國服飾的同化與改造,往往被視為對民族性的毀滅性打擊。例如,明末清初,滿清政府初步穩(wěn)定統(tǒng)治后,立即強(qiáng)制推行滿族服飾政策,“剃發(fā)易服,不從者斬”。這項(xiàng)強(qiáng)硬舉措立即遭到了南方漢人的全面抵制,江浙一帶的漢人士大夫群體最終用生命捍衛(wèi)了最后的尊嚴(yán)。19世紀(jì)中后葉,古老的中華農(nóng)耕文明被動地邁入由西方列強(qiáng)建立的工業(yè)文明體系中,在傳統(tǒng)鄉(xiāng)村文化向現(xiàn)代都市文化轉(zhuǎn)型的過程中,國人的著裝習(xí)慣逐漸西化,但在戲曲、繪畫、小說等藝術(shù)作品中,依舊時常出現(xiàn)對于古人及其服飾的展示和敘述,人們通過消費(fèi)和觀看這些文化產(chǎn)品,以追思古老文明的歷史文化與精神本源,以標(biāo)注中華民族在世界文明中的身份和地位。20世紀(jì)20年代,上海正處于新文化運(yùn)動所孕育的都市文化場域中,在“西學(xué)東漸,東西交融”的時代背景下,文言文、舞臺戲等本土傳統(tǒng)的言說方式已經(jīng)無法滿足新興市民階層的生活和文化需求,城市中漸趨流行的報紙、雜志等新興媒體為通俗白話的“摩登”表達(dá)搭建了更為高效的傳播平臺。在新舊文化碰撞的時代背景下,出現(xiàn)了極為有趣的社會現(xiàn)象:一方面,城市中涌現(xiàn)的大量“新文化”迅速被市民們“消化”和“吸收”,就連魯迅先生來到上海后,也隨即迷上了電影這一新生事物。另一方面,文學(xué)、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傾向似乎依然遵循著“舊文化”的規(guī)律,鴛鴦蝴蝶派小說、武俠小說、神話演義讀本等一大批內(nèi)置了“善惡有報、忠奸對立”等傳統(tǒng)倫理道德觀念的通俗白話文本,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底層市民的審美情趣。于是,這些“新瓶裝舊酒”的通俗讀本在摩登上海的大街小巷盛極一時。恰逢此時,標(biāo)榜“注重舊道德,舊倫理,發(fā)揚(yáng)中華文明,力避歐化”的天一電影公司老板覺察到古代民間故事所蘊(yùn)含的巨大商機(jī),遂沿用自己的戲班班底,借助服裝這一鮮明的文化符號,將婢史傳說、才子佳人等民間通俗故事搬上銀幕。自此,《義妖白蛇傳》《梁祝痛史》等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古裝電影應(yīng)運(yùn)而生。古裝電影的成功并非商業(yè)投機(jī)引發(fā)的一個偶然的現(xiàn)象,如前所述,在20世紀(jì)20年代蓬勃發(fā)展的中國都市文化場域中,觀看古裝電影一方面滿足了上海新興市民階層對于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想象,同時也完成了一場關(guān)乎新文化的摩登消費(fèi)體驗(yàn)。盡管古裝電影在中國商業(yè)電影競爭熱潮中釋放出了驚人的商業(yè)競爭力,但在國民政府的精英階層眼中,這些愚昧無知、怪力亂神的神怪片和自甘墮落、帶有情色元素的古裝片皆應(yīng)被禁拍。“1930年2月3日,電檢會決定禁止‘形狀怪異驚世駭俗’之古裝影片,并于7日通過禁止古裝片辦法。”[1]于是,在國民政府的強(qiáng)勢干預(yù)下,古裝電影創(chuàng)作的蓬勃態(tài)勢戛然而止,然而,寄托著民族文化想象的古裝電影并未就此消亡,在上海租界、香港乃至南洋諸國,中國古裝電影依舊作為一個重要的商業(yè)類型而延續(xù)著生命,等待著歷史的因緣際會。
二、古裝電影敘事中的文化表述
電影《頭號玩家》敘事解析
【摘要】《頭號玩家》是好萊塢王牌導(dǎo)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新作,可謂玩轉(zhuǎn)了虛擬與現(xiàn)實(shí),給廣大影迷和游戲迷帶來巨大的驚喜和視覺享受。《頭號玩家》中有幾十部經(jīng)典電影的互文、數(shù)十個典型電影或動漫人物的互文、幾十個經(jīng)典游戲的互文和音樂、符號、文本互文以及現(xiàn)實(shí)世界的互文,甚至影片中的舞臺置景、服裝設(shè)計、游戲武器也有大量互文存在。諸多互文的應(yīng)用構(gòu)成電影的故事情節(jié)并推動了電影的發(fā)展,可以說互文策略在《頭號玩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guān)鍵詞】互文性;互文;敘事;游戲
《頭號玩家》是著名導(dǎo)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新作,備受熱捧,在大陸上映首周票房高達(dá)3.91億元,24天票房即突破13億元。《頭號玩家》敘事中的互文是該電影的一大亮點(diǎn),正是互文性策略在其中的應(yīng)用,給觀眾帶來一個又一個驚喜,引發(fā)了強(qiáng)烈共鳴。
一、《頭號玩家》與互文性理論概述
《頭號玩家》電影根據(jù)恩斯特•克萊恩的同名小說改編,采用線性敘事,講述2045年的未來故事。那時現(xiàn)實(shí)中的世界混亂不堪,生存環(huán)境極端惡劣,人們生活在集裝箱搭成的“疊樓區(qū)”里,許多人為逃避現(xiàn)實(shí)而將希望寄托于風(fēng)靡世界的VR游戲“綠洲”之中。“綠洲”創(chuàng)始人哈利迪在臨終前宣布,將億萬身家留給尋獲他隱藏在游戲中的彩蛋的游戲玩家,玩家們就此展開了盛大的尋寶之旅。男主韋德•沃茲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沉迷游戲、生活困頓,但在“綠洲”的虛擬世界中卻是名氣玩家,他歷經(jīng)各種磨難找到了隱藏在關(guān)卡中的三把鑰匙,最終尋獲游戲中的彩蛋,同時收獲了愛情與事業(yè)。互文性概念最早由茱莉婭•克里斯蒂娃提出,她認(rèn)為“任何文本的建構(gòu)都是引言的鑲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zhuǎn)化”[1]。隨著研究的發(fā)展,互文性從純文本層面逐漸擴(kuò)展到影視、音樂、繪畫等非文本領(lǐng)域。學(xué)者秦海鷹這樣定義互文性:“互文性是一個文本(主文本)把其他文本(互文本)納入自身的現(xiàn)象,是一個文本與其他文本發(fā)生關(guān)系的特性。”[2]可以說,一個文本如果與其他文本發(fā)生了某些聯(lián)系或產(chǎn)生呼應(yīng),就是一種互文。電影《頭號玩家》中的互文幾乎無處不在,大到故事情節(jié),小到人物服裝、道具、場景元素,都是互文性的組合。本文對電影中的互文敘事表現(xiàn)和互文性策略應(yīng)用做具體分析,以感受互文性對電影的獨(dú)特意義。
二、《頭號玩家》中的互文敘事表現(xiàn)
熱門標(biāo)簽
電影發(fā)展論文 電影海報 電影敘事 電影美學(xué) 電影文化論文 電影劇本 電影院 電影研究 電影畢業(yè)論文 電影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