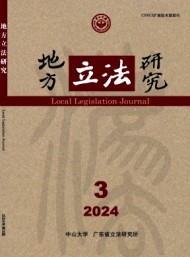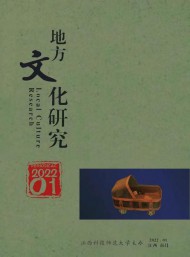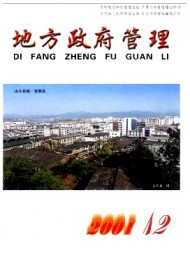地方自治范文10篇
時(shí)間:2024-01-20 08:33:53
導(dǎo)語(yǔ):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yàn),為你推薦的十篇地方自治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地方自治研究論文
摘要:地方自治是近代憲政的有機(jī)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羅馬的自治城市,后成為資產(chǎn)階級(jí)反對(duì)封建專制,實(shí)現(xiàn)參與和人權(quán)保障的表現(xiàn)形式。各國(guó)在長(zhǎng)期的歷史流變過(guò)程中,結(jié)合本國(guó)情況,發(fā)展了不同的地方自治理論,大體有:保護(hù)說(shuō)、欽定說(shuō)、傳來(lái)說(shuō)、固有權(quán)說(shuō)、制度性保障說(shuō)、人民主權(quán)說(shuō)、人權(quán)保障說(shuō)、法人說(shuō)、地方政府論、權(quán)力分立制衡說(shuō)。地方自治被認(rèn)為是對(duì)全國(guó)性政府過(guò)度集權(quán)的一種制衡力量,其理論有一些共同之處,即以中央地方利益上的對(duì)立作為解決中央地方關(guān)系的觀念前提,發(fā)展和確保地方自治權(quán)力的實(shí)現(xiàn),在堅(jiān)持國(guó)家主權(quán)和國(guó)家統(tǒng)一原則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意愿,滿足他們的參與愿望,實(shí)現(xiàn)生動(dòng)、活潑的地方生活。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下,傳統(tǒng)地方自治理論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
關(guān)鍵詞:地方自治,地方分權(quán),中央集權(quán),中央地方關(guān)系
地方自治是近代憲政的有機(jī)組成部分,“無(wú)論對(duì)任何一種憲法體制來(lái)說(shuō),都需要把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問(wèn)題作為民主國(guó)家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予以明確定位”。[1](P187)與此同時(shí),很多國(guó)家和國(guó)際組織重申地方自治原則。1985年通過(guò)的多國(guó)條約《歐洲地方自治憲章》,1985年通過(guò)、1993年再次通過(guò)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加重了對(duì)地方自治的關(guān)注,這意味著在今天,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的積極意義在世界開(kāi)始得到討論,并逐步得到明確。與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相伴隨的是地方公共團(tuán)體事務(wù)優(yōu)先原則的確立,即市鎮(zhèn)村最優(yōu)先、然后是省市縣優(yōu)先的事務(wù)分配原則,而中央政府只負(fù)責(zé)全國(guó)民、全國(guó)家性質(zhì)的事務(wù)。[1](P187)地方自治及地方自主恰好體現(xiàn)了《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在序言中的主張,實(shí)現(xiàn)一種“源于人民,服務(wù)于人民的政治”的政治理想。因此,基于地方分權(quán)的地方自治在“緩和中央權(quán)力過(guò)于集中的弊端方面,改善和提高政府活動(dòng)的效率,激發(fā)地方的獨(dú)創(chuàng)精神,釋放出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革新能力”[1](P187)方面的作用已越來(lái)越成為人權(quán)和民主主義觀念和制度的輔助成分。因此,認(rèn)真探討地方自治理論,對(duì)我國(guó)權(quán)力下放的實(shí)踐和中央地方關(guān)系的完善不無(wú)裨益。
地方自治的起源
一般認(rèn)為,用于某一地域意義上的地方自治來(lái)源于早期的自治市。“自治市”最早的定義起源于羅馬,當(dāng)時(shí)的羅馬帝國(guó)授予一些城市一定的特權(quán)。羅馬帝國(guó)衰亡之后,這一做法在歐洲沿襲下來(lái)。在歐洲,地方自治最早是對(duì)城市而言的,自治是捍衛(wèi)城市特權(quán)的理論根據(jù),是實(shí)現(xiàn)城市自由的手段,其在政治和組織上的典型特征是實(shí)行代議制。[2](P15)因此,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是分不開(kāi)的。
自治,其字面意思為“自己管理自己”,或“自己治理自己”。[3](P73)從表面上看,自治與“他治”相對(duì),有人就持此論。[4](P1100)但其實(shí)不然,自治非與“他治”相對(duì),而與“官治”相對(duì)。日本學(xué)者阿部齊等人認(rèn)為,“自治”與“統(tǒng)治”是分別位于兩個(gè)極端的概念,它的本來(lái)含義是自己的事由自己負(fù)責(zé)處理。而“地方”一詞與中央相對(duì),因而“地方自治”的反義詞是“官治”(中央統(tǒng)治)或中央集權(quán)。[5]此處意義上的地方自治是政治學(xué)領(lǐng)域中的意思,而涉及到政治,必與國(guó)家分不開(kāi),須從探討和思考國(guó)家與個(gè)人的關(guān)系處著手。地方自治是在與國(guó)家概念相對(duì)的意義上展開(kāi)的。有學(xué)者認(rèn)為,“地方自治是相對(duì)于中央政府對(duì)于全國(guó)的絕對(duì)控制而言的,它是對(duì)集中制的突破”。[6](P2)地方政府是實(shí)現(xiàn)個(gè)人自由和分散過(guò)分中央集權(quán)危險(xiǎn)的方式,[2](P23)說(shuō)的就是這個(gè)意思。我國(guó)清末討論地方自治問(wèn)題時(shí),對(duì)自治與官治之間的關(guān)系已有清楚論述。如梁?jiǎn)⒊瑥恼w結(jié)構(gòu)說(shuō)明自治與官治的關(guān)系,認(rèn)為“集權(quán)與自治二者,相依相輔,相維相系,然后一國(guó)之政體乃完”。[7]當(dāng)時(shí)的留學(xué)生也對(duì)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展開(kāi)討論,認(rèn)為“官府為國(guó)家直接行政機(jī)關(guān),以直接維持國(guó)權(quán)之目的”,“自治體為國(guó)家間接之行政機(jī)關(guān),以地方之人,治地方之事,而間接以達(dá)國(guó)家行政之目的”,故“自治之制,蓋所以補(bǔ)官治之不足,而與官治相輔而行”。[8](P617)
地方自治學(xué)研究論文
摘要:地方自治是近代憲政的有機(jī)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羅馬的自治城市,后成為資產(chǎn)階級(jí)反對(duì)封建專制,實(shí)現(xiàn)參與和人權(quán)保障的表現(xiàn)形式。各國(guó)在長(zhǎng)期的歷史流變過(guò)程中,結(jié)合本國(guó)情況,發(fā)展了不同的地方自治理論,大體有:保護(hù)說(shuō)、欽定說(shuō)、傳來(lái)說(shuō)、固有權(quán)說(shuō)、制度性保障說(shuō)、人民主權(quán)說(shuō)、人權(quán)保障說(shuō)、法人說(shuō)、地方政府論、權(quán)力分立制衡說(shuō)。地方自治被認(rèn)為是對(duì)全國(guó)性政府過(guò)度集權(quán)的一種制衡力量,其理論有一些共同之處,即以中央地方利益上的對(duì)立作為解決中央地方關(guān)系的觀念前提,發(fā)展和確保地方自治權(quán)力的實(shí)現(xiàn),在堅(jiān)持國(guó)家主權(quán)和國(guó)家統(tǒng)一原則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意愿,滿足他們的參與愿望,實(shí)現(xiàn)生動(dòng)、活潑的地方生活。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下,傳統(tǒng)地方自治理論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
關(guān)鍵詞:地方自治,地方分權(quán),中央集權(quán),中央地方關(guān)系
地方自治是近代憲政的有機(jī)組成部分,“無(wú)論對(duì)任何一種憲法體制來(lái)說(shuō),都需要把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問(wèn)題作為民主國(guó)家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予以明確定位”。[1](P187)與此同時(shí),很多國(guó)家和國(guó)際組織重申地方自治原則。1985年通過(guò)的多國(guó)條約《歐洲地方自治憲章》,1985年通過(guò)、1993年再次通過(guò)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加重了對(duì)地方自治的關(guān)注,這意味著在今天,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的積極意義在世界開(kāi)始得到討論,并逐步得到明確。與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相伴隨的是地方公共團(tuán)體事務(wù)優(yōu)先原則的確立,即市鎮(zhèn)村最優(yōu)先、然后是省市縣優(yōu)先的事務(wù)分配原則,而中央政府只負(fù)責(zé)全國(guó)民、全國(guó)家性質(zhì)的事務(wù)。[1](P187)地方自治及地方自主恰好體現(xiàn)了《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在序言中的主張,實(shí)現(xiàn)一種“源于人民,服務(wù)于人民的政治”的政治理想。因此,基于地方分權(quán)的地方自治在“緩和中央權(quán)力過(guò)于集中的弊端方面,改善和提高政府活動(dòng)的效率,激發(fā)地方的獨(dú)創(chuàng)精神,釋放出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革新能力”[1](P187)方面的作用已越來(lái)越成為人權(quán)和民主主義觀念和制度的輔助成分。因此,認(rèn)真探討地方自治理論,對(duì)我國(guó)權(quán)力下放的實(shí)踐和中央地方關(guān)系的完善不無(wú)裨益。
地方自治的起源
一般認(rèn)為,用于某一地域意義上的地方自治來(lái)源于早期的自治市。“自治市”最早的定義起源于羅馬,當(dāng)時(shí)的羅馬帝國(guó)授予一些城市一定的特權(quán)。羅馬帝國(guó)衰亡之后,這一做法在歐洲沿襲下來(lái)。在歐洲,地方自治最早是對(duì)城市而言的,自治是捍衛(wèi)城市特權(quán)的理論根據(jù),是實(shí)現(xiàn)城市自由的手段,其在政治和組織上的典型特征是實(shí)行代議制。[2](P15)因此,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是分不開(kāi)的。
自治,其字面意思為“自己管理自己”,或“自己治理自己”。[3](P73)從表面上看,自治與“他治”相對(duì),有人就持此論。[4](P1100)但其實(shí)不然,自治非與“他治”相對(duì),而與“官治”相對(duì)。日本學(xué)者阿部齊等人認(rèn)為,“自治”與“統(tǒng)治”是分別位于兩個(gè)極端的概念,它的本來(lái)含義是自己的事由自己負(fù)責(zé)處理。而“地方”一詞與中央相對(duì),因而“地方自治”的反義詞是“官治”(中央統(tǒng)治)或中央集權(quán)。[5]此處意義上的地方自治是政治學(xué)領(lǐng)域中的意思,而涉及到政治,必與國(guó)家分不開(kāi),須從探討和思考國(guó)家與個(gè)人的關(guān)系處著手。地方自治是在與國(guó)家概念相對(duì)的意義上展開(kāi)的。有學(xué)者認(rèn)為,“地方自治是相對(duì)于中央政府對(duì)于全國(guó)的絕對(duì)控制而言的,它是對(duì)集中制的突破”。[6](P2)地方政府是實(shí)現(xiàn)個(gè)人自由和分散過(guò)分中央集權(quán)危險(xiǎn)的方式,[2](P23)說(shuō)的就是這個(gè)意思。我國(guó)清末討論地方自治問(wèn)題時(shí),對(duì)自治與官治之間的關(guān)系已有清楚論述。如梁?jiǎn)⒊瑥恼w結(jié)構(gòu)說(shuō)明自治與官治的關(guān)系,認(rèn)為“集權(quán)與自治二者,相依相輔,相維相系,然后一國(guó)之政體乃完”。[7]當(dāng)時(shí)的留學(xué)生也對(duì)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展開(kāi)討論,認(rèn)為“官府為國(guó)家直接行政機(jī)關(guān),以直接維持國(guó)權(quán)之目的”,“自治體為國(guó)家間接之行政機(jī)關(guān),以地方之人,治地方之事,而間接以達(dá)國(guó)家行政之目的”,故“自治之制,蓋所以補(bǔ)官治之不足,而與官治相輔而行”。[8](P617)
地方自治學(xué)說(shuō)評(píng)析論文
摘要:地方自治是近代憲政的有機(jī)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羅馬的自治城市,后成為資產(chǎn)階級(jí)反對(duì)封建專制,實(shí)現(xiàn)參與和人權(quán)保障的表現(xiàn)形式。各國(guó)在長(zhǎng)期的歷史流變過(guò)程中,結(jié)合本國(guó)情況,發(fā)展了不同的地方自治理論,大體有:保護(hù)說(shuō)、欽定說(shuō)、傳來(lái)說(shuō)、固有權(quán)說(shuō)、制度性保障說(shuō)、人民主權(quán)說(shuō)、人權(quán)保障說(shuō)、法人說(shuō)、地方政府論、權(quán)力分立制衡說(shuō)。地方自治被認(rèn)為是對(duì)全國(guó)性政府過(guò)度集權(quán)的一種制衡力量,其理論有一些共同之處,即以中央地方利益上的對(duì)立作為解決中央地方關(guān)系的觀念前提,發(fā)展和確保地方自治權(quán)力的實(shí)現(xiàn),在堅(jiān)持國(guó)家主權(quán)和國(guó)家統(tǒng)一原則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意愿,滿足他們的參與愿望,實(shí)現(xiàn)生動(dòng)、活潑的地方生活。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下,傳統(tǒng)地方自治理論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
關(guān)鍵詞:地方自治,地方分權(quán),中央集權(quán),中央地方關(guān)系
地方自治是近代憲政的有機(jī)組成部分,“無(wú)論對(duì)任何一種憲法體制來(lái)說(shuō),都需要把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問(wèn)題作為民主國(guó)家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予以明確定位”。[1](P187)與此同時(shí),很多國(guó)家和國(guó)際組織重申地方自治原則。1985年通過(guò)的多國(guó)條約《歐洲地方自治憲章》,1985年通過(guò)、1993年再次通過(guò)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加重了對(duì)地方自治的關(guān)注,這意味著在今天,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的積極意義在世界開(kāi)始得到討論,并逐步得到明確。與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相伴隨的是地方公共團(tuán)體事務(wù)優(yōu)先原則的確立,即市鎮(zhèn)村最優(yōu)先、然后是省市縣優(yōu)先的事務(wù)分配原則,而中央政府只負(fù)責(zé)全國(guó)民、全國(guó)家性質(zhì)的事務(wù)。[1](P187)地方自治及地方自主恰好體現(xiàn)了《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在序言中的主張,實(shí)現(xiàn)一種“源于人民,服務(wù)于人民的政治”的政治理想。因此,基于地方分權(quán)的地方自治在“緩和中央權(quán)力過(guò)于集中的弊端方面,改善和提高政府活動(dòng)的效率,激發(fā)地方的獨(dú)創(chuàng)精神,釋放出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革新能力”[1](P187)方面的作用已越來(lái)越成為人權(quán)和民主主義觀念和制度的輔助成分。因此,認(rèn)真探討地方自治理論,對(duì)我國(guó)權(quán)力下放的實(shí)踐和中央地方關(guān)系的完善不無(wú)裨益。
地方自治的起源
一般認(rèn)為,用于某一地域意義上的地方自治來(lái)源于早期的自治市。“自治市”最早的定義起源于羅馬,當(dāng)時(shí)的羅馬帝國(guó)授予一些城市一定的特權(quán)。羅馬帝國(guó)衰亡之后,這一做法在歐洲沿襲下來(lái)。在歐洲,地方自治最早是對(duì)城市而言的,自治是捍衛(wèi)城市特權(quán)的理論根據(jù),是實(shí)現(xiàn)城市自由的手段,其在政治和組織上的典型特征是實(shí)行代議制。[2](P15)因此,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是分不開(kāi)的。
自治,其字面意思為“自己管理自己”,或“自己治理自己”。[3](P73)從表面上看,自治與“他治”相對(duì),有人就持此論。[4](P1100)但其實(shí)不然,自治非與“他治”相對(duì),而與“官治”相對(duì)。日本學(xué)者阿部齊等人認(rèn)為,“自治”與“統(tǒng)治”是分別位于兩個(gè)極端的概念,它的本來(lái)含義是自己的事由自己負(fù)責(zé)處理。而“地方”一詞與中央相對(duì),因而“地方自治”的反義詞是“官治”(中央統(tǒng)治)或中央集權(quán)。[5]此處意義上的地方自治是政治學(xué)領(lǐng)域中的意思,而涉及到政治,必與國(guó)家分不開(kāi),須從探討和思考國(guó)家與個(gè)人的關(guān)系處著手。地方自治是在與國(guó)家概念相對(duì)的意義上展開(kāi)的。有學(xué)者認(rèn)為,“地方自治是相對(duì)于中央政府對(duì)于全國(guó)的絕對(duì)控制而言的,它是對(duì)集中制的突破”。[6](P2)地方政府是實(shí)現(xiàn)個(gè)人自由和分散過(guò)分中央集權(quán)危險(xiǎn)的方式,[2](P23)說(shuō)的就是這個(gè)意思。我國(guó)清末討論地方自治問(wèn)題時(shí),對(duì)自治與官治之間的關(guān)系已有清楚論述。如梁?jiǎn)⒊瑥恼w結(jié)構(gòu)說(shuō)明自治與官治的關(guān)系,認(rèn)為“集權(quán)與自治二者,相依相輔,相維相系,然后一國(guó)之政體乃完”。[7]當(dāng)時(shí)的留學(xué)生也對(duì)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展開(kāi)討論,認(rèn)為“官府為國(guó)家直接行政機(jī)關(guān),以直接維持國(guó)權(quán)之目的”,“自治體為國(guó)家間接之行政機(jī)關(guān),以地方之人,治地方之事,而間接以達(dá)國(guó)家行政之目的”,故“自治之制,蓋所以補(bǔ)官治之不足,而與官治相輔而行”。[8](P617)
孫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透析
摘要:現(xiàn)代政治發(fā)展理論認(rèn)為,一定形式的地方自治,是政治現(xiàn)代化的重要條件。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對(duì)西方資產(chǎn)階級(jí)的地方自治理論與實(shí)賤給予了很大的關(guān)注。地方自治思想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之重要內(nèi)容,貫穿其民主革合思想發(fā)展的始終,值得后人認(rèn)真學(xué)習(xí)與研究。
關(guān)鍵詞:孫中山地方自治直接民權(quán)
孫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可劃分為產(chǎn)生、發(fā)展和成熟三個(gè)階段。
早在1897年,孫中山在與宮崎寅藏、平山周談話時(shí)指出:“余以人群自治為政治之極致,故于政治之精神,執(zhí)共和主義。”這是孫中山首次提出地方自治的主張。隨后,孫中山在與興中會(huì)骨干陳少白、鄭士良等8人在致港督仆力書(shū)中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于都內(nèi)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所謂中央政府者,舉民望所歸之人為之首,統(tǒng)轄水陸各軍,宰理交涉事物。惟其主權(quán)仍在憲法之內(nèi),設(shè)立議會(huì),由各省貢士若干名以充議員,以駐京公使為暫時(shí)顧問(wèn)局員。”“所謂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選派駐省總督一人,以為一省之首。設(shè)立省議會(huì),由各縣貢士若干名為議員。所有該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權(quán)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遙制。至于會(huì)內(nèi)之代議士,本由民間選舉”。在信中,孫中山不僅正式提出了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張,而且為實(shí)行地方自治設(shè)計(jì)出了具體方案。1905-1906年,在其手訂的《同盟會(huì)宣言》和《中國(guó)同盟會(huì)革命方略》中,孫中山將革命過(guò)程劃分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gè)階段,此即后期的革命程序論。其中約法之治,即“軍政府授權(quán)地方自治權(quán)于人民,而自總攬國(guó)事之時(shí)代”。這是孫中山首次將“地方自治”寫(xiě)進(jìn)正式的綱領(lǐng)性文件,它標(biāo)志著地方自治思想的初步形成。
辛亥革命后,迫于形勢(shì),孫中山?jīng)Q定讓位于袁世凱,但他對(duì)地方自治的重視并未因此稍減。在袁世凱倒行逆施,復(fù)辟帝制時(shí),他毅然宣布討袁護(hù)國(guó),并在其討袁檄文中將“停罷自治”列為袁世凱的主要罪狀之一。袁世凱死后,民國(guó)政治形式上回歸民主,但孫中山痛感民國(guó)“基礎(chǔ)尚不堅(jiān)固”,認(rèn)識(shí)到“欲民國(guó)之鞏固,必先建其基礎(chǔ)”,而“地方自治,乃建設(shè)國(guó)家之基礎(chǔ)”。他指出:“吾國(guó)自推翻帝制,五年以來(lái),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實(shí)地方自治不發(fā)達(dá)。若地方自治既完備,國(guó)家既可鞏固。”這一時(shí)期,孫中山對(duì)地方自治簡(jiǎn)直到了人迷的程度,僅在1916年7月至8月間,他以地方自治為主題的演講就達(dá)六次之多,而在其后的各種場(chǎng)合對(duì)地方自治的宣傳更是難以計(jì)數(shù)。為促進(jìn)地方自治的實(shí)行,孫中山于1920年發(fā)表了《地方自治實(shí)行法》一文,對(duì)試辦地方自治的區(qū)域范圍、步驟和方法作出了具體規(guī)劃。而在其兼任部長(zhǎng)的內(nèi)政部中,孫中山更是專門設(shè)立了“地方自治局”,意在將地方自治落到實(shí)處。這一切均標(biāo)志著孫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發(fā)展到了一個(gè)新的高度。
隨著孫中山政治思想的演進(jìn),他的地方自治思想在他去世前的幾年間得到了長(zhǎng)足的發(fā)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他先是發(fā)表《中華民國(guó)建設(shè)之基礎(chǔ)》一文,對(duì)中央與地方的關(guān)系、主權(quán)在民的含義和民治與官治等問(wèn)題進(jìn)行了具體的論述,最后指出,要實(shí)現(xiàn)主權(quán)在民,達(dá)致民治,必須要執(zhí)行四個(gè)方略,即分縣自治、全民自治、五權(quán)分立和國(guó)民大會(huì)。其中分縣自治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蓋無(wú)分縣自治,則人民無(wú)所憑籍,所謂全民自治必?zé)o由實(shí)現(xiàn)。無(wú)全民政治,則雖有五權(quán)分立,國(guó)民大會(huì),亦未由舉主權(quán)在民之實(shí)也。……當(dāng)知中華民國(guó)之建設(shè),必當(dāng)以人民為基礎(chǔ),而欲以人民為基礎(chǔ),必當(dāng)先行分縣自治。”但局勢(shì)的進(jìn)展并非一帆風(fēng)順,面對(duì)復(fù)雜多變的政治局面和勢(shì)單力薄的現(xiàn)狀,孫中山感到困惑絕望。“孫中山在絕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guó)人對(duì)中國(guó)人的幫助,歡迎中國(guó)共產(chǎn)黨與他合作。”這直接導(dǎo)致了孫中山從舊三民主義向新三民主義的轉(zhuǎn)變,而“國(guó)民黨一大”則是這種轉(zhuǎn)變的主要標(biāo)志。1924年1月23日,在孫中山的主持下,國(guó)民黨發(fā)表了由孫中山起草的《中國(guó)國(guó)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huì)宣言》和《國(guó)民政府建國(guó)大綱》。《宣言》的第三部分為國(guó)民之政綱,該政綱的對(duì)內(nèi)政策的前三條規(guī)定的全是地方自治的相關(guān)內(nèi)容,而《大綱》則用了多達(dá)11個(gè)條款來(lái)規(guī)定地方自治,舉凡地方自治開(kāi)始的時(shí)間、規(guī)則的制定、應(yīng)辦的事項(xiàng)、執(zhí)行的程序和達(dá)到的目的無(wú)不羅列詳備。這兩個(gè)對(duì)國(guó)民黨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文件的發(fā)表標(biāo)志著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完備與成熟。
地方自治對(duì)策研究論文
論文摘要:
地方自治是近代憲政的有機(jī)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羅馬的自治城市,后成為資產(chǎn)階級(jí)反對(duì)封建專制,實(shí)現(xiàn)參與和人權(quán)保障的表現(xiàn)形式。各國(guó)在長(zhǎng)期的歷史流變過(guò)程中,結(jié)合本國(guó)情況,發(fā)展了不同的地方自治理論,大體有:保護(hù)說(shuō)、欽定說(shuō)、傳來(lái)說(shuō)、固有權(quán)說(shuō)、制度性保障說(shuō)、人民主權(quán)說(shuō)、人權(quán)保障說(shuō)、法人說(shuō)、地方政府論、權(quán)力分立制衡說(shuō)。地方自治被認(rèn)為是對(duì)全國(guó)性政府過(guò)度集權(quán)的一種制衡力量,其理論有一些共同之處,即以中央地方利益上的對(duì)立作為解決中央地方關(guān)系的觀念前提,發(fā)展和確保地方自治權(quán)力的實(shí)現(xiàn),在堅(jiān)持國(guó)家主權(quán)和國(guó)家統(tǒng)一原則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意愿,滿足他們的參與愿望,實(shí)現(xiàn)生動(dòng)、活潑的地方生活。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下,傳統(tǒng)地方自治理論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
關(guān)鍵詞:地方自治,地方分權(quán),中央集權(quán),中央地方關(guān)系
隨著社會(huì)的發(fā)展,經(jīng)濟(jì)、政治及觀念上的變化促使各要素進(jìn)行重新整合。科技發(fā)展和全球化趨勢(shì)進(jìn)-步壓縮空間,政府職能轉(zhuǎn)化引發(fā)的社會(huì)事務(wù)的增多釋放和增加了更多的權(quán)力,打破了原來(lái)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壟斷權(quán)力和社會(huì)資源的狀態(tài),擴(kuò)大了參與主體的范圍,中央地方關(guān)系的格局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因此地方自治觀念面臨著新的發(fā)展。
一、地方自治的起源
1、地方自治的含義
孫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探究論文
論文關(guān)鍵詞:孫中山地方自治直接民權(quán)
論文摘要:現(xiàn)代政治發(fā)展理論認(rèn)為,一定形式的地方自治,是政治現(xiàn)代化的重要條件。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對(duì)西方資產(chǎn)階級(jí)的地方自治理論與實(shí)賤給予了很大的關(guān)注。地方自治思想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之重要內(nèi)容,貫穿其民主革合思想發(fā)展的始終,值得后人認(rèn)真學(xué)習(xí)與研究。
孫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可劃分為產(chǎn)生、發(fā)展和成熟三個(gè)階段。
早在1897年,孫中山在與宮崎寅藏、平山周談話時(shí)指出:“余以人群自治為政治之極致,故于政治之精神,執(zhí)共和主義。”這是孫中山首次提出地方自治的主張。隨后,孫中山在與興中會(huì)骨干陳少白、鄭士良等8人在致港督仆力書(shū)中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于都內(nèi)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所謂中央政府者,舉民望所歸之人為之首,統(tǒng)轄水陸各軍,宰理交涉事物。惟其主權(quán)仍在憲法之內(nèi),設(shè)立議會(huì),由各省貢士若干名以充議員,以駐京公使為暫時(shí)顧問(wèn)局員。”“所謂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選派駐省總督一人,以為一省之首。設(shè)立省議會(huì),由各縣貢士若干名為議員。所有該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權(quán)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遙制。至于會(huì)內(nèi)之代議士,本由民間選舉”。在信中,孫中山不僅正式提出了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張,而且為實(shí)行地方自治設(shè)計(jì)出了具體方案。1905-1906年,在其手訂的《同盟會(huì)宣言》和《中國(guó)同盟會(huì)革命方略》中,孫中山將革命過(guò)程劃分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gè)階段,此即后期的革命程序論。其中約法之治,即“軍政府授權(quán)地方自治權(quán)于人民,而自總攬國(guó)事之時(shí)代”。這是孫中山首次將“地方自治”寫(xiě)進(jìn)正式的綱領(lǐng)性文件,它標(biāo)志著地方自治思想的初步形成。
辛亥革命后,迫于形勢(shì),孫中山?jīng)Q定讓位于袁世凱,但他對(duì)地方自治的重視并未因此稍減。在袁世凱倒行逆施,復(fù)辟帝制時(shí),他毅然宣布討袁護(hù)國(guó),并在其討袁檄文中將“停罷自治”列為袁世凱的主要罪狀之一。袁世凱死后,民國(guó)政治形式上回歸民主,但孫中山痛感民國(guó)“基礎(chǔ)尚不堅(jiān)固”,認(rèn)識(shí)到“欲民國(guó)之鞏固,必先建其基礎(chǔ)”,而“地方自治,乃建設(shè)國(guó)家之基礎(chǔ)”。他指出:“吾國(guó)自推翻帝制,五年以來(lái),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實(shí)地方自治不發(fā)達(dá)。若地方自治既完備,國(guó)家既可鞏固。”這一時(shí)期,孫中山對(duì)地方自治簡(jiǎn)直到了人迷的程度,僅在1916年7月至8月間,他以地方自治為主題的演講就達(dá)六次之多,而在其后的各種場(chǎng)合對(duì)地方自治的宣傳更是難以計(jì)數(shù)。為促進(jìn)地方自治的實(shí)行,孫中山于1920年發(fā)表了《地方自治實(shí)行法》一文,對(duì)試辦地方自治的區(qū)域范圍、步驟和方法作出了具體規(guī)劃。而在其兼任部長(zhǎng)的內(nèi)政部中,孫中山更是專門設(shè)立了“地方自治局”,意在將地方自治落到實(shí)處。這一切均標(biāo)志著孫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發(fā)展到了一個(gè)新的高度。
隨著孫中山政治思想的演進(jìn),他的地方自治思想在他去世前的幾年間得到了長(zhǎng)足的發(fā)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他先是發(fā)表《中華民國(guó)建設(shè)之基礎(chǔ)》一文,對(duì)中央與地方的關(guān)系、主權(quán)在民的含義和民治與官治等問(wèn)題進(jìn)行了具體的論述,最后指出,要實(shí)現(xiàn)主權(quán)在民,達(dá)致民治,必須要執(zhí)行四個(gè)方略,即分縣自治、全民自治、五權(quán)分立和國(guó)民大會(huì)。其中分縣自治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蓋無(wú)分縣自治,則人民無(wú)所憑籍,所謂全民自治必?zé)o由實(shí)現(xiàn)。無(wú)全民政治,則雖有五權(quán)分立,國(guó)民大會(huì),亦未由舉主權(quán)在民之實(shí)也。……當(dāng)知中華民國(guó)之建設(shè),必當(dāng)以人民為基礎(chǔ),而欲以人民為基礎(chǔ),必當(dāng)先行分縣自治。”但局勢(shì)的進(jìn)展并非一帆風(fēng)順,面對(duì)復(fù)雜多變的政治局面和勢(shì)單力薄的現(xiàn)狀,孫中山感到困惑絕望。“孫中山在絕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guó)人對(duì)中國(guó)人的幫助,歡迎中國(guó)共產(chǎn)黨與他合作。”這直接導(dǎo)致了孫中山從舊三民主義向新三民主義的轉(zhuǎn)變,而“國(guó)民黨一大”則是這種轉(zhuǎn)變的主要標(biāo)志。1924年1月23日,在孫中山的主持下,國(guó)民黨發(fā)表了由孫中山起草的《中國(guó)國(guó)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huì)宣言》和《國(guó)民政府建國(guó)大綱》。《宣言》的第三部分為國(guó)民之政綱,該政綱的對(duì)內(nèi)政策的前三條規(guī)定的全是地方自治的相關(guān)內(nèi)容,而《大綱》則用了多達(dá)11個(gè)條款來(lái)規(guī)定地方自治,舉凡地方自治開(kāi)始的時(shí)間、規(guī)則的制定、應(yīng)辦的事項(xiàng)、執(zhí)行的程序和達(dá)到的目的無(wú)不羅列詳備。這兩個(gè)對(duì)國(guó)民黨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文件的發(fā)表標(biāo)志著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完備與成熟。
法律鍥入:政治沖突的秩序和地方自治的缺失
──棲村一樁訴訟案件的解讀
民間法和國(guó)家法的分野和沖突是法學(xué)界關(guān)注農(nóng)村治理的重要視角(蘇力,2000;田成有,2002)。在村治研究當(dāng)中,考察國(guó)家法和民間法的沖突、效力、整合是建立在現(xiàn)代國(guó)家政權(quán)建設(shè)和現(xiàn)代化話語(yǔ)之上的。顯然,由于這樣的特殊背景,使得這些研究帶有強(qiáng)烈的政治言說(shuō)傾向:即政權(quán)建設(shè)和政治力量是實(shí)證法學(xué)研究的不可忽視的維度。但是由于學(xué)科和分析話語(yǔ)的選擇關(guān)系,這些研究又偏偏放棄了對(duì)于政權(quán)建設(shè)和政治力量的正面解剖,使得案例描述滯宥于特定的法律關(guān)系。本文考慮將法律關(guān)系上產(chǎn)生的政治影響和道德影響放在政治制度設(shè)計(jì)──特別是立憲選擇的角度──考察,試圖揭示村莊治理的困境產(chǎn)生的原因和法律制度設(shè)定的理論資源。通過(guò)對(duì)于一個(gè)村莊微觀視角分析,我們?cè)噲D建立地方自治在政治制度演進(jìn)和法律制度構(gòu)建中的初始和淵源的地位。
表面上看,棲村的一樁村干部之間、村干部和村委會(huì)之間的訴訟案,集中體現(xiàn)了民主的政治模式引入村莊社區(qū)后的制度困境──對(duì)于「民主」生存狀態(tài)的迷惑和對(duì)于民主力量的迷戀構(gòu)成的復(fù)合體。與此同時(shí),訴訟引起的村治危機(jī)和社會(huì)成本的最后承擔(dān)者就是棲村社區(qū),法律作為力量鍥入后就產(chǎn)生一個(gè)非均衡的格局,然后這個(gè)格局的均衡的力量又重新在社區(qū)內(nèi)醞釀。不過(guò),我們對(duì)棲村訴訟事件的研究在以下三個(gè)方面得到初步啟發(fā):一是法律作為國(guó)家力量的一種在對(duì)村莊作用時(shí)和行政權(quán)力大為不同,法律的剛性使得政治權(quán)威在村莊范圍得到全面、毫無(wú)余地的調(diào)整,但是正是這樣的調(diào)整使得村莊社區(qū)道德化氣氛被破壞,而重塑這一氛圍需要村民承擔(dān)較多的學(xué)習(xí)成本;二是村莊約定的個(gè)體交易方式和法人交易方式大為不同,實(shí)際上,大宗村莊資產(chǎn)引發(fā)的內(nèi)部沖突就是對(duì)于交易規(guī)則的不認(rèn)同,對(duì)于交易爭(zhēng)端解決的過(guò)程,可以認(rèn)為是達(dá)致交易規(guī)則認(rèn)同的過(guò)程。三是政治組織通過(guò)國(guó)家認(rèn)定的程序集中了大部分人的政治愿望,但是這種程序解決了權(quán)利授予的合法性問(wèn)題,卻難以培育村民自發(fā)的政治忠誠(chéng)。此時(shí),村委會(huì)可能被政治精英當(dāng)作政治競(jìng)爭(zhēng)和玩弄權(quán)術(shù)的工具。這些初步的印象引導(dǎo)出一列問(wèn)題,法律忠誠(chéng)和政治忠誠(chéng)在村莊政治中是如何設(shè)定的,法律調(diào)整政治組織設(shè)定的立法意圖和表達(dá)的正義觀念是甚么,村委會(huì)的法律主體資格是甚么或者法律調(diào)整的限度是甚么,精英政治的動(dòng)員有效性和法律程序自治的外圍支持是如何改變村莊政治秩序的,村莊治理的法律邊界和政治邊界如何劃分──甚么制度可以導(dǎo)致這樣的劃分和維護(hù)真正的村民權(quán)利。這些問(wèn)題是我們面對(duì)棲村案例的思考方向。
本文的展開(kāi),就是隨著訴訟事件的發(fā)展而進(jìn)行鋪陳的。
一訴訟事件的文本解讀
訴訟的起因是對(duì)于村里一樁場(chǎng)地出租協(xié)議的爭(zhēng)議。前任村委會(huì)將村里的一塊場(chǎng)地以租賃的形式交由鄰縣一M姓老板MYT搞建材市場(chǎng)開(kāi)發(fā)經(jīng)營(yíng),棲村的場(chǎng)地約5,500平方,合同期限為11年,由MYT出資建設(shè),合同規(guī)定:前7年MYT建市場(chǎng)的投入作為租金,后4年每年交租金25萬(wàn)元1。合同生效時(shí)間為2001年12月。同年底,村民委員會(huì)進(jìn)行改選,PXY不再擔(dān)任村委會(huì)主任,繼任村委會(huì)主任PSM上臺(tái)。由于涂鎮(zhèn)城市化進(jìn)程加快,位于鎮(zhèn)區(qū)中心地帶的棲村的地價(jià)上升奇快。原先簽訂的合約顯示出利益上的反差,投資方獲利巨大,而村委會(huì)財(cái)務(wù)狀況不佳又加劇了對(duì)原來(lái)決策的懷疑。這些懷疑,在起訴書(shū)的文本上得到最為完整的表現(xiàn)。
自治學(xué)說(shuō)評(píng)析管理論文
摘要:地方自治是近代憲政的有機(jī)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羅馬的自治城市,后成為資產(chǎn)階級(jí)反對(duì)封建專制,實(shí)現(xiàn)參與和人權(quán)保障的表現(xiàn)形式。各國(guó)在長(zhǎng)期的歷史流變過(guò)程中,結(jié)合本國(guó)情況,發(fā)展了不同的地方自治理論,大體有:保護(hù)說(shuō)、欽定說(shuō)、傳來(lái)說(shuō)、固有權(quán)說(shuō)、制度性保障說(shuō)、人民主權(quán)說(shuō)、人權(quán)保障說(shuō)、法人說(shuō)、地方政府論、權(quán)力分立制衡說(shuō)。地方自治被認(rèn)為是對(duì)全國(guó)性政府過(guò)度集權(quán)的一種制衡力量,其理論有一些共同之處,即以中央地方利益上的對(duì)立作為解決中央地方關(guān)系的觀念前提,發(fā)展和確保地方自治權(quán)力的實(shí)現(xiàn),在堅(jiān)持國(guó)家主權(quán)和國(guó)家統(tǒng)一原則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意愿,滿足他們的參與愿望,實(shí)現(xiàn)生動(dòng)、活潑的地方生活。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下,傳統(tǒng)地方自治理論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
關(guān)鍵詞:地方自治,地方分權(quán),中央集權(quán),中央地方關(guān)系
地方自治是近代憲政的有機(jī)組成部分,“無(wú)論對(duì)任何一種憲法體制來(lái)說(shuō),都需要把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問(wèn)題作為民主國(guó)家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予以明確定位”。[1](P187)與此同時(shí),很多國(guó)家和國(guó)際組織重申地方自治原則。1985年通過(guò)的多國(guó)條約《歐洲地方自治憲章》,1985年通過(guò)、1993年再次通過(guò)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加重了對(duì)地方自治的關(guān)注,這意味著在今天,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的積極意義在世界開(kāi)始得到討論,并逐步得到明確。與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相伴隨的是地方公共團(tuán)體事務(wù)優(yōu)先原則的確立,即市鎮(zhèn)村最優(yōu)先、然后是省市縣優(yōu)先的事務(wù)分配原則,而中央政府只負(fù)責(zé)全國(guó)民、全國(guó)家性質(zhì)的事務(wù)。[1](P187)地方自治及地方自主恰好體現(xiàn)了《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在序言中的主張,實(shí)現(xiàn)一種“源于人民,服務(wù)于人民的政治”的政治理想。因此,基于地方分權(quán)的地方自治在“緩和中央權(quán)力過(guò)于集中的弊端方面,改善和提高政府活動(dòng)的效率,激發(fā)地方的獨(dú)創(chuàng)精神,釋放出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革新能力”[1](P187)方面的作用已越來(lái)越成為人權(quán)和民主主義觀念和制度的輔助成分。因此,認(rèn)真探討地方自治理論,對(duì)我國(guó)權(quán)力下放的實(shí)踐和中央地方關(guān)系的完善不無(wú)裨益。
地方自治的起源
一般認(rèn)為,用于某一地域意義上的地方自治來(lái)源于早期的自治市。“自治市”最早的定義起源于羅馬,當(dāng)時(shí)的羅馬帝國(guó)授予一些城市一定的特權(quán)。羅馬帝國(guó)衰亡之后,這一做法在歐洲沿襲下來(lái)。在歐洲,地方自治最早是對(duì)城市而言的,自治是捍衛(wèi)城市特權(quán)的理論根據(jù),是實(shí)現(xiàn)城市自由的手段,其在政治和組織上的典型特征是實(shí)行代議制。[2](P15)因此,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是分不開(kāi)的。
自治,其字面意思為“自己管理自己”,或“自己治理自己”。[3](P73)從表面上看,自治與“他治”相對(duì),有人就持此論。[4](P1100)但其實(shí)不然,自治非與“他治”相對(duì),而與“官治”相對(duì)。日本學(xué)者阿部齊等人認(rèn)為,“自治”與“統(tǒng)治”是分別位于兩個(gè)極端的概念,它的本來(lái)含義是自己的事由自己負(fù)責(zé)處理。而“地方”一詞與中央相對(duì),因而“地方自治”的反義詞是“官治”(中央統(tǒng)治)或中央集權(quán)。[5]此處意義上的地方自治是政治學(xué)領(lǐng)域中的意思,而涉及到政治,必與國(guó)家分不開(kāi),須從探討和思考國(guó)家與個(gè)人的關(guān)系處著手。地方自治是在與國(guó)家概念相對(duì)的意義上展開(kāi)的。有學(xué)者認(rèn)為,“地方自治是相對(duì)于中央政府對(duì)于全國(guó)的絕對(duì)控制而言的,它是對(duì)集中制的突破”。[6](P2)地方政府是實(shí)現(xiàn)個(gè)人自由和分散過(guò)分中央集權(quán)危險(xiǎn)的方式,[2](P23)說(shuō)的就是這個(gè)意思。我國(guó)清末討論地方自治問(wèn)題時(shí),對(duì)自治與官治之間的關(guān)系已有清楚論述。如梁?jiǎn)⒊瑥恼w結(jié)構(gòu)說(shuō)明自治與官治的關(guān)系,認(rèn)為“集權(quán)與自治二者,相依相輔,相維相系,然后一國(guó)之政體乃完”。[7]當(dāng)時(shí)的留學(xué)生也對(duì)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展開(kāi)討論,認(rèn)為“官府為國(guó)家直接行政機(jī)關(guān),以直接維持國(guó)權(quán)之目的”,“自治體為國(guó)家間接之行政機(jī)關(guān),以地方之人,治地方之事,而間接以達(dá)國(guó)家行政之目的”,故“自治之制,蓋所以補(bǔ)官治之不足,而與官治相輔而行”。[8](P617)
清末城市自治思想論文
開(kāi)放基層政權(quán)、實(shí)行地方自治是清末社會(huì)各界的強(qiáng)烈呼聲,也是清政府籌備立憲的重要舉措。考察當(dāng)時(shí)的輿論傾向以及自治活動(dòng)的實(shí)施,可以發(fā)現(xiàn)側(cè)重城市推行地方自治的明確軌跡。
思想界更是依據(jù)西方國(guó)家的歷史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將城市自治視為實(shí)現(xiàn)政治民主化的根基所在,積極要求推進(jìn)城市自治,改革城市政治。作為尋求社會(huì)政治改良的方案,城市自治思想還與20世紀(jì)中國(guó)近代城市化進(jìn)程相伴隨,成為城市近代化在政治訴求方面的主要內(nèi)容,影響著城市的發(fā)展走向。盡管城市自治的實(shí)施效果與理想相去甚遠(yuǎn),但客觀上有助于近代城市的發(fā)展,成為推動(dòng)近代城市發(fā)展的主觀精神動(dòng)力。
一
地方自治是資本主義國(guó)家的一種地方管理制度,是西歐封建社會(huì)城市自治傳統(tǒng)在近代的發(fā)展和演變。鴉片戰(zhàn)爭(zhēng)前后,地方自治思想隨著對(duì)西方議會(huì)制度的介紹傳入中國(guó)。近年來(lái),學(xué)界對(duì)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研究相對(duì)比較充分,對(duì)清末城市自治運(yùn)動(dòng)也多有涉及①,但是對(duì)清末城市自治思想的形成、流變及其對(duì)20世紀(jì)較長(zhǎng)時(shí)段內(nèi)中國(guó)城市發(fā)展走向的影響尚缺乏梳理,本文擬在此宏觀角度作些努力。
城市自治思想盡管形成于清末,然而對(duì)西方
①研究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論著有沈懷玉:《清末西洋地方自治思想的輸入》,臺(tái)灣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8期(1979年10月);丁旭光:《近代中國(guó)地方自治研究》,廣州出版社1993年版等。研究清末城市自治運(yùn)動(dòng)的論文有吳桂龍:《清末上海地方自治運(yùn)動(dòng)述論》,載《紀(jì)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論文選》下冊(cè),中華書(shū)局1983年版;朱英:《戊戌至辛亥地方自治的發(fā)展———湖南保衛(wèi)局與上海總工程局之比較》,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等。
地方權(quán)力憲法化論文
摘要:地方權(quán)力的憲法化是商品(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國(guó)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不平衡的法律體現(xiàn)。地方權(quán)力憲法化是單一制和聯(lián)邦制國(guó)家憲法的共同規(guī)定“,二戰(zhàn)”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權(quán)力的憲法化成為世界憲政發(fā)展的潮流,就連具有中央集權(quán)傳統(tǒng)的法國(guó)也在1982年開(kāi)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quán)的改革。我國(guó)憲法應(yīng)適應(yīng)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要求,順應(yīng)世界憲政發(fā)展的潮流,盡快明確規(guī)定地方權(quán)力。
關(guān)鍵詞:商品(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單一制地方權(quán)力憲法化
地方到底應(yīng)該擁有哪些權(quán)力是我國(guó)憲法所沒(méi)有解決的問(wèn)題。在憲法學(xué)界,有的學(xué)者拘泥于傳統(tǒng),認(rèn)為在單一制國(guó)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權(quán)力完全由中央規(guī)定;有的學(xué)者在這一問(wèn)題上采取了實(shí)用的“描述主義”,對(duì)我國(guó)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現(xiàn)行憲法文本進(jìn)行描述,不加以評(píng)判;更多的學(xué)者在論及這一問(wèn)題時(shí)回避我國(guó)的“中央與地方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只論及單一制的優(yōu)越性,似乎我國(guó)憲法有關(guān)國(guó)家結(jié)構(gòu)形式的規(guī)定完美無(wú)缺。
在許多深諳中國(guó)歷史的學(xué)者的潛意識(shí)里,有一種擔(dān)心,他們害怕地方權(quán)力憲法化之后,地方主義會(huì)抬頭,會(huì)不利于國(guó)家的團(tuán)結(jié)統(tǒng)一。我們認(rèn)為這種心態(tài)是可以理解的,是學(xué)者社會(huì)歷史責(zé)任感的一種體現(xiàn),但這種擔(dān)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國(guó)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成功經(jīng)驗(yàn)表明,地方權(quán)力的憲法化不僅不會(huì)損害國(guó)家的統(tǒng)一和民族的團(tuán)結(jié),反而會(huì)加強(qiáng)這種團(tuán)結(jié)統(tǒng)一;另一方面,地方權(quán)力的憲法化有助于中央對(duì)地方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過(guò)法治化的手段確保國(guó)家的團(tuán)結(jié)統(tǒng)一。
一
地方權(quán)力憲法化是指在單一制國(guó)家由憲法明確規(guī)定地方在國(guó)家權(quán)力體系中的地位或由憲法明確規(guī)定地方權(quán)力由法律具體化。地方權(quán)力憲法化的本質(zhì)是憲政國(guó)家內(nèi)地方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不平衡,地方權(quán)力要求在憲法上的體現(xiàn),類似于自由狀態(tài)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會(huì)的法權(quán)要求。當(dāng)然地方權(quán)力要求與自然人或市民社會(huì)的法權(quán)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從歷史哲學(xué)的視角審視,地方權(quán)力憲法化是分權(quán)或限權(quán)的一極,也是憲法之源。王世杰、錢端升在論及憲法起源時(shí)說(shuō):“歐洲中世紀(jì)時(shí)代是封建時(shí)代,也可以說(shuō)是近現(xiàn)代憲法觀念萌芽時(shí)代。在這個(gè)時(shí)代內(nèi),君主的勢(shì)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諸侯或各城市團(tuán)體的限制;而國(guó)王對(duì)于所屬諸侯或所屬城市,往往以特別法律承認(rèn)各諸侯或各城市的特權(quán)。此項(xiàng)特權(quán),即為國(guó)王權(quán)力的限制;此項(xiàng)法律,亦頗類于近代的憲法或根本法。”①當(dāng)然現(xiàn)代地方權(quán)力的憲法化與歐洲中世紀(jì)諸侯或城市的特權(quán)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屬性相同,它們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