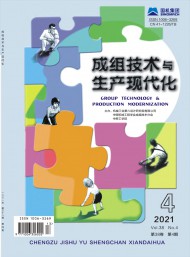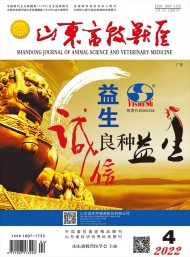第六代范文10篇
時間:2024-01-20 10:38:43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第六代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第六代電影的審美探討論文
[論文關鍵詞]第六代個人化都市邊緣人小人物影像
[論文摘要]以張元、婁燁、王小帥、賈樟柯等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導演群體,以個人化的敘事策略和對都市場景與邊緣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以及強烈的影像塑造意識,體現出他們共同的“代”的意識與審美特質。
以張元、婁燁、王小帥、賈樟柯等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導演群體是在80年代相對開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時也是在中國電影面對一個新的環境中開始拍攝的。與“第五代”相比,他們有著諸多不足以自成一派的因素,甚至其中很多導演也拒絕這種代際劃分。但就筆者個人的看法,隨著“第六代”作品的不斷問世,他們在電影審美追求上的共同之處也漸次清晰。因此,對他們電影的整體特征進行描述,也許是可行的。
一、個人化的敘事策略
“個人化”這一概念,濫觴于日本的“私小說”創作,它是一種無視社會意義、專寫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寫作。是在現代主義哲學思想活躍,“反傳統情緒、個人主義思想,為之彌漫。一般人由關心國家變為關注自我,由國家主義轉為‘沉潛的個人主義’”的社會思潮下,某些對自身處境不滿、對社會極端失望的作家的產物。筆者之所以借用“個人化”這一概念,是因為“第六代”的敘述藝術,與小說界的“個人化”寫作很類似。
“個人化”敘述的特征首先是,放棄“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回歸個人的敘事狀態,遠離公共話語和宏大敘述,而面向個人的狹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從《頭發亂了》,到《北京雜種》、《小武》、《長大成人》、《蘇州河》、《月蝕》、《陽光燦爛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無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長的煩惱等存在主義意義上的精神狀態,成為影片中作為主人公的個人化敘述的中心話語,雖然在這些作品中有社會因素存在,但那不過是作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們的作品中,盡管有很多對社會陰暗現象的揭示,但敘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氣,而只是一種“平民當事人”的個人化講述與宣泄。其次,是敘述中總有紀實與自傳的敘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慮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們的故事在大眾心目中幾乎無足輕重,但由于導演與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齡、經歷、命運方面往往具有相關性——如姜文,在《日光燦爛的日子》中,干脆找一個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與自己經歷的相關——人物形象便不僅是解讀影片的顯形符碼,還成為解讀導演的隱形符碼,因此有理由認為“第六代”電影具有紀實與自傳的敘述性質。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長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當的內心獨白方式,表現某種敢于抗爭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無拘無束的精神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個人化”敘述成了第六代表達個人情緒的一種策略。
第六代電影保守傾向論文
電影是以影像為手段的敘事,在傳達知識、情感、價值和信仰上具有獨特的優勢,其修辭方式具有敘事的共性,也有其特性。本文試圖從讀者反應和敘事修辭中倚重的價值體系兩者的關聯,把握“第六代”電影的文本現象。
沖擊當下社會的原始沖動
網上有一篇影片,是關于劉冰鑒的《哭泣的女人》,雖然這部影片在第五十五屆戛納電影節上受到好評,評審團歷史上第一次授予主演廖琴以評委會特別獎,以表彰她精湛的表演。這篇文章還是認為《哭泣的女人》是一部讓人感到惡心的影片,理由是女主角竟然能夠在情人的懷里為丈夫哭泣,而在監獄里又向勞教干部出賣自己的肉體,在丈夫死后還能繼續哭喪職業,收取大把的鈔票,總之,作者在這部影片里根本看不到社會和人性美麗的一絲一毫,便認為影片虛假造作,不符合現實。
無獨有偶,網上的另一則評論,關于張元的《回家過年》,認為張元這部影片是招安之作,文章對兩人回家時一路上遇到的好人好事尤其感到不滿,比如除夕夜機動車的司機怎么可能把車費從三元降到二元呢?沒這么好的人,更別說有女警官這樣的好心人,放著年飯不吃陪著犯人回家的,“這部影片對于生活的粉飾以及對于人性賣好一面的表現已經到了不顧現實,不求真實的地步。”(注:《磚之看<回家過年>》銀海網。)這種聲音我們聽到的也許比前者更多一些,很多“第六代”導演在體制內拍片時都會受到如此的詰難。
這兩個例子雖然是觀眾觀賞影片時當下感受的兩個極端,他們一邊已經厭倦了高大全式的好人,一邊也不喜歡一無是處的所謂壞人,尤其當這個人是影片的主人公時,但卻說明了電影的敘事修辭都在這一點上遭遇了失敗。
導演總是希望觀眾能認同自己的人物,反過來說,很少有編導會把自己的主人公故意設置成一個令人惡心的人物,可愛的人物總是容易引起觀眾的同情,然后進而認同編導所想要傳達的價值觀念。于是問題就從這里產生,首先編導想要傳達什么樣的價值觀念,其次什么樣的人物是可愛的?前一個問題比較明確,編導都想在影片中表達一定的價值觀念,剩下的問題是這個價值觀念的表達是明確的還是模糊的。后一個問題需要觀眾和編導共同完成,這樣問題就更為復雜,觀眾和編導能達成共識嗎?如果能,那么是在什么基礎上?還有,第一個問題和第二個問題之間又存在著什么樣的關聯呢。實際上,這正是影片的修辭策略和修辭目的所要研究的。
第六代電影審美特征論文
摘要:以張元、婁燁、王小帥、賈樟柯等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導演群體,以個人化的敘事策略和對都市場景與邊緣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以及強烈的影像塑造意識,體現出他們共同的“代”的意識與審美特質。
關鍵詞:第六代個人化都市邊緣人小人物影像
以張元、婁燁、王小帥、賈樟柯等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導演群體是在80年代相對開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時也是在中國電影面對一個新的環境中開始拍攝的。與“第五代”相比,他們有著諸多不足以自成一派的因素,甚至其中很多導演也拒絕這種代際劃分。但就筆者個人的看法,隨著“第六代”作品的不斷問世,他們在電影審美追求上的共同之處也漸次清晰。因此,對他們電影的整體特征進行描述,也許是可行的。
一、個人化的敘事策略
“個人化”這一概念,濫觴于日本的“私小說”創作,它是一種無視社會意義、專寫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寫作。是在現代主義哲學思想活躍,“反傳統情緒、個人主義思想,為之彌漫。一般人由關心國家變為關注自我,由國家主義轉為‘沉潛的個人主義’”的社會思潮下,某些對自身處境不滿、對社會極端失望的作家的產物。筆者之所以借用“個人化”這一概念,是因為“第六代”的敘述藝術,與小說界的“個人化”寫作很類似。
“個人化”敘述的特征首先是,放棄“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回歸個人的敘事狀態,遠離公共話語和宏大敘述,而面向個人的狹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從《頭發亂了》,到《北京雜種》、《小武》、《長大成人》、《蘇州河》、《月蝕》、《陽光燦爛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無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長的煩惱等存在主義意義上的精神狀態,成為影片中作為主人公的個人化敘述的中心話語,雖然在這些作品中有社會因素存在,但那不過是作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們的作品中,盡管有很多對社會陰暗現象的揭示,但敘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氣,而只是一種“平民當事人”的個人化講述與宣泄。其次,是敘述中總有紀實與自傳的敘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慮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們的故事在大眾心目中幾乎無足輕重,但由于導演與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齡、經歷、命運方面往往具有相關性——如姜文,在《日光燦爛的日子》中,干脆找一個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與自己經歷的相關——人物形象便不僅是解讀影片的顯形符碼,還成為解讀導演的隱形符碼,因此有理由認為“第六代”電影具有紀實與自傳的敘述性質。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長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當的內心獨白方式,表現某種敢于抗爭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無拘無束的精神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個人化”敘述成了第六代表達個人情緒的一種策略。
第六代電影審美特征論文
摘要:以張元、婁燁、王小帥、賈樟柯等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導演群體,以個人化的敘事策略和對都市場景與邊緣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以及強烈的影像塑造意識,體現出他們共同的“代”的意識與審美特質。
關鍵詞:第六代個人化都市邊緣人小人物影像
以張元、婁燁、王小帥、賈樟柯等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導演群體是在80年代相對開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時也是在中國電影面對一個新的環境中開始拍攝的。與“第五代”相比,他們有著諸多不足以自成一派的因素,甚至其中很多導演也拒絕這種代際劃分。但就筆者個人的看法,隨著“第六代”作品的不斷問世,他們在電影審美追求上的共同之處也漸次清晰。因此,對他們電影的整體特征進行描述,也許是可行的。
一、個人化的敘事策略
“個人化”這一概念,濫觴于日本的“私小說”創作,它是一種無視社會意義、專寫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寫作。是在現代主義哲學思想活躍,“反傳統情緒、個人主義思想,為之彌漫。一般人由關心國家變為關注自我,由國家主義轉為‘沉潛的個人主義’”的社會思潮下,某些對自身處境不滿、對社會極端失望的作家的產物。筆者之所以借用“個人化”這一概念,是因為“第六代”的敘述藝術,與小說界的“個人化”寫作很類似。
“個人化”敘述的特征首先是,放棄“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回歸個人的敘事狀態,遠離公共話語和宏大敘述,而面向個人的狹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從《頭發亂了》,到《北京雜種》、《小武》、《長大成人》、《蘇州河》、《月蝕》、《陽光燦爛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無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長的煩惱等存在主義意義上的精神狀態,成為影片中作為主人公的個人化敘述的中心話語,雖然在這些作品中有社會因素存在,但那不過是作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們的作品中,盡管有很多對社會陰暗現象的揭示,但敘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氣,而只是一種“平民當事人”的個人化講述與宣泄。其次,是敘述中總有紀實與自傳的敘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慮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們的故事在大眾心目中幾乎無足輕重,但由于導演與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齡、經歷、命運方面往往具有相關性——如姜文,在《日光燦爛的日子》中,干脆找一個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與自己經歷的相關——人物形象便不僅是解讀影片的顯形符碼,還成為解讀導演的隱形符碼,因此有理由認為“第六代”電影具有紀實與自傳的敘述性質。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長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當的內心獨白方式,表現某種敢于抗爭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無拘無束的精神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個人化”敘述成了第六代表達個人情緒的一種策略。
第六代電影保守傾向論文
電影是以影像為手段的敘事,在傳達知識、情感、價值和信仰上具有獨特的優勢,其修辭方式具有敘事的共性,也有其特性。本文試圖從讀者反應和敘事修辭中倚重的價值體系兩者的關聯,把握“第六代”電影的文本現象。
沖擊當下社會的原始沖動
網上有一篇影片,是關于劉冰鑒的《哭泣的女人》,雖然這部影片在第五十五屆戛納電影節上受到好評,評審團歷史上第一次授予主演廖琴以評委會特別獎,以表彰她精湛的表演。這篇文章還是認為《哭泣的女人》是一部讓人感到惡心的影片,理由是女主角竟然能夠在情人的懷里為丈夫哭泣,而在監獄里又向勞教干部出賣自己的肉體,在丈夫死后還能繼續哭喪職業,收取大把的鈔票,總之,作者在這部影片里根本看不到社會和人性美麗的一絲一毫,便認為影片虛假造作,不符合現實。
無獨有偶,網上的另一則評論,關于張元的《回家過年》,認為張元這部影片是招安之作,文章對兩人回家時一路上遇到的好人好事尤其感到不滿,比如除夕夜機動車的司機怎么可能把車費從三元降到二元呢?沒這么好的人,更別說有女警官這樣的好心人,放著年飯不吃陪著犯人回家的,“這部影片對于生活的粉飾以及對于人性賣好一面的表現已經到了不顧現實,不求真實的地步。”(注:《磚之看<回家過年>》銀海網。)這種聲音我們聽到的也許比前者更多一些,很多“第六代”導演在體制內拍片時都會受到如此的詰難。
這兩個例子雖然是觀眾觀賞影片時當下感受的兩個極端,他們一邊已經厭倦了高大全式的好人,一邊也不喜歡一無是處的所謂壞人,尤其當這個人是影片的主人公時,但卻說明了電影的敘事修辭都在這一點上遭遇了失敗。
導演總是希望觀眾能認同自己的人物,反過來說,很少有編導會把自己的主人公故意設置成一個令人惡心的人物,可愛的人物總是容易引起觀眾的同情,然后進而認同編導所想要傳達的價值觀念。于是問題就從這里產生,首先編導想要傳達什么樣的價值觀念,其次什么樣的人物是可愛的?前一個問題比較明確,編導都想在影片中表達一定的價值觀念,剩下的問題是這個價值觀念的表達是明確的還是模糊的。后一個問題需要觀眾和編導共同完成,這樣問題就更為復雜,觀眾和編導能達成共識嗎?如果能,那么是在什么基礎上?還有,第一個問題和第二個問題之間又存在著什么樣的關聯呢。實際上,這正是影片的修辭策略和修辭目的所要研究的。
第六代電影審美創新特性探析論文
摘要:以張元、婁燁、王小帥、賈樟柯等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導演群體,以個人化的敘事策略和對都市場景與邊緣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以及強烈的影像塑造意識,體現出他們共同的“代”的意識與審美特質。
關鍵詞:第六代個人化都市邊緣人小人物影像
以張元、婁燁、王小帥、賈樟柯等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導演群體是在80年代相對開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時也是在中國電影面對一個新的環境中開始拍攝的。與“第五代”相比,他們有著諸多不足以自成一派的因素,甚至其中很多導演也拒絕這種代際劃分。但就筆者個人的看法,隨著“第六代”作品的不斷問世,他們在電影審美追求上的共同之處也漸次清晰。因此,對他們電影的整體特征進行描述,也許是可行的。
一、個人化的敘事策略
“個人化”這一概念,濫觴于日本的“私小說”創作,它是一種無視社會意義、專寫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寫作。是在現代主義哲學思想活躍,“反傳統情緒、個人主義思想,為之彌漫。一般人由關心國家變為關注自我,由國家主義轉為‘沉潛的個人主義’”的社會思潮下,某些對自身處境不滿、對社會極端失望的作家的產物。筆者之所以借用“個人化”這一概念,是因為“第六代”的敘述藝術,與小說界的“個人化”寫作很類似。
“個人化”敘述的特征首先是,放棄“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回歸個人的敘事狀態,遠離公共話語和宏大敘述,而面向個人的狹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從《頭發亂了》,到《北京雜種》、《小武》、《長大成人》、《蘇州河》、《月蝕》、《陽光燦爛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無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長的煩惱等存在主義意義上的精神狀態,成為影片中作為主人公的個人化敘述的中心話語,雖然在這些作品中有社會因素存在,但那不過是作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們的作品中,盡管有很多對社會陰暗現象的揭示,但敘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氣,而只是一種“平民當事人”的個人化講述與宣泄。其次,是敘述中總有紀實與自傳的敘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慮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們的故事在大眾心目中幾乎無足輕重,但由于導演與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齡、經歷、命運方面往往具有相關性——如姜文,在《日光燦爛的日子》中,干脆找一個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與自己經歷的相關——人物形象便不僅是解讀影片的顯形符碼,還成為解讀導演的隱形符碼,因此有理由認為“第六代”電影具有紀實與自傳的敘述性質。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長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當的內心獨白方式,表現某種敢于抗爭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無拘無束的精神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個人化”敘述成了第六代表達個人情緒的一種策略。
第六代電影的審美特征分析論文
一、個人化的敘事策略
“個人化”這一概念,濫觴于日本的“私小說”創作,它是一種無視社會意義、專寫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寫作。是在現代主義哲學思想活躍,“反傳統情緒、個人主義思想,為之彌漫。一般人由關心國家變為關注自我,由國家主義轉為‘沉潛的個人主義’”的社會思潮下,某些對自身處境不滿、對社會極端失望的作家的產物。筆者之所以借用“個人化”這一概念,是因為“第六代”的敘述藝術,與小說界的“個人化”寫作很類似。
“個人化”敘述的特征首先是,放棄“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回歸個人的敘事狀態,遠離公共話語和宏大敘述,而面向個人的狹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從《頭發亂了》,到《北京雜種》、《小武》、《長大成人》、《蘇州河》、《月蝕》、《陽光燦爛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無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長的煩惱等存在主義意義上的精神狀態,成為影片中作為主人公的個人化敘述的中心話語,雖然在這些作品中有社會因素存在,但那不過是作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們的作品中,盡管有很多對社會陰暗現象的揭示,但敘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氣,而只是一種“平民當事人”的個人化講述與宣泄。其次,是敘述中總有紀實與自傳的敘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慮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們的故事在大眾心目中幾乎無足輕重,但由于導演與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齡、經歷、命運方面往往具有相關性——如姜文,在《日光燦爛的日子》中,干脆找一個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與自己經歷的相關——人物形象便不僅是解讀影片的顯形符碼,還成為解讀導演的隱形符碼,因此有理由認為“第六代”電影具有紀實與自傳的敘述性質。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長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當的內心獨白方式,表現某種敢于抗爭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無拘無束的精神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個人化”敘述成了第六代表達個人情緒的一種策略。
第六代導演的以個人化敘事傳達自我情緒在某種意義上表現為“即興創作”。電影不僅丟掉了戲劇的“拐杖”,而且完全不使用劇本,演員在導演情緒感覺的指揮下直接表演,整個電影的建構全部在剪輯室里完成,使電影在一定程度上徹底擺脫了文學的范疇。影片《北京雜種》就是導演張元即興創作的作品,并使導演體驗了這種即興創作中隨意自由的快感:“《北京雜種》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真正的自由的創作。我們那幫人,崔健、杜可風、還有舒琪,那次拍攝經歷是我最大的幸運。我也不知道第二天要拍什么,常常是憑著即興和隨意的想法去做。完全是把自己身邊的幾個人物放在一起,很自由的一個空間。”當然,這種即興創作顯然是第六代導演敘事叛逆性的一種極端表現,旨在表明與傳統的敘事風格的對立。同時,影片中插入了許多搖滾樂隊演出的場面,以此來打破故事的完整性。導演借助現代搖滾樂的叛逆性,在影片敘事中表達自我感受,使這部影片的敘事呈現出個人化、情緒化的特征。
第六代導演所選擇的這種個人化乃至情緒化的敘事策略,使他們放棄了“社會代言人”的角色,遠離公共話語和宏大敘事,回歸到個人的敘事狀態。受西方藝術電影的影響,他們追求的是自我方式的“純藝術”。而并不完全把電影當作“大眾的藝術”。因此在電影敘事中采用直截了當的內心獨自方式表現某種敢于抗爭的、玩世不恭的和任性的無拘無束的精神狀態。有的評論者把這種敘事狀態稱為“主體性敘述”,即將抽象的、邏輯的、清晰的、理性的思維,諸如思想主旨、哲學理念、生活見解,以及藝術風格與造詣等等,全部統領和提契著他們作品的具象敘述。或者通俗地說。就是在觀看他們作品的時候。常常會感到一個無形的解說者在那里對觀眾耳提面命。
二、都市場景與邊緣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
現代性視野電影讀解管理論文
[摘要]現代性,作為備受關注的熱點問題,得到眾多學者的認真反思。置身于現代性的學術視野,第六代電影的讀解可以從現代性反思、真實性深化、先鋒性探索三方面進行探討,審美現代性得以凸顯,正是在此意義上,第六代電影提供了一份可資解讀的文本。
[關鍵詞]現代性新生代真實性先鋒性
現代性作為百年來一個備受關注的熱點問題。得到眾多學者的認真反思;但是。迄今我們仍然不能對現代性問題有一個共同認可的定位、理解和闡述。目前,一個相對統一的界定是將現代性大致分為兩層:社會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社會現代性代表了一種在社會經濟層面強烈追求現代性的理想,這種現代性理想堅守“現代”的時間觀念和價值立場,追求“進步”、“解放”。這種“進步”、“解放”的信念建立在形而上的“歷史不斷進步”的基礎之上從而使現代性以及與之相關的“現代化”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步意識形態化成為一種“進步”的標志。審美現代性則作為審美活動是對現代性的回應,它以主體性和個性為核心,對工業資本主義及其階級社會的種種現實和觀念進行審美的反思和批判。因為社會現代性的極度發展會帶來極度膨脹的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從而排斥“人文理性”反過來異化人性的正常健康發展。
從九十年代初的嶄露頭角,第六代已經走過了近二十年的風風雨雨,今天,我們有理由對第六代走過的這二十年進行一次盤點,其電影的意義何在?在這二十年的風風雨雨里,有哪些得失可以留給后來人借鑒?
置身于現代性的視野筆者認為,第六代電影的讀解至少可以從以下三點進行探討:
一、現代性反思
導演電影審美特征管理論文
摘要第六代導演及其作品表現出了明顯的審美特征:刻意模糊敘事線索和淡化敘事情節,具有新內涵的寫意風格,對邊緣化群體的審美關照,著力于微觀敘事的寫實主義,強烈的文學化傾向,簡約凌厲地給觀眾營造大量想象空間的影像鋪排。這些審美特征促成了第六代導演在大眾審美視野內的崛起,從而形成了中國電影視覺媒介審美范疇內的全新文化景觀。
關鍵詞中國電影第六代導演審美特征突圍
新生代電影導演胡雪楊在其處女作《留守女士》(1992年上海電影制片廠出品)剛推出時。有意無意地向公眾宣稱:北京電影學院87屆五個班的同學是中國電影的第六代工作者。此話一出便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而“第六代導演”這一命名便不斷出現在大眾面前。
第六代導演的電影在文化底層上有著諸多相似之處。盡管這一藝術群體并沒有共同的藝術宣言,但從其歷史發展的脈絡和審美文化的指向性看卻有著基本的精神,從而使之在藝術追求和美學表達上呈現出某種同一性。這種同一性包含了他們對電影藝術的理解和他們所關注的一些命題,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隱含著他們對現實世界的態度。
本文并非要給第六代導演及其作品一個全面的評價,而是嘗試從審美文化和審美特征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影像表現,并努力尋找第六代的意識形態思維邏輯和美學實踐品格。
一、作為審美機制的電影
電影文化策略管理論文
本文是關于近20年中國電影兩大導演群體藝術創作的比較研究,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暫借用大家比較熟悉的“第五代”、“第六代”的稱謂,并從其導演藝術共性中梳理中10個關鍵詞,進行文化學的比較分析。由于學術界對“第五代”的研究相對深入且有著大體確定的觀點,因此對其論述相對簡略。
閱歷/體驗
第五代豐富而廣闊的生活閱歷,無疑成為其鮮明藝術風格得以形成的豐厚底蘊,也成為了其終生取之不盡的精神富礦。其對生活廣度的體認,對于生活艱辛的感受,對于苦難的認同,皆具有非常的經驗。于是在第五代導演的人生資歷上,“苦難”成為了其重要的標識而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并且成為了其傳奇性的經歷:“凱歌插隊”、“老謀子賣血”、“子牛為運糞船拉纖”……第五代在成就其藝術光輝的同時,也最終完成了作為一代人楷模的、歷經苦難的、富有人格魅力的男子漢群像的造型。正是一個病態的時代,造就了擁有健康體魄的一個群體。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由于時代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滯緩,第五代的個性意識都不同程度地被社會的群體意識所支配甚或代替,因之我們看到,他們在其擁有了豐富的生活閱歷的同時,既有的體制與經驗,卻壓抑了個性的極力舒展與自我的自由發揮。
而第六代則與第五代有著迥然相異的人生經歷,他們成長于經濟復蘇的開放時代,盡管他們沒有了第五代豐富的生活閱歷,然而其對生命的體驗卻大為深刻,如果說第五代在生命之軸的橫向上具有很大拓展,那么第六代則在生命之軸的縱向上不斷掘進。因此在觀念上,第六代不認同第五代“苦難成就藝術”的人生閱歷,并公開表示自己的不以為然:“我們的文化中有這樣一種對''''苦難''''的崇拜,而且似乎是獲得話語權的一種資本。因而有人便習慣性地要去占有''''苦難'''',將自己經歷過的自認為風暴,而別人,下一代經歷過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點坎坷。在他們的''''苦難''''與''''經歷''''面前,我們只有閉嘴。''''苦難''''成了一種霸權,并因此衍生出一種價值判斷。”“好像只有這種經歷才叫經歷,他們吃過的苦才叫苦。”[1](P167)于是他們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而這種要求,又與其青少年時期的人生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
如果對第六代的成長經歷稍作了解,我們就會發現,在生命的早期,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在小時候不約而同地曾受到病魔的折磨,而這正好與他們后來的創作發生了密切關系:“我的片子和我的人生經歷很有關系。我自己生過一場大病,這一點對我很重要,雖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得完這場病以后,我突然對一些事情看得很開。當你幾乎看到你的歸宿的時候,很多東西就沒有必要斤斤計較了。當時我躺在病床上的時候,突然覺得親情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都很無聊。我是一個宿命的人。這種情緒在作品中是不自然帶出來的,有時候不找著這種感覺,你就覺得影片沒勁。”[1](P214-215)“支氣管擴張盡管不是大病,但是很嚇人。隔一兩年復發,然后吐血,大口大口的吐血,呼吸很困難。”“我差不多十三四歲的時候開始第一次發作,然后每隔兩年就發作一次。這個發作期有七、八年的樣子,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轉換的階段我其實一直有病,我很慶幸有這種病,它沒有真實的危險,但是它給你一個死亡的幻覺,你真是大口的吐血,然后你窒息,然后覺得不行了。我現在是很不怕血的,我太知道血是什么東西了,一痰盂一痰盂的吐。那會兒就很孤獨,我大學沒考上,就看書,也不管功課。”[1](P152)
即使沒有經歷過大病的賈樟柯,卻在現實生活中看到了太多的生與死,也在自己的影片中探討著生命哲學的問題:“在自然的生、老、病、死背后,蘊含著生命的感傷,花總會凋零,人總有別無選擇的時候。無論如何,這部電影的主題是人,我想通過它去挖掘和展現人民之中蘊藏著的進步的力量;電影講述了群眾的一段經歷,那也是我時刻懷念的一段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