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范文10篇
時間:2024-01-21 21:57:17
導(dǎo)語: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yàn),為你推薦的十篇敦煌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敦煌壁畫藝術(shù)變革研究
【摘要】本文對受張大千畫展影響的林風(fēng)眠進(jìn)行個案研究,探尋其繪畫風(fēng)格、藝術(shù)思想的變化。林風(fēng)眠運(yùn)用其獨(dú)到的中西融合思想將繪畫理論推陳出新,在古老文明和新的藝術(shù)之間尋找平衡點(diǎn),將調(diào)和思想發(fā)揮到極致,對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史上藝術(shù)變革起到功不可沒的影響。因此,對于林風(fēng)眠的個案研究是具有很強(qiáng)的現(xiàn)實(shí)意義的,是引起人們對當(dāng)下美術(shù)發(fā)展的正視和深思的一個途徑。
【關(guān)鍵詞】西北寫生;藝術(shù)變革;敦煌壁畫
一、引言
19世紀(jì)到20世紀(jì),西北寫生變成一個熱門話題。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被發(fā)現(xiàn),伯希和走向敦煌,開啟了海內(nèi)外學(xué)者對敦煌的重視。民國政府同時發(fā)出“開發(fā)西部”的口號,有識之士奔赴敦煌,西行探尋。加之抗戰(zhàn)爆發(fā),“西學(xué)東漸”風(fēng)氣正熱,美術(shù)學(xué)者渴求將“西學(xué)東漸”吸取變?yōu)樽陨眇B(yǎng)料。出現(xiàn)了張大千、林風(fēng)眠、關(guān)山月、董希文、韓樂然等一代代美術(shù)家們,他們是西北美術(shù)寫生之行的開拓者,記錄、推廣敦煌美術(shù),為傳播敦煌美術(shù)做了開創(chuàng)性貢獻(xiàn)。中國畫壇自西北美術(shù)革命以來呈現(xiàn)出一種既繼承傳統(tǒng)又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光明景象。西北美術(shù)寫生之行不只是空間的轉(zhuǎn)移,同時也是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的轉(zhuǎn)移。1938年,自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的藝術(shù)青年到達(dá)延安,奔向黃土高原,構(gòu)建“延安學(xué)派”。1941年的西北藝術(shù)考察團(tuán)深入敦煌長達(dá)一年多,臨摹大量壁畫,他們走向文化現(xiàn)場,對藝術(shù)遺跡進(jìn)行考察與研究。在西北藝術(shù)考察期間,民族藝術(shù)走進(jìn)大眾視野,美術(shù)家對少數(shù)民族進(jìn)行刻畫,正視且尊重民族傳統(tǒng)文化,是藝術(shù)史上難得的視覺轉(zhuǎn)換和民族認(rèn)同增強(qiáng)的形象體現(xiàn),特別是20世紀(jì)30年代開始,被納入藝術(shù)研究的范疇,中國藝術(shù)類學(xué)術(shù)研究邊界拓展。寫生變成藝術(shù)家推崇的記錄方式,寫生作為一種觀察方法和創(chuàng)作手段,凝聚了畫家的個體想法與主體心性,同時承載了民族與時代的主題,可以顯現(xiàn)藝術(shù)與生活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是考察社會的一種重要手段、方法。與之前不同的是,從大多數(shù)的對景寫生變?yōu)閷θ藢懮缌诛L(fēng)眠的戲劇人物畫作,以及更為明顯的董希文的《苗女趕場》作品,改變中國藝術(shù)史在內(nèi)容、題材方面的一種結(jié)構(gòu)。西北美術(shù)寫生是東西部藝術(shù)共生互動的一種表現(xiàn),豐富了創(chuàng)作資源,增加民族認(rèn)同感的同時使藝術(shù)史再構(gòu)建。
二、林風(fēng)眠結(jié)緣西北后對其繪畫風(fēng)格的影響
林風(fēng)眠先生是“中西融合”這個藝術(shù)理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力求在“西學(xué)東漸”這一藝術(shù)背景下找尋中西融合的道路,而敦煌作為20世紀(jì)藝術(shù)西行運(yùn)動的終點(diǎn),其特殊的藝術(shù)地位引起了多數(shù)學(xué)者的關(guān)注,開啟了西北美術(shù)之行這一道路。這是一次對傳統(tǒng)的再認(rèn)識活動,也是一次對傳統(tǒng)的再創(chuàng)新活動。提到美術(shù)西行,不得不提到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重慶舉行的極為震撼的張大千臨摹壁畫展,林風(fēng)眠先生在看過此展后頗為感動,而后受其影響,進(jìn)行美術(shù)研究。林風(fēng)眠先生早期創(chuàng)作多以油畫為主,兼畫水墨山水、花鳥等。早年間先后赴法、德留學(xué),受到楊西斯老師的啟蒙,后受到表現(xiàn)主義思潮的影響,吸收其藝術(shù)精髓,在此基礎(chǔ)上不忘東方傳統(tǒng)藝術(shù),積極倡導(dǎo)二者的融合升華,渴求創(chuàng)造全新的繪畫風(fēng)格。其欣賞西方畫作中的表達(dá)欲和對世俗的批判欲,認(rèn)為應(yīng)該引進(jìn)西方自由創(chuàng)作的主張以及西方現(xiàn)代主義精神,而不是簡單引進(jìn)寫實(shí)主義、技法,在此基礎(chǔ)上創(chuàng)作了大量優(yōu)秀作品,例如1927年《人道》,吸收了西方藝術(shù)中的構(gòu)圖方式,將人體以幾何方式表達(dá),具有強(qiáng)烈的反抗和民主意識。再如1929年創(chuàng)作的《人類的痛苦》(見圖1)這一著名畫作,這一畫作也是林風(fēng)眠先生藝術(shù)風(fēng)格轉(zhuǎn)型的一件標(biāo)志性作品,他遭遇的熊君銳被殺害之痛,以及喪妻之痛,種種痛苦下他卻仍可以以清醒者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把所有感受到的痛苦嚼碎消化吐露在畫面中。畫中筆法粗獷有力,使用大筆觸,粗線條,畫面色調(diào)強(qiáng)烈而濃重,以幾何筆法為人物結(jié)構(gòu)進(jìn)行概括,透露出他個人的悲情又有中華民族面對苦難所背負(fù)的理想和詩意,這幅畫中體現(xiàn)其“為人生而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觀念。誠然,這幅畫與其之前畫做對比,人物都被一定程度的夸張化,形式感更為強(qiáng)烈。由于社會形勢所迫林風(fēng)眠先生不得不尋求新的道路,對水墨畫方面進(jìn)行思考與探索,而西北美術(shù)寫生的這些作品成為影響他轉(zhuǎn)換新道路的一個新途徑。林風(fēng)眠先生受到西北寫生作品的影響后創(chuàng)作出不同于之前的作品。一改之前沉郁的畫風(fēng),作品風(fēng)格更為明快,色調(diào)更為明朗,情緒也由強(qiáng)烈轉(zhuǎn)為平和。創(chuàng)作題材不再以油畫為主,而是多以風(fēng)景、仕女圖、花卉、戲劇人物為主,構(gòu)圖以方形構(gòu)圖為主,創(chuàng)作出《仕女彈阮圖》(見圖2)、《讀書仕女》《綠衣仕女》《戲曲一景——霸王別姬圖》等獨(dú)具自身特色的作品。他的作品深受敦煌壁畫中各類飛天、仕女圖的影響。敦煌壁畫中飛天鼻豐嘴小,五官勻稱,身材修長,衣裙飄曳,與林風(fēng)眠筆下的仕女圖的畫法極為相似。在莫高窟壁畫中的112窟《反彈琵琶》中右面第二任演奏阮咸(見圖3),其樣法與林風(fēng)眠筆下《仕女彈阮圖》如出一轍,衣服刻畫手法相似,姿勢相似,抱阮咸的手法也極為相似,敦煌壁畫對其繪畫生涯影響非常大。一系列仕女圖都具有高度的形式美感,筆法與之前大不相同,多為圓潤細(xì)膩的筆法,線條飄逸,柔中帶剛。背景多為重彩加特質(zhì)細(xì)筆加百分,營造背光透明的質(zhì)感,畫中仕女本身姿態(tài)多為優(yōu)雅文靜,眉眼低垂,衣物多采用大面積平涂,在平涂基礎(chǔ)上加以利落干凈的線條,簡單卻富有層次感,勾勒出仕女的輕盈體態(tài)。不同于當(dāng)代仕女圖,林風(fēng)眠先生筆下的侍女給人感覺若即若離的同時表現(xiàn)性極強(qiáng),富有很強(qiáng)的裝飾性。林風(fēng)眠先生時刻都不忘記中西融合這一藝術(shù)理念,在仕女圖中融合進(jìn)西方繪畫中速寫的以線畫形的手法,以及速寫中提倡線條的節(jié)奏感,同時他將東方的水墨畫法和水粉、水彩復(fù)合使用,獨(dú)具一格,東方與西方融會貫通,使其筆下仕女圖突出一種可望不可及的美。其作品《霸王別姬》系列更是將東西融合發(fā)揮到極致,利用立體畫派手法將人物造型概括為三角形、橢圓形等,同時還有民間剪紙的特色,是立體的、平面的、是東西融合這一理念的集大成者,是對西北藝術(shù)的一次再創(chuàng)造。
敦煌俗賦研究論文
一百年前,敦煌藏經(jīng)洞出土了數(shù)以萬計(jì)的中古時代的寫卷,其中有數(shù)量不少的以“賦”為名的作品和雖不以“賦”名篇但其實(shí)是賦體的作品。這些賦作敘述故事,語言通俗,節(jié)奏鏗鏘,押大體相近的韻,風(fēng)格詼諧,與傳統(tǒng)文人賦迥然不同。它的面世,立即引起了學(xué)術(shù)界的關(guān)注。鄭振鐸、容肇祖、傅蕓子先生分別把這類作品叫“小品賦”、“白話賦”、“民間賦”[1]。程毅中先生寫于1961年的《關(guān)于變文的幾點(diǎn)探索》[2],首次明確提出了“俗賦”這一概念。他說:“敦煌寫卷中,除了變文之外,還有一部分是敘事體的俗賦。”1963年出版的游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xué)史》中,有《俗賦》專節(jié),從此,“俗賦”之名作為中國文學(xué)史研究的一個文體概念,正式確立并很快得到學(xué)術(shù)界的認(rèn)可。
在敦煌俗賦問世的相當(dāng)長一段時間,學(xué)術(shù)界并沒有把它作為獨(dú)立的文體,而是作為“變文”的一類,所以敦煌俗賦的主要作品,都收錄在《敦煌變文集》中。而且一提起“俗賦”,人們只以為是敦煌俗賦,比如馬積高先生在他的《賦史》中就說:“所謂俗賦,是指清末從敦煌石室發(fā)現(xiàn)的用接近口語的通俗語言寫的賦和賦體文。”[3]這種觀點(diǎn),至今仍為一些學(xué)者所接受。
1993年,連云港東海縣出土了西漢時期的《神烏賦》,其文體特征同敦煌俗賦完全一樣。鄭振鐸先生在《中國俗文學(xué)史》中曾評價(jià)王褒的《僮約》是西漢留下的白話賦,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韓朋賦考》一文中還推斷西漢時期民間可能已有這種敘說故事、帶有韻語以使人易聽易記的賦體。《神烏賦》的出土,給鄭先生的說法一個鐵證,也給容先生的推斷一個明確肯定的回答。它把俗賦的歷史由點(diǎn)拉成了一條線,使我們對漢魏六朝以來一些帶有故事性、詼諧性和大體押韻的作品及其文體歸屬有了明確的認(rèn)識,說明在文人大賦蔚為大國的同時,俗賦作為一股不小的暗流一直潛行于地下,偶然也沖決地表涌出涓涓清溪,呈現(xiàn)它多采多姿的風(fēng)貌。
對俗賦進(jìn)行系統(tǒng)地清理和研究,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shí)際意義:1、可以充分證明賦這種文體本來就是從民間來的,它是民間故事、寓言、歌謠等多種技藝相融合的產(chǎn)物;2、它在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與其它各種文體有著千絲萬縷的依附、滲透和交叉關(guān)系。3、早期的賦以娛樂為目的,所以詼諧調(diào)侃是它的主要風(fēng)格特征。優(yōu)人正是利用了這種體裁,把它引入宮廷,逐漸文人化貴族化了。4、文人借用俗賦的形式把它逐漸貴族化的同時,民間俗賦仍然發(fā)展著,并且影響著文人賦的創(chuàng)作,從而形成了賦的“雅”“俗”兩條線索。由于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始終都是“士”的中心任務(wù),由于“士”人整體上對“俗賦”的排斥,因此“俗賦”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著于其它文體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5、俗賦給后世的其它通俗文體以具大的影響,如戲劇、南朝以來形成的講經(jīng)文、變文、唐宋話本等。
敦煌俗賦的文學(xué)史意義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擬從敦煌俗賦入手,并參照其它俗賦的情況,推論秦漢雜賦的有關(guān)情況。當(dāng)然從子孫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實(shí)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孫身上帶有祖宗的遺傳因子,從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應(yīng)該是沒有問題的。劉勰所謂“振葉尋根,觀瀾索源”,大概也有這個意思吧!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將賦分為屈原賦、陸賈賦、荀卿賦、雜賦四類。前三家按時間先后分列賦家姓名和作品數(shù)目,雜賦類以作品題材及數(shù)目為序,無作者姓名。關(guān)于前三類的分類標(biāo)準(zhǔn)和義例,章學(xué)誠、劉師培、章太炎等先生有精辟的論述[4]。而雜賦一類,雖著錄12家233篇賦作,但竟沒有一篇保存下來,故學(xué)者或推測為“后世之總集”,或以為三種之外而無法歸類者,悉入雜賦。顧實(shí)《漢書藝文志講疏》云:“此雜賦盡亡,不可征,蓋多雜詼諧,如《莊子》寓言之類者歟?”[5]現(xiàn)在我順著顧先生的意思,以敦煌俗賦和其它俗賦作為參照物,從若干蛛絲馬跡入手作些探測。
敦煌壁畫研究論文
在莫高窟150窟中有塊《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記》碑,碑文上記敘著:“爾其檐飛鷹翅,砌盤龍鱗,云霧生于戶牖,雷霆走于階陛。左豁坪陸,目極遠(yuǎn)山。前流長河,波映重閣。”
可以想象:在一道灰色的懸崖絕壁上,蜿蜒曲折的木棧閣道,披上金碧輝煌、眩目美麗的彩繪,在綠樹的濃蔭中時隱時現(xiàn)。石窟的腳下流過“大泉”,水波中閃耀不定地映出石窟的倒影,空中回蕩著鐘鼓鈴鐸的聲音,成群結(jié)隊(duì)的善男信女,打扮得很美麗,他們的手里拿著香爐、花束或樂器,嘴里念誦佛號,穿行曲廊,巡回禮拜,從一個洞窟到另一個洞窟。洞窟里香煙繚繞,有的佛座前面,點(diǎn)著整夜不熄的油燈,透過繡繪精絕的帷幔,映照著佛像慈悲而智慧的面容,也映照著天王神將莊嚴(yán)勇猛的法相。四壁大幅的《經(jīng)變圖》和窟頂藻井彩繪五彩繽紛,在黑暗的洞窟中顯示了無限的宗教神秘性。①我們仿佛感受到那漸入佛國人間的佳境,感受到壁畫中的隋唐時代。
隋代是只有38年的短暫王朝(公元581-618年),但卻在莫高窟開鑿了大量石窟,至今仍遺留著95個窟。隋代壁畫從內(nèi)容上看并沒有什么新的東西,但在表現(xiàn)手法上卻顯露出豪放和清新的視覺沖擊力,這種磅礴的氣勢即使在鼎盛時期的唐代壁畫中也沒有過。它來自于二百七十多年分裂后的統(tǒng)一,來自于百姓精神極度痛苦后的爆發(fā)。
在305窟中的《東王公和西王母》②壁畫中,畫面表現(xiàn)出像陣風(fēng)疾馳的場景。云車在空中急速飛逝而過,隨車前的飛天與神怪也在急速中飛行,空中飛舞的花朵,還有飛天的飄帶和飛揚(yáng)的青色旗幟,都朝著同一方向起舞。畫面的青灰色和藍(lán)灰色與黃色及土黃色的對比,給人以強(qiáng)烈之中又帶輕快的感覺。這種氣勢磅礴而輕快的形式以及色彩簡潔卻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效果,明顯地不同于北魏和西魏時期的簡潔與夸張。隋代的壁畫正在脫離南北朝時期的質(zhì)樸粗獷氣息,朝著更加燦爛絢麗的方向過渡和發(fā)展。在這一過渡時期,壁畫中經(jīng)變題材也逐漸多起來了,經(jīng)變是佛經(jīng)的變相,也就是佛經(jīng)的圖像。北魏時經(jīng)變題材的壁畫很少,大多是本生故事,只有比較簡單的幾種經(jīng)變形式。在295隋窟的《涅變》已不同于428魏窟的《涅變》。在魏窟的涅變畫中,釋迦入滅,側(cè)身而臥,后面行列整齊的群弟子悲慟不已,他們幾乎沒有什么動作,只有捏拳表示悲痛的樣子。畫面中的菩提樹列植作球狀,與人物一樣沒有什么變化。在隋窟的涅變中則完全打破這種呆板的格局,人物表情動作都豐富起來。悲痛的釋迦母親摩耶夫人和不忍見世尊入滅而放火自焚的須跋陀羅以及眾弟子,搖頭捶胸,人物有著劇烈的動作和表情,樹木的穿插變化和點(diǎn)綴畫面的飛天也有豐富的動感。與魏窟的涅變畫相比,更顯豪放大膽。我們從中感受到,在這大亂尚未結(jié)束而大治又未開始之際,從毀滅與絕望中掙脫出來的人們,奔放的豪情無法遏制,表現(xiàn)出的豪放和大膽不拘一格。同時,在壁畫中也表現(xiàn)出細(xì)致與清新的美好情懷。如420窟中的《群鳥聽法》③,描寫的是法華經(jīng)變二十八品其中的一品:釋迦在枝葉茂盛柳蔭下盤膝而坐,幾位菩薩和信徒隨后站立,群鳥圍座于四周聆聽佛經(jīng)。遠(yuǎn)處的水鳥成雙成對在塘中停止了游動,枝頭上的蟬兒也停止了鳴唱,荷塘的花蕾從水里露出頭來,似乎一切都在傾心聆聽之中。畫面如同暴風(fēng)雨過后的晴天,那樣清新,畫中的形象宛如荷塘水中的荷花,如此挺秀。盡管隋魏二代經(jīng)變畫的表現(xiàn)形式在手法上有著很多的不同,但都處在一個萌芽階段。經(jīng)變畫與凈土信仰,早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經(jīng)流行,在那個世亂民苦的年代里,找不到構(gòu)成極樂世界幻想的現(xiàn)實(shí)依據(jù),到了唐代則可以依照現(xiàn)實(shí)世界來描寫西方極樂世界,因此,經(jīng)變畫的主體在唐代才得到空前的發(fā)展。
入唐時,莫高窟已經(jīng)是擁有一千多個石窟的佛教圣地。唐代各種題材的凈土變壁畫不斷出現(xiàn),這一時期莫高窟的壁畫藝術(shù)達(dá)到了歷史的頂峰,無數(shù)藝術(shù)家殫精竭慮地創(chuàng)造的成果,使我們目醉心迷,顯示出這個時代不平凡的藝術(shù)高度。
莫高窟的唐代石窟遺存至今有二百余窟,其中各種題材凈土變的壁畫就有一百多壁。洞窟中四壁繪滿巨幅的阿彌陀凈土變、西方凈土變、彌勒凈土變和東方藥師凈土變等壁畫,各式各樣題材的經(jīng)變畫代替了魏隋時期的本生故事,絢麗多彩,場面恢宏。佛教的經(jīng)變很多,經(jīng)變題材的選擇和經(jīng)變畫的表現(xiàn),與當(dāng)時佛教凈土宗信仰的廣泛流行是密切相關(guān)的。凈土宗信仰深入人心,凈土變的壁畫描繪著一個沒有五濁煩惱,莊嚴(yán)皎潔的世界,正對應(yīng)著佛所居住的苦難塵世之外的西方極樂世界。
敦煌之戀民族文化元素分析
摘要:《敦煌之戀》作為中國歌劇民族化道路上的探索之作,以古代絲綢之路及絲路文化重鎮(zhèn)的敦煌為背景,在助推了“一帶一路”建設(shè)的同時,還把歌劇藝術(shù)形式帶入了大眾的視野。該劇從題材選取、演唱形式、唱腔植入、樂隊(duì)編配等諸方面立足于弘揚(yáng)中華民族文化,在歌劇舞臺中植入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音樂元素,為我國現(xiàn)代歌劇的發(fā)展進(jìn)行了富有民族文化的大膽開拓,也為中國歌劇走向世界做出了貢獻(xiàn)。
關(guān)鍵詞:敦煌之戀;民族歌劇;民族文化;音樂元素
隨著我國倡導(dǎo)的“一帶一路”建設(shè)順利推進(jìn),一部以古代絲綢之路及絲路文化為背景的歌劇進(jìn)入人們的視野。2016年11月13日,由指揮家彭家鵬擔(dān)任總策劃、指揮,作曲家劉長遠(yuǎn)作曲,歌劇學(xué)者王景彬編劇、導(dǎo)演的大型歌劇《敦煌之戀》在北京中國國家大劇院隆重上演。該劇系國家“四個一批”人才資助項(xiàng)目中國大歌劇《絲綢之路》四部曲之第一部,由中國廣播藝術(shù)團(tuán)主辦,中國廣播民族樂團(tuán)、青島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山東理工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以及敦煌之戀合唱團(tuán)共同參演。本次演出只是該劇的第一幕和第三幕,但一亮相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當(dāng)演出結(jié)束,音樂家上臺謝幕時,全場觀眾集體起立,以熱烈的掌聲向藝術(shù)家和他們的藝術(shù)精品致以崇高的敬意。2017年1月22日,《敦煌之戀》全部四幕在海南省歌舞劇院完整上演,再次引起強(qiáng)烈反響。歌劇將敦煌恢弘厚重的歷史和燦爛多彩的文化以及濃郁的西域風(fēng)情展現(xiàn)于南國,為“一帶一路”建設(shè)發(fā)揮了很好的宣傳作用。誠如有評論所言,《敦煌之戀》的上演,不僅對國內(nèi)和國際歌劇事業(yè)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也將成為中國文化的使者和名片,助力“一帶一路”建設(shè)。①《敦煌之戀》的創(chuàng)作,有意識地讓中國歌劇與世界接軌,使中國民族器樂和中國風(fēng)格歌唱藝術(shù)走向世界的。歌劇通過敦煌壁畫的繪制、絲綢之路的商貿(mào)、劇中人物的愛情等情節(jié),在描繪古代文明的輝煌和西域風(fēng)情的同時,也寄寓了人們對純真愛情的堅(jiān)貞不渝、對戰(zhàn)爭的控訴、對和平的向往,以及國家興衰與個人命運(yùn)緊密相關(guān)等多重內(nèi)涵。而從藝術(shù)的角度,《敦煌之戀》的成功,更主要在于中華民族文化和音樂元素的大量介入,為中國歌劇走向世界進(jìn)行了大膽的開拓。
一、創(chuàng)作題材的民族文化意義
《敦煌之戀》一上演就備受觀眾喜愛,首先得益于具有深厚民族文化的題材選擇。歌劇以絲綢之路為背景,以敦煌莫高窟壁畫為題材,圍繞畫師李工和粟特人蜜兒在唐朝安史之亂時期一段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用小人物展現(xiàn)大事件,不僅再現(xiàn)了唐朝時期敦煌人的普通生活,對敦煌壁畫的繪制過程、古代絲綢之路的商貿(mào)活動以及西域獨(dú)特的歌舞藝術(shù)都進(jìn)行了展示。公元8世紀(jì),大唐帝國以其強(qiáng)盛的氣象和遼闊的疆域雄踞于世界東方,自先秦便已開通的絲綢之路在唐代更是得到長足的發(fā)展,成為連接?xùn)|西方經(jīng)濟(jì)文化及各民族交往的一條繁榮的通道。而敦煌,則以其不可替代的地理位置擔(dān)負(fù)著樞紐的角色,各民族經(jīng)濟(jì)貿(mào)易與文化藝術(shù)于此交匯。舉世聞名的莫高窟,更是世界文明的一件瑰寶。《敦煌之戀》以壁畫大師與畫師供養(yǎng)者粟特人的特殊關(guān)系和生活經(jīng)歷演繹故事,對敦煌壁畫以及制作過程都做了濃墨重彩的展示,再一次向世界推出中華民族的奇珍異寶,其文化意義不言而喻。在敦煌的石窟藝術(shù)和歷史文獻(xiàn)中,有關(guān)音樂和舞蹈的資料也是一筆厚重的文化遺產(chǎn),《敦煌之戀》以歌劇的形式加以舞蹈的配合反映敦煌,在內(nèi)容與形式上找到了一個天然的切合點(diǎn),對古老民族文化的借鑒和推衍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敦煌之戀》的女主人公為粟特人。這個從祁連山西遷至中亞定居的古老民族,素以善于經(jīng)商聞名,自先秦以來便行走于絲綢之路,無愧為這條商貿(mào)通道的最初開拓者,經(jīng)歷朝歷代的發(fā)展,他們幾乎成了這條路上的商貿(mào)壟斷者。在魏晉南北朝到唐朝這段時期,大量粟特人在他們的經(jīng)商之路上定居下來,沿著絲綢之路及周邊的于闐、樓蘭、高昌、敦煌、武威、長安、洛陽等大大小小城市里,興起了一個個粟特人的移民聚落。遷往內(nèi)地的粟特人逐漸與其他民族融合,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構(gòu)成來源。盛唐時期,由于帝國的強(qiáng)大和經(jīng)貿(mào)的繁榮,粟特人以其驕人的商業(yè)成就,加大了向中原滲透的步伐,不僅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包括高層政治領(lǐng)域亦出現(xiàn)了他們的身影,甚至于左右帝國的命運(yùn),如作為《敦煌之戀》情節(jié)背景的安史之亂,其罪魁禍?zhǔn)装驳撋健⑹匪济鞅愣际撬谔厝撕笠帷L瞥瘯r候?qū)⑺麄兘y(tǒng)稱為“胡人”。被統(tǒng)稱為“胡人”的粟特人也將他們獨(dú)特的文化帶到了中原,在中華文化的融合過程中發(fā)揮了很大的影響。作為一個在中亞特定地域發(fā)展起來的民族,粟特人不僅長于經(jīng)商,在藝術(shù)文化領(lǐng)域如其繪畫、音樂、舞蹈也相當(dāng)發(fā)達(dá)。早在南北朝時期,來自中亞曹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一帶)的粟特人曹仲達(dá),曾任北齊朝散大夫,工于繪畫尤其擅長于人物、肖像和佛教圖像,唐張彥遠(yuǎn)《歷代名畫記》多有提及,并于卷八專列“曹仲達(dá)”條。與張彥遠(yuǎn)同時代的釋道宣則在《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中寫道:“時有北齊畫工曹仲達(dá)者,本曹國人,善于丹青,妙盡梵跡,傳摩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真范。”②可見就在唐代,粟特人便以其繪畫藝術(shù)在中原享有盛譽(yù),其擅畫佛像的專長尤其令人稱善,而這正是敦煌壁畫的重要領(lǐng)域。在音樂方面,粟特人無論器樂還是聲樂都給中原人帶來驚喜。粟特琵琶高手曹婆羅門、曹僧奴、曹明達(dá)祖孫三代相繼在西魏、北齊、隋三朝做官,均以彈奏琵琶而名聞天下。到唐朝,粟特人康昆侖彈奏琵琶時人號稱“長安第一手”,受到唐德宗召見;《新唐書.禮樂志》還有康昆侖用琵琶彈奏改編《涼州曲》的記載。聲樂上,粟特人在唐代也十分風(fēng)光。著名詩人劉禹錫的好友、粟特人米嘉榮在憲宗、穆宗、敬宗三代都擔(dān)任朝廷供奉,也就是宮廷樂官,史稱“三朝供奉”。劉禹錫在《與歌者米嘉榮》一詩中贊嘆道:“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shù)米嘉榮。”說明米嘉榮歌聲的西域色彩,能給人“意外”的感受。至于粟特人的舞蹈,不能不提到胡旋舞。胡旋舞據(jù)史書記載,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原的西域舞蹈。胡旋舞出自何處有多種說法,但諸說都不出一個范圍,即由昭武九姓所掌控的中亞粟特地區(qū)。在唐開元天寶年間,昭武九姓粟特人所建立的城邦制國家中的康國、米國、石國、史國等都多次向唐王朝進(jìn)貢跳胡旋舞的女子,因?yàn)榭祰幱谡盐渚判盏闹行?唐高宗永徽時在這里設(shè)置康居都督府,故康國進(jìn)貢的人次會多一些。白居易在其《新樂府.胡旋女》中說“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余”,此康居應(yīng)包括康居都督府所管轄的整個粟特人區(qū)域。胡旋舞一經(jīng)進(jìn)入中原,其熱烈歡快的節(jié)奏和優(yōu)美的舞姿與大唐強(qiáng)盛樂觀的氣象十分吻合,迅速受到中原人的歡迎和喜愛,一時間成為宮廷內(nèi)外熱情追捧的時尚舞蹈。唐玄宗便對胡旋舞欣賞有加,寵妃楊玉環(huán)亦投其所好,即如李白詩所言:“……臣妾人人學(xué)圜轉(zhuǎn)。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而身為粟特人后裔的胡人安祿山,則以其天生的舞蹈稟賦,將胡旋舞跳得出神入化,以此獲得玄宗的寵幸。《敦煌之戀》以安祿山發(fā)動的安史之亂為重要的情節(jié)元素,劇中亦穿插大段的胡旋舞,這既是內(nèi)容與形式的契合,也是對古老民族文化的藝術(shù)再現(xiàn)。正是由于以上所述題材選取的獨(dú)特視角,《敦煌之戀》不僅展示了舉世矚目的敦煌文化,其以絲路開拓者和建設(shè)者的粟特人為情節(jié)主人公,對于絲綢之路的歷史再現(xiàn),中華民族的多元融合,以及文化藝術(shù)的傳承流變,都具有極其深刻的符號意義。
二、演唱方式的戲曲化植入
敦煌儒家文獻(xiàn)分析論文
其一,敦煌儒家文獻(xiàn)主要是寫本,有六朝本、北朝本、隋唐本、五代宋初本,時間跨度長達(dá)五六百年,比我們現(xiàn)在所用的宋元善本為早,為儒學(xué)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文獻(xiàn)資料,具有較高的學(xué)術(shù)和歷史價(jià)值。
其二,敦煌儒家文獻(xiàn)具有濃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僅保存有學(xué)校的教材、學(xué)郎的作業(yè),還有一些明顯體現(xiàn)著敦煌地區(qū)特點(diǎn)和編撰特色的史學(xué)文獻(xiàn)。這些文獻(xiàn),對敦煌地區(qū)的歷史、教育、語言文字及社會風(fēng)俗等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目前,敦煌儒家文獻(xiàn)作為一個類別的研究,還不夠深入,缺乏整體的把握。近年來,敦煌儒家文獻(xiàn)的專題研究如儒家經(jīng)典、蒙書、書儀等有較為深入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批有價(jià)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專題研究代替不了總體研究。總體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對敦煌儒家文獻(xiàn)進(jìn)行分類,這是一項(xiàng)基礎(chǔ)性工作,是分析、把握敦煌儒家文獻(xiàn)的前提,而這項(xiàng)工作目前卻做得不如人意,屬于薄弱環(huán)節(jié)。
包括儒家文獻(xiàn)在內(nèi)的敦煌遺書,通常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①。這是按照傳統(tǒng)的四部分類法進(jìn)行的分類。四部分類法不能包括敦煌遺書中的宗教文獻(xiàn)、官私文書及胡語文獻(xiàn),這些文獻(xiàn)需要另外分類。1958年,王重民把自己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匯集成《敦煌古籍?dāng)洝芬粫?收錄經(jīng)部24種,史部25種(牒、戶籍除外),子部62種,集部33種。以現(xiàn)在的觀點(diǎn)來看,這種四部分類法,無論從數(shù)量還是種類上都需要修正和增補(bǔ)。
隨著專題研究的深入和細(xì)化,四部分類法已經(jīng)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于是,學(xué)者們開始尋找新的分類方法。張弓主編的《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6年)一書,就打破了四部分類法,將敦煌典籍分為儒學(xué)、佛典、道典、史地、文學(xué)、書儀、雜占、科技、藏文典籍等九大類。這種分類法顯然比四分法涵蓋的內(nèi)容和類別更加全面,而且還把儒學(xué)作為一大類特別單獨(dú)提出,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儒學(xué)在此書中作為一個類別,僅僅包括儒典和蒙書,又有遺漏,不夠周全。
以上兩種分類法都是針對整個敦煌遺書而言的。至于敦煌儒家文獻(xiàn),則迄今不見專門的分類研究。
敦煌儒家文獻(xiàn),數(shù)量龐大,內(nèi)容繁雜,必須進(jìn)行分門別類的梳理,以類相從,理出頭緒,以方便研究和利用。這就需要一個為其“量身制作”的分類法。制定這樣一個分類法,前提是要對敦煌儒家文獻(xiàn)有一個整體的了解和把握,認(rèn)識其性質(zhì)、特點(diǎn),然后考察每一寫本的具體情況。主要有三點(diǎn):一是認(rèn)真分析寫本的內(nèi)容、性質(zhì)和功能;二是根據(jù)寫本原有的序文,以窺知其編纂目的與動機(jī);三是依據(jù)寫本的實(shí)際流傳與抄寫情況、抄者身份等,弄清其作者、時代、內(nèi)容等等,在此基礎(chǔ)上,綜合判定每一寫本的性質(zhì)②,充分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仔細(xì)斟酌、推敲,制定出大致合理的分類原則和標(biāo)準(zhǔn),最后對敦煌儒家文獻(xiàn)作出明確而合理的分類。筆者據(jù)此把敦煌儒家文獻(xiàn)分為四大類,即:經(jīng)典類、歷史類、蒙訓(xùn)類、雜著類。這個分類是粗略的,未必完全適當(dāng),僅僅是筆者的一個嘗試。相信今后隨著對敦煌儒家文獻(xiàn)研究的不斷深入,一定還會總結(jié)出更為科學(xué)和嚴(yán)謹(jǐn)?shù)姆诸惙椒ā?/p>
敦煌壁畫藝術(shù)在服飾設(shè)計(jì)中的運(yùn)用
摘要:以敦煌壁畫為靈感來源,分析不同時期壁畫中的藻井紋樣及其色彩特點(diǎn),結(jié)合當(dāng)下服裝市場的流行趨勢,以藻井紋樣在現(xiàn)代服裝設(shè)計(jì)、絲巾設(shè)計(jì)、團(tuán)扇及胸針設(shè)計(jì)中的應(yīng)用為例,研究品牌服飾設(shè)計(jì)中敦煌元素的運(yùn)用及其表現(xiàn)方法,以壁畫顏色、紋樣圖案的應(yīng)用為研究方向,為現(xiàn)代服飾設(shè)計(jì)中傳統(tǒng)文化內(nèi)涵的表現(xiàn)提供框架結(jié)構(gòu)和展示空間。
關(guān)鍵詞:敦煌壁畫;藻井紋樣;服裝設(shè)計(jì)
中國有著幾千年的文明史,敦煌藝術(shù)是我國人民集體創(chuàng)作智慧的結(jié)晶,壁畫是敦煌石窟藝術(shù)的主要組成部分,在藝術(shù)和色彩表現(xiàn)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特有的風(fēng)格為當(dāng)代設(shè)計(jì)藝術(shù)提供了創(chuàng)作靈感。隨著人們精神追求的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品位越來越偏向于藝術(shù)審美,服裝作為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流行趨勢也逐漸開始融入中國傳統(tǒng)元素。
一、敦煌壁畫概述及特點(diǎn)
(一)敦煌壁畫概述。敦煌壁畫作為敦煌藝術(shù)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其內(nèi)容豐富多彩,描寫的是神的形象活動,以及神與神的關(guān)系、神與人的關(guān)系,用來寄托人們善良美好的愿望,是安撫人類心靈的一門藝術(shù)。[1]敦煌壁畫在我國壁畫中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作為文化的傳播載體,通過壁畫的形式把當(dāng)時的經(jīng)濟(jì)、文化完美地呈現(xiàn)出來。敦煌壁畫是莫高窟藝術(shù)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壁畫作品數(shù)量豐富,據(jù)統(tǒng)計(jì)在五百多個洞窟內(nèi)共有四萬五千平方米壁畫作品,規(guī)模非常大,令人驚嘆。(二)敦煌壁畫的造型特點(diǎn)。敦煌壁畫的造型元素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俗人,人物著裝以中原漢裝為主,其形象富有生活氣息,時代特征也很明顯,人物表現(xiàn)技法采用暈染法;另一類是神靈,其著裝大多保持異國衣冠,造型夸張想象居多,但是變化不多,在表現(xiàn)技法上一般是西域的凹凸法。敦煌壁畫的造型表現(xiàn)一般是在傳統(tǒng)繪畫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變形,巧妙地勾勒出各式各樣的人物造型以及動植物造型。變形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以人物原型進(jìn)行合乎規(guī)律的夸張變形;另一種是經(jīng)過變形徹成風(fēng)流瀟灑的“秀骨治像”,以隋唐時期為分界點(diǎn),早期的形象特征鮮明,變形幅度大,隋唐之后則突出立體感,偏寫實(shí),變形少。(三)敦煌壁畫的色彩表現(xiàn)。敦煌壁畫歷經(jīng)千年,在每個時期顏色表現(xiàn)都有所不同,雖然數(shù)量不多,但卻給人一種獨(dú)特而又別樣的絢麗。這些色彩語言有特殊的感染力,在視覺感官上呈現(xiàn)出敦煌藝術(shù)最感性的因素。[2]敦煌壁畫的初期作品產(chǎn)于北魏,在人物表現(xiàn)上使用龜茲風(fēng)的渲染手法,先用紅土起稿再用黑線描,畫面風(fēng)格類似于西方的繪畫,畫面壯美。北周時期,在繪畫方法上有了一些突破,開始在留白域繪畫,這種繪畫方式既美觀了色彩又突出了畫面。隋唐時期的壁畫仍有不少創(chuàng)新,色調(diào)以紅色、青色、綠色為主,上色方法大多采用平涂法,畫面風(fēng)格富麗高雅。在唐朝,壁畫的顏色不再單一,開始使用復(fù)合色,這個時期開始注重顏色與線條的結(jié)合表現(xiàn)。[3]盛唐是敦煌壁畫創(chuàng)作的成熟期亦是巔峰時期,顏色更為豐富,使用間色表達(dá);內(nèi)容題材上既符合邏輯又不失想象力。例如,人物的著裝顏色改掉以往的厚重而偏向素雅,技法表現(xiàn)上線條清晰而又灑脫,畫面風(fēng)格豐富、典雅、莊重。敦煌壁畫在創(chuàng)作晚期結(jié)合了中原文化,色彩溫和,色調(diào)上開始采用暖色,作畫風(fēng)格上開始融入西域元素和中土元素,形式表現(xiàn)上不再突出色彩而開始著重內(nèi)容的表現(xiàn)。(四)敦煌壁畫中的藻井紋樣。藻井紋樣是敦煌圖案中的精華部分,位于石窟上端,無論是人為因素還是自然因素,都很難受到客觀條件的影響,保存還是比較完整的。每個時期藻井紋樣也會跟著時代的變遷而有各自的特點(diǎn)。首先是北魏,早期的藻井紋樣少了一些繁瑣而多了一些樸實(shí),花紋顏色主要以土紅色、深赭石色、白色、土黃色為主,圖案結(jié)構(gòu)是斗四套疊,圖案元素有幾個代表性的如幾何紋、蓮花紋、飛天紋、水渦紋、火焰紋、忍冬紋。[4]中心圖案一般是圓形的蓮花紋,外層填充水渦紋,四周的角花一般是飛天紋、火焰紋居多,或者是忍冬紋與幾何紋組合而成的邊飾。隋代的藻井紋樣開始運(yùn)用對比色,大面積石青和少面積曙紅的對比讓畫面看起來更加鮮明;紋樣結(jié)構(gòu)上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早期的斗四套疊變成了由方井、邊飾、垂幔組合的三層結(jié)構(gòu),紋樣元素豐富多彩,造型活潑,線條流暢,畫面清新典雅。唐代的藻井紋樣題材豐富,藻井中心的圖案以葡萄藤紋、寶相花、三兔和飛天為主,[5]與隋代相比無論是線條、顏色還是技法表現(xiàn)都更加生動豐富。顏色處理上出現(xiàn)了由深色到中間色再到淺色的暈染處理。在構(gòu)圖上有了新突破,唐代畫家在處理畫面時以重點(diǎn)表現(xiàn)井心圖案為主,以井邊裝飾為輔,這樣既體現(xiàn)了圖案的層次感也體現(xiàn)了畫面的節(jié)奏感。敦煌晚期的藻井圖案在結(jié)構(gòu)上延續(xù)了之前的藻井紋樣,例如在西夏的藻井中出現(xiàn)了各種造型的龍紋裝飾,裝飾表現(xiàn)手法(繪、貼金、塑)別具風(fēng)格。五代時期藻井紋樣的特點(diǎn)是以花卉與龍、花卉與鳳的組合為特色。宋朝時的藻井紋樣大多采用團(tuán)花紋與幾何紋的組合,畫面整體略顯單調(diào)。
二、敦煌壁畫在現(xiàn)代服飾設(shè)計(jì)上的運(yùn)用
敦煌藝術(shù)中的彩塑說課論文
一、教材分析
本課的內(nèi)容、地位、作用
本課是知識傳授與欣賞融為一體的綜合課,主要是對敦煌藝術(shù)中的彩塑作較為系統(tǒng)的介紹。使學(xué)生在對敦煌大背景的了解下,重點(diǎn)突出彩塑藝術(shù)的知識。本顆將以彩塑圖片和學(xué)生的分析回答為主線,教書的引導(dǎo)講解為輔,使學(xué)生在感受美的同時了解到敦煌彩塑的發(fā)展及其獨(dú)特的地位。
2、教學(xué)目標(biāo)
根據(jù)《美術(shù)教學(xué)大綱》和教材的要求,本著是提高學(xué)生藝術(shù)感知能力和審美辨別能力,使學(xué)生了解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思路,確定本課的教學(xué)目標(biāo)為:
了解敦煌彩塑在中國雕塑史和佛教造像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掌握其發(fā)展的歷程。
小議敦煌俗賦文學(xué)史含義
一百年前,敦煌藏經(jīng)洞出土了數(shù)以萬計(jì)的中古時代的寫卷,其中有數(shù)量不少的以“賦”為名的作品和雖不以“賦”名篇但其實(shí)是賦體的作品。這些賦作敘述故事,語言通俗,節(jié)奏鏗鏘,押大體相近的韻,風(fēng)格詼諧,與傳統(tǒng)文人賦迥然不同。它的面世,立即引起了學(xué)術(shù)界的關(guān)注。鄭振鐸、容肇祖、傅蕓子先生分別把這類作品叫“小品賦”、“白話賦”、“民間賦”[1]。程毅中先生寫于1961年的《關(guān)于變文的幾點(diǎn)探索》[2],首次明確提出了“俗賦”這一概念。他說:“敦煌寫卷中,除了變文之外,還有一部分是敘事體的俗賦。”1963年出版的游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xué)史》中,有《俗賦》專節(jié),從此,“俗賦”之名作為中國文學(xué)史研究的一個文體概念,正式確立并很快得到學(xué)術(shù)界的認(rèn)可。
在敦煌俗賦問世的相當(dāng)長一段時間,學(xué)術(shù)界并沒有把它作為獨(dú)立的文體,而是作為“變文”的一類,所以敦煌俗賦的主要作品,都收錄在《敦煌變文集》中。而且一提起“俗賦”,人們只以為是敦煌俗賦,比如馬積高先生在他的《賦史》中就說:“所謂俗賦,是指清末從敦煌石室發(fā)現(xiàn)的用接近口語的通俗語言寫的賦和賦體文。”[3]這種觀點(diǎn),至今仍為一些學(xué)者所接受。
1993年,連云港東海縣出土了西漢時期的《神烏賦》,其文體特征同敦煌俗賦完全一樣。鄭振鐸先生在《中國俗文學(xué)史》中曾評價(jià)王褒的《僮約》是西漢留下的白話賦,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韓朋賦考》一文中還推斷西漢時期民間可能已有這種敘說故事、帶有韻語以使人易聽易記的賦體。《神烏賦》的出土,給鄭先生的說法一個鐵證,也給容先生的推斷一個明確肯定的回答。它把俗賦的歷史由點(diǎn)拉成了一條線,使我們對漢魏六朝以來一些帶有故事性、詼諧性和大體押韻的作品及其文體歸屬有了明確的認(rèn)識,說明在文人大賦蔚為大國的同時,俗賦作為一股不小的暗流一直潛行于地下,偶然也沖決地表涌出涓涓清溪,呈現(xiàn)它多采多姿的風(fēng)貌。
對俗賦進(jìn)行系統(tǒng)地清理和研究,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shí)際意義:1、可以充分證明賦這種文體本來就是從民間來的,它是民間故事、寓言、歌謠等多種技藝相融合的產(chǎn)物;2、它在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與其它各種文體有著千絲萬縷的依附、滲透和交叉關(guān)系。3、早期的賦以娛樂為目的,所以詼諧調(diào)侃是它的主要風(fēng)格特征。優(yōu)人正是利用了這種體裁,把它引入宮廷,逐漸文人化貴族化了。4、文人借用俗賦的形式把它逐漸貴族化的同時,民間俗賦仍然發(fā)展著,并且影響著文人賦的發(fā)表,從而形成了賦的“雅”“俗”兩條線索。由于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始終都是“士”的中心任務(wù),由于“士”人整體上對“俗賦”的排斥,因此“俗賦”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著于其它文體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5、俗賦給后世的其它通俗文體以具大的影響,如戲劇、南朝以來形成的講經(jīng)文、變文、唐宋話本等。
敦煌俗賦的文學(xué)史意義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擬從敦煌俗賦入手,并參照其它俗賦的情況,推論秦漢雜賦的有關(guān)情況。當(dāng)然從子孫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實(shí)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孫身上帶有祖宗的遺傳因子,從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應(yīng)該是沒有問題的。劉勰所謂“振葉尋根,觀瀾索源”,大概也有這個意思吧!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將賦分為屈原賦、陸賈賦、荀卿賦、雜賦四類。前三家按時間先后分列賦家姓名和作品數(shù)目,雜賦類以作品題材及數(shù)目為序,無作者姓名。關(guān)于前三類的分類標(biāo)準(zhǔn)和義例,章學(xué)誠、劉師培、章太炎等先生有精辟的論述[4]。而雜賦一類,雖著錄12家233篇賦作,但竟沒有一篇保存下來,故學(xué)者或推測為“后世之總集”,或以為三種之外而無法歸類者,悉入雜賦。顧實(shí)《漢書藝文志講疏》云:“此雜賦盡亡,不可征,蓋多雜詼諧,如《莊子》寓言之類者歟?”[5]現(xiàn)在我順著顧先生的意思,以敦煌俗賦和其它俗賦作為參照物,從若干蛛絲馬跡入手作些探測。
唐五代敦煌文化研究論文
[摘要]對于唐五代民間社邑的性質(zhì)及功能,以往學(xué)界的研究都集中在喪葬互助、追兇逐吉等實(shí)用性方面,研究所據(jù)之文書都是以英藏、法藏和國內(nèi)所藏之敦煌文書為主,還未涉及到俄羅斯收藏的敦煌社邑文書。在俄藏敦煌ⅡX11038號文書中,有民間社邑的社條、入社狀、社司判等三件社邑文書。它不僅反映了社邑是一種契約性組織,而且還較突出地表現(xiàn)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其教化的指導(dǎo)思想是封建的綱常禮教,強(qiáng)調(diào)的是尊卑之禮,以禮為先,而后才追兇逐吉、喪葬互助。
[關(guān)鍵詞]俄藏;敦煌;社邑;教化;尊卑之禮
俄藏敦煌且Ⅱ11038號文書的圖版刊于《俄藏敦煌文獻(xiàn)》,這件文書是19世紀(jì)初俄國探險(xiǎn)隊(duì)從我國敦煌劫去的古代文獻(xiàn)之一,一直未公布,與世隔絕已有百年,在國內(nèi)學(xué)界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艱辛的努力下,近年終于以影印的方式兩國聯(lián)合出版了17巨冊的《俄藏敦煌文獻(xiàn)》。此件文書的圖版是一個冊頁本,有七件文書,涉及遺書、放妻書、放家僮書、入社狀、還有社邑組織和活動的規(guī)約,即社條。它反映了古代社會經(jīng)濟(jì)生活的諸多方面,具有寶貴的歷史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文學(xué)、社會學(xué)等方面的史料價(jià)值。尤其是其中的三件社邑文書,有社官對違犯規(guī)定的社人進(jìn)行的處罰,有吉兇往來、婚喪儀禮的約定,也有地方名族的禮教、倫理道德的規(guī)范,突出地反映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作用,其教化的指導(dǎo)思想是封建的綱常禮教。
一、對俄藏三件社邑文書內(nèi)容的分析
社邑(社)是一種民間結(jié)社,屬于中國古代民間基層社會組織。民間結(jié)社在先秦已有,到唐五代宋初已達(dá)到興盛階段,從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幾百件該時期的社邑文書資料中可以全面看到它的發(fā)展。
有關(guān)社邑文書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20世紀(jì)30年代,日本學(xué)者那波利貞便有對唐五代社邑的研究,隨后日本學(xué)者竺沙雅章又進(jìn)行了研究。至20世紀(jì)80年代,國內(nèi)學(xué)者寧可先生發(fā)表《述“社邑”》一文,既綜合評論了前人的研究,又對社邑的源流演變發(fā)展,作了綜合性的論述。隨后寧可、郝春文整理出版《敦煌社邑文書輯校》一書,盡管沒有來得及收入俄藏社邑文書,但它仍是目前見到的全部社邑文書之集大成者,有比較準(zhǔn)確的錄文、點(diǎn)校、斷代和說明,為學(xué)者提供了一部系統(tǒng)翔實(shí)的資料,這是一個重要的成果。
敦煌文學(xué)的含義及特征
敦煌文學(xué)是指敦煌遺書中保存的文學(xué)活動、文學(xué)作品和文學(xué)思想。文學(xué)本身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敦煌文學(xué)也一樣,所以要從內(nèi)涵和外延上給它劃分一個明晰的界限,是比較困難的。本文所說的敦煌文學(xué)作品,主要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指的是敦煌遺書中僅存的文學(xué)作品;第二層次既包括敦煌遺書中僅存的文學(xué)作品,也包括敦煌遺書中保存且見于傳世文獻(xiàn)中的文學(xué)作品;第三層次則指敦煌遺書中具有文學(xué)性的文獻(xiàn),包括上面一二層所說的文學(xué)作品,還包括一些有文學(xué)性的應(yīng)用性文章,如世俗應(yīng)用文和宗教應(yīng)用文等。而敦煌的文學(xué)思想,主要指敦煌遺書對有關(guān)文學(xué)的看法和論述以及從敦煌文學(xué)作品中發(fā)掘出來的文學(xué)觀念。
敦煌文學(xu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國古代文學(xué)的一個分支,而具有相對獨(dú)立性。“安史之亂”后,唐王朝由盛而衰,敦煌及整個河西地區(qū)被吐蕃人占領(lǐng),與中原王朝基本上處于文化隔絕狀態(tài)。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張議潮率眾推翻了吐蕃的統(tǒng)治,收復(fù)了瓜、沙諸州,建立了以敦煌為中心,長達(dá)180多年的歸義軍政權(quán)。歸義軍政權(quán)一開始雖則得到中原王朝的認(rèn)可,但由于種種原因,中原王朝的政令并未真正影響敦煌地區(qū),敦煌地區(qū)基本上處于自治狀態(tài)。在這個獨(dú)立的文化圈內(nèi),由于受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敦煌文化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漢文化圈的組成部分,敦煌文學(xué)有自己鮮明的個性。
研究中國古代文學(xué),文學(xué)的自覺是一個免不了的問題。中國文學(xué)自覺的時代,除了比較通行的“魏晉說”外,還有“先秦說”、“漢代說”和“六朝說”等。各家都能擺出很多文學(xué)史實(shí),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我們認(rèn)為,文學(xué)自覺是一個復(fù)雜的問題,不同的文學(xué)體裁自覺的時代并不相同,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學(xué)創(chuàng)造者和接受者對文學(xué)的自覺也不相同;對于中國最下層的老百姓來說,他們對文學(xué)的自覺更是一個慢長而懵懂的過程。研究敦煌文學(xué),應(yīng)當(dāng)清楚這么一種情況:對唐五代敦煌民眾來說,他們對文學(xué)并不是像一般文人那樣的自覺;對他們來說,文學(xué)僅是某種社會文化活動的一種形式,或者說,是某種社會文化儀式的組成部分。正是從這種認(rèn)識出發(fā),我們認(rèn)為,敦煌民眾心目中的文學(xué),和文人心目中的文學(xué)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敦煌遺書中保存且見于傳世文獻(xiàn)的文學(xué),像《詩經(jīng)》、《文選》、《玉臺新詠》及部分唐代詩人的作品,以及獨(dú)賴敦煌遺書保存下來的一部分文人作品,如韋莊的《秦婦吟》等,這是文人心目中最正宗的文學(xué),但它們是不是敦煌民眾心目中的文學(xué),還要做具體分析。因?yàn)槎鼗兔癖娦闹械奈膶W(xué)是某種社會文化儀式的一部分,敦煌民眾并不把文學(xué)作為案頭欣賞的東西看待。所以,這些中原文人的作品只能是敦煌文學(xué)的哺育者,是敦煌民眾學(xué)習(xí)文學(xué)、創(chuàng)造文學(xué)的樣板,其本身并不是他們心中的文學(xué)。然而,這當(dāng)中還有一種情況要區(qū)分。從中原傳來的文人文學(xué),當(dāng)敦煌人把它們運(yùn)用到自己生活的各種儀式中的時候,敦煌民眾已賦予他們另一種涵義,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已經(jīng)變成敦煌文學(xué)了。敦煌文學(xué)寫卷中有諸多民間歌賦和文人作品混淆雜抄在一起,其原因也在于此。因此,敦煌文學(xué)最典型的特點(diǎn)是:以口耳相傳為其主要傳播方式,以集體移時創(chuàng)作為其創(chuàng)作的特征,以儀式講誦為其主要生存形態(tài),而在我們看來隨意性很大的“雜選”的抄本也比較集中地體現(xiàn)著這種儀式文學(xué)的意義。文學(xué)的口耳相傳主要通過各種儀式進(jìn)行。儀式是人類社會生活高度集中的體現(xiàn)形式。人類在長期的生產(chǎn)和勞動中,創(chuàng)造了各種各樣的儀式。這些高度凝煉的禮儀,是人類告別野蠻而進(jìn)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biāo)志。所以,儀式是文化的貯存器,是文化(文學(xué))產(chǎn)生的模式,也是文化(文學(xué))存在的模式。從文學(xué)角度看,儀式的一次展演過程就是一個“文學(xué)事件”。敦煌民間儀式,大致可分為世俗儀式和宗教儀式。世俗儀式主要包括人生里程儀式,如冠禮、婚禮、喪禮等;歲時禮俗儀式,如辭舊迎新的驅(qū)儺儀式、元日敬親儀式、三月三日禊潔儀式、七月七日乞巧儀式、九月九日登高避邪御寒儀式、臘祭儀式;還包括其他儀式,如各種祭祖儀式、求神乞福儀式、民間娛樂儀式等。民間宗教儀式主要指世俗化的佛教儀式,如俗講儀式、轉(zhuǎn)變儀式、化緣儀式等。在這些儀式中,唱誦是必不可少的內(nèi)容,唱誦的內(nèi)容,除了少量的佛經(jīng)、道經(jīng)外,大都是民間歌訣。正是從這一認(rèn)識出發(fā),我們對敦煌文學(xué)作了如下分類。
一、敦煌寫卷中的經(jīng)典文學(xué)和文人創(chuàng)作的典雅文學(xué)
敦煌寫卷中的經(jīng)典文學(xué)主要指唐前文學(xué),像《詩經(jīng)》、《文選》、《玉臺新詠》、諸子散文和史傳散文以及文學(xué)批評著作《文心雕龍》等。敦煌出土的《詩經(jīng)》有30個卷號。這些寫卷,皆為毛詩本,大多數(shù)為故訓(xùn)傳,也有白文傳、孔氏正義、詩音。抄寫的時間,在六朝至唐代。綜合序次,《詩》之《風(fēng)》、《雅》、《頌》,經(jīng)、序、傳、箋、詩音、正義,皆可窺其一斑。抄寫的詩篇達(dá)218首。以之對校今本,其勝義甚多。或能發(fā)古義之沉潛,或能正今本之訛脫,片玉零珠,彌足珍貴。同時,我們還可以由此研究六朝以來《詩》學(xué)的大概情況,并考究六朝以來儒家經(jīng)典的原有形式[1]。敦煌遺書中的《文選》寫卷現(xiàn)在所能看到的有29種,包括白文無注本、李善注本、佚名注本、音注本等。寫本涉及的作品有賦7篇,文85篇(包括48首《演連珠》),詩18首。雖然與《文選》收錄513篇的總數(shù)相比,僅占百分之二十過一點(diǎn),但有很高的文獻(xiàn)學(xué)價(jià)值。從抄寫時間看,有陳隋間寫本,有唐太宗到武則天時期的寫本,白文無注本可反映蕭統(tǒng)三十卷本的原貌;李善注本的抄寫時間距李善《文選注》成書不久,最能反映李善注的本來面目;佚名注本大部分為李善注之前的《文選注》,在《文選》的研究史上,彌足珍貴。敦煌本《玉臺新詠》雖只有一個寫卷(P.2503),保存了張華、潘岳等的10首詩。但作為唐人寫本,比今傳《玉臺新詠》的最早刻本要早數(shù)百年,其文獻(xiàn)價(jià)值也是很珍貴的。
《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文學(xué)批評史上空前絕后的偉大著作。S.5478《文心雕龍》寫本是敦煌抄本中為數(shù)不多的蝴蝶裝殘卷,共22頁,44面,起《原道篇》贊“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效”,訖“諧隱第十五”篇題,抄寫者為唐玄宗以后之人,用章草書寫,筆勢遒勁。著名學(xué)者趙萬里、楊明照、鈴木虎雄、饒宗頤、潘重規(guī)、郭晉稀等先生都曾對唐寫本進(jìn)行過研究。日本學(xué)者戶田浩曉在《作為校勘資料的文心雕龍敦煌本》一文中說:“敦煌殘卷有六善:一曰可糾形似之訛,二曰可改音近之誤,三曰可正語序之倒錯,四曰可補(bǔ)脫文,五曰可去衍文,六曰可訂正記事內(nèi)容。”[2]這些經(jīng)典文學(xué),被敦煌人民傳閱珍藏了數(shù)百年,其養(yǎng)育敦煌本土文學(xué)之功不可磨滅。文人創(chuàng)作的典雅文學(xué)主要指保存在敦煌遺書中的唐代文人的創(chuàng)作。敦煌遺書中保存了數(shù)量甚夥的唐人詩文[3]。《全唐文補(bǔ)遺》第九輯(三秦出版社,2007年)收錄的敦煌文近600篇,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收錄的唐人詩包括殘句合計(jì)為1925首(不包括王梵志詩、應(yīng)用性的民間歌訣、曲子詞及民間俗曲、作為散文之一部分的詩歌、詩體宗教經(jīng)典以及宗教經(jīng)典中的詩歌作品、宗教贊頌作品)、張錫厚主編的《全敦煌詩》收錄敦煌出土的俗詩、歌訣、曲子詞、詩偈、頌贊等4501首。這些作品集中有相當(dāng)多的是文人創(chuàng)作的典雅作品,它們是哺育敦煌文學(xué)的源泉之一。敦煌遺書的散文類作品大部分為傳世文獻(xiàn)所不載,而與民間儀式、宗教儀式相關(guān)的應(yīng)用文居多,不屬于我們所說的典雅文學(xué)。敦煌遺書中的文人典雅詩歌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見于《全唐詩》及其他著作的傳世詩歌,一類是歷代不見記載而獨(dú)賴敦煌遺書保存的佚詩。前一類詩,如劉希夷詩、李白詩、王昌齡詩、孟浩然詩、白居易詩等,敦煌本具有校勘和考訂的重要意義。黃永武先生著有《敦煌的唐詩》和《敦煌的唐詩續(xù)編》,集中討論今存詩篇的文學(xué)文獻(xiàn)價(jià)值。其文獻(xiàn)考證與辭章辨析相結(jié)合的研究方法,充分展示了敦煌詩歌的文獻(xiàn)價(jià)值和文學(xué)藝術(shù)價(jià)值。后一類詩則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文學(xué)資料,對我們?nèi)媪私馓圃姷姆睒s盛況,具有重大的學(xué)術(shù)意義。比如晚唐詩人韋莊的《秦婦吟》238句,是現(xiàn)存唐詩中最長的敘事詩。它以恢宏的結(jié)構(gòu),滿腔的激情,借秦婦之口,生動地描寫了黃巢起義軍攻克長安后的情形,以及給唐王朝的沉重打擊。這首散佚千年的著名詩篇,借敦煌石室而得以重見天日,真是文學(xué)史上的大幸事。
相關(guān)文章
2創(chuàng)意思維在敦煌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設(shè)計(jì)的運(yùn)用
相關(guān)期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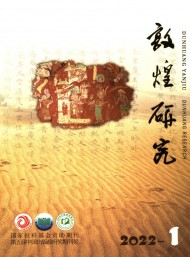
敦煌研究
主管:甘肅省文化和旅游廳
級別:CSSCI南大期刊
影響因子:0.26
-

敦煌吐魯番研究
主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xué)會;首都師范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香港大學(xué)饒宗頤學(xué)術(shù)館;北京大學(xué)東方學(xué)研究院
級別:部級期刊
影響因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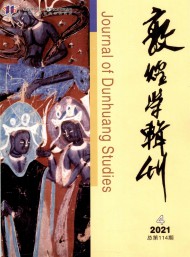
敦煌學(xué)輯刊
主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級別:CSSCI南大期刊
影響因子:0.18
-

敦煌學(xué)國際聯(lián)絡(luò)委員會通...
主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xué)會;首都師范大學(xué)古文獻(xiàn)研究中心;敦煌學(xué)國際聯(lián)絡(luò)委員會
級別:部級期刊
影響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