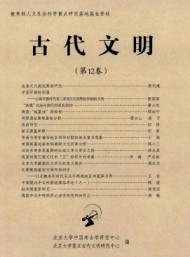古代美學思想范文10篇
時間:2024-02-02 17:08:41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為你推薦的十篇古代美學思想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古代美學思想研究論文
【內(nèi)容提要】
中國古代關于美本質(zhì)的普遍看法不是單一的,而是復合的互補系統(tǒng),以味為美、以意為美、以道為美、同構為美、以文為美,構成了中國古代美本質(zhì)觀的整體特色。中國古代的美本質(zhì)觀本同而末異,如儒家認為自然比德為美、以情為美、以和為美、以“合目的”的形式為美,道家以無、妙、淡、柔、自然、生氣和適性為美,佛家以涅槃、寂滅、死亡以及涅槃的象征——圓相、光明為美,便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美論的多樣性。中國古代的美感論集中論述了審美的特征和方法。審美特征論涉及美感的愉悅性、直覺性、客觀性、主觀性、真實性。審美方法論強調(diào)咀嚼回味、以我觀物、虛靜納物,與中國古代的美本質(zhì)論遙相呼應。
本文試圖對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系統(tǒng)作出簡要而整體的把握。在我看來,審美感知是由審美對象引起的,而普遍引起審美感知滿足、完善、愉快的對象,就是美①。美學不僅應當研究感覺規(guī)律,還應研究感覺對象的規(guī)律。易言之,美學不僅應當成為美感學、主體審美學,還應當成為美的本質(zhì)學、客體審美對象學。因此,本文闡釋中國古代美學思想,將把焦點聚集在中國古代關于美本質(zhì)和美感的理論上。
中國古代普遍的美本質(zhì)觀
中國古代對美的看法,既有異,又有同。所謂“同”,即儒、道、佛各家相通相近、殊途同歸、末異本同之處,或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中頗為流行、占主導地位的觀點。中國古代對美的普遍看法大抵有如下數(shù)端:
一、以“味”為美。這是中國古代關于美本質(zhì)的不帶價值傾向的客觀認識,可視為對美本質(zhì)本然狀態(tài)的哲學界定。從東漢許慎將“美”釋為一種“甘”味,到清代段玉裁說的“五味之美皆曰甘”,文字學家們普遍將美界定為一種悅口的滋味。古代文字學家對“美”的詮釋,反映了中國古代對“美”是“甘”味的普遍認識。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聽到優(yōu)美的《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老子本來鄙棄欲望和感覺,但他又以“為腹不為目”為“圣人”的生活準則,并把自己認可的“大美”——“道”叫做“無味”之“味”,且以之為“至味”。佛家也有“至味無味”的思想。以“味”為美,構成了與西方把美僅限制在視聽覺愉快范圍內(nèi)的美本質(zhì)觀的最根本的差異。
古代美學思想研究論文
一、服飾藝術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古人認為“天”是外在的意志、理想、福地的化身和所在,“天”被視為神圣的、偉大的、無限的,人間事物由天所定。古代服飾的形制和色彩分別體現(xiàn)了人對天的尊崇,乾為天,未明時為玄色(黑色),坤為地,為黃色,故上衣玄下裳黃。古代服飾中尤其重冠,冠上為天,冠的形制更要體現(xiàn)對天的崇拜。天子之冠有十二旒,每旒貫以玉珠十二顆,“十二”這個數(shù)字體現(xiàn)了人們對一年十二個月的天文觀,由“十二”的觀念引伸到宇宙萬物,概括出十二紋飾分別代表不同的意義。
“天人合一”還體現(xiàn)在服飾以寬大、飄逸、含蓄為美。由“天”之神圣、偉大、無限所推演出來的“大”于是也成了一種美的境界。中國古代服裝一直以寬袍大袖為尚,把自然的人體隱藏于寬大的袍袖之中,給人以神秘、內(nèi)斂之美,力求與“天”合而為一的神韻。衣袖裙裳要寬大,如人兩手舞動,則兩寬大袖片隨之飄動,形成氣勢。人行走時,上體衣袖下體裙裳隨之飄動,同樣形成寬大之勢,帝王豪紳尤以衣袍寬大為美。基于此種審美觀,中國古代服飾不追求立體感,而追求平面的“面”感。在裁剪方法上不需做過多的分割組合去追求“體”的感覺。所以,中國服飾的傳統(tǒng)裁剪法為平面裁剪法,不同于西方流行的立體裁剪法。
二、服飾藝術追求禮制秩序美
中國倫理道德對中國審美文化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在中國數(shù)千年的服飾藝術發(fā)展中,儒家的禮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從了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服飾才為美,只有充分體現(xiàn)了社會各個階層等級秩序的服飾才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響了中國后世幾千年,冠服是服裝根據(jù)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類服裝的總稱。什么樣的帽子配什么樣的衣服,都有嚴格細致的規(guī)定。在不同的禮儀場合,不同等級的人必須穿著與其身份相適應的服飾,這些服飾在顏色、材質(zhì)、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規(guī)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規(guī)定極嚴,同為裘服,也要根據(jù)皮質(zhì)、顏色來劃分等級。天子穿白狐裘,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黃狐裘,庶民則穿犬羊裘。自周以后,冠服形制被歷代傳承相襲,雖按各代統(tǒng)治者之意略有改動,但其基本形制卻大同小異,尤其是顯示階級差別的內(nèi)涵始終沒有改變。
三、服飾藝術以華貴、精細、豐富為美
宗白華美學研究論文
一
日本著名美學家今道友信曾說:“所謂方法就是邏輯程序的體系,沒有它就不會有對學問的探討。”[2]在美學研究方面,宗白華是十分重視方法的運用,他雖然沒有很系統(tǒng)地闡述自己關于美學研究方法的理論,但在《漫談中國美學史研究》《關于美學研究的幾點意見》《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等文章中都談到了美學研究的方法問題,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國美學。
在美學研究界,宗白華既是比較方法的實踐者,又是比較方法的倡導者。他多次提出要在比較中總結中國美學的特色、規(guī)律,發(fā)現(xiàn)其與西方美學的不同之處。在1961年的一個戲曲座談會上,宗白華提出:“美學研究應該結合藝術進行,對各種藝術現(xiàn)象,應作比較研究。”[3]二十幾年后,宗白華在《<美學向?qū)?gt;寄語》中再次指出:“研究中國美學不能只談詩文,要把眼光放寬些,放遠些,注意到音樂、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們是否有共同的趨向、特點,從中總結出中國自己民族藝術的共同規(guī)律來。”[4]可見,對各種藝術現(xiàn)象作比較研究,是宗白華一貫的主張。
宗白華的這一觀點,是基于對中國各藝術門類、中國藝術發(fā)展史的特點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礎之上。在《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宗白華談到了中國美學史的特點。在宗白華看來,中國的繪畫、戲劇、音樂、書法、建筑等藝術門類之間存在著水乳交融的天然聯(lián)系,又有著各自的獨特性,中國美學史、藝術史就是一部各藝術門類相互影響交流的互動發(fā)展史。
同時,宗白華的美學研究方法論體現(xiàn)出一種跨學科的文化研究意識。他指出,藝術與哲學、技術等也存在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對中國美學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藝術領域之中,要與哲學、技術等聯(lián)系起來,結合哲學、文學等批評著作進行比較研究,這樣,既可清晰地認識到它們各自的特性,又能發(fā)現(xiàn)它們相同或相通之處,這對把握中國藝術特性和發(fā)展規(guī)律無
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平面設計中的美學應用
摘要:本文首先解釋了平面設計與美學的含義,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和平面設計的四大基本原則。接著介紹了平面設計的三大元素,對每個元素的特點、分類以及重要性和意義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最后從平面設計的藝術性和實用性兩大方面著手,講解了古代的美學觀念對現(xiàn)代設計的影響,并且提出了實用性是設計最終目的的觀點,全面介紹了平面設計中美學運用的理念和原則。
關鍵詞:平面設計;美學;實用性
當前平面設計已經(jīng)成為一種穩(wěn)定的職業(yè)崗位。隨著商品時代的發(fā)展和藝術設計的大眾化,平面設計在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中已經(jīng)十分普遍,隨處可見。提高平面設計的美學性,將實用性與藝術性完美融合,是當下設計中的重中之重。只有美化平面設計,才能達到宣傳的目的和力度,而且能夠為大眾營造出藝術性的生活和消費氛圍。
一、平面設計與美學的概念
首先,平面設計就是二維空間設計,利用圖形、色彩、文字的三大元素進行設計組合,反映在平面上,體現(xiàn)出它的美學效應和實用價值。平面設計在現(xiàn)代已經(jīng)十分流行,包括pop廣告設計、報紙雜志設計、書籍封面設計、宣傳海報和宣傳單設計等類型。平面設計有四大基本特征:相關、對齊、重復、對比。相關是指將相似的元素組成一個視覺單位,使整個平面結構清晰,避免分散帶來混亂的感覺。對齊是指將各元素按照一定的秩序排列,使元素間產(chǎn)生一種視覺的聯(lián)系,形成清晰、巧妙的外觀。重復是指字體、顏色、形狀等元素在一定情況下要相同或者相似,例如字形一致或者顏色同系等。避免造成眼花繚亂的感覺。對比是為了突出某些特點或主題。其次,對于美學的概念而言,美學是哲學的范疇,也是藝術的范疇。因此,美學與哲學思辨和藝術表現(xiàn)息息相關。平面設計就是美學的運用,平面設計需要講究思想,也必須講究藝術,二者缺一不可,又相互滲透。
二、平面設計的構成要素
詩性之根
內(nèi)容提要:“和合”的文化一心理結構,是中國古代詩性智慧與審美運思的源頭活水。突出體現(xiàn)在:以天人異質(zhì)同構為基礎并由此確立二者間和諧化詩意關聯(lián)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潤了古代審美境界論,中國人由此而強調(diào)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的合一;“和合”文化中的整體直觀運思深刻影響了古代審美體驗論,視審美體驗與生命體驗為同一的中國詩性智慧特別強調(diào)物我互感互動的生命運動中的整體直觀把握;“和合”文化中和諧化辯證法的普遍運用,使得中國詩性智慧特別注意以對應性、相融性、辯證性、和諧性來理解和處理一系列審美范疇的構架和展開。“和合”文化構建了中國美學的主導精神——對“和”美的追求,形成了中國美學的和諧基調(diào)。
關鍵詞:和合文化、天人合一、詩性智慧、和諧基調(diào)
美籍華裔學者成中英先生在檢視和反省中國儒道形而上學與本體論后認為,中國式因果律首要特質(zhì)在于“一體統(tǒng)合原理”(“整合性原理”)。即:“世間萬物由于延綿不絕地從相同的根源而化生,因而統(tǒng)合成一體。換一種說法:萬物通過創(chuàng)生的過程得以統(tǒng)合。于是,在道或天的形象覆蓋下的萬物實為一體,萬物都共同分有實在的本性。此外,萬物之間莫不交互相關,因為萬物皆同出一源。……萬物所共同分有的一體(道),既維系萬物之生存,又孳生化育萬物”。①成氏進一步認為,“因為萬物間莫不交互相關,而形成各種過程間的變化網(wǎng)絡,于是運動力的傳送就被視為生命活動的表現(xiàn)”。②由此構架出“內(nèi)在的生命運動原理”(“內(nèi)在性原理”)。復次,“由于‘一體統(tǒng)合原理’之故,世間恒有和諧與平衡存在”③,形成中國因果律之“生機平衡原理”(“生機性原理”)。此因果律的三大基本層面衍生出中國式因果律模型:串連式思考(整體式觀照)和辯證法則④。成氏的上述分析實是對中國“和合”文化之特征作了精辟的理論提攝。重視萬物間的整合關系、辯證運動關系、有機性聯(lián)系正是中國“和合”文化的精髓。這些理論精髓不僅是東方文化中的瑰寶,更是中國古代詩性智慧和審美運思的源頭活水。
筆者認為,在中國“和合”文化中,以人與自然的基本相似性和人與天地萬物的視同對等或異質(zhì)同構為基礎進而在此二者間確立一種和諧化詩意關聯(lián)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漬了中國古代審美境界論,使得古代中國人特別強調(diào)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的合一。其次,“和合”文化中的整體直觀思維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審美體驗論,它使得古代中國人特別強調(diào)在內(nèi)緣已心、外參群意的審美體驗活動中獲得對生命終極意義的瞬間感悟,從而實現(xiàn)審美體驗與生命體驗的合一。再次,“和合”文化中和諧化辯證法的普遍運用,使得中國美學智慧特別注意以對應性、相融性、辯證性、和諧性來理解和處理一系列審美范疇的展開與構架。而縱觀中國古代美學基本特征(如強調(diào)真善統(tǒng)一、情理統(tǒng)一、人與自然的統(tǒng)一、有限與無限的統(tǒng)一、認知與直覺的統(tǒng)一等)和中國古代審美理想(如儒家對“和”、道家對“妙”、佛禪對“圓”的追求),無不是“和合”文化在審美層面的詩性展開和邏輯延伸。這表明,中國詩性智慧和審美意識與“和合”文化有著一種特殊的親和性和關聯(lián)性。“和合”文化,是中國古代詩性智慧之根。
一、“天人合一”思想與中國古代審美境界論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國人處理自然界和精神界關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強調(diào):人與自然間并無絕對的分歧,自然是內(nèi)在于人的存在物,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從自然規(guī)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則與自然規(guī)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調(diào)諧;人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達到一種完滿和理想的境界,是中國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標,質(zhì)言之,在古代中國人看來,自然過程、歷史過程、人生過程、思維過程在本質(zhì)上是同一的。這一思想特征貫穿了“天人合一”觀念源起與演變的基本過程。如孟子的“知性即知天”⑤論就是把人性與天道的合一放在認識論高度上加以思考的。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認為宇宙間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從一個側面確立了人與天的相互關聯(lián)。莊子提倡“與天為一”,《莊子·達生》云:“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就是要求拋棄世事,忘懷生命,使形體健全,精神飽滿,從而達到與天合為一體的自然無為境界。《周易·文言》明確提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時,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兇吉,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的順應自然的“與天地合德”的思想。漢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數(shù)”的觀念為基礎建立起天人感應的讖緯神學體系。《春秋繁露·陰陽義》即云:“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在宋學中,“天人合一”思想更趨成熟、精致、完善。張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命題;《正蒙·誠明》云:“儒者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可以成圣……”。明確指出,“誠”“明”境界的獲得,來自于天道與人性的統(tǒng)一。程頤說:“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程氏遺書》卷十八)實際上直接指出了人道與天道的同一性。程顥干脆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程氏遺書·卷六》),反對有意去區(qū)別天與人及主體與客體。至清代王夫之也強調(diào)“盡人道以合天德”。其《周易外傳》卷二云:“圣人盡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在之理;盡人道者動以順生之幾”。實際明確指出人之動與天之健是一致的。所有這些觀念無不是提倡應在自然與精神間建立一種統(tǒng)一性關系。這種強調(diào)在自然與精神間建立一種和諧化關聯(lián)的“天人合一”思想對中國古代審美境界論的影響是巨大而又深遠的。這表現(xiàn)在:在古代中國人看來,人與自然、情與景、主體與客體、心源與造化、內(nèi)根與外境都是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天?艘熘釋溝惱庵稚畈鬮幕饈妒溝彌泄糯搜в朊姥ъ溆兇拍讜詰謀咎逍怨亓紗耍松辰纈肷竺讕辰緄暮弦懷晌泄災腔圩罹哂刑厴枉攘χ凇?br>“天人合一”思想對古代審美境界論的深刻浸潤,從邏輯結構上講主要體現(xiàn)為相互關聯(lián)的兩個方面,其一:認為“天”是美的本原,美因乎自然,“造乎自然”,主體只有體天道、察天機、悟天理,深契自然之真趣,才能洞悉美的真諦。其二,認為既然美的真諦的獲得源于人對“天”(機、道、理)的洞見,則審美的最高境界和最后歸宿應當是人合于天,即主體的審美極致體驗與本源性世界的本真敞亮應獲得本質(zhì)性的同一。前者為溯源,后者為返本。在此,美的本原問題和審美的歸宿問題就邏輯地統(tǒng)一在“天人合一”觀念中。以下分論之。
傳統(tǒng)美學發(fā)展方向的審視綜述
關健詞:實踐美學生命美學傳統(tǒng)美學
摘要:從實踐美學到生命美學,既是一種超越,亦是一種回歸。這將有助于澄清當下很多理論誤區(qū),也是擺脫西方語境,發(fā)展中國美學的必然要求。實踐美學和生命美學的論爭,成為當今美學界的熱點,論爭的目的是確立中國新世紀美學的發(fā)展方向。因此,僅圍繞“實踐”等范疇作理論的論爭是不夠的,有必要重新審視中國傳統(tǒng)美學。
當代生命美學的理論體系還遠未成熟,甚至招致不少非議和誤解。另一方面,開掘中國傳統(tǒng)美學的現(xiàn)代意義已愈來愈受到美學界的關注。通過對中國傳統(tǒng)美學的審視,我們發(fā)現(xiàn)其中亦涌動著一股強烈的生命氣息。20世紀90年代,中國當代美學進人了一個新的發(fā)展時期。在實踐美學之后,生存美學、生命美學、體驗美學、超越美學等等異彩紛呈。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表現(xiàn)為對人當下生存的關注,它們的理論大致都建立在生命本體的基礎上。為此,可以將它們統(tǒng)稱為生命美學。
華夏民族宇宙意識的大旨是強調(diào)時空一體,時空變化與生生不息的生命創(chuàng)造融為一體。老子提出了“道”、“氣”、“象”“有”、“無”“虛”、“實”等等,無非是在說由“道”展開的一切生命流程。先秦諸子大都是用宇宙生命流動的哲學觀點指導著思考問題。孔子說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見,他也認為世界是自然發(fā)展的生命流程。《易·系辭》云:“夭地之大德曰生。”將事物看成生命的流程,生命通過陰陽交換的方式而展開,而人是特殊的生命,要以體現(xiàn)道的善性對待人類和萬物,從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要透過萬物之生而創(chuàng)和諧環(huán)境以利于自身的生存繁衍。這便是中國古代生命哲學的精髓,它的深層意蘊是從生命出發(fā)視一切為統(tǒng)一于道的生命流程。下面,我們再從構成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主干的儒道兩家美學思想進行分析。
儒家美學思想中審美追求和生命追求是通過“致中和”統(tǒng)一起來的。“人而不仁,如樂何?”“樂”即美的創(chuàng)造活動,審美活動應與“仁”一致。而“仁”的目的在和諧,即順天道以陰陽和合的動態(tài)發(fā)展。只有和諧才有利于從事農(nóng)業(yè)的民族生存。儒家關心的是個人如何為族類生存繁衍作貢獻,而又在這貢獻中體現(xiàn)出個人的價值。這樣能使族類乃至宇宙萬物的生命流程得以順利展開,個人也會得到一種生命充實且能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的美感。按儒家的觀點,這種美感往往根植于人生的內(nèi)在精神世界里。在文藝創(chuàng)造和審美活動中,只要不失本心,就一定會以“致中和”為原則,這原則在《樂記》里有很好的說明,其中一句“合生氣之和”更是點睛之筆。依照“天人合一”的命題,人的藝術精神本來就是自然宇宙的生命創(chuàng)造精神,人的心靈正是宇宙和人生的交合處。因此,儒家美學不是在模仿自然,再現(xiàn)自然,而是在心靈深處發(fā)掘出美來。
至于道家的美學思想,其審美追求和生命追求是直接同一的,儒道之所以能互補,是因為兩者實際上同是生命哲學一根所生,哲學同源,美學也不會有本質(zhì)的差異。道家把生命的自由展開聯(lián)想為美,認為個體生命得以自由展開就能自然達到群體幸福。在道家看來,人并不應該像儒家那樣講“仁”,講“贊天地之化育”,自然生命的流程在正常地開展,你去干預它就是錯,任何干預只會妨礙宇宙生命的流動過程。宗白華認為中國哲學是就“生命本身”體悟“道”的節(jié)奏;燦爛的“藝”賦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給予“藝”以深度和靈魂。
傳統(tǒng)服飾美學對后世的影響透析
論文摘要:從中國傳統(tǒng)服飾美學思想的緣由、歷史發(fā)展線索以及審美趨向等方面,探討其對后世的影響.結果袁明,國人服飾審美觀念體現(xiàn)出趨同化審美、中性化審美、社會效應等三大心理特征.
論文關鍵詞:傳統(tǒng)服飾美學思想;政治倫理思想;等級觀念;趨同化心理;社會效應;民族文化特色
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一談到服飾,人們總會有一種眼前為之一亮的感覺:千姿百態(tài)的款式,姹紫嫣紅的色彩,變幻莫測的材料,出神人化的制作工藝,可以頓時將人體裝扮出各種效果來;一談到服飾美,人們又難免會陷入一種茫然的狀態(tài):穿在別人身上挺漂亮,穿在自己身上卻未必漂亮,在商場里看著不錯,回到家里那種感覺卻找不著了,曾經(jīng)作為“招牌”或“時尚”的服裝,沒過多久很快就變成了昨日黃花,難登大雅之堂.從直覺和現(xiàn)象角度看,服裝確實有誘惑人的地方,讓人愛不釋手;然而要從美學和理論的角度說出服裝美與不美,究竟美在何處,為什么會美,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者靠的是感覺,后者憑的是理性.在2000多年前,柏拉圖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早就記錄了蘇格拉底和希庇阿斯討論什么是美的問題時得出了“美是難的”的結論.感覺是稍縱即逝的,理性則喜歡刨根問底,只有在探究到服飾所蘊含的文化和美學內(nèi)涵之后,才可能有所言說,在知其然中也力求知其所以然.
對于從事服飾專業(yè)研究的人士來說,只有系統(tǒng)深入地了解服飾的歷史演變過程,搞清服裝與政治、經(jīng)濟、倫理觀念、民族文化和審美學之問所存在的微妙關系,研究服飾的深層文化結構和美學意蘊,才有可能在分析中將服飾的文化價值和美學深意挖掘出來,見常人所不能見,說常人所不能說,使服裝從一種現(xiàn)象,升華為一門學問,從悅人眼目的日常實用品,轉變成耐人尋味的文化與美學“符號”,這樣才能真正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基于上述思考,本文試圖從社會發(fā)展的角度,探求中華服飾美學思想的淵源.
1服飾美學思想的緣起
通過一些歷史考古出土的實物和史籍資料記載,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在遙遠的仰韶文化時期便開始制作麻纖維的織物服裝,告別了以獸皮樹葉遮體的原始狀態(tài),從而進入到以手工為主體的服飾文明的時期.進入階級社會之后,早期的奴隸主們?yōu)榱俗约旱慕缴琊ⅲ瑢ǚ椩趦?nèi)的一切生活要素都政治化、等級化和倫理觀念化,將服飾納入鞏固政權和統(tǒng)一思想觀念的組成部分,并以“禮”和“法”的形式來約束人們對服飾的理解和使用,使穿衣戴帽被緊緊地籠罩在政治的光環(huán)之下,所以,對服飾的選擇不再是個人喜好的自由天地.再加上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意識和文化觀念的超穩(wěn)定狀態(tài),使得服飾并沒有因為一頂頂王冠的易主而有所改變,反而成為歷代王朝竭力繼承的傳統(tǒng),對中國傳統(tǒng)服飾美學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更多的歷史階段上,看到的是民族大融合、生產(chǎn)力水平的改變、尤其是社會文化思潮對服飾的發(fā)展變化都有所影響.不管是趙武靈王迫于軍事壓力不得已而為之的“胡服騎射”,還是個體意識覺醒后帶有反叛意味的魏晉士人的著裝習慣;不管是政治開明、民族文化交融時期盛唐服飾表現(xiàn)出來的空前解放,還是明代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人的消費欲望被激發(fā)出來并轉化為智慧與行動之后,人們在服飾方面所表現(xiàn)出來的巨大創(chuàng)造與革新能力,都使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中華傳統(tǒng)服飾在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那種跌宕起伏的力度和張力.
古代審美移情理論發(fā)展基礎
[摘要]中國古代雖然沒有建立起完整的移情說美學體系,但存在著不少對審美移情現(xiàn)象進行探究的理論。作為漢語母語中的“移情”,其概念具有不確定性,一是指改變性情以向善,這個意思又作“移情性”;二是指情誼的改變;三是指心境的變化。前兩個概念與心理學上的移情較為相似,指稱“心境變化”的“移情”則與西方審美中的移情作用比較接近。與西方美學相比,中國古代審美移情更看重自然對自我生命情感的影響以及自我與自然的交流。中國古代審美移情理論成熟于魏晉時期,魏晉玄學在這個成熟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王弼“達自然之性暢萬物之情”的說法為中國古代審美移情理論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
[關鍵詞]移情;悲秋;物境;心境;達自然之性;暢萬物之情
(一)審美中的移情作用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從亞里斯多德到里普斯,西方美學史上關于審美中的移情作用的研究源遠流長,但最早把“移情作用”這個概念明確地作為美學名詞提出來的是R·費舍爾(RobertVischeer,公元1847-1933)。費舍爾在其《論視覺的形式感情》(公元1873)中把與形式主義相對立而被要求的、應引導到事物象征化的心理活動起名叫“移情作用”,指的是觀照者對事物及其心理狀態(tài)無明確表象而且把移入那里的情感內(nèi)容帶到現(xiàn)實的共同體驗中來。后來美國實驗心理學家蒂慶用“Empathy”這個詞來翻譯它。英語中另外有一個詞“Transference”也是指移情作用,但“Transference”僅用于精神分析學領域。作為精神分析學領域的移情作用,他指的是“人在成年時感受到的不為原激發(fā)人而為另一人引起的童年時代所感覺過的情緒”,也即“按照早期的藍圖相互塑造對方形象的方式”,這是弗洛伊德在對奧地利內(nèi)科醫(yī)生與生理學家約瑟夫·布魯爾的醫(yī)療案例進行研究后創(chuàng)立的一種理論。這種移情概念在精神分析學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有人甚至認為移情概念的起源就是精神分析學說本身的起源。〔1〕審美中的移情作用經(jīng)費舍爾提出后,真正將其理論系統(tǒng)化的美學家則是里普斯(TheodorLipps,公元1851-1914)。里普斯把人的情感分為“自我活動的情感”、“自我愉悅的情感”、“自我價值的情感”三種。但“自我價值的情感”本身不成為審美價值。因為審美價值是作為不同于自我的對象的價值感受到的。因此審美價值應該是“客觀化的自我價值情感”。里普斯的移情說美學原理就在于說明這種客觀化的可能性。概略地說,里普斯的移情作用等概念指的是,在審美活動中,審美主體一方面把自己的價值情感在對象中加以客觀化,在這里完成客觀的審美價值內(nèi)容;另一方面觀照給定的對象,使之在自己心靈中主觀化,然后在自己的現(xiàn)實情感中加以體驗。其理論核心在于:把對象主觀情感化過程同時作為自我情感的客觀化加以考慮,據(jù)此深刻地把握審美意識中主客觀融合的關系。〔2〕中國古代有無審美移情理論,對此學界有不同看法。德國美學家W·沃林格認為移情說美學只能解釋文藝復興以前的古典藝術,而無法加以說明古代東方藝術。〔3〕王福雅認為“中國古代雖有‘移情’一詞出現(xiàn),但并沒有移情理論的存在”〔4〕。但王先霈說,移情概念在社會心理學和審美心理學中各有自己的含義,這兩個概念涉及的心理現(xiàn)象、心理能力,中國古人都注意到了,都給予多方面的論述。關于人與自然景象之間的移情,中國古代文論家注意到它的雙向性,認為物移我情和我情注物、移我就物和移物就我是同時發(fā)生的雙向作用。關于人與人之間的移情,古代文論家不僅把它看做心理分析和推想的能力,而且認為是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是滿懷同情心的對待他人。這是中國古代移情思想的精華。〔5〕作為一種審美現(xiàn)象,古今中外的審美活動應具有同樣的移情作用,只不過因為語言、文化和理論形態(tài)本身的差異,我們很難將中外美學的移情理論完全等同,但這并不能說中國古代就沒有審美移情理論的存在。王先霈先生講的人與人之間的移情是“中國古代移情思想的精華”的觀點也似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中國古代關于人與人之間的移情,主要是在道德意志層面上展開,屬于倫理哲學或政治哲學的范疇,而人與自然景物之間,同時也包括人與藝術作品之間的移情更接近西方美學中的移情學說。中國古代雖然沒有建立起相對完整的移情說美學理論體系,但存在著大量的審美移情現(xiàn)象和對這種現(xiàn)象進行探究的理論。本文擬在朱光潛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古代的審美移情理論進行初步的研究,以有助于加深對中國古代美學理論形態(tài)的獨特性的討論。
(二)
審美中的移情作用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xiàn)。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朱光潛先生曾以《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這個故事來說明美感經(jīng)驗移情作用的“結果是死物的生命化,無情事物的有情化”〔6〕。六十年代,朱光潛先生在研究西方美學的移情理論時又說:我國古代語文的生長和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移情的原則進行的,特別是文字的引申義。我國古代詩歌的生長和發(fā)展也是如此,特別是“托物見志”的“興”。最典型地運用移情作用的例是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以及在南宋盛行的詠物詞。〔7〕依照朱光潛先生的這個說法,我國先秦文學中出現(xiàn)的“悲秋”母題,實際上也就是審美中的移情作用。從《詩·秦風·蒹葭》托物言志,以茂密的蘆葦和白露秋霜為情感載體,吟唱出思念情人的哀愁到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泬廖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
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
傳統(tǒng)界畫建筑美學思想與文化認同
摘要:中國傳統(tǒng)界畫是一門獨特的寫實性創(chuàng)造藝術,界畫構思創(chuàng)作過程與建筑工程圖之間關系非常緊密,其繪制時使用的工具、繪制技法與古代建筑圖樣亦非常相似。自東晉以來界畫秉承古建筑工程圖樣要求的嚴謹性,在創(chuàng)作注重寫實的同時還要精通古建筑原理、分解結構、剖析幾何原理與構思布置,繪畫藝術與工藝技術兼?zhèn)涞耐瑫r還要有豐富的想象力。本文旨在通過探究傳統(tǒng)界畫,發(fā)掘界畫背后的建筑美學思想與文化認同。
關鍵詞:界畫;建筑美學;文化認同
界畫是建筑藝術與繪畫藝術的完美結合,在宋代達到了高峰。鄧國祥《界畫與中國古代建筑環(huán)境生態(tài)觀》、潘怡《界畫中的建筑意味與人文精神》、蘇丹《界畫于界線內(nèi)超越限定》、董朝陽《從界畫作品中解讀古建筑的藝術特色》、方振寧《繪畫和建筑在何處相逢?》、陳嘉全《建筑視野中的趣味繪畫藝術形態(tài)》等一批專家學者的論著通過歷時已久的深入研究,對界畫及其相關領域進行了詳盡的論述,爬梳了中國傳統(tǒng)界畫發(fā)展及其理念建樹的起起伏伏。本文擬在眾多研究基礎之上對中國傳統(tǒng)界畫中的建筑美學思想和文化認同進行進一步闡釋。
一、傳統(tǒng)界畫的緣起與發(fā)展
(一)界畫的緣起
要論述中國傳統(tǒng)界畫的建筑美學思想和文化認同,就首先要明晰界畫的緣起與發(fā)展。界畫最初應用于建筑圖稿,后經(jīng)眾多畫家的藝術實踐發(fā)展成為畫科,界畫是一種繪畫的技法,又被稱為“樓觀”或“屋木”,最早起源于東晉時期。顧愷之《論畫》一書中有關于界畫的記載描述:“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
文藝美學構架論文
摘要:文藝美學是傳統(tǒng)美學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和諧論”文藝美學體系弘揚、發(fā)展了古今中外的美學思想和藝術理論,它對藝術審美本質(zhì)的界定吸收了康德的思想,又超越了康德把美歸于形式的傾向,將美與藝術統(tǒng)一起來。“和諧論”文藝美學對美和藝術既有總體的把握,又對藝術作品的審美構成作具體探索。文藝美學的方法論與其理論體系運用以辯證思維為統(tǒng)帥的多元綜合一體化的方法,構筑了一個縱橫結合、網(wǎng)絡式、圓圈型的邏輯框架。
關鍵詞:關學思想;文藝關學;和諧論;審美關系
為了使人們便于理解和掌握“和諧論”的理論體系,我把自己在學術上的一些追求概述一下:
一、我認為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學科,既是傳統(tǒng)美學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又是20世紀誕生的一個新興學科,有的同志說它是中國美學家對世界美學一個獨特的創(chuàng)造和貢獻,是有道理的。因為時一間短,目前學術界對文藝美學的對象、內(nèi)容和學科定位,有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有益的。我根據(jù)長期反復地思考,試從研究視角、方法、對象、內(nèi)容和相關學科的關系等五個方面,界定文藝美學的內(nèi)涵、性質(zhì)和學科位置。我認為文藝美學既是哲學美學和藝術部門美學的中介環(huán)節(jié),又是文藝社會學、文藝心理學的并列學科。但似乎不是美學與文藝學交叉產(chǎn)生的既非美學、又非文藝學的第三種學科,也不是黑格爾式的藝術哲學之一。
因為傳統(tǒng)的藝術哲學只有單一的哲學視角和哲學方法,所以文藝社會學主要是社會學的視角和方法,文藝心理學也主要是心理學的視角和方法,它們都著重從一個方面揭示文藝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而文藝美學則將哲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視角和方法綜合起來,力圖多視角、全方位地展現(xiàn)藝術的審美本質(zhì)和美學規(guī)律。它是哲學美學、藝術哲學的一個新發(fā)展。它是整個美學科學的一個構成部分,在學術范圍和學科性質(zhì)上是屬于美學學科的,同時它又吸收和融合了文藝心理學、文藝社會學的視角和方法,也可成為彼此互動互補的文藝學的并列學科。
二、在理性的科學認識和感性的倫理實踐之間的藝術本質(zhì)的審美規(guī)定上,我也在著力弘揚和發(fā)展古今中外的美學思想和藝術理論。古希臘的摹仿再現(xiàn)美學,在自然和人本、客體與主體的素樸統(tǒng)一中偏重于客觀本體的認知;古代中國偏于抒情的表現(xiàn)美學,在自然和人本、客體和主體的素樸和諧中偏重于主體心靈的呈現(xiàn)。西方17世紀理性派和經(jīng)驗派的對立,特別是康德之后,在自然與人本、主體和客體的二元對立基礎上,日益轉向主體情感的表現(xiàn)。從康德開始客觀本體日益轉向人類理性主體,以后又擅變?yōu)榘馗裆纳黧w。海德格爾則由康德抽象的主體,走向感性的生存著的“此在”(Dasein)。雅斯貝爾斯則由海德格爾原始的主客體未經(jīng)分化但又非個體的“此在”,走向“我”這一“非知識性”個體的決定論。如葉秀山同志所分析的:他認為“我”不是由因果律決定的,不是“我”的過去決定了“我”的現(xiàn)在,“我”的現(xiàn)在決定了“我”的未來,而是“我”吸收了過去和將來,我是決定性的,“我”自己決定我是(什么)。這種“我”的存在論意義上的個體決定論,把個體主體突現(xiàn)到首要地位。解構主義的德里達,則在否定客體本體的基礎上進一步否定了一切本質(zhì)、中心,把一切歸于個體主體的虛構,它用主觀相對主義勾銷了客體、絕對和普遍真理。總之他們拒絕傳統(tǒng)的客觀的理性認識論,拒絕知識哲學,只強調(diào)存在、主體、人、生存的個體的本體性,只承認藝術是“存在的本真的”呈現(xiàn),是人的主體的“呈現(xiàn)”,而否認藝術的客觀性、認識性、真理性。這有部分的真理性,但也似更為極端和片面。因而近現(xiàn)代的中國美學,雖然在西方文化、美學的沖擊和影響之下,卻沒有像西方那樣極端,而是在曲折中走向更高的和諧。和諧美學的藝術審美本質(zhì)論綜合了古代和近現(xiàn)代的美學并予以辯證的發(fā)展,真正突破了西方近代的二兒對立,審美地把理性的科學認識和感性的倫理實踐、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客體再現(xiàn)和主體呈現(xiàn)辯證地和諧地統(tǒng)一起來,力圖在二者之間巧妙地恰到好處地把握藝術的審美特征。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導言》中所說的藝術是對世界“實踐—精神的掌握”方式,也正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理解。1983年我曾寫過《論馬克思關于藝術掌握世界的方式》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我認為藝術掌握“既不是單純的物質(zhì)實踐,也不是單純的精神思維,而是兩者的融合”也就是說,“既與感性實踐活動的感性、具體、物質(zhì)性相聯(lián)系,又與科學認識活動的理性、抽象、精神性相聯(lián)系,同時在根本上又不同于感性實踐和理性認識。它是感性與理性、心理與認識、情感與理智、具體和抽象、物質(zhì)實踐性和精神息識性的和諧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