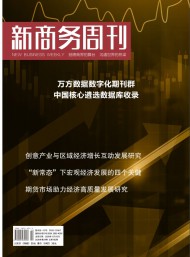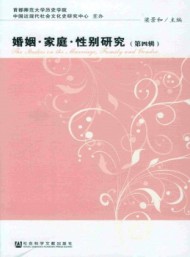宏大敘事范文10篇
時間:2024-02-05 18:15:38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宏大敘事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宏大敘事個性化管理論文
[論文關鍵詞]馮小寧戰爭題材電影歷史化藝術化
[論文摘要]馮小寧對戰爭題材電影模式的突破,體現為從宏大敘事到個性化敘說的轉型,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獨特的意義。這是中國電影藝術思維方式從歷史化向藝術化的根本轉變,它帶來了電影語言從戲劇沖突、場景設置和人物心理挖掘等多方面審美效果的提升,為電影用來表達戰爭與人的關系提供了符合人類共同審美價值的有益探索。
對馮小寧戰爭題材的電影,評論界關注的人比較多,觀眾的評介也很高,但在電影史著作中,評價卻不高,有的電影史甚至無視它的存在,如2006年出版的李少白的《中國電影史》。僅有兩部電影史介紹了馮小寧的電影,一部將它作為娛樂政治化和政治娛樂化的代表,認為它是準娛樂化的電影;另一部則認為“它揉合了戰爭類型片、美國西部片、言情片和風光片的各個要素,因而比傳統的純粹描寫戰爭的影片更新穎,更具觀賞價值。……但無庸諱言,馮小寧的幾部電影在主題、結構等方面陷入了一種固定的模式。雖然在制作水平上一部比一部精致、華麗,但總覺得缺乏一種獨到的主體體驗而有拼湊之嫌,人物缺乏深度。”這些評價抹煞了馮小寧在電影史上的地位,事實并非如此。
馮小寧九十年代以來以《紅河谷》、《黃河絕戀》、《紫日》為代表的幾部戰爭題材影片,突破了已有的模式化,以電影手段表達了自己對戰爭與和平、生與死、愛與恨、情與仇的理解,個性化色彩鮮明,基本上清除了戰爭題材紀錄片的痕跡,向戰爭題材電影藝術化邁進了一大步,在中國電影史上,有它獨特的意義。
過去的戰爭題材電影,往往設置宏大的場景、眾多的人物、二元的敵我對立態勢、模式化的社會背景,造成宏大敘事的格局,追求史詩性的表達,制作目標是再現和還原真實的歷史,使電影成為戰爭歷史的紀錄片。這類電影,創作主體的個性表達被掩蓋,觀念相對陳舊,公式化、概念化色彩被形式主義大場景所迷惑,缺乏對戰爭深刻的反思力度,忽略人性,無視弱小生命。如《大轉折》、《大進軍》、《大決戰》等影片,延續的是五六十年代《南征北戰》、《保衛延安》等電影的制作模式,盡管有所變化,但根本觀念沒變。過去,也有一些小制作,如《百合花》、《渡江偵察記》、《紅色娘子軍》、《英雄兒女》等,但思維模式是一樣的,同樣是為了書寫歷史,只是從小人物的角度去證明宏大敘事的歷史書寫的合法性。
戰爭題材電影的歷史化和藝術化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前者的目標是再現和記錄以某種集體意識為“先見”而書寫的歷史的合法性,后者追求的是創作主體通過戰爭所引發的個體個性化的思想情感的表達,指向的是現實的人對生命的即時感悟,它所敘述的是個體記憶中的歷史。馮小寧的電影,消解了已有的條條框框,他也表現歷史,但他所表現的歷史,不再是已有的經過集體意志裁定了的權威的合法的歷史,而是主體自身感悟到了的具體生動的、人性化的、情感化的歷史。在《紅河谷》中,主體努力彰顯的是民族個體對藏漢民族血脈相融、同仇敵愾的大中華情感的體驗和認同。雪兒達娃與阿媽、與格桑之間的親情與戀情,消解了民族之間的隔閡。正如頭人面對羅克曼的挑釁時所說的:“這個是漢族,這個是回族,這個是藏族,這是一家人,我們家里的事情就不用你們管了。”民族意識的自然流露,是個體對民族大家庭的自然認同。《黃河絕戀》借用歐文的視角來敘述中國人之間的內部矛盾,盡管異常尖銳激烈,但在“家仇”和“國恨”的選擇中,民族大義對每一個中國人而言卻始終擺在第一位,在黑子、安寨主和三炮之間,最終統一的意志體現在抗擊外族入侵的行動中。《紫日》超越了狹隘的民族情感,使之上升為一種對人類各民族之間和平相處的共同愿景的渴望,有著相對豐厚的人類共同的人性基礎,同樣是創作主體個性化的生命感悟。
宏大敘事默化管理論文
論文關鍵詞:春晚的意義意識形態宏大敘事凝聚和諧
論文摘要:特殊的形式構成、特殊的題材內容和特殊的風格追求,使得春節聯歡晚會的藝術展演活動融入了年節民俗的文化意味,體現著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寄托著炎黃子孫的生活理想。節慶聯歡的實用目的與辭舊迎新的功利追求,賦予這臺晚會更為豐富多彩的思想內涵。
春節聯歡晚會問世于1983年的除夕夜,春節晚會劇組采用了現場直播的節目傳輸形式,并用現場開辟的4部熱線電話加強這種“共時性”與臨場感。這樣,人們在觀看晚會節目時,就不再是簡單地與己無關的“觀看”,而是要“在春節晚會中過年三十”了——春節晚會把能夠看到電視的中國觀眾都卷入到了這臺晚會之中。這天晚上,電視節目的收視率驟然上升,人們普遍愛上了這種通過現場直播與億萬同胞在春節晚會中高高興興“過節”的新樣式。春晚發展到今天,也引起了大眾的一些思考,它對于國家,對于社會的發展又有著什么樣的意義呢?
一、春晚所蘊涵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我們從春晚走過的這24年中不難看出春晚每年的節目形式都涵括了歌舞、相聲、小品、戲劇、雜技等傳統的文化節目,有的還增加了西方的歌劇、魔術等吸引人的新穎節目,雖然節目眾多,但每一年的晚會都有一個主題。這些主題都是積極健康向上的,如1984年春晚的主題是愛國、統一、團結;1996年春晚的主題是歡樂、祥和、凝聚、振奮、輝煌;2002年春晚的主題是愛國頌、社會主義頌以及改革開放頌。所有的主題都深刻體現了我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應該從勞動者的立場出發,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出發點,積極吸收現代意識形態發展的成果,在公共利益與個體權利的平衡框架內,確立社會主義的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從而豐富和完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具體表現在: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和為貴,追求社會的和諧;以勞為美,尊重勞動的價值;以法為基,維護公民的權利;以公為善,保障公民當家作主;以家為安,實現安居樂業。
國家宏大敘事探討論文
一、春晚所蘊涵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我們從春晚走過的這24年中不難看出春晚每年的節目形式都涵括了歌舞、相聲、小品、戲劇、雜技等傳統的文化節目,有的還增加了西方的歌劇、魔術等吸引人的新穎節目,雖然節目眾多,但每一年的晚會都有一個主題。這些主題都是積極健康向上的,如1984年春晚的主題是愛國、統一、團結;1996年春晚的主題是歡樂、祥和、凝聚、振奮、輝煌;2002年春晚的主題是愛國頌、社會主義頌以及改革開放頌。所有的主題都深刻體現了我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應該從勞動者的立場出發,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出發點,積極吸收現代意識形態發展的成果,在公共利益與個體權利的平衡框架內,確立社會主義的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從而豐富和完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具體表現在: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和為貴,追求社會的和諧;以勞為美,尊重勞動的價值;以法為基,維護公民的權利;以公為善,保障公民當家作主;以家為安,實現安居樂業。
二、春晚的定位與主題構成
眾所周知,多年來春節聯歡晚會的主題,基本都被定位于諸如喜慶、歡樂、團結、祥和與開拓、奮進、昂揚、向上等等。這不是電視文藝編導包括晚會創演者的一廂情愿,而是全體中華兒女千百年來年節慶典的普遍意愿與共同心聲的高度概括與集中體現。內容決定形式。春節聯歡的特殊需求,決定了這臺電視晚會的形式特征。
很顯然,特殊的形式構成、特殊的題材內容和特殊的風格追求,使得春節聯歡晚會的藝術展演活動融入了年節民俗的文化意味,體現著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寄托著炎黃子孫的生活理想。節慶聯歡的實用目的與辭舊迎新的功利追求,賦予這臺晚會更為豐富多彩的思想內涵。交流和宣傳國家與民族在過去一年里的巨大成就,歷數和展示各行各業在過去一年里的風云變幻,更是春節聯歡晚會的題中應有之義。
國家宏大敘事管理論文
摘要:特殊的形式構成、特殊的題材內容和特殊的風格追求,使得春節聯歡晚會的藝術展演活動融入了年節民俗的文化意味,體現著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寄托著炎黃子孫的生活理想。節慶聯歡的實用目的與辭舊迎新的功利追求,賦予這臺晚會更為豐富多彩的思想內涵。
關鍵詞:春晚的意義意識形態宏大敘事凝聚和諧
春節聯歡晚會問世于1983年的除夕夜,春節晚會劇組采用了現場直播的節目傳輸形式,并用現場開辟的4部熱線電話加強這種“共時性”與臨場感。這樣,人們在觀看晚會節目時,就不再是簡單地與己無關的“觀看”,而是要“在春節晚會中過年三十”了——春節晚會把能夠看到電視的中國觀眾都卷入到了這臺晚會之中。這天晚上,電視節目的收視率驟然上升,人們普遍愛上了這種通過現場直播與億萬同胞在春節晚會中高高興興“過節”的新樣式。春晚發展到今天,也引起了大眾的一些思考,它對于國家,對于社會的發展又有著什么樣的意義呢?
一、春晚所蘊涵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我們從春晚走過的這24年中不難看出春晚每年的節目形式都涵括了歌舞、相聲、小品、戲劇、雜技等傳統的文化節目,有的還增加了西方的歌劇、魔術等吸引人的新穎節目,雖然節目眾多,但每一年的晚會都有一個主題。這些主題都是積極健康向上的,如1984年春晚的主題是愛國、統一、團結;1996年春晚的主題是歡樂、祥和、凝聚、振奮、輝煌;2002年春晚的主題是愛國頌、社會主義頌以及改革開放頌。所有的主題都深刻體現了我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應該從勞動者的立場出發,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出發點,積極吸收現代意識形態發展的成果,在公共利益與個體權利的平衡框架內,確立社會主義的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從而豐富和完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具體表現在: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和為貴,追求社會的和諧;以勞為美,尊重勞動的價值;以法為基,維護公民的權利;以公為善,保障公民當家作主;以家為安,實現安居樂業。
人文審美宏大敘事管理論文
【論文關鍵詞】人文審美新聞作品
【論文摘要】審美表述形態是多元的、個性的,新聞傳播活動是獨具個性魅力的審美創作過程,為了實現審美價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聞作品的審美感染力,它要求審美創造者即新聞記者,要敢于在傳播價值和形態上進行創新和突破。情感是對客觀現實的最活躍的—種表現形式,注重情感氛圍的營造是紀實類報道獲得強勢傳播效果的重要審美特征。《內蒙》系列片從取材、用景、鏡頭處理、細節設計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眾的審美感染力。
《內蒙邊防紀事》系列片(以下簡稱《內蒙》)從策劃到拍攝,從選材到內容,非常注重凸現電視文本人文化的傳播價值和審美性的表述形態。全部紀實內容以審美主體即記者親身經歷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離地感知、接觸和體驗傳播對象,同時該片的取材和選景均從細節、微小處入手,通過生動的畫面和極富感染力的電視語言,體現審美與人文的有效結合,深入客體內心,實現情感共鳴。
正是憑借這種人文化的傳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會極大關注。受眾直視記者對生活原生態的審美化表述和對審美對象深層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體全方位親歷原生態,實現傳播者審美與人文意識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紀實親歷中,記者對審美對象進行探索隱式的解讀,體現了人生對于記者的一種考驗,從某種程度上講,記者體驗的背后其實就是一種“冒險”,在面對特殊的審美對象時,記者要敢于去接觸和征服。因此,主體全方位親歷原生態,是構成審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沒有這種全方位接觸,記者即使去親歷,也只是與審美對象“蜻蜓點水”,難以形成能傳輸深層審美意義的體驗。
春晚宏大敘事凝聚和諧特點論文
摘要:特殊的形式構成、特殊的題材內容和特殊的風格追求,使得春節聯歡晚會的藝術展演活動融入了年節民俗的文化意味,體現著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寄托著炎黃子孫的生活理想。節慶聯歡的實用目的與辭舊迎新的功利追求,賦予這臺晚會更為豐富多彩的思想內涵。
關鍵詞:春晚的意義意識形態宏大敘事凝聚和諧
春節聯歡晚會問世于1983年的除夕夜,春節晚會劇組采用了現場直播的節目傳輸形式,并用現場開辟的4部熱線電話加強這種“共時性”與臨場感。這樣,人們在觀看晚會節目時,就不再是簡單地與己無關的“觀看”,而是要“在春節晚會中過年三十”了——春節晚會把能夠看到電視的中國觀眾都卷入到了這臺晚會之中。這天晚上,電視節目的收視率驟然上升,人們普遍愛上了這種通過現場直播與億萬同胞在春節晚會中高高興興“過節”的新樣式。春晚發展到今天,也引起了大眾的一些思考,它對于國家,對于社會的發展又有著什么樣的意義呢?
一、春晚所蘊涵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我們從春晚走過的這24年中不難看出春晚每年的節目形式都涵括了歌舞、相聲、小品、戲劇、雜技等傳統的文化節目,有的還增加了西方的歌劇、魔術等吸引人的新穎節目,雖然節目眾多,但每一年的晚會都有一個主題。這些主題都是積極健康向上的,如1984年春晚的主題是愛國、統一、團結;1996年春晚的主題是歡樂、祥和、凝聚、振奮、輝煌;2002年春晚的主題是愛國頌、社會主義頌以及改革開放頌。所有的主題都深刻體現了我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應該從勞動者的立場出發,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出發點,積極吸收現代意識形態發展的成果,在公共利益與個體權利的平衡框架內,確立社會主義的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從而豐富和完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具體表現在: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和為貴,追求社會的和諧;以勞為美,尊重勞動的價值;以法為基,維護公民的權利;以公為善,保障公民當家作主;以家為安,實現安居樂業。
新主旋律電影敘事策略分析
摘要:近年來,一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電影在上映后屢獲高票房,甚至成為現象級作品。這些新主旋律電影與傳統主旋律電影存在著明顯的不同,主要體現在敘事策略方面。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由宏大敘事的范式轉向微宏敘事,同時更加注重人文關懷,以平民的家國情懷為視角,運用多元化結構完成敘事,這種敘事策略為今后新主旋律電影的創作提供了參考。
關鍵詞:新主旋律電影;敘事策略;《我和我的祖國》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是在2019年國慶檔期間上映的一部獻禮片,于短時間內獲得了票房和口碑的雙豐收。影片選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以來的7個代表性事件,在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主題下由不同的導演創作完成。電影是敘事的藝術,把故事講好是創作者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作為新主旋律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是如何打破傳統敘事范式,在商業片大行其道的今天獲得成功的?本文在對電影進行文本分析的基礎上探尋其敘事策略,以期為新主旋律電影的發展找尋突破口。
一、新主旋律電影的誕生與發展
電影是具有雙重屬性的文化產品,長期以來,其意識形態屬性是我國電影生產中的重要支撐,由此涌現了一大批符合主流價值觀的主旋律電影,然而其經濟屬性卻遭到忽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很好地吸引受眾。近些年來這一狀況有所變化,在國家政策主導下,電影的商業價值得到業界的重視,在制作過程中不僅更加尊重受眾的需求,還積極轉變創作理念,生產出了有別于主旋律電影的作品,從而獲得了更好的傳播效果。有學者認為,這些同樣是弘揚主旋律的電影,需要與之前的進行區分,所以開始使用“新主旋律電影”的概念。早在20世紀30年代我國就已經出現了反映主流價值觀的電影。新中國成立以來,電影的意識形態導向更加受到國家重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電影市場得到繁榮發展,在數量上出現了較大的增長,也出現了一些滌蕩心靈的作品。與此同時,主旋律電影的概念不斷得到厘清,時任廣電部電影局局長騰進賢在1987年提出了電影制作要堅持主旋律的發展方向,又在1991年的全國電影創作會議后提出具體要求:“我們的電影創作應該突出頌揚時代精神,即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它應成為一種融匯于創作主體的全部藝術思維過程和創作過程中的自覺的內驅力,是充實于電影藝術家創作實踐中的體現著社會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的精神力量。”1994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在會上提出“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主旋律電影的創作再次得到重視。然而,很多主旋律電影堅持宏大敘事這一范式,電影敘事結構單調、視角單一,帶有濃重的說教意味。特別是在商業片大量上映之時,主旋律電影的影響力往往不夠理想。進入21世紀以后,得益于文化產業的不斷改革,這一現象逐漸發生變化。以《建國大業》為標志,官方主導的愛國主義題材電影開始更加注重受眾的需求,并加入商業元素,大批明星聯袂出演,塑造了視覺和聽覺上的“奇觀”。理念上,創作者更加尊重電影的規律,開始回歸到電影的本體層面敘事。為了對不同時期的主旋律電影進行更好的區分并開展相應的研究,有學者提出了“新主旋律電影”的概念。就有關新主旋律電影的研究而言,一些研究者認為新主旋律電影在堅持主流價值觀的基礎上,創作手法更加靈活,具有商業化和娛樂化的特征。也有學者認為主旋律電影實質上等同于主流商業大片,這一觀點是將新主旋律電影放在以經濟效益為導向的商業大片的范疇進行研究,無法充分地與更加重視政治性的主旋律電影進行比較研究,會造成研究的割裂。周漢杰和曲瑋婷則認為,“區別于傳統主旋律電影,新主旋律電影不再將政治性、藝術性和商業性三者割裂開來,而是用更加廣泛的題材、更多樣化的敘事、更豐滿的人物形象、更多元化的影像表現方式來承載中國新時代的精神,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也具有豐富的思想價值內涵。”這一概念更加完整、準確地概括了新主旋律電影的特性、題材和敘事等內涵,因而本文將在這一定義基礎上展開研究。
二、新主旋律電影的敘事策略
民族命運與個體倫理敘事構造
電視連續劇《雪豹》以國家民族命運為敘事背景,以抗日戰爭中的特種部隊作戰這一新題材為敘事脈絡,講述了周衛國跌宕起伏、堅持不懈,從一名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蛻變為優秀的八路軍指揮員的故事,譜寫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國共攜手抗日”的雄渾歷史篇章,再現了當年烽火硝煙、浴血鏖戰的抗日崢嶸歲月,實現了宏大民族命運與個體倫理的敘事同構。劇中宏大的革命歷史敘事中融入對個體生命和生存價值的關注,宏大敘事因個體生命的血液滋養而鮮活,個體生命也因宏大敘事的雄渾浩闊而得以張揚與提升。周衛國集聰慧、精靈、豪氣、俠義于一身的形象,突破了傳統抗戰題材電視劇英雄形象的固定模式,《雪豹》的敘事也因其恢弘敘事的個體性超越而達到一個新的敘事高度。
一.宏大敘事與個體敘事的有機融合
與其他敘事藝術一樣,電視劇是敘事的藝術,而且更多的是一種個體敘事。這種敘事模式以個體為中心和出發點,把個體放在波瀾壯闊的社會大環境中進行展現,呈現個體豐富的情感、多彩的生活、復雜的心理和跌宕起伏的人生。個體敘事離不開社會環境,個體只有在社會這個大背景下才能成為主角,以個體來再現歷史與現實。也就是說,個體敘事只有與宏大敘事融合,才能完成電視劇的敘事功能。宏大敘事又稱“元敘事”,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渾然一體,在宏大敘事中,國家的意識形態始終處于主導地位,掌握著話語權。個體作為“革命者”而存在,其意識和家庭情感被意識形態捆綁,個體是“國”的衛道士、是國家利益的化身。《雪豹》很巧妙地把家、國二者表現出來,它不排斥宏大敘事,而是把此種話語表現得更加隱蔽。個體作為“人”而存在,生命主體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國和家是個體的自然回歸,而不是預定的議程設置。《雪豹》的宏大敘事在這里具有象征意義,而個體作為主體則始終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全劇只是在第一集簡單地介紹了十九路軍淞滬抗戰的戰爭場面,這個場面是作為社會背景交代,為周衛國和陳怡出場作鋪墊。從第二集始,就把周衛國、陳怡作為主角來渲染。之后,大部分的劇情和內容都是圍繞著周衛國而展開的。周衛國槍殺日本武士,是日本人欺負了陳怡,他已經深深愛上了陳怡。周衛國的成長歷程,是貫穿于全劇的主線。《雪豹》將敘事置放于抵御外敵侵略時代背景下的青年成長史,于家庭的聚散和成員的成長關注中,展示那段浩闊的革命歷史和激變慘烈的命運搏戰,雙向映照了一段曲折慘烈的國家和民族建構史。周衛國離家報考軍校,與蕭雅相識、相愛,到德國深造,與日本軍官竹下俊相識,回國抗日,從虎頭山到清風寨落腳,參加八路軍,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始終是作為個體而存在。他最樸素的愿望,就是為蕭雅報仇。他從虎頭山逃走加入清風寨,是因為對八路軍抱著懷疑的心態。他秉持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信念,第二次到虎頭山加入八路軍,后來他通過自己的觀察和體驗,發現八路軍是真心抗日、真心為老百姓的,這時的他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者”,完成了信念的回歸和提升。周衛國和竹下俊這一對人物關系的設定,從根本上對傳統宏大敘事的預設觀念進行了徹底顛覆,人物依照個體倫理敘事的脈絡,關注生命價值和個體意義本身,將信仰與國家、民族命運置放于個體成長的事件和沖突中,將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對立融化于個性生命存在的血脈間。竹下俊教授周衛國劍術和日語,情同手足,抗戰爆發后兩人為了各自的祖國,分別之時劃地絕交。兩人帶領著各自的特戰隊斗智斗勇,最后一次見面,竹下俊砍下自己的右臂謝罪,周衛國血刃竹下俊。我們看到的是彰顯于敘事外層的同窗情和反目為仇,而暗藏于敘事背后的則是信仰運行之下的國家敘事和民族敘事,通過對深深根植于人物血脈的個體生命價值和意義的叩問,深刻而鮮活地揭開那段風起云涌的民族歷史畫卷。在個體敘事和民族敘事的相互嵌入中,周衛國的成長史揭示了歷史的風云際會,歷史和民族的恢宏背景托舉個體生命的存在和意義,宏大敘事中的個體性超越,使得周衛國與時代悲歡與共,如影隨形。
二.新英雄敘事與平民敘事的交相輝映,以民間視角講述個性英雄的傳奇故事
作為大眾文化建構的藝術載體,《雪豹》自覺承擔起挖掘民族文化的生命內核、重新審視民族心理、重鑄民族靈魂的重擔,將新英雄敘事和平民敘事結合起來,以形象生動的鏡像藝術語言定格周衛國、陳怡、張楚、劉遠以及雪豹突擊隊員,重新建構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記憶。新英雄敘事是對傳統英雄敘事的消解與重建,將主要人物置身于想象的戰爭環境中,時空的處置具有相當的個性化和隨意性,歷史的真實性與編導者的歷史想象幾乎同質同構。通過社會與個人、世俗與高尚、平庸與偉大這一系列矛盾的解構,挖掘人性深處的美好品質,實現回望歷史,重塑英雄的文化期待和審美訴求。周衛國是用生命和智慧全力抗日的中華鐵血兒女的化身,編導者將傳奇性與原生態有機地集結在他身上,為電視劇敘事帶來了難能可貴的張力。他受過高等教育,留過學,精通多國語言,與《我的團長我的團》中的龍文章、《亮劍》中的李云龍、《士兵突擊》中的許三多等“另類英雄”不同,在他身上復合了太多的“唯一”,果敢堅定、足智多謀、能文善武。他的成長歷程與最終命運,是這部作品能夠自始至終吸引觀眾的重要原因。他與陳怡、張楚、劉遠、邱明、李勇、許光榮、水生、劉三等等許多具有獨特性情和鮮活個性的人物,共同編織了一個獨具一格的英雄譜系。編導者在理想化與世俗化之間尋找一個平衡支點,以民間視角講述個性英雄的傳奇故事,令受眾耳目一新,凸顯了抗戰題材電視劇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突破與創新。同時也使新英雄敘事突破了概念話語的桎梏與就事論事的藩籬,獲得了更加廣闊、自由的表達空間,擁有了一種與當下觀眾相互溝通、彼此交流的現代意識。周衛國歷盡曲折跌宕,其報國之心不變,不屈不撓的意志不變,舍小家為大家的精神不變。正因如此,在虎頭山根據地才出現了國共合作、軍民聯手,各抗日武裝互幫互助、同仇敵愾的大好局面。這種敘事主體視角,淡化了意識形態的宣傳,使敘事情節的設置顯得自然、合情合理,因而更富人情味與厚重感。一部優秀的電視劇,敘事結構和敘事話語是多維的而非單一,《雪豹》的敘事模式,還有精英文化敘事的痕跡。精英文化敘事不回避對個體存在的叩問,而是促使人們去正視現實,正視歷史,正視人生的意義,為人們提供社會人文遠景和審美理想,復活人類面對生活的勇氣、榮譽感、自尊心、同情心及自我犧牲精神等。周衛國、陳怡、張楚等知識分子尊重生命、尊重友誼,憧憬愛情,更有為國獻身的遠大志向。當個體與革命發生沖突時,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這種選擇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也是個體情感的自然過渡,這種自然過渡使個體的生命意義與國家命運緊密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周衛國、陳怡、張楚在一場阻擊戰中準備突圍時,周衛國叫陳怡跟著張楚,張楚說:“陳怡跟著你我放心,論文化你不如我,論打仗我不如你,跟著你安全。”在敵軍重重包圍之下,張楚想到的是別人,而不是自己,盡管他與周衛國在對待陳怡的情感上有隔閡有矛盾,但他不顧自己的安危把生的希望留給別人,這種精神,是中國精英知識分子的精神,是中國革命的精神。英雄的精神給國人的心靈以慰藉和觀照,構成道德倫理的震撼,形成道德倫理的積淀。積淀愈深,觀眾的精神境界就越高。
三.多維敘事中的個體性超越
淺談電視劇《新世界》的高開低走
摘要:2020年開播的國產電視劇《新世界》,擁有成為年度爆劇的天時、地利、人和。該劇以小見大的劇情設定、和平解放北平的時代風云、別具一格的臺詞對白、場景制作的大手筆、演員的精湛演技,都寄托了主創人員的完美理想和觀眾的較高期待。然而,開播之后業界人士褒貶不一,收視率一路走低,呈現出高開低走的趨勢。本文通過反思藝術的完美與觀眾審美的平衡統一,分析人物塑造、藝術設計、敘事結構三個方面的問題和不足,以期為國產電視劇的未來提供借鑒和思考。
關鍵詞:《新世界》;高開低走;人物塑造;情節設計;敘事結構
《新世界》是由徐兵編劇并執導的一部紅色傳奇電視劇,于2020年1月播出。《新世界》的創作團隊試圖將藝術追求與經濟效益相平衡,在亂世的背景中探索人性的善惡,從小市民生活中發現時代的縮影。不得不說,《新世界》具有成為精品制作的諸多條件:以小見大的劇情設定、和平解放北平的歷史故事、別具一格的人物臺詞、大手筆的場景制作、數位演技派演員的參與……然而,通過業界人士的反響和觀眾的收視數據來看,頂流團隊的價值沒能很好地轉換成電視劇的好口碑和高收視率,編劇導演的理想追求沒能激起觀眾的情感共鳴。這一方面說明中國觀眾的藝術審美能力正在提升,另一方面也提示文藝界的主創人員,中國電視劇若想成為佳品,還應在人物塑造的真實性、情節設計的合理性和敘事結構的完整性三方面多一些思考和實踐。
一、人物塑造游離邏輯真實
《新世界》試圖通過展現角色從平凡人到不平凡人的過程真實地重現戰亂年代的景象。導演“以小見大”的創作理念值得稱贊,但是由于劇情的設定導致人物形象失真,劇中多數人物的行為性格不符合邏輯,甚至使人覺得匪夷所思。以主角徐天為例,導演設定的人物行動主線是尋找“小紅襖”。在尋找的過程中參與到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業中,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在斗爭中不斷得到升華,最終成為新世界的一份子。這個角色本應是劇中最具成長前途的人物,但是為了凸顯他不顧一切追求正義的一面,導演在表現他個性時用力過猛,比如,徐天在抓捕不法分子時經常因為青澀魯莽而惹上麻煩,甚至常有性命之憂,大哥金海多次救他于水火之中。但是,他卻懷疑大哥是殺死小朵的兇手,甚至要與其兵戎相見,絲毫沒有感恩之心。諸如此類的表現已經偏離了正常人物的行為邏輯,不但有損人物在觀眾心目中的好感,還讓人物變得脫離時代,不接地氣,更難以承擔起一部70集電視劇的宏大主題。再說田丹,田丹作為一位留學歸來的年輕女共產黨員,性格“剛柔并濟”。她既承載著創作者對共產黨與人民關系的理解,也承載著創作者對共產黨人作為黨員與作為人的關系的理解,還承載著創作者對性別關系的理解①。“剛柔并濟”本來是女共產主義者完美的特點,但是角色卻在兩方面的拿捏上失去了平衡。創作者為了強調她為人民犧牲的無私奉獻精神,過于突出她“柔”的一面,沒能表現出共產黨人的英勇氣概。演員在劇中自始至終慢條斯理、有氣無力,失去父親的悲痛、被男友背叛的憤怒、越獄時的緊張、受傷時的痛苦,田丹都是相同的氣定神閑,絲毫沒有與劇情呼應的張力②。這樣的表現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演員對于人物性格的把握不夠到位;另一方面,導演將人物的活動范圍大部分設定在監獄中,也使得人物的表現張力受到局限。
二、情節離奇脫離藝術真實
婚戀交友類節目的電視文化
一、主持人———節目風格的顛覆
主持人作為一檔電視節目中的重要符號,觀眾對主持人的首要印象也通常奠定了這檔節目的內在風格。因此,以前傳統的電視節目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規定,就是主持人的風格基本要與節目風格相統一。例如,新聞節目通常需要相對嚴肅、正氣一些的主持人,而綜藝娛樂節目則需要幽默、親和一點兒的主持人。從符號學的視角來說,主持人和節目形式都是電視節目主旨的能指,他們作為電視節目的一種符號,都是為真正的所指服務的。傳統的電視觀念認為,這種能指與所指必須嚴格對應,才能不削弱節目的主旨或造成節目的歧義。例如,當年紅遍兩岸的交友節目《非常男女》的主持人胡瓜和高怡平,他們的搭配是極其相稱的。這種相稱體現在該節目的總體風格基調與主持人高怡平的隨性、胡瓜和藹的外形并且頗具內在的幽默感是極其吻合與相配的。隨著媒介環境的不斷發展,后現代電視觀念有著新的嘗試,《非誠勿擾》就打破了傳統的符號法則。節目組讓一個本是新聞面孔的主持人孟非來和這檔婚戀交友類的綜藝娛樂節目進行混搭,這可以說是對主持人符號的一種“顛覆”。這種看似本來全然不搭界的組合,卻起到了人氣爆棚的節目效果與影響力,以至于后來湖南衛視不惜重金請來原央視新聞主持人邱啟明來給改版后的《我們約會吧》帶來新的活力和生機。對比“胡瓜”、“孟非”這兩個符號,我們會發現他們是截然不同的兩類能指,可他們的所指卻是同一類節目。不同的是,前者處在傳統的電視文化下,而后者則處在后現代主義的電視文化下。當然,他們所面對的觀眾需求確實也發生了迥然變化。
二、節目平衡感的顛覆
“平衡”是傳統電視節目講求的一個基本原則,而后現代電視文化下的電視節目有時卻是在有意打破這種規律,去追求一種所謂的“不平衡”。選擇男女搭配主持,這是《非常男女》的一個節目符號,也是傳統電視節目中平衡原則的一種體現。傳統的電視觀念認為,男女婚戀交友類節目應該是由男女兩個主持人符號才能夠體現出節目本身“男女婚戀”的內涵。然而在后現代電視文化下,這種符號含義已完全失效。大多數交友婚戀類節目,如當年紅火的《非常男女》、《玫瑰之約》、《相約星期六》等,男女嘉賓的人數通常都是相同的。這既與節目中男女需要兩兩搭配的形式有關,也與節目的內在平衡需求相關。而在《非誠勿擾》節目中,每輪上場的一位男嘉賓需要面對24位女嘉賓,這種24∶1的懸殊比例絕對是對傳統過度平衡的電視文化的一大顛覆。后現代文化下顛覆平衡的方式還有很多。美國近幾年熱播的交友婚戀類節Beautyandthegeek,就以另一種形式打破了傳統電視節目的平衡感。他們選擇的男女嘉賓人數雖然相同,但在實際生活中卻是極不搭調的兩類。女孩基本都是胸大無腦的美女(即節目名稱中的Beauty),而男孩則是IQ很高但EQ極低的書呆子(即節目名稱中的Geek)。這種在日常生活中本來難以見到的搭配,卻使得該節目有了相當的視覺效果和收視效果。追根溯源,這種顛覆其實是與節目的訴求有關。Beautyandthegeek與《非常男女》不同,它的訴求并不在于參加的男女選手最后是否能夠婚戀成功,而是節目本身的性質更像一檔游戲節目,參與者娛樂了,觀眾娛樂了,最后的結果就被淡化掉了。
三、個人敘事在節目中的放大———宏大敘事的顛覆
宏大敘事的淪陷,小敘事、個人敘事的出現,是后現代敘事文化的一種轉型。按照利奧塔爾的理解,現代主義在知識問題上的特點就在于:求助于元話語或宏大敘事來使知識合法化。所謂“后現代”其實就是對于元話語和宏大敘事的懷疑。后現代主義文化反對宏大敘事,但是肯定小型敘事的作用。這一點在婚戀交友類節目中就表現在:個人因素、個性行為在電視節目中經常被放大。在《非誠勿擾》中被成功放大的個體符號舉不勝舉,最先出名的便是“馬諾”。馬諾是一名來自北京的平面模特,從《非誠勿擾》的首期一直待到了24期。由于在節目中大膽、犀利的言論(如“我還是坐在寶馬里哭吧”、“放首《解脫》讓他下去吧”)而迅速走紅。我們暫且不論“馬諾”和節目組之間是不是雇傭關系。但是,馬諾在節目中“個人敘事”的放大絕不是一種偶然,而是后現代電視文化下節目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后現代的電視文化認為,個人元素的放大是一項雙贏的工作。個人敘事實際是為宏大敘事服務的,不管是“馬諾”還是“馬伊咪”等,都是節目效果下的“小敘事”與“小元素”,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節目的整體效果。確實,《非誠勿擾》對“馬諾”的放大,成功地捧紅了馬諾,但更重要的是制造出了話題,做出了節目效果。但是不得不說的是,“個人敘事”的放大也要有一個界限,正如《非誠勿擾》中馬諾最終還是要被請走的,但是節目中還是會出現下一個被放大的“馬諾”。對比當年的《非常男女》,在節目的宏大敘事下,每一期的個體元素基本都是很相似的,沒有被刻意放大的小敘事、個人敘事。或許其中某一期的某些男女嘉賓會讓你有比較深刻的印象,但這種印象也并沒有像“馬諾”一樣引起“蝴蝶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