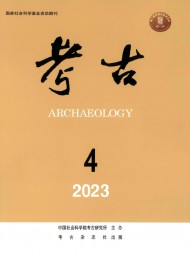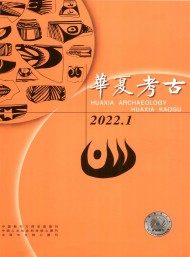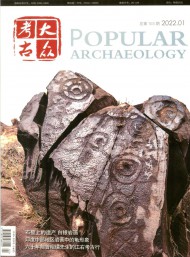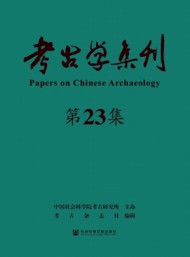考古范文10篇
時間:2024-02-19 12:06:50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考古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美術考古史古琴藝術
2003年11月7日,聯(lián)合國科教文組織公布了第二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國古琴藝術入選其中,可以說是名至實歸。因為古琴藝術在中國音樂史上處于重要地位,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有著深遠影響。與其他種類的傳統(tǒng)樂器相比,有關古琴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即便如此,對于古琴歷史上許多問題,如形制的定型,演奏方式的改變等等,史上或是語焉不詳,或是付諸闕如,總而言之,還是非常缺乏或根本沒有文本資料為之提供證據,以解答琴史上的一些疑問。為此,我們采取圖像證史的方法,應用中國美術考古史上所發(fā)現(xiàn)的圖像資料,如壁畫、畫像石、陶俑、繪畫等作為證據,以期為復原中國古琴藝術的歷史提供參考。所謂“圖像證史”,是西方學術界的一種歷史研究方法,其基本觀念就是:圖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證詞一樣,也是歷史證據的一種重要形式。“圖像”一詞原文為ima-ges,泛指各種繪畫、雕塑、工藝品以及攝影照片,影視畫面等所有視覺藝術作品。本文僅將“圖像”一詞,限定在中國考古所發(fā)現(xiàn)的視覺藝術作品范圍之內。正如《藝術中的音樂》主編茲得拉科夫•布拉熱科維奇所指出的那樣,“藝術作品對于記錄樂器的歷史,它們的結構和演奏技巧具有重要意義”①。粗略檢索一下中國考古史上所發(fā)現(xiàn)的有關古琴的圖像資料,深感布氏所言,實乃不刋之論。本文根據美術考古史和繪畫史所提供的資料,分別從古琴藝術所涵蓋的四個方面,即古琴形制、制作工藝、演奏方式的演變以及古琴從伴奏到獨奏的發(fā)展予以考釋論述。恰如標題所示,本文兼有兩個中心思想,兩個主題:一方面是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琴藝術;另一方面是美術考古所發(fā)現(xiàn)的涉琴藝術作品。與圖像證史方法論者不同之處在于,我們認為,藝術作品不僅僅是為歷史提供見證的資料,更主要的依然是它所具有的審美功能。因此,本文在分析每一幅視覺藝術作品時,既要指出其作為琴史證據的關鍵之所在,同時也不忽略對它的審美觀照。
一、古琴的創(chuàng)制與定型———《竹林七賢畫像石》的意義
琴是中國最為古老的弦樂器之一。關于它的起源,傳說甚多,諸如神農氏、伏羲、堯、舜創(chuàng)制之說,雖不可盡信,但也不是無稽之談。根據古籍文獻所載,其初創(chuàng)的時間,至少可上溯到商代。對此,可以從詞源學上予以說明。殷墟甲骨文中,有一“樂”字,古文學家把它隸定為“樂”字,為“樂”字的繁體。據羅振玉考釋:“此字從絲附木上,琴瑟之象也”②。西周時代的金文與甲骨文之“樂”字構形相同,唯西周金文在兩絲之間增加了一個“白”字,為“樂”,與《說文》之篆文一樣。有研究者認為,金文所加之“白”,以象調弦之器,或象拇指之形,或以搏拊琴瑟之意。我們知道,一個“能指”總是出現(xiàn)在“所指”之后,換言之,正因為先有了琴瑟之類的弦樂器,然后才有可能創(chuàng)造出能夠指稱它的文字和名詞。因此,從“樂”字的起源可以推斷出,至少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中國就己經出現(xiàn)了琴瑟之類的絲弦樂器,這應該是一個勿庸置疑的歷史事實。古籍文獻亦支持了這一結論。《尚書•皋陶謨》就有“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的記載;《詩經》中有許多篇章,如《關睢》、《鹿鳴》、《棠棣》等,更是以琴瑟為比興,來抒寫作者的情志。例如:用“如鼓琴瑟”,以喻“妻子好合”;用“琴瑟友之”,以喻“窈窕淑女”。由此可以看出琴瑟在兩周時期的普及程度。但是,由于制作琴瑟的材料主要是蠶絲和桐梓等材料,容易腐朽霉爛,難以長久保存。所以,直到1977年隨州曾侯乙墓發(fā)掘之前,對于先秦時期的古琴究竟是個什么樣子,除了文獻所述之外,人們一直無緣一睹其芳容與風采。曾侯乙墓出土的琴,根據墓葬年代,制作時間應該在公元前433年之前。從形制上看,此琴的主要特征是半箱式、十弦、無徽。1993年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所出土的古琴,根據該墓下葬年代,此琴制作時間應該在公元前300年之前,其形制亦為半箱式,七弦,無徽。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七弦器之實物標本。與此相似的考古發(fā)現(xiàn),還有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西漢早期七弦琴。就古琴之形制而言,從曾侯乙墓的十弦琴,到郭店楚墓再到馬王堆漢墓的七弦琴,具有明顯的同源關系。而弦數的差異則是古琴形制演變所留下的軌跡③。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從唐代流傳至今所有古琴實物,形有定制,均為全箱式、七弦、并有十三個琴徽。現(xiàn)在的問題是,從先秦到漢代,古琴之形制一直處于不斷發(fā)展演變之中,那么,它究竟是在什么時候基本定型為今天所見之樣式的呢?古籍文獻中沒有記載,考古發(fā)現(xiàn)中未見實物,唯一能給出答案以供參考的只有美術考古史上所發(fā)現(xiàn)的有關古琴的圖像資料。1960年4月,在南京西善橋古墓中出土了以“竹木七賢”和榮啟期為題材的拼鑲磚畫。根據發(fā)掘者對墓葬年代的認定,此畫應為南朝晉宋時期的作品。這是一件非常精彩的淺浮線雕,被研究者認為最能說明魏晉南北朝時期人物畫和山水畫的繪畫藝術之水平④。壁畫為兩幅,南北對稱,其幅面均為240×80厘米,堪稱巨幅。每壁繪有四個人物圖像,均采取席地而坐的姿勢。為了表明“竹林七賢”是如何悠游于竹林樹叢之間,作者獨具匠心,用青松、翠竹、垂柳與銀杏將他們彼此間隔開來。如此一來,既能表現(xiàn)“竹林七賢”的共性特征,又能揭示其各自不同的個性特點。試看所繪八個人物,情態(tài)各具典型,神情均極生動。整個畫面非常簡潔古樸,線條相當流暢,人體比例十分勻稱,尤其是衣褶線條剛柔兼?zhèn)洌胺Q“畫體周瞻”,“體韻遒舉”之作。其中的榮啟期,據《列子•天瑞》所述,為春秋時期的山林隱士,同時也是鼓琴高手。圖中所繪之榮氏,鹿裘帶索,正在撫琴而歌,頗具隱逸風采。“竹林七賢”中的嵇康、阮咸和阮籍,都是音樂史上著名的琴家。尤其是嵇康,不僅琴藝出類拔萃,而且在音樂理論上也頗有建樹。其所著之《聲無哀樂論》和《琴賦》,均為中國音樂美學史上的重要文獻。正如壁畫所描繪的一樣,只見經常以“弾琴詠詩自足于懷”的嵇康,頭梳雙髻,跣足跽坐于銀杏樹下,正在怡然自得地輕撫著琴弦,彰顯出一幅“非湯武而薄周孔”的氣慨,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三國志•魏書》嵇康傳記載,因其傲視權貴而被司馬氏所殺。臨刑前,嵇康從容地援琴而鼓,既而嘆日:“《廣陵散》從此絕矣!”所謂“絕啊”一詞,即因此而來。當然,對于本文來說,所有這些似乎都只是題外話,因為我們所關注的重點,乃是此圖中一個不起眼的細節(jié)———榮啟期和嵇康兩人所彈的琴。具體來說,就是他們所彈古琴之琴面外側赫然布列著的十余琴徽。此乃迄今為止古琴上出現(xiàn)徽位的最早的圖像資料。在此之前,文獻中提及琴徽的有漢代枚乘的《七發(fā)》,揚雄的《解難》,以及魏晉時期的嵇康。嵇康的《琴賦》有這樣的儷句:“弦以園客之絲,徽以鐘山之玉”。但因無實物標本,究竟何時出現(xiàn)琴徽一直無法得到確證,直到“竹林七賢”畫象石的出土,這一疑問才得以破解。就古琴的形制而言,除琴身與琴弦的變化外,琴史上最重大的發(fā)明就是琴的徽制。因為徽制的出現(xiàn),古琴就能實現(xiàn)由一弦一音到一弦數音的變革。如此一來,古琴的音域就能得以拓展,其表現(xiàn)力亦隨之而得到豐富和提高。當然,徽制的發(fā)明,必須有音樂理論上的依據,否則,琴徽之排列的合理性也就得不到保證。換言之,如果沒有十二律的發(fā)明和完善,要想準確地分割弦音以做標點的十三徽制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中國古代的十二律理論完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樣就為徽制的發(fā)明提供了上限年代的理論依據,而南京西善橋晉宋古墓所出土的“竹林七賢”畫像磚,則為徽制的確立提供了下限年代的圖像證據。綜上所述,具有全箱式、七弦、十三徽之特征的古琴,其形制的演變始于戰(zhàn)國早期(公元前433年以前),基本定型于六朝晉宋之際(至遲在公元479之前)。
二、古琴制作的工藝流程———顧愷之《斫琴圖》略說
宋代朱長文在其所著之《琴史》中指出,“琴有四美:一日良質、二日善斫、三日妙指、四日正心。四美兼?zhèn)洌瑒t為天下之善琴”。由此可知,對于古琴藝術而言,選擇合適而又優(yōu)良的材料,繼之以高超的制作工藝,是其必備而又重要的基礎。斫琴之道首先在于選材,古代琴人對此深有體會,《詩經•定之方中》里面就有這樣的詩句:“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據研究者考證,此詩創(chuàng)作于公元前662年。可見早在三千年前,古人就己認識到只有桐梓等木材才是制作琴瑟的最佳材料。從那時起,直到現(xiàn)在,所有的標準古琴,大都以較硬的桐木為琴面,以較軟的梓木為琴底,尤以年久干透的桐梓為佳。我國制琴歷史悠久,經驗豐富,從理論上予以總結的論著也很多,如宋代石汝礪的《碧落子斫琴法》,趙希鵠的《古琴辨》等。其所歸納出的制琴之“秘訣要旨”,除了選材之外,還必須遵循一系列的技術規(guī)范,如材料的厚薄,琴身的規(guī)格尺寸,龍池,鳳沼的布局以及髹漆工藝等等。總而言之,只有選用了優(yōu)良的材料,掌握了精湛的技術,才能夠制作出造型古樸典雅、音質純凈,音色優(yōu)美的古琴。非常有趣的是,美術史不僅為古琴形制的演變提供了圖像見證,而且還對古琴的制作進行了生動,準確而形象的描繪,如顧愷之的《斫琴圖》畫卷。顧作原件不存,今人所見為宋代摹本⑤。由畫上所鈐之印可知此圖從北宋宣和以來,流傳之緒未曾間斷,現(xiàn)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畫卷為絹本設色,畫幅為29.4×130.0厘米,引首題有“斫琴圖”三字,畫面所描繪的正是古琴制作的整個場景:只見那些工匠們有的在刨制琴板,有的在紡制琴弦,有的在組裝琴身,還有的在調弦聽音。如果要給《斫琴圖》加一個副標題的話,名之曰“古琴制作之工藝流程圖”可謂恰如其分。由此可見,繪畫史上以講究神韻著稱的顧愷之,同時也具有驚人的寫實能力。尤其應該注意的一個細節(jié)是,圖中所見之琴面與琴底,不僅兩板寬窄長短一致,而且還可以看到底板上的龍池、鳳沼,表明顧愷之時代的古琴,其琴身是挖薄中空的兩塊木板上下拼合而成為全箱式,較曾候乙墓的十弦琴和郭店楚墓及馬王堆漢墓的七弦琴,已經有了很大改進,因而與唐代以后的古琴在形制上完全一致。《斫琴圖》雖為宋人摹本,但是流傳有緒。特別是圖中所繪人物器具,有著十分明顯的晉畫風格,從中似乎可以領略到顧愷之的“春蠶吐絲”之筆法:不僅線條勻細,而且還有一種真切的自然感。從這一點可以推斷宋人摹本的腳本,斷然不是一般贗品。因此,顧愷之的《斫琴圖》不僅記錄了當時制琴的工藝流程,而且還與《竹林七賢畫像磚》一樣,為古琴形制最后定型年代的斷代提供了依據。定型后的古琴,不僅僅是一件實用的樂器,而且還是一件工藝美術作品,為古往今來的愛好者們所鑒賞、收藏。鑒賞一件古琴,主要從材質、形制、樣式、斷紋、琴銘款識等入手。就像畫家要在自己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標明作畫時間地點一樣,斫琴者往往也會在琴的槽腹或納音兩側鐫上自己的姓名和制作時間地點;就像畫家或鑒藏家往往喜歡在畫卷上題詞賦詩、鈐印畫押一樣,許多琴家或古琴鑒藏家們也樂于在古琴上題琴名、寫琴銘,以抒其獨特的情志,彰顯其高雅的琴趣。由此可見古代琴與畫的共通之處。同時,對于古代知識分子來說,古琴不僅僅是實用樂器,也不僅僅是工藝美術作品,而且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觀念的載體,古代哲學思想在音樂文化方面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如漢代桓譚之《新論•琴道》、蔡邕之《琴操》,都曾說到琴之創(chuàng)制,其目的在于“御邪僻,防心淫,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而琴的形制,則被賦予了諸多象征的意涵:如琴長三尺六寸五分,象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十三徵象征一年十二個月及閏月;琴身上隆象天、下平法地、中虛含無;至于琴弦,初始為五,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總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琴藝術,承載了太多的歷史文化信息⑥。
三、古琴演奏方式的變化軌跡———從東漢武梁祠畫像石到北宋的《聽琴圖》
水利考古研究探索與思考
摘要:楚都壽春城遺址所在的壽縣城位于淮河南岸、八公山南麓,東淝水從東南向西北繞城而過,西邊是壽西湖,西南方有大型水利工程安豐塘(芍陂)。依山傍水的獨特地理環(huán)境造就了壽春城遺址,無論從宏觀角度的都城選址,還是微觀角度的高臺建筑、給排水設施等方面,與水和水利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聯(lián)。文章從回顧壽春城遺址水利考古的嘗試與探索歷程入手,對壽春城遺址研究的成果與收獲進行了小結與思考,以期對將來的工作有所裨益。
關鍵詞:楚都壽春城;水利考古;回顧與思考
作為楚國晚期最后一個都城,楚都壽春城也是為數不多的南方地區(qū)先秦時期大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壽春城遺址的考古研究工作,對于了解楚國城市的發(fā)展過程、對比研究戰(zhàn)國時期南北方都城的異同以及探索中國古代都城從周制向漢制的轉變等問題,均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極具特色的地理位置和區(qū)位條件,使得水利考古成為壽春城遺址考古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研究內容。本文試圖通過對以往考古工作進行簡單的回顧和梳理,以期有助于我們今后工作的思考和探索。
1壽春城遺址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
楚都壽春城遺址位置的確認是文獻記載和考古發(fā)現(xiàn)相結合得出的成果。根據文獻記載,壽春城的地望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是今壽縣縣城附近;第二種是城西四十里;第三種是城西南四十里的豐莊鋪。在李三孤堆楚王墓的發(fā)現(xiàn)揭開了楚文化研究的序幕之后,壽縣地區(qū)陸續(xù)在一些基建工程中發(fā)現(xiàn)了“大之器”[1]、鄂君啟節(jié)[2]、大量的金幣郢爰[3][4]和部分青銅重器等高等級遺物,壽縣地區(qū)的文物工作者還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壽縣縣城東南一帶時常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一些陶器碎片、水井等遺存。圍繞著今壽縣城,其東南方向的長豐、楊公一帶經調查發(fā)現(xiàn)除李三孤堆墓以外仍有一批具有高大封土的墓葬,其中有11座大中型墓葬已經過發(fā)掘[5];其西南的雙橋一帶也發(fā)現(xiàn)有相當數量的保存有較大封土堆的中等貴族墓葬[6][7]①;而北部的八公山南麓至東淝水之間發(fā)現(xiàn)有大量的中小型戰(zhàn)國晚期墓葬。上述這些發(fā)現(xiàn)與研究使學界對壽春城遺址位于壽縣縣城一帶的結論基本達成了共識。壽縣城的位置,從大的地理區(qū)塊上來說,地處黃淮平原的南部,淮河中游的南岸,其主體地形地貌為平原與低矮丘陵、小型山地相間分布的狀態(tài)。壽春城遺址依山傍水,其北部的八公山為一條起自鳳臺、淮南直至定遠、嘉山一線的低山丘陵帶的最高峰。發(fā)源自江淮分水嶺的東淝水和淠河分別從遺址的東、西兩側穿流而過注入淮河干流,淮河北岸最大的支流潁河也在遺址西側的正陽關入淮河,淮河干流則自西南向東北從遺址的西北面流過(圖1)。從氣候方面來看,此地為我國氣候南北分界的過渡地帶,受季風影響較大。這一方面使本地區(qū)降水和地表徑流量均較為豐富,另一方面比較集中的降水季節(jié)性和年際變化均較大,存在較大的水旱隱患。作為都城選址的壽春城,之所以選擇在壽縣城關附近,便利的水陸交通條件和具備良好的軍事屏障的區(qū)位優(yōu)勢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根據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國古代中原通江南之道大概有以下幾條線路:一是關中通往南陽盆地和襄樊的“商山—武關道”;二是河南南陽盆地與湖北襄樊之間的“南襄隘道”,又稱“夏路”;三是淮河上游地區(qū)與長江流域之間的“義陽三關”;四是淮河下游地區(qū)連接長江流域的“邗溝”,即江淮運河;五是連通淮河中游地區(qū)與長江流域的“巢淝通道”[8]。而壽春正是處于中原通江南的“巢淝通道”的交通要沖①。晉伏濤《正淮論》中有描述,壽春“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簡而言之,壽春城北面有八公山作為天然屏障,東淝水在古城的東、北兩面形成天然的護城河,西南部分河湖水網密布,良田沃野千里,物產豐富[9]。春秋晚期受楚國擠壓而遷至州來的蔡國對該地區(qū)的經營與建設,為楚國晚期遷都于此奠定了前期基礎②[10]。戰(zhàn)國初期越滅吳,隨即楚滅蔡并控制江淮,至戰(zhàn)國中期楚人又將江南南陵、銅陵等地的銅礦占據[11],加之春申君黃歇的苦心經略,春秋時期開始修建的安豐塘周圍形成了良田沃野,提供了豐美的糧草,這些均為楚最終遷都壽春提供了有利條件。
2壽春城遺址水利考古的嘗試與探索
文物考古先進事跡材料
欣聞河南省文史研究館確定今年將首次為該館館員出版一套文史叢書,和我一起共同為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yè)奮斗了半個多世紀的文物考古與古建筑著名專家楊寶順同志的《文物考古與古建筑文集》已被列入其中,不勝之喜。
寶順同志自1951年參加工作以后,半個多世紀來一直奮戰(zhàn)在文物考古與古建筑工作的最前線,先是參加了文物調查和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后來又以畢生的精力從事古建筑的勘察測繪和保護維修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受到省和國家的表彰與獎勵。如由他負責主持保護修繕的具有重大歷史藝術價值的唐代古塔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陽修定寺塔,其藝術價值之高在全國古塔之中十分罕見,塔身遍布精美華麗的磚石雕刻,而且均為唐代原構,全國絕無僅有。寶順同志在接受了這一任務之后,首先對塔的現(xiàn)狀和殘壞情況進行了認真的調查研究,勘查測繪,然后擬制出科學的保護維修方案,并一直在工地與其他同志一起參加施工工作。我記得在此塔的年代問題發(fā)生爭論的時候,他多方進行實物研究和文獻查考,向有關專家請教,費盡了千辛萬苦,不僅把這座“中國第一華塔修定寺塔”修繕完工而且還了它唐代原物的真實名份。為此以該塔“飾面花磚的復制研究及補砌鋃嵌工藝的兩項研究成果”而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級科技成果獎。
又如由他負責領隊、深入到太行山區(qū)對素有“神秘的萬佛溝”之稱的寶山靈泉寺及其石窟和摩崖石刻塔林等,進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查和清理研究工作。
因該寺院地處深山峽谷中曾長期遭受山洪泥沙沖擊,自清末以來其寺院建筑遺址多被湮埋地下,附近的石窟及摩崖石刻塔林等也大部被泥沙湮蓋和堵塞。因而要查清這處千年古剎的本來面貌是十分困難的。為了完成勘查清理任務,寶順同志與其他同志一道堅持食宿在這處人煙稀少的山溝里,長達半年之久,從未離開崗位一步。最后終于克服種種困難全部完成了既定的考古勘查清理及現(xiàn)場研究任務。不僅將這處全國現(xiàn)存時代最早、數量最多、雕刻藝術精美、風格獨特并多數刻有塔銘的摩崖石刻塔林(包括北齊雙石塔共158座)全部展現(xiàn)出來。而且還完成了附近三處石窟,即:由著名高僧道憑開創(chuàng)的東魏“大留圣窟”和刻有北齊著名高僧僧稠供養(yǎng)像及碑銘的北齊“善應石窟”及由隋代著名高僧靈裕開鑿的隋代“大住圣窟”,以及寺院基址的勘查清理工作。從而揭開了這處鮮為人知的“神秘的萬佛溝”之謎。大量實物史料表明,寶山靈寺及其石窟塔林,歷經東魏、北齊、隋、唐、宋數個朝代。為我國佛教大發(fā)展的南北朝、隋、唐時期的產物。不論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還是在中國佛教發(fā)展史上,都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作用。因此,我對寶順同志這次擔任領隊克服多種困難完成了全部勘查任務,所獲得的成果,表示高度的稱贊。寶山靈泉寺的考古勘查清理任務完成后,寶順同志又及時將材料進行整理并撰寫成書出版。受到上級領導部門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曾被授予河南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省級獎。寶山靈泉寺及其石窟摩崖塔林,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此外,寶順同志還在地下考古方面,曾主持過許多古遺址和古墓葬等的調查、發(fā)掘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其中比較突出的如:1954年在鶴壁市首次勘查發(fā)現(xiàn)了宋、元時期,具有地方風格和巨大規(guī)模的瓷窯遺址。還曾應邀參加由中科院組織的黃河水庫考古隊,擔任河南地區(qū)領隊,按時完成了對黃河水庫湮沒區(qū)內的考古勘查工作,曾受到上級領導表彰。還負責主持完成了澠池西河南村仰韶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獲。他曾于1959年勘查發(fā)現(xiàn)了鶴壁市一處宋代的大型煤礦遺址。當時他曾在這處距地表50米深的古礦井下,堅持涉水勘查達30多小時之久,終于查清了這一古煤礦的原貌。除發(fā)現(xiàn)一些古瓷器和一方石硯外,更重要的是發(fā)現(xiàn)了古礦的4條巷道及當時的井口,照明用的燈龕、排水井、條筐及生產工具、運輸工具,以及空間巨大的采煤區(qū)10處。經研究新發(fā)現(xiàn)的井下古瓷器,其形狀、質地和釉色均與當地宋代瓷窯遺址中出土的相同,其文具石硯也是宋代遺物。從而表明古煤礦的時代,應為宋、元時期。為我國現(xiàn)今發(fā)現(xiàn)時代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煤礦遺址。對研究我國古代的采煤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史證價值。此外,他還在安陽的洹河之濱,首次調查發(fā)掘了一處規(guī)模較大的隋代瓷窯遺址。過去有些研究中國瓷器史的人,曾有一種“南青北白”的定論,但都被北方經常出土的青瓷所質疑。但北方多次出土的青瓷,其燒造的窯址究竟在何處?卻未曾見到。所以,多年來人們對此問題一直猜測不一。因此,寶順同志對安陽隋代相州瓷窯遺址的調查發(fā)掘成果,確鑿的證實了相州窯(安陽隋代時稱相州)的地點。這對研究我國陶瓷史是一突出貢獻。另外,他還主持過對安陽北齊范粹墓、溫縣唐代楊履庭墓及焦作的金代鄒復畫像石墓等多處重要古墓和古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工作,均取得了重要收獲。
寶順同志除了主持和參加了許多文物考古與古建筑保護維修、勘查測繪的實際工作之外,他還潛心學習,刻苦鉆研,把取得的經驗和成果總結歸納,寫作論文,編輯成書,以廣流傳和交流經驗。除《安陽修定寺塔》(1983年由中國文物出版社出版)、《溫縣慈勝寺》(1988年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寶山靈泉寺》(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及《文物考古與古建筑文集》(2004年由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出版)等專著之外,他幾十年來所寫的文物調查、考古發(fā)掘、古建筑考察研究,時代特征考證,年代鑒別,保護維修工程等的報告、介紹、論文等一百多篇,分別發(fā)表在國家、省各級報刊上,是一筆珍貴的當代歷史文化財富,如不將其收集整理出版,日久散失,將是河南乃至全國文物考古和古建筑歷史文獻的損失。為此,我非常贊佩河南省委、省政府和省文史研究館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視。在省文史館建館50周年之際,在已出版了由館員們撰寫的《中原文史萃編》一書之后,又將出版一套館員叢書,以展示館員的科研成果,豐富科學文化的內容,是屬一件功在當今,利及后代的盛舉。
考古發(fā)掘管理辦法
第一條為加強考古發(fā)掘管理工作,保護我國歷史文化遺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細則》和《國務院關于加強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適用于在中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所進行的一切考古發(fā)掘和水下考古活動。
第三條國家文物局統(tǒng)一管理全國考古發(fā)掘工作,一切考古發(fā)掘工作都必須履行報批手續(xù)。
第二章資格審定
第四條考古發(fā)掘實行團體和個人領隊負責制。具有考古發(fā)掘團體領隊資格的單位可申請考古發(fā)掘項目,具有考古發(fā)掘領隊資格的個人經具有考古發(fā)掘團體領隊資格的單位指派,擔任考古發(fā)掘項目的領隊。
第五條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國家文物局直屬考古科研單位,高等院校考古系(專業(yè))和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所屬文物考古機構及有條件的地、市所屬文物考古機構,具備下列條件者可申請考古發(fā)掘團體領隊資格:
科技考古概論課調查分析
《科技考古概論》是科技考古專業(yè)研究生的必修課,其作為一個基礎環(huán)節(jié),對學生進一步學習研究科技考古有重要影響.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國內較早開設了《科技考古概論》課程,經過多年的教學探索與實踐,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內部講義及教學方法,同時在師資隊伍培育、學生培養(yǎng)等方面取得較為顯著的成果.然而,科技考古是一門新興學科,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均不斷在拓展,而且《科技考古概論》課程涉及面非常廣,無論對教還是學而言,都極具挑戰(zhàn)性.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一直在探索《科技考古概論》課程的教學方法,并不斷進行教學改革.近年來,我們在多年教學積累與改革的基礎上,嘗試了更深入的教學改革.本文旨在通過調查,全面了解《科技考古概論》課程的建設情況,掌握學生的學習動態(tài)與需求,并在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思考,以期為進一步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1調查的基本情況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考古概論》教材與課程建設研究”課題組設計了《科技考古概論》課程調查問卷,并于2011年展開教學調查.
1.1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以2008級(簡稱08級,其余同此)至2010級選修過《科技考古概論》課程的研究生為調查對象.之所以做出如上選擇,主要是從08級開始,《科技考古概論》課程進行新一輪的教學改革研究,調查時08級至10級的研究生都還在校,較容易進行調查,而且他們對課程情況應還有較為清晰的記憶,因此調查結果更可靠.被調查的研究生共23名,其中碩士22名、博士1名;男生15名(65%)、女生8名(35%).
1.2調查工具
市區(qū)考古發(fā)掘方案
省文物局將古軍事城堡遺址向國家文物局申報了大遺址公園保護,為進一步加快推進申報工作,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受省文物局委派,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市文體廣電局、區(qū)文體廣電局聯(lián)合組成考古隊將于2012年對展開調查和考古發(fā)掘工作,為確保申報前期工作順利開展,經區(qū)人民政府研究,并報區(qū)委同意,特制定此工作方案。
一、組織領導
為順利推進古軍事城堡遺址考古發(fā)掘工作,決定成立古軍事城堡遺址考古發(fā)掘工作領導小組。
二、工作目標
此次考古發(fā)掘清理工作涉及總面積約50000平方米,對目前遺存的主要建筑群進行清理,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的考古發(fā)掘面積為500平方米,主要集中在海潮寺后的明代建筑群遺址,即“新王宮”,為深度發(fā)掘的重點。
三、明確職責任務,切實加強協(xié)作配合
宋遼金時代考古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河北;宋遼金時代;考古
【論文摘要】河北是宋遼對峙的前沿地區(qū),在宋遼金考古中的區(qū)域位置十分重要。河北的宋遼金時代考古有許多重要的發(fā)現(xiàn),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與北方遼金文化之間互相交流與碰撞的重要資料,在中國宋遼金考古領域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
一、宋遼金時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為統(tǒng)一北方與遼之間在河北地區(qū)頻發(fā)戰(zhàn)爭,對當地政治、經濟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壞。公元1004年,宋、遼締結澶淵之盟,約定以白溝河(今大清河一線)為界,雙方罷兵求和,從此進入和平相持時期。這種穩(wěn)定的環(huán)境有利于河北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和人們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進入一個南北分裂的時代,中南部地區(qū)屬宋,北部地區(qū)屬遼。這種情況直到公元1127年,金滅北宋后,河北全境統(tǒng)一屬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設路、府、州、縣等,河北主要分為兩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北東路所轄地區(qū)主要有:大名府、開德府、河間府,以及滄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轄地區(qū)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慶源府,以及相州、衛(wèi)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兩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區(qū)。
遼代行政建制設五京道,道以下設府、州、縣。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轄地域,相當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區(qū)。
農業(yè)農耕考古技術分析論文
在原始農業(yè)生產中,因種植作物不同,其收獲方法及使用的工具也不相同。收獲塊根和塊莖作物時,除了用手直接拔取外,主要是使用尖頭木棍(木耒)或骨鏟、鹿角鋤等工具挖取。收獲谷物時則是用石刀和石鐮之類的收割工具來收割。不過根據民族學的資料,人們最初也是用手拔取或摘取谷穗。如云南省金平縣的苦聰人收獲旱谷時,多數仍然用手折下谷穗。西盟佤族在使用鐮刀以前,收獲的方法是把谷穗拔起來或掐斷。怒族老人追憶,最初收旱稻是用手捋下穗上的子粒放進背簍里[146]。臺灣高山族也長期用手收獲谷物,陳第《東番記》記載明代臺南的高山族“無水田,治畬種禾,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明末清初鄭成功進入臺灣時,所看到的情況仍然是這樣,收割時“逐穗拔取,不知鉤鐮之便”(楊英《從征實錄》)。六十七所著的《臺海采風圖考》中也記載“番稻七月成熟,……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铚鐮”。可以推想,原始農業(yè)時期最古老的谷物收獲方法是用手摘取的。后來,當人們使用工具來代替手工之時,當然也會沿襲這個習慣。所以,最早的收割工具石刀和蚌刀等都是用來割取谷穗的。許多石刀和蚌刀兩邊打有缺口,便于綁繩以套在手掌中使用,晚期的石刀和蚌刀鉆有單孔或雙孔,系上繩子套進中指握在手中割取谷穗,不易脫落。商周以后的銅铚仍繼承這一特點,一直沿用到戰(zhàn)國時期。
至少在8000年前,石鐮就已經出現(xiàn)。像裴李崗遺址的石鐮就制作得相當精致,其形狀與后世的鐮刀頗為相似。從民族學的材料得知,一些使用鐵鐮的少數民族也是用它來割取谷穗的。如西藏墨脫縣的門巴族收獲水稻和旱稻時,是用月牙形的小鐮刀一穗一穗割下來放在背籃里,稻草則在地里曬干后燒掉作為來年的肥料。海南島有些地方的黎族,直到現(xiàn)在仍使用鐵鐮割取稻穗,然后將它們集中掛在曬架上曬干,需要時再加工脫粒。稻草留在田里,需要時用鐮刀割取,不需要時就燒掉做肥料。因此推測原始農業(yè)時期,先民們使用石鐮、蚌鐮只是割取谷穗,而不會連稈收割。這是因為當時禾谷類作物馴化未久,成熟期不一致,仍然保留著比較容易脫落的野生性狀,用割穗的方法可以一手握住谷穗,一手持鐮割鋸谷莖,這樣可避免成熟谷粒脫落而造成損失。同時,當時的谷物都是采用撒播方式播種的,用手抓不到幾根植株,要連稈一起收割莊稼是極為困難的。即使是已經使用金屬鐮刀的商周時期,也仍然是用這種方法收獲莊稼的。甚至晚到漢代,還保留著這種習慣。如我們從四川省成都市鳳凰山出土的東漢漁獵收獲畫像磚下半部分可以看到這種場面(圖六三),畫面左邊的三人正在割取稻穗,捆扎成束。最左邊一人將已扎好的稻穗挑走。右邊的兩人則高舉一種大鐮刀在砍割已經割掉稻穗的禾秸(如不需要稻草,則將它留在田中,任其干枯,來年春天就可“燒草下水種稻”了)。這種方法一來是沿襲古老的用鈺割穗的傳統(tǒng)習慣;二來適于在撒播的稻田里使用,可及時搶收,減少損失;三來可減輕運輸過程中的勞動強度。不過,漢代已實行育秧移栽技術,田中已有株行距,水稻品種也遠離野生狀態(tài),再加上鐵農具的普及,鐵鐮已非常輕巧鋒利,為連稈收割技術的運用打下了基礎。而適于割取谷穗的铚,則被鐮刀所淘汰。湖北省江陵縣鳳凰山西漢墓曾出土過四束古稻,是連稈割下的。這說明至少在西漢時期,有些地方已經采用連稈收割的方法(圖六四),此后就逐漸成為主流。我們在甘肅省的唐代壁畫中所看到的一些收獲場面,就是用鐮刀直接收割谷物秸稈的。
6.脫粒加工技術
人類最早的脫粒技術,難以從考古發(fā)掘中獲得實物證據,但從民族學的材料中可以得到啟示。先民們最早的脫粒方法是用手搓,如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大多是用手搓的方法對采集來的植物穗子進行脫粒。相信在原始農業(yè)萌芽時期,人們也是這樣做的。稍后則用腳踩的方法進行脫粒。我國西南地區(qū)的許多少數民族就是用手搓腳踩的辦法使谷穗脫粒的。如云南的布朗族人把收割回來的谷穗曝曬幾日,然后在地上鋪一篾笆,把曬干了的谷穗置于其上,旁栽一木樁,男女手扶木樁,雙腳搓踩脫粒。西藏墨脫縣門巴族則是把谷穗放在石板上腳踩手搓。云南西盟佤族所用腳踩手搓的脫粒習慣一直延續(xù)至今。此外,云南的獨龍族、怒族和傈僳族,西藏的珞巴族等都是用腳踩或手搓來脫粒的。稍后,人們用木棍來敲打谷穗,使之脫粒。如怒族、傈僳族、西盟佤族和門巴族等,解放前都是腳踩和棍打同時使用的。門巴族還敲打水稻。這種方法可以說是連枷脫粒的前身。怒族在收獲玉米后,在地上挖一淺坑,鋪上麻布毯,放上玉米穗,周圍用麻布毯子圍起,然后用木棍敲打。如收獲量少,可放在有眼的籮筐里,圍上衣服或麻布毯,用棍子來舂。這又可說是杵臼的前身了。由于木棍易于腐朽,難以在考古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實物,即使有木棍出土,也無法斷定就一定是用來脫粒的。同樣,連枷的使用已見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文獻,其發(fā)明年代應當更早,也因為竹木不易保存,難以從考古發(fā)掘中取得證明。
目前考古發(fā)掘中能夠確認的脫粒加工農具是杵臼和磨盤。如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木杵和裴李崗遺址出土的石磨盤都有七八千年的歷史。石磨盤是谷物去殼碎粒的工具,杵臼則兼有脫粒和去殼碎粒的功能,因而杵臼的歷史似乎應該更早一些。有些少數民族歷史上甚至沒有使用過石磨盤,而一直是用杵舂。最原始的就是地臼。如苦聰族人在屋角地上挖一個坑,以獸皮或舊布作墊,用木杵舂砸采集來的谷物。西盟佤族原先并沒有木碓,只是在地上挖一個坑用麻布或獸皮墊上,用木棍舂打。也有用布將谷物包起來后用木棍敲打的。海南島的黎族,解放初期還有不少人把帶穗的旱稻放進木臼中,手持木杵舂打,脫粒與去殼同時進行。獨龍族人和苦聰族人脫粒小米和稗子時,也是帶穗舂的。《續(xù)修臺灣府志》記載清代高山族加工谷物的情況是:“番無碾米之具,以大木為臼,直木為杵,帶穗舂。”可見,將谷物脫粒與加工合而為一的“帶穗舂”,是一種相當原始的加工方法。繼木臼之后,至少大約在7000年前出現(xiàn)了石杵臼。各地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都出土了不少石杵臼,其加工谷物的工效當較木杵臼要高。商周時期,石杵臼仍然是主要的加工農具。杵臼一直使用到西漢才有了突破性創(chuàng)造,即發(fā)明了利用杠桿原理的踏碓和利用畜力、水力驅動的畜力碓和水碓。但是手工操作的杵臼并未消失,而是長期在農村使用,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專門用來去殼碎粒的工具是石磨盤,其歷史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采集經濟時代。原始的石磨盤只是兩塊大小不同的天然石塊。它的使用方法應該和一些少數民族使用石磨盤的方法相同。如云南獨龍族的原始石磨谷器叫作“色達”,它由兩塊未經加工的天然石塊組成,一塊較大,一般長約50厘米,寬約30多厘米,厚約7厘米。另一塊較小,是直徑10厘米左右的橢圓形或圓形的鵝卵石。使用時,下置簸箕,大石塊放在簸箕上,一端用小木墩或石頭墊起,使之傾斜,人跪在簸箕前,把谷粒放在石塊上,雙手執(zhí)鵝卵石碾磨,利用石板的傾斜度,使磨碎的谷粒自行落在簸箕上。澳大利亞土著婦女們把采集來的少量種子收拾干凈后,就放在由一塊大而扁的石頭和一塊小而圓的石頭組成的“碾谷器”上去殼、碾碎,然后再加工成餅子一類食物[147]。從考古材料看,至少在8000年前,石磨盤就已經制作得相當精致了(如裴李崗遺址的石磨盤),其加工谷物的技術和功效當也達到很高的水平。
文物局考古優(yōu)秀事跡材料
一、求學之路飽嘗憂患
裴明相(1920~1997),1920年1月出生在位于伏牛山南麓的河南鎮(zhèn)平縣王崗鄉(xiāng)后裴營村的一個世代耕讀之家。當時,舊中國災難深重,民不聊生,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童年時代的裴明相過早地嘗到了生活的艱辛。
裴明相的父親和哥哥雖是農人,然都讀過書,深知讀書的重要。在家里的支持下,裴明相7歲那年,被送到附近的鎮(zhèn)上讀書,由于家里經濟困難,交不起膳費,就與同村的兩位堂兄在學校旁搭起一間草棚,自炊而食。這種艱難的環(huán)境使他從小就養(yǎng)成了奮力讀書的習慣。
裴明相12歲那年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河南鎮(zhèn)平縣立宛西中學,然而,為了湊齊入學的學費使他面臨失學困境。最后,由于他天資聰明,勤奮好學,成績突出,在學校老師和同鄉(xiāng)的幫助下,才得以在宛西中學、省立南陽中學、鎮(zhèn)平省立開封高中,讀完初中和高中。
“九一八”事變之后,縣立宛西中學中的共產黨人和進步教師以拯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積極宣傳和組織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啟發(fā)學生的民族覺悟,激發(fā)學生的愛國熱情。裴明相第一次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擔憂,勇敢地參加到抗日救亡活動之中。然而,由于當地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茍安和百般阻撓,學校的抗日救亡活動受到反動勢力的破壞,富有生氣的宛西中學也被迫解散。之后,裴明相又考入離家七十余華里省立南陽中學高中部繼續(xù)讀書。
1937年7月7日爆發(fā)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者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北平、天津相繼失陷。繼而,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逐漸由華北蔓延至華中,大片國土淪為敵手。由于華北正面戰(zhàn)場的潰敗,河南成了武漢的屏障、西北的門戶、華北抗戰(zhàn)的后方和南北戰(zhàn)場的樞紐,成為中國抗戰(zhàn)的最前線。開封形勢緊張,省立開封高中由開封遷至鎮(zhèn)平。裴明相轉入離家較近的鎮(zhèn)平省立開封高中讀書。開封失陷后,日本侵略者企圖進攻南陽,鎮(zhèn)平省立開封中學被迫舉行畢業(yè)考試,提前結束學期。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蹂躪下,裴明相度過了高中階段的最后一年。
考古遺址公園保護利用分析
摘要:自考古遺址公園新概念提出以來,如何平衡考古遺址的科學保護與利用,使其良性循環(huán),是學術界一直在探索的課題。闡釋文化空間與遺址公園之間的關系,提出遺產保護領域中文化空間的3個屬性:場所物質屬性、精神文化屬性、社會生活屬性,并進一步從文化空間生產的核心理論體系、屬性與理論實踐3個維度將考古遺址公園文化空間保護利用的內容分為3個層面:遺址本體場所、空間表征形態(tài)和文化旅游體驗。以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為例,劃分核心區(qū)、展示區(qū)、輻射區(qū)分析其目前的保護利用措施,并提出其文化空間生產的優(yōu)化策略:虛擬文旅開發(fā)完善遺產活態(tài)展示、數字技術支撐公眾參與保護營建、高校產學研助力廣富林文化傳播、協(xié)同發(fā)展促進文化產業(yè)集群構建,以期為遺址公園保護利用提供新思路。
關鍵詞:風景園林;考古遺址公園;文化空間;廣富林文化遺址;保護與利用
文化遺址的存在記錄了人類的先進文明和歷史發(fā)展,也是城市興起的見證者,無論是深埋水土,還是殘垣斷壁,文化遺存永遠是走向未來的精神源泉。目前我國在大遺址保護工作中存在以下困難:旅游過度開發(fā)對大遺址造成蠶食和破壞;保護限制和政策補償不完善,導致遺址區(qū)內居民對遺址保護缺乏認同而造成破壞[1];大遺址保護占地面積大,監(jiān)管力度與體制存在缺陷;人為的環(huán)境污染以及自然因素等的破壞。因此考古遺址公園應運而生。2009年,國內首次提出遺址公園的新概念并公布《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管理辦法(試行)》,定義“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以重要考古遺址及其背景環(huán)境為主體,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遺址保護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國性示范意義的特定公共空間[2]。
1文化空間與遺址公園保護利用
1.1遺產保護領域中文化空間概念與屬性闡釋
在遺產保護領域中,“文化空間”概念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種重要表現(xiàn)形式被提出。1998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條例》,“‘文化空間’的人類學概念被確定為一個集中了民間和傳統(tǒng)文化活動的地點,但也被確定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節(jié)、日程表等)或是一事件為特點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和這一地點的存在取決于按傳統(tǒng)方式進行的文化活動本身的存在”[3]。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界定“文化空間,即定期舉行傳統(tǒng)文化活動或集中展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的場所,兼具時間性和空間性”[4]。從上述概念中可以看出,文化生產是在“時間-空間”雙重維度下展開的,時間是文化的歷史記錄,空間是文化的展現(xiàn)載體,換言之,文化與空間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由此,有文化遺產領域學者理解其包含3個層次:(1)文化的物理空間或自然空間,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場”;(2)在這個場里有人類的文化建造或文化認定,是一個“文化場”;(3)在這個文化場中,有人類的行為、時間觀念、歲時傳統(tǒng)或者人類本身的“在場”[5]。“場-文化場-在場”三個進階層次揭示文化空間中“空間-文化-人”主客體相互作用關系,與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提出的空間生產核心理論體系“空間實踐、空間表征、表征空間”[6]不謀而合。由此本文總結遺產保護領域文化空間的3個屬性:(1)場所物質屬性。文化空間賴以生存的環(huán)境場所,人們長期聚居于此地與其和諧共生,才能產生富有地方感的文化遺產、文化景觀。(2)博物館的展示之用。廣富林考古研究展示館在埋藏區(qū)北部隔河相望,其由三個嵌入土地的完整陶罐造型建筑組成,其中一個陶罐口正對著太陽升起的地方,晨光透過罐口碎花玻璃灑入展館內部,猶如正在進行先民祭祀(圖4)。整個建筑外環(huán)境設計與原野融為一體。核心區(qū)遺址保護采取措施有二:(1)通過搭建“保護棚”對遺址進行臨時保護;對已經發(fā)掘的遺址進行隔離保護,或在遺址上搭建鋼架結構、玻璃等可視材質對外展示。(2)一些遺址只針對考古人員開放,避免遺址二次傷害,對已研究過的遺址進行回填處理。
相關期刊
精品范文
10考古學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