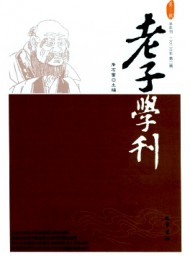老子范文10篇
時間:2024-02-22 09:18:23
導(dǎo)語: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為你推薦的十篇老子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老子
對于終極問題的探究無法依據(jù)現(xiàn)成的概念框架,但又不可能完全憑空而行,因而必須“緣”于某種微妙的技藝(“幾”、“藝”、“術(shù)”),以便讓思想非現(xiàn)成地發(fā)生出來和被維持住。數(shù)學(xué)對于古希臘人、瑜伽對于古印度人都作為這種幾微而起作用。與它們不同,中國古代思想、特別是先秦思想中似乎沒有特別突出的、為人普遍尊崇的思想技藝或藝術(shù)。“易”在漢代之后起過相當(dāng)大的作用,但在先秦時似乎也只是眾多技藝中的一種。而且,對卦象解釋的任意性相當(dāng)大,“象數(shù)”如何切真地激發(fā)和保持本源的“義理”或“道”從來就是一個挑戰(zhàn)。孔子、老莊似乎很少受到易的直接影響,老子“大象無形”的講法甚至可能就是不滿意那種拘于易象的做法的表示。實際上,中國古人看出,各種切身的生存技藝都可能揭示出和維系住道。而且,有真見地者也都看出,離開了這切身技藝的運作,人的思想就會陷入華而不實、“與影競走”的空疏境地。
中國古代的源頭思想的蛻變也與此相關(guān)。這就是說,當(dāng)開創(chuàng)者(比如孔子、老子)的思想與它“緣”出的技藝,比如六藝、歷史、治國、勞作、靜坐、養(yǎng)生、用兵、等等,一旦分離,其中的“要妙”就蔽而難見了。后人對它的理解極易淪為一種概念上的思辨和任意構(gòu)建。本書之所以要在分析老子之先討論韓非子與孫武子,就是因為從某個角度講來,后兩者的勢論更直接地與某種技藝(統(tǒng)馭臣民、用兵)相連,在一個偏狹但緊張發(fā)生的局面中揭示出道的終極構(gòu)成性。而這一見地在后人解釋《老子》時幾乎再也見不到了。所以,這種時間上的逆推,即從韓非到孫武,再及老子,意味著緣構(gòu)道境由狹窄的統(tǒng)馭之術(shù)舒張到對抗之術(shù),再擴大至宇宙人生境地的“還原”。
一、終極處境中的構(gòu)成之道
韓非子探討一種能構(gòu)成臣民的生存、并因而令其無所逃避和蛻變的勢態(tài);孫子則力求領(lǐng)會在軍爭對抗中仍然能立于不敗之地的勢態(tài)。定則、條件之所以不敷用,原道的終極性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因為這是一個總有可能被愚弄、被篡改、被重新做成的局面。“天命靡常”對于古人不僅意味著天不可被現(xiàn)成規(guī)范,更顯示出天的無所不在,并因此而要求一種更本源的領(lǐng)會方式和對待方式。《老子》的道只有置入這樣一個比軍爭還要根本和廣闊的對抗形勢或“靡常”境地才能被激活為一個純構(gòu)成的本源。道論中的所有那些“惚恍”和“難言之隱”都出自這樣一個形勢的造就,甚至逼迫,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一個比笛卡爾的懷疑所假設(shè)的局面還要深徹的靡常形勢下“立于不敗之地”、“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孫》形;謀攻)達(dá)到長生久視、長治久安的境界。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40)“反”首先是對根本的無常局面的認(rèn)識,其次提示出適應(yīng)于這種局面的對策。“反”意味著絕不可依靠任何現(xiàn)成者,而總是在它們的反面和反復(fù)中看出道的動向。[1]這種對于線性的思維來講處處都是陷阱的狀態(tài)卻不是完全無望的,其中確有一個讓大道通流的境域。“弱”、“柔”、“虛”、“靜”、“沖”、等等,是老子用來表示道的一組“無形大象”。它們透露出的“妙”義是:在一切具體法則的終結(jié)處,并沒有更高級的存在者和法則,而只能是一種“柔弱”到再無一絲一毫現(xiàn)成性可循的純勢態(tài)。有一分“堅強”或“形”、“質(zhì)”,就有一分可被“反”對的把柄和實處。而且,這再不被擺弄的終絕處,也不是干癟的空無,因為那樣的空無仍是一種觀念上可把捉的現(xiàn)成者;而只能是將一切現(xiàn)成性“反”過來的發(fā)生的構(gòu)成態(tài)。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fù)。”(《老》16)真正的虛極和篤靜必是一種壁立千仞的終極情境,其中一切都失去了現(xiàn)成存在性。一切形而上的理和形而下的器都禁不住這虛靜的大化。這一點是老子與后來解釋老子者及講形而上下者的最關(guān)鍵的區(qū)別。對于老莊,這虛極處離形而上者(理)絕不比離形而下者更近。正因為達(dá)到了真正切身的“虛極”,才會“萬物并作”。因此,老莊一方面摒棄可被現(xiàn)成化和相對化者,另一方面運用了大量的形而上下混然不分的“大象”來投射出、引發(fā)出至道的意境。象“沖”、“虛”、“谷”、“水”、“嬰孩”、“風(fēng)”、“山木”、“解牛之刃”、等等,都是一些“在世界之中”的、在稱手使用中顯現(xiàn)的活象,比易的卦象更能引發(fā)道境。“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老》21)與后人按某種現(xiàn)成路數(shù)的闡發(fā)方式很不相同。這種“風(fēng)格”的不同正顯示出思想的透徹程度的不同。達(dá)到終極情境的思想必有原發(fā)的“信言”(《老》81)氣象。可惜的是,戰(zhàn)國以后,這種蔥蘢樸茂的氣象就只在文學(xué)、書畫、工藝作品中見得到了。
老子的“禮”學(xué)-以道省禮
老子生活的春秋后期,社會動蕩和政治無序的混亂局面日益加劇。客觀地說,這種“陣痛”是社會轉(zhuǎn)型的必經(jīng)過程和明顯標(biāo)志。當(dāng)時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卻驚恐于這種所謂亂世,都圍繞禮的存廢探討造成此種局面的根由。他們中的多數(shù)人像儒家孔子一樣,將之歸咎于禮崩樂壞,即禮之廢。道家老子則將之歸結(jié)為禮治自身,即禮之存。不同于持“禮廢世亂”觀點的哲人們幻想恢復(fù)禮治來重新整治社會,老子由“禮存而世亂”的思維路徑出發(fā),企圖以道代替禮、以道治取代禮治。為此,有別于前者高揚禮的價值,為禮的存在的合理性作理論說明,老子以道為準(zhǔn)審視和省察禮,幾乎全盤否定禮的存在的必要性及治世功用,為禮的“缺憾”作哲學(xué)證明。這樣,老子所構(gòu)建的禮學(xué)體系便呈顯強烈的批判性,而與其同時代的孔子等所構(gòu)筑的禮學(xué)學(xué)說的顯明的建設(shè)性旨趣大異。
一
禮本身是祀神祈福的儀式規(guī)則,其產(chǎn)生和存在的前提條件與神學(xué)依據(jù)是神靈世界的存在、強大,以及神對于人類的絕對權(quán)威、至上主宰。在人類社會初期,作為祭祀規(guī)則的禮同時也是指導(dǎo)人事的原則。在人類進入文明的門檻時,祭神祀天為少數(shù)人所壟斷,成為少數(shù)人的特權(quán),神人交通的宗教儀式和法則隨之代表著世俗的權(quán)力和等級名分,禮引申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同時依然蘊含原有的風(fēng)俗習(xí)慣、行為規(guī)范等內(nèi)涵。夏、商、周三代即是以禮治國,其治國模式被稱作禮治。老子堅決反對禮治,在《老子"三十八章》中怒斥禮是國家發(fā)生禍亂的罪魁禍?zhǔn)住Kf:“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那么,禮和禮治究竟給國家、社會帶來怎樣的損失?身為思想者的老子沒有在政治層面作詳細(xì)的論說,只在《老子》的《五十三章》和《十二章》中有簡略的表達(dá),而是把批判的焦點集中于理論層面。他在《五十三章》中說:“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余,是謂盜竽,非道也哉。”指責(zé)禮儀中的繁文縟節(jié)浪費了大量的錢財,荒廢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降低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禮的等級性,造成了財物分配的不均衡,導(dǎo)致了社會的極不正常的貧富懸殊。他在《十二章》中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fā)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著重批評禮節(jié)儀式中的樂和舞傷害人的感官,誘發(fā)人過度的感官欲望,使人們?yōu)榱藵M足感性的物欲和享樂而損害他人;批評軍禮中的“田獵”激發(fā)軍隊的侵略好戰(zhàn)心理,勢必為戰(zhàn)爭的爆發(fā)推波助瀾,從而破壞人民的正常生活,造成國破家亡的悲劇。此處,需要解釋的是,《周禮"春官"大宗伯》曰:“大田之禮,簡眾也”,指天子與諸侯定期舉行狩獵活動,意在練兵。《周禮"夏官"大司馬》載每年春、夏、秋、冬均舉行“田獵”之禮。當(dāng)今許多治老者把《老子》中的田獵簡單地解為打獵,似是不妥的。
另外,老子在政治層面攻擊禮與禮治時,還對法令給予了批評。我們知道,三代之禮明顯存有法律效用,禮作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內(nèi)在地包含法。禮治包括法治,禮主法輔、或謂禮主法從是禮治根本的框架結(jié)構(gòu)。春秋中后期,法律的重要性日趨增強,有掙脫禮的拘限走向政治前臺的趨向。老子在此境況下否定禮,必然否定法。他在《老子"五十七章》中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譴責(zé)禮治中法律的實施以及法律條文越來越齊備所帶來的直接政治后果是民眾在生產(chǎn)和生活中遭受各種各樣的限制,在禮的等級制劃定貴賤、貧富之后,更加貧窮,并在貧困中為了活命而被迫偷盜。這樣,貧富矛盾愈加激化,社會下層的生存狀況愈加糟糕,由下層民眾的盜竊而引起的社會動亂不可避免。
老子對禮的批判主要是在理論上。從今存《周禮》和《儀禮》的內(nèi)容來看,禮規(guī)定了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官僚制度,規(guī)定了包括祭禮、兇禮、賓禮、軍禮和嘉禮在內(nèi)的諸多禮節(jié)儀式。可以說,個人的政治行為、家庭生活等所有方面無不處于禮的管轄范圍之內(nèi)。在此意義上,禮可謂“無不為”。但是,在老子看來,個人愿望與禮的要求是根本對立且不可調(diào)和的,在愿望的滿足和禮的規(guī)限之間,每一個人必須割舍自己的愿望而無條件地服從禮,禮對于人來說,是強加于人的外在鉗制力量,它逼迫人,成為人的生命需求的最大障礙。在此意義上,禮之于人可謂“有為”。老子心目中的道統(tǒng)帥自然萬物與人間萬事,無所不為。然而,道的“無不為”是順應(yīng)道所統(tǒng)率的對象的本性而為,即《老子"六十四章》所說的“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如此,道的要求與自然、人事本來的發(fā)展目標(biāo)根本一致,宇宙間的萬事萬物在感受不到外在擠壓的情況下似乎在自由發(fā)展。在此意義上,道之于自然和人間可以說是“無為”。老子強調(diào)道的“無為”。他從道的“無為”特征出發(fā),審視道、禮優(yōu)劣,指出禮與道對峙相背,是所有治國之道中最不合理、最拙劣的治道。《老子"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yīng),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德乃得于道者,指獲得道之無為真諦的“上德”。《老子"二十一章》云:“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即是說德是大德、上德,德、道一致,德從于道。下德表面上與道相似,實則“為之而有以為”,以有為為特征,與道相悖,不是真正的德。老子認(rèn)為,上德主觀上無為,客觀上亦無所為,最接近道;上仁主觀上有為,客觀上無所為,已部分地違背了道,與道的特質(zhì)有著明顯差異;上義主觀上有為,客觀上也有所為,已完全悖離了道的主旨;上禮涵容刑罰,不僅僅以有為為宗旨,而且對于反抗者施以懲罰,迫使對方屈從,這是人類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的最大枷鎖。這樣,天下最理想的治道是道,其次才是德;仁、義和禮均非統(tǒng)治者應(yīng)該選擇的治道,在仁、義、禮三者之中,禮最為低下。基于此,老子得出禮是亂天下之道,是人世間一切苦難之源頭的結(jié)論。既然道是理想中的治世之道,禮是現(xiàn)實中導(dǎo)致天下大亂之道,那么,為什么三代君王擇取禮作為治道?老子的理由是由于道、德、仁、義依次喪失,禮才為君王們所用。老子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即是此意。那么,道、德、仁、義等為什么會喪失?更何況道不生不死,超越于宇宙萬物之上。從《老子"十八章》所言“大道廢,有仁義”來看,老子以為大道被廢棄,不為統(tǒng)治者所用,仁義才被用作治世之道。據(jù)此推論,仁義被廢置,不為統(tǒng)治者所用,禮才乘虛而入,被當(dāng)作治道。這樣看來,老子實際上是認(rèn)為三代君王有意拋棄大道,最終選擇了禮。也就是說,三代實行禮治并非是別無選擇的結(jié)果。此處,老子用道審判禮,在揭露禮亂天下之外,還將哲思的目光深入到歷史深處,探求三代實行禮治的緣由,揭明禮治的歷史悲劇源于夏、商、周的最高統(tǒng)治者。這種關(guān)于禮的理論批判是深刻的。
二
老子的修身分析論文
老子以豐富生動的形象思維,精辟而曉暢的詩文,來深入淺出的闡釋出善為道者的心靈境界和人格品性。老子認(rèn)為,善位道者,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的,他們幽微精妙,他們玄奧通達(dá),他們淵深蘊藏,不是常人所能認(rèn)知,所能想象的,因此,只能勉強的為他們形容,于是,老子運用他的超人智慧,記錄下如珠妙語,從古代真人的言行舉止,外在的氣象、形象、性格、氣質(zhì)等等到其內(nèi)心世界,心靈的深處,以至于心身合道。
為道的人,好似冬天涉渡河川,心中自是如臨深淵,腳下自是欲進而遲疑,但雖猶豫,卻不是不決,而是不冒失燥進,靜以處之,一步一個腳印,步步踩在實處。“若畏四鄰”,猶然戒慎,不敢放肆其膽,時時反省自己。
他好似是賓客,容貌儼然,矜重莊敬,沒有絲毫的放縱,沒有片刻的懈怠,沒有剎那的走神,志意若一,持道修身也該如此。他好似冰凌的溶解,溶于我道,其不合于道的冰凌,若在陽光的照射下,自然層層溶解消融。我們在自我修身的過程中,也應(yīng)把心中的私利與妄見,以及由之而生的性格、習(xí)慣、情感、思維定勢、人際關(guān)系等,像冰山一般,讓其消融。他好似未經(jīng)雕琢的原木那樣純真樸實,虛其心,講俗心、私心、妄心化作道心、公心、正心了,其心敦普,超凡脫俗,歸于自然的本性,樸素的品格。
他好似山谷的寬容,善于容納溪流,無論清與濁,“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他好似流水的渾濁,絕不以道自炫,以功自居,絕不有門戶偏見,立宗立派,神話自己,他只是混沌一團,“我余人之心也哉!”因此,他大道若愚,大清若濁,同時,為道者棄世俗的貪求,“利而不害”,“為而不爭”似水那樣甘居惡地,愿為天下百姓受垢、受不詳、正是若濁的表現(xiàn)。
老子用精煉而富于包蘊性的語言,然天下后來的人們自此道來知道為道者的道心、道性、道骨、道風(fēng)、道鏡,讓“玄而又玄”的“眾妙之門”為有志修身者而開。老子用豫兮、尤兮、儼兮、渙兮、敦兮、曠兮、渾兮、七個方面來形容為道者的狀態(tài),是他道性的自然體現(xiàn),是善為道的正果,同時,也是衡量是否善于為道的標(biāo)尺,修身的廟道和境界。
老子的修身之道“見素抱樸”,表現(xiàn)了他崇高的道德價值取向和修身原則,他說“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取彼取次。”“敦兮若若其樸”“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fù)歸于樸。”“道常無名,樸”“化而欲作,吾將鎮(zhèn)之一無名之樸”。在老子看來,有出自人類樸素天性的自然的道德,也有矯揉造作,被人利用的人為的道德。人性本是樸素的自然的,并不受也無須受任何道德觀念的制約,甚至也不知道仁義理智等道德規(guī)范是什么,卻又是最道德的。自然的道德要高于人為的道德,只有自然道德的失落,才有了人為提倡的道德。處于對人類純真樸素的自然天性的摯愛,出于對恢復(fù)這種自然天性的執(zhí)著,老子將樸作為一種美德,賦予了“樸”很高的價值。守持大道“無名之樸”,“不欲以靜”,天下萬物將自正、自均、自化、自富,我的心身自然康健長壽,我的潛能自然迸發(fā)成長;一小自處,絕不自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其大也,以其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于道,永遠(yuǎn)立足于小,永不自是自見,永不自持自貴。立身敦厚,而不居于淺薄,存心篤實,而不居于浮華。樸之所以可貴,在于他符合自然,體現(xiàn)了自然,向真樸的自然之性的復(fù)歸,取舍之間,這是老子留給我們修身做人的智慧。
老子修身分析論文
他好似是賓客,容貌儼然,矜重莊敬,沒有絲毫的放縱,沒有片刻的懈怠,沒有剎那的走神,志意若一,持道修身也該如此。他好似冰凌的溶解,溶于我道,其不合于道的冰凌,若在陽光的照射下,自然層層溶解消融。我們在自我修身的過程中,也應(yīng)把心中的私利與妄見,以及由之而生的性格、習(xí)慣、情感、思維定勢、人際關(guān)系等,像冰山一般,讓其消融。他好似未經(jīng)雕琢的原木那樣純真樸實,虛其心,講俗心、私心、妄心化作道心、公心、正心了,其心敦普,超凡脫俗,歸于自然的本性,樸素的品格。
他好似山谷的寬容,善于容納溪流,無論清與濁,“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他好似流水的渾濁,絕不以道自炫,以功自居,絕不有門戶偏見,立宗立派,神話自己,他只是混沌一團,“我余人之心也哉!”因此,他大道若愚,大清若濁,同時,為道者棄世俗的貪求,“利而不害”,“為而不爭”似水那樣甘居惡地,愿為天下百姓受垢、受不詳、正是若濁的表現(xiàn)。
老子用精煉而富于包蘊性的語言,然天下后來的人們自此道來知道為道者的道心、道性、道骨、道風(fēng)、道鏡,讓“玄而又玄”的“眾妙之門”為有志修身者而開。老子用豫兮、尤兮、儼兮、渙兮、敦兮、曠兮、渾兮、七個方面來形容為道者的狀態(tài),是他道性的自然體現(xiàn),是善為道的正果,同時,也是衡量是否善于為道的標(biāo)尺,修身的廟道和境界。
老子的修身之道“見素抱樸”,表現(xiàn)了他崇高的道德價值取向和修身原則,他說“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取彼取次。”“敦兮若若其樸”“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fù)歸于樸。”“道常無名,樸”“化而欲作,吾將鎮(zhèn)之一無名之樸”。在老子看來,有出自人類樸素天性的自然的道德,也有矯揉造作,被人利用的人為的道德。人性本是樸素的自然的,并不受也無須受任何道德觀念的制約,甚至也不知道仁義理智等道德規(guī)范是什么,卻又是最道德的。自然的道德要高于人為的道德,只有自然道德的失落,才有了人為提倡的道德。處于對人類純真樸素的自然天性的摯愛,出于對恢復(fù)這種自然天性的執(zhí)著,老子將樸作為一種美德,賦予了“樸”很高的價值。守持大道“無名之樸”,“不欲以靜”,天下萬物將自正、自均、自化、自富,我的心身自然康健長壽,我的潛能自然迸發(fā)成長;一小自處,絕不自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其大也,以其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于道,永遠(yuǎn)立足于小,永不自是自見,永不自持自貴。立身敦厚,而不居于淺薄,存心篤實,而不居于浮華。樸之所以可貴,在于他符合自然,體現(xiàn)了自然,向真樸的自然之性的復(fù)歸,取舍之間,這是老子留給我們修身做人的智慧。修身之道,說到底乃是修心之道,因而使心達(dá)到或是出于何種狀態(tài),是修身之道的關(guān)鍵,老子闡明心的理想狀態(tài)是“至虛極,守靜篤。”虛是形容心境本來是空明的狀態(tài),靜是形容心靈不受外物擾動的狀態(tài),都是指心靈的自然狀態(tài)。只因私欲的活動和外物的干擾,使心閉塞不安,不再有自然的狀態(tài)。要達(dá)到篤,極這樣心靈修養(yǎng)的最高境地,就要“少私寡欲”,私欲是障蔽心靈、損害自然真性的主要原因,人類的私欲往往是無止境的,溝壑難填。人們無休止的追逐聲色名利,不但對社會造成危害,同時也戕害了自己真樸的自然天性和自然之德。要“知足知止”,人生而有私有欲,“少私寡欲”,不是要滅絕私欲,而是主張?zhí)竦瓰樯希阉接刂圃谝欢ǖ南薅戎畠?nèi),是心靈保持相對的“虛靜”狀態(tài),人最大的禍患莫過于不知足,無休止的追求名利,結(jié)果必然是招致物質(zhì)和精神上的嚴(yán)重?fù)p失,只有知足而止,才能“不辱”、“不怠”,才是長久的、真正的富足,于是老子說“甚愛必大廢,多藏必后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禍莫過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要“覺巧棄智”,私欲雖為人生固有,然而其膨脹擴張,卻與智巧詐偽的助長有關(guān)。世俗之心攻心斗智、奸巧詐偽,不僅造成社會的混亂,而且毀了人類純真樸實的自然之性與自然之德。老子之愚,不是世人所輕視的愚笨、愚拙之愚,也不是世人所稱贊的大智若愚之愚,他是善為道,深于道,玄同一切的玄德風(fēng)貌,以道自養(yǎng),抱道而行、為道是從,化世俗的私欲為大道的公欲。
我們當(dāng)繼承老子的智慧,豫而謀而后定,行不躁進,擇善而從,猶而自省慎獨,戒慎戒懼,常不放肆,偐而莊敬如賓,虛心謙退,必信必誠,渙而去私存妄,無所障礙,敦而敦厚淳樸,不受污染,不假雕琢,曠而虛懷若谷,寬容萬物,渾澤爾渾然一體,超凡脫俗。讀老子,使我們的生命寬大而充盈,玄靜而獨立,這是我們的修身之路。
老子的私的研究論文
摘要:中國哲學(xué)研究不僅存在著對道家思想重視不夠的傾向,而且對道家本身的概念也有忽視的現(xiàn)象。因此,以老子的“私”為切入口,通過“私”與“身”的聯(lián)系,以及“身”與“我”、“吾”實際相同的使用例,我們清楚地認(rèn)識到,不僅“私”的本義與我們現(xiàn)在使用的“偏”相異而表示我自己的意思,而且在人際關(guān)系里,“私”的價值追求取向是“與人己愈多”,這一傾向與儒家形成鮮明的差異。
關(guān)鍵詞:道家;老子;私
我國以孔子《論語》為中國文化之最的看法,似乎基本排除了中國文化里其他思想星座的存在價值,這顯然不是科學(xué)合理的做法,只能說是長期以來儒家思想“儒教化”特點的現(xiàn)實反映。不說別的,《論據(jù)》成為中國事實上的《圣經(jīng)》,并非完全自然篩選的結(jié)果所致,其中政治因素的作用是無法否定的,尤其是漢代,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另一方面,1815年至今,中國道家創(chuàng)始人老子在西方受到格外的重視,《道德經(jīng)》的各種譯本已達(dá)500多種,僅次于《圣經(jīng)》而排列第二的位置。而與儒家思想研究相比,國內(nèi)的道家研究要少得多。審視現(xiàn)實的研究,我們?nèi)匀荒軌虬l(fā)現(xiàn)許多沒有開墾的處女地,這一現(xiàn)實要求我們的研究者切實立足中國文化自身的軌道,不追逐時尚,腳踏實地地做好基本的研究工作。本文就是在這樣的運思之下,對不為大家所重視的《老子》的“私”做一分析,以就教于同仁。
一
“私”和“公”作為一對范疇,這是中國哲學(xué)文化本身的內(nèi)容;現(xiàn)實生活里公私不分、損公肥私、假公濟私等的用語,自然也是古代文化延續(xù)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審視老子的哲學(xué)思想就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雖然也是一個重要概念,但由于在我們今天的語境里,它們沒有太大的價值意義,因此總是為人所忽視。形成這一現(xiàn)實的深層原因,關(guān)鍵在于老子“私”和“公”的概念本身,并不具備我們今天一般意義上的立論基點。換言之,老子“私”和“公”概念的價值意義,不在一般意義的理解維度,而在他自身獨有的系統(tǒng)里。因此,只有在明確了這一前提的情況下,對老子“私”的概念進行揭秘才成為可能。
綜觀通行本《老子》,“公”字一共有4例,其中“王公”、“三公”等2例不屬于這里討論的范圍②;“私”字約有3例。為了徹底明辨其含義,下面以從“公”到“私”的演進形式來具體進行分析。
老子管理思想分析論文
一、“無為而治”——老子管理思想的本質(zhì)
1.“無為而治”思想的人性假設(shè)
一切管理理論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設(shè)為前提。老子雖未明確將人性假設(shè)作為管理前提,但也曾系統(tǒng)地探討過人性問題,且有意無意地將之作為管理的前提。在人性問題上,他提出了“自然人”假設(shè),認(rèn)為人和自然一樣也有其規(guī)律,管理措施須符合之才有效。所以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本來如此之意)老子強調(diào)管理者要通過無為的策略來獲得民心,認(rèn)為管理者能以“無為而治”理念進行管理,將收到“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六十章)效果。何謂“無為”?其義包括:其一在個人方面少為,在政治方面“近樸還淳”;其二率性而為,人皆有有所能,有所不能;其三因勢而為,人或社會能隨時勢走就是無為。其四順理而為。
2.休養(yǎng)生息和管理者加強自身道德修養(yǎng)是實現(xiàn)“無為而治”思想的重要措施
實現(xiàn)“無為而治”需兩條措施。一是休養(yǎng)生息。“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三章)指執(zhí)政者治理天下,要使官吏少私寡欲,使人民得到溫飽,弱化人民的期望值,增強人民的體魄和自立自強精神,使百姓淡化政治斗爭意識,減少貪欲。“無為”不是主張人們不為,而是反對違反自然規(guī)律的妄為。用無為的態(tài)度去對待一切,順應(yīng)自然的規(guī)律,輔助萬物自身的發(fā)展,不勉強用人為的力量去干擾它,不背離自然規(guī)律去追求個人的目的。另一措施是管理者加強自身道德修養(yǎng),達(dá)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子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八章)強調(diào)統(tǒng)治者應(yīng)當(dāng)行善有如水的品格,把自己擺在行善的地位,心胸總是保持寬廣和寧靜,交往總是講求愛人利物,說話總是講求誠信可靠,行政總是追求民眾安居樂業(yè),做事總是講究創(chuàng)造實效,行動總是講究抓緊時機。這種策略恰恰是大智慧,因為一味爭強好勝,易心勞神傷,退避三舍,則海闊天空,以柔克剛,則無往而不勝。
二、“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
孔子與老子消費觀對比研究論文
【內(nèi)容提要】消費觀是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占主導(dǎo)地位的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等級消費觀與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無為消費觀。對消費,孔子主張禮的等級規(guī)范、仁義的道德約束、寧儉的行為準(zhǔn)則;老子則提倡道的自然法則。不欲的心理約束、知足的行為準(zhǔn)則。兩者都傾向于黜奢崇儉,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消費思想的主要特點。比較而言,孔子強調(diào)倫理道德,老子強調(diào)自然無為,從而反映出學(xué)派特色與思想內(nèi)涵的不同。
【關(guān)鍵詞】消費觀/孔子/老子/等級/無為
【正文】
中圖分類號:F092.2文獻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4-4892(2001)03-0010-07
在中國古代經(jīng)濟思想史研究中,對傳統(tǒng)消費觀的專題研究似不多見。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古代思想家對消費問題的系統(tǒng)論述較少,另一方面學(xué)者對此似缺少關(guān)注。惜其常棄而不論,本文就孔子與老子的消費觀試作闡述,以期拾遺補缺。同時,用比較的方式進行研究,以揭示儒道消費觀的異同。
一
章太炎老子研究學(xué)術(shù)特點論文
摘要:章太炎在詮釋老子學(xué)術(shù)時援佛入老,致力于老子詮釋的近代化。在研究中善于將老子置于先秦諸子的大背景下,注重老子與其他諸子學(xué)說的比較、聯(lián)系。由于其革命家的身份,使老子研究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
關(guān)鍵詞:章太炎;援佛入老;近代化;比較研究;現(xiàn)實關(guān)懷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有學(xué)問的革命家”,這種特殊的身份使他在近代環(huán)境下闡述先秦諸子的思想理論價值,具有其獨到之處。就老子而論,章氏的研究在近代老學(xué)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學(xué)界對此也有研究[1]。但對章氏研究老子所顯現(xiàn)的學(xué)術(shù)特點則似著墨不多。以下試簡論之。
一、援佛入老
章氏早年雖對宗教作過批判,但對佛教情有獨衷。在他思想中,佛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認(rèn)為,先秦諸子“惟以師說為宗,小有異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狹隘、喜寬容、惡門戶、矜曠觀也”。佛教與之不同。又引用《成唯識論》中的話說:“佛家有言,何等名為所熏,若法平等,無所違逆,能容習(xí)氣,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勢力強盛,無所容納,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堅密能受習(xí)氣,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無為法,依他堅密,故非所熏。此可見古學(xué)之獨立者,由其持論強盛,義證堅密,故不受外熏也。”[2]這里以佛教標(biāo)準(zhǔn)評論中國先秦諸子。佛教思想已經(jīng)滲入到他學(xué)術(shù)思想的各個方面。在很多著作中將先秦諸子學(xué)說和佛學(xué)互相比附解析。
有人評價章氏“先是由儒入佛,次則以佛反儒、以佛解莊,最后是儒釋道互補”[3]。他不但以佛解莊,而且還援佛解老。他說:“《大乘入楞伽經(jīng)》喚作菩薩一闡提,經(jīng)中明說:‘菩薩一闡提,知一切法本來涅盤,畢竟不入。’像印度的文殊、普賢、維摩詰,中國的老聃、莊周,無一不是菩薩一闡提。”[4]因此把老子思想、佛學(xué)互融。他表示:“所以老子的話,一方是治天下,一方是無政府,只看當(dāng)時人情所好,無論是專制,是立憲,是無政府,無不可為。仿佛佛法中有三乘的話,應(yīng)機說法。老子在政治上也是三乘的話,并不執(zhí)著一定的方針,強去配合。……這是老莊的第一高見。就使維摩詰生在今日,必定也主張這種議論,發(fā)起這種志愿,斷不是只說幾句慈善事業(yè)的話,就以為夠用了。”[5]
論析老子以柔克剛的智慧應(yīng)用
摘要:社會道德的復(fù)興又離不開以人為本進行精神文明的建設(shè),因為人是社會的細(xì)胞,所以和諧社會的構(gòu)建與實現(xiàn),關(guān)鍵是構(gòu)建人人本身生命內(nèi)環(huán)境中一性和一命這兩大系統(tǒng)的真和諧,實現(xiàn)人體內(nèi)性與命的真和諧,復(fù)歸于人體內(nèi)環(huán)境中本真的道德原生態(tài)。什么叫人體內(nèi)環(huán)境中本真的道德原生態(tài)呢?就是說,只有人人都復(fù)歸于自己15歲以前的心靈狀態(tài)和身體狀態(tài),復(fù)歸于7歲之前天真無邪的心靈狀態(tài),那就是人人本來都曾經(jīng)共同具備過、擁有過,但是都被拋棄了的道德原生態(tài),是我們每個人都曾經(jīng)具備過的道德和諧狀態(tài)。
關(guān)鍵詞:復(fù)歸以柔克剛?cè)崛鯃詮娭腔?/p>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生之初柔弱似無骨,人到老年骨頭會僵硬壞死。草木生之時也柔弱,到秋天也枯黃變硬,所以通過對事物柔弱便可知它們發(fā)展情況。兵將過于強大反而不能獲勝,樹木過于高大則預(yù)示著死亡。強大處于下方柔弱處于上方。在當(dāng)今社會中,處于弱勢看似卑微,但正因為如此,對手不會把卑微者放于心上,這樣一來,反而使得弱者自身擁有了生長的契機。總而言之生命真正的原則在于內(nèi)里與生長而不是外在與既有。這里的弱,亦并非卑微,而是順其自然,從而也就有了“以柔克剛”,“以弱勝強”,“大者宜為下”的道理,這也是老子呈現(xiàn)給世人的一種大智若愚的智慧。
首先,老子的這一觀點體現(xiàn)出辯證法思想,他認(rèn)為矛盾雙方是處于相互轉(zhuǎn)化之中的。除此之外,在他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靜勝躁,寒勝熱。清靜為天下正。”鞭辟入里地論證了矛盾雙方相互轉(zhuǎn)化而又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道理。老子認(rèn)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柔與剛相互轉(zhuǎn)化,他們是力量的兩種極端,對于其中一極占有之后,力量必然會向著另一極轉(zhuǎn)化,因此,事物無所謂好與壞,只是他們所處的狀態(tài)不同而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征。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天下事福禍相依,一切事同,不可辨別,也不值得大喜大悲。只有一切順其自然,與世無爭,無為而治,才是智者的本分。
再者,老子從這種“以柔克剛”,“以弱勝強”,“大者宜為下”辯證法思想中生發(fā)出“劍氣合一”的劍道。在這里,引用日本電影中一句臺詞:“別人逼你,你就退后,再逼,你再退,最后推入絕境,則如山河涌迸。”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講究一個“忍”字,但忍并不是怯懦,而是為了以之前的處于弱勢來積蓄力量,以達(dá)到力量的處于強勢而完成最終的爆發(fā)。與此同時,在中國古代,一個劍客的最重要的品質(zhì)不是擁有優(yōu)良的劍術(shù),而是能夠擁有超乎常人的克己的“忍”,也就是不為情所動而能隨時地能看清楚一切。這一點無疑是受老子辯證思想的影響。老子生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主張以清心寡欲,超然物我來得劍道之精髓。劍如水,將水之柔、韌、活融合與劍之中,以達(dá)到真正的劍人合一的境界。與此同時,中國的太極拳中的“以柔克剛”“引進落空”“舍己從人”也蘊含了老子的哲學(xué)思想。這使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體會到“無為而無不為”的真正樂趣。
然而,老子的“以柔克剛”的思想的影響并不完全是積極的,在他的這一辯證法思想中,體現(xiàn)出一種“天人合一”的灑脫,“超然物外”的大氣和“看淡功名”的怡然自得,但也正因為如此,從中也體現(xiàn)出老子因為當(dāng)時所處階級地位低下而帶來的自卑,這其中包含著他的一種自我安慰。而這與老子的所處的時代與環(huán)境是息息相關(guān)的。老子生活在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轉(zhuǎn)變的春秋末期,社會的動蕩以及政治上昏暗奢靡之風(fēng)引發(fā)了老子對現(xiàn)實社會的不滿。因此,他提倡“與世無爭”的出世生活,遠(yuǎn)離紛爭,從而保全自己,避免禍害的發(fā)生。老子的思想為那些在時代中絕望的人們建立了精神家園,使得他們在混亂動蕩的社會中依然保持內(nèi)心的寧靜。但這種“消極避世”的做法未必是最明智的,它也在某種意義上破壞了人們的進取精神和積極心態(tài),它教給人們的更多的是“逃避”而不是以“面對”的方式去改變世道。
老子韓非道法淵源論文
內(nèi)容摘要:道家與法家這兩種看似差別很大的學(xué)派之間其實存在著明顯的淵源關(guān)系,法家通過對某些道家思想資源的吸收,從而使道法之間出現(xiàn)了合流的趨勢。
關(guān)鍵詞:老子韓非道法淵源
道家思想①和法家思想這兩種看似差別很大的學(xué)派之間本來就有著十分深厚的淵源,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申子之學(xué)本于黃老而主刑名。”“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yuǎn)矣。”從道家到法家的發(fā)展是先秦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轉(zhuǎn)折,但過去我們對這一點似乎重視得不夠,這里僅就以下幾個方面提出一點淺見。
第一,道家思想為法家思想提供了哲學(xué)基礎(chǔ)。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把“道”當(dāng)作萬物的本原和規(guī)律。老子認(rèn)為天下萬物都是由道產(chǎn)生的,即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下引《老子》只標(biāo)注篇章數(shù))。“道”也是天下萬物的總規(guī)律,老子說道是“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地高懸于社會之上對社會生活起著根本的指導(dǎo)作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老子的“道”簡直成了萬物的主宰,“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超越了傳統(tǒng)思想中至上神的地位。“道”的作用是無處不在的,“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三十九章)從老子對“道”的這些描述可以看出道實際具有自然規(guī)范的意義,這種規(guī)范是客觀存在的絕對權(quán)威,而人類社會作為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也要服從“道”的規(guī)范。在道家看來人是只能服從于這樣的外在規(guī)律的,《莊子》②中說:“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忘”(《莊子·天運》)。這種對外在的自然規(guī)范的強調(diào)的進一步發(fā)展必然會導(dǎo)致純?nèi)畏ㄖ嗡枷氲漠a(chǎn)生。葛兆光先生認(rèn)為道家“對‘道’的超越性理解和普遍性解釋,正好為權(quán)勢主義者所強調(diào)的君主權(quán)勢至高無上而又廣大普施,提供了宇宙依據(jù)”。范文瀾先生也在《中國通史》第一冊中指出老子思想認(rèn)為“人對自然只能任(順從)和法(效法),不能違背它。”“后來法家引申這種思想為極端的專制主義,就是君主制定法令,臣民絕對服從,象服從自然規(guī)律一樣。”
韓非子繼承了老子關(guān)于“道”的思想,他把“道”看成萬物的根本,“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jì)也”(《主道》,以下引《韓非子》只標(biāo)注篇名),“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他把“道”作為萬物之所以成為該事物的根本依據(jù):“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tǒng),圣人得之以成文章(《解老》)①,這和《老子》第三十九章的話如出一轍。韓非子還把“道”看做是事物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yīng)”,“是以死生氣稟焉,萬物斟酌焉,萬事興廢焉”(《解老》)。這樣的“道”是宏大無邊無所不在的,“夫道者,弘大而無形”(《揚權(quán)》)。當(dāng)然韓非子對老子的“道”并不僅是繼承,也有所發(fā)展。韓非子明確區(qū)分了“道”和“德”,他認(rèn)為“道”的實際功用就是“德”,“道有積,而積有功;德者,道之功”(《解老》),他還提出了“理”的范疇,即萬物各自的“道”的特殊性規(guī)定,他說:“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理”和“道”的關(guān)系就是一般和特殊的關(guān)系,“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黑白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故曰:道,理之者也”(《解老》)。
韓非子之所以要繼承老子的“道”是因為他要把“道”來作為自己社會哲學(xué)的依據(jù)。韓非子在分析了“道”對萬物的控制能力之后,把道引向人類社會,他指出人也要依“道”而行,“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人民而亡其資財也。眾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yuǎn)若是也”(《解老》),所以他念念不忘要人們從失敗中汲取教訓(xùn)“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同上),他心目中的圣人就是能“從于道而服于理者也”(同上)。這樣的“道”已經(jīng)由絕對的規(guī)律性引申為外在的規(guī)定性,由“道”引出法是很自然的事。韓非子進一步把“道”擴展到治理國家上來,把“道”看成一個國家能夠生存的根本,他說:“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國之術(shù)”(同上)。不僅如此,他還把“道”的絕對獨尊地位引申為君主的獨尊,而為獨裁找到依據(jù),他說:“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揚權(quán)》),這樣的明君也就是道在人間的體現(xiàn)者,是活生生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