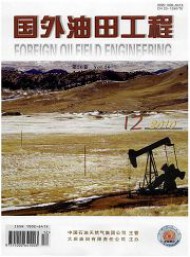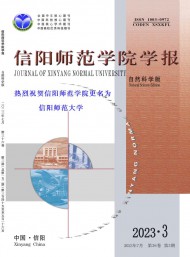連續劇范文10篇
時間:2024-02-23 07:07:20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連續劇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電視連續劇敘事策略分析論文
一.雙向互動中的電視劇敘事
從接受美學的觀點看,電視劇文本并不是完整的作品,而只是一些蘊含著藝術家思考和情感的藝術信息,這種信息必須被觀眾接受才能最后完成,才能產生社會作用;它借助接受者的藝術鑒賞活動得以“具體化”,借助接受者的審美活動并通過欣賞者的審美反應最終得以完成。而這種反應必須是藝術文本與欣賞者之間的互動。沃爾夫岡·伊瑟爾將這一過程分為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藝術極和審美極,藝術極是作家寫出來的本文,而審美極是讀者對本文的實現,“作品既不能等同于本文也不能等同于具體化,而必須處于兩者之間的某個地方……由于讀者經歷了作者提供的各種透視角度,把不同視點的模式相互聯結起來,所以他就使作品開始運動,從而也使自己開始運動”。①根據這一理論,或許我們也可以斷言:電視劇敘事策略成敗的關鍵,就是使這種藝術極和審美極的“互動”過程能夠順利進行,從而使作品通過“互動”得以最終完成。
我們或許可以將電視劇的敘事同觀眾之間的關系看作一種“契約”關系:電視劇必須為觀眾并且通過觀眾而存在,即必須覆行自己的義務,為觀眾理解作品創造條件,換言之,他們之間相互依存,互為前提。作為接受者,當代的電視觀眾已經具備了理解作品所必需的影視文化素養,為理解電視劇敘事本文進行了必要的準備;而作為敘事本文,電視劇必須為觀眾理解和領會作品并產生共鳴創造條件。他們之間相互依存,互為前提;電視劇必須被觀眾理解和認可才是有意義和有價值的,才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
電視劇作為敘事藝術,是一種信息交流手段,而這種交流的效果如何,不僅取決于信息的內容及其組合方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信息接受者的理解程度,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為條件的。詹·莫納柯在分析電影接受過程時指出,“有極其豐富的電影經驗的人,有高度視覺文化的人,較那些很少看電影的人看到的要多,聽到的也要多。”事實上,“一個人對畫面的讀解愈好,他對它的理解便愈多,而畫面對他的威力也就愈大……他們的智力活動愈多,觀眾參與創作者之間在這個過程中則愈能達成平衡;這種平衡愈好,那么這部藝術作品就愈有生命力,愈能引起共鳴。”②因此,為便于觀眾接受,電視劇的結構應該是開放性和啟發性的,它更多地傾向于:促使觀眾打破對故事本文的幻覺認同,以便能夠自主判斷,保持一種置身事外和評價性態度。
眾所周知,小說借助語言和文字塑藝術形象,讀者必須借助想象與聯想,才能把用文字描述的內容還原,從而進行一系列審美活動。而電視劇的敘事本文都是由短路符號構成的,其中能指和所指幾乎相等,觀賞電視劇時,無需進行藝術形象的還原。由于電視劇是以視覺形象直接反映現實生活,觀眾一般無需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因而也就使得這種審美活動變得更加直接;但同時也常常使觀眾失去主動性,總是跟著情節走,這樣就構成了觀眾理解和欣賞的一個重要缺陷。而增強電視劇敘事文本的觀賞效果,就是要有利于觀賞者與作品之間的雙向互動,促使觀眾在欣賞電視劇的同時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去領會作品中表現的內容,并作出客觀的、理性的評判。這就意味著要打破傳統的戲劇式的、封閉性的敘事模式,使觀眾的藝術審美活動由被動接受變為主動參與。事實上,現代敘事學發展的一個主要傾向,就是打破各種對故事文本的幻覺認同,對故事進行自主思考判斷,保持一種置身事外的客觀態度。
二.旨在增進雙向互動的敘事策略
電視連續劇香審美品格論文
【內容提要】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在審美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產生,但它不追蹤流行時尚,而是通過對百姓生活的深切關注、對人的內心世界的真誠關懷、對現實生活的詩意闡述、對地方風味和地域文化的準確把握,贏得了市場和觀眾。本文從現實主義的回歸、風格化的審美形態、詩意化的人文關懷等方面闡釋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的審美品格,揭示其獨特的藝術魅力。
【摘要題】佳作品評
【關鍵詞】審美品格/現實主義/京味風格/人文精神
【正文】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影視的發展逐漸步入了市場機制下的大眾文化轉型時期,電影、電視作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越來越被強調,觀眾的關注焦點越來越被重視,影視劇作家們紛紛放下精英知識分子的文化姿態走進百姓生活,影視劇(特別是電視劇)悄然從深度開掘轉向通俗娛樂,從批判的熱情轉向文化的消費,從崇高化轉向平民化,形成多元共存的文化審美形態。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就是在這種審美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它沒有追蹤流行時尚,而以自己獨特的審美追求探索著“市場的”和“審美的”雙贏之路。它通過對百姓生活的深切關注、對人的內心世界的真誠關懷、對現實生活的詩意闡述、對地方風味和地域文化的準確把握,既贏得了良好的市場,又受到了觀眾的青睞。本文試圖從現實主義的回歸、風格化的審美形態、詩意化的人文關懷等方面闡釋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的審美品格,揭示其獨特的藝術魅力。
一、現實主義的回歸
連續劇五月槐花香審美管理論文
【摘要題】佳作品評
【關鍵詞】審美品格/現實主義/京味風格/人文精神
【正文】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影視的發展逐漸步入了市場機制下的大眾文化轉型時期,電影、電視作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越來越被強調,觀眾的關注焦點越來越被重視,影視劇作家們紛紛放下精英知識分子的文化姿態走進百姓生活,影視劇(特別是電視劇)悄然從深度開掘轉向通俗娛樂,從批判的熱情轉向文化的消費,從崇高化轉向平民化,形成多元共存的文化審美形態。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就是在這種審美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它沒有追蹤流行時尚,而以自己獨特的審美追求探索著“市場的”和“審美的”雙贏之路。它通過對百姓生活的深切關注、對人的內心世界的真誠關懷、對現實生活的詩意闡述、對地方風味和地域文化的準確把握,既贏得了良好的市場,又受到了觀眾的青睞。本文試圖從現實主義的回歸、風格化的審美形態、詩意化的人文關懷等方面闡釋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的審美品格,揭示其獨特的藝術魅力。
一、現實主義的回歸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國電視劇創作,受西方現代、后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對解構經典、娛樂搞笑、碎片組合等手法趨之若鶩,有的電視劇打著“娛樂”的旗號進行市場運作,卻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對人的終極關懷的缺席而墮入了平面化庸俗化的泥潭。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這種現象猶為顯著,一些搞笑娛樂、戲說歷史的電視劇成了“文化垃圾”的代名詞。現代性的碎片能否反映現代人的生活狀況?剪切、粘貼能否展現現代人的精神面貌?消解深度模式是否符合當下中國觀眾的審美需求?……一系列問題的提出引起藝術家和理論家的廣泛爭鳴與思考,作為對這種思考的呼應,電視劇創作領域出現了現實主義的回歸,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在這種“回歸潮”中脫穎而出。
連續劇大雪無痕觀感論文
綜合美學與復合樣式
《大雪無痕》講述故事的第一個特點體現在樣式上。實際情節的內核并不復雜,是一宗以數額很大的原始股賄賂高級干部的反貪題材。可編導卻運用了綜合思維的結構手法將其講得有聲有色,講的富于特點而又吸引人。創作者將反貪樣式與偵破樣式以及家庭愛情樣式相結合、相綜合,形成具有現代特征、多信息、獨特的電視劇。幾條不同特點的戲相互交叉、穿插、融合,增強了影片的可看性與信息量。實際上,《大雪無痕》還具有心理劇的因素,可惜未加以發展運用。比如周密這條線的后半部分,日記的因素、犯罪后心理的因素、犯罪的靈魂剖析,如何從自殺轉為殺人,以及公安局方雨林等對周密的心理攻堅及雙方的心理仗等。而廖紅宇與馮祥龍的線也可以往心理方面發展。如果綜合進心理劇因素,相信戲會更豐富更好看。而后半部分戲也不至于蹋下去。
模糊思維與懸念構置
以往我們比較強調要把故事講清楚,強調的是明確性。實際上要講好故事還必須強調另一方面即事物的不確定性。《大雪無痕》開局開的好就在于表現了事物的不確定性,制造了大量的懸念。第一集表現了為衣錦還鄉的軍區丁司令員舉行歌舞升平的招待會,山莊戒備森嚴,通過“攔車”揭示了丁潔與方雨林的神秘關系,接著找張秘書、槍聲、張秘書被害、“他殺!”點明規定情境;如何在違背常規的時間地點作案……提出一系列懸案。主人公方雨林的出現也是充滿懸念,他與丁潔的愛情關系?他本人的被處分處境?他與馬局的矛盾?通過這兩組撲朔迷離,顯影式地提出5·25“東鋼”原始股案件的中止,接著表現了兩位關鍵知情人的死亡。又通過方雨林與馬局的矛盾點出案件牽涉到上邊的復雜性。更巧妙的是讓第一嫌疑人周密通過愛情線浮出,而且是在他升職為市長的背景下……編導在講述這一復雜的故事時設置了許多“突來之筆”“懸來之筆”“神來之筆”。為觀眾構置了一個個懸念,形成了一個個期待,使連續劇抓人好看。懸念的基本特點在于它的模糊性,其核心內容是不確定性。《大雪無痕》的開局正是取了情節的一些非感性的點、面、線、表現了事件運動過程中模糊與不確定的波紋。這就好比將一個石子扔進湖里,我們不去表現“撲通”的中心處,而是有選擇地去描述富于懸念的波紋,通過一系列跳躍式的波紋的描述以顯影的方式逐漸深入到中心。懸念的運動過程的非線性及不平衡、不明確狀態卻顯現出波瀾起伏、跌宕多姿、曲折有致,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在有關情節的點、面、線上,都延伸著無窮的懸念魅力與韻味,而在情節的縱深角度上,采用的是點與點的跳躍,不是僅停在一個點或一條線上,形成縱深感的誘導性拓展性的懸念。而在情節的橫向上,則由點、線通過相互的關連性因素擴展為面,復合的面形成開拓性,生發性和多義性。自然,模糊性思維應來自于整體性的思維,而模糊與清晰是彼此交融,相得益彰的。《大雪無痕》的懸念成果無疑是來自模糊思維的藝術觀念,特別是前半部分取得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圍棋思維與復雜形象
情節是人物性格的歷史,因此,主要人物的塑造,人物性格的構成與發展對講好故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大雪無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如周密、丁潔、方雨林、馬局等,都因為塑造了人物形象的復雜性。創作中情節敘事與人物塑造的簡單化、直白化,往往來自于宏觀創作思維模式的淺顯。為了更形象地講述,我們一般將創作、思維模式稱之為:“多米諾”——“跳棋”——“圍棋”思維模式。多米諾(骨牌)思維一般都是直來直去,雖有變化但永遠是一種線性簡單思維,如創作一個人高興,就一個勁兒歡樂,痛苦呢,一個勁兒悲痛欲絕,塑造一個好人就好到底,壞人就一無是處。然而生活并非如此。該劇正因為表現了周密性格中的兩面性、還因為表現了方雨林性格中對待愛情不可理喻的復雜性、表現了馬局在復雜規定情境下性格中的靈活多樣性、丁潔的愛情生活體現在靈魂深處斗爭的豐富性,才使得這些圓整的復雜形象更真實、更抓人。跳棋思維雖然在跳的進程中有許多變化,但,怎么變化也是從這個三角跳向那個三角,有始有終,有因有果,這種過于明確的因果思維有時難以反映人與生活的復雜性。而圍棋思維更接近人與生活的本體,充滿復雜,辯證,并在幾百個方格中立體展開。看似在這邊圍你,突然那邊擺一個棋子,似乎不著邊際,實際很有道道,也許是關鍵的一著。這是一種結構,它更能反映現實生活與人的豐富性、復雜性與生動性。比如槍殺事件發生后,不去寫周密如何恐懼,如何掩蓋罪行……而是寫他與丁潔的戀愛,寫他對童年及自己成長奮斗史的回顧,甚至寫他居然將自己的日記給戀人丁潔看等等。這無疑增強了人物的神秘感及劇情的懸念。顯然創作者試著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靈魂,表現更復雜、更隱秘的第二宇宙——人的心靈。這種情節構置與人物塑造頗有些圍棋的味道,可惜在后邊沒有把它下到底。
電視連續劇觀感管理論文
綜合美學與復合樣式
《大雪無痕》講述故事的第一個特點體現在樣式上。實際情節的內核并不復雜,是一宗以數額很大的原始股賄賂高級干部的反貪題材。可編導卻運用了綜合思維的結構手法將其講得有聲有色,講的富于特點而又吸引人。創作者將反貪樣式與偵破樣式以及家庭愛情樣式相結合、相綜合,形成具有現代特征、多信息、獨特的電視劇。幾條不同特點的戲相互交叉、穿插、融合,增強了影片的可看性與信息量。實際上,《大雪無痕》還具有心理劇的因素,可惜未加以發展運用。比如周密這條線的后半部分,日記的因素、犯罪后心理的因素、犯罪的靈魂剖析,如何從自殺轉為殺人,以及公安局方雨林等對周密的心理攻堅及雙方的心理仗等。而廖紅宇與馮祥龍的線也可以往心理方面發展。如果綜合進心理劇因素,相信戲會更豐富更好看。而后半部分戲也不至于蹋下去。
模糊思維與懸念構置
以往我們比較強調要把故事講清楚,強調的是明確性。實際上要講好故事還必須強調另一方面即事物的不確定性。《大雪無痕》開局開的好就在于表現了事物的不確定性,制造了大量的懸念。第一集表現了為衣錦還鄉的軍區丁司令員舉行歌舞升平的招待會,山莊戒備森嚴,通過“攔車”揭示了丁潔與方雨林的神秘關系,接著找張秘書、槍聲、張秘書被害、“他殺!”點明規定情境;如何在違背常規的時間地點作案……提出一系列懸案。主人公方雨林的出現也是充滿懸念,他與丁潔的愛情關系?他本人的被處分處境?他與馬局的矛盾?通過這兩組撲朔迷離,顯影式地提出"5•25"“東鋼”原始股案件的中止,接著表現了兩位關鍵知情人的死亡。又通過方雨林與馬局的矛盾點出案件牽涉到上邊的復雜性。更巧妙的是讓第一嫌疑人周密通過愛情線浮出,而且是在他升職為市長的背景下……編導在講述這一復雜的故事時設置了許多“突來之筆”“懸來之筆”“神來之筆”。為觀眾構置了一個個懸念,形成了一個個期待,使連續劇抓人好看。懸念的基本特點在于它的模糊性,其核心內容是不確定性。《大雪無痕》的開局正是取了情節的一些非感性的點、面、線、表現了事件運動過程中模糊與不確定的波紋。這就好比將一個石子扔進湖里,我們不去表現“撲通”的中心處,而是有選擇地去描述富于懸念的波紋,通過一系列跳躍式的波紋的描述以顯影的方式逐漸深入到中心。懸念的運動過程的非線性及不平衡、不明確狀態卻顯現出波瀾起伏、跌宕多姿、曲折有致,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在有關情節的點、面、線上,都延伸著無窮的懸念魅力與韻味,而在情節的縱深角度上,采用的是點與點的跳躍,不是僅停在一個點或一條線上,形成縱深感的誘導性拓展性的懸念。而在情節的橫向上,則由點、線通過相互的關連性因素擴展為面,復合的面形成開拓性,生發性和多義性。自然,模糊性思維應來自于整體性的思維,而模糊與清晰是彼此交融,相得益彰的。《大雪無痕》的懸念成果無疑是來自模糊思維的藝術觀念,特別是前半部分取得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圍棋思維與復雜形象
情節是人物性格的歷史,因此,主要人物的塑造,人物性格的構成與發展對講好故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大雪無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如周密、丁潔、方雨林、馬局等,都因為塑造了人物形象的復雜性。創作中情節敘事與人物塑造的簡單化、直白化,往往來自于宏觀創作思維模式的淺顯。為了更形象地講述,我們一般將創作、思維模式稱之為:“多米諾”——“跳棋”——“圍棋”思維模式。多米諾(骨牌)思維一般都是直來直去,雖有變化但永遠是一種線性簡單思維,如創作一個人高興,就一個勁兒歡樂,痛苦呢,一個勁兒悲痛欲絕,塑造一個好人就好到底,壞人就一無是處。然而生活并非如此。該劇正因為表現了周密性格中的兩面性、還因為表現了方雨林性格中對待愛情不可理喻的復雜性、表現了馬局在復雜規定情境下性格中的靈活多樣性、丁潔的愛情生活體現在靈魂深處斗爭的豐富性,才使得這些圓整的復雜形象更真實、更抓人。跳棋思維雖然在跳的進程中有許多變化,但,怎么變化也是從這個三角跳向那個三角,有始有終,有因有果,這種過于明確的因果思維有時難以反映人與生活的復雜性。而圍棋思維更接近人與生活的本體,充滿復雜,辯證,并在幾百個方格中立體展開。看似在這邊圍你,突然那邊擺一個棋子,似乎不著邊際,實際很有道道,也許是關鍵的一著。這是一種結構,它更能反映現實生活與人的豐富性、復雜性與生動性。比如槍殺事件發生后,不去寫周密如何恐懼,如何掩蓋罪行……而是寫他與丁潔的戀愛,寫他對童年及自己成長奮斗史的回顧,甚至寫他居然將自己的日記給戀人丁潔看等等。這無疑增強了人物的神秘感及劇情的懸念。顯然創作者試著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靈魂,表現更復雜、更隱秘的第二宇宙——人的心靈。這種情節構置與人物塑造頗有些圍棋的味道,可惜在后邊沒有把它下到底。
電視連續劇大雪無痕探析論文
綜合美學與復合樣式
《大雪無痕》講述故事的第一個特點體現在樣式上。實際情節的內核并不復雜,是一宗以數額很大的原始股賄賂高級干部的反貪題材。可編導卻運用了綜合思維的結構手法將其講得有聲有色,講的富于特點而又吸引人。創作者將反貪樣式與偵破樣式以及家庭愛情樣式相結合、相綜合,形成具有現代特征、多信息、獨特的電視劇。幾條不同特點的戲相互交叉、穿插、融合,增強了影片的可看性與信息量。實際上,《大雪無痕》還具有心理劇的因素,可惜未加以發展運用。比如周密這條線的后半部分,日記的因素、犯罪后心理的因素、犯罪的靈魂剖析,如何從自殺轉為殺人,以及公安局方雨林等對周密的心理攻堅及雙方的心理仗等。而廖紅宇與馮祥龍的線也可以往心理方面發展。如果綜合進心理劇因素,相信戲會更豐富更好看。而后半部分戲也不至于蹋下去。
模糊思維與懸念構置
以往我們比較強調要把故事講清楚,強調的是明確性。實際上要講好故事還必須強調另一方面即事物的不確定性。《大雪無痕》開局開的好就在于表現了事物的不確定性,制造了大量的懸念。第一集表現了為衣錦還鄉的軍區丁司令員舉行歌舞升平的招待會,山莊戒備森嚴,通過“攔車”揭示了丁潔與方雨林的神秘關系,接著找張秘書、槍聲、張秘書被害、“他殺!”點明規定情境;如何在違背常規的時間地點作案……提出一系列懸案。主人公方雨林的出現也是充滿懸念,他與丁潔的愛情關系?他本人的被處分處境?他與馬局的矛盾?通過這兩組撲朔迷離,顯影式地提出"5•25"“東鋼”原始股案件的中止,接著表現了兩位關鍵知情人的死亡。又通過方雨林與馬局的矛盾點出案件牽涉到上邊的復雜性。更巧妙的是讓第一嫌疑人周密通過愛情線浮出,而且是在他升職為市長的背景下……編導在講述這一復雜的故事時設置了許多“突來之筆”“懸來之筆”“神來之筆”。為觀眾構置了一個個懸念,形成了一個個期待,使連續劇抓人好看。懸念的基本特點在于它的模糊性,其核心內容是不確定性。《大雪無痕》的開局正是取了情節的一些非感性的點、面、線、表現了事件運動過程中模糊與不確定的波紋。這就好比將一個石子扔進湖里,我們不去表現“撲通”的中心處,而是有選擇地去描述富于懸念的波紋,通過一系列跳躍式的波紋的描述以顯影的方式逐漸深入到中心。懸念的運動過程的非線性及不平衡、不明確狀態卻顯現出波瀾起伏、跌宕多姿、曲折有致,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在有關情節的點、面、線上,都延伸著無窮的懸念魅力與韻味,而在情節的縱深角度上,采用的是點與點的跳躍,不是僅停在一個點或一條線上,形成縱深感的誘導性拓展性的懸念。而在情節的橫向上,則由點、線通過相互的關連性因素擴展為面,復合的面形成開拓性,生發性和多義性。自然,模糊性思維應來自于整體性的思維,而模糊與清晰是彼此交融,相得益彰的。《大雪無痕》的懸念成果無疑是來自模糊思維的藝術觀念,特別是前半部分取得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圍棋思維與復雜形象
情節是人物性格的歷史,因此,主要人物的塑造,人物性格的構成與發展對講好故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大雪無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如周密、丁潔、方雨林、馬局等,都因為塑造了人物形象的復雜性。創作中情節敘事與人物塑造的簡單化、直白化,往往來自于宏觀創作思維模式的淺顯。為了更形象地講述,我們一般將創作、思維模式稱之為:“多米諾”——“跳棋”——“圍棋”思維模式。多米諾(骨牌)思維一般都是直來直去,雖有變化但永遠是一種線性簡單思維,如創作一個人高興,就一個勁兒歡樂,痛苦呢,一個勁兒悲痛欲絕,塑造一個好人就好到底,壞人就一無是處。然而生活并非如此。該劇正因為表現了周密性格中的兩面性、還因為表現了方雨林性格中對待愛情不可理喻的復雜性、表現了馬局在復雜規定情境下性格中的靈活多樣性、丁潔的愛情生活體現在靈魂深處斗爭的豐富性,才使得這些圓整的復雜形象更真實、更抓人。跳棋思維雖然在跳的進程中有許多變化,但,怎么變化也是從這個三角跳向那個三角,有始有終,有因有果,這種過于明確的因果思維有時難以反映人與生活的復雜性。而圍棋思維更接近人與生活的本體,充滿復雜,辯證,并在幾百個方格中立體展開。看似在這邊圍你,突然那邊擺一個棋子,似乎不著邊際,實際很有道道,也許是關鍵的一著。這是一種結構,它更能反映現實生活與人的豐富性、復雜性與生動性。比如槍殺事件發生后,不去寫周密如何恐懼,如何掩蓋罪行……而是寫他與丁潔的戀愛,寫他對童年及自己成長奮斗史的回顧,甚至寫他居然將自己的日記給戀人丁潔看等等。這無疑增強了人物的神秘感及劇情的懸念。顯然創作者試著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靈魂,表現更復雜、更隱秘的第二宇宙——人的心靈。這種情節構置與人物塑造頗有些圍棋的味道,可惜在后邊沒有把它下到底。縱觀20集,也有遺憾之處,感覺編導的創新追求不完整,不徹底,有一種跛腳的感覺。一是前半部分好,后半部分弱;另外是方雨林——丁潔——周密線好,廖紅宇——馮祥龍線弱。好就好在有創新觀念新;弱就弱在比較落套,缺少創造力。
電視連續劇大雪無痕觀感分析論文
綜合美學與復合樣式
《大雪無痕》講述故事的第一個特點體現在樣式上。實際情節的內核并不復雜,是一宗以數額很大的原始股賄賂高級干部的反貪題材。可編導卻運用了綜合思維的結構手法將其講得有聲有色,講的富于特點而又吸引人。創作者將反貪樣式與偵破樣式以及家庭愛情樣式相結合、相綜合,形成具有現代特征、多信息、獨特的電視劇。幾條不同特點的戲相互交叉、穿插、融合,增強了影片的可看性與信息量。實際上,《大雪無痕》還具有心理劇的因素,可惜未加以發展運用。比如周密這條線的后半部分,日記的因素、犯罪后心理的因素、犯罪的靈魂剖析,如何從自殺轉為殺人,以及公安局方雨林等對周密的心理攻堅及雙方的心理仗等。而廖紅宇與馮祥龍的線也可以往心理方面發展。如果綜合進心理劇因素,相信戲會更豐富更好看。而后半部分戲也不至于蹋下去。
模糊思維與懸念構置
以往我們比較強調要把故事講清楚,強調的是明確性。實際上要講好故事還必須強調另一方面即事物的不確定性。《大雪無痕》開局開的好就在于表現了事物的不確定性,制造了大量的懸念。第一集表現了為衣錦還鄉的軍區丁司令員舉行歌舞升平的招待會,山莊戒備森嚴,通過“攔車”揭示了丁潔與方雨林的神秘關系,接著找張秘書、槍聲、張秘書被害、“他殺!”點明規定情境;如何在違背常規的時間地點作案……提出一系列懸案。主人公方雨林的出現也是充滿懸念,他與丁潔的愛情關系?他本人的被處分處境?他與馬局的矛盾?通過這兩組撲朔迷離,顯影式地提出"5•25"“東鋼”原始股案件的中止,接著表現了兩位關鍵知情人的死亡。又通過方雨林與馬局的矛盾點出案件牽涉到上邊的復雜性。更巧妙的是讓第一嫌疑人周密通過愛情線浮出,而且是在他升職為市長的背景下……編導在講述這一復雜的故事時設置了許多“突來之筆”“懸來之筆”“神來之筆”。為觀眾構置了一個個懸念,形成了一個個期待,使連續劇抓人好看。懸念的基本特點在于它的模糊性,其核心內容是不確定性。《大雪無痕》的開局正是取了情節的一些非感性的點、面、線、表現了事件運動過程中模糊與不確定的波紋。這就好比將一個石子扔進湖里,我們不去表現“撲通”的中心處,而是有選擇地去描述富于懸念的波紋,通過一系列跳躍式的波紋的描述以顯影的方式逐漸深入到中心。懸念的運動過程的非線性及不平衡、不明確狀態卻顯現出波瀾起伏、跌宕多姿、曲折有致,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在有關情節的點、面、線上,都延伸著無窮的懸念魅力與韻味,而在情節的縱深角度上,采用的是點與點的跳躍,不是僅停在一個點或一條線上,形成縱深感的誘導性拓展性的懸念。而在情節的橫向上,則由點、線通過相互的關連性因素擴展為面,復合的面形成開拓性,生發性和多義性。自然,模糊性思維應來自于整體性的思維,而模糊與清晰是彼此交融,相得益彰的。《大雪無痕》的懸念成果無疑是來自模糊思維的藝術觀念,特別是前半部分取得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圍棋思維與復雜形象
情節是人物性格的歷史,因此,主要人物的塑造,人物性格的構成與發展對講好故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大雪無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如周密、丁潔、方雨林、馬局等,都因為塑造了人物形象的復雜性。創作中情節敘事與人物塑造的簡單化、直白化,往往來自于宏觀創作思維模式的淺顯。為了更形象地講述,我們一般將創作、思維模式稱之為:“多米諾”——“跳棋”——“圍棋”思維模式。多米諾(骨牌)思維一般都是直來直去,雖有變化但永遠是一種線性簡單思維,如創作一個人高興,就一個勁兒歡樂,痛苦呢,一個勁兒悲痛欲絕,塑造一個好人就好到底,壞人就一無是處。然而生活并非如此。該劇正因為表現了周密性格中的兩面性、還因為表現了方雨林性格中對待愛情不可理喻的復雜性、表現了馬局在復雜規定情境下性格中的靈活多樣性、丁潔的愛情生活體現在靈魂深處斗爭的豐富性,才使得這些圓整的復雜形象更真實、更抓人。跳棋思維雖然在跳的進程中有許多變化,但,怎么變化也是從這個三角跳向那個三角,有始有終,有因有果,這種過于明確的因果思維有時難以反映人與生活的復雜性。而圍棋思維更接近人與生活的本體,充滿復雜,辯證,并在幾百個方格中立體展開。看似在這邊圍你,突然那邊擺一個棋子,似乎不著邊際,實際很有道道,也許是關鍵的一著。這是一種結構,它更能反映現實生活與人的豐富性、復雜性與生動性。比如槍殺事件發生后,不去寫周密如何恐懼,如何掩蓋罪行……而是寫他與丁潔的戀愛,寫他對童年及自己成長奮斗史的回顧,甚至寫他居然將自己的日記給戀人丁潔看等等。這無疑增強了人物的神秘感及劇情的懸念。顯然創作者試著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靈魂,表現更復雜、更隱秘的第二宇宙——人的心靈。這種情節構置與人物塑造頗有些圍棋的味道,可惜在后邊沒有把它下到底。
電視連續劇大雪無痕觀感論文
綜合美學與復合樣式
《大雪無痕》講述故事的第一個特點體現在樣式上。實際情節的內核并不復雜,是一宗以數額很大的原始股賄賂高級干部的反貪題材。可編導卻運用了綜合思維的結構手法將其講得有聲有色,講的富于特點而又吸引人。創作者將反貪樣式與偵破樣式以及家庭愛情樣式相結合、相綜合,形成具有現代特征、多信息、獨特的電視劇。幾條不同特點的戲相互交叉、穿插、融合,增強了影片的可看性與信息量。實際上,《大雪無痕》還具有心理劇的因素,可惜未加以發展運用。比如周密這條線的后半部分,日記的因素、犯罪后心理的因素、犯罪的靈魂剖析,如何從自殺轉為殺人,以及公安局方雨林等對周密的心理攻堅及雙方的心理仗等。而廖紅宇與馮祥龍的線也可以往心理方面發展。如果綜合進心理劇因素,相信戲會更豐富更好看。而后半部分戲也不至于蹋下去。
模糊思維與懸念構置
以往我們比較強調要把故事講清楚,強調的是明確性。實際上要講好故事還必須強調另一方面即事物的不確定性。《大雪無痕》開局開的好就在于表現了事物的不確定性,制造了大量的懸念。第一集表現了為衣錦還鄉的軍區丁司令員舉行歌舞升平的招待會,山莊戒備森嚴,通過“攔車”揭示了丁潔與方雨林的神秘關系,接著找張秘書、槍聲、張秘書被害、“他殺!”點明規定情境;如何在違背常規的時間地點作案……提出一系列懸案。主人公方雨林的出現也是充滿懸念,他與丁潔的愛情關系?他本人的被處分處境?他與馬局的矛盾?通過這兩組撲朔迷離,顯影式地提出5·25“東鋼”原始股案件的中止,接著表現了兩位關鍵知情人的死亡。又通過方雨林與馬局的矛盾點出案件牽涉到上邊的復雜性。更巧妙的是讓第一嫌疑人周密通過愛情線浮出,而且是在他升職為市長的背景下……編導在講述這一復雜的故事時設置了許多“突來之筆”“懸來之筆”“神來之筆”。為觀眾構置了一個個懸念,形成了一個個期待,使連續劇抓人好看。懸念的基本特點在于它的模糊性,其核心內容是不確定性。《大雪無痕》的開局正是取了情節的一些非感性的點、面、線、表現了事件運動過程中模糊與不確定的波紋。這就好比將一個石子扔進湖里,我們不去表現“撲通”的中心處,而是有選擇地去描述富于懸念的波紋,通過一系列跳躍式的波紋的描述以顯影的方式逐漸深入到中心。懸念的運動過程的非線性及不平衡、不明確狀態卻顯現出波瀾起伏、跌宕多姿、曲折有致,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在有關情節的點、面、線上,都延伸著無窮的懸念魅力與韻味,而在情節的縱深角度上,采用的是點與點的跳躍,不是僅停在一個點或一條線上,形成縱深感的誘導性拓展性的懸念。而在情節的橫向上,則由點、線通過相互的關連性因素擴展為面,復合的面形成開拓性,生發性和多義性。自然,模糊性思維應來自于整體性的思維,而模糊與清晰是彼此交融,相得益彰的。《大雪無痕》的懸念成果無疑是來自模糊思維的藝術觀念,特別是前半部分取得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圍棋思維與復雜形象
情節是人物性格的歷史,因此,主要人物的塑造,人物性格的構成與發展對講好故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大雪無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如周密、丁潔、方雨林、馬局等,都因為塑造了人物形象的復雜性。創作中情節敘事與人物塑造的簡單化、直白化,往往來自于宏觀創作思維模式的淺顯。為了更形象地講述,我們一般將創作、思維模式稱之為:“多米諾”——“跳棋”——“圍棋”思維模式。多米諾(骨牌)思維一般都是直來直去,雖有變化但永遠是一種線性簡單思維,如創作一個人高興,就一個勁兒歡樂,痛苦呢,一個勁兒悲痛欲絕,塑造一個好人就好到底,壞人就一無是處。然而生活并非如此。該劇正因為表現了周密性格中的兩面性、還因為表現了方雨林性格中對待愛情不可理喻的復雜性、表現了馬局在復雜規定情境下性格中的靈活多樣性、丁潔的愛情生活體現在靈魂深處斗爭的豐富性,才使得這些圓整的復雜形象更真實、更抓人。跳棋思維雖然在跳的進程中有許多變化,但,怎么變化也是從這個三角跳向那個三角,有始有終,有因有果,這種過于明確的因果思維有時難以反映人與生活的復雜性。而圍棋思維更接近人與生活的本體,充滿復雜,辯證,并在幾百個方格中立體展開。看似在這邊圍你,突然那邊擺一個棋子,似乎不著邊際,實際很有道道,也許是關鍵的一著。這是一種結構,它更能反映現實生活與人的豐富性、復雜性與生動性。比如槍殺事件發生后,不去寫周密如何恐懼,如何掩蓋罪行……而是寫他與丁潔的戀愛,寫他對童年及自己成長奮斗史的回顧,甚至寫他居然將自己的日記給戀人丁潔看等等。這無疑增強了人物的神秘感及劇情的懸念。顯然創作者試著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靈魂,表現更復雜、更隱秘的第二宇宙——人的心靈。這種情節構置與人物塑造頗有些圍棋的味道,可惜在后邊沒有把它下到底。
電視連續劇大雪無痕觀感分析論文
《大雪無痕》講述故事的第一個特點體現在樣式上。實際情節的內核并不復雜,是一宗以數額很大的原始股賄賂高級干部的反貪題材。可編導卻運用了綜合思維的結構手法將其講得有聲有色,講的富于特點而又吸引人。創作者將反貪樣式與偵破樣式以及家庭愛情樣式相結合、相綜合,形成具有現代特征、多信息、獨特的電視劇。幾條不同特點的戲相互交叉、穿插、融合,增強了影片的可看性與信息量。實際上,《大雪無痕》還具有心理劇的因素,可惜未加以發展運用。比如周密這條線的后半部分,日記的因素、犯罪后心理的因素、犯罪的靈魂剖析,如何從自殺轉為殺人,以及公安局方雨林等對周密的心理攻堅及雙方的心理仗等。而廖紅宇與馮祥龍的線也可以往心理方面發展。如果綜合進心理劇因素,相信戲會更豐富更好看。而后半部分戲也不至于蹋下去。
模糊思維與懸念構置
以往我們比較強調要把故事講清楚,強調的是明確性。實際上要講好故事還必須強調另一方面即事物的不確定性。《大雪無痕》開局開的好就在于表現了事物的不確定性,制造了大量的懸念。第一集表現了為衣錦還鄉的軍區丁司令員舉行歌舞升平的招待會,山莊戒備森嚴,通過“攔車”揭示了丁潔與方雨林的神秘關系,接著找張秘書、槍聲、張秘書被害、“他殺!”點明規定情境;如何在違背常規的時間地點作案……提出一系列懸案。主人公方雨林的出現也是充滿懸念,他與丁潔的愛情關系?他本人的被處分處境?他與馬局的矛盾?通過這兩組撲朔迷離,顯影式地提出5·25“東鋼”原始股案件的中止,接著表現了兩位關鍵知情人的死亡。又通過方雨林與馬局的矛盾點出案件牽涉到上邊的復雜性。更巧妙的是讓第一嫌疑人周密通過愛情線浮出,而且是在他升職為市長的背景下……編導在講述這一復雜的故事時設置了許多“突來之筆”“懸來之筆”“神來之筆”。為觀眾構置了一個個懸念,形成了一個個期待,使連續劇抓人好看。懸念的基本特點在于它的模糊性,其核心內容是不確定性。《大雪無痕》的開局正是取了情節的一些非感性的點、面、線、表現了事件運動過程中模糊與不確定的波紋。這就好比將一個石子扔進湖里,我們不去表現“撲通”的中心處,而是有選擇地去描述富于懸念的波紋,通過一系列跳躍式的波紋的描述以顯影的方式逐漸深入到中心。懸念的運動過程的非線性及不平衡、不明確狀態卻顯現出波瀾起伏、跌宕多姿、曲折有致,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在有關情節的點、面、線上,都延伸著無窮的懸念魅力與韻味,而在情節的縱深角度上,采用的是點與點的跳躍,不是僅停在一個點或一條線上,形成縱深感的誘導性拓展性的懸念。而在情節的橫向上,則由點、線通過相互的關連性因素擴展為面,復合的面形成開拓性,生發性和多義性。自然,模糊性思維應來自于整體性的思維,而模糊與清晰是彼此交融,相得益彰的。《大雪無痕》的懸念成果無疑是來自模糊思維的藝術觀念,特別是前半部分取得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圍棋思維與復雜形象
情節是人物性格的歷史,因此,主要人物的塑造,人物性格的構成與發展對講好故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大雪無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如周密、丁潔、方雨林、馬局等,都因為塑造了人物形象的復雜性。創作中情節敘事與人物塑造的簡單化、直白化,往往來自于宏觀創作思維模式的淺顯。為了更形象地講述,我們一般將創作、思維模式稱之為:“多米諾”——“跳棋”——“圍棋”思維模式。多米諾(骨牌)思維一般都是直來直去,雖有變化但永遠是一種線性簡單思維,如創作一個人高興,就一個勁兒歡樂,痛苦呢,一個勁兒悲痛欲絕,塑造一個好人就好到底,壞人就一無是處。然而生活并非如此。該劇正因為表現了周密性格中的兩面性、還因為表現了方雨林性格中對待愛情不可理喻的復雜性、表現了馬局在復雜規定情境下性格中的靈活多樣性、丁潔的愛情生活體現在靈魂深處斗爭的豐富性,才使得這些圓整的復雜形象更真實、更抓人。跳棋思維雖然在跳的進程中有許多變化,但,怎么變化也是從這個三角跳向那個三角,有始有終,有因有果,這種過于明確的因果思維有時難以反映人與生活的復雜性。而圍棋思維更接近人與生活的本體,充滿復雜,辯證,并在幾百個方格中立體展開。看似在這邊圍你,突然那邊擺一個棋子,似乎不著邊際,實際很有道道,也許是關鍵的一著。這是一種結構,它更能反映現實生活與人的豐富性、復雜性與生動性。比如槍殺事件發生后,不去寫周密如何恐懼,如何掩蓋罪行……而是寫他與丁潔的戀愛,寫他對童年及自己成長奮斗史的回顧,甚至寫他居然將自己的日記給戀人丁潔看等等。這無疑增強了人物的神秘感及劇情的懸念。顯然創作者試著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靈魂,表現更復雜、更隱秘的第二宇宙——人的心靈。這種情節構置與人物塑造頗有些圍棋的味道,可惜在后邊沒有把它下到底。
縱觀20集,也有遺憾之處,感覺編導的創新追求不完整,不徹底,有一種跛腳的感覺。一是前半部分好,后半部分弱;另外是方雨林——丁潔——周密線好,廖紅宇——馮祥龍線弱。好就好在有創新觀念新;弱就弱在比較落套,缺少創造力。
國產電視劇困境對策分析論文
一、剪接失度冗長拖沓
我們不是一味地反對拍長劇,而是當長則長,當短則短。應像魯迅先生倡導的要以內容的含量為依據,以不脫離主題為原則來安排劇的長短,即要深刻、生動、精彩、充實、飽滿、好看。不要人為地將單本能完成的戲硬拉成連續劇;將10集能完成的連續劇硬拉成20集;將20集能完成的連續劇硬拉成30集的長篇連續劇。現播出的電視劇動輒20集30集40集,而視其內容含量有的用其一半的集數足矣。有的電視劇如再緊湊些本是很好的,可正是由于拖拖拉拉地太長而顯得乏味了。這就如同一塊餅干,本來是很好吃的,你硬用水將它泡大,結果就無味了。比如《康熙微服私訪記》第一部很好,第二部就乏味了,又不是什么大題材,小故事拉拉雜雜地拍了30集,實在是太長了,嚴重地削弱了藝術的魅力,完全沒必要。《西游記》(續集)情節與前雷同,無新意,也完全沒有必要續出25集來。本來很好的故事倒使人越看越無味;《大明宮詞》可以說是一部很成功的片子,無論是內容、語言,還是主要演員的表演都頗具特色,屬上乘之作。但有的段落節奏亦顯過慢,播出時雖已由40集壓縮到37集,但若壓到30集似更好些。《罪證》《黃金緝私隊》等亦顯過長。而有的故事內容非常豐富的,如《三國演義》雖則84集,但并不覺長;《紅樓夢》20集亦不覺得長;《水滸傳》43集,不但不長,而且有些短了,原作中的好多重要英雄人物的入伙原因及過程都未得以充分展現,若再用幾集加以補充當會更精彩些。因此不能機械地論長短,而是該長則長,該短則短,現有好多劇是該短些卻未短。
二、見好不收狗尾續貂
常言道“見好就收”,這是很有道理的。電視劇制作上也應該這樣,適可而止,最熱鬧時收場,讓人回味無窮。而現實情況是,一部劇播出后,反應良好,于是制片單位或主創人員便想讓“好”持續下去。約來編劇(或另換編劇)再創續集。編劇只好挖空心思地杜撰,全不像當初的靈氣與自然。導演也硬是將質地完全不同的兩部分強行地拼接起來,這樣拍攝出來的續集便多有狗尾續貂之弊了。如《西游記》之續集,基本是“師傅趕走悟空,師徒遇難難解,悟空重返”的老一套情節的重復,雖有高科技幫忙,卻也不很成功;與前一部迥然不同的集與集間的連接方式(向唐皇匯報取經經過)使得與前一部很不諧調,也無新意,完全沒有必要拍續集。可以說由于續集的播出,倒淡化了《西游記》這一精品劇在觀眾心目中已有的完好印象。《康熙微服私訪記》續集雖未受到觀眾更多的非議,但筆者認為,第二部的“康劇”未能超越第一部,也如不續。
三、移植失當膨化虛空
將優秀的小說改編成電視劇,這是電視劇劇本創作的途徑之一,是正常的,無可非議的。但當某部小說已先行被改編成了電影,還要不要再編成電視劇,這可要慎之又慎了。筆者認為,當被改編的電影拍得非常成功時,則千萬不要再打電視劇的念頭了。如果原小說十分優秀而電影拍得又很不理想或影響很小,將來改編拍成的電視劇有超過電影的把握,那么則可將小說改編成電視劇(這樣成功的例子,筆者至今未看到)。因先前改編的電影的成功使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已在觀眾心目中確定了毋庸置疑的肯定地位(也有先入為主的因素),那么再重新塑造的電視劇人物形象和拉長的故事情節會令看過電影的人很難接受。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又何必去干呢?可我們的電視劇創作中卻偏偏有這樣敢于鋌而走險的電視編導,任你電影再成功,他也要重新將小說改編成電視連續劇。最終拍成的電視連續劇可能演員比電影中的漂亮,情節比電影更豐富,編導也自我感覺良好,可觀眾就是不認可。比如,早些年謝鐵驪導演根據現代名著《青春之歌》改編拍攝的同名電影,可算得上是電影中公認的精品,可是近年又有人把它改編成20集電視連續劇,拍得固然也有聲有色,但終未能超過原來的電影。盡管新聞媒體在拍片前進行了大肆的宣傳,但也終不及未經怎么宣傳的當年同名電影的影響之深、之廣。即使是剛剛播出不久的20集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從藝術質量的角度看,也遠遠不及蘇聯早年拍攝的同名電影生動、光彩、震撼人心。當然以不很多的資金,將當年較有影響的革命影片重拍成電視劇以對年輕人進行思想政治上的再教育也是必要的,但那是與影視藝術不相關的另一層意義的事。還有一種情況是,有的電視劇編導將目光盯在了獨立創作的話劇的改編上,這也是不足取的。你改編不成功的話劇沒有意義,而久演不衰的經典話劇作品,其穩固的樣板般的地位和影響是不會輕易被取代的。特別是有些話劇劇本不是脫胎于小說或其它姐妹藝術的,而是有固定的獨立的劇本,是經過話劇作者千錘百煉“打造”而成的。你將它改編成電視劇無非是想讓他更豐富、更生動,而它又不像由小說改編成的話劇劇本,要參照原小說。在無可參照的前提下增加內容,這就勢必要對原劇本加以膨化、拉長,添枝加葉地敷衍成連續劇了。那么電視編導附會進去的東西也許恰恰是原話劇編劇已想到的并舍棄的東西,而優秀的原話劇作家的功力往往又是我們電視劇的編劇不能相比的。這樣由話劇膨化了的、拉長了的電視連續劇往往會出現蛇足之弊,試想它能超過原話劇的影響嗎?我想不會,也沒見過由話劇改編成的電視連續劇超過原話劇的。與其如此,不如不作。比如20集電視連續劇《雷雨》便是由曹禺的同名話劇改編的。這部連續劇的導演功力是不淺的,演員也是十分優秀的,可以說,該劇如果不是脫胎于曹禺的同名話劇而是獨立創作的,應該說是拍得很成功的。但它畢竟是依據當代中國最著名的劇作家的作品改編的,其人其劇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都閃爍著灼人目睛的光輝,而且在世界當代文學史上亦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雷雨》又是大師的代表作,劇本是煉到了精而又精多一字少一字皆不宜的程度。數十年來該話劇在中國各地舞臺上久演不衰,怎么可以想象有人居然能把這樣的2個小時的佳品膨化成十五六個小時的東西呢。改編成電視連續劇的《雷雨》頗失原劇的凝重、洗煉,注定是超不過原劇的,超不過即是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