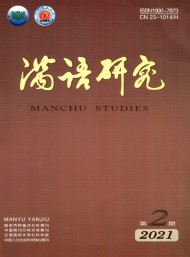滿洲族范文10篇
時間:2024-02-26 12:23:57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滿洲族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滿洲族的社會性質研究論文
1583年(明神宗萬歷十一年),滿洲(當時稱為建州女真)的沒落的上層分子努爾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討伐他的仇人,經過了三十三年,到1616年(萬歷四十四年),建立了以自己為首的滿洲政權金國——后來稱為清朝。又經過了二十八年,到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滿洲貴族統兵入關,逐步統治了明代原來的整個疆域。直到1911年(宣統三年)才被推翻。
滿洲族建立的清朝,以一個少數族在二十八年間能人關統治高度封建化的廣大的漢人地區,而且后來在和祖國廣大民族共同努力下對祖國疆土的奠定和祖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在歷史上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此,滿洲入關前的社會經濟究竟發展到什么階段,也就值得我們注意了。
關于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問題,目前史學界還存在不同意見。
我們從接觸到的資料中知道,滿洲族的社會發展是和其它民族所經歷的社會發展階段一致的。它經過了原始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
在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建州女真曾擄掠朝鮮邊境的人口、物資,朝鮮官吏李競令邊將切責他們說,“汝等近居我境,乞索鹽醬口糧,輒便給與,恩養足矣。但爾等虜掠中國人口及我邊民為奴婢使喚,往往有逃來者,審問根腳,中國人發還遼東,我國之人仍令復業。……我國何負于汝,……近者結聚群黨,暗入作賊,虜去男女七十余口,殺害四十余口,牛馬財物,盡數搶奪……”(么朝鮮李朝實錄·世宗》十五年,日本縮印本8冊,240頁)。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朝鮮成宗八年),朝鮮官吏曾說,“野人(指建州女真)剽掠上國(指明朝)邊氓,做奴使喚,乃其俗也”(《李朝實錄·成宗》卷八十,縮印本16冊,59頁)。
努爾哈赤十歲(1568年)喪母,和繼母不相得,在十九歲時(1577年)和父母分居。《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說:“父惑于繼母言,遂分居,……家私止給些須”(故宮博物院鉛印本,3頁)。這里的“家私”,在《滿洲實錄》,漢文作“家產”,滿文作“阿哈·烏勒哈”(ahaulha)。“阿哈”,漢語是奴隸;“烏勒哈”,漢語是家畜。
滿洲族的社會性質分析論文
1583年(明神宗萬歷十一年),滿洲(當時稱為建州女真)的沒落的上層分子努爾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討伐他的仇人,經過了三十三年,到1616年(萬歷四十四年),建立了以自己為首的滿洲政權金國——后來稱為清朝。又經過了二十八年,到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滿洲貴族統兵入關,逐步統治了明代原來的整個疆域。直到1911年(宣統三年)才被推翻。
滿洲族建立的清朝,以一個少數族在二十八年間能人關統治高度封建化的廣大的漢人地區,而且后來在和祖國廣大民族共同努力下對祖國疆土的奠定和祖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在歷史上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此,滿洲入關前的社會經濟究竟發展到什么階段,也就值得我們注意了。
關于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問題,目前史學界還存在不同意見。
我們從接觸到的資料中知道,滿洲族的社會發展是和其它民族所經歷的社會發展階段一致的。它經過了原始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
在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建州女真曾擄掠朝鮮邊境的人口、物資,朝鮮官吏李競令邊將切責他們說,“汝等近居我境,乞索鹽醬口糧,輒便給與,恩養足矣。但爾等虜掠中國人口及我邊民為奴婢使喚,往往有逃來者,審問根腳,中國人發還遼東,我國之人仍令復業。……我國何負于汝,……近者結聚群黨,暗入作賊,虜去男女七十余口,殺害四十余口,牛馬財物,盡數搶奪……”(么朝鮮李朝實錄·世宗》十五年,日本縮印本8冊,240頁)。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朝鮮成宗八年),朝鮮官吏曾說,“野人(指建州女真)剽掠上國(指明朝)邊氓,做奴使喚,乃其俗也”(《李朝實錄·成宗》卷八十,縮印本16冊,59頁)。
努爾哈赤十歲(1568年)喪母,和繼母不相得,在十九歲時(1577年)和父母分居。《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說:“父惑于繼母言,遂分居,……家私止給些須”(故宮博物院鉛印本,3頁)。這里的“家私”,在《滿洲實錄》,漢文作“家產”,滿文作“阿哈·烏勒哈”(ahaulha)。“阿哈”,漢語是奴隸;“烏勒哈”,漢語是家畜。
滿漢文化的沖突與融合探析論文
摘要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發展的集成,歷史上滿、漢族的文化沖突與融合是中華民族豐富、燦爛文化的縮影,漢族的發展影響了滿族,滿族的發展也影響了漢族。中華民族的子集不是漢族、滿族、回族,而是一個求同存異,共同認同中華,但是風俗各異的聯合體。
關鍵詞中華民族文化史漢族滿族沖突融合
中華民族歷史的演進,離不開中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華文化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是一個自我禁錮的系統,漢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鮮卑人、黨項人、吐藩人、女真人.....還有臺灣的“原住民”,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祖先的組成部分。在中國歷史上,正因為中華各族文化相激蕩,所以才有蘇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飛“精忠報國”,有文天祥在伶仃洋邊的感嘆....,所以才有萬里長城橫亙中國大地,才有中國文化內容的生氣勃勃、氣象萬千。
滿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從宋代開始,“半游牧”的滿族的先人女真族就與中原腹地的“農耕民族”的漢族開始了爭奪與反爭奪、控制與反控制的沖突和斗爭,開始了思想文化、意識觀念的交鋒,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親,中華民族的血脈就這樣雜交、優選地生存著和發展著。明代末年,當滿洲上層階級祭出“七大恨”、披堅執銳地以旋風之勢征服大江南北、情緒高漲的南下,當八旗取得對中國這片土地的統治時,古老燦爛但積弱不振、低迷徘徊的“農耕”漢文化必然地與有進取意識的滿洲“游牧”滿文化發生尖銳沖突。
一、滿漢文化沖突
1、在精神思想領域上的交鋒。
滿漢文化的研究論文
摘要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發展的集成,歷史上滿、漢族的文化沖突與融合是中華民族豐富、燦爛文化的縮影,漢族的發展影響了滿族,滿族的發展也影響了漢族。中華民族的子集不是漢族、滿族、回族,而是一個求同存異,共同認同中華,但是風俗各異的聯合體。
關鍵詞中華民族文化史漢族滿族沖突融合
中華民族歷史的演進,離不開中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華文化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是一個自我禁錮的系統,漢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鮮卑人、黨項人、吐藩人、女真人.....還有臺灣的“原住民”,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祖先的組成部分。在中國歷史上,正因為中華各族文化相激蕩,所以才有蘇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飛“精忠報國”,有文天祥在伶仃洋邊的感嘆....,所以才有萬里長城橫亙中國大地,才有中國文化內容的生氣勃勃、氣象萬千。
滿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從宋代開始,“半游牧”的滿族的先人女真族就與中原腹地的“農耕民族”的漢族開始了爭奪與反爭奪、控制與反控制的沖突和斗爭,開始了思想文化、意識觀念的交鋒,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親,中華民族的血脈就這樣雜交、優選地生存著和發展著。明代末年,當滿洲上層階級祭出“七大恨”、披堅執銳地以旋風之勢征服大江南北、情緒高漲的南下,當八旗取得對中國這片土地的統治時,古老燦爛但積弱不振、低迷徘徊的“農耕”漢文化必然地與有進取意識的滿洲“游牧”滿文化發生尖銳沖突。
一、滿漢文化沖突
1、在精神思想領域上的交鋒。
滿漢文化沖突與融合論文
——兼談中國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發展的共生體
摘要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發展的集成,歷史上滿、漢族的文化沖突與融合是中華民族豐富、燦爛文化的縮影,漢族的發展影響了滿族,滿族的發展也影響了漢族。中華民族的子集不是漢族、滿族、回族,而是一個求同存異,共同認同中華,但是風俗各異的聯合體。
關鍵詞中華民族文化史漢族滿族沖突融合
中華民族歷史的演進,離不開中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華文化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是一個自我禁錮的系統,漢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鮮卑人、黨項人、吐藩人、女真人.....還有臺灣的“原住民”,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祖先的組成部分。在中國歷史上,正因為中華各族文化相激蕩,所以才有蘇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飛“精忠報國”,有文天祥在伶仃洋邊的感嘆....,所以才有萬里長城橫亙中國大地,才有中國文化內容的生氣勃勃、氣象萬千。
滿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從宋代開始,“半游牧”的滿族的先人女真族就與中原腹地的“農耕民族”的漢族開始了爭奪與反爭奪、控制與反控制的沖突和斗爭,開始了思想文化、意識觀念的交鋒,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親,中華民族的血脈就這樣雜交、優選地生存著和發展著。明代末年,當滿洲上層階級祭出“七大恨”、披堅執銳地以旋風之勢征服大江南北、情緒高漲的南下,當八旗取得對中國這片土地的統治時,古老燦爛但積弱不振、低迷徘徊的“農耕”漢文化必然地與有進取意識的滿洲“游牧”滿文化發生尖銳沖突。
一、滿漢文化沖突
滿族統一分析論文
我國東北包括黑龍江、烏蘇里江江外廣大地區,從女真族全國政權金王朝以后,一直在元、明、清三個王朝政權統屬之下,也就是中國的領土。王朝雖然更迭,領土人民始終是中國的,這是絕對不能改變的。一個新王朝的成立和鞏固有一個過程,各地的土地人民隸屬于新政權也有先后。在歷史悠久土地廣大的國家里,某一地方在某—時期還未隸屬于新王朝仍然打著舊王朝旗幟是常見之事,例如明洪武初年的云南,清順治初年的廈門。這只能說它那時還不屬于新王朝,而不能說它不屬于中國。
清王朝締造者努爾哈赤出身于女真族建州衛貴族。建州衛在明代是“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1]的東北少數族衛所之一。同它一樣的東北少數族,在永樂時有一百七十九衛[2]。經過不斷地分合發展,天順時增加到一百八十四衛[3],到萬歷時增加到三百八十四衛[4]。這些不同氏族不同部族甚至不同民族的幾百個單位,都經過明王朝的任命,成為明王朝的也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明東北少數族,法令上稱為“屬夷”[5],就是直屬朝廷的少數族,和西南少數族“土官”的隸屬于地方政府有所不同。朝廷經常舉行“大閱”[6],派人“巡邊”[7]、“燒荒”[8],稽察統治比較嚴格,壓迫剝削也比較殘酷。明中葉以后,政治越來越腐朽,控制的效能雖然降低,本質上還是一樣。努爾哈赤在1623年(天命八年)曾歷數明萬歷帝對少數族的壓迫、干涉等罪惡,認為滿族的戰爭不息都是萬歷帝罪惡造成的[9]。
東北屬夷由明廷按照它們各族的血緣團體和聯合體的族屬大小、人丁多少、力量強弱分為都司、衛和千戶所,給以都督、都督僉事、指揮、指揮僉事、千戶、百戶、鎮撫等不同等級的名位。
法定的衛所頭目,明王朝發給他們“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不等[10]。誥也叫誥敕、貢敕,又稱敕書,是任命的證書,憑著它才能到北京朝貢,并領“年例賞物”;印是管理權的象征,有它才能對部下發號施令;冠帶襲衣是規定的制服,朝貢時要穿戴。
所謂朝貢,就是臣屬關系的表現,就是統治與被統治、保護與被保護關系的確定。1613年(萬歷四十一年)努爾哈赤進攻葉赫,葉赫報告明廷,明廷一面派人制止,一面虛張聲勢派兵往葉赫駐防,努爾哈赤也就親到撫順解釋,并投遞一份書面報告。雙方都在做戲。可以看出,在明中葉衰弱之后,保護與被保護的實際作用雖然已不存在,而走過場的空架子還在保留著。因此,誥敕印記的象征觀念依然根深蒂固,互相兼并首先要把誥敕信記搶過來。嘉靖時,哈達奪葉赫貢敕七百道,1537年(嘉靖十六年)哈達和葉赫平分了海西諸部敕書九百九十九道[11],1588年(萬歷十六年)努爾哈赤派人持五百道敕書向明廷領年例[12],我們還在滿文老檔看到努爾哈赤集團保存無數的努爾哈赤家族以外的敕書[13],都是這個原因。
滿漢文化分析論文
——兼談中國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發展的共生體
摘要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發展的集成,歷史上滿、漢族的文化沖突與融合是中華民族豐富、燦爛文化的縮影,漢族的發展影響了滿族,滿族的發展也影響了漢族。中華民族的子集不是漢族、滿族、回族,而是一個求同存異,共同認同中華,但是風俗各異的聯合體。
關鍵詞中華民族文化史漢族滿族沖突融合
中華民族歷史的演進,離不開中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華文化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是一個自我禁錮的系統,漢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鮮卑人、黨項人、吐藩人、女真人.....還有臺灣的“原住民”,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祖先的組成部分。在中國歷史上,正因為中華各族文化相激蕩,所以才有蘇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飛“精忠報國”,有文天祥在伶仃洋邊的感嘆....,所以才有萬里長城橫亙中國大地,才有中國文化內容的生氣勃勃、氣象萬千。
滿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從宋代開始,“半游牧”的滿族的先人女真族就與中原腹地的“農耕民族”的漢族開始了爭奪與反爭奪、控制與反控制的沖突和斗爭,開始了思想文化、意識觀念的交鋒,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親,中華民族的血脈就這樣雜交、優選地生存著和發展著。明代末年,當滿洲上層階級祭出“七大恨”、披堅執銳地以旋風之勢征服大江南北、情緒高漲的南下,當八旗取得對中國這片土地的統治時,古老燦爛但積弱不振、低迷徘徊的“農耕”漢文化必然地與有進取意識的滿洲“游牧”滿文化發生尖銳沖突。
一、滿漢文化沖突
清代薩滿祭祀分析論文
自從十七世紀末葉和清代初年,隨著中國薩滿信仰習俗被介紹到西方[1],引起西方學者對阿爾泰語系廣袤世界同類民俗事象的關注,并在此后的三個世紀中,學者們對薩滿世界的考察和研究就從未停止,而且使薩滿文化的研究發展成為世界性的課題。
國際上許多學者對薩滿習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歸于對“薩滿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國學術界通常也使用“薩滿教”一詞,但誰都知道,薩滿在中國北方諸民族中的傳承由來已久,它從形成的時候起就是一種原始的民間崇拜和信仰的產物,其傳承和傳播完全處于一種自發的狀態之中,屬于信仰文化或巫術文化的范疇。直到今天,“薩滿”絕非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它的傳承和傳播方式,仍然是一種巫術行為,也可以稱之為薩滿巫術。這樣看來,薩滿信仰屬于中國巫文化系統,或者說它是中國巫文化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
中國的巫文化是一個歷史悠久,內容十分龐雜的系統,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和現代的民俗傳承,如果將中國的巫文化作學術上的分類,筆者認為它包括了兩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即中國北方諸民族傳承的薩滿文化和中國南方諸民族中傳承的儺文化(即面具文化)。這也是近幾年來中國民俗學對中國巫文化的宏觀關照和學術研究的新的走向。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薩滿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熱門,考察所得資料異常豐富。最近幾年,儺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來居上,造成一種十分熱烈的空氣。薩滿文化與儺文化的相互關照,一定會使中國巫文化的研究出現嶄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學研究中往往將其歸入原始信仰,有時也稱為“民俗宗教”[2],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一詞使用了廣義的概念。長期以來,“宗教”一詞在民俗學研究中經常給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們很難描述某些民俗事象。為了區別于“現代宗教”,學者們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適用的。“民俗宗教”將巫文化包含其中,為敘述和研究帶來方便。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巫文化曾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中國古老的科學和文化發展均與巫文化有關,如文字、天文、醫療、數學、文學、音樂、舞蹈、繪畫、歷史學的產生、發展,都和巫術活動有關,甚至連知識分子階層都是由巫發展而來。可見巫文化作為各種文化的母體,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嚴格說來,巫文化是一種民間傳承,它在原始社會尚未出現階級分化時,尤其如此。在那時由巫文化所構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觀。當社會出現階級分化,特別是國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傳播情景則完全不同。這時,巫文化除在民間繼續傳承外,其中許多成分被統治階級吸收,并將其系統化,儀禮化,用來為鞏固其統治地位服務。作為中國巫文化組成部分的儺文化和薩滿文化,都沒有逃脫這種命運。本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探討清代宮廷的薩滿祭祀。并在此基礎上將民間薩滿信仰和宮廷薩滿典禮作些比較。
清代宮廷的薩滿祭祀是民俗宗教——薩滿信仰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為歷來的薩滿文化研究所忽視了的問題。現在將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為清代文獻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會典》(雍正、嘉慶時代)、《禮部則例》、《大清會典事例》、《紐祜祿氏滿洲祭天、祭神典禮》、《國朝宮史》等,詳細記載了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鈞的《天咫偶聞》、昭梿的《嘯亭雜錄》、吳振城的《養吉齋叢錄》、姚元之的《竹葉亭雜錄》、麟慶的《鴻雪因緣圖記》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宮廷、王室有關薩滿祭祀的實錄。特別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編纂的《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為我們研究滿族薩滿習俗和清代宮廷薩滿儀典,提供了翔實可靠的資料。
薩滿及其信仰,本是中國北方阿爾泰語系諸民族普遍傳承的一種習俗,流傳地區十分廣闊。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白山黑水和大小興安嶺一帶的滿族、達斡爾族、赫哲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錫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漢族(漢軍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薩滿習俗流傳。中國東北地區的薩滿信仰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圈,也是薩滿文化傳承最穩固的地區。這種傳承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帶有森林、狩獵和漁獵色彩,可稱為森林薩滿文化圈。華北蒙古族地區,是中國薩滿傳承的又一個文化圈,這一文化圈帶有濃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稱為草原薩滿文化圈。蒙古族薩滿,傳承十分古老,但變異也較大。在元代(1279-1368)隨著藏傳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和逐漸占據統治地位,一部分薩滿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漸次消失,人為的因素曾一度割斷了蒙古族薩滿信仰的傳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薩滿信仰在部落上層和民眾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當時一些大薩滿(巫師)都被收羅在蒙古宮廷中,他們守護偶像,并諳星術,預言日月之蝕,擇定吉日兇日,人們有事必去咨詢。“凡宮廷所用之物,以及貢品,必經此輩以火凈之,此輩得留取若干。兒童之誕生,則召其至,以卜命運。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術。托其欲構諂某人,只須言某人之疾,蓋因某人厭禳所致。人有咨詢者,此輩則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偽作神語以答之。”[3]當時,薩滿幾乎主宰部落或國家大事。據《多桑蒙古史》載:“塔塔爾諸游牧部落既平,鐵木真應有適合其新勢權之尊號。1206年春,遂集諸部長開大會于斡難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蠻或卜者闊闊出者,常代神發言,素為蒙古人所信奉,茲莊然告鐵木真曰:‘具有古兒汗和大汗尊號之數主既已敗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跡之同一尊號。今奉天命,命其為成吉思汗或強者之汗。’諸部長群贊其議,乃上鐵木真尊號成吉思汗。時年44歲。”[4]此類記載,在蒙古族古代文獻中經常見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層社會,喇嘛與薩滿之間的斗爭從未間斷過,特別是對薩滿供奉的偶像“翁袞”,歷加取締。元代滅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漸深入民間,薩滿更處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衛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規定取締翁袞。對邀請男女薩滿來家者,給予不等馬匹的處罰。對請來男女妖術師耍魔術者的乘馬和妖術師的馬,歸告發者所有,知而不報者受罰,甚至使高貴者受到詛咒,也要罰馬五匹等等[5]。這些條律,對薩滿信仰是很大的打擊。但盡管如此,在廣袤的蒙古草原,薩滿信仰并未絕跡,甚至在近代,科爾沁草原仍流行薩滿信仰[6]。
薩滿祭祀探究論文
自從十七世紀末葉和清代初年,隨著中國薩滿信仰習俗被介紹到西方[1],引起西方學者對阿爾泰語系廣袤世界同類民俗事象的關注,并在此后的三個世紀中,學者們對薩滿世界的考察和研究就從未停止,而且使薩滿文化的研究發展成為世界性的課題。
國際上許多學者對薩滿習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歸于對“薩滿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國學術界通常也使用“薩滿教”一詞,但誰都知道,薩滿在中國北方諸民族中的傳承由來已久,它從形成的時候起就是一種原始的民間崇拜和信仰的產物,其傳承和傳播完全處于一種自發的狀態之中,屬于信仰文化或巫術文化的范疇。直到今天,“薩滿”絕非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它的傳承和傳播方式,仍然是一種巫術行為,也可以稱之為薩滿巫術。這樣看來,薩滿信仰屬于中國巫文化系統,或者說它是中國巫文化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
中國的巫文化是一個歷史悠久,內容十分龐雜的系統,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和現代的民俗傳承,如果將中國的巫文化作學術上的分類,筆者認為它包括了兩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即中國北方諸民族傳承的薩滿文化和中國南方諸民族中傳承的儺文化(即面具文化)。這也是近幾年來中國民俗學對中國巫文化的宏觀關照和學術研究的新的走向。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薩滿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熱門,考察所得資料異常豐富。最近幾年,儺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來居上,造成一種十分熱烈的空氣。薩滿文化與儺文化的相互關照,一定會使中國巫文化的研究出現嶄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學研究中往往將其歸入原始信仰,有時也稱為“民俗宗教”[2],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一詞使用了廣義的概念。長期以來,“宗教”一詞在民俗學研究中經常給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們很難描述某些民俗事象。為了區別于“現代宗教”,學者們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適用的。“民俗宗教”將巫文化包含其中,為敘述和研究帶來方便。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巫文化曾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中國古老的科學和文化發展均與巫文化有關,如文字、天文、醫療、數學、文學、音樂、舞蹈、繪畫、歷史學的產生、發展,都和巫術活動有關,甚至連知識分子階層都是由巫發展而來。可見巫文化作為各種文化的母體,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嚴格說來,巫文化是一種民間傳承,它在原始社會尚未出現階級分化時,尤其如此。在那時由巫文化所構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觀。當社會出現階級分化,特別是國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傳播情景則完全不同。這時,巫文化除在民間繼續傳承外,其中許多成分被統治階級吸收,并將其系統化,儀禮化,用來為鞏固其統治地位服務。作為中國巫文化組成部分的儺文化和薩滿文化,都沒有逃脫這種命運。本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探討清代宮廷的薩滿祭祀。并在此基礎上將民間薩滿信仰和宮廷薩滿典禮作些比較。
清代宮廷的薩滿祭祀是民俗宗教——薩滿信仰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為歷來的薩滿文化研究所忽視了的問題。現在將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為清代文獻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會典》(雍正、嘉慶時代)、《禮部則例》、《大清會典事例》、《紐祜祿氏滿洲祭天、祭神典禮》、《國朝宮史》等,詳細記載了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鈞的《天咫偶聞》、昭梿的《嘯亭雜錄》、吳振城的《養吉齋叢錄》、姚元之的《竹葉亭雜錄》、麟慶的《鴻雪因緣圖記》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宮廷、王室有關薩滿祭祀的實錄。特別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編纂的《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為我們研究滿族薩滿習俗和清代宮廷薩滿儀典,提供了翔實可靠的資料。
薩滿及其信仰,本是中國北方阿爾泰語系諸民族普遍傳承的一種習俗,流傳地區十分廣闊。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白山黑水和大小興安嶺一帶的滿族、達斡爾族、赫哲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錫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漢族(漢軍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薩滿習俗流傳。中國東北地區的薩滿信仰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圈,也是薩滿文化傳承最穩固的地區。這種傳承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帶有森林、狩獵和漁獵色彩,可稱為森林薩滿文化圈。華北蒙古族地區,是中國薩滿傳承的又一個文化圈,這一文化圈帶有濃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稱為草原薩滿文化圈。蒙古族薩滿,傳承十分古老,但變異也較大。在元代(1279-1368)隨著藏傳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和逐漸占據統治地位,一部分薩滿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漸次消失,人為的因素曾一度割斷了蒙古族薩滿信仰的傳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薩滿信仰在部落上層和民眾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當時一些大薩滿(巫師)都被收羅在蒙古宮廷中,他們守護偶像,并諳星術,預言日月之蝕,擇定吉日兇日,人們有事必去咨詢。“凡宮廷所用之物,以及貢品,必經此輩以火凈之,此輩得留取若干。兒童之誕生,則召其至,以卜命運。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術。托其欲構諂某人,只須言某人之疾,蓋因某人厭禳所致。人有咨詢者,此輩則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偽作神語以答之。”[3]當時,薩滿幾乎主宰部落或國家大事。據《多桑蒙古史》載:“塔塔爾諸游牧部落既平,鐵木真應有適合其新勢權之尊號。1206年春,遂集諸部長開大會于斡難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蠻或卜者闊闊出者,常代神發言,素為蒙古人所信奉,茲莊然告鐵木真曰:‘具有古兒汗和大汗尊號之數主既已敗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跡之同一尊號。今奉天命,命其為成吉思汗或強者之汗。’諸部長群贊其議,乃上鐵木真尊號成吉思汗。時年44歲。”[4]此類記載,在蒙古族古代文獻中經常見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層社會,喇嘛與薩滿之間的斗爭從未間斷過,特別是對薩滿供奉的偶像“翁袞”,歷加取締。元代滅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漸深入民間,薩滿更處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衛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規定取締翁袞。對邀請男女薩滿來家者,給予不等馬匹的處罰。對請來男女妖術師耍魔術者的乘馬和妖術師的馬,歸告發者所有,知而不報者受罰,甚至使高貴者受到詛咒,也要罰馬五匹等等[5]。這些條律,對薩滿信仰是很大的打擊。但盡管如此,在廣袤的蒙古草原,薩滿信仰并未絕跡,甚至在近代,科爾沁草原仍流行薩滿信仰[6]。
古代薩滿祭祀研究論文
自從十七世紀末葉和清代初年,隨著中國薩滿信仰習俗被介紹到西方[1],引起西方學者對阿爾泰語系廣袤世界同類民俗事象的關注,并在此后的三個世紀中,學者們對薩滿世界的考察和研究就從未停止,而且使薩滿文化的研究發展成為世界性的課題。
國際上許多學者對薩滿習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歸于對“薩滿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國學術界通常也使用“薩滿教”一詞,但誰都知道,薩滿在中國北方諸民族中的傳承由來已久,它從形成的時候起就是一種原始的民間崇拜和信仰的產物,其傳承和傳播完全處于一種自發的狀態之中,屬于信仰文化或巫術文化的范疇。直到今天,“薩滿”絕非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它的傳承和傳播方式,仍然是一種巫術行為,也可以稱之為薩滿巫術。這樣看來,薩滿信仰屬于中國巫文化系統,或者說它是中國巫文化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
中國的巫文化是一個歷史悠久,內容十分龐雜的系統,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和現代的民俗傳承,如果將中國的巫文化作學術上的分類,筆者認為它包括了兩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即中國北方諸民族傳承的薩滿文化和中國南方諸民族中傳承的儺文化(即面具文化)。這也是近幾年來中國民俗學對中國巫文化的宏觀關照和學術研究的新的走向。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薩滿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熱門,考察所得資料異常豐富。最近幾年,儺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來居上,造成一種十分熱烈的空氣。薩滿文化與儺文化的相互關照,一定會使中國巫文化的研究出現嶄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學研究中往往將其歸入原始信仰,有時也稱為“民俗宗教”[2],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一詞使用了廣義的概念。長期以來,“宗教”一詞在民俗學研究中經常給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們很難描述某些民俗事象。為了區別于“現代宗教”,學者們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適用的。“民俗宗教”將巫文化包含其中,為敘述和研究帶來方便。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巫文化曾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中國古老的科學和文化發展均與巫文化有關,如文字、天文、醫療、數學、文學、音樂、舞蹈、繪畫、歷史學的產生、發展,都和巫術活動有關,甚至連知識分子階層都是由巫發展而來。可見巫文化作為各種文化的母體,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嚴格說來,巫文化是一種民間傳承,它在原始社會尚未出現階級分化時,尤其如此。在那時由巫文化所構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觀。當社會出現階級分化,特別是國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傳播情景則完全不同。這時,巫文化除在民間繼續傳承外,其中許多成分被統治階級吸收,并將其系統化,儀禮化,用來為鞏固其統治地位服務。作為中國巫文化組成部分的儺文化和薩滿文化,都沒有逃脫這種命運。本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探討清代宮廷的薩滿祭祀。并在此基礎上將民間薩滿信仰和宮廷薩滿典禮作些比較。
清代宮廷的薩滿祭祀是民俗宗教——薩滿信仰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為歷來的薩滿文化研究所忽視了的問題。現在將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為清代文獻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會典》(雍正、嘉慶時代)、《禮部則例》、《大清會典事例》、《紐祜祿氏滿洲祭天、祭神典禮》、《國朝宮史》等,詳細記載了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鈞的《天咫偶聞》、昭梿的《嘯亭雜錄》、吳振城的《養吉齋叢錄》、姚元之的《竹葉亭雜錄》、麟慶的《鴻雪因緣圖記》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宮廷、王室有關薩滿祭祀的實錄。特別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編纂的《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為我們研究滿族薩滿習俗和清代宮廷薩滿儀典,提供了翔實可靠的資料。
薩滿及其信仰,本是中國北方阿爾泰語系諸民族普遍傳承的一種習俗,流傳地區十分廣闊。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白山黑水和大小興安嶺一帶的滿族、達斡爾族、赫哲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錫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漢族(漢軍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薩滿習俗流傳。中國東北地區的薩滿信仰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圈,也是薩滿文化傳承最穩固的地區。這種傳承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帶有森林、狩獵和漁獵色彩,可稱為森林薩滿文化圈。華北蒙古族地區,是中國薩滿傳承的又一個文化圈,這一文化圈帶有濃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稱為草原薩滿文化圈。蒙古族薩滿,傳承十分古老,但變異也較大。在元代(1279-1368)隨著藏傳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和逐漸占據統治地位,一部分薩滿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漸次消失,人為的因素曾一度割斷了蒙古族薩滿信仰的傳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薩滿信仰在部落上層和民眾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當時一些大薩滿(巫師)都被收羅在蒙古宮廷中,他們守護偶像,并諳星術,預言日月之蝕,擇定吉日兇日,人們有事必去咨詢。“凡宮廷所用之物,以及貢品,必經此輩以火凈之,此輩得留取若干。兒童之誕生,則召其至,以卜命運。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術。托其欲構諂某人,只須言某人之疾,蓋因某人厭禳所致。人有咨詢者,此輩則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偽作神語以答之。”[3]當時,薩滿幾乎主宰部落或國家大事。據《多桑蒙古史》載:“塔塔爾諸游牧部落既平,鐵木真應有適合其新勢權之尊號。1206年春,遂集諸部長開大會于斡難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蠻或卜者闊闊出者,常代神發言,素為蒙古人所信奉,茲莊然告鐵木真曰:‘具有古兒汗和大汗尊號之數主既已敗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跡之同一尊號。今奉天命,命其為成吉思汗或強者之汗。’諸部長群贊其議,乃上鐵木真尊號成吉思汗。時年44歲。”[4]此類記載,在蒙古族古代文獻中經常見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層社會,喇嘛與薩滿之間的斗爭從未間斷過,特別是對薩滿供奉的偶像“翁袞”,歷加取締。元代滅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漸深入民間,薩滿更處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衛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規定取締翁袞。對邀請男女薩滿來家者,給予不等馬匹的處罰。對請來男女妖術師耍魔術者的乘馬和妖術師的馬,歸告發者所有,知而不報者受罰,甚至使高貴者受到詛咒,也要罰馬五匹等等[5]。這些條律,對薩滿信仰是很大的打擊。但盡管如此,在廣袤的蒙古草原,薩滿信仰并未絕跡,甚至在近代,科爾沁草原仍流行薩滿信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