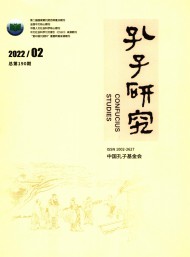儒家傳統范文10篇
時間:2024-03-09 13:49:50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儒家傳統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儒家傳統研究論文
一、確立制度環境
在上述問題中,亨廷頓強調要研究在什么樣的環境條件下,儒家傳統中的有利于民主的因素可以取代其非民主的成分。這實際上是在暗示,即使儒家傳統中存在著有利于民主的因素或資源,其作用的發揮也需要依賴于一定的環境條件。那么,這種環境條件究竟是什么?
根據近年來學者的研究,這種環境條件首先是市場經濟。通過對東亞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觀察,學者們發現,在包括日本和“四小龍”(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地區)的東亞儒教文化圈中,由于在實踐中插入了市場經濟,儒家傳統與民主政治已處于或者正趨向于對接、兼容狀態。由此,他們認為,“儒家傳統或許可以通過某種中介物與民主實現對接。這一中介物必須是在新加坡和另外三小龍中共同存在的。……這個中介物即是以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為基礎建立或繼承下來的市場經濟(故又稱自由經濟)。在日本,儒教(還有當地的文化傳統)與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三者已完全對接,運作也較成功(尤其在經濟方面)。在新加坡、臺灣和韓國,儒教與市場秩序已銜接,現正處于銜接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進程。不難看出,這條路線的走向是三點一線:儒家傳統(作為固有傳統的出發點)———市場經濟(中介與基本目標)———民主政治(現代化的另一目標),而不是繞開市場經濟,直接拿儒教去嫁接或對抗民主政治。”②上述“三點一線”論,作為對東亞政治經濟發展經驗觀察而來的理論概括,可能還有待于實踐與事實的進一步檢驗:但從探討儒家傳統與現代民主的關系來看,它強調不能繞開市場經濟,必須把市場經濟作為連接儒家傳統與現代民主學術研究的制度環境,這不僅具有較為堅實的現實基礎,而且有充分的理論依據。因為,一方面,現代民主本身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只有隨著市場經濟秩序的確立,現代民主在儒家傳統社會中的生長才能獲得堅實的土壤、深厚的根基。因而,儒家傳統的精神資源要在民主政治中起到某種支援、輔助的功能,根本性的制度條件之一是在儒家傳統與現代民主之間插入市場經濟,這也就是上述“三點一線”論的要義所在。另一方面,只有立足于市場經濟的現代民主在儒家傳統社會中得到逐步的生長、發育,這一并非完滿無缺的現代政治運作機制,才需要得到來自傳統文化的支援和輔助,同時,儒家傳統中的思想資源、道德精神對現代民主可能具有的正面功能、作用,才有現實的作用對象。因為,在儒家傳統社會中,如果根本缺乏市場經濟秩序,現代民主難以得到生長、發育,那么,即便儒家思想傳統中蘊涵著某種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資源要素,這些資源要素也失去了發揮作用的制度條件和作用對象。
不過,除了市場經濟以外,儒家傳統有可能支援現代民主所需要的另一制度環境是法治框架。這不僅因為構成現代民主基礎的市場經濟本身是法
治之下的經濟,更重要的是,現代民主是(憲)法(主)治之下的民主,亦即憲政民主。憲政民主意味著即使用民主方式產生的政府,其權力也要受到憲政制度的限制、約束。因為民主只解決了誰來行使公共權力的問題:由于人人行使公共權力絕無可能,現代民主對此問題所給出的回答是一套制度安排,比如大眾參與,公民投票等。然而,不論誰來行使公共權力,都有一個如何限制公共權力的問題,而憲政恰恰是在(憲)法(主)治之下,通過建立政府權力的內部制衡結構和外部約束邊界而形成的一套限制權力的制度安排。在此意義上,法治、憲政框架本身就是現代民主的制度前提。因而,正如不能離開市場經濟來分析儒家傳統與現代民主的關系一樣,同樣也不能離開法治、憲政這些制度環境來討論儒家傳統如何成為支援、輔助現代民主運作的文化資源。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儒家傳統要成為支援現代民主的一種可資利用的文化資源,必須首先確立一個基本的制度環境,這就是市場經濟秩序、法治憲政框架。因而,不能把儒家傳統與現代民主進行直接對接,而需要通過四點一線———儒家傳統、市場經濟、法治憲政、現代民主來發揮儒家傳統對現代民主運作的支援、輔助功能。換言之,也只有在市場經濟、法治憲政的制度環境之下,才談得上儒家傳統中的有利于民主的因素如何取代其非民主的成分以及如何成為一種有利于現代民主的文化資源的問題。③
儒家傳統與人權
一“人權”概念之發展及其意涵
“人權”(humanrights)的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產物,這已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但未發展出“人權”的概念,連“權利”的概念都付諸闕如,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人權”與“權利”這兩個詞匯都是中國人在近代與西方接觸后,透過翻譯而引進的。過去流行一種說法,認為:中國文化以義務為本位,西方文化則以權利為本位;這種說法似乎為一般人、甚至不少學者所接受。但是這種說法大有商榷的余地,因為它把問題過分簡化了。這種說法之不當,可由以下的事實看出來:直到中世紀結束,在西方的主要語言中并未出現明確地表示現代“權利”概念的字眼。梁漱溟也曾強調中西文化之對比:“在中國彌天漫地是義務觀念者,在西洋世界上卻活躍著權利觀念了。”但是他同時指出:西方文化的這種特色是近代的產物,其形成是由于對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的反動。
“權利”的概念尚且如此,“人權”的概念就出現得更晚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學者大致同意:“人權”的概念是西方啟蒙運動的產物。有關“人權”的第一份正式文獻是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國民議會于1789年公布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這份《宣言》不但正式采用了“人權”這個字眼,而且也對“人權”概念作了全面而有系統的闡述,對“人權”概念的發展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945年聯合國成立之后,鑒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發生的種種嚴重違反人權的暴行,“人權”概念進一步被提升到國際政治的層面,成為普遍的要求。在《聯合國憲章》里,人權成為一項重要的原則。《憲章》的前言便強調“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其第一條規定聯合國之宗旨,而在第三款要求各會員國“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并激勵對于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但是《聯合國憲章》對人權的內容并未作具體的規定,這方面的規定見于聯合國于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份《宣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東西冷戰剛開始的歷史背景下擬定的,故仍不免帶有西方意識形態的痕跡。不過,大體而言,這份《宣言》不但大大地擴展了以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為代表的十八世紀人權觀,也試圖將世界各大宗教與文化傳統的價值觀融合于其中。事實上,當時中華民國代表張彭春也叁與了此一《宣言》的草擬過程,并且將儒家的價值觀融入其中。例如,《宣言》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其中,“良心”(conscience)一詞便是基于張彭春的建議,為了反映儒家的價值觀而加入。因此,有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領袖與學者批評《世界人權宣言》,認為它僅代表西方的價值觀,恐非持平之論。
隨后,聯合國以公約與宣言的形式進一步落實《世界人權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1966年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1986年通過的《發展權宣言》。這三種公約和宣言基本上反映了“三代人權”之說。此說最初由法國法學家瓦薩克(KarelVasak)所提出,以后廣為學者所采用。瓦薩克將“人權”概念的發展區分為三代:第一代人權涉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第二代人權涉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第三代人權則涉及所謂的“連屬權”(solidarityright)。他將這三代“人權”概念分別對應于法國大革命時所提出來的“自由”、“平等”、“手足之情”(通常不恰當地譯為“博愛”)三個口號。大體而言,第一代人權著重于在形式上(法律上)保障個人自由,反映的是十七、十八世紀的個人自由主義思想;第二代人權著重于在實質上為個人自由之實現提供基本的社會與經濟條件,反映的是十九世紀開始勃興的社會主義思想;第三代人權則著重于集體人權,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第三世界國家對于全球資源重新分配的要求,它包括自決權、發展權、和平權,以及對資源共享、健康、生態平衡、災害救濟等的權利。因此,也有學者將這三代的人權分別稱為“第一世界的人權”、“第二世界的人權”與“第三世界的人權”。經過這三代的發展,“人權”概念的內涵可說包羅萬象,遠非十八世紀西方的人權論者所能想像。
自由主義與儒家傳統論文
百年中國的行憲歷程自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始。清人不堪擔當舊邦維新的重任,示國人以行憲之騙局。辛亥志士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啟傾覆帝制之政局。孫中山先生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學說,并以臨時約法初建中華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雖除,皇權與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張勛復辟、曹錕賄選憲法等畢現行憲之艱難。內憂頻仍之際,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經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之后,中華民族仍無化干戈為玉帛、和平民主建國的智慧,而兄弟鬩墻,遂使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不具全民共識之基礎。中共建國之后,33年中四易憲法。自八二憲法以來則三次修憲,以適應風雷激蕩之變局。
觀察與反思百年憲政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經驗:
(一)古今中西的文化問題關系到憲政問題的解決。中西文化問題方案主要有中體西用論,如張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全盤西化論,如胡適等;以及綜合創新論,如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及張岱年等。中華文化之中,政治問題與文化問題本不分為兩片,而天人關系、群己關系、身心關系綜括為內圣外王關系。內圣外王關系即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政治與宗教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等關系的綜會。內圣外王問題可統領以下的政治宗教關系、國家社會關系、上中下社會結構問題,乃至革命改良關系問題。這一問題乃是中國新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至今仍未最后解決。
(二)政治與宗教的關系為憲政問題的一大關鍵。憲政問題之中有兩重關系:第一重關系是國家與社會之關系。這之中存在著權利(包括財產權、基本人權和人民主權)與權力(憲政的要義是分權制衡與法治)之對立、互動和平衡。第二重關系是政治與宗教之關系。百年中國有三大主流意識形態: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皆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的思想、信仰與實踐的統一,但中國的新道統、學統、政統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此中值得重視的是中共的公民宗教,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黨倫理:三民主義與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公民社會的建設乃是憲政建設的基礎,亦是中國憲政問題的最大難題。憲政建設的核心:公民權利與國家公共權力的恰當安排實就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適當調整。憲政有三個觀念:人道政府(關心公民的權利:財產權和人權)、有限政府(關切國家公共權力:通過主權和分權制衡的原理既授予權力又限制、約束權力,以達致權力的正當行使)、法治政府(法治:權利與權力資源的恰當乃至最優化配置)。而這三個觀念都需要公民社會的支持。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宗法社會到政黨社會三個時期。國民黨和中共建立的政黨倫理成功整合與轉化了傳統政治的思想資源和制度資源,把中國社會從宗法社會轉變為政黨社會。而中國社會轉型的真正成功在于從政黨倫理到契約倫理,從政黨社會到公民社會的轉變。
(四)重視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關系,以及中層結構的建設。國民黨建立了中國的上層結構,中共建立了中國的下層結構。新的變革任務是建立和優化溝通上下結構的中層結構,進而建立現代中國社會的整體結構[1]。而憲政制度恰是中層結構的核心部分。憲政法治是現代國家的通行治理方式。
儒家傳統美學思想在現代社會的作用
儒家美學思想是中國美學思想的代表之一,同道家美學、楚騷美學和禪宗美學構成中國美學史上的四大思潮,儒家提出的的“美善統一”、“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怡情之美”等觀點是中國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時代變遷,在現代社會,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王權政治土崩瓦解,中國走向市場經濟,開始強調社會公平和對人權的保護,此時傳統儒家美學思想所依附的經濟政治背景產生變化,儒家傳統美學思想勢必會同這種轉型的現代社會在某些方面產生碰撞,比如儒家美學過于強調藝術的社會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個體主觀情感的訴求,這與注重個體情感表達和滿足的現代社會有些格格不入。兩者之間的碰撞衍生新質,也相當于儒家傳統美學思想在現代社會的“返本開新”,而這種衍生的新質正是我國社會轉型期開創中國特色設計所需要的理論指導,值得探究。下面以儒家核心美學思想“美善統一”和“中庸之道”為例探討儒家傳統美學思想在現代社會的新質涌現。
“美善統一”是儒家核心的美學思想,整個美學思想體系都基本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論語•八佾》記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這是由于兩者雖都是優美的樂律,但《韶》樂表現堯舜禪讓之事,表達的是仁義禮智的理想,孔子評論其盡善盡美;而《武》樂表現戰爭,不符合道德要求,所以孔子評其盡美而未盡善。其中“美”是指外在形式,“善”是指內容,在最根本意義上是指高尚的道德品格。由此可見,孔子主張的盡善盡美,是表現形式和通過形式所傳達的高尚道德能夠統一,才是美的最高境界。但孔子的美學思想受其恢復周禮的最終目的的制約,有明顯的保守色彩,過多的強調藝術的社會功能,“善”所傳達的內容規定了刻板的社會的道德美,將個體情感賦予了太多社會性的意義和使命感,最終是為了維護王權統治。而在現代社會人權的解放的大背景下,“善”衍生了新質,更強調在道德和法律容許的范圍內個體情感的充分表達,不受刻板的社會道德美的限制,不會因為作品表現的內容是社會陰暗面而否定他的價值。同原來相比,現代的“美善統一”的善更多是指表達的內容通過貼切的表達形式帶給人愉悅、啟發、警醒等對人類和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有益的作用。因此,與現代設計相結合,將“美”和“善”作為獨立的兩方面來看:“美”,現代社會各設計流派雜糅,風格萬千,不同的表現形式難以評定好與壞;而“善”,提供的服務、營造的生活方式和環境友好的指向性很強,就是有益于人和社會的生存與發展,不再追求藝術的社會功能而是人類發展的更高層次,而這正是設計美學的真正價值。所以就現代設計藝術層面而言,從人和環境出發的“善”是“美”的前提和基礎,而“盡‘善'盡美”也對設計的流程,消耗的資源,所用材料和工藝,人機交互和情感表達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善統一”是孔子提出的美學的基本原則,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美學批評的尺度——“中庸”。“中庸”以“過猶不及”為準則,強調情感的適度表達。孔子曾贊美《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認為藝術的情感表達如果超過適度,歡樂的情感就變成放肆的享樂,悲哀的情感表現就成了無限的傷痛,只有情與理的和諧統一才是最理想的,才符合“中庸”的原則。儒家中庸美學思想對我國傳統藝術影響頗深,形成獨特的“中和”之美。所以我國傳統藝術基本建立在中和之美的基礎上,形成傳統藝術的特殊風格,藝術形象溫柔敦厚,追求意境的恬淡寧靜,表現方式講究委婉比喻,講求含蓄美。“中庸”之美之所以強調在藝術創作中避免走向極端和片面性,達到恰當而不“過”,力求溫柔敦厚之美,是因為儒家認為欣賞者在喜、怒、哀、樂任一種情緒上產生“過”,就會損害身心,影響社會穩定和諧。但是這種對情感表達的度的要求使情感被牢籠、禁錮在一個相對安寧和諧的形式中,這對維持王權統治下的社會穩定頗有成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適合現代社會更不適合對藝術的發展和創新。一方面,現代社會快節奏的生活使人們需要恬淡寧靜的美來中和忙碌的疲憊和壓力來放慢腳步享受生命,但并不是人人都要聽《關雎》、觀水墨畫和用竹制品,來陶冶情操克制住情緒的度才能驅走疲憊紓解壓力。很多人壓力大時愛聽搖滾樂或蹦極,瘋狂的節奏和行為超出了“中庸”之道規定的尺度,但是卻能讓人拋開重壓再次充滿前進的動力。這就意味著傳統的“中庸”之道單純講求藝術的“中和”之美和溫柔敦厚并不能適應現代社會,而是應當變換方式,追求藝術和生活的“中和”之美,藝術的表現形式和內容是活的,隨時根據生活的需要來調整,兩者達到中和才能化解不良的情緒,只有不壓抑個人情感,才真正能達到個人情感的恬淡寧靜,達到最終的和諧之美。另一方面,對藝術的發展和創新而言,一味的追求和諧安穩就沒了創造力,沒有創造力就不能返本開新,繼而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無法創造價值。這正是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中國設計缺少創造力的原因。因此,在對藝術的發展和創新方面,不能一味滿足在相對安寧和諧的形式里,要有創新精神,要打破原本的形式去探索新的方向。
上文概述了“美善統一”和“中庸之道”的美學思想在藝術層面上同現代社會相碰撞所涌現的新質,這些新質對中國發展當代美學,構建中國特色設計風格,探索前沿藝術理論都有一定程度的推進和幫助。因此,從民族的長遠發展而言,不斷總結和汲取儒家思想的智慧,轉而同發展現代美學,構建和諧社會相結合,研究儒家傳統美學思想在現代社會的新質涌現,是十分有開拓意義和重要價值的事情。
作者:范文潔 單位:華僑大學機電及自動化學院
儒家傳統初論管理論文
一中國憲政問題與內圣外王問題
風云際會的二十世紀已然成為歷史。沉思百年中國行憲史的屈辱與光榮、苦難與奮爭,當有益于未來的再造與復興、昌盛與輝煌。
百年中國的行憲歷程自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始。清人不堪擔當舊邦維新的重任,示國人以行憲之騙局。辛亥志士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啟傾覆帝制之政局。孫中山先生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學說,并以臨時約法初建中華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雖除,皇權與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張勛復辟、曹錕賄選憲法等畢現行憲之艱難。內憂頻仍之際,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經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之后,中華民族仍無化干戈為玉帛、和平民主建國的智慧,而兄弟鬩墻,遂使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不具全民共識之基礎。中共建國之后,33年中四易憲法。自八二憲法以來則三次修憲,以適應風雷激蕩之變局。
觀察與反思百年憲政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經驗:
(一)古今中西的文化問題關系到憲政問題的解決。中西文化問題方案主要有中體西用論,如張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全盤西化論,如胡適等;以及綜合創新論,如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及張岱年等。中華文化之中,政治問題與文化問題本不分為兩片,而天人關系、群己關系、身心關系綜括為內圣外王關系。內圣外王關系即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政治與宗教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等關系的綜會。內圣外王問題可統領以下的政治宗教關系、國家社會關系、上中下社會結構問題,乃至革命改良關系問題。這一問題乃是中國新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至今仍未最后解決。
(二)政治與宗教的關系為憲政問題的一大關鍵。憲政問題之中有兩重關系:第一重關系是國家與社會之關系。這之中存在著權利(包括財產權、基本人權和人民主權)與權力(憲政的要義是分權制衡與法治)之對立、互動和平衡。第二重關系是政治與宗教之關系。百年中國有三大主流意識形態: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皆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的思想、信仰與實踐的統一,但中國的新道統、學統、政統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此中值得重視的是中共的公民宗教,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黨倫理:三民主義與思想鄧小平理論。
自由主義與儒家傳統分析論文
一中國憲政問題與內圣外王問題
風云際會的二十世紀已然成為歷史。沉思百年中國行憲史的屈辱與光榮、苦難與奮爭,當有益于未來的再造與復興、昌盛與輝煌。
百年中國的行憲歷程自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始。清人不堪擔當舊邦維新的重任,示國人以行憲之騙局。辛亥志士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啟傾覆帝制之政局。孫中山先生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學說,并以臨時約法初建中華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雖除,皇權與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張勛復辟、曹錕賄選憲法等畢現行憲之艱難。內憂頻仍之際,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經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之后,中華民族仍無化干戈為玉帛、和平民主建國的智慧,而兄弟鬩墻,遂使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不具全民共識之基礎。中共建國之后,33年中四易憲法。自八二憲法以來則三次修憲,以適應風雷激蕩之變局。
觀察與反思百年憲政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經驗:
(一)古今中西的文化問題關系到憲政問題的解決。中西文化問題方案主要有中體西用論,如張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全盤西化論,如胡適等;以及綜合創新論,如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及張岱年等。中華文化之中,政治問題與文化問題本不分為兩片,而天人關系、群己關系、身心關系綜括為內圣外王關系。內圣外王關系即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政治與宗教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等關系的綜會。內圣外王問題可統領以下的政治宗教關系、國家社會關系、上中下社會結構問題,乃至革命改良關系問題。這一問題乃是中國新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至今仍未最后解決。
(二)政治與宗教的關系為憲政問題的一大關鍵。憲政問題之中有兩重關系:第一重關系是國家與社會之關系。這之中存在著權利(包括財產權、基本人權和人民主權)與權力(憲政的要義是分權制衡與法治)之對立、互動和平衡。第二重關系是政治與宗教之關系。百年中國有三大主流意識形態: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皆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的思想、信仰與實踐的統一,但中國的新道統、學統、政統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此中值得重視的是中共的公民宗教,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黨倫理:三民主義與思想鄧小平理論。
試探荀子對儒家傳統思想的超越性
摘要:荀子秉承儒家的傳統,講求禮義教化。在性惡論的基礎上,荀子主張“禮法并用”,同時吸收了“術”、“勢”思想以完善其“內圣外王”的思想體系。他把孔孟所追求的宗教性道德敬畏修正為對外在的禮法規范的敬畏,把內在的道德追求發展為外在的客觀規范約束。
關鍵詞:荀子/儒家/人性/法
西周末年,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度漸趨崩潰,原有的社會秩序遭到根本性破壞。以恢復舊秩序為己任的思想家孔子清醒地認識到,宗法制度之所以得不到遵守,就是因為以祖先祭祀為表現形式的原始宗族崇拜為人們日益覺醒的主體意識所代替,人們不再是自然的盲從,而是根據獲得現實利益的需求肆意踐踏著約束不同等級身份者的禮。要把人們重新引導進禮的規范,就要讓社會成員在心理上樹立一種敬畏意識,從而使其在內在的約束下自愿自覺地遵守客觀外在的社會規范———禮。在歷史上,他第一次根據社會主體的情感提出“仁”的哲學思想體系。他企圖通過啟發人的自然的血緣情感,建立起人的道德文化心理,從而使“孝悌”、“仁義”等范疇成為人們的宗教性道德追求。孔子所創立的“仁”的哲學思想體系也就成為他所創立的儒家學派的思想基礎,由于這種思想體系所追求的目標是使人建立起道德文化心理,因此,重視道德情感、道德心理、道德評價,強調道德教育、人治也就成為儒家的基本傳統,成為先秦儒家區別其他各家的基本標志之一。
身處戰國后期的荀子,秉承儒家的傳統,講“修身”,講禮義教化。他在《君道》中說;“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荀子·君道》)他強調君子在治國中的作用。“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有治人,無治法。”(《荀子·君道》)完全是儒家本色。但荀子畢竟是生活在戰國后期,其時七國均通過變法初步建立了君主專制制度,且兼并戰爭已接近最后的決戰時刻。荀子兩次游學于齊,在稷下講學時曾看到前期法家的著作,尤其是他打破儒者西行不到秦的傳統,親見秦“威強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的“治之至”(《荀子·強國》)的法治局面,認識到像孟子那樣只空洞地從理論上論述儒家“德治”、“仁政”的思想,已不能使人們通過道德追求建立新的秩序,道德的自我約束已在諸侯爭雄逐霸的殘酷現實面前敗下陣來。荀子在為已建立起來的諸侯政權富國強兵獻計獻策的同時,在主體之外尋找價值根源,把孔孟所追求的宗教性道德敬畏修正為對外在的禮法規范的敬畏,把內在的道德追求發展為外在的客觀規范約束,只不過他還沒有像后來韓非那樣只信賴外在法的強制,而不關注行為者的內心情感和道德評價。
一、禮法根源的重構
荀子從商鞅的“民性有欲”(《商君書·算地》)以及民趨名利的思想得到啟示,提出了與孟子相反的人性理論———性惡論。他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仁義文理亡焉。”(《荀子·性惡》)荀子所謂“性”乃“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荀子·性惡》)。“生而有”、“天之就”的“不可學,不可事”之性,顯指人生而有之本能。
語文儒家傳統管理論文
一中國憲政問題與內圣外王問題
風云際會的二十世紀已然成為歷史。沉思百年中國行憲史的屈辱與光榮、苦難與奮爭,當有益于未來的再造與復興、昌盛與輝煌。
百年中國的行憲歷程自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始。清人不堪擔當舊邦維新的重任,示國人以行憲之騙局。辛亥志士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啟傾覆帝制之政局。孫中山先生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學說,并以臨時約法初建中華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雖除,皇權與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張勛復辟、曹錕賄選憲法等畢現行憲之艱難。內憂頻仍之際,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經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之后,中華民族仍無化干戈為玉帛、和平民主建國的智慧,而兄弟鬩墻,遂使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不具全民共識之基礎。中共建國之后,33年中四易憲法。自八二憲法以來則三次修憲,以適應風雷激蕩之變局。
觀察與反思百年憲政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經驗:
(一)古今中西的文化問題關系到憲政問題的解決。中西文化問題方案主要有中體西用論,如張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全盤西化論,如胡適等;以及綜合創新論,如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及張岱年等。中華文化之中,政治問題與文化問題本不分為兩片,而天人關系、群己關系、身心關系綜括為內圣外王關系。內圣外王關系即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政治與宗教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等關系的綜會。內圣外王問題可統領以下的政治宗教關系、國家社會關系、上中下社會結構問題,乃至革命改良關系問題。這一問題乃是中國新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至今仍未最后解決。
(二)政治與宗教的關系為憲政問題的一大關鍵。憲政問題之中有兩重關系:第一重關系是國家與社會之關系。這之中存在著權利(包括財產權、基本人權和人民主權)與權力(憲政的要義是分權制衡與法治)之對立、互動和平衡。第二重關系是政治與宗教之關系。百年中國有三大主流意識形態: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皆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的思想、信仰與實踐的統一,但中國的新道統、學統、政統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此中值得重視的是中共的公民宗教,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黨倫理:三民主義與思想鄧小平理論。
語文道統政統管理論文
上世紀90年代初,余英時教授發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系統而尖銳地批評當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其中特別是關涉到熊、牟以”心性”論”道統”的講法。該文頗受關注。遺憾的是,在有關的討論與爭論中,無論是余文的支持者還是反駁者,差不多都是在前者所設定的圈內鉆來鉆去,基本上無助于問題的明晰與深化。
事實上,如果我們超越了當代儒學發展中師承與門派之間的種種糾葛與限制,那么更深一層的問題似乎就不在于熊、牟一系如何講,而在于他們為甚么要這樣講。余先生的著眼點主要在于哲學(熊、牟)與史學(錢穆)兩種進路的分判,似乎沒有關注到后一層面的問題。近讀鄭家棟教授新著《斷裂中的傳統--信念與理性之間》,方知曉從儒家傳統的”斷續之間”來看,熊、牟有關儒家”道統”的講法,實關系甚大;并由此也在內在脈絡和理路上,對于80年代以來眾說紛紜的儒家傳統”斷續之間”的問題,了然于心。
”斷裂中的傳統”之所謂”斷裂中”,似可以理解為”斷續之間”。而”斷續之間”事關重大,也極為復雜。今日與傳統相關的諸種討論、爭論、研究等等,可以說莫不與”斷續之間”的問題有關。而對于鄭著來說,”斷續之間”并不是一個判斷或結論,而是展開為極其復雜的思想脈絡與學理系統,其中不僅關涉到思想、歷史、社會等不同層面的解析與學術史意義上嚴謹而精微的考辨,而且亦關涉到思想家個人的稟性、才情、學識、經歷等諸種因素的探討,關涉到必然的與偶然的、主流的與枝節的及思想與歷史、政治與學術之間的相互影響、制約與限定。
鄭著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儒家還活著,活在思想而非歷史中。”此一論斷有一前提,即認為”知行合一”的儒家傳統較之任何思想與文化形態都更完整的體現了”思想與歷史之間的統一”:”在儒家傳統中,思想與歷史是統一在一起的,思想應當能夠在歷史的具體性中體現出來,實現出來,脫離歷史的思想會被認為是抽象的,不真實的。”1所謂思想”在歷史的具體性中體現出來,實現出來”,即表現為社會法規、制度與禮俗,表現為社會的”文制”方面。”儒教中國”或”儒家中國”一類概念,即是著眼于”思想”與”歷史”(社會)之間的統一性。那么在現代社會中情況又如何呢?”儒教中國”是連續的還是斷裂的?這在經驗的層面可以說是一個無從回答的問題,因為不同的說法同樣可以得到論證。而鄭著所要處理的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就儒學自身發展的義理結構及其演化,表現當代儒家如何處理”思想”與”歷史”之間的關系,這其中發生了怎樣的改變,此種改變又具有怎樣的意義?
書中用相當大的篇幅疏理和論析后”五四”時期的”道統”觀念,此大有深意。二十世紀以來,講”道統”的一個基本趨向就是”泛化”。到了90年代,余英時肯定錢穆先生所主張的以”整個文化大傳統”為道統,反駁余氏而衛護熊、牟一系者(如牟氏弟子李明輝等),居然亦論辯后者同樣是以”整個文化大傳統”為道統。顯然,到了這里,所謂”道統”已經”泛化”得沒了邊際,而且此”泛化”是作為某種理想的狀態被肯定。而實際上,道統觀念的”泛化”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現當代儒家的茫無歸著和游離不定。
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當然不是以”整個文化大傳統”為道統,至少牟宗三不是如此。如余英時先生言,熊、牟等是”以對’心性’的理解和體證來判斷歷史上的儒者是否見得’道體’”。這里我們不討論熊、牟以”心性”論”道統”與宋儒以”傳心之法”論”道統”的區別,此區別或許并不重要,問題在于牟宗三等以”心性”論”道統”的意義何在?
道統與政統研究論文
上世紀90年代初,余英時教授發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系統而尖銳地批評當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其中特別是關涉到熊、牟以”心性”論”道統”的講法。該文頗受關注。遺憾的是,在有關的討論與爭論中,無論是余文的支持者還是反駁者,差不多都是在前者所設定的圈內鉆來鉆去,基本上無助于問題的明晰與深化。
事實上,如果我們超越了當代儒學發展中師承與門派之間的種種糾葛與限制,那么更深一層的問題似乎就不在于熊、牟一系如何講,而在于他們為甚么要這樣講。余先生的著眼點主要在于哲學(熊、牟)與史學(錢穆)兩種進路的分判,似乎沒有關注到后一層面的問題。近讀鄭家棟教授新著《斷裂中的傳統--信念與理性之間》,方知曉從儒家傳統的”斷續之間”來看,熊、牟有關儒家”道統”的講法,實關系甚大;并由此也在內在脈絡和理路上,對于80年代以來眾說紛紜的儒家傳統”斷續之間”的問題,了然于心。
”斷裂中的傳統”之所謂”斷裂中”,似可以理解為”斷續之間”。而”斷續之間”事關重大,也極為復雜。今日與傳統相關的諸種討論、爭論、研究等等,可以說莫不與”斷續之間”的問題有關。而對于鄭著來說,”斷續之間”并不是一個判斷或結論,而是展開為極其復雜的思想脈絡與學理系統,其中不僅關涉到思想、歷史、社會等不同層面的解析與學術史意義上嚴謹而精微的考辨,而且亦關涉到思想家個人的稟性、才情、學識、經歷等諸種因素的探討,關涉到必然的與偶然的、主流的與枝節的及思想與歷史、政治與學術之間的相互影響、制約與限定。
鄭著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儒家還活著,活在思想而非歷史中。”此一論斷有一前提,即認為”知行合一”的儒家傳統較之任何思想與文化形態都更完整的體現了”思想與歷史之間的統一”:”在儒家傳統中,思想與歷史是統一在一起的,思想應當能夠在歷史的具體性中體現出來,實現出來,脫離歷史的思想會被認為是抽象的,不真實的。”1所謂思想”在歷史的具體性中體現出來,實現出來”,即表現為社會法規、制度與禮俗,表現為社會的”文制”方面。”儒教中國”或”儒家中國”一類概念,即是著眼于”思想”與”歷史”(社會)之間的統一性。那么在現代社會中情況又如何呢?”儒教中國”是連續的還是斷裂的?這在經驗的層面可以說是一個無從回答的問題,因為不同的說法同樣可以得到論證。而鄭著所要處理的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就儒學自身發展的義理結構及其演化,表現當代儒家如何處理”思想”與”歷史”之間的關系,這其中發生了怎樣的改變,此種改變又具有怎樣的意義?
書中用相當大的篇幅疏理和論析后”五四”時期的”道統”觀念,此大有深意。二十世紀以來,講”道統”的一個基本趨向就是”泛化”。到了90年代,余英時肯定錢穆先生所主張的以”整個文化大傳統”為道統,反駁余氏而衛護熊、牟一系者(如牟氏弟子李明輝等),居然亦論辯后者同樣是以”整個文化大傳統”為道統。顯然,到了這里,所謂”道統”已經”泛化”得沒了邊際,而且此”泛化”是作為某種理想的狀態被肯定。而實際上,道統觀念的”泛化”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現當代儒家的茫無歸著和游離不定。
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當然不是以”整個文化大傳統”為道統,至少牟宗三不是如此。如余英時先生言,熊、牟等是”以對’心性’的理解和體證來判斷歷史上的儒者是否見得’道體’”。這里我們不討論熊、牟以”心性”論”道統”與宋儒以”傳心之法”論”道統”的區別,此區別或許并不重要,問題在于牟宗三等以”心性”論”道統”的意義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