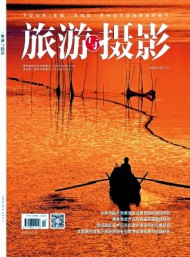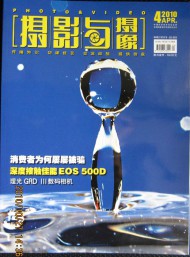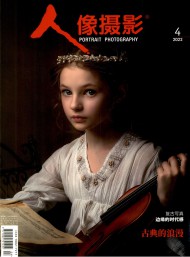攝影機范文10篇
時間:2024-03-14 03:01:43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攝影機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電影攝影機前后分析論文
打從近代婦女運動開始以來,美國女性主義者一直在文學、繪畫、電影及電視等藝術領域中,探索女性性欲的再現。隨著我們努力朝向更具意義的理論方向前進,必須注意的是,在做為一種新的閱讀文本的方法上,女性主義批評是從日常生活的課題中發(fā)源而來的──女性重新評估她們被社會化且受教育的文化。從這個角度,女性主義評論與早期從主導理論發(fā)展出來的批評運動(即在知性層面上所發(fā)生的反應)有幾個基本的不同。女性主義之所以不尋常,在于它綜合了理論(廣泛地說)和意識型態(tài)兩個部分(馬克思的文學理論也有類似的雙重重點,但是前提非常不同)。
第一波女性主義理論者廣泛地使用社會學方法來觀察女性在不同虛構的作品中,如從高級藝術到大眾娛樂中的性別角色。她們依據一些外在原則,用「正面/好」(positive)或「負面/壞」(negative)來形容完全自主、獨立的女人。當然這種方法對初期女性主義理論相當重要(如凱特·米麗特KateMillett的《性別政治》SexualPolitics,是破土巨著)。受到七○年代一些電影理論新趨勢的影響,女性主義電影評論首先指出它的限制。首先,因為受到符號學的影響,女性主義理論家強調藝術形式是相當重要的角色;第二,受到心理分析學的影響,她(他)們認為伊底帕斯情結(戀母情結)產生過程是藝術的核心。換句話說,她(他)們愈發(fā)注意電影中意義是如何被制造的(howmeaningisproduced),而不再只是社會學批評家們老強調的「內容」(content);并且特別重視心理分析學與電影之間的聯結。
在更深入說明法國理論家主要開發(fā)并影響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思潮前,讓我稍微說明為何我要使用心理分析學的方法來分析好萊塢電影。為什么在許多女性主義者對佛洛伊德及拉康學說采敵對排斥態(tài)度下,我仍視心理分析學是有用的工具?首先,讓我表白清楚:在整個歷史或不同文化范疇中,我并不認為心理分析足以揭露人類心靈本質上的「真相」。在歷史的范疇中,去類別化人類心理產生的過程是困難的,原因是要去類別化的工具/方法幾乎不存在。然而,在西方文明中的文學歷史卻也令人驚異地呈現戀母情結主題的循環(huán)。我們可以說戀母情結主題是發(fā)生在特定家庭結構的時代中;而由于我關心電影這個近代藝術形式及戀母情結問題的近論(從佛洛伊德以降),我要聲明心理分析運用的適當性,只存在于二十世紀工業(yè)社會組織的狀態(tài)中。
有人會辯稱資本主義社會以及人際關系結構(尤指自十九世紀末延續(xù)到二十世紀的形式)所產生的心理模式,當然需要一個機器(電影)來釋放人們的潛意識,也需要一個分析工具(即心理分析學)來了解、調適這些因結構限制所造成的心理困擾。就此來說,這兩樣機制(電影及心理分析學)支持了現狀,但它們并非不朽/不變的形式,它們反而在歷史中被聯結起來,也就是說,它們在特殊的中產階級資本主義歷史時代中獲得生命。
如果情形是這樣的,使用心理分析學做為工具對女性來說則極端重要,因為它破解了資本主義父權制度中社會形成的秘密。如果我們同意商業(yè)電影(尤其是本書所專注的通俗劇的類型)采用的形式是在某些方式上滿足了十九世紀家庭組織(即生產戀母情結創(chuàng)痛的組織)所制造出來的欲望及需要;那么心理分析學用來檢視這些反映在電影中的需要、欲望及男性-女性配置,就變得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工具。好萊塢電影中的符號傳遞著父權制度意識型態(tài)的訊息,它們隱藏在我們的社會結構中,并使女性依特定的方式存在──這些方式則正巧反映了父權制度的需要及其潛意識。
在讓我們去接受傳襲下來對立于主體及自主的位置這個說法上,心理分析學論說可能真地壓迫了女性;但如果是這樣,就得去了解到底心理分析學是如何運作的;因此我們必須掌握這個論說的重點,并依此提出問題。首先,「凝視」必須一定是「男性的」(在語言結構、潛意識、象征系統,即所有社會架構中因襲下來的理由)嗎?我們可不可以也架構起一些東西以致于女性也擁有「凝視」?如果這是可能的,女性會不會要這個「凝視」?最后,不管是哪種情形,做為一個女性觀眾(femalespectator)的意義是什么?只要在心理分析學的學說框架中來問這個問題,我們才可以開始在男性主導并排除女人的歷史論說中插入女性的位置,并尋找其論說的空隙和罅隙(fissures)。如此,我們方可朝著改變社會來開始第一步。
攝影機前后管理論文
打從近代婦女運動開始以來,美國女性主義者一直在文學、繪畫、電影及電視等藝術領域中,探索女性性欲的再現。隨著我們努力朝向更具意義的理論方向前進,必須注意的是,在做為一種新的閱讀文本的方法上,女性主義批評是從日常生活的課題中發(fā)源而來的──女性重新評估她們被社會化且受教育的文化。從這個角度,女性主義評論與早期從主導理論發(fā)展出來的批評運動(即在知性層面上所發(fā)生的反應)有幾個基本的不同。女性主義之所以不尋常,在于它綜合了理論(廣泛地說)和意識型態(tài)兩個部分(馬克思的文學理論也有類似的雙重重點,但是前提非常不同)。
第一波女性主義理論者廣泛地使用社會學方法來觀察女性在不同虛構的作品中,如從高級藝術到大眾娛樂中的性別角色。她們依據一些外在原則,用「正面/好」(positive)或「負面/壞」(negative)來形容完全自主、獨立的女人。當然這種方法對初期女性主義理論相當重要(如凱特·米麗特KateMillett的《性別政治》SexualPolitics,是破土巨著)。受到七○年代一些電影理論新趨勢的影響,女性主義電影評論首先指出它的限制。首先,因為受到符號學的影響,女性主義理論家強調藝術形式是相當重要的角色;第二,受到心理分析學的影響,她(他)們認為伊底帕斯情結(戀母情結)產生過程是藝術的核心。換句話說,她(他)們愈發(fā)注意電影中意義是如何被制造的(howmeaningisproduced),而不再只是社會學批評家們老強調的「內容」(content);并且特別重視心理分析學與電影之間的聯結。
在更深入說明法國理論家主要開發(fā)并影響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思潮前,讓我稍微說明為何我要使用心理分析學的方法來分析好萊塢電影。為什么在許多女性主義者對佛洛伊德及拉康學說采敵對排斥態(tài)度下,我仍視心理分析學是有用的工具?首先,讓我表白清楚:在整個歷史或不同文化范疇中,我并不認為心理分析足以揭露人類心靈本質上的「真相」。在歷史的范疇中,去類別化人類心理產生的過程是困難的,原因是要去類別化的工具/方法幾乎不存在。然而,在西方文明中的文學歷史卻也令人驚異地呈現戀母情結主題的循環(huán)。我們可以說戀母情結主題是發(fā)生在特定家庭結構的時代中;而由于我關心電影這個近代藝術形式及戀母情結問題的近論(從佛洛伊德以降),我要聲明心理分析運用的適當性,只存在于二十世紀工業(yè)社會組織的狀態(tài)中。
有人會辯稱資本主義社會以及人際關系結構(尤指自十九世紀末延續(xù)到二十世紀的形式)所產生的心理模式,當然需要一個機器(電影)來釋放人們的潛意識,也需要一個分析工具(即心理分析學)來了解、調適這些因結構限制所造成的心理困擾。就此來說,這兩樣機制(電影及心理分析學)支持了現狀,但它們并非不朽/不變的形式,它們反而在歷史中被聯結起來,也就是說,它們在特殊的中產階級資本主義歷史時代中獲得生命。
如果情形是這樣的,使用心理分析學做為工具對女性來說則極端重要,因為它破解了資本主義父權制度中社會形成的秘密。如果我們同意商業(yè)電影(尤其是本書所專注的通俗劇的類型)采用的形式是在某些方式上滿足了十九世紀家庭組織(即生產戀母情結創(chuàng)痛的組織)所制造出來的欲望及需要;那么心理分析學用來檢視這些反映在電影中的需要、欲望及男性-女性配置,就變得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工具。好萊塢電影中的符號傳遞著父權制度意識型態(tài)的訊息,它們隱藏在我們的社會結構中,并使女性依特定的方式存在──這些方式則正巧反映了父權制度的需要及其潛意識。
在讓我們去接受傳襲下來對立于主體及自主的位置這個說法上,心理分析學論說可能真地壓迫了女性;但如果是這樣,就得去了解到底心理分析學是如何運作的;因此我們必須掌握這個論說的重點,并依此提出問題。首先,「凝視」必須一定是「男性的」(在語言結構、潛意識、象征系統,即所有社會架構中因襲下來的理由)嗎?我們可不可以也架構起一些東西以致于女性也擁有「凝視」?如果這是可能的,女性會不會要這個「凝視」?最后,不管是哪種情形,做為一個女性觀眾(femalespectator)的意義是什么?只要在心理分析學的學說框架中來問這個問題,我們才可以開始在男性主導并排除女人的歷史論說中插入女性的位置,并尋找其論說的空隙和罅隙(fissures)。如此,我們方可朝著改變社會來開始第一步。
電影空間構筑管理論文
[內容提要]楊德昌電影總是力圖還原人類真實的生存環(huán)境。在客觀冷靜的長鏡頭的統率之下,結合攝影機的運動和不完整的畫面構圖,使得楊德昌電影中的空間呈現出完整統一、流動開放的特點。
[關鍵詞]空間長鏡頭移動攝影“框架構圖”
楊德昌是臺灣新電影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憑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國戛納電影節(jié)的最佳導演獎。如果說臺灣新電影導演們存在著某種共性的話,那就是他們都立志成為“電影作者”。以法國“作者論”的立場而言,只有擁有一貫的特定風格的導演,才能躋身“電影作者”的行列。楊德昌電影便存在著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記,這在其影片的空間處理方面表現得極為突出。從早期的《青梅竹馬》、《恐怖分子》開始,楊德昌已經確立了其表達空間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這些手法更加純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麻將》、《一一》等作品為例,試從鏡頭、攝影以及構圖三個方面解析楊德昌電影中空間的構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論家卡紐德視電影為獨立于舞蹈、詩、音樂、建筑、雕刻、繪畫之外的“第七藝術”,并指出電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種藝術統合歸一”[1](P.791)。卡紐德認為藝術向來循著時間的或空間的、韻律的或造型的、動的或不動的幾種途徑獨立發(fā)展,唯獨電影能將各種藝術的特點集于一身。也就是說,電影是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的統一。這種“統合論”旨在強調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分割性,無關二者的主次之分。對于電影敘事是時間還是空間占據支配地位的問題,理論界一直存在著爭論。法國理論家馬賽爾•馬爾丹篤信空間依附于時間,理由是電影本身有一定的時間長度,卻不占據實際的空間。但隨著電影藝術自身的發(fā)展,特別是藝術電影在敘事上大膽顛覆常規(guī)電影之后,這個觀點引起越來越多的質疑。藝術電影便經常刻意模糊時間的觀念,也不求展現合邏輯的時間關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規(guī)電影,其時間的變化和延續(xù)最終仍依賴于空間表現出來。究其所以,這與電影首先是一種視覺藝術有很大的關系。基于此,喬治·布魯斯東在比較小說與電影的異同時明確指出:“電影的結構原則是空間……電影采取假定的時間,通過空間的安排來形成它的敘述”;[2](P.216)并得出“在電影中空間是首要的”[2](P.217)這一結論。
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臘語言中沒有空間一詞,希臘人心目中的空間實際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離、范圍和體積。在電影中,空間可以具體為故事得以發(fā)生發(fā)展的場所。馬爾丹認為電影在處理空間時有兩種方式:再現空間和構成空間。[3](P.170)這兩種方式實際上對應著長鏡頭與蒙太奇兩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與長鏡頭往往是并存的,因為它們都是電影必不可少的技術手段。但從美學意義上講,兩者的對峙是顯而易見的。蒙太奇重主觀表現,長鏡頭重客觀再現。按照蘇聯蒙太奇學派的觀點,蒙太奇是指把被攝對象分割成一個個鏡頭,再依照創(chuàng)作者的觀念重新組合以產生新的意義,借此表達創(chuàng)作者對該對象的態(tài)度和看法。長鏡頭美學的倡導者——安德烈•巴贊則認為電影是完整的寫實主義的神話,是再現世界原貌的神話。[4](P.21)巴贊反對以創(chuàng)作者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長鏡頭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處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現在一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中就足夠了”。[4](P.61)這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不動聲色地隱藏藝術家的觀點,讓影像成為“十足的現實”。同時,它還能實現蒙太奇用若干個鏡頭完成的景別、節(jié)奏等各種轉換。這正是巴贊從德•西卡、奧森•威爾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見,有一定長度的長鏡頭是一個可以涵蓋所有鏡頭類型的完整的鏡頭語言系統,其核心正是備受巴贊推崇的段落鏡頭和景深鏡頭。
電影攝影藝術管理論文
[摘要]好萊塢電影自誕生時刻開始,就特別重視電影攝影藝術和技術。在好萊塢,電影攝影師是光的藝術家,他們是在用光代替畫筆在電影膠片上進行作畫的畫家,與畫家不同的是電影攝影師的作品,不是展覽在美術館和畫廊內的大眾可以觀看欣賞的畫作,而是制作在電影膠卷上的負片,到洗印車間沖洗后印制出可以放映的正片。在好萊塢,電影攝影師的地位很高,人們更喜歡稱他為“攝影導演”,他同導演一樣是一部電影作品的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創(chuàng)作者。
[關鍵詞]好萊塢電影攝影藝術格里菲斯光學鏡頭
電影攝影(cinematography)一詞由兩個詞即cinema電影和photography攝影結合而成。電影,cinema這個第七藝術,從其誕生的時刻。就和她的姐妹攝影藝術photography有著親密無間的關系。電影離不開攝影藝術,沒有攝影也就不會有電影。但電影攝影藝術,又不是簡單地照相。好萊塢電影自誕生時刻開始,就特別重視電影攝影藝術和技術。這就是cinematography電影攝影這個詞的內涵。
在好萊塢,所有的電影攝影師都知道,他們是光的藝術家(artistoflight)。他們是在用光(light)代替畫筆在電影膠片上進行作畫的畫家;與畫家不同的是電影攝影師的作品,不是展覽在美術館和畫廊內的大眾可以觀看欣賞的畫作,而是制作在電影膠卷上的負片,到洗印車間沖洗后印制出可以放映的正片,或在電視上播映。現在美國加州的洛杉磯電影資料館內收藏有大量的電影攝影的資料。在好萊塢,電影攝影師的地位很高,人們更喜歡稱他為“攝影導演”(directorofphotography),是以藝術家,專家級別來尊敬。他同導演一樣是一部電影作品的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創(chuàng)作者。在美國電影藝術學院,我們有機會拜訪了著名電影攝影大師,法國人阿爾蒙·德洛斯。我們問他一個天真的問題:“什么是電影攝影師?他都干一些什么事情?”這位大師笑著回答:“答案很簡單:他什么事都干,也什么都不做!他從這部影片到另外一部影片,要干的事情是不太一樣的。所以,無法給他一個十分確切的定義……我的工作有時就是簡單地按一下電影攝影機的快門;也有時,坐在上面寫有我的名字的折疊軟椅上去監(jiān)督我的助手去拍攝,動動嘴就行了……現在問題復雜了,在一些好萊塢大片中,我們需要的是一群人集體合作拍攝,有時一個鏡頭需要幾個電影攝影師通力合作完成拍攝,誰也不清楚誰到底干了什么,反正最后,一切都體現在銀幕畫面上。”
“在一些小投資低成本的電影中,有時擔當一個電影攝影師很難很苦。我就最怕同導演新手合作,我不但要去選擇使用什么樣的攝影機鏡頭,而且還要決定用什么樣的大小景框——例如遠景,中景等,還有攝影機的運動方向與部位等,有的時候還要去指導演員的活動范圍,此外還有燈光的布置……雖然作為電影攝影師,我們想要發(fā)展自己的藝術風格;但我認為最重要的如何依靠您的技術能力,在電影作品中去表現您的藝術。您一定記住,您是在幫助導演去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記住您自己的地位和作用:這樣就要求您首先要理解導演的意圖和創(chuàng)作理念。要多和他探討,要多體會,您對于導演的理解越多,就越有助于您的電影攝影工作。在拍攝電影的過程中,一般是導演指示要什么鏡頭;但我總喜歡在具體拍攝之前,要首先同導演談談自己的想法;有的時候我提出具體的視覺修改建議(visualmodificationsuggestions)。比如說要選擇什么樣的攝影鏡頭——鏡頭的口徑和具體的鏡頭框架,還有攝影的拍攝活動,乃至演員的位置和在攝影機前面活動的區(qū)域范圍等。當然,最后的決定權還是在導演那里。有一些導演不喜歡同他的合作者交談和商量。但記住他是導演,您不是……”
電影攝影師在電影拍攝和制作中的角色和地位,早在默片時期就確定下來了。一個攝影導演要親自掌握電影攝影機來進行拍攝,此外有時還要雇傭第二攝影師,他的攝影機就架設在您旁邊,他要拍攝另外一個負片,以備將來送到歐洲去洗印。電影藝術的先驅們經過自己的不懈努力,逐漸地形成電影攝影的基本的視覺語言,同時一些電影攝影的基本技術和典型特技也開始定型。比如基本的光學效果,鏡頭的形式,方位等,像淡出,淡入,色調,光調乃至一些基本的洗印剪輯等技法,大都在這個時期發(fā)明和發(fā)展了。不言而喻,當時電影攝影導演的權威地位是公認的。
電影空間構筑管理論文
[內容提要]楊德昌電影總是力圖還原人類真實的生存環(huán)境。在客觀冷靜的長鏡頭的統率之下,結合攝影機的運動和不完整的畫面構圖,使得楊德昌電影中的空間呈現出完整統一、流動開放的特點。
[關鍵詞]空間長鏡頭移動攝影“框架構圖”
楊德昌是臺灣新電影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憑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國戛納電影節(jié)的最佳導演獎。如果說臺灣新電影導演們存在著某種共性的話,那就是他們都立志成為“電影作者”。以法國“作者論”的立場而言,只有擁有一貫的特定風格的導演,才能躋身“電影作者”的行列。楊德昌電影便存在著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記,這在其影片的空間處理方面表現得極為突出。從早期的《青梅竹馬》、《恐怖分子》開始,楊德昌已經確立了其表達空間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這些手法更加純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麻將》、《一一》等作品為例,試從鏡頭、攝影以及構圖三個方面解析楊德昌電影中空間的構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論家卡紐德視電影為獨立于舞蹈、詩、音樂、建筑、雕刻、繪畫之外的“第七藝術”,并指出電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種藝術統合歸一”[1](P.791)。卡紐德認為藝術向來循著時間的或空間的、韻律的或造型的、動的或不動的幾種途徑獨立發(fā)展,唯獨電影能將各種藝術的特點集于一身。也就是說,電影是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的統一。這種“統合論”旨在強調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分割性,無關二者的主次之分。對于電影敘事是時間還是空間占據支配地位的問題,理論界一直存在著爭論。法國理論家馬賽爾•馬爾丹篤信空間依附于時間,理由是電影本身有一定的時間長度,卻不占據實際的空間。但隨著電影藝術自身的發(fā)展,特別是藝術電影在敘事上大膽顛覆常規(guī)電影之后,這個觀點引起越來越多的質疑。藝術電影便經常刻意模糊時間的觀念,也不求展現合邏輯的時間關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規(guī)電影,其時間的變化和延續(xù)最終仍依賴于空間表現出來。究其所以,這與電影首先是一種視覺藝術有很大的關系。基于此,喬治·布魯斯東在比較小說與電影的異同時明確指出:“電影的結構原則是空間……電影采取假定的時間,通過空間的安排來形成它的敘述”;[2](P.216)并得出“在電影中空間是首要的”[2](P.217)這一結論。
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臘語言中沒有空間一詞,希臘人心目中的空間實際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離、范圍和體積。在電影中,空間可以具體為故事得以發(fā)生發(fā)展的場所。馬爾丹認為電影在處理空間時有兩種方式:再現空間和構成空間。[3](P.170)這兩種方式實際上對應著長鏡頭與蒙太奇兩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與長鏡頭往往是并存的,因為它們都是電影必不可少的技術手段。但從美學意義上講,兩者的對峙是顯而易見的。蒙太奇重主觀表現,長鏡頭重客觀再現。按照蘇聯蒙太奇學派的觀點,蒙太奇是指把被攝對象分割成一個個鏡頭,再依照創(chuàng)作者的觀念重新組合以產生新的意義,借此表達創(chuàng)作者對該對象的態(tài)度和看法。長鏡頭美學的倡導者——安德烈•巴贊則認為電影是完整的寫實主義的神話,是再現世界原貌的神話。[4](P.21)巴贊反對以創(chuàng)作者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長鏡頭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處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現在一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中就足夠了”。[4](P.61)這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不動聲色地隱藏藝術家的觀點,讓影像成為“十足的現實”。同時,它還能實現蒙太奇用若干個鏡頭完成的景別、節(jié)奏等各種轉換。這正是巴贊從德•西卡、奧森•威爾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見,有一定長度的長鏡頭是一個可以涵蓋所有鏡頭類型的完整的鏡頭語言系統,其核心正是備受巴贊推崇的段落鏡頭和景深鏡頭。
楊德昌電影中空間構筑論文
[內容提要]楊德昌電影總是力圖還原人類真實的生存環(huán)境。在客觀冷靜的長鏡頭的統率之下,結合攝影機的運動和不完整的畫面構圖,使得楊德昌電影中的空間呈現出完整統一、流動開放的特點。
[關鍵詞]空間長鏡頭移動攝影“框架構圖”
楊德昌是臺灣新電影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憑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國戛納電影節(jié)的最佳導演獎。如果說臺灣新電影導演們存在著某種共性的話,那就是他們都立志成為“電影作者”。以法國“作者論”的立場而言,只有擁有一貫的特定風格的導演,才能躋身“電影作者”的行列。楊德昌電影便存在著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記,這在其影片的空間處理方面表現得極為突出。從早期的《青梅竹馬》、《恐怖分子》開始,楊德昌已經確立了其表達空間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這些手法更加純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麻將》、《一一》等作品為例,試從鏡頭、攝影以及構圖三個方面解析楊德昌電影中空間的構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論家卡紐德視電影為獨立于舞蹈、詩、音樂、建筑、雕刻、繪畫之外的“第七藝術”,并指出電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種藝術統合歸一”[1](P.791)。卡紐德認為藝術向來循著時間的或空間的、韻律的或造型的、動的或不動的幾種途徑獨立發(fā)展,唯獨電影能將各種藝術的特點集于一身。也就是說,電影是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的統一。這種“統合論”旨在強調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分割性,無關二者的主次之分。對于電影敘事是時間還是空間占據支配地位的問題,理論界一直存在著爭論。法國理論家馬賽爾•馬爾丹篤信空間依附于時間,理由是電影本身有一定的時間長度,卻不占據實際的空間。但隨著電影藝術自身的發(fā)展,特別是藝術電影在敘事上大膽顛覆常規(guī)電影之后,這個觀點引起越來越多的質疑。藝術電影便經常刻意模糊時間的觀念,也不求展現合邏輯的時間關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規(guī)電影,其時間的變化和延續(xù)最終仍依賴于空間表現出來。究其所以,這與電影首先是一種視覺藝術有很大的關系。基于此,喬治·布魯斯東在比較小說與電影的異同時明確指出:“電影的結構原則是空間……電影采取假定的時間,通過空間的安排來形成它的敘述”;[2](P.216)并得出“在電影中空間是首要的”[2](P.217)這一結論。
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臘語言中沒有空間一詞,希臘人心目中的空間實際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離、范圍和體積。在電影中,空間可以具體為故事得以發(fā)生發(fā)展的場所。馬爾丹認為電影在處理空間時有兩種方式:再現空間和構成空間。[3](P.170)這兩種方式實際上對應著長鏡頭與蒙太奇兩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與長鏡頭往往是并存的,因為它們都是電影必不可少的技術手段。但從美學意義上講,兩者的對峙是顯而易見的。蒙太奇重主觀表現,長鏡頭重客觀再現。按照蘇聯蒙太奇學派的觀點,蒙太奇是指把被攝對象分割成一個個鏡頭,再依照創(chuàng)作者的觀念重新組合以產生新的意義,借此表達創(chuàng)作者對該對象的態(tài)度和看法。長鏡頭美學的倡導者——安德烈•巴贊則認為電影是完整的寫實主義的神話,是再現世界原貌的神話。[4](P.21)巴贊反對以創(chuàng)作者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長鏡頭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處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現在一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中就足夠了”。[4](P.61)這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不動聲色地隱藏藝術家的觀點,讓影像成為“十足的現實”。同時,它還能實現蒙太奇用若干個鏡頭完成的景別、節(jié)奏等各種轉換。這正是巴贊從德•西卡、奧森•威爾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見,有一定長度的長鏡頭是一個可以涵蓋所有鏡頭類型的完整的鏡頭語言系統,其核心正是備受巴贊推崇的段落鏡頭和景深鏡頭。
楊德昌電影空間構筑論文
[內容提要]楊德昌電影總是力圖還原人類真實的生存環(huán)境。在客觀冷靜的長鏡頭的統率之下,結合攝影機的運動和不完整的畫面構圖,使得楊德昌電影中的空間呈現出完整統一、流動開放的特點。
[關鍵詞]空間長鏡頭移動攝影“框架構圖”
楊德昌是臺灣新電影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憑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國戛納電影節(jié)的最佳導演獎。如果說臺灣新電影導演們存在著某種共性的話,那就是他們都立志成為“電影作者”。以法國“作者論”的立場而言,只有擁有一貫的特定風格的導演,才能躋身“電影作者”的行列。楊德昌電影便存在著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記,這在其影片的空間處理方面表現得極為突出。從早期的《青梅竹馬》、《恐怖分子》開始,楊德昌已經確立了其表達空間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這些手法更加純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麻將》、《一一》等作品為例,試從鏡頭、攝影以及構圖三個方面解析楊德昌電影中空間的構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論家卡紐德視電影為獨立于舞蹈、詩、音樂、建筑、雕刻、繪畫之外的“第七藝術”,并指出電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種藝術統合歸一”[1](P.791)。卡紐德認為藝術向來循著時間的或空間的、韻律的或造型的、動的或不動的幾種途徑獨立發(fā)展,唯獨電影能將各種藝術的特點集于一身。也就是說,電影是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的統一。這種“統合論”旨在強調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分割性,無關二者的主次之分。對于電影敘事是時間還是空間占據支配地位的問題,理論界一直存在著爭論。法國理論家馬賽爾•馬爾丹篤信空間依附于時間,理由是電影本身有一定的時間長度,卻不占據實際的空間。但隨著電影藝術自身的發(fā)展,特別是藝術電影在敘事上大膽顛覆常規(guī)電影之后,這個觀點引起越來越多的質疑。藝術電影便經常刻意模糊時間的觀念,也不求展現合邏輯的時間關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規(guī)電影,其時間的變化和延續(xù)最終仍依賴于空間表現出來。究其所以,這與電影首先是一種視覺藝術有很大的關系。基于此,喬治·布魯斯東在比較小說與電影的異同時明確指出:“電影的結構原則是空間……電影采取假定的時間,通過空間的安排來形成它的敘述”;[2](P.216)并得出“在電影中空間是首要的”[2](P.217)這一結論。
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臘語言中沒有空間一詞,希臘人心目中的空間實際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離、范圍和體積。在電影中,空間可以具體為故事得以發(fā)生發(fā)展的場所。馬爾丹認為電影在處理空間時有兩種方式:再現空間和構成空間。[3](P.170)這兩種方式實際上對應著長鏡頭與蒙太奇兩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與長鏡頭往往是并存的,因為它們都是電影必不可少的技術手段。但從美學意義上講,兩者的對峙是顯而易見的。蒙太奇重主觀表現,長鏡頭重客觀再現。按照蘇聯蒙太奇學派的觀點,蒙太奇是指把被攝對象分割成一個個鏡頭,再依照創(chuàng)作者的觀念重新組合以產生新的意義,借此表達創(chuàng)作者對該對象的態(tài)度和看法。長鏡頭美學的倡導者——安德烈•巴贊則認為電影是完整的寫實主義的神話,是再現世界原貌的神話。[4](P.21)巴贊反對以創(chuàng)作者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長鏡頭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處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現在一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中就足夠了”。[4](P.61)這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不動聲色地隱藏藝術家的觀點,讓影像成為“十足的現實”。同時,它還能實現蒙太奇用若干個鏡頭完成的景別、節(jié)奏等各種轉換。這正是巴贊從德•西卡、奧森•威爾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見,有一定長度的長鏡頭是一個可以涵蓋所有鏡頭類型的完整的鏡頭語言系統,其核心正是備受巴贊推崇的段落鏡頭和景深鏡頭。
楊德昌電影空間構筑論文
[內容提要]楊德昌電影總是力圖還原人類真實的生存環(huán)境。在客觀冷靜的長鏡頭的統率之下,結合攝影機的運動和不完整的畫面構圖,使得楊德昌電影中的空間呈現出完整統一、流動開放的特點。
[關鍵詞]空間長鏡頭移動攝影“框架構圖”
楊德昌是臺灣新電影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憑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國戛納電影節(jié)的最佳導演獎。如果說臺灣新電影導演們存在著某種共性的話,那就是他們都立志成為“電影作者”。以法國“作者論”的立場而言,只有擁有一貫的特定風格的導演,才能躋身“電影作者”的行列。楊德昌電影便存在著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記,這在其影片的空間處理方面表現得極為突出。從早期的《青梅竹馬》、《恐怖分子》開始,楊德昌已經確立了其表達空間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這些手法更加純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麻將》、《一一》等作品為例,試從鏡頭、攝影以及構圖三個方面解析楊德昌電影中空間的構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論家卡紐德視電影為獨立于舞蹈、詩、音樂、建筑、雕刻、繪畫之外的“第七藝術”,并指出電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種藝術統合歸一”[1](P.791)。卡紐德認為藝術向來循著時間的或空間的、韻律的或造型的、動的或不動的幾種途徑獨立發(fā)展,唯獨電影能將各種藝術的特點集于一身。也就是說,電影是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的統一。這種“統合論”旨在強調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分割性,無關二者的主次之分。對于電影敘事是時間還是空間占據支配地位的問題,理論界一直存在著爭論。法國理論家馬賽爾•馬爾丹篤信空間依附于時間,理由是電影本身有一定的時間長度,卻不占據實際的空間。但隨著電影藝術自身的發(fā)展,特別是藝術電影在敘事上大膽顛覆常規(guī)電影之后,這個觀點引起越來越多的質疑。藝術電影便經常刻意模糊時間的觀念,也不求展現合邏輯的時間關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規(guī)電影,其時間的變化和延續(xù)最終仍依賴于空間表現出來。究其所以,這與電影首先是一種視覺藝術有很大的關系。基于此,喬治·布魯斯東在比較小說與電影的異同時明確指出:“電影的結構原則是空間……電影采取假定的時間,通過空間的安排來形成它的敘述”;[2](P.216)并得出“在電影中空間是首要的”[2](P.217)這一結論。
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臘語言中沒有空間一詞,希臘人心目中的空間實際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離、范圍和體積。在電影中,空間可以具體為故事得以發(fā)生發(fā)展的場所。馬爾丹認為電影在處理空間時有兩種方式:再現空間和構成空間。[3](P.170)這兩種方式實際上對應著長鏡頭與蒙太奇兩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與長鏡頭往往是并存的,因為它們都是電影必不可少的技術手段。但從美學意義上講,兩者的對峙是顯而易見的。蒙太奇重主觀表現,長鏡頭重客觀再現。按照蘇聯蒙太奇學派的觀點,蒙太奇是指把被攝對象分割成一個個鏡頭,再依照創(chuàng)作者的觀念重新組合以產生新的意義,借此表達創(chuàng)作者對該對象的態(tài)度和看法。長鏡頭美學的倡導者——安德烈•巴贊則認為電影是完整的寫實主義的神話,是再現世界原貌的神話。[4](P.21)巴贊反對以創(chuàng)作者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長鏡頭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處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現在一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中就足夠了”。[4](P.61)這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不動聲色地隱藏藝術家的觀點,讓影像成為“十足的現實”。同時,它還能實現蒙太奇用若干個鏡頭完成的景別、節(jié)奏等各種轉換。這正是巴贊從德•西卡、奧森•威爾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見,有一定長度的長鏡頭是一個可以涵蓋所有鏡頭類型的完整的鏡頭語言系統,其核心正是備受巴贊推崇的段落鏡頭和景深鏡頭。
電影空間構筑管理論文
[內容提要]楊德昌電影總是力圖還原人類真實的生存環(huán)境。在客觀冷靜的長鏡頭的統率之下,結合攝影機的運動和不完整的畫面構圖,使得楊德昌電影中的空間呈現出完整統一、流動開放的特點。
[關鍵詞]空間長鏡頭移動攝影“框架構圖”
楊德昌是臺灣新電影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憑借影片《一一》曾得到法國戛納電影節(jié)的最佳導演獎。如果說臺灣新電影導演們存在著某種共性的話,那就是他們都立志成為“電影作者”。以法國“作者論”的立場而言,只有擁有一貫的特定風格的導演,才能躋身“電影作者”的行列。楊德昌電影便存在著清晰可辨的作者印記,這在其影片的空間處理方面表現得極為突出。從早期的《青梅竹馬》、《恐怖分子》開始,楊德昌已經確立了其表達空間的基本手法。在其后的影片中,這些手法更加純熟、精巧。本文主要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麻將》、《一一》等作品為例,試從鏡頭、攝影以及構圖三個方面解析楊德昌電影中空間的構筑方式。
一
意大利理論家卡紐德視電影為獨立于舞蹈、詩、音樂、建筑、雕刻、繪畫之外的“第七藝術”,并指出電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種藝術統合歸一”[1](P.791)。卡紐德認為藝術向來循著時間的或空間的、韻律的或造型的、動的或不動的幾種途徑獨立發(fā)展,唯獨電影能將各種藝術的特點集于一身。也就是說,電影是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的統一。這種“統合論”旨在強調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分割性,無關二者的主次之分。對于電影敘事是時間還是空間占據支配地位的問題,理論界一直存在著爭論。法國理論家馬賽爾•馬爾丹篤信空間依附于時間,理由是電影本身有一定的時間長度,卻不占據實際的空間。但隨著電影藝術自身的發(fā)展,特別是藝術電影在敘事上大膽顛覆常規(guī)電影之后,這個觀點引起越來越多的質疑。藝術電影便經常刻意模糊時間的觀念,也不求展現合邏輯的時間關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規(guī)電影,其時間的變化和延續(xù)最終仍依賴于空間表現出來。究其所以,這與電影首先是一種視覺藝術有很大的關系。基于此,喬治·布魯斯東在比較小說與電影的異同時明確指出:“電影的結構原則是空間……電影采取假定的時間,通過空間的安排來形成它的敘述”;[2](P.216)并得出“在電影中空間是首要的”[2](P.217)這一結論。
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臘語言中沒有空間一詞,希臘人心目中的空間實際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離、范圍和體積。在電影中,空間可以具體為故事得以發(fā)生發(fā)展的場所。馬爾丹認為電影在處理空間時有兩種方式:再現空間和構成空間。[3](P.170)這兩種方式實際上對應著長鏡頭與蒙太奇兩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與長鏡頭往往是并存的,因為它們都是電影必不可少的技術手段。但從美學意義上講,兩者的對峙是顯而易見的。蒙太奇重主觀表現,長鏡頭重客觀再現。按照蘇聯蒙太奇學派的觀點,蒙太奇是指把被攝對象分割成一個個鏡頭,再依照創(chuàng)作者的觀念重新組合以產生新的意義,借此表達創(chuàng)作者對該對象的態(tài)度和看法。長鏡頭美學的倡導者——安德烈•巴贊則認為電影是完整的寫實主義的神話,是再現世界原貌的神話。[4](P.21)巴贊反對以創(chuàng)作者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長鏡頭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處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現在一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中就足夠了”。[4](P.61)這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不動聲色地隱藏藝術家的觀點,讓影像成為“十足的現實”。同時,它還能實現蒙太奇用若干個鏡頭完成的景別、節(jié)奏等各種轉換。這正是巴贊從德•西卡、奧森•威爾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見,有一定長度的長鏡頭是一個可以涵蓋所有鏡頭類型的完整的鏡頭語言系統,其核心正是備受巴贊推崇的段落鏡頭和景深鏡頭。
楊德昌電影研究論文
一
意大利理論家卡紐德視電影為獨立于舞蹈、詩、音樂、建筑、雕刻、繪畫之外的“第七藝術”,并指出電影的特性在于“把既有的各種藝術統合歸一”[1](P.791)。卡紐德認為藝術向來循著時間的或空間的、韻律的或造型的、動的或不動的幾種途徑獨立發(fā)展,唯獨電影能將各種藝術的特點集于一身。也就是說,電影是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的統一。這種“統合論”旨在強調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分割性,無關二者的主次之分。對于電影敘事是時間還是空間占據支配地位的問題,理論界一直存在著爭論。法國理論家馬賽爾•馬爾丹篤信空間依附于時間,理由是電影本身有一定的時間長度,卻不占據實際的空間。但隨著電影藝術自身的發(fā)展,特別是藝術電影在敘事上大膽顛覆常規(guī)電影之后,這個觀點引起越來越多的質疑。藝術電影便經常刻意模糊時間的觀念,也不求展現合邏輯的時間關系,而即便是一部常規(guī)電影,其時間的變化和延續(xù)最終仍依賴于空間表現出來。究其所以,這與電影首先是一種視覺藝術有很大的關系。基于此,喬治·布魯斯東在比較小說與電影的異同時明確指出:“電影的結構原則是空間……電影采取假定的時間,通過空間的安排來形成它的敘述”;[2](P.216)并得出“在電影中空間是首要的”[2](P.217)這一結論。
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奔格勒指出在希臘語言中沒有空間一詞,希臘人心目中的空間實際上就是事物的位置、距離、范圍和體積。在電影中,空間可以具體為故事得以發(fā)生發(fā)展的場所。馬爾丹認為電影在處理空間時有兩種方式:再現空間和構成空間。[3](P.170)這兩種方式實際上對應著長鏡頭與蒙太奇兩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方法。在影片中,蒙太奇與長鏡頭往往是并存的,因為它們都是電影必不可少的技術手段。但從美學意義上講,兩者的對峙是顯而易見的。蒙太奇重主觀表現,長鏡頭重客觀再現。按照蘇聯蒙太奇學派的觀點,蒙太奇是指把被攝對象分割成一個個鏡頭,再依照創(chuàng)作者的觀念重新組合以產生新的意義,借此表達創(chuàng)作者對該對象的態(tài)度和看法。長鏡頭美學的倡導者——安德烈•巴贊則認為電影是完整的寫實主義的神話,是再現世界原貌的神話。[4](P.21)巴贊反對以創(chuàng)作者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蒙太奇,提出以長鏡頭代替蒙太奇:“只要把被蒙太奇分散處理的各元素集中表現在一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中就足夠了”。[4](P.61)這個“選擇恰當的鏡頭”,不動聲色地隱藏藝術家的觀點,讓影像成為“十足的現實”。同時,它還能實現蒙太奇用若干個鏡頭完成的景別、節(jié)奏等各種轉換。這正是巴贊從德•西卡、奧森•威爾斯等人的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可見,有一定長度的長鏡頭是一個可以涵蓋所有鏡頭類型的完整的鏡頭語言系統,其核心正是備受巴贊推崇的段落鏡頭和景深鏡頭。
“電影之重新發(fā)現空間是同有意識地運用景深和放棄最后造成空間時間化和觀念化的蒙太奇美學有關的”。[3](P.183)蒙太奇締造空間的辦法是許多片斷的并列和聯接,而這些片斷彼此之間可以毫無聯系。比如庫里肖夫名為“創(chuàng)造的地理”的實驗,他將五個在不同地點拍攝的鏡頭組接成一場戲,人們卻無法看出其中的破綻,認為空間在這里是統一的。這種統一感實際上是基于空間感的失去才獲得的。因為在蒙太奇的統攝下,“藝術家的工作就是將素材加以安排……使觀眾不去探求時間與空間的聯系。”[5](P.74)如此一來,空間自始至終只是觀念上的。馬爾丹在分析愛森斯坦的《戰(zhàn)艦波將金號》時說:“我們是絕對不可能對敖德薩全城、它的港口和海灣的地理位置具有明確概念的,影片從未表現過任何全景,以使我們能看到戰(zhàn)艦距碼頭臺階有多遠”。[3](P.171)如果采用強調寫實的長鏡頭方法來拍攝,無疑能避免這種缺憾。長鏡頭關注的焦點是每個鏡頭內部的表現力,在現場場面調度下,攝影機忠實地記錄下各事物的位置、大小以及彼此之間的關系,并且保持一種連續(xù)性。因而,長鏡頭所表現的空間是完整而統一的。這種統一不同于上述純想象性的統一,它作用于觀眾的現實經驗而被感知。正是通過長鏡頭,電影影像得以將現實的空間關系呈現在觀眾的眼前。
在一次訪談中,楊德昌說:“電影一開始就是在記錄人類生活片段,并且可以重復呈現,讓更多人認識不同的生活經驗。我們喜歡看電影,其實是在看別人的生活經驗,并從中得到一些訊息,這是生物的本能特性。”在談到蒙太奇時,他說:“我們到電影學校學的蒙太奇,其實是因為技術的限制才產生的一種剪接方法。早期機器要上發(fā)條,只能拍20秒,影片要用很多20秒連接起來,其實這就是剪接,是被逼出來的。”[6]楊德昌強調電影的紀錄功能,并且把電影與生活以及人關注現實的本性聯系在一起,這與巴贊對電影本質的看法相當契合。蒙太奇在楊德昌的心中也恢復了最初的面目,是一種將鏡頭連接起來的技術。由此可見,楊德昌是個不折不扣的長鏡頭理論的擁護者,而他的影片可以說都是以長鏡頭為中心拍攝而成的。
空間在楊德昌電影中具有一種直觀性。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為例,觀眾可以像主人公小四一樣對他家的結構和方位了然于胸,一樣熟悉從建國中學回家的路。不需要對比蒙太奇,小四家的簡陋、小馬家的富麗、眷村的破敗,同樣產生了強烈的視覺沖擊效果。楊德昌電影最常見的是用長鏡頭來表現全景、中遠景以及景深。通過冷靜客觀的長鏡頭,這些鏡頭的內涵得到充分展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小四得知小明的背叛,雙手抓著門框有如受難基督的全景鏡頭就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小四殺死小明后,人物被置于毫無阻擋的大全景中,小明兀自躺在地上,小四低頭叫她,然后蹲下身一邊哭喊一邊想將她拉起來,在他身后,書攤前的人自顧自看書,幾個女學生有所察覺,遠遠地、驚愕地看著這一切,一個過路人也駐足觀望,人物的絕望無助和恐懼不安靜靜地彌漫整個畫面空間。再如景深,巴贊認為景深鏡頭是實現空間統一的最好方法,因為它大大拓展了銀幕的縱深感和寬度,彌補了立體感不足的短處。景深鏡頭還可以使同時出現在一個畫面中的前后景產生一種關系,將人物的內在情緒和外在環(huán)境的氣氛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第二個鏡頭,小本論文由整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