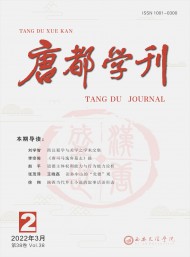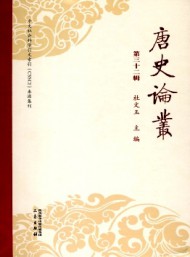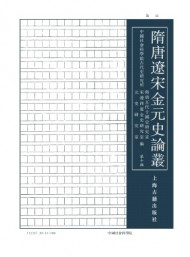唐范文10篇
時間:2024-03-20 10:18:47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唐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先秦至唐的歷史考察
內容提要:本文考察了先秦至唐道家和道教各派“理(治)身理(治)國”思想的發展。道家及道教各派都曾圍繞著理(治)身與理(治)國的關系進行過不同層次地探討。從“天人合一”原則出發,道家和道教各派不僅將身與國比擬為結構和功能相似的有機系統,而且對于理(治)身與理(治)國的終極基礎和實踐原則作了深入地剖析。隨著語境的變遷,特別是在唐代,原道家語義被轉換或開掘出新的內涵,故“理身理國”的實質內涵也在變化。“理身理國”觀體現了道家和道教各派對個體生命及其生存狀態的深度人文關切。
關鍵詞:理身理國.道.自然.無為
自從先秦老子創立道家學派以降,歷代的道家及道教各派都曾圍繞著理(治)身與理(治)國的關系展開過不同層次地探討。從“天人合一”原則出發,道家和道教各派不僅將身與國比擬為結構和功能相似的有機系統(身國相擬),而且對于理(治)身與理(治)國的終極基礎和實踐原則(身國同道)作了深入地剖析。本文試圖在學界前輩研究之基礎上,原創:對道家和道教“理身理國”(唐以前稱“治身治國”,唐則“理身理國”并稱。)觀所體現的“身國共理(治)”內涵作初步探討。
一、先秦以降道家和道教“理身理國”觀的演變
按《說文解字》,“理”者“治玉也”。(《韓非子和氏》:“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作為動詞的“理”后引申為治理(《詩經大雅江漢》:“于理于理,至于南海。”)、治療(《后漢書崔寔傳政論》:“是以梁肉理疾也。”)等義。“理”字又與“亂”字義反,同“治”字義同(《管子霸言》:“堯舜非生而理也,桀紂非生而亂也。故理亂在上也。”)。成玄英在注解《道德經》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時注云:“治,理也。”為避唐高宗李治諱,唐用語多以“理”代“治”字,故“理身理國”,亦可轉語為“治身治國”。唐代之前的道家和道教各派,雖無“理身理國”并稱,卻早已蘊含“理身理國”之義理。
道家和道教墳典,老子《道德經》強調了“推天道以明人事”,力圖將自然之天道當作個體(身)安身立命及社會制度(國)建構之基礎。在老子看來,常道是道之體,體現道的虛無和因應變化于無為的本然狀態(“道法自然”);可道之道是道之用,是道的“可為之、可執之”的非常狀態。將常道推用于理(治)身,則能“滌除玄覽”(章),復歸虛靜的生命本性,將常道運用于理(治)國,則能做到“為而弗有”(章)、“為而不恃”(章)、“為而弗爭”(章),“以百姓之心為心”(章)。總之,要治身理國,就應以符合常道之自然體性的“無為”為實踐原則(“上德無為而無以為”(章)“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章)),反對自然生命的馳騁和觀念的造作,反對行人事時的強作妄為。在確立治身理國的本體依據和實踐原則的同時,老子亦將身國比擬為功能相似的系統:“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章)就身國關系論,國本質上是身(個體生命)的外在化和社會化的表現。二者都是或處于常態或處于異化狀態下的生命共同體。貴身、愛身喻示了合乎自然的生命形態的張揚,以此對生命的至愛推及于天下,天下自然呈現出清明、凈化的政治生態。故“砉鋇氖抵適嵌浴襖砩懟鋇哪D狻
唐袒露裝習俗之議
摘要:唐代是一個非常注重時尚的朝代,女性更是時髦成風,袒露裝的流行更是唐代女子追求時尚的巔峰。它的流行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同時又是民族融合和交流的結果。
關鍵詞:唐袒露裝;習俗;文化
一、袒露裝及其形式
袒露裝是唐代貴族婦女的一種時尚服飾,最初為歌女所穿,后來流行于貴族婦女群體。袒露裝的形式是,無領,袒露胸部,內襯抹胸,適身窄袖,襦長至腰。這種服飾,不但將女性的脖頸徹底暴露,而且連胸部也處于半掩半露的狀態。唐代眾多陶俑和壁畫中婦女形象,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佐證。在唐朝,袒胸露肌,這是自然的、美的、時尚的。初唐歐陽詢有“胸前如雪臉如花”①,其毫無保留的贊美,則更是反映了當時的時尚風氣和審美標準。
唐代袒露裝形式多樣,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變化。但不論怎么變化,都圍繞著表現女子的形體美來進行,唐代女子的形體美因為袒露裝被展現得淋漓盡致。
第一種樣式是袒胸大袖衫,此樣式為袒胸貫頭式,而且有很華美的紋飾,其袒胸處呈雙桃形,恰與女子隆起的胸脯協調一致,充分體現了女子的形體美。其特點是袖口寬大,肥闊,并有很寬的繡花邊緣,是盛唐時期頗為時髦的一種服裝,除了供宮中樂舞和宮女穿著外,也受到達官貴族婦女的喜愛。唐詩中多處說到婦人著袒胸衫子的形象,如李群玉《贈歌姬詩》:“胸前瑞雪燈斜照”等。
唐富笙演奏藝術研究論文
內容摘要:在笙的發展史中,涌現出了數位對笙的發展有巨大貢獻的人,而在這數位演奏家中,筆者對唐富先生的笙演奏藝術之魅力頗有感觸。本文從唐富先生的藝術貢獻、笙演奏的特點及演奏風格、技巧的運用及作品情感的處理、舞臺藝術表演等方面進行分析,粗略探討研究唐富先生的笙演奏藝術。
關鍵詞:演奏特點作品處理舞臺表演
唐富先生是繼胡天泉、閆海登等老一輩演奏家之后,在我國中青年笙演奏家排行榜中,居于首位的笙演奏家、作曲家、改革家和教育家,被笙界前輩譽為“南高北唐”中的“北唐”。四十多年來,他共獨創或與他人合創笙曲近三十首,他的作品內容豐富,技巧新穎,形象鮮明,風格大氣豪放。他還發明了許多笙的技巧,如撥舌、手顫、喉吐等。在笙的改革方面,唐富先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勇于改革,編排設計了21簧笙、26簧笙、33簧笙,他研究改革的新指法合理實用,得到同行、專家及初學者的贊評和喜愛。
談起唐富先生的笙演奏藝術,就必然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唐富先生的演奏特點及風格
由于歷史文化、人文地理等條件影響,音樂的形式與風格也各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從大家最易接觸到的民歌談起其風格,南方民歌風格細膩婉轉,陜北民歌風格高亢嘹亮,東北民歌風格則粗獷豪放。笙的作品風格也亦然,南方笙名家翁鎮發演奏的笙曲風格大都纖柔、婉轉、甜美,山東、河北一帶以笙大師胡天泉為代表的笙曲風格剛勁有力、剛柔并濟,東北笙演奏家唐富的作品風格則大氣、豪放。
漢唐銅鏡分析論文
一、漢鏡不同時期的藝術特點
漢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興盛時期,漢武帝在經過文景之治、修養生息后,國力恢復,掃平匈奴設立沙河四郡,使西漢人形成“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雄強國家意識。同時,開辟了絲綢之路。溝通歐亞。對外交流,使國力達到漢代強盛的頂點。這一階段流行的銅鏡在中國銅鑒史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氣度恢弘、凜然而不可侵犯,透射出一種咄咄逼人的兇悍之氣。厚厚的邊沿,凸起的銘文帶都顯示出一種堅實的存在感,有巖巖泰山之氣象。
西漢前期,漢鏡主要仍沿襲戰國鏡類風格,此時最流行的是蟠螭紋鏡,其地紋較粗疏,主紋多由雙線和三線構成,布局有纏繞式,間隔式及博局紋相間式,并出現了銘文。具有了新的裝飾特征。
西漢中期。銅鏡工藝高度發展,形制和花紋都出現了顯著的變化,鏡面增大,鏡壁加厚,弦紋鈕和橋形鈕少見,代之而起的是半球形圓鈕和連峰鈕、獸形鈕等。平素緣或內向連弧紋緣。主題紋飾廣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即以四乳為基點,將鏡背分為四區,其間布置主要紋飾。此時,戰國以來流行的地紋已經消失。這時期流行的鏡類有星云紋鏡、日光鏡、昭明鏡、重圈銘文鏡、禽獸紋鏡、連弧紋鏡等。
西漢后期至東漢中期,銅鏡工藝又有新的變化。鏡背紋飾由靜化趨于動化,出現了象征祥瑞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種及各種瑞獸、禽鳥和具有升仙之意的羽人等形象,圖案生動活潑,具有強烈的現實感。表現手法仍以陽線勾勒,但比以前更細膩。非常美觀。這一時期銅鏡注重邊緣裝飾,多在邊緣上飾花紋帶,同時,銘文種類繁多。內容豐富。常見的銘文有“尚方”、“善銅”和紀氏銘等,并出現了地支十二字和七言韻語。
東漢晚期出現的神獸鏡和龍虎鏡等,采用浮雕技法,使鏡背紋飾成為半立體狀,高低起伏,形象逼真。同時。也出現了以剔地平雕技法刻畫的龍鳳紋鏡、對鳥紋鏡和變形四葉彎鳳鏡、變形四葉獸首紋鏡等,圖案清晰,具有剪紙效果,富有民間藝術風味。此時的紋飾布局也有新的變化,出現了“軸對稱”的新方式,如直行銘文鏡類,即在鈕上下直行書寫“位至三公”或“可至三公”等銘文,兩側對稱飾雙夔紋或雙頭龍鳳紋,使內容和形式更好的統一,這時期銅鏡銘文有“位至三公”、“長宜子孫”和“君宜高官”等,反映了當時的人們渴望高官厚祿、子孫繁昌和家常富貴的愿望。
唐初史館研究論文
自古以來,中國歷朝統治者非常重視歷史著述,以冀達到“懲惡勸善,貽鑒將來”的目的。歷代王朝都設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發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館修史制度。本文擬就唐初設館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館特點、史館修史成就及對后世的影響作一論述。
一史官、史館沿革及正式確立
中國是世界上重視歷史最早的國家。“蓋史之建官,其來尚也。昔軒轅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1](P304)“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內、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職已有分工。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識。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漢興之時,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馬談、遷父子曾司其職。政府設立修史機構則始于東漢,東漢的蘭臺、東觀既是國家文獻檔案館,又是“當時著述之所也”[1](P310)。經東漢明、安、桓、靈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編修國史《東觀漢記》,開創了政府組織史官,成立機構修史的先例,對后世史館建置有深遠的影響。但這只是史館的濫觴,非專職機構,參與修史的人員多是臨時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專職。魏晉始設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雜取他官,不恒厥職”,于“秘書置著作局”,后“別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監修國史(如谷纂)。北齊改修史局為史閣(又稱史館),“史閣史館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襲之,以修北朝諸史。唐沿隋制,史館制度漸臻完善。“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4](P1089),修撰國史。同年,“于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確立。史館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職,隸屬門下、中書省,地處國家政治權力中心。宰相監修成為定制,“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5](P591)。史館中設有修撰、直館、典書、掌固等職,分工明確。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正式確立史館修史制度,這絕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加強在史學領域的體現。唐太宗這位在中外歷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他曾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統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對應措施,以樹立大一統的歷史觀點。而私人修史已無法適應、無法滿足這種形勢的需要。所以,設館修史成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館制度正式確立是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私修歷史,多奉行“直書”傳統書法,因而易觸犯統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筆見誅”[7](P199)。私修歷史,資料不如官方豐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盡通諸門學術,因而著述速度與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適應統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學的發展。所以在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詔令:“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8](P38)隋文帝的詔令很明確,官方就是要壟斷修史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唐承隋制,正式設立史館,修前代史和當代史。這是史學發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對修史機構的進一步完善與確立。
二唐初史館特點
唐初史館與以前的史館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過,東漢蘭臺、東觀是中國古代史館建置的濫觴,但當時蘭臺、東觀主要還是中央文獻檔案館,非專門修史機構;撰修國史人員如班固、劉珍、邊韶、馬日磾等多是他官,臨時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館是北齊統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礎上設置的,其組織與編制相對固定,主要由監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書郎等組成。史官的品級、俸祿比較低,如著作郎(從第五品)歲祿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校書郎(九品)歲祿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賄賂以求溫飽。他們多無視史實,任情褒貶,以至于《魏書》剛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稱之為“穢史”。
秦漢隋唐現象分析論文
一、兩次數百年分裂后的統一王朝與短命帝國
在中華文明史上,從夏商建國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曾經出現過兩次持續四、五百年之久的國家分裂。前者發生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間,自平王東遷以后,周便喪失了對各諸侯國的實際支配權,歷史進入了諸侯爭霸的春秋與七雄兼并的戰國兩個持續相連的分裂時期,直到秦王嬴政掃滅山東六國,建立強大的秦王朝,中國才再度實現統一。其間中國歷史經歷了約550年之久的分裂,這是最長的一次分裂。
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出現長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東漢政府在它的打擊下從此也就失去了對地方各路豪強的控制。從公元184年至589年隋滅南陳,除去晉武帝“太康”十年短暫的統一外,中國歷史在民族之間血與火的大沖擊、大碰撞中渡過了它長達400年左右的分裂。這次分裂在時間上比春秋戰國略短,但其混亂與復雜卻有過之而無不及。
結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國,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強大。秦,“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其盛可謂空前!隋,更是“統一寰宇,甲兵強盛”,“風行萬里,威動殊俗”(《貞觀政要·君道》),傲然俯視萬邦。然而,如此強盛的兩個統一王朝,卻又都僅只經歷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數百年之久的兩次分裂,短命夭折的兩個統一王朝,這種相似的漫長前奏與歷程,最終歸宿與命運,在中國歷史上僅此二家,其它歷史時期不曾出現過。
二、功過相參的開國皇帝,堪稱典型的亡國暴君
秦、隋帝國的相似命運,還在于歷史贈予了它們幾乎一樣特征的開國皇帝與亡國之君。秦始皇與隋文帝,都可稱得上是曠世少見的一代英主,是他們結束了國家的長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強大的統一帝國,又是他們在制度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與建設,并對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然而,也正是他們,一個不能順應時代的變遷,統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國,施民以暴政;一個則在施政上,尤其是統治后期,“好為小數,不識大體”(《隋書·文帝紀》)。導致舉措失當,“蘊藏大亂”(《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79頁)。因而又都對這兩個新興王朝的短命而亡,負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漢唐村落形態探究論文
內容提要:村落是與城邑相應的社會單位概念,源于龍山時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茲至漢,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鄉村基本聚居形態。漢代鄉村組織的特點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單元與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晉南北朝時代出現了里聚分離,作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義;至唐代,里正成為鄉政的主持者,村正開始行使里正職掌,村落的行政與法律地位得到確認,鄉里之制演化為鄉村之制。這一演化實質上是行政單元與自然聚落的分合變化,并不具有城鄉分離的內容,與“城邦帝國”、“領土帝國”之概念亦無干涉。不論作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時代具有多少稱謂,它一直是與城邑對應的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地緣組織與血緣組織的共同體。
關鍵詞:漢唐村落聚落
漢唐時代,是中國古代鄉里之制與聚落形態演化的重要轉折時期。從兩漢時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晉南北朝時代里與聚的分離,再到唐代的鄉里合署與村落地位的確認,無論是外在形態還是內在結構,它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中國中古社會的變革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
討論漢唐村落形態,首先面臨的是關于村落的發生問題。對此,日本學者進行了比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宮崎市定、宮川尚志等學者的論述最具代表性。宮崎市定先生認為,自上古到現代,中國古代國家結構為都市國家,以大小城邑為地方社會集合體的基本構成,“聚落恰似一個個細胞,在一定面積的耕地中心,存在著細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內,被區分為數個區域,那就是里。不僅是工商業者,就連農民也居住在城內的里中。在漢代,根據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別定級為縣、鄉、亭”。他還認為,城內農民開始移居城外,鄉制開始瓦解,“促使這種瓦解趨勢進一步發展者,是漢代豪族勢力的擴張。可能是一方面便利農耕的負郭、帶郭之田都被有勢力者所獨占,貧民要想擁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須求之于遙遠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們在遠距離的地方開拓莊園,招募勞動者,于是城內的農民漸漸脫出城外,前來居住應募。這里出現的就是另一種新形態的聚落——村(邨)”①。盡管學界對于宮崎市定的“都市國家說”爭論頗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興聚落形態之說卻被多數學者接受,此后學術界有關中國古代村落問題的研究也多以此為基點展開。宮川尚志提出:“在漢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戶設里的制度。到唐代,雖然單位一樣,但在城市與鄉村分別稱之為坊和村。這是城市和鄉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時也使人聯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遠離中央政權的邊鄙地區呢?”在經過一番分析討論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結論,認為“總體來看,村莊分布在山間河谷地帶以及一般遠離城市地區的實例較多”②。侯旭東先生對此說進行了修訂,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僅見于邊僻之地,城鎮周圍同樣廣泛存在……重要交通線附近亦廣泛分布。”③這是正確的。但他只是較宮川尚志更強調了村落分布的廣泛性,仍未脫出村落是新興聚落形態這一范疇。
源于宮崎市定先生的村落為城郭之外的新興聚落形態說,有一個重要前提值得進一步討論,這就是漢代里的設置問題。依宮崎市定先生之說,漢代的里設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無居民聚落,也就沒有里的設置。但是,從文獻資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獻資料看,并非如此。在兩漢社會,雖然史籍與法律文書都以鄉、里涵蓋整個鄉村社會,然而實際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層單位鄉里之外,還存在著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們實際上是鄉里之制的基礎。這些村落,漢人稱之為“聚”、“落”或“格”。《史記·五帝本紀》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說文解字》釋“聚”曰:“聚,會也。從*,取聲,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謂邑中村落。”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廣雅》曰:“落,謂村居也。”格,為漢人對村落的別稱。《史記·酷吏列傳》:“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垢購告言奸,置伯格長以牧司奸盜賊。”裴骃集解引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司馬貞索隱:“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
探討隋唐時期司法政策
中國古代通過集體會議,以討論的形式,集思廣益,為決策提供參考和依據的制度起源甚早,在秦漢時期已基本形成,到隋唐時期則日益成熟,稱為“集議”,還被寫入了王朝的令、式,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制度。《唐六典》卷八門下省侍中條:“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并在注釋中解釋“議”云:“謂朝之疑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①集議已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各種重大的關涉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諸方面的問題,均可通過一定的程序,成為集議的主題。有關法律問題的集議是集議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具體的程序和運作方面,更為完備,有著自身鮮明的特點,對當時的法制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到目前為止,盡管學界對唐代的集議制度本身已有一定的研究②,但關于司法過程中之集議的研究還付之闕如。本文將嘗試對這一問題做較為詳細的探討,望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一、司法集議的發動
隋唐時期,在司法運行的過程中,可因一定的情形發動集議。從發動集議的主體看,大致可分為指定集議、法定集議和申請集議三種情況。
(一)指定集議
指定集議指就某些重大或疑難的案件,由皇帝直接下詔,命令百官進行集議。隋代,嗣滕穆王楊綸曾被告怨望咒詛,煬帝命黃門侍郎王弘審理此案,“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煬帝令公卿集議,“以公族不忍,除名為民”③。指定集議針對的多為制獄。對于制獄,根據王朝的律令,有關機關在審斷后,要直接上奏皇帝,由皇帝權斷定罪①。這些案件一般來說或是事關重大,或是疑難復雜,或是牽連廣泛,或是涉及到了宗室、重臣等特權群體,或是關涉國家的重大利益,所以盡管皇帝可以權斷定罪,但案件本身的復雜性又使他沒有充分的把握行使好這項權力,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在隋唐時期,特別是在制定律令的隋及唐前期,貴族階層尚有較強的勢力,而制獄又常和這一階層有關,所以或是出于審慎的目的,或是為了獲得輿論的支持,或是為了顯示自己的“無私”以塞眾議,或是為了推脫責任并彰顯皇恩浩蕩,皇帝在做出最終裁決之前,常會命令百官集議,作為決斷的依據或緩沖之階。
在這種情況下,司法集議實際上是一種輔助皇帝行使其司法權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皇帝權斷權行使中的剛性和不確定性,是對皇帝權斷權行使中缺乏程序性制約的一種補救,因而是一種緩沖性和補充性的司法機制。在這一機制運行過程中形成的多數意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看作是官僚集團的整體意見,皇權也不得不予以重視。這樣就在皇帝行使其權斷權的過程中,加入了國家法律權力的因素②,對理論上不受制約的皇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約。與此同時,這種機制也將皇帝權斷權的行使由隱秘轉為公開,可看做是中古時期司法公開的一種形式③。司法集議使司法過程具備了更加豐富的合理性,相對就更容易達到司法本身的目的。因指定集議是由皇帝所發動,所以并無范圍上的限制。在制獄之外,如果普通司法案件因其引發的爭議或轟動性效應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也可以隨時指定一定范圍的官員進行集議。從唐初開始,隨著三省制的日漸完備、權力制衡機制的日益嚴密,司法程序和司法過程也日趨繁密。在三省制下,尚書省裁斷流刑以上之罪,按照律令的規定必須使用奏抄這一文書形式,而門下省有審署奏抄之權④,如此一來,在文書運作的過程中,相關案件在經刑部復審后,還要由門下省奏定。然而,王朝設計的權力制衡機制是雙向的,案件即使已由門下省奏定,刑部仍可提出異議。然后,再由門下省審核,另行奏定。即使經過了如此復雜的程序,如皇帝認為有疑問,仍可下令集議。《魏鄭公諫錄》卷二“諫處張君快等死”條:“刑部奏:‘張君快、歐陽林謀殺蘇志約取銀,君快不下手。貞觀九年三月赦:劫賊不傷財主,免死,配流。經門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舉斷合死。’門下執依前奏。尚書任城王道宗錄奏。太宗謂侍臣曰:‘國有常典,事跡可明,何得各為意見,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當。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謀為劫殺,何得免死?’因令殺之。公進諫曰:……太宗令議。議定奏聞……因令配流。”⑤就是對上述司法程序較為完整的反映。從制度上講,皇帝是所有流以上案件的最后裁斷者,對其中引發爭議的案件均可發動集議。對于普通案件而言,這實際上等于在最后的審級之前又加設了一道臨時性程序,從而可以集體的力量,以多元化的視角和觀點為終審提供智力上的支持,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因此,指定集議是“慎刑”思想在司法制度設計上的直接反映。
漢唐舞蹈傳承與發展研究
摘要:我國的漢唐舞蹈是漢唐兩朝之間的舞蹈文化體現,它獨具一格的風格是我國古代人民對于漢唐文化的總結與歸納。現如今,漢唐文化的發展也受到了更多人們的喜愛和崇拜。那么,對于漢唐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就更加的重要了。漢唐舞蹈的有利傳承和發展會大大推動我國的社會文化的進步和繁榮。本篇文章就針對漢唐文化進行了簡要的介紹,以及針對漢唐文化傳承和發展的必要性以及發展的注意事項進行了一系列的闡述。
關鍵詞:漢唐舞蹈;傳承;發展;探究
在我國舞蹈的發展歷史中,漢唐古典舞以它獨特的風格成為了中國舞蹈文化里極具代表性的舞種。漢唐舞蹈主要以最明麗的漢、唐精神和社會特征而組成。它的獨特風格以及氣質在我國的舞蹈中占有很重要的舞蹈地位。那么我們要更加重視漢唐舞蹈的傳承與發展,因為它可以更好的展示漢唐文化,讓整個漢唐文化可以用舞蹈的形式展現給更多人。這樣一來,不僅可以有力的展示漢唐文化的豐富性、多彩性,還能夠推動我國的社會文化的發展和進步,為祖國豐富多彩的文化添磚加瓦。
一、漢唐舞蹈的風格特點
(一)袖,袖得輕盈和唯美。在舞蹈文化中,“袖”是最為出色的舞蹈表達方式之一。袖分為拂袖、抖袖、拋袖、振袖等袖法,由于它的多變性,就塑造了比較多元的舞蹈形態。袖可以根據舞者對于身體的自身形態而自然的發生變化,通過身體的一揚一頓,以拋一收,就好像流水般順滑,在無意間轉換了多種姿態,從而“袖”出了具有漢唐舞蹈獨特風味的輕盈、唯美。(二)“韻”出婉約柔媚。漢唐舞蹈主要就是在“韻”出一種柔媚和婉約。其中“韻”包含有少女的嬌羞,流露少女的純真以及質樸的韻味。這樣一來就可以讓欣賞的觀眾切身體會漢唐女子的獨特風味。
二、漢唐舞蹈傳承與發展的必要性
唐初史館研究論文
自古以來,中國歷朝統治者非常重視歷史著述,以冀達到“懲惡勸善,貽鑒將來”的目的。歷代王朝都設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發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館修史制度。本文擬就唐初設館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館特點、史館修史成就及對后世的影響作一論述。
一史官、史館沿革及正式確立
中國是世界上重視歷史最早的國家。“蓋史之建官,其來尚也。昔軒轅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1](P304)“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內、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職已有分工。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識。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漢興之時,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馬談、遷父子曾司其職。政府設立修史機構則始于東漢,東漢的蘭臺、東觀既是國家文獻檔案館,又是“當時著述之所也”[1](P310)。經東漢明、安、桓、靈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編修國史《東觀漢記》,開創了政府組織史官,成立機構修史的先例,對后世史館建置有深遠的影響。但這只是史館的濫觴,非專職機構,參與修史的人員多是臨時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專職。魏晉始設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雜取他官,不恒厥職”,于“秘書置著作局”,后“別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監修國史(如谷纂)。北齊改修史局為史閣(又稱史館),“史閣史館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襲之,以修北朝諸史。唐沿隋制,史館制度漸臻完善。“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4](P1089),修撰國史。同年,“于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確立。史館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職,隸屬門下、中書省,地處國家政治權力中心。宰相監修成為定制,“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5](P591)。史館中設有修撰、直館、典書、掌固等職,分工明確。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正式確立史館修史制度,這絕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加強在史學領域的體現。唐太宗這位在中外歷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他曾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統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對應措施,以樹立大一統的歷史觀點。而私人修史已無法適應、無法滿足這種形勢的需要。所以,設館修史成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館制度正式確立是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私修歷史,多奉行“直書”傳統書法,因而易觸犯統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筆見誅”[7](P199)。私修歷史,資料不如官方豐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盡通諸門學術,因而著述速度與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適應統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學的發展。所以在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詔令:“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8](P38)隋文帝的詔令很明確,官方就是要壟斷修史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唐承隋制,正式設立史館,修前代史和當代史。這是史學發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對修史機構的進一步完善與確立。
二唐初史館特點
唐初史館與以前的史館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過,東漢蘭臺、東觀是中國古代史館建置的濫觴,但當時蘭臺、東觀主要還是中央文獻檔案館,非專門修史機構;撰修國史人員如班固、劉珍、邊韶、馬日磾等多是他官,臨時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館是北齊統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礎上設置的,其組織與編制相對固定,主要由監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書郎等組成。史官的品級、俸祿比較低,如著作郎(從第五品)歲祿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校書郎(九品)歲祿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賄賂以求溫飽。他們多無視史實,任情褒貶,以至于《魏書》剛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稱之為“穢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