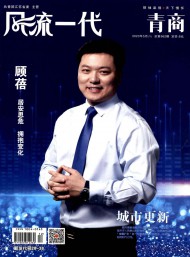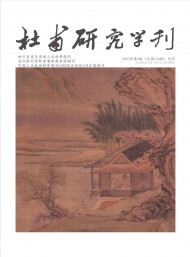唐代范文10篇
時(shí)間:2024-03-20 10:25:55
導(dǎo)語: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yàn),為你推薦的十篇唐代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唐代禁軍司法職責(zé)
唐代司法制度是古代司法制度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作出的獨(dú)特的貢獻(xiàn)。唐代司法制度由于所產(chǎn)生發(fā)展的條件和環(huán)境不同,一些現(xiàn)代意義上的制度還處于萌芽狀態(tài),沒有充分地發(fā)展起來。但是,也形成了自己鮮明的時(shí)代特色,諸如審判制度、監(jiān)察制度、監(jiān)獄制度已經(jīng)發(fā)展起來。并在此基礎(chǔ)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司法機(jī)構(gòu)。唐代普通的司法機(jī)構(gòu)系統(tǒng)是延續(xù)先秦商鞅變法以降一千年來的傳統(tǒng),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套系統(tǒng)。中央司法系統(tǒng)分為刑部、大理寺和御史臺(tái),這三大司法機(jī)關(guān),分掌司法眾務(wù),居于主導(dǎo)地位;地方司法機(jī)關(guān)仍由各地行政機(jī)關(guān)兼理,所以也因行政區(qū)變化而變化。唐初地方分為州、縣兩級(jí)行政,開元二十八年時(shí)有州(府)328個(gè),縣1573個(gè)[1]959,所以地方司法機(jī)關(guān)一般也分為兩級(jí),但是司法制度的權(quán)很有限,這充分體現(xiàn)了唐朝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制傾向。但是隨著唐朝國力的式微、社會(huì)矛盾的尖銳復(fù)雜,這些專門司法機(jī)關(guān)開始分割普通司法機(jī)關(guān)的司法權(quán),故又具有普通司法機(jī)關(guān)的特點(diǎn)。其中尤以北衙禁軍的北軍獄、神策獄最為突出,目前學(xué)界對(duì)北軍獄、神策獄分割普通司法機(jī)關(guān)職能的問題沒有專文論述,可見有進(jìn)一步探討的價(jià)值。
一、北軍獄
唐代軍事制度基本上是沿襲北魏、隋以來的府兵制度,后根據(jù)唐代實(shí)際情況有所增益和發(fā)展,即府兵制度繼續(xù)存在,由南衙統(tǒng)轄中央十六衛(wèi)的番上府兵組成,成為唐中央宿衛(wèi)京師的主要武裝力量;而守衛(wèi)京師長安宮城和禁苑中的禁軍,號(hào)稱北衙禁軍,駐在皇城北面,負(fù)責(zé)保衛(wèi)宮城,是專職保衛(wèi)天子的親軍,分為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左右神武軍、左右神策軍和左右神威軍,總稱北衙十軍。安史之亂后曾設(shè)過威武、長興、英武、天威等軍,不過很快廢棄。北衙十軍中,左右神策軍是中堅(jiān)力量。在安史之亂以前一百余年中,包括禁軍在內(nèi)的軍司并沒有取得司法權(quán),也沒有設(shè)置監(jiān)獄。因?yàn)椤短坡墒枳h•斗訟》明確規(guī)定“:諸犯罪欲自陳首者,皆經(jīng)所在官司申牒,軍府之官不得輒受。其謀叛以上及盜者,聽受,即送隨近官司。若受經(jīng)一日不送及越覽余事者,各減本罪三等。其謀叛以上,有須掩捕者,仍依前條承告之法。”[2]441而在司法實(shí)踐層面上,也是如此。如肅宗朝時(shí)對(duì)軍司擅捕人犯、審理案件現(xiàn)象進(jìn)行嚴(yán)格控制,如乾元二年四月壬寅詔“:英武軍及六軍諸使,比因論竟,便行追攝。今后須經(jīng)臺(tái)府,如處斷不平,具狀聞奏。”[3]255此詔規(guī)定明顯地說明,此時(shí)臺(tái)、府等普通司法機(jī)關(guān)的案件管轄權(quán)力尚未遭致嚴(yán)重侵奪,而軍司只能針對(duì)御史臺(tái)及地方府縣對(duì)軍士犯法判決不服的,可以具狀申訴。代宗朝仍可見地方長吏懲治軍士之事《:舊唐書•竇參傳》言大歷中,竇參任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兇暴,因醉毆其女弟,其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竇參捕理曹芬兄弟當(dāng)死,并力排眾議,杖殺曹芬。后又有“盜殺富平令韋當(dāng),縣吏捕獲賊黨,而名隸北軍,監(jiān)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qǐng)?jiān)t原其罪”,后給事中韓滉密疏駁奏,賊遂伏法。這些事例說明北軍監(jiān)獄實(shí)際上還沒有真正取得司法權(quán)。
總之,晚至肅、代之際,軍司還沒有訴訟管轄權(quán)力的司法職能,地方府、縣仍可依據(jù)唐律以及皇帝的詔令負(fù)責(zé)審理有關(guān)軍士之間、軍民之間的糾紛案件。相承一百多年的訴訟傳統(tǒng)和法司權(quán)威還能繼續(xù)延續(xù),沒有被完全破壞。但是,到代宗朝,情況開始發(fā)生變化。代宗大歷五年(770),宦官魚朝恩于“北軍置獄,召坊市兇惡少年,羅織城內(nèi)富人,誣以違法,捕置獄中,忍酷考訊,錄其家產(chǎn),并沒于軍,或者舉選之士,財(cái)貨稍殷,客于旅舍,遇橫死者非一。坊市苦之,謂之‘入地牢’”[3]4765。從材料中北軍獄捕人、考訊、置獄等行為看,說明“北軍獄”開始設(shè)立,而且還是專門的軍事法庭負(fù)責(zé)關(guān)押、審判有罪的軍人。但是,其司法活動(dòng)已相當(dāng)廣泛,超出了設(shè)計(jì)的初衷,開始介入民事司法領(lǐng)域,對(duì)民事偵緝、羈押、審訊、判決均有涉及。由此表明,北軍獄從設(shè)立之時(shí)就有著分割普通司法權(quán)的傾向。唐代司法制度規(guī)定,御史每月在京城巡囚一次,“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直至德宗“建中初,敕京城諸使及府縣系囚,每季終御史巡按,有貧濫者以聞”,表明監(jiān)察御史仍按照唐律規(guī)定巡按北軍獄。但自貞元之后,此制遭到勢(shì)力大漲的宦官的破壞,御史不得監(jiān)察,北軍獄從此成為能夠?qū)徖碥娛隆⒚袷碌奶貏e法庭了。德宗貞元末年,已開始染指地方獄訟,如“帝晚節(jié)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xué)生何諫、曹壽系訊,人情大懼”[1]5867。顯然北軍獄此時(shí)能有權(quán)橫干地方司法,那就已成為皇帝的詔獄了。此后由于宦官嚴(yán)密地控制了北軍和北軍獄“,宦官勢(shì)橫,御史不敢復(fù)入北軍按囚,但移文北司,牒取系囚姓名及事,因應(yīng)故事而已,不問其有無冤濫”。即使有人還想急需維護(hù)普通司法機(jī)關(guān)的權(quán)威,也會(huì)遭到皇帝的貶斥,如敬宗寶歷元年十月,馮詡縣尉劉行余“坐擅決軍人,貶道州延昌尉”[4]8154就是一例。
二、神策獄
“神策獄”,設(shè)置在神策軍內(nèi),也是一個(gè)專門的軍事審判機(jī)關(guān)。德宗建中年間曾發(fā)生藩鎮(zhèn)叛亂,神策等軍因有功于朝廷,得到德宗在司法上的優(yōu)待,即貞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詔規(guī)定:射生、神策及六軍將士犯法,府縣法司不得徑行逮捕,皆須奏請(qǐng)聽裁“:如有關(guān)府縣其須其辨對(duì)者,先具奏聞,然后移牒本軍,不得懸有追捕。”[5]8040由是驕橫日增,遂得對(duì)地方司法秩序恣意踐踏:“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wèi)從之勞,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官領(lǐng)之,撫恤優(yōu)厚。禁軍恃恩驕橫,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垢辱官吏,毀裂案贖。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由是府縣雖有公嚴(yán)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5]7523隨后,德宗對(duì)府縣審判權(quán)進(jìn)行分割,即把各類訴訟依據(jù)涉案主體劃分為軍、民兩類,神策獄取得軍人間各類訴訟之專門管轄權(quán),是繼北軍獄之后再次出現(xiàn)脫離普通司法機(jī)關(guān)訴訟管轄權(quán)的專門司法機(jī)關(guān)“:辛巳,詔神威、神策六軍將士自相訟,軍司推助;與百姓相訟,委府縣推助;小事移牒,大事奏取處分,軍司、府縣不得相侵。”[3]371及至太和四年十二月,文宗以京城頻有寇賊,府縣防制實(shí)難為由,委派左右神策軍派員協(xié)同府縣緝捕盜賊,由此,神策軍開始插手地方司法有了法律依據(jù),從單一負(fù)責(zé)神策軍司法事物的專門司法機(jī)關(guān),演變?yōu)閹в衅胀ㄋ痉C(jī)關(guān)職責(zé)的具有軍事、民事司法職責(zé)的司法機(jī)關(guān)了“:宜令左右神策各差人與府縣計(jì)會(huì),如有盜賊,同力追擒,仍具所差人數(shù)姓名,并所配防界,牒報(bào)京兆府。應(yīng)捕獲賊,并先送府縣推問,如有諸軍諸使勘驗(yàn)知情狀,如實(shí)是殺人及強(qiáng)盜,罪跡分明,不計(jì)贓之多少聞奏訖,牒報(bào)本司,便付京兆府決殺。其余即各牒送本司,令準(zhǔn)百姓例之罪科決。待府司添補(bǔ)所由,人力稍足,即別條流。其外縣有軍鎮(zhèn)處,亦準(zhǔn)此處分。”[3]688盡管是以“準(zhǔn)百姓例之罪科決”審判民事案件,且還是臨時(shí)性的幫忙,但是,畢竟為神策獄介入民事司法領(lǐng)域打開了法律之門,改變了其專門審理軍事案件的性質(zhì)。神策獄存在時(shí)間較長,很可能與神策軍之廢置相伴始終。
唐代繪畫藝術(shù)歷史思索
在唐代時(shí)期,中國的繪畫水平在藝術(shù)上成就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進(jìn)展,其藝術(shù)水準(zhǔn)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gè)朝代。唐初,中國疆域遼闊,國力雄厚,經(jīng)濟(jì)空前繁榮,從而為文化繁榮提供了良好的物質(zhì)基礎(chǔ)。尤其在唐代后期,在繼承前期文化上得到了不斷發(fā)展,繪畫藝術(shù)也日趨成熟。繪畫題材已開始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繪畫的表現(xiàn)手法隨之豐富起來。唐代繪畫名家輩出,其在題材內(nèi)容與作畫技法等方面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與當(dāng)時(shí)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繁榮發(fā)展密不可分。
一、初唐時(shí)期的繪畫作品
初唐時(shí)期,繪畫題材多以宗教佛像和貴族人物畫為主要對(duì)象,其中人物畫又逐漸發(fā)展成為唐代繪畫的主流,取得的成就也最為燦爛,代表畫家包括閻立本、張萱、尉遲乙僧和周窻等。現(xiàn)存的《歷代帝王圖》和《太宗步輦圖》就是閻立本的杰作代表。在畫技方面,人物畫著眼于對(duì)人物的精到描寫,其不但追求人物形象上的客觀相似,而且關(guān)注人物內(nèi)心的傳神描繪。唐代人物畫不太注重描繪人物所處的具體生活環(huán)境,即便描寫也是十分簡略的。比如閻立本創(chuàng)作的《步輦圖》中,為了描寫唐太宗坐步輦接見前來拜訪的使者祿東贊的人物情態(tài),整幅作品中竟然沒有絲毫具體的環(huán)境描繪,構(gòu)圖的重要落腳點(diǎn)在于刻畫主要人物的神情姿態(tài),為人們展示了親切、穩(wěn)重的唐太宗和真誠、恭敬的祿東贊的生動(dòng)形象。閻立本畫技精湛、手法獨(dú)到,生動(dòng)刻畫了人物的容貌服飾和神情舉止,呈現(xiàn)出肖像畫應(yīng)具有的獨(dú)有特征。通過《步輦圖》的人物刻畫,可以看到群女團(tuán)簇、花環(huán)映襯的歡慶氣氛下唐太宗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也間接暗示著當(dāng)時(shí)唐朝的強(qiáng)大與繁榮[1]127。中國古代人物畫的獨(dú)特藝術(shù)傳統(tǒng),也在技巧與技法的多樣性方面得到體現(xiàn)。還是以《步輦圖》為例。這幅人物畫屬于古代工筆畫,體現(xiàn)了中國畫作中相當(dāng)重要的工筆重彩品類,在很長時(shí)間內(nèi)也是繪畫史上的主流,在對(duì)人物的描畫和作品的設(shè)色等方面,其不但反映了創(chuàng)作者在繪畫語言、繪畫技巧方面所能夠達(dá)到的高度,也顯示出作者的探究鉆研方向和個(gè)性審美情趣。也應(yīng)該看到,在中國古代歷史文化過程中,盡管隋唐時(shí)期處于最為燦爛和輝煌的時(shí)期,但依然無法擺脫封建社會(huì)嚴(yán)格等級(jí)觀念的強(qiáng)大約束,因此,在畫作中,人物所處的具體位置以及構(gòu)型的尺寸大小,都明確體現(xiàn)出了“主大從小,尊大卑小”的基本原則。這也是畫家們無法規(guī)避而受到歷史條件制約的一個(gè)佐證。在唐代仕女圖畫家中,較著名的是周窻和張萱。張萱擅長于畫人物題材,他巧于構(gòu)思全圖,強(qiáng)調(diào)人物畫線條的工細(xì)勁健。在張萱創(chuàng)作的《虢國夫人游春圖》中,精心描繪了虢國夫人,也就是楊貴妃的姐姐,一行七人外出游春的生活場(chǎng)景,整幅畫作的色彩著調(diào)清新明麗,特別是其中描繪的婦女形象,是當(dāng)時(shí)唐代仕女人物的典型代表,并且對(duì)后期晚唐五代的畫風(fēng)造成了直接影響。周窻創(chuàng)作的比如《簪花仕女圖》、《聽琴圖》、《紈扇仕女圖》等畫中婦女的臉型多是圓潤豐滿,體態(tài)多是豐滿艷媚,她們濃麗肥胖、酥胸長裙、妖嬈多姿,表現(xiàn)出唐代仕女畫作的典型風(fēng)格。
二、盛唐以后的繪畫題材
隨著唐朝經(jīng)濟(jì)日漸繁榮,繪畫題材和繪畫技巧也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人物畫開始關(guān)注普通世俗生活,山水畫也日益出現(xiàn)了興盛的趨勢(shì)。在這個(gè)時(shí)期,最有成就的畫家是吳道子,他在人物畫和山水畫方面都有了很高的造詣,在當(dāng)時(shí)有“畫圣”稱謂。從畫法技巧分析,在繼承傳統(tǒng)的蘭葉描和西域鐵線描之后,吳道子還首次創(chuàng)造了一種莼菜條的精妙獨(dú)到筆法,深受百姓的喜愛。他還發(fā)展創(chuàng)新了梁朝張僧繇所采用的暈染法(即凹凸法),增強(qiáng)了繪畫的立體感。此外,他的創(chuàng)作成就還體現(xiàn)在他的宗教繪畫方面。吳道子具有壁畫創(chuàng)作的豐富經(jīng)歷和深厚的創(chuàng)作熱情,并且畫作涉及的范圍也非常廣泛,涵蓋了經(jīng)變、佛陀、普賢、菩薩等多種類型。吳道子的畫作由于生動(dòng)自然,在民間獲得了相當(dāng)高的評(píng)價(jià)而被人們廣為傳頌,被視為“活畫”。此外,吳道子也是一位全能型畫家,他的畫作涉及人物山水、亭臺(tái)樓閣、花木鳥獸等多種內(nèi)容。吳道子繪畫創(chuàng)作的高峰與鼎盛時(shí)期大概是在開元天寶年間,當(dāng)時(shí)在長安、洛陽寺廟之中,就有他創(chuàng)作的大概三百多幅壁畫作品以及大量的卷軸畫作品。現(xiàn)在人們公認(rèn)的吳道子畫作的主要代表作品包括《孔子行教像》、《菩薩》、《天王送子圖》、《八七神仙卷》等[2]42。
山水畫中分水墨和青綠兩個(gè)大的體系,根據(jù)地域風(fēng)格不同分為南、北派;李思訓(xùn)、李昭道父子主要擅長描繪金碧山水,畫作設(shè)色絢麗,描繪工細(xì),尤其是景物逼真自然,成為山水畫北派之祖。青綠山水畫基本上是用細(xì)筆勾勒出山石樹木,然后用石青石綠填染為主,表現(xiàn)出繪畫對(duì)象的固有顏色和主觀化的畫畫手法。由于廣泛使用了青、綠為主的顏色,其在當(dāng)時(shí)被統(tǒng)稱為“青綠山水”。唐代詩人王維則首創(chuàng)了水墨山水畫,意境淡雅甜美,富于濃情詩意,成為山水畫的南派之祖,對(duì)于后世的繪畫創(chuàng)作影響較大。王維常以詩入畫,創(chuàng)造出淡雅抒情的浪漫意境,尤其是他第一個(gè)采用“潑墨”山水技法,從而對(duì)山水畫的筆墨意境進(jìn)行了發(fā)展,推動(dòng)了當(dāng)時(shí)山水畫的變革。盛唐除了人物畫之外,隨著繪畫的發(fā)展,花鳥、鞍馬、山水等畫科也開始出現(xiàn)并獨(dú)立成科。此外,唐朝還出現(xiàn)了諸多擅長描繪花、鳥、禽、獸的各類畫家,比如薛稷以畫鶴、韓干以畫馬、韓滉以畫牛等非常知名。在許多寺院、石窟和陵墓中,還都留存有這樣的壁畫,構(gòu)成了唐朝繪畫藝術(shù)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在敦煌千佛洞中,壁畫數(shù)量繁多,內(nèi)容豐富,可謂是空前絕后。繪畫的題材盡管以佛經(jīng)故事為主,但也涉獵廣泛,反映了唐代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生活面貌。這些壁畫沒有作者具名,但筆調(diào)生動(dòng),真實(shí)地描繪出當(dāng)時(shí)的生活,壁畫中的飛天、窟頂?shù)脑寰畧D案等藝術(shù)表現(xiàn)都極富于獨(dú)創(chuàng)精神和民族特色[3]19。
唐代送別詩藝術(shù)特征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自從有了人類,有了社會(huì),便有了分離,許多本該是天長地久的,卻不得不天隔一方。唐代自然也是如此。這個(gè)中國封建社會(huì)的鼎盛時(shí)期,經(jīng)濟(jì)繁榮,疆域廣大,國內(nèi)和國際交流頻繁,所以人們的活動(dòng)場(chǎng)范圍也在不斷擴(kuò)大,人口的流動(dòng)性增強(qiáng),上至達(dá)官貴人下到黎民百姓,都有機(jī)會(huì)主動(dòng)或被動(dòng)地離開自己的家。所以,送別的種類很多,涉及領(lǐng)域廣泛,而且又都是一往情深。而特殊的社會(huì)背景,特別的人格追求等,又使得唐人的送別詩有了自己獨(dú)特的特點(diǎn)。
一.送別詩的類型之多,情感之深
孟郊的《古別離》、杜甫的《新婚別》寫的是夫妻間的離別,那份別離的幽怨與痛苦,自是感人至深的。李益的《喜見外弟又言別》和柳宗元的《別舍弟宗一》則是兄弟間的骨肉分離,難舍之情溢于言表。而孟郊的《古怨別》、杜牧的《贈(zèng)別》則極寫情人間的纏綿悱惻。這些可算是親人間的、情人間的離別,而在唐人的送別詩中,抒寫更多的則是同僚間的、朋友間的離別之情。
(一)友人的離別,直接抒寫離別之情的送別詩
友情是世上最真摯,最復(fù)雜的情感之一。詩仙李白的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以水深比情深,形象地道出了這段友情真實(shí)質(zhì)樸,“不及”二字更形象的說明彼此的友情深厚。可見詩仙的神來之筆是多么的精妙,化無形的思念之情為有形的流水,詩中毫無悲傷之情。而盧綸的詩雖是直接抒寫離別之情,卻多了一層濃郁的悲情色彩。“故關(guān)衰草遍,離別自堪悲”,在這一蕭瑟,冷清的景象中,離別的悲情格調(diào)格外沉重。
他們有的是寫送好友到外地去做官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和《送梓州李使君》、李白的《送友人入蜀》等,好友外出做官,詩人擺酒相送,其間充滿了殷殷的叮囑和深深的情誼。
唐代文學(xué)特征新模式
1唐代文學(xué)研究的瓶頸問題
回首半個(gè)世紀(jì)以來的唐代文學(xué)研究之路,可以說無論是從宏觀還是從微觀的研究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如陳有冰所說:“唐代文學(xué)研究是20世紀(jì)中國古典文學(xué)研究中研究觀念變化最大、研究方法較為豐富、研究隊(duì)伍相當(dāng)整齊、研究成果更為豐碩的一個(gè)領(lǐng)域,是中國古典文學(xué)學(xué)科畛域確立過程中最有華彩的一個(gè)階段。”l1我們?cè)谛老蔡拼膶W(xué)研究取得成績的同時(shí),不得不正視這樣的事實(shí)——唐代文學(xué)研究正面臨著發(fā)展頸瓶的嚴(yán)重挑戰(zhàn),造成這些發(fā)展頸瓶的一個(gè)主要原因就是研究者過度依賴新文獻(xiàn)和新方法。唐代文學(xué)研究在新文獻(xiàn)和新方法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shí),也出現(xiàn)了令人疑惑的新問題,即面臨著“集體沉默”的啞語尷尬境遇,“唐代文學(xué)研究難以出新”幾成研究界的普遍共識(shí)。這里筆者不是說文獻(xiàn)與方法不重要,事實(shí)上任何學(xué)術(shù)研究都離不開文獻(xiàn)與方法,沒有文獻(xiàn)基礎(chǔ)作為依托和研究方法理論指引的研究必然歸于蒼白空泛。重方法、重文獻(xiàn)本身沒有問題,但許多事物往往是雙刃劍,過度依賴方法和文獻(xiàn)以至于唯方法論、唯文獻(xiàn)論,由于過于講求研究方法往往有跑題之嫌而成了其他專業(yè)的研究,最終淡化了文學(xué)的本質(zhì)之美;由于過于注重文獻(xiàn)材料的積累,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研究即材料,沒有新材料就不會(huì)有新的研究成果,如此便忽視了對(duì)現(xiàn)有文獻(xiàn)本身更高層次的考索,不能分析蘊(yùn)涵在現(xiàn)有文獻(xiàn)中的文學(xué)精神之美。我們進(jìn)行學(xué)術(shù)研究,面對(duì)浩如煙海的文獻(xiàn),既要扎得進(jìn)去,也要跳得出來,陷于文獻(xiàn)不能自拔無異失路于廬山迷霧;一旦有了理論的指引,跳出文獻(xiàn)并在更高層次上駕馭文獻(xiàn),就會(huì)感受到高屋建瓴的爽快和收獲柳暗花明的喜悅。在技術(shù)主義、工具至上主義盛行的今天,人們要么太迷信材料工具,要么過分強(qiáng)調(diào)方法,其結(jié)果往往是研究主體迷失了心靈的方向,人為地限制了自己主觀能動(dòng)力量的充分發(fā)揮。在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界研究存在一股學(xué)術(shù)逆流,那就是過度地依賴材料技術(shù)手段,過分地強(qiáng)調(diào)研究方法。如今學(xué)術(shù)資料容易獲得了,電腦、網(wǎng)絡(luò)更是方便了查找資料,鼠標(biāo)一點(diǎn),幾十條、幾百條材料就出來了,所以這大大加速了研究的進(jìn)程,也造就出一部分“高產(chǎn)學(xué)者”。電腦在給人們研究帶來方便的同時(shí),它的弊端日益顯現(xiàn)出來,那就是“電腦體文章”的泛濫。“電腦體文章”缺少的是人的精神與靈感,缺乏感動(dòng)人的“情”的力量。我們進(jìn)行文學(xué)研究要心懷人文關(guān)懷,但“新方法論加文獻(xiàn)考據(jù)”的研究方式很容易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左東嶺《中國古代文學(xué)研究轉(zhuǎn)型期的技術(shù)化傾向及其缺失》一文就抓住了問題的要害,指出由于技術(shù)化的追求而導(dǎo)致了文學(xué)研究中更為重要的學(xué)術(shù)特性的缺失:人文精神的缺失;理性思辨的缺失;可讀性的缺失。如其所說:“文學(xué)研究需要有人文的關(guān)懷、審美的體驗(yàn),從而在提高人生境界、豐富人類情感上發(fā)揮其它學(xué)科難以替代的功能。”
筆者認(rèn)為,在文學(xué)研究過程中要心懷人文關(guān)懷,要充分挖掘蘊(yùn)涵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情感、美感因素,人文精神絕不能缺失。筆者的一個(gè)初衷就是想探討在沒有新文獻(xiàn)材料的情況下唐代文學(xué)研究如何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事實(shí)上唐代文學(xué)研究遠(yuǎn)沒有窮盡,尤其從文學(xué)美感本身進(jìn)行研究潛能巨大,這就是選擇從生命美學(xué)視角研究唐代文學(xué)的原因所在。
2生命美學(xué)揭橥唐代文學(xué)之靈魂
唐代是一個(gè)善于繼承總結(jié)而又能做到兼收并蓄的朝代,生產(chǎn)的發(fā)展、經(jīng)濟(jì)的高漲、國勢(shì)的強(qiáng)大、政治的清明、文化的繁榮,使國家、民族處于欣欣向榮、蓬勃向上的時(shí)期,使整個(gè)時(shí)代充滿了朝氣和希望。唐代盛世雄風(fēng)不僅體現(xiàn)于彪炳千古的盛世景象上,更體現(xiàn)在唐人生機(jī)勃勃的精神世界中。對(duì)唐人來說,自由、自信、解放、超越猶如與生俱來的天性,“他們想方設(shè)法,幾乎是尋找一切機(jī)會(huì)謀求歡娛、快樂和自由,他們渴望肉體的解放和精神的超越”J。雄強(qiáng)的社會(huì)激發(fā)了唐代文士對(duì)功業(yè)理想和自由人生的追求,激發(fā)了他們的生命精神和浪漫情緒,他們充滿憧憬,積極進(jìn)取,滿懷抱負(fù),渴望實(shí)現(xiàn)精彩的人生價(jià)值。在這樣的時(shí)代氛圍感召下,唐代文士創(chuàng)作熱情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大爆發(fā)、大釋放,創(chuàng)造了后世難以為繼的繁榮局面。在大唐盛世“精神氣候”的影響下,唐代文學(xué)的審美觀念、審美趣味、審美理想、審美風(fēng)尚折射出一種昂揚(yáng)激越的審美因子,廣大文士將自身的生命理想、自由精神、主觀情愫付諸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實(shí)踐,顯現(xiàn)出一種富于自由品質(zhì)與浪漫氣息的精神氣韻。在中國歷史上,士人曾有三次較大的思想解放,即先秦諸子百家時(shí)期、魏晉時(shí)期以及大唐時(shí)代。但就其生命的自由性、思想的開放性、人格的真實(shí)性而言,大唐時(shí)代的士人具有其他時(shí)代士人無法比擬的巨大優(yōu)越性。唐代文士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主體之“人”,具備卓爾不群的生命精神狀態(tài),他們那種高揚(yáng)人性、追求自由的神情風(fēng)貌必然反映在文學(xué)、宗教、藝術(shù)各個(gè)方面:具有“盛唐氣象”的詩歌氤氳壯闊,歌詠生命、贊美英雄之作比比皆是,唐傳奇中有大量的瀟灑人生的才子和一諾千金的俠士。唐代文論中,陳子昂高唱“風(fēng)骨”精神,韓愈提出“氣盛言宜”之說,司空?qǐng)D主張“生氣遠(yuǎn)出”。唐代道教,追求性命雙修,強(qiáng)調(diào)本真自然,實(shí)現(xiàn)由外丹到內(nèi)丹的轉(zhuǎn)變;唐代佛教上禪宗確立,“即心即佛”的超然頓悟,徹底解放了束縛人們心性的一切桎梏……質(zhì)言之,上述諸例無不說明唐代是一個(gè)充滿生命激情的時(shí)代,人們的所作所為演繹著淋漓盡致的生命之情,此等生命精神已經(jīng)上升到一種具有風(fēng)范百代的“生命美學(xué)”。
這種“生命美學(xué)”的審美特質(zhì)在于:唐代文士生活在一個(gè)雄強(qiáng)的時(shí)代,普遍煥發(fā)出灼灼的激情與夢(mèng)想,他們精神振奮,意志高揚(yáng),善于抓住一切機(jī)遇來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生命價(jià)值。唐代文學(xué)中最震撼人心的是一種千古猶存、戛然獨(dú)造的風(fēng)姿神韻,這種風(fēng)韻的核心特質(zhì)是活潑潑的生命力,富于自由品質(zhì)與浪漫氣息,饒具風(fēng)骨精神與雄強(qiáng)之態(tài),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為一種生命美學(xué)。唐代文學(xué)充溢著勃勃生機(jī)的飛動(dòng)氣勢(shì),張揚(yáng)著熾熱的生命脈動(dòng),在一定意義上講,生命美學(xué)揭橥唐代文學(xué)之靈魂。大唐時(shí)代重視人本精神和人性解放,充分發(fā)揮各種人的創(chuàng)造性和進(jìn)取心,一旦我們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以探索人的生命存在與超越為旨?xì)w的生命美學(xué)無疑便納入了筆者的研究視野,一個(gè)新的口號(hào)必須呼喊出來:文學(xué)藝術(shù)必須體驗(yàn)生命,把生命解釋為人的價(jià)值存在,人的超越性生成,人的終極意義顯現(xiàn),這才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本原。概言之,生命美學(xué)關(guān)愛生命,追求自由,帶有令人自身解放的性質(zhì),體現(xiàn)著一種人文精神的價(jià)值倡導(dǎo),這無疑對(duì)唐代文學(xué)特質(zhì)的形成產(chǎn)生深遠(yuǎn)而重要的影響。唐人激昂勃發(fā)的生命情韻鑄就了唐代整個(gè)文學(xué)、藝術(shù)大繁榮的局面,被譽(yù)為“唐代三絕”的李白詩、張旭草書、裴曼劍舞就是這個(gè)偉大時(shí)代精神氣韻的經(jīng)典代表。正如史仲文所說:“大唐時(shí)代的詩人和文士,大多是一些敢想敢說,能想能說,善講善說的人物,他們不象漢儒那樣循規(guī)蹈矩,不像魏晉南北朝文士那樣吞吞吐吐、彎彎曲曲,不像宋明理學(xué)家那樣一味講理講氣、講心講性,不像明清文人那樣提心吊膽懼怕文字獄。他們甚至不屑于如同先秦諸子那樣相互爭鳴。盛唐以詩而鳴,首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表現(xiàn)。”質(zhì)言之,執(zhí)著熱切的兼濟(jì)意識(shí)、建功立業(yè)的雄心壯志、昂揚(yáng)奮發(fā)的進(jìn)取精神構(gòu)成了唐詩的主體審美色調(diào),這樣的詩歌彰顯出廣大詩人昂揚(yáng)奮發(fā)的生命斗志、剛勁強(qiáng)健的情感內(nèi)涵、狂放不羈的精神個(gè)性以及自由獨(dú)立的文化人格。唐代文學(xué)中的生命美學(xué)精神不是游離于實(shí)踐操作的空洞理論,我們可以將其落歸于實(shí)處:其一,唐代生命美學(xué)生發(fā)于閎闊雄放的大唐盛世,是唐代社會(huì)良好的人文環(huán)境孕育了這樣的生命美學(xué)精神,同時(shí)這種生命美學(xué)精神反過來又促進(jìn)了唐代文學(xué)乃至文化的高度繁榮;其二,唐代儒、道、佛三教并舉為生命美學(xué)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思想理論基礎(chǔ),儒家的積極人世精神、道家的生命感悟以及禪宗的自性理論都對(duì)唐代生命美學(xué)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其三,唐代士人的生命人格范式可以體現(xiàn)在詩意人生、少年精神、酒神氣韻、諫諍膽魄、文士風(fēng)流等諸方面,展現(xiàn)出了自信、解放、自由、狂放的生命情韻;其四,唐代學(xué)術(shù)文化中也蘊(yùn)含著豐富的生命美學(xué)特質(zhì),唐人在學(xué)術(shù)文化中敢于大膽疑古,勇于向經(jīng)典、權(quán)威挑戰(zhàn),他們重人事、輕天命,發(fā)出“人定勝天”的呼喊;其五,唐代文藝?yán)碚撝懈翘N(yùn)涵著一種鮮明的生命化批評(píng)傾向,如陳子昂論“風(fēng)骨”,王昌齡論“勢(shì)”,杜甫論“神”,韓愈論“氣”與“不平則鳴”,司空?qǐng)D論“生氣遠(yuǎn)出”,無不體現(xiàn)出一種生命精神。我們可以在唐代的詩論、畫論、書論、樂論中找到大量的生命化批評(píng)跡象,這說明文學(xué)的生命化特征在當(dāng)時(shí)不是一種孤立的文化現(xiàn)象,而是有著一種與唐代社會(huì)文化特征廣泛一致的深層次因素。質(zhì)言之,我們既重視對(duì)唐代時(shí)代背景的宏觀把握,又重視對(duì)唐代文士生命性格的具體分析,緊緊圍繞“生命美學(xué)”這個(gè)核心線索對(duì)唐代文學(xué)進(jìn)行深人的人文闡釋。
段成式與唐代文學(xué)研究
在晚唐文人中,段成式是一位在詩、詞、駢文、傳奇、筆記小說等各類文體方面都有著獨(dú)特建樹的全才文學(xué)家,尤以筆記小說《酉陽雜俎》著稱于世。他豐富的著述為唐代文學(xué)尤其是晚唐文學(xué)增添了一道靚麗的風(fēng)景,帶來了無限生趣。但因有唐一代以詩相夸,以傳奇為異,筆記小說尚沒有得到充分認(rèn)識(shí)和重視,遂致段成式在唐代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得不到應(yīng)有的肯定和公正的評(píng)價(jià)。茲就段成式的詩文等做一檢討,以期重新認(rèn)識(shí)段成式于唐代文學(xué)的意義。
一、段成式的詩詞
段成式的詩作存留的數(shù)量不算很多,清人席啟寓編《唐詩百名家全集》收錄其詩一卷,現(xiàn)見于《全唐詩》者凡30余首(包括聯(lián)句、詞)。另有《漢上題襟集》十卷。①《漢上題襟集》屬于唱和總集。清人汪師韓《詩學(xué)纂聞•詩集》云:“詩有數(shù)人唱和因繼而匯為一集者,白香山與元稹、劉夢(mèng)得有《還往集》、《因繼集》……段成式、溫庭筠、逢皎、余知古、韋瞻、徐商諸人之《漢上題襟集》是也。”可知《漢上題襟集》乃段成式與溫庭筠、逢皎(應(yīng)為溫庭皓)、余知古、韋蟾、徐商等人的唱和之作。《文獻(xiàn)通考》卷二百四十八《經(jīng)籍考七十五•總集》云:“《漢上題襟集》三卷,陳氏曰:唐段成式、溫庭筠、崔皎、余知古、韋蟾、徐商等唱和詩什,往來簡牘。蓋在襄陽時(shí)也。”段成式曾于大中十三年(859年),坐累解印,閑居襄陽,任職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徐商幕府,《漢上題襟集》當(dāng)為此時(shí)與諸人唱和之作。段成式尤其擅長唱和詩,這和他的貴公子出身喜好交游及博學(xué)多才分不開。今人元鋒、煙照整理的《段成式詩文輯注》[1]收錄其詩歌31首,酬唱之作有《和徐商賀盧員外賜緋》、《怯酒贈(zèng)周繇》(一作答周為憲看牡丹)、《題僧壁》(一本有和韋蟾三字)、《和周繇見嘲》(一作和周為憲廣陽公宴見嘲詩)、《和張希復(fù)詠宣律和尚袈裟》等五首,可以作為段成式唱和詩風(fēng)的代表,反映了晚唐士大夫的交游情況以及生活情趣。他的《游長安諸寺聯(lián)句》12篇,作于武宗會(huì)昌三年(843年)任職于集賢院時(shí),是與同僚張希復(fù)、鄭符等共游長安諸寺,如靖恭坊大興善寺、長樂坊安國寺、常樂坊趙景公寺、大同坊云華寺、道政坊寶應(yīng)寺等18處所作。詩中多佛語,涉及佛寺人物、故事、植物、壁畫等,尤其是《吳畫聯(lián)句》、《先天幀贊聯(lián)句》、《諸畫聯(lián)句》等,可謂唐代著名畫家吳道子、韓干等人的創(chuàng)作寫照,對(duì)了解唐代長安的宗教、文化、藝術(shù)具有較高的資料價(jià)值。段成式崇信佛教,經(jīng)常光顧佛寺,與僧人關(guān)系密切,《呈輪上人》、《送僧二首》、《題石泉蘭若》、《題谷隱蘭若三首》、《桃源僧舍看花》等,描繪僧人散淡曠逸形象,曲折指斥“會(huì)昌法難”,表現(xiàn)了僧侶的生活追求。如《題谷隱蘭若三首》描寫了尋訪谷隱寺所見峴山深秋的景色,點(diǎn)綴以村情野趣,被明人鐘惺《唐詩歸》評(píng)為:“自成堅(jiān)響。”段成式亦好道術(shù),《牛尊師宅看牡丹》、《哭房處士》即是道士生活的寫照,房處士因服食丹砂而意外身亡令人遺憾不已。段成式自己也熱心煉丹,《不赴光風(fēng)亭夜飲贈(zèng)周繇》即寫忙于煉丹,無暇赴宴。《寄周繇求人參》言及靈芝仙草和人參的藥用,希望長生久壽。段成式出身于官宦之家,喜佛好道,可見唐代佛道兩教的興盛以及士人生活與佛道的密切關(guān)系。段成式又有多首描寫下層妓女、宮人處境的詩,如《漢宮詞二首》:“歌舞初承恩寵時(shí),六宮學(xué)妾畫蛾眉。君王厭世妾白頭,聞唱歌聲卻淚垂。二八能歌得進(jìn)名,人言選入便光榮。豈知妃后多嬌妒,不許君前唱一聲。”以漢寓唐,寫出了宮女命運(yùn)的悲慘,文辭深婉,意境悲涼,脫出了宮怨詩的一般窠臼。《折楊柳七首》則托柳寄情,以柳喻宮女,含蓄蘊(yùn)藉,內(nèi)容兼涉宮怨閨情,離愁別緒。其一云:“枝枝交影鎖長門,嫩色曾沾雨露恩。風(fēng)輦不來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黃昏。”胡次焱云:“鳳輦不來,空留鶯語,隱然見孤處寂寞,無人共訴之意;曰‘春盡’、曰‘黃昏’,又隱然見老之將至。少而蒙恩,老而失寵,以色事人,恩愛難久,豈可以容貌自恃也?”[2](卷58)道出了宮女的悲哀。
段成式言及妓人的詩有《光風(fēng)亭夜宴妓有醉毆者》、《嘲元中丞》(一作襄陽中堂賞花為憲與妓人戲語嘲之)、《嘲飛卿七首》、《柔卿解籍戲呈飛卿三首》、《戲高侍御七首》等,以戲謔的筆法嘲諷溫庭筠、高侍御等人的狎妓、蓄妓、納妾之事及妓女之間的斗毆行為,令人見出世間百態(tài)。其《光風(fēng)亭夜宴妓有醉毆者》作于大中十三年(859年)閑居襄陽時(shí),戲詠妓女酒后斗毆。②賈晉華認(rèn)為:這一類詩固然價(jià)值不高,但也真實(shí)揭示了晚唐文人士大夫生活和心理的一個(gè)側(cè)面。又《嘲飛卿七首》恰似一場(chǎng)七幕喜劇,敘述溫庭筠與青樓女子男才女貌,由相慕而相愛,并經(jīng)歷了較長時(shí)間離別相思的考驗(yàn),而終于團(tuán)聚合歡的過程。詩題雖出一“嘲”字,詩中卻絕無輕佻側(cè)艷之意,而是充滿了對(duì)這一對(duì)才子佳人的稱贊與祝愿。《柔卿解籍戲呈飛卿三首》詩生動(dòng)描繪出一位有幸脫離青樓、初為人婦的少女的美麗外表和欣喜心情。柔卿應(yīng)即上引唱和詩中與飛卿情意相合的青樓女子,則飛卿終于為其解籍并與之結(jié)合,二人的情事竟以喜劇而結(jié)局。飛卿與青樓女子的這一段真情,不但有助于我們了解襄陽詩人群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而且可由此加深對(duì)溫詞內(nèi)容的認(rèn)識(shí)。初盛唐文人士大夫?qū)懜杓耍话阒皇恰坝^妓”詩。中唐時(shí)漸多以歌女飲妓為酒宴游戲的伴侶。晚唐五代同類詩作卻有較多抒寫與妓女的真實(shí)情事,這正是此時(shí)期愛情詩詞大量涌現(xiàn)的重要背景之一。[3]段成式一生仕途時(shí)有坎坷,曾因誣難罷職閑居襄陽,于是常借機(jī)抒懷,一發(fā)胸中塊磊。如《醉中吟》,感慨人生榮辱無常,命運(yùn)變化不定,但求長醉,忘卻煩憂。《觀山燈獻(xiàn)徐尚書》三首,表達(dá)在正月十五上元節(jié)山燈輝煌的夜晚,想到自己解印賦閑,不免悵然難抑。《題商山廟》有感于商山四皓,抒發(fā)懷才不遇的牢騷。《送穆郎中赴闕》借送人赴京,發(fā)泄淪落失意。這些抒懷之作是其真實(shí)思想的流露,也能給人以生活啟迪。段成式的交游極其廣泛,親密者如李群玉、溫飛卿等。《寄溫飛卿箋紙》一詩前有小序,言在九江,“出意造云藍(lán)紙,輒分五十枚”,與朋友共享。《哭李群玉》有兩首,悼念友人,凄愴不已,痛徹肺腑。詩人同情李群玉恃才傲物、遭遇誹謗、含冤而死的悲慘境況,為之憤慨不平。清人黃周星《唐詩快》評(píng)曰:“昔人持忠入地,此乃持傲入地。語特挺倔有生氣。”段成式的情誼義氣可謂感人至深。他的《河出榮光》是一首完整的試帖詩,是科舉考試中的范文。清人臧岳編《應(yīng)試唐詩類釋》卷六評(píng)曰:“首句從題原說起,三、四句點(diǎn)清全題,五、六、七、八句實(shí)疏題意,第九、十句,襯貼‘榮光’,第十一、二句,襯貼‘河’字,第十三、四句,將榮光出河,合寫一筆,作一總束,末以干進(jìn)寓意結(jié)之。”此詩別有價(jià)值。其他如《觀棋》、《猿》等及一些佚句,亦皆有可賞之處。從段成式僅存的為數(shù)不多的詩作中,我們?nèi)阅芨惺艿剿姼枭娅C的廣博,情感的真摯,情趣的廣泛,有些還具有資料價(jià)值和認(rèn)識(shí)意義。段成式的詞僅存《閑中好》一首,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詞徵》卷五云:“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shí)舞榭,東禪院亦曰本塔院。武宗癸亥三年,為諸名流游咽之所,鄭符、段成式、張希復(fù)閑中好詞,乃寓居禪院時(shí)所撰者。”可知《閑中好》詞是他同鄭符、張希復(fù)游永壽寺所作。詞云:“閑中好,塵務(wù)不縈心。坐對(duì)當(dāng)窗木,看移三面陰。”詞義清新可人,俞陛云《唐詞選釋》評(píng)此詞和鄭符的《閑中好》曰:“鄭言人在松陰,但聽風(fēng)傳僧語,乃耳聞之靜趣;段言清晝久坐,看日影之移盡,乃目見之靜趣。皆寫出靜者之妙心。”鄭振鐸論曰:“唐末,鄭府、段成式與張希復(fù)三人酬答的《閑中好》三首,清雋可喜。像成式之作……后來的詞里便很難見到這樣渾樸的東西了。”[4](P419)在詞體初興的階段,段成式的《閑中好》獲得如此好評(píng),可謂難能可貴。
二、段成式的文章
《宋史•藝文志》錄有《段成式集》7卷。段成式博聞強(qiáng)記,能詩善文,其文駢散兼擅,尤以駢文著稱,創(chuàng)作量應(yīng)該很大,但流傳下來現(xiàn)見于《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七的只有18篇,《唐文拾遺》卷三十又補(bǔ)收5篇。《全唐文補(bǔ)編》卷七十九錄有序文2篇及殘文數(shù)十句,《全唐文又再補(bǔ)》卷六又錄《金剛經(jīng)鳩異序》一文。段成式的文章包括書、序、記、碑、傳、連珠等多種體裁。元鋒、煙照《段成式詩文輯注》收錄段成式文13篇,關(guān)于段成式的駢文,元鋒、煙照認(rèn)為其最突出的特點(diǎn)是:“征事用典,儷對(duì)協(xié)韻,詞藻富贍。……顯示出他逞才炫博的優(yōu)勢(shì)。如《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軟健筆十管書》、《與溫飛卿書八首》等,使事用典,信手拈來,連篇累牘,層出不窮。……其他文章則大都以散為主,韻散交錯(cuò),形式與手法比較靈活多樣。”[1](P5)段成式的駢文以書體文和連珠為突出。其書體文有《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軟健筆十管書》、《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fù)書》、《與溫飛卿書八首》等,寫給溫庭筠的居多,內(nèi)容主要是稱頌溫庭筠才情超眾,學(xué)富五車,為己所不及。語言行文堆砌詞華,對(duì)偶工整,廣搜故事,用典繁密,矜比夸示之意十分明顯。如《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軟健筆十管書》語帶戲謔,句句用典,意無重復(fù),句法靈活,將與毛筆有關(guān)的人事典故搜羅殆盡,給讀者以翔實(shí)的毛筆歷史、材料、制作工藝等知識(shí)信息,敘述清晰典雅。《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fù)書》作于江州刺史任上,巧用惠施之瓠和屈轂之瓠的典故,抒發(fā)了自己有志難伸,有才不為用的苦悶抑郁之情。《與溫飛卿書八首》因贈(zèng)墨而作,駢四儷六,屬對(duì)工切,旁征博引,論墨議書,不吝褒揚(yáng)之詞頌贊友人才學(xué)文章。其《連珠二首》亦是整煉的駢體文,廣譬博喻,妥帖得體地表現(xiàn)了閨中女子孤寂愁怨的情感。駢文的隸事用典極為適合發(fā)揮段成式的博學(xué)之長,而且其作駢文沒有功利目的,不是為了升遷、仕進(jìn),只是為了展現(xiàn)才華學(xué)識(shí)。正如他的《寄溫飛卿箋紙》序云:“奔墨馳騁,有貴長廉,下筆縱橫,偏求側(cè)理。所恨無色如鴨卵,狀如馬肝,稱寫璇璣,且題裂綿者。”借詠紙表達(dá)了只有華美的箋紙才能配得上縱橫馳騁、文雅秀麗之文章的觀點(diǎn)。追求華美典麗,隸事精博,詼諧幽默,變化流暢,使得他的駢文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價(jià)值。段成式的其他記、序、碑、傳等,則以散體為主,駢散相間。《好道廟記》游心黃老,記述處州好道廟建造的始末,表現(xiàn)百姓祭神乞雨的信仰風(fēng)俗,行文胼散結(jié)合,記敘中穿插議論、描寫,布局靈活,別具一格。《寺塔記序》為《寺塔記》首篇,追述游寺經(jīng)歷,悼念亡友,放情釋緣,情真意切。《金剛經(jīng)鳩異序》乃《金剛經(jīng)鳩異》之序言,回憶先父段文昌在蜀地奇異往事,自己的學(xué)習(xí)過程,所受父親的影響等,皆歷歷在目,樸拙動(dòng)人。《諾皋記序》交作《諾皋記》的緣由,用典博恰,文氣流暢,具有很強(qiáng)的敘事性。其長文《寂照和尚碑》,文筆幽澀,為佛言尤奇。《金石文補(bǔ)》評(píng)曰:“碑文險(xiǎn)怪,用內(nèi)典極夥,樊宗師之亞流也。”其《韋斌傳》實(shí)乃韋斌、韋陟兄弟二人的逸聞趣事雜記,擷取點(diǎn)滴生活小事,刻畫二人獨(dú)特性格,語簡詞暢,栩栩如生。如狀寫韋陟疏懶文字往來,乃令侍婢云:“每令侍婢主尺牌往來復(fù)章奏,常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云,當(dāng)時(shí)人多仿效,謂之郇公五云體。”此篇雜傳在晚唐具有代表性,“唐代上繼六朝,雜傳盛行,寫法愈益隨便靈活,柳宗元成就尤高;而在晚唐雜傳中,段氏此篇當(dāng)屬佳作。”[5](P371)段成式的抒懷文有《送窮文》、《毀》等。《送窮文》文筆艱澀奇僻,寄寓失意不平,抒發(fā)窮愁潦倒不得志的憤慨,語調(diào)詼諧。明人謝榛《四溟詩話》卷四論曰:揚(yáng)子云《逐貧賦》曰:“人皆文繡,予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dú)藜餮。貧無寶玩,予何為歡。”此作辭雖古老,意則鄙俗,其心急于富貴,所以終仕新莽,見笑于窮鬼多矣。韓昌黎作《送窮文》,其文勢(shì)變化,辭意平婉,雖言送而復(fù)留。段成式所作,效韓之題,反揚(yáng)之意,雖流于奇澀,而不失典雅。較之揚(yáng)子,筆力不同,揚(yáng)乃尺有所短,段乃寸有所長。惟韓子無得而議焉。以為“雖流于奇澀,而不失典雅”,所論極是。宋人張淏云:“韓退之、段成式皆有《送窮文》,退之之作固不下成式。姚鉉編《文粹》,錄成式而不取退之。《平淮西碑》,亦只載成式父文昌所作。鉉自謂所編掇菁擷華,得唐人文章之精粹。舉此一端,則得謂唐文之精粹,可乎?”[6](卷2,P26)《唐文粹》編于宋初,姚鉉取段氏父子之作而舍韓愈之文,可見宋初推崇駢文的風(fēng)尚甚于古文,段氏父子可稱得上一時(shí)作手。與《送窮文》同時(shí)作的另一篇《毀》,區(qū)區(qū)53字,“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shù)于眾人,人得而防之。今之大人也,有張其所違,嚬戚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jī)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道盡古今形形色色的毀人之術(shù),慨嘆世風(fēng)愈下,人心不古。
透析唐代兩稅法
關(guān)鍵詞:兩稅法;楊炎;量出為入
摘要:兩稅法是中唐時(shí)期為解決財(cái)政危機(jī)而實(shí)行的一次重要的稅制改革,它不僅對(duì)改善唐朝的財(cái)政起到了顯著作用,對(duì)以后的稅制改革也有深遠(yuǎn)影響。其中的很多稅收思想都是史無前例的,因而具有進(jìn)步意義。
1引言
由于唐初的稅制給國家?guī)磉@么多的經(jīng)濟(jì)問題,楊炎便上書請(qǐng)作兩稅法,唐德宗最后也采納了楊炎的意見,首開中國稅改費(fèi)的先河。
1.1兩稅法的主要思想及其評(píng)價(jià)
1.1.1兩稅法的主要思想
唐代仕女服飾研究論文
內(nèi)容摘要:唐朝對(duì)異國衣冠服飾的兼收并蓄,創(chuàng)造了繁榮富麗、博大自由的服飾文化,將中華服飾的發(fā)展推到了頂峰,掀起了一場(chǎng)服飾美學(xué)的革命。
關(guān)鍵詞:唐代仕女服飾特色開放流行時(shí)尚胡服現(xiàn)代服裝設(shè)計(jì)
唐代是我國政治、經(jīng)濟(jì)高度發(fā)展,文化藝術(shù)繁榮昌盛的時(shí)代,是封建文化燦爛光輝的時(shí)代。至今,東亞地區(qū)的一些國家仍把唐朝時(shí)期的服飾作為正式的禮服,可見影響之久。
唐朝對(duì)異國衣冠服飾的兼收并蓄,創(chuàng)造了繁榮富麗、博大自由的服飾文化,將中華服飾的發(fā)展推到了頂峰。而身處其中的宮婦、貴婦及聲色技藝行業(yè)的女性更是作為時(shí)代潮流的引領(lǐng)者,掀起了一場(chǎng)服飾美學(xué)的革命。
一、唐代仕女服飾的特色
1.開放的唐代女裝
從科舉文學(xué)視野看唐代文學(xué)
唐承隋制,以科舉取士,前人對(duì)此的研究已經(jīng)很多了,從《新唐書》有《選舉志》始,宋元明清各朝都對(duì)唐代之科舉有評(píng)論或研究,清朝徐松的《登科記考》則是后人研究唐代科舉的重要資料來源,后孟二冬著《登科記考補(bǔ)證》,更拓寬了科舉研究之資料來源,后又有王洪軍著《登科記考再補(bǔ)證》,綜合碑志材料,為唐代科舉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新的材料;閻文儒著有《唐代貢舉制度》、吳宗國著有《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從制度上對(duì)科舉制度進(jìn)行了深入的研究,給我們提示了唐代科舉制度的本來面目;程千帆著的《唐代進(jìn)士行卷與文學(xué)》,首次將科舉考試中的現(xiàn)象與文學(xué)結(jié)合起來研究;傅璇琮在20世紀(jì)80年成《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一書,對(duì)唐代科舉進(jìn)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開了唐代制度與文學(xué)研究相結(jié)合的先河;鄭曉霞著《唐代科舉詩研究》,從科舉詩的角度對(duì)唐代科舉進(jìn)行研究;金瀅坤則從科舉與社會(huì)變遷的角度著有《中晚唐五代科舉與社會(huì)變遷》一書,詳細(xì)論述了科舉與社會(huì)變遷的關(guān)系。還有很多碩士論文也從各個(gè)方面進(jìn)行唐代科舉研究,也還有一些單篇論文對(duì)科舉與文學(xué)進(jìn)行了研究,總的來說,對(duì)唐代科舉的研究可以說已經(jīng)是比較全面了。從以上所列的專著來看,對(duì)唐代科舉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一是對(duì)唐代科舉制度的研究,如吳宗國、閻文儒的專著;一是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的研究,從科舉對(duì)文學(xué)的影響的方面進(jìn)行研究,如程千帆、傅璇琮的專著;再就是從科舉與社會(huì)的角度研究,如金瀅坤的專著。那么我們可以認(rèn)為,前人對(duì)科舉與文學(xué)的研究尚是不全面的,應(yīng)該還有一些角度可以對(duì)唐代的科舉進(jìn)行研究,比如從科舉文學(xué)的角度。
一、從科舉文學(xué)的角度研究的可行性
臺(tái)灣的龔鵬程在他的《唐代思潮》一書中《文學(xué)化社會(huì)的形成》一章明確地提出了一個(gè)“文學(xué)崇拜”的概念,認(rèn)為唐代存在一種對(duì)文學(xué)的全社會(huì)的崇拜,而這種崇拜最主要的表現(xiàn)方式就是進(jìn)士科舉,以至于在社會(huì)的各個(gè)階層,都對(duì)文學(xué)有一種近乎著魔的崇拜,從皇帝到普通百姓,從讀書人到官員,甚至山林中的僧人也參與了起來[1]。從這個(gè)角度來看,與其說是科舉———進(jìn)士考試———影響了文學(xué),倒不如說是文學(xué)崇拜影響了科舉考試,從科舉考試的名目以及考試內(nèi)容來看,文學(xué)崇拜對(duì)科舉考試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當(dāng)然,科舉考試最終也不可避免地對(duì)文學(xué)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唐五代時(shí)期的筆記小說來看,很多內(nèi)容都是與科舉有關(guān)的。如《唐摭言》,幾乎就都是記錄唐代科舉的事,又《唐語林》、《北夢(mèng)瑣言》等筆記小說中都記錄了大量與科舉有關(guān)的事。一些文學(xué)作品,如傳奇小說也是以進(jìn)士科舉為題材,至于科舉詩則更不待言。從文體發(fā)展的情況來看,律賦的形成就不能不說與唐代的科舉有關(guān)了,彭紅衛(wèi)的《唐代律賦考》對(duì)唐代律賦的產(chǎn)生及演變過程有詳細(xì)的考證。這些都是科舉對(duì)文學(xué)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明證。綜上所述,筆者認(rèn)為我們可以從另一個(gè)角度來思考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很明顯,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的影響是相互的,作為一種在唐代最引人注目的取士制度,反應(yīng)在文學(xué)上也是深刻的,那么,我們有理由認(rèn)為,因?yàn)榭婆e的出現(xiàn),在唐代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文學(xué)———科舉文學(xué)①。所謂文學(xué),《新編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以語言文字為記述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xiàn)實(shí)的藝術(shù),包括戲劇、詩歌、散文等。”[2]從科舉對(duì)社會(huì)產(chǎn)生的影響看,科舉完全可以稱之為一種文化,而與之相關(guān)的一些作品,如詩歌、小說、散文,還有在科舉考試中產(chǎn)生的大量省試詩、試策、律賦,都是用語言文字記述下來的、反應(yīng)客觀現(xiàn)實(shí)的藝術(shù)。由此,我們就找到了對(duì)唐代科舉進(jìn)行研究的另一個(gè)視角,那就是,以科舉文學(xué)為研究對(duì)象進(jìn)行研究。唐代科舉對(duì)唐代的政治和社會(huì)生活產(chǎn)生了那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了唐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那么,單從詩歌或者小說的角度、從制度本身來觀照科舉文學(xué)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不能算是完全地把握了科舉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劉海峰在《科舉文學(xué)與“科舉學(xué)”》一文中指出:“大量反映科舉活動(dòng)的文學(xué)作品,尤其是個(gè)案人物的科舉經(jīng)歷和體驗(yàn)的細(xì)節(jié),有助于重構(gòu)科舉場(chǎng)景,還原科舉實(shí)態(tài),有助于加深對(duì)科舉的認(rèn)識(shí),研究科舉文學(xué)為全面深入地了解科舉制提供具體而生動(dòng)的歷史圖景,可以豐富‘科舉學(xué)’的內(nèi)容,拓展‘科舉學(xué)’的空間。”[3]從文學(xué)的角度進(jìn)行科舉的研究,研究者們已經(jīng)做過很多艱難而有成效的工作,也正如劉海峰在上文說的那樣:“從文學(xué)角度研究‘科舉學(xué)’,成果層出不窮,除了集中研究八股文、試帖詩以外,還關(guān)注科舉制與《文選》學(xué)、與唐代進(jìn)士行卷、唐詩及唐宋傳奇、唐宋的韻圖、唐宋律賦、元曲及明清小說等的相互關(guān)系,還有大量關(guān)于文學(xué)家的科舉生涯、文學(xué)群體的科舉生活與心態(tài)、文學(xué)作品與科舉的關(guān)系、古代文人的科第情結(jié)、舉子與青樓文學(xué)等方面的論文出現(xiàn)。”雖然如此,我以為,既然能夠提出科舉文學(xué)這個(gè)概念,那么我們也能從科舉文學(xué)的角度對(duì)這一個(gè)領(lǐng)域進(jìn)行研究,而不是把視角只限于“科舉與文學(xué)”的研究。唐代科舉文學(xué),本身就是構(gòu)成唐代文學(xué)的一個(gè)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然也可以作為唐代文學(xué)研究的一個(gè)對(duì)象,從文學(xué)的角度對(duì)之進(jìn)行系統(tǒng)的研究。唐代的科舉文學(xué)研究,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作為一個(gè)研究領(lǐng)域在唐代文學(xué)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也是“文學(xué)研究”原本的任務(wù)。
二、唐代科舉文學(xué)的研究范圍
從筆者能查到的資料來看,現(xiàn)在對(duì)科舉文學(xué)的研究,從文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的,主要是在小說與詩歌,如鄭曉霞的《唐代科舉詩研究》,滕云的《唐代落第詩研究》,還有一些碩士論文也是從落第詩的角度進(jìn)行研究①。近年來,學(xué)界對(duì)唐代的省試詩研究也逐漸多了起來[4],但都還在詩歌的范圍。從小說角度出發(fā)的則應(yīng)該是程國賦先生的《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的有關(guān)章節(jié)和王汝濤的《唐代小說與唐代政治》的有關(guān)章節(jié)。而從文學(xué)的角度對(duì)唐代科舉中的賦及贈(zèng)序等的研究則極少見。唐代科舉文學(xué)的研究范圍,筆者以為可以包括以下內(nèi)容:唐代科舉詩、唐代與科舉有關(guān)的筆記小說、唐傳奇、科舉賦、還有與科舉有關(guān)的各種贈(zèng)序等。似乎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東西,但是我們從文學(xué)的角度來看,則會(huì)發(fā)現(xiàn)很多新的東西。唐代科舉雖承隋制,但并非一成不變地沿用,而是有了較大的改變,對(duì)于隋代科舉的具體情況,杜佑的《通典》、《隋書》、馬端臨的《文獻(xiàn)通考》都提到過,《通典》卷十四《選舉二》說:“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謹(jǐn)、清平才干二科舉人。……煬帝始建進(jìn)士科。”[5]《隋書》卷第三云:“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jié)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fēng)化。強(qiáng)毅正直,執(zhí)憲不撓,學(xué)業(yè)優(yōu)敏,文才美秀,并為廊廟之用,實(shí)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御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采錄,眾善畢舉,與時(shí)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yuǎn)。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備。朕當(dāng)待以不次,隨才升擢。”[6]其實(shí)隋代的科舉取士之法并不清楚,唯劉肅《大唐新語》卷十《厘革》云“隋煬帝改置明、進(jìn)二科”[7],雖隋代已經(jīng)有明經(jīng)進(jìn)士之科目,但隋的科舉是如何進(jìn)行的并不明確。按諸書所說唐承隋制,大概其內(nèi)容也差不多,只是后來唐代的科舉制度發(fā)生了改變,如秀才一科最終消失,并增加了明法、明字、明算三科。再如明經(jīng)本與進(jìn)士一樣,不分高下,到唐代慢慢演變?yōu)檫M(jìn)士倍受重視,而明經(jīng)則出現(xiàn)了“明經(jīng)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的故事[8]。唐代科舉其實(shí)一開始與文學(xué)并未有多大的關(guān)系,《新唐書選舉志》說:“凡進(jìn)士,試時(shí)務(wù)策五道,帖一大經(jīng)。經(jīng)策全能為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為乙第。”足見科舉與文學(xué)并沒有在一開始就發(fā)生了關(guān)系,《選舉志》又說:“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建言,明經(jīng)多抄義條,進(jìn)士惟誦舊策,皆無實(shí)才,而有司以人數(shù)充第。乃詔自今明經(jīng)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jìn)士試雜文兩篇,通文律者然后策試。”[9]至此,科舉與文學(xué)才算正式發(fā)生了關(guān)系。然孟二冬在《登科記考補(bǔ)正》《別録上》的按語中說:“按進(jìn)士試雜文,先用賦,后增以詩,皆在玄宗時(shí)。”[10]那么至遲在玄宗時(shí),科舉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就非常密切了。談到科舉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就不能不談到唐詩與舉的關(guān)系,自嚴(yán)羽《滄浪詩話•詩評(píng)》說:“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xué),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11]關(guān)于唐詩與科舉關(guān)系的探討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到現(xiàn)代也還有人在討論這個(gè)問題。如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就談及這個(gè)問題,他認(rèn)為進(jìn)士試詩賦時(shí)唐詩已經(jīng)有了長足的發(fā)展,科舉對(duì)唐詩并無促進(jìn)作用,相反還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①。筆者認(rèn)為唐代科舉對(duì)文學(xué)的影響并不能只看到科舉跟詩歌的關(guān)系,而應(yīng)該全面地考察。文學(xué)并不就只是詩歌,雖然唐詩是唐代文學(xué)的主流,但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學(xué)樣式。程千帆先生有一段話說得非常有道理,他說:“個(gè)人年來涉獵文史,鳩集了一些有關(guān)這些問題的資料,因而大致明白了進(jìn)士行卷是怎么一回事,并且進(jìn)一步認(rèn)識(shí)到,對(duì)于唐代文學(xué)發(fā)展起著進(jìn)一步積極作用的,并非科舉制度本身,而是在這種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這一特殊風(fēng)尚。”[12]確實(shí),如果光從科舉制度本身來看,與之有關(guān)的只有省試詩,而在科舉制度的影響下,文學(xué)產(chǎn)生的一些新內(nèi)容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對(duì)唐代科舉文學(xué)的研究,應(yīng)該改變那種只把重心放在詩歌和筆記小說上的現(xiàn)象。當(dāng)然,唐代詩歌作為有唐一代的最主要的文體,受關(guān)注程度高這本身也無可厚非,但是,我們要做的是對(duì)科舉文學(xué)進(jìn)行全面的研究,那就不能,也不應(yīng)當(dāng)只把研究視野局限在詩歌或筆記小說的范圍內(nèi),而應(yīng)該把視野拓展到科舉文學(xué)的各個(gè)方面。只有這樣,才能算是對(duì)科舉文學(xué)的全面的研究。
三、唐代科舉文學(xué)的演變
淺論唐代海外貿(mào)易管理
【內(nèi)容提要】
大體說來,唐代海外貿(mào)易的管理,主要包括唐政府對(duì)朝貢貿(mào)易和市舶貿(mào)易的管理兩個(gè)方面。以下依據(jù)有關(guān)史料,分別予以探討。(一)朝貢貿(mào)易的管理唐政府不僅與其周邊諸少數(shù)族政權(quán)之間存有朝貢貿(mào)易,與海外諸國之間也存有朝貢貿(mào)易,同樣在政權(quán)關(guān)系的政治色彩的光環(huán)下,進(jìn)行著實(shí)際上的物與物的商品交換。史料表明,在朝貢使的禮儀接待和貢物的回贈(zèng)酬答方面,唐政府對(duì)海外諸國也實(shí)行著與對(duì)周邊諸蕃相同的制度和規(guī)定。《新唐書》卷221下《西域傳》贊語稱唐對(duì)朝貢使“有報(bào)贈(zèng)、冊(cè)吊、程糧、傳驛之費(fèi),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堅(jiān)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視地遠(yuǎn)近而給費(fèi)”。[1]就對(duì)朝貢物品的酬答而言,唐政府也有著一套較為細(xì)致的制度,其詳見前文民族貿(mào)易的管理部分,茲不贅述。不過,有所不同的是,在朝
論文分類
國際經(jīng)濟(jì)國際貿(mào)易行業(yè)經(jīng)濟(jì)新經(jīng)濟(jì)學(xué)中國經(jīng)濟(jì)國債研究發(fā)展戰(zhàn)略稅收理論稅務(wù)研討財(cái)政稅收財(cái)政政策財(cái)稅法規(guī)財(cái)政研究金融研究證券金融證券投資債務(wù)市場(chǎng)地方戰(zhàn)略銀行管理公司研究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保險(xiǎn)學(xué)西方經(jīng)濟(jì)經(jīng)濟(jì)貿(mào)易保險(xiǎn)信托計(jì)量經(jīng)濟(jì)財(cái)務(wù)分析期貨市場(chǎng)
大體說來,唐代海外貿(mào)易的管理,主要包括唐政府對(duì)朝貢貿(mào)易和市舶貿(mào)易的管理兩個(gè)方面。以下依據(jù)有關(guān)史料,分別予以探討。
(一)朝貢貿(mào)易的管理
唐代服飾對(duì)現(xiàn)代服裝設(shè)計(jì)的影響
一、絢麗多彩的唐代服飾形成因素
唐代疆域?qū)拸V,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jì)繁榮,對(duì)外開放,促進(jìn)了多元文化相互融合。這種多民族性與其他西域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和相互借鑒催生了手工業(yè)的不斷發(fā)展,特別是紡織業(yè)中的印染技術(shù)得到了空前繁榮。唐代染織工藝,從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域新穎的染料和配色方式的引進(jìn),為唐朝的服飾增加了新的圖案和色彩。唐代服飾染料大多數(shù)來自古印度及西域地區(qū)的植物染料和礦物質(zhì)。異域染料對(duì)唐代服飾的影響是一個(gè)漸漸滲透,又互相融合的過程。譬如,紅花染料是通過與西域的文化交流而引入,在傳入中原后,中原染織技術(shù)不成熟,人們常把紅花染料調(diào)配染成的紡織品為橙色或黃色,而并非紅色,常把紅花中的黃色素當(dāng)作珍貴的黃色染料來使用。到了唐代,人們擴(kuò)大紅花染料種植面積,加之不斷改進(jìn)染料配方,將紅花中的黃色素和紅花素用酸、堿分解提煉處理,便可染成橙色、黃色、水紅色、蓮紅、桃紅色、銀紅、胭脂等多種顏色。外來艷麗自然的黃色調(diào)染料郁金、奕華、和黃屑,紅色調(diào)染料還有蘇扔、山石榴等,使唐代服飾染料變得更為豐富,服飾色彩也變得絢麗多彩。據(jù)說楊貴妃最愛穿郁金香草染成的黃裙,我們從唐代詩人李商隱的詩句“折腰多舞郁金裙”證明了這一點(diǎn)。再從唐代李白的“移舟木蘭卓,行酒石榴裙”,萬楚的“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等詩句,說明了紅裙顏料從植物染料石榴花中提取,由此紅裙稱之為“石榴裙”。在唐代人們運(yùn)用天然植物充當(dāng)服飾染料的方法和技術(shù),表達(dá)了人們的服飾外表形態(tài)以及人們對(duì)色彩審美的變化。絢麗多彩的服飾與人們審美變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中外文化交融促進(jìn)了唐代服飾豐富多彩。唐代人們受佛教美學(xué)的影響頗深,在人們的觀念中,形成了萬物有情、萬物皆有生命之說。正如后代的美學(xué)理論家婆羅在《舞論》中解釋“:艷情常由常情(固定的情)歡樂而生,以光彩的服裝為其靈魂。正如世間凡是清白的,純潔的,光彩的或美麗的都以‘艷’表示”。艷麗的色調(diào)與創(chuàng)新的裝飾手法結(jié)合,使唐代服飾的色調(diào)由古樸色調(diào)變?yōu)槊骺炱G麗色調(diào),并洋溢著濃厚的異域風(fēng)情,服色的艷麗華美前所未有。唐代織錦不但色彩繁麗,而且圖案典雅華美,我們從唐代圖案結(jié)構(gòu)的變化便知,慣用通幅排列和菱格骨架排列,增添了圓形骨架排列表現(xiàn)了圖案紋樣的多樣性,圖案構(gòu)圖活潑自由、疏密勻稱、豐滿圓潤。我們從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可以證實(shí)。《簪花仕女圖》(從圖左起)第一位貴婦的服飾,內(nèi)穿高束曳地紅底色長裙,束裙上由圓形骨架排列的寶相花圖案,使本來因色彩的艷麗而濃重俗氣的畫面產(chǎn)生統(tǒng)一的視覺效果,從而達(dá)到了“艷而不俗”的色彩美感。第二(左起)位貴婦服飾,內(nèi)穿白底紫綠色團(tuán)花紋樣高束曳地長裙,外罩紅色背中嵌有少許綠色的紗衫,紗衫面料色彩采用大面積朱紅色與小面積綠色補(bǔ)色對(duì)比,外觀十分艷麗。第三(左起)位貴婦,內(nèi)穿紅色高束曳地長裙、外穿白色菱形圖長衫,雖有點(diǎn)呆板,但肩上的深紫色披帛,其卷草紋圖案由淡紅、綠、藍(lán)等色構(gòu)成,紅裙與披帛上以淡紅色點(diǎn)綴,色彩濃艷富貴。第四(左起)位侍女,她外穿紅色菱形圖案的紗衫,內(nèi)穿圓形蓮花圖裙衫,腰系白色圓形圖案的披帛,趨于簡單的搭配,達(dá)到了“典雅不俗”的境界。第五(左起)位貴婦,她內(nèi)穿紅底色團(tuán)花高束曳地長裙,圓形花團(tuán)錦簇、層次分明,有富麗堂皇之感。第六(左起)位貴婦,頭插牡丹,身著紅色長裙,裙的下方顯現(xiàn)出圓形寶相花紋蔽膝,外披紫褐色紗罩衫,面料顏色深沉,上搭朱紅色飾有藍(lán)白卷草紋樣披帛,紅裙與朱紅色披帛互相呼應(yīng),增強(qiáng)了裝飾效果的節(jié)奏感,顯現(xiàn)了圖案與色彩的妙用。
二、絢麗多彩的唐代服飾成為身份的重要標(biāo)志
服飾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但在不同的時(shí)代背景下總與政治色彩聯(lián)系在一起。服色作為一種無聲的語言成為我國歷朝歷代尊卑等級(jí)的重要標(biāo)志,服色在唐代成為社會(huì)身份的鮮明符號(hào)。就黃色而言,在色譜中,黃色明度最高,作為生命之依的太陽的顏色,同時(shí)也是佛教的神圣之色,為袈裟所用。純凈而亮麗的黃色為佛教所推崇,認(rèn)為其有驅(qū)逐邪惡的力量,黃袍加身就成為帝王的專寵。譬如,在唐代高宗時(shí)期,認(rèn)為黃近似于日,日是帝王的象征,禁止官民穿著黃色,把赭黃規(guī)定為皇帝常服專用之色。從早期閻立本的《步輦圖》便知,畫面描繪了貞觀十四年(640)吐蕃(今西藏)贊普松贊干布派使者祿東贊入長安見唐太宗的場(chǎng)面。畫卷賦色沉著深厚,利用畫中唐太宗身著黃袍表明了至尊天子的身份。“貴賤有級(jí),服位有等,……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賈誼《新書•服疑》),以服色辨別身份的等級(jí)差別,衣紫、緋者高貴,著青衫者貧賤成為社會(huì)定式。由于紫色難得,所以紫衣為貴是西周以來逐漸形成,唐高祖時(shí)代,紫色、緋色為高級(jí)官員品服,限制他人任意選用。他還規(guī)定了大臣們的常服用色,親王至三品用紫色大團(tuán)花的絞羅制作,五品以上用朱色小團(tuán)花綾羅制作,六品用檸檬黃色幾何紋綾制作,七品用綠色龜甲、雙巨、十花綾制作,九品用青色絲布雜綾制作。從此正式形成了黃、紫、朱、綠、青、黑、白等服飾顏色序列,黃色則成為了封建社會(huì)色彩等級(jí)的最高標(biāo)志。雖說白色在服飾顏色序列中排列最后,但唐代首開先河,流行舉子著白衣,這與佛教中的善“白”思想觀念有著某種必然的聯(lián)系。佛教的色彩美學(xué)有象征性的一面,亦有裝飾性與自然性的一面。從《唐六典》記載:天子服有白紗帽,又唐制,新進(jìn)士皆白袍,故有“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之句。而至唐之后,白色唐錦的使用引人注目,除去做地色之外,還常常用來勾勒紋樣的輪廓。白居易用“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yīng)似天臺(tái)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詩中描繪了“繚綾”的形狀和色彩,用“鋪煙”、“簇雪”作比,寫出了底、花俱白。可見“白”色的作用意味深長。
三、絢麗多彩的唐代服飾給予的啟示
絢麗多彩的唐代服飾主要體現(xiàn)服飾顏色與審美觀的變革,往往色彩的對(duì)比與和諧,色相的色度和純度,對(duì)人的高級(jí)神經(jīng)細(xì)胞的興奮和抑制產(chǎn)生了各不相同的作用,使得不同的顏色在人的審美感受中也會(huì)產(chǎn)生不同的表現(xiàn)性。通常色相的色度和純度較高的顏色,其相對(duì)審美價(jià)值較高,反之則較低。作為皇帝御用顏色的黃色,其色相的色度和純度都是最高的。“在整個(gè)光譜的所有色彩中,最亮的是黃色,以黃色為中心,越往兩端,亮度就越小。”其二,由于不同顏色對(duì)比效果,特別是兩種互補(bǔ)色對(duì)比,如黃與紫、紅與綠、橙與藍(lán)并置在一起,便可產(chǎn)生最強(qiáng)烈的色彩對(duì)比效果,均顯得更加明亮艷麗,如張萱在《搗練圖》中,共畫了十二人,在服飾色彩選用了朱紅、朱黃、草綠、翠綠、石青、白等顏色表達(dá),紅色與綠色之間相互對(duì)比,交相輝映,既有富麗華美,又有明快活潑的情調(diào)。再從張萱的《虢國夫人游春圖》中可見,服飾用濃淡墨色勾勒,色彩以粉紅、胭脂紅、淺黃、蟹青、赭石、花青等多種顏色描繪,繽紛艷麗的服飾色調(diào)在濃淡墨色的調(diào)和下,光艷炫目。張萱在整個(gè)畫面中很好地運(yùn)用了色度的層次變化和冷暖相生規(guī)律,畫面和諧統(tǒng)一在輕重、強(qiáng)弱、明暗及色相的對(duì)比之中。艷麗的服飾在灰色馬的襯托下,顯現(xiàn)了絢麗多彩的效果,又豐富了畫面的層次感。唐代服飾色彩搭配的精妙之處,主要體現(xiàn)了服飾用色注重色彩的相互對(duì)比,用各種不同性質(zhì)的色彩對(duì)比,互相襯托,相互穿插,色彩層次分明,色中有色,色中有變,于厚重中變化,于深淺中見層次,于變化中求統(tǒng)一。這給當(dāng)今許多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以啟迪。譬如,我國著名設(shè)計(jì)師勞倫斯•許設(shè)計(jì)的“敦煌寫意”,整件禮服用綠色做底,精心繡上五彩繽紛的花卉,微妙的是在大腿與中腿之間,采用朦朧透明的金紗面料,行走時(shí)裙擺猶如行云流水,顯現(xiàn)流麗的色彩,呈現(xiàn)唐代敦煌意境。再看勞倫斯•許設(shè)計(jì)“東方祥云”龍袍、“孔雀”、“丹鳳朝陽”等禮服,正是汲取了唐人用色精華,繡以絢麗多彩的吉祥圖案,意在讓絢麗的東方文化走向世界,再次向世界展示神奇的東方神韻。再如我國知名品牌———“漁”牌服飾。“漁”牌傳承我國傳統(tǒng)服飾精髓,在2005春夏:“蝴蝶”、2005秋冬:“刀馬旦”、2006秋冬:“絲綢之旅”、2012秋冬:“錦繡”等系列服飾,傳承了唐代絢麗多彩的服飾色彩,艷麗而醒目。“漁”牌在刺繡中的水溶浮雕繡花、剪貼繡花等圖形配色上,注重色彩的相互對(duì)比,相互穿插,做到了色中有色,色中有變,層次分明,于變化中求統(tǒng)一。設(shè)計(jì)師們用現(xiàn)代設(shè)計(jì)理念為平淡的生活注入舞臺(tái)般熱鬧的情愫,在“漁”的世界里,以復(fù)古為流行,在設(shè)計(jì)中進(jìn)行重構(gòu),讓“漁”變得新穎,而且與眾不同,由此表達(dá)“漁”牌服飾最完美的意境。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一段輝煌燦爛的鼎盛歲月,絢麗多彩的服飾在當(dāng)代服飾文化和時(shí)尚流行中的作用不容忽視。筆者認(rèn)為,如今我們不提倡唐代服飾色彩等級(jí)觀,但當(dāng)代中國服飾文化仍然需要體現(xiàn)多樣性和創(chuàng)造性。我們應(yīng)當(dāng)弘揚(yáng)民族精神,以“古為今用”的思想理念,品味古老的神韻。我們知道,任何文化藝術(shù)的創(chuàng)新都少不了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和異域文化的融合,在大唐盛世中我們不僅感受到唐代服飾的魅力,同時(shí)還讓我們看到唐代與周邊多國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它們的相互融合構(gòu)筑了唐代最絢麗的服飾,這種立足于民族服飾文化的沃土,博采眾長,吸收異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的設(shè)計(jì)理念值得我們當(dāng)今借鑒和學(xué)習(xí)。唐代服飾色彩有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魅力和厚重的人文底蘊(yùn),是現(xiàn)代服飾設(shè)計(jì)創(chuàng)新的寶藏和源泉。如今我們?cè)诮虒W(xué)中,該考慮如何選擇其中的服飾元素去體現(xiàn)唐代文化的精髓與神韻,能動(dòng)地吸收和借鑒唐代服飾色彩的文化理念,與各類時(shí)尚理念加以整合,以合乎自身的目的,讓我們“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賦傳統(tǒng)以新意”,將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相結(jié)合,將傳統(tǒng)與西方服飾相結(jié)合,新創(chuàng)一些符合其鑒賞趣味的服飾元素,使我們的設(shè)計(jì)作品注入新的生命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