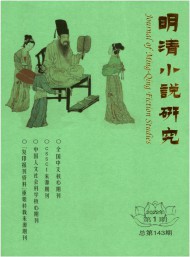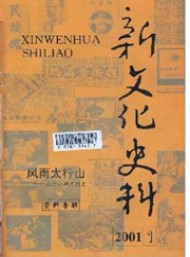晚清漢學范文10篇
時間:2024-03-24 14:53:30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晚清漢學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晚清漢學研究論文
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所指為兩漢時期的學術思想。清代的“漢學”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時代和士人的思想、學術差異而有所不同。
清中期以后,重實證的乾嘉學風漸興,學者治經多尊信、歸依漢儒經說,貶抑宋學,形成“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乾嘉漢學。道咸以降,隨著今文經學的興起,清代“漢學”的概念又為之一變。清末民初,學者多把今、古文經學都納入漢學范疇。
清代“漢學”的這種流變,正好反映了清代學術主流的時代特征,也為中國現代學術的萌生、發展打開了一道閘門。
清代以來,“漢學”一詞使用很廣而語義不同。一為彰顯于清中期的傳統漢學(HanStudies),相對于宋學而言,偏重考據研究,近代學者多沿用此意;一為18世紀以后產生于歐洲的西方漢學,即Sinology,本意為中國學,中譯時借用了“漢學”一詞,內容包括有關中國的歷史、學術、文化和社會等所有研究,不限于考據。清末學者已注意到兩者的差異,經學家皮錫瑞指出:日本“所謂‘漢學重興’者,乃其國人以中國之學為漢學,非中國之所謂‘漢學’,且亦冀幸之詞耳,未知將來如何?”(《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其后,兩者在觀念、方法上有所借鑒和汲取,但并未渾然一體。事實上,傳統漢學也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概念。
漢代經學與宋明理學曾為儒學發展的兩個高峰,也是中國傳統學術的兩大范式。清中期以后的學術主流是漢學,士人治經多歸依于漢儒經說,在研究方法和價值取向方面也呈現出異于前代的學術風尚。關于“漢學”一詞的出現,目前學術界的說法有二:多數論著認為“漢學”一詞最早見于惠棟的《易漢學》;此外,劉師培曾說,康熙年間的臧琳“樹漢學以為幟,陳義淵雅”(《清儒得失論》)。有的論著因此認為臧琳最先把經學研究稱作“漢學”。實際上,臧琳和惠棟只是加強了經學領域“唯漢是好”的趨向。“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而且均指兩漢時期的學術思想。南宋劉克莊評論漢、魏學術云:“《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季父易稿》,《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他所謂漢學既指西漢之學,又包括東漢鄭玄之學,認為“鄭司農區區訓詁,不離漢學”(《恕齋讀易詩》,《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宋人所謂“漢學”多側重于兩漢《易》學。一些學者貶評漢儒以象、數釋《易》,而重視王弼以理求《易》,這與宋學背景密切相關。元、明時期,“漢學”不再囿于兩漢《易》學,而涉及諸多經學領域。宋末元初的戴表元提到:“秦禍息,漢學興,傳言者雜”(《天原發微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他推重西漢之學,認為“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注猶近古哉!”(《急就篇注釋補遺自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元、明士人的著述中,“漢學”一詞流傳不絕。
清代學者逐漸尊信和歸依于漢儒經說,“漢學”的價值評判也在實證學風的輝映下發生了根本變化。康熙年間,士人多以“漢人之說”、“兩漢之學”指稱漢學,這與當時治經不分漢、宋的氛圍相關。不過,少數學者已明確崇信兩漢經學,而排斥宋儒經解,從而推動了清代漢學的興起。武進臧琳為諸生30年,生前默默無聞,讀經不輟,將心得輯為《經義雜記》30卷。該書無“漢學”之名,卻有鮮明的尊漢抑宋傾向,故有“漢學”之實。他自稱“考究諸經,深有取于漢人之說,以為去古未遠也”(《經義雜記》“題記”,卷一)。臧琳的書未刊行,即受到閻若璩的贊譽,稱其“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訓詁,又雅擅二劉、楊子云之長”(《序》,《經義雜記》“敘錄”)。康熙年間,“漢學”在江南學術圈中不再含有宋儒那樣的貶義。乾隆九年,惠棟著成《易漢學》8卷,仍著眼于《易》學而論漢學,與宋儒的概念不無相似,但《易漢學》既揭橥漢學的旗幟,又明確排斥宋儒經說,彰顯了尊崇漢學的色彩。惠棟為首的吳派學者歸依漢儒經說,“漢學”成為其經學體現。稍后,戴震為首的皖派興起,不單純“唯漢是好”,而強調求是,但吳、皖學者均重視音韻訓詁,由考據以求義理。他們解經、注經多歸依于東漢經學,一時形成所謂“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局面。
晚清漢學的源流探究論文
“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所指為兩漢時期的學術思想。清代的“漢學”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時代和士人的思想、學術差異而有所不同。
清中期以后,重實證的乾嘉學風漸興,學者治經多尊信、歸依漢儒經說,貶抑宋學,形成“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乾嘉漢學。道咸以降,隨著今文經學的興起,清代“漢學”的概念又為之一變。清末民初,學者多把今、古文經學都納入漢學范疇。
清代“漢學”的這種流變,正好反映了清代學術主流的時代特征,也為中國現代學術的萌生、發展打開了一道閘門。
清代以來,“漢學”一詞使用很廣而語義不同。一為彰顯于清中期的傳統漢學(HanStudies),相對于宋學而言,偏重考據研究,近代學者多沿用此意;一為18世紀以后產生于歐洲的西方漢學,即Sinology,本意為中國學,中譯時借用了“漢學”一詞,內容包括有關中國的歷史、學術、文化和社會等所有研究,不限于考據。清末學者已注意到兩者的差異,經學家皮錫瑞指出:日本“所謂‘漢學重興’者,乃其國人以中國之學為漢學,非中國之所謂‘漢學’,且亦冀幸之詞耳,未知將來如何?”(《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其后,兩者在觀念、方法上有所借鑒和汲取,但并未渾然一體。事實上,傳統漢學也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概念。
漢代經學與宋明理學曾為儒學發展的兩個高峰,也是中國傳統學術的兩大范式。清中期以后的學術主流是漢學,士人治經多歸依于漢儒經說,在研究方法和價值取向方面也呈現出異于前代的學術風尚。關于“漢學”一詞的出現,目前學術界的說法有二:多數論著認為“漢學”一詞最早見于惠棟的《易漢學》;此外,劉師培曾說,康熙年間的臧琳“樹漢學以為幟,陳義淵雅”(《清儒得失論》)。有的論著因此認為臧琳最先把經學研究稱作“漢學”。實際上,臧琳和惠棟只是加強了經學領域“唯漢是好”的趨向。“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而且均指兩漢時期的學術思想。南宋劉克莊評論漢、魏學術云:“《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季父易稿》,《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他所謂漢學既指西漢之學,又包括東漢鄭玄之學,認為“鄭司農區區訓詁,不離漢學”(《恕齋讀易詩》,《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宋人所謂“漢學”多側重于兩漢《易》學。一些學者貶評漢儒以象、數釋《易》,而重視王弼以理求《易》,這與宋學背景密切相關。元、明時期,“漢學”不再囿于兩漢《易》學,而涉及諸多經學領域。宋末元初的戴表元提到:“秦禍息,漢學興,傳言者雜”(《天原發微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他推重西漢之學,認為“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注猶近古哉!”(《急就篇注釋補遺自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元、明士人的著述中,“漢學”一詞流傳不絕。
清代學者逐漸尊信和歸依于漢儒經說,“漢學”的價值評判也在實證學風的輝映下發生了根本變化。康熙年間,士人多以“漢人之說”、“兩漢之學”指稱漢學,這與當時治經不分漢、宋的氛圍相關。不過,少數學者已明確崇信兩漢經學,而排斥宋儒經解,從而推動了清代漢學的興起。武進臧琳為諸生30年,生前默默無聞,讀經不輟,將心得輯為《經義雜記》30卷。該書無“漢學”之名,卻有鮮明的尊漢抑宋傾向,故有“漢學”之實。他自稱“考究諸經,深有取于漢人之說,以為去古未遠也”(《經義雜記》“題記”,卷一)。臧琳的書未刊行,即受到閻若璩的贊譽,稱其“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訓詁,又雅擅二劉、楊子云之長”(《序》,《經義雜記》“敘錄”)。康熙年間,“漢學”在江南學術圈中不再含有宋儒那樣的貶義。乾隆九年,惠棟著成《易漢學》8卷,仍著眼于《易》學而論漢學,與宋儒的概念不無相似,但《易漢學》既揭橥漢學的旗幟,又明確排斥宋儒經說,彰顯了尊崇漢學的色彩。惠棟為首的吳派學者歸依漢儒經說,“漢學”成為其經學體現。稍后,戴震為首的皖派興起,不單純“唯漢是好”,而強調求是,但吳、皖學者均重視音韻訓詁,由考據以求義理。他們解經、注經多歸依于東漢經學,一時形成所謂“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局面。
清學研究論文
清學沿承宋、元、明,但有著自己的特點。
一、無主峰可指,無大脈絡可尋
關于清學,錢穆在《〈清儒學案〉序》中曾說:“至論清儒,其情勢又與宋、明不同;宋、明學術易尋其脈絡筋節,而清學之脈絡筋節則難尋。清學之脈絡筋節之易尋者在漢學考據,而不在宋學義理。”又說:“清儒理學既無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無大脈絡大條理可尋,如宋儒之有程、朱與朱、陸。”[1](P361-362)論斷精到。誠如錢氏所言,清代于順治、康熙朝雖有一批理學名儒名臣,但多守成而少創獲,實無可與明展陸九淵心學之王守仁相比肩,更不能與宋學開派者、集大成者的程顥、程頤、朱熹和陸九淵相比擬。“無主峰可指”,“無大脈絡大條理可尋”,洵為有清一學的一個特點。
二、學理無創新,重在道德規范
清學,總的說來,陸王心學一系趨于衰頹,程朱理學一脈則多在于衛護、闡釋程、朱之說,于學理無甚創新發展,而作為清政府的官方統治思想,更為突出的是綱常倫理的道德規范,強調躬行實踐。康熙帝稱“自幼好讀性理之書”,將朱熹從原配享孔廟東廡先賢之列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頒行《朱子全書》、《四書注釋》、定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但他對理學有自己的解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683年12月11日)與講官張玉書、湯斌等人談論理學時說:“朕見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之事全與其言悖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皆與道理符合,此真理學也。”張玉書回應說:“皇上此言真至言也。理學只在身體力行,豈尚辭說。”[2](P1089-1090)三十三年(1694),又以“理學真偽論”為題考試翰林院官員。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1715年12月12日),康熙帝在聽取部院各衙門官員面奏后訓誡說:
爾等皆讀書人,又有一事當知所戒,如理學之書,為立身根本,不可不學,不可不行。朕嘗潛玩性理諸書,若以理學自任,則必至于執滯己見,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實無愧于屋漏乎?……昔熊賜履在時,自謂得道統之傳,其沒未久,即有人從而議其后矣。今又有自謂得道統之傳者,彼此紛爭,與市井之人何異?凡人讀書,宜身體力行,空言無益也。[3](P2222)
王先謙駢文研究論文
摘要:《十家四六文鈔》和《駢文類纂》是晚清著名樸學家王先謙編選的兩部駢文選本,本文結合這兩部選本分析了王先謙對待駢散之爭的態度以及他的駢文理論,這對于我們全面認識王先謙的學術思想是有幫助的。
關鍵詞:王先謙;駢文;選本;文論
王先謙是晚清著名樸學家,一生撰著多種樸學著作,可謂成就卓著。對于選本編纂王先謙亦頗為重視,其編纂的《續古文辭類纂》,收錄姚鼐《古文辭類纂》之后的古文作家、作品,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十家四六文鈔》和《駢文類纂》是他編選的兩部駢文選本。這兩部駢文選本反映了王先謙的駢文理論,也是王先謙學術思想的重要體現。
對待駢散之爭的態度
清代學術,自乾嘉漢學盛行,遂有漢、宋之爭,文章學領域的駢散之爭也隨之而起。桐城派固守古文義法,崇散拒駢;阮元一派,嚴格文筆之辨,崇駢拒散;李兆洛等人則主張援駢人散,以求拓展古文寫作之新境界。王先謙身處晚清時代,以漢學名家,他既纂輯了以桐城“義法”為旨歸的《續古文辭類纂》,又編選了《十家四六文鈔》和《駢文類纂》,那么,他對駢散之爭有怎樣的看法呢?
王先謙對待駢散之爭的態度與其對待漢宋之爭的態度是相一致的。
清末經學管理論文
當代儒學話語——無論是敘事還是論辯,基本上循著兩個路數:一是歷史的,重其發展脈絡、遷延歷程;二是觀念的,往往揀金棄沙,只把握根本的傳統。前者多為治歷史學者所取,處之極端,往往陷溺于所謂“史學的偏見”。三十年代以還,喜宋明理學或研哲學者,于此多有掊擊,茲不具論。而后者為習哲學諸人慣常所用,不管是批判儒家,還是復興儒學,關鍵處均是一些觀念鋪陳和范式架構,難免于“良知的傲慢”之譏。海外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派學者對此多有指證。如張灝謂“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一種哲學體系或學術研究的傾向是危險的”。[1]自稱“更注重哲學的框架”以著述的艾爾曼也指出:迄今以新儒家討論為中心的思想史領域,只不過是“較為淺顯的中國哲學史”。深受德國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學史之取向的影響,普遍服膺“觀念史”的模式,“結果,中國思想史只能以敘事方式進行,精于哲學卻短于歷史脈絡”。[2]因現代知識體系的學科分際而造成的史、哲之別,深深濡染了當代的儒學識辨與言說,使儒家的本來面貌在強烈的古今之辯意識的現代闡釋之下,更多增添了難以圓合的裂痕。“史學的偏見”與“良知的傲慢”之爭訟與對壘不見消彌,反愈加劇。于此,若不能有更深刻的說明和消解緊張的有效途徑,勢必將成儒?Ы胂執雜錁車募笳習?BR>也許用發生學的方法以觀其眇是一可行之道。當代的儒學話語(批判的、旁觀的、弘揚的)及其復雜的形態,均是在百年間原有體系發生劇烈的動蕩、裂變、轉型過程之中的遷延或歧出。盡管有西學東來的重大外緣,但起決定因素的還是體系內在的變化。所以,對清末儒學的狀況作些了解和分析,當有助于這一問題的清理。另外,我們今天所說辯騰喧于口的儒學,早已走出了經學時代的范式,在形態上已被現代的知識體系所夾裹和切割,這一轉換的發生機制和微妙歷程也是饒有趣味的問題。本文即圍繞清末經學的解構和現代形態儒學的創發作一思考,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三大爭論宣告了經學時代的結束
清末,皮錫瑞總結有清一代經學。謂有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底,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后,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后,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于道。”[3]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承繼此說,以佛理生、住、異、滅喻思潮之流轉,將這一段思想史概括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又進而將清學“屢遷而返其初”的獨特現象解釋成為“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鄭許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4]鹿門“義愈推而愈高”、“一變而至于道”的說詞,明顯帶有保守的今文家自吹自許之意,遠不能和任公“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的揭示之敏銳與深刻相比。但皮、梁二人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是站在清學的落幕處,對已經逝去的一個時代作全景式的觀察和描述。這一“離場”的宏大敘事雖有助于從全體上把握清代學術的綱節,?灰歡蓯刮頤欽嬲氳角逖翁壞母叢勇雎韁小?BR>倒是《漢學師承記》這樣在今天看來過于偏宕、缺少客觀性的譜系,更能引發出來問題和思考。江藩堅執漢學的純潔性,以三惠之學為典范,擯除一切經世和義理的成分,甚至將公認的樸學開山顧炎武附贅在卷末。這一切都表現了乾嘉考據學發展到極盛之時,正統漢學家“唯我獨尊”、“目無余子”的自大心態。以經學考據為正統、以吳派為標準,不但徹底否定了程朱理學的權威,實際上也顛覆了儒學賴以存在的整個基礎。沉溺于文獻考據之中,以文本、音符為道統,可以無關社會、不涉人生,此固能成就一二經生的安身立命之業,但于整個社會、蕓蕓大眾懸隔千里。這絕不是孔孟的初衷。江藩的譜系學一方面說明考據在清代學術界的主流地位,至乾嘉后期勢力是何等的強大;另一方面視野如此的狹限,似乎也把儒學納入到了沒有出路的犄角之中。所以,隨后激起的反彈,在形式上是挽救儒學,而實質上則是“對于孔孟而得解放”,最終導致了傳統儒學的解體。梁啟超在解釋“道咸以后,清學曷為而分裂耶”時,舉出了內、外各三因。內因一是考據之范圍“甚拘迂”,末流落入空而不實;二是成一“漢學專制”之局,其騶卒多為盛氣臨人的“學閥”;三是自身發展,不斷突創,必至異端涌現。外因一是“嘉道以還,積威日馳,人心已漸獲解放”,學問必由虛逐實;二是咸同間,清學的根據地江浙一帶“受禍最烈,文獻蕩然”,致“百學中落”;三是國難日重,西學漸輸,學者“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對舊學體系做根本的沖擊。[5]錢穆也指出,“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皆有“途窮將變”之跡。諸先進“起而變之者,始于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于思人才,極于正學術”,最后導出康南海的“盡變祖宗之法”,于是乎傳統徹底瓦解。[6]“所謂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到這會只成為望古遙集的資料。考證學本已在落潮的時代,到這會更未絕如縷了”。[7]伴隨著漢學的衰落,是宋學復振的呼聲、今文經學的崛起和諸子學的興盛,正是在漢宋、今古文、經子三大爭論之中,一步一步迎來了經學時代的終結。
清后期的復宋思潮以“經世”為志幟,它并非簡單回到宋儒的義理之學,和清初的“漢宋兼采之學”也不盡相同。面對考據的學術霸權,先是理學家唐鑒等人發出抗爭的聲音;繼之桐城派的方東樹挑起了漢宋爭論的巨大波瀾,曾國藩以理學名臣身份所創下的經國大業無疑為復宋勢力增添了重要的法碼;最后是嶺南陳澧等人調和漢宋的努力,不但打擊了乾嘉學術的正統觀,而且也起到了分化漢學家陣營和扭轉清末漢學走向的作用。宋學派、桐城派、調和派均站在正統漢學的對立面,對乾嘉考據學的權威提出了重大的挑戰,動搖了漢學的獨霸地位。
清代前期的理學家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修身層面,服膺宋儒的道德義理,因缺乏對應現實的創造性而逐漸被邊緣化了。到了嘉慶年間,開始有一部分理學人物力圖糾正這種偏差,重新將社會政治內容納入儒家的信仰體系。如唐鑒的“守道救世”說,雖不離“守敬”和“窮理”的道德根本,但還是對儒家經世致用的關懷給予了相當的肯定。如果說積衰已久的理學之老鳳雛聲已難引起漢學正統派的注目;那么,來自桐城派的方東樹則以《漢學商兌》一書給了對方以極大的震憾。方著可以看作是漢學權力強壓下的反彈,所謂“孤蹤違眾,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力之弗勝也,要心有難已”,[8]頗能道出作者心跡。對于江藩門戶森嚴的譜系學,來自漢學陣營的焦循等人只是委蜿商榷。而龔自珍則以考核名實(“十不安”)的方式提出異議。唯方東樹直接了當,以強大火力直攻漢學要塞,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羅列材料,攸舉事實,對漢學家中重頭人物的言論,逐條批駁。方氏之言,多能切中漢學弊端,且有很強的針對性。如斥漢學“六蔽”之四,“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9]是指當時漢學家“內苞污行,外飾雅言,身為倡優而欲高談伏鄭”的普遍情形。[10]《漢學商兌》后來因得到曾國藩的大力表彰而風行一時,從此對考據學的抨擊日起而日興,漢學威勢開始走向衰落。是不是因為方東樹的批判而使漢學之焰“遂漸熄”尚可考量,[11]但陳澧《與徐子遠書》中的一段話卻明白道出道、咸之間小學頹敗的消息。“今海內大師,凋謝殆盡。……后生輩好學者,則不過二三人耳。夫以百年來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推原其故,非盡時文之為害”。[12]由是,漢宋調和之風日盛,漢學陣營迅速分化,形成了以嶺南派為中堅的綜合漢學與宋學的運動,純漢學退居到次席,晚清學風隨之大變。
反漢學思潮的得勢,從表面來看似乎只是清代義理、考據、詞章三大學術板塊的力量比重發生了改變,考據學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宋學派的義理和以桐城派為代表的詞章借學術復古的面貌重又恢復了自身的價值,奪回了自己在儒學中應占有的份額。但實際上,打落漢學正統派權威的既不是義理也不是詞章,而是經世致用之學。反漢學的三大思想流派都強調經世致用,這正是乾嘉考據學的致命弱點,以此為利器,對壘之下,漢學焉能不敗?但是,以經世思想批判漢學,同時也就面臨了脫軌的危險,傳統經學結構中的三個板塊可能一損俱損、一起打落,義理、詞章是不可能真正挽救經學的。如果說漢宋之爭尚能保持在傳統儒學體系之內而尚未出軌;那么,隨之而來的今古文之爭則從根本上顛覆了儒學,宣告了經學時代的完結。
儒學形態轉換管理論文
當代儒學話語——無論是敘事還是論辯,基本上循著兩個路數:一是歷史的,重其發展脈絡、遷延歷程;二是觀念的,往往揀金棄沙,只把握根本的傳統。前者多為治歷史學者所取,處之極端,往往陷溺于所謂“史學的偏見”。三十年代以還,喜宋明理學或研哲學者,于此多有掊擊,茲不具論。而后者為習哲學諸人慣常所用,不管是批判儒家,還是復興儒學,關鍵處均是一些觀念鋪陳和范式架構,難免于“良知的傲慢”之譏。海外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派學者對此多有指證。如張灝謂“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一種哲學體系或學術研究的傾向是危險的”。[1]自稱“更注重哲學的框架”以著述的艾爾曼也指出:迄今以新儒家討論為中心的思想史領域,只不過是“較為淺顯的中國哲學史”。深受德國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學史之取向的影響,普遍服膺“觀念史”的模式,“結果,中國思想史只能以敘事方式進行,精于哲學卻短于歷史脈絡”。[2]因現代知識體系的學科分際而造成的史、哲之別,深深濡染了當代的儒學識辨與言說,使儒家的本來面貌在強烈的古今之辯意識的現代闡釋之下,更多增添了難以圓合的裂痕。“史學的偏見”與“良知的傲慢”之爭訟與對壘不見消彌,反愈加劇。于此,若不能有更深刻的說明和消解緊張的有效途徑,勢必將成儒?Ы胂執雜錁車募笳習?BR>也許用發生學的方法以觀其眇是一可行之道。當代的儒學話語(批判的、旁觀的、弘揚的)及其復雜的形態,均是在百年間原有體系發生劇烈的動蕩、裂變、轉型過程之中的遷延或歧出。盡管有西學東來的重大外緣,但起決定因素的還是體系內在的變化。所以,對清末儒學的狀況作些了解和分析,當有助于這一問題的清理。另外,我們今天所說辯騰喧于口的儒學,早已走出了經學時代的范式,在形態上已被現代的知識體系所夾裹和切割,這一轉換的發生機制和微妙歷程也是饒有趣味的問題。本文即圍繞清末經學的解構和現代形態儒學的創發作一思考,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三大爭論宣告了經學時代的結束
清末,皮錫瑞總結有清一代經學。謂有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底,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后,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后,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于道。”[3]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承繼此說,以佛理生、住、異、滅喻思潮之流轉,將這一段思想史概括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又進而將清學“屢遷而返其初”的獨特現象解釋成為“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鄭許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4]鹿門“義愈推而愈高”、“一變而至于道”的說詞,明顯帶有保守的今文家自吹自許之意,遠不能和任公“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的揭示之敏銳與深刻相比。但皮、梁二人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是站在清學的落幕處,對已經逝去的一個時代作全景式的觀察和描述。這一“離場”的宏大敘事雖有助于從全體上把握清代學術的綱節,?灰歡蓯刮頤欽嬲氳角逖翁壞母叢勇雎韁小?BR>倒是《漢學師承記》這樣在今天看來過于偏宕、缺少客觀性的譜系,更能引發出來問題和思考。江藩堅執漢學的純潔性,以三惠之學為典范,擯除一切經世和義理的成分,甚至將公認的樸學開山顧炎武附贅在卷末。這一切都表現了乾嘉考據學發展到極盛之時,正統漢學家“唯我獨尊”、“目無余子”的自大心態。以經學考據為正統、以吳派為標準,不但徹底否定了程朱理學的權威,實際上也顛覆了儒學賴以存在的整個基礎。沉溺于文獻考據之中,以文本、音符為道統,可以無關社會、不涉人生,此固能成就一二經生的安身立命之業,但于整個社會、蕓蕓大眾懸隔千里。這絕不是孔孟的初衷。江藩的譜系學一方面說明考據在清代學術界的主流地位,至乾嘉后期勢力是何等的強大;另一方面視野如此的狹限,似乎也把儒學納入到了沒有出路的犄角之中。所以,隨后激起的反彈,在形式上是挽救儒學,而實質上則是“對于孔孟而得解放”,最終導致了傳統儒學的解體。梁啟超在解釋“道咸以后,清學曷為而分裂耶”時,舉出了內、外各三因。內因一是考據之范圍“甚拘迂”,末流落入空而不實;二是成一“漢學專制”之局,其騶卒多為盛氣臨人的“學閥”;三是自身發展,不斷突創,必至異端涌現。外因一是“嘉道以還,積威日馳,人心已漸獲解放”,學問必由虛逐實;二是咸同間,清學的根據地江浙一帶“受禍最烈,文獻蕩然”,致“百學中落”;三是國難日重,西學漸輸,學者“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對舊學體系做根本的沖擊。[5]錢穆也指出,“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皆有“途窮將變”之跡。諸先進“起而變之者,始于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于思人才,極于正學術”,最后導出康南海的“盡變祖宗之法”,于是乎傳統徹底瓦解。[6]“所謂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到這會只成為望古遙集的資料。考證學本已在落潮的時代,到這會更未絕如縷了”。[7]伴隨著漢學的衰落,是宋學復振的呼聲、今文經學的崛起和諸子學的興盛,正是在漢宋、今古文、經子三大爭論之中,一步一步迎來了經學時代的終結。
清后期的復宋思潮以“經世”為志幟,它并非簡單回到宋儒的義理之學,和清初的“漢宋兼采之學”也不盡相同。面對考據的學術霸權,先是理學家唐鑒等人發出抗爭的聲音;繼之桐城派的方東樹挑起了漢宋爭論的巨大波瀾,曾國藩以理學名臣身份所創下的經國大業無疑為復宋勢力增添了重要的法碼;最后是嶺南陳澧等人調和漢宋的努力,不但打擊了乾嘉學術的正統觀,而且也起到了分化漢學家陣營和扭轉清末漢學走向的作用。宋學派、桐城派、調和派均站在正統漢學的對立面,對乾嘉考據學的權威提出了重大的挑戰,動搖了漢學的獨霸地位。
清代前期的理學家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修身層面,服膺宋儒的道德義理,因缺乏對應現實的創造性而逐漸被邊緣化了。到了嘉慶年間,開始有一部分理學人物力圖糾正這種偏差,重新將社會政治內容納入儒家的信仰體系。如唐鑒的“守道救世”說,雖不離“守敬”和“窮理”的道德根本,但還是對儒家經世致用的關懷給予了相當的肯定。如果說積衰已久的理學之老鳳雛聲已難引起漢學正統派的注目;那么,來自桐城派的方東樹則以《漢學商兌》一書給了對方以極大的震憾。方著可以看作是漢學權力強壓下的反彈,所謂“孤蹤違眾,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力之弗勝也,要心有難已”,[8]頗能道出作者心跡。對于江藩門戶森嚴的譜系學,來自漢學陣營的焦循等人只是委蜿商榷。而龔自珍則以考核名實(“十不安”)的方式提出異議。唯方東樹直接了當,以強大火力直攻漢學要塞,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羅列材料,攸舉事實,對漢學家中重頭人物的言論,逐條批駁。方氏之言,多能切中漢學弊端,且有很強的針對性。如斥漢學“六蔽”之四,“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9]是指當時漢學家“內苞污行,外飾雅言,身為倡優而欲高談伏鄭”的普遍情形。[10]《漢學商兌》后來因得到曾國藩的大力表彰而風行一時,從此對考據學的抨擊日起而日興,漢學威勢開始走向衰落。是不是因為方東樹的批判而使漢學之焰“遂漸熄”尚可考量,[11]但陳澧《與徐子遠書》中的一段話卻明白道出道、咸之間小學頹敗的消息。“今海內大師,凋謝殆盡。……后生輩好學者,則不過二三人耳。夫以百年來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推原其故,非盡時文之為害”。[12]由是,漢宋調和之風日盛,漢學陣營迅速分化,形成了以嶺南派為中堅的綜合漢學與宋學的運動,純漢學退居到次席,晚清學風隨之大變。
反漢學思潮的得勢,從表面來看似乎只是清代義理、考據、詞章三大學術板塊的力量比重發生了改變,考據學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宋學派的義理和以桐城派為代表的詞章借學術復古的面貌重又恢復了自身的價值,奪回了自己在儒學中應占有的份額。但實際上,打落漢學正統派權威的既不是義理也不是詞章,而是經世致用之學。反漢學的三大思想流派都強調經世致用,這正是乾嘉考據學的致命弱點,以此為利器,對壘之下,漢學焉能不敗?但是,以經世思想批判漢學,同時也就面臨了脫軌的危險,傳統經學結構中的三個板塊可能一損俱損、一起打落,義理、詞章是不可能真正挽救經學的。如果說漢宋之爭尚能保持在傳統儒學體系之內而尚未出軌;那么,隨之而來的今古文之爭則從根本上顛覆了儒學,宣告了經學時代的完結。
儒學形態研究論文
當代儒學話語——無論是敘事還是論辯,基本上循著兩個路數:一是歷史的,重其發展脈絡、遷延歷程;二是觀念的,往往揀金棄沙,只把握根本的傳統。前者多為治歷史學者所取,處之極端,往往陷溺于所謂“史學的偏見”。三十年代以還,喜宋明理學或研哲學者,于此多有掊擊,茲不具論。而后者為習哲學諸人慣常所用,不管是批判儒家,還是復興儒學,關鍵處均是一些觀念鋪陳和范式架構,難免于“良知的傲慢”之譏。海外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派學者對此多有指證。如張灝謂“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一種哲學體系或學術研究的傾向是危險的”。[1]自稱“更注重哲學的框架”以著述的艾爾曼也指出:迄今以新儒家討論為中心的思想史領域,只不過是“較為淺顯的中國哲學史”。深受德國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學史之取向的影響,普遍服膺“觀念史”的模式,“結果,中國思想史只能以敘事方式進行,精于哲學卻短于歷史脈絡”。[2]因現代知識體系的學科分際而造成的史、哲之別,深深濡染了當代的儒學識辨與言說,使儒家的本來面貌在強烈的古今之辯意識的現代闡釋之下,更多增添了難以圓合的裂痕。“史學的偏見”與“良知的傲慢”之爭訟與對壘不見消彌,反愈加劇。于此,若不能有更深刻的說明和消解緊張的有效途徑,勢必將成儒?Ы胂執雜錁車募笳習?BR>也許用發生學的方法以觀其眇是一可行之道。當代的儒學話語(批判的、旁觀的、弘揚的)及其復雜的形態,均是在百年間原有體系發生劇烈的動蕩、裂變、轉型過程之中的遷延或歧出。盡管有西學東來的重大外緣,但起決定因素的還是體系內在的變化。所以,對清末儒學的狀況作些了解和分析,當有助于這一問題的清理。另外,我們今天所說辯騰喧于口的儒學,早已走出了經學時代的范式,在形態上已被現代的知識體系所夾裹和切割,這一轉換的發生機制和微妙歷程也是饒有趣味的問題。本文即圍繞清末經學的解構和現代形態儒學的創發作一思考,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三大爭論宣告了經學時代的結束
清末,皮錫瑞總結有清一代經學。謂有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底,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后,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后,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于道。”[3]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承繼此說,以佛理生、住、異、滅喻思潮之流轉,將這一段思想史概括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又進而將清學“屢遷而返其初”的獨特現象解釋成為“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鄭許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4]鹿門“義愈推而愈高”、“一變而至于道”的說詞,明顯帶有保守的今文家自吹自許之意,遠不能和任公“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的揭示之敏銳與深刻相比。但皮、梁二人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是站在清學的落幕處,對已經逝去的一個時代作全景式的觀察和描述。這一“離場”的宏大敘事雖有助于從全體上把握清代學術的綱節,?灰歡蓯刮頤欽嬲氳角逖翁壞母叢勇雎韁小?BR>倒是《漢學師承記》這樣在今天看來過于偏宕、缺少客觀性的譜系,更能引發出來問題和思考。江藩堅執漢學的純潔性,以三惠之學為典范,擯除一切經世和義理的成分,甚至將公認的樸學開山顧炎武附贅在卷末。這一切都表現了乾嘉考據學發展到極盛之時,正統漢學家“唯我獨尊”、“目無余子”的自大心態。以經學考據為正統、以吳派為標準,不但徹底否定了程朱理學的權威,實際上也顛覆了儒學賴以存在的整個基礎。沉溺于文獻考據之中,以文本、音符為道統,可以無關社會、不涉人生,此固能成就一二經生的安身立命之業,但于整個社會、蕓蕓大眾懸隔千里。這絕不是孔孟的初衷。江藩的譜系學一方面說明考據在清代學術界的主流地位,至乾嘉后期勢力是何等的強大;另一方面視野如此的狹限,似乎也把儒學納入到了沒有出路的犄角之中。所以,隨后激起的反彈,在形式上是挽救儒學,而實質上則是“對于孔孟而得解放”,最終導致了傳統儒學的解體。梁啟超在解釋“道咸以后,清學曷為而分裂耶”時,舉出了內、外各三因。內因一是考據之范圍“甚拘迂”,末流落入空而不實;二是成一“漢學專制”之局,其騶卒多為盛氣臨人的“學閥”;三是自身發展,不斷突創,必至異端涌現。外因一是“嘉道以還,積威日馳,人心已漸獲解放”,學問必由虛逐實;二是咸同間,清學的根據地江浙一帶“受禍最烈,文獻蕩然”,致“百學中落”;三是國難日重,西學漸輸,學者“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對舊學體系做根本的沖擊。[5]錢穆也指出,“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皆有“途窮將變”之跡。諸先進“起而變之者,始于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于思人才,極于正學術”,最后導出康南海的“盡變祖宗之法”,于是乎傳統徹底瓦解。[6]“所謂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到這會只成為望古遙集的資料。考證學本已在落潮的時代,到這會更未絕如縷了”。[7]伴隨著漢學的衰落,是宋學復振的呼聲、今文經學的崛起和諸子學的興盛,正是在漢宋、今古文、經子三大爭論之中,一步一步迎來了經學時代的終結。
清后期的復宋思潮以“經世”為志幟,它并非簡單回到宋儒的義理之學,和清初的“漢宋兼采之學”也不盡相同。面對考據的學術霸權,先是理學家唐鑒等人發出抗爭的聲音;繼之桐城派的方東樹挑起了漢宋爭論的巨大波瀾,曾國藩以理學名臣身份所創下的經國大業無疑為復宋勢力增添了重要的法碼;最后是嶺南陳澧等人調和漢宋的努力,不但打擊了乾嘉學術的正統觀,而且也起到了分化漢學家陣營和扭轉清末漢學走向的作用。宋學派、桐城派、調和派均站在正統漢學的對立面,對乾嘉考據學的權威提出了重大的挑戰,動搖了漢學的獨霸地位。
清代前期的理學家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修身層面,服膺宋儒的道德義理,因缺乏對應現實的創造性而逐漸被邊緣化了。到了嘉慶年間,開始有一部分理學人物力圖糾正這種偏差,重新將社會政治內容納入儒家的信仰體系。如唐鑒的“守道救世”說,雖不離“守敬”和“窮理”的道德根本,但還是對儒家經世致用的關懷給予了相當的肯定。如果說積衰已久的理學之老鳳雛聲已難引起漢學正統派的注目;那么,來自桐城派的方東樹則以《漢學商兌》一書給了對方以極大的震憾。方著可以看作是漢學權力強壓下的反彈,所謂“孤蹤違眾,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力之弗勝也,要心有難已”,[8]頗能道出作者心跡。對于江藩門戶森嚴的譜系學,來自漢學陣營的焦循等人只是委蜿商榷。而龔自珍則以考核名實(“十不安”)的方式提出異議。唯方東樹直接了當,以強大火力直攻漢學要塞,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羅列材料,攸舉事實,對漢學家中重頭人物的言論,逐條批駁。方氏之言,多能切中漢學弊端,且有很強的針對性。如斥漢學“六蔽”之四,“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9]是指當時漢學家“內苞污行,外飾雅言,身為倡優而欲高談伏鄭”的普遍情形。[10]《漢學商兌》后來因得到曾國藩的大力表彰而風行一時,從此對考據學的抨擊日起而日興,漢學威勢開始走向衰落。是不是因為方東樹的批判而使漢學之焰“遂漸熄”尚可考量,[11]但陳澧《與徐子遠書》中的一段話卻明白道出道、咸之間小學頹敗的消息。“今海內大師,凋謝殆盡。……后生輩好學者,則不過二三人耳。夫以百年來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推原其故,非盡時文之為害”。[12]由是,漢宋調和之風日盛,漢學陣營迅速分化,形成了以嶺南派為中堅的綜合漢學與宋學的運動,純漢學退居到次席,晚清學風隨之大變。
反漢學思潮的得勢,從表面來看似乎只是清代義理、考據、詞章三大學術板塊的力量比重發生了改變,考據學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宋學派的義理和以桐城派為代表的詞章借學術復古的面貌重又恢復了自身的價值,奪回了自己在儒學中應占有的份額。但實際上,打落漢學正統派權威的既不是義理也不是詞章,而是經世致用之學。反漢學的三大思想流派都強調經世致用,這正是乾嘉考據學的致命弱點,以此為利器,對壘之下,漢學焉能不敗?但是,以經世思想批判漢學,同時也就面臨了脫軌的危險,傳統經學結構中的三個板塊可能一損俱損、一起打落,義理、詞章是不可能真正挽救經學的。如果說漢宋之爭尚能保持在傳統儒學體系之內而尚未出軌;那么,隨之而來的今古文之爭則從根本上顛覆了儒學,宣告了經學時代的完結。
陳澧文學思想綜述
陳澧,晚清嶺南著名學者,平生致力于經學研究,旁及歷史、地理、金石、音樂、文學等,著有《聲律通考》《漢儒通義》《東塾讀書記》等著作,對近代廣東學術發展產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今人一般將陳澧視為經學家、思想家,對其詩文及文學思想則較少關注。陳澧雖無專門的文論著作,但在大量的札記、書信、文評、序跋中,他的文學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并且與他的經學思想相輔相成、互相輝映。陳澧在經學上持漢宋調和的立場,其文學思想正如他的經學主張,“本之于經”的同時對當時文壇上的各種矛盾基本上持調和折中的立場。作為漢宋兼采派經學家的代表人物,陳澧的文學思想在近代文論轉型的過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文論觀點“本之于經”
作為一名經學家,陳澧亦兼擅文學,其經學思想及其學術方法不知不覺向文學的領域延伸。陳澧的文論觀點皆“本之于經”,將《詩經口小雅》中“有倫有脊”一詞作為作文指導法則,并將文學視為學術經世的手段之一。對于作文之法,陳澧拈出了“有倫有脊”的原則,并且明確指出自己的文論觀點“本之于經”:“昔時讀《小雅》‘有倫有脊’之語,嘗告山舍學者,此即作文之法,今舉以告足下,可乎?倫者,今日老生常談,所謂層次也。脊者,所謂主意也。夫人必其心有意而后其口有言,有言而其手書之于紙上,則為文。無意則無言,更安得有文哉!有意矣,而或不止有一意,則必有所主,猶人身不止一骨,而脊骨為之主,此所謂有脊也。意不止一意而言之,何者當先?何者當后?則必有倫次。即止有一意而一言不能盡意,則其淺深本末又必有倫次,而后此一意可明也。……雖然,倫猶易為也,脊不易為也,必有學有識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仆之說雖淺,然本之于經,或當不謬。”[1所謂“有脊”,是指文章必須要有思想、有內容。所謂“有倫”,是指文章層次清楚、條理分明,也就是要求文章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然而,“倫猶易為也,脊不易為也”,如何才能做到文章“有倫有脊”?陳澧提出“必有學有識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的韓愈被陳澧推為文章家的典范:“凡為學者,當于古人中擇師;仆為足下擇之,其昌黎乎?昌黎進學解日:‘先生口不絕吟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此昌黎讀書法也。昌黎一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一一自言之,又屢言之,燥然而可見,確然而可循如此,才真高矣,志真博矣。”[2韓愈為學尊孟子、茍卿,讀書披百家,吟六藝,其作為文章始能“陶冶镕裁合為一家,而猶可以尋其所自出。”文章家當師范韓愈“一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才能作出“有倫有脊”的優秀篇章。對于文章的“意”和“脊”,陳澧尤其重視,他所推崇的是具有“古詩人之旨”的詩文作品。他稱贊馮子皋的詩“蓋大令之詩,尤善者《徐鄉竹枝詞》二十一首,凡耕植絲布之業,沙草魚蟹之利,歲時燈火酒食之樂,男女婚嫁思慕之感,歷歷如繪,此近于古詩人之詩,陳之可以觀民風者。,[釘評方子箴詩“及其怡懌乎心靈,流連乎古昔,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卓乎古詩人之旨也。[]所謂“古詩人之詩”,也就是文章內容需“原于古,切于時”,具有“怡懌乎心靈”的感人力量。陳澧論文“本之于經”,主張作文“求圣人之道”,同時要“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陳之可以觀民風”,秉承了儒家“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論精神。這與陳澧學術經世的思想直接相關。經世致用思想本就是儒家的學術傳統之一,陳澧生活在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時期,這一學術思潮重新得到張揚。齊思和說:“夫晚清學術界之風氣,倡經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5]處于這樣的社會現實和學術氛圍中,陳澧雖關心政治,卻自認并無經世之才,自然不能像他所佩服的魏源那樣“以經術為治術,[,他選擇了學術經世的途徑,通過著書立說、教育人才來達到間接救世的目的。“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于天下事也。以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于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于天下。”[7他將學問看得異常重要,甚至認為“學術衰壞”直接關系“人心風俗”,這是他經世思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文學同樣具備經世的功能。陳澧提出“凡經學,要識義理,非徒訓詁考據而已。”“凡史學,要知治亂興亡之由。‘凡讀古人詩文,要取其開我之心胸,養我之性情。”[8]不論是經學、史學還是文學,陳澧看重的是他們幫助士人識義理、通古今,提升道德修養,從而有用于世的致用功能。他贊揚鄭小谷的文章“觀君之文之論事者,則亦可識之矣。必原于古,必切于時,必可行而后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后陳其弊,是三者不徒在于文,而又有在于文之外者也o.[93文章應“必可行而后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后陳其弊”,發揮經世之效用。陳澧的詩文亦表現出強烈的對時事的關切之情。如《大水嘆》指出廣州的水災不僅是天災,還與官吏管理不善,濫收田租、誘民墾荒有極大的關系。《有感》諷刺鴉片戰爭期間兩廣總督葉名琛臨敵而不設防,致使廣州城陷落的荒唐舉動。《炮子謠》寫吸食鴉片給中國人帶來的身心健康的損害,對世道人心的破壞,這正是他“切于時”的文學理念在創作領域的貫徹。
二、文章家當“學、識、才”兼長
陳澧在《鄭小谷補學軒文集序》中,提出了文章家當“學、識、才”兼長的理想要求:“昔人謂史家有三長:學也,識也,才也。澧嘗論之,以為文章家亦然,無學則文陋,無識則文乖,無才則文弱而不振。然持此以論文,其可以號為文人者,寡矣。求之于今,其刑部象州鄭君乎?君讀四部書不知幾萬卷,宏綱巨目,靡不舉也。奇辭雋旨,靡不收也。其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久之,是日有學。通漢唐注疏,而碎義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不取也。兼擅六朝、唐、宋時文而模仿沿襲,尤深恥而不為也,是日有識。其為文也,能同乎古人而毅然必自為也,能異乎今人而又坦然莫不解也,其鋒英英焉,其氣磊磊焉,其力轉轉而不竭焉,是日有才。'''',[9]這是他在當時文壇考據、義理、辭章三者關系的論爭中,主張調和漢宋、貫通相左的折中的學術立場在文論領域的反映。陳澧“學、識、才”兼長的文學理念受到章學誠的深刻影響。“才、學、識”兼備的觀點最早由史學家劉知己所提出,清代章學誠將之引用到古文創作的理論中,提出“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于稼穡也。”[1叩認為理想的古文應將文辭、考據、義理也就是才、學、識三者完美融合。頗具深意的是,章學誠提出“才、學、識”,陳澧則將其排序變為“學、識、才”,并在具體闡釋中融人個人之思想。對“學”的要求被陳澧放在首位,提出“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久之”,也就是訓詁精確,博聞強記。強調為文精于考據,與陳澧崇尚漢學的學術取向密切相關。陳澧雖主張漢宋調和,但他的學術出發點是漢學,其學術成果也基本集中在漢學領域,正像錢穆所說“是子襄雖亦主融漢、宋,而與陳東塾之為見異。東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論,則在納康成于諸子。’,[n因此,他將漢學家所重視的考據放在首要位置,強調在詩文創作中避免因疏于考據而出現知識性的錯誤。所謂“識”,是指“通漢唐注疏,而碎義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不取也。”也就是漢宋融通,不拘泥于一家的學術識見。清代中期以后,漢學和宋學各執門戶之見,爭論不休。陳澧學術思想的特點在一“通”字,拋卻門戶偏見,主張漢宋融通,考據與義理兼長。“百余年來,說經者極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然則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義理也。若不思其義理,則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仆之此書,冀有以藥此病耳。既成此書,乃著《學思錄》,通論古今學術,不分漢宋門戶。,[]學有識見,“以其所學發而為文,為詩”,則不會流于瑣碎空虛,也不會流于乖張臆說。漢宋通融的經學立場影響到陳澧的文論建構,強調“學”與“識”兼長,也就是考據與義理兼擅構成其文論的重要內容。所謂“才”,主要指深厚的文學表現才能,也就是章學誠所說之“文辭”。在為友人文集所作序中,陳澧對“才”作出了進一步的解釋。“凡方伯之詩之美,澧能言之矣。其健也,巨篇連章,橫翔而杰出。其奇也,狹韻僻字,斗險而爭新。其艷也如春,其清也若秋,其巧也雕刻窮纖微,其和也鏘鏘中宮徵。若是者,猶才人之能事乎!虻]這里的“才”主要指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從用字到音韻到風格都有精到的論述,可見陳澧對文學作品具有相當高的審美鑒賞能力。陳澧雖提倡文章家應“學識才”兼備,但這三者在他的心目中并非處于同等位置。他欣賞辭章之美,但卻將“學”和“識”置于“才”之前:“作詩寫字,但能不俗可矣。若求工妙,讓專門者為之。……若夫著述之體,切宜留意……學人之著述,非才人之辭章所可同日而語者,俗人更不識也。”C14]這里的“著述之體”指的是經說與史論,陳澧提明確地將著述之體置于詩文之上。對于詩文,陳澧則提出“不俗”的評價標準,而將文章藝術的工妙置于其次。何為‘不俗’?陳澧認為“不俗者,狂狷也。俗者,鄉原也,同乎流俗也,孔、孟以為賊,可懼也。志狂者之志,行狷者之行,是為不俗。,E143所謂“狂狷不俗”是指特立獨行,絕不同流合污的個性。陳澧對清末“廉恥道喪”的世風極為不滿,將“行己有恥,博學多文”作為教育的宗旨,一貫強調道德的修養,他的贊揚“狂狷”,痛詆“鄉原”,就是要警醒世人,要做個性獨立,道德高尚的“狂狷”君子。此種思想反映到文學上,就是“不俗”的詩文品格的提出。“不俗”論的提出更多是偏向于對詩文作者學識修養、道德品格的要求,也就是將“學”與“識”放在首要之位置。
陳澧“學識才”兼長的詩文理想對克服當時空虛、瑣碎、淺薄的文風確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我們也要看到盡管意識到文學作品具有獨特的藝術感染力,陳澧為宣傳自己的經世主張,將著述文體凌駕于才人辭章之上,對文學作品流露出貶低的情緒,這是他文學批評的不足之處。對陳澧頗有些菲薄態度的劉師培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一文中曾說:“宋代以前,‘義理’‘考據’之名未成立,故學士大夫,莫不工文。……至宋儒立‘義理’之名,然后以語錄為文,而詞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據’之名,然后以注疏為文,而文無性靈。夫以語錄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筆之于書,以其多方言俚語也;以注疏為文,可筆于書,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無抗墜抑揚也。綜此二派,咸不可目之為文。”E15]批評宋學家以語錄為文,文章俚俗;漢學家以考據為文,文無性靈,明確提出義理、考據之作皆不可稱為“文”。這段話或可讓我們對陳澧文論未能擺脫經學思想羈絆的不足之處有更深的了解。
陳澧經學觀形成研究論文
[摘要]陳澧是晚清漢宋調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漢學,中年以后論學不分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對陳澧會通漢宋、回歸孔孟的經學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陳澧;漢宋;王懋竑;顧炎武
陳澧(1810—1882),廣東番禺人,字蘭甫,一字蘭浦,人稱東塾先生。陳澧早年受業于廣東學海堂,秉承乾嘉漢學的治學方法,所著《切韻考》和《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為士林推重。中年以后走出漢學舊轍,融合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晚年所著《東塾讀書記》,闡發孔孟要義和五經大旨,考索經學源流正變,通論古今儒學得失,為其代表作。
在陳澧經學觀的演變過程中,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但王氏的影響,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視。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使陳澧契接朱子學,這是他會通漢學和宋學的關鍵;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則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陳澧,以下詳述之。
被稱為“漢學護法”的阮元,在兩廣總督任上,大倡乾嘉漢學之風。道光四年創建學海堂,仿撫浙時的詁經精舍例,以經史小學課士。阮元在《學海堂集序》中說:“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師法……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于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于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此后訓詁考據學在廣東興起,而學海堂則成為漢學重鎮。
1826年,時年十七歲的陳澧應學海堂季課,開始接受乾嘉樸學教育。從1826年至1844年,是陳澧治學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陳澧尊奉漢學,撰寫了《切韻考》、《說文聲統》等音韻學專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三統術詳說》、《弧三角平視法》等天文、輿地、歷算類考據專著。散篇的考據文章也不少,如《明堂圖說》、《深衣說》、《校毛傳也字說》、《月令考》等。
陳澧經學觀形成分析論文
[摘要]陳澧是晚清漢宋調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漢學,中年以后論學不分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對陳澧會通漢宋、回歸孔孟的經學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陳澧;漢宋;王懋竑;顧炎武
陳澧(1810—1882),廣東番禺人,字蘭甫,一字蘭浦,人稱東塾先生。陳澧早年受業于廣東學海堂,秉承乾嘉漢學的治學方法,所著《切韻考》和《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為士林推重。中年以后走出漢學舊轍,融合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晚年所著《東塾讀書記》,闡發孔孟要義和五經大旨,考索經學源流正變,通論古今儒學得失,為其代表作。
在陳澧經學觀的演變過程中,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但王氏的影響,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視。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使陳澧契接朱子學,這是他會通漢學和宋學的關鍵;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則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陳澧,以下詳述之。
被稱為“漢學護法”的阮元,在兩廣總督任上,大倡乾嘉漢學之風。道光四年創建學海堂,仿撫浙時的詁經精舍例,以經史小學課士。阮元在《學海堂集序》中說:“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師法……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于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于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此后訓詁考據學在廣東興起,而學海堂則成為漢學重鎮。
1826年,時年十七歲的陳澧應學海堂季課,開始接受乾嘉樸學教育。從1826年至1844年,是陳澧治學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陳澧尊奉漢學,撰寫了《切韻考》、《說文聲統》等音韻學專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三統術詳說》、《弧三角平視法》等天文、輿地、歷算類考據專著。散篇的考據文章也不少,如《明堂圖說》、《深衣說》、《校毛傳也字說》、《月令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