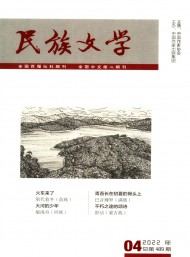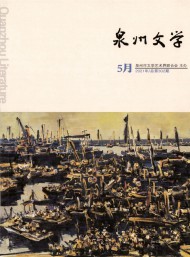文學(xué)觀范文10篇
時(shí)間:2024-03-26 13:54:42
導(dǎo)語: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yàn),為你推薦的十篇文學(xué)觀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消費(fèi)社會(huì)文學(xué)景觀研究
摘要:文學(xué)景觀在高科技時(shí)代和數(shù)字化覆蓋的今天逐漸成為文化消費(fèi)的熱門,具有極大的潛力并且已經(jīng)創(chuàng)造出巨大的商業(yè)利潤(rùn)。多樣化的需求使得文學(xué)景觀在以文學(xué)為起點(diǎn)的基礎(chǔ)上衍生出了不同方向的發(fā)展路徑和方向。不同路徑的發(fā)展過程之間為何產(chǎn)生不同方向,所導(dǎo)致的效果有何區(qū)別以及對(duì)未來發(fā)展的影響和建議將是討論的終點(diǎn)所在。
關(guān)鍵詞:文學(xué)景觀化;創(chuàng)意文化;文化產(chǎn)業(yè);文學(xué)與商業(yè)
文學(xué)景觀化的概念提出是伴隨著第二媒介時(shí)代到來的,它的產(chǎn)生使文學(xué)與新興傳播方式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創(chuàng)造出符合時(shí)展潮流的文化產(chǎn)業(yè)。所謂文學(xué)景觀,即是指與文學(xué)密切相關(guān),根植于文學(xué)而創(chuàng)造出的景觀。與傳統(tǒng)景觀相比,文學(xué)景觀多了一份文學(xué)內(nèi)涵和文學(xué)色彩,有著強(qiáng)大的生命延續(xù)力,是當(dāng)今文學(xué)與商業(yè)融合的較佳典范。
一、消費(fèi)社會(huì)中文學(xué)“景觀化”的必然
法國(guó)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了“景觀社會(huì)”這一概念,突出了視覺文化在當(dāng)今社會(huì)中的重要地位。從20世紀(jì)40-50年代開始,隨著電子傳媒在西方世界的興起,特別是電視的普及,使西方社會(huì)進(jìn)入到被學(xué)者們所稱的“文化消費(fèi)”時(shí)代。根據(jù)德波的說法:“一切事物的影像價(jià)值取代了它們的使用價(jià)值,事物景觀化的程度決定著它能產(chǎn)生多大的文化意義”,信息傳播與接受媒介已經(jīng)明顯嚴(yán)重地依賴于機(jī)械復(fù)制的“視覺機(jī)制”,日益擴(kuò)張中新的視覺文化占據(jù)了整個(gè)社會(huì)文化的主導(dǎo)地位。大眾媒體的崛起象征著影像物品生產(chǎn)和物品影像消費(fèi)滲透我們的生活,以景觀為代表的視覺文化成為獨(dú)特的文化發(fā)展方式。在這樣一種趨勢(shì)下,文學(xué)的景觀化開始萌芽并且在良好的法扎勢(shì)頭中迸發(fā)出極大的潛力。當(dāng)今的中國(guó)也在步入景觀化的進(jìn)程之中,突出表現(xiàn)在當(dāng)前文化傳播的高度視覺化:從靜態(tài)的書本插圖、街頭海報(bào)商品包裝,到動(dòng)態(tài)的商業(yè)廣告、彩色電視和3D電影,不論是休閑領(lǐng)域、商業(yè)領(lǐng)域還是文學(xué)領(lǐng)域,傳播方式的視覺化都占有了絕對(duì)的主導(dǎo)地位。圖像從本質(zhì)上講是直觀的、確定性的,并且給人以存在感。這就導(dǎo)致了當(dāng)今社會(huì)審美的轉(zhuǎn)換,人們更加能被動(dòng)態(tài)的、視覺的甚至全方位的效果所吸引。文學(xué)在景觀化的過程中有著很大的優(yōu)勢(shì)將虛擬的文學(xué)世界映射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打造出虛擬與現(xiàn)實(shí)相融合的消費(fèi)文化,吸引不同的人將文學(xué)作品中的想象進(jìn)行實(shí)踐,從而得到巨大的經(jīng)濟(jì)效益。這也是在景觀社會(huì)中,文學(xué)景觀化的巨大契機(jī)。文學(xué)的景觀化是一個(gè)發(fā)展趨勢(shì),單薄的文字不再是承載文學(xué)作品的唯一途徑。文學(xué)是語言的藝術(shù),是一種靜態(tài)的主觀世界,它對(duì)讀者所產(chǎn)生的閱讀空間存在限制。人們通過文學(xué)作品營(yíng)造一個(gè)虛擬的世界,然而這個(gè)虛擬的世界多引發(fā)的想象無法具象的體現(xiàn)是阻礙產(chǎn)生更多的審美價(jià)值的重要點(diǎn)。在這一點(diǎn)上,鮑德里亞提出的“擬象”“仿真”,即以高科技為背景由模型復(fù)制出來的具體的形象與模型可以完全一致,二者沒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復(fù)制完全可以代替模型的說法與多媒體迅速發(fā)展的今天不謀而合,也為文學(xué)單一的延續(xù)途徑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擬像不再是對(duì)一個(gè)領(lǐng)域的模擬,對(duì)一個(gè)指涉性存在的模擬,或是對(duì)一種本質(zhì)的模擬。它不需要原物或?qū)嶓w,而是以模擬來產(chǎn)生真實(shí):一種超真實(shí)。”我們可以通過對(duì)文學(xué)作品中虛擬的世界進(jìn)行復(fù)制,利用視覺的沖擊,還原讀者的想象,營(yíng)造“真實(shí)”,從而完成文學(xué)景觀化的最大目的和意義。第二媒介時(shí)代的到來迫使著文學(xué)不得不從印刷文化轉(zhuǎn)向影像文化,多媒體技術(shù)手段革新了傳播的方式,而與文學(xué)一向掛鉤的大眾傳播也迎來了嶄新的革命。視覺文化的入侵以及審美生活化的趨向令文學(xué)單一的視覺享受不再成為社會(huì)審美價(jià)值的主流。黑格爾早就指出,在人的所有感官中,惟有視覺和聽覺是認(rèn)識(shí)性的感官。也許正是這個(gè)原因,我們把握世界的方式不是視覺就是聽覺,抑或視聽同時(shí)運(yùn)用。文學(xué)作品所呈現(xiàn)的單一的、靜態(tài)的文字閱讀無法滿足多方位的閱讀需求,因此文字圖像化成為文學(xué)景觀的一種主要存在方式。影視改編的文學(xué)景觀化的方式是較早存在和發(fā)展的存在形式,并且已經(jīng)發(fā)展成較為成熟的文化形態(tài)。近年來流行的“IP熱”正反映了文學(xué)景觀化的迅速成長(zhǎng),從傳統(tǒng)影視改編發(fā)展至今,影視改編儼然已成為一種當(dāng)代影視發(fā)展的主力軍。“IP”改編實(shí)現(xiàn)了雙向獲益,但同時(shí)也令文學(xué)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變化。作為近年來發(fā)展迅速的創(chuàng)意文化產(chǎn)業(yè),真人密室逃脫成為新興的,有著巨大發(fā)展?jié)摿Φ奈膶W(xué)景觀。密室逃脫是以推理文學(xué)為基礎(chǔ)衍生出來的文學(xué)景觀,最初被開發(fā)成一種基于動(dòng)畫的線上解謎類游戲,主要形式是玩家被困在一個(gè)密閉的環(huán)境通過控制電腦操作尋找線索和關(guān)鍵物品并進(jìn)行推理,最終逃出“密室”。隨著高科技的不斷進(jìn)步以及要求更高的閱讀體驗(yàn),密室逃脫從線上走到線下,衍生出“真人密室逃脫”的新形式。
二、消費(fèi)社會(huì)中文學(xué)景觀代償機(jī)制對(duì)比
文學(xué)場(chǎng)邏輯與文學(xué)觀分析論文
要討論當(dāng)代西方思想家,對(duì)于治文學(xué)的人來說可能有著更便利的條件。因?yàn)楫?dāng)代西方許多哲人,在提出一個(gè)個(gè)自成一格的話語系統(tǒng)的同時(shí),總是不約而同地傾向于把文學(xué)或藝術(shù)當(dāng)成自己的殖民地。伊格爾頓不無譏諷地說:"當(dāng)哲學(xué)家變成實(shí)證哲學(xué)家的工具時(shí),美學(xué)就可以用來拯救思想了。哲學(xué)強(qiáng)有力的主題被某種具體、純粹、斤斤計(jì)較的理論所排遣,現(xiàn)在正變得無家可歸,四處漂泊,它們尋求著一片蔽身的瓦頂,終至在藝術(shù)的話語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這當(dāng)然是事情的一方面。但從策略的角度來看,至少對(duì)于我們即將要討論的布迪厄來說,文學(xué)藝術(shù)之所以容易成為思想家所關(guān)注的寵兒,可能還因?yàn)樽鳛榫瘳F(xiàn)象,文學(xué)藝術(shù)具有更普遍的可通約性。一種理論,倘若能在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的分析中站得住腳,在其他領(lǐng)域中也許就顯得是不言而喻的了。更何況文學(xué)藝術(shù)在人類社會(huì)中又有類乎廣告效應(yīng)那么強(qiáng)大的影響力。
盡管主要身份是社會(huì)學(xué)家的布迪厄在原則上反對(duì)建立一種普遍性元話語,然而,他的確在事實(shí)上創(chuàng)造了一整套話語系統(tǒng),并將它令人咋舌地運(yùn)用在農(nóng)民、失業(yè)、教育、法律、科學(xué)、階級(jí)、政治、宗教、體育、語言、住房、婚姻、知識(shí)分子、國(guó)家制度等極為廣闊的領(lǐng)域里,而他特別留意的對(duì)象之一,似乎是文學(xué)藝術(shù)。他不僅在許多著作中屢屢提及文學(xué)藝術(shù),而且還專門寫了幾部專著如《區(qū)隔:趣味判斷的社會(huì)批判》、《藝術(shù)之戀:歐洲藝術(shù)博物館及其觀眾》、《藝術(shù)的法則:文學(xué)場(chǎng)的發(fā)生和結(jié)構(gòu)》、《文化生產(chǎn)場(chǎng):論藝術(shù)和文學(xué)》等等。要紹介布迪厄的文學(xué)理論,我們可能會(huì)有一種浩浩茫茫不知從何處說起的慨嘆,因?yàn)椴际蠋缀鯖]有遺漏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任何一個(gè)重要領(lǐng)域,但是,正如上述書名所暗示的那樣,文學(xué)場(chǎng)顯然是布迪厄文學(xué)理論的一個(gè)關(guān)鍵詞。正是通過文學(xué)場(chǎng)的概念,布迪厄的文學(xué)理論才得以清楚的表述。所以,不妨讓我們從文學(xué)場(chǎng)開始說起。
一、為什么是文學(xué)場(chǎng)?
布迪厄自認(rèn)獨(dú)擅勝場(chǎng),并得到了一些學(xué)者贊同的學(xué)術(shù)閃光點(diǎn)之一是,他超越了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經(jīng)驗(yàn)研究和理論研究、內(nèi)部閱讀與外部閱讀、存在主義與結(jié)構(gòu)主義等之間的二元對(duì)立。具體到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布迪厄認(rèn)為,主觀主義或本質(zhì)主義的文學(xué)分析方法,諸如浪漫主義者基于卡理斯瑪意識(shí)形態(tài),將作者視為獨(dú)創(chuàng)者;新批評(píng)派之類的形式主義者沉迷于文本的形式之中,將陌生化等形式因素視為文學(xué)性的一般特質(zhì);實(shí)證主義者相信經(jīng)驗(yàn)數(shù)據(jù)的科學(xué)性,把賴以統(tǒng)計(jì)的分類范疇當(dāng)成文學(xué)事實(shí)的自在范疇;薩特在傳記材料中尋求作者的個(gè)人特性,并將它與文學(xué)作品中所呈現(xiàn)的特性混為一談;弗洛伊德或榮格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結(jié)或集體無意識(shí)來解釋文學(xué)的本質(zhì);而福科則拒絕在話語場(chǎng)之外發(fā)現(xiàn)文學(xué)發(fā)生的解釋原則;……凡此種種,都不同程度地把文學(xué)觀念、文學(xué)實(shí)踐和文學(xué)作品當(dāng)作理所當(dāng)然的現(xiàn)實(shí)加以接受,而完全忽視了這種現(xiàn)實(shí)在人的頭腦中賴以構(gòu)成的社會(huì)條件和歷史條件。另一方面,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例如盧卡契或者以發(fā)生學(xué)結(jié)構(gòu)主義者自命的戈德曼,則完全無視文學(xué)自身相對(duì)獨(dú)立的形式特性,無視作家作為能動(dòng)者在文學(xué)生產(chǎn)中對(duì)于文學(xué)意義的塑造,而將作者簡(jiǎn)化為某個(gè)社會(huì)集團(tuán)的無意識(shí)人,將文學(xué)的發(fā)生發(fā)展簡(jiǎn)化為政治經(jīng)濟(jì)力量的直接作用。
布迪厄超越二元對(duì)立的理論工具是場(chǎng)域、資本和習(xí)性(habitus,或譯慣習(xí))諸概念。就文學(xué)而言,布迪厄使用了文學(xué)場(chǎng)或者文化生產(chǎn)場(chǎng)的概念。一方面,文學(xué)場(chǎng)在作為元場(chǎng)域的權(quán)力場(chǎng)中居于被支配地位,也就是說,歸根到底,還是要受到政治經(jīng)濟(jì)因素的制約;另一方面,文學(xué)場(chǎng)可以被描述為獨(dú)立于政治、經(jīng)濟(jì)之外,具有自身運(yùn)行法則,具有相對(duì)自主性的封閉的社會(huì)宇宙。這說起來很有點(diǎn)類似于阿爾都塞對(duì)于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和上層建筑之間關(guān)系的表述。但是,對(duì)于布迪厄來說,文學(xué)場(chǎng)的隱喻不僅僅是對(duì)于文學(xué)與宏觀的社會(huì)世界之間互動(dòng)關(guān)系的一個(gè)闡釋工具,重要的是,它還是超越上述二元對(duì)立、反對(duì)本質(zhì)主義文學(xué)觀的一種敘事框架,同時(shí)也是理解文學(xué)的本質(zhì)、文學(xué)作品的形式與內(nèi)容,文學(xué)家的文學(xué)觀與創(chuàng)作軌跡,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與變革,文學(xué)的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等等幾乎重大的文學(xué)理論的問題。當(dāng)然,還需要提上一筆的是,他的文學(xué)場(chǎng)的理論主要關(guān)注的文學(xué)事實(shí)是近世以來逐漸獲得文學(xué)自主性的文學(xué)現(xiàn)象,換句話說,前資本主義的文學(xué)實(shí)踐基本上不在他考察的范圍之內(nèi)。
二、什么是文學(xué)場(chǎng)?
阿英革命文學(xué)政治觀思索
“阿Q時(shí)代是早已死去了”,這是時(shí)年28歲的阿英在其名篇《死去了的阿Q時(shí)代》中的驚人之語。1928年的革命文學(xué)論爭(zhēng)后,作家阿英轉(zhuǎn)而以勇猛的評(píng)論家姿態(tài)登陸文壇,鋒芒畢露、咄咄逼人,讓論戰(zhàn)對(duì)手們頗不服氣,阿英就此被劃歸激進(jìn)幼稚派不得翻身。實(shí)際上,如果不局限于階級(jí)決定論的二元對(duì)立視角,像過去那樣籠統(tǒng)地認(rèn)為他在文學(xué)與政治之間劃了一個(gè)簡(jiǎn)單等號(hào),主張“錢杏邨的錯(cuò)誤并不在于他提出文藝的政治化,而在于他實(shí)際上取消了文藝,放棄了文藝的特殊工具”[1],“錢杏邨等人以絕對(duì)否定藝術(shù)的獨(dú)立性,把藝術(shù)價(jià)值簡(jiǎn)單地歸結(jié)為所謂社會(huì)價(jià)值即政治價(jià)值”[2],甚至直指阿英由于犯下革命的意識(shí)形態(tài)錯(cuò)誤,“帶來的是對(duì)事物的扭曲和變形,是對(duì)人的認(rèn)識(shí)的局限”[3],這都是并不完全符合事實(shí)的。在我看來,阿英所討論與肯定的文學(xué)與政治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或者說,從政治、革命、階級(jí)的角度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并建立相關(guān)的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并非一無是處。如果從阿英對(duì)“革命文學(xué)”的階段認(rèn)定和對(duì)“政治”概念的多重理解來探討阿英的文學(xué)政治觀,將有可能打開認(rèn)識(shí)阿英的另一扇窗。
1作為一種文類模式的革命文學(xué)
討論一個(gè)問題,首先必須確定討論的范圍與邊界。同樣,討論阿英的文學(xué)政治觀,首先要解決的是阿英在何種框架內(nèi)提出他的理論,這就需要回到阿英的批評(píng)實(shí)踐。一般認(rèn)為1930年代的中國(guó),社會(huì)矛盾已主要地體現(xiàn)為無產(chǎn)階級(jí)與大地主、官僚資產(chǎn)階級(jí)的階級(jí)革命,所以關(guān)于中國(guó)無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的討論,在它甫一出生,即主要地體現(xiàn)為對(duì)“革命文學(xué)”理論與創(chuàng)作的檢討,這種討論從1923年提出“革命文學(xué)”口號(hào),到1928年“革命文學(xué)論爭(zhēng)”時(shí)達(dá)到高峰。基于這個(gè)前提,1928年,阿英發(fā)表《批評(píng)的建設(shè)》,借批評(píng)三種錯(cuò)誤傾向具體表達(dá)了自己的文學(xué)理想,傳統(tǒng)的批評(píng):沒有統(tǒng)一的、系統(tǒng)的批評(píng)原理;沒有科學(xué)的方法;批評(píng)家的態(tài)度不誠(chéng)懇、不謙虛。因此,阿英主張“文學(xué)和政治分不開的”[4]18,要求批評(píng)家用科學(xué)的方法“估定作品的價(jià)值,為讀者指示解釋作品的思想和技巧,以及改正作品的思想和技巧的錯(cuò)誤”,以促進(jìn)文化的發(fā)展和社會(huì)的進(jìn)步。
1.1革命文學(xué)的全新規(guī)范
阿英之所以自覺地把作家論、作品論和文學(xué)史論(思潮批評(píng)、流派研究等)等批評(píng)實(shí)踐納入科學(xué)范疇,追求一種系統(tǒng)的政治批評(píng),以“改正錯(cuò)誤”,并賦予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批評(píng)促進(jìn)“文化發(fā)展”和“社會(huì)進(jìn)步”的重任,其原因在于。第一,正如克羅齊所說,“每一個(gè)真正的藝術(shù)作品都破壞了某一種已成的種類,推翻了批評(píng)家們的觀念”[6]。作為一種全新的文學(xué)類型,新生的無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革命文學(xué),要想迅速獲得文學(xué)生產(chǎn)的生存權(quán),進(jìn)而取得“文化霸權(quán)”,急需一套嚴(yán)整規(guī)范的操作系統(tǒng),來反抗舊的文類規(guī)范。這種反抗,在年輕的革命文學(xué)倡導(dǎo)者看來,首要地建立在對(duì)五四以來文學(xué)傳統(tǒng)的批判之上。第二,“文學(xué)不能產(chǎn)生文學(xué)”,它們的誕生“依靠陽性元素的參與,即歷史、革命活動(dòng)的參與”,從而創(chuàng)造“新人”,即新的社會(huì)關(guān)系。[7]引而申之,“文化霸權(quán)”的斗爭(zhēng),不僅在于確立無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的地位,更內(nèi)在的目的是建立無產(chǎn)階級(jí)的全民集體意志,即“為革命而文學(xué)”,而非“為文學(xué)而革命”,取得政治霸權(quán)———即無產(chǎn)階級(jí)的革命勝利。所以,阿英通過破壞與建設(shè)兩個(gè)方面,來規(guī)整并確立無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的獨(dú)立性與合理性。一方面在于破壞,阿英通過批判五四以來的文壇創(chuàng)作與批評(píng),為革命文學(xué)的生存爭(zhēng)取空間。所以,阿英首先選擇了魯迅和魯迅的《阿Q正傳》,作為他宣判的導(dǎo)言。顯然,這篇文章引起爭(zhēng)論的激烈程度達(dá)到了阿英的預(yù)期,一是在于魯迅本身的旗幟性;一是在于阿英的批判是相當(dāng)徹底的:魯迅的創(chuàng)作模式———從內(nèi)容到形式,總體上被阿英所否定,即魯迅的風(fēng)格“冷氣逼人,陰森森如入古道”,所以阿Q時(shí)代是已經(jīng)死去了,《阿Q正傳》的技巧也已經(jīng)死去了。按照這種批判模式,阿英逐一對(duì)茅盾、葉圣陶、郁達(dá)夫、徐志摩、冰心等眾多聲名顯赫的作家作了定性,從而為新興的階級(jí)文學(xué)提供一個(gè)可以借鑒、反思的類型庫。另一方面在于建設(shè),阿英通過組織和創(chuàng)作、批評(píng)等多種形式,為革命文學(xué)建章立制。組織方面,1927年秋阿英與蔣光慈等人組成太陽社,出版《太陽月刊》、“太陽小叢書”等書刊,成為“革命文學(xué)論爭(zhēng)”的主陣地之一。20世紀(jì)30年代前后,結(jié)社是相當(dāng)普遍的現(xiàn)象,創(chuàng)造、太陽、未名以至集大成者左聯(lián),這些團(tuán)體的成立除了志同道合以外,更重要的是結(jié)社者要用團(tuán)體的力量,來為自己的文學(xué)范式斗爭(zhēng)。創(chuàng)作批評(píng)方面,阿英不僅創(chuàng)作了為數(shù)不少的詩歌、小說,如《革命的故事》、《一條鞭痕》、《餓人與饑鷹》等來實(shí)踐其文學(xué)理論,還編輯出版《怎樣研究新興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生活》、《青年作家ABC叢書》等多部理論著作,傳播無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理論的基礎(chǔ)知識(shí)。更多地,阿英通過批評(píng)實(shí)踐來建構(gòu)他的文學(xué)理想。阿英主張,“形式的批評(píng)是不能和內(nèi)容的批評(píng)分裂的,在事實(shí)上,它們是要互相溶解著的”[8]457,并且在他這里,美學(xué)的形式的批評(píng)是不能獨(dú)立于社會(huì)學(xué)的內(nèi)容的批評(píng)存在的。革命文學(xué)內(nèi)容與形式的統(tǒng)一,在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斗爭(zhēng)階段,阿英認(rèn)為最恰當(dāng)?shù)谋憩F(xiàn)即“暴動(dòng)就是藝術(shù)”。而所謂“暴動(dòng)就是藝術(shù)”并不等同“藝術(shù)=暴動(dòng)”,實(shí)際是要求革命文學(xué)必須具備與暴動(dòng)相似的美學(xué)特征:“烈風(fēng)雷雨般的粗暴偉大,力量很足,感人很深”,并且是“躍動(dòng)的,有新生命的。”[4]75這種“力之美”即是“革命文學(xué)”這一文類模式的總體特征。
1.2革命文學(xué)與無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的差異性
大慶石油文學(xué)文藝觀
對(duì)于1980年代大慶石油文學(xué)特質(zhì)的理解,固然離不開這一地域經(jīng)濟(jì)—文化的獨(dú)特性,但同時(shí)也應(yīng)當(dāng)注意到當(dāng)時(shí)我國(guó)文壇主流文藝觀對(duì)其產(chǎn)生的影響。不難理解,作家的創(chuàng)作活動(dòng)并非是一種封閉的、凝滯的或者是獨(dú)立自足的行為,而是一種較為開放的、嬗變的與時(shí)代文藝潮流不斷融合的過程。從這一意義上講,1980年代大慶石油文學(xué)的主體思想一方面是對(duì)新時(shí)期之初主流文藝思想的接納與吸收,另一方面則是對(duì)其進(jìn)行本土化實(shí)踐的表現(xiàn)。具體來說,極具中國(guó)化馬克思主義氣質(zhì)的人道主義話語體系乃是當(dāng)時(shí)思想界與文藝界所探索與實(shí)踐的核心,而對(duì)“人”自身價(jià)值的思索則在文藝學(xué)領(lǐng)域獲得了“本體論”的地位。正如洪子誠(chéng)先生在論及1980年代文藝思潮時(shí)指出:“人道主義,主體性等,成為80年代‘新啟蒙’思潮的主要‘武器’,是進(jìn)行現(xiàn)實(shí)批判,推動(dòng)文學(xué)觀念更新的最主要的‘話語資源’。”[1]回望1980年代大慶石油文學(xué)作品的基本面貌,不難看出,較為引人注目的是那種少數(shù)的、直面人性、揭發(fā)人較為本質(zhì)的“存在”狀態(tài)的篇章。在這部分作品中,文本不再重復(fù)建構(gòu)歷史性、階級(jí)性、時(shí)代精神乃至大慶精神的神話,而是朝向個(gè)體化的人的自身,呈現(xiàn)在我國(guó)當(dāng)時(shí)的工業(y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生存在“油田”這樣一個(gè)特定空間中的人與自然的或者人文的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以及這種相互關(guān)系對(duì)人的心理所產(chǎn)生的影響。除此之外,絕大部分石油文學(xué)的作品文本則在思想上還留有“頌歌”的痕跡,依循“十七年”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的慣性在既定的軌跡下運(yùn)行。
一、回歸社會(huì)的渴望:石油人對(duì)生存環(huán)境的思考
作為工業(yè)城市的大慶油田,前身是人煙稀少、水草稠密的一片荒原。1950年代末“松基三井”試噴成功,中央決定開發(fā)大慶油田,其指導(dǎo)方針是“邊勘探、邊開發(fā)、邊建設(shè)”。在這種毫無油田基礎(chǔ)設(shè)施支撐以及住房、醫(yī)療、文教等社會(huì)配套體系保障的情況下,來自五湖四海的石油工人走上了一條艱苦而漫長(zhǎng)的創(chuàng)業(yè)之路。然而,在物質(zhì)欲望被意識(shí)形態(tài)所壓抑與排斥的那個(gè)時(shí)代,肉體上的“苦”并不與“難”相互聯(lián)系,人們?cè)讷I(xiàn)身革命事業(yè)的要求下先驗(yàn)地將享樂主義視為一種精神上的污濁,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的是,在公共空間中艱苦生活的背后所隱藏的光榮感可謂昭然若揭。1960年代流行這樣一段民謠:“天當(dāng)房屋地當(dāng)床,棉衣當(dāng)被草當(dāng)墻,五兩三餐保會(huì)戰(zhàn),為國(guó)奪油心歡唱”,后來被作為大慶石油工人“創(chuàng)業(yè)”之初的真實(shí)寫照收入文獻(xiàn)資料[2]。這首民謠顯然反映出的石油工人安于甚至樂于現(xiàn)狀的心理狀況,也是不符合所謂“人性”化的生活狀態(tài)的典型代表。1980年代以后,“新啟蒙”思維在一定層面上顛覆了這種意識(shí),一方面人道主義的價(jià)值觀念對(duì)具體的人來講存在著巨大的吸引力,而與此同時(shí),朦朧詩、傷痕文學(xué)、反思文學(xué)等文藝作品對(duì)人道主義思想的藝術(shù)化宣揚(yáng)與傳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當(dāng)時(shí)的大慶石油文學(xué)對(duì)于上述觀念也做出了積極的反應(yīng),思索石油人在荒原中所經(jīng)歷的磨難便是其表現(xiàn)之一。楊利民的短篇小說《灰色的羽毛》是反映人與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之間的矛盾關(guān)系的典型,作家以異常冷靜的態(tài)度來描述他意識(shí)當(dāng)中石油人的生存狀態(tài),在荒原之中的孤獨(dú)體驗(yàn),為求解脫而做出的不計(jì)代價(jià)的努力,以及最終不得不接受的失敗結(jié)果。一支“常年在野外打井”的井隊(duì),完成鉆井任務(wù)后卻被困在“變成一片”的沼澤當(dāng)中,百無聊賴的鉆工們“憋得汗毛直打挺兒”,一個(gè)叫慶兒的孱弱鉆工為了給室友解悶,冒險(xiǎn)往返40里地到附近的村子買酒和煙葉,回來時(shí)因被草原的蚊蟲叮咬昏死過去,而他的室友卻為準(zhǔn)備下酒菜而殺死了慶兒豢養(yǎng)的一只孤雁,知道此事后慶兒“把胸脯抓出一條條血道子”,喊叫著“我心里難受啊!讓我死,讓我死吧……”這是一篇值得花費(fèi)腦力的小說,表面來看,讓慶兒“心里難受”的是孤雁的死,孤雁是慶兒的室友殺死的,不消說,慶兒的痛苦是室友的行為所造成的。但問題是室友殺死孤雁的目的并非為了傷害慶兒,與之相反,在他們眼里搞來酒和煙葉的慶兒簡(jiǎn)直就是他們的“親爹活祖宗”,是值得他們“好好地犒勞犒勞”的,殺雁的目的簡(jiǎn)單而純粹———做菜下酒。室友們知道那只孤雁是慶兒的“小伙伴,他離不開它”,但在殺雁的過程中他們的意識(shí)里卻有悖常理地忽略了此事對(duì)慶兒造成傷害的可能性,甚至荒唐地設(shè)想和慶兒一起以雁肉下酒。問題是,室友們意識(shí)當(dāng)中的“忽略”與“荒唐”的根源是什么,或者說為什么他們不能以一種常態(tài)思維去思考,并作出合乎常理之事。一名室友在接受“審判”時(shí)給出了上述問題的答案:“在井隊(duì)一沒活干,我就不知咋好。”事實(shí)上,被困在草原上的日子的確“使人寂寞得要發(fā)瘋了”。不難想象,人的生命過程基本上由社會(huì)生活與日常工作兩部分組成,而在家庭、愛情等狹義上的社會(huì)生活缺失的情況下,人心理的空虛所導(dǎo)致的精神異常現(xiàn)象是難以避免的。正是在這種狀態(tài)下,慶兒的室友才產(chǎn)生了這樣不正常的心理與行為。1980年代的文藝界與思想界,周揚(yáng)是人道主義思想的重要闡發(fā)者和倡導(dǎo)者。新時(shí)期之初,在《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gè)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中,周揚(yáng)對(duì)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guān)系做出了自己的理解,認(rèn)為“馬克思主義是包含著人道主義的”,而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本質(zhì)則是“馬克思主義是關(guān)心人,重視人的,是主張解放全人類的”[3]。結(jié)合周揚(yáng)的觀點(diǎn),我們發(fā)現(xiàn)《灰色的羽毛》所呈現(xiàn)的石油人的生存狀態(tài)卻是與上述人道主義相違背的。一方面在小說中人并未得到應(yīng)得的關(guān)心與重視,因?yàn)椤澳怯凶逃形兜那镉辍狈恋K了特車隊(duì)(運(yùn)輸大型機(jī)械的專用車輛隊(duì)伍,筆者注)對(duì)設(shè)備———也就是鉆井所使用的工具的搬遷,結(jié)果作為人的鉆工只能與設(shè)備一起被留在沼澤中,無所事事地“窩在列車房里叫苦”。對(duì)勞動(dòng)者與勞動(dòng)工具一視同仁,這顯然是非人道主義的表現(xiàn)。另一方面,人首先是社會(huì)的人,而讓個(gè)別人———如小說中“常年在野外打井”的鉆工,置身于群體社會(huì)之外,則是另一種非人道主義的表現(xiàn)。以自然環(huán)境對(duì)人性的壓抑的敘寫來喚起人道主義精神的回歸,正是這篇小說所代表的一部分石油文學(xué)對(duì)當(dāng)時(shí)文藝思想進(jìn)行應(yīng)和的具體體現(xiàn)。
二、異化感受的表露:石油人的主體化訴求
對(duì)于石油能源的開采無疑是一種復(fù)雜而持久的工業(yè)生產(chǎn)過程,在這個(gè)過程中,人將不可避免地將本來處于原始狀態(tài)的自然環(huán)境變更為承載現(xiàn)代化工業(yè)文明的人文環(huán)境。這樣的變更行為與我們祖先“逐水草而居”的行為特征有所不同,因?yàn)槎叩淖兏康木哂斜举|(zhì)的區(qū)別,后者是為了求得生存,而前者首要目的是為了獲取資源,并將其運(yùn)輸?shù)狡渌娜丝诟鼮槊芗牡赜颉>褪窃谶@種情況下,1980年代大慶作家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活動(dòng)一方面自覺接納了大慶精神,并對(duì)之進(jìn)行藝術(shù)化的再現(xiàn);另一方面,在他們的作品中卻表現(xiàn)出另一種“文學(xué)自覺”,一種較為符合人性的“自覺”,即對(duì)個(gè)體生存狀態(tài)與社會(huì)“全局”之間所存在的難以彌合的裂隙所產(chǎn)生的疑慮。當(dāng)然,這樣的疑慮很少直接地在文本中直接呈現(xiàn),畢竟大慶精神自形成之日起便是一種被人們所普遍接納的精神品格,因此作家在處理這種疑慮時(shí),往往通過更高層次的超驗(yàn)性政治話語———如“國(guó)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道德倫理話語,將其表象性地化解開來。在高文鐸的小說《罰電費(fèi)》中,主人公趙子虛因違反了油田限電條例遭到相關(guān)部門的處罰,他先是心有不滿,給《人民日?qǐng)?bào)》寫信狀告油田巧立名目,任意罰款,后又擔(dān)心這樣的“告狀”行為會(huì)給自己帶來麻煩,害怕遭到上級(jí)領(lǐng)導(dǎo)的打擊報(bào)復(fù)而忐忑不安。小說結(jié)尾處趙接到市政府發(fā)給他的“檢討信”,市長(zhǎng)表示接受他的批評(píng),這時(shí)趙卻一改初衷,認(rèn)為:“當(dāng)市長(zhǎng)也不易呀!國(guó)務(wù)院哪天不注視著D市的原油產(chǎn)量啊……D市為保年產(chǎn)五千萬噸———也就是給國(guó)家挑了一半擔(dān)子———不得不在年末采取節(jié)電、限電措施,這是完全必要的。”最終趙子虛認(rèn)識(shí)到,真正該檢討的人其實(shí)是自己。表面看來,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gè)普通群眾在領(lǐng)導(dǎo)的感化下提高了自身認(rèn)識(shí),樹立起全局觀念的思想轉(zhuǎn)變歷程,但依照主人公的思想發(fā)展邏輯脈絡(luò)來看,情況要復(fù)雜得多。開篇趙所面臨的矛盾是他與制度———“限電令”的矛盾,之后因?yàn)橥碌淖I笑與挑撥:“這些人純粹欺負(fù)你老實(shí),看你是個(gè)白丁!你看哪個(gè)市長(zhǎng)———不說大的,就算是局長(zhǎng)吧———挨罰了?”于是才給《人民日?qǐng)?bào)》寫信告狀。經(jīng)此一轉(zhuǎn),他與制度的矛盾轉(zhuǎn)化為與制度的制定者———高層領(lǐng)導(dǎo)的矛盾,小說中擔(dān)心報(bào)復(fù)這一細(xì)節(jié)正是上述矛盾轉(zhuǎn)化的例證。結(jié)尾處市長(zhǎng)所做出的以德服人的姿態(tài),既讓趙解除了憂慮,又讓他進(jìn)一步產(chǎn)生了慚愧的心理,因此意識(shí)到自己才是“該檢討”的人。顯然,小說最初的矛盾在結(jié)尾時(shí)并未得以化解,整個(gè)敘事行為成為一個(gè)“偷換概念”的過程,事實(shí)上,發(fā)生這一情況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作家無法對(duì)小說所涉及的制度———“限電令”做出合理化說明。按照今天的理解,石油開采是為了全體國(guó)民更好地生活,而趙子虛也是國(guó)民的一分子,從這個(gè)角度看,“限電令”表面來看是為國(guó)民群體謀求利益,實(shí)際上卻損害了石油人個(gè)體的利益。1980年代的文藝思想中,與人道主義密切聯(lián)系的還有關(guān)于人的“異化”問題。我國(guó)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異化這一概念的關(guān)注,源自王若水1979年發(fā)表的《關(guān)于“異化”的概念》,文章從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出發(fā),描述了作者對(duì)于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理解。此后,他又在《談?wù)劗惢瘑栴}》一文中對(duì)“異化”給出具體的定義:“本來是自己創(chuàng)造的東西,或者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它發(fā)展的后果,成為一種異己的力量,超出了人們的控制,結(jié)果反過來支配自己,壓制了自己。”[4]不難看出,《罰電費(fèi)》中趙子虛憤懣的深層次原因便來自于上述理論,即大慶人開采石油,而自己的生活反而受石油所牽制。盡管小說設(shè)置了一個(gè)趙在市長(zhǎng)的感化下“提高覺悟”的完滿結(jié)局,但這并不能彌補(bǔ)上述敘事中的裂隙。很難判斷作家高文鐸在寫作過程中存在著什么動(dòng)機(jī),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篇小說是1980年代石油文學(xué)中為數(shù)不多的繞開意識(shí)形態(tài)中“總體性”的思維方式,將人作為“主體”加以表現(xiàn)的文本個(gè)案。
三、疏離人道主義:石油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主流的選擇方向
戲曲家文學(xué)價(jià)值觀
在《中國(guó)古代戲曲的詩樂教化傳統(tǒng)》一文中,我們?cè)懻摿擞伞睹娦颉匪於ǖ摹霸娧灾尽钡奈膶W(xué)價(jià)值觀以及“詩樂教化”傳統(tǒng)對(duì)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以及中國(guó)古代戲曲的影響。我們認(rèn)為《毛詩序》所確立的“上以風(fēng)化下”和“下以風(fēng)刺上”的詩教原則以及“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的詩教規(guī)范決定了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包括中國(guó)古代戲曲的基本發(fā)展方向。本文想就《毛詩序》的詩樂教化觀對(duì)中國(guó)古代戲曲家的文學(xué)價(jià)值觀念的影響進(jìn)一步展開討論。因?yàn)檎侵袊?guó)古代戲曲家的文學(xué)價(jià)值觀,決定著戲曲家的戲曲創(chuàng)作傾向。
一、中國(guó)古代戲曲家的社會(huì)地位與詩樂教化傳統(tǒng)
在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中,與正統(tǒng)的詩文作家相比,戲曲作家,特別是一些有成就的戲曲作家,大多出身較低。這些人有的由于時(shí)代的原因,如元代戲曲家關(guān)漢卿、馬致遠(yuǎn)、王實(shí)甫、白樸等;有的由于個(gè)人遭際,如明代的徐渭、清代的李漁、孔尚任、洪昇;有的是科舉仕進(jìn)無門,如馮夢(mèng)龍、蒲松齡等;有的是官場(chǎng)失意急流勇退,如湯顯祖、沈璟等。種種原因,促使這些文化精英把自己的卓越才華獻(xiàn)身于當(dāng)時(shí)被一些正統(tǒng)文人鄙棄的戲曲事業(yè)。這也許應(yīng)了那句老話:“患難出詩人。”現(xiàn)實(shí)的遭際,特別是社會(huì)的黑暗,才造成有識(shí)之士的覺悟:“布衣中,問英雄,王圖霸業(yè)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宮,楸梧遠(yuǎn)遠(yuǎn)千官冢,一場(chǎng)惡夢(mèng)!”只有這種覺醒,才使他們走出官場(chǎng),出入瓦舍勾欄,甚至“躬踐排場(chǎng),面敷粉墨,偶倡優(yōu)而不辭”。豐富的舞臺(tái)經(jīng)驗(yàn)和熟悉社會(huì)人情以及對(duì)觀眾心理的了解,成就了他們的另一番事業(yè):“戰(zhàn)文場(chǎng),曲狀元,姓名香貫滿梨園。”由于中國(guó)古代戲曲作家這種特殊的社會(huì)地位,使得大多數(shù)戲曲作家在思想傾向上往往具有鮮明的兩重性:一是由于其出身較低,或是身處社會(huì)底層,使他們比較接近民眾,因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眾的呼聲,使其作品具有一定的民主性或曰人民性的思想傾向。而且相對(duì)來說,越是身處底層,這種傾向就越為鮮明。
另一方面,中國(guó)古代戲曲作家畢竟是讀書人,屬于士階層。即使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后期的一些知識(shí)分子,其出身屬于市民階層,如李卓吾等,其在經(jīng)濟(jì)上、政治上,仍然依附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jí),加之其思想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永遠(yuǎn)也不能成為與封建政治根本對(duì)立的所謂“拆天派”,而是不折不扣的“補(bǔ)天派”。他們的“孤憤”與“牢騷”,只是因?yàn)椤盁o才補(bǔ)天”的遺憾,是“不被見用”的憤懣:他們既使“身在山林”,卻永遠(yuǎn)地“心存魏闕”。戲曲成了他們?yōu)榉饨ńy(tǒng)治階級(jí)服務(wù)的一種“代言”的工具。中國(guó)古代戲曲作家的這一雙重身份恰與《毛詩序》所確立的詩教的雙重意義相吻合。“上以風(fēng)化下”,決定其為統(tǒng)治階級(jí)服務(wù),向民眾進(jìn)行政治教化;“下以風(fēng)刺上”,表達(dá)其用文學(xué)批評(píng)政治,傳達(dá)下層人民呼聲的愿望。由此決定了中國(guó)古代戲曲作家的文學(xué)價(jià)值觀,也決定了中國(guó)古代戲曲在思想傾向上所體現(xiàn)的鮮明的兩重性:一是利用戲曲鞭撻社會(huì),諷刺現(xiàn)實(shí);二是利用戲曲宣揚(yáng)封建教化,為統(tǒng)治階級(jí)張目。這二者還常常糾纏在一起,或互相融合,或互為表里,從而造成對(duì)中國(guó)古代戲曲思想評(píng)價(jià)上的困難和分歧,乃至見仁見智,或褒或貶,爭(zhēng)論不休。周貽白先生在《中國(guó)戲曲發(fā)展史綱要》一書中曾多次強(qiáng)調(diào)提出:中國(guó)古代戲曲所具有的“人民性和斗爭(zhēng)性”,這也正是中國(guó)古代戲曲在當(dāng)時(shí)深受人民歡迎,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社會(huì)意義的價(jià)值所在。
但是,我們認(rèn)為,在充分肯定中國(guó)古代戲曲所具有的“人民性和斗爭(zhēng)性”的歷史意義,從而對(duì)中國(guó)古代戲曲的思想傾向做出積極肯定的同時(shí),也必須看到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中國(guó)古代戲曲對(duì)黑暗政治的“揭發(fā)或暴露”,往往局限在一定尺度中。這個(gè)尺度就是《毛詩序》所規(guī)定的“發(fā)乎情,止乎禮義”,是“怨悱而不怒”。我們?cè)凇吨袊?guó)古代戲劇的詩樂教化傳統(tǒng)》一文中曾經(jīng)以關(guān)漢卿的戲曲對(duì)此做出說明。其實(shí),湯顯祖之《牡丹亭》亦是如此。在《牡丹亭》中,湯顯祖把“情”上升到可以使人“死而復(fù)生”的高度,然而,湯顯祖認(rèn)為“情”的作用仍然是“可以合君臣之節(jié),可以浹父子之恩,可以增長(zhǎng)幼之睦,可以東夫婦之歡。”“情”還是為封建禮義服務(wù)的。不僅如此,中國(guó)古代戲曲家在“揭發(fā)或暴露”社會(huì)黑暗或官場(chǎng)腐敗時(shí),往往別有懷抱,即希望“觀民風(fēng)者得之。”就如《國(guó)語·邵公諫彌謗》所說:“為川者決之使導(dǎo),為民者決之使宣。”因此,對(duì)這種“揭發(fā)或暴露”評(píng)價(jià)過高,恐怕也失之偏頗。比如洪昇的《長(zhǎng)生殿》即是如此。
《長(zhǎng)生殿》之劇情,基本上是按《長(zhǎng)恨歌》所敘之情節(jié),寫楊玉環(huán)之死,大體與白樸之《梧桐雨》相近似。但《長(zhǎng)生殿》與上述作品之不同處乃在于它把當(dāng)時(shí)人民的疾苦與楊氏一門的驕縱奢侈作對(duì)比。如《進(jìn)果》一出,寫進(jìn)果之使者不擇途徑,踏壞田禾,甚至踹死行人,有力地揭露統(tǒng)治階級(jí)虐害人民的罪行。再看《疑讖》一出,寫郭子儀目睹了楊氏兄弟炙手可熱,感慨外戚寵盛:“怪私家恁僭竊,競(jìng)豪奢,夸土木。一班兒公卿甘作折腰趨,爭(zhēng)向權(quán)門如市附。再?zèng)]有一個(gè)人呵,把輿情向九重分訴。可知他朱甍碧瓦,總是血膏涂!”這種揭露是深刻的,其批判也是無情的。洪昇的《長(zhǎng)生殿》被推崇為清之杰作,其確有超越前人之處,但卻不可對(duì)其反抗性評(píng)價(jià)過高。《長(zhǎng)生殿》在清代宮廷中演出大受歡迎,其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因?yàn)槠淠軌驗(yàn)榻y(tǒng)治階級(jí)提供借鑒,其藝術(shù)效果也充分說明這一點(diǎn)。
文學(xué)的傳播學(xué)視角觀照
一
今時(shí)代,大眾傳播對(duì)人類社會(huì)和人們的生活產(chǎn)生日益深刻的影響,身處這樣一種社會(huì)環(huán)境和傳播環(huán)境,文學(xué)的存在現(xiàn)狀和發(fā)展趨向受其制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并構(gòu)成了當(dāng)代“文學(xué)場(chǎng)”,在如此時(shí)空關(guān)系里,文學(xué)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價(jià)值取向都具有其新的特點(diǎn)。一種適應(yīng)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特點(diǎn)、多元并存的新的文學(xué)格局正在構(gòu)建之中。
傳播是“人類關(guān)于賴以存在和發(fā)展的機(jī)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且通過空間傳達(dá)它們和通過時(shí)間保存它們的手段”。(1)就傳播學(xué)的核心概念而言,它是人們一種信息的交流和分享。那么,從文學(xué)傳播的角度著眼,什么樣的信息拿出來讓大家分享?是誰拿出來這些信息?通過什么渠道或載體?誰在分享?信息制造者是誰?為什么在這樣的時(shí)刻和場(chǎng)合以這種方式顯示出來?能產(chǎn)生什么效果?等等。對(duì)這些從傳播學(xué)原理出發(fā)所提出的問題的探究,使我們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當(dāng)前的文學(xué)傳播語境上。人們常常用“后現(xiàn)代”或“后新時(shí)期”等概念來為當(dāng)今社會(huì)轉(zhuǎn)型命名。這是一個(gè)政治、經(jīng)濟(jì)、科技、文化一體化的時(shí)代,伴隨著資本的流通以及商業(yè)廣告與大眾傳播媒介的鼓噪,人們的消費(fèi)欲望被點(diǎn)燃起來,在市場(chǎng)流通過程中逐漸衍生成一種“消費(fèi)主義文化”。那些以守護(hù)靈魂家園為文化使命的文人敏銳地意識(shí)到“今天時(shí)代的熱點(diǎn)不在精神而在物質(zhì),不在追求完善而在追求舒適。形而上的道遠(yuǎn)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則有益于生存……我們面臨的將是一個(gè)世俗的、淺表的、消費(fèi)文化繁榮的時(shí)期”。(2)這正是當(dāng)代文學(xué)生存的處境和傳播語境,一切都在消費(fèi)當(dāng)中,物質(zhì)的欲求、觀念的更新、信息的分享等,最終都可以視為某種物質(zhì)的或精神的,或兩者兼而有之的消費(fèi)現(xiàn)象。大眾傳播媒介多聲道、立體聲的傳播,不僅刺激起消費(fèi)的欲望,而且正是通過媒體消費(fèi)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shí)現(xiàn)。
與這種“后現(xiàn)代”的消費(fèi)主義與文化相聯(lián)系的另一個(gè)特征就是消解一切。在消費(fèi)過程中,同時(shí)也在進(jìn)行著消解原有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價(jià)值,消解著傳統(tǒng)的中心意識(shí)。社會(huì)的文化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重大的改變,當(dāng)今中國(guó)文學(xué)已從結(jié)構(gòu)的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滑落。身處這樣一個(gè)消費(fèi)與消解的時(shí)代,正如馬爾庫塞所洞察的那樣,它們“限制著升華的領(lǐng)域,同時(shí)也降低了對(duì)升華的需要”。(3)受制于時(shí)代的語境的變遷,文學(xué)的價(jià)值被重新定位,現(xiàn)今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生了許多重大變化,文稿競(jìng)賣、作家簽約、媒體炒作、自由撰稿人、快餐讀物、小說百強(qiáng)等等,一一映證了這種文學(xué)生態(tài)環(huán)境和價(jià)值趨向正在發(fā)生改變。
既然有新的要素注入文學(xué)領(lǐng)域,對(duì)文學(xué)的認(rèn)識(shí)把握就需要有新的視角、新的理論和新的方法與之相適應(yīng)。現(xiàn)代社會(huì)是傳播業(yè)發(fā)達(dá)的信息化社會(huì),文學(xué)不僅不可能置身于傳播環(huán)境之外,其反映社會(huì)生活的內(nèi)在規(guī)定性還促使其積極參與其中,文學(xué)要滿足社會(huì)對(duì)它的需要首先得表明自己的存在,需要有媒介來負(fù)載它們,使其能往來穿梭于社會(huì)大眾之間。尤其是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下,文學(xué)與大眾媒介傳播之間有著精神文化和物質(zhì)利益雙重密切聯(lián)系。進(jìn)入市場(chǎng)后的文學(xué),同樣也被市場(chǎng)這只看不見的手所操縱著。其實(shí)只要我們掌握媒介的特點(diǎn)和運(yùn)行規(guī)律,對(duì)已經(jīng)出現(xiàn)和將要出現(xiàn)的種種文學(xué)現(xiàn)象是能夠把握其脈絡(luò)并加以解讀的。由于大眾傳播媒介在市場(chǎng)化背景下的運(yùn)作,一種新的文學(xué)關(guān)系出現(xiàn)了,即“作家——傳播者——受眾”,以及與之對(duì)應(yīng)耦合的“文本生產(chǎn)——媒介傳播——文本消費(fèi)”這樣一種結(jié)構(gòu)功能關(guān)系。
這一文學(xué)關(guān)系的最大特點(diǎn)是引入了一個(gè)中介層,而不同于以往作家與作品、讀者與作品那么一種簡(jiǎn)單的、封閉的文學(xué)聯(lián)系。作家思考什么、寫什么,讀者愿看什么、希望得到什么,有如一堵墻分隔開來,彼此互不相擾,顯得非常陌生。作家作為主體只是根據(jù)自己的生活感受、興趣愛好和內(nèi)心的使命感自發(fā)地創(chuàng)作,當(dāng)然,有時(shí)也會(huì)結(jié)合政策背景來寫作。相對(duì)而言,讀者只是被動(dòng)選擇,他們的要求、愿望,還沒有找到一種合適的渠道表達(dá)出來。作家對(duì)此不了解,似乎也不太關(guān)心,即使作家與讀者之間存在著某些聯(lián)系,也是非常松散的、可有可無的,對(duì)文學(xué)的影響無關(guān)大局。所謂純文學(xué)多少與這種文學(xué)關(guān)系有關(guān),是其關(guān)系下的產(chǎn)物。而在“作家(文本生產(chǎn))——傳播者(媒介傳播)——受眾(文本消費(fèi))”的結(jié)構(gòu)中,三者之間存在自變量和因變量的動(dòng)態(tài)協(xié)調(diào)整合過程,是三方有機(jī)地結(jié)合,彼此互動(dòng)參與文學(xué)活動(dòng)的三方主體地位都能得到充分尊重。讀者市場(chǎng)的因素進(jìn)入文學(xué)活動(dòng)中,作家的寫作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必須充分考慮到讀者的閱讀需求,一旦失去了讀者市場(chǎng),作家、作品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chǔ)。那么讀者市場(chǎng)如何產(chǎn)生?如何把握?媒介和傳播者起了關(guān)鍵性的作用,媒介直接與受眾發(fā)生聯(lián)系,對(duì)其接受的品味、愛好、注意力等及其變化因素,不斷進(jìn)行收集、分析、整理,并且通過供給運(yùn)作(有時(shí)是炒作)的方式來制造市場(chǎng)需求。同時(shí),把讀者市場(chǎng)信息反饋給作家,作家們又根據(jù)這些信息創(chuàng)作出新的作品,再由媒介推向讀者市場(chǎng)。這是一個(gè)不斷循環(huán)的雙向運(yùn)動(dòng)過程。文學(xué)的生成機(jī)制、生存狀態(tài)、影響方式、反饋原理、運(yùn)行規(guī)則等都在這種結(jié)構(gòu)功能關(guān)系中得到實(shí)現(xiàn)。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環(huán)境中,在信息時(shí)代的背景下,它為我們考察文學(xué)及其變化,提供了一個(gè)新的視角和便于操作的方法。
語文學(xué)生觀指導(dǎo)教學(xué)論文
[內(nèi)容]
我從事中學(xué)語文教學(xué)工作,至今已經(jīng)十六年。在十幾年的教學(xué)中,我對(duì)教育對(duì)象——學(xué)生的認(rèn)識(shí),經(jīng)歷了一個(gè)由模糊到明確的認(rèn)識(shí)過程。其間遇到了不少問題,也存在許多困惑,這些促使我對(duì)教學(xué)實(shí)踐不斷地思考。
第一次教《背影》這篇課文,我是按照很規(guī)范的教學(xué)模式進(jìn)行的,介紹背景,朗讀課文,分析課文,還特別注意抓住關(guān)鍵詞語和句子進(jìn)行具體分析。例如:“他……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讓學(xué)生分析其中的動(dòng)詞所包含的人物思想感情,這些動(dòng)詞如何用得好,不可替換等等。但是,學(xué)生學(xué)起來并不認(rèn)為這篇名作精彩,講到這段內(nèi)容,學(xué)生還覺得很好玩,很可笑,甚至認(rèn)為父親給兒子買橘子這樣的小事,實(shí)在不值一提。作為語文教師,我把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語言感受能力和分析能力當(dāng)作重要任務(wù)完成,精心設(shè)計(jì),認(rèn)真落實(shí),學(xué)生卻并不喜歡,他們沒有真正領(lǐng)會(huì)到《背影》這篇文學(xué)名作的藝術(shù)魅力,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后來,我又兩次教這篇課文,換了教法:我先談我和父母之間的關(guān)系,講父母對(duì)我生活上思想上的關(guān)心幫助,特別是母親在我插隊(duì)、考大學(xué)、擇業(yè)等重大問題上對(duì)我的支持和鼓勵(lì)。然后由學(xué)生談他和父母之間的關(guān)系,談父母對(duì)他的關(guān)心和幫助。在這兩次教學(xué)中,學(xué)生都非常激動(dòng),發(fā)言十分踴躍。更令人感動(dòng)的是,兩次都有學(xué)生含著熱淚向大家講述父母對(duì)自己關(guān)懷備至的故事。接著師生一起學(xué)習(xí)《背影》,學(xué)生的精神狀態(tài)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不但不笑,而且連讓學(xué)生表演父親爬上月臺(tái)的吃力動(dòng)作,都非常投入。在這樣特別的情境之中,師生一起認(rèn)真體味、分析了文章的語言,理解了文章的內(nèi)容。整個(gè)教學(xué)過程,教師、學(xué)生、教材三者達(dá)到了一種融和。
我曾經(jīng)把大量精力放在研究教材、教法上,放在研究如何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語文能力上,因?yàn)槲易铌P(guān)注的是學(xué)科能力。然而,《背影》一課的兩種教法所帶來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教學(xué)效果,給我的觸動(dòng)很大。我問自己,我在教學(xué)中首先關(guān)注的應(yīng)該是什么?
按照傳統(tǒng)的教育觀,教師把學(xué)生僅僅看作學(xué)生,那么教師的任務(wù)就是教課,就是傳授知識(shí),培養(yǎng)能力。這樣,在教學(xué)過程中教師關(guān)注最多的是學(xué)生的認(rèn)知活動(dòng),學(xué)生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思想、情感、心理、個(gè)性等或是被忽略,或是被置于次要地位。而學(xué)生的任務(wù)就是學(xué)習(xí),甚至是以聽代思的學(xué)習(xí)。師生雙方的關(guān)系是不平等的,教師主宰一切,學(xué)生則處于被動(dòng)狀態(tài),課堂上缺乏“人”的互愛與互信,缺乏民主的、融洽的教育氣氛。但是今天,時(shí)代的發(fā)展,社會(huì)的進(jìn)步,已經(jīng)迫使教師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簡(jiǎn)單地看待學(xué)生。教師說什么學(xué)生聽什么,這樣對(duì)待學(xué)生,似乎已經(jīng)不可能。現(xiàn)代社會(huì)更注重的是人本身——人的潛能、人的發(fā)展、人的個(gè)性和人的價(jià)值,這就要求教師必須改變傳統(tǒng)的學(xué)生觀。
語文學(xué)生觀指導(dǎo)教學(xué)論文
我從事中學(xué)語文教學(xué)工作,至今已經(jīng)十六年。在十幾年的教學(xué)中,我對(duì)教育對(duì)象——學(xué)生的認(rèn)識(shí),經(jīng)歷了一個(gè)由模糊到明確的認(rèn)識(shí)過程。其間遇到了不少問題,也存在許多困惑,這些促使我對(duì)教學(xué)實(shí)踐不斷地思考。
第一次教《背影》這篇課文,我是按照很規(guī)范的教學(xué)模式進(jìn)行的,介紹背景,朗讀課文,分析課文,還特別注意抓住關(guān)鍵詞語和句子進(jìn)行具體分析。例如:“他……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讓學(xué)生分析其中的動(dòng)詞所包含的人物思想感情,這些動(dòng)詞如何用得好,不可替換等等。但是,學(xué)生學(xué)起來并不認(rèn)為這篇名作精彩,講到這段內(nèi)容,學(xué)生還覺得很好玩,很可笑,甚至認(rèn)為父親給兒子買橘子這樣的小事,實(shí)在不值一提。作為語文教師,我把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語言感受能力和分析能力當(dāng)作重要任務(wù)完成,精心設(shè)計(jì),認(rèn)真落實(shí),學(xué)生卻并不喜歡,他們沒有真正領(lǐng)會(huì)到《背影》這篇文學(xué)名作的藝術(shù)魅力,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后來,我又兩次教這篇課文,換了教法:我先談我和父母之間的關(guān)系,講父母對(duì)我生活上思想上的關(guān)心幫助,特別是母親在我插隊(duì)、考大學(xué)、擇業(yè)等重大問題上對(duì)我的支持和鼓勵(lì)。然后由學(xué)生談他和父母之間的關(guān)系,談父母對(duì)他的關(guān)心和幫助。在這兩次教學(xué)中,學(xué)生都非常激動(dòng),發(fā)言十分踴躍。更令人感動(dòng)的是,兩次都有學(xué)生含著熱淚向大家講述父母對(duì)自己關(guān)懷備至的故事。接著師生一起學(xué)習(xí)《背影》,學(xué)生的精神狀態(tài)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不但不笑,而且連讓學(xué)生表演父親爬上月臺(tái)的吃力動(dòng)作,都非常投入。在這樣特別的情境之中,師生一起認(rèn)真體味、分析了文章的語言,理解了文章的內(nèi)容。整個(gè)教學(xué)過程,教師、學(xué)生、教材三者達(dá)到了一種融和。
我曾經(jīng)把大量精力放在研究教材、教法上,放在研究如何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語文能力上,因?yàn)槲易铌P(guān)注的是學(xué)科能力。然而,《背影》一課的兩種教法所帶來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教學(xué)效果,給我的觸動(dòng)很大。我問自己,我在教學(xué)中首先關(guān)注的應(yīng)該是什么?
按照傳統(tǒng)的教育觀,教師把學(xué)生僅僅看作學(xué)生,那么教師的任務(wù)就是教課,就是傳授知識(shí),培養(yǎng)能力。這樣,在教學(xué)過程中教師關(guān)注最多的是學(xué)生的認(rèn)知活動(dòng),學(xué)生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思想、情感、心理、個(gè)性等或是被忽略,或是被置于次要地位。而學(xué)生的任務(wù)就是學(xué)習(xí),甚至是以聽代思的學(xué)習(xí)。師生雙方的關(guān)系是不平等的,教師主宰一切,學(xué)生則處于被動(dòng)狀態(tài),課堂上缺乏“人”的互愛與互信,缺乏民主的、融洽的教育氣氛。但是今天,時(shí)代的發(fā)展,社會(huì)的進(jìn)步,已經(jīng)迫使教師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簡(jiǎn)單地看待學(xué)生。教師說什么學(xué)生聽什么,這樣對(duì)待學(xué)生,似乎已經(jīng)不可能。現(xiàn)代社會(huì)更注重的是人本身——人的潛能、人的發(fā)展、人的個(gè)性和人的價(jià)值,這就要求教師必須改變傳統(tǒng)的學(xué)生觀。
教師在教學(xué)過程中首先要把學(xué)生看作一個(gè)人,要確認(rèn)學(xué)生作為“人”的地位和作用。因?yàn)槲覀兊慕虒W(xué)面對(duì)的是一個(gè)個(gè)活生生的人和他們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而不是以往教學(xué)理論和實(shí)踐所看到的諸如教材、教法、作業(yè)、分?jǐn)?shù)等沒有生命力的東西。學(xué)生的認(rèn)知活動(dòng)(學(xué)習(xí)活動(dòng)),絕不僅僅是大腦的思維活動(dòng),絕不僅僅是局部的、孤立的、某一方面的活動(dòng),而是作為一個(gè)整體的人——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有個(gè)性、有行為的人全身心都參與和投入的活動(dòng)。所以教師在教學(xué)過程中,首先應(yīng)該關(guān)注的是學(xué)生作為“人”的全部因素,其次才是學(xué)生的認(rèn)知活動(dòng),才是教授知識(shí)、培養(yǎng)能力。而且,學(xué)生的認(rèn)知活動(dòng)也只有在首先成為了充滿生命活力的人的活動(dòng)的時(shí)候,才能夠煥發(fā)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從而推動(dòng)學(xué)生的認(rèn)知活動(dòng)順利、高效地進(jìn)行。正像前蘇聯(lián)教育學(xué)家阿莫納什維利所說的:“兒童單靠動(dòng)腦,只能理解和領(lǐng)悟知識(shí);如果加上動(dòng)手,他就會(huì)明白知識(shí)的實(shí)際意義;如果再加上心靈的力量,那么知識(shí)將成為他改造事物和進(jìn)行創(chuàng)造的工具。”
電影文學(xué)觀評(píng)價(jià)管理論文
【內(nèi)容摘要】本文圍繞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中國(guó)電影界對(duì)著名電影理論家、劇作家、導(dǎo)演張駿祥提出電影的文學(xué)價(jià)值等主張的評(píng)價(jià)問題作了分析,充分肯定了張駿祥電影文學(xué)觀的學(xué)理價(jià)值。
【關(guān)鍵詞】張駿祥;電影的文學(xué)性;敘事傳統(tǒng)
20世紀(jì)80年代,中國(guó)電影工作者曾密切關(guān)注過電影文學(xué)性和文學(xué)價(jià)值的電影學(xué)術(shù)問題,90年代電影界有學(xué)者重申和發(fā)揮了當(dāng)時(shí)參與該問題討論的重要人物——著名電影理論家、劇作家、導(dǎo)演張駿祥所提電影的文學(xué)價(jià)值等主張,肯定了張駿祥電影文學(xué)觀的合理性①,本人雖已發(fā)表《論張駿祥的電影文學(xué)觀》②,但意猶未盡,加一補(bǔ)充,以期引起進(jìn)一步探求電影本體論意義上電影文學(xué)的價(jià)值。
一
張駿祥指出:“電影文學(xué)應(yīng)該不是指紙上印出來的劇本,而是最后通過電影表現(xiàn)手段拍出來的電影。真正最后完成的電影文學(xué)是在銀幕上放出來的電影。”③
“電影文學(xué)究竟是指什么而言呢?一般講電影文學(xué),往往想到的是印在紙上的電影劇本,說是影片的基矗……但劇本確實(shí)還不是完成了的電影文學(xué)。真正的電影文學(xué)的完成形式是最后在銀幕上放映出來的影片。……真正完成的戲劇文學(xué)是在舞臺(tái)上對(duì)觀眾演出了的那臺(tái)戲。人們對(duì)那些只能在書房里讀讀,在舞臺(tái)上沒有效果的‘書齋劇’,是不承認(rèn)它是好戲劇文學(xué)的。即使是好作品,例如契訶夫的劇本,在沒有得到莫斯科小劇院的演出之前,也不可能真正顯現(xiàn)出它的光輝。一個(gè)電影劇本的光輝,更是非拍成影片在銀幕上放映,就不能完全顯現(xiàn)出來。”④
朱自清文學(xué)批評(píng)觀述評(píng)
朱自清的“背影”被世人記住是在上世紀(jì)30年代,他用溫潤(rùn)的筆尖細(xì)膩地勾勒著一個(gè)又一個(gè)人們熟悉又陌生的生活細(xì)節(jié),月色映照下的荷塘、年邁的背影、指縫中的時(shí)間等一起組成了他豐富多彩的散文世界。獨(dú)特的生存體驗(yàn)使他多了幾許平常人少有的靈性與感悟,他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散文佳作一時(shí)間如雨后春筍般在中國(guó)的大地上生根發(fā)芽,開花結(jié)果。半個(gè)多世紀(jì)以來,對(duì)于朱自清的研究,學(xué)者們從不同角度全面關(guān)照探索,均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但仔細(xì)分析之后,我們發(fā)現(xiàn)從理論的層面關(guān)注其文學(xué)批評(píng)觀及其批評(píng)實(shí)踐的著作論文卻少之又少。作為一名作家,朱自清不僅在散文創(chuàng)作,新詩研究,語文教學(xué)方面有所建樹,同時(shí)也給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諸如《新詩雜話》、《什么是散文》等理論文章及批評(píng)著作,對(duì)較長(zhǎng)時(shí)間文學(xué)的發(fā)展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dòng)作用。朱自清的文學(xué)批評(píng)觀注重向作家作品審美心理的逼近,關(guān)注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時(shí)刻為人民大眾、為文學(xué)發(fā)展著想,其精髓所代表的那種“理想主義”正像背影一樣,正漸漸地被這個(gè)時(shí)代所遺忘。現(xiàn)代社會(huì)注重現(xiàn)實(shí)功利性,評(píng)論家缺少的是坐下來靜靜地欣賞文學(xué)內(nèi)部的精彩世界,忽略了文學(xué)體驗(yàn)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拗口的學(xué)術(shù)術(shù)語。因而,我們有必要對(duì)朱自清的文學(xué)批評(píng)觀做一完整的剖析,尋求文學(xué)批評(píng)真正的源頭活水。
一、文學(xué)批評(píng)觀的形成
早在《朱自清書評(píng)序跋集》的序言中,先生就已經(jīng)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現(xiàn)狀做了精確的把握。當(dāng)時(shí),大多數(shù)人認(rèn)為沒有創(chuàng)作才能的人才去從事文學(xué)批評(píng),批評(píng)只是二流貨色,因此人們都不愿意研究它。另一方面是與我國(guó)的文學(xué)發(fā)展史有關(guān),我們的詩文評(píng)片斷的多,成形的少,文學(xué)批評(píng)不易下手。鑒于文學(xué)批評(píng)不被重視又不可忽視的這種尷尬現(xiàn)狀,朱自清以一個(gè)學(xué)者批評(píng)家的姿態(tài)介入其中。一生在文學(xué)批評(píng)方面著述頗多,有《詩言志辨》、《朱自清序跋集》、《民眾文學(xué)談》、《文藝的真實(shí)性》、《中國(guó)新文學(xué)大系詩集導(dǎo)言》等多部著作流傳于世。朱自清正式從事文學(xué)批評(píng)活動(dòng)是在20世紀(jì)30年代初,正值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發(fā)展相對(duì)活躍與成熟之時(shí)。那個(gè)年代的中國(guó)學(xué)界,“教授批評(píng)已是蔚為大觀,周作人、梁實(shí)秋、朱自清、朱光潛、錢鐘書、梁宗岱等都是在大學(xué)執(zhí)教的批評(píng)家,而這些教授同時(shí)也是當(dāng)時(shí)文壇上創(chuàng)作的活躍分子。”“當(dāng)時(shí)的教授文學(xué)批評(píng)極大地促進(jìn)了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發(fā)展,是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不可忽視的一支‘正規(guī)軍’,甚至可以說,沒有這些教授批評(píng)家,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在批評(píng)方法、批評(píng)問題上要獲得健康發(fā)展是比較困難的。”[1]在這樣的時(shí)代背景下,朱自清開始了他的批評(píng)生涯。對(duì)他而言,雖然最初并不是以一位職業(yè)批評(píng)家的身份登上文壇,但知識(shí)分子應(yīng)有的良知與社會(huì)責(zé)任感促使一切外界的力量并未能削弱他關(guān)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發(fā)展的熱情。朱自清時(shí)刻以歷史的眼光和“為人生”又“為人民”的文學(xué)情操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作家作品進(jìn)行著獨(dú)特的審美關(guān)照。其評(píng)論文章字出有據(jù)、深入淺出,對(duì)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dòng)作用。
二、文學(xué)批評(píng)觀的內(nèi)容
面對(duì)當(dāng)時(shí)文壇的嚴(yán)峻形勢(shì),知識(shí)分子與生俱來的使命感讓作家出身的朱自清明白,他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使當(dāng)時(shí)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擺脫目前這種尷尬的境地,從創(chuàng)作的附庸地位提高到獨(dú)立的學(xué)科地位。于是,在教學(xué)之余,他時(shí)刻關(guān)注文藝動(dòng)向,批評(píng)活動(dòng)能夠跳出傳統(tǒng)的批評(píng)模式,合理吸收西方近代批評(píng)的理論方法,這使得朱自清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在當(dāng)時(shí)的批評(píng)界體現(xiàn)出獨(dú)特的批評(píng)特點(diǎn),發(fā)出自己獨(dú)特的聲音。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1、注重考據(jù)的批評(píng)方法。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體認(rèn),讓朱自清在批評(píng)活動(dòng)中不由自主地運(yùn)用到歷史考據(jù)的方法,體現(xiàn)出濃厚的史筆意識(shí)。統(tǒng)觀其評(píng)論文章,回溯歷史以資評(píng)價(jià)的方式俯拾皆是。他對(duì)批評(píng)對(duì)象的把握與梳理大都以動(dòng)態(tài)的眼光去權(quán)衡,對(duì)當(dāng)時(shí)文壇的新興作家作品的品評(píng)也都是站在歷史的高度點(diǎn)明利弊得失,為作家發(fā)展指明方向。這種考據(jù)方法的運(yùn)用和歷史意識(shí)的貫穿,顯然不是秉承乾嘉學(xué)派的考據(jù)傳統(tǒng),而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一個(gè)學(xué)者式批評(píng)家治學(xué)的嚴(yán)謹(jǐn)態(tài)度與良好作風(fēng),反映了一種文學(xué)漸進(jìn)的觀念。他很少將批評(píng)對(duì)象放在毫無所依的歷史背景中隨意闡釋,而是時(shí)刻不忘文學(xué)發(fā)展史這條永不停息的河流,批評(píng)文字言出有據(jù),筆無虛譽(yù)。他的批評(píng)文章中,類似“漢興以來”、“到了正始”等時(shí)間類詞俯拾皆是。比如在《詩言志辨》中,他以“詩言志”為開山綱領(lǐng),從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角度論詩。在《詩言志》篇中,朱自清考察《詩經(jīng)》及歷代詩論原著,爬梳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的“詩言志”說,對(duì)“詩”、“志”考鏡源流。考據(jù)方法的運(yùn)用也貫穿在先生的其它批評(píng)活動(dòng)。提及中國(guó)散文的發(fā)展,他開篇便說:“現(xiàn)存的中國(guó)最早的無韻文(散文),是商代的卜辭。……后來《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如此。不過經(jīng)卜官和史官按著卦爻與年月的順序編纂起來,比卦爻顯得整齊些罷了。”[2]文章從漢武帝時(shí)盛行的辭賦,到唐代韓愈的“古文運(yùn)動(dòng)”、“唐宋八大家”,到“五四”時(shí)期的“白話文”。所涉及研究對(duì)象無不在考據(jù)的基礎(chǔ)上出現(xiàn),讀后使讀者能夠?qū)χ袊?guó)歷代的問題有一個(gè)全面的把握與認(rèn)識(shí),且往往在不經(jīng)意間增強(qiáng)了批評(píng)文章的說服力。在《<老張的哲學(xué)>與<趙子曰>》中,朱自清首先通過《時(shí)事新報(bào)》上的兩則有關(guān)文本介紹的廣告指出:兩本書的特色是“諷刺的情調(diào)”和“輕松的文筆”。接下來他并沒有著手分析作品為何具有“諷刺的情調(diào)”和“輕松的文筆”,而給我們展現(xiàn)了一副諷刺小說歷史演變軌跡的畫卷。在讓讀者對(duì)諷刺小說的起源與內(nèi)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朱自清進(jìn)而提出:“這兩部書里的‘諷刺的情調(diào)’是屬于哪一種呢?[2]”可見,在朱自清這里,考據(jù)方法的運(yùn)用并不是一味地進(jìn)行源流上的探究。追溯源頭只為了引出今天的批評(píng)對(duì)象,使它不至于孤零零地站在讀者面前,而是攜帶著一股歷史的氣息,讓讀者先了解它的來由,進(jìn)而更好地把握批評(píng)對(duì)象。
熱門標(biāo)簽
文學(xué)評(píng)論 文學(xué)鑒賞 文學(xué)批評(píng) 文學(xué)性 文學(xué)賞析 文學(xué)論文 文學(xué)評(píng)論論文 文學(xué)論文論文 文學(xué)創(chuàng)作 文學(xué)賞析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