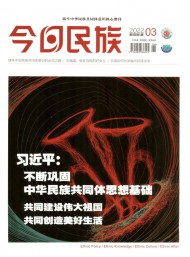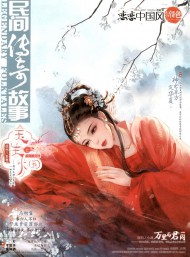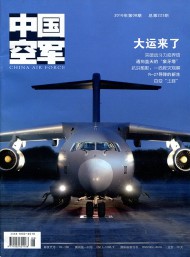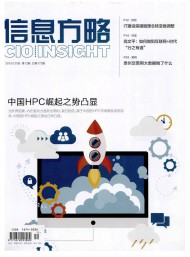英雄化范文10篇
時間:2024-04-08 11:22:33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英雄化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現代幽默喜劇英雄化研究論文
在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史上,曾經先后出現過三種主要的創作潮流,它們分別是:機智化、世態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機智化回應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在其初創期對于新型話語形式的建設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態化試圖滿足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對于豐盈肌膚、壯健骨骼的藝術成長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開始的英雄化,努力實現的則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希望更為緊密地擁抱時代與人生的現實情懷。
本文擬就中國現代幽默喜劇的英雄化問題,談幾點粗淺的認識。
一、英雄化取向的確立
大多數世態化喜劇的作者,都不缺少對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這種思考,概括地說,主要體現在人和環境的關系問題上。在分析那些世態化的中國現代幽默喜劇作品時,我們會發現它們一般都有著兩個重要的前提:一是對于人性的信賴,二是對于社會缺失的表現。為了在表現缺失的同時不傷及人性優美的根性,它們往往將人物身上的缺點或錯誤歸結為環境影響的結果,所以它們在世態展現和形象塑造的過程中,總愛描寫人物身不由己的苦衷。換句話說,它們強調的是環境對于人的支配。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這類作品表達了自身對于社會世態、風俗或傳統的批判性認識。
人的確是環境的產物,但環境——這里當然是指社會的和人文的環境——同時又必然是人的產物。人擁有在一定條件下改造和創新自身生存環境的能力與義務。
正是在如何描寫人支配環境的問題上,世態化作品表現出了某種局限。中國歷史進入抗日戰爭階段以后,這種局限與時代的精神氛圍形成了日益明顯的反差。在一個需要英雄并且已經產生出無數英雄的時代里,現代喜劇不能不對時代的需求做出積極的回應。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情勢下,中國的現代諷刺喜劇在政治化的進程中凸現出愈來愈濃重的崇高色調,而中國的現代幽默喜劇也隨之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英雄化。
幽默喜劇英雄化管理論文
在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史上,曾經先后出現過三種主要的創作潮流,它們分別是:機智化、世態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機智化回應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在其初創期對于新型話語形式的建設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態化試圖滿足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對于豐盈肌膚、壯健骨骼的藝術成長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開始的英雄化,努力實現的則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希望更為緊密地擁抱時代與人生的現實情懷。
本文擬就中國現代幽默喜劇的英雄化問題,談幾點粗淺的認識。
一、英雄化取向的確立
大多數世態化喜劇的作者,都不缺少對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這種思考,概括地說,主要體現在人和環境的關系問題上。在分析那些世態化的中國現代幽默喜劇作品時,我們會發現它們一般都有著兩個重要的前提:一是對于人性的信賴,二是對于社會缺失的表現。為了在表現缺失的同時不傷及人性優美的根性,它們往往將人物身上的缺點或錯誤歸結為環境影響的結果,所以它們在世態展現和形象塑造的過程中,總愛描寫人物身不由己的苦衷。換句話說,它們強調的是環境對于人的支配。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這類作品表達了自身對于社會世態、風俗或傳統的批判性認識。
人的確是環境的產物,但環境——這里當然是指社會的和人文的環境——同時又必然是人的產物。人擁有在一定條件下改造和創新自身生存環境的能力與義務。
正是在如何描寫人支配環境的問題上,世態化作品表現出了某種局限。中國歷史進入抗日戰爭階段以后,這種局限與時代的精神氛圍形成了日益明顯的反差。在一個需要英雄并且已經產生出無數英雄的時代里,現代喜劇不能不對時代的需求做出積極的回應。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情勢下,中國的現代諷刺喜劇在政治化的進程中凸現出愈來愈濃重的崇高色調,而中國的現代幽默喜劇也隨之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英雄化。
幽默喜劇英雄化管理論文
在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史上,曾經先后出現過三種主要的創作潮流,它們分別是:機智化、世態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機智化回應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在其初創期對于新型話語形式的建設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態化試圖滿足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對于豐盈肌膚、壯健骨骼的藝術成長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開始的英雄化,努力實現的則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希望更為緊密地擁抱時代與人生的現實情懷。
本文擬就中國現代幽默喜劇的英雄化問題,談幾點粗淺的認識。
一、英雄化取向的確立
大多數世態化喜劇的作者,都不缺少對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這種思考,概括地說,主要體現在人和環境的關系問題上。在分析那些世態化的中國現代幽默喜劇作品時,我們會發現它們一般都有著兩個重要的前提:一是對于人性的信賴,二是對于社會缺失的表現。為了在表現缺失的同時不傷及人性優美的根性,它們往往將人物身上的缺點或錯誤歸結為環境影響的結果,所以它們在世態展現和形象塑造的過程中,總愛描寫人物身不由己的苦衷。換句話說,它們強調的是環境對于人的支配。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這類作品表達了自身對于社會世態、風俗或傳統的批判性認識。
人的確是環境的產物,但環境——這里當然是指社會的和人文的環境——同時又必然是人的產物。人擁有在一定條件下改造和創新自身生存環境的能力與義務。
正是在如何描寫人支配環境的問題上,世態化作品表現出了某種局限。中國歷史進入抗日戰爭階段以后,這種局限與時代的精神氛圍形成了日益明顯的反差。在一個需要英雄并且已經產生出無數英雄的時代里,現代喜劇不能不對時代的需求做出積極的回應。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情勢下,中國的現代諷刺喜劇在政治化的進程中凸現出愈來愈濃重的崇高色調,而中國的現代幽默喜劇也隨之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英雄化。
我國現代幽默喜劇英雄化論文
在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史上,曾經先后出現過三種主要的創作潮流,它們分別是:機智化、世態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機智化回應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在其初創期對于新型話語形式的建設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態化試圖滿足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對于豐盈肌膚、壯健骨骼的藝術成長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開始的英雄化,努力實現的則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希望更為緊密地擁抱時代與人生的現實情懷。
本文擬就中國現代幽默喜劇的英雄化問題,談幾點粗淺的認識。
一、英雄化取向的確立
大多數世態化喜劇的作者,都不缺少對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這種思考,概括地說,主要體現在人和環境的關系問題上。在分析那些世態化的中國現代幽默喜劇作品時,我們會發現它們一般都有著兩個重要的前提:一是對于人性的信賴,二是對于社會缺失的表現。為了在表現缺失的同時不傷及人性優美的根性,它們往往將人物身上的缺點或錯誤歸結為環境影響的結果,所以它們在世態展現和形象塑造的過程中,總愛描寫人物身不由己的苦衷。換句話說,它們強調的是環境對于人的支配。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這類作品表達了自身對于社會世態、風俗或傳統的批判性認識。
人的確是環境的產物,但環境——這里當然是指社會的和人文的環境——同時又必然是人的產物。人擁有在一定條件下改造和創新自身生存環境的能力與義務。
正是在如何描寫人支配環境的問題上,世態化作品表現出了某種局限。中國歷史進入抗日戰爭階段以后,這種局限與時代的精神氛圍形成了日益明顯的反差。在一個需要英雄并且已經產生出無數英雄的時代里,現代喜劇不能不對時代的需求做出積極的回應。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情勢下,中國的現代諷刺喜劇在政治化的進程中凸現出愈來愈濃重的崇高色調,而中國的現代幽默喜劇也隨之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英雄化。
電影論文:論中國現代幽默喜劇的英雄化詳細內容
在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史上,曾經先后出現過三種主要的創作潮流,它們分別是:機智化、世態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機智化回應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在其初創期對于新型話語形式的建設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態化試圖滿足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對于豐盈肌膚、壯健骨骼的藝術成長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開始的英雄化,努力實現的則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希望更為緊密地擁抱時代與人生的現實情懷。
本文擬就中國現代幽默喜劇的英雄化問題,談幾點粗淺的認識。
一、英雄化取向的確立
大多數世態化喜劇的作者,都不缺少對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這種思考,概括地說,主要體現在人和環境的關系問題上。在分析那些世態化的中國現代幽默喜劇作品時,我們會發現它們一般都有著兩個重要的前提:一是對于人性的信賴,二是對于社會缺失的表現。為了在表現缺失的同時不傷及人性優美的根性,它們往往將人物身上的缺點或錯誤歸結為環境影響的結果,所以它們在世態展現和形象塑造的過程中,總愛描寫人物身不由己的苦衷。換句話說,它們強調的是環境對于人的支配。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這類作品表達了自身對于社會世態、風俗或傳統的批判性認識。
人的確是環境的產物,但環境——這里當然是指社會的和人文的環境——同時又必然是人的產物。人擁有在一定條件下改造和創新自身生存環境的能力與義務。
正是在如何描寫人支配環境的問題上,世態化作品表現出了某種局限。中國歷史進入抗日戰爭階段以后,這種局限與時代的精神氛圍形成了日益明顯的反差。在一個需要英雄并且已經產生出無數英雄的時代里,現代喜劇不能不對時代的需求做出積極的回應。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情勢下,中國的現代諷刺喜劇在政治化的進程中凸現出愈來愈濃重的崇高色調,而中國的現代幽默喜劇也隨之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英雄化。
探討影視作品中英雄形式的發展特點
【摘要】英雄歷來被我們所崇拜和敬仰,任何時代我們都離不開英雄,但是不同時代對英雄形象的要求并不一致,這一點在我們新時期的影視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早期影視劇中出現的英雄人物大都是完美無缺的“神”,后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自我意識的提高,英雄開始向人性回歸,英雄也可以有缺點,于是各個階層都出現了個性十足,血肉豐滿、為廣大觀眾所喜愛的英雄形象,同時也給我們廣大影視創作者以啟示,引導著他們沿著這一思路去創作出更多符合時代要求的英雄形象。
【關鍵詞】英雄英雄模式精神人性個性
一、英雄的內涵
我國歷史悠久,在不同時代的舞臺上生活著面目、形態各異的英雄。縱觀我國古代文學創作中,所塑造的英雄大都是“忠義”兩全,以喪失人性為代價,滿腔只有“男兒自當馬革裹尸還”的壯志,悲涼之情濫于言表。
那么,究竟何謂英雄呢?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解讀,金庸在《神雕》中說,俠之大者,為國為民,英雄就是俠之大者;古龍則說英雄并不僅是憤怒、仇恨、悲哀、恐懼、其中也包含了愛與情,慷慨與俠義、幽默與機智;何平導演帶著個人的理解在《天地英雄》中粉碎了岳飛的神話,認為真英雄是能把握自己的信念,不惜違抗皇命而不殺婦孺的人;那么我們最終該遵從的標準是什么呢?我認為,無論英雄的表現如何,在本質上他都是一個“人”,因此英雄可以是怒發沖冠與玉石俱焚的藺相如,可以是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可以是獨行萬里求得真經的玄獎法師,可以是十年心酸著紅樓的曹雪芹,更可以是笑著面對生命無常的桑蘭。所以,要想成為英雄“立人”是關鍵,而“立人”的根本內涵是:個體、自由和精神的結合。可見真正的英雄應是“自立”的,需要生命之“興”(興:肯定生命的激情和欲求,追求特定人格與價值理想)的,需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哀吟中解放出來,因此首先要成為“個體”的英雄,懷有自尊,秉持著對生命的執著和向往,然后才能成為“集體”的英雄。
二、影視作品中英雄模式的發展
幽默喜劇英雄研究論文
在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史上,曾經先后出現過三種主要的創作潮流,它們分別是:機智化、世態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機智化回應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在其初創期對于新型話語形式的建設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態化試圖滿足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對于豐盈肌膚、壯健骨骼的藝術成長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開始的英雄化,努力實現的則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希望更為緊密地擁抱時代與人生的現實情懷。
本文擬就中國現代幽默喜劇的英雄化問題,談幾點粗淺的認識。
一、英雄化取向的確立
大多數世態化喜劇的作者,都不缺少對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這種思考,概括地說,主要體現在人和環境的關系問題上。在分析那些世態化的中國現代幽默喜劇作品時,我們會發現它們一般都有著兩個重要的前提:一是對于人性的信賴,二是對于社會缺失的表現。為了在表現缺失的同時不傷及人性優美的根性,它們往往將人物身上的缺點或錯誤歸結為環境影響的結果,所以它們在世態展現和形象塑造的過程中,總愛描寫人物身不由己的苦衷。換句話說,它們強調的是環境對于人的支配。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這類作品表達了自身對于社會世態、風俗或傳統的批判性認識。
人的確是環境的產物,但環境——這里當然是指社會的和人文的環境——同時又必然是人的產物。人擁有在一定條件下改造和創新自身生存環境的能力與義務。
正是在如何描寫人支配環境的問題上,世態化作品表現出了某種局限。中國歷史進入抗日戰爭階段以后,這種局限與時代的精神氛圍形成了日益明顯的反差。在一個需要英雄并且已經產生出無數英雄的時代里,現代喜劇不能不對時代的需求做出積極的回應。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情勢下,中國的現代諷刺喜劇在政治化的進程中凸現出愈來愈濃重的崇高色調,而中國的現代幽默喜劇也隨之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英雄化。
電影藝術喜劇管理論文
在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史上,曾經先后出現過三種主要的創作潮流,它們分別是:機智化、世態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機智化回應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在其初創期對于新型話語形式的建設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態化試圖滿足的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對于豐盈肌膚、壯健骨骼的藝術成長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開始的英雄化,努力實現的則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希望更為緊密地擁抱時代與人生的現實情懷。
本文擬就中國現代幽默喜劇的英雄化問題,談幾點粗淺的認識。
一、英雄化取向的確立大多數世態化喜劇的作者,都不缺少對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這種思論文考,概括地說,主要體現在人和環境的關系問題上。在分析那些世態化的中國現代幽默喜劇作品時,我們會發現它們一般都有著兩個重要的前提:一是對于人性的信賴,二是對于社會缺失的表現。為了在表現缺失的同時不傷及人性優美的根性,它們往往將人物身上的缺點或錯誤歸結為環境影響的結果,所以它們在世態展現和形象塑造的過程中,總愛描寫人物身不由己的苦衷。換句話說,它們強調的是環境對于人的支配。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這類作品表達了自身對于社會世態、風俗或傳統的批判性認識。人的確是環境的產物,但環境——這里當然是指社會的和人文的環境——同時又必然是人的產物。人擁有在一定條件下改造和創新自身生存環境的能力與義務。正是在如何描寫人支配環境的問題上,世態化作品表現出了某種局限。中國歷史進入抗日戰爭階段以后,這種局限與時代的精神氛圍形成了日益明顯的反差。在一個需要英雄并且已經產生出無數英雄的時代里,現代喜劇不能不對時代的需求做出積極的回應。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情勢下,中國的現代諷刺喜劇在政治化的進程中凸現出愈來愈濃重的崇高色調,而中國的現代幽默喜劇也隨之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英雄化。能夠代表這一藝術趨向最早的重要作品是曹禺在1939年創作的《蛻變》(1940)。劇本以1938年末到1939年初的中國社會情況和戰爭情勢為背景,通過一所傷兵醫院的前后變化,表現出中華民族應該在戰爭中蛻舊變新的主題。其中的第一幕對于這所醫院腐敗現象的揭露,固然可以使人聯想到《欽差大臣》對于俄羅斯舊官吏的諷刺,但它只是全劇構成的第一步,旨在說明蛻舊變新的必要性以及蛻變的現實起點。正如曹禺所說:在抗戰的大變動中,我們眼見多少動搖分子,腐朽人物,日漸走向沒落的階段。我們更喜歡地望出新生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艱苦的斗爭里醞釀著,育化著,欣欣然地發出來美麗的嫩芽。(注:曹禺:《關于“蛻變”二字》,《曹禺全集》第2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57頁。)這里的后一點才是決定劇本基本性質的所在。《蛻變》是一部以歌頌為主的喜劇作品,劇中的兩位主要人物——梁專員和丁大夫——是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創作中最早出現的英雄角色。正直無私、恪盡職守的專員梁公仰,在烏煙瘴氣、腐化茍且、悲觀消極的惡劣環境里,大刀闊斧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受到醫院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和擁戴。這一形象在中國現代幽默喜劇英雄化的過程中,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他證明了:人是完全可以改造環境、征服環境的,只要有理想、敢犧牲、肯努力、嫉惡如仇、團結同志并且持之以恒。丁大夫既是一位名醫又是一位母親。作品讓慈母和良醫兩種角色在她身上構成內在的沖突,通過這位剛強女性自覺將國家和民族利益置于母子私情之上的行為,使其個人的品德超越了一般醫德的范圍。這種超常性則構成了這一形象英雄性的基礎。梁專員的形象主要代表著英雄的人可以主宰環境的一面,丁大夫的形象主要代表著英雄的人必然具備超乎常情的崇高品德的一面,從而構成英雄化取向的兩個基點。在《蛻變》以后的英雄化走向當中,多數作品正是圍繞著上述兩點展開的。這也就是我們為什么把《蛻變》看作英雄化喜劇開山之作的主要原因。就戰勝環境而言,在《蛻變》以后的英雄化喜劇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徐昌霖的《密支那風云》(1945)、成蔭的《打得好》(1944)、洛丁等人的《糧食》(1946)、張駿祥的《邊城故事》(1941)、吳鐵翼的《河山春曉》(1944)、王銳的《健飛的求婚》(1948)等。前三篇作品直接表現抗日斗爭,后三篇主要描寫后方建設,兩者合起來形成了“抗戰建國”的共同主題。在上述作品中,作家們雖然也曾描寫了主人公們的種種美德,但藝術表現的重心卻始終放在人物的行為上。至于美德,只是人物在行動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品格。在人物的行為描寫中,作品突出的是這些行為同歷史的進步事業與民族的正義使命之間的緊密聯系,而后者的偉大與崇高才是人物行為英雄性質的主要源泉。正因如此,除《打得好》和《糧食》以外,其他作品固然存在著純粹個人性質的情感糾葛,但作家的主要筆力仍在人物的公民生活方面。他們著意反映的是人物在投身偉大而正義事業的過程中,為了戰勝各種艱難險阻所體現出來的勇敢精神和創造精神。這無疑為英雄化取向的多數作品增添了一種十分明顯的社會實踐品格。在機智化和世態化取向中,中國現代幽默喜劇主要描寫的是人物的日常生活,而現在它育化的卻是對于人物公民生活的表現力,從而進一步開拓了現代幽默喜劇反映生活的攝取視野。這不能不說是英雄化對于現代幽默喜劇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在藝術表達上,這種內在的社會實踐品格為英雄化喜劇帶來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對故事和情節因素的重視。這或許就是張駿祥將他的《邊城故事》說成是“一個五幕的Melodrama”(注:Melodrama,在現代時期可譯為“鬧劇”或“情節劇”,現一般譯為后者。)的原因。在這部大型喜劇作品中,作家正是在一種險象環生的情節進展中,為我們刻畫出主人公楊誠專員對于祖國的忠誠、對群眾的信任和勇于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英雄精神。一般來說,在這類英雄化的喜劇作品中,為了滿足表現人物英雄行為的基本要求,作家往往要創造出一種極端化的情節。在這種非比尋常的情節中,英雄主人公將會遇到難以想象的挑戰和考驗。這種藝術處理方式不僅可以體現出人物卓越的品格,而且可以有效地引發觀眾緊張的期待,進而構成喜劇審美心理“緊張——松弛”模式的前半部分。極端化的情節必然要求極端化的結局,要么是大獲全勝,要么是滿盤皆輸。我們談論的既然是喜劇,那么,英雄化要求的自然是前者。由于最終的成功和勝利,“緊張——松弛”模式的后半部分得以實現。這種爭取成功和勝利的情節模式,加上主人公或詼諧或樂觀的可愛性格以及某些喜劇性的穿插成分,則構成了英雄喜劇幽默性的主要內容。
二、走向英雄就嚴格意義而言,“英雄化的喜劇”并不等同于“英雄喜劇”。前者固然以后者為核心,但在其所涵蓋的內容上又絕不僅限于此。正如宋之的在1939年所說:我們現在尤其需要喜劇型的英雄,在各戰場上,有著不少的英雄在戰斗著,他們的影響,強化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力量,這類英雄在喜劇里將是一把火,燃燒起民眾們熱烈的抗敵情緒,鑄就了鐵一般的民族再生力量。(注:《宋之的研究資料》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頁。173頁。172頁。172頁。)在一大批英雄化的幽默喜劇中,作家更樂于表現的是那些作為人類鹽中之鹽的英雄們對于普通人的影響,他們試圖表現的是更多的人走向英雄的過程和可能性。《等太太回來的時候》(1941)是丁西林唯一一部緊密配合政治現實問題的作品。劇中正直愛國的兒子剛從國外回到“孤島”家里沒幾天,就毅然決定離開已經成為漢奸的父親。他愛母親,他唯一擔心的是自己的出走對于多病的母親心理上可能帶來的打擊。為了抗日事業,兒子最后決定將母子間的私情置諸一邊。但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愛國行動得到了母親的充分理解。劇尾,深明大義的母親帶著兒子和小女兒一同離開了上海,準備投身于大后方抗日救國的行列。吳祖光的《少年游》(1944)是表現這方面內容最為典型的作品,同時也是英雄化喜劇當中的優秀之作。劇本主要表現四位女大學畢業生及其男友在北平淪陷時期的人生選擇。姚舜英和周栩是全劇中帶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在兇險的環境中從事著秘密工作。在他們的影響下,洪薔開始反省自己過去那種任性好玩的生活。她在周栩和洋場闊少之間的選擇早已越出了戀愛的范圍,體現的是一種人生價值的重估和對于有意義人生的追求。為肺病所苦的董若儀,在現實的教育下,改變了悲觀消極的生活態度。為了獲取積極的人生,她寧愿死在尋找新生活的路上,而不愿茍活在北平的鬼蜮世界里。劇本最后,勝利完成了刺殺日酋任務的周栩帶領劇中的革命者和進步分子離開北平,奔向了延安。無論《等太太回來的時候》中的兒子和母親,還是《少年游》里的洪薔和董若儀,他們在未來的生活和斗爭中未必一定就能成為英雄,但至少可以肯定:只要他們能夠始終同偉大的事業聯系在一起,必將會縮短自己同英雄之間的距離,或者換句話說,事業的偉大將會使他們具備某些英雄主義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英雄化的喜劇在抒寫英雄們對于多數人影響的過程中,對道德升華問題給予了相當的關注。英雄性不僅可以視為一種審美基本概念的變體,而且始終是一個道德概念。黑格爾在分析古希臘時代英雄性的時候,曾經指出在當時英雄形象中所包含著的某些非道德的因素:海格立斯曾在一夜強奸了第斯庇烏斯的50個女兒;他在清洗過奧吉亞斯牛欄之后,僅僅為了主人的違約就殺死了后者。黑格爾由此證明當時的英雄未必一定是那種“道德上的英雄”。(注:參見《朱光潛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228頁。海格立斯(Herkules)是希臘神話中的大力士。)但上述情況或許只是古代人野性崇拜的遺存,充其量能夠說明的不過是古代的道德不同于今天的道德。不管怎么說,在現代中國意義上的英雄性和道德性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天然的聯系。一個人之所以成為英雄,可能主要并不是因為他的德行,但是英雄在道德上或道德的某些方面必然具備著崇高的因素。這樣,英雄化喜劇通過英雄主義精神的發散,不僅寫出了進步的社會實踐力量的不斷壯大,而且也表現出了一場偉大戰爭中的民眾普遍道德的遷善與升華。陳白塵的《秋收》(1941)、洪深的《包得行》(1939)和胡可的《喜相逢》(1949)等喜劇正是這樣的作品。根據艾蕪同名小說改編的《秋收》,敘述了三個國民黨傷兵幫助當地抗屬姜老太婆一家搶收稻子的故事,意在表現全民抗戰新形勢在一些抗日士兵當中所引發的新變化。《包得行》中的包占云是四川某地年輕的無業游民,由于看不慣內地的腐敗而變得玩世不恭,但戰爭教育了他,最后使之踏上了保家衛國的征程。《喜相逢》中的解放軍戰士劉喜,拿走了俘虜的五萬元法幣,后來向班長坦白了錯誤,卸下了思想包袱,保證了道德上的完美。戰爭與道德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方面,戰爭造成了人性的退化和獸性的泛濫,給人間帶來了難以計數的慘劇和罪行;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以強有力的方式促成了人類對于自身的道德反省。尤其是在正義的戰爭中,志士仁人們的舍身取義、慷慨赴難的崇高精神必定會使愈來愈多的人跳出小我平庸的拘囿,完成道德上的凈化和升華。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就是這樣的戰爭。一方面是空前的破壞和災難,一方面又是前所未有的進步和建樹。億萬人民在創造英雄業績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改造著自身,其中當然也包括著革命和進步民眾的道德狀況。這種道德的提高也正是宋之的所說的“民族再生力量”的一部分。英雄化喜劇對于這一方面的關注和藝術表現顯然具有重要的意義。這種關于道德遷善的描寫同時也給英雄化喜劇人物塑造方面帶來了明顯的影響。以夸張的方式去凸現人物的丑惡,并在這一藝術表現過程中不斷對丑惡施以辛辣的針砭,是諷刺喜劇的基本手段。在機智化的幽默喜劇中,作家對人物往往持贊賞的態度,但他們贊賞的主要是人物機智可愛的方面。喜劇的人物塑造在世態化的幽默喜劇中達到了相當的深度。然而這種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環境對于人物的影響實現的,而環境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對穩定的一面。可見在上述類型的喜劇中,人物的性格大體處于靜止的狀態,即便是在一些優秀的作品中,作家所做的也只是對于給定性格多方面的揭示或展示,性格本身仍是一種常數。而在我們提到的這類英雄化作品中,情況發生了變化。道德的遷善必然導致性格的發展,包占云從最初的玩世不恭到后來肩負起自己對國家和親人的責任正是對此很好的說明。應當承認,英雄化喜劇在塑造性格變化方面所取得的總體成就是值得懷疑的,但盡管如此,其有關這一方面的描寫,即便算不上是對中國現代喜劇的重大貢獻,也完全算得上是對中國現代喜劇的重要啟示。在英雄化喜劇里,還有一類作品,它們直接表現的雖然并不是社會的公民生活,但即便是在日常生活領域的藝術表現中,人們仍然能夠發現那種英雄化的內在特征。這類喜劇里較為成功因而也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石華父的《職業婦女》(1941)、李健吾的《青春》(1948)、魯思的《十字街頭》(1944)等。相對于英雄化取向的軸心部分而言,這些喜劇其實是一種帶有邊緣性質的作品,它們一般帶有由世態化向英雄化過渡的痕跡。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英雄化取向在這種邊緣領域卻取得了更為顯著的藝術成就。《職業婦女》中,女主人公張鳳來為了實踐自己的女權主張,不僅在機關里隱瞞了自己已經結婚的事實,而且巧妙而機智地捉弄了上司——作為男性和權力象征的方維德局長。表現中國都市婦女的生活狀況,是楊絳喜劇的重要內容。我們不妨將《職業婦女》與之作一番對比。在最終意義上,楊絳喜劇中所有的女性都是被動的。周老太如此,李君玉如此,受過“五四”新思潮影響的張太太亦如此。趙祖蔭夫人和趙祖懋夫人的爭寵與固寵,說穿了,無非是男性中心社會傳統的折光。即便是個性很強的張燕華也難以離開男性而獨立,正因為她社會地位的改變要通過對于男性的選擇來實現,所以她最后的“征服命運”也只能從“督促”丈夫的“改造”開始。可見在這些形象中,女人始終是不能單獨面對世界的。然而在這一點上,張鳳來是不同的。隱瞞結婚已經兩個月的事實,固然是為了對付方局長的性別歧視,但對張鳳來似乎還有別的含意。“張小姐”和“王太太”并非僅僅是稱謂的不同,前者抹殺掉的是王道本作為丈夫的存在。王道本抱怨說:“你看我們兩個誰是勝利者,誰是被壓迫的,自從結了婚,我一直沒有出頭過”。張鳳來對此的回答是:“這你不能怪我,只能怪我們的局長,他逼得我把你藏起來的。”其中“我把你”三個字明顯地點染出說話人作為女性的自得,因為她不僅是獨立的,而且是主動的。更可貴的是,張鳳來對于女性力量的認識是同其理性的自覺相聯系的。她說:國家愈是多難的時候,愈是我們婦女翻身的好機會,因為表現我們事業的機會也多了。這樣男女斗爭著,搶著事業做,不但我們自身的地位提高了,連社會也可以不斷地進步著。如此的覺悟以及在這種覺悟基礎上形成的力量顯示和主動精神,在世態化喜劇中是極為罕見的。我把它看作是英雄化潮流給現代幽默喜劇帶來的一種新因素。張鳳來是幸運的。或許是因為對手的愚蠢,她從一開始就在較量中掌握了主動權。但是事情不會總是如此,特別是當主人公需要對抗的不僅僅是個別人,而是他們背后的某種傳統或是整個社會體制的時候。在那種對手不僅表現出愚蠢而且也顯示出其暫時的強大的情況下,正面的喜劇主人公往往還需要具有一種樂觀主義的精神品格。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夠在困苦中堅持,在斗爭中等待。李健吾《青春》中的田喜兒,在和香草的愛情上屢受挫折,這一度曾使他痛不欲生。但對于“趕明兒”的信仰幫助了他,“活著總有出頭的一天”,這一希望給了他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和香草最終可能出現的結合顯然同這種樂觀主義精神密不可分。魯思的《十字街頭》(注:該劇系根據沈西苓的同名電影劇本改編。)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對知識青年。社會的和經濟的壓迫直到最后也不能讓他們氣餒。當失業的打擊再次襲來的時候,一種“向上的理想”支持了他們,“只要我們有勇氣,總可以活下去”的人生格言使他們滿懷希望地肩并肩走向了十字街頭。應當指出,樂觀主義是整個中國現代幽默喜劇的一種總體的基調,但是,其內部不同類型作品在樂觀主義藝術表達的方式和深度上卻又有所區別。一般來說,機智化取向中缺少嚴重的沖突,因此,它所表達的與其說是樂觀不如說是輕松。世態化作品由于逐漸接近客觀化的描寫原則,所以樂觀的人生態度主要是通過創作主體對于生活的總體把握來實現的。至于喜劇人物本身,除少數例外,并未明顯直接地體現出樂觀主義的情緒。我們在王太太、汪夢龍、徐守清、康如水、周大璋、馬翠芬這類人物的身上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的。(注:他們分別為《委曲求全》、《五里霧中》、《以身作則》、《新學究》、《弄真成假》、《郎財女貌》中的主要人物。)而到了英雄化取向中,主人公形象本身就已經成為了樂觀主義的載體。在《十字街頭》的失業四學士當中,趙柯干和劉大哥代表著積極向上的樂觀主義精神,唐祿天代表著玩世的“樂天主義”,而害著初期肺病的徐瀟杰則代表著悲觀主義。作品通過小徐最后的跳海自殺,小唐的認識轉變,肯定了以趙、劉為代表的健康向上的樂觀主義人生態度。英雄化喜劇的樂觀主義固然是理想主義的表現,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種純浪漫的東西,因為它同時也有著現實的根基。既然中華民族已經經受住了一場空前慘烈悲壯的戰爭考驗,那么其它的一切在這個民族的眼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三、浪漫的寫實在談到自己早期喜劇的時候,丁西林曾認為,它們大都近乎改譯之作,這當然是謙辭。但其中畢竟反映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中國現代幽默喜劇在機智化階段確實保留了某些外國影響的明顯的胎記。那些世態化作品為了使新的喜劇形式同中國人日常生活、風俗與傳統的結合做出了可貴的努力。李健吾對于中國特色或地方色彩的神往正是對于這種可貴努力的最好說明。楊絳的《弄真成假》被認為充盈著一種“中國氣派的機智和幽默”,可以讓人從中體味到“中國民族靈魂的博大和幽深”,(注:孟度:《關于楊絳的話》,《雜志》第15卷第2期,1945年5月。)則是對于上述努力的高度評價。英雄化喜劇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更廣泛地表現出中華民族對于幽默喜劇的審美需求。在這類作品中,處于特殊歷史情勢下的中國民眾包括公民生活在內的多種生活圖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現。尤其重要的是,它們深刻體現出了中國現代歷史最后十年里整個中華民族精神風貌所發生的巨大變遷,并且從一個側面顯示了古老的中國將要以新的姿態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明前景。就此而言,英雄化作品在中國現代幽默喜劇民族化進程中的實際地位和影響,是其他類型所難以比擬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則是這一民族化進程的重要成果。機智化的作品多為浪漫情懷的產物,對此我們似乎無須質疑。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這一點,它們的作者至少在當時是不以為恥而以為榮的。在30年代大部分的時間里,浪漫主義命運多艱,背負惡名。
從入世英雄到隱世智者──黑澤民電影中的「完人」主題
每個藝術家這一生,都會透過他最擅長的藝術形式,環繞幾個對他而言是再重要不過的主題。這些主題,多半都是藝術家最關切的、最想告知世人的、或是藝術家自己最想解開的謎題。
剛過世的世界級大導演黑澤明,一樣透過電影的藝術形式,環繞著他最在乎的幾個議題。最初的議題是「被西方文化沖擊后的日本,英雄形象到底是什么?」個人決斷下的人道主義對日本而言,武士道結合禪道下的英雄形象,已是日本文化中不可分割、且引以為傲的文化象徵。這恰像「儒士」在華人文化下的精神象徵一樣。華人文化中的儒,的確在西方文化沖擊下,漸漸失去其定位,這文化沖擊使儒在這一世紀,經過不知多少的旁徨與陣痛,最終還是免不了淡去其色彩。日本文化中的武士精神,一樣經歷了類似的歷程。旁徨陣痛的這一世紀,恰好與黑澤民導演生涯期間相遇,因此「何為英雄?」與「英雄的出路」,就成為黑澤民電影回繞的基調。這基調,黑澤民同時用現代劇與歷史劇來對應探討。
從1943年黑澤民拍出第一部重要電影「姿三四郎」,到1965年拍出「紅胡子」,這二十年間,黑澤民都將英雄定義集中于「個人決斷下的人道主義」。這種個人決斷,又以在亂世中的決斷最是艱難。因此,黑澤民愛將劇情背景置于亂世景觀之中,來凸顯其英雄的決斷能力。
這種亂世中的人道主義,是一種屬于個人性而非群體性的意志,是一種近似貴族化的、是少數人(一如武士精神是少數人才擁有的能力)才能做出的決斷,也因此,黑澤民電影中的英雄,就注定要承受孤獨。
亂世下的個人決斷黑澤明是要讓『羅生門』中竹藪這個意象,象徵『人心』這個黑暗迷宮。『生之欲』中,堪治(志村喬)堅持要單獨面對死亡,因此而與身邊的人產生疏離,并與社會秩序構成挑戰。
我們來看看黑澤民第一部轟動國際影壇的電影「羅生門」。
電影完人主題管理論文
每個藝術家這一生,都會透過他最擅長的藝術形式,環繞幾個對他而言是再重要不過的主題。這些主題,多半都是藝術家最關切的、最想告知世人的、或是藝術家自己最想解開的謎題。
剛過世的世界級大導演黑澤明,一樣透過電影的藝術形式,環繞著他最在乎的幾個議題。最初的議題是「被西方文化沖擊后的日本,英雄形象到底是什么?」個人決斷下的人道主義對日本而言,武士道結合禪道下的英雄形象,已是日本文化中不可分割、且引以為傲的文化象徵。這恰像「儒士」在華人文化下的精神象徵一樣。華人文化中的儒,的確在西方文化沖擊下,漸漸失去其定位,這文化沖擊使儒在這一世紀,經過不知多少的旁徨與陣痛,最終還是免不了淡去其色彩。日本文化中的武士精神,一樣經歷了類似的歷程。旁徨陣痛的這一世紀,恰好與黑澤民導演生涯期間相遇,因此「何為英雄?」與「英雄的出路」,就成為黑澤民電影回繞的基調。這基調,黑澤民同時用現代劇與歷史劇來對應探討。
從1943年黑澤民拍出第一部重要電影「姿三四郎」,到1965年拍出「紅胡子」,這二十年間,黑澤民都將英雄定義集中于「個人決斷下的人道主義」。這種個人決斷,又以在亂世中的決斷最是艱難。因此,黑澤民愛將劇情背景置于亂世景觀之中,來凸顯其英雄的決斷能力。
這種亂世中的人道主義,是一種屬于個人性而非群體性的意志,是一種近似貴族化的、是少數人(一如武士精神是少數人才擁有的能力)才能做出的決斷,也因此,黑澤民電影中的英雄,就注定要承受孤獨。
亂世下的個人決斷黑澤明是要讓『羅生門』中竹藪這個意象,象徵『人心』這個黑暗迷宮。『生之欲』中,堪治(志村喬)堅持要單獨面對死亡,因此而與身邊的人產生疏離,并與社會秩序構成挑戰。
我們來看看黑澤民第一部轟動國際影壇的電影「羅生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