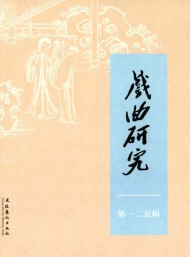袁世凱范文10篇
時間:2024-04-11 17:04:08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袁世凱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詮釋袁世凱與清末軍事改革
十九世紀中后期,隨著西方殖民者的侵入,清王朝軍隊節節失利,使之喪失了許多國家利益。“庚子之變”以后,民族危機和晚清政府的統治危機日趨嚴重。為適應日益高漲的軍事、政治斗爭的需要,清王朝軍隊開始了強弱興替的演化過程,其軍制變化呈現出由封建化逐漸向近代化演變的趨勢。而在這場變革中,獲益最大且有成效的當屬北洋軍閥的頭目——袁世凱。他一手編練創建的北洋新軍是中國第一支近代化軍隊,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軍閥武裝,在歷史上起著反動作用,但是,這并不能否認袁世凱軍事改革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應有的地位。
袁世凱認為,清王朝原有軍隊腐化,不具備國家機器的職能。他說:中國軍政廢弛,匪伊朝夕,其弊端之尤著者,在于營制不一、操法不齊、器械參差、號令歧異。為將者不習謀略,為兵者半屬惰游,平時而心志不相孚,臨陣而臂指不相使。聚同烏合,散同瓦解。而當時清軍的狀況是:
一、原有軍隊腐化,形同虛設
八旗是清入關前原有的軍隊,始建于滿洲戶口編制上,是兵民合一的軍事組織,但是入關后迅速腐敗,1673年三藩事件發生時,八旗幾乎不能打仗。清軍入關后,新招募的漢人軍隊——綠營在平三藩的過程中取代了八旗,處于沖鋒陷陣的地位,但不久也沒落了。
雍正八年以后,開始招募鄉軍和防軍,綠營形同虛設,到鴉片戰爭時,已經“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滋事,全無紀律。八旗、綠營的蛻化,是封建地主階級政權的武裝力量在當權后的優越條件下必然走向衰落的一種現象,他們既不能對外御辱,也無力鎮壓國內人民的反抗,于是清政府不得不依賴漢族地主武裝——湘軍、淮軍。
雖然湘軍、淮軍在鎮壓太平天國、捻軍以及維護清廷統治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本身的缺點卻給了他們致命的打擊。《光緒政要》中關于清朝的軍事作如下描述:“軍需如故;勇額日缺,上浮開,下折扣,百弊叢生”,“各營員皆以鉆謀為能事,不以韜矜為實政,是兵官先不知戰,安望教民以戰”,“同屬一軍,而此營與彼營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備數,德制奧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舊習,湘楚各軍,尚有以大旗刀矛為戰具者”。這是清軍的如實寫照。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清軍既不能御辱于外,鞏固清王朝的統治,更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改革勢在必行。
袁世凱出任民國臨時總統分析論文
首先,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來自現代生產關系,現代生產關系沒有確立,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不可能鞏固地存在下去,馬克思認為“如果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經濟條件沒有充分成熟,君主專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暫時的。”[2]辛亥革命推翻清統治,建立了共和國,但資產階級遠沒有成熟到足以獨立締造共和制度并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里。據統計,截至1911年,中國還只有近代廠礦企業562家,資本1.32億元,其中商辦企業只有469家,資本8700余萬元。[3]可見,資產階級經濟力量十分微弱。另從資產階級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繳納主要貢賦厘金看,1910年清政府所作的1911年全國財政預算,總收入為2.96億兩,厘金收入僅為4300萬兩,故在該年財政預算中,其所占份額僅為9.43%。[4]上述事實表明,資產階級弱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微弱,不能為辛亥革命提供一個有力的經濟基礎。辛亥革命可以猝然成功,但無堅實的經濟基礎,勢必會影響革命政權的鞏固。
此前革命黨人發動的起義屢戰屢敗,武昌起義猝然發動,猝然成功,革命形勢蓬勃發展。但蓬勃之下掩蓋著混亂。擺在國人面前的景象是:“盜賊縱橫,土匪充斥,失業之民,全國皆是,焚燒劫掠,盜竊淫戮,商民之家被害者日必數起。”[5],“言外患則日逼南滿,俄涎蒙古也,言內憂則會黨充塞,匪盜如毛也,再觀內部意見叢生,內訌可懼。四崩五裂,論之堪憂,嗚呼!天禍吾國乎?”[6]社會動蕩,列強環伺,革命尚末成功,清軍尚在眼前。面對此景,軟弱的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個鐵腕人物來完成革命的任務——推翻滿清,同時又要這個鐵腕人物來幫助他們穩定秩序,迅速統一內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誰能夠擔當這樣的重任呢?環顧四海,人們覺得袁世凱是最合適的人選。首先立憲派看好袁世凱。在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半年,上海、廣東、漢口、天津四商會推張謇晉京,洽談組織赴美游歷報聘團事,同時向清廷進“最后忠告”。張謇繞道彰德拜訪袁世凱,一夕深談,達成默契。張對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資產階級立憲派對袁深篤的政治感情和隱約的期待。武昌起義后四天,以立憲派為主體的江浙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就開始制定擁護袁世凱以及收拾大局的計劃,即有名的“惜陰堂計劃”。他們一方面讓擁有實力的袁迫使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則壓迫革命黨人交出政治權力,由袁任共和政府的總統。在他們的活動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會作出決議:若袁君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張謇電告袁: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
不僅立憲派看好袁,就是革命黨人也看好袁。在袁的幫助下出獄后,極力鼓吹袁餓反正的論調。他還以“民黨代表”的名義,向袁表示:“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不可(總統)不可。”[7]黃興雖然對袁心存警惕,但就在同一天,他又寫信給袁,稱“明公之才,高出興等”,呼懇他“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宋教仁也一再表示擁護袁做總統,并曾對人說:“現在非新舊勢力合糅不可,正式大總統非袁公不克當此選。”[8]孫中山在擔任臨時大總統后,面對動蕩不安的局勢,窮于應付,頗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認為,清帝退位,民國統一,彼此建設之事,自應讓熟有政治經驗之人。孫中山在執行各省代表會議時應允:如果袁君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
為什么大家都看好袁世凱?這是因為當時滿漢矛盾十分尖銳。滿漢矛盾由來已久,反滿思想在清朝入關后,便深深地植根于漢民族的思想意識之中。同時它既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投入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礎,又是他們用來動員群眾的重要思想。早先孫中山的排滿思想不免有些偏狹之見,但同盟會成立后,逐浙將排滿與救亡圖存,將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結合起來,而大部分領導人和人民群眾并末達到孫中山這樣的思想境界,在他們民族意識之中仍摻雜著偏狹的種族主義色彩。毫無疑問,宣傳革命排滿,使辛亥革命帶有一定的種族主義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辛亥革命的進程和結局,為袁提供了可乘之機。
由于辛亥革命的“反滿”色彩,袁世凱很便成了各派政治勢力競相爭取的對象和穩定政局的強有力的人選。就革命派而言,由于袁的漢人身份及他同滿人的某些矛盾,使他們從一開始就希望袁能以“民族大義”為重,支持革命事業,至于袁本人,則充分利用革命黨人的排滿心理,以調和者自居,誘使革命黨人和平了結。1909年袁開缺回籍之后,遠離政治斗爭的漩渦,受到清廷猜疑,而這卻使得資產階級產生袁是清廷對立面的錯覺,更有一部分革命黨人在狹隘排滿的大漢族主義支配下,把袁視為“同種”,并把他與“異族”的清王朝相區別,對其寄予厚望。
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時的歷史背景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袁世凱;臨時總統;國內背景
[論文摘要]:對于袁世凱出任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原因,學界眾說紛紜,文章中作者試從當時國內背景分析袁世凱出任民國臨時總統的歷史原因。
武昌起義猝然成功和各省相繼獨立,共和革命成為中國政壇的主流。然而辛亥革命卻以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總統而收場。對于袁世凱何以能夠當選為民國臨時總統這一問題,學界眾說紛紜,以往有學者對袁世凱出任民國總統的國際背景進行了探討[1],認為,列強在中國需要的間接統治工具,必然是既衰弱得足以俯首聽命,又強得足以鎮壓人民,而在革命中一觸即潰的清廷,已不能充當這樣的工具。列強看來,最適合的人選莫過于袁世凱。由此列強支持袁世凱取代孫中山出任民國總統。文章則試從當時的國內背景來闡釋袁世凱出任民國臨時總統的原因,希讀者批評指正。
首先,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來自現代生產關系,現代生產關系沒有確立,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不可能鞏固地存在下去,馬克思認為“如果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經濟條件沒有充分成熟,君主專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暫時的。”[2]辛亥革命推翻清統治,建立了共和國,但資產階級遠沒有成熟到足以獨立締造共和制度并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里。據統計,截至1911年,中國還只有近代廠礦企業562家,資本1.32億元,其中商辦企業只有469家,資本8700余萬元。[3]可見,資產階級經濟力量十分微弱。另從資產階級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繳納主要貢賦厘金看,1910年清政府所作的1911年全國財政預算,總收入為2.96億兩,厘金收入僅為4300萬兩,故在該年財政預算中,其所占份額僅為9.43%。[4]上述事實表明,資產階級弱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微弱,不能為辛亥革命提供一個有力的經濟基礎。辛亥革命可以猝然成功,但無堅實的經濟基礎,勢必會影響革命政權的鞏固。
此前革命黨人發動的起義屢戰屢敗,武昌起義猝然發動,猝然成功,革命形勢蓬勃發展。但蓬勃之下掩蓋著混亂。擺在國人面前的景象是:“盜賊縱橫,土匪充斥,失業之民,全國皆是,焚燒劫掠,盜竊淫戮,商民之家被害者日必數起。”[5],“言外患則日逼南滿,俄涎蒙古也,言內憂則會黨充塞,匪盜如毛也,再觀內部意見叢生,內訌可懼。四崩五裂,論之堪憂,嗚呼!天禍吾國乎?”[6]社會動蕩,列強環伺,革命尚末成功,清軍尚在眼前。面對此景,軟弱的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個鐵腕人物來完成革命的任務——推翻滿清,同時又要這個鐵腕人物來幫助他們穩定秩序,迅速統一內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誰能夠擔當這樣的重任呢?環顧四海,人們覺得袁世凱是最合適的人選。首先立憲派看好袁世凱。在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半年,上海、廣東、漢口、天津四商會推張謇晉京,洽談組織赴美游歷報聘團事,同時向清廷進“最后忠告”。張謇繞道彰德拜訪袁世凱,一夕深談,達成默契。張對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資產階級立憲派對袁深篤的政治感情和隱約的期待。武昌起義后四天,以立憲派為主體的江浙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就開始制定擁護袁世凱以及收拾大局的計劃,即有名的“惜陰堂計劃”。他們一方面讓擁有實力的袁迫使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則壓迫革命黨人交出政治權力,由袁任共和政府的總統。在他們的活動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會作出決議:若袁君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張謇電告袁: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
袁氏當國讀后感
唐老有許多代表作:《晚清七十年》、《李宗仁回憶錄》、《美國民權運動》等,當然《袁氏當國》也在其中。捧讀完這部史學傳記,最深的印象莫過于他文白相雜,書口并用的寫作風格。以袁世凱為主線的民國史在他筆下娓娓道來,絕無戲說成分卻有引人入勝,史家講故事的能力可見一斑。白壽彝大師曾言:“歷史不能干巴巴,要讓人愛看”,《袁氏當國》大抵符合這條要求。為了更好的體會唐老的寫作風格,又去找了遠流版本,果然收獲頗豐,例如孫中山想聯日倒袁就被唐老唾棄為“更是屎棋”,怒其不爭的韻味十足,讀來讓人不禁莞爾。
接下來該說說本書男主角,他出使朝鮮,小站練兵,廢除科舉,可恰恰是他,或許就因他的出賣而失敗,不僅如此,刺殺宋教仁,做起來絲毫不手軟。唐德剛評價他為“畢竟是近代中國數一數二的治世能臣”,在余看來,他就是一個深諳民意的重要性卻摸不透民意的政治老手,成也民意,敗也民意。
之所以說他深諳民意的重要性,是因為他懂得為自己造勢,利用民意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孫中山暫代臨時大總統后隨即電袁表示虛位以待,無非迫于“非袁不可”的局勢,不然也不會千方百計制定法律來約束“猛虎”了。國民黨成立之際,袁為造出與國民黨交好的假象,與孫公晤面達13次之多。蜜月期中的孫公還沉浸在三民主義已成二者,自己只要再修多20萬里鐵路就大功告成的美夢里,何曾想到自己只是袁世凱造勢,拉攏民意的一著棋子呢?后來袁更把國民黨掃地出門,自己當上終身大總統,可謂飛龍在天了,只是左右逢源,春風得意之時卻忘了亢龍有悔,盛極而衰的道理,臨了還要像汪曾祺、那樣晚節不保,不可悲乎?可他遠沒有那樣幸運,歷史對他太苛刻,以至于竊國賊的罵名蓋過他先前所有功績。眾人知道他野心勃勃要倒行逆施,卻少有人為他辯解,他的洪憲年號實為弘揚憲法之意,只是此中有幾分真情幾分假意就沒人在意了。
追根溯源,袁世凱稱帝固有被袁克定坑了的緣故,但當時的政局也起了催化作用。共和這個美國模式原本是被新派人士視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萬靈法寶,事實卻是,民國成立后,連袁總統也失掉信心了。留學回來對共和制有親身體會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唐老更是斷言“袁世凱對現代政治思想是一無所知”,當時的國民只覺得皇帝換了姓而已,民主?選舉?啥玩意兒,能吃嗎?再加上總統、內閣分權不清分權制衡這種舶來品來到中國就走樣變型,袁有他的智囊團,宋教仁就搞他的政黨內閣,雙方都在掰手腕,能不亂嗎?結果就是內閣還沒斷奶就夭折,議會那“八百羅漢”把民國攪得天翻地覆。其實早在1908年美國記者托馬斯•F•來拉德造訪袁世凱就有過報道”雖然袁世凱主張他的國家能真正適應西方的觀念和方法,即是大清國也許還未做好充分的準備去接納他們”,只是袁不撞南墻不回頭而已。
等撞到頭破血流了就想起昨日種種,這時候民意又粉墨登場了,君不見民怨民憤多強烈嗎?民國不如大清!看重民意的袁大概覺得開倒車也比翻車強一百倍吧?這雖有為他開脫之嫌,但也算是實話。壞就壞在這次袁世凱摸不準民意了。大清比民國好和民國不如大清兩種說法,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前者恰是他以為的民意,卻不料共和政體之于民眾就如月信之于女人,女人每月那幾天總會咒罵大姨媽,恨不得“她”快走,可等到親戚不來了,又火燒眉毛似的求醫問藥。共和政體再不濟,也算是跨出了第一步,緩慢前行著的列車斷沒有回頭之理,袁世凱硬要回頭,焉有不車毀人亡的結局呢?在他彌留之際,民意又有了新風向,從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不知病榻上的袁世凱作何感想?想必是百感交集,五味雜陳。
其二公子諷父詩曰“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唐老覺得如果袁世凱守著本分,一輩子也就過去了,但他如背叛民國,必然是不得善終。如果袁沒有倒行逆施,歷史對他的評價又會如何?中華民國走向又會是怎樣一番景象?蝴蝶效應之下,我們如今還會不會是社會主義社會呢?只是沒有那么多如果,歷史在我們探索之時就已塵埃落定。《袁氏當國》大大激發了我對民國史的興趣,這可能是作者一開始的寫作目的。
同盟會內部矛盾研究論文
中國同盟會是中國資產階級早期的革命政黨,一九○五年八月成立,一九一二年演化為國民黨。在這短短七年里,它經歷了一個由聯合而分化,由分化而解體的歷史過程。本文通過對同盟會上述歷史過程的初步分析,闡明軟弱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獨立而堅強的階級政黨,因而不具備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并從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方面說明這次革命必然失敗的主觀原因。
一
中國同盟會產生于我國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個具有兩重性質的政治組織,既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又是一個包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急進派、資產階級自由派和地主階級反滿派的松懈的同盟。作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同盟會提出了一個以推翻封建專制、建立共和國和實際上只能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的“平均地權”為內容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推動了辛亥革命的發展。作為反清各派別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員沒有在同盟會綱領的基礎上真正地統一和結合起來,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觀點的前提下,以“反滿革命”為紐帶才聯系在一起,這就埋藏著必然分化的種子。
“反滿”成為同盟會內部各派暫時聯結起來的共同基礎,是由特定的歷史環境決定的。清朝統治的最后半個多世紀,即十九世紀后半期到二十世紀初年,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極點并向帝國主義階段轉變的時期,也是國內各種矛盾空前尖銳和激化的時期。在國內外矛盾的猛烈沖擊下,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瀕臨崩潰,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一天比一天深重。而這一切恰恰發生在清王朝這樣一個長期堅持民族歧視政策的異族王朝統治的年代。人們很自然地認為清政府是中國積弱貧困和一切苦難的淵藪。于是,“反滿”這個曾經長期以來被漢族地主階級反滿派用以激勵人們起來恢復“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幟,被資產階級揀來作為號召和聯合一切“反滿”力量的大□。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們儼然以地主階級“未竟之業”的繼承者自許,認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首先是從異族手里奪回政權,即所謂“傾覆現今之惡劣政府,此造端之事業也<%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一般地說,“反滿”宣傳在資產階級革命派這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排他主義和民族優越論,他們鼓吹“反滿”,但很少同恢復明王朝或重建另一個漢族王朝聯系起來,而是同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聯系在一起。正如孫中山所說:“我們推翻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孫中山選集》上卷第75頁%>”。這就給“反滿”這個傳統口號賦予民主主義的時代內容,成為資產階級政治綱領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滿”的口號過于簡單了,它不但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階級包括地主階級中的反滿派的脾胃,為他們所贊同和接受,成為同盟會這個松懈聯盟的思想基礎,即同盟會組織的兩重性賴以統一起來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會組織的兩重性本身包含著深刻的矛盾。“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同盟會綱領明確地提出了當時中國革命所面臨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革命任務,但它并沒有為所有的同盟會會員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問題上也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有的人抱著傳統的“反滿興漢”的陳舊觀念參加同盟會,他們從“夷夏之辨”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出發,狂熱地宣傳“排滿”,以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國人(指漢人)做皇帝,他們也是歡迎的”,或者認為“只要能夠排滿,民族主義能夠達到目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便自然跟著做去,沒有別樣枝節<%同上書,下卷第795頁%>”。章太炎就是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許多言論中,常常直接從清初漢族地主反滿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語言,認為他們要做的事業“不離呂、全、王、曾之舊域<%章太炎:《光復軍志》。“呂、全、王、曾”指呂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靜。%>”。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嘗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在他看來,所謂共和、總統之類,只能在革命動亂時起某種“調劑”作用,所以他說“共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任他人與之稱號耳<%《章太炎自定年譜》載《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頁%>”,否認“共和”與“專制”之間有嚴格的區別。這些人是同盟會中的“一民主義”者,他們對孫中山極力倡導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表示冷漠。在同盟會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國建立一個純粹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贊同“反滿”和擁護民權革命的,但對于同盟會綱領中以“平均地權”為內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興趣。宋教仁、胡漢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對于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的社會革命學說從來不贊一辭,只說“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與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國<%宋教仁:《我之歷史》%>”。胡漢民因為不同意“平均地權”思想與孫中山進行過激烈的爭論。他們是同盟會中的“二民主義”者。只有孫中山和他的少數追隨者如廖仲愷、朱執信等人才是同盟會三民主義綱領的真正服膺者。他們主張推翻清朝統治,不單因為它是一個滿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為它是一個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社會進步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僅如此,由于孫中山等人目擊過西方國家里貧富懸殊和“社會革命其將不遠”的現實,又初步接觸到早期社會主義的思想學說,于是幻想用所謂“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的辦法,使中國成為不但能夠“媲跡歐美”,而且能夠避免資本主義流□的理想國家。他們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綜上所述,可見對于同盟會的政治綱領真正能夠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擁護到底的,只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急進分子,其余的絕大多數會員只是根據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的需要決定棄取,對綱領中的民主主義的急進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對。這種對于同盟會綱領的不同認識,乃是同盟會必然分化和解體的思想原因。
同盟會內部矛盾分析論文
中國同盟會是中國資產階級早期的革命政黨,一九○五年八月成立,一九一二年演化為國民黨。在這短短七年里,它經歷了一個由聯合而分化,由分化而解體的歷史過程。本文通過對同盟會上述歷史過程的初步分析,闡明軟弱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獨立而堅強的階級政黨,因而不具備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并從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方面說明這次革命必然失敗的主觀原因。
一
中國同盟會產生于我國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個具有兩重性質的政治組織,既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又是一個包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急進派、資產階級自由派和地主階級反滿派的松懈的同盟。作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同盟會提出了一個以推翻封建專制、建立共和國和實際上只能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的“平均地權”為內容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推動了辛亥革命的發展。作為反清各派別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員沒有在同盟會綱領的基礎上真正地統一和結合起來,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觀點的前提下,以“反滿革命”為紐帶才聯系在一起,這就埋藏著必然分化的種子。
“反滿”成為同盟會內部各派暫時聯結起來的共同基礎,是由特定的歷史環境決定的。清朝統治的最后半個多世紀,即十九世紀后半期到二十世紀初年,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極點并向帝國主義階段轉變的時期,也是國內各種矛盾空前尖銳和激化的時期。在國內外矛盾的猛烈沖擊下,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瀕臨崩潰,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一天比一天深重。而這一切恰恰發生在清王朝這樣一個長期堅持民族歧視政策的異族王朝統治的年代。人們很自然地認為清政府是中國積弱貧困和一切苦難的淵藪。于是,“反滿”這個曾經長期以來被漢族地主階級反滿派用以激勵人們起來恢復“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幟,被資產階級揀來作為號召和聯合一切“反滿”力量的大□。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們儼然以地主階級“未竟之業”的繼承者自許,認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首先是從異族手里奪回政權,即所謂“傾覆現今之惡劣政府,此造端之事業也<%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一般地說,“反滿”宣傳在資產階級革命派這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排他主義和民族優越論,他們鼓吹“反滿”,但很少同恢復明王朝或重建另一個漢族王朝聯系起來,而是同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聯系在一起。正如孫中山所說:“我們推翻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孫中山選集》上卷第75頁%>”。這就給“反滿”這個傳統口號賦予民主主義的時代內容,成為資產階級政治綱領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滿”的口號過于簡單了,它不但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階級包括地主階級中的反滿派的脾胃,為他們所贊同和接受,成為同盟會這個松懈聯盟的思想基礎,即同盟會組織的兩重性賴以統一起來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會組織的兩重性本身包含著深刻的矛盾。“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同盟會綱領明確地提出了當時中國革命所面臨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革命任務,但它并沒有為所有的同盟會會員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問題上也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有的人抱著傳統的“反滿興漢”的陳舊觀念參加同盟會,他們從“夷夏之辨”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出發,狂熱地宣傳“排滿”,以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國人(指漢人)做皇帝,他們也是歡迎的”,或者認為“只要能夠排滿,民族主義能夠達到目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便自然跟著做去,沒有別樣枝節<%同上書,下卷第795頁%>”。章太炎就是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許多言論中,常常直接從清初漢族地主反滿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語言,認為他們要做的事業“不離呂、全、王、曾之舊域<%章太炎:《光復軍志》。“呂、全、王、曾”指呂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靜。%>”。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嘗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在他看來,所謂共和、總統之類,只能在革命動亂時起某種“調劑”作用,所以他說“共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任他人與之稱號耳<%《章太炎自定年譜》載《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頁%>”,否認“共和”與“專制”之間有嚴格的區別。這些人是同盟會中的“一民主義”者,他們對孫中山極力倡導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表示冷漠。在同盟會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國建立一個純粹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贊同“反滿”和擁護民權革命的,但對于同盟會綱領中以“平均地權”為內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興趣。宋教仁、胡漢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對于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的社會革命學說從來不贊一辭,只說“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與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國<%宋教仁:《我之歷史》%>”。胡漢民因為不同意“平均地權”思想與孫中山進行過激烈的爭論。他們是同盟會中的“二民主義”者。只有孫中山和他的少數追隨者如廖仲愷、朱執信等人才是同盟會三民主義綱領的真正服膺者。他們主張推翻清朝統治,不單因為它是一個滿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為它是一個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社會進步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僅如此,由于孫中山等人目擊過西方國家里貧富懸殊和“社會革命其將不遠”的現實,又初步接觸到早期社會主義的思想學說,于是幻想用所謂“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的辦法,使中國成為不但能夠“媲跡歐美”,而且能夠避免資本主義流□的理想國家。他們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綜上所述,可見對于同盟會的政治綱領真正能夠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擁護到底的,只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急進分子,其余的絕大多數會員只是根據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的需要決定棄取,對綱領中的民主主義的急進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對。這種對于同盟會綱領的不同認識,乃是同盟會必然分化和解體的思想原因。
同盟會內部矛盾分析論文
一
中國同盟會產生于我國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個具有兩重性質的政治組織,既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又是一個包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急進派、資產階級自由派和地主階級反滿派的松懈的同盟。作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同盟會提出了一個以推翻封建專制、建立共和國和實際上只能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的“平均地權”為內容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推動了辛亥革命的發展。作為反清各派別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員沒有在同盟會綱領的基礎上真正地統一和結合起來,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觀點的前提下,以“反滿革命”為紐帶才聯系在一起,這就埋藏著必然分化的種子。
“反滿”成為同盟會內部各派暫時聯結起來的共同基礎,是由特定的歷史環境決定的。清朝統治的最后半個多世紀,即十九世紀后半期到二十世紀初年,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極點并向帝國主義階段轉變的時期,也是國內各種矛盾空前尖銳和激化的時期。在國內外矛盾的猛烈沖擊下,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瀕臨崩潰,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一天比一天深重。而這一切恰恰發生在清王朝這樣一個長期堅持民族歧視政策的異族王朝統治的年代。人們很自然地認為清政府是中國積弱貧困和一切苦難的淵藪。于是,“反滿”這個曾經長期以來被漢族地主階級反滿派用以激勵人們起來恢復“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幟,被資產階級揀來作為號召和聯合一切“反滿”力量的大□。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們儼然以地主階級“未竟之業”的繼承者自許,認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首先是從異族手里奪回政權,即所謂“傾覆現今之惡劣政府,此造端之事業也<%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一般地說,“反滿”宣傳在資產階級革命派這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排他主義和民族優越論,他們鼓吹“反滿”,但很少同恢復明王朝或重建另一個漢族王朝聯系起來,而是同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聯系在一起。正如孫中山所說:“我們推翻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孫中山選集》上卷第75頁%>”。這就給“反滿”這個傳統口號賦予民主主義的時代內容,成為資產階級政治綱領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滿”的口號過于簡單了,它不但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階級包括地主階級中的反滿派的脾胃,為他們所贊同和接受,成為同盟會這個松懈聯盟的思想基礎,即同盟會組織的兩重性賴以統一起來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會組織的兩重性本身包含著深刻的矛盾。“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同盟會綱領明確地提出了當時中國革命所面臨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革命任務,但它并沒有為所有的同盟會會員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問題上也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有的人抱著傳統的“反滿興漢”的陳舊觀念參加同盟會,他們從“夷夏之辨”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出發,狂熱地宣傳“排滿”,以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國人(指漢人)做皇帝,他們也是歡迎的”,或者認為“只要能夠排滿,民族主義能夠達到目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便自然跟著做去,沒有別樣枝節<%同上書,下卷第795頁%>”。章太炎就是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許多言論中,常常直接從清初漢族地主反滿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語言,認為他們要做的事業“不離呂、全、王、曾之舊域<%章太炎:《光復軍志》。“呂、全、王、曾”指呂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靜。%>”。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嘗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在他看來,所謂共和、總統之類,只能在革命動亂時起某種“調劑”作用,所以他說“共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任他人與之稱號耳<%《章太炎自定年譜》載《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頁%>”,否認“共和”與“專制”之間有嚴格的區別。這些人是同盟會中的“一民主義”者,他們對孫中山極力倡導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表示冷漠。在同盟會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國建立一個純粹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贊同“反滿”和擁護民權革命的,但對于同盟會綱領中以“平均地權”為內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興趣。宋教仁、胡漢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對于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的社會革命學說從來不贊一辭,只說“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與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國<%宋教仁:《我之歷史》%>”。胡漢民因為不同意“平均地權”思想與孫中山進行過激烈的爭論。他們是同盟會中的“二民主義”者。只有孫中山和他的少數追隨者如廖仲愷、朱執信等人才是同盟會三民主義綱領的真正服膺者。他們主張推翻清朝統治,不單因為它是一個滿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為它是一個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社會進步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僅如此,由于孫中山等人目擊過西方國家里貧富懸殊和“社會革命其將不遠”的現實,又初步接觸到早期社會主義的思想學說,于是幻想用所謂“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的辦法,使中國成為不但能夠“媲跡歐美”,而且能夠避免資本主義流□的理想國家。他們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綜上所述,可見對于同盟會的政治綱領真正能夠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擁護到底的,只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急進分子,其余的絕大多數會員只是根據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的需要決定棄取,對綱領中的民主主義的急進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對。這種對于同盟會綱領的不同認識,乃是同盟會必然分化和解體的思想原因。
二
歷史教學中批判性思維的培育
在新世紀的課程改革中,學校教育積極倡導教學方式和學習方式的轉變,實現從“記憶型教學文化”到“思維型教學文化”的轉變。為達成這一目標,在中學歷史教學過程中,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是一個重要途徑。當批判性思維成為歷史教學的常態時,歷史教學的質量必將發生質的變化。
一、何謂批判性思維
對什么是批判性思維,學術界有不同的解釋。學者任長松指出,批判性思維是指這樣的思維過程,即對他人或自己的判斷(觀點)做法或思維過程(論證過程)所開展的深入系統的審視與質疑,嚴謹的比較、分析與評估,以及在此基礎上,通過綜合,提出新的更科學全面、更系統完整的判斷(觀點)、做法或論證[1]52。學者劉儒德認為,批判性思維是指對所學的東西的真實性、精確性、性質與價值進行個人的判斷,從而對做什么和相信什么做出合理的決策[2]。高中歷史課程標準提出了“增強歷史洞察力”“培養探究歷史問題的能力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養成獨立思考的學習習慣”“注重探究學習,善于從不同角度發現問題”等要求,這些提法均與發展批判性思維相聯系。培養批判性思維能力,不在于給學生多少高深的理論,而是提倡學會對問題進行深刻的探索性思考,并從中獲得真知[3]。下面筆者就結合高考第一輪復習中《辛亥革命》一課的教學,談談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的幾點體會。
二、歷史教學中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的策略
為了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筆者在復習過程中采用的教學步驟是:第一,選定有利于培養批判性思維的典型議題;第二,精選有利于批判性思維培養的典型史料,基于史料提出并探討有意義的問題;第三,采取自主學習和小組合作學習相結合的學習方式。在《辛亥革命》一課中,依據課程標準和江蘇省考試說明的要求,結合相關學術研究成果,選定如下幾個議題。
(一)辛亥革命的爆發是偶然還是必然?
陳宦幕僚特點分析論文
[摘要]陳宦幕僚的成份復雜,新舊雜糅、進步勢力與落后勢力并存,具有異質性;陳宦的幕僚具有濃郁的地緣與業緣色彩。體現了其地城主義與任人唯索的用人特點。幕僚團隊的異質性導致陳宦內部四分五裂,內耗和不穩定,無法形成堅強的戰斗力;濃郁的地緣與業緣色彩及其用人的地城主義、任人唯索而不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導致四川失勢者對他恨之入骨,從而使陳宦在四川的權力基礎很不牢固,最終不得不敗退四川。
[關鍵詞]陳宦;幕僚;特點
春秋戰國以來,幕僚問題一直是中國的一種典型而有特殊意義的政治現象,尤其是天下大亂、軍閥割據之時。太平天國之后的近代中國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軍閥或者軍政集團,也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幕僚群體,目前學術界著重研究近代四大幕僚群體——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四人的幕僚以及其他著名人物的幕僚,如劉建強的《曾國藩幕府》,梁勤的《曾國藩幕府》,朱安東的《曾國藩幕府研究》,歐陽躍峰的《人才薈萃——李鴻章幕府》,牛秋實的《李鴻章幕府》,黎仁凱的《張之洞幕府》,張學繼的《袁世凱幕府》,閻團結的《試論馮玉祥幕僚的特點》。這些著述為研究陳宦的幕府提供了較為清晰的借鑒思路,也成為本文的寫作起點和基礎。本文針對陳宦主政四川期間的幕僚群體的兩個特點及其影響進行一些探討,以推進對陳宦和近代幕僚群體的研究。而值得指出的是,陳宦1915年2月20日被袁世凱內定為四川軍政負責人后,他就開始組織自己的幕僚團隊——建立會辦行營的五大處:參謀處、軍務處、秘書處、軍需處、副官處,其聚集的有名字記載的幕僚就有50人之多,到1916年7月他被各方政治勢力趕出四川之后,其近百人的幕僚團隊解體了,所以本文選取1915年2月-1916年7月這段時間來研究陳宦幕僚團隊的特點及其影響。
首先,陳宦幕僚的成份復雜,新舊雜糅、進步勢力與落后勢力并存,具有異質性。
從職業與出身看,陳宦的幕僚中既有從各種新式學堂畢業的人員,甚至留學歸國人員,又有取得一定科舉功名的人員。從各種新式學堂畢業的人員有:張聯菜(1880—1966),字馥卿,山東淄博人,先后就讀于北洋武備學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陸軍大學第一期炮兵科(1906—1908)。胡鄂公(1884—1951),字新三,湖北江陵人,先后就讀于郝穴預備中學堂(1906—1908)、北京江漢學堂(湖北旅京中學堂)(1908—1909)、保定高等農林學堂林業科(1909—1911)。鄧漢祥(1888—1979),字鳴階,貴州盤縣人,先后就讀于昆明高等師范學堂(1905—1906)、貴州陸軍武備學堂(1906—1909)、湖北陸軍中學(1909—1911)。季自求(1887—1944),字天復,江蘇南通人,曾經先后就讀于南通中學堂(1902—1903)、江南將備學堂(1903—1906)。李炳之(1882—1968),字彪臣,河北正定人,先后就讀于北洋保定武備學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陸軍大學第一期(1906—1908)。雷飆(1873-?),字時若,湖南邵陽人,曾經就讀于湖北武備學堂(1903—1905.8)。劉郁芬(1880—1943),字蘭江,河北清苑人,先后就讀于直隸省陸軍小學、保定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孔繁錦(1881—1951),安徽合肥人,畢業于清末陸軍講武堂。其他如王彭年、張慶云、劉延杰、趙錫齡等人均接受過新式學堂教育。留學歸國人員有:劉一清(?一?)。字杏村,湖北武昌人,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四期步兵科(1906.7—1908.5)。熊祥生(1880—1942),字吉安,湖北孝感人,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四期炮兵科(1906.7—1908.5)。王炳坤(1876—1926),字壽乾,安徽肥東人,曾經在日本留學了五年(1904—1909)。劉虎臣,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1906—1908)。取得一定科舉功名的人有:駱成驤(1865—1926),字公輔,四川資中人,1893年中舉、1895年中第一名進士(狀元),陳宦的老師——他曾經擔任過陳宦母校京師大學堂第一提調。他還是陳宦在四川期間的幕后高級政治參謀,曾經在日本考察過兩年憲政(1906—1908)。何積祜,湖南道縣人,清末舉人。出身于書香門第,其曾祖父何凌漢為探花,其祖父何紹基為進士(1836)、翰林編修,書畫家,學者,其叔祖父何紹業、何紹祺、何紹京均為書畫篆刻家。鄧文瑗,藍天蔚岳父,舉人,河北著名書法家,尤其擅長于鐘鼎文。樓薔庵,浙江諸暨人,書法家。修承浩(1875~1953),字翰青,湖南沅陵人,1902年舉人,曾經擔任過廣西宜山縣、富川縣知事,廣東陽江廳同知,云南都督府副秘書長。張之江(1882—1966.5),字子姜,河北鹽山縣人,1899年考取了秀才。
從政治立場看,陳宦的幕僚分為涇渭分明的兩大派:“帝制派”(舊派、北派)和“反帝制派”(新派、南派),兩派圍繞支持袁世凱還是支持護國軍這個政治立場問題進行了劇烈的斗爭。“帝制派”(舊派、北派)以張聯菜為首,包括馮仲書、李炳之、熊祥生、劉虎臣、張慶云等人,大部分是北方的北洋派。“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以劉一清為首包括胡鄂公、鄧漢祥、雷飆、王彭年、馮玉祥等人,大部分有過反清革命歷史。曾任陳宦成武將軍公署軍務處參謀的張之江回憶說:“陳的左右分新舊兩派,舊系以參謀長張聯菜為首,是傾向擁袁世凱的;新系以總參議劉一清為首,是同情護國軍的。”曾任陳宦成武將軍公署軍需處參謀的王彭年在1960年7月回憶道:“及籌安會起……凡籌安會傀儡場合,皆不令我參加。我等積極密謀,如何反袁,一時帝制派,反帝制派形成兩大壁壘,暗斗頗劇。”1916年4月20日晚,“反帝制派”“集會于鄧漢祥宅,討論進止”。“反帝制派”采取各種措施推動陳宦宣布四川獨立反袁,如屢次向陳宦分析時局、以輕重利害向他進言,最終促成陳宦決策宣布四川獨立并和袁世凱斷絕關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四川獨立反袁統一戰線;擔任反袁聯絡官,東進南下秘密聯合其他反袁政治勢力,為四川獨立創設了良好的外部條件。以張聯菜為首的“帝制派”除了游說陳宦擁護袁世凱之外,還狂熱地與護國軍激戰于瀘州、綦江,如熊祥生和李炳之就與蔡鍔部激戰于瀘州,導致護國軍收復的瀘州得而復失,損失慘重。劉虎臣與戴勘激戰于綦江,曹錕說他“率領全團分赴合川、墊江防剿土匪,匝月以來,勤勞卓著”。熊祥生還在1916年3月27日致電袁世凱反對袁世凱退皇帝位:“忽奉撤消帝制之電,全體官兵同深憤懣……早殲巨憨,仰慰圣懷。我軍休養數日,銳氣全復,驟聞帝制撤消之命,官兵心無憑依,頗滋疑慮。乞諸公竭力聳動,勿輕聽人言,遽變大計。務懇收回成命,以給人民之望,而系天下之重……副司令熊祥生叩。”李炳之在1916年5月10日得到陳宦在5月3日致電北京勸袁世凱退位的電文之后,馬上發表《擁護中央決不聽鼓(蠱)惑電》表示效忠袁世凱:“陸軍部段總長,參謀部王總長鈞鑒,借用唐次長定密。頃閱陳將軍通電,懇求主座(即袁世凱一引者)退位,殊深駭異。吾輩始終以擁護中央為心,斷不聽信鼓惑謠言,現職旅第一團駐扎在重慶,其第二團之兩營雖駐成都,軍心可靠,請勿為念。惟此后本旅一切行動……仍懇鈞座指示方針,俾資循率。毋任叩禱。李炳之叩。”盡管如此,“帝制派”還是沒有阻擋住四川獨立反袁的步伐。陳宦幕僚成份復雜,新舊雜糅、進步與落后并存,具有異質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民國初期的社會是一個處于新舊交替的轉型期社會,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仍然是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但是政治層面與器物層面上出現了西方近代化因素。比如軍隊開始利用西洋、東洋的操典、器械。第二,這和陳宦的政治立場和態度有關,久經官場的陳宦為了減少政治風險、左右逢源、進退有據,特意在幕僚中既安排擁袁的“帝制派”,又安插同情蔡鍔的“反帝制派”。正如劉一清所說:“其他調用人員,亦夾雜有不少民黨分子,如修承浩、雷飆等系蔡鍔所薦。陳處處含有兩套手法,能說他無所容心,是偶然巧合嗎?”第三,這和陳宦的經歷、背景、嗜好、情趣、價值取向有關。陳宦接受過幾十年的儒家經典教育,并且考取過秀才、廩生、撥貢,但他又曾經就讀于新式學堂,如湖北武備學堂、京師大學堂,而且追隨錫良推行新政達8年之久,1911年初曾經到德國考察軍事。可見,他本身就是一個新舊雜糅的人物。
民初憲政歷史經驗論文
辛亥革命結束了清帝國260多年的統治。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的中國同盟會取得了重大勝利。可是,以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敗為標志,不但國民黨陷入困境,民國亦名存實亡。從1911年10月10日起義至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國內政局跌宕起伏,成敗交替。痛罵袁世凱專制、反動,可以解恨但無法增加政治智慧。袁氏本來是新舊參半的人物,要回答的問題恰恰是這個清末新政的翹楚,為什么沒有在各方壓力下繼續前進。這里蘊藏著值得認真探討的政治經驗。本文著重從國民黨和孫文方面的策略失誤來看其中的癥結。“春秋責備賢者”,與其罵反動派,不如讓有志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人們得到必要的教益。
南北議和與同盟會改組
民國成立,在新的形勢下,如何適時調整自己的奮斗目標和策略,推動歷史前進,成了考驗同盟會領袖們的重大課題。有的史家至今仍在指責他們“軟弱”,把政權輕易地讓給了袁世凱。這有失公允。政治家必須審時度勢,南北議和,讓權于袁世凱,是基于以下形勢的無可奈何的選擇:
首先,軍事力量對比十分不利于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控制著訓練有素的北洋六鎮7萬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國的禁衛軍和其他新軍,總兵力達14萬多人。而南京臨時政府方面,號稱革命的各色民軍很多,絕大部分是會黨乃至綠林隊伍改編而成。雖然人數上遠多于北方,武器裝備、訓練、指揮和紀律等都遠遜于對方。
其次,經濟力量對比懸殊,南京臨時政府已到了難于支撐的邊緣。雙方在財政上都困難重重,但袁氏出任清帝國內閣總理后畢竟仍牢牢控制著東北和華北大部,中央財政的基礎仍在,原有的征稅系統沒有打亂,軍費比較充足。于是,除了維持正常運作外,袁氏還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幾十萬乃至幾百萬兩白銀收買清帝國的王公大臣和革命黨人。與此同時,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卻為維持臨時政府所必需的經費在國內外頻頻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談話中坦率地承認:“倘近數日內,無足夠之資金以解燃眉之急,則軍隊恐將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將面臨瓦解之命運……之所以斷然實行漢冶萍日中合辦,以取得五百萬元資金者為此;此次又苦心焦慮,欲以招商局為擔保,籌措一千萬元借款者,亦為此。然而,雖經種種籌劃,而時光荏苒,交涉迄無結果……于軍隊解散、革命政府崩潰之前,作為最后之手段,唯有與袁世凱締結和議,以防天下大亂。”[1]當時各省雖然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但起義軍、民團等急劇增加,支出浩繁,自顧不暇,不但無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撥款。再加上關稅收入被列強在“中立”的名義下凍結,臨時政府在經濟上顯然已走進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驅除韃虜”成了同盟會政綱的頭一條。占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發“遜位詔”,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于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于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當時民眾心理,俱祝福于和議。逆之而行,乃至不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