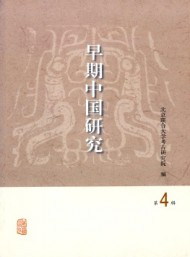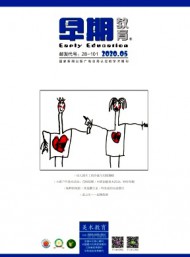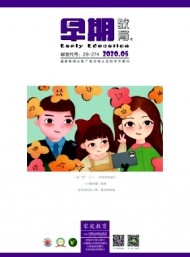早期電影范文10篇
時間:2024-04-13 04:33:24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早期電影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早期電影敘事研究論文
【內容提要】
在中外文化相互交織、新舊思想彼此對話的錯雜語境中,中國早期電影呈現出獨特的敘事格局并形成了優良的敘事傳統。通過曲折的情節設置和動人的情感訴求,電影生產者充分發掘出大量的民族民間故事資源,使電影接受者養成了一種獨特的類型期待視野和故事消費心理。“故事”的生產和消費及其互動,不僅構筑著中國早期電影的民族氣派、大眾面向和產業景觀,而且為亂世中國創造了一大批無負于時代、也無愧于世界的電影經典。
本文視野里的中國早期電影,特指1905年至1949年間,由中國人所從事并主要訴諸中國觀眾的電影生產和電影消費實踐。
將中國早期電影納入一個更加豐富、更加多元的復雜語境之中,是推動中國早期電影研究走向深廣的必由之路;而在考察相關作者、文本和類型之時增加觀眾分析的維度,更是重讀中國電影敘事傳統的有效途徑。正是建立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筆者提出:在中外文化相互交織、新舊思想彼此對話的錯雜語境中,中國早期電影呈現出獨特的敘事格局并形成了優良的敘事傳統。通過曲折的情節設置和動人的情感訴求,電影生產者充分發掘出大量的民族民間故事資源,使電影接受者養成了一種獨特的類型期待視野和故事消費心理。“故事”的生產和消費及其互動,不僅構筑著中國早期電影的民族氣派、大眾面向和產業景觀,而且為亂世中國創造了一大批無負于時代、也無愧于世界的電影經典。
中國早期電影:民族民間故事的引入
中國電影產生于一種異常錯雜的語境,正是這種特殊的語境制約著中國早期電影的敘事格局。在《現代中國電影史略》(1936)中,鄭君里相當深入地分析和闡發了“推動并約制”中國影業前程進而顯現中國電影發展“規律性”的各種“矛盾的總和”①。實際上,無論是“藝術性”與“民族文化”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還是“帝國主義國家”與“半殖民地”的文化事業在“投資”方面的矛盾;無論是中國電影的“企業性質”與“文化運動”之間的關系,還是電影的“藝術性”與“商業性”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甚至半殖民地的“電影技術條件的落后”等許多問題,都是中國早期電影不可回避也無法克服的癥結之所在。在這里,中外文化相互交織,新舊思想彼此對話,而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強勢地位,跟半殖民地的弱勢中國形成鮮明的反差;“中學”與“西學”、“舊學”與“新學”之間的不期而遇和劇烈沖突,也將中國早期電影置于一種前所未有的復雜境地。
早期電影表演風格的轉變
摘要:中國早期電影演員表演時夸張的肢體動作、定格化的戲劇表情、以及跳躍的節奏構筑成了“戲”味濃厚的早期電影表演風格。筆者通過從戲曲、文明戲、西方電影表演與電影技術幾方面淺析了中國早期電影表演“戲”味濃厚的成因。以及在左翼電影運動下,早期電影表演風格是如何從“戲”味濃厚向求“真”自然的轉變的。
關鍵詞:早期電影;左翼電影;電影表演
一、中國早期故事片“戲”味表演的形成
縱觀中國早期的電影我們可以發現,演員的表演通常都有著大幅度的肢體動作、定格化格化的戲劇表情以及跳躍的表演節奏,這些都與當今生活化的電影表演風格相去甚遠,給人以一種脫離真實生活“戲”味濃厚的感覺。這種“戲”味濃厚的表演方式是受戲曲、文明戲、西方電影表演以及電影技術方的綜合影響下的結果。1.戲曲、文明戲“戲”的綜合影響中國早期電影表演受到傳統戲曲影表演的影響很深。在電影傳入中國以前,京昆為主的戲曲表演是當時廣大觀眾最為熟悉的一種表演方式。戲曲表演深受觀眾的喜愛與認可,它有著深厚的觀眾基礎。電影傳入后,在很大程度上電影這門新興藝術是受到傳統戲曲藝術母體哺育的。當時許多電影的取材與演員就是直接從戲曲中套用而來的。被學術界視作是中國電影萌芽之作的《定軍山》就是一部戲曲題材電影。當時許多戲曲演員如:梅蘭芳、周信芳、楊小樓等都名角兒都拍攝了一系列的戲曲影片。在這些影片當中演員的表演,仍舊是承襲傳統戲曲表演“唱念做打”的基本程式,唯一不同的只是將舞臺表演搬到了電影之中。熒幕上中國戲曲表演高度凝煉與極度寫意化的表演方式,似乎為后來的電影演員們做定下了一條鐵的規則:即表演應當與生活拉開距離,演戲都應有“戲”的意味、“戲”的樣式。加之中國傳統的“文以載道”潛意識文化心理的影響,早期電影中演員演“戲”意識很強。隨后,文明戲伴隨著革命來到了中國。文明戲的表演方式也跟隨著文明戲演員一起走進了電影。雖然文明戲在表演方式上擺脫了“以歌舞演故事”的形式,比起傳統的戲曲表演來說,它的表演形式似乎拉近了與生活的距離。但是文明戲表演仍屬于舞臺表演藝術的范疇。從本質上來說,它仍就屬于對生活的高度模擬,而并非對生活逼真的再現。文明戲演員對于攝影機對前的表演是陌生的,他們沒有鏡頭感意識。他們只是依據自己文明戲的舞臺表演經驗,連續不斷地進行下去而已。在拍攝故事片《難夫難妻》時張石川就吩咐演員在“鏡頭前面做戲,連續不斷的表演下去。”1同時,戲曲表演中的“女角男扮”觀念在這里得到了延續。《難夫難妻》這部故事片中女性角色都是由男性演員扮演,全片沒有一個女性演員。在張石川隨后拍攝的幾部短片中,也只有男性演員沒有女性演員。戲曲表演中“女角男扮”這種“反串”模擬性的表演方式,作為舞臺藝術在劇場里行得通,是因為劇場空間距離與中國戲曲本高度寫意化的表達能為觀眾接受。但在以紀實為美學特征的電影中。男性演員扮演女性角色,在銀幕上就會有較強的牽強與扭捏之感。并且男性演員為了接近女性形象,在形體表情上難免就會更為夸張,所以做“戲”的意味也就更加濃厚。2.西方電影對早期電影表演的影響早期中國電影表演之所以“戲”味濃厚還受西方電影的影響。現在所留存下來的最早的故事片是1932年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拍攝的《勞工之愛情》。這是一部立意上有些膚淺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滑稽短片。是張石川“處處惟興趣是尚”制片方針下的產物。影片的取材與拍攝都是對當時西方“打鬧劇”電影的模仿。《勞工之愛情》這部影片不僅在敘事上借鑒了西方“打鬧片”的常用模式。在表演上也是完全模仿西方滑稽片的表演風格。夸張的思考判斷、快速的形體變化、跳躍的行動節奏,這些無疑都是對卓別林滑稽劇的直接模仿和搬用。這樣夸張的西式滑稽片表演套路,無疑也是早期中國電影“戲”味濃厚的原因之一。3.電影技術手段對早期電影表演的影響早期電影演員表演“戲”味的濃厚,不僅是受戲曲、文明戲與西方電影的共同影響的結果,同樣也有著來自無聲電影技術條件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演員的表演主要是依靠形體和語言來呈現”2初期許多電影都是無聲電影,所以在表達人物內心情感與想法時往往就更加依賴形體動作,因為無法通過聲音與臺詞來表情達意,所以早期無聲片為了交代清楚人物關系與劇情發展、人物情感變化,演員往往就需要通過夸張的肢體動作,與定格化的戲劇表情來表達。如夸張化的思索與頓悟的表情來展現人物內心想法,雙手抱頭表示痛苦,拍掌跳躍表示高興,而這樣的表演方式在結果上就顯得十分的夸張與做作。并且中國早期電影,尤其是滑稽片當中都不約而同的運用了降格拍攝的辦法。降格拍攝雖然能使演員表演節奏更快,跳躍感更強更符合滑稽片的審美要求。但是也打亂了演員正常表演節奏,不符合現實生活的真實狀態,是一種變形的夸張,它拉開了與生活真實的距離,這些原因都從一定程度上促使演員表演“戲”味濃厚。
二、左翼電影運動推動電影表演求“真”轉變
中國電影表演開始從求“戲”到“求”真是19世紀30年代,當時由于日寇侵華,在民族危機不斷加深,廣大電影觀眾不再醉心于銀幕上的“風花雪月”、“怪力亂神”,而是把目光紛紛聚焦現實生活。于是左翼電影運動隨之興起,各大電影公司的經營者為了擺脫自身發展困境,紛紛開始與左翼文化人合作。陸續創作完成了一大批現實主義的影片如:《春蠶》、《神女》、《十字街頭》等,這些影片取材現實生活,開創了我國電影的現實主義電影傳統。電影“向現實生活看”的創作觀念革新,雨后春筍般涌現的現實主義題材的劇本所帶來的是電影表演觀念的變化。現實主義作品的內容都是來源于實際生活與之前滑稽片、俠神怪片脫離實際生活的內容大相徑庭。一味求“戲”、不真實的表演風格在現實主義的光芒照耀下顯得不合時宜。追求“真實性”的表演,是當時進步演員的共同目標。演員們的眼光開始觀察生活、體驗生活,以生活真實感價的標尺來錘煉自己的表演。1.新題材推進表演的求“真”根據矛盾小說改編,拍攝于1933年的電影《春蠶》對早期電影表演風格轉變有著重要意義。這部作品沒有夸張離奇的情節,只是江南人家采桑養蠶的逼真再現。劇本對生活無限的貼近,帶來的必然是演員在表演風格上的轉變。片中真實的江南生活場景的呈現,充滿生活意味的勞動細節如:抽煙蒂、洗蠶箅子、喂蠶這些細節都要求演員去認真地觀察生活和逼真的再現生活,表演中不容一絲的浮夸。片中原本擅長扮演交際花、舞女的嚴月嫻,在這部電影中改換戲路扮演四大娘,表演上真實再現了農家婦女的樸實與勤勞。為了體驗人物相同的著急情感,曾因俠神怪片走紅的演員肖英甚至徹夜不寐來獲得相似的真實體驗。雖然《春蠶》這部影片被當年觀眾評價“太沒戲”,被軟性電影論者詬病為“缺乏電影的感覺”3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種新的創作觀念的挑戰,它在極力去掉“戲味”還原生活的真實。《春蠶》這部影片的演員對生活的觀察,和在電影表演時力圖還原生活、細膩真實的表演狀態,可以說是電影表演邁向求“真”表演的第一步。2.演員生命體驗熔鑄表演的真實如果說《春蠶》這部影片中求“真”表演方式是由現實主義劇本帶來的嘗試,那么誕生于無聲電影末期,由阮玲玉主演的無聲電影《神女》其劇作的現實主義魅力與阮玲玉真實細膩的表演,則可以視作早期故事片求“真”表演的經典之作。在《神女》這部影片當中,女主角“阮嫂”這個角色的身上同時兼具了“偉大的母親”與“卑微的妓女”兩種身份形象。這樣的性格化的“圓形”人物形象,比起單一化地“扁平”人物形象來說,她更具有深度也更加真實。這種多側面真實化的人物形象在早期中國電影中是比較少見的,這需要演員去觀察生活。并且,演員要同時將這兩種極端的形象和情感要做到自然地融合在一個角色身上,在兩種情感、兩種身份之間游刃有余,在表現上分毫不差,這對演員來說著實是很難的考驗,需要演員的思考。如果妓女的形象多一分就會讓觀眾覺得妖媚從而產生厭惡,如果母親的形象少了一分又不能激起觀眾無限同情,產生不了強烈的矛盾沖擊,達不到編劇與導演要表達的意圖。面對這樣一個在中國電影之前從未出現過的人物形象。作為一個有天賦的演員,阮玲玉從少年時期寄人籬下的真實遭遇中尋求相似的情感體驗,并與劇中人物孤兒寡母的悲慘生活相重疊,引發了阮玲玉對人物的同情,讓她創造出了真實化的表演。尤其是影片當中,流氓到“阮嫂”家收刮錢財的一段戲,攝影機透過流氓的胯下拍攝阮嫂護子的鏡頭時,阮玲玉緊緊護著孩子時那驚恐的眼神,著實地再現出了人物嬌弱、哀怨、凄慘的形象,讓無數觀眾為之動容。影片《神女》的成功在于演員創造出了一個真實的豐滿的人物形象,而這樣成功的創造依靠的正是演員個體生命體驗與角色情感的完美契合所帶來的真實化地表演。同樣拍攝于1934年的電影《新女性》中,阮玲玉同樣也有著深切的情感體驗與共鳴。尤其是片中阮玲玉飾演的女主人公偉明服安眠藥自殺的那場戲,阮玲玉把自身對于黑暗社會現實的感受融進了角色,她曾說“我在演這場戲時,重新體驗了我自殺時的心情”4所以這場戲現在看來也是非常的真實和生動的。表演的真實感中,一個演員只有自己的真情實感參與到了角色的創作中,她所創造出的角色才可能是真實的、感人的、能讓觀眾長久記憶的。阮玲玉注重對生活的體驗和再現,將演員個體的生命體驗與情感帶進角色,實現了演員與角色的統一。阮玲玉自然、樸素、生活化的真實化表演,讓她塑造的角色自然地流露出真實情感,營造出了無窮的銀幕魅力,這也讓阮玲玉成為了無聲電影時期最優秀的女演員。3.“求真”的現實主義表演風格形成如果我們把阮玲玉在表演上去掉“戲”味,扮演出真實生動的人物形象,得益于她與角色類似的人生經歷與體驗,歸于她自身的遭遇、良好的悟性、天賦才華。那么主動向外國表演體系學習,尋求電影表演的“真”,則是早期電影人自覺的探索。在這些演員里,趙丹是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與現實主義表演創作緊密結合的演員。在拍攝電影的同時他仍然活躍在戲劇舞臺上,參與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指導下的戲劇作品演出中,去學習與體驗人物形象創造的方法。他本人也曾說:“就是從《娜拉》和《大雷雨》的藝術實踐,開始踏上現實主義的藝術道路。”表演上求“真”的最大美學特點是在于創造出真實可信的人物形象,“創作的人物要使觀眾有似曾相似的感覺”5趙丹表演的求“真”不僅在于對國外先進表演體系的學習吸收,還體現在對生活細節的細微捕捉和觀察。在表演中,細節往往是能使表演增加真實感的好方法。在趙丹創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中,他總是首先向生活學習,觀察生活中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為了扮演好他們趙丹總會通過觀察到的一些生活化的小動作,來避免戲劇式的夸張。諸如在影片《馬路天使》中,人物面對新環境的左顧右盼,用衣作扇,對飲水機的好奇引發的一些列小動作等等。這些富有生活氣息的動作設計使他扮演的人物看上去親切自然。趙丹這些表演上的求“真”的做法,使他創造出了真實的、似曾相似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斯式體系的影響與演員在表演求“真”上的自我探索。左翼電影運動時期還有很多的電影作品如:《風云兒女》《桃李街》《大路》等,這些影片反映了編導們對時代的紀實性的共同追求。在這些作品影響下,演員們所飾演的角色往往很多是過去電影里所沒有的,因此他們不得不向生活學習,開始注重對生活的觀察和感受,在塑造小人物時不再以夸張的表情與程式化的肢體動作為手段,轉而注意自身情感體驗與流露,注重內心情感體驗與生活化的表演。這些都促使早起電影表演風格從“戲”味表演到求“真”的變化。
早期電影敘事管理論文
【內容提要】
在中外文化相互交織、新舊思想彼此對話的錯雜語境中,中國早期電影呈現出獨特的敘事格局并形成了優良的敘事傳統。通過曲折的情節設置和動人的情感訴求,電影生產者充分發掘出大量的民族民間故事資源,使電影接受者養成了一種獨特的類型期待視野和故事消費心理。“故事”的生產和消費及其互動,不僅構筑著中國早期電影的民族氣派、大眾面向和產業景觀,而且為亂世中國創造了一大批無負于時代、也無愧于世界的電影經典。
本文視野里的中國早期電影,特指1905年至1949年間,由中國人所從事并主要訴諸中國觀眾的電影生產和電影消費實踐。
將中國早期電影納入一個更加豐富、更加多元的復雜語境之中,是推動中國早期電影研究走向深廣的必由之路;而在考察相關作者、文本和類型之時增加觀眾分析的維度,更是重讀中國電影敘事傳統的有效途徑。正是建立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筆者提出:在中外文化相互交織、新舊思想彼此對話的錯雜語境中,中國早期電影呈現出獨特的敘事格局并形成了優良的敘事傳統。通過曲折的情節設置和動人的情感訴求,電影生產者充分發掘出大量的民族民間故事資源,使電影接受者養成了一種獨特的類型期待視野和故事消費心理。“故事”的生產和消費及其互動,不僅構筑著中國早期電影的民族氣派、大眾面向和產業景觀,而且為亂世中國創造了一大批無負于時代、也無愧于世界的電影經典。
中國早期電影:民族民間故事的引入
中國電影產生于一種異常錯雜的語境,正是這種特殊的語境制約著中國早期電影的敘事格局。在《現代中國電影史略》(1936)中,鄭君里相當深入地分析和闡發了“推動并約制”中國影業前程進而顯現中國電影發展“規律性”的各種“矛盾的總和”①。實際上,無論是“藝術性”與“民族文化”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還是“帝國主義國家”與“半殖民地”的文化事業在“投資”方面的矛盾;無論是中國電影的“企業性質”與“文化運動”之間的關系,還是電影的“藝術性”與“商業性”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甚至半殖民地的“電影技術條件的落后”等許多問題,都是中國早期電影不可回避也無法克服的癥結之所在。在這里,中外文化相互交織,新舊思想彼此對話,而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強勢地位,跟半殖民地的弱勢中國形成鮮明的反差;“中學”與“西學”、“舊學”與“新學”之間的不期而遇和劇烈沖突,也將中國早期電影置于一種前所未有的復雜境地。
閱讀早期電影理論管理論文
提要:本文評述近年在西方迅速發展的有關早期電影的理論,指出漢森的“白話現代主義”體系雖然挑戰封閉式的經典電影理論(如心理分析-符號學、形式主義-認知學),成功地將電影文化與都市現代性在公共空間領域里緊密結合起來,但她描述“獨特的”上海默片缺乏歷史、文化的具體性,而其以動感為基礎的“集體感官機制”學說也有待與意識形態批評做進一步的對話,以推進電影的新文化史的研究。
關鍵詞:電影理論早期電影白話現代主義集體感官機制新文化史
在早期中國電影這個較新的研究領域里,至今最引入注目的海外理論探索,來自張真的《“銀幕艷史”:電影文化,城市現代性與中國的白話經驗》(美國芝加哥大學1998年博士論文)和張真的導師米連姆•漢森2000年在美國《電影季刊》上發表的文章《墮落女性,冉升的明星,新的視野:試論作為白話現代主義的上海無聲電影》。(1)張真的博士論文于1999年獲得美國電影研究學會最佳博士論文獎,實為在美國研究非西方電影的博士論文中的上乘之作。經過幾年的修改,張真將于2005年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書,新題為《銀幕艷史:上海電影與白話現代主義,1896-1937》,重點與漢森的文章更為接近。(2)雖然從師漢森與湯姆•甘寧,張真在自己的研究中發展了漢森的白話現代主義和甘寧的早期電影理論,并參考近年國內外陸續發表的研究早期中國電影的書籍。(3)當然,“早期電影”在中國的電影史中的概念與西方電影史的分期不同,可從1905年中國電影的誕生算到中國有聲片發展多年后的1937年,因此,1937年成為漢森和張真研究中的下限年。(4)漢森文章的中文翻譯現已刊登在《當代電影》2004年第1期。這樣,在“中國電影百年”這一大的學術語境中討論白話現代主義和早期中國電影之間的關系,現在時機已到。
漢森將自己的理論區分于注重封閉式敘事的“經典好萊塢電影”的兩大電影理論主流:其一,心理分析-符號學理論(以及與此產生的意識形態的機構理論);其二,近十多年來發展的形式主義-認知學理論。這樣,我們可以把漢森的理論歸為西方電影理論發展的第三條途徑,而這一發展的背景是西方文科領域近來“文化轉向”后對文化史的偏好。用張真的話說,漢森的理論“將有關現代性的哲學爭論的焦點從心智移到身體,從預言移到現實,從上層建筑移到下層建筑,從崇高移到低俗,從個人移到集體”。張真跟隨這一學術方向的轉變,在自己的研究中力求“通過上海國際性的電影文化的鏡頭,建構一個中國現代性的文化史”,“一個以電影為中介的情感方式的文化史”,或更簡單地說,“一個電影的感官史”。以下我用“集體感官機制”、“白話現代主義”和“新文化史”為題,評述漢森和張真對早期中國電影的理論探索,并提出我自己的例證和見解。
作為集體感官機制的早期中國電影
漢森的理論中幾個關鍵詞包括“感官”(或“感官機制”)、“直接性”、“情感性”(affect)、“空間”(horizon)和“公共領域”等。按漢森看來,經典好萊塢電影在世界上的壟斷地位與電影的經典性質(即永久性和普遍性)的關系不太大,而與電影能為海內外的大批觀眾提供一種經歷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感官—反射空間的關系更大。她把“感官-反射空間”定義為一種話語形式,通過這種形式,個人經驗可能在公共領域里他人的表達和承認中找到共鳴。而且,這種公共領域不只包括印刷媒體,也在視覺和聽覺媒體中流傳,產生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換言之,除了好萊塢的圓熟的故事和敘事方式及其強大的經濟、文化資本外,漢森認為感官經驗(即視、聽、聞、味、觸、動等感覺)也為好萊塢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使其電影成為世界上最流行、最有力的大眾娛樂形式。
國內外早期電影管理論文
【內容提要】
格里菲斯對于中國早期電影的影響,近來愈為研究者所重視。本文從報紙雜志廣泛搜索歷史資料,追溯到1920年代上半期的歷史語境,認為對于“萌芽時代”的中國電影,格里菲斯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由于他的影片所表現的思想和藝術,中國人真正接受了電影,并視之為教育工具。格里菲斯不僅被當作電影藝術的楷模,也是為新興的電影話語所打造的偶像,與好萊塢文化一起,被融匯到中國自身的社會改良方案中。本文揭示了《賴婚》、《重見光明》等影片的成功,在啟動電影廣告、報紙影評等方面產生了歷史性效應。在流通與詮解中,格里菲斯像一個炫目的影像舞臺,衍生出本土的電影話語,交織著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思想潮流,其中文字和文學傳統的中介作用,如萬花筒般千姿百態。
【關鍵詞】格里菲斯中國電影影響研究形象中介
一、格里菲斯的歷史與記憶
在1920年代上半期的中國影壇,格里菲斯(DavidWarkGriffith,1875—1948)可說是光焰萬丈。報紙常用“萬人空巷,風靡一時”來形容其影片上映的盛況,甚至說“皆以競映葛雷非斯之影片為榮耀”,明明是廣告的夸張,卻造就了格里菲斯的中國傳奇。曾幾何時,像在好萊塢一樣,他的名字在中國也沉入遺忘之河,成為歷史往跡。正如安德森對于新舊大陸的地名研究所示,集體記憶與民族“想象共同體”相糾纏,或如福柯所說印刷物中歷史記錄的“見與不見”,受到社會權力機制的操縱。在20世紀中國,有關格里菲斯的集體記憶歷經滄桑,與“革命”的意識形態相顛簸。在60年代的正統電影史中,他的名字是同美國影響一起被鏟除的。陳立(1910—1988)于1971年出版了《電影》(DianyingElectricShadow)一書,被英語世界視作有關中國電影史的經典之作,但他對于格氏在中國的情況不甚了了,提到那部善意表現華人的影片《殘花淚》(BrokenBlossoms)時,不無困惑地說他不清楚該片是否在中國放映過。(1)
1993年畢克偉(PaulG.Pickowicz)教授發表《情節劇再現與中國“五四”電影傳統》一文,論述好萊塢與“五四”的密切關系,已是打破禁忌之作,石破天驚地提出20年代“鴛鴦蝴蝶派”的電影比“五四”文學要“現代”得多。(2)該文提及格里菲斯在當時中國的盛況,當然對于好萊塢經典敘事的“情節劇”(melodrama),格氏也是主要打造者。在1996年酈蘇元、胡菊彬的《中國無聲電影》一書中,這一盛況得到了更為肯定的反映。(3)特別近數年來,隨著早期電影記憶不斷出土,對于格氏愈加重視,資料挖掘也越趨細致,但不無遺憾的是,一般所依據的材料不外乎鄭君里1936年《現代中國電影史略》中的一段話。(4)其中對于格里菲斯在華上映的影片開列了一份可觀而不全的清單,主要問題是說《賴婚》(WayDownEast)在1924年春到中國,則弄錯了時間。事實上是在1922年5月先在上海獻映,后至天津和北京。雖然只差兩年,但格里菲斯在中國走紅,恰恰是在這兩年。根據《申報》的電影廣告,自1922至1924年間在上海各影院共上映了10部格氏影片,其中最突出的是《賴婚》,前后映過5次;《重見光明》(TheBirthofaNation)、《歐戰風流史》(TheGirlWhoStayedatHome)、《亂世孤雛》(OrphansoftheStorm)、《孝女沉舟》(TheLoveFlower)各演過兩次;《黨同伐異》(Intolerance)是舊片重映;《最大之問題》(TheGreatestQuestion)和《恐怖的一夜》(AnExcitingNight)各演了三四天;而《殘花淚》只映了3天就被因故腰斬了。(5)
早期電影詩性元素分析
摘要:安德烈•塔爾科夫斯基是俄國著名的電影導演,其獨特的詩性電影風格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伊萬的童年》便是塔式詩性電影風格的發軔之作。通過對《伊萬的童年》中意象的作用分析,能夠從“作者批評”的角度來理解其后期作品中的詩性電影風格。
關鍵詞:詩性電影;意象;作者批評
1社會歷史環境對塔爾科夫斯基創作的影響
安德烈•塔爾科夫斯基生于1932年,1986年病逝于瑞典。在塔爾科夫斯基成長的社會環境里,這一代人對二戰的直接記憶是比較模糊的。然而,社會的動蕩不安、生活的窘迫艱難和人民的顛沛流離,這些戰爭帶給人們的創傷則是難以撫平心靈的。這些社會外部環境使塔爾科夫斯基“較多地看到了戰爭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創傷,感受到了生活的動蕩,因而有著強烈的對和平與安定生活的向往和反戰、反暴力的傾向。”[1]同時,“隨著‘斯大林時代’的結束與赫魯曉夫‘解凍’時代開始的歷史轉折,樹立起比較自由獨立的思維方式和富于人道主義的生活立場。”[1]這些現實的社會環境對塔爾科夫斯基的影響是顯著的,再加上塔爾科夫斯基電影中深厚的多元文化影響,如俄羅斯民族優秀的精神文化傳統和西方宗教思想的內在作用,使塔爾科夫斯基具備了藝術創作的前提。其中,優秀的俄羅斯精神文化使塔爾科夫斯基形成了獨特的俄羅斯藝術氣質,他的作品明顯受到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在繼承前者偉大精神之后形成了其對人性的關照與悲憫,對人世間充滿博愛的人道主義精神。正如塔爾科夫斯基自己所說:“我在電影里力求表現典型的俄羅斯特點,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其中包含著某種來源于同情、憐憫的東西,甚至是一種感受別人痛苦的愿望。”[2]這些民族精神和宗教思想等內在因素和現實性社會外部環境,對其的影響構成了塔爾科夫斯基藝術創作的內在動力和前提條件。她的父親阿爾謝尼•塔爾科夫斯基是蘇聯著名的詩人。塔爾科夫斯基成長與文化氣氛濃郁的家庭之中,具備了良好的文學與藝術素養。這些影響再加上在電影學院師從哈伊爾•羅姆的專業性學習,奠定了塔爾科夫斯基本人的詩性電影創作風格,形成了其獨特而嚴肅的藝術觀。表現在藝術作品中,這種實行風格便成為薩瑞斯所謂的“個人印記”,“這種個人的‘印記’是社會、歷史、文化、家庭等眾多因素‘合力’所烙下的。因此,對導演本人所處的社會時代、歷史文化環境、家庭背景和個人經歷的深入了解、分析、研究,是考察作者思想藝術風格形成的必要前提。”[3]
2《伊萬的童年》中對詩性電影的初步探索與最終形成
《伊萬的童年》是塔爾科夫斯基1962年拍攝的第一部長劇情片。電影在當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上獲得了“金獅獎”,法國批評家薩特曾評論說:“這部影片是我近年來看到的最出色的影片之一。”[4]1965年,著名的意大利導演帕索里尼在他的理論文章《詩電影》中提出了“詩電影”的概念:“電影能夠根據敘事和內在符式的需要描繪出多重主觀性,這使得任何觀眾都能夠獲得高度的自我體驗。”“塔爾科夫斯基的作品和理論也許就是帕索里尼‘詩電影’概念最完美的詮釋者。”[5]在《伊萬的童年》這部電影中便可以看出塔爾科夫斯基強烈的個人風格。開始段落的夢中出現了構成塔爾科夫斯基“詩電影”的重要意象,詩的特征是講求語言的精煉和意蘊的深遠,詩的本身是抽象而凝練的。在這個夢中出現的母親、水、蝴蝶等一系列意象都是高度凝練而富有深意的,用這種詩意的鏡像語言構筑起來的電影有著詩一樣的凝練和深淵。伊萬的童年是雙親缺失的童年,尤其是母愛的缺失對伊萬日后雙重性格的形成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伊萬是強硬勇敢的,他承受了他的年齡所不能承受的壓力,本應是快樂無憂的童年卻因戰爭而扭曲了人格,幼小的心靈被蒙上了陰影。當伊萬趟過冰冷的河水找到隊伍時,暫時完成偵察任務的他第二次進入了夢境。這次的夢境之中井水成為構成夢的主要意象,“井”經常作為故鄉的意象出現在懷鄉的詩中。在這個夢中“井”的出現不是偶然,而是塔爾科夫斯基對戰爭中流離失所的人們心理最精準的把握。“井”的意象對戰爭中的人們象征的是故鄉與安寧,“水”則象征著故鄉對人們的滋養。讓伊萬游離在夢與現實之間,一邊作為一個擁有自由幸福、天真爛漫的孩子,一邊則是作為直面殘酷冷峻的戰爭現實、內心充滿強烈仇恨的英雄。夢與現實之間明顯的二元對立導致了伊萬最終的人格分裂。游離在夢與現實之中的伊萬變得瘋狂,伊萬在黑暗中變成戰爭中的狂人。對此,薩特對伊萬進行了深入解釋:“對于他們而言,清醒狀態下的噩夢與夜睡時的夢魘并沒有什么分別。他們被人殺,也要起來殺人,并開始習慣屠戮。他們唯一具有勇氣的決定,就是在面對這難受的苦痛中選擇仇恨和逃避。他們戰斗,并在戰斗中逃離這種恐懼。而一旦黑夜卸除他們的警備,一旦他們入睡,就又恢復了兒童的稚弱,這時,恐懼再次出現,而他們又重拾起想要忘卻的記憶。這就是伊萬。”[4]人們從前兩個夢境中對伊萬的同情開始轉為恐懼,這種“恐懼”便是人們對戰爭扭曲人性的理性思考,原本擁有美好童年的伊萬因戰爭變得殘忍與冷酷,在戰場上他是個英雄,然而在人性層面,他早已成為戰爭中復仇的機器。
淺談我國早期的電影檢查
摘要:中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檢查,經歷了從地方到中央的階段,取締了神怪武俠片,并出臺了中國第一部電影檢查法,在推動國產電影發展上做出了貢獻。
關鍵詞:電影檢查;神怪武俠片;電影法
民國初年,電影作為舶來品進入中國后并未受到檢查。當時的北洋政府抱著放任的態度,電影可以不經檢查自由映演。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支持在當時作為“新媒體”的電影的發展,而是無暇也無力顧及電影事業。
一、電影檢查的濫觴
中國最早的電影檢查始于1923年。當時的江蘇省教育會成立了一個審閱會,開始審查電影,但所用的標準非常簡單,主要有以下幾項①:1.確合教育原理,能與社會發生良好成績者,該影片得以加入會,經江蘇省教育會電影審閱委員會認可字樣,以寓表彰之意;2.通常影片但為營業關系,可無流弊者,本會不加可否;3.如確系有損風化,曾經本會勸告,未能改良者,本會當請官廳干涉。這種檢查主要還是看電影是否“有損風化”,如果有也只是以勸誡為主。這樣的尺度彈性非常大,也缺乏可操作性。江蘇省教育會在辛亥革命前是立憲運動的領導力量,在辛亥革命時期又是推動上海和江蘇地區光復的重要社團之一,有著很強的革命性,而電影的大本營是“十里洋場”的上海,所以由江蘇的這個組織來推行電影檢查也是歷史的必然。但檢查的成效不顯著,除了審查標準的問題,還因為1923年前后國產片的產量很小:1923年國產片僅有5部,1924年增加到16部,1925年為51部。當時上海的電影市場基本上是好萊塢電影的天下,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沒有能力對這些外片進行審查,也沒有力量對江蘇省教育會的電影檢查提供有力支持。加上這個審閱會組織不健全,檢查人員也都是教育界人士,對新興的電影藝術不甚了了,所以江蘇教育會的電影檢查很快以失敗告終。與江蘇省教育會幾乎同時,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教育部也頒布了電影檢查標準,共分兩款②。1.禁止或剪除者。包括四項內容:跡近煽動有妨治安者;跡近淫褻有傷風化者;兇悖暴亂足以影響人心風化者;外國影片中之近于侮辱中國及中國影片中之有礙邦交者。2.緩演或酌改者:情節離奇不合事理者;扮演惡劣易起反感者;意在勸戒而反近誘惑者;大體尚佳間有疵累者。這個標準就具體了一些,也不局限于風化問題,甚至上升到了兩國邦交的高度,但受政局變換的影響,隨著北伐的成功、中華民國北洋軍閥政府的垮臺,這一電影檢查也不了了之了。這一時期,電影檢查沒有實質性的成果,算是電影檢查的濫觴。
二、取締神怪武俠片和第一部電影檢查法的出臺
早期城市電影管理論文
“在波德萊爾那里,巴黎第一次成為抒情詩的題材。他的詩不是地方民謠;這位寓言詩人以異化的眼光凝視著巴黎城。這是游手好閑者的凝視。”1這是上個世紀30年代,德國思想家本雅明對早他70年而生的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描述,這描述是如此適用于本雅明的同時代人——中國電影導演孫瑜,以至于只需把巴黎換成上海。在中國電影界,孫瑜同樣被譽為詩人,只是他用電影膠片寫詩,1934年孫瑜在一篇題為《我可以接受這“詩人的桂冠”嗎》的文中說,“假如那一頂桂冠是預備賜給一個‘理想詩人’的,他的眼睛是睜著的,朝前的,所謂他的詩——影片——是充滿朝氣,不避艱苦,不怕謾罵,一心把向上的精神向頹廢的受苦的人們心里灌輸,……我是極盼望那一頂‘詩人的桂冠’,愿意永遠地愛護它!”2
中國電影誕生于1905年,最初20年以雜耍的姿態摸索前進,題材集中于神怪武俠和家長里短。中國現代都市(主要指上海)則崛起于20年代資本主義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縫隙,30年代初剛剛浮出海面。在這種背景下,孫瑜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通過《野玫瑰》(1932)、《天明》(1933)和《體育皇后》(1934),對現代都市上海進行的意味深長的凝視,即便不是第一次,也是最早一批以上海為抒情詩題材的創作。而考慮到一•二八淞滬抗戰后,電影界日益左傾和抗戰主題日盛,孫瑜對上海的凝視更顯得格外有意義,因為,這些尚未過渡到階級主題和抗戰主題的都市電影,是研究中國現代性問題的最佳標本,它們記錄了現代性初臨中國的歷史,也記錄了中國知識者面對現代性的復雜心態。
1、城市、電影與震驚:用現代性的方式表現現代性
作為學術話語的“現代性”在中國被提起,已有十多年的歷史,盡管學界普遍感覺要給這個貌似簡單實則涵義復雜的概念下個定義是件非常困難的事,但是熱烈討論之后,學界還是達成了如下共識:“現代性從西方到東方,從近代到當代,它是一個‘家族相似的’開放概念,它是現代進程中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層面的矛盾和沖突的焦點”,換句話說,現代性是“現代這個歷史概念和現代化這個社會歷史過程的總體性特征”。3
什么是現代與古代的最大區別?或者說,現代化的最大標志是什么?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有很多,但相信沒人會否認“城市和城市化”在其中的分量。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化就是城市化,城市是現代社會最龐大最醒目的標志!城市是現代民主政治和民族國家的基礎,是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和產物,是現代工具理性的滋生地和競技場,是所謂現代文明的展覽館和集散地。一句話,城市是現代進程中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層面矛盾和沖突的集中體現。因此,當三十年代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都市突然崛起在太平洋的西岸時,現代性也就同時被打包帶來。
對進入城市或者生活在城市中的個體來說,“震驚”可謂城市這個現代性的龐然大物給他們的最大體驗。“震驚”抑或“驚悸”從詞源上來說是一個很早就有的普通的詞匯,它變得別有意味源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其《超越唯樂原則》(又譯《超越快樂原則》)一書中提到一種“創傷性神經癥”,認為構成其病因的“主要是驚愕和驚悸的因素”,所謂“驚悸”是“一個人在陷入一種危險時,對這種危險毫無思想準備”情況的描述。4“驚悸”即“震驚”這一弗洛伊德的醫學術語,被本雅明拿來用在波德萊爾身上,認為“震驚屬于那些對波德萊爾的人格有決定意義的重要經驗之列”,“波德萊爾把震驚經驗放在了他的藝術作品的中心”。5然而隨即,本雅明就意識到,波德萊爾的這種“震驚”體驗并不屬于他個人,而是人們對現代都市的普遍體驗。他認為十九世紀中葉的革新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手突然一動就能引起一系列運動,他舉了電話和照相機的例子,并認為“照相機賦予瞬間一種追憶的震驚”,而“這類觸覺經驗同視覺經驗聯合在一起,就像報紙的廣告版或大城市交通給人的感覺一樣”——什么樣的感覺呢?“在這種來往的車輛行人中穿行把個體卷進了一系列驚恐與碰撞中。在危險的穿越中,神經緊張的刺激急速地接二連三地通過體內,就像電池里的能量”。6毋庸置疑,本雅明對19世紀60年代巴黎生活的描述,融會了他自身對現代都市的感受,而這感受也完全適用于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或許這就是為什么當時的上海被稱為東方巴黎的原因吧。
張藝謀早期電影中紅色悲劇探討論文
張藝謀的《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無一不展示了他對紅色的摯愛。他曾坦言:“影片中的紅色是他最為喜歡的。”但他卻一反紅色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的象征意義,紅色是我國文化中的崇尚色,它體現了中國人在精神和物質上的追求。紅色象征了吉祥、喜慶和幸福,而在張藝謀的影片中紅色卻被賦予了神秘、凄涼和反抗的意義。張藝謀用吉祥的紅色為我們營造了一個個人間悲劇,人物的悲劇在一片紅色中展開,又在一片紅色中落幕。張藝謀的影片充滿了悲劇,悲劇在他的影片中達到了極至,他早期的影片反復的渲染著這一基調,男性的襯托悲劇、女性的愛情悲劇、專制者的命運悲劇。他給影片中所有的人都打上了標簽。這些人在悲劇中掙扎,在悲劇中抗爭,最終在悲劇中消亡。悲劇成為其影片的主旋律,一切人物的活動都是為了突出他的主旋律悲劇。
張藝謀影片中的紅色寓言
《紅高粱》中的九兒被火紅的喜轎抬回了十八里坡。火紅的轎子、紅紅的嫁衣、無一不體現了喜慶和吉祥,但在奶奶九兒的眼里這些火紅的顏色與象征死亡的白色沒有什么區別。她是在父親的逼迫下嫁給麻風病人李大頭的,嫁入十八里坡對奶奶來說無疑走向了死亡。無奈的九兒在父親的眼里竟然抵不過李大頭的聘禮,九兒的心里充滿了恐懼、無奈和痛苦。所以在轎把式戲弄式的顛轎下發出了她壓抑已久的哭聲,這哭聲充滿了抗爭、不平。片中特意交代了爺爺的身份,他是唯一被雇來的轎把式,他年輕、健壯充滿了活力。這與奄奄一息的李大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有意的戲弄奶奶激發了奶奶抗爭的哭聲,哭聲在十八里坡的野高粱地里回蕩。畫面在紅高粱的襯托下顯的更為壯觀,火紅的高粱地絲毫沒有給人以喜慶祥和。相反,它給了人一種神秘和恐怖。《紅高粱》對紅色的使用可謂是張藝謀所有作品中最登峰造極的一部作品。影片中的紅高粱、高粱酒無一不給人滿眼的紅色。但這些紅色的使用卻更多了神秘、反抗、凄涼。來源于公務員之家/
當日本人的鐵蹄走進這片紅色的土地時,影片更是為我們展示了紅色的血腥。血紅的牛皮被日本人當成了向中國人示威的工具。血跡順著牛皮一滴滴地流了下來。正當我們為這一切驚嘆的時候,一向罪惡深重的土匪頭子三炮卻成了第一個起來反抗的英雄。在民族面臨危險的時候無論你以前干過什么,但民族的召喚都是讓你為它付出你的所有。影片中高粱地的人們也為我們證明了這一點。日本人的殘暴激怒了這火紅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屠夫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成了行刑的兇手,但他最終選擇了反抗。他的血不斷的流淌著,滋潤這片土地,更滋潤著人們的心,而羅汗大哥的死最終激起了人們的反抗意識。“紅紅的血跡”、“冰涼的子彈”為我們營造了一場動人心弦的紅色悲劇。奶奶是從火紅的十八里坡嫁進來的,她大膽的與爺爺野合。奶奶生活的所有轉折點都與這紅高粱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影片的結尾處她倒在了象征她一生悲劇的高粱地里,在這里紅色再一次被張揚起來,那刺人心痛的紅色與奶奶九兒的命運形成了完美的契合,而在結尾處張藝謀設計了日全食這個意象再次為我們突現了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并再一次升華了影片中的紅色意象。《紅高粱》這部影片折射了太多的血腥和凄涼。
《菊豆》講述的是江南某農村染坊老板楊金山出于傳宗接代的目的而續娶了年輕的菊豆為妻。染坊內掛滿了紅色的染布,但這里卻上演著另外一場人間悲劇。年邁的楊金山為了傳宗接代,他沒日沒夜的折磨著菊豆。菊豆在似人非人的生活中苦苦的掙扎,菊豆對于楊金山來說只是一具生兒育女的肉體。絲毫沒有做人的尊嚴,長時間的掙扎和沉淀最終讓她選擇了楊天青,而菊豆對楊金山的恨卻絲毫沒有減退,楊金山也不斷的利用他專制者的身份折磨著她。他們的婚姻關系完全是建立在相互折磨的基礎之上的。正像前一組鏡頭中出現的那個晚上一樣楊金山把菊豆綁在椅子上,說道:“老子花錢了,得聽老子的,買了牲口,要踢要打隨老子的脾氣,你算個什么。一樣,聽話吧,生個兒子。我給你當牛做馬。不聽話,我抽死你。”正是這種絲毫沒有尊嚴的生活,強烈的激發了菊豆的怒火。當她第一次與天青偷情的時候,畫面上出現了整批的紅色染布被降到了染池之內。紅色的染布緩緩地落了下來,紅布的墜落象征了以楊金山為首的專制者的沒落。它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因果報應,正是由于金山的毫不尊重、殘酷的對待這個可憐的女人,才最終激怒了她。她要將一切銷毀,她要把金山負在她身上的一切枷鎖都扔掉。她成功的用自己的身體報復了楊金山,但兒子的出生給了這個悲苦的女人更大的不幸。他是菊豆與天青畸形愛情下的產兒,他的出生被賦予了更大的悲劇,楊金山的恥辱、天青的無奈、菊豆的悲痛以及自己的弒父悲劇。他的成了這部影片最大的悲劇,整部影片楊天白沒有一句臺詞,但他的眼神,他的行動無一不體現了他的憤怒和無助。他成了一個弒人的魔鬼整部影片他都在凝重的氣憤之中,他唯一的一次笑容是楊金山被他誤殺之后。他看著在染池里掙扎的楊金山時,才露出了久違的笑容。他就像一個魔鬼只有看到血腥才會露出微笑。這部影片雖然不像《紅高粱》那種把紅色做為背景,但《菊豆》中紅色的染布和染池又一次展示了張藝謀影片中的“血腥之紅”。紅色在這里重新被賦予了憤怒、報復和血腥。故事的一切轉折點都沒有離開這讓人壓抑的紅染坊“血腥之紅”再一次被推向了高潮。紅色的染池成了殺人的魔窟,楊金山和楊天青先后被殺于這紅色的染池之內,而痛失天青的菊豆一把火燒了這禁錮了她一生的牢籠。楊家的染坊在紅紅的火蛇吞噬下化成了灰燼,大染坊的毀滅表現了封建倫理綱常的毀滅,以及它對人性的摧殘。《菊豆》中張藝謀又為“紅色”賦上了復仇的意象。
如果說《紅高粱》是張藝謀影片對紅色的探索,那么《菊豆》則是張藝謀用點概面對紅色進行了獨特的使用,而《大紅燈籠高高掛》卻是張藝謀對紅色解讀的成熟表現。張藝謀再次用別樣的方式表達了他對紅色的獨特認識。紅燈籠是我國的吉祥物,只有逢年過節的時候才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但陳家大院的紅燈籠卻成了殘酷、地位、無情的象征。陳家大院神秘莫測的深灰色建筑,高高的圍墻、恐怖的角樓、陰深的甬道、使整座大院與世隔絕。一種恐怖感始終懸在觀眾的心頭,壓抑的喘不過氣來。低垂的鉛灰色天空下,眾多的受害這之間相互傾扎、互相殘殺。妻妾、妾仆之間的仇恨與院子里的大紅燈籠形成了強烈的視覺沖擊。紅色在這座古老的大院里被賦予了新的色彩。它成了權利、地位的象征。在這個古老而寂靜的大院里只有點上紅燈籠的女人才有資格享受老爺的寵愛,才會被人尊重。在這個冷酷的世界里,沒有溫情、沒有希望,只有各房姨太太之間的爭奪。來源于公務員之家/
電影文化現代性研究論文
摘要:《銀幕艷史》是一部具有自指性白話現代性質的紀錄劇情片,也是記錄了中國早期電影和觀眾結構及其轉變的范例。從性別的角度檢視身體和電影科技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從女演員的銀幕形象和影迷文化所體現出來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發現,中國早期電影是由媒體傳導的、具有白話性或通俗性的一種現代體驗,女明星的身體是中國20世紀早期現代性的體現。
關鍵詞:《銀幕艷史》;白話現代性;身體;視覺研究
AdventureofAnAmorousFilm2Star
———FemaleStarsasEmbodimentoftheVernacularExperienceinChineseEarlyFilmCulture
(DepartmentofFilm&MediaStudies,NewYorkUniversity,NY10012,USA)
Abstract:Asadocumentaryfeaturefilmcharacteristicofself2exposeandvernacular2modernity,AdventureofAnAm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