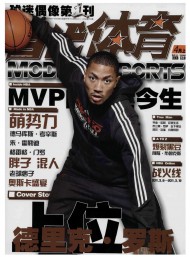周星馳范文10篇
時間:2024-04-19 03:06:10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周星馳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周星馳電影《功夫》的視聽語言分析
摘要:本文從視聽語言元素出發分析電影《功夫》。導演用了許多非常規手法拍攝的創意性鏡頭,運鏡風格有“古靈精怪”之感,創造力十足。其次,帶關系鏡頭拍攝和多樣蒙太奇的剪輯手法在拉出人物關系的同時拓展了電影的時空維度。致敬經典、領先觀眾的創作技巧以輕松詼諧的格調言說底層人物的俠肝義膽。臺詞、音樂和武術動作無不彰顯出傳統武術文化和嶺南文化的精髓,讓觀眾在捧腹大笑中體會草根人物的悲歡喜樂。
關鍵詞:《功夫》;視聽語言;草根人物
電影《功夫》是香港著名導演周星馳執導拍攝的一部經典喜劇片。影片講述了不學無術的混混阿星一心想加入第一大黑幫斧頭幫,在斧頭幫急欲鏟平唯一未收入勢力范圍的地頭中邂逅了一群生活在豬籠寨的隱士俠客,阿星在歷經正邪對抗之后最終成長為一代武術家的故事。導演運用一系列夸張搞怪的鏡頭營造出別樣的武俠世界,詮釋了正邪不兩立的俠義精神和功夫情結。
一、視聽元素的應用
(一)帶關系拍攝鏡頭分析。《功夫》中有多個帶關系拍攝鏡頭,尤其是長鏡頭的使用,意在拉出人物關系、交待環境背景。這種鏡頭的使用在考驗導演拍攝功底的同時也突出了周星馳的場面調度能力。下文就電影中的幾個經典場景進行分析。一是長鏡頭的使用拉出人物關系。開場鏡頭定位在局長臉上,再拉出來帶出警察局環境和人物位置的關系。鏡頭一直上移落到牌匾上,接著人入畫切背拍,簡短的55秒干凈利落。第二個經典長鏡頭是在三位隱姓埋名的高手離開時,一段時長38秒的鏡頭展示豬籠城寨市井生活的長鏡頭調度。從跟拍包租婆沿走廊下樓和劇中角色醬爆走五五位,接著包租婆演員走位,一個人面對眾人顯示她的強勢,鏡頭繼續推,改變景別,引出三個高手;橫移過來前置醬爆,和包租婆構成縱深。這一個長鏡頭從高到低然后跟隨人物走橫移,一氣呵成,給觀眾帶來連貫順暢的觀影體驗。二是帶關系拍攝。在鱷魚幫大佬欺負完警探后,鏡頭隨著大佬前推,預示著前方肯定有某種事物出現。特寫下移,鏡頭十分靈活,全運動鏡頭一推一拉形容斧頭幫人多勢眾,鏡頭移過來帶上側面群演。這些鏡頭的運用不僅輕松地交代了環境背景布局,拉出人物位置關系,還構造出縱深關系,如琛哥拿斧頭過來形成縱深三層景深:琛哥、鱷魚幫大佬和斧頭幫嘍啰,畫面瞬間有了層次縱深感。同樣,在包租公出場鏡頭中,前置包租公喝酒畫面,后置阿鬼揉面背景也形成了縱深格局。(二)蒙太奇手法的使用。蒙太奇借由建筑學術語的構成裝配引用到電影中,《功夫》多次使用平行蒙太奇和隱喻蒙太奇以及心理蒙太奇手法,通過不同鏡頭的剪輯和組接拓展了電影的時空自由度,帶給觀眾不同于現實生活的時空感。一方面彰顯了周星馳導演技巧的高超,另一方面也展示了電影畫面非同尋常的時空感。一是平行蒙太奇的使用。開場斧頭幫老大跳舞和斧頭幫殺人放火的兩組場面交叉同時進行,以凝練的敘事和鏡頭語言,交代了斧頭幫罪惡的積累。同時跳舞的人員越來越多也暗示了斧頭幫勢力逐步壯大。這組平行蒙太奇的敘事技巧,在讓觀眾處在荒誕的喜感之中又深切感受到惡勢力的恐怖、瘋狂和極端。二是隱喻蒙太奇的使用。電影開場由一只蝴蝶帶出“功夫”兩個大字,一來暗示正片人物化蛹成蝶的蛻變劇情;二來也用以小見大的方式,配上磅礴的音樂把觀眾代入一個充滿神秘感的世界。后面劇情中再次出現破繭重生的畫面隱喻混混阿星起死回生、棄惡從善。第三組鏡頭是星爺打劫啞女用刀威脅的動作姿勢和背景墻上掛的電影海報《禮貌》場景如出一轍,一來交代電影背景,二則預示星爺和啞女美好的結局。三是心理蒙太奇的使用。混混阿星受斧頭幫老大琛哥委托去精神病院救出火云邪神,當他突破重重關卡后來到了病房前的走道時,突然從盡頭的門后涌出了洪水一般的血水,但這一切都是星爺自己的心理活動和心理幻想。作為電影中心理描寫的刻畫手段,從而凸顯出門內人物的威脅性和星爺的恐懼心理,通過幻想和心理活動來烘托氣場氛圍。(三)致敬經典。電影中多次出現了向經典電影和經典人物的致敬,其中包括臺詞、動作、場景的構建等,這充分說明了周星馳導演的深厚電影知識儲備和融會貫通的學習實踐能力。這些致敬鏡頭貼合電影故事情節的同時也調動了觀眾的別樣情懷和記憶,可謂一舉兩得,應用得十分成功。致敬1:影迷觀眾看到救火云邪神的場景,周星馳想象著大門開啟時鮮血如潮水般涌出的鏡頭,是來自庫布里克的名作《閃靈》。周星馳在此刻借鑒,不僅是“惡搞”,致敬的情節能貼合自己電影本身的氛圍,更是難能可貴。致敬2:當火云邪神上位后,帶領斧頭幫圍剿豬籠城寨時,所有人堵在一個房間的門口,當大家以為周星馳要走出來時,在緊張的氛圍之下,周星馳卻從另外一個房間走出。這段致敬來自《沉默的羔羊》,此刻的借鑒利用觀眾的情緒變化,由緊張到期待,再到長舒一口氣,這種拿經典段落為我所用營造出的喜劇感,不可謂不高明。致敬3:電影打戲動作設計干凈果斷致敬李小龍;星爺最終打戲的白衣黑褲造型是在致敬李小龍;包租婆用手勢比劃威脅琛哥的動作是在致敬李小龍電影《猛龍過江》;結尾處小孩舔棒棒糖流鼻涕的形象致敬的是李小龍兒時的造型。(四)領先觀眾。電影中多次利用聲畫關系給觀眾帶來出乎意料的感覺,處處領先觀眾,帶來先人一步的高超感。混混阿星和嘍啰被抓住后利用開鎖技能解開了手銬,斧頭幫老大琛哥向手下伸手動作讓觀眾原以為是想拿斧頭砍阿星,結果卻只是點煙反而放走了星爺;另一組鏡頭是聲音先入,阿星在受重傷后躲入街頭的信號箱里療傷,先出現揮拳擊打的聲音,而后人物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處處領先。琛哥觀看天殘地缺武斗卻被包租公包租婆打敗后叫司機趕緊開車逃路時,包租婆包租公早已坐進車內,領先觀眾一步。(五)臺詞的精妙應用。周星馳電影中人物的臺詞設計充滿了無厘頭,幽默十足的同時恰如其分地契合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折射出對現實社會的思考。《功夫》中天殘地缺臺詞“一曲肝腸斷,天涯何處覓知音”,改編自“一曲肝腸斷,輕羽此去莫留連,更有南國花正好”,這句話既暗示了聾人和盲人的殺人手法,用琴聲殺人,又暗示他倆武功高強,天涯何處覓知音,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感覺。鐵線拳回答聾人問詢布料的藝術成分說,有三四樓那么高,包括前面買衣服在后面都有隱喻,暗指包租公和包租婆住在三樓,最終他們是被這對夫妻打敗的。最終天殘地缺被包租婆的獅吼功打得衣不蔽體都在臺詞里有精妙的暗示。(六)音樂的應用。一是民族性。電影的配樂選用了以《東海漁歌》《十面埋伏》《四川將軍令》為代表的民族音樂作品,極具民族性。《東海漁歌》舒緩輕柔的節奏被應用到豬籠寨的生活場景,描繪出寨子里人們生活的隨性安逸。聾人、盲人對打鐵線拳和阿鬼時,用中國古典樂器古琴作為戰斗媒介,并演奏了黃華英的名曲《箏鋒》,改編自琵琶曲《霸王卸甲》中的高潮部分,殺戮之氣躍然紙上。整場打斗都是和聲波在戰斗,無形勝有形。二是經典性。不論是民族音樂《十面埋伏》《闖將令》等還是西方經典曲目《流浪者之歌》《馬刀舞曲》,都是不同時代中西方音樂中的代表作,擁有良好的群眾基礎。《流浪者之歌》小提琴的快節奏配合包租婆追趕阿星的運動畫面,節奏輕快緊扣畫面。《馬刀舞曲》應用在主人公去精神病院搭救火云邪神的一系列場景中,舞曲的高強節奏感和緊密的旋律結合救人過程的驚險刺激極大提升了畫面的張力和表現力,引人入勝的同時又驚險萬分。
二、《功夫》電影中的傳統文化
周星馳電影粗鄙語言分析論文
【內容提要】
粗鄙語言的運用為周星馳電影的一大特色,然而往往為評論者所忽略。本文主要通過對周星馳電影中粗鄙語言的特點分析和來源的分析,結合巴赫金和福柯的理論論述了周星馳電影中粗鄙語言的深層意義。
【關鍵詞】粗鄙語言狂歡權力話語解構
周星馳的系列電影以其強烈的反叛性和顛覆性而受到青年一代的歡迎,從總體上看來,貫穿其電影始終的一個總體精神就是對一切成規的解構。他的電影中的故事情節、畫面設置、對話設計、音樂使用等都具有解構性,這些各種因素又合成一股力量,直接沖擊銀幕前的觀眾。而“粗鄙語言”在周星馳電影中的運用,與其它的因素是結合在一起的。它在周星馳的電影中有其深刻的文化意義。本文將就此現象展開論述。
一
可以說任何人觀看周星馳的電影都會強烈地感受到,不論在什么場景中,只要能用上粗鄙語言,周星馳電影都會用上。它們有參與解構的作用,同時也會對人物的塑造有所幫助。那么,周星馳電影經常會運用一些什么樣的“粗鄙語言”呢?首先是人體的排泄物;其次是與性有關事物,經常用隱喻性和指涉性器官的語言來表達;再次是民間的罵人句子的直接引入(雖然也經常與性有關,但是還是可以把它單獨列出來)。仔細分析,其實這三個方面是統一在一起的,即都與人體的下半身有關,都與解構的主題或者是人物有關。
周星馳電影無厘頭分析論文
對于周星馳的討論似乎只能從“無厘頭”開始,盡管這可能已經成為時下最為流俗的俗套,可是,很多時候,要想直抵事實的真相,就真的不能免俗。對于這一點,周星馳本人恐怕也是深有會心吧!
一
平心而論,在周星馳之前,有誰想到,電影竟然可以這樣拍攝!看吧!嘔吐,奶白色的液體自口中汩汩而出,甚至發生在接吻的緊要關頭(《情圣》);衣冠楚楚的一群人器宇軒昂的闊步前進,忽然遇到刁難者在電梯門前拉屎撒尿(《食神》);為了掩蓋罪行可以當眾喝光精液(《逃學威龍》);誤服春藥的老尼姑看見形似陰莖的柱狀物就瘋狂地追逐(《鹿鼎記•神龍教》);機器人李澤星的生殖器是可以噴水的蓮蓬頭,他面不改色的握著它當著男女學生的面對著花朵像灌溉一樣撒尿(《百變星君》);皇帝的內褲可以醫治不孕不育,而包龍星因為說錯了話只好將一把明晃晃的長劍硬生生地吞掉(《九品芝麻官》);還有那些振振有辭的東扯西拉和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以及那三聲標志性的虛張聲勢的狂笑“哈——哈——哈”,因為得意、沮喪、恐慌、狂喜,或者僅僅是為了讓你莫名其妙。
“他”(周星星、阿星、星星、星、李澤星、包龍星、史蒂夫星等等)肆無忌憚地在確保生活現實性的邏輯分界線兩邊穿梭往返,厚顏無恥,像個小丑那樣逗人發笑。然而,“他”絕不是馬戲團平面化的小丑,“他”有著深刻的生存之痛!雖然“他”總是大言炎炎,張牙舞爪,可是,“他”永遠作為一個“小人物”被塑造。冥冥中似乎總有宿命的力量為“他”量身定造生存之障,“他”總是無可奈何的被投入混亂的災難渦流。一切生活場景對“他”而言都必然陷阱密布,危機四伏,小到尖釘扎腳,大到粉身碎骨。可是,“他”究竟觸犯了何等天條而必遭不幸?究竟是什么樣的結構性力量造成了小人物如蛆附骨般的生存困擾?
如果不能滿足于泛泛的抽象性概括,那么,考察“他”遭受困厄的原初社會文化場景中經由霸權話語塑造的英雄譜系可能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誠然,李玉和、郭建光、楊子榮式的人物從來都不是基于自由市場的香港以及同質于香港的社會文化系統建構自身的能指形象,可是,這決不意味著香港是一個逾越了規訓原則的武陵源、烏托邦!
“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的每一句話都將成為呈堂證供!”
周星馳無厘頭電影風格論文
摘要:周星馳經過二十多年的電影生涯,已經逐漸演變為香港無厘頭喜劇的代名詞,他的無厘頭喜劇根植于香港東西方夾縫中掙扎而成的“無根情懷”,在香港傳統喜劇的基礎上,又自成風格,用滑稽夸張的動作和顛狂的語言,形成了一種娛樂的狂歡。
關鍵詞:無根情懷顛狂狂歡
世界上的電影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周星馳的電影,一種是沒有周星馳的電影。當無數的星迷開始用這樣的標準來劃分電影類型的時候,電影明星周星馳對于電影的影響可見一斑。
周星馳風格的形成,離不開香港本土特有的社會文化土壤,在東西方夾縫中掙扎的香港文化促成了香港人特有的無根情懷,而周星馳無厘頭的喜劇風格就是根植與這樣的文化土壤。
無根情懷的土壤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周星馳幾乎成了香港喜劇的代名詞,他所特有的喜劇風格使得“無厘頭”這樣的一個名詞真正進入了喜劇的世界,同時也進入了觀眾的視野,并且成為喜劇中最有代表性同時也最具有香港特色的一支。“無厘頭”原是廣東佛山等地的俗語,意思是一個人做事、說話都令人難以理解、無中心,其言語和行為沒有明確的目的,粗俗隨意,亂發牢騷,莫名其妙,但并非沒有道理。轉嫁到電影中的無厘頭,便成了“惡搞”的代名詞。
周星馳電影粗鄙語言分析論文
【內容提要】
粗鄙語言的運用為周星馳電影的一大特色,然而往往為評論者所忽略。本文主要通過對周星馳電影中粗鄙語言的特點分析和來源的分析,結合巴赫金和福柯的理論論述了周星馳電影中粗鄙語言的深層意義。
【關鍵詞】粗鄙語言狂歡權力話語解構
周星馳的系列電影以其強烈的反叛性和顛覆性而受到青年一代的歡迎,從總體上看來,貫穿其電影始終的一個總體精神就是對一切成規的解構。他的電影中的故事情節、畫面設置、對話設計、音樂使用等都具有解構性,這些各種因素又合成一股力量,直接沖擊銀幕前的觀眾。而“粗鄙語言”在周星馳電影中的運用,與其它的因素是結合在一起的。它在周星馳的電影中有其深刻的文化意義。本文將就此現象展開論述。
一
可以說任何人觀看周星馳的電影都會強烈地感受到,不論在什么場景中,只要能用上粗鄙語言,周星馳電影都會用上。它們有參與解構的作用,同時也會對人物的塑造有所幫助。那么,周星馳電影經常會運用一些什么樣的“粗鄙語言”呢?首先是人體的排泄物;其次是與性有關事物,經常用隱喻性和指涉性器官的語言來表達;再次是民間的罵人句子的直接引入(雖然也經常與性有關,但是還是可以把它單獨列出來)。仔細分析,其實這三個方面是統一在一起的,即都與人體的下半身有關,都與解構的主題或者是人物有關。
周星馳無厘頭電影風格分析論文
摘要:周星馳經過二十多年的電影生涯,已經逐漸演變為香港無厘頭喜劇的代名詞,他的無厘頭喜劇根植于香港東西方夾縫中掙扎而成的“無根情懷”,在香港傳統喜劇的基礎上,又自成風格,用滑稽夸張的動作和顛狂的語言,形成了一種娛樂的狂歡。
關鍵詞:無根情懷顛狂狂歡
世界上的電影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周星馳的電影,一種是沒有周星馳的電影。當無數的星迷開始用這樣的標準來劃分電影類型的時候,電影明星周星馳對于電影的影響可見一斑。
周星馳風格的形成,離不開香港本土特有的社會文化土壤,在東西方夾縫中掙扎的香港文化促成了香港人特有的無根情懷,而周星馳無厘頭的喜劇風格就是根植與這樣的文化土壤。
無根情懷的土壤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周星馳幾乎成了香港喜劇的代名詞,他所特有的喜劇風格使得“無厘頭”這樣的一個名詞真正進入了喜劇的世界,同時也進入了觀眾的視野,并且成為喜劇中最有代表性同時也最具有香港特色的一支。“無厘頭”原是廣東佛山等地的俗語,意思是一個人做事、說話都令人難以理解、無中心,其言語和行為沒有明確的目的,粗俗隨意,亂發牢騷,莫名其妙,但并非沒有道理。轉嫁到電影中的無厘頭,便成了“惡搞”的代名詞。
無厘頭電影風格管理論文
摘要:周星馳經過二十多年的電影生涯,已經逐漸演變為香港無厘頭喜劇的代名詞,他的無厘頭喜劇根植于香港東西方夾縫中掙扎而成的“無根情懷”,在香港傳統喜劇的基礎上,又自成風格,用滑稽夸張的動作和顛狂的語言,形成了一種娛樂的狂歡。
關鍵詞:無根情懷顛狂狂歡
世界上的電影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周星馳的電影,一種是沒有周星馳的電影。當無數的星迷開始用這樣的標準來劃分電影類型的時候,電影明星周星馳對于電影的影響可見一斑。
周星馳風格的形成,離不開香港本土特有的社會文化土壤,在東西方夾縫中掙扎的香港文化促成了香港人特有的無根情懷,而周星馳無厘頭的喜劇風格就是根植與這樣的文化土壤。
無根情懷的土壤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周星馳幾乎成了香港喜劇的代名詞,他所特有的喜劇風格使得“無厘頭”這樣的一個名詞真正進入了喜劇的世界,同時也進入了觀眾的視野,并且成為喜劇中最有代表性同時也最具有香港特色的一支。“無厘頭”原是廣東佛山等地的俗語,意思是一個人做事、說話都令人難以理解、無中心,其言語和行為沒有明確的目的,粗俗隨意,亂發牢騷,莫名其妙,但并非沒有道理。轉嫁到電影中的無厘頭,便成了“惡搞”的代名詞。
影視幽默語言修辭藝術
電影也稱之為映畫,它是一種現代藝術,也是一種綜合藝術,包含文學戲劇、舞蹈、文字等多種藝術。電影具有恐怖、動作、犯罪、喜劇、愛情、武俠等多種類型,而周星馳的眾多搞笑電影堪稱喜劇之最,在他的影片中,我們不僅被無厘頭式的風格所吸引,也從中看到了社會的現實面。他用詼諧幽默的語言讓我們仰天長笑,也用電影中許多社會底層的平民角色給我們呈現了社會生活中最真實的一面。本文將通過對周星馳電影幽默語言修辭藝術的分析,反映出中國電影幽默語言的魅力所在,從而反觀社會現實,弘揚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及勇敢追求的情感觀念。
一、電影及其修辭藝術
(一)電影的幽默語言
周星馳的眾多搞笑電影堪稱喜劇之最,他的電影之所以能讓觀眾笑得酣暢淋漓,其中大多歸功于其語言的幽默性。幽默語言的產生不僅依賴于語言自身的內在規律,也依賴于語境。
(二)幽默語言的修辭藝術
我們從微觀的角度分析藝術修辭,它包括綜合運用多種辭格,靈活地選擇句式以及詞語錘煉的個性化。觀看周星馳的電影,它里面的語言給我們帶來的是強烈的新鮮感,其使用也具有創造性。電影通過無厘頭式風格的表述,引人人勝,更創下票房佳績,而綜合運用多種修辭手段則是呈現這一景象的重要途徑。修辭手法包括夸張、仿擬、反復、比喻、頂真以及其他一些生僻辭格如降用、拈連、同異、呼告、示現等。辭格通常情況下是綜合運用的,一般有連用、套用和兼用幾種形式,它是對語言表述進行的特定的藝術加工。辭格讓人們的語言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失去辭格的幽默語言電影將會暗淡無光。辭格的運用在我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如文學作品、電影、廣告等,而周星馳的眾多電影中也運用了多種辭格,夸張便是其電影語言中的一種代表。夸張包括內容以及形式上的夸張,在《:趕話西游》中,噦嗦的唐僧更是將語言的夸張發揮得淋漓盡致,顛覆了傳統中的唐僧形象,令人們嘆為觀止。句式的選擇也被看做是修辭手段的一種,它必須按照特定的模式去規劃、組織,這個模式便被稱之為句式。它包括排比旬、命令句、判斷句、被動句等,同樣的詞語,由不同的句式組織在一起便會風格迥異。在不同的情景下,靈活地選擇句式,不僅可以增強語言的感染力,也可以強化情感色彩。在周星馳的《九品芝麻官》中,運用了散句的特點,長短參差不齊,使整句和散句交錯綜合,獨特新穎。詞語錘煉作為我國一門傳統的修辭藝術,它追求的是整齊均勻、準確精練以及鮮明色彩等,然而,為凸顯其個性化,常常需要打破常規。周星馳便創造出無厘頭式的電影風格,使語言環境及語言色彩陌生化,如《越光寶盒》中,為制造幽默,將牛魔王與上帝放在了一起,在觀眾覺得滑稽荒誕的同時,無厘頭式的幽默感也油然而生。
狂笑小品---星爺vs本山
狂笑小品---星爺vs本山
周星馳vs趙本山
韓學生:各位觀眾,各位聽眾,海外僑胞們,港澳同胞們,中秋節剛過,我給大家拜個晚年。可能有的觀眾剛剛打開電梯,這里是無厘頭衛視一套的《娛樂動態》節目,我是主持人老韓,據可靠消息,大陸巨腕趙本山和香港大哥級的無厘頭巨匠周星馳正在拍一部投資5億美金的大制作《功夫老根》。今天我把這兩位超級大腕請到了直播室跟大家交流交流,有請兩位嘉賓。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音樂起,周星馳上)
周星馳:各位大哥們好嗎?天氣好冷呀,有沒有多穿件衣服呀?
(趙本山上)
電影間隔效果管理論文
【摘要題】導演藝術
【正文】
在對當代電影的審讀中,筆者認為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與布萊希特的陌生化理論有著觀念上的相近、實踐上的相似和精神上的相通之處。筆者以為將角色的陌生化和時空結構的改變,是布萊希特陌生化理論的兩個主要方面,同樣可以用來闡述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
A:布萊希特的陌生化理論
著名的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的戲劇理論是同傳統的戲劇理論直接對立的產物:傳統的戲劇理論要求演員消失于角色之中,觀眾與劇中人一體化,追求共鳴效應。而布萊希特所建立的戲劇樣式則強調演員與角色保持距離、觀眾與劇中人保持距離、以驚愕和批判來代替共鳴。這種徹底的反叛具體化為藝術原則和藝術方法時,便是布萊希特所說的陌生化效果(Verfremdungseffekt)。Verfremdung在德語中是一個非常富有表現力的詞,具有間離、疏離、陌生化、異化等多重涵義。布萊希特用這個詞首先意指一種方法,然后才指這種方法的效果。它作為一種方法主要具有兩個層次的含義:1.演員將角色表現為陌生的;2.觀眾以一種保持距離(疏離)和驚異(陌生)的態度看待演員的表演或者說劇中人。布萊希特為陌生化方法下過一個簡潔的定義:“陌生化的反映是這樣一種反映:對象是眾所周知的,但同時又把它表現為陌生的。”(注:《布萊希特論戲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然后他強調陌生化的對象是社會動作:“陌生化效果的目的,在于把事件里的一切社會動作陌生化。”(注:《布萊希特論戲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把社會動作陌生化又使美學具有了社會學意義,使觀眾通過戲劇呈現的可變的現實來培養自己批判現實和改造現實的能力:“必須把觀眾從催眠狀態中解放出來,必須使演員擺脫全面進入角色的任務。演員必須設法在表演時同他扮演的角色保持某種距離。演員必須對角色提出批評。演員除了表現角色的行為外,還必須能表演另一種與此不同的行為,從而使觀眾作出選擇和提出批評。”(注:《布萊希特論戲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演員和角色之間的距離和觀眾與演員之間的距離必須破除舞臺上發生的一切是“正在進行的生活”這一幻覺,從而推翻“第四堵墻”,消除戲劇在以往所具有的魔幻作用。與亞里士多德式戲劇強調“動之以情”相反,布萊希特的戲劇主張“曉之以理”,即如研究布萊希特的學者恩斯特·舒瑪赫所說的那樣:“戲劇最主要的不是面向感情,而是面向理性。不應該引起對現實的幻覺,而應該引起對現實的看法。觀眾不應該獲得一種體驗,而是應該獲得一種世界觀。”(注:《布萊希特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這種訴諸理智的戲劇的最終目的是社會批判和社會變革:“這是一種批判的立場。面對一條河流,它就是河流的整修;面對一株果樹,就是果樹的接枝;面對移動,就是水路、陸路和交通工具的設計;面對社會,就是社會的變革。”(注:《布萊希特論戲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
在對當代電影的審視中,我們發現不管是將角色陌生化還是將時空結構改變,在周星馳的電影中都極為常見,以下我將具體進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