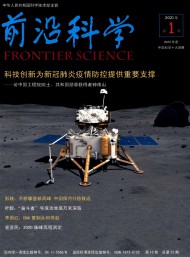朱自清范文10篇
時間:2024-04-20 06:58:55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朱自清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朱自清匆匆讀后感
讀了朱自清的散文《匆匆》,讓我深受感悟,思緒萬千。《匆匆》使我真正明白了“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的道理。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的確是的,露珠兒干了,有再晶瑩奪目的時候;太陽落山了,有再從東方升起的時候;天空被烏云遮蔽了,有重現光明的時候......可我們手中的日子呢,卻如江河入海,一去不復返!
“在默默里算著,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里,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回想一下,我又何曾不是這樣每天都快速地把作業在學校寫好,放學把書包一扔,不是看電視,就是玩耍。父母看見了多次批評,可我卻說寫好了,書上的內容也記得。可當試卷發下來,卻是處處掛“紅燈”。我也就像朱自清先生寫的那樣“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珍惜時間的人,哪怕給他幾分幾秒,他也會過得充實;;浪費時間的人,哪怕給他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光陰,他也會一無所獲,過得空虛。上天對任何人都是公平的,給每個人都是一天24個小時,主要看你怎樣掌握,怎樣分配。魯迅先生說得好:“時間就像海洋里的水,只要你能擠,總能擠出。”
時間,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玩耍的人們啊!快睜開你的雙眼,不然,時間將在你身邊消逝。
朱自清文學批評觀述評
朱自清的“背影”被世人記住是在上世紀30年代,他用溫潤的筆尖細膩地勾勒著一個又一個人們熟悉又陌生的生活細節,月色映照下的荷塘、年邁的背影、指縫中的時間等一起組成了他豐富多彩的散文世界。獨特的生存體驗使他多了幾許平常人少有的靈性與感悟,他創作的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散文佳作一時間如雨后春筍般在中國的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半個多世紀以來,對于朱自清的研究,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全面關照探索,均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但仔細分析之后,我們發現從理論的層面關注其文學批評觀及其批評實踐的著作論文卻少之又少。作為一名作家,朱自清不僅在散文創作,新詩研究,語文教學方面有所建樹,同時也給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諸如《新詩雜話》、《什么是散文》等理論文章及批評著作,對較長時間文學的發展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朱自清的文學批評觀注重向作家作品審美心理的逼近,關注社會現實,時刻為人民大眾、為文學發展著想,其精髓所代表的那種“理想主義”正像背影一樣,正漸漸地被這個時代所遺忘。現代社會注重現實功利性,評論家缺少的是坐下來靜靜地欣賞文學內部的精彩世界,忽略了文學體驗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拗口的學術術語。因而,我們有必要對朱自清的文學批評觀做一完整的剖析,尋求文學批評真正的源頭活水。
一、文學批評觀的形成
早在《朱自清書評序跋集》的序言中,先生就已經對當時的文學批評現狀做了精確的把握。當時,大多數人認為沒有創作才能的人才去從事文學批評,批評只是二流貨色,因此人們都不愿意研究它。另一方面是與我國的文學發展史有關,我們的詩文評片斷的多,成形的少,文學批評不易下手。鑒于文學批評不被重視又不可忽視的這種尷尬現狀,朱自清以一個學者批評家的姿態介入其中。一生在文學批評方面著述頗多,有《詩言志辨》、《朱自清序跋集》、《民眾文學談》、《文藝的真實性》、《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等多部著作流傳于世。朱自清正式從事文學批評活動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正值現代文學批評發展相對活躍與成熟之時。那個年代的中國學界,“教授批評已是蔚為大觀,周作人、梁實秋、朱自清、朱光潛、錢鐘書、梁宗岱等都是在大學執教的批評家,而這些教授同時也是當時文壇上創作的活躍分子。”“當時的教授文學批評極大地促進了現代文學批評的發展,是現代文學批評不可忽視的一支‘正規軍’,甚至可以說,沒有這些教授批評家,現代文學批評在批評方法、批評問題上要獲得健康發展是比較困難的。”[1]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朱自清開始了他的批評生涯。對他而言,雖然最初并不是以一位職業批評家的身份登上文壇,但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與社會責任感促使一切外界的力量并未能削弱他關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熱情。朱自清時刻以歷史的眼光和“為人生”又“為人民”的文學情操對當時的作家作品進行著獨特的審美關照。其評論文章字出有據、深入淺出,對現代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文學批評觀的內容
面對當時文壇的嚴峻形勢,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使命感讓作家出身的朱自清明白,他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使當時的文學批評擺脫目前這種尷尬的境地,從創作的附庸地位提高到獨立的學科地位。于是,在教學之余,他時刻關注文藝動向,批評活動能夠跳出傳統的批評模式,合理吸收西方近代批評的理論方法,這使得朱自清的文學批評在當時的批評界體現出獨特的批評特點,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注重考據的批評方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體認,讓朱自清在批評活動中不由自主地運用到歷史考據的方法,體現出濃厚的史筆意識。統觀其評論文章,回溯歷史以資評價的方式俯拾皆是。他對批評對象的把握與梳理大都以動態的眼光去權衡,對當時文壇的新興作家作品的品評也都是站在歷史的高度點明利弊得失,為作家發展指明方向。這種考據方法的運用和歷史意識的貫穿,顯然不是秉承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而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個學者式批評家治學的嚴謹態度與良好作風,反映了一種文學漸進的觀念。他很少將批評對象放在毫無所依的歷史背景中隨意闡釋,而是時刻不忘文學發展史這條永不停息的河流,批評文字言出有據,筆無虛譽。他的批評文章中,類似“漢興以來”、“到了正始”等時間類詞俯拾皆是。比如在《詩言志辨》中,他以“詩言志”為開山綱領,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論詩。在《詩言志》篇中,朱自清考察《詩經》及歷代詩論原著,爬梳春秋戰國時的“詩言志”說,對“詩”、“志”考鏡源流。考據方法的運用也貫穿在先生的其它批評活動。提及中國散文的發展,他開篇便說:“現存的中國最早的無韻文(散文),是商代的卜辭。……后來《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如此。不過經卜官和史官按著卦爻與年月的順序編纂起來,比卦爻顯得整齊些罷了。”[2]文章從漢武帝時盛行的辭賦,到唐代韓愈的“古文運動”、“唐宋八大家”,到“五四”時期的“白話文”。所涉及研究對象無不在考據的基礎上出現,讀后使讀者能夠對中國歷代的問題有一個全面的把握與認識,且往往在不經意間增強了批評文章的說服力。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中,朱自清首先通過《時事新報》上的兩則有關文本介紹的廣告指出:兩本書的特色是“諷刺的情調”和“輕松的文筆”。接下來他并沒有著手分析作品為何具有“諷刺的情調”和“輕松的文筆”,而給我們展現了一副諷刺小說歷史演變軌跡的畫卷。在讓讀者對諷刺小說的起源與內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朱自清進而提出:“這兩部書里的‘諷刺的情調’是屬于哪一種呢?[2]”可見,在朱自清這里,考據方法的運用并不是一味地進行源流上的探究。追溯源頭只為了引出今天的批評對象,使它不至于孤零零地站在讀者面前,而是攜帶著一股歷史的氣息,讓讀者先了解它的來由,進而更好地把握批評對象。
朱自清先生與語文現代化探析論文
在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白話文運動當屬最成功的,而在這成功的進程中,那些平易、新鮮、通俗明了的優秀白話文作品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一個文學運動的最有力的推動者不是學說而是作品。在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眾口一辭的贊賞。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評論他的散文,而且多著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談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的價值和作用,朱光潛先生的一段話極有概括性,他說:“在寫語體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語體文運動的歷史還不算太長,作家們都還在各自摸索路徑。較老的人們寫語體文,大半從文言文解放過來,有如裹小的腳經過放大,沒有抓住語體文的真正的氣韻和節奏;略懂西文的人們處處模仿西文的文法結構,往往冗長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們大半過信自然流露,任筆直書,根本不注意到文字問題,所以文字一經推敲,便見出種種字義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極少數人中的一個,摸上了真正語體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簡潔精煉不讓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確是日常語言所用的字,語句聲調也確是日常語言所有的聲調。就剪裁錘煉說,它的確是‘文’;就字句習慣和節奏說,它的確是‘語’。任文法家們去推敲它,不會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給一般老百姓聽,他們也不會感覺有什么別扭。”因此,說到白話文運動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這方面的成就要和語體文運動共垂久遠的”[2]。
國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一直相依發展。朱自清先生始終支持國語用活的方言———北京話(當時稱北平話)做標準,他認為,國語應該有一個自然的標準。他說:“有人主張不必用活方言作標準,該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謂‘國語’。而所謂‘國語’就是從前人所稱的‘藍青官話’。但個人‘藍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結果只是四不像罷了。我覺得總是有個活方言作標準的好。”朱自清先生還以他本人為例來表明他的觀點,他說:雖然本人是蘇北人,但也贊成將北平話作為標準語,其中一個原因,是北平話的詞匯差不多都寫得出來[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對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學者對此評論說:北方方言的許多語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紙上,生動、自然、親切,而且很有分寸。這又使人想到一個問題:“能不能完全用一種方言———比如北平話———寫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動,才有個性,也才能在民間生根。可是方言有時就不夠用,特別在學術用語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話,也覺得流利的有點俗。朱先生在這方面的主張,是以北平話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話。那也就包含一個結論,便是:我們文章的語言,必須是出于一種方言,這是語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種方言術語,加以擴大,成為自創的語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對誦讀情有獨鐘,在他的著述中多處談到誦讀的話題。朱光潛先生曾回憶說:“我們都覺得語文體必須讀得上口,而且讀起來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悅耳,所以大家定期集會,專門練習朗誦,佩弦對于這件事最起勁。”[5]朱自清先生認為白話文并非怎樣說就怎樣寫,而是“對于說話,作一番洗煉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話,那么就體例說是純粹,就效果說,可以引起念與聽的時候的快感”。他認為,朗誦的發展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的成長。“只要把握住一個標準,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純粹的、理想的白話文[6]。
在用白話文寫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標點符號的作用,他認為,標點符號和從前的圈點或句讀符號不一樣。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幫助讀者的了解;對于文字的關系是機械的。前者卻是用在文字里,幫助寫作者表達情思;對于文字的關系是有機的。因為用了標點符號,才有了新的“句”的觀點。現在還有些人不大會用標點符號,先寫好了文字,再去標點起來。這真是所謂“加”標點了。后“加”標點的文字里,往往留著舊白話的影子。他把這原因之一歸于當初由胡適起草的標點符號施行條例,因為其中所舉的例句都是古書和文言,加上一些舊小說的白話,現代的白話文似乎沒有。他認為這種例句“加”上標點符號,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種標點符號的用處。而白話文之所以成為白話文,標點符號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標點符號的人,將標點符號當作文字的一部分,不當作文字外的東西。他們寫作時,隨著句讀標點下去;這是“用”進去,不是“加”上去。這些人的文字,現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話文發展過程中的“歐化”傾向引發了激烈的討論。朱自清先生對此則從時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討。他的態度應該也與他曾在英國專修過語言學有關系。他認為時代處于向現代化邁進的過程中,“現代化的語言是比舊文言舊白話復雜得多、精密得多”。這種精密也體現在文法的現代化上,即體現了分析的精神。他將白話文的歐化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模仿歐化語法,一般人行文時,往往有牽強不過的詞匯,讀起來感覺非常蹩扭。第二個時期注意到歐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這個時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評一些人的“歐化”是堆砌形容詞,使人眼花繚亂,語句艱澀等等的同時,也提出:現作的人,大約不止我一個,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謂“歐化”與熟語化兩條路中間。他們求清楚,不得不“歐化”;他們求親切,又不得不熟語化。怎樣才能使“歐化”與熟語化調和得恰到好處,還待研究和練習。這是留心語言現代化的人所應當努力的。白話文不但不全跟著國語的口語走,也不全跟著傳統的白話走,卻有意的跟著翻譯的白話走。這是白話文的現代化,也就是國語的現代化。中國一切都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語言的現代化也是自然的趨勢,是不足怪的。語言的“歐化”在適應和發展現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8]。
白話文的“歐化”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交匯融合,而翻譯是介紹外國的文化到中國來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寫了《譯名》一文,專門談名詞術語的翻譯問題。談到借用外語時,朱自清先生認為:原來中國的六書文字同西洋音標的文字性質本是格格難入,同他們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國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國,沒有什么新語輸進來;只有漢到六朝之間,印度哲學輸入,佛經譯出的很多;結果也只是在中國文字里添了許多新詞,并沒有借用梵語的所在。直到近幾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詞的現象。至于西洋文字,因為同中國的文字相差的實在太遠了,所以一直沒有借用的事情。他們的音形都差的太厲害,就是借過來,要叫他普遍通行,讓人人明白他的意義,恐怕是千難萬難呢!主張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名著讀后感
近來我們高一學習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首先我想到朱自清其人。在江南水鄉他度過了童年,確實有著平和中正的品性和向往自然美的情趣,但他也曾說,兒時的記憶只剩下“薄薄的影”“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驚人的程度”,這與荷塘月色中透出的孤寂也有聯系吧。而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上,兒時畢竟是首發的驛站。看了他的《綠》《春》《匆匆》《背影》后,覺得他真是個適合寫散文的人,語文優美、靈活,文思細膩樸素。如果說魯迅的語言精練深刻,郭沫若氣勢磅礴,巴金樸素優美,冰心委婉明麗,那么朱自清真的是很清雋,很沉郁。而這樣的人身為清華教授卻一生清貧,甚至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人世,想到其人其事其文,心中有些明白了,也很受感動。而這樣一位民主戰士,也不吃美國救濟糧寧愿餓死,心里感到很震撼,我感覺他的堅強與魯迅先生雖有不同,和老舍先生卻很類似,那是一個中國文學家的尊嚴與氣節。
讀《荷塘月色》,我最欣賞的是意境美,朦朧美,那是清風靜謐,那分明是寧靜里的心靈吶喊,濃濃的思緒。在我的印象里,荷花是大方明麗的花,是亮麗爽眼的花,是適合扯一暴風與之一起的掛在陽光下的花。而在朱自清筆下,只有抑郁、寧靜、蘊藉和甘醇。
以前也見過大片的荷,曾在洪湖的荷塘里于荷海間乘舟穿行。那時的荷花荷葉給人感覺很明麗,而那時也確是有一種隱郁的清氣,很獨特地顯出荷的透明感,時時也飄動著如初般的心事,而點點微細的水光從葉隙花間不斷流涌之景,真的很美。荷稈像從水中射出的箭,純凈而堅韌,但我仍無法體味朱自清所感覺的那意境,因為我畢竟不是朱自清。
人教版教材課文中,有金志華寫的評點。但我認為文章就是文章,閱讀是靠每個人的心情,每個人的理解去解讀,所以每個人都能讀出不同的東西。誰也沒有權利去斷定誰的評賞是正確的,或是錯誤的。學者看文章要分析結構,普通人看文章也許注重內容。金志華認為《荷塘月色》是圓的,而我自第一眼看到這文章就被它的意境它的“情”所打動。許多人們就是這樣,看到一篇好文章,馬上分析表現了什么中心思想,哪里寫得如何之精辟,絕妙。其實很多東西作者都沒想到過,卻被他人賦予了新說,我只想“看”文章,用自己的心情去看,最后找到只因為我的心情我的理解而看到的東西,我就很滿足。剛如“但熱鬧是它們的,我什么也沒有”只簡單的一句話,就體現了作者在熱鬧之景中的孤寂與冷清。一個瞬時的感情轉換,也為全文作了感情鋪墊,這使我立刻想到了徐志摩的詩:“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這兩位寫蟲鳴一動一靜,卻同樣表達了內心的傷感。
想起那些對文學的感動,我越發覺得對文字美的感受是一瞬間的領悟。以前讀賈平凹的《我的小桃樹》,別人說他是鬼才,文筆優美,我不信,但其中有一句是真的打動了我,在他感慨我自己的小桃樹片片付給風和雨后,在描寫桃樹于風雨中頑強戰斗前,中間有句很平常的話:“我心里喊著我的奶奶!”如今再品,我想這大概就是散文的“文眼”了,點出了作者寄托在小桃樹感情。只一句,美得令人驚嘆。我想《荷塘月色》中的“只不見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我令我到底惦著江南了”,與賈平凹的語言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吧!現在我更加確定美足以作為生命存在的理由。
讀《荷塘月色》,我擁有了一片美麗的荷塘,也認識了一位多情孤寂的作家。
朱自清與語文現代化分析論文
摘要五四之后,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持續高漲,對此,朱自清先生一直給予積極的關注與支持。他的散文創作也是對白話文運動最有力的推動;同時朱自清先生還在他的許多著述中闡述了他的中國語文觀。本文是對朱自清先生的著述中有關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論述和觀點的綜述。
關鍵詞朱自清語文現代化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歐化簡體字拼音化
朱自清先生曾寫了一篇文章《魯迅先生的中國語文觀》,綜合引述魯迅先生對中國語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對這些觀點的價值性評說,但從朱自清先生不同時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對魯迅的語文觀是大體贊同的。帶來了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簡化字運動的持續高漲。這些運動所追求的就是中國語文的現代化:即語言的共同化、文體的口語化、文字的簡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1]。而朱自清先生同魯迅先生一樣,一直在倡導與追隨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主流。從五四時期在北京大學就學時起,直至后來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關注著中國語文的改革運動,這并非全是出于這些運動在當時與他所從事的文學創作與研究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他不僅支持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主流學說與理論,而且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影響知識分子,這無疑起了推動中國語文現代化進程的作用。
在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白話文運動當屬最成功的,而在這成功的進程中,那些平易、新鮮、通俗明了的優秀白話文作品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一個文學運動的最有力的推動者不是學說而是作品。在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眾口一辭的贊賞。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評論他的散文,而且多著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談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的價值和作用,朱光潛先生的一段話極有概括性,他說:“在寫語體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語體文運動的歷史還不算太長,作家們都還在各自摸索路徑。較老的人們寫語體文,大半從文言文解放過來,有如裹小的腳經過放大,沒有抓住語體文的真正的氣韻和節奏;略懂西文的人們處處模仿西文的文法結構,往往冗長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們大半過信自然流露,任筆直書,根本不注意到文字問題,所以文字一經推敲,便見出種種字義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極少數人中的一個,摸上了真正語體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簡潔精煉不讓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確是日常語言所用的字,語句聲調也確是日常語言所有的聲調。就剪裁錘煉說,它的確是‘文’;就字句習慣和節奏說,它的確是‘語’。任文法家們去推敲它,不會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給一般老百姓聽,他們也不會感覺有什么別扭。”因此,說到白話文運動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這方面的成就要和語體文運動共垂久遠的”[2]。
國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一直相依發展。朱自清先生始終支持國語用活的方言———北京話(當時稱北平話)做標準,他認為,國語應該有一個自然的標準。他說:“有人主張不必用活方言作標準,該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謂‘國語’。而所謂‘國語’就是從前人所稱的‘藍青官話’。但個人‘藍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結果只是四不像罷了。我覺得總是有個活方言作標準的好。”朱自清先生還以他本人為例來表明他的觀點,他說:雖然本人是蘇北人,但也贊成將北平話作為標準語,其中一個原因,是北平話的詞匯差不多都寫得出來[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對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學者對此評論說:北方方言的許多語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紙上,生動、自然、親切,而且很有分寸。這又使人想到一個問題:“能不能完全用一種方言———比如北平話———寫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動,才有個性,也才能在民間生根。可是方言有時就不夠用,特別在學術用語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話,也覺得流利的有點俗。朱先生在這方面的主張,是以北平話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話。那也就包含一個結論,便是:我們文章的語言,必須是出于一種方言,這是語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種方言術語,加以擴大,成為自創的語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對誦讀情有獨鐘,在他的著述中多處談到誦讀的話題。朱光潛先生曾回憶說:“我們都覺得語文體必須讀得上口,而且讀起來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悅耳,所以大家定期集會,專門練習朗誦,佩弦對于這件事最起勁。”[5]朱自清先生認為白話文并非怎樣說就怎樣寫,而是“對于說話,作一番洗煉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話,那么就體例說是純粹,就效果說,可以引起念與聽的時候的快感”。他認為,朗誦的發展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的成長。“只要把握住一個標準,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純粹的、理想的白話文[6]。
朱自清與語文現代化試析論文
摘要五四之后,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持續高漲,對此,朱自清先生一直給予積極的關注與支持。他的散文創作也是對白話文運動最有力的推動;同時朱自清先生還在他的許多著述中闡述了他的中國語文觀。本文是對朱自清先生的著述中有關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論述和觀點的綜述。
關鍵詞朱自清語文現代化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歐化簡體字拼音化
朱自清先生曾寫了一篇文章《魯迅先生的中國語文觀》,綜合引述魯迅先生對中國語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對這些觀點的價值性評說,但從朱自清先生不同時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對魯迅的語文觀是大體贊同的。帶來了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簡化字運動的持續高漲。這些運動所追求的就是中國語文的現代化:即語言的共同化、文體的口語化、文字的簡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1]。而朱自清先生同魯迅先生一樣,一直在倡導與追隨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主流。從五四時期在北京大學就學時起,直至后來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關注著中國語文的改革運動,這并非全是出于這些運動在當時與他所從事的文學創作與研究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他不僅支持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主流學說與理論,而且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影響知識分子,這無疑起了推動中國語文現代化進程的作用。
在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白話文運動當屬最成功的,而在這成功的進程中,那些平易、新鮮、通俗明了的優秀白話文作品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一個文學運動的最有力的推動者不是學說而是作品。在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眾口一辭的贊賞。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評論他的散文,而且多著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談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的價值和作用,朱光潛先生的一段話極有概括性,他說:“在寫語體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語體文運動的歷史還不算太長,作家們都還在各自摸索路徑。較老的人們寫語體文,大半從文言文解放過來,有如裹小的腳經過放大,沒有抓住語體文的真正的氣韻和節奏;略懂西文的人們處處模仿西文的文法結構,往往冗長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們大半過信自然流露,任筆直書,根本不注意到文字問題,所以文字一經推敲,便見出種種字義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極少數人中的一個,摸上了真正語體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簡潔精煉不讓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確是日常語言所用的字,語句聲調也確是日常語言所有的聲調。就剪裁錘煉說,它的確是‘文’;就字句習慣和節奏說,它的確是‘語’。任文法家們去推敲它,不會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給一般老百姓聽,他們也不會感覺有什么別扭。”因此,說到白話文運動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這方面的成就要和語體文運動共垂久遠的”[2]。
國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一直相依發展。朱自清先生始終支持國語用活的方言———北京話(當時稱北平話)做標準,他認為,國語應該有一個自然的標準。他說:“有人主張不必用活方言作標準,該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謂‘國語’。而所謂‘國語’就是從前人所稱的‘藍青官話’。但個人‘藍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結果只是四不像罷了。我覺得總是有個活方言作標準的好。”朱自清先生還以他本人為例來表明他的觀點,他說:雖然本人是蘇北人,但也贊成將北平話作為標準語,其中一個原因,是北平話的詞匯差不多都寫得出來[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對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學者對此評論說:北方方言的許多語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紙上,生動、自然、親切,而且很有分寸。這又使人想到一個問題:“能不能完全用一種方言———比如北平話———寫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動,才有個性,也才能在民間生根。可是方言有時就不夠用,特別在學術用語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話,也覺得流利的有點俗。朱先生在這方面的主張,是以北平話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話。那也就包含一個結論,便是:我們文章的語言,必須是出于一種方言,這是語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種方言術語,加以擴大,成為自創的語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對誦讀情有獨鐘,在他的著述中多處談到誦讀的話題。朱光潛先生曾回憶說:“我們都覺得語文體必須讀得上口,而且讀起來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悅耳,所以大家定期集會,專門練習朗誦,佩弦對于這件事最起勁。”[5]朱自清先生認為白話文并非怎樣說就怎樣寫,而是“對于說話,作一番洗煉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話,那么就體例說是純粹,就效果說,可以引起念與聽的時候的快感”。他認為,朗誦的發展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的成長。“只要把握住一個標準,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純粹的、理想的白話文[6]。
詮釋朱自清語文教育思想
朱自清是中國現代散文領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們發現他還是現代中國一位出色的語文教育家。只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總是無法擺脫朱自清是一位現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響,或者說朱自清大量的文學創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創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蓋了他實際上相當豐厚細致的語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師范、揚州第八中學、吳淞中國公學、臺州六師、溫州第四中學、寧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戰爆發后,隨學校南遷,任昆明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論著有與葉圣陶合著的《國文教學》、《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標準與尺度》和《語文拾零》等。我們把目光從他的散文作品轉移到他眾多的教育論著,明顯可以看到他的語文教育思想自成體系。我想:站在歷史的長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審視作為語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斷地從各個方面來加深對他的教育思想的認識,將十分有助于提高我們目前以及將來語文教育發展解決重大問題的自覺性。我們把朱自清關于教育目的、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獨特主張和論述,總稱為朱自清的語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對此作一初步探討。
一、“使學生了解本國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賞文學能力”的教育目的論
他在《古文學的欣賞》一文中相當獨特地提出了語文教育的兩項目的,非常值得我們注意:一是選讀古書,了解、認識和接受本國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賞作為情感的操練,設身處地地欣賞古文學,弄清古文學的立場或揚棄或清算,培養欣賞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語文教育的遠大目標確定在了解本國固有的燦爛文化,加強民族意識并以此提高學生欣賞文學的水平,這種觀念顯然區別于語文教育就是講授語文知識使學生語文成績考試合格或者語文教育就是一種解析作家作品和語言現象的學術研究的一般觀念。朱自清這種對語文教育目的的嶄新揭示讓我們感覺到了他的一種具有特定意義對于前人的舉步跨越。他還認為:中國人雖然需要現代化,但是中國人的現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獨尊本國固有文化的理論家。在他看來,本國固有文化遺產不僅是中國奔向未來的一個重要依據,而且也是語文教育必須把握的一個重要目的。在這方面,朱自清把語文教育獨特地理解為一種繼承文化遺產宏揚民族精神的特殊行為,這顯然體現了他個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張的“了解本國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學的篇章字句、語體、詞匯、成語、風格和技巧,設身處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寫作態度、喜怒哀樂愛惡欲。他認為語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對古文學的了解來幫助青年人信古、學古。他說:“有些青年人以為古書古文學里的生活跟現代隔得太遠,遠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們不能也不愿意接受這些……我想從頭說起,盡管社會組織不一樣、盡管意識形態不一樣,人情總還有不相遠的地方,喜怒哀樂愛惡欲總還是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然對象不盡同,表現也不盡同”。[1]朱自清的這種見解清晰地指明語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們把青年對我國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遠變為對它的親近。朱自清以為無論古今人物、人情總還有不相遠的地方,人類的喜怒哀樂愛惡欲可以跨越歷史的長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達到青年讀者與中國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著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聯系來親近、認識和了解中國固有文化,實際上是從方法途徑方面強調了在語文教育實踐中怎樣達到了解本國固有文化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語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讓學生接受文學,培養欣賞力,培養批判力。他說:“接受文學,我們有我們的立場。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場,再弄清楚古文學的立場。所謂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別出那些是該揚棄的,那些是該保留的……自己有立場,卻并不妨礙了解或認識古文學,因為一面可以設身處地地為古人著想,一面還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場上批判的。……這‘設身處地’是欣賞的重要的關鍵,也就是所謂‘感情移入’。”[2]這段話今天看來似乎相當普通,但其體會切身,因而其意義也就不同尋常。它指出了欣賞的首要問題是解決立場,并且作品的立場和讀者閱讀時自我的立場更不能混為一談。這里清楚地說明以堅定的立場和批判力對待文學是培養學生欣賞文學能力的第一要義。這種說法反映出欣賞能力培植的關鍵又在于對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設身處地地體味原來作家作品的喜怒哀樂。這樣特殊的意義,理應真正深刻地通過語文教育的課堂介紹給自己的學生,讓這些體現中國最主要的文化歷史內涵的作品從培養學生的欣賞力批判力的角度出發給學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著眼于發掘學生欣賞文學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這些見解是頗為嶄新的。
論朱自清先生與語文現代化
摘要五四之后,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持續高漲,對此,朱自清先生一直給予積極的關注與支持。他的散文創作也是對白話文運動最有力的推動;同時朱自清先生還在他的許多著述中闡述了他的中國語文觀。本文是對朱自清先生的著述中有關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論述和觀點的綜述。
關鍵詞朱自清語文現代化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歐化簡體字拼音化
朱自清先生曾寫了一篇文章《魯迅先生的中國語文觀》,綜合引述魯迅先生對中國語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對這些觀點的價值性評說,但從朱自清先生不同時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對魯迅的語文觀是大體贊同的。帶來了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簡化字運動的持續高漲。這些運動所追求的就是中國語文的現代化:即語言的共同化、文體的口語化、文字的簡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1]。而朱自清先生同魯迅先生一樣,一直在倡導與追隨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主流。從五四時期在北京大學就學時起,直至后來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關注著中國語文的改革運動,這并非全是出于這些運動在當時與他所從事的文學創作與研究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他不僅支持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主流學說與理論,而且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影響知識分子,這無疑起了推動中國語文現代化進程的作用。
在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白話文運動當屬最成功的,而在這成功的進程中,那些平易、新鮮、通俗明了的優秀白話文作品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一個文學運動的最有力的推動者不是學說而是作品。在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眾口一辭的贊賞。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評論他的散文,而且多著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談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的價值和作用,朱光潛先生的一段話極有概括性,他說:“在寫語體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語體文運動的歷史還不算太長,作家們都還在各自摸索路徑。較老的人們寫語體文,大半從文言文解放過來,有如裹小的腳經過放大,沒有抓住語體文的真正的氣韻和節奏;略懂西文的人們處處模仿西文的文法結構,往往冗長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們大半過信自然流露,任筆直書,根本不注意到文字問題,所以文字一經推敲,便見出種種字義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極少數人中的一個,摸上了真正語體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簡潔精煉不讓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確是日常語言所用的字,語句聲調也確是日常語言所有的聲調。就剪裁錘煉說,它的確是‘文’;就字句習慣和節奏說,它的確是‘語’。任文法家們去推敲它,不會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給一般老百姓聽,他們也不會感覺有什么別扭。”因此,說到白話文運動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這方面的成就要和語體文運動共垂久遠的”[2]。
國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一直相依發展。朱自清先生始終支持國語用活的方言———北京話(當時稱北平話)做標準,他認為,國語應該有一個自然的標準。他說:“有人主張不必用活方言作標準,該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謂‘國語’。而所謂‘國語’就是從前人所稱的‘藍青官話’。但個人‘藍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結果只是四不像罷了。我覺得總是有個活方言作標準的好。”朱自清先生還以他本人為例來表明他的觀點,他說:雖然本人是蘇北人,但也贊成將北平話作為標準語,其中一個原因,是北平話的詞匯差不多都寫得出來[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對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學者對此評論說:北方方言的許多語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紙上,生動、自然、親切,而且很有分寸。這又使人想到一個問題:“能不能完全用一種方言———比如北平話———寫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動,才有個性,也才能在民間生根。可是方言有時就不夠用,特別在學術用語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話,也覺得流利的有點俗。朱先生在這方面的主張,是以北平話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話。那也就包含一個結論,便是:我們文章的語言,必須是出于一種方言,這是語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種方言術語,加以擴大,成為自創的語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對誦讀情有獨鐘,在他的著述中多處談到誦讀的話題。朱光潛先生曾回憶說:“我們都覺得語文體必須讀得上口,而且讀起來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悅耳,所以大家定期集會,專門練習朗誦,佩弦對于這件事最起勁。”[5]朱自清先生認為白話文并非怎樣說就怎樣寫,而是“對于說話,作一番洗煉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話,那么就體例說是純粹,就效果說,可以引起念與聽的時候的快感”。他認為,朗誦的發展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的成長。“只要把握住一個標準,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純粹的、理想的白話文[6]。
朱自清與語文現代化研究論文
摘要五四之后,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持續高漲,對此,朱自清先生一直給予積極的關注與支持。他的散文創作也是對白話文運動最有力的推動;同時朱自清先生還在他的許多著述中闡述了他的中國語文觀。本文是對朱自清先生的著述中有關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論述和觀點的綜述。
關鍵詞朱自清語文現代化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歐化簡體字拼音化
朱自清先生曾寫了一篇文章《魯迅先生的中國語文觀》,綜合引述魯迅先生對中國語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對這些觀點的價值性評說,但從朱自清先生不同時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對魯迅的語文觀是大體贊同的。帶來了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簡化字運動的持續高漲。這些運動所追求的就是中國語文的現代化:即語言的共同化、文體的口語化、文字的簡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1]。而朱自清先生同魯迅先生一樣,一直在倡導與追隨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主流。從五四時期在北京大學就學時起,直至后來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關注著中國語文的改革運動,這并非全是出于這些運動在當時與他所從事的文學創作與研究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他不僅支持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主流學說與理論,而且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影響知識分子,這無疑起了推動中國語文現代化進程的作用。
在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白話文運動當屬最成功的,而在這成功的進程中,那些平易、新鮮、通俗明了的優秀白話文作品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一個文學運動的最有力的推動者不是學說而是作品。在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眾口一辭的贊賞。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評論他的散文,而且多著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談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語文現代化運動中的價值和作用,朱光潛先生的一段話極有概括性,他說:“在寫語體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語體文運動的歷史還不算太長,作家們都還在各自摸索路徑。較老的人們寫語體文,大半從文言文解放過來,有如裹小的腳經過放大,沒有抓住語體文的真正的氣韻和節奏;略懂西文的人們處處模仿西文的文法結構,往往冗長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們大半過信自然流露,任筆直書,根本不注意到文字問題,所以文字一經推敲,便見出種種字義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極少數人中的一個,摸上了真正語體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簡潔精煉不讓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確是日常語言所用的字,語句聲調也確是日常語言所有的聲調。就剪裁錘煉說,它的確是‘文’;就字句習慣和節奏說,它的確是‘語’。任文法家們去推敲它,不會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給一般老百姓聽,他們也不會感覺有什么別扭。”因此,說到白話文運動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這方面的成就要和語體文運動共垂久遠的”[2]。
國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一直相依發展。朱自清先生始終支持國語用活的方言———北京話(當時稱北平話)做標準,他認為,國語應該有一個自然的標準。他說:“有人主張不必用活方言作標準,該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謂‘國語’。而所謂‘國語’就是從前人所稱的‘藍青官話’。但個人‘藍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結果只是四不像罷了。我覺得總是有個活方言作標準的好。”朱自清先生還以他本人為例來表明他的觀點,他說:雖然本人是蘇北人,但也贊成將北平話作為標準語,其中一個原因,是北平話的詞匯差不多都寫得出來[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對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學者對此評論說:北方方言的許多語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紙上,生動、自然、親切,而且很有分寸。這又使人想到一個問題:“能不能完全用一種方言———比如北平話———寫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動,才有個性,也才能在民間生根。可是方言有時就不夠用,特別在學術用語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話,也覺得流利的有點俗。朱先生在這方面的主張,是以北平話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話。那也就包含一個結論,便是:我們文章的語言,必須是出于一種方言,這是語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種方言術語,加以擴大,成為自創的語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對誦讀情有獨鐘,在他的著述中多處談到誦讀的話題。朱光潛先生曾回憶說:“我們都覺得語文體必須讀得上口,而且讀起來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悅耳,所以大家定期集會,專門練習朗誦,佩弦對于這件事最起勁。”[5]朱自清先生認為白話文并非怎樣說就怎樣寫,而是“對于說話,作一番洗煉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話,那么就體例說是純粹,就效果說,可以引起念與聽的時候的快感”。他認為,朗誦的發展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的成長。“只要把握住一個標準,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純粹的、理想的白話文[6]。
朱自清散文的語言藝術探究論文
內容摘要: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清新自然,語言優美,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朱先生主要是從樸素美、音韻美、裝飾美和綺麗美四個方面提煉語言的。學習研究朱先生散文的語言對于豐富語言,創新和提升文學素養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朱自清;散文;語言藝術
朱自清先生是我國“五四”以來最膾炙人口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不論記人、敘事、說理、抒情,都如實抒發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的情感性感染了廣大讀者。文章的思想和情感的意蘊美向來是文學創作的最高追求,這種內在美是通過怎樣的外在形式體現出來的呢?語言的運用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研究朱先生的散文創作,我們不難發現,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突出表現在語言藝術的運用上。
一、精選口語入文,體現樸素美
關于散文的語言風格_朱自清強調文章最重自然,他明確提出要用“活的口語”寫文章。認為這樣的文章才能像“尋常談話一般,讀了親切有味。”
《春》里,他不說春天來臨,各種花競相開放,爭妍斗艷,而說“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花趕趟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