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大道美學管理論文
時間:2022-07-29 11:01:00
導語:金光大道美學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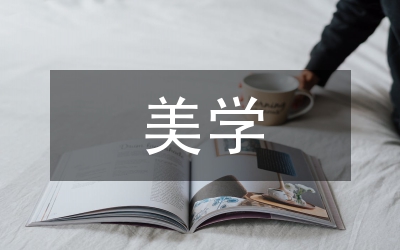
一、緣起:
連日陰雨綿綿,困守在家,把過去買的舊碟片倒騰出來重新過目。
雖然偶一買碟,但集腋成裘,一不小心,電腦桌下已被碟片占領,成為食之無味、丟之可惜的雞肋。
這些碟片大多是商店清艙時貪便宜賣來的,翻了翻,大部分沒有拆封,有什么《公民凱恩》、《偷自行車的人》、《發條橘子》、賽珍珠《大地》、好萊塢版《十誡》,三教九流,五花八門,林林總總。
也有在盜版市場上買到的一些的片子,像什么《春苗》、《青松嶺》以及部分樣板戲。其中就有《金光大道》(上、中集)(《艷陽天》一直沒有賣到,遺憾)。
雨天好看書,現在應該是好看碟了。于是終于看到了精品《金光大道》。
在國產片中,這個電影好長。一集都有兩個小時,上、中兩集就是近四個小時,耗盡了我半天的時間,花了我兩天的功夫,才算看完。
不好意思,看完后,我竟然感動與激動不已。剔除影片中的部分夸張的動作表現,影片的總體氣氛仍是難能可貴的樸質的,體現出的中國人的努力探索的歷史遺痕,至少具有一種備檔的意義,而其中透露出的雖蜻蜓點水般卻至為寶貴的人性的因素,則使影片散發出一種人情的美好。
于是就想到美學。
有沒有美學?
二、尷尬的研究現狀:
于是就到網上找方面的材料。
看到一些資料,移錄如下:
資料1:“‘在中國、學在國外’,這是許多中國學者不無感慨的政治現實。近年來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20世紀中國的文化藝術,包括不同時期的大眾文化。越來越多的海外華人批評家和歷史學者也在運用新的方法探討時期的文學藝術。大家都看到了搶救這些歷史材料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隨著藝術市場的擴大,對時期藝術品及其圖像的考鑒研究也日益深入細致,逐漸勾出了中國現代美術史整體中這一被忘卻了的部分的輪廓。但是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這次展覽只是中專出了很有意義的一步。(本文摘自《典藏今藝術》)”
資料2:“研究“學”的洋人以美國最多,無論資料與學術水準,都堪稱海外研究的中心。這些美國人幾乎在一開始,即以極大興趣投入了研究。美籍韓裔學者李鴻永在一九七八年即出版了有關廣州的專著,其研究的深入與細致,連國內的學者也為之折服。七十年代,南加州大學的羅森為了撰寫《廣州紅衛兵的派性與》,采訪了一千個當時到香港的廣州人,掌握的數據包括各種家庭出身的學生在紅衛兵中的比例。美籍華裔學者陳佩華通過個案調查收集口述材料,撰寫了另一部紅衛兵研究專著——《毛的孩子們》。從七十年代在臺灣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美國學者,到八十年代研究學的美國學者,或者都在其研究——尋找中國百年歷史變遷規律的范疇之內。”
相比之下,在國內的描述中仍是千篇一律、眾口一詞的。
三、有沒有美學?
這是美學學者研究的課題。
如果說暴力都能產生美學的話,那么,美學的內涵實際上已經被表述為一種具有共同審美特征的流派,一種趨向。
正像負增長也被作為一種增長率的概念一樣,審美在進行自我的主觀發言的時候,也意味著把審丑作為自己所注目的一個必然的領域。即使拋開美與丑這一個純粹主觀上產生的判斷,至少審美應該有權利、有資格對具有相同特征的文化現象進行觀望、觀察與觀看。
正是在這樣的對概念的最通融的寬容的前提下,“美學”這樣的概念表述就無法讓我們視而不見。
期間的連環畫成為收藏新品,郵票一直是收藏的熱門,油畫的拍賣也時常掀起波瀾,而的音樂借助前幾年的“紅太陽”系列,風靡全國,“收租院”的雕塑在國內遭受到滅頂之災的批判,卻在國外以復制品的形式引起轟動。
在這種對意向的陣發性、返祖性的回放中,難道僅僅是作為一個歷史概念被人們所追蹤嗎?在這里有沒有一種純粹的剔除了政治因子的美學因素,成為人們熱衷于其中的引擎呢?
在當年的“紅太陽”的歌曲聯唱中,難道引起全國人民癡迷的就沒有旋律中的美學成份嗎?
樣板戲中提出的“三突出”概念是否是一條放之五湖四海而皆成立的美學原則?看看好萊塢電影中的那些所謂超人的英雄,誰不是在特殊環境下一塊優秀的好鋼?誰不是在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狀況中,顯示出頂天立地的大英雄?那些拯危救難的好萊塢林林總總的英雄們、或者我們縮小范圍就以007為例吧,整個電影中哪一處沒有突出這個英雄人物的與眾不同呢?
實際上,在“”藝術作品總是出其不意地襲擊到當代的文化空間里的時候,由于先驗地否定美學的獨立存在,最后往往使某些人士陷入某種尷尬,往往把藝術品的借尸還魂看成是一種情結的噴發。
正像當年說“紅太陽”音樂的橫空出世、席卷全國是一種情結的再次返祖一樣,最終顯示出是一種可笑的對流行文化的錯誤判斷。在那次影響最為廣大的全面的對藝術作品的懷舊潮流中,實際上里邊的政治因素已經被消釋為零,而放大了藝術品中的可以與現代人們的情感趨向相與時俱進、相同步且可以接受的真誠、溫馨、親切的成份。也就是說,人們欣賞的是藝術作品中的獨立于政治之外的美學成份。
藝術作品總是在特定的情境下,重新闖入人們的視線,我們難以回避它存在著獨特的自成體系的美學風格。至今,已經三十余年,我們應該有足夠的理智與冷靜,去解析它為什么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它們的鮮明的特色,給我們一個不同的美學刺激。我們可以像鴕鳥一般地拒絕對它的承認,但從現實的角度,顯然這是一種可笑的極其軟弱的自欺欺人的行為。
有人必然要提到期間的混亂、血腥、丑陋、人性惡的釋放等丑惡因素。我想,這一切丑惡的暴力因素顯然不是藝術作品中所倡導的主題。出現這種一系列的對人性的踐踏的丑惡的現象,是當時社會呈現出無政府狀態而激發出的一種人性惡的徹底暴露,正是魯迅先生用他的如櫞之筆前無古人地揭示出中國歷史就是人吃人的實質的現代重演。沒有任何一部藝術作品是倡導這種人吃人的中國人的社會規律的,出現這種當年的主流藝術作品的主體基調與社會中人性惡的泛濫的強烈反差與對立,只能說明藝術作品的教化功能的無奈、無力與無能,而因此把歷史上發生的所有血腥與暴力等同為藝術作品的本質特點,無疑就像期間所流行的“用文學進行反革命”的概念一樣,再次讓一個政治年代的藝術作品,受到一種不公正的待遇。
為了便于我們敘述的方便,我們姑且承認有一個存在的美學,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美學傾向還在世界電影史上產生影響。眾所周知的世界級名導戈達爾也參加了法國受中國很大影響而爆發的“1968年五月風暴”。在這一紅色風暴中,法國文化界就中國式的共產主義進行討論與對話,支持大革命。他們身穿綠軍裝,手拿紅寶書。在現今的小資派的電影觀摩者的心目中,戈達爾無疑是一個名牌導演,其實,戈達爾的行為更像是一個被中國紅衛兵鼓動的激進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五月風暴后,這位老戈兄提出一套“電影革命的理論”,提出了“為了攝制革命的電影,首先應對電影進行革命”的口號,認為革命的電影應同資產階級的藝術觀念徹底決裂,并且付諸于實踐,拍了許多戰斗電影,如《東風》、《真理》、《直到勝利》、《弗拉基米和羅莎》等等。用《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影卷》的介紹說:這些極左的影片更加抽象、晦澀。
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拋開政治的偏見,提取中的藝術作品的共性成份,承認它具有一個共同的內質,視之為一個獨立的流派,信奉的是同樣的美學主張,姑且稱之為“美學。”
下面,我們將從《金光大道》這部電影來具體看看“美學”的一些微觀成份。當然,咱這不是論文,只是一點隨感而已,加之本人對電影無法全部找到,也缺乏深入的、系統的研究,更沒有親身參與的體驗,僅是管中窺豹,一孔之見吧,也希望給國內的文藝學的提供一個可以參照的視角。
四、關于作者浩然
對于浩然的認識我是從《西沙兒女》開始的。
可能那時還是小學,班上的同學帶著一打廢紙,沒頭沒尾,隨撕隨扔。上課開小差,就把同學那本撕毀的書拿來看了,看到描寫打越南人,捉到越南一俘虜,我民兵在他的手上寫字,作為憑據,讓他回去好交差,一下子就被這個情節吸引住了。就找這個小說,回家問父親,問出是《西沙兒女》。但當時這個小說已經被作為毒草了,圖書館是找不到的,于是,就跑舊書攤,居然真找到了。這本書,有兩種不同的開本,我找到的是一個小開本,后來還看到大開本,印刷紙張要好于小開本的。
我居然被這個書吸引住了。小說是以一種詩意一樣的語言,描寫了南海的神奇的風景和獵奇般的地域特點,前半部分是解放前打擊日本鬼子、保衛西沙的故事,下半部分是描寫打擊南越軍隊的故事。后來,我一直想弄明白,這個小說為什么是毒草,官方的書上解釋的大意是說,這里邊把一位女性阿寶作為女主角,影射著對的拍馬屁,小說中在寫到對人物產生精神影響的一首詩的時候,用了的“天生一個仙人洞”的詩,而這首詩是送給的。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這個小說中有什么惡毒的成份。也許至目前為止,它也是唯一一部表現對我國最南端疆域生活的一部小說。它把南海的奇特的自然現象,有機地融入到歷史的變遷和人物命運的走向上來,使其對兒童來說,就像《魯賓遜漂流記》那樣,帶著一種強大的誘惑的成份。
從后來的閱讀體驗來看,這個小說也是浩然小說中最洋氣的一部。他拋開了過去農村小說中的土氣甚至說政治氣太濃的特點,而在這個小說里玩了藝術一把,用散文詩體的風格,弱化了現實性的描繪,而采用了一種飄渺的寫意式的筆觸,展現了一幅輕靈的中國南疆保衛史的暄麗的楊柳青年畫。
我不知道這個小說將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如何,但它的唯一性是值得重視的。它涉入到一個中國文學從沒有涉足過的地域,真實地記錄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南海上發生的那一場不亞于八十年代初期南疆戰事那般壯烈的風云,而它對中國領土的界碑式的肯定,使這個小說即使在政治上可能犯有某種錯誤,但它的如同文天祥、岳飛是否是民族英雄的討論的答案一樣的鐵定的事實,都使它在主導方向是應該被中國文學史所記取的。
后來,基本在舊書市場上看到浩然的書,就買。居然湊全了《艷陽天》三卷,《金光大道》前二卷。《金光大道》第一卷缺少好的品相,磨損嚴重,我勉強用了幾本的舊書,才找到了一份全本。后來華齡出版社出版浩然長篇小說文庫,重新出版了《金光大道》全部,當時一直惦記著要買一套,但懾于當時上學時的拮據,一直沒有買成,后來沒多久,突然間發現這一套書不翼而飛,跑了所有的書店都看不到任何一點影子,出差時,也時常到書店里找找這本書,但似乎它們約好了突然失蹤似的,再也沒有見過。不知道是賣光了呢,還是被雪藏了呢?總感到奇怪,這樣的書,不會這么熱銷吧。
倒是華齡版的浩然的小說文庫的其它品種如《迷陣》,經常在半價書市上見到,我只好湊合著買回來了。
五、關于小說《金光大道》
在看電影之前,我看過《金光大道》,說實話,閱讀的趣味明顯低于《西沙兒女》。
在痛苦的閱讀中,我只能稱之為這是一部奇書。
一個用稿紙寫作的上個世紀的作家,居然有耐力、有激情、有沖動,寫出這樣一部長篇的農村小說,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是一種奇跡,正如作者浩然自己所說的那樣。這樣的小說對于中國文學畸形不發達的國家來說,實在是一種不可多得的奇跡。
中國的文學從魯迅的《狂人日記》開始,才真正地實現了與世界文學內質上的接軌。當然,你可以說,中國有《紅樓夢》,但是那個小說里邊有沒有一點現代人感情?有沒有一點對人物心理的深刻揭示?直至多少年后,巴金在小說《家》中的卷首說出“青春是美好的”這一幼稚的判斷,還被作為經典佳句被人傳誦。在中國文學剛剛邁出瘦弱的步伐的時候,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等一大批外國作家,卻已經寫就卷軼浩繁的作品,表現了廣闊的社會、鮮活的思想與深刻的人性溝壑,這些作品對社會的描摹與刻劃,即使在相隔二個世紀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在那些遙遠的文字中觸摸到一顆活著的靈魂與相通的思想情境。
在中國的文學中,看不到真正的低層的人民,看不到對下里巴人的生活的真實寫照,那種下層人民的相互憐憫、相互關愛的真摯情感,由于漢語言的高高在上的特質,還無法被記錄在案,使中國文學中充斥著大量的貴族紳士無病呻吟的垃圾。當今天書店里一排排地陳列著的中國百部古典文學名著的時候,你甚至提升不起一起購買的欲望,在那種幾乎完全是克隆才子佳人千篇一律模式的所謂小說中,你看到的是一樣的沒有現代人物感情的男女,看到的是低劣的故事大于思想的刻劃的乏味情節,特別是其中的霉變的主題意旨,就像你必須讓自己整天泡在三寸金蓮的博物館里而受不了臭氣熏天的步步相逼,最終你不得不突圍而走。在最近一部的古典小說《孽海花》中,你根本感受不到早已出現的托爾斯泰、雨果小說中的那種美好的人文之氣,依舊是一股俗不可耐的舊式的對女人的白描式的皮囊表相。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就像被囚禁著地心深處,似乎一直等到魯迅喊出“救救孩子”的那一聲驚雷裂帛般的吶喊才會爆發出來。
把《金光大道》放在遍地狼籍的垃圾文學群落里,我們實在感到這樣的文學的石破天驚的意義。僅就公開出版且當年廣為流傳的前二卷小說中,作者以一種上識天時、下窮人事的氣魄,細膩、細致地刻劃了鄉土農村的各種人等。
浩然小說采取了中國傳統的白描敘事筆法,以對話展開故事的進展,雜以謹慎的心理議論,淋漓地繪制出農村一幅幅有血有肉的風俗畫片斷。
如果說王朔運用了口語化的敘事方式,那么,浩然同樣是一個用口語代替文學敘事的作家。這樣敘事方式的基礎,就是作者對大量農村口語的熟稔掌握。這突出表現在浩然除了對人物對話進行了生動的口語還原外,還在對小說的主體敘事部分,也采取了口語化的表述,這使得浩然的這種政治化小說,最大限度地拋棄了現行政治的說教與鸚鵡學舌的笨拙,這一點顯示出浩然與同時期的任何一部此類的政治圖解小說相比都來得更加生動,也最缺少政治幫閑的丑惡面孔。
不僅在語言上,而且在人物的心理上,浩然完全把他的鄉村奉為中國的中心,所以,他筆下的農村舞臺幾乎成為尺幅千里、人情練達的最美好的境地。他的鄉村濃縮了中國人情最美好的結晶,聚集著最優秀的精英,密布著一個社會據以成立的各種富有特色的人物,在作者展開的一幅幅畫卷中,可以對應地讀解到任何一個大千社會里雜色人等,這使得浩然的鄉村成為一個具有跨越時空價值的中國社會的標準范本。我想,這正是浩然的小說歷久彌新、且永遠散發出藝術感染力的原因。
浩然的鄉村敘事筆法以及鄉村視角,奠定了他的小說成為最偉大事件、最優秀人物的聚集所,所以,他小說中的鄉村具有一種強大的感召力與號召力,使人物最大限度地摒棄了農村小說中通常具有的對農村悲天憫人的情懷。在浩然的文學視野中,農村是世界的舞臺中心,而小說中涉及的城市生活,永遠不具備對農村人物的任何吸引力。這一點,如果我們比較柳青的《創業史》就可以鮮明地看出與浩然的迥異來。柳青的敘事語言完全是一種知識分子的書面語,他所描寫的農村,始終受到城市生活的挾迫與壓力,他書中的人物,一個典型的選擇就是如何應對城市生活的誘惑。像《創業史》中的梁生寶的戀人改霞根本不具備浩然筆下農村姑娘的那種安居樂業、以農村為最終選擇的坦然與命定,而是始終徘徊在鄙視農村生活而向往城市生活的那種與小說主題相違背的憂傷與痛苦中,這種憂傷與痛苦也鮮明地通過小說,傳達給讀者,使人感受到作者筆下的農村所無法擁有收斂其農村優秀人才的磁力。
實際上,離開了浩然的文學作品,農村生活在作家的筆下,往往是被拋棄了的對象。這種典型的選擇的艱難,以路遙的《人生》最有代表性。在他的小說中,城市生活欺壓在農村生活之上,小說中的高加林在農村姑娘與城市姑娘的搖擺不定的痛苦抉擇中,始終把農村作為一個丟棄的目標。
而在這樣的同時期有《創業史》、后有《人生》這樣的始終悲憫地注視農村的文學理念的情況下,我們來看看浩然執著地把農村生活與農民視野作為他小說天經地義的圣經,就可以看出這種理念,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既沒有先例,也缺乏后來的承繼者。你可以說這種主題與立意是一種陳腐與落后的表示,但幾千年來從來沒有進入過文學的視野、且從未占據過文學表述的主體的農民,第一次在浩然的小說中,以一種勿庸置疑的堅定與強硬得到表現,這是這樣小說的一個拍案驚奇之處。
通常意義上農村小說中的青年人往往是背叛農村的主導力量,上面我們舉例有《創業史》中的改霞與《人生》中的高加林。而青年人中,尤以農村姑娘的選擇更能反映出鄉村的價位所在。而浩然筆下的姑娘們,始終把她們的愛情奉獻農村社會中的最優秀的人物,始終以簡單的直率的心理愛惜著農村的氛圍。他小說中的姑娘最少城市人觀看農村人的小芳情結,最少那種賈寶玉看到襲人的表妹們身在山野居然也靚麗可人的虛偽憐憫,他把小說中的女孩被描寫成在鄉村中得到最青春的美好表現,這在《艷陽天》的焦淑紅與肖長春的愛情中,得到了最深刻的揭示。在《金光大道》中,浩然也以不經意的筆觸,表現了鄉村女孩周麗平、巧桂等美好的農村姑娘形象,他們絲毫沒有經受到城市生活的誘惑,其中周麗平在鞋廠里作為臨時工的身份,還有勇氣、膽略與不法奸商作堅決的斗爭,這樣的農村女孩,她把她的心靈歸宿與砝碼始終放在鄉村的價值準則這一邊。
浩然的這種中國歷史上首次以農村的視野作為文學立論的主調的樣式,在某種程度上講,是一個時代精神的折射。在同時期的《五朵金花》、《劉三姐》等流行樣式的影片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一種以鄉村精神作為主旨的人文關懷,《五朵金花》里的城里采風的藝術家們,成為鄉村愛情的觀望與贊譽的局外人,他們根本無法插入到鄉村愛情的進程。《劉三姐》中的女歌手的愛情始終在鄉村里的同村的男青年二牛身上,得到回報,而那些貴族紳士企圖對她的占有,在鄉村精神的強大的正氣面前,顯得是如此的猥瑣與狼狽。這是浩然時代的一種集體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文學在進入到僅僅與浩然的文學作品相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藝術作品的主旨卻發生了耐人尋味的悄然的嬗變。在《白鹿原》中,地主的生活方式被作為鄉村溫馨的一種典范,而低賤的長工再也不會在自己的同類中找到愛情的共鳴,而把覬覦的目光瞄準向地主家的女人。這種逆反地對農村生活的鄙視轉而悲憫地站在上層貴族的層面,揭示農村低賤人士掠取女人、財物,在《大鴻米店》中得到了最集中的反映。從某種程度上講,優秀的品質在文學作品中已經從浩然時代的農民層次,轉移到過去的高貴階層。對義和團的視角的轉變、對農民的鄙視轉而對地主的同情,都深刻地反映出一個時代的立場的位移。從這個角度上講,浩然對農民視角的張揚,反應出中國文學所能達到的一個對農民進行劃時代首肯的最高極限。正是在這里,構成了浩然作品的“奇”字來。
中國文學多年來深受其害的政治因素,可能使浩然當年獲得了某種益處,但同時,這種政治的戕害,也使浩然作品中的值得珍視的農民視角曇花一現地被忽略了。畢竟相對于中國異常空白的平民文化的尷尬,浩然起到了填補盲點的作用。不管農民視角是否被這個時代重視與否,畢竟在中國文學史上曾經有人真誠地記載過農民們的思考、情趣與生存的天地。這一點,將是浩然在中國文學史永遠不曾泯滅的價值。
六、關于電影《金光大道》。
電影《金光大道》上集,改編自當年出版的小說前二部。中集,改編自當年沒有出版的第三部。可以說它是電影比正式出版的小說早半拍的一部電影。
上集集中表現了從互助組到合作社的發展歷程。下集則反映了是否是走投機倒把的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中集之間,還是有著明顯的故事區別的。因為上集結束,合作社成立,是否單干已經沒有再爭論的必要,所以中集把走什么樣的道路擺上了位置。
影片是通過人物之間的抉擇來體現它所圖解的歷史的必然的。它的基本構架,就是它所設置的人物,經過痛苦的實踐與血淚的教訓,選擇了影片中所確定的金光大道——也就是合作化的道路。
在上集中,影片中通過高大泉的弟弟高二林分家、劉祥作為困難戶的代表而堅定地走向互助組,以及劉萬單干致使妻子死亡等一系列鮮明的對比,來表現了互助組的優越性。
這一模式,在中集中繼續得到強化。中集中已經解決了高二林的回到正確道路上的問題,著重表現了一個叫秦文吉的農民,走資本主義道路所帶來的離婚、失事等困境,以此來闡明走正確道路的必然性。
影片所設置的事例,呈現出一種強烈的對比效應,把兩種不同道路的兩類人的結果強烈地擺放在一起,以此來不言而喻地闡明影片的主題。
影片鏡頭樸質,但也不乏技巧。在段落之間的跳躍與省略之間產生巨大的彈性與空間,使影片呈現出一種明快的節奏,著重把握住主線,松弛相間,收放自如。電影對浩然的冗長的不厭其煩的描寫,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編,把中心細節提煉出來,組織成可視的畫面。
正像中國的紅樓夢中所習慣對人物姓名進行隱射一樣,《金光大道》中的人物也帶有這種機械的影射的特征。如高大泉幾乎成為作品“高大全”的代名詞,影片中的反革命分子“范克明”就是反革命的諧音,沈記掌柜“沈義仁”無疑就是生意人的代名詞。
高大泉的這一形象,影片塑造得頗有光彩。從某種程度上講,他是一個三突出的典型,但小說仍至電影,在突出他的高大形象的同時,仍然沒有脫離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的喜怒哀樂。
“三突出”這一概念的是非功過,自然有歷史去裁定,但它作為一個藝術的概念,是否就沒有一點現實的意義?這我們在上面闡述過。
影片在塑造高大泉的形象時,始終把他融匯于鄉土環境,反映了他的高瞻遠矚的動機都是幫助鄉親們如何克服困難,過上幸福的日子,這一定調,就把這個人物完全納入到人性化的塑造動機里來。
看到有人說高大泉這個角色沒有特點,沒有個性,其實,這并不能反映電影實際上形成的最終效果。影片通過一系列精練的細節,反映了這一人物的關愛鄉民、作風正派、挺身而出的高貴品質。如他把自己家的糧食幫助窮困斷糧的劉祥,幫助劉萬干活,危急關頭托住傾復的大車,以及跳進急流搶救落水的鄉民,這一切,都使他的出現,給人一種異常光彩的感覺。這也是我們在好萊塢類型電影中經常接觸到的振臂一呼、應者云集、拯救世界的那種超人的英雄形象。
在嘲弄影視作品的文章中,往往不能切中要害地任意上綱上線,如最常見的評論,就是說什么龍江頌的江水英看不到丈夫,海港中的女主角似乎單身一人,紅色娘子軍沒有愛情描寫等等,實際上,一部電影是否都有必要把家庭納入到故事中來?與紅色娘子軍中沒有愛情的空白相比,現今的一些軍事題材影片無一不是在電影漾入愛情的作料,像《DA師》等電視劇中,都把粉紅色的愛情作為綠色軍營里一抹浪漫的紅暈,最后卻深受觀眾的詬病。沒有愛情的軍事片是否就不能塑造出人物,是否就沒有吸引人觀看的看點?我想是否定的,在美國電視劇《兄弟連》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一個完整的女性形象,都是清一色的純粹的美國大兵,但卻深深地吸引了中國觀眾的視線,幾乎無一例外地得到了中國觀眾的好評,我想,粉紅女郎的加盟,并不是電影人物關系合理性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吸引觀眾的眼睛的不可或缺的調料。
因此,略去愛情的松散與冗長,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人物的主要行動中,并不一定影響一部藝術作品的精神品位。
影片中,高大泉與妻子的那種沒有溢于言表的恩愛之情,還是通過有限的鏡頭,得到了最東方化的表現。在期間,能如此點到為止而又恰到好處地表現出這種夫妻的人倫親情,實在令人感到是一種奇跡。這種愛情符合東方人的收斂特點。如高大泉夜里到地里干活,影片在音樂聲中,表現了由王馥荔扮演的妻子突然出現在車子后邊施以援手,然后在兩人深情地相視而笑的鏡頭上,把那種相濡以沫的情愫得到了非常美好地表現。
在高大泉的勞作的過程上,他的兒子小龍的天真可愛的表現,可以讓人深刻地體味到他身上的父子情深的所在。這種情在影片中的畫龍點睛的寥寥幾個鏡頭的交待中,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根本看不出這是一部具有某種政治圖解的電影。人物永遠是電影成敗的關鍵,它承載的主題可能事過境遷,失去了討論合理性的必要,但它留下的人物形象,將超越政治的是與非,而帶有永恒的感染人的價值。
在影片上集中的一個勞作的鏡頭中,影片中一個表現小龍跟著大人后邊,非常懂事地把種子用手埋入泥土的鏡頭就給人一種驚鴻一瞥的震撼感。在這里,體現出一種對鄉土勞動的熱愛之情,對土地的熱愛之情,以及一個農民的后代那種受上輩人感染的對于土地養家糊口的渴望之情。這一切,都被影片深情地表達出來了。
在影片中,我們還可以感受到高大泉那種人格魅力所產生的巨大的影響。作為反面角色代表的張金發雖然是高大泉的斗爭對象,但高對張金發的女兒巧桂卻是關懷備至,和顏悅色,非常具有人情的美好。在中集中,他們一行運糧進鎮,表現高大泉關心巧桂的那一節非常有意思。高大泉拉上巧桂,問她:“冷不冷。”“不冷。”“不冷怎么打哆嗦。”“哆嗦也不冷。”把孩子氣的小女孩的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而同時作為長輩的高大泉的幽默寬廣的性格也得到了涉筆成趣的揭示。
在《金光大道》中,我們看到了最少限度的虛假,影片的時代的做舊氣氛,基本讓人覺得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事情,而與此相反的是,近期拍攝一些建國前后的影視作品中,人物濃裝艷抹,虛假造作,與影片中的那種樸質的場面幾乎不能相差好幾個檔次。
因此,這個電影畢竟記錄了歷史上中國人曾經有過的思考與努力,記錄了在大背景下的農民們為了一個目標而作出的艱辛的拼搏,它所體現出的細節中的人情的美好,是不應該隨著某種政治概念化的弊端而被掩沒。我們應該尊重上一輩人所作出的努力,以及藝術家們為了這種精神而付出的真誠。
七、電影的導演
影片的上集導演是林農與孫羽。下集是孫羽。
林農曾經導演過《兵臨城下》、《甲午風云》,孫羽在這之后導演過《人到中年》、《丫丫》等影片。
影片的鏡頭調度相當嫻熟,注重運用特寫,切換快捷,基本沒有冷場的鏡頭。其成熟的水準比七十年代后的電影要高出許多。有一度時期,內線電視上放映了七、八十年代的電影,其實有一部可能叫《元帥與士兵》,表現關心運動員的故事,人物動作呆板,完全可以看出一個個鏡頭拼揍起來的生硬感。七、八十年代是中國電影全面滑坡的時候,到九十年代就積習難返,令觀眾棄之如弊履了。
影片還根據農村片的特點,在里邊增加了幾場小噱頭,為影片增添了幾分輕松幽默的成份。如秦富與劉祥簽訂合同準備買房里,這時高大泉進來,秦富跑到窗戶上觀看,一抬頭,撞到額頭,作痛苦捂頭狀,令人發笑。這一切在小說中是沒有這個撞頭的情節的,完全是根據電影的故事的需要,而設置了這么一個小動作。
還有劉萬痛恨秦富的自私行為,一拳把他打倒,倒在水田里,也令人感到滑稽可笑。
秦富的兒子文慶與嫂子聯手頂撞他,秦富舉棒欲打,但叔嫂不相讓,秦富無奈,只好叫老婆應聲蟲出來,命令膽小怕事的老婆:“你給我打。”把一個權威日益喪失卻還死要面子的農民表現得入木三分,活靈活現。
影片中還罕見地表現了開夫妻之間的玩笑。影片中,高大泉與妻子手拉在一起,突然進來的朱鐵漢開玩笑地說道:“行握手禮了。”這也許是那個時代最涉及到男女之間葷話的玩笑了吧。
剛剛看到《電影藝術》第四期上有《金光大道》編劇肖伊憲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工農兵”電影的概念,并且把這一概念與張藝謀為代表的第五代電影作為中國電影的一個階段,反映了這個老編劇對他從事電影時代的一種別有用心的肯定。此為題外話,不多講。
- 上一篇:在選調生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
- 下一篇:經濟學與倫理學分析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