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電影時代電影的“真實性”
時間:2022-01-10 10:16:30
導語:數字電影時代電影的“真實性”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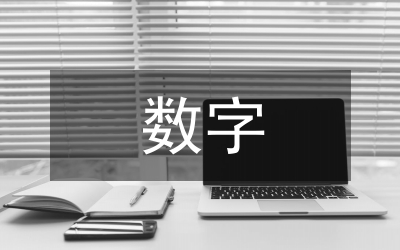
摘要:電影作為一門視聽藝術,從誕生之初到后期發展完善都得益于技術的發明與進步。尤其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數字化電影發展迅猛,在整個電影行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新的數字技術沖擊了傳統的電影產業,大量特技的使用,拓展了人們的想象空間,電影的“真實性”再次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關鍵詞:電影;真實性;數字化;藝術;技術
對于傳統電影來說,“真實性”是其重要的美學范疇。即使電影自誕生之初分裂出兩條不一樣的道路,以盧米埃爾兄弟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和以喬治•梅里愛為代表的造型主義,“真實性”始終是其共同的客觀基礎與現實依據。但是,隨著電影進入數字化時代,甚至當傳統電影的物質技術基礎———攝影機和膠片可以被完全取代之后,大量由電腦加工合成或者由電腦直接生成的數字影像的出現,電影的“真實性”開始受到挑戰。電影與真實的現實生活之間的聯系不斷弱化,數字技術挑戰了傳統電影表現形式的極限,也使得經典電影理論受到一定質疑。在數字時代對于“電影是什么”這一本體論的問題進行再度思考,直接關系到對于數字時代電影本性的認識。
一、“影像本體論”并未走向解體
“影像本體論”是巴贊電影美學體系的哲學基礎,主要探討了影像與現實的關系問題。巴贊認為,電影與攝影技術的出現,是人類追求逼真的復現現實的產物。這種復現現實的沖動起源于人們心中的“木乃伊情結”。“影像本體論”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可以說是對于傳統早期電影的本質性總結。自1895年電影誕生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近一百年的時間里,“影像本體論”因為符合當時所處時代電影的整體創作狀況,總體上被理論界所接受。即使后期遭受到結構主義學者和電影符號學家的批評,其經典地位依舊不可動搖。但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IT行業飛速發展,CGI技術大規模介入到電影創作領域,甚至CGI完全不用攝影機參與便可直接創造出像傳統影像同樣逼真的圖像來。數字電影時代的到來使人們深信不疑的“影像本體論”面臨著重大挑戰,甚至不少學者紛紛提出,巴贊的“影像本體論”已經走向解體甚至過時。這一觀點是非常武斷的。在數字電影時代,需要對于“影像本體論”進行重新審視,它并未走向解體,依舊是傳統電影理論最為穩固的基石,仍對數字電影具有指導意義。首先,在解讀巴贊的紀實美學時,應當客觀而全面地認識巴贊所提出的“真實”。巴贊紀實美學的核心應當是一種“真實觀”,是哲學和心理學層面的真實,是社會和心理情感上的真實,并不僅僅是攝影機所拍攝出的真實。正如宗白華所言:“藝術的模仿不是一種徘徊于自然的外表,乃是深深透入真實的必然性。”[1]巴贊強調的“真實”,從來不是單純的對于外表的單純復制,而是指對于人們心靈產生的意義。其次,要正確地解讀“電影是現實的漸近線”這一觀點。“漸近線”是指無限接近、永不相交的兩條曲線。巴贊在提出這一觀點之初,就表明了他從未提倡絕對的真實。電影作為一項創作活動,是以內在的尺度來創造真實,這是一種藝術真實而非生活真實本身。電影與現實或者說真實之間,始終無限接近,卻從不可能重合。這兩者之間的差異,表明電影作為藝術,表現“真實”時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而這差異卻恰恰是藝術存在之根本。當年盧米埃爾兄弟未經處理過的影像雖激起一時的驚嘆,但觀眾很快就將其拋棄,尋找更有表現力的影像。再次,巴贊對于真實程度的論述也應當重視。巴贊意識到電影像其他藝術一樣,必然牽涉到一定程度的選擇、組織和闡釋。他認為電影制作者的價值觀必然會影響其感知真實的方式,這些變形不僅不可避免,甚至大多數還是值得提倡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德西卡的《偷自行車的人》以及德•桑蒂斯的《羅馬11時》,兩部作品在用紀實手法摹寫戰后意大利社會現狀時,雖然都從社會新聞中提取了電影的主要情節,但是在實際創作中卻增加了一些戲劇性的情節,例如《偷自行車的人》中最終父親偷車的情節,《羅馬11時》中不同女性的戲劇化遭遇。但這些變形并非是對于電影真實性的侵害,他們依舊能讓觀眾目睹和感受到戰后千瘡百孔、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因此在電影創作的藝術化過程中,電影既不是對于物質世界完全客觀的記錄,也不是對其象征化的抽象,而是在原始生活和傳統藝術的再造世界之間占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所以,電影創作者對對象世界的理解、反映、闡釋,只要合情合理,他的電影“作品”就具有“真實性”的品格,而具有“真實性”品格的作品,才會讓觀眾產生信任感及認同感,從而獲得精神上的享受。同時,巴贊對于新技術的出現也是包容的。巴贊在論述電影演進歷史時曾指出,基本上每一項技術革命都將電影媒體向寫實主義的理想推進了一步。所以,當我們重新審視巴贊的“影像本體論”時不難發現,巴贊強調的其實是“真實觀”,而不是指攝影機這一“真實的表現手段”,這種“真實觀”是心理空間的真實。因此,數字電影所創造的影像,對巴贊的“真實觀”不構成根本性的威脅,“影像本體論”也從未走向解體。
二、數字化對“真實”的還原與延伸
電影作為藝術與技術的結晶,技術的完善從未阻止過電影藝術的進步,雖然并非所有的技術都能進入電影本體,但是在這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技術的完善使電影的面貌煥然一新,也越來越接近“真實”。在默片時代,電影攝制者為了使無聲電影獲得音響、獲得音響效果、獲得音響形象付出了不懈努力。直到1927年《爵士歌手》一片的出現,才漸漸使得電影擺脫了單一造型手段的困擾,從而使視覺藝術真正轉變為視聽藝術。聲音進入電影創作后,縮小了電影的假定性,增強了現實性,開啟了電影歷史的新篇章。同時,在電影發展初期,銀幕只能用黑白表現現實生活,顏色的失真使得人們不斷嘗試為電影著色。在彩色片主導銀幕的今天,許多電影只有在表現獨特的形式與風格追求時,才會采用黑白攝影。究其原因,也是緣自觀眾內心對于“真實”的渴求。綜上,通過簡單回顧數字電影時代來臨之前幾次重大技術變革可以得出,技術的進步始終都在擴展著電影藝術表現力的范圍,使電影越來越接近現實生活,“真實性”不斷增強。而數字化更是對于“真實性”進行了拓展。愛因漢姆曾在《電影作為藝術》中列舉出了電影影像感知方式和日常生活中感知方式的六大差異。數字電影時代縮短甚至消解了這種差異,尤其是在3D電影出現后,二維畫面得到解放,更具立體感。甚至在VR技術逐步發展、開始介入電影創作領域后,限制的邊框都已不復存在。1946年,巴贊曾提出“完整電影神話”這一觀點,他指出:“電影這個概念與完整無缺的再現現實是等同的;他們所想象的就是再現一個聲音、色彩、立體感等一應俱全的全部世界的幻景。”[2]人類想要獲取外界的信息,最重要的媒介就是視覺和聽覺這兩大感官。技術的變革使得電影最大程度再現了視聽信息,這是電影讓觀眾產生“神話”理想的最重要的原因。而數字電影的出現以及普及更加使電影向“完整電影神話”逼近,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首先,影像的結構更加真實。在數字時代,新技術雖然影響了電影的知覺式樣,改變了電影的拍攝對象、拍攝方式以及影像的生成媒介,但是,電影最終呈現在觀眾眼前的動態聲畫的影像媒介屬性并未發生改變,電影的敘事任務、電影美學與電影語言的傳達意義也沒有被改變。與照相機相比,攝影機所拍攝的運動影像讓觀眾產生了真實的感覺。進入數字技術時代,尤其是當3D電影出現后,畫面不僅呈現運動狀態,而且縱深感更加強烈;巴贊所推崇的長鏡頭賦予了觀眾對真實感受極大的自由度,而3D數字電影將畫面從平面運動推進到立體運動,對現實進行了突破性的再造與描摹。因此,技術的進步實際上是使觀眾與影像的關系更為貼近他們與現實的關系,影像的結構更具真實性。其次,新技術的發展反過來對“真實”的現實進行再創造。英國后現代消費文化理論家邁克•費瑟斯通曾說過:“在消費文化影像中,在獨特而直接產生的身體刺激與審美快感的消費場所中,情感快樂與夢想欲望總是大受歡迎。”[3]如今技術的發展,使得一部分“美夢成真”。影像與現實的關系甚至發展到“模型先行,現實跟隨”。電影中所創造的奇幻世界對觀眾內心產生實際影響,誘導現實中的人與事物去追隨影片中所營造的虛幻世界。著名的迪士尼樂園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迪士尼樂園中,屬于影像中的幻覺成為真實體驗,觀眾變身游客,進入由童話角色構成的世界。在這里,幻覺與現實的界限消失,這個世界“不是為了掩飾現實的不在場,而是為了重新創造現實的仿擬,首先將不存在的事物表現為存在的、將想象的事物表現為現實的,繼而它還試圖去同化現實,將現實吸融進自身”[4]。除了迪士尼樂園,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在數字技術應用最多的科幻片領域,影片中有些令人驚嘆的科技發明正在現實中真實產生,并改變現實生活的進程。雖然影像的“能指”漸漸不再依附于現實的“所指”,數字電影中產生的模型或是幻想在真實的世界中逐漸找不到基礎與原型,但是這些影像并非沒有力量,反過來推動了現實的發展,甚至已經開始逐步邁入“生活模仿藝術”的時代。
三、對數字時代電影美學走向的幾點思考
愛因漢姆曾在《電影作為藝術》一書中指出,技術的不斷追求是做到現實的最大程度逼真化的保證。近年來不論是國際電影市場還是國內電影市場,數字電影所掀起的浪潮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有目共睹,數字化手段的運用越來越深入電影制作甚至成為觀眾品評一部電影作品好壞的標準。在數字電影突飛猛進、大刀闊斧地改造著傳統電影時,我們應該保持清醒認識,理智對待這一潮流。首先,對于數字技術本身,我們應該認識到,今天數字影像與現實的關系和觀眾的關系早已超出單純的技術領域,呈現出復雜的文化關聯。數字技術作為一把雙刃劍,應該承認其積極的、正面的影響。數字技術幫助人們再現了歷史、記錄了現在、創造了未來,并且數字技術在應用時,事實上與傳統的紀實電影的美學追求是基本一致的,盡管數字技術繪制的是某種虛擬影像,但在追求“真實”的精神上并沒有太大差別。同時,技術雖然會使真實疊加,但是并不一定會生成真實感。真實感更源自內容與呈現形式完美搭配。不可否認的是,數字技術也會產生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不是說單純地為了技術而忽視電影本身內容的那種負面影響,因為造成單純強調技術,而忽略影片質量的始作俑者是人,而不是技術本身所攜帶的缺陷。這里所說的負面影響,是其對于我們的認知方式與思維方式所造成的影響。當數字技術能夠越來越接近現實,從傳統的二維到三維,甚至VR逐漸從游戲領域進軍影視領域,電影與現實的這兩條“漸近線”甚至開始異化,接近重疊。面對數字技術難以估量的發展前景,我們擔心的是,“超真實”出現后,未來的數字影像是否會通過技術理性暗中將大眾浸染為視覺與幻覺的機器人。當真實與幻覺混為一體真假難辨,觀眾能夠隨意進出虛擬與現實之間時,人類的思維方式與對于現實的把控是否能夠守住理性的防線,走向一個更高意義上的超越現實的自由的審美境界,還是在幻境中迷失與沉淪?與此同時,在這種對于以好萊塢技術大片為代表的強烈推崇下,那些樸實的現實主義影片與不夾雜任何炫技般光影效果的文藝片的生存空間是否會越來越狹窄?這種技術狂潮對于人們審美趨向的影響所帶來的問題已經在國內電影市場初露端倪,這些問題必須得到重視。其次,應當引起注意的是,作為新技術使用者的電影制作者對于數字技術抱有的態度。數字技術進入電影領域似乎比電影史上任何一種新技術推動電影的變革進程都輕松得多。在《雨中曲》中戲謔地演繹了聲音進入電影的歷程,聲音進入電影在當年遭到了諸多默片大師的反對,觀眾也認為這樣的影片難以接受。但是反觀數字電影,它進入電影似乎過于順利。確實,從制作成本與拍攝角度來看,數字技術解決了諸多難題。但是,這一跨越過于快速,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短短20余年,數字技術“血洗”膠片,大牌膠片公司紛紛倒閉,能堅持使用膠片拍攝的導演也屈指可數。從國內來看,近幾年王家衛的《一代宗師》、徐皓峰的《箭士柳白猿》、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與青年導演楊超的《長江圖》是為數不多的膠片電影。在國外,堅持使用膠片的導演代表則是昆汀•塔倫蒂諾、克里斯托弗•諾蘭、馬丁•斯科塞斯等人。這些大師級導演紛紛表達了他們對于膠片電影的迷戀與堅持。但是這樣的創作者畢竟在這場浪潮中是少數的存在。也許有一天膠片會從電影的歷史舞臺中退場,但我們希望能看到的是,膠片的美學不會消失,膠片所獨具的那種多層次、復合的、緩慢變化的質感,能夠在數字的自由度中繼續保留下來。所以,當數字電影這一潮流洶涌而來時,尤其是在數字技術普及后,甚至當觀看者都可以轉變成拍攝者時,作為電影制作者和愛好者的我們,對于數字技術必須抱有嚴謹的態度。本文從三個角度探究了數字電影時代電影的“真實性”。首先應當認識到安德烈•巴贊理論的復雜性,對于其經典理論進行重新審視與解讀,對其經典地位予以肯定與認可。其次,數字電影時代并未改變電影的“真實性”,反而是對于“真實”的一次延展。最后,對于新技術,作為觀眾與影視制作者都應當抱有謹慎態度。
參考文獻:
[1]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39.
[2]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17.
[3]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19.
[4]鐘麗茜.從數字影像到符號經濟———論數字技術對傳統電影美學的沖擊[J].文藝論叢.2012(7):134.
作者:馮碩 單位:蘭州大學
- 上一篇:“沖奧”電影文化視點變遷研究
- 下一篇:電影鏡頭在電影攝影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