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流電影敘事策略與創作探討
時間:2022-08-03 09:43:35
導語:新主流電影敘事策略與創作探討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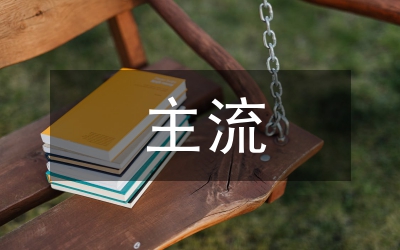
【摘要】隨著國家打贏脫貧攻堅戰,新主流電影占據電影市場的核心位置,“國慶檔/賀歲檔+新主流”模式應運而生,商業與主旋律電影逐漸融合形成國家主流與商業電影并存的創作新格局。“我和我的”系列電影以集錦式單元電影獲得近兩年新主流電影的高口碑高票房,《我和我的家鄉》緊扣脫貧攻堅時代主題,勇于創新脫離傳統主旋律電影創作的窠臼,將主流意識形態傳達與受眾審美有機結合,以輕松幽默的喜劇風格將充滿生活氣息的小人物故事贊頌全國脫貧攻堅的偉業。本文將從個體化敘事、喜劇類型的探索與視覺奇觀美學三個方面進行的創新探索,為新主流電影在喜劇類型電影的創作過程中提供有效新形態。
【關鍵詞】新主流電影;個體化敘事;喜劇類型
一、迎合分眾視角:個體化敘事
近十年來主旋律電影受到商業電影市場的影響,國家主流電影與主流商業電影的新格局逐漸形成,盡可能協調國家意識邏輯與商業電影邏輯相統一,政治色彩在敘事主題中逐漸削弱,繼而轉向社會邊緣群體,將時代變遷下的小人物變為敘事主體,以一種平民化的視角描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真情實感,在敘事中主流意識形態、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滲入引起受眾的共鳴,達到主旋律電影與受眾間的共情,2020年的國家獻禮片《我和我的家鄉》中無論是從創作理念還是表現形式都發生了一定的轉向,在商業性與主旋律電影二者相互辯證關系中取得巨大的突破,受眾獲得巨大驚喜的同時也解構了主旋律電影在受眾內心“說教式”的刻板印象。電影通過熒幕講述發生在某人身上的某事都是相對具體真實的,“人”成為一種符號表征社會大部分人的縮影,通過電影藝術的渲染使受眾與熒幕中的人物建立認同,迅速帶觀眾進入熒幕鏡像。集體群像、群體事件同樣需要通過具體的人物單元進行刻畫,以達到觀眾通過某一人物的鏡像作用而產生情感投射。從傳統主旋律電影演化而來的國家主流電影,之所以更適應市場,很重要的點就在于其敘事策略的轉向,由家國集體的宏大敘事轉化為突出某個小人物的個體敘事,宏大敘事中的英雄轉化為個體敘事中的普通人,重點呈現普通人蛻變為英雄的成長經歷,塑造“個體化的新英雄形象”。[1]《我和我的家鄉》將較宏大的“國家”概念細化為風格迥異的家鄉,首先,截取時間長河中某個重要的事件作為敘事空間,“平民英雄”的呈現通過空間敘事將不同地區中個體人物形象進行塑造。其次,該影片在個體敘事層面也為人物行動線設置了合理的動機,家國不再是二元對立的狀況人物,無須在國家利益與個體利益間做選擇題,英雄的神性光環削弱,不再壓抑“人”的本性,建構人神相融合的新英雄形象,投身國家事業為祖國奉獻也由被動位置變為主動,不再弘揚犧牲個體造福全國人民,從而實現情感升華傳統主旋律敘事策略。影片中黃大寶這一人物行動動機十分貼合個體與集體之間的密切聯系,他在鄉村中堅持科技發明并運用當今最有效短視頻的傳播方式,“發明”UFO吸引廣大群體并引發電視臺的到訪獲得知名度,也為整個村莊帶來了一定的利益與知名度;馬亮放棄出國深造的機會而下鄉建設新農村,對家鄉伸出扶貧之手是一種私人情感投射,希望將稻田畫帶動整個家鄉的發展,彰顯對整個村的付出是潛意識中對家鄉情感的表達。
二、消解傳統模式:喜劇類型的探索
(一)“喜劇+主旋律”新模式填補市場空白。好萊塢的商業電影產業化飛速發展影響著世界各地的商業電影體系的發展。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受到好萊塢類型電影的影響開始走產業化發展道路,但類型化探索還未涉足至深。隨著內地與香港密切經貿關系的往來,眾多香港導演踴躍創作專屬的電影風格,娛樂元素類型被成功帶入新主流電影創作過程中,將主流電影以類型片承載主流價值觀的創作思路,使商業片與主旋律電影雙重訴求得以滿足。新主流電影在保證影片內容優質生產的前提下,將藝術審美和多類型混合敘事為載體,使主流價值觀滲透于商業電影之中。截止到2020年底,我國紅色電影題材類型已拓展到動作片、科幻片、災難片、動畫片、劇情片和戰爭片等多元化的類型范式,但青春片、喜劇片、愛情片等類型在新主流電影中還未涉足。2020年國慶檔《我和我的家鄉》橫空出世,一方面以“幽默+抒情”的創作風格填補新主流電影對于喜劇類型電影市場的空白,給觀眾帶來笑中帶淚的觀感體驗,另一方面為新主流電影類型的多元化發展提供創作新思路。(二)異軍突起的新主流喜劇美學風格。喜劇作為“表現底層人物之間的一段情節的戲劇作品,具有圓滿結局,追求真實性(有別于悲劇類體裁)。這類劇作總是引人發笑,而有實在的喜劇意義。電影中,這是一種定義模糊、范圍寬泛,但普遍流行的類型”[2]。“新主流”電影中的喜劇風格還未涉及過多的荒誕喜劇,浪漫喜劇與黑色喜劇是該電影的初次嘗試,該類電影通過塑造小人物的真人真事呈現當下大眾的真實生存狀態、集體心理期待以及社會文化并以此獲得大眾對此類人物的認同。首先,該影片在五個單元的存在明顯的喜劇標簽,因這一共性存在觀眾觀影過程中對不同故事銜接迅速辨別喜劇標識而不會產生跳脫感,能夠迅速接受引起令人發笑的喜劇效果。其次,在敘事策略上趨向相同,將喜劇套路的呈現發揮得淋漓盡致。巧妙運用喜劇中的誤會、反差、沖突、巧合等劇作手段,使主人公身陷不同程度的囹圄并逐漸增強,令挫折情境不斷加大以此形成喜劇張力,如陰差陽錯的代替表叔住院的張北京,吐露UFO真相的黃大寶,放棄留學建設美好鄉村與妻子產生誤會的馬亮。每一位主人公都不斷地解決問題再產生問題中,對于這些夸張與戲謔的窘境設置,使產生的間離效果不會讓觀眾產生同樣的憂慮。單元喜劇類型的風格化使導演風格在電影中無處不在,五位導演在創作過程中與主創人員以及導演本身代表作承接,呈現出多元化的喜劇美學風格。《北京好人》延續寧浩一以貫之的運用黑色幽默營造犯罪氛圍的喜劇風格;《天上掉下個UFO》中陳思誠運用“唐探”系列的喜劇人物組合,懸疑犯罪的風格削弱轉為以長鏡頭下歌舞MV效果營造歡樂的喜劇氛圍。《最后一課》中回憶與現實不斷交織如夢如幻,前半段以“懸疑+推理”的方式渲染氣氛,后部分則以“回憶+懷舊”的方式進行情感表達。《神筆馬亮》是典型的帶有“開心麻花”劇組風格的影片,彰顯其超高的喜劇水平,無論是馬麗與沈騰的經典組合,還是影片整體的烏托邦式的理想國的建構。
三、視覺奇觀美學:新媒體促進敘事
新媒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開辟了媒介升級的新境界,它的出現及發展成為大眾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的闖入者,并且扭轉了大眾的心理狀態與審美趣味,推動了社會飛速發展。融媒體發展勢如破竹,短視頻的出現使電影、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不再居于優勢位置,新媒體在競爭中共生,形成新舊媒體融合并存的多元媒體的新格局。多屏終端與跨屏合作成為生活常態,新媒體的升級已經使電影傳播形式悄然發生變化,傳統媒體的霸權主義被消解,觀影環境更為自由,大眾可以選擇更為私密的場景或環境中,去遴選、評論與再創作任意影像片段,影院與膠片電影不再成為電影放映的唯一載體。在新的媒介語境背景下,長短視頻、二次元文化、手游等網生代產物都在無意識中影響電影藝術的創作,受眾審美不可避免被控制。“新媒體作為一種文化意識形態的力量,倒逼著創作者在‘更改’作品由內及外的文化形態和美學樣式。這是一個微妙卻又醒目的現實。而且這種力量,既是一種營銷手段,也成為了逐漸成型的美學標準。”[3]《我和我的家鄉》成為近年來新主流電影的代表作,無論是在形式方面還是內容創作方面都融合了網絡審美的特征。一方面在敘事上貼合后現代碎片化的片段集錦式的敘事結構,該影片首次使用網絡流行豎屏短視頻的形式將電影的五個單元聯結,通過五湖四海的中國人對家鄉印象的回憶,成功消除五個故事間的區隔,增加其敘事的連貫性,使電影具有極強的新媒體色彩。另一方面在影片的內容層面,黃大寶與閆主播都是運用豎屏短視頻成功的網絡紅人、直播帶貨主播的新型職業身份出現在受眾面前,揭示網絡新型職業身份背后引起的粉絲經濟與電商時代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境界,“新媒體帶來了一種新鮮的趣味,這種趣味有別于傳統的敘事趣味,它在文本當中不斷地被強化。”[3]該影片相比之前的新主流電影,主創人員對網絡意識的敏銳性、媒介與電影融合是前所未有且極具前瞻性的,網絡形式的積極探索體現我國電影創作人員開始重新審視新媒體對電影創作、人物設置、電影審美的導向作用。綜上所述,《我和我的家鄉》是我國新主流電影喜劇類型探索的開拓者,以較高的創作水準優越的市場反饋得到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雙重豐收,成為主旋律題材發展過程中的優秀影片。但是在本片中依舊存在不足,比如影片將“家鄉”的范圍局限于“鄉村”,后農業時代的社會眾多人在文化意義上已經失去家鄉,對家鄉的概念十分模糊,每個人在文化意義的層面像孤兒一般,新主流喜劇電影需要在文化層面上建構一些形而上的家鄉概念,使更多的圈層都能喚起內心十分久遠的家鄉情,這也是新主流電影在日后創作層面需要思索的問題。在新媒體迅猛發展下中國新主流電影迫切希望將主流意識的傳遞與商業片間的創作難題,以具體可觀、真實的人物形象激發手中的觀影欲望,在探索受眾期待視野時要兼顧國內意識形態的輸出以及國外的中國大國形象與文化輸出,主動背負起新時代、新媒介背景下中華民族文化不斷前進的重任,正如周星教授提到的“期待中國的新主流電影不僅是‘簡單的政治正確’,更是成就經典,早日建構顯耀中華文化的‘中國電影學派’”。[4]期待在不遠的未來中國電影的主創人員能夠找到屬于中國電影的專屬類型與創作方式,能夠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發揚中國精神。
參考文獻:
[1]尹鴻.從2019年國慶檔影片分析中國主流電影形態重構[J].中國文藝評論,2019,(12):21-26.
[2]峻冰,酈沄.幽默俗俚的對白:當代國產喜劇電影的敘事與表達[J].學術論壇,2020,(12):3-10.
[3]張衛,陳旭光,趙衛防等.界定·流變·策略:關于新主流大片的研討[J].當代電影,2017,(1):6-20.
[4]周星.從主旋律電影到新主流電影:中國電影核心價值觀與豐富性發展之路[J].藝苑,2019,(6):6-9.
作者:臧悅 顏梓汐 單位:河北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 上一篇:中職化學教學問題意識培養意義
- 下一篇:虛擬仿真實訓環境建設與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