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化型搶劫罪研究論文
時間:2022-12-18 05:05:00
導語:轉化型搶劫罪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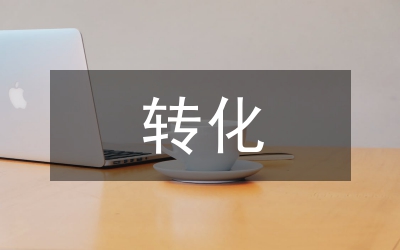
論文摘要:關于轉化型搶劫罪的停止形態,一直存在不少有待解決的理論爭議。從司法實踐看,轉化型搶劫罪的預備行為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對于這種預備行為,沒有必要將其作為搶劫罪的預備犯進行處罰。在滿足時間、自動性、有效性三方面條件的情況下,轉化型搶劫罪可以成立中止犯。對于轉化型搶劫罪既、未遂的標準,應以是否最終取得財物作為標準,但對于具有加重構成的轉化型搶劫罪,只要具備加重構成要件,不論是否取得財物,都成立既遂。
犯罪停止形態,是指犯罪在其發展過程中由于主客觀原因而永久停止下來的各種犯罪狀態。在刑法理論上,將犯罪停止狀態區分為完成形態和未完成形態。前者是指既遂犯,后者則包括預備犯、未遂犯和中止犯。按照刑法的規定,轉化型搶劫罪是以搶劫罪來定罪處罰,普通的搶劫罪存在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態,那么轉化型搶劫罪是否也存在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態呢?如果存在,成立的條件或者判斷的標準是什么?對此,刑法理論界還存在較大分歧和爭議。
一、關于轉化型搶劫罪是否存在預備犯的問題
對于轉化型搶劫罪是否存在預備形態,我國刑法理論界鮮有論及。現有的觀點大都認為轉化型搶劫罪不存在犯罪的預備形態。其理由大致為:刑法第269條規定的“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是指已經著手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的當場,才具備向搶劫罪轉化的前提條件。如果說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只停留在犯罪預備階段,即還沒有開始著手實施實行行為,就不可能產生轉化的情況。在先行行為的犯罪預備階段采取的抗拒抓捕等行為,其手段行為構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處理,但不構成搶劫罪。如果在后行行為處于預備階段,只是因為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著手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情況下,依據刑法典的規定,“當場實施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表明后行行為已經著手,其預備階段因為不具備轉化的客觀條件,所以就不可能轉化為搶劫罪。這種觀點實際上把先行的盜竊等行為作為轉化型搶劫罪實行行為的一部分,從而將先行的盜竊等行為的犯罪預備階段視為轉化型搶劫罪的預備階段。但是,如果從轉化型搶劫罪為身份犯的角度考慮,轉化型搶劫罪的預備行為并不等同于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的預備行為。這是因為先行的盜竊等行為無論處在何種停止形態上,其作用都是對主體附加一個作為轉化前提的特殊身份。而著手實行行為的起點是行為人給予特定目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在實行行為著手以前,行為人都可能為犯罪的實行作準備,而這可能是在先行的盜竊等行為未遂、既遂甚至中止之后。比如,甲入室盜竊,竊取財物之后準備離開,聽到另一房間內有人起床,甲擔心被抓,于是在房間內尋找可以用來行兇的器具備用,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停止下來。也就是說,行為人為可能發生的暴力、脅迫行為做準備的行為,并非一定是發生在實施盜竊等行為之前,也有可能是在實施過程之中或者之后。因此,從行為樣態上看,并不能完全否認轉化型搶劫罪預備行為的存在。但是對于轉化型搶劫罪的預備行為是否有必要將其作為搶劫罪的預備犯進行處罰,卻存在疑問。
對于這一問題,日本刑法學界在對事后搶劫罪進行研究時,給予了相當的關注。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是以日本刑法第237條搶劫預備罪的規定是否適用于事后搶劫罪為切入點。日本刑法第237條規定:持有搶劫犯罪的目的,并做過此種預備的人處以兩年以下的處罰。比如說,行為人企圖行竊時,考慮到可能被人發現,為免除逮捕,準備刀等兇器以備使用,這種行為可以理解成是持事后搶劫的目的而所作的準備。于是,刑法第237條中所言及的“搶劫目的”中,如果包含事后搶劫目的的話,行為人就構成了搶劫預備罪;如果不包含在其中的話,就可以否定搶劫預備罪的成立。對此,日本有判例(最高裁昭和54年11月19日決定·刑集33卷7號710頁)持肯定觀點,認為“刑法第237條‘搶劫目的’中,包含有刑法第238條中規定的以準搶劫為目的的情況”。在理論界,支持判例的肯定說占大多數,但認為事后搶劫的目的并不成搶劫預備罪的否定說也有相當的影響。肯定說與否定說從條文的位置、目的確定性、與身份犯之關系等方面,提出各自的理由。這些觀點不乏可供參考之處,但僅從這些方面看,還很難說哪種觀點更具優勢。
究竟采取何種立場,筆者認為,關鍵取決于轉化型搶劫之預備是否具有與普通搶劫預備同等的可罰性。預備犯因為對法益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所以應該遭到處罰。搶劫預備不過是暴力預備、脅迫預備,但是由于它的目的在于奪取財物,所以它便對財產法益產生危害,這可以理解為其可罰性的基礎。而轉化型搶劫的預備(如準備兇器),不過是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并不是為奪取財物而準備。因此,準備兇器行為,也不能說是對“財物”產生危害。即使是為窩藏贓物,為“強行占有”所作的準備和為“確保占有”所作的準備之間,在對法益侵害的因果力這一點上,兩者相隔甚遠,很難說兩者具有同等的可罰性。因此,從實質上考慮,否認轉化型搶劫罪之預備犯的成立,更為妥當。
二、關于轉化型搶劫罪中止犯的成立條件
轉化型搶劫罪作為一種故意犯罪,行為人能夠故意實施,就有可能“自動放棄犯罪”,因而犯罪中止形態有存在的可能。不過,由于轉化型搶劫罪具有轉化性、行為的復數性等特征,其中止犯的成立有一定的特殊性。如前文所述,轉化型搶劫罪的預備行為不具有可罰性,因此不考慮犯罪預備階段的中止。那么就可以推斷出,轉化型搶劫罪只存在犯罪實行階段的中止犯。轉化型搶劫罪中有兩個行為,如果停止只是先行行為,則成立盜竊、詐騙、搶奪罪的中止;如果停止的是作為實行行為的暴力、脅迫行為,就有可能成立轉化型搶劫罪的中止犯。但中止犯的成立,必須有兩個前提:其一,行為人并沒有最終取得財物;其二,行為人的后行行為尚未造成他人重傷或死亡。因為一旦行為人取得財物或造成他人重傷或死亡,就已經成立轉化型搶劫罪的既遂,而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轉化型搶劫罪中止犯的成立條件,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時間條件
轉化型搶劫罪的犯罪中止不同于一般情況下的犯罪中止,不存在犯罪預備階段的中止和犯罪結果發生之后的中止,其中止的成立只能發生在后行行為的實行階段,也就是只能發生在當場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過程中。這是成立轉化型搶劫罪犯罪中止的時間條件。應當注意,不能把行為人當場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后自動恢復原狀和賠償損失的情況認定為轉化型搶劫罪的犯罪中止,因為此種情形中轉化型搶劫罪的犯罪行為全部實施完畢,已經齊備了此罪的構成要件,犯罪已經既遂,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時間條件。但是這種自動恢復原狀和賠償損失的情況可以作為酌定情節,在量刑時給予考慮。
(二)自動性
要成立轉化型搶劫罪的犯罪中止,必須具備自動性條件,即行為人的主觀內容是自愿放棄非法占有他人財物或者抗拒抓捕、毀滅罪證的意圖,客觀上停止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行為的實施。行為人自認為能夠將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行為實施完畢,出于本人的意愿,而不是出于外界的壓力或自身能力的限制而中止的,就具備了轉化型搶劫罪犯罪中止的自動性條件。
(三)有效性
在轉化型搶劫罪實施過程中,犯罪未實行終了行為人就主動放棄了犯罪,并且以后也不再繼續實施,這種放棄意味著行為人主觀上真正地完全拋棄了犯罪意圖,客觀上徹底終止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行為,而不是暫時中斷,伺機再犯。
三、關于轉化型搶劫罪既、未遂的標準
對于轉化型搶劫罪,是否存在未遂犯,學界存在一定的爭議。部分學者認為轉化型搶劫罪不存在未遂犯。如有學者將轉化型搶劫罪視為行為犯,認為只要犯罪嫌疑人當場使用了暴力或脅迫,就可以認定為實施完畢并既遂,不存在未遂的情形。但是大多數學者則認為,作為財產犯罪,轉化型搶劫罪同普通搶劫罪一樣,存在未遂形態,需要研究的是轉化型搶劫罪既、未遂的標準問題。對轉化型搶劫罪既、未遂的判斷標準,綜合國內外刑法理論界,主要存在以下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轉化型搶劫罪只有在盜竊既遂的場合才能成立,其既遂、未遂的標準,應該根據盜竊者采用暴力、脅迫手段是否達到防止所竊財物被他人奪回的目的而定。如果財物未被他人奪回(目的已達到),那就是既遂。如果已被奪回(目的未達到),則是未遂。這種觀點認為只有基本犯罪既遂者,才可能構成轉化型搶劫罪,這是不符事實的。因為基本犯罪未遂者雖不可能出現為防止所盜財物被奪回而采用暴力、脅迫的問題,但為免受逮捕、毀滅罪證、窩藏贓物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則完全有可能發生,這當然也構成轉化型搶劫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以暴力、脅迫行為本身作為認定既未遂的標準。只要基本罪犯人基于刑法規定的三種目的而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即使基本犯罪是未遂,轉化型搶劫罪也算是既遂;只有著手實行暴力、脅迫而未遂者,才能視為搶劫罪未遂。這種觀點忽視了轉化型搶劫罪的本質是以財產權為主要客體的貪利犯。如果以是否侵犯人身權利作為標準,不免有本末倒置的嫌疑。而且按照這種觀點,本罪不可能存在未遂的情形。
第三種觀點認為,以基本犯罪的既遂還是未遂,作為認定轉化型搶劫罪的既遂、未遂的標準。即基本犯罪既遂后,轉化為搶劫罪也是既遂;基本犯罪未遂,則轉化為搶劫罪也是未遂。這種觀點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缺陷。首先轉化型搶劫罪是身份犯,它的實行行為是暴力、脅迫行為,以實行行為前的行為來決定轉化犯罪的既未遂,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持。其次,盜竊既遂之后,行為人為防止財物被奪回而當場實施暴力,但財物還是被奪回,若按既遂處理,也不合理。因為在普通搶劫的場合,最終未得到財物,一般只能算是未遂;而在轉化型搶劫罪中按既遂處理,不免有失公允。
第四種觀點認為,應當以最終是否取得財物作為轉化型搶劫罪既、未遂的標準。即便是基本犯罪既遂,如果采用暴力、脅迫手段沒有達到目的,財物還是被他人奪回,這仍然屬于搶劫未遂;如果基本犯罪未遂,為免受抓捕,毀滅罪證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盡管達到了這樣的目的,但由于沒有取得財物,也只能算是搶劫罪未遂。這種觀點是以暴力、脅迫行為實施之后,最終是否得到了財物作為既、未遂的劃分標準。這一方面不違反既、未遂只能發生在實行行為之后的理論,另一方面注重了轉化型搶劫罪所保護的法益,與普通搶劫罪的既、未遂標準相協調。但這種觀點沒有把轉化型搶劫罪中存在的加重情節區別開來,略顯不足。
轉化型搶劫罪是需要特定身份(犯盜竊、搶奪、詐騙罪的人)才能構成的犯罪,其實行階段始于暴力、脅迫行為,其犯罪性質與典型搶劫罪的基本相同。這對于我們正確認識該罪的犯罪形態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明確了轉化型搶劫罪的實行行為,實行行為的著手是構成既、未遂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由于轉化型搶劫罪在犯罪構成上與典型搶劫罪的性質基本相同,罪名上也與普通搶劫罪一致,因而在認定轉化型搶劫罪的既未遂時,也應當與認定普通搶劫罪的既、未遂相協調。對于轉化型搶劫罪既、未遂的標準,在基本贊同上述第四種觀點之外,本人還認為,有必要將具有基本構成的轉化型搶劫罪與具有加重構成的轉化型搶劫罪區分開來。對于具有基本構成的轉化型搶劫罪的既、未遂應當以是否最終是否取得財物作為既、未遂的標準。對于具有加重構成的轉化型搶劫罪,只要加重構成要件成立,而不論最終是否取得財物,都成立既遂。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不以是否最終取得財物作為判斷既、未遂的標準。如此,不僅符合普通搶劫罪既未遂的認定標準,也有利于科學地認定轉化型搶劫罪的構成,從而公正合理地確定刑事責任。
- 上一篇:財政部門科學發展觀整改落實階段工作總結
- 下一篇:刑事庭審方式改革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