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人作證豁免權探討論文
時間:2022-11-20 04:25:00
導語:證人作證豁免權探討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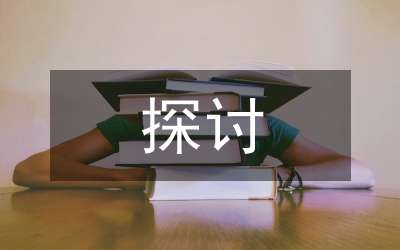
摘要
一、證人作證豁免權的界定……………………………………………………1
二、證人作證豁免權的體現……………………………………………………2
三、證人作證豁免權的正當化分析……………………………………………4
結語…………………………………………………………………………6
參考文獻…………………………………………………………………………7
提綱
一、證人作證豁免權的界定
二、證人作證豁免權的體現
(一)公務特權
(二)拒絕自陷于罪的特權
(三)“親親相為隱”的特權
(四)職務上的特權
三、證人作證豁免權的正當化分析
(一)證人作證豁免權的制度價值,在于它是對證人人權保障的體現。
(二)證人作證豁免權制度的價值,體現了對人文精神的關懷和親情關系的尊重,以及對正常社會倫理道德觀的維持。
(三)證人作證豁免權的制度價值,還在于它體現了對特定社會關系的保護和對社會公眾利益的維持。
四、結語
論文摘要
證人作證豁免權是證人的適格性與可強迫性相分離的一種體現,它包括“公務特權”、“拒絕自陷于罪”的特權、“親親相為隱”的特權、“職務上的特權”和“非法取得證據的排除”第五種情況;證人作證豁免權體現了對證人及其相關社會利益與特定社會關系的保護,是各種利益均衡的產物;我國有關證人作證豁免權的立法闕如,未來制定的證據法典應確立一套關于我國證人作證豁免權的法律適用規則。
證人作證問題,是當前理論界與實務界中的重大問題。長期以來,人們在抱怨證人作證難的同時,卻忽視了對證人合法權益的保障;人們在一味追求證人出庭作證率的過程中,同時又淡漠了與此相關聯社會關系的保護。因此,關注和重視證人權益,加強與此相關聯社會關系的保護,實現利益價值選擇的均衡,乃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其中,證人作證豁免權問題,就是一個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與現實意義的問題。
關鍵詞:證人權利證人作證豁免權立法建議
一、證人作證豁免權的界定
豁免(Immunityty)一詞,通常具有“免除”、“免去”的意思;相應地,“證人作證豁免權”(Immunitytyofwitness)的內涵,要比通常所說的“證人特權”(Pivilegeofwitness)或證人的“證言拒絕權”等含義豐富得多,它是特指對于負有作證義務的證人,在特殊情形時,法律免除其作證義務的權利。其核心內容在于:“一個證人可依法對已掌握的有關涉及案情的事實不予陳述,拒絕法庭對其進行的調查詢問以及提供有關的證據材料”。[1]
而按照傳統理論,證人的適格性與可強迫性是相一致的,或者至少是“相聯系”的。[2]凡是證人,都有義務作證,這是我們的一貫立場,比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就明確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但是真如此嗎?筆者不以為然。因為證人的適格性(Competence)的關鍵,主要是解決證人能力或者證人資格的問題,也就是哪些人有權作證。一般認為,自然人只要具備四個條件,就有資格作證:(1)有感受和記憶能力;(2)能正確表達;(3)親自耳聞目睹了案件事實;(4)理解宣誓作證的義務。而證人的可強迫性(Commpellability),是指對于適格的證人可以強迫其出庭作證,對于拒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將給予一定的懲戒。在證人的適格性與可強迫性的關系上,一般學者認為,“證人的適格性是可強迫性的前提,不具有適格性的人,就不具有可強迫性;具有可強迫性者,必須是適格的證人。”這實際上是同義反復,而對問題的另一方面――“具有適格性的人,未必可以強迫作證”,卻避而未談。筆者認為這是不全面的,事實上,證人的適格性與可強迫性是可以分離的,“證人作證豁免權”就是這種分離的體現。
另外,關于“證人作證豁免權”的性質,有學者認為,它是一種“公法上的抗辯權”,并闡述道:“將證言拒絕權的性質界定為公法上的權利,其實就是將證言拒絕限定為法定權利,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出現,才有可能行使該權利。這樣規定的目的,一可以排除證人等基于民事實體法上意思自治等原則將私法權利擴大為公法權利,二可以明確該權利的重要性質,禁止證人濫用該權利。”[3]筆者認為,這種將“證人作證豁免權”的性質界定為“公法上抗辯權”的作法,有失偏頗。毫無疑問,證人作證涉及到公共利益,它具有公法上的屬性,但同時它有時又會體現出私法上的特點,這在民事案件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在一貨物買賣的合同糾紛中,某享有作證豁免權的證人,就可以通過與一方當事人的討價還價來決定是否放棄作證豁免權。因此,“證人作證豁免權”的任意處置性,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了這種權利的私權性質。所以,“證人作證豁免權”――恰當的說,兼具公權與私權的特性。
二、證人作證豁免權的體現
證人作證豁免權的內容,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公務特權
證人有權就有關公務秘密的問題拒絕回答。例如,英國法律規定,本國國王(或元首)、外國國王(或元首)、駐外大使、高級專員和外交官,不能被迫作證;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72條、第273條和第274條對此也予以有條件的承認,該法規定“以官吏或曾為官吏的人為證人而就其職務上的秘密進行詢問時,法院應得到該監督官廳的許可”,以內閣總理大臣、其他國務大臣、眾議院、參議院議員或曾任其職務的人為證人,而就其職務上的秘密進行詢問時,法院應得到內閣或眾、參議院的許可。而在德國,以法官、公務員或其他從事公務的人為證人時,詢問關于職務上應守秘密的事項,以及許可其作證的問題,適用公務員法中的特別規定。我國臺灣地區對此也有類似的規定。
可見,對從事公務的人員在職業活動中獲取的秘密予以特殊保護,免除其就此作證的義務,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
(二)拒絕自陷于罪的特權
如果證人提供證言,有可能使自己或自己的親屬受牽連以至受刑事追究或被判有罪時,就可以免除該證人提供證言的義務。這一原則是被告人所享有的“拒絕自證其罪特權”(Privilegeagainstselfincrimination)的延伸,它最早起源于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后在世界各國中得到普遍確立。
證人所享有的拒絕自陷于罪的特權不僅適用于民事、刑事審判程序、大陪審團調查程序(美國),而且適用行政的、立法機關的聽證、調查程序。[4]這種特權的特點表現為:(1)在適用主體上,較為寬泛,既適用于證人,又適用證人的親屬;(2)在適用事由上,既包括有可能遭致刑事追訴或處罰的事項,也包括名譽上受損(Disrepution)的情形,還有財產上權益受損害的情況。可見,證人享有拒絕自陷于罪的特權,對證人權益保障的力度是很大的。
(三)“親親相為隱”的特權
這是指夫妻之間或者特定親等的親屬之間,不得就從對方獲知的信息作證或作不利于對方陳述。如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83條第1款規定,凡證人遇以下婚姻關系或親屬關系的,有權拒絕作證:1.系當事人一方的未婚配偶;2.系當事人一方的配偶,包括婚姻關系已不存在的;3.系現在或者過去是當事人一方的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或三親等以內的旁系血親,或二親等以內的旁系姻親。而菲律賓新證據規則第130條第25條“父母子女的特權”中規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強迫作證反對其父母及其他直系尊親屬、子女及其他直系卑親屬。而當在一有數位被告的訴訟程序中,證人雖只與該數位證人中之一人有親屬關系,仍有拒絕證言的權利。我國臺灣地區對有關身份關系的規定更為寬泛。[5]證人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1.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或家長、家屬者;2.與被告或自訴人訂人婚約者;3.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法定人或現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訴人為其法定人者。香港《訴訟證據條例》規定,拒絕作證權主要體現在夫妻之間,任何訴訟事件,都不得強使夫或妻泄露婚姻期間所收其配偶之通訊。而在美國,婚姻特權包括拒絕提出不利對方的證據權和夫妻間的談話守秘權,但能夠證明夫妻間交談內容的其他人,可以在法庭中予以披露。可見,賦予夫妻和親屬之間的作證豁免權,是世界各國證據立法的普遍趨勢。這對于維持人們正常的倫理道德觀,不無益處。
(四)職務上的特權
這是指證人由于職務上或業務上的保密義務而享有的作證豁免權,它是基于保護特定職務上的社會關系而產生的。至今,在美國享有作證豁免權的職務關系有:律師與其當事人、醫生和病人、心理治療人員與病人、神職人員與懺悔者、甚至新聞記者、告發人都享有特權(不得暴露提供情報人身份的特權)。而加拿大證據法第41條和42條,也分別規定了對因職業關系所獲得的應當受到保密的事項以及律師與委托人之間的保密事項,證人享有拒絕作證權。
綜上所述,“公務特權”、“拒絕自陷于罪”的特權、“親親相為隱”的特權、“職務上的特權”,是證人作證豁免權的重要體現。世界各國在此作法上可能有所差異,但立法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是相同的。
三、證人作證豁免權的正當化分析
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知道,證人作證豁免權是一種相對權,而不是絕對權,它并不是不受限制的,而是要受到法官、相對人或社會公共利益等多方面的制約,世界各國在此問題上的大量“但書”規定,即是明證。
應該說,國家為了保護公共利益和訴訟的順利進行,維護社會正義,普遍規定了證人負有作證的義務;為確保證人作證義務的履行,又都規定了當證人拒絕作證的,國家可以采取一定的硬性手段強制其作證,這種立法的補衷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現實中又是容易產生流變的。因為“這一強制性規定必然會對證人的自由權利構成一定的限制。盡管我們從確保社會公正的角度來審視這一規定,或者即便從一般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來看,都不會去懷疑立法的目的。然而,同樣在證人權利和社會、法律利益的比較之間,在法律強制之下的證人作證對他們自身造成的損害也是令人十分驚訝的。這不得不使我們對良好意圖支配下制定的法律在適用于社會現實時,法律的妥當性是否還能保全產生深刻的懷疑。”[6]畢竟,當我們在保護一種社會利益的同時,不宜忽視其他利益的保障,還應照顧各種利益的均衡,也就是說,當我們維護一項社會正義的時候,還應考慮這同時會不會造成另一種不公正?
證人作證豁免權,就是這種利益均衡的產物。也就是說,它是為了克服片面強調證人作證義務所帶來的消極影響而產生的,它珍重證人利益和與此相關的特定社會利益,它珍視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它反對對證人動輒施暴(如懲處“藐視法庭罪”),更反對為了追求某種形而上學的“案件利益”,而犧牲更大的社會整體利益或者某種更值珍貴的社會關系。或者說,證人作證豁免權的目的,在于促進某種社會關系的發展。借用華爾茲先生的話說,這種豁免權存在的一個基本理由是:“社會期望通過保守秘密來促進某種關系。社會極度重視某些關系,寧愿為捍衛保守秘密的性質,基于不惜失去與案件結局關系的重大情報(例如,很難想象有什么事情比‘律師――當事人’豁免權更能阻礙事實的查明)。”[7](P283)或許可以說,這正是證人作證豁免權的最大價值所在。
應當承認,片面強調證人出庭作證義務的立法在實踐中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是很難靠“不公開審判”等一般制度性措施所能預防的。唯有徹底確立證人作證的豁免權制度,才能對此產生真正地制約。
首先,證人作證害免權的制度價值,在于它是對證人人權保障的體現。
這應該從憲法和憲政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因為任何人所享有的拒絕自證有罪的特權,表面上是個訴訟權利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公民的憲法性權利和國家根本利益,它不僅適用于被告人,而且適用于證人;不僅適用于刑事案件,而且在“民事訴訟、民事賠償、行政訴訟以及行政程序中,只要某人的證言有被用來在未來的刑事案件中證明他有罪的傾向時,他也同樣享有這項權利”。或者說,“如果某一證言本身就帶有明顯的對提供證言的人自證有罪的傾向,根據法律規定,毫無疑問,他享有拒絕自證有罪的權利”。[8](P428)“拒絕自陷于罪”的作證特免權,就是這種權利的體現。
應當說,處于對立的訴訟結構中,任何人都沒有義務協助對方追究自己的責任。在美國,證人所享有的“拒絕自陷于罪”的特權,通常被認為是一項“基本的”、“非常重要的”權利,英國等國家的一些法學家也主張,這是最重要的個人特權之一。他們認為,“這項特權的確立,是為了糾正政府官員為取得證據不惜采取任何強迫手段,以使人受到刑事懲罰的傳統做法,是為了加強政府官員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感。同時,證人享有此項特權,可以消除后顧之憂,毫無顧忌的提供證言”。可見,“豁免”的功能,就在于消除證人被刑事追究的危險,讓證人大膽作證。而要做到這點,兩項配套措施的實施尤為重要:一是罪行豁免制度(Transactionalimmunity),二是證據禁用制度(Useimmunity)。前者是指如果某人對某事提供了證據,或者在此案相關的問題上作過證,則永遠不再就此事對該證人提起刑事訴訟;而后者乃指,經許諾豁免而取得的證言或其他證據材料,以及以此為線索找到的其他證據,不得在將來任何刑事訴訟中作為于他不利的證據而使用。
其次,證人作證豁免權制度的價值,還在于它體現了對人文精神的關懷和親情關系的尊重,以及對正常社會倫理道德觀的維持。
證人作證豁免權制度,不僅保障證人的利益,而且還延及對其親屬的保護。這與我國古代所形成的“親親相為隱”原則非常類似,所謂“《春秋》之義,為親者諱”,“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對于共同生活的親屬,以及“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對于共同生活的親屬,以及“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或(及)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之間“有罪相為隱”的,“皆勿論”。應該說,除去其中封建性的東西,它是非常有道理的。因為強制性的要求一個人揭發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配偶、子女,這在心理上是無論如何也很難接受的,即使這種類型內的人被強迫陳述時,對證言的價值亦不高,這種強行迫害家庭隱私的方式無法使其價值合理化。――由于每個人都是“血性動物”,具有情感,讓一個人昧著自己的良心來指控自己的親人,這無異于是對人性的摧殘。倘若“親親不得隱”,那么必然是夫妻之間相互提防,父母兄弟之間相互猜疑,生怕有朝一日,現在的陳述成為不利于己的證據,正所謂人人自危,親人之間的親情、信任喪失怠盡,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很難維持。而這又必然會危及社會最基本構成單位――家庭的安定、團結和友愛,進而危及整個社會的穩定與有序。鑒此,世界各國普遍規定了“親親相為隱”的作證特權規則,這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聲。
最后,證人作證豁免權的制度價值,還在于它體現了對特定社會關系的保護和對社會公眾利益的維持。眾所周知,一個有效運轉,依賴于各個行業的存在與健康發展。但如果允許律師可以出示當事人的證據,醫生可以透露病人的隱私,牧師可以告發懺悔者的罪行,這無異于監守自盜,其結果將是:當事人不敢請律師,病人和懺悔者不敢向醫生與神父吐露真情,生怕他們哪天變成了“便衣警察”,轉而告發了自己,這實際上將會使整個律師、醫院、宗教等行業的存在與發展,名存實亡,形同虛設。
結語
筆者認為,今后我國的證據立法,“不應該單純強調證伯作證義務,甚至過分強調立即采取強制措施強制證人作證。相反,應該客觀、冷靜地看待證人作證義務與權利保障義務之間是否存在失衡狀態,承認證人在符合法律精神前提下的拒絕提供證言的權利”。立法上應該有“證人作證豁免權”的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1]畢玉謙.民事證據法判列實務研究[M].北京:法律降福,1999.
[2]常怡.民事訴訟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3]〔日〕兼子一,等.條解民事訴訟法〔M〕.東京:弘文堂,1986.
[4]〔美〕喬恩.R.華爾茲.刑事證據大會〔M〕.何家弘,等.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
[5]崔敏,張文清.刑事證據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
[6]苛葛壯.刑事訴訟法比較〔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7]劉榮軍.論證人的證言拒絕權〔J〕.法學,1999,(5):24-30.
[8]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參考資料〔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 上一篇:我國離婚制度研究論文
- 下一篇:中小股東權益保護分析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