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司法福利性之質(zhì)疑
時間:2022-06-03 02:59:00
導(dǎo)語:少年司法福利性之質(zhì)疑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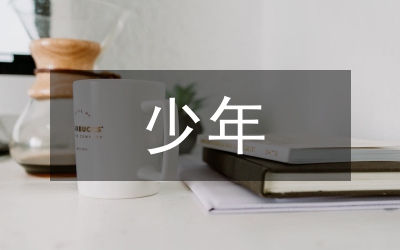
少年司法起源于人們對兒童利益的特殊關(guān)照,兒童福利運動是促成少年法院建立的最強動力。“最好、最明智的父母所希望給予其孩子的”,約翰﹒杜威于1899年宣稱,“應(yīng)當成為社會所力圖給予其所有孩子的”。這位教育改革家的宣言反映了無數(shù)代美國人對本民族少年的素有的責任感。①少年法院建立的首要理念就是防止將罪錯少年作為罪犯對待。社會對待罪錯少年應(yīng)該像慈愛的父母對待自己犯錯的孩子一樣,充滿關(guān)愛而不僅僅是懲罰。雖然少年法院是作為社會福利機構(gòu)產(chǎn)生于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但從其基礎(chǔ)理念到社會實踐都充滿了與“福利”相背離的因素,與其說是建構(gòu)兒童福利的神話,倒不如說是對兒童福利的剝奪。
一、“親權(quán)”和“國家親權(quán)”的非福利性分析
國家親權(quán)思想是美國伊利諾斯州少年司法制度誕生的重要理論基礎(chǔ),并一直是指導(dǎo)美國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國家親權(quán)”就是要取代父母的“親權(quán)”,成為少年兒童的最高監(jiān)護人,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親權(quán)”的產(chǎn)生緣由進行一番探討。親權(quán)是父母針對自身子女所享有的,有助于父母撫養(yǎng)、教導(dǎo)子女順利成長的一種自然權(quán)利。人類為什么需要將這一自然權(quán)利法定化,對其進行法律意義上的保護?人類自身的繁衍需求這一生理現(xiàn)象并不能對其進行足夠合理的解釋,而對子女進行身份性的確權(quán)才是問題根源。人類從母系社會進入父系社會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父權(quán)和夫權(quán)的確立。對人類個體身份的確認是以其隸屬于某一成年男性為標志的。親權(quán)來源于古羅馬時期的“家長權(quán)”,此時的子女被視為父母尤其是父親的私有財產(chǎn),父親對自己的子女享有生殺予奪的大權(quán)。在親權(quán)制度下,子女被劃歸為父親的“財產(chǎn)”,根本性原因在于人類個體保證自身對財產(chǎn)的長久占有,即使個體的生命有限,也要讓帶有自身基因的個體一代代地占有財產(chǎn)。財產(chǎn)對人類生存的基石性作用,產(chǎn)生了對婦女貞操的要求以及對通奸的極度厭惡,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證自身家族血統(tǒng)的純正,尤其在物資稀缺的社會,人們對血統(tǒng)的純正性更為看重。所以在人類進入物質(zhì)極大豐富的社會之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能是一種理想狀態(tài),對自身基因的維持是人類的本能。對此非常有力的一個證明就是,在醫(yī)學(xué)如此發(fā)達的今天,器官移植依舊會引起接受體的排斥反應(yīng)。國家是一個抽象體,是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政治組織。社會契約理論認為,國家權(quán)力是人們將自身權(quán)利讓渡出來的集合體。因此,在民主國家人人平等。從理論上講,罪錯少年、無人照管的少年應(yīng)該得到國家的統(tǒng)一照管。即使在君主制國家,君主自身的后代連同近親屬的后代與全國少年相比,所占比例也微乎其微。從粗略意義上講,為維護自身統(tǒng)治,君主會對全國少年予以平等照顧。但從發(fā)生學(xué)意義上講,“國家親權(quán)”理論產(chǎn)生的最初動因是對有產(chǎn)者少年的保護,而非一種博愛性的平等保護。中世紀時期,英國大法官法庭首先開始運用國家親權(quán)理論作為干預(yù)未成年人的合理化根據(jù)。當時的大法官法庭主要關(guān)心的是財產(chǎn)權(quán)利的保護,但其管轄權(quán)已經(jīng)涉及到兒童福利。具體來說,中世紀時期英國大法官法庭審理的案件主要包括監(jiān)護人職責、財產(chǎn)的使用和控制、臣民與君主的關(guān)系等。大法官法庭奉行的一個重要理論是認為未成年人和其他無行為能力人都處于國王的保護之下,這樣一種理論被稱為國家親權(quán)理論。為了使干涉封臣子女(他們的地位和財產(chǎn)直接與君主利益相關(guān))生活的做法合理化,英國國王首先應(yīng)用了國家親權(quán)這樣一種理論,使之成為大法官法庭維護國王利益時的理論基礎(chǔ)。不過,大法官法庭僅處理富有階層的財產(chǎn)及監(jiān)護問題,并不管轄少年犯罪案件,少年犯罪案件仍然是在普通刑事司法體系中處理。
二、理想與現(xiàn)實對接中少年權(quán)利的喪失
在少年法院創(chuàng)設(shè)者的設(shè)想中,這個“社會機器的嶄新有機部件”不僅可以使少年脫離嚴厲的刑事司法體系,而且使得他們免于因遭受刑罰而被打上恥辱性的標簽。他們設(shè)想少年法院將進行不公開審理,案卷也會保持其秘密性,而且私人律師或者陪審團不會出現(xiàn)在法定程序中。它將成為兒童的庇護所,特別是對于處于躁動青春期的兒童,而這些最終將會寫進絕大多數(shù)國家的法律里。②人類崇高的理想在嚴峻的社會現(xiàn)實面前往往會變形走樣,嚴密的制度設(shè)計往往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審理的秘密性和程序的非法定性,這些本為保護少年兒童權(quán)利的設(shè)計在實踐中卻成為剝奪少年兒童權(quán)利的夢魘。絕對的隱秘有利于對少年兒童隱私的保護,但同時也是滋生肆意妄為的溫床。沒有法定的訴訟程序,也就剝奪了少年兒童的辯護權(quán),結(jié)果只能是任人宰割。為了避免罪錯少年與成年罪犯之間的交叉感染,人們開始動議以公立學(xué)校為模型建立一個專門的少年庇護所。1825年1月1日,歷史上第一座少年庇護所——紐約庇護所,正式開始運作。不過,從庇護所的運作來看,它更像是在模仿成人監(jiān)獄的模式。庇護所的管理十分嚴格甚至殘酷,手銬、腳鏈、鞭打等用以管教成年罪犯的手段,在庇護所被廣泛地運用。庇護所在某些方面又像早期的濟貧院。由于當時人們認為,游手好閑是邪惡的工廠,因此被收容的少年經(jīng)常被送去給農(nóng)場主或其他人做學(xué)徒,作為回報,庇護所也因此獲得不少好處。據(jù)統(tǒng)計,每年大約90%從庇護所釋放的孩子都被送去做學(xué)徒。將少年送去做學(xué)徒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使庇護所異化為一種經(jīng)濟實體,被收容的少年則異化成了為庇護所掙錢的合法童工。③在少年司法演進的二百年間,也有很多人對收容權(quán)提出質(zhì)疑,并訴諸法律。但受庇護所的學(xué)校性質(zhì)和國家親權(quán)哲學(xué)的影響,法律的理性陽光長期以來并沒有照耀到這一領(lǐng)域。1839年賓夕法尼亞州高級法院對克勞斯案的裁決書中寫到:“庇護所不是監(jiān)獄,而是教養(yǎng)學(xué)校,懲罰不是最終目的,這個慈善團體通過訓(xùn)練其收容人員達致勤奮,將道德和信仰的原則注入他們的心靈,讓他們掌握謀生技能。總之,是通過使他們脫離不當聯(lián)系的腐化影響來達到矯正目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當生身父母無力承擔教育子女的義務(wù)或不配這樣做時,難道就不能為國家親權(quán)或社區(qū)的普通監(jiān)護人所代替嗎?這個未成年人已經(jīng)從必須結(jié)束的確定墮落過程中救回來,不僅監(jiān)禁她是合法的,再把她放回去也是非常殘忍的行為。”但作為案件一方當事人的克勞斯的父親卻堅決主張自己對女兒的撫養(yǎng)權(quán)。親情和物質(zhì)相比,哪個更有利于青少年的成長?再者,自由的生存環(huán)境與被強制性接受教育相比,哪個更符合人類自身的本能需求?如果說家庭經(jīng)濟的困窘是導(dǎo)致克勞斯與父親分離的原因,那么在馬丁﹒羅斯訴庇護所案中,羅斯是一位紳士,這名父親認為自己無論是在經(jīng)濟上還是道德上都有能力照顧自己的兒子,可法院最后還是駁回了馬丁﹒羅斯的請求。這種不經(jīng)法定程序、未經(jīng)法院判決,就可以限制少年自由的做法直到1967年的高特爾案才發(fā)生轉(zhuǎn)變。
三、標簽理論對身份罪的質(zhì)疑
與少年法院相聯(lián)系的“身份罪”是一種藝術(shù)化術(shù)語,不同于刑法上的“身份罪”。此處的“身份”專指未成年人,一種行為被認為違法的原因是行為主體是未成年人。兒童在未成年期擁有一種身份,所以會被加以諸多特殊限制。受少年法院管轄的身份罪行為違反了如下幾類規(guī)則:第一類包含了僅針對青年人的禁止性規(guī)則(“不得為”,諸如此類),例如法律禁止那些特定年齡以下的人飲酒或某一時間后在街上逗留;第二類包括要求其對象去做一些積極的事情的命令性規(guī)則,例如兒童應(yīng)服從他們父母或監(jiān)護人的命令。違反此類規(guī)則可能顯示出兒童是“頑愚不化的”或“桀驁不馴的”;第三類規(guī)則針對被認為是“恣意妄為”或“在懶惰和罪行中長大”的青年人。這些兒童或許并未違反任何他們設(shè)定的特定規(guī)則或違反父母特定的命令,但顯示出在一些情況中已經(jīng)或可能做過錯事。①如果在此的分類還不足以讓我們對少年法院所管轄的罪錯少年有一個非常直觀的認識,那么1907年伊利諾斯州《少年法院法》對少年罪錯行為的定義則讓一個頑劣少年的形象躍然紙上。“‘罪錯兒童’這個詞是指任何在17周歲之下的男孩和18周歲之下的女孩,違反州法令的;或者參與盜竊,品性不端或不道德的人;或者無故且未經(jīng)父母同意擅自離開家或住所,或在懶惰與罪行中長大;或經(jīng)常去聲名狼藉的家庭;或者經(jīng)常被傳喚去警察局或光顧出售烈性酒的酒吧;或者光顧,進入任何公開的臺球房或投機商號;深夜無正當事由或職業(yè)在街上游蕩;或者習慣性地在鐵路沿線上游蕩或跳上或者試圖跳上正在行駛的火車;未經(jīng)合法授權(quán)進入汽車或火車頭;或在公共場所、家庭、學(xué)校使用卑鄙、淫穢、粗俗、污穢或下流的語言;或有下流的犯罪動機或流氓行為。”人生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兒童期和青春期最大的特點就是頑皮甚至是叛逆。曠課、逛網(wǎng)吧、抽煙、喝酒等惡習在廣大青少年中屢見不鮮,一定程度上曾影響了社會治安的穩(wěn)定,但這是否需要國家權(quán)力的強力介入?或者說國家權(quán)力對此介入到何種程度就應(yīng)停止?按照身份罪的構(gòu)成要件看,這些“壞孩子”統(tǒng)統(tǒng)應(yīng)該被送到少年法院并予以監(jiān)禁。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社會免遭青少年的危害還是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長?這是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
頑劣少年一旦被歸為“罪錯少年”,其一生始終有可能被外人以一種有色眼鏡來看待,那么他或她的社會化之路必定比常人充滿更多的荊棘,同時促使其走上犯罪之路的誘因會更多。犯罪學(xué)中的標簽理論對此有非常好的解釋:當某個人被社會中的權(quán)威階層認定具有偏差行為或犯罪行為時,他就會以社會給予其的角色定位為坐標,逐漸成為偏差行為者或犯罪者。負面的標簽,如認為某人是“愚笨”、“精神病患者”、“犯罪人”等,都是使他自我形象受到長期損害的主要來源。既然如此,與少年司法相聯(lián)系的“身份罪”對青少年成長的益處不得不大打折扣,對于\少年司法政策制定者的心理不得不有一個重新的定位。歷史學(xué)家羅伯特•布雷姆納曾認為:從積極方面而言,在民主國家里,兒童是未來的公民,是國家最有價值的資源;為了其自身的安全,國家必須貫徹執(zhí)行兒童受教育的權(quán)利,以使他們成為有益的公民;從消極方面而言,國家必須保護自身免遭那幫被允許在無知、無紀和無敬中成長起來的危險少年的侵害。①美國社會對待兒童的態(tài)度始終糾結(jié)于“擔心孩子”與“害怕孩子”的矛盾之中。紐約兒童救助協(xié)會的創(chuàng)始人布雷斯(CharlesLoringBrace)的話更為露骨,他宣稱:“本協(xié)會就是為了解決紐約不斷增長的兒童犯罪率與貧窮問題。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凈化城市。”②在為了孩子的崇高外衣的遮蓋下,兒童福利運動者的真正服務(wù)對象卻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
- 上一篇:區(qū)政辦違法建筑清理整治方案
- 下一篇:少年司法規(guī)律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