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打擊有組織黑社會性質(zhì)犯罪的立法與實踐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30 12:00:00
導語:香港打擊有組織黑社會性質(zhì)犯罪的立法與實踐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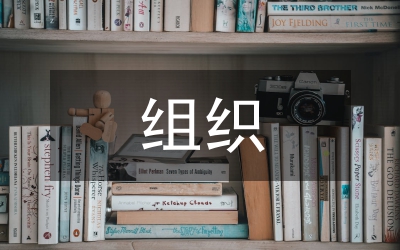
關(guān)鍵詞:三合會有組織罪行指明罪行加重刑罰犯罪得益
內(nèi)容提要: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為打擊香港地區(qū)有組織犯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jù)。香港地區(qū)在實施加重刑罰、打擊洗黑錢犯罪及要求披露犯罪財富等方面的司法實踐亦已趨于靈活,并在防止、偵查和打擊有組織犯罪的各環(huán)節(jié)上都已漸見成效。但香港打擊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的立法仍有值得改進的空間,主要是應當提高立法的預防性、前瞻性、完備性和針對性。具體而言,可以從打擊黑社會主要犯罪、增設黑社會犯罪新罪名、修改刑法中對黑社會的定義以及考慮充公黑社會財富的特別立法等方面予以完善。
一、香港打擊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的立法
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自1994年10月21日立法后,分階段從1994年12月2日先后推出“清洗黑錢”犯罪和針對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的“加重刑罰”特別判刑程序等條款;2000年6月1日香港又進一步對《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作出修訂,[1]立法規(guī)定匯款人及貨幣兌換商須向香港警務處注冊及保留大額交易紀錄。
(一)有關(guān)立法之目的
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立法與修訂之主要目的是:透過第3—5條有關(guān)證人令、提交令、搜查令等規(guī)定,為執(zhí)法人員提供能夠剝奪證人于香港刑事司法制度下本來擁有的保持緘默權(quán)利的特別偵查權(quán)力;透過第8、15、16條有關(guān)沒收令、限制令、押記令等規(guī)定,授權(quán)香港區(qū)域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沒收被告人直接或間接從實施附表1及附表2所列的“指明罪行”所獲包括財產(chǎn)增值的收入及利益;透過第25條規(guī)定,任何人于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些財產(chǎn)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之情況下處理該財產(chǎn)為犯罪;透過第27條的特別判刑程序條款,令香港法院可以應檢控一方的請求,于犯罪屬于有組織罪行時或于犯罪屬于“指明罪行”時,對實施該犯罪的被告作“加重刑罰”的判處;透過于2000年修訂了的《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4A條的修訂條款規(guī)定,匯款人及貨幣兌換商必須于開業(yè)一個月內(nèi)向香港警務處調(diào)查科總警司登記本人及業(yè)務資料詳請,且須核實親身交易港幣20000元或以上顧客的身份及備存有關(guān)交易紀錄6年。
(二)“有組織罪行”之刑法定義
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對“有組織罪行”作了法律上的定義。按第2條規(guī)定,“有組織罪行”是指屬于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中所列的“普通法罪行”及“法定罪行”,而且該罪行必須是:“與某三合會的活動有關(guān);與2名或以上的人的活動有關(guān)連的,而該等人聯(lián)合一起的唯一或部分目的是為作出2項或以上的行為,每一項均為附表1所列罪行及涉及相當程度的策劃及組織的;或與2名或以上的人所犯的,而且涉及相當程度的策劃及組織,以及(i)有人喪失生命的相當程度的危險;(ii)有人身體或心理上受嚴重傷害或有人受該等傷害的相當程度的危險;或(iii)有人嚴重喪失自由。”[2]
這個定義雖然表面上是局限于《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中的4種包括謀殺及綁架等的“普通法罪行”及19條香港成文法規(guī)定的包括與出入境、危險藥品、賭博、侵犯人身、侵犯財產(chǎn)及放債等有關(guān)的法定罪行,但由于“與某三合會的活動有關(guān)”是定義中三個規(guī)定組成因素其中之一,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基本上已涵蓋了絕大部分香港黑社會一般會進行的犯罪行為。這個設計彌補了香港以往為了專門針對黑社會(亦即“三合會”)已制訂逾百年的香港《社團條例》及目前其他的香港成文法刑事條例于單獨應用上,對打擊香港黑社會所實施的有組織犯罪之阻嚇力的不足之處。
二、香港打擊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的若干重要司法實踐
香港法例第445章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qū)自有法制以來第一個特別為打擊有組織犯罪而訂立的法例,條例的宗旨是:“增設偵查有組織罪行和其他罪行及某些犯罪的犯罪得益的權(quán)力;就沒收犯罪得益作出規(guī)定;就某些犯罪者的判刑訂定條文;增訂關(guān)于犯罪得益或關(guān)于代表犯罪得益的財產(chǎn)的罪行;及就附帶及相關(guān)事宜訂定條文。”[3]這個宏大的宗旨是否能夠達到,要視乎執(zhí)法機關(guān)能否妥善運用所新增設的偵查罪行及犯罪得益的權(quán)力,以及法院對于有組織犯罪的罪犯作出懲處的時間能否藉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賦予的加重刑罰及充公犯罪所得的規(guī)定,有效地對有組織及嚴重犯罪產(chǎn)生阻嚇性及懲教性的效果及壓止有組織犯罪的孳生。
(一)實施“加重刑罰”
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中對黑社會有組織犯罪在懲治上的主要作用,是規(guī)定香港區(qū)域法或原訟法庭于裁定罪犯觸犯了第2條所述的“指明罪行”(SpecificOffence)時有權(quán)作加重刑罰判處的條文。第2條所述“指明罪行”是指包括:附表1或附表2所指的任何罪行;串謀犯任何該等罪行;煽惑他人犯任何該等罪行;企圖犯任何該等罪行;協(xié)助、教唆、慫使或慫使他人犯任何該等罪行。
第27條第11(a)款更規(guī)定,香港區(qū)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原訟庭可以在無合理疑點信納犯罪人所被裁定罪成的指明罪行乃屬有組織犯罪的情況下對該人作加重刑罰的判決。第27條第11(b)款規(guī)定,香港法院在無合理疑點信納檢控一方根據(jù)第27條第2或第8款所提出與該有組織犯罪指明罪行“有關(guān)資料”或與案中所涉三合會活動的指明罪行的性質(zhì)及程度“有關(guān)資料”的情況下,法院亦可對該人作加重刑罰的判處。第27條第2款所指的“有關(guān)資料”包括:該指明罪行直接或間接引致他人受損害性質(zhì)及程度;因該指明罪行的實施為該人或其他人直接或間接帶來的利益或希望藉此帶來的利益的性質(zhì)及程度;該指明犯罪的普遍性;因最近期發(fā)生的該指明罪行直接或間接導致社區(qū)受損害的性質(zhì)及程度;最近期發(fā)生該指明罪行為任何人的直接或間接帶來的總利益的性質(zhì)及程度。
眾所周知,香港大部分有組織犯罪多是由黑社會(“三合會”)成員所實施的。而這些有組織犯罪,例如:販毒、非法賭博、高利貸及色情等犯罪,許多情況下不僅對受害人造成傷害,也對社會造成嚴重影響及損失。通過引用第27條第2款或第8款,由檢控一方向法院提供“有關(guān)資料”,從而令法院可以對罪犯作加重刑罰判處的規(guī)定,原則上會令黑社會犯罪分子罪有應得及收以儆效尤之效。
1.實施“加重刑罰”的程序
檢控一方對指明罪行申請加重刑罰可以通過兩種法定程序進行。首先,檢控一方可按第27條第25款規(guī)定,于被告人答辯前向他提出會向法院作出有關(guān)加重刑罰的請求的通知;并于法院對被告人作出判處前,請求法院考慮審判案中已被接納的證據(jù)于裁定有關(guān)的犯罪乃屬有組織犯罪時處以加重刑罰。在被告人答辯前通知他,檢控一方會作出有關(guān)請求之目的是讓被告人可以就有關(guān)的請求于判處前充分響應,以便法院于決定是否作加重刑罰判處和決定有關(guān)加刑幅度時予以考慮。
倘若檢控一方是因該有組織犯罪與黑社會活動有關(guān)而申請對被告人作加重刑罰判處者,則有關(guān)的程序是請求法院因被告人所實施的犯罪屬指明罪行和因該犯罪是與三合會活動有關(guān)而對被告人處以加重刑罰。在這種情況下,檢控一方除要按第27條第2款須事前通知被告人將向法院提出有關(guān)加重刑罰的申請外,亦需于法院作出判處前邀請“三合會”專家或其他證人向法院提供能證明該指明罪行是與“三合會”活動有關(guān)且屬于有組織犯罪的性質(zhì)及程度之資料。法院于信納該等資料后即可對被告人處以加重刑罰。
其次,檢控一方亦可通過向法院提供與該指明罪行“有關(guān)資料”,請求法院就被告人所實施的指明罪行處以加重刑罰。在這種情況下,法院除可參考案中的證據(jù)去確定該指明罪行的組織性外,亦可參考由檢控一方提供之“有關(guān)資料”內(nèi)包括例如罪案數(shù)字及其他統(tǒng)計,去證明該指明罪行的普遍性以作考慮決定是否作“加重刑罰”判處和有關(guān)加刑的幅度。
2.“加重刑罰”的幅度
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有關(guān)“加重刑罰”的司法實踐,是否真的能令有組織犯罪之罪犯罪有應得和收以儆效尤之效,至今仍未能完全肯定。主要是因為第27條第11款僅訂明,香港區(qū)域法院及高等法院可于加重刑罰時,對罪犯處以較在沒有信納該指明罪行屬有組織罪行或沒有信納檢控一方提供的“有關(guān)資料”時可能所作宣判為加重的刑罰,但第27條第11款并未有具體說明法院可以加重刑罰的幅度。加重刑罰是由法官視罪犯本來所觸犯的指明罪行之個別案情,再依該犯罪直接或間接引致他人的損害、為罪犯或其他人帶來的得益、該指明罪行當時的普遍性、該指明罪行對社會危害的程度、該指明罪行帶予其他人的總利益的性質(zhì)及程度等等而作酌情決定。亦因為這個原因,由檢控一方提供的“有關(guān)資料”,正是對法院作出加重刑罰的決定起了關(guān)鍵性作用。
由于香港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普通法原則,目前香港法院可以作出的加重刑罰判處是必須依照之前案例所訂之幅度作為基礎(chǔ)的,一般加重刑罰幅度的上限是根據(jù)1998年“李世榮(譯音)”一案所訂下的50%作為標準。[4]此案主審法官在判決中指出,當某個犯罪行為屬于有組織犯罪時,對有組織犯罪組織及參與該有組織犯罪者處以50%加重刑罰,既是符合公義的懲罰,也可收阻嚇之作用。該案例指明了當有證據(jù)證明某類于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中的指明罪行有急促增長的趨勢而且變成普遍的時候,判處阻嚇性懲罰亦為適合,但亦指明了倘若某指明罪行只是漸趨普遍的罪行,若檢控一方先行向法院提示,加重50%刑罰可能并不恰當。就后者的情況,該案例指明了有關(guān)刑罰增加的幅度,要視乎有關(guān)罪行的嚴重性、普遍性及對社會造成的影響。這個案例基本上規(guī)定了加刑幅度的上限為50%,但卻保留了一個彈性加重刑罰的機制,亦因此在若干其后的加重刑罰判決中造成令人懷疑加重刑罪是否能夠令包括黑社會實施的有組織犯罪罪犯得到應得判決的疑慮。
3.實施“加重刑罰”法官的考慮
不論檢控一方是依哪一個程序向香港法院申請對觸犯有組織犯罪的罪犯作加重刑罰判決,法院一般都會視該犯罪的組織性、合作性、專業(yè)性、分工性及重復性,去決定該犯罪是否為有組織犯罪。
(1)考慮犯罪的組織性
2002年港人鄭敬龍(譯音)與其他被告人向法院承認了共13項“串謀行騙罪”及其他控罪。[5]這些控罪包括使用他人身份證開設銀行戶口及透過銀行自動柜員機提取一名被騙人士港幣370000元;用一名受害人身份制造假公司印章于受害人戶口提取港幣27000元;使用偽造印章和簽名及剪斷電話線的方法令銀行無法實時與受害人接觸而多次從多名受害人戶口非法轉(zhuǎn)移港幣共4381000元,法院于判案時指出,控方尋求引用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第11(b)款請求法院因被告人的作為引致他和其他人直接或間接帶來的利益或希望藉此帶來利益性質(zhì)及程度而判處加重刑罰,雖并無不當亦不盡適合。法院認為該案是明顯具有組織性的犯罪,故此控方亦可以引用第27條第4款的規(guī)定要求法院依審判過程中有關(guān)犯罪組織性的證據(jù)顯示,而按裁定被告人所實施的罪行為有組織犯罪作加重罪罰的判處。由此案我們可知,檢控一方可能面對多于一個申請對罪犯加重刑罰的理據(jù),但引用條文申請的失誤有可能令加重刑罰不能達到好的效果。
(2)考慮犯罪的普遍性
有關(guān)檢控一方于審訊時就犯罪的普遍性向法院提供“有關(guān)資料”,對尋求法院就大部分能夠?qū)ι鐣?gòu)成危害及嚴重影響的犯罪處以加重刑罰是非常有效的工具。在這方面香港的執(zhí)法部門以往曾就若干例如走私香煙、偷運人口、非法賭博、經(jīng)營淫窟、扒竊集團等犯罪引用第27條第2款第3節(jié),令法院對被告人處以加重刑罰。
1998年港人譚偉浦(譯音)向香港法院上訴庭尋求推翻他于1997年就兩項走私香煙控罪被法院依第27條作加重刑罰所處共2年徒刑的判決。[6]案中譚偉浦開設一貿(mào)易公司及聘請搬運工人走私兩批市值分別為港幣9840000元和10405810元的未完稅香煙,譚氏亦承認曾進行7—8次類似紀錄及收取每次港幣15000元的報酬。上訴法庭推翻譚氏上訴申請時指原審法官已正確接納由香港海關(guān)一名助理監(jiān)督就走私香煙普遍性所作有關(guān)證供,指出走私香煙趨勢已由2004年的17900萬多根增加至2006年的25400萬根,故此認為加重刑罰50%為十分恰當。此案證明了,單獨就指明罪行的普遍性此所提供之“有關(guān)資料”已足夠令法院對有組織和嚴重犯罪處加重刑罰的方便。
(3)考慮犯罪為罪犯本人或他人帶來利益
2003年印尼華僑KamSusanto于香港高等法院就一項非法足球博彩收受外圍“波纜”及就一項處理犯罪所得利益罪被加重刑罰50%而合被處罰徒刑四年半。[7]案情指被告在家中收受2002年世界杯及英國超級足球大賽非法外圍足球博彩投注,當場被搜獲投注紀錄共港幣4970660元及被告人向買家投注紀錄港幣5020000元。被告及其妻子當時合共持有的11個銀行戶口中于2003年期間的大額交易非常頻密,其中7個銀行戶口的總交易共約為港幣471619779元,而被告于此期間向香港稅務局所申報收入只有港幣約40至50萬元。被告辯稱只是替印尼同鄉(xiāng)向印尼一間IndoSoccer賭博公司下注而收取0.25%作報酬。被告人于2003年對判決的上訴亦被駁回。由此案我們可知,被告人的個人犯罪得益可能只是他所述的0.25%這一區(qū)區(qū)之數(shù),但包括他印尼同鄉(xiāng)在內(nèi)的其他人因他犯罪而獲得益卻可能極其龐大,這正是第27條第2款規(guī)定加重刑罰針對打擊有組織犯罪為他人直接或間接帶來利益的目標。
(4)考慮犯罪為任何人帶來的總利益
2003年2月7日港人林希杰(譯音)于香港地方法院因2項處理犯罪得益及2項非法獲取旅游證件案被定罪,經(jīng)法院加重刑罰后被判處徒刑4年。[8]案中所涉非法犯罪得益為一張港幣1780000元支票及現(xiàn)金120000美元,相信該支票是與由中國內(nèi)地經(jīng)香港特區(qū)走私往英國丹佛港的非法偷渡人口犯罪得益有關(guān)。而所涉旅游證件包括25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護照、72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及25本日本國護照。所有中國護照俱是從非法途徑獲得的,而所有日本國護照則全為已被報失和相信是準備用作偷運非法入境者之用的。被告人于判處后要求減刑和上訴均被駁回。由此案可以看到,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對打擊屬于最嚴重級別的跨境有組織犯罪亦是極為有效的一件工具。通過引用第27條加重刑罰的規(guī)定,香港執(zhí)法機關(guān)就能夠?qū)Σ辉谙愀劬硟?nèi)實施,亦沒有證據(jù)可以在香港法院提起刑事控訴的跨境有組織犯罪,通過對于香港境內(nèi)提供協(xié)助者的檢控進行間接的打擊。
(5)考慮犯罪為社會帶來的傷害。
2003年10月30日蔡光(譯音)于香港高等法院承認10項串謀經(jīng)營不道德場所及1項串謀處理非法犯罪所得,被法院共處罰5年徒刑。[9]案情透露被告于1998年至2002年間協(xié)助經(jīng)營為數(shù)10間共有客房140套的不道德場所,而該等場所是用作為中國內(nèi)地、越南、泰國女子進行之用。這些女子部分為該集團以“雙程證”由中國內(nèi)地輸入,而部分為該集團及以旅游身份由東南亞輸入者。她們每次交易收費港幣420元,但每名妓女只分得港幣100元,而估計這些場所歷年的總收入約港幣4200萬元之多。這些場所均以熟客為主,且有閉路電視作監(jiān)察及秘密信道作進出,令警方難加打擊。被告人其后提出上訴但被駁回,原因乃法院認為對于嚴重走私、賭毒及娼妓等有關(guān)犯罪加重刑罰50%甚至更高也未為不妥。從這類案件的判處我們得到啟發(fā)就是,利用進口軟弱無助婦女去經(jīng)營淫業(yè)乃是極之嚴重及踐踏法律的有組織犯罪,加重刑罰恰恰能給予該組織及參與實施該組織犯罪活動的罪犯更嚴重和更適當?shù)男塘P,以收阻嚇作用。
香港既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是一個旅游地區(qū),扒竊集團隨著香港的旅游日益蓬勃而增加,香港的扒竊案由2001年的717宗已逐漸上升至2002年的859宗及2003年的1681宗。2004年2月18日,屬于一個扒竊集團的越南籍男子VGOVANHUY于香港區(qū)域法院承認一宗發(fā)生于旺角鬧市的扒竊罪之后,被判徒刑共30個月。這個極重徒刑之判決乃包括判刑起點的18個月徒刑、被告屢犯不改的6個月徒刑以及依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檢控一方提供“有關(guān)資料”指出扒竊罪普遍性而額外加上的25%加重刑罰,合總刑期變?yōu)?0個月。被告人后來上訴只獲上訴庭就其他原因?qū)⒖傂唐谳p微減低至20個月,但上訴庭強調(diào)依第27條加重刑罰的原則是正確的,只是指出此案之加幅應為20%而非25%。此案除為將來對有組織性扒竊集團的罪刑確立了刑罰“普遍性”的加刑準則,亦令我們認識到有組織性地于鬧市扒竊是一種社會應該嚴厲打擊的犯罪,因為這種犯罪雖然表面上只構(gòu)成受害人的金錢損失且一般損失可能不大,但卻能引起如受害人需重新申領(lǐng)所有證件等極大之不便,而且亦是對個人財物權(quán)的肆意侵犯,而更罪無可恕的是令香港治安聲譽受損,是既屬有組織性也具嚴重性之罪行的一種。
(二)打擊處理犯罪得益(清洗黑錢)犯罪
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為香港在刑法中增訂了處理犯罪得益這個打擊有組織犯罪運作及擴展的犯罪,規(guī)定任何人凡于“相信”或“已知”的情況下仍然去“處理”犯罪得益,循公訴罪起訴,可以被處罰金港幣500萬元及徒刑14年。公訴罪是可于區(qū)域法院或以上法院提出檢控的犯罪。《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條把“處理”廣泛定義為包括:收受或取得;隠藏或掩飾該財產(chǎn);處置或轉(zhuǎn)換;將財產(chǎn)運入或調(diào)離香港;以該財產(chǎn)作借貸或保證。
由于“處理”一詞的廣泛定義,令打擊有組織犯罪的工作不再局限于如“接收贓物”等情況,而是可覆蓋于有組織犯罪進行或重復進行期間所涉及的所有金錢交易。換而言之,執(zhí)法人員可以用處理犯罪得益(洗黑錢)犯罪對直接或間接、曾經(jīng)及正在參與有組織犯罪的人進行刑事司法治理。
上述港人林希杰(譯音)牽涉在中國偷運人蛇到英國丹佛港一案,被告人只是因藏有代表偷運人蛇得益的一張港幣1780000元支票和現(xiàn)金170000美元,以及基于法院相信他是準備處理這些犯罪得益,因而被法院依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重判徒刑4年。實際上,此案在香港的證據(jù)并不能作為支持被告人曾參與該偷運人蛇的有組織犯罪的充分罪證,但香港法院對被告人的判決已足夠間接打擊于香港境外進行的有組織犯罪行為。
2002年12月23日張錦侖(譯音)于香港區(qū)域法院因一項串謀清洗黑錢犯罪被判徒刑2年零9個月,被告人涉嫌替偷運人蛇分子將犯罪所得港幣500萬元帶往澳門,交由賭廳換賭場籌碼之后轉(zhuǎn)換回銀行本票。被告與2名香港廉政公署臥底在香港購買值15萬美元的銀行本票時被捕,雖然被告所述的500萬元自始至終未被搜獲,法院仍基于廉政公署人員與被告談話內(nèi)容的錄音將被告定罪。該案指明了被告明知他聲稱的500萬元乃犯罪所得而安排處理,法院是可以于未能最終尋獲那犯罪所得500萬元的情況下,仍然依第25條以洗黑錢犯罪懲處被告人,間接亦打擊了偷運人蛇集團的銷贓活動,證明了《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對打擊處理犯罪得益的靈活性。
被告人“明知”及“相信”而處理犯罪得益是第25條的基本構(gòu)件。有關(guān)“相信”及“犯案所得”的解釋自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立法后曾出現(xiàn)若干爭議性問題,這些問題包括:(1)檢控一方是否必須證明被告人所處理的有關(guān)財富確實是代表從公訴罪得益的財產(chǎn)呢?(2)“處理”犯罪得益是否亦應包括被告人自身犯罪所得利益呢?(3)檢控一方是否需要證明被告人所處理來自境外的犯罪利益是由一個在境外可以被公訴罪起訴的犯罪之所得呢?
2006年香港終審法院就OEIHENGKYWIRYO上訴一案指出,被告人的“相信”并非有賴于該財富是否真的需要代表一個公訴罪得益的財富,主要的是被告人的意圖,若他意圖處理他相信是代表一個公訴罪所得的財富就已足夠,控方是不必去證明該財富確實代表一個公訴罪所得益。[10]至于剩下的兩個問題,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終審法院亦于1999年就3名香港甲組職業(yè)足球員于泰國曼谷參加世界杯外圍賽香港對泰國一場賽事中貪污打假球一案的上訴作出終審裁決,香港終審法院認為第25條所指處理代表公訴罪犯罪所得財富應包括被告人自身參與犯罪的得益,同時認為第25條第1款應該從字義狹義地解釋,只需證明該犯罪得益有關(guān)的犯罪是一個可以被公訴罪起訴的犯罪便足夠,而檢控一方是無需證明該犯罪在境外亦是可以被公訴罪起訴的。[11]
上述法庭就第25條應用的澄清給打擊清洗黑錢犯罪和打擊有組織犯罪敞開了門戶,令此條不僅可以應用于純?yōu)樗饲逑春阱X的犯罪上;也可以應用于被告人正在或曾經(jīng)參與的有組織犯罪上;亦可以應用于打擊非法販運大麻及若干于外國不需處方可以獲得的違禁藥品跨境有組織犯罪上。
(三)不披露犯罪得益(黑錢)罪
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A條規(guī)定,任何人已知及懷疑代表可被公訴罪起訴犯罪的財富時,得向香港警察、香港海關(guān)及其他獲香港律政司授權(quán)人員進行披露,而這種犯罪財富亦包括該犯罪的得益及任何曾或擬使用于該可被公訴罪起訴的犯罪的財富,違者即屬犯罪,可以公訴罪被起訴處最高的罰金港幣50萬元及徒刑5年。
由第25A條規(guī)定看,對不披露的合理辯護理由似乎只可以是被告人確實對有關(guān)犯罪財富的無知與沒有懷疑或持有特權(quán)而不能披露者。在此筆者要重申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為尋求和提供法律意見的通訊是屬于本條下所包括的特權(quán)之一種,這特權(quán)曾于2002年被挑戰(zhàn)。事件牽涉一名被香港有組織犯罪及三合會調(diào)查科拘捕的商人JohnHui,該商人被懷疑于1999—2002年間欺詐中國銀行廣東省分行共7500萬美元而被控清洗黑錢。他延聘香港律師彭耀雄(譯音)辯護申請保釋及司法復核,在該律師知情下,JohnHui把名下兩個尚有股票約值900萬元之股票戶口結(jié)余轉(zhuǎn)至該律師之事務所客戶專戶,警方事后拘捕該彭姓律師,而該律師提出司法復核,最終法律頒令宣告警方對該律師實施的拘捕為非法并確認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法律特權(quán)”是不容被侵犯的。[12]
上述判決可能使人覺得,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A條似乎未能增加執(zhí)法人員打擊小部分協(xié)助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律師及會計師等專業(yè)人士的權(quán)力。但在實際情況下,我們知道法律特權(quán)只限于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為尋求法律意見的通訊,并不是不披露犯罪所得的保護傘。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已經(jīng)為打擊有組織犯罪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優(yōu)勢及環(huán)境,而實施加重刑罰、打擊洗黑錢犯罪及要求披露犯罪財富等條例的司法實踐亦已趨于靈活,在防止、偵查及打擊有組織犯罪各環(huán)節(jié)上都已經(jīng)漸見成效;但是在遏止專業(yè)人士借用專業(yè)特權(quán)的保護對犯罪財富不須披露甚至協(xié)助有組織犯罪集團的活動方面,仍然有著若干灰色地帶,有待深入研究及改善。
三、香港打擊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立法的反思
香港特別行政區(qū)逾百年反黑斗爭的歷史和現(xiàn)實早已確切表明香港黑社會組織的存在,而香港政府亦早在回歸祖國之前已正視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的問題,并借著香港《社團條例》和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立法去尋求完善反黑法律體系,以遏止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的孳生和發(fā)展。就香港反黑法律規(guī)范與外地及祖國其他地區(qū)作比較,香港現(xiàn)時的反黑社會有組織犯罪法制工作似乎已頗為完善,但從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于1994年10月立法至今的司法實踐成效去看,香港在這方面的立法仍有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具體而言,尚待改進和完善的地方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立法缺乏預防性
打擊黑社會有組織犯罪主要包括預防及懲治兩個方面。就前者,筆者雖然認同中外學者們普遍主張以社會綜合治理方式去進行預防的工作,以消滅如學者康樹華所指出的引致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的組織成因、經(jīng)濟成因、社會成因及個體成因,[13]但筆者卻傾向贊同打擊黑社會有組織犯罪應從促使黑社會存在和發(fā)展包括黃、賭、毒等犯罪的預防工作開始的觀點。[14]歐美各國和我國港臺等地黑社會犯罪活動主要均是以黃、賭、毒、暴力等犯罪為主,而黑社會犯罪所以能夠變得組織化,主要亦是因為社會對此類犯罪的控制能力薄弱和司法打擊乏力,令黑社會有組織犯罪得以壯大及蔓延,甚至進一步與外地黑社會勢力勾結(jié)而趨向跨境化甚至國際化。公務員之家
因此,我們在反黑立法對策的設計上,應該重新思考是否應該對黑社會實施的黃、賭、毒及暴力犯罪作特別立法,規(guī)定較一般非與黑社會有關(guān)的黃、賭、毒、暴力犯罪更高的刑罰,以杜絕黑社會犯罪。
(二)立法缺乏前瞻性
打擊香港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的困難之處,主要是因為其有別于一般犯罪團伙糾集進行的有組織犯罪。新一代的黑社會除知識及文化水平比以往為高外,許多黑社會亦聘用會計師及律師等專業(yè)人士,為其進行有組織犯罪時提供專業(yè)意見,且善于利用尖端信息科技及采納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制度,使他們能夠更有組織和更緊密地實施犯罪與回避警方的偵查。故此,現(xiàn)代黑社會組織雖然仍會利用中國舊社會青幫和洪幫等三合會的神秘色彩和幫規(guī)戒律以操控其成員,但許多黑社會實際上早已經(jīng)把入會儀式、管理方法、通訊方式簡單化和現(xiàn)代化。然而,由于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對黑社會(“三合會”)的定義仍然沿用舊有的香港《社團條例》對“三合會”的定義,規(guī)定可以視包括使用“三合會”普遍使用的儀式、任何類似或部分類似該儀式的任何社團或采用任何“三合會”名銜、稱謂及術(shù)語的社團為黑社會,[15]對不采納“三合會”傳統(tǒng)儀式、名銜、稱謂及術(shù)語的新一代黑社會組織,在司法實踐中對其進行打擊會出現(xiàn)技術(shù)性的困難。由于1994年10月立法的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并未有在這方面作考慮,著實久缺前瞻性,香港確有必要作適當?shù)难a充和修改以彌補在這方面的空缺。
(三)立法缺乏完備性
香港打擊黑社會的立法最早源自于1950年被香港《社團條例》所替代的1949年第28號法律。除香港《社團條例》于1952年至2004年間經(jīng)歷多次修改外,香港亦就打擊有組織犯罪于1994年10月制訂了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理論上,在打擊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的刑事立法方面,應當完備地就各主要黑社會的嚴重危害社會行為作刑事犯罪的立法,以確保反黑除惡的罪刑法定原則能被充分落實。但從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現(xiàn)今打擊黑社會犯罪法例可見,有關(guān)刑法亦未有對若干存在已久的和一些可以預見的黑社會危害社會行為作出規(guī)定。由于相關(guān)規(guī)定付之闕如,致使香港的執(zhí)法和司法機構(gòu)在法無明文不罪的原則下,無從全面和根本性地打擊黑社會有組織犯罪。這些香港刑法并未明確規(guī)定的行為主要有組織黑社會及于境外發(fā)展香港黑社會活動等犯罪行為。
香港《社團條例》只規(guī)定身為或自稱“三合會”社團干事或會員,管理或協(xié)助管理“三合會”社團,以“三合會”會員身份行事或參加“三合會”集會,以暴力、威脅或恐嚇、煽惑、誘使或邀請他人成為“三合會”會員等行為為犯罪,但并未有對發(fā)起、組織及領(lǐng)導“三合會”的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
故此,嚴格而言,香港《社團條例》只可以于新的“三合會”模式的黑社會組織出現(xiàn)了之后才能發(fā)揮功效,如此一來就不能發(fā)揮杜漸于微的作用。香港自1997年回歸祖國之后,雖然依據(jù)一國兩制的原則以特別行政區(qū)的身份實行高度自治,但對于一些在香港境內(nèi)屬刑事犯罪的發(fā)展黑社會活動,在跨境進入如中國內(nèi)地或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內(nèi)之后實施則不能作出司法管轄,實在是一個亟待研究解決的問題。雖然,理論上這些人的行為在中國內(nèi)地有可能已觸犯了中國《刑法》第294條第2款之境外黑社會入境發(fā)展黑社會組織罪,但假若這些人于實施犯罪行為之后潛逃回香港,則依香港目前的刑法規(guī)定是不能對他們予以制裁的。此外,香港黑社會目前與外地黑社會勾結(jié)進行有組織犯罪的情況亦有增加的趨勢,在此勾結(jié)過程中可能同時為外地黑社會分子于香港提供協(xié)助和庇護,以便外地黑社會能避過偵查實施所勾結(jié)的有組織犯罪活動。根據(jù)現(xiàn)時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規(guī)定,假若香港黑社會為外地黑社會所提供的協(xié)助和保護并不牽涉于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境內(nèi)實施洗黑錢犯罪或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和附表2所列的“指明罪行”時,香港執(zhí)法和司法機關(guān)因無法可依的問題而無從給予任何懲處,令犯罪分子因不被追究刑事責任而可反復作為,間接促使了香港黑社會犯罪向有組織化和國際化方向的發(fā)展。
(四)立法缺乏針對性
香港《社團條例》只是針對香港黑社會(“三合會”)社團本身,如參加、管理及參與該“三合會”的活動的非法性進行刑法規(guī)范。這種有限度的刑法規(guī)范除對根本性地打擊黑社會的基礎(chǔ)和運作并未能起針對性的作用外,實際的功效亦只限于以徒刑監(jiān)禁方式懲治參加黑社會的成員和他們于黑社會內(nèi)擔當不同角色的活動。由于黑社會本身的隱密性使得對身為黑社會成員和參與黑社會活動指控的取證非常困難,除極少數(shù)的長期臥底行動能獲得成果以外,香港《社團條例》的刑法效力根本就不可能把黑社會領(lǐng)導層和財政基礎(chǔ)連根拔起。
故此,針對根治黑社會有組織犯罪,亦即針對黑社會本身及黑社會的存活與發(fā)展,似乎只有倚賴打擊作為黑社會的給養(yǎng)基礎(chǔ)之財政的刑法規(guī)范。在這方面,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條所規(guī)定的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chǎn)犯罪和香港《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25條規(guī)定與清洗黑錢有關(guān)犯罪,雖然已給予了香港法院充公黑社會有組織犯罪所得財富的權(quán)力,但對于黑社會通過以前的犯罪所得利益而囤積超過6年之財富,該第25條所規(guī)定充公財富的權(quán)力便不能產(chǎn)生作用。要針對作為黑社會的存活給養(yǎng)的財政基礎(chǔ),香港特別行政區(qū)于打擊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立法上,實在有必要反思是否需要引入如意大利對付黑手黨而特別制訂于黑手黨員被判罪成時,意大利法院可以充公沒收其名下明顯與他收入不相稱的財富資源的刑法規(guī)定。
四、完善香港反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立法的方向構(gòu)想
(一)從打擊黑社會主要犯罪方向構(gòu)想
雖然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規(guī)定,香港法院可于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被判罪成的“指明罪行”屬有組織罪行,或于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檢控官向法院提供有關(guān)被判罪成的“指明罪行”的資料時可作加重刑罰的判處。但由于申請引用該程序之步驟繁復,而且許多黑社會成員參與實施的黃、賭、毒及暴力犯罪可能都并非直接與該黑社會的活動有關(guān),而僅是由這些黑社會成員所自主實施的。為防黑社會犯罪由個別成員簡單實施向組織化擴張,實在有必要考慮在與黃、賭、毒及暴力有關(guān)的法定犯罪條文中規(guī)定由黑社會成員實施這些犯罪時需要判處特定水平的刑罰,以收阻嚇黑社會分子實施這些黑社會主要的犯罪之效,藉此壓制這些性質(zhì)的黑社會犯罪的有組織化。
(二)從增設黑社會犯罪新罪名方向構(gòu)想
為確保香港刑法可以把各種主要的黑社會嚴重危害社會行為完全納入刑事制裁的范疇內(nèi),并增強打擊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的功能及作用的發(fā)揮,筆者認為香港于打擊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的立法作檢討與補充時,要考慮新增若干黑社會犯罪罪名以完善反黑刑法的覆蓋。初步構(gòu)想包括:
1.在香港《社團條例》中加入發(fā)起、組織及領(lǐng)導黑社會罪名,而建議刑罰應該是與目前香港《社團條例》中屬最嚴重的使用暴力、威脅或恐嚇,以誘使人成為黑社會會員或協(xié)助管理黑社會犯罪同等之最高程度的罰金250000元及監(jiān)禁7年。
2.在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中增加“境外發(fā)展香港黑社會”及“協(xié)助境外黑社會”兩項指定有組織犯罪罪名。首項新罪名可令香港黑社會成員于包括中國內(nèi)地的香港境外地區(qū)進行與其黑社會有關(guān)的活動后于返回香港時仍可于香港法院被刑事檢控,同時可避免可能需要移交該人往香港境外接受刑事審判所引起的國際或區(qū)際刑事司法合作上的問題。次項新罪名可以切實打擊香港黑社會與外國黑社會因勾結(jié)而于香港境內(nèi)進行與有組織犯罪有關(guān)的各種活動。為避免對此新罪名的舉證困難,亦應同時規(guī)定香港法院可于無須舉證情況下接納外地司法機關(guān)向香港法院提出該外地組織為黑社會的證明。
(三)從修改香港刑法中黑社會定義的方向構(gòu)想
在香港各項有關(guān)黑社會刑法條文中,“三合會”一直以來都是等同于黑社會的一個同義詞。但有關(guān)“三合會”的法律定義確有必要從沿用已久、只局限于使用“三合會”普遍使用的儀式、任何類似或部分類似該儀式的任何社團或采用任何“三合會”名銜、稱謂及術(shù)語的社團的狹窄定義擴張至一個較具彈性的定義。筆者認為香港立法會可通過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4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4日作出的《關(guān)于審理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及香港現(xiàn)時黑社會發(fā)展狀況,把“三合會”的法律定義作一彈性擴張,將人數(shù)較多,組織結(jié)構(gòu)比較緊密,有領(lǐng)導或骨干成員,有較嚴格組織紀律,以通過違法活動及包括暴力等其他手段獲取經(jīng)濟利益為目標的組織亦收納于黑社會法律定義中。尋求通過這個新增彈性定義,使香港目前在不斷演變中的和新一代棄用傳統(tǒng)“三合會”儀式但沿用“三合會”制度及模式的非法社團均能被收納于包括香港《社團條例》和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等條例內(nèi)的“三合會”定義中。
(四)從考慮充公黑社會財富的特別立法的方向構(gòu)想
我國《憲法》第13條及《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第6條均規(guī)定保護包括香港市民在內(nèi)的中國公民之財產(chǎn)權(quán)。故此,為打擊作為黑社會生命泉源的財政基礎(chǔ)而考慮通過立法去充公黑社會財富的同時,亦應就憲法下保障中國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chǎn)不受侵犯權(quán)利二者之間取得平衡。在這方面,可以參考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第10條規(guī)定現(xiàn)任或曾任政府雇員人士有責任向香港法院解釋其財產(chǎn)與其現(xiàn)在或過去官職薪酬不相稱者,若不能作圓滿解釋者乃屬犯罪的規(guī)定,以考慮制訂充公黑社會財產(chǎn)的條文內(nèi)容和罰則。[16]可以預見到這方面的立法將面對是否符合我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的許多挑戰(zhàn),但在為求打擊黑社會有組織犯罪的大前提下,在這方向的構(gòu)想實在有必要和值得作進一步的探討。
注釋:
[1]參見香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2000年。
[2]參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條,香港法例第455章。
[3]參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詳題(序文),香港法例第455章。
[4]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訴李世榮(譯音)案[1998]4HKC280。
[5]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訴鄭敬龍(譯音)等人案CACC67/2002。
[6]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訴譚偉浦(譯音)等人案CACCC32/1998。
[7]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KamSusanto案HCCC214/2002,CACC542/2003。
[8]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訴林希杰(譯音)案DCCC405/2002,CACC84/2003。
[9]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訴蔡光(譯音)案CACC545/2003。
[10]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訴OEIHENGKYWIRYOFACC4/2006。
[11]參見絡加榮(譯音)、陳志強(譯音)、韋君龍(譯音)訴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案FAMC27/1999。
[12]參見彭耀雄(譯音)訴香港警務處處長魏樹基高級督察案HCAL133/2002。
[13]參見康樹華:《有組織犯罪透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280頁。
[14]參見李文燕、柯良棟主編:《黑社會性質(zhì)犯罪防治對策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頁。
[15]參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條,香港法例第455章。
[16]《防止賄賂條例》第10條,香港法例第20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