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群體受害人刑法保護(hù)
時(shí)間:2022-03-19 02:55:53
導(dǎo)語:弱勢群體受害人刑法保護(hù)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diǎn),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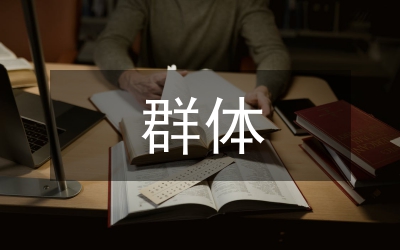
一、問題的提出
在形式上,弱勢群體是一個(gè)虛擬群體,是社會中一些生活困難,能力不足或被邊緣化,受到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稱。在我國,弱勢群體是一個(gè)相對化的概念,而我國學(xué)術(shù)界一般把弱勢群體分為兩類:生理性弱勢群體和社會性弱勢群體[1]。事實(shí)上,在生活中由于弱勢群體缺乏自我保護(hù),侵害弱勢群體利益的事件屢有發(fā)生,每個(gè)人的身邊都不乏活生生的例子。以筆者所生活的城市為例,2018年六、七月間發(fā)生的一起案件便令人心碎。2018年6月26日,南京江寧公安分局官方微博“江寧公安”在線了一則尋找九歲溺水女童尸源的啟事,7月25日,溺水女童家人被找到,隨后南京警方通報(bào)稱,女童是被其父親楊際響和爺爺楊世松推入河中溺亡。而據(jù)江蘇省南京市人民檢察院官方微信公眾號的消息,南京市人民檢察院已經(jīng)批準(zhǔn)逮捕犯罪嫌疑人楊世松,楊際響,其構(gòu)成的罪名則是故意殺人罪。上述的這位九歲女童是一位家境貧寒的腦癱患者,既屬于生理性弱勢群體,也屬于社會性弱勢群體。正是由于該女童的家庭貧困,其爺爺和父親不堪重負(fù),而女孩又沒有自我保衛(wèi)的能力才慘遭厄運(yùn)。女孩小小年紀(jì)卻早早離世的消息,著實(shí)令人惋惜。但這件事背后的問題仍值得我們思考。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弱勢群體本身會具有怎樣易受侵害的特點(diǎn)。就本案中的女童而言,受害人患有腦癱,她的生活幾乎全部由她的家人照顧,其本身不具備思考和防御能力,因此一旦受到侵害,便極有可能遭遇不幸或者不可挽回的后果。不難看出,弱勢群體缺乏自我保護(hù)能力,對抗外來侵害的手段也極為有限。此外,社會公眾也缺乏對于弱勢群體的積極關(guān)注。在日常生活中,大眾對于弱勢群體的重視程度較低,對于弱勢群體予以特殊保護(hù)的宣傳和措施也是比較少見,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弱勢群體的保護(hù)效果。最后,我國缺乏對于弱勢群體的具體性立法保護(hù),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長了弱勢群體受到侵害后所引起的不良社會后果。正是由于我國對于弱勢群體保護(hù)的相關(guān)規(guī)定還不夠完善和健全,以至于弱勢群體的合法權(quán)益缺少有力的法律保障。這一社會現(xiàn)狀越發(fā)引起了教育界、法學(xué)界、專門性保護(hù)機(jī)構(gòu)等的重視。在這其中,由于刑法在社會關(guān)系調(diào)整方面具有威懾性高、嚴(yán)肅性強(qiáng)的特點(diǎn),站在預(yù)防效果和報(bào)應(yīng)效果相結(jié)合的立場上,可以對弱勢群體予以更為直接有效的保護(hù)。因此,研究弱勢群體受害人的刑法保護(hù)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二、弱勢群體受害人的刑法保護(hù)
2.1弱勢群體受害人的刑事立法現(xiàn)狀眾所周知,我國的刑法分為總則和分則兩個(gè)部分。刑法總則主要是從宏觀的角度規(guī)定出什么是犯罪和對于犯罪人員如何適用刑罰的一般原則。經(jīng)筆者研究發(fā)現(xiàn),在目前的刑法總則第一章至第五章的全部內(nèi)容中,我國并未對于弱勢群體受害人的刑法規(guī)制進(jìn)行系統(tǒng)性的梳理和規(guī)定。由于刑法總則缺少對于弱勢群體受害人所實(shí)施的的犯罪的直接規(guī)定,而刑法分則的規(guī)定又相對分散,這就使得弱勢群體受害人在遭遇侵害后,無法得到最根本意義上的明確保護(hù)。而在其他的具有總則性質(zhì)的規(guī)范中,少有的規(guī)定主要是將弱勢群體受害人作為酌定量刑情節(jié)而加以了規(guī)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dǎo)意見》第13條中規(guī)定,對于犯罪對象為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孕婦等弱勢人員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zhì),犯罪的嚴(yán)重程度等情況,可以增加基準(zhǔn)刑的20%以下。然而,由于司法機(jī)關(guān)頒布的量刑指導(dǎo)意見并不具有最根本的強(qiáng)制性,具體辦案法院在最終決定量刑時(shí),仍然會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弱勢群體受害人的保護(hù)很難合理落實(shí)。而從分則的視角看,刑法分則中對于弱勢群體受害人的個(gè)別性保護(hù),主要體現(xiàn)在了以弱勢群體為犯罪對象的定罪事實(shí)或者量刑加重情節(jié)的規(guī)定上。我國刑法分則中,將是否把弱勢群體受害人作為定罪事實(shí),從而保護(hù)弱勢群體受害人利益的分則條文較多,例如我國刑法分則第240條規(guī)定的拐賣婦女兒童罪、第262條規(guī)定的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以及第260條所規(guī)定的虐待被監(jiān)護(hù)、看護(hù)人罪等,都具體闡釋了某些犯罪行為嚴(yán)重危害了弱勢群體合法利益時(shí),需要受到刑法的譴責(zé)和刑罰的處罰。而具體的刑罰適用,則需根據(jù)不同犯罪的不同犯罪要件而定。經(jīng)筆者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刑法分則中規(guī)定的弱勢群體傾斜性保護(hù)的對象多為婦女、兒童和老年人等社會公認(rèn)的弱勢群體,顯然很難涵蓋住本論文開篇處所提到的弱勢群體的定義。因此,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通過刑法分則規(guī)定出特定定罪事實(shí)而全方位救濟(jì)弱勢群體的有效性也不免大打折扣。另外在刑法分則中,將犯罪對象為社會弱勢群體規(guī)定為量刑加重情節(jié)的條文也不在少數(shù)。例如,刑法分則第263條搶劫罪中規(guī)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搶險(xiǎn),救災(zāi),救濟(jì)物資的,可加重處罰直至死刑;又例如刑法第237條的強(qiáng)制猥褻侮辱罪中規(guī)定,猥褻兒童的,依照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qiáng)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規(guī)定從重處罰。以上兩條立法例充分展現(xiàn)了在我國分則中,對于極其嚴(yán)重的犯罪行為的從重處罰不僅十分重要,而且同樣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然而,不能忽視的是,刑法的調(diào)整往往具有事后性,而在刑法分則的條款,只涉及了社會生活中已經(jīng)料想到的情況,相比社會中的各種現(xiàn)象,涵蓋面仍然較小。面對現(xiàn)實(shí)社會中日新月異,層出不窮的新問題,分則還有待完善和改進(jìn)。以上筆者概述了我國現(xiàn)有刑法中涉及弱勢群體受害人保護(hù)的基本內(nèi)容。總的來說,我國刑法總則缺少對于弱勢群體受害人的原則性保障,刑法分則中以弱勢群體為犯罪對象的定罪事實(shí)或者量刑加重情節(jié)的規(guī)定,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們還必須進(jìn)一步全面分析弱勢群體受害人刑法保護(hù)的不足,以期實(shí)現(xiàn)法律的準(zhǔn)確認(rèn)識和再完善。2.2對我國弱群體受害人刑法保護(hù)的法學(xué)分析筆者認(rèn)為,對于我國目前弱勢群體受害人刑法保護(hù)的分析,可以從以下幾點(diǎn)展開。1、刑事政策視角的分析。長久以來,我國堅(jiān)持“寬嚴(yán)相濟(jì)”的刑事政策,其基本要求是要根據(jù)犯罪的具體情況,實(shí)行區(qū)別對待,做到該寬則寬,當(dāng)嚴(yán)則嚴(yán),寬嚴(yán)相濟(jì),罰當(dāng)其罪,堅(jiān)持打擊和孤立極少數(shù)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數(shù),最大限度的減少社會對立面,促進(jìn)社會和諧穩(wěn)定,維護(hù)國家長治久安。在刑法總則中的“寬”與“嚴(yán)”應(yīng)當(dāng)是一對相對的概念,例如刑法第17條規(guī)定的“未成年的限制責(zé)任”以及第49條規(guī)定的“對于死刑適用的未成年人、婦女、老年人適用限制”等內(nèi)容均體現(xiàn)了該寬則寬的刑事政策,從限制刑事責(zé)任能力、人道主義保護(hù)等角度考慮,以上該寬則寬的原則,有利于實(shí)現(xiàn)社會實(shí)質(zhì)公平正義的目標(biāo),達(dá)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然而,我國刑法總則部分缺少弱勢群體受害人傾斜性保護(hù)的內(nèi)容,不僅使得弱勢群體受害人缺少整體性的傾斜保護(hù),也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當(dāng)嚴(yán)則嚴(yán)”的刑事政策。鑒于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存在對于弱勢群體進(jìn)行特別保護(hù)的必要性,對于上述保護(hù)性內(nèi)容的缺失,應(yīng)當(dāng)考慮在刑法總則中加以系統(tǒng)性的補(bǔ)充。2、從憲法平等原則的角度分析。我國憲法第33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不等于均等,平等是具有一定現(xiàn)實(shí)意義的,即在社會經(jīng)濟(jì)政治等領(lǐng)域,不論種族,性別,階層,共同地平等享有權(quán)利,適用法律。憲法所規(guī)定的平等原則是蘊(yùn)含了社會資源分配之平等、公平等諸多價(jià)值的綜合性原則,這不僅表現(xiàn)在憲法權(quán)利的平等實(shí)現(xiàn),也體現(xiàn)在了特別情況下所允許的合理差異被正確地貫徹落實(shí)。在條件相同或類似的情況下,平等意味著同樣情況同樣對待,不應(yīng)有差別,但在條件不相同或不類似的情況下,就應(yīng)根據(jù)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例如,當(dāng)弱勢群體為受害人時(shí),考慮到社會實(shí)質(zhì)平等的正義要求,給予一定的特殊保護(hù),不僅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合理性,同樣也體現(xiàn)出了憲法平等原則所允許的合理差別。因此,對于受害人的傾斜保護(hù)作為憲法合理差異原則的應(yīng)有之義,可以為刑法的進(jìn)一步完善提供理論基礎(chǔ)。3、從罪刑法定原則的視角分析。根據(jù)我國刑法第2條的規(guī)定,罪刑法定原則是指犯罪行為的界定、種類、構(gòu)成條件和刑罰處罰的種類、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規(guī)定。對于刑法中沒有明文規(guī)定為犯罪行為的行為,不得定罪處罰。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dǎo)意見》第13條的規(guī)定,酌定量刑情節(jié)是刑法未文明規(guī)定,僅僅根據(jù)立法精神與刑事政策,在量刑時(shí)酌情考慮的情節(jié)。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dǎo)意見》為代表的酌定量刑情節(jié)缺乏統(tǒng)一的適用標(biāo)準(zhǔn),自由裁量權(quán)空間過大,這不免導(dǎo)致了弱勢群體受害人在刑法總則層面的保護(hù)難以統(tǒng)一和明確,而酌定量刑情節(jié)無法統(tǒng)一量刑標(biāo)準(zhǔn),恰恰是與罪刑法定精神相違背的。4、從刑法的社會效果進(jìn)行分析。在我國刑法分則中,涉及弱勢群體受害人保護(hù)的相關(guān)內(nèi)容較為分散零碎,其中所體現(xiàn)出的教育意義也難以被社會大眾所廣泛接受,這使得刑法所應(yīng)當(dāng)具有的社會預(yù)防效果不明顯。通常而言,刑法分則主要是通過各構(gòu)成要件的明確規(guī)定,將部分弱勢群體的刑法保護(hù)上升至較為明確的程度,從而起到警示犯罪的作用。然而,對于沒有將弱勢受害群體作為法定構(gòu)成要件的犯罪行為而言,分則中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很難起到警示犯罪、事前預(yù)防的作用。因此,站在如何將刑法的報(bào)應(yīng)效果與預(yù)防效果相結(jié)合的立場上,這勢必要求在刑法總則和分則中進(jìn)一步完善和協(xié)調(diào)弱勢群體受害人保護(hù)的相關(guān)問題。5、從國家救助立法與刑法交叉視野的角度分析。必須指出的是,弱勢群體作為極易受到不法侵害的一方,一旦受到侵害,僅通過刑罰的制裁,很難實(shí)現(xiàn)修復(fù)已被破壞的社會關(guān)系,一旦犯罪分子不積極履行民事賠償責(zé)任,弱勢群體一方的合法利益就難以得到切實(shí)的保護(hù)。由于刑法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以刑罰為手段,嚴(yán)懲犯罪,預(yù)防犯罪,而面對特定社會轉(zhuǎn)型時(shí)期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問題,我國法律缺少系統(tǒng)的事后補(bǔ)償機(jī)制,因此無法將被破壞的社會關(guān)系還原到被破壞以前的狀態(tài)。對于以上問題,采取制度手段使刑法與其他配套制度相結(jié)合,從而維護(hù)弱勢群體受害人的合法權(quán)利就顯得十分必要。如果可以使國家救助立法與刑法相結(jié)合,在社會弱勢一方無法得到應(yīng)有的補(bǔ)償時(shí),由國家進(jìn)行行之有效的救助和事后補(bǔ)償,這未必不是我國未來立法的一個(gè)發(fā)展方向。綜上分析,無論弱勢群體受害人的刑事專門立法還是相關(guān)配套制度都存在立法供給的明顯不足。因此研究國外相關(guān)立法,并對我國弱勢群體受害人的刑法保護(hù)相關(guān)制度提出建議將十分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三、我國弱勢群體受害人刑法保護(hù)的進(jìn)一步完善
3.1在刑法原則中建立起“弱勢受害群體的傾斜保護(hù)”原則。首先,傾斜性保護(hù)弱勢受害群體符合憲法的平等原則。合理差別本是平等原則的題中之意,其正是在合理程度上所采取的具有合理依據(jù)的差別,進(jìn)而充分體現(xiàn)出憲法平等原則的價(jià)值和理念。其次,樹立這一原則有利于社會生活中樹立起保護(hù)弱勢群體的整體價(jià)值觀念。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忽視了對弱勢群體的保護(hù),如果在刑法原則中建立弱勢群體的傾斜保護(hù)機(jī)制,將有利于引領(lǐng)人們認(rèn)識到弱勢受害群體保護(h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而形成良好的社會風(fēng)氣,促進(jìn)弱勢群體受害人的保護(hù)。另外,由于刑法原則具有宏觀指導(dǎo)性,從宏觀層面上來看,更有利于加強(qiáng)社會弱勢群體的刑法分則保護(hù)效果。因此,刑法原則上的規(guī)定將給予弱勢群體最根本、有效、直接的保護(hù)。3.2法定量刑情節(jié)的完善。誠如筆者在上文中的分析,我國總則層面對弱勢群體的保護(hù)主要體現(xiàn)在了《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dǎo)意見》等規(guī)范性文件之中,其是否具有充足的法定性和穩(wěn)定性仍值得研究。為了彌合我國社會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社會制度的不足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所帶來的社會結(jié)構(gòu)變化,對弱勢群體應(yīng)當(dāng)通過法定量刑情節(jié)的明確規(guī)定予以傾斜性保護(hù)。從國外立法來看,例如俄羅斯刑法典總則第36條就規(guī)定,對于犯罪人明知正在懷孕的婦女實(shí)施犯罪,以及對幼年人及其他沒有自衛(wèi)能力或孤立無援的人實(shí)施犯罪或者從屬于犯罪人的人實(shí)施犯罪的,加重處罰[2]。以上是俄羅斯刑法典總則中涉及弱勢群體受害人保護(hù)的一條加重情節(jié),該加重情節(jié)具體詳細(xì)地表述了對于弱勢群體的法律量刑規(guī)范,其為司法實(shí)踐提供了明確的標(biāo)準(zhǔn),相較于我國分則中的散布的規(guī)定,俄羅斯刑法典更為整合明確,而且強(qiáng)化了弱勢群體刑法保護(hù)的力度,值得我國借鑒。3.3受害人國家補(bǔ)償機(jī)制的建立。相比于我國國家補(bǔ)償機(jī)制的相對欠缺,國外已經(jīng)普遍建立起了較為成熟的刑事補(bǔ)償制度。二戰(zhàn)之后,新西蘭在1963年建立了第一個(gè)刑事?lián)p害補(bǔ)償法庭。此后,英格蘭,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也陸續(xù)開始對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實(shí)行國家補(bǔ)償。1985年11月29日聯(lián)合國大會根據(jù)聯(lián)合國第七屆預(yù)防犯罪和犯罪待遇大會的建議,通過了《關(guān)于被害者》的決議及其附件《為罪行和濫用權(quán)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該公約明確規(guī)定了國家補(bǔ)償制度的對象、方式、資金來源和補(bǔ)償程序。從上述內(nèi)容中不難發(fā)現(xiàn),受害人國家補(bǔ)償機(jī)制在世界各地普遍采用。由此也可以證明,建立受害人國家補(bǔ)償機(jī)制是十分必要的。在日常生活中,不容否認(rèn)的是,存在一些弱勢群體受害人在遭遇侵害后,由于罪犯本身的原因或是社會轉(zhuǎn)型時(shí)期所帶來的矛盾問題,使得弱勢群體受害人的相關(guān)權(quán)益無法得到保障的現(xiàn)象。這就需要由國家的補(bǔ)償機(jī)制來保證各方權(quán)益最大化,平衡社會矛盾,實(shí)現(xiàn)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四、總結(jié)
以上,筆者以南京女童案為切入點(diǎn),根據(jù)我國弱勢群體受害人保護(hù)制度所存在的問題,通過梳理我國目前對于弱勢群體的相關(guān)保護(hù)的立法現(xiàn)狀,主要從刑法、憲法、社會救助法等多個(gè)角度,對我國立法中所存在的不足之處進(jìn)行了分析。根據(jù)筆者的分析,我國關(guān)于弱勢群體受害人保護(hù)的立法雖然散布在刑法分則的具體條文中,但是仍存在著刑法總則中缺少原則性保護(hù)和具體制度規(guī)范,社會補(bǔ)償機(jī)制不完善等問題。為此,在我國已有的立法基礎(chǔ)上,如何使弱勢群體的權(quán)益得到最好的保護(hù),如何做到防治犯罪,建立整體性的保護(hù)弱勢群體的價(jià)值觀念,需要我國進(jìn)一步完善和改進(jìn)法律,更需要我們每一位公民的共同努力,這其中的改進(jìn)之策仍值得我們進(jìn)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xiàn)
[1]趙秉志、杜邈:“論弱勢群體的刑法保護(hù)——由孫志剛案引發(fā)的思考”,載《中州法學(xué)》2005年第5期,第73頁。
[2]陳志剛:“弱勢群體保護(hù)的法律之維”,載《政法論叢》2015年第1期,第64頁。
作者:樂馨 單位:南京東山外國語學(xu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