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筑的文化閱讀論文
時間:2022-08-04 03:26:00
導語:城市建筑的文化閱讀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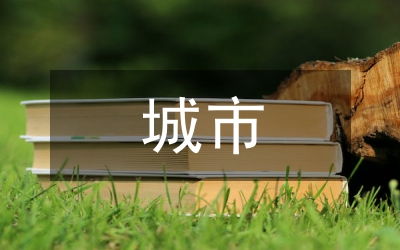
摘要:關于城市的界說之一,是美國城市建筑學家劉易斯。芒福德的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確,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觀,是我們區別、認識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徑。城市建筑被稱為“凝固的”,它承載、凝固的不僅僅是建筑,而且是不同的文化、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文化等等。
關鍵詞:建筑文化城市建筑
大都市的形成主要源自兩種不同的歷史:一些口岸城市如上海、香港、青島、大連等,在殖民統治或租界時期,主要是在外國人的管理下形成的今天的城市格局和面貌;而內地的歷史文化古城,如北京、南京、西安等,主要是在近幾十年的社會變遷中,由中國人自己管理、建設和改造,形成的今天的城市面貌。
作為新中國首都,北京成為一個活的標本,一個令人讀之不盡、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僅在體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種不同文化的沖突和張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而發生在北京的事往往是具有全國性的。
北京和南京
雖然在許多方面,北京和上海最顯著地形成一種對比;但在城市建設和規劃上,最具有可比性的卻是北京和南京,它們是兩個時代分別由中國人自己規劃、建設的國都。
1927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后,即成立了“首都建設委員會”,以美國設計師墨菲和古力治為顧問,負責制定《首都計劃》。于1929年底完成并公布的這一計劃,包括史地概略、人口預測、中央政治區、建筑形式、道路系統、水道改良、管理、鐵路與車站、港口計劃、飛機場、自來水、電力、住宅、學校、、浦口建設、城市分區、實施程序、款項籌集等許多方面。按照《首都計劃》,南京城明確分為幾個功能不同的區域,如中央政治區、南京市行政區、公園區、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這是我國按照現代城市規劃的理念,按功能分區進行城市規劃的最先嘗試。如何設置首都的政治功能是該規劃最核心的之一。起初,也有仿照柏林、倫敦之例,在南京城外另建新都的設想,因費時耗力,未予通過。規劃確定的是在中山門外、紫金山南麓新建中央政治區。
在規劃和城市建筑風格的指導思想上,《首都計劃》稱其主旨是“發揚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城市建筑采用“中國固有之形式”,“以中國之裝飾,施之我國建筑之上”(羅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設》,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沿街的重要建筑,均為傳統大屋頂的民族樣式,如財政部、勵志社、兵工署、中央博物院等。出現了一批現代宮殿式建筑,如南京大學教學樓、南京師范大學教學樓等;以及一批在實質上融合中西的優秀建筑,如中山陵音樂臺、軍區總、江蘇省美術館、第二歷史檔案館等。由于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該規劃的不少未能全部實施,包括中央政治區的建設。但現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城市面貌基本是由這一規劃奠定的,今日南京濃蔭匝地的城市道路,鼓樓、新街口的環島式街心廣場,都是在那時形成的。
與南京相似的是,五十年代初新中國首都北京的城市規劃,也是由一批留學歐美的建筑家進行的,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也是中央政治區的設置。出于保護古都文化的考慮,梁思成、陳占祥按照按功能分區的規劃思想,提出在舊城之外的公主墳一帶另建中央行政區的方案,遭完全否定。當時之否定另建新區,除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也有坐擁皇城的心理,以及視舊城為封建遺留,需要加以“革命”和改造等意識形態方面的深層原因。隨著大規模拆毀城墻、城樓、牌樓,在舊城區內對王府、壇廟、名宅等“廢物利用”,見縫插針地興建工廠、機關、學校,北京古城的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五十年代確立的以舊城改建、擴建為中心的思路一直延續至今。對二環路以內舊城的超強度開發,致使人流、物流、車流向內城過度集中,造成嚴重的住房壓力、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問題。它被恰當地定名為“破壞性建設”。其實際效果,就建筑面貌而言,吳良鏞先生為“好的拆了,濫的更濫,古城毀損,新建凌亂”(吳良鏞《城市規劃設計論文集》,燕山出版社,1988年)。雖然建立功能分散的、多個城市中心的意見始終不絕,但北京仍以“鋪大餅”的方式迅速擴張。近年來在近郊已經建立了若干個規模巨大的新居民區,然而,那些擁有幾十萬人口的新區卻并沒有建立和發育城市的功能,居民們仍需長途跋涉,到市中心工作和活動。
今日北京的事實已經回答了當年的爭論。城市輪廓線東起高碑店,西至石景山,南抵大紅門,北達清河鎮,方圓約六百平方公里,已經是老北京城面積的十倍。換而言之,我們已經建設了相當于十個北京城,而那個世界上獨一無二、具有高度歷史文化價值的北京明清古城,卻終于在我們眼前日新月異地消失了。
新北京: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新北京的建筑風貌成為我們透視體制文化變遷的一個窗口。
1953年所作的首都建設“規劃草案”,其基本要點包括:以舊城的中央區為中央首腦機關所在地,使其成為全國人民向往的中心;首都要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特別是要成為中國強大的工業基地和技術中心;改建擴建北京,要打破舊格局的限制和束縛,使首都成為適應集體主義生活方式的社會主義城市;改造道路系統、改變水資源缺乏等條件,為工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其總方針的表述十分奇特也很傳神:“為生產服務,為中央服務,歸根結底就是為勞動人民服務。”(《當代中國的北京》上冊,第86頁)這一實現革命化、工業化的思路,直接導致了“破舊立新”的城市建設方針。
五十年代北京建設的突出成就主要體現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的建設和一批標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長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廣場,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民族文化宮、軍事博物館、中國美術館等“十大建筑”,構成了以雄偉、莊嚴、壯麗、堂皇、開闊等為特征的新國都的視覺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類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門城樓等歷史建筑文化意蘊的轉換,突出體現了新體制文化對傳統權威的借助和重構。在很長的時間內,在人們心目中它們已不再是一個歷史建筑,而成為黨中央、的象征符號,如“天安門上太陽升”、“中南海的燈光”之類話語所寄寓的意義。
“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學上的體現,是“經濟、實用,在可能的情況下追求美觀”的原則。一批民族風格的公共建筑,體現了當時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為三里河一帶“四部一會”琉璃瓦大屋頂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費”,然后上升為政治問題━但這一早期嘗試畢竟為新中國建筑的文脈寫下重要一筆。這一時期的建筑實踐與南京民國時期的新建筑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妙。現在看來,當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敘事”大體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個時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氣度和有明確理念的審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規劃)的能力。
在城市建設的歷史上,六、七十年代是一個停滯和平庸的時期,唯一迅速增長的是人口。以北京為例,1982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比1949年底增長了4.8倍,達917.8萬人。那也是簡易房、筒子樓大行其道的時期。除了十里長街的觀瞻之外,沉重的人口壓力,革命時期的混亂無序,使城市不堪重負,大多數四合院正是從那時起,變成了破敗凋敝、人際關系緊張的大雜院。
當八十年代新的建設高潮來臨時,和中國的各大城市一樣,北京又一次成為到處開膛破肚、徹夜施工的大工地,但其面臨的問題卻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樣單一和單純。城市建設承載著人口壓力、民生改善、國家形象、商業利益、政治利益、部門利益、政府政績等來自不同方向的復雜壓力,處于各種不同的欲望、抱負、追求、利益前所未有的緊張擠壓之中。
在市場經濟、分權管理的新體制下,嚴整統一、“君臨天下”的中央意志漸漸退隱了,城市改造新的主體是有關政府部門和房地產商,新的強勁動力是商業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環境和利益機制中,統一的城市規劃雖然仍在制定,卻失去了整合、制約的力量。北京又一次脫胎換骨。但與同期的上海相比,無論在單體建筑的新穎和獨特性上,還是在整體風格的協調上,都遠遠落在了上海之后。號稱“中華第一街”的長安街上的當代建筑成為北京人調侃的對象:正面棕黃色、側面銀白色的交通部大樓被稱為“陰陽臉”,門字型的海關大樓被稱為“大褲衩”,曲折有致、中間有一月亮門的婦聯大樓名為“肚臍眼”……
首都的建筑何以難以保持協調的風格和應有的水準,這似乎是很令人費解的。其所透露的其實是體制文化的變異。北京市各行其是、參差不齊的公共建筑,可以說是條塊分割的“部門所有制”(有人稱為“部落主義”)典型的文化體現。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各部門的建筑主要是由本部門按照一己需要設計、建造的,無論選址還是建筑風格,都是首都規劃委員會難以干預和協調的。同時,這種部門主義的建筑,較多地凝固了“長官意志”。
權力所及,各個城市都不乏歷屆領導人留下的“標志性建筑”。在北京,典型為前市長陳希同提倡的在高樓頂上加蓋小亭子的建筑(被稱為“戴綠帽子”)。其頂尖之作、也是收山之作是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它可能是一個標本,集中了此類建筑的某種文化特性:將個人的喜好蠻霸地強加于社會,把巨大當成偉大,把紀念性的氣概不凡放在首位,而無視公共建筑方便、實用的功能。西客站頂上一個沒有實際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資竟達八千萬元之巨。近年來,在一些城市“領導人工程”、“形象工程”仍呈蔓延擴大之勢,導致無功能建筑的大量興起。一些城市大興建廣場、修草地、鑄大鐘、建城市雕塑之風,在這場比“大”的競爭中,有的縣級市的廣場面積甚至超過了天安門廣場。
與之相應的是,在部門割據和地方主義的體制格局中,跨地域、跨地區的城市規劃幾乎成為不可能。盡管專家、學者一再呼吁,北京市的建設和發展,應在華北經濟圈、京津冀唐地區的整體發展中,按照“大北京”的概念進行設計和規劃,如同大東京、大巴黎那樣,但這至今仍是知識分子的紙上談兵。
高度之爭:城市建設的“香港模式”
對高度的崇拜和競爭,成為當代城市建設突出的主題,它也尖銳地體現在北京的建筑中。嚴格地說,這種崇拜非自今日始,它滲透在中國人的現代化意識之中。從大半個世紀以來國人對上海灘24層高的國際飯店的嘖嘖贊嘆,到對今日浦東88層高的金茂大廈的滿腔自豪,都反映了這種“現代化=高樓大廈”的集體認同。事實上,在西方國家經歷了工業化某個時期對高層建筑的新奇之后,對高樓大廈的競爭幾乎集中在東亞,尤其是那些“從稻田中拔地而起的”新興國家和城市,無不把自己的經濟成就和自豪感主要寄托在對建筑物高度的追求上。
由于特殊的地理條件,八十年代以來對國人最大的當屬港臺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當城市開始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之時,香港高樓密集的都市風光作為“化”的典型圖景,早已深入人心,成為內地競相仿效的對象。當然,香港對內地建設的深刻影響,不止于作為現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額的商業資本和大規模房地產開發,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記。
在北京城,對高度的競爭是悲劇性的。因為開闊舒緩的平面布局和遼闊無礙的天際輪廓線,正是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體現。對建筑物高度的控制和反控制馬上白熱化。八十年代中期,混亂無序的商業開發,致使在緊鄰故宮的舊城的核心區內,在王府井一帶相繼出現了一批高層建筑,如王府飯店、和平賓館等。與此同時,京廣中心、京城大廈和國貿中心等玻璃幕墻的摩天大樓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傳統的天際線和城市景觀。今天,無論在故宮、北海還是頤和園四望,背景無不是林立的高樓。在學術界的呼吁下,1985年北京市出臺市區建筑高度控制方案,規定以故宮為中心,分層次由內向外控制建筑高度。1993年中央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規定,“長安街、前三門大街兩側和二環路內側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許建部分高層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個別地段控制在45米以下”。
對這一控制最強烈的挑戰,來自香港李嘉誠所屬集團在王府井路口建立的亞洲最大的商業性房地產建筑群“東方廣場”。它招致海內外許多有識之士的批評,引起強烈爭議的原因基本是文化性的,擔憂其對北京古都風貌將造成難以估量的破壞。斥資20億美元,建造面積達80萬平方米的東方廣場,原設計方案東西寬480米,建筑高度70多米。而近在咫尺的天安門高度為35米;人民英雄紀念碑高度為38米;人民大會堂的建筑高度為31米,最高處才40米,總建筑面積17萬平方米。這意味著,這座體量4倍于大會堂、高度2倍于大會堂的龐然大物將使天安門廣場上的這些標志性建筑變得矮小,導致城市中心偏移,從而打亂形成的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首都城市格局。作為妥協的產物,東方廣場終于被攔腰截斷,呈現粗壯矮胖的身姿(經修改降低高度和容積率后,仍近40米高)。與之相映成趣的是東方廣場西側建于七十年代初的北京飯店新樓。它也是經修改設計后被“裁短”的,原因是出于對中南海安全的考慮。兩者命運相同原因卻大不相同,也算是一種進步了。
近年來,北京市廣建“金街”、“銀街”,“中央商務區”,孜孜追求成為中國的“曼哈頓”、“華爾街”和“硅谷”時,作為文化中心的建設幾乎淡不可聞。在這一建設高潮中,長安街東側已經被港資為主的一批寫字樓、商廈搶灘。而城市高度控制在舊城區則被全面突破,幾無嚴肅性、權威性可言。這一事態并不是孤立的。類似的一例,是李嘉誠所屬集團在福州市中心區進行的成片房地產開發,將擁有眾多文物的著名歷史文化街區“三坊七巷”毀壞殆盡,面目全非。
最早對“香港模式”表示擔憂、發出警告的是被稱為建筑界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建筑大師張開濟。早在七十年代末,當火柴盒建筑剛剛出現、備受青睞時,他就指出“現代化不等于高層建筑”。當前,他主要是反對北京和內地在住宅建設上盲目仿效香港超高、超密的模式,興建“塔樓+梅花樁”式的小區。高層住宅由于造價高、使用系數低、能源消耗大、經常費用高,朝向造成大量“陽光貧困戶”,以及不利于老人、兒童戶外活動和鄰里交往等諸多問題,在許多國家已被控制和禁止建設,一些國家則正在拆除幾十年前建造的此類建筑。他認為比較可行的是用“多層、高密度”替代“高層、高密度”。
一些高層建筑的支持者認為,這是在我國土地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大規模解決住房問題的必然選擇,日本、香港均是在這一壓力之下選擇了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層住宅群換取了較為疏朗的整體生存環境。但正如識者所言,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并不是某種建設理念的產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問題上任由市場力量主宰,爆炒地價至離奇的程度,房地產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產物。它損害的,正是大多數普通市民的生活質量和利益(詳見1998年9月2日、9月9日、10月7日《北京青年報》討論文章)。
這恐怕是當下正在中國發生,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城市建設為房地產開發浪潮所牽引,不受制約的商業化正在成為主宰城市命運的決定性力量。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不同民族、國家城市建筑風格的任務更為復雜艱巨。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稱,有十家左右美國的跨國房地產開發公司在操縱世界建筑市場,以跨國資本為后盾的文化中心則在制造和輸出各種建筑和流行風格,這一現象已引起國際建筑協會的高度重視(《北京青年報》1999年4月2日,《北京晚報》1999年6月4日)。
,知識分子的意見很難改變什么。玻璃幕墻高樓仍然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各地推進。在云南邊城麗江,興建起了類似希爾頓飯店那樣的華麗大廈。西湖之濱早已高樓林立,新建的杭州市政府大廈,被市民詬病為“削尖腦袋,挖空心思,兩面三刀,歪門邪道”。適值世紀之交,城市之間對高度的競爭又增加新的動力━興建“跨世紀的標志性建筑”。據稱,福州市將建一座主樓高306米、88層的摩天大樓,主體建筑由金銀兩色的玻璃幕墻組成,總投資20多億,高度為福建第一,全國第三。而上海浦東在新竣工的金茂大廈附近,又將建設一座更高的高樓。
建筑中的流行文化
當上海以“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自詡和驕傲時,它標識的是城市之間的另一場競爭━速度之爭。每一個城市的領導者都惟恐變化太小、變得太慢,落在人后,因為領導人的任期是短暫的。以北京為例,近年來僅住宅建設的速度,即達到每年竣工800多萬平方米。為了加快速度,采用的是用推土機開路、大拆大建的成片土地開發的模式。許多有數百年歷史的文化遺跡、胡同和老房子,甚至未及甄別、鑒定便被夷為平地。當張開濟等建筑和文物專家呼吁北京城市建設應放慢速度,以為文物保護留下必要的時間時,建設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了,并且將開發的權力下放到各區,鼓勵各區之間開展速度的競賽。
當社會向市場化、世俗化轉變之時,建筑從過去更為重視具有恒久價值的審美感受、意識形態的超越性力量、統治者的意志和權威,以及精英階層的文化趣味,轉為重視和強調現實的功利、即時需要、潮流等等。權力的結構也發生了轉移,從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轉為純粹的商業操作。在許多情況下,地方政府放棄了其應有的職責,成為房地產商的合伙人。新的工作機制于是成為“規劃聽領導的,領導聽老板的”。這種不甚健康的商業化,必然意味著歷史傳統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化旁落,意味著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麥當勞化。一座座失去記憶的城市被大量復制,一批批速成、單調的建筑迅速填充著城市的空間,粗暴地改變著人們的視覺。在新人類的詞典中,“廣場”不再是巨大的和物理空間,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園”是樓旁狹窄的綠化帶,“森林”則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園”式諧謔、游戲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歐洲古典建筑紛紛出籠,加入著世紀末大眾文化的狂歡。
大眾的流行文化和社會心理鮮明地積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東部的中小城市、城鎮和廣大,不變的時尚是磁磚貼面、藍玻璃的現代建筑。它為什么會如此深入人心、廣為流行而且經久不衰,當成為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課題。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建筑時尚則經歷了火柴盒式的高層建筑、高樓大廈+小亭子、摩天大樓+玻璃幕墻,以及仿歐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階段。許多人到了歐洲之后,只見綠樹掩映中的小樓而難覓高樓,不禁悵然若失,不知究竟誰更現代化。
歐陸風情不可阻擋地成為最新的流行。當上海含情脈脈地重溫其晚近的這一小傳統時,各個城市則由娛樂場所大力張揚這一最新時尚。形形色色的娛樂城無不裝飾著羅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調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請法國建筑師設計成為最酷的豪舉。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國人之手,在建筑風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當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國門的街頭漫步,經常會產生不知身在何處、時空倒錯的感覺。
法國建筑師在北京的最新成就是備受爭議的國家大劇院。由于它的復雜功能和在天安門廣場一側的特殊位置,其入選方案舉國矚目。它最終被擅長機場設計的法國建筑師安德魯設計成浮在水面之上、銀光閃閃的巨大金屬半球,被北京人稱為“大水泡”。作為北京市最獨特的另類建筑,它因其后現代風格、建筑功能不甚合理和極其高昂的造價,遭到了家、建筑師的強烈抵制。有趣的說法之一,是法國人總算報了貝聿銘在盧浮宮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的確,不論我們喜歡與否,它橫陳在首都的中心和世紀交替的時點上,是一個觸目的標志,一個強烈的象征,宣告著老北京文化的消解、一段錯綜復雜的歷史和情感的終結,宣告著多元文化、異質文化融合的時期到來。
另一種疑問是這樣的:北京目前并不算很多的文化設施、演出場所得到充分利用了嗎?北京究竟能為國家大劇院提供多少高水平的演出?十分巧合的是,廣州市擬建的大劇院因其耗資巨大,在務實的人大代表的質詢下終告流產。這一提問的價值在于它觸及了城市現代化的本質。對城市這個“文化的容器”,歸根到底,其中有沒有文化、有什么樣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說,城市的現代性最終是由其文化軟件制約和說明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北京和上海的區別,比它們在城市建筑上表現出的更為重大。
十字路口的城市
城市社會的真正內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間、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擴大。市民文化成為城市社會的一個恰當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體味了街道的人間尺度和城市的人間情懷。充滿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馬路兩側的綠樹可以熱烈地相互交接。接續了昔日茶館、咖啡館的傳統,上海街頭遍布的紅茶館再次成為老百姓的生活空間,在那里年輕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處。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況味。然而,北京的茶館自幾十年前消匿之后,成為了話劇舞臺上的保留節目。當它重返人間時,卻成為向洋人展銷京味的場所,或者人開辦的高消費去處,在那里,我看見過白領在下圍棋。類似地,毗鄰使館區的三里屯酒吧一條街明確成為外國人的社交場所、北京的高級白領和文化另類的身份認證處。
廣場的處境是另一個說明。當群眾性政治集會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門廣場便越來越因缺乏實際功用而顯得大而無當和無所適從。在這片干燥、炎熱、堅硬和廣闊的場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寧,難以解決各種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廣場則迅速完成了轉型,用博物館和歌劇院標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場、綠地和廣場鴿使之成為市民休閑、購物的實用場所,消解了體制文化的傳統象征。然而,精明強干的政府在它巨細無余的管理中,也消解著另一種可能性。整潔干凈的上海,既沒有北京那樣的遍地流民、猖獗的盜版,也沒有北京那樣豐富活潑的體制外文化空間;既沒有浙江村,也沒有中關村。
被現代生活割裂在胡同、大院和小區里的北京市民,自有內在的力量和邏輯。當《北京晚報》炮制著類似小靳莊詩歌那樣歌頌美好生活的新民謠時,北京市民對平庸生活的抗爭從未停止。一種是貧嘴張大民式的,以小人物自嘲自賤的傳統方式,化解生活的辛酸和無奈。另一種是家張大力式的,他用“把臉畫在墻上”的先鋒行為,向這個喧囂而沉悶的社會作出一個怪誕的姿態,發出一個奇異的聲響。而游歷西藏達十年之久的自由電視人溫普林,寫下這樣的句子:“我深深地懷念有酒有狼有姑娘笑聲的夜晚,那一切是我們人生中的珍藏。”(溫普林《茫茫轉經路》,227頁,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
城市快車依然循著世俗化和商業化的軌道凱歌行進。北京市開始興建的又一條通衢大道,使發現不久的曹雪芹故居遺址面臨滅頂之災,引發了知識分子新的抗議浪潮。建筑師和規劃專家的反思認為,二戰以來在現代主義理論指導下以大規模改建為特征的城市更新運動,在西方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應該認識到“社區”規劃、漸進式規劃、公共選擇規劃、歷史街區修復、小規模改建、住戶自建等多種新的理論和實踐的價值。大城市的生與死成為令人興奮的話題,一個重要原因是今年春天狂烈的沙塵暴、嚴重的干旱和水資源的極度匱乏,凸顯了北京作為沙漠化邊緣城市的危急地位。人們公開和私下議論的問題是:北京會被迫遷都嗎?
- 上一篇:建筑審美標準分析論文
- 下一篇:建筑外部空間設計分析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