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論綱
時間:2022-05-26 12:39:00
導語:心理學論綱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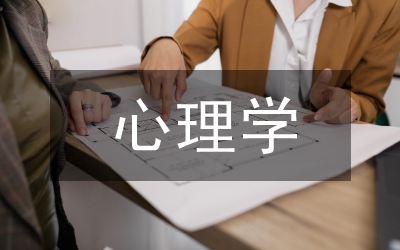
在古代的印度和中國,各大宗教的思想家通過對經典的微言大義加以詮釋和組織建立了一系列體大思精的形上學體系。在近代中國,這一古老的思想傳統因為熊十力的《新唯識論》獲得了新生。以唯識學的觀念詮釋儒家原典《周易》,熊氏成功地將作為東方思想之兩大支柱的儒學和佛學結合在一個渾然天成的理論系統之中。概而言之,新唯識論以為作為本心的純白之意在沾染感性經驗的客塵后即迷以逐物,由此將思緒湍飛的內宇宙混同于森然萬象之外宇宙;本心一旦與經驗記憶相合即生“辟”與“翕”這兩種相反相成的勢用:辟勢表達為發動意識行為的隱微的意向性,翕勢則顯示為賦予純白之意以形質的理性閥限;只有即流行而識主宰,于跡象而證真常,方可領略本體寂而能化。靜而譎變的復雜面相。馮特以來的現代心理學之主流注重觀察者與觀察物的分離,而傳統的東方心性論只以觀察者的主觀內省為依歸——前者主要研究普通的心理現象,后者則大量涉及特殊的宗教經驗。作為東方心性論之大成,新唯識論的整個理論系統象是結合著精神分析學的人格結構學說進行現象學的心理描述——由靈明悟性所體驗的本體渾然至善,不同于情欲沸騰之"伊德",故而可為個人靈魂解脫的依據;而解釋意識行為的翕辟成變論又兼攝意向之張與理性之斂,較之純任辟勢的意向性學說更為嚴謹周密。我將嘗試以西方心理學的的形式改造新唯識論,進而以之為核心將這一獨特的思想體系擴展至文科的其他分支領域。
在弗羅伊德之前,崇尚理性的西方思想界一直傾向將憶想思維的醒位視為自我的本然狀態;與之不同,東方人在《易傳》和《奧義書》的時代即已意識到醒位只是更為原始的熟眠位在結合經驗記憶之后的異變形態。在無夢的熟睡中,“我”回到了聞見未染。思維斷滅的原初狀態;此時,作為本心的純白之意因蛻去感性經驗的外殼而呈現本來面目,只以無知之知證會無相之相。寂然不動的主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醒覺之后,“我”即依止外在聞見和先前意識以歷時順序熏染而成的經驗結構展開思活動--清醒狀態下的意動深受經驗理性所含藏的翕勢之牢籠。思之時猶如心靈之眼的內自我實為感性經驗隱含的五識之見分在意識宇宙所投射的幻影--它認同外在的五識身,從而憑藉經驗記憶計度分別種種名相及其實指。形象的感性經驗屬于時空之中的個體生命,而抽象的名言符號則屬于包含無數跨越時空之個體的文化生命——在憶想思維的過程中,后者必以前者為依托。“我”所以能在思考時熟練地使用"房屋"這一名言是因為個人的經驗記憶含有不計其數的樓房屋舍的具體印象。外在的五識身須以意志克服肉體的惰性才能站立起來,而作為五識見分之幻影的內自我亦須以相同的意志克服精神的惰性才能展開憶想思維。就寢之后,隨著支撐五識身之意志的消失,伸張的辟勢終于掙脫翕勢的約束--當此之際,“我”猶如松弛的彈簧,開始在自動力用的牽引下進入光怪陸離的夢境。意識清醒時,主體每以情節完整的事件為記憶的單元;職此之故,在全整的經驗結構解紐的夢幻中,意動的慣性總是自然而然地接著偶爾呈現的念頭編織可為“我”接受的故事情節。這是當事人向自己講述的故事,所以“我”時常作為主人公出現于形形色色的夢中——主角為第一人稱的小說似乎源于相同的心理機制。夢境呈現時,辟勢極度膨脹,但仍受制于先前的夢幻內容。經驗記憶的抽象理路以及與當下意念密切相關的記憶片段。夢中之“我”誤以先前的夢幻內容和與之相銜的脫序的記憶片段為全整的經驗結構,故而總是執幻為真,將心意識變顯得虛無飄渺的境相認作客觀實際。一旦蘇醒過來,君臨全整的經驗結構的主體即刻證知夢之為夢。
本心猶如蘊含豐厚的種子,由經驗記憶之滋養發育成長,形成因人而異的人格氣質。多血質的人翕辟二勢均甚強旺——辟勢始終居于主導,在與翕勢和諧互動的過程持續產生敏銳而靈活的應變心智。膽計質的人則辟勢強而翕勢弱,意向之張與理性之斂難以協調和合。樹體時常因外部刺激而失控,爆發短促而激烈的情緒反應。作為心理活動之理性閥限的翕勢在外傾性氣質中處于被動的客位,而在內傾性氣質中則進據能動的主位。黏液質的人翕勢強而辟勢弱,理性的過度抑制造成保守閉鎖的心態。表現為性格內向,對外部刺激反應遲鈍。抑郁質的人一如多血質的人翕辟二勢均甚強旺——只是翕勢居于主導,不斷引誘辟勢逆向發用。反映在心理活動上則是沉郁而深刻的情緒反應。就個人心智發育而言,幼年時代辟盛于翕:此時,內心渾沛的意蘊使“我”耽于幻想,不務實際;而言談舉止則天真浪漫,無所繩檢。理性的抑制力隨著經驗的累積日益成長,到了成年時代一變而為翕盛于辟:當此之際,“我”遇事每能深思熟,斟酌利害;而言談舉止則老成持重,不逾規矩。幼童所以長于記憶是因為純白之意黏附感性經驗與意識內容的能力較之外敷經驗結構之意為強,成人所以長于理解則由于以名言為載體的抽象思維須以經驗記憶所含具體印象為依托。形象的“花卉草木”乃個體生命之記憶,而抽象的“花卉草木”則為文化生命之記憶。蕓蕓眾生皆由語言文字之視聽濡染外在的文化意蘊,而唯有人類中的天才方能經深刻的內心體驗與文化生命融為一體,進而使之生發全新的意蘊。成人憑其經驗理性懂得只有以意志節制童稚的沖動才能獲取長遠的利益。這追逐個體利益的“理性心態”在有著千百年歷史的文化生命看來可能仍然無異童稚的沖動。文化生命先是以內化于心的道德觀念告誡它的成員勿妨群體福祉,如若無效則只能以代表其意志的禮法令加以節制。
我們對翕辟成變的機制已有粗略的認識,若欲深入探究內宇宙的奧秘就唯有具體分析意識層面變化密移的心所或心數。心所依其性質可分為意指對象明確型與意指對象缺如型兩類——前者包括妒、諂、訛、喬(做作)、驚、懼、憂、疑、悔、喜、怒、愛、惡等十三數,后者則包括苦、煩、癡、羞、慚、哀、樂、貪、慳、謙、傲、懈怠、精進等十三數。
妒數:認同外在五識身的內自我自覺有與某公爭鋒的某種資格,而實際表現卻不如對方,遂將自傷之感轉化為怨憎意指對象的情緒。妒數翕辟二勢均甚強旺。
諂數:內自我出于自利的目的思忖應如何討好意指對象——“諂”指心態而非行為。此數呈現時主體浮上下意識表層的經驗結構,是故翕勢熾盛,完全牢籠了辟勢。
訛數:自我思量應如何掩蓋真相或歪曲事實以欺瞞意指對象,從而使自己獲得利益。此數翕辟成變的機制略同諂數。
喬數:在與人交流的過程中,“我”有意識地將不可告人的動機加以掩飾以緩和內心的緊張與不安--這不可告人的動機多屬違背社會公德的利己心思。喬數翕盛于辟一如諂、訛二數。
驚數:與個人經驗理性相矛盾的信息突然呈現,使“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強烈震動。此時,翕勢的突發性紊亂造成辟勢急劇收縮,由此生發短促而強烈的心理反應。
懼數:主體對意指對象危害自身的可能感到緊張。辟勢因“我”之不安開始向內收縮,而心理反應的強度較之驚數則有所不及。
優數:主體因自身或與之相關的人事前景難側而感抑郁不安。此數翕勢較盛,壓迫辟勢向內收縮,而心理反應的強度較之懼數則有所不及。
疑數:“疑”常與“惑”聯用,實則含義略有不同——內自我感到記憶中的特定狀況或與事實不符為“疑”,而對特定狀況是否屬實把握不定則為“惑”。此數翕盛于辟,與思量之相相伴而生。
悔數:“我”對以往錯誤決策造成的后果深以為憾,但愿時光倒流,能有機會重新作出抉擇。此數翕辟成變的機制略同憂數。
喜數:主體由意指對象感覺輕松快意為“喜”。當此之際,伴隨辟勢之伸張,內自我忽然解脫了翕勢造成的凝重氛圍--因伸張力度不同而又“稍喜”、“大喜”之別。
怒數:主體對意指對象宣泄強烈不滿為“怒”。當此之際,辟勢借助發作之勢突破了理性的抑制閥限--因發作狀況不同而有“慍怒”、“狂怒”之別。
愛數:指內自我將依戀之感傾注于特定的意指對象,與喜數之區別在于前者無我而后者有我。此數一旦呈現,主體即可領略辟勢和緩伸張帶來的難以言傳的溫暖之意。
惡數:指內自我對意指對象懷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拒斥心理。此數一旦呈現,主體即可領略與辟勢收縮相伴生的某種近乎生理反應的不適之感。
苦數:心意未遂引發某種類似味覺之苦的抑郁情緒,其形狀平緩而持久。此數之辟勢因所愿為翕勢否決被迫收斂,使得主體深感不適。
煩數:內自我因難忍記憶中的特定情境而不安于位。此數之翕辟二勢相互訐格,由此破壞了各自穩定的性狀。
癡數:內自我因精神過于專注而對外界信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此數翕勢甚盛,而生發者僅為經驗結構的某一狹小區域。
羞數:對人際交流有恐慌感,“我”希冀能在閉鎖的環境里單人獨處。羞數呈現時,辟勢在翕勢的引誘下向內和緩收縮。
慚數:因良知的譴責而不安于位,“我”直有無地自容之感。羞。慚二數之區別在于前者對人而后者對己。慚數呈現時,辟勢在翕勢的刺激下逆向伸張。
哀數:念及自身不幸的際遇,內自我不由得興起強烈的自傷之感。哀數的成因是辟勢逆向伸張造成下意識深層的波動。
樂數:瞬間解脫經驗理性的束縛,內自我感到了難以言說的精神上的松弛。樂數的成因是翕辟交運的緊張狀態由特定的因緣忽然化為烏有。
貪。慳二數:主體對記憶中不屬己有的物事執著不舍為"貪",對為己所有的物事執著不舍則為"慳"。前者之辟勢在翕勢的引誘下向外伸張,后者之辟勢則在翕勢的壓迫下向內收縮。
謙。傲二數:主體對自己的評估低于實際為"謙",高于實際則為"傲"。前者之辟勢因文化教養之裁抑向內收縮,后者之辟勢則由自然本能之激發向外伸張。
懈怠。精進二數:“我”當困乏之際即隨松弛的意志進入休眠,而在神旺之時則由凝聚的意志蘇醒過來——這一生理特征在清醒狀態下表現為一對相反相成的心所。翕勢所含憊怠懶散之根性在前數中引誘異化為內在意志的辟勢持續松弛,而在后數中則激發其不斷增強。
最后探討的是信仰。認知。藝術創作及審美等人類基本的精神活動的心理機制。真正意義的宗教信仰通常包括創教者。經典。信眾三個有機層次,在經典與信眾之間或者尚有作為其媒介的僧。創教者以獨特的人格塑造了宗教信仰的原初形態,這意蘊渾沛的精神生命在其肉身羽化后即依托經典長存天壤,成為千千萬萬信眾確立正信的依據。當真誠的信眾由經文之指引證會創教者不死的生命時,他們開始因內心的感動不由自主地將自己最原始的“我”融入這玄妙莫測的意蘊中,從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的滿足。在宗教系統中,信眾并不總是被動的接收者,有時也作為能動的一方參與信仰的塑造。比如,佛教的觀音和天主教的圣母在各自宗教的經典中并不突出,但因信眾對于母愛的心理需要而分量陡增,一躍而為地位尊崇的主神。在信仰興起之際,伸張的辟勢煽起人們追求真知的熱情——對教義的執著不可避免地導致派別的紛爭和新宗的創生;而當信仰衰弱之際,凝斂的翕勢則造成求同存異。不求甚解的風氣——社會人心因像法的流行變得理智圓滑而無所執著。信仰源于對下意識深層本心的體驗,而認知則無法脫離表層的經驗結構。認知行為發生時,“我”必專注于特定的經驗記憶并以名言的形式對隱含其間的問題加以思索——實質是在下意識的意蘊中尋求與之對應的所以然之理。是故認識的真偽不僅系于記憶所儲相關信息的可靠程度,而且還與思維的過程中翕辟二勢的強弱密切相關。熾盛的翕勢使“我”思周全,由此避免了錯誤的出現;強旺的辟勢則使“我”靈感泉涌,時能開拓全新的思路。就認知方式而言,文理兩科即因學術性質的差異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理科的進步端賴實驗觀測的成果——肉眼可視空間的超越帶來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信息,而翕勢日新月異的更新則使得辟勢不得不被動地隨之發用。感性經驗永遠居于無可爭議的裁判地位,“我”之論斷未經自然或人為之"客觀實際"的檢驗便不得認以為真。與之不同,文科所研究的是與人之類存在緊密相連的人文現象——唯有當其中的文化意蘊融入本心時,遍計所執之“我”才恍然大悟,理解了問題的實質所在。若以自然科學的思想方法處理文科問題,則人文精神必然淪為一如自然現象的死物。文科在性相上似乎介于科學與藝術之間,而與后者較為鄰近。沒有什么比藝術創作更適于表現人類的精神自由。當“我”沉浸于創作的迷狂時,辟勢揮灑自如地借用經驗記憶的素材變現出令記憶感到陌生的美妙意境——并未賦閑的翕勢則麻醉了自己清醒的意識,只以恍惚記得的經驗印象的條理幫助搭檔合理布局。可以說真正的藝術創作總是一方面超越了生活的經驗而在另一方面又不違生活的常理。藝術創作乃本心之外在顯揚,藝術鑒賞則為本心之內在體驗。主體在感知藝術作品的外觀時必然駐于下意識表層的經驗結構,而當生起美感之際已由它所體現的文化意蘊回到了自己無思無為的內心深處——這一過程發生于剎那之間并且一再重復,使“我”得以不斷重溫返樸歸真的精神快感。"美"作為高尚的精神享受從不拒斥較之低級的感官享受——帶來感官愉悅的未必同時帶給“我”美感,但帶給“我”美感的卻往往同時帶來感官的愉悅。唯有具備高度文化修養的靈魂才能與意蘊深厚的藝術作品發生相互之間的精神交流--此即普通所謂審美經驗。(公務員之家整理)